苯教
- 格式:doc
- 大小:52.5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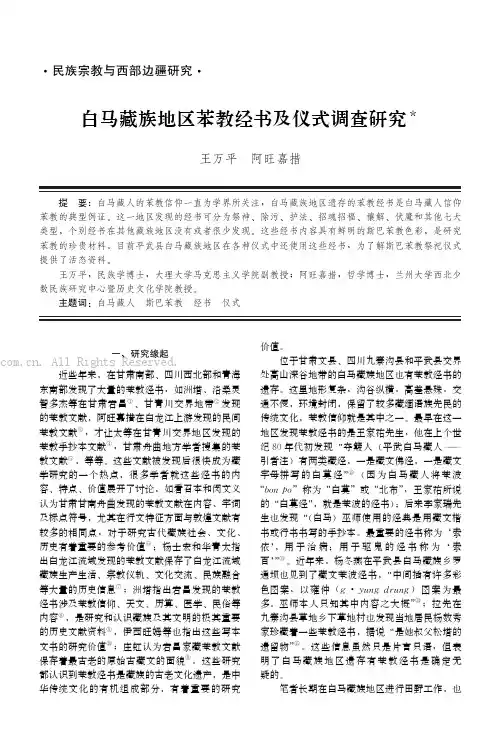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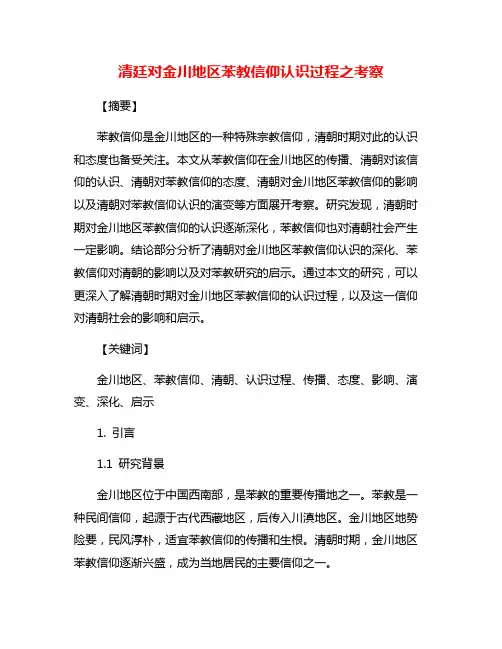
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之考察【摘要】苯教信仰是金川地区的一种特殊宗教信仰,清朝时期对此的认识和态度也备受关注。
本文从苯教信仰在金川地区的传播、清朝对该信仰的认识、清朝对苯教信仰的态度、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影响以及清朝对苯教信仰认识的演变等方面展开考察。
研究发现,清朝时期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认识逐渐深化,苯教信仰也对清朝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结论部分分析了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的深化、苯教信仰对清朝的影响以及对苯教研究的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深入了解清朝时期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认识过程,以及这一信仰对清朝社会的影响和启示。
【关键词】金川地区、苯教信仰、清朝、认识过程、传播、态度、影响、演变、深化、启示1. 引言1.1 研究背景金川地区位于中国西南部,是苯教的重要传播地之一。
苯教是一种民间信仰,起源于古代西藏地区,后传入川滇地区。
金川地区地势险要,民风淳朴,适宜苯教信仰的传播和生根。
清朝时期,金川地区苯教信仰逐渐兴盛,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信仰之一。
研究金川地区苯教信仰对清朝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朝对西南边疆地区宗教信仰的态度和政策。
通过研究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的过程,可以揭示清朝时期对外地民族信仰的认知和态度变迁。
这对于深入探讨清朝时期民族宗教政策、理解清朝对外地民族的统治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研究意义苯教信仰在金川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通过深入探讨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认识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清朝统治下宗教政策的演变和影响。
清朝对苯教信仰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历史上宗教与统治之间的关系。
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的深化和演变,不仅对金川地区的文化传承产生了影响,也对清朝政权的控制和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研究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讨历史现象本身,更在于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脉络,为我们理解和审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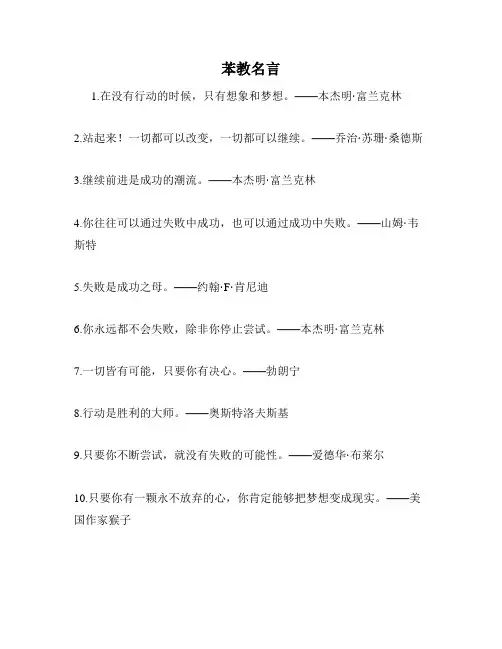
苯教名言
1.在没有行动的时候,只有想象和梦想。
——本杰明·富兰克林
2.站起来!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继续。
——乔治·苏珊·桑德斯
3.继续前进是成功的潮流。
——本杰明·富兰克林
4.你往往可以通过失败中成功,也可以通过成功中失败。
——山姆·韦斯特
5.失败是成功之母。
——约翰·F·肯尼迪
6.你永远都不会失败,除非你停止尝试。
——本杰明·富兰克林
7.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有决心。
——勃朗宁
8.行动是胜利的大师。
——奥斯特洛夫斯基
9.只要你不断尝试,就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爱德华·布莱尔
10.只要你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你肯定能够把梦想变成现实。
——美国作家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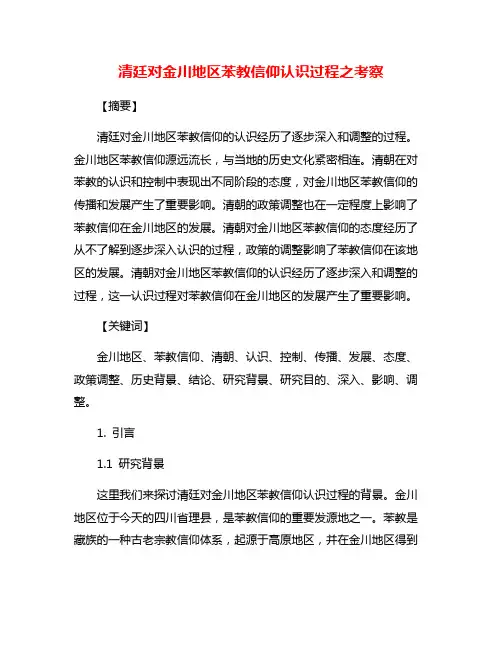
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之考察【摘要】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入和调整的过程。
金川地区苯教信仰源远流长,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
清朝在对苯教的认识和控制中表现出不同阶段的态度,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朝的政策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苯教信仰在金川地区的发展。
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态度经历了从不了解到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政策的调整影响了苯教信仰在该地区的发展。
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入和调整的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对苯教信仰在金川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金川地区、苯教信仰、清朝、认识、控制、传播、发展、态度、政策调整、历史背景、结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深入、影响、调整。
1. 引言1.1 研究背景这里我们来探讨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的背景。
金川地区位于今天的四川省理县,是苯教信仰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苯教是藏族的一种古老宗教信仰体系,起源于高原地区,并在金川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清朝时期,金川地区处于清廷的统治之下,苯教信仰逐渐成为了清廷关注的焦点之一。
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认识和控制,不仅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交织。
在研究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清朝时期对藏区宗教信仰的态度和政策调整,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苯教信仰在金川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通过对这一历史背景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揭示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的复杂性和变迁过程,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思路。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清廷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认识过程的考察,探讨清朝对苯教的态度和政策调整,以及苯教在金川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情况。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了解清朝对金川地区苯教信仰的认识历程,分析清朝对苯教信仰的态度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揭示清朝政策对苯教在金川地区的影响,从而全面了解清朝对苯教信仰的处理方式及其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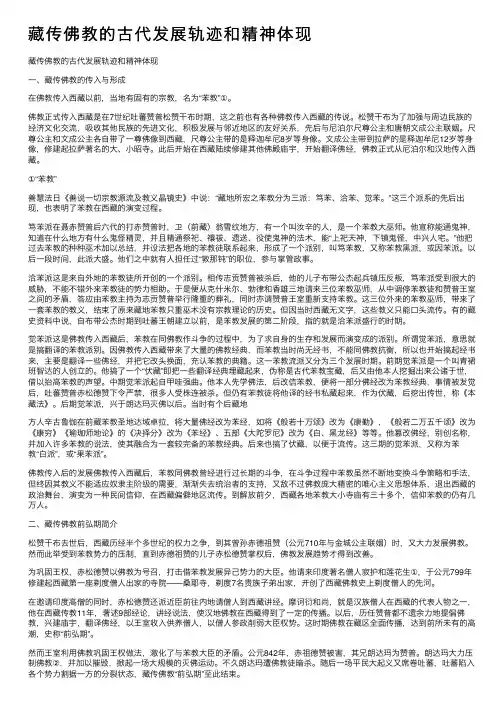
藏传佛教的古代发展轨迹和精神体现藏传佛教的古代发展轨迹和精神体现⼀、藏传佛教的传⼊与形成在佛教传⼊西藏以前,当地有固有的宗教,名为“苯教”①。
佛教正式传⼊西藏是在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布时期,这之前也有各种佛教传⼊西藏的传说。
松赞⼲布为了加强与周边民族的经济⽂化交流,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化,积极发展与邻近地区的友好关系,先后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成公主联姻。
尺尊公主和⽂成公主各⾃带了⼀尊佛像到西藏,尺尊公主带的是释迦牟尼8岁等⾝像。
⽂成公主带到拉萨的是释迦牟尼12岁等⾝像,修建起拉萨著名的⼤、⼩昭寺。
此后开始在西藏陆续修建其他佛殿庙宇,开始翻译佛经,佛教正式从尼泊尔和汉地传⼊西藏。
①“苯教”善慧法⽇《善说⼀切宗教源流及教义晶镜史》中说:“藏地所宏之苯教分为三派:笃苯、洽苯、觉苯。
”这三个派系的先后出现,也表明了苯教在西藏的演变过程。
笃苯派在聂⾚赞普后六代的打⾚赞普时,卫(前藏)翁雪纹地⽅,有⼀个叫汝⾟的⼈,是⼀个苯教⼤巫师。
他宣称能通⿁神,知道在什么地⽅有什么⿁怪精灵,并且精通祭祀、禳祓、遗送、役使⿁神的法术,能“上祀天神,下镇⿁怪,中兴⼈宅。
”他把过去苯教的种种巫术加以总结,并设法把各地的苯教徒联系起来,形成了⼀个派别,叫笃苯教,⼜称苯教⿊派,或因苯派。
以后⼀段时间,此派⼤盛。
他们之中就有⼈担任过“敦那钝”的职位,参与掌管政事。
洽苯派这是来⾃外地的苯教徒所开创的⼀个派别。
相传志贡赞普被杀后,他的⼉⼦布带公杰起兵镇压反叛,笃苯派受到很⼤的威胁,不能不错外来苯教徒的势⼒相助。
于是便从克什⽶尔、勃律和⾹雄三地请来三位苯教巫师,从中调停苯教徒和赞普王室之间的⽭盾,答应由苯教主持为志贡赞普举⾏隆重的葬礼,同时亦请赞普王室重新⽀持苯教。
这三位外来的苯教巫师,带来了⼀套苯教的教义,结束了原来藏地苯教只重巫术没有宗教理论的历史。
但因当时西藏⽆⽂字,这些教义只能⼝头流传。
有的藏史资料中说,⾃布带公杰时期到吐蕃王朝建⽴以前,是苯教发展的第⼆阶段,指的就是洽苯派盛⾏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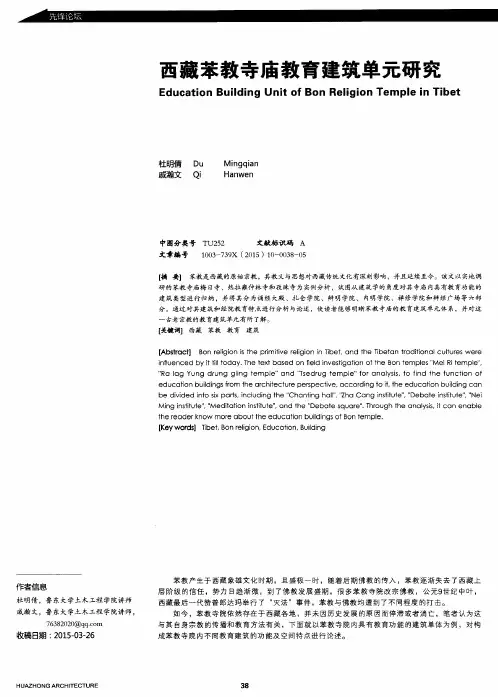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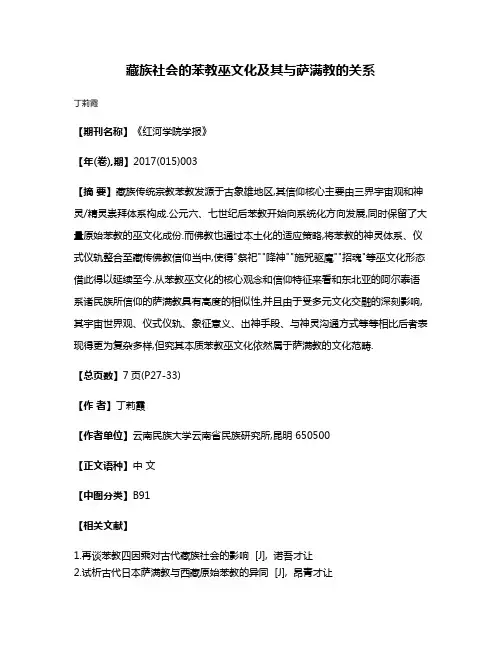
藏族社会的苯教巫文化及其与萨满教的关系
丁莉霞
【期刊名称】《红河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15)003
【摘要】藏族传统宗教苯教发源于古象雄地区,其信仰核心主要由三界宇宙观和神灵/精灵崇拜体系构成.公元六、七世纪后苯教开始向系统化方向发展,同时保留了大量原始苯教的巫文化成份.而佛教也通过本土化的适应策略,将苯教的神灵体系、仪式仪轨整合至藏传佛教信仰当中,使得"祭祀""降神""施咒驱魔""招魂"等巫文化形态借此得以延续至今.从苯教巫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信仰特征来看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并且由于受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刻影响,其宇宙世界观、仪式仪轨、象征意义、出神手段、与神灵沟通方式等等相比后者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但究其本质苯教巫文化依然属于萨满教的文化范畴.
【总页数】7页(P27-33)
【作者】丁莉霞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昆明 6505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1
【相关文献】
1.再谈苯教四因乘对古代藏族社会的影响 [J], 诺吾才让
2.试析古代日本萨满教与西藏原始苯教的异同 [J], 昂青才让
3.试论“苯教是否为萨满教”问题的争论 [J], 孟万鹏
4.论斯巴苯教与雍仲苯教之间的关系——以古藏文苯教文献和雍仲苯教文献之间的关系为视角 [J], 羊本才让; 张泽洪
5.西藏苯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 [J], 张云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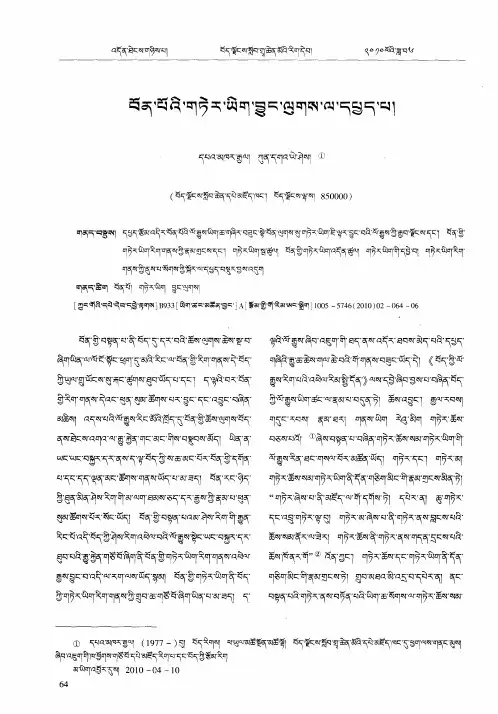
’ ’ 事 1 < ’ 习1 司1 气。 。商茂’嗣 日 _一_一 、 、 、 司 ’ ’ ’ ’ ’ ’ ’ ’ 1 I 1 。 口1 。 ’ 1① ( 管 蓠目’ J ’闰<1 气 ’ 1 850000) 日1 ’目 1 善因 珂a ’霉 日1 缶 习1 。q ’曹 ’ 习1 亏 习1 食’ q度’ ’菩 亘日 < ‘ 1 1 日守】1 司1 习1 习1 罨 ’ 1 日1 《 1訇 目1歹 日1‘ 气 《 1 ’硼日1’玎1f 司1习11歹 习1 ’ ‘j’ 习1 q 。昌 q 口1 ’富叠1 1 玎1 ‘ 习] < 习1 1 [ ’黾茂’ 自’气目’ 亩‘亏口1 ]B933[函 ’ ’ 蓍 ‘8 ’]A[善嗣’ ’ ’号茅j’ ‘蚤口1]1005—5746(2010)02—064—06
 ̄一 ^ 司 奄 ’ ’ q 。击 习1 ’ q
联 闰’
5 < 币 荐目1 日 ’q <1 目 ^ .、 ^ 日1 玎1 ’ 仅< { 击目1 ’q ’ < <’司q 困 1-‘I 商 ’ 贳 ’ 茸 I \ 0 、\ 1 v I \ 叩 。 目1 < 司 目 1 ‘ ’ <。 ’ ’ ’ ’五 ’ 。 ‘ ‘ ’ 习1 习1 ‘ 司 1 訇 9 、 ^ ‘困‘ ’ 1 ‘ 司 ‘J 困 ’ 日1 ’霉 。 哥 ∞ 自 ’q 目 ‘3茂 。 ’日1苦哥 日1 ‘ 日1 日1 ‘ 。 q ‘ ’ q。q ’ ‘ 日1 ’ 5J1 自 ‘ 日1 訇 I 苦 弓习u 习1 ’ 司 aI ’司 q习1’ ai ’ 司 1 ’ ^ 、 ^ qq’ 习1 习1’目 。 ’ ‘目q ’ 日1 击 甲 日茂 日 《 ’ , 鼋 》 即 目南 △ f 、 值 叫 。磊 ’ 。日 ’歹1 仅 <’I 日 习1 < 司 1 香 目 1口1 1 1 ’贳 ’ 目 ① 司 ’ 蒉 1 目1 ’ 目 噎i ’ ’ 1 亨 1目1亨 ’困11 1 1 \ l, \ j l, l 1 ’蒉 1 ’ ’ 1 目1 。 ‘习 。 ’ “ ’ q‘ 。 再‘ 习11歹 ’ 1 习11歹 司 q ‘J ’习1{歹 ’ 窝 。 ‘ 、 、 ^、 ^ .、 ^ 瑟 ’ 。 1 羞 ’ 亨 ‘J&。 『哥 ”② 1 f、 f、 ^ ^、 ^ ^、 日1 习 1 q’ 目 5 q。 日 1 。 习1 ’酉 ’q 百。茂 目1 闰 日1 羞 ‘q 歹 ’ ’q亨 。 闰 歹 击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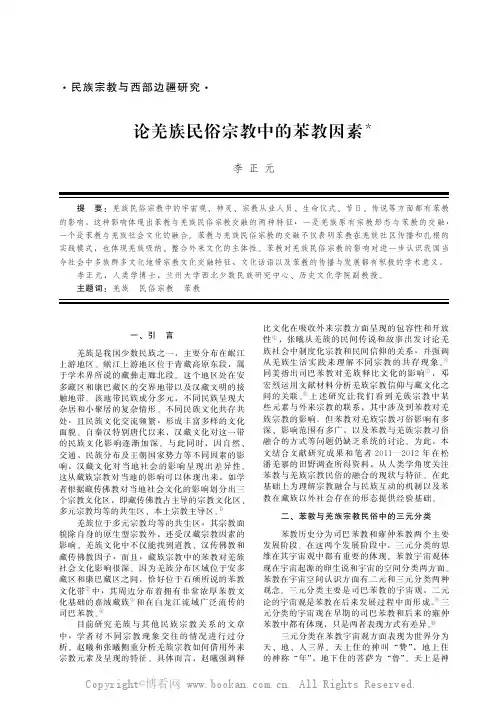
·民族宗教与西部边疆研究·论羌族民俗宗教中的苯教因素*李正元提要:羌族民俗宗教中的宇宙观、神灵、宗教从业人员、生命仪式、节日、传说等方面都有苯教的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出苯教与羌族民俗宗教交融的两种特征,一是羌族原有宗教形态与苯教的交融,一个是苯教与羌族社会文化的融合。
苯教与羌族民俗宗教的交融不仅表明苯教在羌族社区传播和扎根的实践模式,也体现羌族吸纳、整合外来文化的主体性。
苯教对羌族民俗宗教的影响对进一步认识我国当今社会中多族群多文化地带宗教文化交融特征、文化话语以及苯教的传播与发展都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李正元,人类学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羌族民俗宗教苯教一、引言羌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区。
岷江上游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段,属于学术界所说的藏彝走廊北段。
这个地区处在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的交界地带以及汉藏文明的接触地带。
该地带民族成分多元,不同民族呈现大杂居和小聚居的复杂情形。
不同民族文化共存共处,且民族文化交流频繁,形成丰富多样的文化面貌。
自秦汉特别唐代以来,汉藏文化对这一带的民族文化影响逐渐加深。
与此同时,因自然、交通、民族分布及王朝国家势力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汉藏文化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
这从藏族宗教对当地的影响可以体现出来,如学者根据藏传佛教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划分出三个宗教文化区,即藏传佛教占主导的宗教文化区、多元宗教均等的共生区、本土宗教主导区。
①羌族位于多元宗教均等的共生区,其宗教面貌除自身的原生型宗教外,还受汉藏宗教因素的影响。
羌族文化中不仅能找到道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因子,而且,藏族宗教中的苯教对羌族社会文化影响很深。
因为羌族分布区域位于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之间,恰好位于石硕所说的苯教文化带②中,其周边分布着拥有非常浓厚苯教文化基础的嘉绒藏族③和在白龙江流域广泛流传的司巴苯教。
④目前研究羌族与其他民族宗教关系的文章中,学者对不同宗教现象交往的情况进行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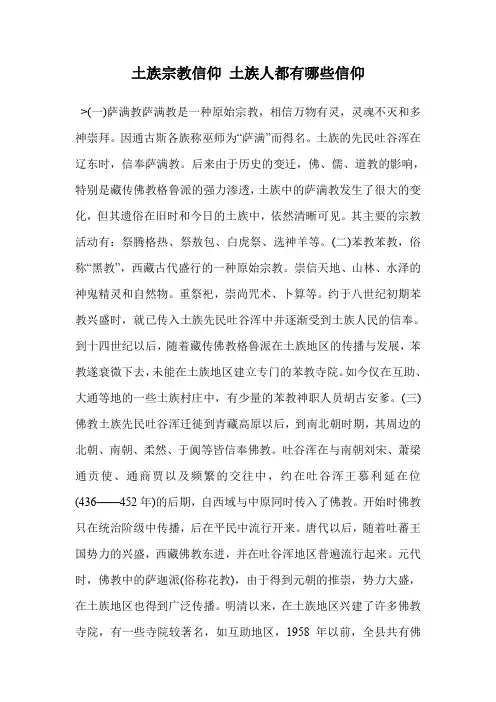
土族宗教信仰土族人都有哪些信仰>(一)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多神崇拜。
因通古斯各族称巫师为“萨满”而得名。
土族的先民吐谷浑在辽东时,信奉萨满教。
后来由于历史的变迁,佛、儒、道教的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强力渗透,土族中的萨满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遗俗在旧时和今日的土族中,依然清晰可见。
其主要的宗教活动有:祭腾格热、祭敖包、白虎祭、选神羊等。
(二)苯教苯教,俗称“黑教”,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
崇信天地、山林、水泽的神鬼精灵和自然物。
重祭祀,崇尚咒术、卜算等。
约于八世纪初期苯教兴盛时,就已传入土族先民吐谷浑中并逐渐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
到十四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苯教遂衰微下去,未能在土族地区建立专门的苯教寺院。
如今仅在互助、大通等地的一些土族村庄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职人员胡古安爹。
(三)佛教土族先民吐谷浑迁徙到青藏高原以后,到南北朝时期,其周边的北朝、南朝、柔然、于阗等皆信奉佛教。
吐谷浑在与南朝刘宋、萧梁通贡使、通商贾以及频繁的交往中,约在吐谷浑王慕利延在位(436——452年)的后期,自西域与中原同时传入了佛教。
开始时佛教只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后在平民中流行开来。
唐代以后,随着吐蕃王国势力的兴盛,西藏佛教东进,并在吐谷浑地区普遍流行起来。
元代时,佛教中的萨迦派(俗称花教),由于得到元朝的推崇,势力大盛,在土族地区也得到广泛传播。
明清以来,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佛教寺院,有一些寺院较著名,如互助地区,1958年以前,全县共有佛教寺院十五座。
尕扎寺与甘冲寺为宁玛派寺院,其余的均为格鲁派寺院。
尚有数十座佛堂,称为“拉康”。
著名寺院有佑宁寺、白马寺和却藏寺。
大通地区,历史上在今大通县境内修建过十八座佛教寺院或静房(日朝)、佛堂。
至1958年尚存八座。
以广惠寺最为著名。
(四)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与儒、佛教鼎足而立,并称“三教”。
苯教特征与华夏⽂明起源苯教特征与华夏⽂明起源徐江伟苯教与萨满教的共同特征是,都把祖先说成从动物中来。
藏⼈祖先是⼀只名叫“啪之根·强久·森巴”的弥猴,与⼀个住在岩洞⾥,名叫“绮”的嗜⾎罗刹⼥所⽣,在⼀个名叫“那玛嘉措”(意为“天湖”)地⽅,⽣出四猴崽:赛、穆、顿、东,最后繁衍成了藏族。
⽽蒙古⼈说他们的祖先是⼀只名叫“孛⼉帖·⾚那”的狼。
满洲⼈说他们的祖先由“鹊”卵⽽⽣。
这种把祖先定位于动物的思维⽅式,本质上是⼀种价值取向。
我们应当看到,萨满教的天地观来⾃苯教。
苯教认为天地是有多层的,⼤地是⽅形的,且飘浮于⼤海中,天是有柱⼦⽀撑着的,天上曾有数个太阳和数个⽉亮。
此外萨满教的轮回观念也是苯教所固有。
还有“卍”字符(旋转⼗字符),转经筒,沿敖包顺时针转圈等,都是苯教天地万物轮回观念的⼀种表达⽅式。
⽽西⽅⾃古就有以⼆元论看待世界万物的习惯,他们总是把事物分成善恶、对错、⿊⽩、洁秽、丑美等等两⼤类。
他们还有明确的太阳崇拜习俗。
但苯教与萨满教都认为世界是圆的,万物以循环往复的形式存在,⽽不是以两元对⽴的形式存在。
东⽅⼈并不特别地崇拜太阳,天地万物、⽇⽉星⾠、祖先神灵,都是崇拜对象。
考古也已经反复证明,华夏⽂明中并⽆所谓的太阳崇拜。
藏学家乌丙安教授所著《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化根基》说,他在西藏横断⼭⼀带的藏族和羌族中调查到的情况是,羌藏类游牧民族的神话传说与中原古籍记载的远古神话传说完全相同。
乌丙安因此认为华夏民族有共同的萨满教根基。
问题是,羌藏类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的汉民族有完全不同的⽣存⽅式和语系归属,这种共同根基是如何产⽣的呢?华夏古⼈确是⾃认为来⾃昆仑之巅的神族,这昆仑⼭在何处虽然⾄今说法不⼀,但此⼭在青藏⾼原及其延伸出来的帕⽶尔⾼原上却是世所公认的。
苯教,萨满教和游牧⽂化的另⼀特征是,都认为部族军事⾸领是从天⽽降者的“天⼦”。
《敦煌吐蕃历史⽂书·赞普世系表》⽈:“天神⾃天空降世,在天空降神处上⾯,有天⽗六君之⼦,三兄三弟,连同墀(chi)顿祉共为七⼈(指七代赞普),来作雅砻⼤地之主。
#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唐宋之际敦煌苯教史事考索陈于柱提要:在唐宋敦煌宗教史的既有研究中,对苯教始终付诸阙如,然敦煌藏文本佛教疑伪经、苯教仪轨书、占卜书、医书等相关资料显示,苯教教团不仅曾经流寓敦煌,而且在经受敦煌佛教界竭力排挤的境况下,仍广泛地从事丧葬祭祀、占卜禳厌、驱鬼疗疾等宗教社会活动,并在特定时期扮演着敦煌吐蕃族群利益代言人的角色。
同时在宗教仪轨、民俗信仰等领域对敦煌佛教和社会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是敦煌区域史中不应忽视的宗教力量。
陈于柱,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主题词:唐宋敦煌区域宗教史苯教学术界关于敦煌区域宗教史的研究业已比较全面,特别是对佛教、道教的探讨尤显深入。
但是敦煌宗教史的研究并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存在某种遗漏,即学术界一方面承认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大量的藏文苯教文献,但另一方面对唐宋敦煌社会是否存在苯教教团及其活动却始终语焉不详,更未见到直奔敦煌苯教这一主题成果的出现,这就不足以解释苯教文献出现于敦煌的合理性。
这一情形至今仍为学术界所默认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敦煌学界多以敦煌汉文文献为研究重点,而汉文材料对苯教鲜有记载;二是苦于敦煌藏文文献的零碎缺略以及古藏文的考释难度大,藏学界目前仍主要以定名和译读为工作重心;三是敦煌苯教文献尽管早已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然多是以探讨吐蕃苯教史为主旨,忽略了敦煌苯教文献与敦煌地域之间的联系性。
基于以上原由,笔者试图就敦煌是否存在过苯教教团,如若有,其在敦煌地区的生存情景又是如何这两大核心问题展开探索,旨在推动敦煌区域宗教史的整体认识。
笔者认为敦煌地区应存在过苯教教团的活动。
苯教虽在8至9世纪的吐蕃本土经受了/佛苯争斗0和官方打压,但并未因此受到重创,在吐蕃社会中仍有较大影响,且随着吐蕃的军事扩张而不断向西域等周边地区传播¹,新疆出土吐蕃时期木简,如米兰v ii20,iv60,iv121,x x-v ii15,iii7等号对苯教徒的活动即有着丰富记述º。
文化长廊 CulturalCorridor22教育前沿 Cutting Edge Education丁青地区苯教文化的历史发展与传承研究——以丁青县孜珠寺为例文/樊晓莹摘要:在佛教传播、兴盛之前,苯教在吐蕃已存在、发展了上千年。
对苯教的探究是研究“雪域”文明产生和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苯教作为西藏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最能反映出藏族文化的独有特征。
针对2019年在丁青县孜珠寺开展的田野调查为例,梳理了苯教在丁青地区的历史发展和传播概况,分析了孜珠寺在该地区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
关键词:苯教;孜珠寺;丁青县;西藏;发展;传承公元8世纪后,佛教在藏区的发展逐步替代了苯教,虽然苯教原有的圣地都被佛教化,但在西藏昌都一些地区苯教文化仍旧得到了完整的保存,甚至有所发展。
昌都地区的丁青县拥有西藏最大的悬空而建的苯教寺庙——孜珠寺、藏区著名的苯教圣山——布加雪山以及作为民族文化交流纽带的“茶马古道”,这为研究苯教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资源。
1 苯教在丁青地区的传播在西藏昌都地区,苯教寺院共有53座。
其中丁青县有31座,江达6座;四川的甘孜地区的苯教寺院共有43座,其中德格县10座,新龙县8座,炉霍县3座,雅江县2座,理塘县1座,马尔康5座,汶川2座。
以上记录都是经由政府批准登记的寺院。
事实上,还有一小部分寺庙散落在藏区各地,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还未正式报批的小型寺院和苯教的一些活动中心。
丁青地区被认为是古代象雄里、中、外三部分中外象雄的中心地带,是古代象雄的三个文化聚集地之一,也是古代琼部落从象雄西部东迁后以琼部落的后裔为主形成的一个群体。
20世纪50年代初,对四川嘉绒地区的调查中记载说:“传说现在的嘉绒族多谓其远祖来自琼部,其地据说在拉萨西北,距拉萨18日程,传说该地古代有三十九族,人口很多,因地贫瘠而迁址康北与四川西北者甚众,后渐繁衍,遂占有现在的广大地区。
”所以源自象雄的苯教及“琼鸟”等观念很可能是随人群迁徙先由象雄向东传到藏北琼部(即今藏北丁青县一带,亦称三十九族地区),再由琼部向东传入嘉绒地区。
拜访苯教故地听说这里有一位对苯教很有研究的学者,我就想去拜访。
因为阿里与苯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苯教在藏语中称为“苯波”。
汉文有时写成钵或笨。
它是佛教传入西藏前在象雄即今天的阿里地区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的宗教。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苯教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原始宗教,而是一个苯佛混杂的历史产物,其内容已十分庞杂,既有比较古老的原始巫教的一些特点,又有大量系统化的神学宗教的成分。
要了解原生形态的早期苯教,阿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
据晚期形成的苯教文献记载,苯教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就盛行于象雄,然后从象雄传入西藏。
就在我们去阿里的几年前,在阿里的日土县境内发现了一些与苯教有关的岩画。
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岩画的族属是古代象雄人。
岩画中几乎没有象征农业文化的踪迹,由此可知古代象雄居民以狩猎、畜牧为生。
同时岩画中没有见到任何宣扬佛教的内容,而最为丰富的是任姆栋一组一号岩画展示的杀牲献祭的宏大场面。
作为献祭用的祭品有125个羊头和10个估计是盛血的陶罐;作为祭祀对象的神则有太阳、月亮、象征苯教的“雍仲”符号、鱼、男性生殖器,还有象征“天梯”的“目”字形符号。
在一条人称“齐吾普”的页岩峭壁上,有众多的野牛、羚羊、山羊、鹿、马等动物形象,还有一些分别持盾、格斗、骑马、跳舞的人物形象,有的像是热带岛国的土著,有的像是中原汉画里的“羽人”。
大多数人物画面以抽象的简单符号区别男女。
从日土三处地点的岩画中可以明显看出“雍仲”符号是从太阳的图案演变而来的。
由此可知原始形态的苯教的某些信仰特点:崇拜自然、崇拜动物、杀牲献祭等。
苯教对大自然中的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都很崇拜,这种带有自然宗教特色的信仰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依然盛行。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王朝在举行会盟大典时,即“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
其中对天神的崇拜在早期苯教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苯教认为天为上界,是天神“赞”的居所,并认为苯教始祖辛饶米沃切和吐蕃王统第一代藏王都是从天而降的天神。
试论“苯教是否为萨满教”问题的争论
孟万鹏
【期刊名称】《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22)002
【摘要】苯教,又称为“苯波教”,是根植于藏族原始文化之中,并对藏族文化的特性及传统有着深远影响的一种古老的宗教.学界一直都对苯教的研究保持着强劲的热情,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研究者及其颇具功力的论著,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无疑是可喜可贺的.然而在欣慰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如就“苯教是否为萨满教”这一问题的认识就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和混乱.对此,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梳理和规范.
【总页数】4页(P1-4)
【作者】孟万鹏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陕西咸阳71208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33
【相关文献】
1.关于苯教研究中“苯教是否为原始宗教”问题的争论 [J], 孟万鹏
2.试析古代日本萨满教与西藏原始苯教的异同 [J], 昂青才让
3.藏族社会的苯教巫文化及其与萨满教的关系 [J], 丁莉霞
4.西藏苯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 [J], 张云
5.试论维吾尔族萨满教与日本民族萨满教的异同及国外萨满教研究的几个问题 [J], 王建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苯教】苯教(Bon Religion)(有时也译为本教、苯波教)在古藏文的记载中,苯教的苯(Bon)是“颂咒”“祈祷”“咏赞” 之义,这在原始信仰的各种仪式中是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以念颂各种咒文为主要仪式的各种原始的苯被传统被称之为“原始苯教”(或“世续苯教”),另外由辛绕弥沃所创立的“雍仲苯教”。
在“Bon”之后加上一个“Po”(Bonpo 苯波)就变成信仰和参与各种原始信仰的人。
因为雍仲苯教最传统的法帽“尔莫泽杰”(dkar mo rtse rgyal)(又称“胜尖白帽”)是白色的,因此早期的雍仲苯教曾被称作“白帽苯”,由于西藏古代政治、历史、宗教等原因,许多西藏人都忽略了西藏本土的历史,他们认为印度佛教对西藏文化特性的形成有着巨大的贡献,并认为所有来自印度的都是有伟大价值的,同时也认定西藏本土文化以及与印度或佛教不相关的都没什么价值,一些古代藏地学者的著作中描写苯教的章节,往往是人云亦云地搬照前代学者的文章或宗教范本的史记,因此很多著作都简单地把苯教描写成“鬼神崇拜”“杀生祭祀”或“巫术”等等,正是这种状况,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导致了西藏真实历史和本土文化的遗失,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对苯教研究的兴趣。
【历史传说】藏人们自己恐怕只熟悉引入佛教的松赞干布国王,而对松赞干布之前的历史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其实,在松赞干布前面至少有三十位藏王,或者三十二位,即使这一点有所分歧,但毫无疑问的是,松赞干布并非第一位藏王。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记载,西藏第一位蕃王聂赤赞普是由苯教的僧团认证并且加冕的,聂赤赞普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是同时代的人,也有一些记载说略晚于佛陀。
但无论真相是什么样的,这已经将我们带回了洪荒的古代。
在佛教传入藏地前、那个名字与地理位置都与现在大不相同的西藏王朝之前,苯教就已经存在了,它的历史甚至比君主制的历史还要悠久……但很多藏人认为在佛教到来西藏之前,西藏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文化非常愚昧落后等等,这种荒谬的说法被一些正统的狂热者宣扬了数个世纪,这种做法也严重地毁坏了西藏历史和本土文化,此状况一直到近些年才有所改变。
传承与发展根据苯教徒的传统解释,苯教大体可分两种:1、原始苯教(srid pa rgyud kyi bon)2、雍仲苯教(g.yung drung bon)辛饶弥沃(gShen rab mi bo)(顿巴辛饶)在吸收和改革原始苯教的基础上创建了雍仲苯教,使苯教得以统一,辛饶弥沃被认为曾是象雄的王子,出生于冈底斯山(Kailas Range)(藏人叫它“神山冈仁波切”)附近的俄摩隆仁(vol mo lung ring)。
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说法不一(学术认为辛饶生于距今4000年前左右,苯教认为辛饶出生于公元前16017年),一般学术上把辛绕弥沃创立的宗教也叫做苯教。
但在苯教的文献中把辛绕所创立的并且是正统的苯教叫作雍仲苯教,也就是说“苯教”并不等于“雍仲苯教”,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因为,“苯教”并非和辛绕的理论同时产生。
早在远古时代辛绕弥沃出生之前,青藏高原就已经盛行着各种各样的原始信仰,那就是被统称为原始苯教的多神教,有“魔苯”、“赞苯”、“沐浴苯”、“招财苯”、“占卦苯”、“龙苯”、“神鬼苯”、“历算苯”等三十多种原始的“苯教”,他们为民众禳解灾祸,祛除病邪,拥有众多的信徒。
这证明当时象雄、吐蕃地区“苯教”一词的解释范围非常广。
“苯”这一个字,是藏文,从象雄文“吉”(gyer)(或译为“杰尔”),意译过来的,实际上是“念”和“读”的意义,就像念经读书。
“苯”有许多释义,据苯教经典记载:“苯一字蕴藏着无穷含义,即在苯教因明学和般若部里记载说“苯”谓能维持其自体者;或摄持其自性相。
“苯”有八大类别,即有为苯、无为苯、轮回苯、涅盘苯、道谛苯、法处苯、所知苯和福德苯。
详细情况见般若大小等别处。
苯与在汉传佛教里所谓的“法”、古印度梵文中的“达磨”、象雄文中的“吉”、藏传佛教经典中的“秋”等意义基本相同。
总而言之、它涵盖了有寂含有的万事万物,如在苯教的《般若智慧经》中就有云:“轮回苯与涅盘苯、有寂诸苯为空性。
”万事万物都可以叫“苯”。
辛绕弥沃创立的雍仲苯教与原始的苯教的区别还在于:当辛绕从象雄来蕃地传教时,他已经有一整套理论和相应的教规,而这时原始苯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宗教,辛饶弥沃在善巧地吸收原始苯教并对其进行大量改革的基础上创建了雍仲苯教,比如,辛饶吸收了原始苯教中包括藏医、天文、历算、地理、占卦、超度、梦兆、招财、招福、石碑铭文、雕刻以及沐浴等法,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仪轨仍然被村民用以防止来自人和动物的疾病,或者用于带来日常生活中的利益。
以上的世间法被苯教列为“南伏藏九乘”的“因四乘”:“卡辛”、“朗辛”、“楚辛”、“斯辛”(另外还有出世间法“果四乘”和“无上大圆满乘”等五乘,详见于别处)。
另外,原始苯教的杀生祭祀仪式遭到了辛绕弥沃的反对,他采用糌粑捏成各种形状的方法来代替原始苯教中要杀生祭祀的动物并取得了成功,叫做“堆”(mdos)或“耶”(yas),这就是朵玛(gtor ma)(多尔玛)的最初起源。
现在,朵玛不仅被苯教徒而且被藏传佛教徒广泛用来做供品并成为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虽然杀生祭祀的劣习至今在藏区还存在,但这并非辛饶的教理所允许的。
因此,辛绕的改革不仅对当时藏地杜绝大量杀生祭祀等劣习和保护动物中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还对西藏后期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绕创立的宗教叫做雍仲苯教而有别于原始苯教,“卍”雍仲,这个古老的符号有“永恒不变”、“金刚”、“善妙”、“吉祥”之意,这个符号也象征着集中的能量。
“卍”是藏地十分常见的吉祥物。
“卍”常与“卐”(右旋万字)和“十字金刚杵”一起出现在藏传佛教僧侣法坐下面的唐卡图案中。
“卍”不仅仅存在于西藏和象雄地区,也存在与其他地方的文明中。
参照印度文化,这个左旋雍仲的符号可能来自古老的巴利语字母中的“阿”字。
同样的在象雄语也如此,左旋的雍仲符号也与其字母中的“阿”字非常相似,比如这个雍仲的符号也在古希腊的花瓶纹饰中存在、另外在意大利Paestum的博物馆的一件文物上也有这样的符号,因此,很难轻易地下结论,说某些事物属于一个特定的文化。
苯教的主要标志为“雍仲恰辛",它由两个“卍”连接在一起组成。
这个金制雍仲钤记,表示“苯”无变无灭,象征证得雍仲之藏及具十八文义。
”据苯教《雍仲业尽》一书记载:“从太古斯巴传来的恰辛,由通晓十八藏之辛绕,常持不离身、旋绕诸宗之上,能使雍仲苯教立胜幢,常断邪见疑惑皆威慑。
”“雍仲恰辛”的字面释义为:“雍”表示胜义无生;“仲”表示世俗无灭;“恰”表示降灭邪见;“辛”表示引入解脱,恰辛两端的雍仲符号,象征显密两宗,居中的连接处象征心识部无上大圆满。
早在印度佛教传入藏地以前雍仲苯教的经文中就有对此法义的多种解释,因此说“苯教为了对抗印度佛教而采用与“卐”相反的“卍”作为标志”的这一说法是不客观的。
一直到公元七世纪,辛饶所创立的雍仲苯教曾经是整个吐蕃地区的唯一宗教和信仰基础。
当然,从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传入吐蕃以后,苯教和印度佛教在互相排斥的同时,又各自吸收了许多对方的内容,苯教吸收了印度佛教的内容,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印度佛教吸收了苯教的内容,也使其能够更深入地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并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藏传佛教。
(佛教在进入不同的文化本体中时,必须要面对不同的本土信仰形式,除苯教外,又如儒教、道教、日本的神道等等,这才能使其在民众中更广泛地传播。
这也就导致了佛教不可避免地与其本土传统信仰的维护与界定者产生哲学与精神层面的交流,佛教与本土文化融合不仅在藏地,在其他地域都有所变化,最有力的证明的是观音菩萨的伟丈夫形象,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了女性,民间关帝庙中的“关老爷”则成为汉传佛教的护法“伽蓝菩萨”等等,都是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的现象)佛苯之间碰撞的结果也是吐蕃王朝政治斗争的终结,由于信封苯教的大臣政治势力过大而遭到了王室的忌惮,公元八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开始扶植印度佛教并灭苯,这次大法难让苯教徒们至今记忆犹新,在那次大劫难当中,苯教被斥为“黑教”(nag-chos)(邪教的意思),苯教徒们被迫改宗印度佛教,不愿意改宗的苯教僧人被迫亡命天涯,到阿里、安多和康区等边远地区,继续信仰和传播他们的宗教。
这次法难,使苯教与公元7世纪始传吐蕃的印度佛教之间两百多年的斗争见了分晓,最终以印度佛教的胜利而告终,赤松德赞也扫清了影响其政治的阻碍并巩固了政权。
这次法难也成为佛苯斗争史上的一个分界线,此前,苯教仍然是主宰吐蕃的主要宗教,而印度佛教则仅仅是一个主要局限在吐蕃王室传播的外来宗教。
但是此后,印度佛教作为一个强势文化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占领了吐蕃宗教文化的主导地位,尤其从其后宏期开始,印度佛教从安多地区逐渐开始重新传播,并且逐渐在民间得势,在很少几个世纪里,遍及整个吐蕃。
而苯教在赤松德赞以后一直处于劣势,尤其在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卫藏地区,基本上被清除逸尽。
但是,苯教毕竟是藏民族的本土宗教,经过几千年的信仰实践,它的精神和传统已经渗透到这个民族的骨髓里,它完全统治着这个民族的心灵世界,左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这个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苯教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藏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苯教的仪轨、修法、密宗、大圆满等传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承,这对于我们研究藏传文化是极其重要的。
苯教《大藏经》(《甘珠尔》)就记载了苯教这个西藏本土宗教的教义、仪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经过上千年的磨合,苯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在一些重要教义上的融合缩短了这两个宗教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两者之间的许多分歧,促成了这两个宗教传统在许多重要教义上的共识,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在变化值得一提的方面。
夏扎巴(1858-1934),法号扎西坚赞(译为吉祥胜利幢),在大圆满方面的修行、研究和著作。
夏扎巴一生修习大圆满,是一个虹化了的苯教大圆满大成就者,在夏扎巴三十岁前后,他在四川康区与康着仁波切、蒋扬钦哲旺波、秋吉林巴等人发起了称之为“利美”的无教派运动并成为其中苯教的代表,也使他明确的了解了佛教各派系的修法,由于他不需修持各派教授而一见之下就能自然通达,由此获得了很大的声誉,据说当时藏传佛教的五大派都有拜访求学于他或探讨学习的。
如今,他的著作成为很多苯教寺院里的必读文献(夏扎巴的著作汇集成册的有十八部,其中最重要的有五部:思慧库(dbyings rig mdzod)、教理库(lugs rigs mdzod)、藏理库(sde snod mdzod)、虚空库(nam mkhav mdzod)和嘉言库(legs bshad mdzod)),苯教大圆满和印度佛教大圆满两个传统在夏扎巴的修行和著述中的统一标志着苯教和印度佛教在又一个重要领域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