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统战部长李逸三
- 格式:doc
- 大小:17.58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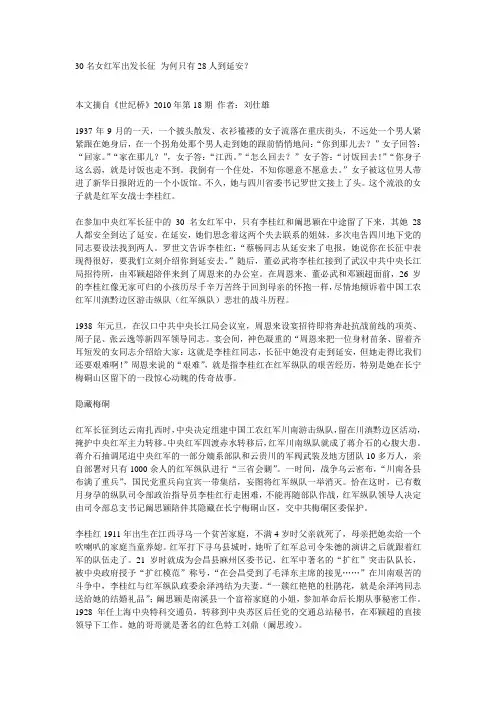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作者:刘仕雄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
”“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
”“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
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
”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
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
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
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
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
”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
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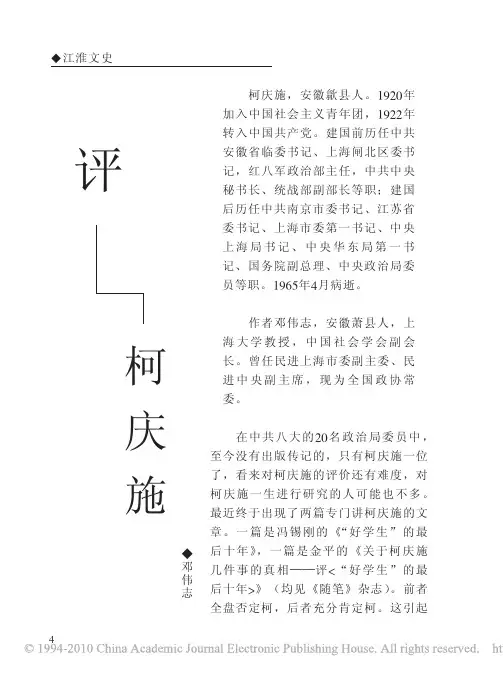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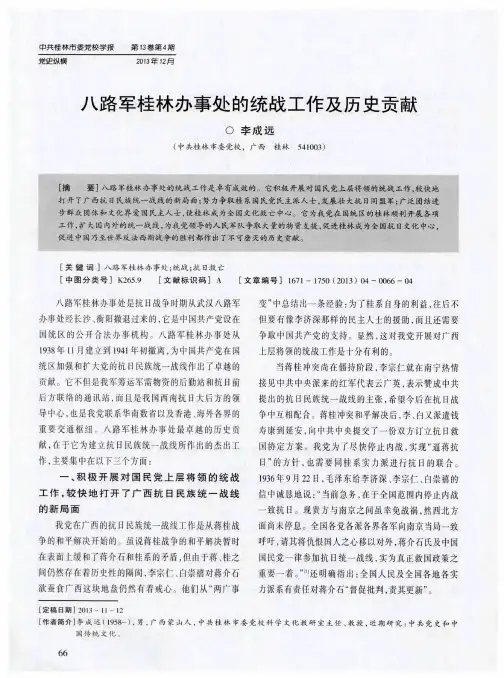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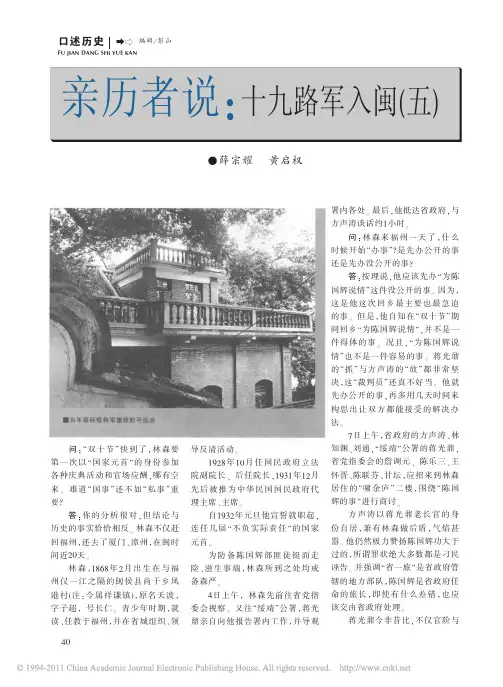

国共两党争夺名人大战作者:孙士东来源:《决策与信息》2006年第10期胡适,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1948年1月13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
第二天,蒋介石又两次亲自打电话催胡适飞南京,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
“抢救”对象首先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
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表示留在亲戚家。
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是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
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梅贻琦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电台,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
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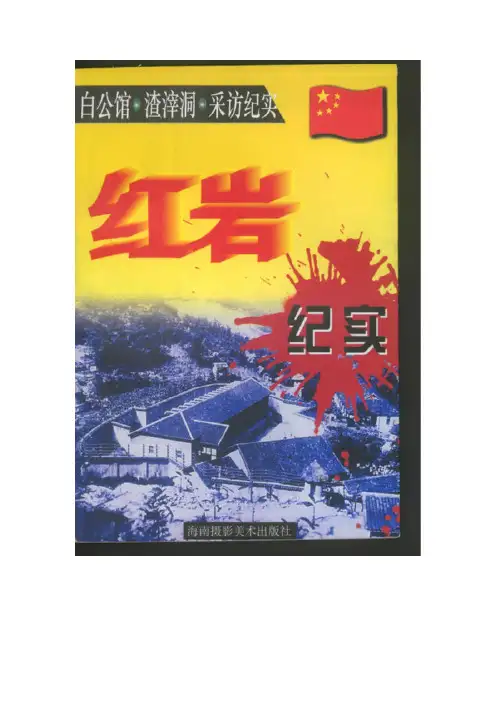

12岁那年转读新舟小学,首任校长李碧书。
协六公一生酷爱书法,尝用灰斗装灰,用木棍在灰斗中书写,孜孜以求,乐此不倦,传一时佳话。
1905年遵义知府袁玉锡饬遵义知县戴永清在城北火神庙(今遵义四中)开设遵义师范讲习所,次年清政府废止了从隋朝开始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
1907年,袁玉锡又呈准巡抚林昭年筹办遵义府初级师范学堂,是为遵义有现代教育的开始。
1908年遵义师范停止招生,遵义初级师范学堂易名为遵义中学堂。
首任堂长为四川人邓玉昆,在此执行教的有贵州第一批赴日留学生牟贡三,与严寅亮同为光绪十七年的举人王乐生、余沅芬、杨灿英,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李道堃、陈文裕,光绪三十年(1904)恩贡赵乃康等饱学之士在此执教。
诸先生敦品励行,深受乡人敬重。
是年农历2月27日新生入学,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省里也派一督学参加,据说这位督学与遵义知府袁玉锡同为湖北襄阳人,在学校大门上作了一副对联以贺,联中有开辟山荒兴学校之句,一时激怒了探花公杨兆麟。
是夜,杨探花派人将这位督学的对联撕下换上自己的撰写的一联:“我本学界中人,五百年教启阳明,鄨邑素称文物地;尔乃荆蛮下士,七千里趋承太守,犬獒乱吠夜郎天!”这位督学得知系当朝大名鼎鼎的遵义杨探花所为,也就只好忍气吞声。
遵义中学堂位于老城武将衙署(今十一中附近),教学大楼气势磅礴,规模宏大。
学校一改旧式书院的许多陈规陋习,吸收了西方近代教育的某些形式和内容,是黔北的最高学府,桐梓、绥阳、正安、湄谭、甚至思南、印江等县的学子也慕名前往。
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曾遭受顽固派的非议。
一些俯背虾腰、腿迈方步的遗老遗少,他们留连科举仕途,依念功名富贵,对新学报以仇恨,经常对师生冷嘲热讽,说什么学校里的唱歌、体育等课程都是鬼混;学生在街上挺胸亮怀,简直是赳赳武夫,哪里有点读书人的气质。
照他们的说法,只有那些循规私塾老套,读圣贤之书,才能成才。
他们见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呼之曰“新学家”,师生们对此嗤之以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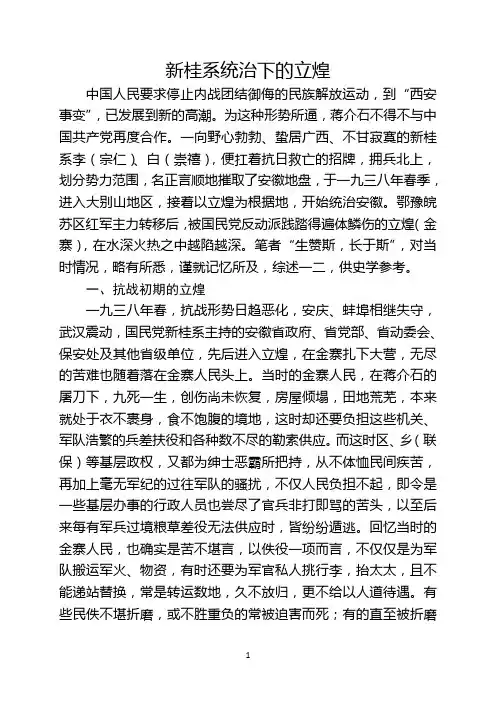
新桂系统治下的立煌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民族解放运动,到“西安事变”,已发展到新的高潮。
为这种形势所逼,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
一向野心勃勃、蛰居广西、不甘寂寞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便扛着抗日救亡的招牌,拥兵北上,划分势力范围,名正言顺地摧取了安徽地盘,于一九三八年春季,进入大别山地区,接着以立煌为根据地,开始统治安徽。
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转移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践踏得遍体鳞伤的立煌(金寨),在水深火热之中越陷越深。
笔者“生赞斯,长于斯”,对当时情况,略有所悉,谨就记忆所及,综述一二,供史学参考。
一、抗战初期的立煌一九三八年春,抗战形势日趋恶化,安庆、蚌埠相继失守,武汉震动,国民党新桂系主持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省动委会、保安处及其他省级单位,先后进入立煌,在金寨扎下大营,无尽的苦难也随着落在金寨人民头上。
当时的金寨人民,在蒋介石的屠刀下,九死一生,创伤尚未恢复,房屋倾塌,田地荒芜,本来就处于衣不裹身,食不饱腹的境地,这时却还要负担这些机关、军队浩繁的兵差扶役和各种数不尽的勒索供应。
而这时区、乡(联保)等基层政权,又都为绅士恶霸所把持,从不体恤民间疾苦,再加上毫无军纪的过往军队的骚扰,不仅人民负担不起,即令是一些基层办事的行政人员也尝尽了官兵非打即骂的苦头,以至后来每有军兵过境粮草差役无法供应时,皆纷纷遁逃。
回忆当时的金寨人民,也确实是苦不堪言,以佚役一项而言,不仅仅是为军队搬运军火、物资,有时还要为军官私人挑行李,抬太太,且不能递站替换,常是转运数地,久不放归,更不给以人道待遇。
有些民佚不堪折磨,或不胜重负的常被迫害而死;有的直至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始被抛弃,讨饭还乡。
因此,不少民佚,往往中途潜逃,而被追击损命者亦大有人在。
于是民怨沸腾,恨声载道。
白色恐怖后的苦难的金寨人民,虽不敢公开抗拒,但为了活命,一听兵到或见有保长、保丁出现时,就都躲进山林。
过往军队有时找不着乡、镇、保长,无法觅足所需要的民佚,便亲自动手乱抓,甚至有将年轻的行政人员也抓去迫充伏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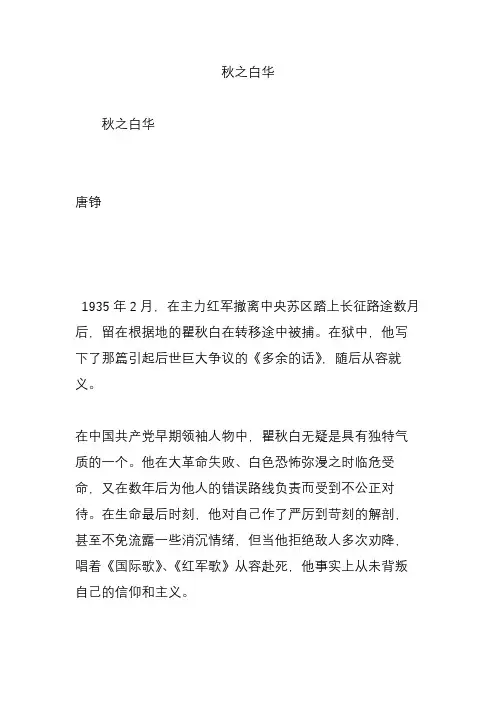
秋之白华秋之白华唐铮1935年2月,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数月后,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
在狱中,他写下了那篇引起后世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随后从容就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中,瞿秋白无疑是具有独特气质的一个。
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对自己作了严厉到苛刻的解剖,甚至不免流露一些消沉情绪,但当他拒绝敌人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
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
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噩耗传来临危受命1935年4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背面盖着一个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说明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
5月时,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
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
没有上学。
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
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
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
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四十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的火眼金睛。
在后人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无不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来刻画两人的深厚友谊。
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送瞿秋白,被传为佳话。
而瞿秋白也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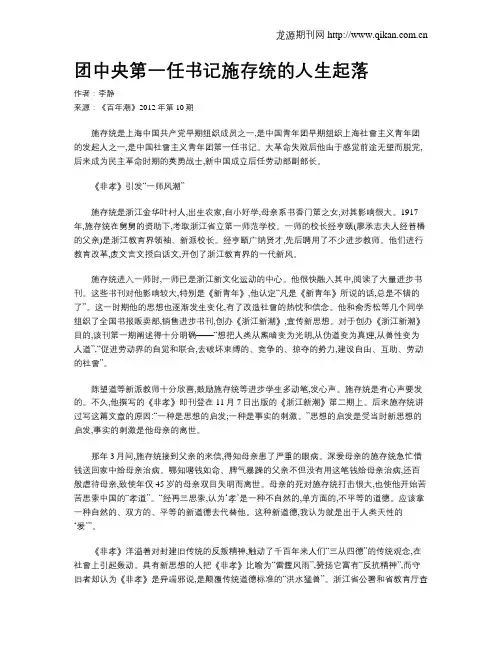
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施存统的人生起落作者:李静来源:《百年潮》2012年第10期施存统是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是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上海社會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国社會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他由于感觉前途无望而脱党,后来成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英勇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副部长。
《非孝》引发“一师风潮”施存统是浙江金华叶村人,出生农家,自小好学,母亲系书香门第之女,对其影响很大。
1917年,施存统在舅舅的资助下,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师的校长经亨颐(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父亲)是浙江教育界领袖、新派校长。
经亨颐广纳贤才,先后聘用了不少进步教师。
他们进行教育改革,废文言文授白话文,开创了浙江教育界的一代新风。
施存统进入一师时,一师已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他很快融入其中,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这些书刊对他影响较大,特别是《新青年》,他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
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有了改造社會的热忱和信念。
他和俞秀松等几个同学组织了全国书报贩卖部,销售进步书刊,创办《浙江新潮》,宣传新思想。
对于创办《浙江新潮》目的,该刊第一期阐述得十分明确——“想把人类从黑暗变为光明,从伪道变为真理,从兽性变为人道”,“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會”。
陈望道等新派教师十分欣喜,鼓励施存统等进步学生多动笔,发心声。
施存统是有心声要发的。
不久,他撰写的《非孝》即刊登在11月7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二期上。
后来施存统讲过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一种是思想的启发;一种是事实的刺激。
”思想的启发是受当时新思想的启发,事实的刺激是他母亲的离世。
那年3月间,施存统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母亲患了严重的眼病。
深爱母亲的施存统急忙借钱送回家中给母亲治病。
哪知嗜钱如命、脾气暴躁的父亲不但没有用这笔钱给母亲治病,还百般虐待母亲,致使年仅45岁的母亲双目失明而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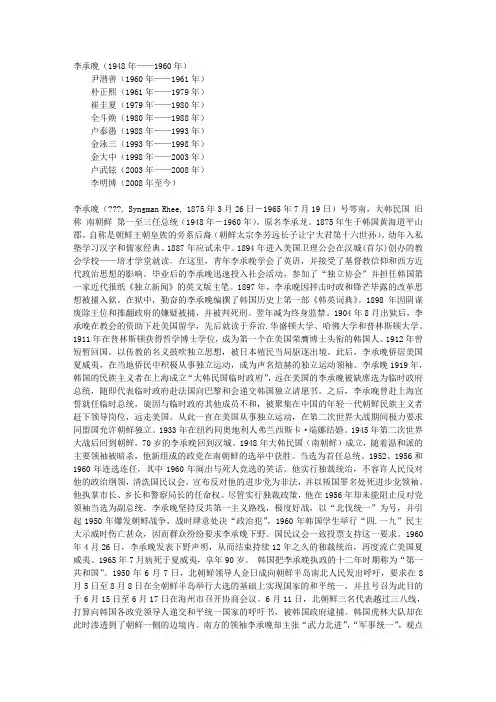
李承晚(1948年——1960年)尹潽善(1960年——1961年)朴正熙(1961年——1979年)崔圭夏(1979年——1980年)全斗焕(1980年——1988年)卢泰愚(1988年——1993年)金泳三(1993年——1998年)金大中(1998年——2003年)卢武铉(2003年——2008年)李明博(2008年至今)李承晚(???, Syngman Rhee, 1875年3月26日-1965年7月19日)号雩南,大韩民国旧称南朝鲜第一至三任总统(1948年-1960年)。
原名李承龙。
1875年生于韩国黄海道平山郡。
自称是朝鲜王朝皇族的旁系后裔(朝鲜太宗李芳远长子让宁大君第十六世孙)。
幼年入私塾学习汉字和儒家经典。
1887年应试未中。
1894年进入美国卫理公会在汉城(首尔)创办的教会学校——培才学堂就读。
在这里,青年李承晚学会了英语,并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
毕业后的李承晚迅速投入社会活动,参加了“独立协会”并担任韩国第一家近代报纸《独立新闻》的英文版主笔。
1897年,李承晚因抨击时政和锋芒毕露的改革思想被捕入狱。
在狱中,勤奋的李承晚编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部《韩英词典》。
1898年因阴谋废除王位和推翻政府的嫌疑被捕,并被判死刑。
翌年减为终身监禁。
1904年8月出狱后,李承晚在教会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1911年在普林斯顿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荣膺博士头衔的韩国人。
1912年曾短暂回国,以传教的名义鼓吹独立思想,被日本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此后,李承晚侨居美国夏威夷,在当地侨民中积极从事独立运动,成为声名煊赫的独立运动领袖。
李承晚1919年,韩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远在美国的李承晚被缺席选为临时政府总统,随即代表临时政府赴法国向巴黎和会递交韩国独立请愿书。
之后,李承晚曾赴上海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旋因与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不和,被聚集在中国的年轻一代朝鲜民族主义者赶下领导岗位,远走美国。
统战元老——平杰三
温民法;乔秀玲
【期刊名称】《中州今古》
【年(卷),期】1999(000)004
【摘要】平杰三,1906年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原属河北省濮阳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初期,开始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历任中共濮(阳)内(黄)滑(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兼统战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顾...
【总页数】4页(P7-10)
【作者】温民法;乔秀玲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
【相关文献】
1.陈毅与“统战三杰” [J], 张衡
2.平杰三的统战生涯 [J], 温民法;乔秀玲
3.宛西解放中的统战"三杰" [J], 陈志坚;吕仁献;
4.努力开创新时期统战工作新局面全省统战宗教工作会议召开——谢世杰、秦玉琴、欧泽高、张延翰分别作重要报告 [J], 周勇
5.安徽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缪学刚莅临杰事杰调研考察 [J], 杰事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金以林:论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在蒋介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下野,都很快复出。
第一次是在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第三次是在1949年国共决战期间。
对这两次下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
但对1931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
[1]蒋氏这次下野,同前后两次最大的不同点是压力完全来自国民党内部。
胡汉民曾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
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
”[2]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冲突,再度引起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发难,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
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
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重组。
本文主要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档案,重新梳理并说明这一看起来扑朔迷离的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希望借蒋氏下野与再起这一个案,揭示国民党内权力重组、变迁的内在因素和各方相互争夺和妥协的真实心态。
一蒋介石被逼下野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是难以忍受的。
11月7日,宁粤上海和谈结束。
12日,南京四全大会首先举行。
会议期间,蒋介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
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
”当晚,蒋令负责同粤方谈判的宁方代表陈铭枢,赴上海邀请已从粤方分化出来的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
[3]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一些难言之隐的顾忌。
第二天,陈铭枢电蒋报告同汪会商结果: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
惟汪与哲生(孙科)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
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
林⽴果与“⼩舰队”成员密谋制定“571⼯程”来龙去脉2019-05-28庐⼭会议后,相继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所作的严厉批评,使、叶群更加惊恐和忧虑。
找来林⽴果商议当前的形势,林⽴果表⽰:“与其束⼿就擒,不如破釜沉⾈!”在的⽀持下,林⽴果辗转杭州和上海,与⾃⼰的“⼩舰队”成员进⾏了⼏次密谈……林⽴果向提出搞政变苏州南园,过去曾是宋美龄的私⼈别墅,解放后成了接待中央领导的著名胜地。
苏州⼀直为所钟爱。
苏州南园1号楼,亦即院⼦中的⼀幢西式建筑,就成了的“⾏宫”。
⾃从1970年8⽉的庐⼭会议后,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了明显变化。
就连不了解内情、只是负责保卫他安全的⾝边警卫⼈员都察觉到,⾃从庐⼭下来后,他们所保卫的这位党的副主席、接班⼈“情绪不那么好,整⽇愁眉苦脸,满⾯阴郁,不见⼀丝笑容。
他外出活动原本就很少,这⼀段就更少了。
”1971年2⽉12⽇,、叶群从北京到达苏州。
夫妇⼆⼈的情绪都不好,因为庐⼭犯错误⽽检讨尚未过关的叶群少了许多平时惯有的那种贵妇⼈常见的颐指⽓使和盛⽓凌⼈,变得待⼈接物和⽓了、沉稳了。
也不像过去那样三天两头乘汽车外出“转车”兜风了,⽽是躲在苏州南园深处那21摄⽒度恒温、没有阳光和风的密室⾥,⼀个⼈终⽇闷闷地枯坐。
半年过去了,、叶群⼀直没有从庐⼭会议失败的阴影⾥⾛出来。
在庐⼭会议后采取的步步紧逼的各项措施,相继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所作的严厉批评,使、叶群更加惊恐和忧虑,也加重了和的嫌隙。
对的不满加深了。
⽐谁都清楚,采取的⼀个个措施,⽆⼀不是冲着他来的,只是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不知什么时候,叶群已经悄悄来到他⾝旁。
机警的猛地⼀个鲤鱼打挺,双⽬顿时炯炯有神,问道:“怎么,有事吗?”“我本不想打扰你,可这下不说不⾏了。
刚才,黄永胜⼜来电话,说军委座谈会开不下去了,他们⼏个看样⼦过不了关啦!这是黄总长第三次来电话了。
还有,吴法宪也打来电话诉苦,说⼈家揪住他不放,看样⼦要往死⾥整。
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获得者简历(3)总政治部总政治部 (2)栗光祥 (2)林月琴 (3)张少庭 (3)黄志勇 (3)于克法 (3)丁毅 (4)郑锦波 (4)赵工 (4)丁里 (5)洪涛 (5)张桐 (5)何德林 (5)王苹 (6)李英儒 (6)杨剑龙 (6)朱为流 (7)鲁挺 (7)刘海山 (7)夏云成 (7)白刃 (8)夏川 (8)乐群 (8)张通达 (9)贺庆 (9)霍健 (9)吴坚 (9)李敏 (10)刘夫洪 (10) 黎萍 (10) 黎光 (10) 王工学 (11) 张健民 (11) 周力 (11) 伍坤山 (12) 耿宏 (12) 王明宣 (12) 赵少和 (12) 彭合朋 (13) 丁铁石 (13) 刘耀礼 (13) 张锐 (14) 许清 (14) 彭海贵 (14) 肖春先 (15) 张云山 (15) 陈德三 (15) 程荣耀 (15) 雷铁鸣 (16) 岳心广 (16) 刘谦益 (16) 徐元甫 (16) 谢华 (17) 田仁明 (17) 王万祥 (17) 李万华 (18) 彭绍智 (18)苏志乾 (19)牛载丰 (19)罗彬 (19)李馨诚 (20)李思元 (20)张兰 (20)田波 (20)吴茵 (21)总政治部栗光祥(1921--2009) 原名栗广祥,山西省襄垣县人。
1936年9月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10月入八路军115师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教育股长,1941年10月任716团1营政治教导员,1947年8月任716团政委。
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军1师副政委,1953年1月任1军2师政委。
1957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授会主任,1964年6月任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1969年12月调总政治部宣传部主持工作,1983年2月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1988年6月免职,1998年8月离休。
施平 1911年生,云南大姚县人,现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 1926年在昆明投身第一次大革命 1931年9月在浙大参加左翼文化同盟,任全国学联执委 1935年任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浙江省云和县党工委书记,庆元县委书记 1939年12月任国际新闻社记者 1941年8月进入苏中参加新四军,任苏中区调研室副主任、主任 1943年2月任苏中第一地委民运部长 1946年5月任中共南通县委副书记、书记,县警卫团政委 1949年5月任中共苏北区党委青委书记、团委书记 1950年3月任中共苏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副书记 1951年8月任华东团工委宣传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副书记 华东团委副书记、代书记 1953年10月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代校长 1962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投入监狱52个月,后又“劳改”两年 1978年8月 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4月 任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1986年 离休
周克 1917年2月生 88岁 江苏江宁县人,现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 1935年在北平精业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参加一二九运动 任团区委宣传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 1937年转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期间在敌后区从事地下工作。 全国解放后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市轻工业局局长、市工业部副部长。 粉碎四人帮后、任上海市市科委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五个落伍者的结局2010年03月12日19:21:3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一生。
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有的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
如李汉俊、李达。
但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
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
然而,也有几个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
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这里,笔者对他们落伍后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飨读者。
二号巨奸陈公博托派分子刘仁静中共一大闭幕后,刘仁静回到北京。
他与邓中夏一道筹备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
这份杂志在国内小有影响,深受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
后来,该刊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
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
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
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
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
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
第二任统战部长李逸三李逸三,1956年7月—1964年4月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其生平简介如下:李逸三同志,1906年11月1日出生于武乡县故城镇北良候村的一个中农家庭。
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青年时代就奠定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1921年15岁时考入武乡县乙种农校。
1924年乙种农校改办县立师范学校,他继续读书,在进步教师籍雨农的影响下,他思想认识有了飞跃的发展。
1925年四、五月间,他带动学生罢课、闹学潮,要求县长高槐撤职顽固校长郝新民。
同年7月,只身到太原,在张磐石开办的补习班学习。
后太原国民师范招生,他考入国师读书。
入学后,由焦金棠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6年第二学期,大革命高潮中,国民党成立工人部,他担任了太原市党部工人部长(兼职)。
1926年12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正向河南进军。
当时,黄埔军校招生,李逸三投笔从戎,1927年1月,到了武汉,考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该校为黄埔军校分校,他为第五期。
求学期间,李逸三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波格达纳夫的《通俗资本论》,从此他信仰了马列主义,努力追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运动。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叛变后,军校的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归叶挺指挥。
中央独立师与叛军夏斗寅部展开了激战,夏部溃不成军,被缴械投降。
同年7月下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蒋介石,李逸三随师部于7月底出发,8月2日晚到达九江,后沿赣江西侧经吉安、赣州、南雄,到了广州。
在斗争中,李逸三的思想逐步成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与日俱增,于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前夕,经严育英(四川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揭开了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肩负起了解救中华民族的重任。
12月11日,李逸三参加了著名的广州暴动,以叶剑英任团长的铁军军官教导团打出了“红军”旗号,称红军第四师,在战斗中,李逸三右眼负伤。
1928年,李逸三担任了国民党薛岳四师十一旅黄振球旅部准尉录事。
他秘密组织了中共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1928年夏,李逸三返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刘伯承安排下,进入中央流动训练班学习。
1929年秋,中央军委派李逸三去宜昌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接头,同年9月,周逸群命他参加洪湖区的武装斗争,任红军鄂区游击第二纵队政委。
1930年12月,周逸群派李逸三去上海向党中央交党费,并汇报洪湖苏区的情况。
同月离上海返洪湖苏区途中时,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团防局拘留,后经军法处判徒刑3年。
李逸三在身陷囹圄期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2年春末,李逸三被依令减刑释放。
由于他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于1932年10月回到武乡。
李逸三回到家乡不久,就开始和本村北良候的贫雇农李尚文、李华英一起酝酿闹革命,首先筹备组织抗债团,向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开展斗争。
1933年春,李逸三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在高沐鸿、武光汤等的倡议下,经县长吕日薪同意,在县城创办了《武乡周报》,他任编辑。
《武乡周报》采取了公开合法形式,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的宣传,从中传播革命思想,鼓舞群众斗志。
同年夏,李逸三利用去县立师范讲课的合法地位给学生们大讲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启发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报。
后来,这些学生大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王锦心、张桂森、李衍授、李步云等进步青年都加入了地下共青团。
同时,李逸三搜集了有关世界各国人民斗争的资料,编写了《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宣传斯大林所讲的世界人民革命理论,在结语中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要爆发的观点。
这本小册子,共印300册,不到月余,全部售完。
继《武乡周报》之后,李逸三又筹办了“武乡流通图书馆”、“武乡通讯社”和“印刷合作社”等合法机构。
“流通图书馆”内收存进步书籍约千余册,并在学校和乡村组织了广大读者。
在团结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方面起了桥梁作用。
可以说,李逸三是在武乡这块土地上,第一个撒下革命种子的人。
李逸三为了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曾两次到太原。
1933年6月初去太原没找到党组织,到了8月又第二次去太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关系,他向太原工委书记维公汇报了武乡县的工作情况,并要求在武乡建立党组织。
李逸三得到维公同意成立党组织后,立即返回武乡,先后发展了史怀璧、赵瑞璧、武三友、程登瀛等人入党,于当年8月15日,在县城(今故县)高沐鸿家西房正式成立县委领导机关。
李逸三任书记,赵瑞璧分管组织,史怀璧分管宣传。
会议开了一上午,李逸三传达了太原工委指示后,讨论了当时的工作。
会议决定:(1)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主要从“抗债团”的积极分子中选拔;(2)出版党内刊物《上党红花》,以教育党员;(3)加强对“抗债团”的领导,推动开展群众性的五抗运动(五抗指:抗债、抗租、抗粮、抗税、抗丁);(4)全县分东区、中区、西区三个党的活动地区。
县委分工,李逸三和李尚文负责西区,史怀璧、武三友负责中区,赵瑞璧、程登瀛负责东区,后来东区以窑头、中区以段村、西区以北良候这三个村为中心,成立了三个党支部。
从此,武乡党的组织就在农村中扎下了根。
秋初,李逸三借用“流通图书馆”的地址,召开了农民抗债团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雇工武三友为团长,贫农李尚文为副团长。
同时,李逸三还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王锦心负责。
这时,县党委、抗债团、共青团成为武乡党的三个地下活动机构。
武乡党组织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斗争,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惧与仇恨,乡间地主豪绅纷纷告状。
1934年春节,武乡县派出警察,半夜包围了李逸三家,他不幸被捕,押到太原山西反省院,以他写的《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作为罪证,加上“宣传共产”的罪名,被判徒刑6年。
在狱中,李逸三组织了秘密通讯网,进行狱中斗争。
他利用亲友设法送进狱中的进步书籍,经常给难友上马列主义课。
1937年3月8日,李逸三串通同难,绝食三日,要求释放,出狱抗日。
同年5月23日,李逸三与同难20余人全部释放。
出狱后,李逸三第一个应邀去薄一波领导的军政训练班学习。
不久,被党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五团任二连政治指导员。
1937年秋,教五团开赴武乡,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
教五团改编为决死队一纵队二总队,李逸三调三营为营教导员。
1938年春,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他随该部又开赴襄垣参战。
同年夏,调任太岳区游击二团政治部主任。
1939年春调太岳区保安司令部任游击一支队支队长。
1941年调太岳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岳北区敌工站站长。
1943年春,调太岳军区政治部敌工部任干事。
1945年春任命太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1946年李逸三调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学习三个月后,调人民日报社任编辑。
1947年夏调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党总支书记,兼任教务科长。
1948年夏石家庄解放,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大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李逸三任二部党总支书记。
1949年3月李逸三进北京。
1950年华北大学改中国人民大学,他任专修科党总支书记,1951年调任预科主任。
1953年夏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兼任组织部长和人事处处长。
1954年兼任人大职工业余学校校长,1955年兼人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委书记,从1956年夏开始兼任统战部部长,直到1964年调离学校为止。
1964年夏李逸三被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党委书记兼任副所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李逸三被诬为资本主义当权派,靠边站,接受审查。
靠边站,长达12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靠边站的12年中,李逸三除了被批斗半年,在植物所住“牛棚”约2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3年外,其余6年时间,他都在研究语言文字改革问题。
因此,1979年春,曾奉命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帮助工作。
1980年春,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国务院决定任命李逸三为国务院参事,1983年8月离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同志,虽年逾古稀,但怎么也坐不住了,他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和几十年来先后担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领导的工作经验,决心走出一条民办高等教育的新路。
1982年3月,由李逸三同志牵头经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教师筹建的“中华社会大学”正式成立,并面向社会招生。
1983年5月,李逸三又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筹建了朝阳科文大学。
1984年3月,朝阳科文大学易名为“培黎职业大学”。
如今黎培职业大学共有八个分校,一所针灸学院、四个直属系,30几个专业,10几个单科班,分布在北京市、郊十几个区、县。
有在校学生2500多人。
这所大学自建校以来,共培养各类专业毕业生1700多人。
从1979年到1988年,李逸三同志用了近10年时间,为民办高等教育事业辛苦操劳,四处奔走。
前五年不但没有分文报酬,而且还要自己掏腰包筹措办学资金。
为了办好民办大学,李逸三的足迹遍布北京四城八区,他经常早出晚归,有时在外达十六个小时。
李逸三曾说:“3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比中国高出近一倍的效率、效益,如果不抓紧各个层次的基础文化教育,不尽快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照老样子下去,中国的球籍就是个问题了。
每每想到这些,我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 为表彰李逸三同志辛勤的工作,1989年,中华全国老龄委员会授予他“老有所为精英奖”;1990年6月28日,中共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委员会评选李逸三为“优秀党员”,同月29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评选李逸三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2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选李逸三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1992年6月、1994年7月、1996年1月,又三次被评为国务院办公厅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2003年10月16日,李逸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资料来源:《留得风范在人间——深切缅怀武乡党组织创始人李逸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