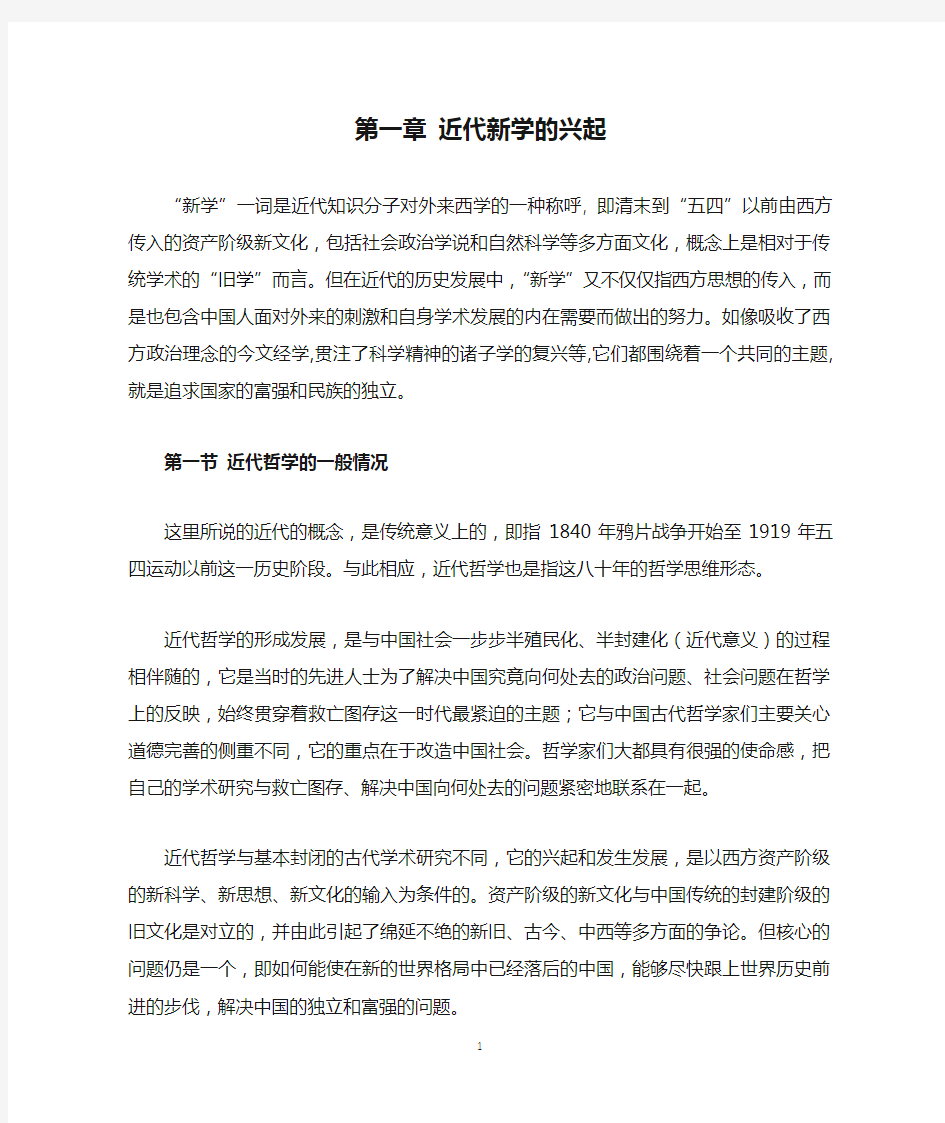

第一章近代新学的兴起
“新学”一词是近代知识分子对外来西学的一种称呼, 即清末到“五四”以前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包括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文化,概念上是相对于传统学术的“旧学”而言。但在近代的历史发展中,“新学”又不仅仅指西方思想的传入,而是也包含中国人面对外来的刺激和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而做出的努力。如像吸收了西方政治理念的今文经学,贯注了科学精神的诸子学的复兴等,它们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追求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
第一节近代哲学的一般情况
这里所说的近代的概念,是传统意义上的,即指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这一历史阶段。与此相应,近代哲学也是指这八十年的哲学思维形态。
近代哲学的形成发展,是与中国社会一步步半殖民化、半封建化(近代意义)的过程相伴随的,它是当时的先进人士为了解决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在哲学上的反映,始终贯穿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最紧迫的主题;它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主要关心道德完善的侧重不同,它的重点在于改造中国社会。哲学家们大都具有很强的使命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救亡图存、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代哲学与基本封闭的古代学术研究不同,它的兴起和发生发展,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科学、新思想、新文化的输入为条件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封建阶级的旧文化是对立的,并由此引起了绵延不绝的新旧、古今、中西等多方面的争论。但核心的问题仍是一个,即如何能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已经落后的中国,能够尽快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解决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的问题。
与此同时,近代哲学的发展,又是与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为自己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西方输入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普遍传播并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和认同,在古代社会缺乏生长机制的自由意志尤其是政治自由的问题,开始走到了时代的前台,而且一跃成为了近代新学的一个重要导向。
与传统社会注重稳定和连续性的价值追求不同,近代中国在整体上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不论是被动的应对还是主动的参与,面对无处不变、无时不变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的呼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千古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作为必然的集中体现,“天”的至上地位是由对封建制度的不变和永恒的信念来支撑的。如此的天或道虽然也有不尽圆满之处,但在古代社会,思想家们总是相信能够通过“补天”的办法来解决。在贯穿旧时代始终的“补天”情结中,人的意志在总体上不是与必然对抗,而是使必然更圆满。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深刻地揭示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弥补天道、天命以期盼其更加圆满的持续不懈的努力。
但是,这样的历史情结到了清代中叶曹雪芹撰写他那不朽名著《红楼梦》时,终于发生了动摇,封建专制“大厦”这个天在他心中已经无法再修补了。在“无材可去补苍天”的贾宝玉身上,实际寄托着作者深深的哀怨。“忽喇喇似大厦倾”的令人心悸的前景,在思想的先驱者这里,已经可以预见。补天希望的破灭带给人们的,是百年后从“我”出发的“造天”、“变天”的自由意志的风行。
当然,古代思想家也希冀“自由”地处理天人、物我的关系问题,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和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便是典型的代表。但面对天道和人事的外在必然,包括荀子在内的思想家的基本导向,是因循天道而加人为利用的模式,即所谓天人“交相胜”。而这在认识
论上,都可以归结到以人为补天的范畴。近代的自由追求显然已超越了这一模式,它由认识论进入到了历史观中,自由表现为社会的运动。“我”的力量被充分地释放出来,“心力”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等思想家发出了“我气造天地”、“平等生万化”、“依自不依他”的时代呼唤。历史翻开了造天和改天的一页。
对他们来说,“自由”的人已经不再是拘束于“天下”的臣民,而是理直气壮地遨游于“天上”。从“天下”到“天上”,并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的层面,而是意味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进化论的传播和推广,人们了解到人作为种群和国家的生存本身就是自由的现实,因为他们已经在过去的生存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得到了保存;而要在近代继续得到保存,就必须自觉适应自然和社会的选择,积极主动地为自身造命。
造命改天并非完全否定天范畴的存在地位。天作为必然的代表,在近代社会同样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它已经不再是专制和奴役的庇护者,而是变成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来源。“民之自繇(由),天之所畀也”(严复:《辟韩》)。由卢梭“斯民生而自由”而来的天赋人权观,成为了近代思想家心中最为神圣的理想。强权专制所以失去合法性,就在于它“侵犯人之界,是压人之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康有为:《论语注》),理当被取代和推翻。
传统社会虽也流行“天命之谓性”的天予人性观,人性对天命也有平等的意义。但人在这里并没有脱离开天命的自由。人所有的是自觉复性、“变化气质”以回归天命的义务,而不享有作为人本来当有的权利。但在近代学者看来,义务应当是与权利“相对待”的概念,“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严复:《法意》按语)。
由于几千年传统形成的对天命的敬畏和面临高高在上决定人间命运的制度化主宰,人的自由被限定在心性和认识的层面,权利意识缺乏生存的土壤。故与天变、道亦变相伴随的,是近代天道与人的自由的关联。人的任务,已主要不是向外争自由,而是向内除“心奴”。梁启超认为,人之不自由,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或为古人之奴隶,或为世俗之奴隶,或为境遇之奴隶,或为情欲之奴隶。破除长期以来积淀于民众心理中的奴隶意识,成为争取自由权利的当务之急。
相较而言,“身奴”的控制容易解脱,“心奴”的逆来顺受心理才是自由的真正大敌。所以,“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新民说·论自由》)。然而,“心奴”的驱除事实上又总是与人对外在必然如强权、圣人、命运的畏惧和依赖分不开的。尽管“天予人权”观将天道与人权、自由、平等相联系并为其来源,强化了人的自由权利生来享有和不可侵犯,但将其归结为天赐,表明人间的自由仍然是一种“有待”,离不开外来必然的支持。孙中山对此进行了改造,强调“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人事胜天,就是人依据自身的力量和愿望去造天,民权也就不再被系于天赋,而是主张由时势和潮流所造就,是“人为力”自身奋斗的成果。
当然,孙中山的“人为力”同样也是一种“心力”,对“心力”的推崇是近代新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此心力虽然也从“三界唯心”和良知发动去解释,但不论是心还是良知,都已经不再是道德天理的扩充和心性的体验,而是理性或意志自由活动的表征,与人的权利和幸福密切关联。在它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近代先进思想家们急切希望民族自决自强和渴求幸福的理想。
近代哲学是在激烈变动中形成的,通常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首先是基于今文经学的传统学术的自我救赎,这在性质上仍属于旧学的范畴,仍是希望补天,故变器不变道;其后则进入了真正具有近代气息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范畴,它包括一般称之为维新派的哲学和革命派的哲学这两大阵营,二者虽也有保守和激进之分,但总体上都是要求积极变革的。他们的目的不再是补天,而是要改天,不但变器,更要变道。在他们身上,最终体现了中国哲学从古典形态到近代形态、从传统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转变,延续几千年的旧学让位于新学。
第二节近代西学的传入
近代西学的传入,为近代哲学的形成提供了科学基础。这里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理论等人文社科方面的成就,对于中国传统的固有学术来说,它们的的确确可以归之为“新学”的范畴。
一、明清之际西方科学的传入
西方科学的输入,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开始。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利玛窦是明万历十年(1582)由澳门入境的,此后直到明末清初,有不少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在他们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思想和著作带来了中国。在这中间,较为有名的是:
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未译完),这是数学。物理学方面,主要有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讲水利的;邓玉函和中国学者王徵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讲机械力学。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五大洲说。天文历算方面,利玛窦、艾儒略、熊三拔等人引进了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体系。思想方法方面,主要是中国学者李之藻和传教士傅汎际合译的《名理探》,讲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宇宙观方面,主要有李之藻和傅汎际合译的《寰有诠》,讲经院哲学的世界图像。这后两本书是十七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Coimbra)耶稣会大学的哲学教本。此外还有关于火器制造、医药、艺术等方面的译著。
总起来,这一时期传教士们传入的西方科学和哲学著作数量是不少的,仅就有中文著译可考的,就有三百七十种左右,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计一百二十种左右。当然这时传入的西学从质量上看并不高,大体上没有超出西方古典科学的范畴。但是,传入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它帮助中国人开始看到了自身学术的不足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可惜这股风气并没能持久,到清雍正帝(1723年即位)以后基本上就停止了。清统治者接下来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中国文化与当时西方日新月异的科学文化发展隔绝了,中国的真正落后,也就在随后的二百年中。
二、近代西学的重新引进
十九世纪中叶,列强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中国的先进人士徐寿、华蘅芳游览上海,看到介绍西洋学术的书籍,眼界大开,十分震惊中西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得很大了,于是又重回到二百年前中西交汇的起点,重新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
近代西学的传入主要有两个阶段,即八十年代以前和九十年代以后。前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李善兰主要介绍了天文学和牛顿力学;徐寿主要介绍了化学;华蘅芳则主要介绍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包括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这一阶段的科学传入与明清之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所引入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这对于中国的旧思想和旧文化来讲,本身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李善兰他们作为科学家,也是洋务运动的参加者,与政治的直接关联虽不大,但又不得不面对政治,故一方面要驳斥封建顽固派的迂腐理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到儒家经典中去寻找立论的根据,以防被人说成是“离经叛道”。
九十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普遍地介绍各门自然科学的情况不同,是着重介绍和引进进化理论和西方科学的最新成果。这中间最著名的代表是严复,才外还有马君武、李郁、鲁迅等多人。而且,在形式上,前一阶段还是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如《谈天》是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合译的,《地学浅释》是华蘅芳同美国传教士合译的。后一阶段则主要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直接吸收和传播。通过他们的努力,十九世纪西
方科学的三大发现都被及时地引进了中国,并成为维新派和革命派进行哲学革命的理论武器。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被系统地引入中国。例如严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国民财物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密尔)的《名学》(《逻辑体系》)和《群己权界论》(《论自由》),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法》),爱德华?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社会进化简史》)等。同时,大量的西方哲学和哲学家也被介绍给中国人。如梁启超在1901~1902年间,就写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的学案和达尔文学说、孟德斯鸠学说、边沁学说,一年后又写了康德学说等。这些著作的引进和传播,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和哲学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节近代哲学的主要特点
近代新学虽然历史相对短暂,但由于是在变局中倡言变革,涉及中外古今的众多方面,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出现了各具特色的思想代表及其成果,故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一、历史进化论成为时代的重心
中国近代哲学史以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而要救亡图存,唯一的道路就是中国要发展、要进化以至要革命。因此,历史进化论比之自然或生物进化论更为人们所关注。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历史进化的学说,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变易思想,一是公羊“三世”说,这二者在近代社会都得到了广泛运用。讲变易的《周易》和讲公羊三世的《春秋公羊传》都是儒家的经典,从它们这里引出历史发展观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古代是如此,近代开初也是如此。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都是这样做的。但龚自珍时尚无进化论的武器,康有为则把变易思想、公羊三世说与进化论结合了起来。不过,严复和后来的革命派不是如此,他们已抛掉了经学的外衣,直接宣扬历史进化论。后者表明了资产阶级自身意识的成熟。
就此,可以说近代的历史进化论吸取了古代社会的变化发展观念,这可说是古今的问题;但在这里更有中西的问题,即它比之西方亦颇具特色。一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大都是从宗教领域、从自然领域开始的,处在第一位的是自然观;另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讲阶级或等级的革命,基本没有民族独立(民族革命)的成分。卢梭说过历史的发展是为阶级的更替,中国人讲历史的发展则既要为阶级,也要为民族和国家,而后者在当时更为突出,讲前者也是为了讲后者。所以,中国人从西方学来了进化论,首先就应用于历史。这一特点,就是在1919年后也是如此。同理,中国人从西方学来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应用的也是唯物史观,然后才是自然观。
二、进化论代替了元气论
元气论或更一般的气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形态之一,在宋明时期,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气论都是其宇宙观的主要构架,现实的世界都是由气所构成,区别只在理是在气之外还是气之中而已。元气论发展到明末清初就已经熟透了,毛病也逐渐显露出来。即到王廷相时为止,人们公认元气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的,是两间无不备,是无限的。但这一观点到宋应星、王夫之这里已经发现其漏洞,即在大地的一定高度以上是所谓“清虚之境”即无气的领域,将宇宙实际上区分为元气(大气)世界和真空世界,这在实质上是正确的。
但这样一来,元气的世界统一性就成了问题,无气的清虚之境怎么可能以气去作为它的根据或本体呢?因此,在理论上元气论已不可能再有发展了。但在当时并没有新的理论可以来代替,所以元气论直到戴震也还在继续。
近代西学的传入,使国人知道了星云假说和以太的概念。星云的流动状态和元气相似,很自然地被康有为用来改造元气,元气起源被星云演化所取代。可以说,从这时起,元气论
从本质上被扬弃了。但从形式看,它在康有为这里还保留着。到谭嗣同、严复,则彻底抛开了元气论的形势。谭嗣同用“以太”否定了气,严复则以“物竞天择”和“质力相推”解释宇宙的演化,回避了宇宙的本体。章太炎和孙中山则完全是以进化论作为思想基础的。进化论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哲学的发展也由此进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论哲学的新阶段。
三、人道博爱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中国古代的儒家是倡导仁爱的。自孔子答樊迟问仁曰“爱人”和讲“泛爱众”开始,历代儒家都是讲爱人和博爱的。但儒家不仅讲博爱,也有爱有差等的思想;前者与墨子的兼爱相通,在此意义上,仁爱、博爱、兼爱就是同一的蕴涵;而后者则是儒家仁爱的另一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共组为儒家的仁爱观。《礼记?礼运》托孔子之口描述了大同与小康,大同便成为儒墨等不同学派学者乃至整个中国人的共同向往。
近代最早提倡人道博爱的是洪秀全。洪秀全从基督教那里搬来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又吸取了先秦墨子等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原道觉世训》)的理想社会,批判了儒家的爱有差等。他的“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原道醒世训》)的对等级差别的批判,代表着农民阶级反封建的最高水平。
就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来看,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是主张人道博爱的。梁启超评价他的老师的哲学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南海康先生传》)。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也是以普遍的人道博爱思想来鼓动民众的。在这种普遍之爱面前,一切差别都不复存在。如谓“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天人同气,无内外之分”(《孟子微》卷一),主张“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的大同之道。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人道:“夫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求乐而已,无他道焉”(《大同书?甲部?绪言》)。谭嗣同以“通”即平等来解释仁,批判了作为对立面的传统纲常伦理。孙中山的人道主义还加进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他认为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即“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的主义,是“为人类谋幸福”主义,是“地尽五洲,时历万世”的最“广义之博爱”。只有这样来理解博爱,才能真正懂得“博爱之精神”(《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简言之,资产阶级的这种全人类普遍之爱的抽象形式,是以直接反对封建等级转制为其实质内容的。即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来说,它是非常具体而毫不抽象的。
四、佛教“唯心”论重受重视
梁启超在1920年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人不与佛学有关系”。事实也大致是如此。龚自珍最先疾呼“更法”,但力量所在却局限于“心力”,把解脱“无量痛苦”的希望寄托于佛祖身上。魏源的情况与他相似。即认为现存的一切(物质)手段都不足以变革社会,故不得不到现实世界之外的天国去寻求支持。所谓“一切有为皆不可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与周冶朴书》)。即以佛心来支持我心,依此解救众生。
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来说,大体情况也差不多。差别自然也是有的,如康有为和孙中山就不太看重佛教。但他们的不看重,并非是对佛教有什么深刻的认识,而是同他们的个人阅历有关。康有为是从今文经学走出来的,即是以儒家为本,当然儒家后来本身也吸收佛教资源,这对康有为也是有影响的;孙中山则是长期生活于国外,是典型的西方式民主主义者。
与他们有别,谭嗣同是在国内接受西方文明的,在他通过梁启超而接受康有为的思想时,又从杨文会等学习佛教,深受维识、华严和禅宗思想的影响。章太炎本是古文经学大家,后来在革命受挫、被投入监狱后,发现法相维识宗讲“自贵其心、不依他力”,最为妥帖,能
够使人民“发起信心”。故在狱三年间,一心专修法相维识之学。并把它与自己所酷爱的古文经学、近代科学等同起来。认为都是实事求是,超过以往一切学术。在这里,他们与德国半个世纪前费尔巴哈有所相似,即要求建立新宗教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它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走的道路,是通过依靠心力而不是人民大众去实现他们的目的。当然,孙中山最后在俄国、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有突破,看到了农工的力量。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什么大都崇佛的问题,梁启超1902年末有两篇文章(《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论宗教与群治之关系》)可以参考。
第二章龚自珍、魏源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古代社会步入后期,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人士和进步思想家,依托于今文经学,强调经世致用,联系学术和政治,主张变革,在思想界引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他们的主要代表是龚自珍和魏源。从思想性质上说,这可看作是封建阶级的思想家们为挽救既有制度而进行的自我批判,他们的理论可以说达到了在旧制度框架内所能够容纳的最大的限度。
一、变易与变法
龚自珍、魏源所在的时代,已经进入到了清王朝的“衰世”,其时的社会状况,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不可支日月,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多种,如贫富两级严重分化,鸦片走私,白银外流等,但统治者却把负担转嫁到小农身上,致使农村经济迅速破产。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改革、要变法。所谓“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倘不然,“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命噍类靡有孑遗”(《平均篇》),多么触目惊心!
因此,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自己不变,后来者也会变,而“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即希望清王朝自己能主动起来改革。龚自珍鼓吹改革的武器,主要是变易思想和公羊三世说。从变易看,他强调“一祖之法无不弊”,故社会的发展就必然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同上)。这一变易思想表现在历史发展中,就是所谓公羊三世说。
“三世”来源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谓(孔子)“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注解《公羊传》时,把三者分别注解“见治起于率乱之中”(所传闻~衰乱世),“见治升平”(所闻~生平世)和“著治太平”(所见~太平世),社会的发展,便是三世间的循环更替: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简言之,就是由衰乱世向升平世和太平世变化。但就此点说,《公羊传》只是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十二公的历史作讲解,龚自珍也只是一般性地讲到循环变易,所谓“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际胎观第五》),到康有为它才真正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
魏源讲变易的特点,是强调今胜于古,反对把上古三代看作是不可企及的人间盛世。因为三代本身就是在变化之中,“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必然的结论就是“后世之事胜于三代”(《默觚?治篇五/九》)。魏源认为,对于“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筹鹾篇》)的变法必然要求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点,这就是“人情”。故变祖宗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便民”。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变革就将是不可逆转的。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胜。……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之于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默觚下?治篇五》)
“变古愈尽,便民愈胜”的提出,表明魏源已朦胧地意识到,古代制度亦即封建制度是不“便民”、“利民”的制度而应当予以否定。当然,在自觉的意义上,他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的这些观点,主要还是立足于他所目睹的鸦片战争惨败的现实和作为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上。
魏源强调,要“知《大易》作者之忧患”,故“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海国图志叙》)。这种忧患或忧愤的意识,可以说是改革的原动力。即他所称:“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同
上)
但是,要改革光有动力还不行,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手段,他以为这就是学习外国,故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同上)的策略方针。这里的“长技”,具体指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但也有一般性的学习西方的意义,开了我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先河。因为在魏源看来,道理很简单,“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州各国总叙》)。他据此批驳了那些宁愿向外国赔偿巨款以求妥协,而不愿学习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封建顽固派(见《海国图志?畴海篇三》),表现了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情怀。
二、自我与心力
龚自珍、魏源哲学一个显著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特点,就是他们对“自我”的极端看重,把自我推崇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龚自珍提出:“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翅,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不过,在他们这里,“自我”不是孤独的我自身的自我,而是指众人、即集体的自我。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同上)。显然,这种以集体的自我出现的,是一种过去未曾有过的意志力量,是一种主体精神,它与绵亘古代哲学二千余年的圣人史观、圣人主宰是针锋相对的,表明了人的意识已开始觉醒,已经可以嗅到近代人文主义的气息。
龚自珍认为,人的意志力量(心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提出“人心者,世俗之本也”(《平均篇》),故“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这种对心力的过分推崇,也说明他们没有能找到变革社会的真正现实力量,于是就只好借助从佛教或心本论哲学家那里搬来的心力。魏源说,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点,“人知心在身中,不知身在心中也,万物皆备于我矣”(《默觚上?学篇五》)。这种自我之心也就成为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所谓“事必本乎心”,“物必本乎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从而,必然的结论就是:“人定胜天”(《默觚上?学篇八》)。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改造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预示着封建统治的“天”实际上无法再补,而应当予以改换了。尽管从他们的主观愿望说,他们是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的。但是,毕竟这些新思想的提出,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所谓“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可以看作是对他们思想的最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