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女性作品中看女性悲剧命运论文
- 格式:doc
- 大小:24.5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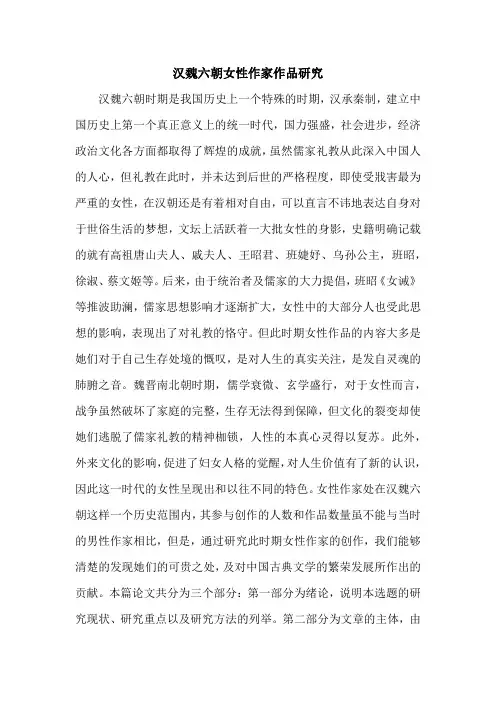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研究汉魏六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汉承秦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时代,国力强盛,社会进步,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儒家礼教从此深入中国人的人心,但礼教在此时,并未达到后世的严格程度,即使受戕害最为严重的女性,在汉朝还是有着相对自由,可以直言不讳地表达自身对于世俗生活的梦想,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女性的身影,史籍明确记载的就有高祖唐山夫人、戚夫人、王昭君、班婕妤、乌孙公主,班昭,徐淑、蔡文姬等。
后来,由于统治者及儒家的大力提倡,班昭《女诫》等推波助澜,儒家思想影响才逐渐扩大,女性中的大部分人也受此思想的影响,表现出了对礼教的恪守。
但此时期女性作品的内容大多是她们对于自己生存处境的慨叹,是对人生的真实关注,是发自灵魂的肺腑之音。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微、玄学盛行,对于女性而言,战争虽然破坏了家庭的完整,生存无法得到保障,但文化的裂变却使她们逃脱了儒家礼教的精神枷锁,人性的本真心灵得以复苏。
此外,外来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妇女人格的觉醒,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这一时代的女性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特色。
女性作家处在汉魏六朝这样一个历史范围内,其参与创作的人数和作品数量虽不能与当时的男性作家相比,但是,通过研究此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我们能够清楚的发现她们的可贵之处,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繁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本篇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说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的列举。
第二部分为文章的主体,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汉魏六朝时期女性风貌,从社会地位、受教育状况、才智、以及独立意识几个方面来作一细致的阐述,从而回顾了这一时期女性作家作品繁荣的文化背景和成因。
第二章:从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及女性心灵探究入手,分时代研究了各个时期女性作品中折射出的女性心灵,此外对女性作家的创作动机进行探讨,以展示此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动因。
第三章:选取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四位女性作家,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揭示其独特的人生体验,探索在以男性文化为主的时代背景之下,女性文学创作的共性和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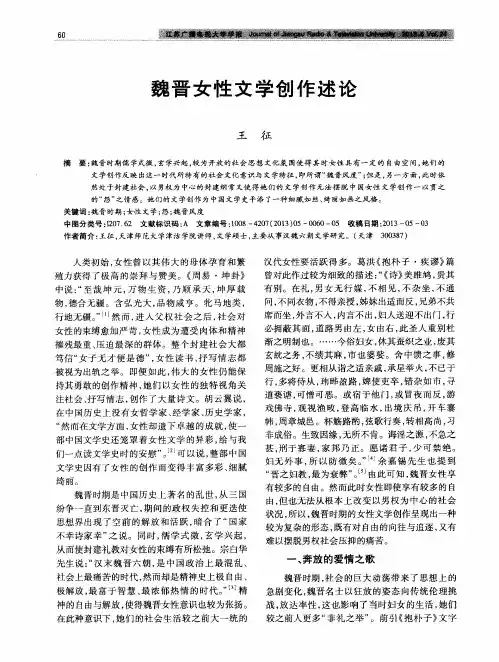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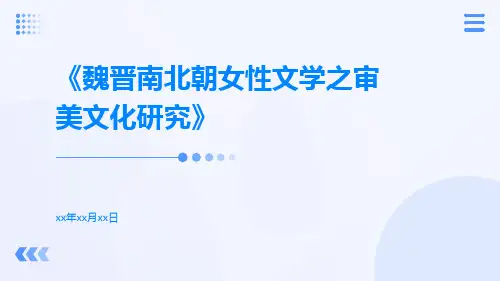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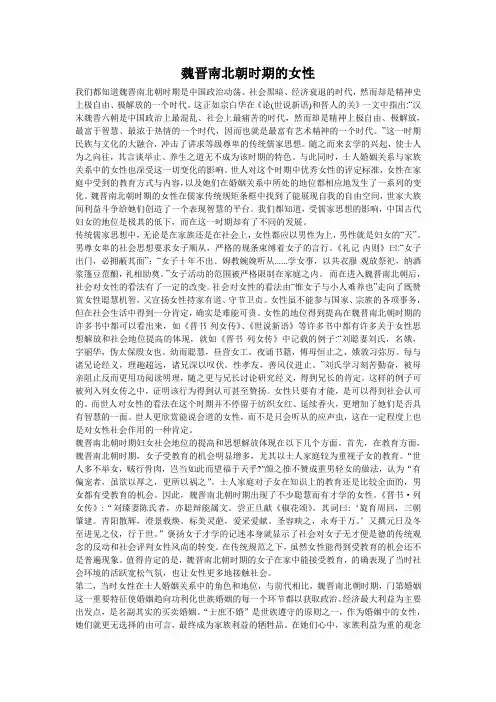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动荡、社会黑暗、经济衰退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代。
这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关》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一时期民族与文化的大融合,冲击了讲求等级尊卑的传统儒家思想。
随之而来玄学的兴起,使士人为之向往,其言谈举止、养生之道无不成为该时期的特色。
与此同时,士人婚姻关系与家族关系中的女性也深受这一切变化的影响。
世人对这个时期中优秀女性的评定标准,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方式与内容,以及她们在婚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都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在儒家传统规矩条框中找到了能展现自我的自由空间,世家大族间利益斗争给她们创造了一个表现智慧的平台。
我们都知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极其的低下,而在这一时期却有了不同的发展。
传统儒家思想中,无论是在家族还是在社会上,女性都应以男性为上,男性就是妇女的“天”。
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要求女子顺从,严格的规条束缚着女子的言行。
《礼记·内则》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女子十年不出。
姆教婉娩听从......学女事,以共衣服·观放祭祀,纳酒浆篷豆范酿,礼相助奠。
”女子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
而在进入魏晋南北朝后,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
社会对女性的看法由“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走向了既赞赏女性聪慧机智,又宣扬女性持家有道、守节卫贞。
女性虽不能参与国家、宗族的各项事务,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一分肯定,确实是难能可贵。
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书中都可以看出来,如《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等许多书中都有许多关于女性思想解放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体现,就如《晋书·列女传》中记载的例子:“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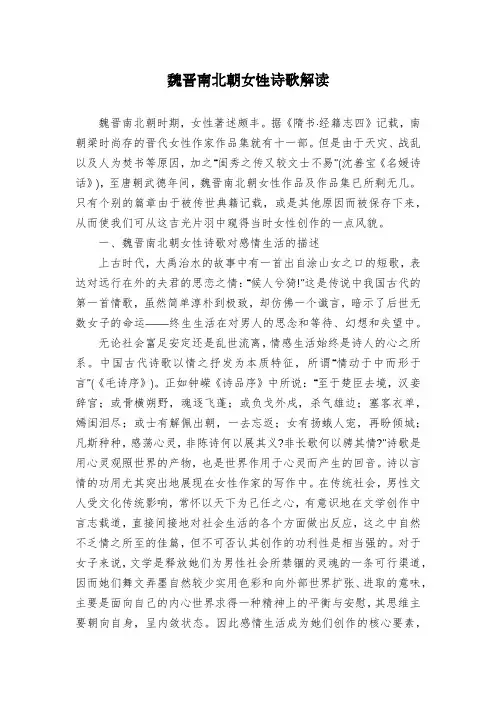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女性诗歌解读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著述颇丰。
据《隋书·经籍志四》记载,南朝梁时尚存的晋代女性作家作品集就有十一部。
但是由于天灾、战乱以及人为焚书等原因,加之“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沈善宝《名媛诗话》),至唐朝武德年间,魏晋南北朝女性作品及作品集已所剩无几。
只有个别的篇章由于被传世典籍记载,或是其他原因而被保存下来,从而使我们可从这吉光片羽中窥得当时女性创作的一点风貌。
一、魏晋南北朝女性诗歌对感情生活的描述上古时代,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有一首出自涂山女之口的短歌,表达对远行在外的夫君的思恋之情:“候人兮猗!”这是传说中我国古代的第一首情歌,虽然简单淳朴到极致,却仿佛一个谶言,暗示了后世无数女子的命运——终生生活在对男人的思念和等待、幻想和失望中。
无论社会富足安定还是乱世流离,情感生活始终是诗人的心之所系。
中国古代诗歌以情之抒发为本质特征,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
正如钟嵘《诗品序》中所说:“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嫣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人宠,再盼倾城;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歌是用心灵观照世界的产物,也是世界作用于心灵而产生的回音。
诗以言情的功用尤其突出地展现在女性作家的写作中。
在传统社会,男性文人受文化传统影响,常怀以天下为己任之心,有意识地在文学创作中言志载道,直接间接地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反应,这之中自然不乏情之所至的佳篇,但不可否认其创作的功利性是相当强的。
对于女子来说,文学是释放她们为男性社会所禁锢的灵魂的一条可行渠道,因而她们舞文弄墨自然较少实用色彩和向外部世界扩张、进取的意味,主要是面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求得一种精神上的平衡与安慰,其思维主要朝向自身,呈内敛状态。
因此感情生活成为她们创作的核心要素,在作品篇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相思之情。
女性的生活状态随着社会的变动而起伏不定,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封建社会的妇女始终处于对男性的依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情的命运就是她们的根本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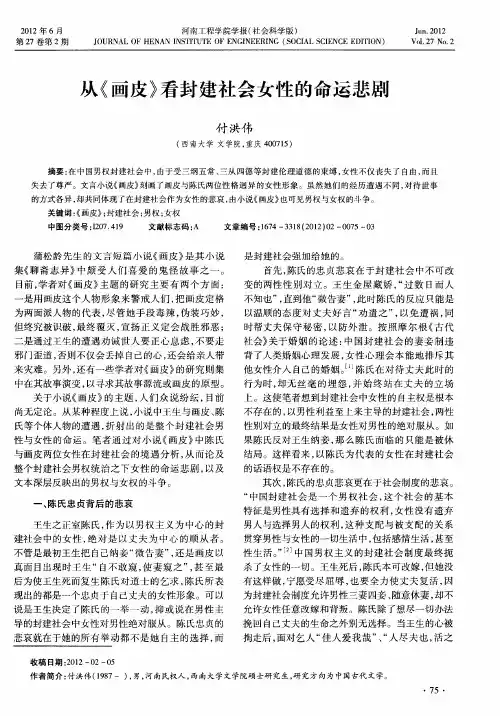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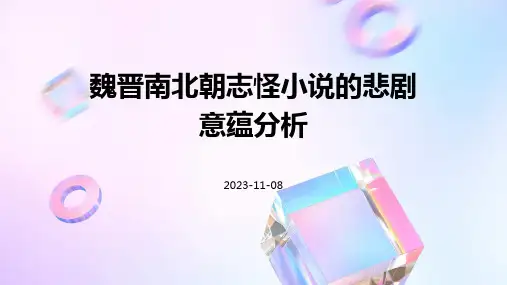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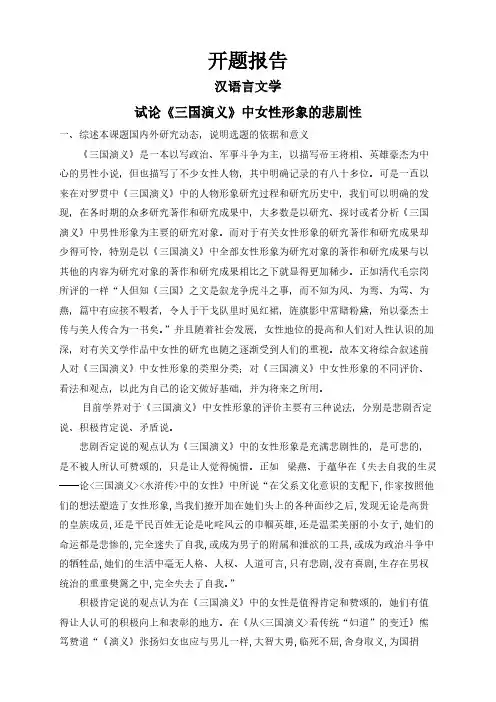
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试论《三国演义》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三国演义》是一本以写政治、军事斗争为主,以描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为中心的男性小说,但也描写了不少女性人物,其中明确记录的有八十多位。
可是一直以来在对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研究过程和研究历史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在各时期的众多研究著作和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是以研究、探讨或者分析《三国演义》中男性形象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而对于有关女性形象的研究著作和研究成果却少得可怜,特别是以《三国演义》中全部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与以其他的内容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就显得更加稀少。
正如清代毛宗岗所评的一样“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风、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杰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和人们对人性认识的加深,对有关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故本文将综合叙述前人对《三国演义》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分类;对《三国演义》中女性形象的不同评价、看法和观点,以此为自己的论文做好基础,并为将来之所用。
目前学界对于《三国演义》中女性形象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说法,分别是悲剧否定说、积极肯定说、矛盾说。
悲剧否定说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是充满悲剧性的,是可悲的,是不被人所认可赞颂的,只是让人觉得惋惜。
正如梁燕、于蕴华在《失去自我的生灵——论<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女性》中所说“在父系文化意识的支配下,作家按照他们的想法塑造了女性形象,当我们撩开加在她们头上的各种面纱之后,发现无论是高贵的皇族成员,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还是温柔美丽的小女子,她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完全迷失了自我,或成为男子的附属和泄欲的工具,或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她们的生活中毫无人格、人权、人道可言,只有悲剧,没有喜剧,生存在男权统治的重重樊篱之中,完全失去了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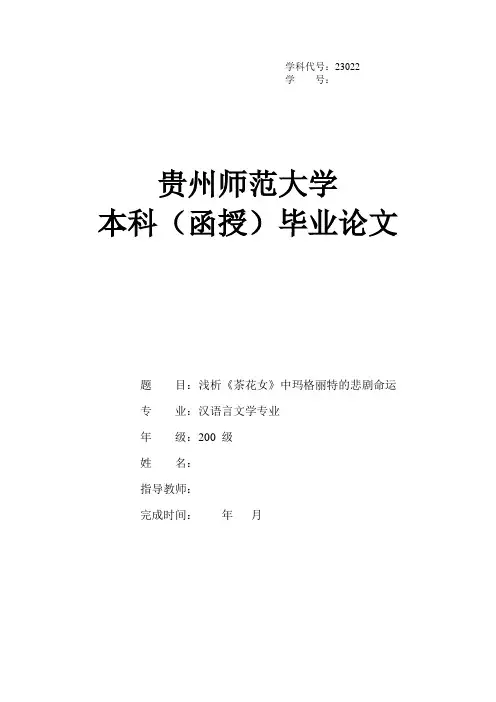
学科代号:23022学号:贵州师范大学本科(函授)毕业论文题目:浅析《茶花女》中玛格丽特的悲剧命运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年级:200 级姓名:指导教师:完成时间:年月论文开题报告贵州师范大学凯里学院成教(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语浅析《茶花女》中玛格丽特的悲剧命运XXX(凯里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函授本科2008级,贵州凯里556000)摘要:《茶花女》中玛格丽特的性格和与阿耳芒所谓爱情故事为故事的主要内容和线索,叙述了一个“纯洁妓女”的善良与宽容,她因爱而美丽,因爱而高尚,她为爱积极向上,为爱而积极的反抗命运。
然而,她个人的力量是脆弱的,他们的爱不仅是玛格丽特性格的悲剧,是伦理道德造成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玛格丽特、善良、高尚、脆弱、悲剧。
Abstract: "La Traviata" in Margaret's character and the so-called with A love storyfor the ear mount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story and clues, described a "pure prostitute" kindness and tolerance, love and beautiful she was, because of love noble, her love of positive, for the love and positive resistance to fate. However, her personal power is fragile, and their love is not only a tragedy of character, Margaret, is the moral cause of the tragedy, it is a social tragedy.Keywords: Margaret, kind, noble, fragile tragedy.小仲马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小说家、戏剧家。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后妃研究姓名:李玉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指导教师:郑佩欣20040506 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
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奎垂日期:丝Q螳皇里鲤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论文作者签名:奎垂导师签名:耋幽丝日期:至QQ喧兰目纽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魏晋南北识前后跨度近400年,社会极端动荡、思想却极为自由活跃。
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本时期皇后、嫔妃的生存状况、价值取向大不同于其他时期,在古代中国后妃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笔者在查阅正史、稗史、笔记、文集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借助于数据统计与量化分析的方法,全方位地展现了魏晋南北朝后妃的生活全貌。
力求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后妃的研究,透视这一时期后妃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分析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及区域人文环境对后妃生活、个性的影响,进而为魏晋南北朝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观察视角。
本文共包括九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魏晋南北戟时期后妃的入宫途径着手,对其婚龄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她们的婚龄趋势。
这一时期后妃的入宫途径,大致有采选、政治联姻、战乱中迎娶或劫夺、籍没等。
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看到:从曹魏到北魏末年,后妃的婚龄一般呈下降趋势,但北齐、北周后妃的婚龄有所上升,高于北魏时期。
南朝后妃的婚龄则普遍高于北朝。
浅谈古代中国的女子悲剧古代中国的女子悲剧古代中国,女子向来是以悲剧的形式存在,比如说我最爱的宋朝,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这件事涉及了皇帝,欧阳修,王安石以及当时的宋朝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
有一个叫阿芳的女孩,因为家里穷被卖给同乡的一个家徒四壁(真的穷的家里只有承重墙)叫阿大的,但是阿芳不愿意嫁给他于是在举办结婚典礼的晚上,阿芳找了家里的砍柴刀试图暗杀阿大。
但是她失败了不过逃脱了,第二天县令就抓住了前来自首的阿芳,县令判她暗杀老公未遂,死刑!死刑在宋朝是最高的刑罚,仅次于死刑的是流放海南岛。
在宋朝,死刑是要通过皇上审核,只有获准审核通过才能执行,宋仁宗也是出了名的心地善良,于是不忍心看在阿芳受这么大苦的份上于心不忍,不批准执行。
但是文武百官却对皇帝的行为表示驳斥,王安石为首的宰相认为支持皇帝的意见,阿芳的行为是实在是情有可原的,谁都不会去嫁给一个穷的家徒四壁四面承重墙的家伙。
但是欧阳修为首的宰相则普遍认为,不能放过阿芳,应该立即执行死刑以视对国家法律的敬畏与遵守。
随着事态的发展,人多嘴杂,包括宫廷也好,民间也好,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人说皇帝太仁慈了,有人说阿芳是被人陷害的工具,有人说是县令搞的鬼故意偏袒阿大。
总之是众说纷纭,但是宋仁宗还是顶住压力试图去无罪释放阿芳,可是御史台和谏院死活不给皇上台阶下,他们一致认为不处罚阿芳无论是否是死刑都一定要给阿芳定罪,这让宋仁宗很难堪。
连着好几个月从上朝到下朝都在无休止的争吵,阿芳最终还是被宋仁宗皇帝下令释放了。
她开始更名改姓又嫁给了一个农夫但是至少比阿大强不少,她也心甘情愿地生活但是是提心吊胆的生活着,她害怕阿大找到她带她回去。
不过显然她是多虑了,阿大已经死了,这个她不知道。
有一个大臣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他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从坚定的要杀掉阿芳!终于欧阳修盼到了机会,宋仁宗驾崩,宋神宗即位,王安石也死了,只有欧阳修是一朝宰相,我官最大百官之首。
于是他下令将改头换面的阿芳抓住了,终于将她处以死刑,告诫天下。
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一)论文关键词:妇女的文学批评;《与妹刘氏书》;“以诗论诗,卒章见志”论文摘要: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
首要表征在于从“人物藻鉴”发展为专门的文学批评,并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等一批论着。
特征之二是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东晋才女谢道韫以其形象化的批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时人及后人;早见于《诗经》的“卒章见志”在这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两相结合,成为了一种时代风尚。
经历了从先秦至两汉的漫长滥殇阶段之后,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特征有二:其一,“文学批评”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初期带有较多的“人物藻鉴”的痕迹,后期则转向专门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答程骏表上(庆国颂)令》、《答程均表上(得一颂)令》等一批论着;其二,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
”一、从“人物藻鉴”到“文学批评”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文学批评,其中夹杂着相当多的“人物藻鉴”,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就是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就具体发展过程来看,则大约经历了一个从“纯粹的人物藻鉴”到“在人物品评中包含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再到“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人物”直至最终独立为专门的“文学批评”的过程。
汉末以降,女学渐衰,惟晋代稍隆,六朝妇女能文者多出缙绅之家,尤以两晋为最,如:晋左思妹左棻、谢安侄女谢道韫、卫展女卫铄;齐鲍照妹鲍令晖;梁刘孝绰妹刘令娴等;皆出缙绅之家,从父兄受业,并有才名。
藻鉴人物的风气既在社会广为流传,受父兄影响,女子也多有浸染,如:韩氏之观狐赵,钟琰之相兵儿,卫铄之赞曦之,道韫之叹王郎……眼观口赞之外,更有一些妇女干脆书之文字:左棻有《孟轲母赞》等十余篇关于贤妇人的赞辞,王绍之有《姜螈颂》、《启母涂山颂》,孙琼有《公孙夫人序赞》其中的佼佼者当属左棻,她大概是第一位专事人物品评的女性,写作了《巢父惠妃赞》、《虞舜二妃赞》、《周宣王姜后赞》等十余篇赞辞,用于歌颂、评价自古迄晋素有才德的名女。
一部中国封建史,是一部中国古代妇女悲剧命运的血泪史,一部女性向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史。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但凡伟大的作品,作者都能由自己的生命个体对人生、自然、宇宙的思考后而认识到人类的终极命运的悲剧性。
一个生命个体,由生则会死,由喜则有忧,由胜就有败,由聚就有散,由祸就有福。
人生尚且不满百,何必常怀千岁忧。
人生在世,日月相生,阴阳交替,乾坤转移,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盛宴。
德国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因意志而生活着,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意志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生是痛苦的。
我想叔本华所说意志应该就是人的欲望吧。
《红楼梦》中说出了人生的几个欲望:功名、金银、娇妻、儿孙。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子孙满堂,延续香火,绿叶成阴子满枝,是古人的追求。
由于古代公子本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思想,必须在仕途上谋个前程,这也是古代年轻男子的唯一出路。
却不像现在条条大路通罗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为此,封建家长总打着一些旗号,或者是影响功名,或者是无嗣,或者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将所有的罪过统统压在了女性的身上。
《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对妇女具有歧视性的“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由于受到这个顽固不化思想的禁锢,在古典文学中有许多女性的悲剧或多或少可以从中找到它的影子。
这也为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
说到爱情,我想大多数人会有自己不同的感悟,魂牵梦绕,痛彻心扉….女人作为常用感性思考问题的动物,对于爱情更是如罂粟般,一染就无法自拔。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可以发现,女性的感情故事总是以悲剧收场。
祝英台跳进梁兄的坟墓为爱化蝶;白素贞千里迢迢为许仙盗取仙草,甘冒天规水漫金山,即使最后被镇雷锋塔;关盼盼被白居易一首“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而逼死。
封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小组成员:蔡煌、周健、胡龙飞论文撰写:蔡煌中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
因此,诸如“男尊女卑”(语出《周易》)、“男主外,女主内”(语见《大易通解》)、“女子以弱为美”(源自班昭《女诫》),与“女子无才便是德”(参见《易酌》)等说法,确实对中国的女性影响深远,也已发展成多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导致极多女性的才艺,终其一生,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些女性的处境与心声,透过一些优秀艺术品的诠释,如《红楼梦》、《西厢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作品,才幸运地博得同情与关注。
中国古代有不少给女性的人身自由加以摧残和束缚的封建礼教和陋习,其中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妻四妾”、以缠足为美等。
商周二代是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两个王朝的更迭完成了由父系制的高级阶段(商代)向父权制时代(以周礼确立为标志)的过渡。
从此,为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造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
女性地位之全面低落,既肇因于这种宗法伦理所维护的男性统治,男性统治更藉这种宗法伦理而大行其道,世泽绵长。
一、女性是父权社会的经济附庸。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丧失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只得借助婚姻或血缘的关系,依附于男子,沦为家庭的奴隶。
旧时有“男称丁,女称口”之说,封建时代皆以一家中“丁”的数目分配土地和担负赋税,把女性排除在外。
这“计丁受田”制度最典型说明女性毫无经济地位的事实。
女性在家庭中也没有私有财产。
《礼记•内则》谓“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这就是说,女子在出嫁前没有财产,出嫁后作为妻媳也无私有财产,甚至女子从娘家带去的财产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了。
有些女性出于家庭的原因被迫出外劳动,仍一样为男性所歧视,冠以“三姑六婆”之称。
有时女性甚至沦为男性买卖的对象,有卖为奴婢、卖为妻妾、卖为童养媳、卖为娼妓,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都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造成的。
从魏晋南北朝女性作品中看女性悲剧命运
摘要:在封建社会中,女性从来都被人为是男性的附属品而存
在,因此她们的命运也多数具有悲剧色彩。在大量的女性作品中可
以反映着一点,在社会动荡变革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悲剧性更加
突出。本文将从魏晋南北朝的女性作品入手分析,从亲人分离的无
奈、独守空房的咏叹、壮志难酬的愤懑这三个方面解读当时女性的
悲剧命运,从而了解当时社会女性心理。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时期 女性作品 悲剧命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革,时局动荡,男儿尚且朝不保夕,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女性的命运就更为悲惨。但也正是
因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封建礼教的束缚力也大大减弱,使得这段时
期女性作品也空前繁荣。正如钟嵘《诗品序》中所说:“感荡心灵,
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其作品往往能反映当时
作者的内心情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她们的作品里也能折射
出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时代人物的命运。由于社会大背景动乱的原
因,在这些女性作品中,反映多为悲情之作。纵观这一时期的女性
作品,悲情固然是她们在诗文中的主旋律,然而因为个人身份地位,
人生际遇不同,所表现的悲剧特征也有所差异,根据她们在作品中
所反映的主题,可以分为以下情况。
一、 亲人分离的无奈
魏晋时期,士族寒门等级观念十分严重,下层寒门女子往往比
士族女性更加受人歧视,接受的教育也比较少。而有一个女子则是
一个例外,她就是左思的妹妹左棻。也因为她的才华,使得当时附
庸风雅的皇帝召其进宫,也导致了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对于有机会嫁入天家的女子来说,本应欢喜,但是左棻的认识
是清醒的,即将离开自幼相依为命的兄长,左棻的心中是无限的悲
苦与迷惘。她在所作《感离诗》写到:“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
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其中辛酸,可见一斑。入宫之后,事
实证明左棻的担忧并不是多虑的,“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
多患,常居薄室……”1对于后宫佳丽众多的皇帝来说,又丑又病
的左棻自然只能作为皇帝一时兴起的牺牲品,从此孤苦无依,在她
的作品中怨怼之情溢于言表:《离思赋》中“何宫禁之清切兮,欲
瞻睹而莫因”描述与兄长分离的思念与痛苦;“惨怆愁悲,梦想魂
归,见所思兮。”则是她对家乡的眷恋与不舍;“狐死首丘,人何以
堪”这种连死也不能落叶归根的愁苦令这位女诗人肝肠寸断,因此
她只能执笔抒怀: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
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眺,心不自聊,泣涟湎兮。援笔
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2 这样一份颇有盛名的才女命运尚且
如此,对于无数口不能语,笔不能书的寒门女子其悲惨境遇我们更
是可想而知了。
二、独守空房的咏叹
作为封建时代的女性,无论是端庄的嫔妃贵妇,还是穷困的下
层糟糠,生活大都是不尽人意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女性作品中,这
方面的反映也非常多。南朝宋代文学家鲍照之妹鲍令晖的《代葛沙
门妻郭小玉诗二首》中,描绘了当时妻妾在闺中的相思之情,也向
我们宣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咏怀文化。“明月何皎皎,垂櫎照罗茵。
若共相思夜,知同忧怨晨。芳华岂矜貌,霜露不怜人。君非青云逝,
飘迹事咸秦。妾持一生泪,经秋复度春。”以郭小玉的口吻写出了
女子的辛酸苦悲,而“一生泪”三个字,更是高度凝练了丈夫久久
不归,妻子担忧、恐惧,终日以泪洗面的情景,可谓感人至深。而
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之中“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相思。君忘妾,未
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中一句“君忘妾,未
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则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女之不公,
也反映出作为女性心中之苦悲。在当时残酷的社会背景中,统治者
无能而奢华,导致战乱四起,离人不归,生死不定,千万妇女饱受
忧虑之苦。她们把满腔悲恸诉于笔墨,字字血泪,句句控诉,诉说
着乱世女子的悲剧命运。
三、壮志难酬的愤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混乱的时代。朝不保夕的生活是当时
的人有一种无力感。生逢乱世,命如朝露,渴望建功立业不只是男
儿的梦想,许多有才华有抱负的女性也在诗文中表现了心中不平之
气。在魏晋时期,男儿尚且不敢轻言政治,清谈玄言,在重男轻女
的观念,女子纵然心怀天下,却也无可奈何,使得这些自负才学的
女子只有“以诗言志”,表现自我志趣。
东晋的谢道韫被世人认为是“女中豪杰”的原因不仅因为她出
身名门望族,而是因为她临危不惧的气度,据史料记载,“既闻夫
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婶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
乃被虏。其外孙刘涛时年数岁,贼又欲害之,道韫曰:‘事在王门,
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恩虽毒虐,为之改容,乃不害
涛。”3由此可看出谢道韫的气度果敢。在其所作的《拟嵇中散诗》:
“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飘”和《泰山吟》中“峨峨东岳高,秀极
冲青天”中无不留露出作者满腔斗志却流离于乱世的内心愤懑之
情,而这种情感不仅是反映作者的个人际遇,更是整个社会给女性
带来的心理冲击。
而左棻的作品《啄木诗》中:“无干于人,唯志所欲。”4则以啄
木鸟自比,表现自己无欲无求、洁身自好的独立人格和高洁品德。
钟琰的《遐思赋》通过对秋景的描写表现出是对世事变迁的伤叹,
亦是对生命瞬时即逝的无奈。这些女性作品中借着对物事的咏怀寄
托生于乱世的幽怨以及对生命自身的悲悯。
魏晋南北朝的女性作品虽然在数量上有限,但其意义却是深远
的。这些作品中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面貌,
但也可以从其中所描写的女性情感把握她们生活中与整个社会的
联系,窥见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人民生活状况。战乱四起、社会
动荡不安给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其中以处于
劣势的女性尤为突出,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她们将心中的无奈,哀伤,
悲恸,愤懑诉于作品中,对于这些作品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当时女
性的悲剧命运以及当时的心理,这对研究魏晋时期的文学史有着重
要的意义。
注释:
1 《晋书》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第731页
3《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第730页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