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_李喜仁
- 格式:pdf
- 大小:157.11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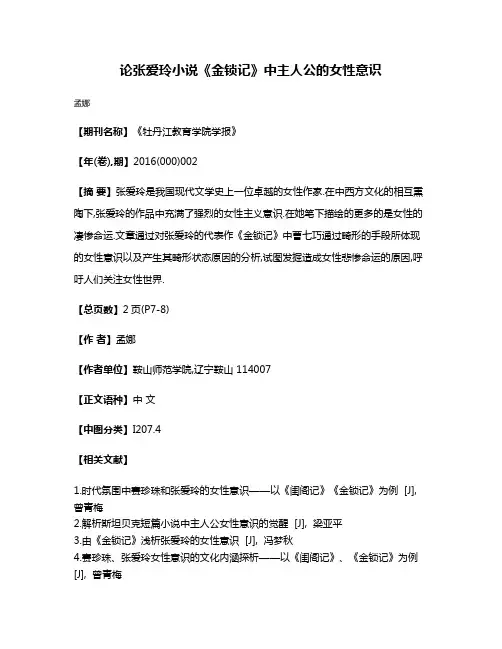
论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主人公的女性意识
孟娜
【期刊名称】《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00)002
【摘要】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卓越的女性作家.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熏陶下,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她笔下描绘的更多的是女性的凄惨命运.文章通过对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中曹七巧通过畸形的手段所体现的女性意识以及产生其畸形状态原因的分析,试图发掘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原因,呼吁人们关注女性世界.
【总页数】2页(P7-8)
【作者】孟娜
【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辽宁鞍山 114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
【相关文献】
1.时代氛围中赛珍珠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以《闺阁记》《金锁记》为例 [J], 曾青梅
2.解析斯坦贝克短篇小说中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 [J], 梁亚平
3.由《金锁记》浅析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J], 冯梦秋
4.赛珍珠、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文化内涵探析——以《闺阁记》、《金锁记》为例[J], 曾青梅
5.包天笑小说《金粉世家》中的金太太形象——兼与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比较 [J], 丘雪晶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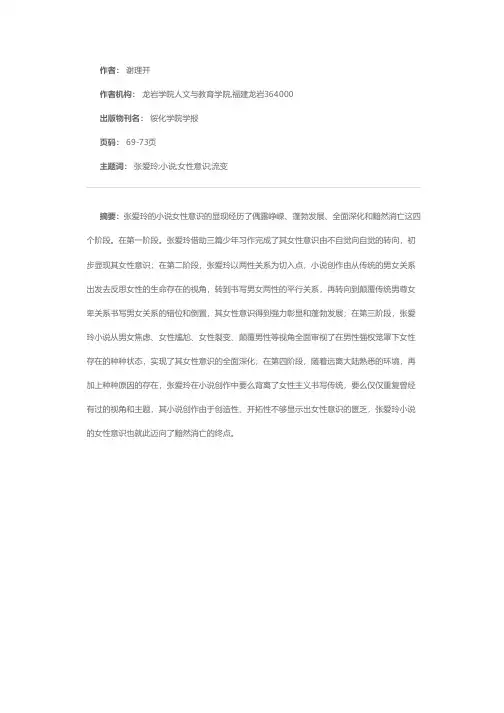
作者: 谢理开
作者机构: 龙岩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福建龙岩364000
出版物刊名: 绥化学院学报
页码: 69-73页
主题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流变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女性意识的显现经历了偶露峥嵘、蓬勃发展、全面深化和黯然消亡这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张爱玲借助三篇少年习作完成了其女性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向,初步显现其女性意识;在第二阶段,张爱玲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小说创作由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的视角,转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行关系,再转向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其女性意识得到强力彰显和蓬勃发展;在第三阶段,张爱玲小说从男女焦虑、女性尴尬、女性裂变、颠覆男性等视角全面审视了在男性强权笼罩下女性存在的种种状态,实现了其女性意识的全面深化;在第四阶段,随着远离大陆熟悉的环境,再加上种种原因的存在,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要么背离了女性主义书写传统,要么仅仅重复曾经有过的视角和主题,其小说创作由于创造性、开拓性不够显示出女性意识的匮乏,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也就此迈向了黯然消亡的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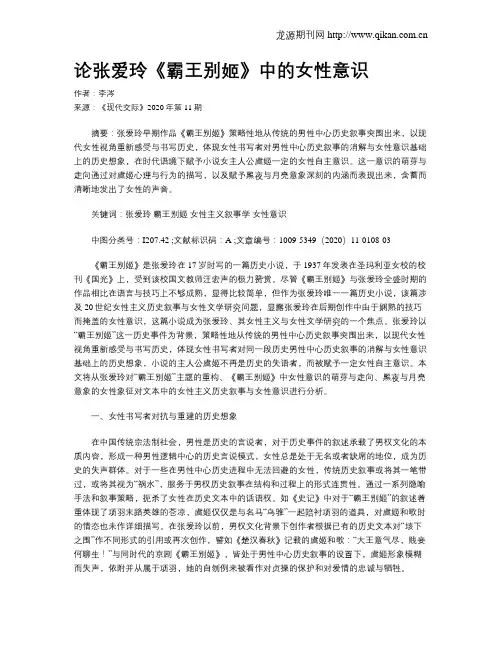
论张爱玲《霸王别姬》中的女性意识作者:李涔来源:《现代交际》2020年第11期摘要:张爱玲早期作品《霸王别姬》策略性地从传统的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突围出来,以现代女性视角重新感受与书写历史,体现女性书写者对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消解与女性意识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在时代语境下赋予小说女主人公虞姬一定的女性自主意识。
这一意识的萌芽与走向通过对虞姬心理与行为的描写,以及赋予黑夜与月亮意象深刻的内涵而表现出来,含蓄而清晰地发出了女性的声音。
关键词:张爱玲霸王别姬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1-0108-03《霸王别姬》是张爱玲在17岁时写的一篇历史小说,于1937年发表在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国光》上,受到该校国文教师汪宏声的极力赞赏。
尽管《霸王别姬》与张爱玲全盛时期的作品相比在语言与技巧上不够成熟,显得比较简单,但作为张爱玲唯一一篇历史小说,该篇涉及20世纪女性主义历史叙事与女性文学研究问题,显露张爱玲在后期创作中由于娴熟的技巧而掩盖的女性意识,这篇小说成为张爱玲、其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
张爱玲以“霸王别姬”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策略性地从传统的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突围出来,以现代女性视角重新感受与书写历史,体现女性书写者对同一段历史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消解与女性意识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小说的主人公虞姬不再是历史的失语者,而被赋予一定女性自主意识。
本文将从张爱玲对“霸王别姬”主题的重构、《霸王别姬》中女性意识的萌芽与走向、黑夜与月亮意象的女性象征对文本中的女性主义历史叙事与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女性书写者对抗与重建的历史想象在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男性是历史的言说者,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承载了男权文化的本质内容,形成一种男性逻辑中心的历史言说模式,女性总是处于无名或者缺席的地位,成为历史的失声群体。
对于一些在男性中心历史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女性,传统历史叙事或将其一笔带过,或将其视为“祸水”,服务于男权历史叙事在结构和过程上的形式连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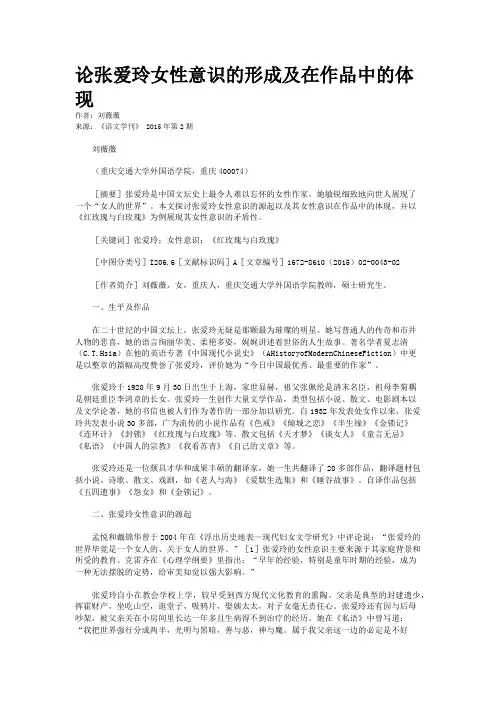
论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形成及在作品中的体现作者:刘薇薇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2期刘薇薇(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摘要]张爱玲是中国文坛史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作家,她敏锐细致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女人的世界”。
本文探讨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源起以及其女性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并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例展现其女性意识的矛盾性。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意识;《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2-0043-02[作者简介]刘薇薇,女,重庆人,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
一、生平及作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张爱玲无疑是那颗最为璀璨的明星。
她写普通人的传奇和市井人物的悲喜,她的语言绚丽华美、柔艳多姿,娓娓讲述着世俗的人生故事。
著名学者夏志清(C.T.Hsia)在他的英语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中更是以整章的篇幅高度赞誉了张爱玲,评价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张爱玲于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自1932年发表处女作以来,张爱玲共发表小说30多部,广为流传的小说作品有《色戒》《倾城之恋》《半生缘》《金锁记》《连环计》《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散文包括《天才梦》《谈女人》《童言无忌》《私语》《中国人的宗教》《我看苏青》《自己的文章》等。
张爱玲还是一位颇具才华和成果丰硕的翻译家,她一生共翻译了20多部作品,翻译题材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如《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和《睡谷故事》。
自译作品包括《五四遗事》《怨女》和《金锁记》。
二、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源起孟悦和戴锦华曾于2004年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评论说:“张爱玲的世界毕竟是一个女人的、关于女人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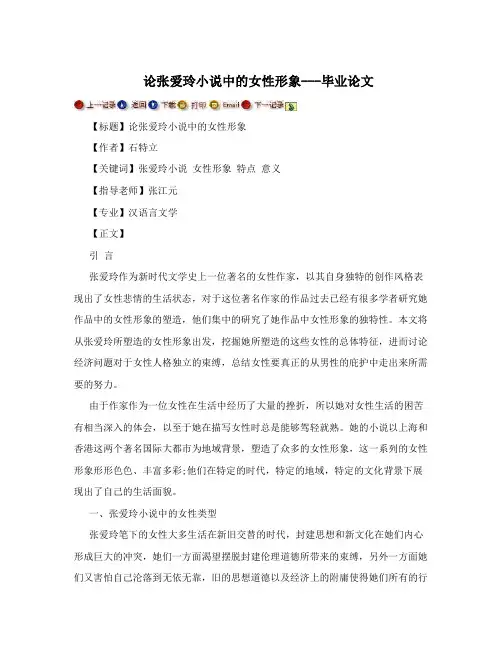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毕业论文【标题】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者】石特立【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特点意义【指导老师】张江元【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引言张爱玲作为新时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女性作家,以其自身独特的创作风格表现出了女性悲情的生活状态,对于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过去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他们集中的研究了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独特性。
本文将从张爱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出发,挖掘她所塑造的这些女性的总体特征,进而讨论经济问题对于女性人格独立的束缚,总结女性要真正的从男性的庇护中走出来所需要的努力。
由于作家作为一位女性在生活中经历了大量的挫折,所以她对女性生活的困苦有相当深入的体会,以至于她在描写女性时总是能够驾轻就熟。
她的小说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著名国际大都市为地域背景,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形形色色、丰富多彩;他们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现出了自己的生活面貌。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类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在她们内心形成巨大的冲突,她们一方面渴望摆脱封建伦理道德所带来的束缚,另外一方面她们又害怕自己沦落到无依无靠,旧的思想道德以及经济上的附庸使得她们所有的行为都围绕在生存这一基本点上。
她们为人妇或为人母,一生都在追求所谓的家庭幸福,但是她们所采用的方法带来的结果却常常与想法大相径庭。
往往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依旧是痛苦。
(一)为人妇张爱玲小说中依附在男性身影下的女性大体上可分成两类。
其一,为了生活,游走于不同的男人之间,成为别人的情人;其二,做成了别人的妻子,成为一家的女主人。
这两种女性都想在经济上找到自己的依靠,有一个落脚的空间,但由于自身经济上的不独立,所以只能成为被选择的对象,而没有掌握到婚姻的主动权。
具体表现为:1.沦为别人的情人这一类女性,由于自身的境遇,导致了她们自甘堕落,再加上社会的无情摧残,使得她们不得不放下自身的尊严,自觉地沦落到了这个群体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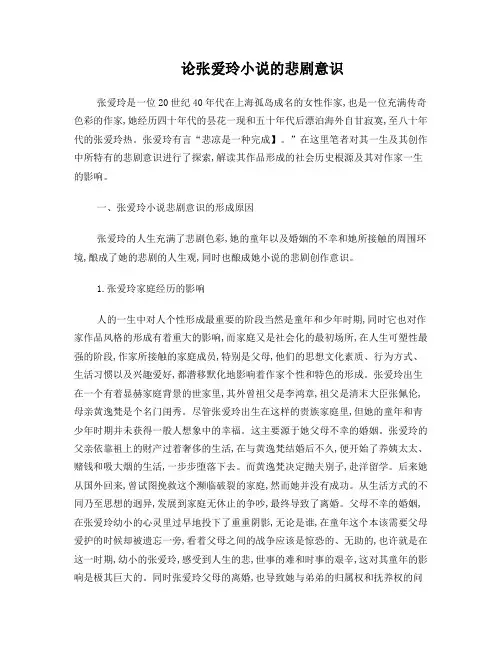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一位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的女性作家,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经历四十年代的昙花一现和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至八十年代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有言“悲凉是一种完成】。
”在这里笔者对其一生及其创作中所特有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探索,解读其作品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对作家一生的影响。
一、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张爱玲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她的童年以及婚姻的不幸和她所接触的周围环境,酿成了她的悲剧的人生观,同时也酿成她小说的悲剧创作意识。
1.张爱玲家庭经历的影响人的一生中对人个性形成最重要的阶段当然是童年和少年时期,同时它也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家庭又是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在人生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作家所接触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个性和特色的形成。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有着显赫家庭背景的世家里,其外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清末大臣张佩伦,母亲黄逸梵是个名门闺秀。
尽管张爱玲出生在这样的贵族家庭里,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未获得一般人想象中的幸福。
这主要源于她父母不幸的婚姻。
张爱玲的父亲依靠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的生活,在与黄逸梵结婚后不久,便开始了养姨太太、赌钱和吸大烟的生活,一步步堕落下去。
而黄逸梵决定抛夫别子,赴洋留学。
后来她从国外回来,曾试图挽救这个濒临破裂的家庭,然而她并没有成功。
从生活方式的不同乃至思想的迥异,发展到家庭无休止的争吵,最终导致了离婚。
父母不幸的婚姻,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里过早地投下了重重阴影,无论是谁,在童年这个本该需要父母爱护的时候却被遗忘一旁,看着父母之间的战争应该是惊恐的、无助的,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幼小的张爱玲,感受到人生的悲,世事的难和时事的艰辛,这对其童年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同时张爱玲父母的离婚,也导致她与弟弟的归属权和抚养权的问题,结果是她俩被判为父亲监护和抚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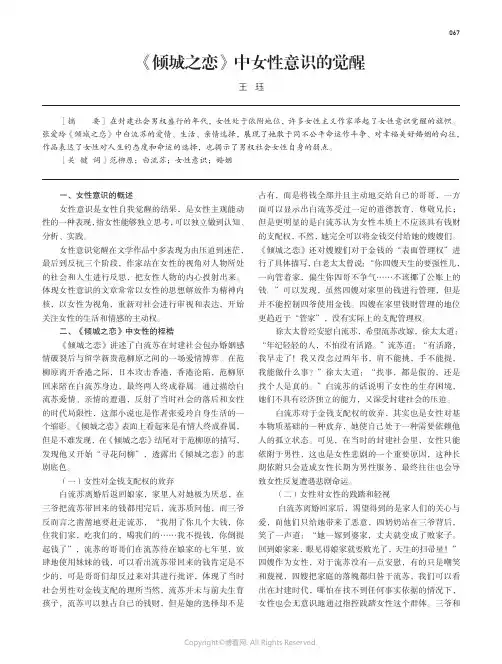
067一、女性意识的概述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结果,是女性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指女性能够独立思考,可以独立做到认知、分析、实践。
女性意识觉醒在文学作品中多表现为由压迫到迷茫,最后到反抗三个阶段,作家站在女性的视角对人物所处的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把女性人物的内心投射出来。
体现女性意识的文章常常以女性的思想解放作为精神内核,以女性为视角,重新对社会进行审视和表达,开始关注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的主动权。
二、《倾城之恋》中女性的桎梏《倾城之恋》讲述了白流苏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感情破裂后与留学新贵范柳原之间的一场爱情博弈。
在范柳原离开香港之际,日本攻击香港,香港沦陷,范柳原回来陪在白流苏身边,最终两人终成眷属。
通过描绘白流苏爱情、亲情的遭遇,反射了当时社会的落后和女性的时代局限性,这部小说也是作者张爱玲自身生活的一个缩影。
《倾城之恋》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不难发现,在《倾城之恋》结尾对于范柳原的描写,发现他又开始“寻花问柳”,透露出《倾城之恋》的悲剧底色。
(一)女性对金钱支配权的放弃白流苏离婚后返回娘家,家里人对她极为厌恶,在三爷把流苏带回来的钱都用完后,流苏质问他,而三爷反而言之凿凿地要赶走流苏,“我用了你几个大钱,你住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我不提钱,你倒提起钱了”,流苏的哥哥们在流苏待在娘家的七年里,放肆地使用妹妹的钱,可以看出流苏带回来的钱肯定是不少的,可是哥哥们却反过来对其进行批评,体现了当时社会男性对金钱支配的理所当然,流苏并未与前夫生育孩子,流苏可以独占自己的钱财,但是她的选择却不是占有,而是将钱全部并且主动地交给自己的哥哥,一方面可以显示出白流苏受过一定的道德教育,尊敬兄长;但是更明显的是白流苏认为女性本质上不应该具有钱财的支配权,不然,她完全可以将金钱交付给她的嫂嫂们。
《倾城之恋》还对嫂嫂们对于金钱的“表面管理权”进行了具体描写,白老太太曾说:“你四嫂天生的要强性儿,一向管着家,偏生你四哥不争气……不该挪了公账上的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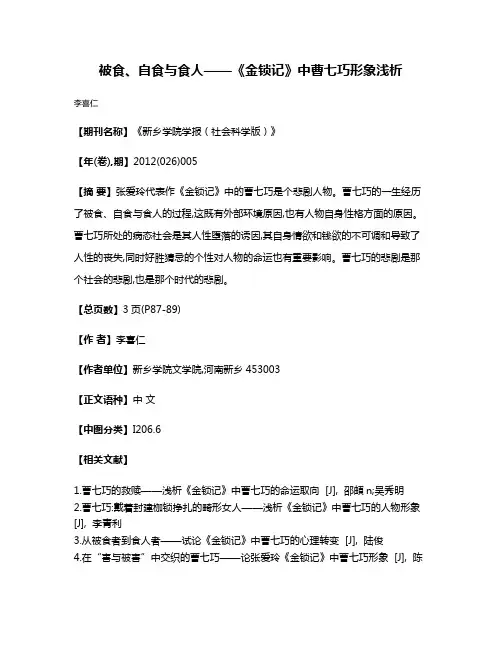
被食、自食与食人——《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浅析
李喜仁
【期刊名称】《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26)005
【摘要】张爱玲代表作《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个悲剧人物。
曹七巧的一生经历了被食、自食与食人的过程,这既有外部环境原因,也有人物自身性格方面的原因。
曹七巧所处的病态社会是其人性堕落的诱因,其自身情欲和钱欲的不可调和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同时好胜猜忌的个性对人物的命运也有重要影响。
曹七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总页数】3页(P87-89)
【作者】李喜仁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曹七巧的救赎——浅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命运取向 [J], 邵頔n;吴秀明
2.曹七巧:戴着封建枷锁挣扎的畸形女人——浅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J], 李青利
3.从被食者到食人者——试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心理转变 [J], 陆俊
4.在“害与被害”中交织的曹七巧——论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 [J], 陈
婷
5.被食、自食与食人——曹七巧形象浅析 [J], 韩蕊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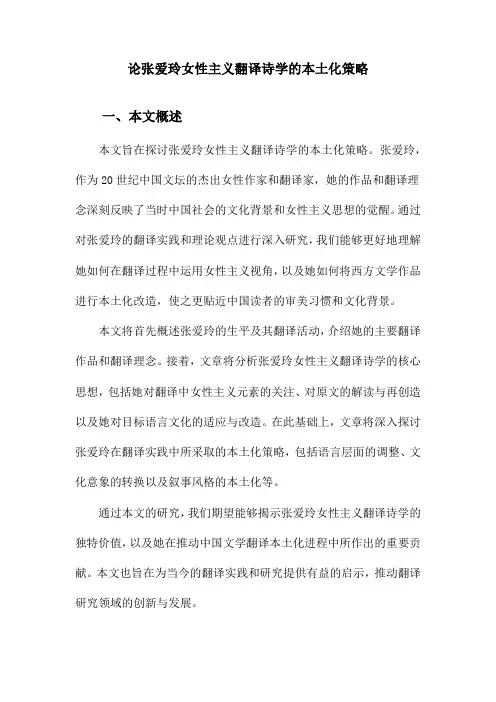
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
张爱玲,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的杰出女性作家和翻译家,她的作品和翻译理念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和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
通过对张爱玲的翻译实践和理论观点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她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运用女性主义视角,以及她如何将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更贴近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文化背景。
本文将首先概述张爱玲的生平及其翻译活动,介绍她的主要翻译作品和翻译理念。
接着,文章将分析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核心思想,包括她对翻译中女性主义元素的关注、对原文的解读与再创造以及她对目标语言文化的适应与改造。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深入探讨张爱玲在翻译实践中所采取的本土化策略,包括语言层面的调整、文化意象的转换以及叙事风格的本土化等。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揭示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独特价值,以及她在推动中国文学翻译本土化进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本文也旨在为当今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推动翻译研究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二、张爱玲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的理论基础张爱玲,原名张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和翻译家。
她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女性主义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她在翻译领域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她的翻译作品不仅准确传达了原作的精神,更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和本土化策略,形成了她独特的女性主义翻译诗学。
张爱玲的女性主义翻译诗学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她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实践,二是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热爱。
她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而女性主义翻译则应当站在女性视角,以女性的经验和情感去理解和传达原作。
在张爱玲看来,女性主义翻译诗学不仅要关注原作的语言表达,更要关注原作中的女性意识和文化内涵。
她主张在翻译过程中要尊重原作的女性主义精神,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进行适度的本土化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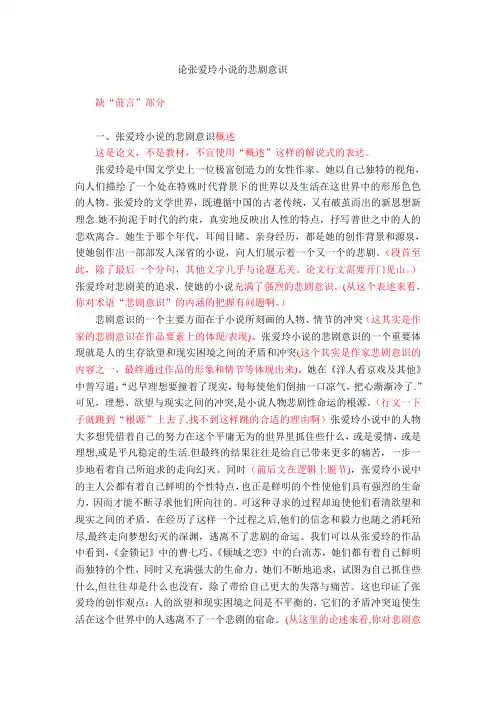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缺“前言”部分一、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概述这是论文,不是教材,不宜使用“概述”这样的解说式的表达。
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女性作家。
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处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世界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既遵循中国的古老传统,又有破茧而出的新思想新理念.她不拘泥于时代的约束,真实地反映出人性的特点,抒写普世之中的人的悲欢离合。
她生于那个年代,耳闻目睹、亲身经历,都是她的创作背景和源泉,使她创作出一部部发人深省的小说,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段首至此,除了最后一个分句,其他文字几乎与论题无关。
论文行文需要开门见山。
)张爱玲对悲剧美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意识。
(从这个表述来看,你对术语“悲剧意识”的内涵的把握有问题啊。
)悲剧意识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小说所刻画的人物、情节的冲突(这其实是作家的悲剧意识在作品要素上的体现/表现)。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的生存欲望和现实困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其实是作家悲剧意识的内容之一,最终通过作品的形象和情节等体现出来)。
她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曾写道:“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可见,理想、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是小说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根源。
(行文一下子就跳到“根源”上去了,找不到这样跳的合适的理由啊)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想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平庸无为的世界里抓住些什么,或是爱情,或是理想,或是平凡稳定的生活.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所追求的走向幻灭。
同时(前后文在逻辑上脱节),张爱玲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也正是鲜明的个性使他们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因而才能不断寻求他们所向往的。
可这种寻求的过程却迫使他们看清欲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他们的信念和毅力也随之消耗殆尽,最终走向梦想幻灭的深渊,逃离不了悲剧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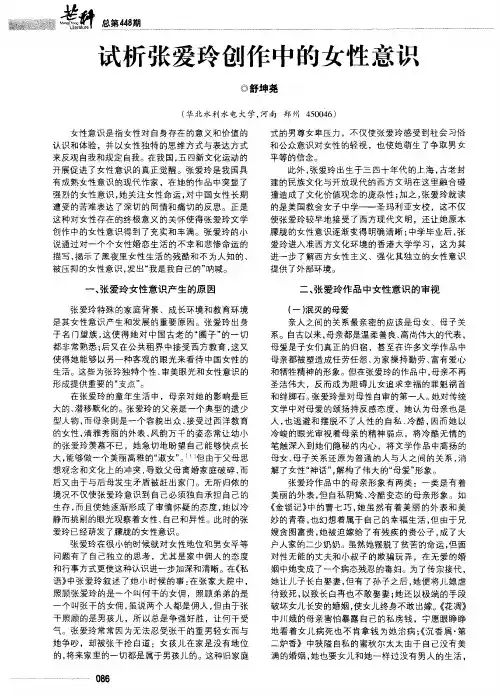
本科毕业论文论文题目: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指导老师:徐珊学生姓名:林少名学号:W44941012220004院系:网络教育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写作批次:2011秋批次我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若本论文及资料与以上承诺内容不符,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毕业论文作者签名:__林_少_名_________日期:2011年12月16日目录摘要 (I)Abstract (Ⅱ)-、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 (1)(一)《金锁记》的曹七巧 (1)(二)《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葛薇龙 (1)(三)《倾城之恋》的白流苏 (1)二、张玲小说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类型 (2)(一) 交际花类型 (2)(二) 畸型女类型 (2)(三) 懦弱女类型 (3)三、小说中女性悲剧产生的原因 (4)(一) 特殊的时代 (4)(二) 个人的性格原因 (4)(三)女性的社会地位 (5)参考文献 (7)致谢词 (8)摘要张爱玲是现代女性作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一个传奇,深深吸引着人们去品读她的作品,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感叹其悲剧意味.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尤其突出。
本文就从她的几部经典作品去分析女性在其小说中的重要性,主要类型和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键词:女性主角女性类型悲剧原因AbstractZhang ailing’s is the modern women writers of a unique scenery line, is a legend, deeply attracted people to read her work,reap happy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gedy means sigh。
In her novel,the female image especially prominent. This paper from her several classic works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women in his novels,the main types and cause the cause of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Key words:Female protagonist Women type Tragedy reason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张爱玲是现代女性作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一个传奇,深深吸引着人们去品读她的作品,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感叹其悲剧意味。
在女性主义之外 ———张爱玲女性意识新探 辛倩儿 ( 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 要: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并不具有颠覆父权体制的女性主义内涵。她摒弃一切外在理论的影响, 以纯女性的感性体验和智慧来直面人生本质, 从而书写出一向被遮蔽或否定的女性意识: 男性崇拜和依附心理; 爱慕虚荣和同性倾轧; “真”!“好”世界的对立。对此, 张爱玲秉持理解和认同的叙事态度, 其作品呈现出批判话语的空缺。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4225(2008)02- 0021- 04 收稿日期: 2007- 07- 02 作者简介: 辛倩儿(1980- ) , 女, 广东汕头人, 汕头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女性意识虽然缺乏简单明确的定义, 在不同的著作中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或底蕴,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女性意识是女性对自己生命本体的特殊性和本质性的体验、发现和认识, 它必须与女性主体化、私人化的生命体验相联系, 忠实于女性自身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灵与肉的 感受, 并以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表达, 而不是在接受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基 础上, 以某种规范化了的、固定的女性理论模式来反观自我和规定自我, 并以此去批判他人或社会。从这一点来看,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与整个五四女作家群有很大区别。随着女性生存空间的日益拓展, “女性的觉醒”成为“人的觉醒”这一“五四”新文化思想核心的具体化。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普遍产生先觉者意识, 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进行叙述。从正面建构来说, 冰心、苏雪林、凌叔华、林徽因、冯沅君都是爱的哲学的忠诚信奉者, 渴望以爱心温暖人间, 实现“两性和谐”。而庐隐对男权社会使妇女丧失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的批判, 丁玲“莎菲式”性苦闷的书写和女性的自强意识, 萧红关于妇女悲惨命运的愤怒言说与不断反抗的努力„„又无不从反面解构了男权视点中的女性神话。但是从文本的内在精神来看, 他们秉承的仍然是男性的启蒙主义立场, 运用的仍然是男性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只有张爱玲摒弃一切 外在理论的影响, 以纯女性的感性体验和智慧来直面人生本质, 从而书写出历来不为人所知,被压抑进女性潜意识深处的女性意识。 一、男性崇拜和依附心理 从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者便一直追求男女双方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平等和思想独立。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 不平等的两性等级制度是被父母、教育 者、书籍和文化构造出来的, 女性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崇拜、顺从、被动的宗教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快乐完全是一种非真实的渴望。[1]324-344但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 指出“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 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宁愿放弃独立的权利, 因为“用丈夫的钱, 如果爱他的话, 那却是一种快乐, 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 穿他的衣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 第 2 期 SHANTOU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IMONTHLY) Vol.24.No.2 2008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2008 年)那是女人的传统和权利。”(《苏青张爱玲对谈录》) 与张爱玲一样, 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对男性的爱或态度中积淀的也是由男性崇拜而来的种种依附心理, 主动消解或放弃的是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爱、自强。《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的人生依附,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对乔琪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依附, 《小艾》中席五太太、《花凋》中郑太太、《鸿鸾禧》中娄太太对丈夫毫无退路的经济依附、《心经》中小寒对父亲峰仪根深蒂固几至疯狂的情感依附„„都展示出女性强烈的依附意识。张爱玲的小说真切地揭示出: 在这样一种看似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 女性感受到的不是痛苦, 而是陶醉、满足和自我欣赏。“男性崇拜”容易导致“男尊女卑”的思维/心理定势, 被女权主义者视为奴性意识而加以唾弃。然而面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下贱难堪的地位, 张爱玲虽然有不绝如缕的悲剧性感受, 但却没有对现实失望的巨大愤怒, 也没有重构两性秩序的理想热忱, 相反, 她实事求是地指出: “实 际上女人总是低的, 气愤也无用, 人生不是赌气的事。”她甚至赞美日本女人“低卑的美”, 认为其“温厚光致, 有绢画的画意, 低是低的, 低得泰然”。(《罗兰观感》) 在送给胡兰成的照片上, 张爱玲题下谦卑的字句: “见了他, 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段文字让当时和后世的读者感到痛心和不解, 但张爱玲从不想矫饰和拔高自己,她只是书写自己真实的女性感受。《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甘心、固执而谦卑地爱着浪子乔琪, 张爱玲这样分析她强烈的爱: “最初, 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 但是后来, 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当然, 他爱她不过是方才一刹那。———可是她自处这么卑下, 她很容易就满足了。”说的是薇龙, 但更像是张爱玲自己。在张爱玲看来, “女人是喜欢被屈服的”(《倾城之恋》), 为了这种“喜欢”, 付出的岂止是尊严的丧失、肉体的疼痛、精神的困窘, 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色戒》中爱国女学生王佳芝试图以色诱人, 暗杀汉奸, 却反而为情所困,身死人手。当她因一念之差放走易主任随后又被他无情杀害时, 她恨虽恨, 却分明更爱他, “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 只是有感情”。因为“无毒不丈夫”, “不是这样的男子汉, 她也不会爱他”。这似乎是可悲的,然而却是女人无可奈何的宿命———“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 念的是男人, 怨的是男人, 永远永远(《有女同车》)。”女性的主体性力量是否能强大到打破男性中心主义这一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打破这一结构的同时, 女性是否要体验无从立足的虚无并使自我的确认成为一种悬置的渴望? 女性如何把自身揭示为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同时又实现女性的快乐和幸福? 一直以来被女性主义忽略和遮蔽的问题, 张爱玲却提了出来。她表达着她的质疑, 但这不是来源于任何女性主义理论, 而是出于个人敏锐的观察、思考和真切的女性生命体验。 二、爱慕虚荣和同性倾轧 当女性在男性世界中对自身位置产生种种失望和悲剧性感受之后, 往往便会退回到女性群体内部去寻找生命存在的慰藉, 某种真诚平等互相理解的友情。这也就是女性主义者所呼吁的团结一致的“姐妹情谊”。然而, 张爱玲以冷峻的笔调, 写出女性建立在个体虚荣心之上的 彼此之间互相竞争、倾轧的心理, 从而对“姐妹情谊”的乌托邦性质予以揭露。对于女性来说, 肯定和实现自我不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超越性的行动; 相反, 是通过不断地沉溺在内在性的满足中。讲究装扮、调情、耍小计谋、排挤同性„„无疑都是走向人生成功的方法, 都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男性的爱, 被更多的女性羡慕和嫉妒。从理论上来说, 这是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虚幻的胜利, 然而在现实中, , 却是潜藏在每一个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心底深处的真实愿望。女性爱慕虚荣的心理在张爱玲笔下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看着姑妈替她买的一壁橱金碧辉煌的衣服, 虽然想到“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 有什么分别”, 但是对未来“改良为娼”的不祥预感并不能克制住她的虚荣心理, 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 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 并不住安慰自己: “看看也好! ”后来她果然穿着这22辛倩儿 在女性主义之外 第 2 期些衣服在交际场上大出风头, 一步步堕落为“不 是替乔琪弄钱, 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的高级娼妓, 成为“死世界”中的新鬼。葛薇龙为何对华衣锦饰的引诱如此无法抗拒? 因为对女性来说, 衣服并不仅仅是衣服而已, 它还意味着人生的美好前景: 增加自身的性吸引力, 得到异性的恭维和 赞 美 , 进一步 满足 女 性 永 不 满 足 的 虚 荣心———得到异性的爱„„当然, 女性虚荣心的最高满足形式恐怕还在于能够击败其他同性, 像白流苏, “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 出尽她胸中这一口恶气”。当流苏因抢走妹妹宝络的结婚对象范柳原而遭众人咒骂时, 她不但不生气, 反而“微笑着”。因为“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 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 肃然起敬。一个女人, 再好些, 得不着异性的爱, 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倾城之恋》)。”张爱玲认为“同行相妒”,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我看苏青》), 并且在散文《双声》中指出: 女性还有一种奇异的虚荣心理, 即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 谁都喜欢他, 不然自己也不嫁给他。于是女人会一方面贬损丈夫的其他女人, 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自己的情敌太差, 结果便是 “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 让自己也喜欢她。“当然, 喜欢了之后, 只有更敌视。”《花凋》中美丽的川嫦因病重而被男友抛弃, 当她见到他新的女朋友并发现其容貌平常时, 除了放心和嗔怪情人没有眼光之外, “最强的感觉是愤懑不平, 因为她爱他, 她认为惟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方才配得上他”。她不怨恨章云藩的无情无义, 却对余美增的“不够资格”和 “还不知足”感到“又惊又气”, 因为“她心里的云藩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接下来她只能努力去发现情敌的“好处”, 自惭形秽之余更恨她。在张爱玲小说的阅读体验中,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女性之间终日勾心斗角!互相诋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场景: 曼璐会因妒生恨, 变态到残害自己的亲生妹妹; 七巧会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 在女儿未婚夫面前丑化她的形象, 将女儿从“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变为抽鸦片的烟鬼, 会两度不见血地逼死儿媳。然而这种寒冷彻骨的自相残杀其实只不过是女性之间最一般化的敌对情感发展到极致的现象而已。在女性主义者看来, 女性是一个可以团结起来的群体, 她们之间是天然有着爱和温情的,所谓仇恨是后天的, 是男性造成的, 然而在张爱玲笔下我们却看到了女性之间全部历史的绝望处境: 孤独的、纯粹性的存在、无法实现的爱和无法逃避的恨、分离的必然性和注定互相伤害的命运„„。这就是真实: 女性之间并没有什么惺惺相惜的同性情谊, 她们不过是分裂的、彼此对抗的个体, 而这一切并非由于男性的压迫和异化, 而是因为她们的本质。 三、“真”/“好”世界的对立冲突 在和他人的关系中, 女性似乎命定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即使回到女性本体的心理世界, 女性存在的真相也仍然扑朔迷离。有研究者指出,张爱玲小说《封锁》写的是“真”"“好”两个世界的对立。[2]那么, 对于女性来说, “真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像娄太太(《鸿鸾禧》)、芝寿(《金锁记》)、金少奶奶(《创世纪》)、郑夫人(《花凋》)、孟烟鹏(《红玫瑰与白玫瑰》) 等“女结婚员”, 满足于传统宗法父权制所规范的从属身份和价值标准, 终日在贤良、温顺、清白的自我肯定中焦虑、恐惧、缄默、无助; 还是像敢于追求婚恋自由的新式女子密斯范(《五四遗事》)、王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 蔑视传统封建道德, 拥有较为独立的思想、人格, 敢于反抗压迫, 力图改写导致自我与主体性丧失的他者位置„„我们都只能说是“好的”世界, 而不是“真的”世界。女性“真的”世界应该是源于自我生命的纯粹感性体验, 是非理性和反逻辑的, 是独立于外在种种文化、思想、道德之外的。“真的”世界的建构过程, 是女性生命力被不断唤醒、触发、创造的过程。对“真的”世界自觉或非自觉的渴望虽然贯穿着张爱玲作品中每一位女性的心理, 但 “真的”世界是难以进入的。《花凋》中川嫦希望为自 己做体格检查的云藩以男性的态度来看待作为女性的她, 但云藩却以典型的医生态度来看待作为病人的她, 他以“微凉的科学的手指”代替了川嫦“从前一直憧憬的接触”, 使她因失望而痛苦, 不但没有得到安慰, 反而病情日渐加重。23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 2008 年)“真的”世界即使偶尔存在, 也往往只是昙花一现, 瞬即消失。《封锁》中的吴翠远, 是模范家庭的好女儿和好学生, 年轻的大学英文教师。但她并没有因为得到女性世世代代渴望得到的高等教育和崇高社会地位而自豪快乐。相反, 讲究温文尔雅的良好家庭教育使她备受压抑, 终日从事脑力劳动使她感到空虚、厌倦、远离真实生命的不安„„于是在电车上批改卷子时, 她竟莫名其妙地将“A”批给了一位写得既不合文法又充满猥亵话语的男学生。当她质问自己时,不由得“竟涨红了脸”, 此时吴翠远开始一步步背叛日常的 “好的”世界而体验被层层隔绝的“真的”自己。当素不相识的会计师吕宗桢突然调戏她时, 吴翠远“觉得炽热、快乐”, 她不要他的钱、他的聪明、他的诚实, 而只要他生命中“谁也不稀罕的一部分”———“一个真的人”。正因这个“单纯的男子”对吴翠远的家庭好、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