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理想人格
- 格式:doc
- 大小:29.5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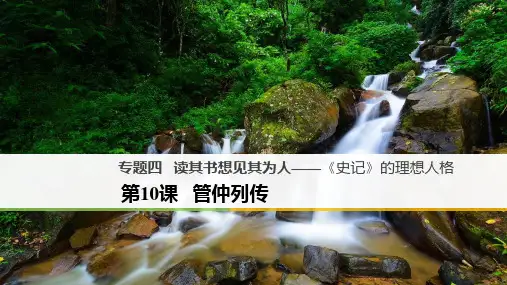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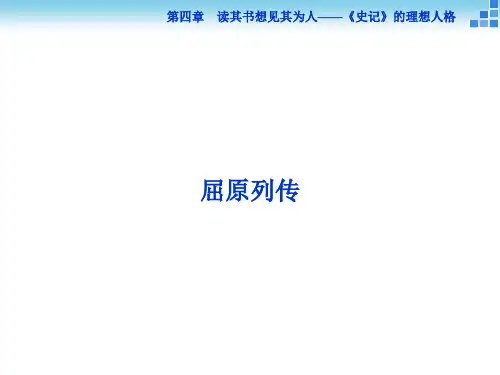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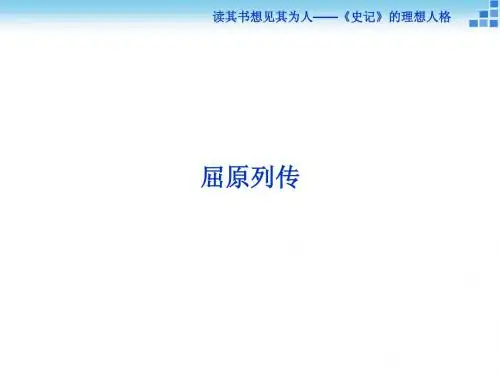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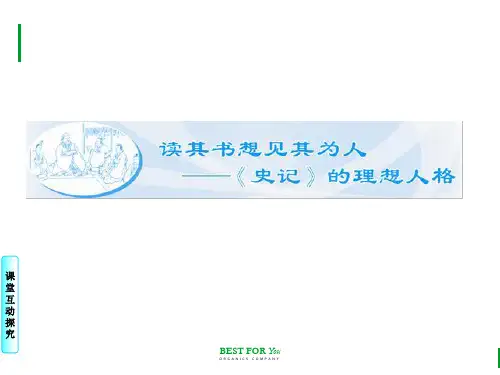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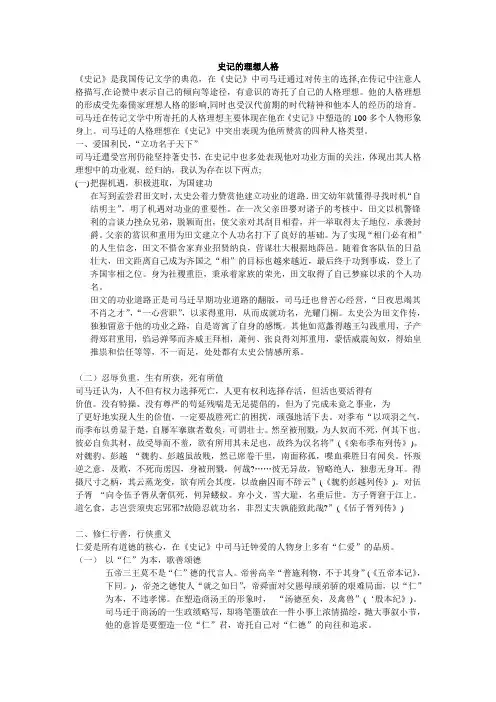
史记的理想人格《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传主的选择,在传记中注意人格描写,在论赞中表示自己的倾向等途径,有意识的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
他的人格理想的形成受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影响,同时也受汉代前期的时代精神和他本人的经历的培育。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中所寄托的人格理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史记》中塑造的100多个人物形象身上。
司马迁的人格理想在《史记》中突出表现为他所赞赏的四种人格类型。
一、爱国利民,“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遭受宫刑仍能坚持著史书,在史记中也多处表现他对功业方面的关注,体现出其人格理想中的功业观,经归纳,我认为存在以下两点;(一)把握机遇,积极进取,为国建功在写到孟尝君田文时,太史公着力赞赏他建立功业的道路.田文幼年就懂得寻找时机“自结明主”。
明了机遇对功业的重要性。
在一次父亲田婴对诸子的考核中,田文以机警锋利的言谈力挫众兄弟,脱颖而出,使父亲对其刮目相看,并一举取得太子地位,承袭封爵。
父亲的赏识和重用为田文建立个人功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现“相门必有相”的人生信念,田文不惜舍家弃业招贤纳良,营谋壮大根据地薛邑。
随着食客队伍的日益壮大,田文距离自己成为齐国之“相”的目标也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功到事成,登上了齐国宰相之位。
身为社稷重臣,秉承着家族的荣光,田文取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个人功名。
田文的功业道路正是司马迁早期功业道路的翻版,司马迁也曾苦心经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一心营职”,以求得重用,从而成就功名,光耀门楣。
太史公为田文作传,独独留意于他的功业之路,自是寄寓了自身的感慨。
其他如范蠡得越王勾践重用,子产得郑君重用,驺忌弹琴而齐威王拜相,萧何、张良得刘邦重用,蒙恬威震匈奴,得始皇推祟和信任等等,不一而足,处处都有太史公情感所系。
(二)忍辱负重,生有所获,死有所值司马迁认为,人不但有权力选择死亡,人更有权利选择存活,但活也要活得有价值。
没有特操、没有尊严的苟延残喘是无足提倡的,但为了完成未竟之事业,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一定要战胜死亡的困扰,顽强地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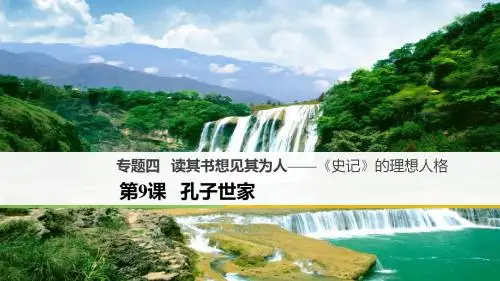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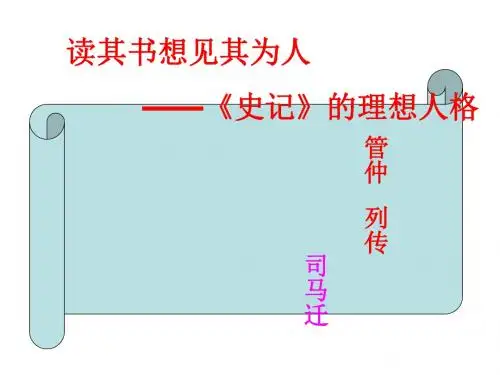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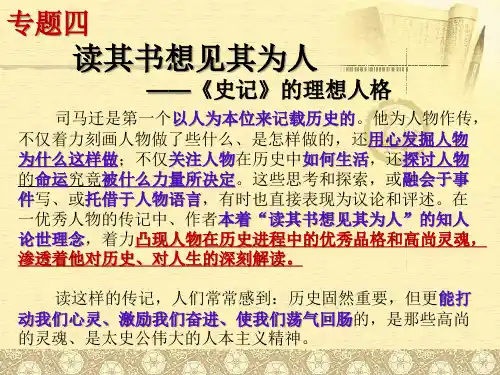

由《管仲列传》窥《史记》的理想人格作者:王炜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7年第12期《〈史记〉选读》苏教版教材使用的选修教材之一,如何在教学引领学生综合思考、深刻领悟文学巨著《史记》呢?《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司马迁也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因此我一直引导学生要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读书。
下面我就以《管仲列传》为例,谈谈如何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不仅了解到管仲的为人和为政,更能管中窥豹,理解司马迁对人生和历史的深刻思考,领悟《史记》的理想人格。
《管仲列传》选自《史记·管晏列传》,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对选修课本提出的相关要求,我在第一课时与学生一起疏通文本,准确地翻译重点语句和语段。
在第二课时的教学设置上,我首先抛出一个问题:“谈谈你眼中的管仲”。
同学们通过研读文本,积极思考,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学生说他对管仲的第一印象就是自私、贪婪和小仁小义。
但也有学生觉得管仲孝顺、懂得感恩、重友情、富贵而不忘本。
对于管仲的为人,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管仲该不该像召忽那样,为公子纠殉节。
一种认为,他选择活下来,并且效忠于齐桓公,失了气节,一种认为他很识时务,转变政治立场,才有了后期的作为。
看到学生讨论热烈、各执一词,我适时展示孔子的学生子贡和子路与孔子的两段对话。
1.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2.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看来,子贡和子路也因为管仲没有选择殉节,而认为他并不符合儒家所说的“仁”的标准,但是他们的老师孔子给出的回答却截然相反。
有了这两段对话的提示,同学们都若有所思。
郭澄同学站起来说:“我认为,鲍叔牙了解管仲的所谓‘自私贪婪’‘小仁小义’的行为都只是现实所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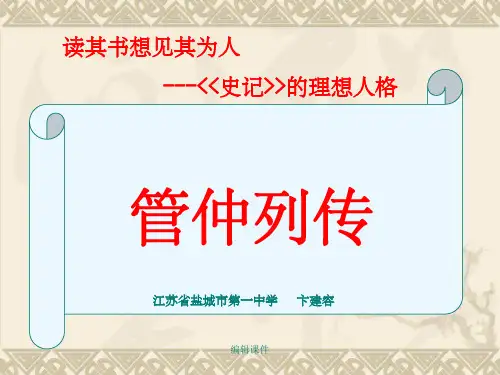
从《屈原列传》看《史记》中的理想人格作者:刘云飞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21年第10期司马迁曾与人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可见其著《史记》有大雄心、大理想。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富裕而豪迈的时代,此时,国家“蓄积岁增,户口寝息”,而《史记》也是从这繁华盛世中诞生。
但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却实非容易。
武帝登位,大力推行制度改革,对人才极度重视,为此“群士慕响,异人并出”,这是一个群雄争辉的时代,因而司马迁内心渴慕英雄,向往兴功造业,但不想遭李陵之祸,受宫刑凌辱。
他一度想过自裁,却不舍心中丘壑,所以《史记》又是司马迁的人格寄托与精神向往。
司马迁对屈原的感情是深厚的,屈原是司马迁心中最理想的英雄之一,也是自身的意念化身。
一、司马迁写作的悲剧英雄人物情结失意时候压抑的欲望,是作家不断做“白日梦”的动力。
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那些很难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才会不断的发出诉求。
幻想的动力是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对一个愿望的满足,是对未满足的现实的补偿。
同样的这番理论放在司马迁身上,揭示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情结。
他深切感受到“李陵之祸”所带来的痛苦与及对他撰写《史记》带来的影响。
他的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这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这些人生经历造就了司马迁最初的悲剧情结,这种悲剧情结伴随着司马迁的写作而深深地隐藏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
悲剧情结来自司马迁的失意经历,当这些失意经验在“李陵之祸”中再一次扩大,就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其实,这种冲突在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会成为各种负面情绪。
当冲突爆发时,脆弱的情感无法与冲突抗争,心理就会处于失衡状态。
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情结起到了一定的防御机制作用。
植根于司马迁的悲剧情结,作为司马迁的心理能量和动力,激发了司马迁的灵感和创造力。
《<史记>选读》——试论《史记》中理想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司马迁对人格价值的看法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在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个以儒家为尊的年代。
难保他的人生价值观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太史公自序》)以人世为主的儒学既重视个人的适当发展来谋取社会幸福,同时亦重视社会责任以至个人人格的完善。
个人不可侵犯之尊严与价值是儒家人格的核心信念。
它用冷静、现实、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与传统,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人生的平衡。
这种实践理性的特征,首肯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
就拿屈原为例吧。
屈原生活在社会变化剧烈的战国后半期。
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周传统政教的失范,使“士”这一阶层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分庭抗礼;虽然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他们拥有着和儒家一样对责任的担当和对真理的追求,这种人格观念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屈原的心志与理念。
他是被现实的烈火焚烧得只剩下灵魂和人格的光芒的饱经忧患之士,他对人生、家国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开拓精神世界的情感动力,也正是司马迁所极力宣扬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屈原恐怕就是司马迁除了钦慕古典的孔子而外,和他的浪漫气质最相吻合的了。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屈原正直忠贞的人格被楚王及其群小所摧折而作《离骚》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
《史记·屈原列传》的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深挚而沉痛的同情,他为屈原垂涕,为屈原讴歌,他明白屈原孤身与“愚妄战”的坚韧不屈,明知自己力量的单薄,但为着正义与光明,依然是“终刚强兮不可陵”。
正是儒家历史责任感的体现。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引用了这么一段话来礼赞屈原的人格,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史记的理想人格
《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传主的选择,在传记中注意人格描写,在论赞中表示自己的倾向等途径,有意识的寄托了自己的人格理想。
他的人格理想的形成受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影响,同时也受汉代前期的时代精神和他本人的经历的培育。
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中所寄托的人格理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史记》中塑造的100多个人物形象身上。
司马迁的人格理想在《史记》中突出表现为他所赞赏的四种人格类型。
一、爱国利民,“立功名于天下”
司马迁遭受宫刑仍能坚持著史书,在史记中也多处表现他对功业方面的关注,体现出其人格理想中的功业观,经归纳,我认为存在以下两点;
(一)把握机遇,积极进取,为国建功
在写到孟尝君田文时,太史公着力赞赏他建立功业的道路.田文幼年就懂得寻找时机“自结明主”。
明了机遇对功业的重要性。
在一次父亲田婴对诸子的考核中,田文以机警锋利的言谈力挫众兄弟,脱颖而出,使父亲对其刮目相看,并一举取得太子地位,承袭封爵。
父亲的赏识和重用为田文建立个人功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现“相门必有相”
的人生信念,田文不惜舍家弃业招贤纳良,营谋壮大根据地薛邑。
随着食客队伍的日益壮大,田文距离自己成为齐国之“相”的目标也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功到事成,登上了齐国宰相之位。
身为社稷重臣,秉承着家族的荣光,田文取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个人功名。
田文的功业道路正是司马迁早期功业道路的翻版,司马迁也曾苦心经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一心营职”,以求得重用,从而成就功名,光耀门楣。
太史公为田文作传,独独留意于他的功业之路,自是寄寓了自身的感慨。
其他如范蠡得越王勾践重用,子产得郑君重用,驺忌弹琴而齐威王拜相,萧何、张良得刘邦重用,蒙恬威震匈奴,得始皇推祟和信任等等,不一而足,处处都有太史公情感所系。
(二)忍辱负重,生有所获,死有所值
司马迁认为,人不但有权力选择死亡,人更有权利选择存活,但活也要活得有
价值。
没有特操、没有尊严的苟延残喘是无足提倡的,但为了完成未竟之事业,为
了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一定要战胜死亡的困扰,顽强地活下去。
对季布“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自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
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
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栾布季布列传》)。
对魏豹、彭越“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干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
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
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魏豹彭越列传》)。
对伍子胥“向令伍予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
方子胥窘于江上。
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伍子胥列传》)
二、修仁行善,行侠重义
仁爱是所有道德的核心,在《史记》中司马迁钟爱的人物身上多有“仁爱”的品质。
(一)以“仁”为本,歌善颂德
五帝三王莫不是“仁”德的代言人。
帝喾高辛“普施利物,不于其身”(《五帝本记》,下同。
),帝尧之德使人“就之如日”,帝舜面对父愚母顽弟骄的艰难局面,以“仁”
为本,不违孝悌。
在塑造商汤王的形象时,“汤德至矣,及禽兽”(‘殷本纪》)。
司马迁于商汤的一生政绩略写,却将笔墨放在一件小事上浓情描绘,抛大事叙小节,他的意旨是要塑造一位“仁”君,寄托自己对“仁德”的向往和追求。
(二)赞赏侠义,重情守诺
司马迁赞赏在一般人际关系中、在交友中要有侠义精神,侠义型人格也是司马迁的一种人格理想。
《史记》中除《游侠列传》中的侠士具有侠义型人格,另外如《季布栾布传》中的栾布虽非游侠,但也有侠义精神。
这主要表现在哭祭彭越事件上。
司马迁在该传末称赞说: “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
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司马迁赞同为信义、道义而献身的精神,这既是受儒家忠孝节义思想的浸染,也是汉朝游侠风气日盛的结果。
为此他塑造了为报答先君知遇之恩,相信以诺,营救孤儿,弃生求死的陈婴和公孙杵臼。
杵臼为施救儿之计,能“请先死”,把生的希望让给朋友,把死的选择留给自己;陈婴为遵朋友生死之盟,毅然求死复命。
二人为了朋友之义,为了昔日的允诺,勇敢地、清醒而又理智地选择了死亡。
同时,司马迁个人重情守诺的人格以及这种人格在冷漠现实中的碰壁都促使他在《史记》中再造这种理想信念。
三、自尊自爱,自强不息
司马迁所肯定和赞赏的具有自尊型人格的人物具体又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为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而不惜自杀的自殉精神。
《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是个失败的英雄,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自刎乌江。
这是一种惭愧心理,是一种道德信念,也是一种不服输的糊涂观念,但更是英雄自尊心的表现。
《李将军列传》写了汉代抗匈名将李广,受卫青的排
挤。
他为了“终不能复对刀笔吏”而“引刀自到”。
同样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自尊。
另一种是具有为维护自己人格尊严而敢于抗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陈涉世家》记述了陈涉和吴广反秦起义的过程。
他们受暴秦的迫害,为了维护做一个人的起码的生存权,被迫走上反抗道路。
《史记》中有一类人物在生活的道路上严重受挫,人格上受到莫大的
侮辱,但他们没有自杀,而是发愤有为,表现了发奋进取的精神。
司马迁由于自己有过同样不幸的遭遇,因而尤为赞赏自强型人格。
这种自强型人格早在夏禹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夏本纪》中记述禹父亲稣治水不成功,被舜延于羽山。
禹承父业,“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全身心投人治水事业,终于取得成功。
继承夏禹自强人格的人,司马迁首推越王勾践。
《越王勾践世家》记述了勾践经过22年奋斗灭吴称霸的事迹,司马迁称勾践“有禹之遗烈”。
司马迁笔下的伍子青、虞卿、范唯、蔡泽、韩信、季布、栗布等人物,都曾在人格上遭受严重的侮辱,但他们都能忍辱奋斗,终成大事。
他们都是自强型人格的典型。
以上是对史记理想人格的分析,主要概括为三方面即自立,立功及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