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 格式:ppt
- 大小:2.69 MB
- 文档页数: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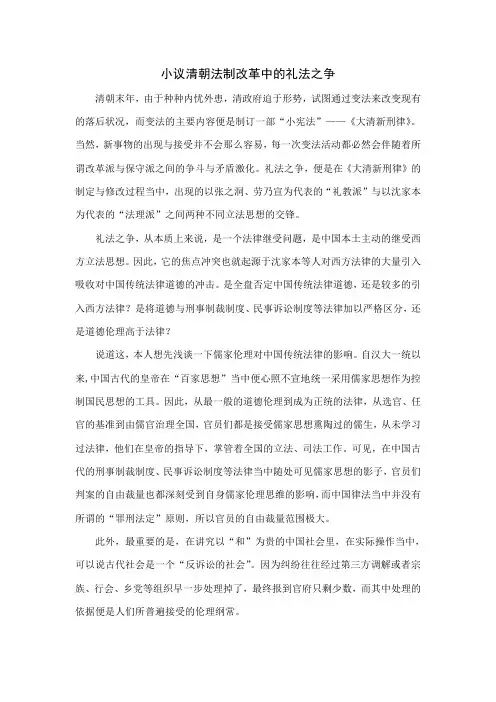
小议清朝法制改革中的礼法之争清朝末年,由于种种内忧外患,清政府迫于形势,试图通过变法来改变现有的落后状况,而变法的主要内容便是制订一部“小宪法”——《大清新刑律》。
当然,新事物的出现与接受并不会那么容易,每一次变法活动都必然会伴随着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与矛盾激化。
礼法之争,便是在《大清新刑律》的制定与修改过程当中,出现的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之间两种不同立法思想的交锋。
礼法之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法律继受问题,是中国本土主动的继受西方立法思想。
因此,它的焦点冲突也就起源于沈家本等人对西方法律的大量引入吸收对中国传统法律道德的冲击。
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法律道德,还是较多的引入西方法律?是将道德与刑事制裁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等法律加以严格区分,还是道德伦理高于法律?说道这,本人想先浅谈一下儒家伦理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自汉大一统以来,中国古代的皇帝在“百家思想”当中便心照不宣地统一采用儒家思想作为控制国民思想的工具。
因此,从最一般的道德伦理到成为正统的法律,从选官、任官的基准到由儒官治理全国,官员们都是接受儒家思想熏陶过的儒生,从未学习过法律,他们在皇帝的指导下,掌管着全国的立法、司法工作。
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刑事制裁制度、民事诉讼制度等法律当中随处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子,官员们判案的自由裁量也都深刻受到自身儒家伦理思维的影响,而中国律法当中并没有所谓的“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官员的自由裁量范围极大。
此外,最重要的是,在讲究以“和”为贵的中国社会里,在实际操作当中,可以说古代社会是一个“反诉讼的社会”。
因为纠纷往往经过第三方调解或者宗族、行会、乡党等组织早一步处理掉了,最终报到官府只剩少数,而其中处理的依据便是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伦理纲常。
第三,古代的中国人因为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聚居在一起,由此便形成家族、乡党、行会这些地方自治组织来处理内部纠纷,承担法律的运行。
家法、行规、地方风俗这三者活生生的法律,也就是所谓的“礼”,制约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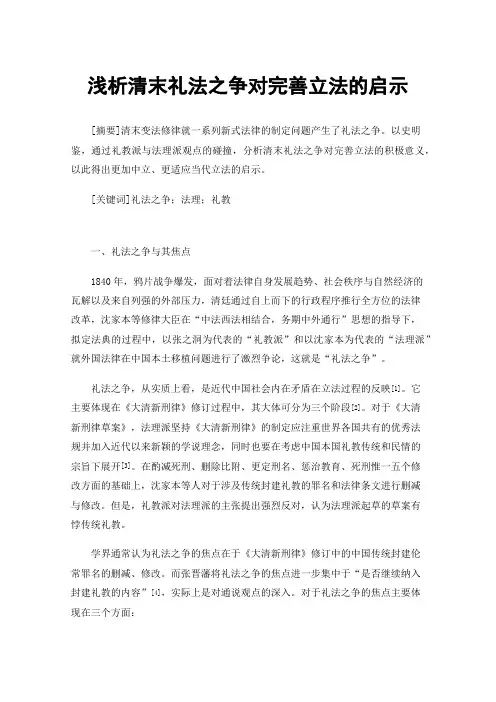
浅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启示[摘要]清末变法修律就一系列新式法律的制定问题产生了礼法之争。
以史明鉴,通过礼教派与法理派观点的碰撞,分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积极意义,以此得出更加中立、更适应当代立法的启示。
[关键词]礼法之争;法理;礼教一、礼法之争与其焦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着法律自身发展趋势、社会秩序与自然经济的瓦解以及来自列强的外部压力,清廷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全方位的法律改革,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在“中法西法相结合,务期中外通行”思想的指导下,拟定法典的过程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就外国法律在中国本土移植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这就是“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从实质上看,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反映[1]。
它主要体现在《大清新刑律》修订过程中,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
对于《大清新刑律草案》,法理派坚持《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应注重世界各国共有的优秀法规并加入近代以来新颖的学说理念,同时也要在考虑中国本国礼教传统和民情的宗旨下展开[3]。
在酌减死刑、删除比附、更定刑名、惩治教育、死刑惟一五个修改方面的基础上,沈家本等人对于涉及传统封建礼教的罪名和法律条文进行删减与修改。
但是,礼教派对法理派的主张提出强烈反对,认为法理派起草的草案有悖传统礼教。
学界通常认为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大清新刑律》修订中的中国传统封建伦常罪名的删减、修改。
而张晋藩将礼法之争的焦点进一步集中于“是否继续纳入封建礼教的内容”[4],实际上是对通说观点的深入。
对于礼法之争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修律指导思想:西方法律原则或传统礼教沈家本主张如果想要学习西方法律的宗旨,那么就必须要认真研究西方人的学说和书籍[5]。
沈家本等人通过研习西方先进的法律原理原则,对旧律进行改革,提出删除比附、罪刑法定。
他们认为比附存在以下弊端:在司法中,审判官根据自我的意志,当法律无明确规定时,比照类似的条文使得他人受到惩罚,这时司法者取代了立法者的作用;法律应具有可预测性,若保留比附,使得司法官可以根据自身的意见进行律外适用,就会导致人民无法预测其行为是否合法;比附使得司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更高的地位,由于每个司法官主观判断不同,易造成同罪异罚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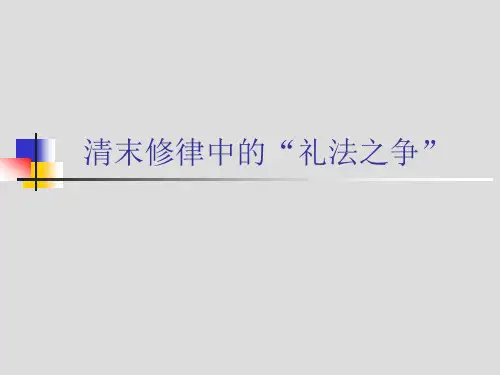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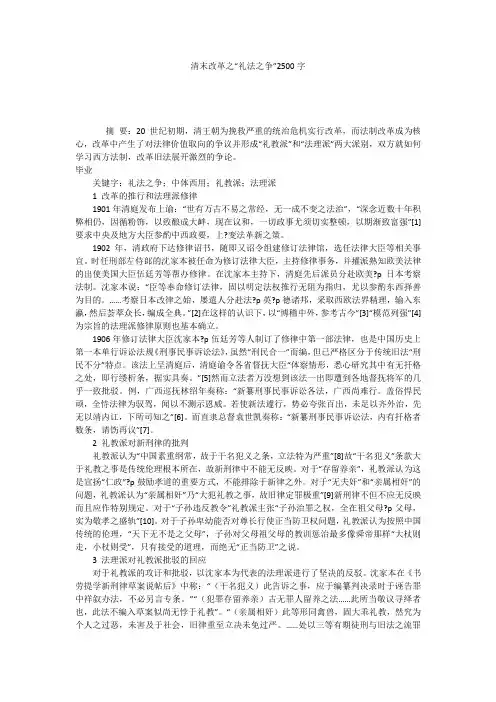
清末改革之“礼法之争”2500字摘要:20世纪初期,清王朝为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实行改革,而法制改革成为核心,改革中产生了对法律价值取向的争议并形成“礼教派”和“法理派”两大派别,双方就如何学习西方法制,改革旧法展开激烈的争论。
毕业关键字:礼法之争;中体西用;礼教派;法理派1 改革的推行和法理派修律1901年清庭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1]要求中央及地方大臣参酌中西政要,上?变法革新之策。
1902年,清政府下达修律诏书,随即又诏令组建修订法律馆,选任法律大臣等相关事宜。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事务,并擢派熟知欧美法律的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等帮办修律。
在沈家本主持下,清庭先后派员分赴欧美?p日本考察法制。
沈家本说:“臣等奉命修订法律,固以明定法权推行无阻为指归,尤以参酌东西择善为目的。
……考察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p英?p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
”[2]在这样的认识下,以“博稽中外,参考古今”[3]“模范列强”[4]为宗旨的法理派修律原则也基本确立。
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p伍廷芳等人制订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虽然“刑民合一”而编,但已严格区分于传统旧法“刑民不分”特点。
该法上呈清庭后,清庭谕令各省督抚大臣“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扦格之处,即行缕析条,据实具奏。
”[5]然而立法者万没想到该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抚将军的几乎一致批驳。
例,广西巡抚林绍年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广西尚难行。
盖俗悍民顽,全恃法律为驭驾,闻以不测示恩威。
若使新法遽行,势必夸张百出,未足以齐外治,先无以靖内讧,下所司知之”[6]。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法,内有扦格者数条,请饬再议”[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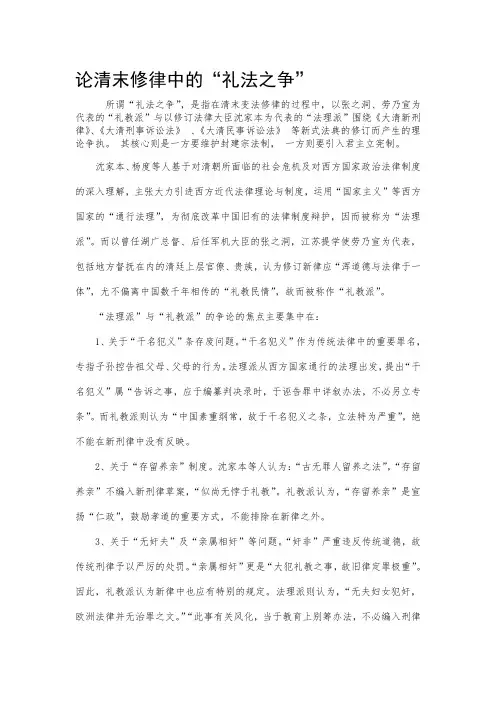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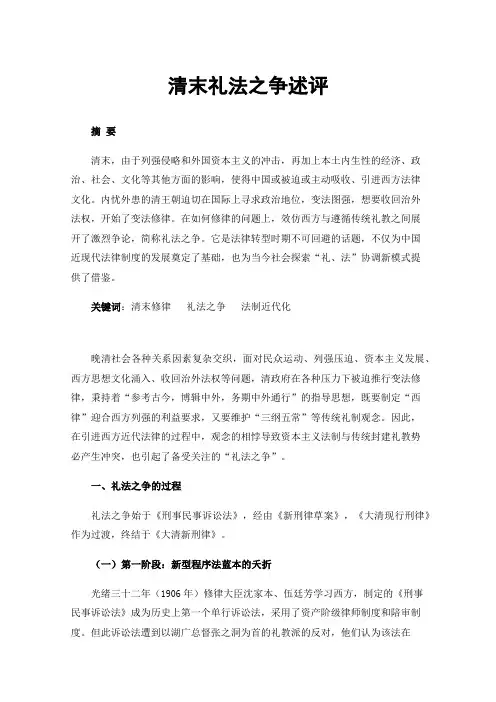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摘要清末,由于列强侵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再加上本土内生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使得中国或被迫或主动吸收、引进西方法律文化。
内忧外患的清王朝迫切在国际上寻求政治地位,变法图强,想要收回治外法权,开始了变法修律。
在如何修律的问题上,效仿西方与遵循传统礼教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简称礼法之争。
它是法律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社会探索“礼、法”协调新模式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争法制近代化晚清社会各种关系因素复杂交织,面对民众运动、列强压迫、资本主义发展、西方思想文化涌入、收回治外法权等问题,清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变法修律,秉持着“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务期中外通行”的指导思想,既要制定“西律”迎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要求,又要维护“三纲五常”等传统礼制观念。
因此,在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的过程中,观念的相悖导致资本主义法制与传统封建礼教势必产生冲突,也引起了备受关注的“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的过程礼法之争始于《刑事民事诉讼法》,经由《新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终结于《大清新刑律》。
(一)第一阶段:新型程序法蓝本的夭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学习西方,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单行诉讼法,采用了资产阶级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但此诉讼法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在“诉讼权利男女尊卑长幼应该平等,私有财产应该得到政府承认、法律保护”这两个问题上坏明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有违纲常伦纪,并认为仅以改良中国司法不可能使列强放弃领事裁判权。
《刑事民事诉讼法》在立法程序、收回治外法权、法律范畴等方面经不住推敲,效仿西方鼓励个体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企图一步到位,反而操之过急,成为礼教派攻击的致命缺陷,最终只能束之高阁。
(二)第二阶段:对《新刑律草案》的攻击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二月,沈家本奏进《刑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并附《刑事总则清单案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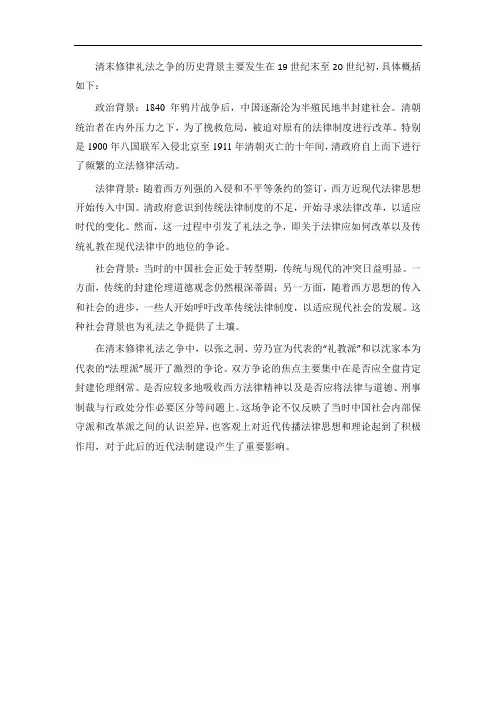
清末修律礼法之争的历史背景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具体概括如下:
政治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朝统治者在内外压力之下,为了挽救危局,被迫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
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十年间,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了频繁的立法修律活动。
法律背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清政府意识到传统法律制度的不足,开始寻求法律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然而,这一过程中引发了礼法之争,即关于法律应如何改革以及传统礼教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的争论。
社会背景: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日益明显。
一方面,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社会的进步,一些人开始呼吁改革传统法律制度,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这种社会背景也为礼法之争提供了土壤。
在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全盘肯定封建伦理纲常、是否应较多地吸收西方法律精神以及是否应将法律与道德、刑事制裁与行政处分作必要区分等问题上。
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认识差异,也客观上对近代传播法律思想和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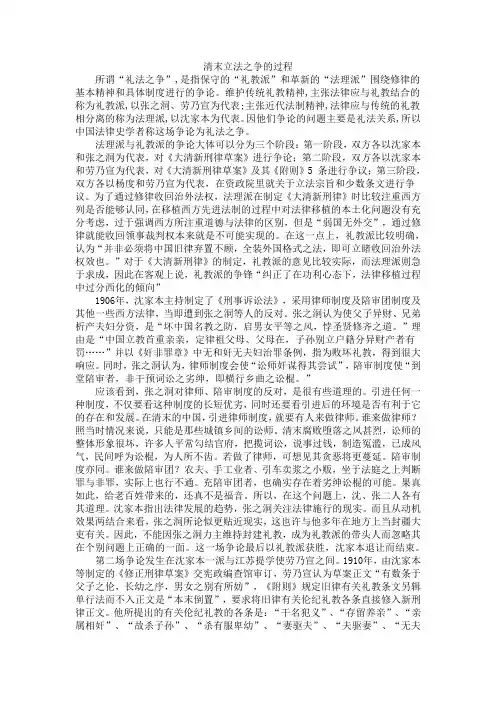
清末立法之争的过程所谓“礼法之争”,是指保守的“礼教派”和革新的“法理派”围绕修律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制度进行的争论。
维护传统礼教精神,主张法律应与礼教结合的称为礼教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主张近代法制精神,法律应与传统的礼教相分离的称为法理派,以沈家本为代表。
因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礼法关系,所以中国法律史学者称这场争论为礼法之争。
法理派与礼教派的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各以沈家本和张之洞为代表,对《大清新刑律草案》进行争论;第二阶段,双方各以沈家本和劳乃宣为代表,对《大清新刑律草案》及其《附则》5 条进行争议;第三阶段,双方各以杨度和劳乃宣为代表,在资政院里就关于立法宗旨和少数条文进行争议。
为了通过修律收回治外法权,法理派在制定《大清新刑律》时比较注重西方列是否能够认同,在移植西方先进法制的过程中对法律移植的本土化问题没有充分考虑,过于强调西方所注重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但是“弱国无外交”,通过修律就能收回领事裁判权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一点上,礼教派比较明确,认为“并非必须将中国旧律弃置不顾,全装外国格式之法,即可立睹收回治外法权效也。
”对于《大清新刑律》的制定,礼教派的意见比较实际,而法理派则急于求成,因此在客观上说,礼教派的争锋“纠正了在功利心态下,法律移植过程中过分西化的倾向”1906年,沈家本主持制定了《刑事诉讼法》,采用律师制度及陪审团制度及其他一些西方法律,当即遭到张之洞等人的反对。
张之洞认为使父子异财、兄弟析产夫妇分资,是“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道。
”理由是“中国立教首重亲亲,定律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有罚……”并以《奸非罪章》中无和奸无夫妇治罪条例,指为败坏礼教,得到很大响应。
同时,张之洞认为,律师制度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陪审制度使“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词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
”应该看到,张之洞对律师、陪审制度的反对,是很有些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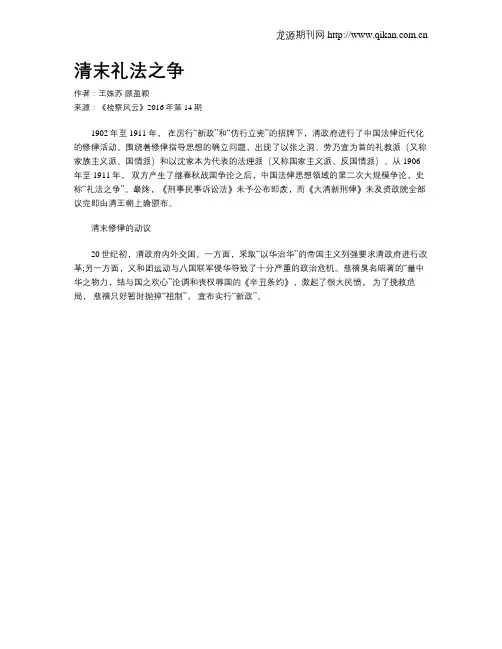
清末礼法之争作者:王姝苏顾盈颖来源:《检察风云》2016年第14期1902年至1911年,在厉行“新政”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清政府进行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修律活动。
围绕着修律指导思想的确立问题,出现了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又称家族主义派、国情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又称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
从1906年至1911年,双方产生了继春秋战国争论之后,中国法律思想领域的第二次大规模争论,史称“礼法之争”。
最终,《刑事民事诉讼法》未予公布即废,而《大清新刑律》未及资政院全部议完即由清王朝上谕颁布。
清末修律的动议20世纪初,清政府内外交困。
一方面,采取“以华治华”的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导致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危机。
慈禧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论调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激起了很大民愤,为了挽救危局,慈禧只好暂时抛掉“祖制”,宣布实行“新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仓皇西逃的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极言变法之必要,痛斥戊戌变法之荒谬。
光绪二十八年,法律改革被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二月初二,清政府下诏命令出使各国大臣搜集各国法律,以资修律时参考;同时命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列者,报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始编纂”。
根据这道谕旨,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保举沈家本和伍廷芳主持修律。
光绪三十年法律馆开馆,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莫瑞等任修律大臣主持修律。
修律大臣们认为,中西的刑制和罪名有着很大差别,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刑罚比西方的更为严厉。
正因为这样,外国旅居中国的人以此为借口,不愿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修律大臣随即指出了三种最重之刑: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
他们称这三种刑法不变通废除,指望别人受我法律约束,无异南辕北辙。
由于当时清政府最关心的就是收回领事裁判权,所以提议很快得到认可:今后凡是死罪,到斩决为止,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缘坐各条除知情者治罪外,其余均予宽容;刺字等项永远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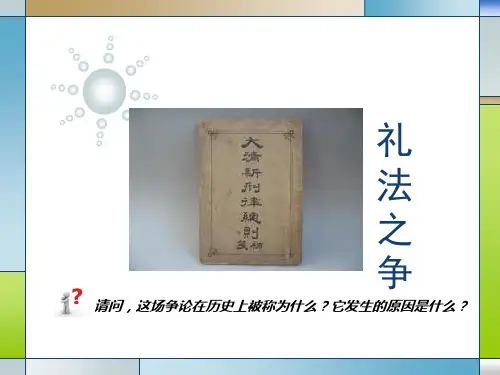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的内容及意义清末礼法之争啊,这可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呢。
咱得先知道这礼法之争是咋回事儿。
简单来说,就是在清末修律的时候,新派和礼教派之间有了很大的分歧。
新派呢,想引进西方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让咱的法律变得更现代。
礼教派呢,就觉得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礼教可不能丢,这法律得和礼教相结合。
比如说在关于“干名犯义”这个事儿上就有大分歧。
新派觉得这种封建时期的罪名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应该废除。
礼教派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这可是维护家族伦理关系的重要东西啊,要是没了,那不就乱套了吗?就好比一个家庭本来有一套很传统的规矩,突然有人说这规矩都得扔了,按照外面新的方式来,家里的老人肯定觉得不行啊,这就像礼教派的想法一样。
还有关于子孙违反教令这一规定,新派觉得这不该在刑法里规定,这更多的是家庭内部教育的事儿。
礼教派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要管的,子孙要是不听长辈的话,就得用法律来约束,不然礼教何在呢?这就像一群人在讨论一个孩子不听话该咋办。
新派说这是家里自己教育的事儿,别用法律插手。
礼教派就说,这要是不管,就像放羊一样,孩子不就没了约束,到处乱跑了吗?再说说这礼法之争的意义吧。
这可太重要了。
它就像是一场新旧观念的大碰撞。
新派的想法呢,其实是想让咱中国的法律走向世界,和国际接轨。
这就像一个封闭的小村子,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想把这些好东西引进来,让村子变得更好。
礼教派的存在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守护的礼教也是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要是全扔了,就像把自己的根给砍了,这多可怕呀。
通过这场礼法之争,咱中国的法律开始慢慢转型了。
新的法律思想开始一点点地渗透进来。
就好比给一个老旧的房子慢慢地换上新的部件,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在一点点地变好。
这让咱们后来的法律发展有了新的方向,不再只是拘泥于传统的礼教约束。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到底该怎么平衡传统和现代呢?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以前大家都觉得礼教就是天,不可违背。
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对当代的启示作者:邢程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1期摘 ;要: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继续维护其统治,开展了一场以礼教派和法理派之间的争论为主的修律运动,这场思想的大争论被称为“礼法之争”。
本文将对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进行阐述,通过对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这场争论的现实影响以及对当代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爭;启示关于“礼”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早在西周时期就认为礼与刑都属于法的一部分,起着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的关于“礼”与“法”的争论,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争论,另一次便是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之间的论战。
本文将对清末的“礼法之争”做初步的分析,从中探寻出当代的可借鉴之处。
一、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概述1.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大门逐渐被帝国主义打开,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
但是,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其内部的封建法制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领事裁判权的建立也使得国家主权大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清政府为继续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向西方的先进制度学习,大量修改法律,进行一些的改革运动。
2.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一直存着在明确的等级制度,清王朝时期亦是如此,其表现就在于祖宗之制不可更动,所以晚晴时的法律已经多年没有修改,与社会严重脱节,与西方先进制度相比其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
清末修律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已达到列强的满意。
因此,清末修律中既把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作为基准,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程度的借鉴。
二、礼教派与法理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1.张之洞的法律思想张之洞生长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在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之后更是深知礼教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对礼教大力推崇。
礼法之争的主要内容
礼法之争,是指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
以下是关于礼法之争的一些主要内容:
1. 关于“干名犯义”条款的存废。
法理派认为“不必另立专条”,主张予以废除;礼教派认为“中国素重纲常,立法特为严重”,主张予以保留。
2. 关于“留存养亲”条款的存废。
法理派认为“留存养亲”不宜编入新刑律草案;礼教派认为应在新刑律中体现。
3. 关于“无夫奸”和“亲属相奸”是否定罪。
法理派认为无夫奸“当以教育为方”、亲属相奸“未害及社会,处立决未免过严”,主张废除无夫奸定罪处刑,对亲属相奸从轻处断;礼教派认为无夫奸、亲属相奸“大犯礼教之事”,主张重刑治罪。
4. 关于“子孙违反教令”是否废除。
法理派主张废除,礼教派主张保留。
5. 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
法理派主张子孙卑幼有权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而礼教派则反对。
此外,关于服制和“十恶”重罪也在礼法之争中有所涉及。
总的来说,这场争论不仅关涉法律制度的改革,也反映出不同社会群体在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与冲突。
清末礼法之争的反思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潮涌动,其中礼法之争成为了当时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挣扎与抉择,也对中国后来的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礼法之争,简单来说,就是在法律改革的过程中,关于如何处理传统礼教与现代法律原则之间关系的激烈辩论。
在当时,一部分人主张大力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摒弃传统礼教对法律的束缚;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传统礼教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法律改革应当在保留礼教的基础上进行。
我们先来看看主张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这一方。
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体系,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西方的法律强调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这些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只有引进西方的法律,才能使中国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实现现代化。
而且,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经济交流的增加,中国也不得不与国际接轨,采用西方通行的法律规则,以保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然而,主张保留传统礼教的一方也有他们的理由。
他们认为,礼教在中国社会已经延续了数千年,深入人心,是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力量。
如果贸然摒弃礼教,将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道德的沦丧。
比如,孝道、夫妻之道、君臣之礼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轻易抛弃。
而且,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而应该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实际进行改革。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主张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一方,看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弊端和落后之处,希望通过改革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过于激进地追求西化,可能导致法律与社会的脱节。
而主张保留传统礼教的一方,虽然强调了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传统礼教中存在的封建糟粕和不合理之处,容易阻碍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从更深层次来看,清末礼法之争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一、背景清末变法的礼法之争,是指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曾任湖广总督、后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及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
二、双方1、法理派。
该派以沈家本为代表,主张运用“国家主义”等政法理论来改革中国旧法律制度,因在修订《大清新刑律》、《大青民事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常用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来对抗保守派的攻击,因而被称为“法理派”。
2、礼教派。
该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主张修订新法律应当“浑道德与法律与一体”,不应偏离中国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因而被称为“礼教派”。
三、焦点1、“干名犯义”的废存“干名犯义”是指子孙控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得相首匿”,亲属相互告言“亏教伤情,莫此为大”,因此在明清律中“干名犯义”属“十恶”之条。
鉴于此,礼教派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因此“干名犯义”之条大于礼教之事,是传统伦理的根本所在,因而应当在新刑律有所反应。
而法理派根据西方通行法理,指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2、“存留养亲”的废存“存留养亲”指“亲老丁单”时即凶犯属系独子、父母年老有病、家中无其他男丁,考虑到其父母无人奉养,又无其它男丁继承宗嗣,经皇帝特许,可免其死罪,施以其它处罚,令其回家“奉养其亲”的制度。
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从新律中排除。
沈家本则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且指出嘉庆六年上谕中曾表示:“是承祀、留养、非以施仁,实以长奸,转以诱人犯法”。
3、“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的定罪量刑礼教派认为内,无夫奸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而亲属相奸属于“大犯礼教之事”,因此应当在新律中对上述情况有特别规定。
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因此“此事有伤风化,当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简述清末“礼法之争”一、背景清末变法的礼法之争,是指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曾任湖广总督、后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及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
二、双方1、法理派。
该派以沈家本为代表,主张运用“国家主义”等政法理论来改革中国旧法律制度,因在修订《大清新刑律》、《大青民事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常用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来对抗保守派的攻击,因而被称为“法理派”。
2、礼教派。
该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主张修订新法律应当“浑道德与法律与一体”,不应偏离中国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因而被称为“礼教派”。
三、焦点1、“干名犯义”的废存“干名犯义”是指子孙控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得相首匿”,亲属相互告言“亏教伤情,莫此为大”,因此在明清律中“干名犯义”属“十恶”之条。
鉴于此,礼教派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因此“干名犯义”之条大于礼教之事,是传统伦理的根本所在,因而应当在新刑律有所反应。
而法理派根据西方通行法理,指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2、“存留养亲”的废存“存留养亲”指“亲老丁单”时即凶犯属系独子、父母年老有病、家中无其他男丁,考虑到其父母无人奉养,又无其它男丁继承宗嗣,经皇帝特许,可免其死罪,施以其它处罚,令其回家“奉养其亲”的制度。
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从新律中排除。
沈家本则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且指出嘉庆六年上谕中曾表示:“是承祀、留养、非以施仁,实以长奸,转以诱人犯法”。
3、“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的定罪量刑礼教派认为内,无夫奸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而亲属相奸属于“大犯礼教之事”,因此应当在新律中对上述情况有特别规定。
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因此“此事有伤风化,当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