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身份的再认识
- 格式:pdf
- 大小:348.98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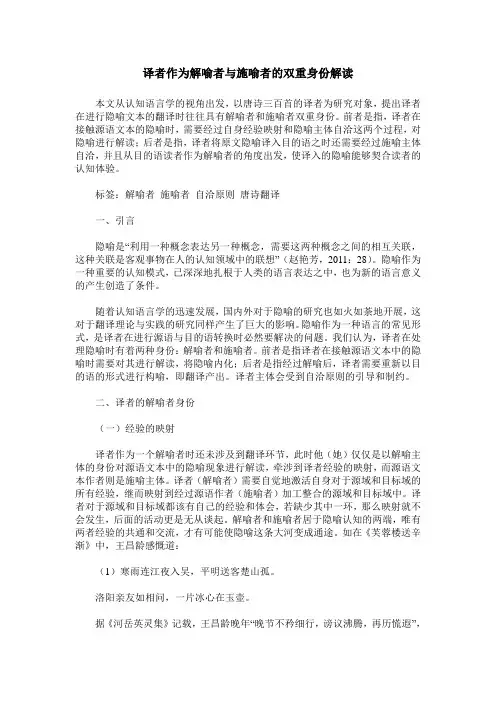
译者作为解喻者与施喻者的双重身份解读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以唐诗三百首的译者为研究对象,提出译者在进行隐喻文本的翻译时往往具有解喻者和施喻者双重身份。
前者是指,译者在接触源语文本的隐喻时,需要经过自身经验映射和隐喻主体自洽这两个过程,对隐喻进行解读;后者是指,译者将原文隐喻译入目的语之时还需要经过施喻主体自洽,并且从目的语读者作为解喻者的角度出发,使译入的隐喻能够契合读者的认知体验。
标签:解喻者施喻者自洽原则唐诗翻译一、引言隐喻是“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认知领域中的联想”(赵艳芳,2011:28)。
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已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语言表达之中,也为新的语言意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对于隐喻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这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的常见形式,是译者在进行源语与目的语转换时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译者在处理隐喻时有着两种身份:解喻者和施喻者。
前者是指译者在接触源语文本中的隐喻时需要对其进行解读,将隐喻内化;后者是指经过解喻后,译者需要重新以目的语的形式进行构喻,即翻译产出。
译者主体会受到自洽原则的引导和制约。
二、译者的解喻者身份(一)经验的映射译者作为一个解喻者时还未涉及到翻译环节,此时他(她)仅仅是以解喻主体的身份对源语文本中的隐喻现象进行解读,牵涉到译者经验的映射,而源语文本作者则是施喻主体。
译者(解喻者)需要自觉地激活自身对于源域和目标域的所有经验,继而映射到经过源语作者(施喻者)加工整合的源域和目标域中。
译者对于源域和目标域都该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若缺少其中一环,那么映射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活动更是无从谈起。
解喻者和施喻者居于隐喻认知的两端,唯有两者经验的共通和交流,才有可能使隐喻这条大河变成通途。
如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感慨道:(1)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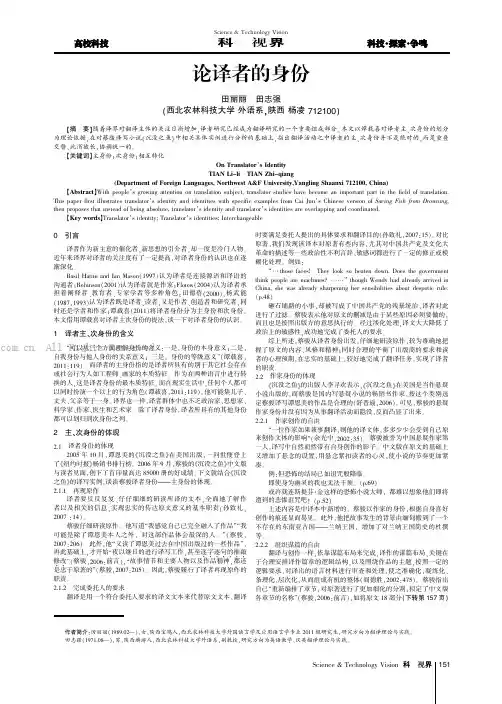
0引言译者作为新主意的催化者,新思想的引介者,却一度是冷门人物。
近年来译界对译者的关注度有了一定提高,对译者身份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
Basil Hatim and Ian Mason(1997)认为译者是连接源语和译语的沟通者;Robinson(2001)认为译者就是作家;Flotow(2004)认为译者承担着阐释者、教育者、专家学者等多种角色;田德蓓(2000),杨武能(1987,1993)认为译者既是译者、读者,又是作者、创造者和研究者,同时还是学者和作家;谭载喜(2011)将译者身份分为主身份和次身份。
本文借用谭载喜对译者主次身份的提法,谈一下对译者身份的认识。
1译者主、次身份的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身份的含义:一是,身份的本身意义;二是,自我身份与他人身份的关系意义;三是,身份的等级意义”(谭载喜,2011:119)。
而译者的主身份指的是译者所具有的别于其它社会存在或社会行为人如工程师、画家的本质特征。
作为在两种语言中进行转换的人,这是译者身份的最本质特征。
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可以同时扮演一个以上的行为角色(谭载喜,2011:119)。
他可能集儿子、丈夫、父亲等于一身。
译界也一样,译者群体中也不乏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医生和艺术家。
除了译者身份,译者所具有的其他身份都可以划归到次身份之列。
2主、次身份的体现2.1译者身份的体现2005年10月,谭恩美的《沉没之鱼》在美国出版,一问世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2006年9月,蔡骏的《沉没之鱼》中文版与读者见面,创下了首印量高达85000册的好成绩。
下文就结合《沉没之鱼》的译写实例,谈谈蔡骏译者身份———主身份的体现。
2.1.1再现原作译者要反反复复、仔仔细细的研读所译的文本,全面地了解作者以及相关的信息,实现忠实的传达原文意义的基本职责(孙致礼,2007:14)。
蔡骏仔细研读原作。
他写道“我感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作品”“我可能是除了谭恩美本人之外,对这部作品体会最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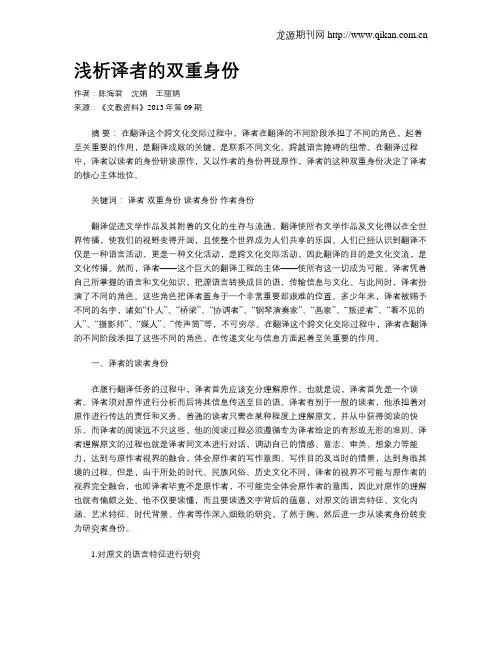
浅析译者的双重身份作者:陈海君沈娟王丽娟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09期摘要:在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在翻译的不同阶段承担了不同的角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是联系不同文化、跨越语言障碍的纽带。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以读者的身份研读原作,又以作者的身份再现原作,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译者的核心主体地位。
关键词:译者双重身份读者身份作者身份翻译促进文学作品及其附着的文化的生存与流通。
翻译使所有文学作品及文化得以在全世界传播,使我们的视野变得开阔,且使整个世界成为人们共享的乐园。
人们已经认识到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是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翻译的目的是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播。
然而,译者——这个巨大的翻译工程的主体——使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
译者凭着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和文化知识,把源语言转换成目的语,传输信息与文化。
与此同时,译者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这些角色把译者置身于一个非常重要却艰难的位置。
多少年来,译者被赐予不同的名字,诸如“仆人”、“桥梁”、“协调者”、“钢琴演奏家”、“画家”、“叛逆者”、“看不见的人”、“摄影师”、“媒人”、“传声筒”等,不可穷尽。
在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在翻译的不同阶段承担了这些不同的角色,在传递文化与信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译者的读者身份在履行翻译任务的过程中,译者首先应该充分理解原作。
也就是说,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
译者须对原作进行分析而后将其信息传送至目的语。
译者有别于一般的读者,他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的读者只需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原文,并从中获得阅读的快乐。
而译者的阅读远不只这些。
他的阅读过程必须遵循专为译者给定的有形或无形的准则。
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同文本进行对话,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力等能力,达到与原作者视界的融合,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写作目的及当时的情景,达到身临其境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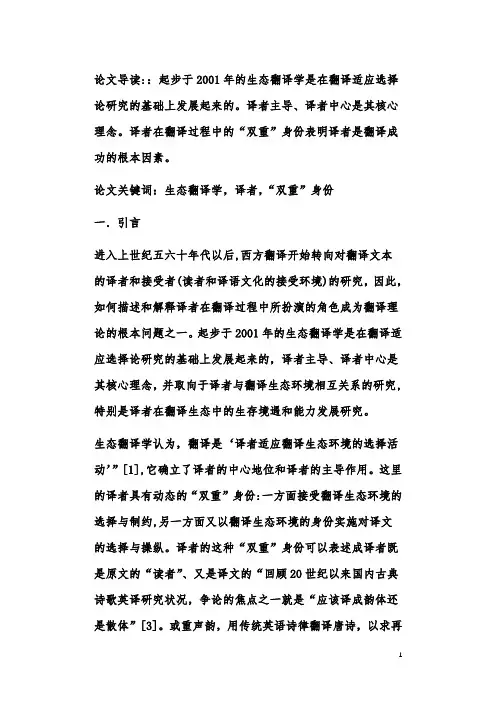
论文导读::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双重”身份表明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
论文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双重”身份一.引言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开始转向对翻译文本的译者和接受者(读者和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
起步于2001年的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它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的主导作用。
这里的译者具有动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与制约,另一方面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
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回顾20世纪以来国内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状况,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应该译成韵体还是散体”[3]。
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
这两种方向,既有其成功之处,又有其遗憾不足。
诗律有碍达意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对唐诗的翻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译者一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4],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
基于这个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唐诗英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其实质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在其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本文运用“生态翻译学”来分析著名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双译本的异同,探讨唐诗翻译中译者的双重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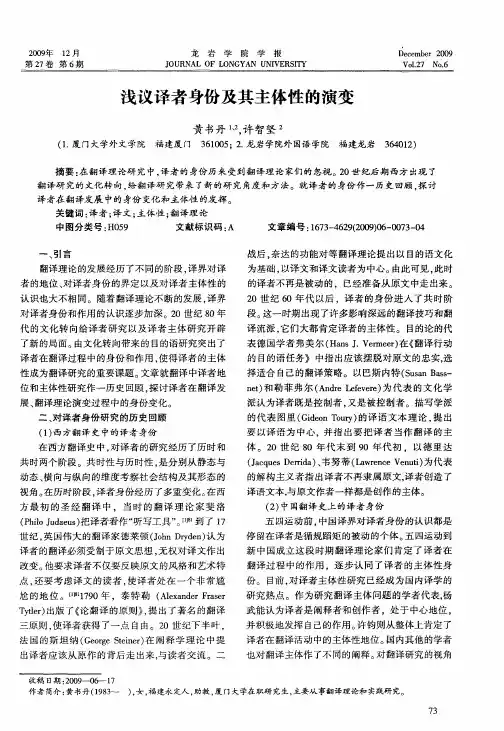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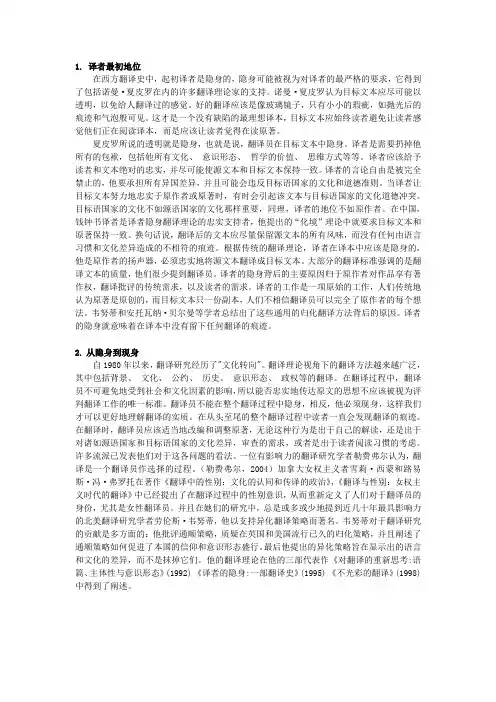
1. 译者最初地位在西方翻译史中,起初译者是隐身的,隐身可能被视为对译者的最严格的要求,它得到了包括诺曼·夏皮罗在内的许多翻译理论家的支持。
诺曼·夏皮罗认为目标文本应尽可能以透明,以免给人翻译过的感觉。
好的翻译应该是像玻璃镜子,只有小小的瑕疵,如抛光后的痕迹和气泡般可见。
这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最理想译本,目标文本应始终读者避免让读者感觉他们正在阅读译本,而是应该让读者觉得在读原著。
夏皮罗所说的透明就是隐身,也就是说,翻译员在目标文本中隐身。
译者是需要扔掉他所有的包袱,包括他所有文化、意识形态、哲学的价值、思维方式等等。
译者应该给予读者和文本绝对的忠实,并尽可能使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保持一致。
译者的言论自由是被完全禁止的,他要承担所有异国差异,并且可能会违反目标语国家的文化和道德准则。
当译者让目标文本努力地忠实于原作者或原著时,有时会引起该文本与目标语国家的文化道德冲突。
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不如源语国家的文化那样重要,同理,译者的地位不如原作者。
在中国,钱钟书译者是译者隐身翻译理论的忠实支持者,他提出的“化境”理论中就要求目标文本和原著保持一致。
换句话说,翻译后的文本应尽量保留源文本的所有风味,而没有任何由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造成的不相符的痕迹。
根据传统的翻译理论,译者在译本中应该是隐身的,他是原作者的扬声器,必须忠实地将源文本翻译成目标文本。
大部分的翻译标准强调的是翻译文本的质量,他们很少提到翻译员。
译者的隐身背后的主要原因归于原作者对作品享有著作权,翻译批评的传统需求,以及读者的需求。
译者的工作是一项原始的工作,人们传统地认为原著是原创的,而目标文本只一份副本,人们不相信翻译员可以完全了原作者的每个想法。
韦努蒂和安托瓦纳·贝尔曼等学者总结出了这些通用的归化翻译方法背后的原因。
译者的隐身就意味着在译本中没有留下任何翻译的痕迹。
2.从隐身到现身自1980年以来,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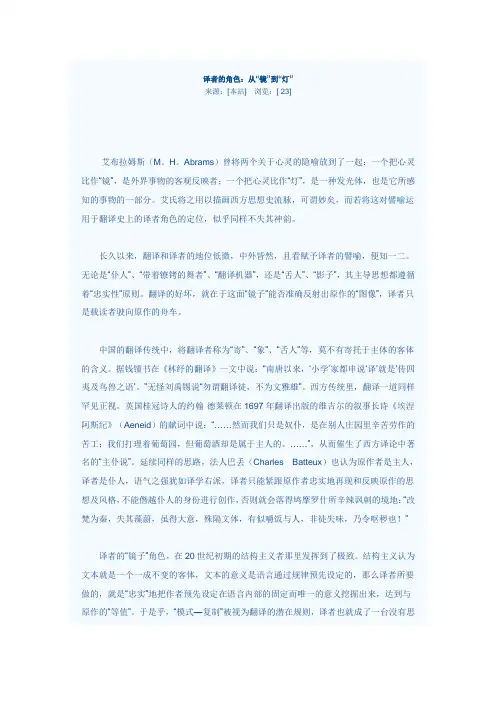
译者的角色:从“镜”到“灯”来源:[本站]浏览:[ 23]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曾将两个关于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镜”,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反映者;一个把心灵比作“灯”,是一种发光体,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艾氏将之用以描画西方思想史流脉,可谓妙矣,而若将这对譬喻运用于翻译史上的译者角色的定位,似乎同样不失其神韵。
长久以来,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低微,中外皆然,且看赋予译者的譬喻,便知一二。
无论是“仆人”、“带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还是“舌人”、“影子”,其主导思想都遵循着“忠实性”原则。
翻译的好坏,就在于这面“镜子”能否准确反射出原作的“图像”,译者只是载读者驶向原作的舟车。
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将翻译者称为“寄”、“象”、“舌人”等,莫不有寄托于主体的客体的含义。
据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
”无怪刘禹锡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
西方传统里,翻译一道同样罕见正视。
英国桂冠诗人的约翰·德莱顿在1697年翻译出版的维吉尔的叙事长诗《埃涅阿斯纪》(Aeneid)的献词中说:“……然而我们只是奴仆,是在别人庄园里辛苦劳作的苦工;我们打理着葡萄园,但葡萄酒却是属于主人的。
……”,从而催生了西方译论中著名的“主仆说”。
延续同样的思路,法人巴丢(Charles Batteux)也认为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语气之强犹如译学右派,译者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及风格,不能僭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否则就会落得鸠摩罗什所辛辣讽刺的境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译者的“镜子”角色,在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者那里发挥到了极致。
结构主义认为文本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那么译者所要做的,就是“忠实”地把作者预先设定在语言内部的固定而唯一的意义挖掘出来,达到与原作的“等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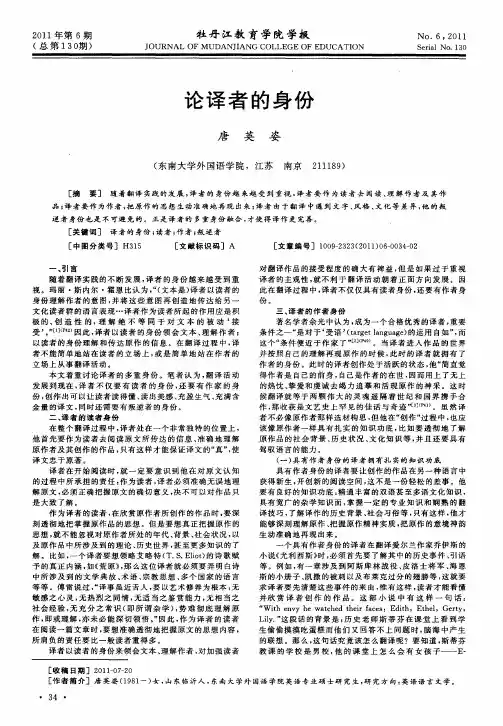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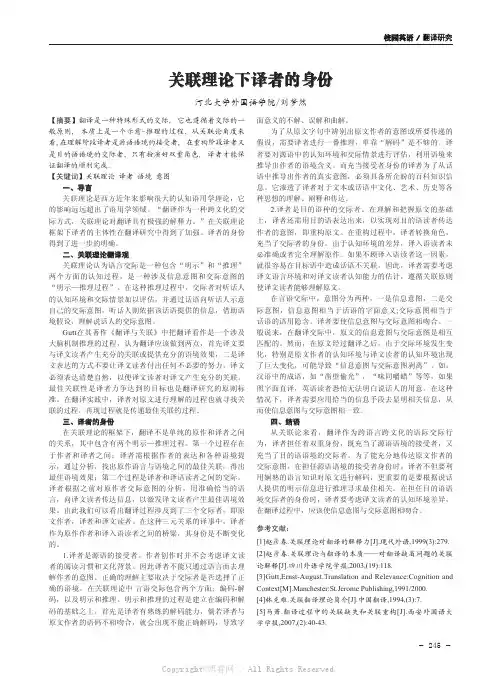
- 245 -校园英语 / 翻译研究关联理论下译者的身份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刘梦然【摘要】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际, 它也遵循着交际的一般原则, 本质上是一个示意-推理的过程。
从关联论角度来看,在理解阶段译者是源语语境的接受者, 在重构阶段译者又是目的语语境的交际者。
只有扮演好双重角色, 译者才能保证翻译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关联理论 译者 语境 意图一、导言关联理论是西方近年来影响很大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方式,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加强。
译者的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二、关联理论翻译观关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包含“明示”和“推理”两个方面的认知过程,是一种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
在这种推理过程中,交际者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和交际情景加以评估,并通过话语向听话人示意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则依据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借助语境假设,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Gutt 在其著作《翻译与关联》中把翻译看作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推理的过程,认为翻译应该做到两点,首先译文要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或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二是译文表达的方式不要让译文读者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译文必须表达清楚自然,以便译文读者对译文产生充分的关联。
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的过程也就寻找关联的过程,再现过程就是传递最佳关联的过程。
三、译者的身份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不是单纯的原作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有两个明示—推理过程。
第一个过程存在于作者和译者之间:译者需根据作者的表达和各种语境提示,通过分析,找出原作语言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得出最佳语境效果;第二个过程是译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
译者根据之前对原作者交际意图的分析,用准确恰当的语言,向译文读者传达信息,以激发译文读者产生最佳语境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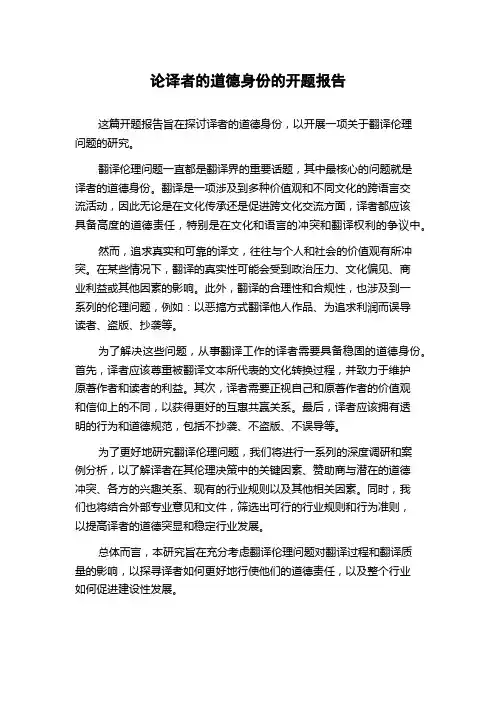
论译者的道德身份的开题报告这篇开题报告旨在探讨译者的道德身份,以开展一项关于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
翻译伦理问题一直都是翻译界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译者的道德身份。
翻译是一项涉及到多种价值观和不同文化的跨语言交流活动,因此无论是在文化传承还是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译者都应该具备高度的道德责任,特别是在文化和语言的冲突和翻译权利的争议中。
然而,追求真实和可靠的译文,往往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有所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翻译的真实性可能会受到政治压力、文化偏见、商业利益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此外,翻译的合理性和合规性,也涉及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例如:以恶搞方式翻译他人作品、为追求利润而误导读者、盗版、抄袭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需要具备稳固的道德身份。
首先,译者应该尊重被翻译文本所代表的文化转换过程,并致力于维护原著作者和读者的利益。
其次,译者需要正视自己和原著作者的价值观和信仰上的不同,以获得更好的互惠共赢关系。
最后,译者应该拥有透明的行为和道德规范,包括不抄袭、不盗版、不误导等。
为了更好地研究翻译伦理问题,我们将进行一系列的深度调研和案例分析,以了解译者在其伦理决策中的关键因素、赞助商与潜在的道德冲突、各方的兴趣关系、现有的行业规则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同时,我们也将结合外部专业意见和文件,筛选出可行的行业规则和行为准则,以提高译者的道德突显和稳定行业发展。
总体而言,本研究旨在充分考虑翻译伦理问题对翻译过程和翻译质量的影响,以探寻译者如何更好地行使他们的道德责任,以及整个行业如何促进建设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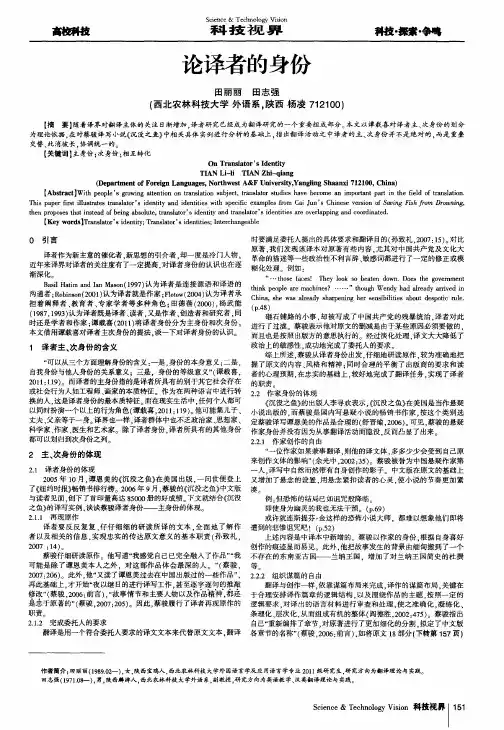
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
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
沟通越来越频繁,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由于每个译者的文化
身份不同,其对翻译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
本文将探讨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并
分析其中的原因和挑战。
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体现在译文的选择和表达上。
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译
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影响其选择和表达译文的方式。
一个译者的文化身份所承载
的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会在翻译过程中被融入到译文之中,使得译文更加符合目标文
化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
这也可能导致译文与原文在某些方面存在偏差,从而影响读者
对原作的理解和接受。
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注意和调整。
译
者应该注重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和反思,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从而提高自
身的跨文化意识和语言能力。
译者需要注重对原作和目标文化的深入了解,以便更准确地
理解和传达原作的意义和情感。
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需要尊重原作的风格和内涵,同时也要
尊重目标文化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努力寻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平衡和统一。
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通过加强跨文化意识和语言能力,译者可以更好地应对不同文化间的翻译挑战,从而实现
更好地传播和交流。
希望今后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能够更加重视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
的影响,从而推动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的进一步发展。
第 37 卷第 2 期 2021 年 4 月V ol .37,No .2 Apr .,2021历史语境中的译者身份之辨卞建华,石 灿(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青岛 266071)收稿日期:2021-04-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林语堂作品的中国文化变译策略研究”(14BYY012);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 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传译策略研究——以林语堂编译写策略为个案”(11CWXJ03)。
作者简介:卞建华(1969-),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西译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翻译教学等研究。
德州学院英语专业1988届毕业生。
① 以罗马尼亚裔的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1913-1970)为代表。
摘 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连接文本、读者乃至源语言语境、目的语语境的关键因素。
历史语境中的译者身份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被忽视到被认可的过程,这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对翻译的认知差异,更是我们进一步研究译者主体性的基础。
关键词:译者身份;译者主体性;翻译史中图分类号:H315;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44(2021)02-0064-04一、译学视域中的译者因素当代文学理论发生过两次研究重点的转移: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重点从以作家为主转向以作品文本为主,比如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文论;第二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重点由以作品文本为主转向以读者接受为主,比如存在主义文论、接受理论。
换言之,经由文学活动所延展的研究视野,在当代最终呈现出“作家——文本——读者”这一独特的嬗变轨迹。
受文学思潮的影响,翻译学研究视角也逐渐超越了语言层面,进入到更广阔的视野,表现在两种向度:一是阐发宏观传统翻译问题的视角发生转变,比如文化转向之后我们倾向于在源语言语境与目的语语境之下解读语际转换中的语言形态,至此,阐释视角转变到有关“选择与呈现”的诸问题中;二是解读具体传统翻译问题的视角开始纵深化,比如对于译者身份的看法不再拘泥于“附庸”,甚至不再困囿于“隐身”,而是充分考察到了译者与双重语境的多层互动关系。
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
每个人的文化身份是不可避免地与其语言、价值观、信仰和行为等方面紧密相连的。
在翻译工作中,翻译人员的文化身份对其能否准确传达源语言的含义和文化背景,保证译文符合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期望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
首先,译者的文化身份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如一个母语为英语的美国人可能更容易理解来自美国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和社会常规,而不同的翻译人员之间则可能有不同的看待同一文化现象的方式。
例如,“猫在温习”这个成语在中文中非常普遍,意思是“大意已经明白,但还要再复习一遍”。
但是对于非中文背景的翻译人员来说,他们可能难以理解这个成语的意思以及文化背景。
其次,译者的文化身份也可能对翻译的流畅度和语感产生影响。
译者所使用的语言,语调、习惯用语和语言的节奏都可能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
例如,一个法国翻译员在用英语进行翻译时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法语语调和语言节奏,这可能会影响其英语译文的流畅性。
最后,译者的文化身份还可能对译文中的文化因素和隐喻产生影响。
如果译者不了解某些文化传统或隐喻,则可能会产生误解并导致译文不准确甚至无效。
例如,美国国旗的颜色和形式被用来传达各种意义,而如果翻译人员不熟悉这些意义,则可能无法准确传达原文中的意思。
总之,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译者具备强大的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技能。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准确地传达源语言的含义和文化背景,同时又能够满足目标语言受众的文化需要。
历史上译者的地位摘要任何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译者的身份在整个翻译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明确译者的身份与地位无疑能够帮助翻译学明确自身的定位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完善本文拟穿越历史梳理译者在翻译史主要的几个阶段的地位与身份从而更好地认识译者及其地位明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关键词译者翻译史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一引言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与再表达译者在其中兼有独特的身份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到底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身份明确这一点无疑会对整个翻译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翻译作品更准确更完美地传达原作的信息本文拟穿越历史以不同的翻译流派为线索梳理译者在翻译史上各个阶段不同的地位与身份从而更好地认识译者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二译者的奴仆身份德莱顿John Dryden 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谭载喜1991 153 巴托Charles Batteux 则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超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在这样的翻译理念指导下译者地位低下的奴隶或仆人身份形成了译者不但要为原作者和原作负责而且要对译文读者负责要让他们领略原作的优点并得到同样强烈的感受译者受到极大程度的束缚译者主体性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三译者的复写者身份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语言的结构功能性质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也给涉及语言转换的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语言学派影响较大的翻译家应首推美国的奈达EugeneA.Nida 奈达是语言的共性论者他坚持认为各种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他把翻译定义为在译入语中使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第一是意义第二是文体奈达将交际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后修正为功能对等的标准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要求对等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C.Catford 则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模式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文本等值的概念他在界定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的定义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他对形式对应和文本等值作了区别并指出翻译实践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等值的译语而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则是界定翻译等值的性质和条件卡特福特认为源语和译语之间的等值关系基本上是可以量化的翻译就是在所有潜在的等值译语中为源语寻找最合适的等值语的过程屠国元廖晶2001 41到了80年代纽马克Peter Newmark 将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前者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后者则注重再现原文的要旨和接受者的理解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地道流畅这两种翻译方法其实只是部分地化解了直译与意译的矛盾是对早期翻译理论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究其根本语义翻译注重的是译者对原作者的忠实而交际翻译强调的则是译者对读者的忠实仍然没有脱离忠实的巢臼从以上的分析看虽然语言学派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人类语言的共性把等值看作是翻译理论的核心认为语言间存在着对等关系坚信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共核译者只要努力便可以找到从而达到所谓的与原作的等值在此种理念的关照下翻译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语符转换或是一种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甚至只是复写式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性译者在这里也就成为了一台脱离时空或情感制约的翻译机器语言学派过于关注语言的确定性刻意寻求所谓的转换规律而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性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四译者的操纵者身份20世纪70 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传统的翻译理论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文艺学或语言学的模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翻译研究派翻译研究派中文化学派的核心人物非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莫属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种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rewrite 改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它实际上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由此可以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反之也可以破坏它们两人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简直具有颠覆性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把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在他们眼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的协调和操控译文的地位不仅可以与原文平起平坐而且有时超过了原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自然也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上五译者的解放者身份翻译界一直流传的一句名言翻译即叛逆Translator is a traitor. 号召译者冲破源语的束缚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由此法国著名文论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系河南郑州450000常丽丽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之路翻译史上的译者。
重新审视译者作为“第二作者”的地位 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科学性,翻译活动涉及文本客体、主体(作者、译者、读者)及社会等因素,是一项复杂的语言活动。长期以来,人们对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基本上都基于一种“规范性”的要求,即处于特殊地位的译者应该如何面对作者与读者。传统翻译观对译者的要求可归结为两个词:一是忠实,二是客观。但是这种笼统的要求过于死板。忠实与客观这两个词很模糊,译者应该忠实于原著内容还是忠实于读者的要求?译者应该客观地阐释原著内容还是客观地面对读者的要求?在中西翻译史中,对译者要求的争论无休无止,这是一个根本不会有定论的争辩。 译者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客体存在,本身就有客观性、选择性和不确定性。所谓“橘生淮南而为枳”。译者有自己的本土语言,自身的文化社会背景,因此,译者有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想法,翻译不可能有定本。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换个角度来审视和分析一下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呢?如果我们把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看成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审视译者的主体地位就更有鲜明的立场。 倘若我们把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看成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那么译者就是原著的“第二作者”。“第二作者”的身份和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应该受到尊重,无论“第二作者”是否符合传统翻译观的要求,他具有自己的主观性,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和社会背景,对原著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以出自“第二作者”的外国文学译著是不可能有定本的。 一、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不同体系 外国文学译著与外国文学原著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有实质差别,翻译过程实际上是文学再创作的过程。翻译作品本质上是两种文学、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相互融合与交汇的产物,是以中文和中国文学为表述方式对外国文学进行的诠释和再表述,是外国文学的中国化。伟大的思想家加达默尔曾说过:“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翻译文学作品并不等于原著本身,而是以外国文学原著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的中文读本。我们读外国文学译著时,往往会感觉像在读中国文学作品,觉得外国作家在用中文进行写作与表述。事实上,翻译文学首先是由翻译者对外国文学原著进行阅读和诠释,经过思想内化后,再由其用中文进行表述成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中文文本,因此,翻译文学即外国文学译著并不等同于原著,很多语言上的巧妙之处来自于中文,表达方式已中国化或本土化。 二、从翻译的本质上来分析翻译文学是一种更新的文学模式 尽管中西方传统翻译都力求做到忠实原文,但绝对的忠诚是不可能的,在西方一直有“翻译即叛逆”的说法,歌德还曾把翻译家比作“下流的职业媒人”,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有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我们姑且不管这些说法的褒贬性,但文学翻译与原著之间在内涵与性质上存在巨大差异确是不争的事实。翻译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搬运,而是一项复杂且艰辛的工作,不仅要求翻译者要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还要尽力避免误解和障碍,将两种语言和文化融会贯通起来,最后将“不完美”的翻译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翻译总会有所增益和缺失,这是由语言的本性决定的,因为语言不是单纯的语言信号,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信号”是一个技术性名词,它是一个内在的、孤立的存在系统,不与其它别的事物产生联系,更不能反应和折射其它任何事物,更不会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任何关系。“符号”则是一个具有折射和反应功能且与其他事物有着一定联系的复杂体系,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功能。语言作为一个符号体系,它具有指示性、稳定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强制性,作为表达人的思维方式,与主体的文化背景有着内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涉及到两个语言符号体系,是语言积极地介入到意义的创造过程,是文化类型的转换,亦是文学模式的更新。如果把原著的写作看作生产过程,那么翻译则是再加工与再生产,它是一种新的写作实践和尝试,充满了无限的创造性。因此,翻译文学不是西方文学,但也不能简单的归为中国文学,它是以西方文学为蓝本,将其思想内涵与新意用中国文学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从根本上说,翻译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模式。 三、从翻译的主体性看译者作为“第二作者”的主体地位 在一个翻译过程中,原作是出发点,译作是目的地,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则是翻译者,他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隐形人,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枢纽地位,他的语言基础、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背景无疑会对翻译作品有深刻的影响。翻译作品的阅读对象是目的语读者,他们的理解能力和阅读诉求制约着翻译文本的性质,而读者是处于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的,所以翻译始终要站在目的语的立场和角度,始终受到目的语的文化和时代制约。很多外来词语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内涵有增有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这并不是译者有意为之,而是为了适应目的语的语言环境而做的本土化改造。可以说,翻译者一方面扮演读者的身份,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其内化、分解和填充;另一方面翻译者又扮演创造者即“第二作者”的身份,在目的语中赋予原作新的表现形式,使之与目的语读者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在另一个文化氛围里延续这原作的生命。所以说,翻译者作为“第二作者”是有其主体性的,译著是“第二作者”对原著的重新创作。 四、“忠”对于“第二作者”来说只是一个伦理概念 “忠实”始终是翻译者坚持的原则之一,包括形式上和意义上的忠实,但翻译是一项错综复杂的语言创造活动,保持译文与原文的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原则对于翻译者这个“第二作者”来说只能是一个伦理概念。翻译者在对两种语言进行翻译时,由于受到自身语言能力、文化背景、时代特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把一种语言的内容一成不变地搬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翻译的再生产和再创作过程也需要有艺术性和审美性。著名翻译学家许渊冲先生曾说过“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所以,翻译文学不必故作“忠实”而受到这一标准的制约和牵绊。 译者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译者的客观性和他的主体地位。外国文学原著和外国文学译著是有着一定联系的两个不同体系,在外国文学译著这个体系内,译者就是“第二作者”,身份地位等同于原著作者。著名学者余光中有言“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或是作家的声誉,但其影响未必较小,甚或更大。译者日与伟大的心灵为伍,见贤思齐,当其会意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这可谓是对翻译者的最佳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