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电影传媒中的女性形象
- 格式:pdf
- 大小:176.56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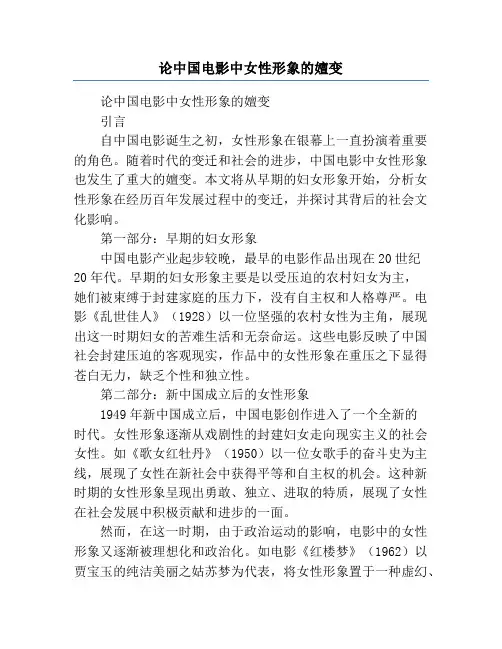
论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嬗变论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引言自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女性形象在银幕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也发生了重大的嬗变。
本文将从早期的妇女形象开始,分析女性形象在经历百年发展过程中的变迁,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影响。
第一部分:早期的妇女形象中国电影产业起步较晚,最早的电影作品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
早期的妇女形象主要是以受压迫的农村妇女为主,她们被束缚于封建家庭的压力下,没有自主权和人格尊严。
电影《乱世佳人》(1928)以一位坚强的农村女性为主角,展现出这一时期妇女的苦难生活和无奈命运。
这些电影反映了中国社会封建压迫的客观现实,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重压之下显得苍白无力,缺乏个性和独立性。
第二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形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女性形象逐渐从戏剧性的封建妇女走向现实主义的社会女性。
如《歌女红牡丹》(1950)以一位女歌手的奋斗史为主线,展现了女性在新社会中获得平等和自主权的机会。
这种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呈现出勇敢、独立、进取的特质,展现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积极贡献和进步的一面。
然而,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又逐渐被理想化和政治化。
如电影《红楼梦》(1962)以贾宝玉的纯洁美丽之姑苏梦为代表,将女性形象置于一种虚幻、理想化的境地中。
这种女性形象远离现实,使女性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受到了限制。
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与女性形象的转变1978年改革开放的推进,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新的思想和多元化的表现方式。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开始呈现出更多的现代特征。
如电影《舞台姐妹》(1985)以两个在大街小巷打拼的姐妹为主线,展现了女性在社会迅速变化中的多变角色。
这种新时期的女性形象更加突出了女性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展现了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成果。
然而,改革开放也给部分女性形象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化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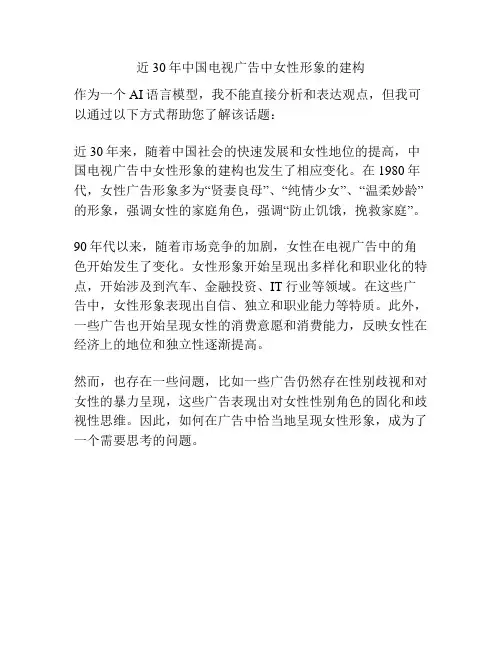
近30年中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建构
作为一个AI语言模型,我不能直接分析和表达观点,但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您了解该话题:
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中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在1980年代,女性广告形象多为“贤妻良母”、“纯情少女”、“温柔妙龄”的形象,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强调“防止饥饿,挽救家庭”。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女性在电视广告中的角色开始发生了变化。
女性形象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和职业化的特点,开始涉及到汽车、金融投资、IT行业等领域。
在这些广告中,女性形象表现出自信、独立和职业能力等特质。
此外,一些广告也开始呈现女性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反映女性在经济上的地位和独立性逐渐提高。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广告仍然存在性别歧视和对女性的暴力呈现,这些广告表现出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固化和歧视性思维。
因此,如何在广告中恰当地呈现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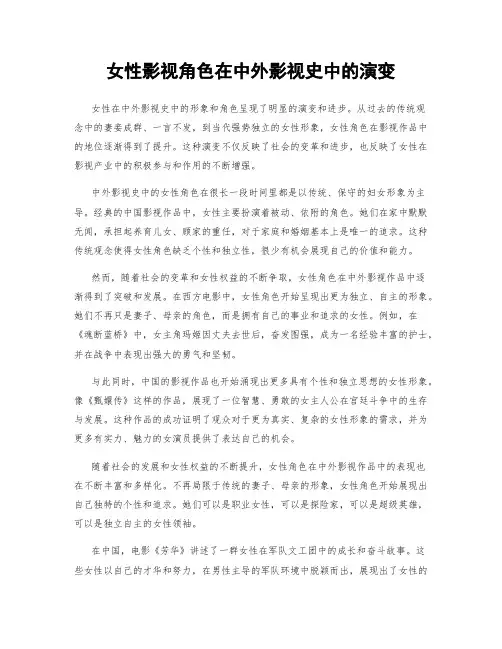
女性影视角色在中外影视史中的演变女性在中外影视史中的形象和角色呈现了明显的演变和进步。
从过去的传统观念中的妻妾成群、一言不发,到当代强势独立的女性形象,女性角色在影视作品中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提升。
这种演变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也反映了女性在影视产业中的积极参与和作用的不断增强。
中外影视史中的女性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传统、保守的妇女形象为主导。
经典的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性主要扮演着被动、依附的角色。
她们在家中默默无闻,承担起养育儿女、顾家的重任,对于家庭和婚姻基本上是唯一的追求。
这种传统观念使得女性角色缺乏个性和独立性,很少有机会展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女性权益的不断争取,女性角色在中外影视作品中逐渐得到了突破和发展。
在西方电影中,女性角色开始呈现出更为独立、自主的形象。
她们不再只是妻子、母亲的角色,而是拥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的女性。
例如,在《魂断蓝桥》中,女主角玛姬因丈夫去世后,奋发图强,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护士,并在战争中表现出强大的勇气和坚韧。
与此同时,中国的影视作品也开始涌现出更多具有个性和独立思想的女性形象。
像《甄嬛传》这样的作品,展现了一位智慧、勇敢的女主人公在宫廷斗争中的生存与发展。
这种作品的成功证明了观众对于更为真实、复杂的女性形象的需求,并为更多有实力、魅力的女演员提供了表达自己的机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权益的不断提升,女性角色在中外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也在不断丰富和多样化。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妻子、母亲的形象,女性角色开始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追求。
她们可以是职业女性,可以是探险家,可以是超级英雄,可以是独立自主的女性领袖。
在中国,电影《芳华》讲述了一群女性在军队文工团中的成长和奋斗故事。
这些女性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男性主导的军队环境中脱颖而出,展现出了女性的智慧和勇气。
这样的影片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女性价值和能力的重新认可,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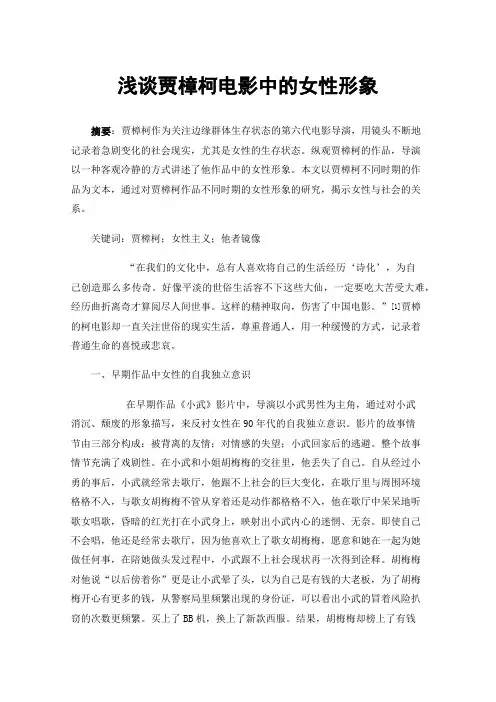
浅谈贾樟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摘要:贾樟柯作为关注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用镜头不断地记录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
纵观贾樟柯的作品,导演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方式讲述了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以贾樟柯不同时期的作品为文本,通过对贾樟柯作品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揭示女性与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贾樟柯;女性主义;他者镜像“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
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世事。
这样的精神取向,伤害了中国电影。
”[1]贾樟的柯电影却一直关注世俗的现实生活,尊重普通人,用一种缓慢的方式,记录着普通生命的喜悦或悲哀。
一、早期作品中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在早期作品《小武》影片中,导演以小武男性为主角,通过对小武消沉、颓废的形象描写,来反衬女性在90年代的自我独立意识。
影片的故事情节由三部分构成:被背离的友情;对情感的失望;小武回家后的逃避。
整个故事情节充满了戏剧性。
在小武和小姐胡梅梅的交往里,他丢失了自己。
自从经过小勇的事后,小武就经常去歌厅,他跟不上社会的巨大变化,在歌厅里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与歌女胡梅梅不管从穿着还是动作都格格不入,他在歌厅中呆呆地听歌女唱歌,昏暗的红光打在小武身上,映射出小武内心的迷惘、无奈。
即使自己不会唱,他还是经常去歌厅,因为他喜欢上了歌女胡梅梅,愿意和她在一起为她做任何事,在陪她做头发过程中,小武跟不上社会现状再一次得到诠释。
胡梅梅对他说“以后傍着你”更是让小武晕了头,以为自己是有钱的大老板,为了胡梅梅开心有更多的钱,从警察局里频繁出现的身份证,可以看出小武的冒着风险扒窃的次数更频繁。
买上了BB机,换上了新款西服。
结果,胡梅梅却榜上了有钱大老板抛弃了小武。
小武在胡梅梅原来的出租屋内,呆呆地望着床,窗外马路上嘈杂的环境音响体现小武复杂的内心环境,一下子回到现实中,再次迷失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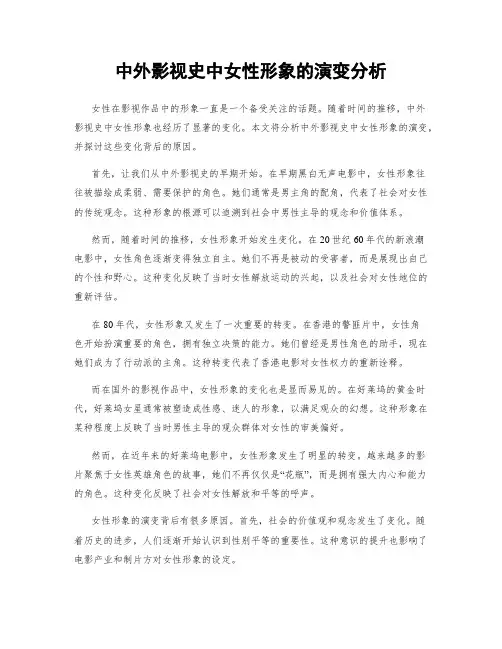
中外影视史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分析女性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影视史中女性形象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本文将分析中外影视史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并探讨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从中外影视史的早期开始。
在早期黑白无声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被描绘成柔弱、需要保护的角色。
她们通常是男主角的配角,代表了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观念。
这种形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社会中男性主导的观念和价值体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浪潮电影中,女性角色逐渐变得独立自主。
她们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野心。
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重新评估。
在80年代,女性形象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
在香港的警匪片中,女性角色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拥有独立决策的能力。
她们曾经是男性角色的助手,现在她们成为了行动派的主角。
这种转变代表了香港电影对女性权力的重新诠释。
而在国外的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好莱坞女星通常被塑造成性感、迷人的形象,以满足观众的幻想。
这种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男性主导的观众群体对女性的审美偏好。
然而,在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影片聚焦于女性英雄角色的故事,她们不再仅仅是“花瓶”,而是拥有强大内心和能力的角色。
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解放和平等的呼声。
女性形象的演变背后有很多原因。
首先,社会的价值观和观念发生了变化。
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这种意识的提升也影响了电影产业和制片方对女性形象的设定。
其次,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和职场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影视作品的变化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化,试图展现女性的强大和独立。
此外,观众的需求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影响。
观众对电影的呈现期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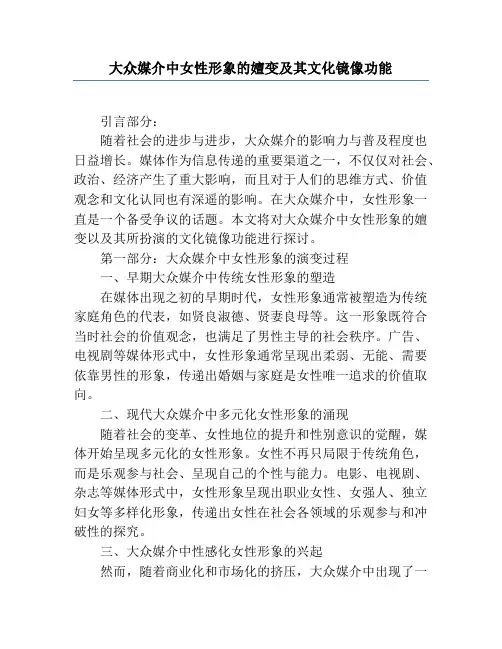
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镜像功能引言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进步,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普及程度也日益增长。
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之一,不仅仅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也有深遥的影响。
在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本文将对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以及其所扮演的文化镜像功能进行探讨。
第一部分: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的演变过程一、早期大众媒介中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媒体出现之初的早期时代,女性形象通常被塑造为传统家庭角色的代表,如贤良淑德、贤妻良母等。
这一形象既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也满足了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
广告、电视剧等媒体形式中,女性形象通常呈现出柔弱、无能、需要依靠男性的形象,传递出婚姻与家庭是女性唯一追求的价值取向。
二、现代大众媒介中多元化女性形象的涌现随着社会的变革、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性别意识的觉醒,媒体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女性不再只局限于传统角色,而是乐观参与社会、呈现自己的个性与能力。
电影、电视剧、杂志等媒体形式中,女性形象呈现出职业女性、女强人、独立妇女等多样化形象,传递出女性在社会各领域的乐观参与和冲破性的探究。
三、大众媒介中性感化女性形象的兴起然而,随着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挤压,大众媒介中出现了一种以性感化女性形象为特征的现象。
商业广告、电影、音乐视频等媒体形式中,女性形象开始被过度强调身体曲线、外貌和性感特质,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视觉性欲和审美要求。
女性形象逐渐被固化为“性感偶像”,并且成为商业利益的来往对象。
第二部分:大众媒介中女性形象的文化镜像功能媒体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文化态度和观念。
女性形象在大众媒介中的呈现不仅仅是媒体对女性的塑造,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认同和价值观念。
一、女性形象的创设与文化认同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创设通常是基于社会文化中对女性的认同和期待。
媒体通过展示女性的特质、行为和观念,传递出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和价值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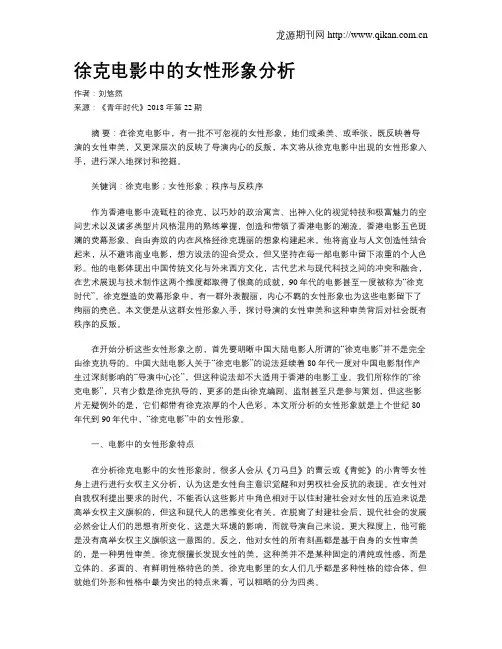
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作者:刘悠然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22期摘要:在徐克电影中,有一批不可忽视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柔美、或乖张,既反映着导演的女性审美,又更深层次的反映了导演内心的反叛,本文将从徐克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入手,进行深入地探讨和挖掘。
关键词:徐克电影;女性形象;秩序与反秩序作为香港电影中流砥柱的徐克,以巧妙的政治寓言、出神入化的视觉特技和极富魅力的空间艺术以及诸多类型片风格混用的熟练掌握,创造和带领了香港电影的潮流。
香港电影五色斑斓的荧幕形象、自由奔放的内在风格经徐克瑰丽的想象构建起来。
他将商业与人文创造性结合起来,从不避讳商业电影,想方设法的迎合受众,但又坚持在每一部电影中留下浓重的个人色彩。
他的电影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古代艺术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在艺术展现与技术制作这两个维度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90年代的电影甚至一度被称为“徐克时代”。
徐克塑造的荧幕形象中,有一群外表靓丽,内心不羁的女性形象也为这些电影留下了绚丽的亮色。
本文便是从这群女性形象入手,探讨导演的女性审美和这种审美背后对社会既有秩序的反叛。
在开始分析这些女性形象之前,首先要明晰中国大陆电影人所谓的“徐克电影”并不是完全由徐克执导的。
中国大陆电影人关于“徐克电影”的说法延续着80年代一度对中国电影制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导演中心论”,但这种说法却不大适用于香港的电影工业。
我们所称作的“徐克电影”,只有少数是徐克执导的,更多的是由徐克编剧、监制甚至只是参与策划,但这些影片无疑例外的是,它们都带有徐克浓厚的个人色彩。
本文所分析的女性形象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一、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特点在分析徐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时,很多人会从《刀马旦》的曹云或《青蛇》的小青等女性身上进行进行女权主义分析,认为这是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和对男权社会反抗的表现。
在女性对自我权利提出要求的时代,不能否认这些影片中角色相对于以往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来说是高举女权主义旗帜的,但这和现代人的思维变化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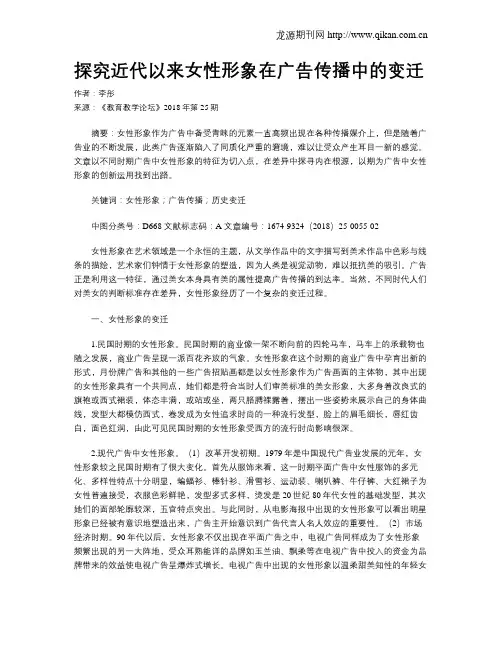
探究近代以来女性形象在广告传播中的变迁作者:李彤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8年第25期摘要:女性形象作为广告中备受青睐的元素一直高频出现在各种传播媒介上,但是随着广告业的不断发展,此类广告逐渐陷入了同质化严重的窘境,难以让受众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章以不同时期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特征为切入点,在差异中探寻内在根源,以期为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创新运用找到出路。
关键词:女性形象;广告传播;历史变迁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8)25-0055-02女性形象在艺术领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描写到美术作品中色彩与线条的描绘,艺术家们钟情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因为人类是视觉动物,难以抵抗美的吸引。
广告正是利用这一特征,通过美女本身具有美的属性提高广告传播的到达率。
当然,不同时代人们对美女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
一、女性形象的变迁1.民国时期的女性形象。
民国时期的商业像一架不断向前的四轮马车,马车上的承载物也随之发展,商业广告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气象。
女性形象在这个时期的商业广告中孕育出新的形式,月份牌广告和其他的一些广告招贴画都是以女性形象作为广告画面的主体物,其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具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符合当时人们审美标准的美女形象,大多身着改良式的旗袍或西式裙装,体态丰满,或站或坐,两只胳膊裸露着,摆出一些姿势来展示自己的身体曲线,发型大都模仿西式,卷发成为女性追求时尚的一种流行发型,脸上的眉毛细长,唇红齿白,面色红润,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女性形象受西方的流行时尚影响很深。
2.现代广告中女性形象。
(1)改革开发初期。
1979年是中国现代广告业发展的元年,女性形象较之民国时期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从服饰来看,这一时期平面广告中女性服饰的多元化、多样性特点十分明显,蝙蝠衫、棒针衫、滑雪衫、运动装、喇叭裤、牛仔裤、大红裙子为女性普遍接受,衣服色彩鲜艳,发型多式多样,烫发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基础发型,其次她们的面部轮廓较深,五官特点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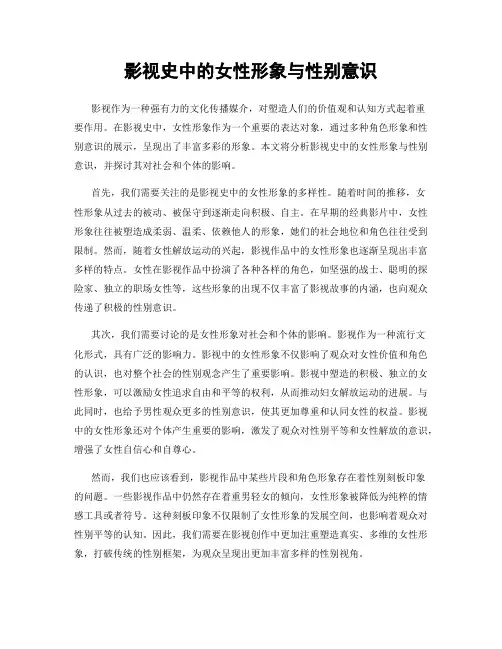
影视史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影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播媒介,对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起着重要作用。
在影视史中,女性形象作为一个重要的表达对象,通过多种角色形象和性别意识的展示,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象。
本文将分析影视史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并探讨其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影视史中的女性形象的多样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形象从过去的被动、被保守到逐渐走向积极、自主。
在早期的经典影片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塑造成柔弱、温柔、依赖他人的形象,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往往受到限制。
然而,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逐渐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
女性在影视作品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如坚强的战士、聪明的探险家、独立的职场女性等,这些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影视故事的内涵,也向观众传递了积极的性别意识。
其次,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女性形象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
影视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影响了观众对女性价值和角色的认识,也对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影视中塑造的积极、独立的女性形象,可以激励女性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从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进展。
与此同时,也给予男性观众更多的性别意识,使其更加尊重和认同女性的权益。
影视中的女性形象还对个体产生重要的影响,激发了观众对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意识,增强了女性自信心和自尊心。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作品中某些片段和角色形象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
一些影视作品中仍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倾向,女性形象被降低为纯粹的情感工具或者符号。
这种刻板印象不仅限制了女性形象的发展空间,也影响着观众对性别平等的认知。
因此,我们需要在影视创作中更加注重塑造真实、多维的女性形象,打破传统的性别框架,为观众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性别视角。
为了呈现更加积极多样的女性形象,影视行业需要鼓励和支持女性电影人的创作。
目前,女性导演、编剧、制片人在影视行业的比例依然较低,这也导致了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单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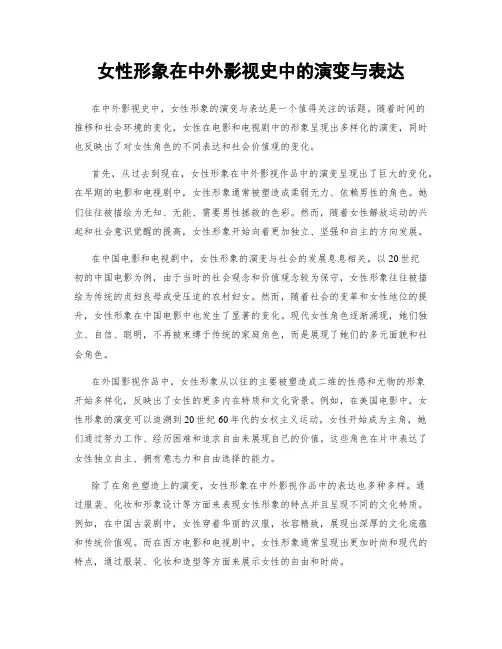
女性形象在中外影视史中的演变与表达在中外影视史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与表达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形象呈现出多样化的演变,同时也反映出了对女性角色的不同表达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首先,从过去到现在,女性形象在中外影视作品中的演变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
在早期的电影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通常被塑造成柔弱无力、依赖男性的角色。
她们往往被描绘为无知、无能、需要男性拯救的色彩。
然而,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社会意识觉醒的提高,女性形象开始向着更加独立、坚强和自主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电影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以20世纪初的中国电影为例,由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较为保守,女性形象往往被描绘为传统的贞妇良母或受压迫的农村妇女。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形象在中国电影中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现代女性角色逐渐涌现,她们独立、自信、聪明,不再被束缚于传统的家庭角色,而是展现了她们的多元面貌和社会角色。
在外国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从以往的主要被塑造成二维的性感和尤物的形象开始多样化,反映出了女性的更多内在特质和文化背景。
例如,在美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
女性开始成为主角,她们通过努力工作、经历困难和追求自由来展现自己的价值。
这些角色在片中表达了女性独立自主、拥有意志力和自由选择的能力。
除了在角色塑造上的演变,女性形象在中外影视作品中的表达也多种多样。
通过服装、化妆和形象设计等方面来表现女性形象的特点并且呈现不同的文化特质。
例如,在中国古装剧中,女性穿着华丽的汉服,妆容精致,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价值观。
而在西方电影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通常呈现出更加时尚和现代的特点,通过服装、化妆和造型等方面来展示女性的自由和时尚。
此外,女性形象在中外影视作品中的演绎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地位和价值观的认知与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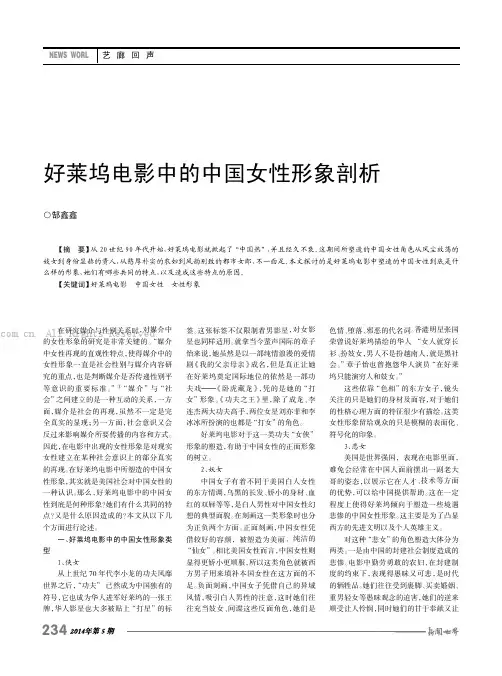
第4卷第1期2004年1月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H UNAN MASS MEDIA VOCATIONAL TE CH NIC AL C OLL EGE Vol.4No.1Janu.2004[收稿日期] 2003-07-09[作者简介] 黄宝峰(1978-),男,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传媒与女性百年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黄宝峰(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摘 要] 通过考查近百年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女性的属性特点,探讨女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从一个方面揭示女性形象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借以探寻女性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
[关键词] 女性形象 女性意识 时代女性 文化传统[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454(2004)01-0074-04杰克 贝尔登这样描述中国妇女与社会的关系: 三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权力始终与对妇女的控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宗法社会也植根于家长的地位以及他作为物质财产源泉的妇女的占有 妇女当奴隶,成为私有财产和统治阶级传宗接代工具的地位,不仅对总的中国社会,甚至国家结构,下至农村上至朝廷,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妇女的地位低下,不仅给妇女本身带来可怕的结果,同时也造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遭到破坏 [1]中国女性与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中国女性成为中国电影格外偏爱的对象,女性始终是银幕剧作中的重要形象群。
影视以有声有色的画面展示着社会生活,塑造着不同的女性形象,更以充满艺术感染力的个性话语传达着某个时代的观念。
女性意识属于观念形态,不只具有性别意味,同时含有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从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 难夫难妻 ,或是第一部故事片 阎瑞生 ,到20年代的 海誓 ,30年代的左翼电影,40年代的战后电影 乃至今天影视中的 新 女性,这一传统的、剧作家爱写、观众爱看的女性形象系列,到底发生了什么革命性的变化?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影视画面中女性形象的变迁,借以辨识女性意识的嬗变过程,分析由于时代观念的变异以及影视人对影视艺术的广泛探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变迁来看女性意识的变迁。
浅谈当代中国电影艺术中的女性角色[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中国电影社会制约[论文摘要]在我们看到过的影视作品中,总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光鲜亮丽,温柔婉约,她们戴着与生俱来的母性光辉,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惊叹。
在中国的传统意念中,女性应当是扮演着温柔体贴,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在我们生活的时下,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有了更多层次的开展空间,和更多生活途径的选择权。
这使生活在当今的女性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等同于男人的尊严,她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争取明天的开展权,对婚姻,对事业,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都由她们自己来主宰。
以前那些只有男人拥有的特权之门,在现如今已经不能再把女性阻挡在外。
电影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变相传达,女性如此巨大的改变,自然也逃不过摄影机的镜头。
在中国现代的电影艺术中,我们惊喜地从中看到中国女性动人的蜕变,从封闭保守的表到达开放张显的张示,这期间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转变,是值得我们寻味的。
19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女性开始反省自身的价值,并确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奉献被充分揭示出来。
在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电影艺术中的女性意识也渐渐觉醒,同时期出现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电影也崭露头角。
运动中的电影批评主要是针对一些男性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犀利的批评,进一步揭示对女性的探讨,描写更细腻的女性感情世界。
由此,女性角色被史无前例的关注和讨论。
中国女性由于其所受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所散发出的气质与其他地区的女性有很大不同,而在讨论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时,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和地域的烙樱那些闪耀的荧幕之星,她们的出现曾带给多少人沉醉的喜悦和游离的梦想,也带给人多少无奈的追问与失落的伤感。
正是因为她们的付出和努力点缀了那苍白的灰色的大荧幕,幻化出一场场惟妙惟肖的尘世闹剧。
一、第五代电影创作者对女性的表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崛起,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光辉的新时代,中国电影从此走上了国际影坛,并频频获奖,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悄然兴起,电影也开始面临商业化的挑战。
《东方影像中的女性——中、日、朝、韩银幕女性形象创作及其特征》篇一在东方电影艺术中,女性形象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在不同国家的电影银幕上展现着独特的魅力。
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家的电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创作和表现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鲜明的特征。
本文将探讨这些国家银幕上女性形象的创作及其特征。
一、中国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创作及其特征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历经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保守到开放的转变。
在经典的老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塑造为贤良淑德、温柔体贴的典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银幕上的女性形象逐渐丰富多元,开始展现出独立、自信、勇敢的现代特质。
近年来,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更加多样化,涵盖了不同年龄、职业、性格的群体,展现了女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二、日本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创作及其特征日本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常常带有浓厚的文化特色和情感色彩。
从传统的“艺妓”、“女学生”到现代的“都市女性”、“独立女性”,日本电影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
这些形象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表达力和艺术感染力,展现出日本文化的细腻和深沉。
同时,日本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也常常涉及到性别平等、女性独立等社会议题。
三、朝鲜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创作及其特征朝鲜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通常带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在朝鲜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塑造为勤劳、善良、坚韧的典型,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集体主义精神。
这些形象在展现女性的传统美德的同时,也体现了朝鲜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四、韩国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创作及其特征韩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多样且富有现代感。
韩国电影善于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来探讨社会问题,如性别平等、家庭关系等。
韩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魅力和情感力量,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同时,韩国电影也善于通过女性的成长和奋斗来展现女性的独立和自强。
五、东方银幕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征与差异尽管中、日、朝、韩四国的银幕女性形象在创作上各有特色,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比如,这些国家的电影都善于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社会现实和文化特色;都关注女性的成长和奋斗;都强调女性的独立和自强等。
中外影视史中的女性形象演变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中外影视史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显著的演变。
从早期的被动、依赖男性的形象,到现代女性在影视作品中展现出的坚强、独立和有主见的形象,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对女性价值观的转变。
首先,在早期的中外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往往被描绘成一种被动、依赖男性的角色。
在西方电影中,女性常常被描绘成温柔、柔弱的受害者。
而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则常常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社会上的传统角色,强调她们在家庭中的牺牲和奉献。
这种被动角色定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权益运动的兴起,中外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发生转变。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开始呈现出一种坚强和独立的特质。
例如,在《红高梁》中,女主角秀珍作为一名女工展现出强大的生活力量和乐观精神。
同样,西方影片中也出现了一些强势和独立的女性形象,如《绝望的主妇》中的伊夫林和《钢铁侠》系列中的佩珀·波茨等。
这些形象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她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角色定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形象在中外影视作品中展现出了更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不再仅限于传统的家庭角色,出现了更多拥有事业和追求梦想的职业女性形象。
例如,在电影《湄公河行动》中,女特警队长韩杰饰演的角色展现出坚毅和勇敢的一面,向观众展示了女性在面对危险和困难时的强大能力。
而在西方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多样性也日益增加。
从《饥饿游戏》系列中的卡特尼丝到《小妇人》中的玛奇,女性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刻板印象,而是呈现出了更多的个性和社会角色。
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中外影视作品中也有不少作品探讨了这一问题。
例如,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龙母丹妮莉丝·坦格利安,她既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又是一个有决策能力的领导者。
大陆小妞电影的女性形象分析
小妞电影(Chick Flick)作为一种亚类型片,是小妞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小妞文化是新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中的投射。
20世纪90
年代开始小妞电影在好莱坞兴起,2009年这个概念被引入中国电影市场,掀起了小妞电影拍摄和上映的狂潮。
由于中国传统伦理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女性特殊的解放方式等原因,大陆小妞电影中所体现出的小妞形象颇具独特性:在女性的家庭形象中,大部分电影专注表现作为“准妻子”角色的小妞,对其他角色表现较少;在表现职业女性时,带有一定偏见性,不仅弱化了女性的职业表现,强调拜金主义价值观,而且对女性成功的判断有失公正。
这是目前内地小妞电影中表现出的女性形象的局限性,但我们已经看到了电影人在改进这种局限的努力,以及小妞电影在中国市场存在的必要,因此对于大陆小妞电影的前景,本文持乐观态度。
浅谈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与发展一、中国电影里女性形象的初始模样咱都知道,中国电影刚起步那会,女性形象可单一啦。
就像那种传统的、被设定好的角色。
大多是温柔、贤惠,在家相夫教子的那种类型。
你看那些老电影里,女性往往是围着家庭转,丈夫孩子就是她们的全部世界。
那时候的女性形象就像是被框在一个小盒子里,导演们刻画的她们就是为了体现传统的家庭观念,就像电影里那些妈妈们,总是在厨房忙碌,脸上带着那种逆来顺受的表情。
二、女性形象的转变阶段慢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形象开始有了变化。
就像一阵春风吹过,女性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在一些电影里,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她们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比如想当一名歌手或者演员。
这个时候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了,不再只是家庭的附属品。
就拿巩俐演的一些电影来说吧,她演的角色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敢于和传统的观念作斗争。
而且在穿着打扮上也更加时尚,更能体现现代女性的魅力。
三、现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现在啊,中国电影里的女性形象那可真是丰富多彩。
有那种超级厉害的职场女精英,就像电影杜拉拉升职记里的杜拉拉,在职场上披荆斩棘,和男人们竞争也毫不逊色。
还有那种充满冒险精神的女性,像在一些冒险电影里,女性不再是拖后腿的,而是团队里的核心力量。
甚至还有一些电影开始探讨女性内心的复杂情感,比如在爱情里的迷茫、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挣扎。
而且现在的女性形象也不再局限于年轻漂亮的,各种年龄段的女性都能在电影里找到自己的代表。
老阿姨也可以有自己精彩的故事,就像电影桃姐里的桃姐,那种平凡中的伟大让人感动。
四、女性形象演变发展的原因这里面的原因可不少呢。
首先,社会的进步是个大因素。
现在的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在现实生活里的地位提高了,在电影里当然也要体现出来呀。
再就是观众的需求变了,大家不再想看那种单一的女性形象,都希望看到更真实、更多样化的女性。
而且现在的导演们也更加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他们想要通过电影来表达女性的各种情感和想法。
90年代电影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屈雅君 90年代中国的电影市场,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变化,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难辨方向波动后,才现出一个大致轮廓的。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至少有三道不同的风景交替呈现于银幕之上。
第一类是肩负着政治使命的,处于权威地位的,掌握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旋律”影片。
第二类影片应该说是肩负文化使命的,代表着新潮、上乘鉴赏口味的,并试图与世界电影“接轨”的艺术片。
第三类是服务于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消费目的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娱乐片”的作品。
而我们关于“电影传播媒体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也只能镶嵌在这样一个独特、具体、复杂的背景之中。
一、永恒的“大地之母”“主旋律”的作品中的女性,无疑是妇女解放理论统帅下的传统“花木兰”形象的变体。
在这一脉妇女理论中,“妇女解放”的动作是由处于社会和历史中心的男性主体发出的,这个动作的“完成”句号也由男性主体来标定,因此“妇女解放”的意义不在于女性主体的价值回归,而在于它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明证。
这里借用戴锦华的话说:“花木兰”/一个化妆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是主流文化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镜象。
①在90年代的“主旋律”的作品中,花木兰(女八路,女游击队长,女战士等)们除了继续充当着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点缀”外。
比起五六七十年代的姐妹们,多了许多“诱惑”的主动性。
她们一方面承担着“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神话最简明扼要的图解,另一方面,她们作为男性目光“注视”的对象,躲在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意识形态话语背后,曲曲折折地满足着男性视角的愿望。
以写女性为主的这类题材为数有限,《中国霸王花》颇具代表性。
在众多的女兵中,照例有一个“洪常青”,但最能代表时代特点的是,这个洪常青已不同于从前的洪常青,他除了做女兵们的导师和引路人外,还兼做她们的异性偶像甚至情人。
而这些“当代花木兰”比起吴琼花来,身姿更矫健,容貌更娇美。
她们靓丽而单纯、豪爽又多情、倔犟得显出娇横,坚强得招人疼爱。
她们从“无性差”的银幕中走出来,却照例没有改变作为男性动作的承受者的被动的、客体的地位。
“贤妻良母”形象是被女性主义批评家说滥了的话题。
然而在这里仍然有重提的必要,因为在当代中国,它的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80年代,一代名导演①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
谢晋曾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冯晴岚、李玉芝、胡玉音等系列“爱妻”。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编导沉潜于叙事之中,以一种内化了的情感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女主人公的召唤力。
这些女性形象是为了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承担起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而降生于世的。
她们有的是文盲,有的是才貌平平的知识女性。
在那个阴差阳错的时代,她们与一个为不公正的命运所戏弄、由天之骄子伦为阶下囚的精神贵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之改变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道路。
她们是男人们漫漫寒夜中的灯塔,默默发芽开花、默默奉献的小草,以及扶助男人走出泥泞的忠实情侣。
这些女性名为“妻”,而实为“母”,她们不是以其“审美的属性”而是以其“实用的属性”去对应男性观众的欣赏心理的。
这种属性在以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体验为情感基调的“伤痕”题材影片中,显得尤为珍贵。
由此看来,这些处处实践着“母”性功能的“妻子”们,一方面,作为男性各个不同层次的生命需求的“物化”形态,为时代和社会提供着女性的人格模式,继续着女性主体被放逐的历史;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创造物,她们身上折射出数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中重道德理性、重实用价值的品格。
应该说,三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故事片《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拍得是相当感人的。
它们都以质朴的写实风格,入情入理的人生体验,批判自省的历史眼光和恰如其分的道德定位赢得了千百万观众流自内心的泪水。
像这样的题材,在金钱无孔不入,价值日益下滑的市场经济下,要想引起大众真诚的感动,对上至编导下至演职人员的艺术素养的要求绝不亚于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红高粱》。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凑巧这些“好人”的故事身边都有一个“好妻子”的故事———一个女人的生活完全融化在另一个男人的生活中;她们关心、理解、崇拜、无条件地服从;她们无声无息地做,但很少说;她们总是退到焦点以外,心甘情愿地让另一个更加高大的身影来遮蔽自己。
谢晋以一部重合了一“妻”一“母”两个好女人的杰作《高山下的花环》为80年代的辉煌战果———“爱妻”群像———划上了句号。
一进入90年代,他就开始专门为母亲画像(《清凉寺的钟声》)。
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影坛上小成气候的“地母”热:《继母》描写了一位不计得失,不思回报,以全部心血去养育一群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女的女人;《九香》中的身患绝症的女主人公无声地证明着母爱所能达到的生命极限;《中国妈妈》将一个为人们熟知的帮助自己失聪的儿子走上人生旅程的母亲搬上了银幕。
当然,最杰出的、最精美的、最感人的、最大气的“母亲之歌”,要首选《黑骏马》。
导演谢飞用他自己创造的画面语言,让母爱象阳光和空气一样充盈于他镜头所及的每一寸空间。
谢飞的电影都称得上大雅之作。
80年代,当《黑骏马》作为张承志的成名作为文学界所瞩目的时候,谢飞和他的同道们或许正准备投身于声讨封建婚姻制度的最后和声中。
与他的《湘女萧萧》时间相仿佛,还有黄健中的另一个极相似的、极美的故事《良家妇女》。
他们用纯净的、严肃的语调描述着生活在角落里的,被钉死在特殊婚姻角色中的,迷失在姐姐、妻子、母亲多重体验中的女人的凄婉动人的故事。
后来,谢飞又因《香魂女》而声名大噪。
影片刻画了一个在母亲、婆婆、妻子、情人和女强人等无数沉重无比的角色中间挣扎得死去活来的女人。
忧伤多于欢乐,困惑多于期待,作者并不刻意去询唤什么,只是从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出发去质疑生活,同时让生活本身的岐义性变成现实的自明性。
二、永远的“大众情人”公平地说,法国著名导演特吕弗的“电影是女性的艺术”的名言,在作为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惯性延续的影片中,是多少要打些折扣的。
当电影传媒结束了“无性时代”后,中国银幕又经历了一个蹒跚学步的过程。
展现在90年代电影观众面前的“女人”已经出落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了。
无论怎样说,当代电影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为男性郁积多年的“力比多”的释放,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
捧着大把的奖杯进入90年代的张艺谋继续着他大红大紫的电影创造。
他推向中国银幕的“大众情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客观一点说,导演的“第五代”是沉重的一代,无论他们的镜头玩得有多“帅”,无论他们让观众笑得有多轻松,他们也很难卸掉历史所赋予的重任。
张艺谋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将一个立体多面的电影世界朝向中国和西方不同观众的不同需求;他以艺术上的大胆突破对传统话语进行,获得了实际上的认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作品在世界电影节领奖台上纷纷亮相后,又进入了“金鸡”“百花”的提名并且获奖),他用夸张的和甚至虚构的民族风情画去“寻找一种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东方呈现”,自觉地“将西方式的文化视点、国际电影节评委的口味、其对中国电影之预期投射内在化”②,并且大获全胜;他和他的“性感明星”珠联璧合地讲述着一个个发生在令中国观众都感到陌生的场景中的风月故事,尽职尽责地为在90年代在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双重压抑下的中国(男)人缓解性焦虑,并以此保持了票房价值不倒的记录;他把这些性的故事装进一个反封建的大包袱里,使他们不至于在“扫黄”中落网,也为相当一些批评家呈送了一道理直气壮津津乐道的盛餐;他把同这些性的故事有关的沉重的文化思考献给了那些忧国忧民的思想家,总之,张艺谋方方面面都做得相当出色。
但张艺谋的确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界刮起了一股旋风。
以至于当漂亮的九儿已经摇身变为秋菊,捧着大肚子摇摇晃晃地走上银幕时,张艺谋播种的那些“高粱”长势正猛———《大磨坊》、《黄河谣》、《天出血》、《黄沙・青草・红太阳》、《炮打双灯》、《狂》、《五魁》等等,短短几年内,银幕上充斥着黄土地、黄沙滩、黄河水;红灯笼、红轿子、红嫁衣,它们重复地讲述着那些不知发生在何年何月何种背景下的庄稼地里的、四合院里的、染房的、豆腐房的、磨房的、炮仗作坊里的故事。
而且讲得越来越离奇,却也越来越相似了。
“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之所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还在于,它根本上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
”这一时代的“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原本’的消失,同样,转喻到女性,便是‘真实女性’的篡改和失落———即或有不为他人控制的真正属于女性自身意愿欲望表达的瞬间,那‘真实的愿望’亦在为机械复制‘再现’的那一刻而‘当时已惘然了”。
③对于上述电影作品来说,“原本”的消失可以说是双重的,一方面,银幕上的那些于今天的观众十分陌生的生活场景已由原初的、真实生活感受的载体变成了频频传承抄袭的画面,在这个“复制”的过程中,艺术创造的神髓———主体的感受力开始层层剥落耗损,所增加的只是花样翻新的形式上的浮华;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这是这类题材必不可少的主人公)也在被反复如此这般地言说中成为某种“女性”人格的范型,而这种被公众在毫无觉察地认可的“女人”却有可能早已远离了女性的真实存在。
不难发现,张艺谋及其追随者创造的女性形象,不仅仅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同时,她们自身也是一种“欲望主体”。
九儿在被迫与一个麻疯病人成婚时偶遇体魄强健的余占鳌,菊豆在一个性无能者的残酷折磨下主动投入了天青的怀抱,颂莲即使在与众姨太争风吃醋的激烈搏斗中仍不失时机地向风华正茂的大少爷调情(而这些作品在由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女人肉体上、感情上所受的摧残都被程度不同地淡化,而女人对“性”的要求都有所加强),同样,《炮打双灯》中的女掌柜,《狂》中的蔡大嫂,《五魁》中的少奶奶,包括以②③黎慧《欲望、代码、升华———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
戴锦华《裂谷:90年代电影笔记》,《艺术广角》1992年第6期。
创造“女性电影”而闻名的男导演王进的镜头下的那些正常的和变态的年轻貌美的姑娘们(《寡妇村》、《女人花》),都无一例外地被突出了赤裸裸的、强烈的“性欲”。
这些欲火中烧的女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真实存在呢?我们有理由怀疑。
因为同是当代电影,那些由女性执导的(特别是编剧、导演同为女性的)影片,却常常是热衷于“爱情”而淡化单纯的“性欲”。
这不禁使人想到西方女性主义最热衷探讨同时也是争议颇大的问题,那就是:女人除了生理构造以外,是否还具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不同于男人的特点?这是一个险象环生、处处陷阱的话题,却又是一个诱人的话题。
一个成功的张艺谋所引出的这许多为欲望所折磨的女人,映射出这样一个事实:两性之间在相互体察和相互认知过程中,双方都可能会带着无法避免也难以克服的性别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