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
- 格式:docx
- 大小:12.49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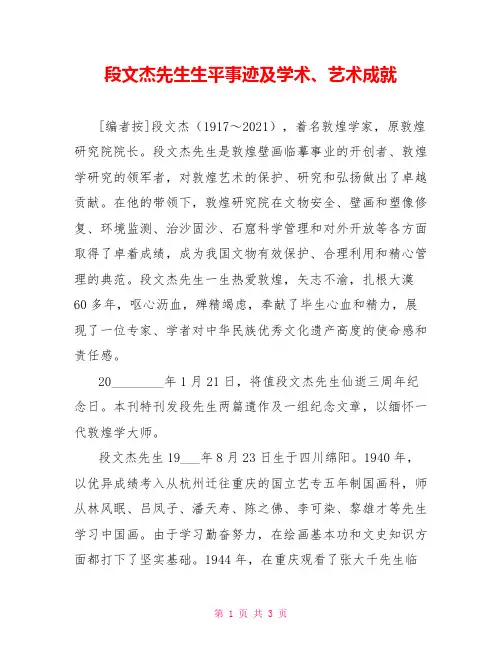
段文杰先生生平事迹及学术、艺术成就[编者按]段文杰(1917~2021),着名敦煌学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创者、敦煌学研究的领军者,对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他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文物安全、壁画和塑像修复、环境监测、治沙固沙、石窟科学管理和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取得了卓着成绩,成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段文杰先生一生热爱敦煌,矢志不渝,扎根大漠60多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展现了一位专家、学者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0________年1月21日,将值段文杰先生仙逝三周年纪念日。
本刊特刊发段先生两篇遗作及一组纪念文章,以缅怀一代敦煌学大师。
段文杰先生19___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绵阳。
194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从杭州迁往重庆的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科,师从林风眠、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李可染、黎雄才等先生学习中国画。
由于学习勤奋努力,在绘画基本功和文史知识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4年,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同时也了解到地处边远荒漠的敦煌石窟艺术遗产需要有识之士去保护和研究,就下决心要担当一名志愿者。
他的想法得到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等先生和同学们的支持。
1945年毕业后,几经曲折,义无反顾,于1946年到达敦煌莫高窟。
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并担任美术组组长和考古组代组长。
1950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代理所长、副研究员。
1957年后,遭错误处理。
1962年,经上级组织甄别平反,恢复原有职务和待遇。
“文革”期间又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农村劳动。
1972年,回所工作。
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
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1998年以后,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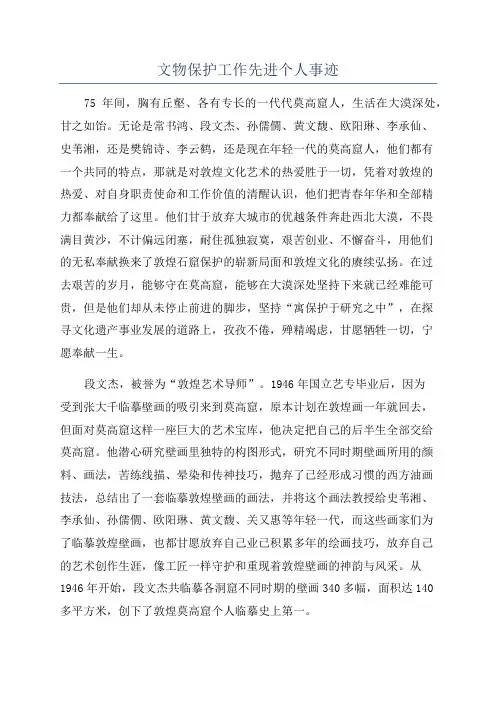
文物保护工作先进个人事迹75年间,胸有丘壑、各有专长的一代代莫高窟人,生活在大漠深处,甘之如饴。
无论是常书鸿、段文杰、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还是樊锦诗、李云鹤,还是现在年轻一代的莫高窟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热爱胜于一切,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对自身职责使命和工作价值的清醒认识,他们把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里。
他们甘于放弃大城市的优越条件奔赴西北大漠,不畏满目黄沙,不计偏远闭塞,耐住孤独寂寞,艰苦创业、不懈奋斗,用他们的无私奉献换来了敦煌石窟保护的崭新局面和敦煌文化的赓续弘扬。
在过去艰苦的岁月,能够守在莫高窟,能够在大漠深处坚持下来就已经难能可贵,但是他们却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坚持“寓保护于研究之中”,在探寻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甘愿牺牲一切,宁愿奉献一生。
段文杰,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
1946年国立艺专毕业后,因为受到张大千临摹壁画的吸引来到莫高窟,原本计划在敦煌画一年就回去,但面对莫高窟这样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他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给莫高窟。
他潜心研究壁画里独特的构图形式,研究不同时期壁画所用的颜料、画法,苦练线描、晕染和传神技巧,抛弃了已经形成习惯的西方油画技法,总结出了一套临摹敦煌壁画的画法,并将这个画法教授给史苇湘、李承仙、孙儒僩、欧阳琳、黄文馥、关又惠等年轻一代,而这些画家们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也都甘愿放弃自己业已积累多年的绘画技巧,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生涯,像工匠一样守护和重现着敦煌壁画的神韵与风采。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第一。
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1963年,樊锦诗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从繁华的大城市到条件最艰苦的西北荒漠,同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工作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住土屋、睡土炕、坐土凳、用土桌、点油灯、喝咸水,而这一来竟然就是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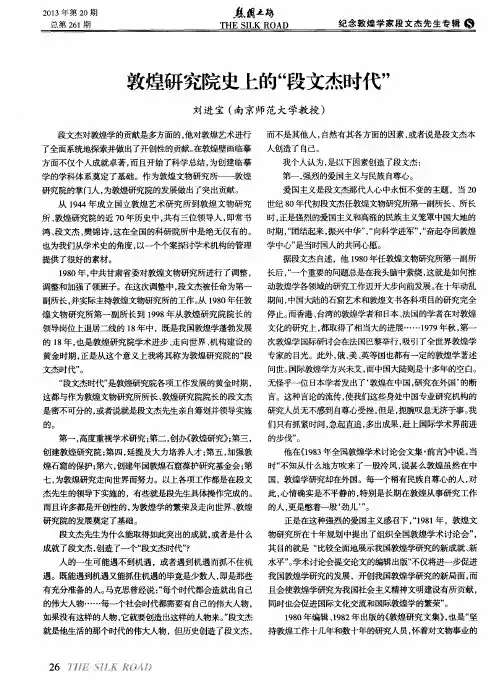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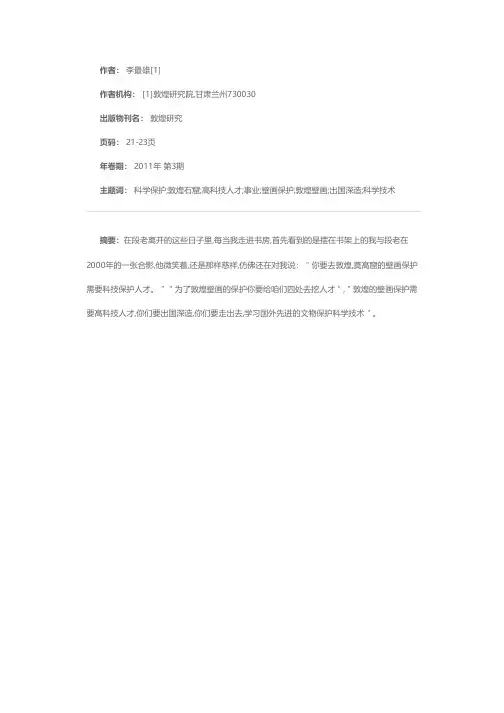
作者: 李最雄[1]
作者机构: [1]敦煌研究院,甘肃兰州730030
出版物刊名: 敦煌研究
页码: 21-23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3期
主题词: 科学保护;敦煌石窟;高科技人才;事业;壁画保护;敦煌壁画;出国深造;科学技术
摘要:在段老离开的这些日子里,每当我走进书房,首先看到的是摆在书架上的我与段老在2000年的一张合影,他微笑着,还是那样慈祥,仿佛还在对我说:"你要去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保护需要科技保护人才。
""为了敦煌壁画的保护你要给咱们四处去挖人才","敦煌的壁画保护需要高科技人才,你们要出国深造,你们要走出去,学习国外先进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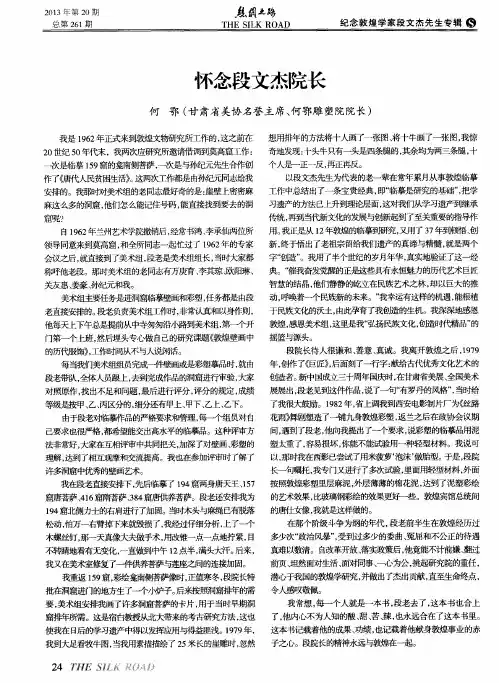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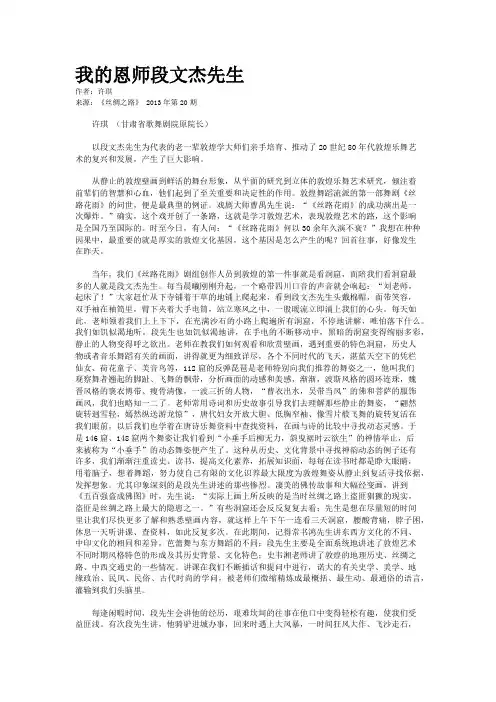
我的恩师段文杰先生作者:许琪来源:《丝绸之路》 2013年第20期许琪(甘肃省歌舞剧院原院长)以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敦煌学大师们亲手培育、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敦煌乐舞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静止的敦煌壁画到鲜活的舞台形象,从平面的研究到立体的敦煌乐舞艺术研究,倾注着前辈们的智慧和心血,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
敦煌舞蹈流派的第一部舞剧《丝路花雨》的问世,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说:“《丝路花雨》的成功演出是一次爆炸。
”确实,这个戏开创了一条路,这就是学习敦煌艺术,表现敦煌艺术的路,这个影响是全国乃至国际的。
时至今日,有人问:“《丝路花雨》何以30余年久演不衰?”我想在种种因果中,最重要的就是厚实的敦煌文化基因,这个基因是怎么产生的呢?回首往事,好像发生在昨天。
当年,我们《丝路花雨》剧组创作人员到敦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洞窟,而陪我们看洞窟最多的人就是段文杰先生。
每当晨曦刚刚升起,一个略带四川口音的声音就会响起:“刘老师,起床了!”大家赶忙从下寺铺着干草的地铺上爬起来,看到段文杰先生头戴棉帽,面带笑容,双手袖在袖筒里,臂下夹着大手电筒,站立寒风之中,一股暖流立即涌上我们的心头。
每天如此,老师领着我们上上下下,在充满沙石的小路上爬遍所有洞窟,不停地讲解,唯怕落下什么。
我们如饥似渴地听,段先生也如饥似渴地讲,在手电的不断移动中,黑暗的洞窟变得绚丽多彩,静止的人物变得呼之欲出。
老师在教我们如何观看和欣赏壁画,遇到重要的特色洞窟,历史人物或者音乐舞蹈有关的画面,讲得就更为细致详尽,各个不同时代的飞天,湛蓝天空下的凭栏仙女、荷花童子、美音鸟等,112窟的反弹琵琶是老师特别向我们推荐的舞姿之一,他叫我们观察舞者翘起的脚趾、飞舞的飘带,分析画面的动感和美感,渐渐,波斯风格的圆环连珠,魏晋风格的褒衣博带、瘦骨清像,一波三折的人物,“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佛和菩萨的服饰画风,我们也略知一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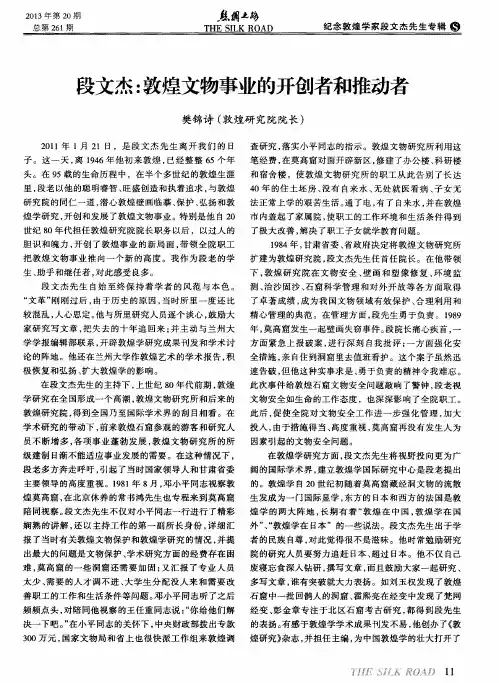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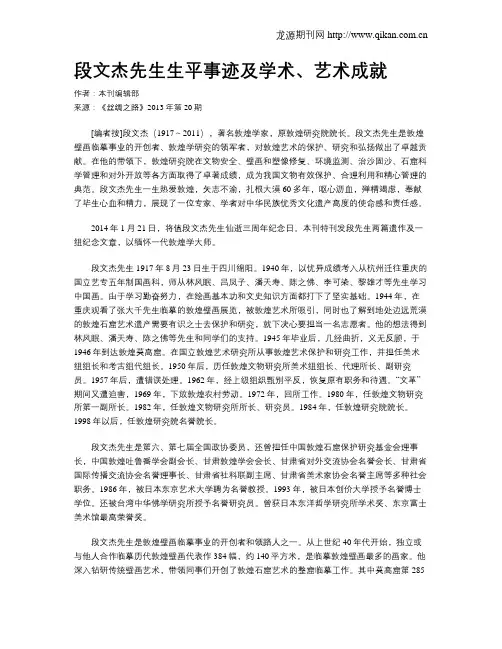
段文杰先生生平事迹及学术、艺术成就作者:本刊编辑部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20期[编者按]段文杰(1917~2011),著名敦煌学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创者、敦煌学研究的领军者,对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他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文物安全、壁画和塑像修复、环境监测、治沙固沙、石窟科学管理和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成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段文杰先生一生热爱敦煌,矢志不渝,扎根大漠60多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展现了一位专家、学者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014年1月21日,将值段文杰先生仙逝三周年纪念日。
本刊特刊发段先生两篇遗作及一组纪念文章,以缅怀一代敦煌学大师。
段文杰先生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绵阳。
194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从杭州迁往重庆的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科,师从林风眠、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李可染、黎雄才等先生学习中国画。
由于学习勤奋努力,在绘画基本功和文史知识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4年,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同时也了解到地处边远荒漠的敦煌石窟艺术遗产需要有识之士去保护和研究,就下决心要担当一名志愿者。
他的想法得到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等先生和同学们的支持。
1945年毕业后,几经曲折,义无反顾,于1946年到达敦煌莫高窟。
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并担任美术组组长和考古组代组长。
1950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代理所长、副研究员。
1957年后,遭错误处理。
1962年,经上级组织甄别平反,恢复原有职务和待遇。
“文革”期间又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农村劳动。
1972年,回所工作。
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
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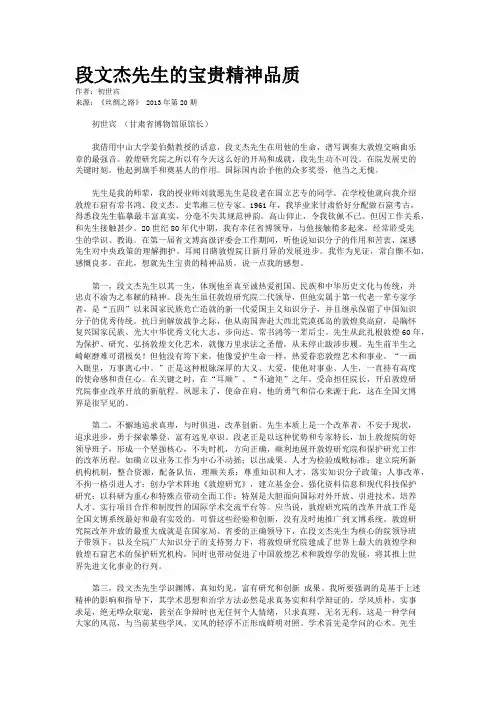
段文杰先生的宝贵精神品质作者:初世宾来源:《丝绸之路》 2013年第20期初世宾(甘肃省博物馆原馆长)我借用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的话意,段文杰先生在用他的生命,谱写调奏大敦煌交响曲乐章的最强音。
敦煌研究院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好的开局和成就,段先生功不可没。
在院发展史的关键时刻,他起到旗手和奠基人的作用。
国际国内给予他的众多奖誉,他当之无愧。
先生是我的师辈,我的授业师刘敦愿先生是段老在国立艺专的同学。
在学校他就向我介绍敦煌石窟有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三位专家。
1961年,我毕业来甘肃恰好分配做石窟考古,得悉段先生临摹最丰富真实,分毫不失其规范神韵。
高山仰止,令我钦佩不已。
但因工作关系,和先生接触甚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任省博领导,与他接触稍多起来,经常聆受先生的学识、教诲。
在第一届省文博高级评委会工作期间,听他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苦衷,深感先生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拥护。
耳闻目睹敦煌院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
我作为见证,常自惭不如,感慨良多。
在此,想就先生宝贵的精神品质,说一点我的感想。
第一,段文杰先生以其一生,体现他至真至诚热爱祖国、民族和中华历史文化与传统,并忠贞不渝为之奉献的精神。
段先生虽任敦煌研究院二代领导,但他实属于第一代老一辈专家学者,是“五四”以来国家民族危亡造就的新一代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并且继承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抗日到解放战争之际,他从南国奔赴大西北荒漠孤岛的敦煌莫高窟,是胸怀复兴国家民族、光大中华优秀文化大志,步向达、常书鸿等一辈后尘。
先生从此扎根敦煌60年,为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就像万里求法之圣僧,从未停止跋涉步履。
先生前半生之崎岖磨难可谓极矣!但他没有垮下来,他像爱护生命一样,热爱眷恋敦煌艺术和事业。
“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
”正是这种根脉深厚的大义、大爱,使他对事业、人生,一直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在关键之时,在“耳顺”、“不逾矩”之年,受命担任院长,开启敦煌研究院事业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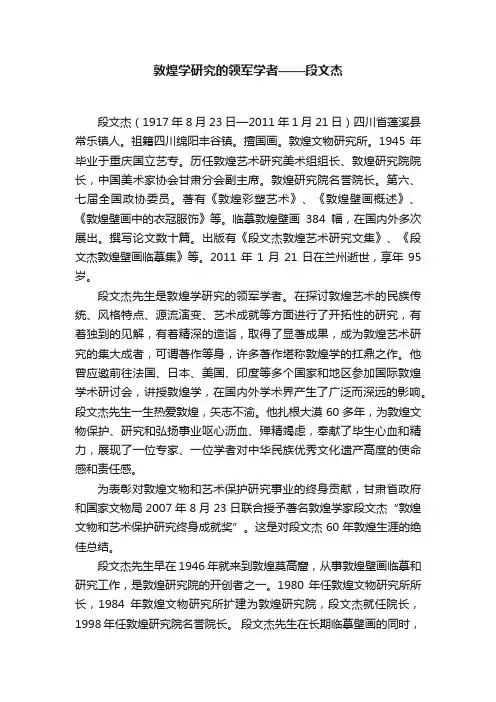
敦煌学研究的领军学者——段文杰段文杰(1917年8月23日—2011年1月21日)四川省蓬溪县常乐镇人。
祖籍四川绵阳丰谷镇。
擅国画。
敦煌文物研究所。
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
历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有《敦煌彩塑艺术》、《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
临摹敦煌壁画384幅,在国内外多次展出。
撰写论文数十篇。
出版有《段文杰敦煌艺术研究文集》、《段文杰敦煌壁画临摹集》等。
2011年1月21日在兰州逝世,享年95岁。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学研究的领军学者。
在探讨敦煌艺术的民族传统、风格特点、源流演变、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有着精深的造诣,取得了显著成果,成为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可谓著作等身,许多著作堪称敦煌学的扛鼎之作。
他曾应邀前往法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讲授敦煌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段文杰先生一生热爱敦煌,矢志不渝。
他扎根大漠60多年,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展现了一位专家、一位学者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表彰对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事业的终身贡献,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2007年8月23日联合授予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这是对段文杰60年敦煌生涯的绝佳总结。
段文杰先生早在1946年就来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研究工作,是敦煌研究院的开创者之一。
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就任院长,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段文杰先生在长期临摹壁画的同时,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对敦煌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书即为他的成果之一,对敦煌石窟艺术各时代的风格及艺术特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壁画中的服饰、飞天以及唐僧取经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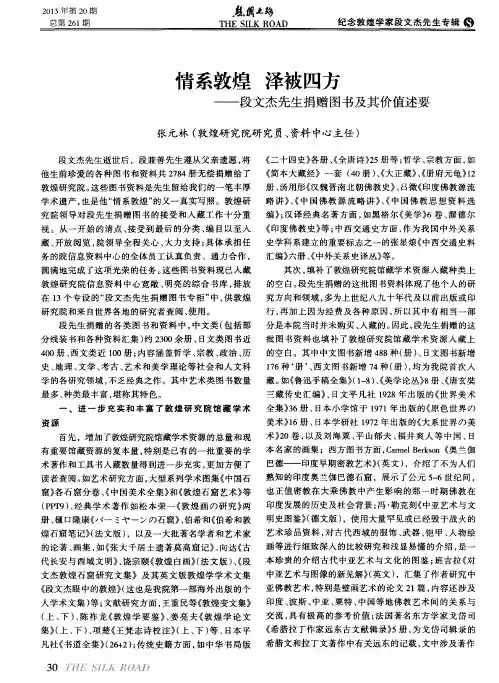
敦煌,五色轮回“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似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敦煌就注定是国内外艺术家们关注和向往的地方。
从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前辈艺术家一直到今天,敦煌艺术在几代画家的笔下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在这“佛”的大世界里,艺术家们六根裹在五彩云锦中,用百年的修行守护着莫高千年的“魂”。
——题记这几天在构思《走进敦煌》系列作品的时候,就有想写写那些百年守候莫高窟“信徒”们的冲动。
但真正下笔前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难以启齿的浅薄和不安,我越是接近,越是恐慌。
几日来,两次前往莫高窟和三危山,两次去常书鸿墓地拜谒,抚今追昔,用心灵去感悟,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却是痛苦和沉重的。
作为一个再次踏上敦煌这块土地的行者,我对敦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仅是我多次走进过莫高窟、走进过月牙泉,重要的是,我曾经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了七年。
从一个住客到一个行客,离开敦煌十年又再次回到敦煌。
我曾用一部分青春岁月,与敦煌这博大的精神世界相伴。
而当时那种理解和介入,敦煌的名胜古迹似乎就是一种以休闲为目的的游兴,彼时的我对敦煌丰富的宗教艺术,繁杂的历史演变,独处黄沙的落寞与繁华,超越千年的沉重与曼妙,只是惊叹并不真正了解。
离开的这十年,我用各种方式回忆敦煌,回忆所感知的一切,忽远忽近,忽近忽远,却怎么也具象不起来。
直到春节后的一天,一个偶然的缘分,我和我的先生结识了敦煌著名的青年画家李建英,直到走进他坐落在敦煌文化街一角的悬挂有著名敦煌学家、画家段文杰题写的“李建英画展”的画室,因为他的画,打开了我一直延展不开的心绪,我有想写一下的冲动。
刚一踏进李建英的画室,一种古朴、厚重而绚丽的气息立刻迎面扑来。
在这“佛”的世界里,我恍惚进入了莫高窟洞窟。
那一幅幅长约数米的巨型佛像、千姿百态的飞天、神情凝重的西域人物等等,使整个画室弥漫着浓浓的艺术气息。
130多平米的画室内,把它比成一个小小的莫高洞窟一点不为过。
我仿佛漫游了天堂、净土,漫游了古代世界、漫游了神话世界。
作者: 樊锦诗
作者机构: 敦煌研究院,甘肃敦煌736200
出版物刊名: 敦煌研究
页码: 1-3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3期
主题词: 敦煌研究院;事业;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研究》;敦煌学研究;世界范围;身体不适;采访记录
摘要:2011年1月,著名敦煌学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因病逝世。
段文杰先生于1917年出生于四川锦阳,1946年到敦煌开始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和研究工作,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研究》期刊的创办者并长期担任《敦煌研究》主编,为提高期刊水平,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缅怀段文杰先生,本刊开辟专栏,邀请段文杰先生当年的同事、故友及相关学者发表笔谈,以纪念这位敦煌学专家。
其中部分学者因年事已高或身体不适,我们采取了谈话记录的方式。
孙儒们、李其琼、关友惠、贺世哲、施萍婷先生的谈话,均由赵声良根据采访记录整理成文。
其中贺世哲先生在与编者谈话后不久,也于3月初不幸逝世,在此,亦谨向贺世哲先生表示深切的悼念。
情系敦煌泽被四方——段文杰先生捐赠图书及其价值述要作者:张元林来源:《丝绸之路》 2013年第20期张元林(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资料中心主任)段文杰先生逝世后,段兼善先生遵从父亲遗愿,将他生前珍爱的各种图书和资料共2784册无偿捐赠给了敦煌研究院。
这些图书资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学术遗产,也是他“情系敦煌”的又一真实写照。
敦煌研究院领导对段先生捐赠图书的接受和入藏工作十分重视。
从一开始的清点、接受到最后的分类、编目以至入藏、开放阅览,院领导全程关心、大力支持;具体承担任务的院信息资料中心的全体员工认真负责、通力合作,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这些图书资料现已入藏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宽敞、明亮的综合书库,排放在13个专设的“段文杰先生捐赠图书专柜”中,供敦煌研究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查阅、使用。
段先生捐赠的各类图书和资料中,中文类(包括部分线装书和各种资料汇集)约2300余册、日文类图书近400册、西文类近100册;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历史、地理、文学、考古、艺术和美学理论等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各研究领域,不乏经典之作。
其中艺术类图书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堪称其特色。
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敦煌研究院馆藏学术资源首先,增加了敦煌研究院馆藏学术资源的总量和现有重要馆藏资源的复本量,特别是已有的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入藏数量得到进一步充实,更加方便了读者查阅。
如艺术研究方面,大型系列学术图集《中国石窟》各石窟分卷、《中国美术全集》和《敦煌石窟艺术》等(PPT9)、经典学术著作如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两册、樋口隆康《バーミヤーンの石窟》、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文版),以及一大批著名学者和艺术家的论著、画集,如《张大千居士遗著莫高窟记》、向达《古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饶宗颐《敦煌白画》(法文版)、《段文杰敦煌石窟研究文集》及其英文版敦煌学学术文集《段文杰眼中的敦煌》(这也是我院第一部海外出版的个人学术文集)等;文献研究方面,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上、下)、陈祚龙《敦煌学要鉴》、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上、下)、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下)等、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26+2);传统史籍方面,如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各册、《全唐诗》25册等;哲学、宗教方面,如《简本大藏经》一套(40册)、《大正藏》、《册府元龟》12册、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吕徵《印度佛教源流略讲》、《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汉译经典名著方面,如黑格尔《美学》6卷、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等;中西交通史方面,作为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系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中外关系史译丛》等。
段文杰先生与敦煌学学术史研究r——以段文杰致王子云、何
正璜信为中心
刘进宝
【期刊名称】《敦煌研究》
【年(卷),期】2017(000)006
【摘要】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开创了"段文杰时代".作为敦煌艺术研究者,他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段文杰不仅为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呐喊呼吁,而且还特别注重敦煌研究院院史和敦煌学学术史的编写,并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本文转录了新公布的6封段文杰给王子云、何正璜夫妇的信件,从中看到段先生对院史和学术史编写的构想和计划,请求王子云夫妇将《莫高窟全图》赠送研究院,并写文章表彰王子云于20世纪40年代初率团考察敦煌、临摹壁画、进行敦煌艺展的功绩和贡献.
【总页数】8页(P21-28)
【作者】刘进宝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系, 浙江杭州 31002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0.6
【相关文献】
1.敦煌学专家段文杰先生 [J], 夏冬
2.美术大家风范敦煌学界丰碑r——我心目中的段文杰先生 [J], 史晓明;WANG
Pingxian
3.段文杰先生对北石窟寺文物的断代r——从张鲁章先生笔记中整理 [J], 吴正科;WANG Pingxian
4.情注敦煌六十载——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事迹简介 [J], 马玉蕻
5.中国敦煌古代艺术及科技博览会在台北展出段文杰等赴台北参加海峡两岸敦煌学术讨论会 [J], 马木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作者: 段文杰
出版物刊名: 敦煌研究
页码: 1-6页
主题词: 敦煌研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敦煌石窟;敦煌学研究;石窟艺术;常书鸿;敦煌壁画;敦煌莫高窟;敦煌文化
摘要: 敦煌研究院五十年段文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莫高窟则是一颗灿烂的艺术明珠,保存着四世纪至十四世纪千年间的建筑、彩塑和壁画,加上藏经洞出土的四五万件文献,它是我国中古时代最大又最集中的文化遗存,不仅是我国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敦...。
敦煌研究院史上的“段文杰时代”作者:刘进宝来源:《丝绸之路》 2013年第20期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段文杰对敦煌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敦煌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索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在敦煌壁画临摹方面不仅个人成就卓著,而且开始了科学总结,为创建临摹学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近70年历史中,共有三位领导人,即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在全国的科研院所中是绝无仅有的。
也为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以一个个案探讨学术机构的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1980年,中共甘肃省委对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调整,调整和加强了领班子。
在这次调整中,段文杰被任命为第一副所长,并实际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
从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到1998年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18年中,既是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的18年,也是敦煌研究院学术进步、走向世界、机构建设的黄金时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其称为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时代”。
“段文杰时代”是敦煌研究院各项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都与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就是段文杰先生亲自筹划并领导实施的。
第一,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第二,创办《敦煌研究》;第三,创建敦煌研究院;第四,延揽及大力培养人才;第五,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第六,创建年国敦煌石窟葆护研究基金会;第七,为敦煌研究走向世界而努力。
以上各项工作都是在段文杰先生的领导下实施的,有些就是段先生具体操作完成的。
而且许多都是开创性的,为敦煌学的繁荣及走向世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段文杰先生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或者是什么成就了段文杰,创造了一个“段文杰时代”?人的一生可能遇不到机遇,或者遇到机遇而抓不住机遇。
既能遇到机遇又能抓住机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是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
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段文杰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历史创造了段文杰,而不是其他人,自然有其各方面的因素,或者说是段文杰本人创造了自己。
我个人认为,是以下因素创造了段文杰: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自尊心。
爱国主义是段文杰那代人心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当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时,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笼罩中国大地的时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向科学进军”,“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是当时国人的共同心愿。
据段文杰自述,他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总是在我头脑中萦绕,这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迈开大步向前发展。
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书各科项目的研究完全停止。
而香港、台湾的敦煌学者和日本、法国的学者在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
此外,俄、美、英等国也都有一定的敦煌学著述问世。
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是十多年的空白。
无怪乎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
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
但是,扼腕叹息无济于事。
我们只有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
他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前言》中说,当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冷风,说甚么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却在外国。
每一个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对此,心情确实是不平静的,特别是长期在敦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更是憋着一股‘劲儿’”。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召下,“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十年规划中提出了组织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其目的就是“比较全面地展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成就、新水平”。
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的编辑出版“不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开创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会使敦煌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同时也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敦煌学的繁荣”。
1980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也是“坚持敦煌工作十几年和数十年的研究人员,怀着对文物事业的责任性和扭转敦煌文物研究在国际上处于落后地位的革命热情,重整旗鼓,埋头苦干”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第二,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
在敦煌研究院近70年的风风雨雨中,肯定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尤其是经历过“反右”、“文革”,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恩恩怨怨也属正常。
但如何处理、化解这些矛盾,则需要一定的领导艺术,尤其是要有一颗宽阔善良的心。
据段文杰自述,1980年“我担任第一副所长后,过去在历次运动中积极参与批斗我的一些人有些紧张,担心我搞报复”。
而段文杰先生“不是一个纠缠个人恩怨的人”,或者说将个人恩怨“抛在脑后”的人。
他“认为有些人在运动中参与整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是迫于某些人的压力,无可奈何的行为,很多人也不是出白本意,不应过多计较。
不能把政治运动中的恩恩怨怨埋在心里,变成下一次人与人斗争的种子,决不能把这种错误的斗争延续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
敦煌研究院关友惠先生说:“实际上段先生与常先生在学术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在50年代到70年代末,段先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所里的业务工作实际上是由段先生主持的,虽然经过多次冲击,段先生却一直认真地工作,他经常说的一句话说是‘内心无私天地宽’。
他从不背后议论人,虽然与常有些个人恩怨,他从不议论。
这是难能可贵的。
”“内心无私天地宽”,“从不背后议论人”,正是段文杰先生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人心自有公道,人心自有公理。
也正是由于段先生高尚人格的感召和以身作则的榜样,“才化解矛盾,促进团结,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和保护工作上来”,并尽力发挥老中年研究人员的作用,开创了敦煌研究的新局面。
第三,高尚的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
段先生能得到省委的重用和“敦煌人”的尊敬,还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密切相关。
如1980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就是在段先生主持下编辑出版的,段先生也为《文集》撰写了“前言”。
但本书署名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而不是“段文杰主编”。
随后的《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及以后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等也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看看敦煌研究院编辑的各类出版物,基本上没有个人署名的,就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也都是集体署名。
这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学人反思和学习。
另据贺世哲先生回忆,段文杰“把研究院的很多年轻人送到国外进修学习,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
他的儿子也是搞艺术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利用敦煌研究院与日本的这种关系,为他的儿子谋过利益。
对比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什么‘官二代’、‘富二代’之类,像段先生这样清廉的领导实在是很少的。
这在我们院里也可以说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现在院领导也都非常清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正是由于段先生的以身作则和高尚情操,为敦煌研究院和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我曾在《“敦煌人”和敦煌石窟》中说,随着老一代“敦煌人”的离世退休,“不仅仅使我们失去了学术上的老师,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使我们在做人、做事方面缺少了楷模”。
希望段先生的精神永存,为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保存一点点人性的纯真。
2004年,敦煌研究院举行会议,纪念常书鸿先生百年诞辰;2007年,煌研究院举行了“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座谈会”;现在,我们又在这里缅怀段文杰先生,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敦煌研究院的现任领导不忘历史、尊重前辈的创业成就,本身就值得我们尊敬和赞赏。
段文杰选择了敦煌,敦煌成就了段文杰。
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像段文杰这样在本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型知识分子,更需要像段文杰这样热切地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义无反顾地为敦煌事业无私奉献的公共知识分子。
傅国涌先生曾说:“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科研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许多许多,但在浮躁的社会中,我们却变得更实际、更实在、更实惠了,常常被各种利益所诱惑,而缺少的则是事业性、责任性和敬业精神,尤其是对事业的执着。
实际上,历史是很公正的,在变幻不定的现世评判标准之外,在人类的文明史当中,始终有不变的确定的尺度。
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像段文杰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历史会记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我们的社会,就需要像段文杰这样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会为拥有他们而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