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戏仿
- 格式:doc
- 大小:66.00 KB
- 文档页数: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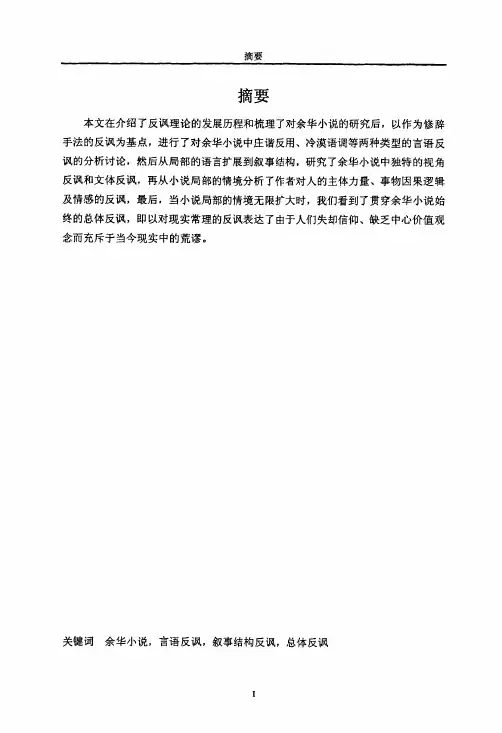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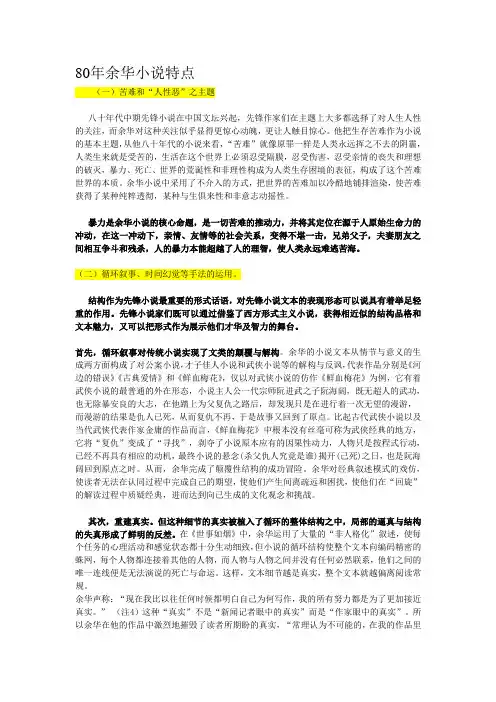
80年余华小说特点(一)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
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
暴力是余华小说的核心命题,是一切苦难的推动力,并将其定位在源于人原始生命力的冲动,在这一冲动下,亲情、友情等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堪一击,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相互争斗和残杀,人的暴力本能超越了人的理智,使人类永远难逃苦海。
(二)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
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首先,循环叙事对传统小说实现了文类的颠覆与解构。
余华的小说文本从情节与意义的生成两方面构成了对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的解构与反讽,代表作品分别是《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仅以对武侠小说的仿作《鲜血梅花》为例,它有着武侠小说的最普通的外在形态,小说主人公一代宗师阮进武之子阮海阔,既无超人的武功,也无除暴安良的大志,在他踏上为父复仇之路后,却发现只是在进行着一次无望的漫游,而漫游的结果是仇人已死,从而复仇不再,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原点。
比起古代武侠小说以及当代武侠代表作家金庸的作品而言,《鲜血梅花》中根本没有丝毫可称为武侠经典的地方,它将“复仇”变成了“寻找”,剥夺了小说原本应有的因果性动力,人物只是按程式行动,已经不再具有相应的动机,最终小说的悬念(杀父仇人究竟是谁)揭开(己死)之日,也是阮海阔回到原点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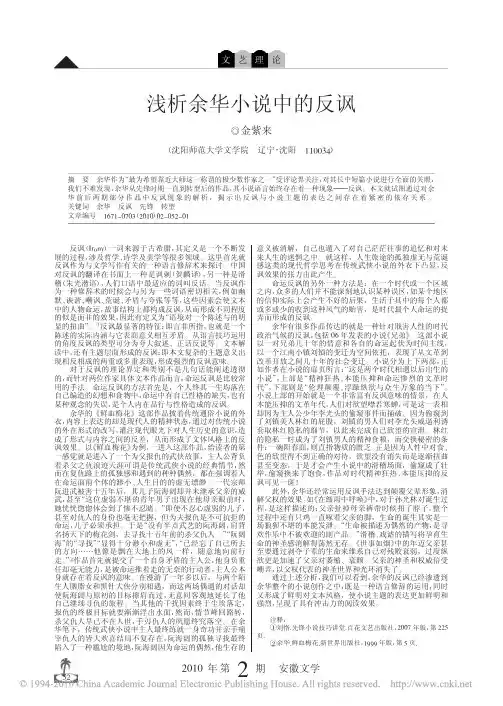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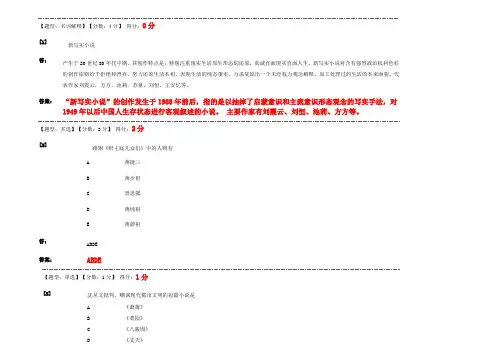
【题型:名词解释】【分数:4分】得分:0分[1]新写实小说答: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创作特点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新写实小说对含有强烈政治权利色彩的创作原则给予拒绝和背弃,努力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生活的纯态事实。
力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
代表作家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刘恒,王安忆等。
答案:“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发生于1988年前后,指的是以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人生存状态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
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
【题型:多选】【分数:2分】得分:2分[2]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人物有A 蒋捷三B 蒋少祖C 曾思懿D 蒋纯祖E 蒋蔚祖答:ABDE答案:ABDE【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3] 沈从文批判、嘲讽现代都市文明的短篇小说是A 《萧萧》B 《菜园》C 《八骏图》D 《丈夫》答:C答案: C【题型:简答】【分数:8分】得分:6分[4]闻一多诗歌理论中的“三美”指的是什么?答:“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绘画美”强调辞藻的选择要浓烈鲜明,有色彩感;每一句诗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存在的画面。
“建筑美”强调游街的匀称,有句的均齐。
答案: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诗歌“三美”主张,即音乐的美(音节和韵脚的和谐),绘画的美(辞藻富有色彩)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题型:论述】【分数:13分】得分:0分[5] 结合《雷雨》作品实际,分析蘩漪的思想性格及其意义。
答:答案:出身名门|意识觉醒|痛苦|忍受|性格扭曲|乖戾阴郁|报复|畸形爱情|最残酷的爱|最不忍的恨【题型:名词解释】【分数:4分】得分:0分[6]京派答:20世纪30年代,在京津一带的作家《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表作品和批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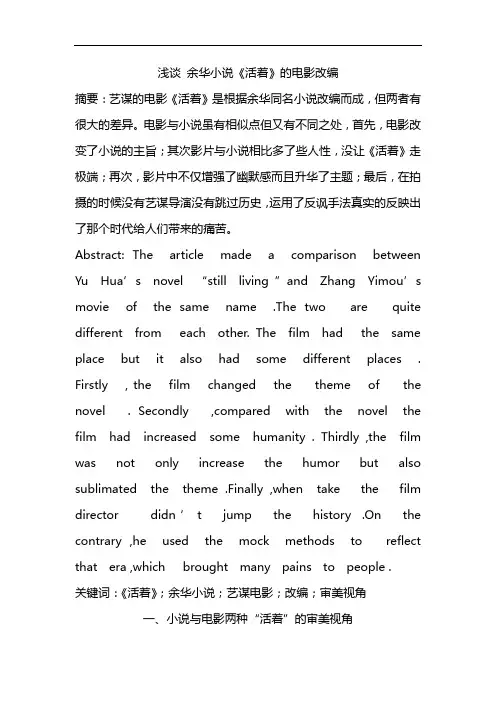
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艺谋的电影《活着》是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但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电影与小说虽有相似点但又有不同之处,首先,电影改变了小说的主旨;其次影片与小说相比多了些人性,没让《活着》走极端;再次,影片中不仅增强了幽默感而且升华了主题;最后,在拍摄的时候没有艺谋导演没有跳过历史,运用了反讽手法真实的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Abstract: The article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Yu Hua’s novel “still living ”and Zhang Yimou’s movie of the same name .The two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film had the same place but it also had some different places . Firstly , the film chang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novel the film had increased some humanity . Thirdly ,the film was not only increase the humor but also sublimated the theme .Finally ,when take the film director didn’t jump the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he used the mock methods to reflect that era ,which brought many pains to people .关键词:《活着》;余华小说;艺谋电影;改编;审美视角一、小说与电影两种“活着”的审美视角艺谋导演改编余华小说《活着》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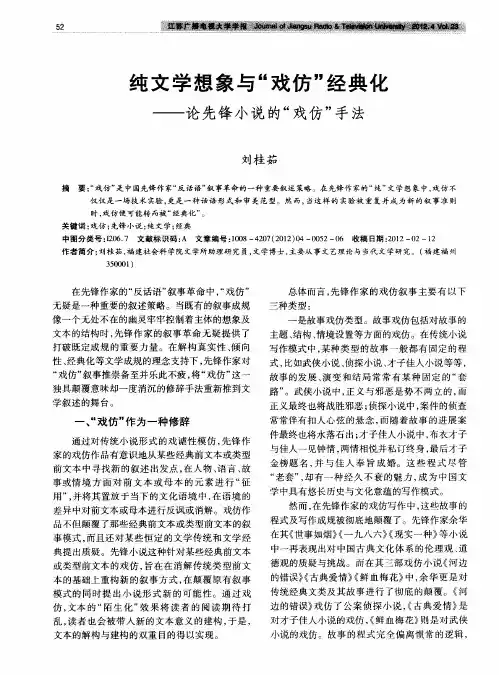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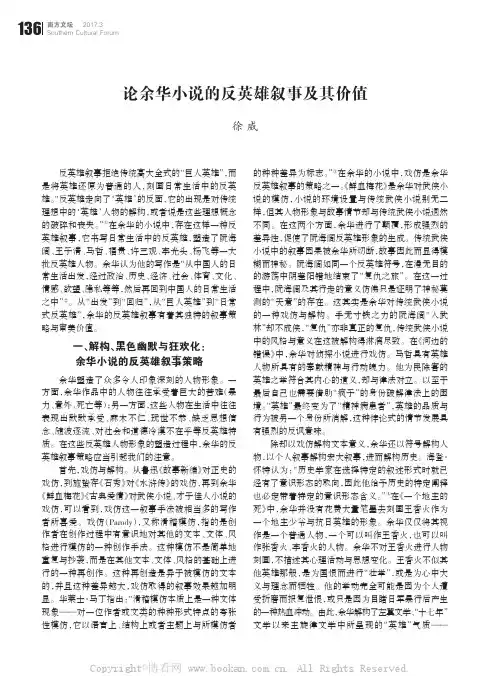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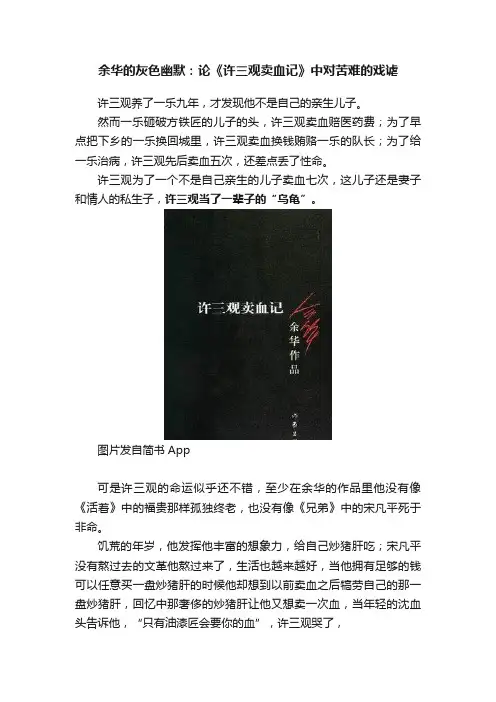
余华的灰色幽默:论《许三观卖血记》中对苦难的戏谑许三观养了一乐九年,才发现他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然而一乐砸破方铁匠的儿子的头,许三观卖血赔医药费;为了早点把下乡的一乐换回城里,许三观卖血换钱贿赂一乐的队长;为了给一乐治病,许三观先后卖血五次,还差点丢了性命。
许三观为了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卖血七次,这儿子还是妻子和情人的私生子,许三观当了一辈子的“乌龟”。
图片发自简书App可是许三观的命运似乎还不错,至少在余华的作品里他没有像《活着》中的福贵那样孤独终老,也没有像《兄弟》中的宋凡平死于非命。
饥荒的年岁,他发挥他丰富的想象力,给自己炒猪肝吃;宋凡平没有熬过去的文革他熬过来了,生活也越来越好,当他拥有足够的钱可以任意买一盘炒猪肝的时候他却想到以前卖血之后犒劳自己的那一盘炒猪肝,回忆中那奢侈的炒猪肝让他又想卖一次血,当年轻的沈血头告诉他,“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许三观哭了,他说“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
”许三观一生追求平等,到头来却发现连自己身上的屌毛和眉毛都不平等。
于是他用插科打诨和调侃揶揄的话语“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表达对生活的无奈。
在作品中许三观只是一名普通的小市民,他花了八角三分钱请许玉兰吃东西,就要求许玉兰要嫁给他;他知道许玉兰给他戴绿帽子后,用不干活要享受来惩罚许玉;当他自己也出轨的时候,他又主动认错;知道情敌何小勇被车撞了以后,他很开心,逢人便说……许三观是当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所有的这些都是弱势群体所追求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却是荒诞虚妄的。
世界是荒诞的,存在是一种苦难。
经过了二战和文革的灾难,作家们开始对世界和人生、人存在的价值产生思考,关注人的命运。
余华在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中谈到自己受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先锋余华的作品中贯穿着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并且具有某种荒诞性。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揭示了人生存之难,存在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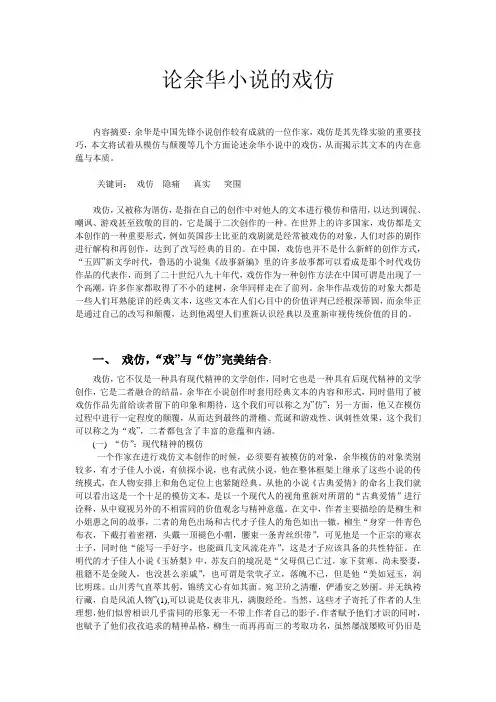
论余华小说的戏仿内容摘要:余华是中国先锋小说创作较有成就的一位作家,戏仿是其先锋实验的重要技巧,本文将试着从模仿与颠覆等几个方面论述余华小说中的戏仿,从而揭示其文本的内在意蕴与本质。
关键词:戏仿隐痛真实突围戏仿,又被称为谐仿,是指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他人的文本进行模仿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它是属于二次创作的一种。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戏仿都是文本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经常被戏仿的对象,人们对莎的剧作进行解构和再创作,达到了改写经典的目的。
在中国,戏仿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作方式,“五四”新文学时代,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里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戏仿作品的代表作,而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戏仿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国可谓是出现了一个高潮,许多作家都取得了不小的建树,余华同样走在了前列。
余华作品戏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这些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评判已经根深蒂固,而余华正是通过自己的改写和颠覆,达到他渴望人们重新认识经典以及重新审视传统价值的目的。
一、戏仿,“戏”与“仿”完美结合:戏仿,它不仅是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同时它也是一种具有后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它是二者融合的结晶。
余华在小说创作时套用经典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借用了被戏仿作品先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和期待,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仿”;另一方面,他又在模仿过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颠覆,从而达到最终的滑稽、荒诞和游戏性、讽刺性效果,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戏”,二者都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
(一) “仿”:现代精神的模仿一个作家在进行戏仿文本创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被模仿的对象,余华模仿的对象类别较多,有才子佳人小说,有侦探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他在整体框架上继承了这些小说的传统模式,在人物安排上和角色定位上也紧随经典。
从他的小说《古典爱情》的命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足的模仿文本,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对所谓的“古典爱情”进行诠释,从中窥视另外的不相雷同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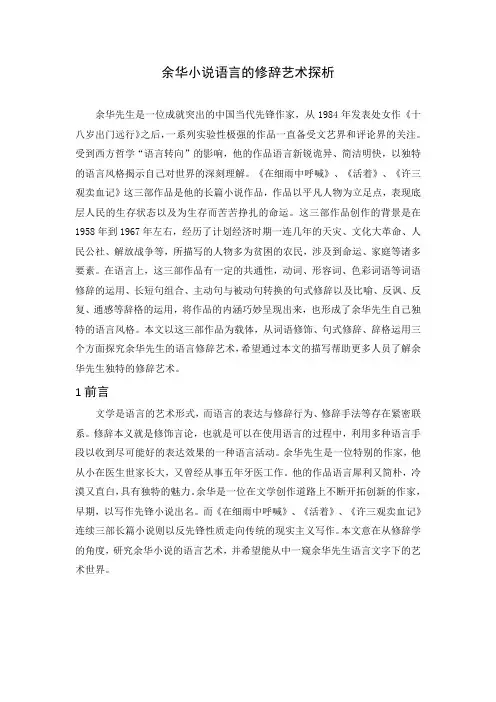
余华小说语言的修辞艺术探析余华先生是一位成就突出的中国当代先锋作家,从1984年发表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一系列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一直备受文艺界和评论界的关注。
受到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影响,他的作品语言新锐诡异、简洁明快,以独特的语言风格揭示自己对世界的深刻理解。
《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作品,作品以平凡人物为立足点,表现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命运。
这三部作品创作的背景是在1958年到1967年左右,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一连几年的天灾、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解放战争等,所描写的人物多为贫困的农民,涉及到命运、家庭等诸多要素。
在语言上,这三部作品有一定的共通性,动词、形容词、色彩词语等词语修辞的运用、长短句组合、主动句与被动句转换的句式修辞以及比喻、反讽、反复、通感等辞格的运用,将作品的内涵巧妙呈现出来,也形成了余华先生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本文以这三部作品为载体,从词语修饰、句式修辞、辞格运用三个方面探究余华先生的语言修辞艺术,希望通过本文的描写帮助更多人员了解余华先生独特的修辞艺术。
1前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形式,而语言的表达与修辞行为、修辞手法等存在紧密联系。
修辞本义就是修饰言论,也就是可以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
余华先生是一位特别的作家,他从小在医生世家长大,又曾经从事五年牙医工作。
他的作品语言犀利又简朴,冷漠又直白,具有独特的魅力。
余华是一位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的作家,早期,以写作先锋小说出名。
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连续三部长篇小说则以反先锋性质走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
本文意在从修辞学的角度,研究余华小说的语言艺术,并希望能从中一窥余华先生语言文字下的艺术世界。
2余华小说的词语修辞2.1动词的选用在阅读余华的小说的时,我们常常会对其小说的语言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汉民族语言历经几千年发展历程所积淀下来的那些相对稳定的文化信息和形象特征在此被一一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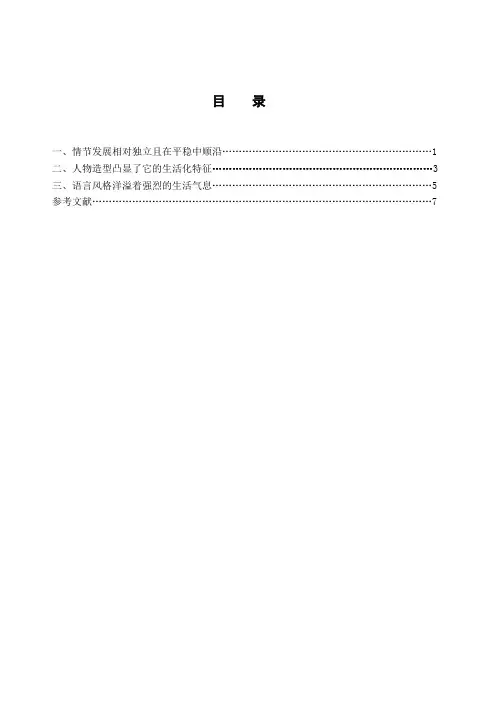
目录一、情节发展相对独立且在平稳中顺沿 (1)二、人物造型凸显了它的生活化特征 (3)三、语言风格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 (5)参考文献 (7)试论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艺术特色[提要]: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以其质朴的笔调抒写了一群普通人的生活历程。
它以它独特的戏谑和悲悯展示着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无论在情节运用、人物表达、语言运用上,朴素构成了全文的基调。
而余华的成功在于:它在这种看似平白的表达再现了一群普通人纯生活化而又洋溢着浓烈的人性美展示的人物生活历程,这不得不得益于余华在整部小说中独具个性的情感把握和情景展开,它是余华作品本色生活观和写作风格的体现。
[关键词]:《许三观卖血记》质朴人物表达人性美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以平实的笔调抒写了一群普通人的生活历程。
小说没有突兀的情节设置,也没有华丽的文辞运用,以纯生活化的笔调描摹纯生活化的人物,但自始自终洋溢了它对生活最深刻和最浓烈的体验,这不得不得益于余华在整部小说中独具个性的情感把握和情景展开,他是余华作品本色生活观和写作风格的体现。
以下本文将以《许三观卖血记》为切入点,试图从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解析余华小说的内在特点。
一、情节发展相对独立且在平稳中顺沿。
《许三观卖血记》没有贯穿全文的矛盾冲突,它以最平白的文字展示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它的情节发展始终是相对独立且在平稳中顺沿,这是《许》文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余华的成功则在于他把这种生活本象打造的平凡而又不失艺术魅力,在这朴实的外相下升腾起超越时空的人性“悲壮美”,构成他独特的行文风格。
《许三观卖血记》全文没有任何情节悬念的设置,它所展现的,是一种彻底的线性结构。
它所再现的,是最为普通的生活本象。
因而它的情节安排始终是平实的。
作者没有刻意去勾勒一条主线引导全文的发展,也没有试图艺术化的放大生活的某个截面来给人造成情感的突然跃升。
《许》文的情节自始自终都稳定在一个层面上,即使是由小矛盾引发的情节起伏也是自然而然地所达成。
小说论丛余华小说中的叙事空缺——以《河边的错误》为例⊙郝子靖[天津大学, 天津 300350] 摘 要:《河边的错误》是余华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其中运用了大量叙事的空缺,使推理出真凶的逻辑链发生断裂,从而造成了某种意义上作案凶手、作案手法和作案动机的空缺。
叙事的空缺丰富了小说的主题内涵,提升了故事情节的荒诞性。
小说运用了视角的切换、人物的模糊化处理以及象征等艺术手法,这些艺术手法和空缺相辅相成。
除了先锋小说外,研究其他小说中的空缺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河边的错误》 空缺 主题内涵 艺术手法传统的小说叙事是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的,它具有一种“历史的完整性”,而后现代主义小说“力图消除历史的起源性或历史的连续统一性”a。
也就是说,它打破了小说中事件的因果关系,故意空出来逻辑链中的一环,使小说变得非连续性,从而也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变得多解性。
余华作为先锋派的代表,在很多小说中同样运用了空缺叙事这一叙述策略,《河边的错误》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部作品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它空有一个侦探小说的架子,实际上并不是严格的侦探小说。
传统的侦探小说主要强调对作案凶手、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法的推理,“一切都须以一种理性的方法来解释”, 而且“必须遵循连续的同一性”b,强调证据的充足和严密的逻辑推理。
而在《河边的错误》中,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推理,使得逻辑链上出现了漏洞,从而导致在凶手、动机和手法这三个要素上出现了疑点;同时,小说在人物和背景等交代上产生了空缺,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从而增添了小说的荒诞性和主题的不确定性。
一、 空缺的内容(一)证据在证据方面,首先是证物的空缺。
凶器是一把柴刀,而么四婆婆遇害前一个月也遗失了一把柴刀,所以“凶手很有可能就是用的这把柴刀”c。
而后来,警察搜查了疯子的房间,找到了这把柴刀,“上面沾满血迹。
经过化验,柴刀上的血迹与么四婆婆的血型一致”d。
而在第二起命案中,也同样在疯子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沾有血迹的柴刀。
戏仿与《鲜血梅花》的形式特征与意义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中,余华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写作手法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是一位耀眼的文学明星。
他于198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鲜血梅花》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戏仿。
通过戏仿这种艺术形式所造成的荒诞讽刺效果,余华对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典型英雄人物形象和故事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消解。
本文从分析《鲜血梅花》在人物、叙事等角度戏仿的使用,表现出余华对武侠小说程式化叙事的否定和反思,进而探讨该小说颠覆传统武侠小说叙事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余华、鲜血梅花、讽刺性模仿、艺术形式Abstract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riters, Yu Hua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with their own unique artistic writing style, is a dazzling literary star. In 1989 he created the short story "Blood Plum" is a parody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By absurd parody satire effect caused by this form of art, Yu Hua typical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hero characters and the story mode a bold diges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blood plum" in character, narrative perspectives parody of use, showing stylized narrative novels Yu Hua denial and reflection, then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novels subvert narrative. Keywords: Yu Hua, blood plum, parody, art forms引言在中国的许多作家中,余华无疑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迥然异常,被公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极具实力与个性和创作力的作家。
余华情节“戏仿”的颠覆与消解作者:李缙英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20期摘 ;要:余华在先锋时期创作了一些才子佳人、侦探—推理、武侠小说的模仿之作,这种文类颠覆的创作方法叫做“戏仿”,体现了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观念对余华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文艺、哲学观念入手把握余华戏仿作品叙事上的深层涵义。
关键词:余华;戏仿;小说情节;哲学;解构[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20-0-02一、情节与情节模式韦勒克和沃伦将“情节”界定为戏剧、故事和小说的叙事性结构,高尔基认为情节是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与构成历史[1]P244,而徐岱对“情节”的概括则更全面:就是对于人的行为的有目的地加以使用,其功能是对生活的原生形态中的那些相对的混乱与无序作出挑战,通过某种因果关系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
[2]P246那么情节模式就可以说是某种小说文类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发展成熟并稳定下来的、固定了的故事情节。
本文以余华的三部作品,研究其对才子佳人、武侠和侦探—推理小说情节模式戏仿的意义。
二、传统情节模式的“戏仿”“戏仿”是指在创作中对其他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甚至致敬目的的文学再创造。
在文学创作中,利用谐音、象征、隐喻、情节颠覆等方式,使再创造的作品兼有模仿加反讽的意味。
在中国先锋文学创作中有许多戏仿之作,余华的“文类颠覆”之作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一)对才子佳人小说情节的戏仿对于才子佳人小说,鲁迅说:“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
”有人认为它形成了三个基本情节组成的模式:一见钟情、拨乱离散、终得团圆。
[3]《古典爱情》就是从中汲取灵感并对其颠覆的佳作,余华将其冠之以唯美古典之名,将内容分为类似的三部分:第一才子佳人花园邂逅;第二书生落榜情人离散、荒年离散、赎身收尸;第三再续前缘、缘尽人散。
作者对情节的戏仿主要在第二、三部分。
摘要: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余华,其作品的先锋性之一可以说是“叙事革命”:一是重复循环手法的运用,二是叙事距离的转变。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以上两点,来探讨余华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叙事的,从而更好地理解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性。
关键词:余华;叙事;重复;循环;叙述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叙事的艺术。
以《十八岁出门远行》而跻身文坛的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在“叙事革命”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1.重复循环重复,在中外文学创作中,本是一种修辞手法,它通过重复某个词、短语或句子而使文章达到某种特殊效果。
在小说叙事中,重复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它主要是指多次讲述发生过一次的事或类似的事,包括事件重复和话语重复。
一般来说,重复难免显得罗嗦、唠叨,一般作家都把重复作为禁忌,少用或不用。
但重复作为叙事策略,曾被先锋小说家普遍采用,而其中余华在这方面取得突出而独特的成绩,这在余华90年代以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体现得较为典型。
下面就结合余华的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来分析这一叙事策略。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一个小城丝厂的送丝工人许三观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生。
小说中主人公许三观一生共卖了12次血,故事情节就是随着这12次卖血而徐徐展开的。
许三观的一生最主要的事件就是不断地卖血,重复地卖血就标志着他需要不断地克服生活的苦难。
许三观的生活显然是一种简单的生活,重复的生活,不断失血的生活。
也正是这种曲折的卖血经历,表现出了普通民众的爱与恨、善与恶;表现了普通人身上具有的人类的优秀品质:牺牲、奉献、无私、忍耐……在这种“重复卖血”中,隐含着丰富深刻的“重复性经验”,从而使作品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曲线和回环激荡的主旋律,让人看后都不禁为许三观的一生而感到沉痛和心酸。
叙述许三观的12次卖血,这是对事件的重复。
除了事件的重复,还有话语的重复。
这一手段并非是将同一段话语原原本本地反复讲述,而是每一次重复讲述的角度、层次都有所不同,从而使一个事件的意义得到多层次、多方面的展示。
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及其价值反英雄叙事拒绝传统高大全式的“巨人英雄”,而是将英雄还原为普通的人,刻画日常生活中的反英雄。
“反英雄走向了‘英雄’的反面,它的出现是对传统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解构,或者说是这些理想概念的破碎和丧失。
”①在余华的小说中,存在这样一种反英雄叙事,它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反英雄,塑造了阮海阔、王子清、马哲、福贵、许三观、李光头、杨飞等一大批反英雄人物。
余华认为他的写作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②。
从“出发”到“回归”,从“巨人英雄”到“日常式反英雄”,余华的反英雄叙事有着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与审美价值。
一、解构、黑色幽默与狂欢化: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策略余华塑造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
一方面,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承受着巨大的苦难(暴力、意外、死亡等);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在生活中往往表现出默默承受、麻木不仁、玩世不恭、缺乏思想信念、随波逐流、对社会和道德冷漠不在乎等反英雄特质。
在这些反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余华的反英雄叙事策略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戏仿与解构。
从鲁迅《故事新编》对正史的戏仿,到施蛰存《石秀》对《水浒传》的戏仿,再到余华《鲜血梅花》《古典爱情》对武侠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戏仿,可以看到,戏仿这一叙事手法被相当多的写作者所喜爱。
戏仿(Parody),又称滑稽模仿,指的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其他的文本、文体、风格进行模仿的一种创作手法。
这种模仿不是简单地重复与抄袭,而是在其他文本、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再创作。
这种再创造是异于被模仿的文本的,并且这种差异越大,戏仿取得的叙事效果越加明显。
华莱士·马丁指出:“滑稽模仿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文类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性模仿,它以语言上、结构上或者主题上与所模仿者的种种差异为标志。
”③在余华的小说中,戏仿是余华反英雄叙事的策略之一。
论余华小说的戏仿内容摘要:余华是中国先锋小说创作较有成就的一位作家,戏仿是其先锋实验的重要技巧,本文将试着从模仿与颠覆等几个方面论述余华小说中的戏仿,从而揭示其文本的内在意蕴与本质。
关键词:戏仿隐痛真实突围戏仿,又被称为谐仿,是指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他人的文本进行模仿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它是属于二次创作的一种。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戏仿都是文本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经常被戏仿的对象,人们对莎的剧作进行解构和再创作,达到了改写经典的目的。
在中国,戏仿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作方式,“五四”新文学时代,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里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戏仿作品的代表作,而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戏仿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国可谓是出现了一个高潮,许多作家都取得了不小的建树,余华同样走在了前列。
余华作品戏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这些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评判已经根深蒂固,而余华正是通过自己的改写和颠覆,达到他渴望人们重新认识经典以及重新审视传统价值的目的。
一、戏仿,“戏”与“仿”完美结合:戏仿,它不仅是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同时它也是一种具有后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它是二者融合的结晶。
余华在小说创作时套用经典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借用了被戏仿作品先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和期待,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仿”;另一方面,他又在模仿过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颠覆,从而达到最终的滑稽、荒诞和游戏性、讽刺性效果,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戏”,二者都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
(一) “仿”:现代精神的模仿一个作家在进行戏仿文本创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被模仿的对象,余华模仿的对象类别较多,有才子佳人小说,有侦探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他在整体框架上继承了这些小说的传统模式,在人物安排上和角色定位上也紧随经典。
从他的小说《古典爱情》的命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足的模仿文本,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对所谓的“古典爱情”进行诠释,从中窥视另外的不相雷同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意蕴。
在文中,作者主要描绘的是柳生和小姐惠之间的故事,二者的角色出场和古代才子佳人的角色如出一辙,柳生“身穿一件青色布衣,下截打着密褶,头戴一顶褪色小帽,腰束一条青丝织带”,可见他是一个正宗的寒衣士子,同时他“能写一手好字,也能画几支风流花卉”,这是才子应该具备的共性特征。
在明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中,苏友白的境况是“父母俱已亡过,家下贫寒,尚未娶妻,祖籍不是金陵人,也没甚么亲戚”,也可谓是茕茕孑立,落魄不已,但是他“美如冠玉,润比明珠。
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
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
并无纨袴行藏,自是风流人物”(1),可以说是仪表非凡,满腹经纶。
当然,这些才子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他们似曾相识几乎雷同的形象无一不带上作者自己的影子。
作者赋予他们才识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孜孜追求的精神品格,柳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考取功名,虽然屡战屡败可仍旧是屡败屡战,《西厢记》中张生面对重重困难却知难而进,佳人还有幸福是他们奋斗和进取的不竭动力。
柳生和小姐惠的不期而遇,他们的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同时起到穿针引线牵线搭桥的丫鬟,这些与传统小说如出一辙的人物和情节,余华在小说中也并未遗漏。
在余华戏仿武侠小说的文本《鲜血梅花》中,阮海阔是一个为父复仇的形象,其实在大多数的武侠小说中,“复仇”是作家百写不厌的现象,子女为长辈复仇,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余华对传统的借鉴。
在这篇小说中,有青云道长有白雨潇有胭脂女,他们武功深不可测,我们从传统武侠小说中似乎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胭脂女是“天下第二毒王,满身涂满了剧毒的花粉,一旦花粉洋溢开来,一丈之内的人便中毒身亡”,简直就是一个半人半妖的形象,这与金庸小说中的李莫愁、梅超风等人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一个地主的死》中塑造了一对地主父子的形象,在《河边的错误》中塑造了马哲这个侦探的人物形象,所以说余华的戏仿小说在人物的塑造上和整体故事的结构安排上都秉承了传统小说的固有模式,它同样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将读者带入到传统阅读的心理体验上,也就是说,我们在浏览余华的文本时,会很自然的把他的《古典爱情》当做才子佳人小说,把《鲜血梅花》当做武侠小说,余华的“仿”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模仿,是“一种对个人意识的肯定和尊重,是能够体现出人类深刻的理解能力和丰富的阐释能力的创作形式”(2),通过模仿我们看到了戏仿者对自身丰富能力的阐释和表现,因为在这种表象模仿的背后隐藏的是作者最为深刻的颠覆意图。
(二)“戏”:后现代精神的颠覆颠覆是余华戏仿小说最根本的意义和内在的本质所在,他“剥掉了传统小说的种种神圣的外衣,彻底的改变了小说艺术形式“真实性”等种种观念,使小说艺术获得一次彻底的解放”(4)。
余华在对传统文本进行实验的时候,企图改变传统小说深层艺术形式的某些东西,对它们所依赖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做了后现代意义的解构和反叛,在他的小说中,读者可以体味到与传统截然相反的“真实”的文化价值。
余华的小说走的是以一条循序渐进的颠覆模式,当人物都具备时,故事的开始和发生都会在情理之中,随着时间推移和故事发展,读者犹如走进了他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完全背离了读者的内心期望。
在小说《古典爱情》中,柳生和小姐惠从相识相恋再到离别,让人感受到了传统小说中才子与佳人之间的浪漫与温情,但是随后的情节却出人意料,柳生归来时的物是人非,小姐沦为“菜人”的悲惨命运,人鬼殊途的无限伤感,无一不体现了余华的颠覆意图,最后小姐死而复生让人眼前一亮,可是作者依然让她消逝,余华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真正的爱情消失了,现实中美丽的爱情已经荡然无存了,惠的无理离去,是与爱情断裂的隐喻。
在古代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无一逃出大团圆的窠臼,“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理念正是儒家伦理思想对士人的直接影响,是无数读书人的人生目标。
《河边的错误》的前半部一直以推理的笔调来呈述案情侦查的过程,而故事的结局却令人惊奇:疯子杀人当然无动机可言,也难以受到法律的制裁,执法者以疯子的名义去杀疯子,也失去了谋杀的正常理由。
而目击者多次极巧合的出现在现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余华就是如此打破常规,砸碎了本来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
在这篇小说中,孩子的话每次都是真实的可没有人相信,根据经验推断自己是重要嫌疑犯的大人却心智失常而自杀,没有理性的疯子杀人不必负法律责任,有理性的刑警杀人不得不装疯,竟真的说话颠三倒四,进了精神病院。
这里法律变得苍白无力,理性更是无力和荒谬。
《一个地主的死》讲述的是一对地主父子的故事,在其中没有“黄世仁”那般凶狠残暴卑鄙无耻的地主,也没有“杨白劳”那样贫苦至极命运悲惨的农民,相反地主的儿子竟担负起将日本人引向死亡的责任,而一些百姓对日本人的残暴对同胞的痛苦遭遇却显得麻木不仁,这就在形象层面上完全颠覆了抗战题材的小说,在抗战小说中,地主阶级无一例外是打击的对象,是剥削农民的罪魁,是日本人的走狗,人民群众都是抗战的积极拥护者,而余华似乎要告诉我们,其实地主中也有爱国者,人民中也有投机者,这就背离了大众的传统观念,以达到他反叛的意图。
《鲜血梅花》这篇小说恰好是余华最为彻底的颠覆尝试。
“武侠小说再‘新’再‘变’,它也还是武侠小说。
它必须有‘武’又有‘侠’。
”“武”属于技术范畴,“侠”则是某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主人公阮海阔与我们习惯认同的杨过(《神雕侠侣》)等一般武侠小说中的的人物毫无相同:他既不武功盖世,又无高人相助,更谈不上行侠仗义,义薄云天。
杀父之仇本应是刻骨之恨,不共戴天的,但在他心中却燃不起对仇人的丝毫恨意。
他整个人像个习惯漂泊的影子,漫无方向,就算有了美好的志向也难以实现。
几乎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偶然的莫名其妙的冲动,他走上通往胭脂女的荒凉大道,同样莫名其妙的违背自己的意愿走近了黑针大侠,与他所要寻找的白雨潇相遇,却又阴错阳差般的错过了。
大雨冲垮了桥使他无法到达对岸,却因此找到了青云道长。
他完成了胭脂女和黑针大侠的嘱托,却失去了询问谁是杀父仇人的机会。
结局也无所谓目的的实现与否,他只是伤心地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
有复仇而没有仇恨,这使复仇本身毫无意义。
武侠小说中的必然与因果被消解得荡然无存了,“少侠”的形象也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因复仇而存在的符号。
作家戏仿经典的第一步就是要对经典中的人物改头换面,戏仿后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更接近生活的真实,这其实是另一种现实。
《古典爱情》中的柳生和小姐惠,《一个地主的死》中的那对地主父子,《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余华把这些形象从经典文本中剥离出来,赋予了他们新的更加接近生活真实的面孔,现实的本质被揭露无遗。
戏仿,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精神,它同样体现了作家对语言观念的反动。
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每一种文体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固定的模式,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按照某种程式去阅读理解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因此面对同一种文体总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案件发生———侦探介入———真相大白,这就是侦探小说的基本套路,再加上表达上的通俗性与情节的紧凑性,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河边的错误》中,余华完全打破了这个侦探小说的模式,用非理性的笔调来代替理性的叙述,传统被抛到九霄云外。
传统小说创作是以承认存在本身具有固定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为前提的,而叙述的逼真性又使得人们往往把文本中的自足系统等同于现实,所以传统小说中的形式仅仅成了内容的仆从,表现出对“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因而颠覆传统小说必须触及它的核心和要害———真实性(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
在余华等当代作家眼中,世界是荒诞的,“生活是不真实的”,现象不再是纵深的“本质”或“目的”的呈现形式,而只是它本身。
他们割裂了现实与文本的对应关系,叙述不再是为了追求“本质”而变得分外自由,是游戏性的,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也是随意性的,形式是无政府主义的。
作家怎样叙述,笔下就呈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判断这个世界的真与伪是没有意义的。
余华通过对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传统小说的戏仿,并不是为了展示人类世界中的理性和规律性,而是表现了偶然性、神秘性的发生;他的小说充满着的不是文明、规范,而是反文明、反规范的暴力、死亡等。
余华不仅是一位富于文化批判精神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不断创新、自我超越的作家,他关注着人类生存所必须面对的永恒苦难和窘境,通过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历史观进行颠覆,使我们反省现实处境,得以警醒。
二戏仿,内心的隐痛暴力和鲜血是余华先锋小说的共同主题,在他的戏仿小说中这两大主题依然存在。
在余华心中,“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的内心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3)余华认为暴力这种外在的形式事实上只是一种暴力欲望的释放,而真正促成暴力发生的,则是人们内心中那股蠢蠢欲动而又不可遏止的欲望,欲望这一在余华看来真实的甚至可以触摸的东西,无疑属于精神范畴,因此可以说暴力本身便是人类主题精神自我出场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