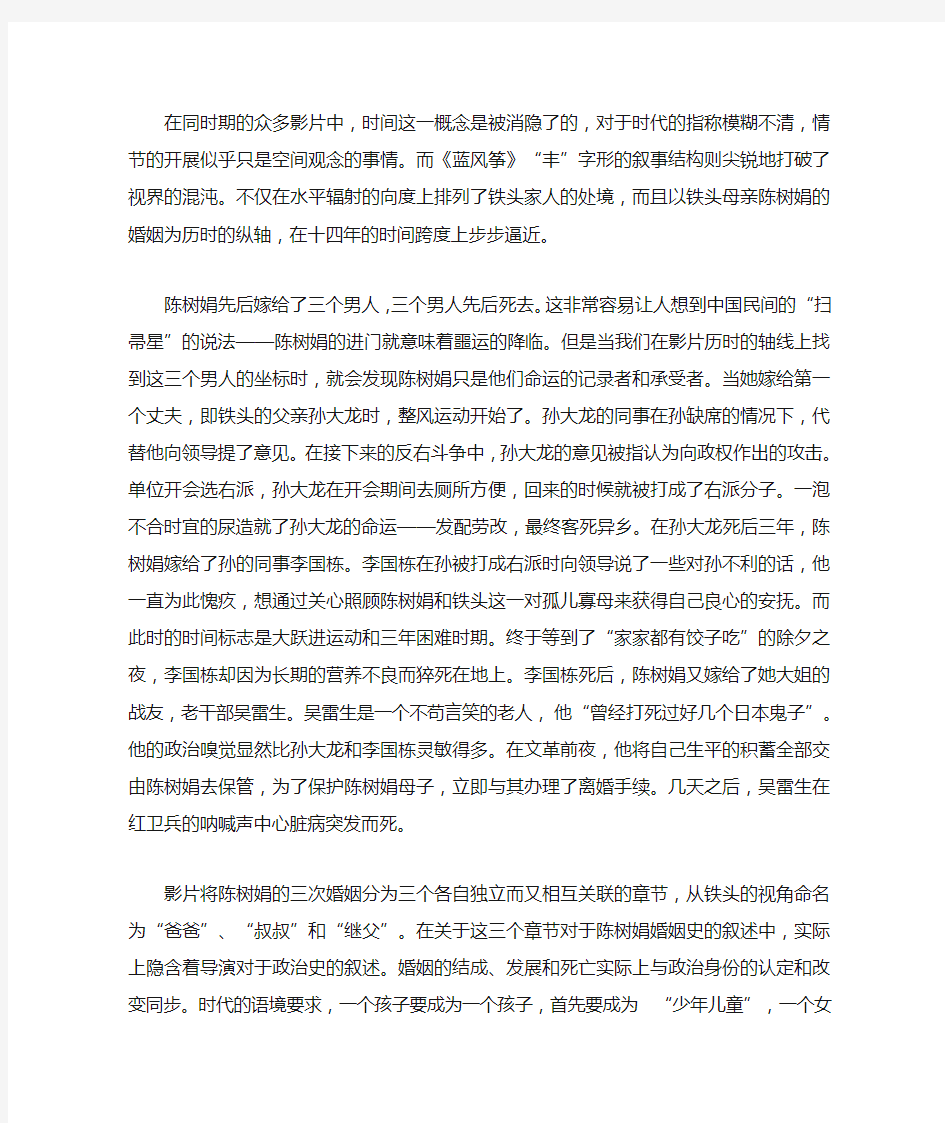
蓝风筝简介
- 格式:doc
- 大小:29.5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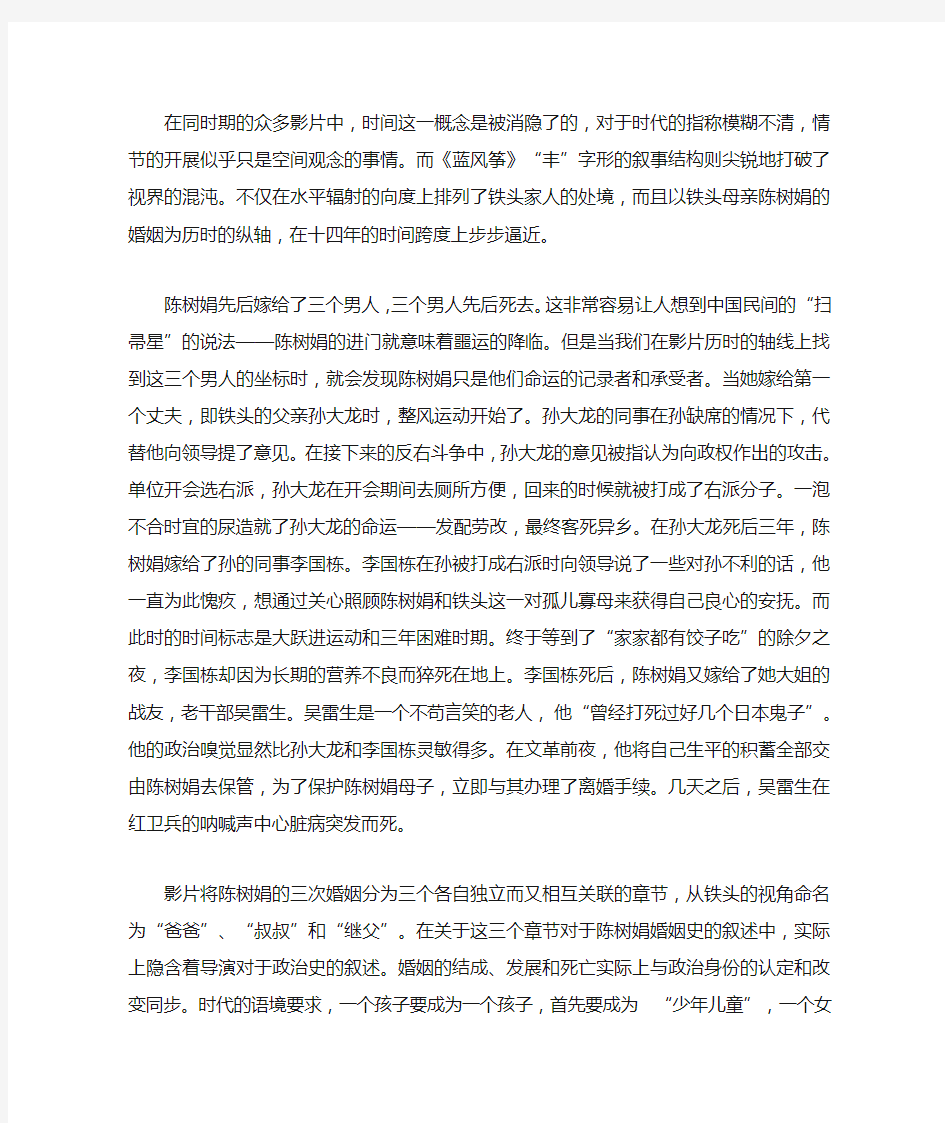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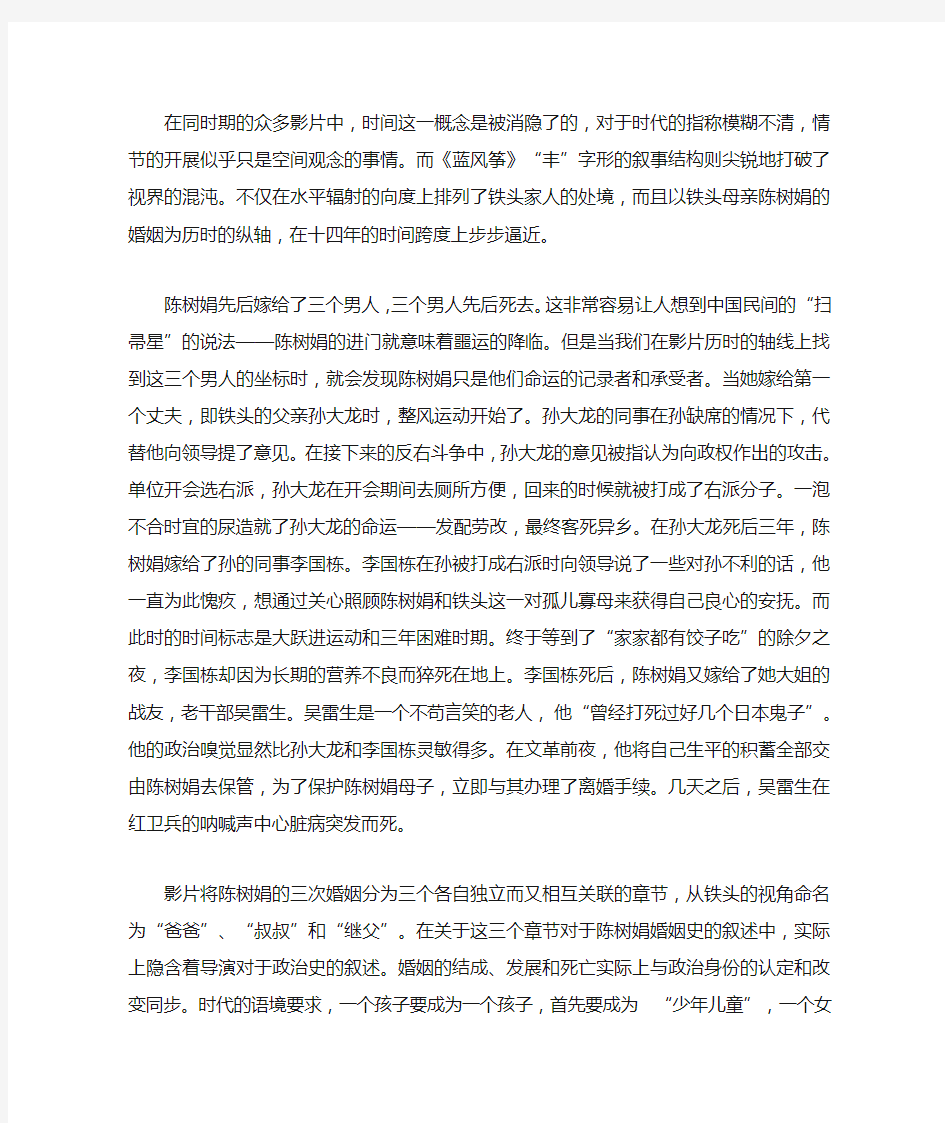
在同时期的众多影片中,时间这一概念是被消隐了的,对于时代的指称模糊不清,情节的开展似乎只是空间观念的事情。而《蓝风筝》“丰”字形的叙事结构则尖锐地打破了视界的混沌。不仅在水平辐射的向度上排列了铁头家人的处境,而且以铁头母亲陈树娟的婚姻为历时的纵轴,在十四年的时间跨度上步步逼近。
陈树娟先后嫁给了三个男人,三个男人先后死去。这非常容易让人想到中国民间的“扫帚星”的说法——陈树娟的进门就意味着噩运的降临。但是当我们在影片历时的轴线上找到这三个男人的坐标时,就会发现陈树娟只是他们命运的记录者和承受者。当她嫁给第一个丈夫,即铁头的父亲孙大龙时,整风运动开始了。孙大龙的同事在孙缺席的情况下,代替他向领导提了意见。在接下来的反右斗争中,孙大龙的意见被指认为向政权作出的攻击。单位开会选右派,孙大龙在开会期间去厕所方便,回来的时候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泡不合时宜的尿造就了孙大龙的命运——发配劳改,最终客死异乡。在孙大龙死后三年,陈树娟嫁给了孙的同事李国栋。李国栋在孙被打成右派时向领导说了一些对孙不利的话,他一直为此愧疚,想通过关心照顾陈树娟和铁头这一对孤儿寡母来获得自己良心的安抚。而此时的时间标志是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终于等到了“家家都有饺子吃”的除夕之夜,李国栋却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而猝死在地上。李国栋死后,陈树娟又嫁给了她大姐的战友,老干部吴雷生。吴雷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他“曾经打死过好几个日本鬼子”。他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孙大龙和李国栋灵敏得多。在文革前夜,他将自己生平的积蓄全部交由陈树娟去保管,为了保护陈树娟母子,立即与其办理了离婚手续。几天之后,吴雷生在红卫兵的呐喊声中心脏病突发而死。
影片将陈树娟的三次婚姻分为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章节,从铁头的视角命名为“爸爸”、“叔叔”和“继父”。在关于这三个章节对于陈树娟婚姻史的叙述中,实际上隐含着导演对于政治史的叙述。婚姻的结成、发展和死亡实际上与政治身份的认定和改变同步。时代的语境要求,一个孩子要成为一个孩子,首先要成为“少年儿童”,一个女人要成为一个女人,首先要成为“革命姐妹”,一个男人要成为一个男人,首先要成为“阶级兄弟”。除非陈树娟嫁给了意识形态,否则她嫁给任何一个具体的男人,她都将是同样的命运。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根本就没有命运,只有形势。
在影片“丰”字形的叙事结构图上,还展开了陈树娟一家其他人的命运嬗变。在第一章节内,树娟的树生哥哥结识了女友祝英,陈树言的身份是军官,祝英的身份是文工团的进步骨干。树娟的弟弟树言,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学生。三人的身份在第二章节之中就发生了变化。陈树言的女友祝英因为拒绝与首长跳舞而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陈树生因为眼睛的疾病而退伍专业,又因为与权威力量的疏离而被纯粹的革命战士,他的大姐,批评为散布反动言论。陈树言在因为向教育主管部门提意见,而被认为是攻击教育分配体制,重复了他姐夫孙大龙的劳改之路。在第三章节中,政治身份的认定同样是最高的唯一的人生标准。祝英被释放出狱,而陈树生的眼睛在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这似乎与政治风云无关。但如果将之与陈树娟的婚姻,亦即吴雷生之死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祝英的出狱只是政治话语权力转移的结果而已。
在“伤痕”淡化、“反思”退场之后,一切有关时代的痛切记忆都变成了痛切之外的任何东西,比如藏品展览,比如政治波普,但田壮壮的《蓝风筝》绝不类于此。影片将婚姻史与政治史合一的叙述策略虽然没有容纳过多的政治表征符号,也没有在镜头语言的癫狂中一泻千里,但是这个看似保守的结构图式却可以无限
衍深开来。
三、父、母何在?父母何为?
如果说这样的解读因为在某些地方沾染了学院派的色彩,因而显得生硬,或者沦为一相情愿的牵强的话,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剖析——从大众普遍认同的叙述角度出发,即从铁头的角度出发,看看这一视阈之内的影象风景到底说了些什么。
上文已经提到,影片的三个章节都有各自不同的命名,“爸爸”、“叔叔”和“继父”,但是命名的依据却是唯一的——“以父之名”。那为什么没有“父亲”这一个充满了尊严与权威的词汇?“父亲”在哪里?这个子之神灵与导师在哪里?孙大龙/爸爸、李国栋/叔叔和吴雷生/继父分别承担了铁头的名义之父,但都从不曾成为铁头的内心之父。在一个父之形象消失之后,又有新的一个顽固地树立起来,新的形象再次消失,另一个新的形象继之而起。在出场——消隐——再出场——再消隐的循环之中,父亲一直是被疏离、被抗拒和被怀疑的形象。
孙大龙虽然是铁头的生身之父,但他在铁头很小的时候就死在了异乡。在孙大龙离家之后,铁头曾无心中对他妈妈说爸爸死了,当孙大龙真的死去之后,妻子陈树娟掩面而泣,但铁头却安然入睡,他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爸爸已经死去的事实,一直到第二个名义之父李国栋的出场。影片故意忽略了铁头的认识觉醒,生身之父因而成了陌生之父。当李国栋和陈树娟结婚后,铁头有了第二个名义之父,亦即衰老之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表现李国栋与铁头这对新结成的父子关系时,影片安排了铁头的仰拍镜头和李国栋的俯拍镜头(李国栋将铁头举过头顶,由于没有站稳而使自己摔倒在地上)。这一镜语暗示了子之成长与父之衰老的鲜明对比。这一章节的另一个深有意味的镜头是:铁头在除夕之夜跟伙伴们玩捉迷藏,当众人隐匿之后,铁头一个人手提灯笼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四顾茫然,被一只扔到脚下的爆竹吓了一跳,灯笼也被烧破了。这一镜头一方面暗示了子之觉醒与独立——独自站在暗夜之中的铁头;另一方面又隐含了子之命运——象征了光明之源的灯笼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毁灭。名义之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光源提供者/精神之父,李国栋猝死在地上,父之形象再一次消失。当吴雷生作为父之形象的继任者重新在场之时,铁头已经完成了子之独立的过程。从孙大龙到吴雷生,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父之形象的叠加和演化,即从陌生之父到衰老之父,再到威严之父。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能够成为子之内心的精神之父。当吴雷生被红卫兵抬走的时候,愤怒的铁头上前解救,这与其说是子对父之拯救,莫如说是一个完成了力量聚集的人对另一个被解除了力量的人的拯救。
在这样一个类似于西西弗斯式的重复过程之中,建立精神之父的企图彻底地失败了。父亲的形象顽固地在场,又无奈地离去,父亲死了,没有谁是真正的内心之父
那么,母亲/女性在哪里呢?
影片所反映的时代恰恰是高唱男女平等的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女人能生产,女人能战斗,但这一表述的潜在前提是“女人跟男人一样能生产”,“女人跟男人一样能战斗”,女人必须男人生产、男人战斗的前提下才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女人也能。她们必须得到父权/夫权的庇佑才能得以成为女人。陈树娟的三次婚姻,也是她被三次摆放/安置在男性羽翼之下的记录。在她的第一次婚姻结束之后,甚至连她的大姐,一名纯粹的革命战士都要求她考虑自己的将来,建议她和李国栋结婚。影片中虽然也流露出了李、陈二人之间的情感,但更多的色彩却是李国栋以此来赎罪,获得自己良心的安抚。一方面,陈树娟是道德交易的筹码,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