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汉语音韵学的发展》
- 格式:doc
- 大小:28.00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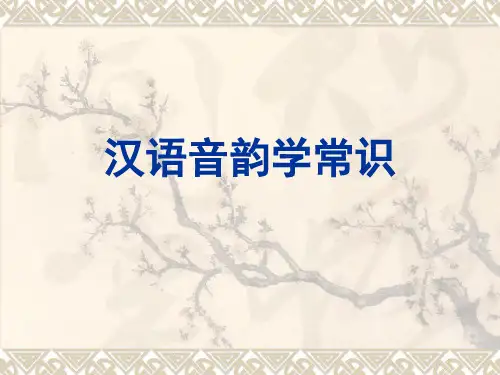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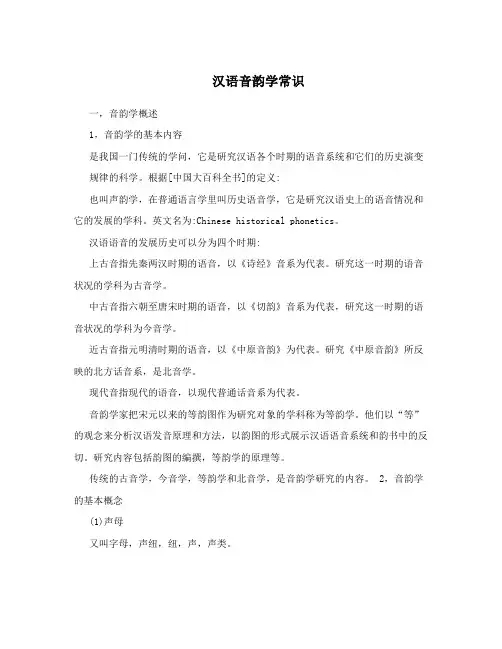
汉语音韵学常识一,音韵学概述1,音韵学的基本内容是我国一门传统的学问,它是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和它们的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也叫声韵学,在普通语言学里叫历史语音学,它是研究汉语史上的语音情况和它的发展的学科。
英文名为:Chinese historical phonetics。
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上古音指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以《诗经》音系为代表。
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状况的学科为古音学。
中古音指六朝至唐宋时期的语音,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状况的学科为今音学。
近古音指元明清时期的语音,以《中原音韵》为代表。
研究《中原音韵》所反映的北方话音系,是北音学。
现代音指现代的语音,以现代普通话音系为代表。
音韵学家把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为等韵学。
他们以“等”的观念来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和方法,以韵图的形式展示汉语语音系统和韵书中的反切。
研究内容包括韵图的编撰,等韵学的原理等。
传统的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和北音学,是音韵学研究的内容。
2,音韵学的基本概念(1)声母又叫字母,声纽,纽,声,声类。
字母是声母的代表字,唐朝和尚守温制定了三十字母,宋代学者又增加了六个,补成了三十六个字母。
(2)五音,七音音韵学上按照声母的发音部位把声母分唇,舌,齿,牙,喉五类,又加上半舌音,半齿音为七音。
(3)反切是一种传统的标音方法,较之譬况,读若,直音是较为科学的标音法。
反切的产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
”(孙炎,字叔然,名炎)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渐繁。
”事实上,孙炎以前已有人使用反切了,如东汉服虔注《汉书》“惴,音章瑞反”。
孙炎对反切进行了整理,并编成了〖尔雅音义〗。
反切是两字配合起来切出一个汉字的读音,分反切上字,反切下字和被切字。
黄侃在《音略》中云:“反切之理,上字定其声理,不论其为何韵,下字定其韵律,不论其为何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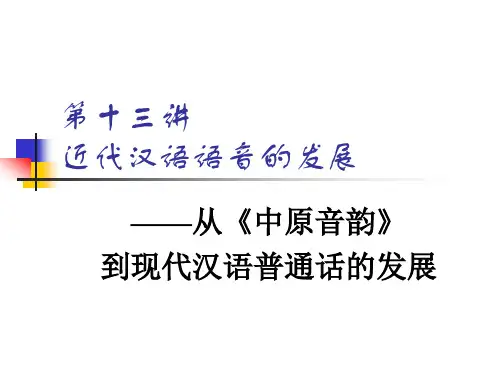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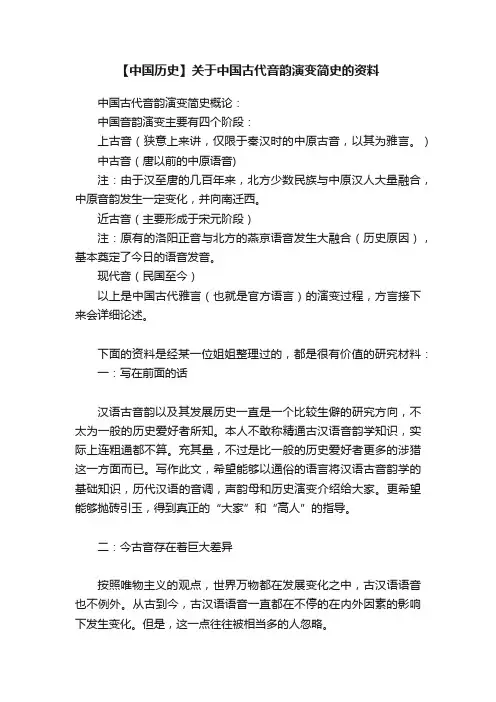
【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古代音韵演变简史的资料中国古代音韵演变简史概论:中国音韵演变主要有四个阶段:上古音(狭意上来讲,仅限于秦汉时的中原古音,以其为雅言。
)中古音(唐以前的中原语音)注:由于汉至唐的几百年来,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大量融合,中原音韵发生一定变化,并向南迁西。
近古音(主要形成于宋元阶段)注:原有的洛阳正音与北方的燕京语音发生大融合(历史原因),基本奠定了今日的语音发音。
现代音(民国至今)以上是中国古代雅言(也就是官方语言)的演变过程,方言接下来会详细论述。
下面的资料是经某一位姐姐整理过的,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材料:一:写在前面的话汉语古音韵以及其发展历史一直是一个比较生僻的研究方向,不太为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所知。
本人不敢称精通古汉语音韵学知识,实际上连粗通都不算。
充其量,不过是比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更多的涉猎这一方面而已。
写作此文,希望能够以通俗的语言将汉语古音韵学的基础知识,历代汉语的音调,声韵母和历史演变介绍给大家。
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得到真正的“大家”和“高人”的指导。
二:今古音存在着巨大差异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古汉语语音也不例外。
从古到今,古汉语语音一直都在不停的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
但是,这一点往往被相当多的人忽略。
我曾在某网络帖子上看到有人大言不惭的宣称:“汉语是最优秀的语言,因为其稳定性高,传承性好,现在的小学生还能琅琅上口的朗诵楚辞”。
此论断简直慌天下之大谬!首先不说语言文字都是文化的直接载体,文化本身便不存在优劣,那么其载体也没有优劣之分了。
其次,此论断混淆了语音和文字的关系,汉语是通过像形,表“义”的文字,而不是西方文明体系的拼音文字,方块文字的读音变化是很难从书面文字上发觉的,于是便往往被人忽略。
从汉语的上古时代到现代,经历三四千年,汉字读音会因内外因素不断的变化,比如原本只是细微差异的读音变成有明显的差异;民族融合带来的外来语言与本地语言融合,或者某地区长期隔绝导致与其他地区的语音差异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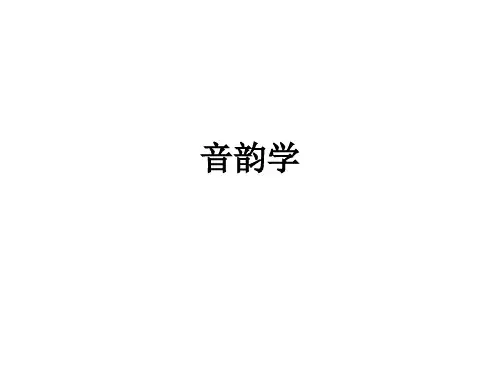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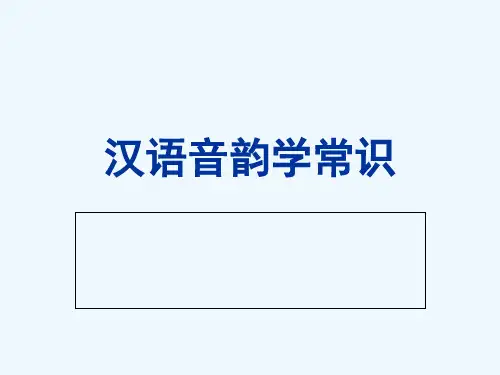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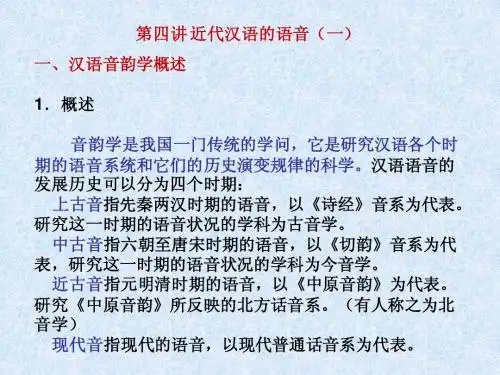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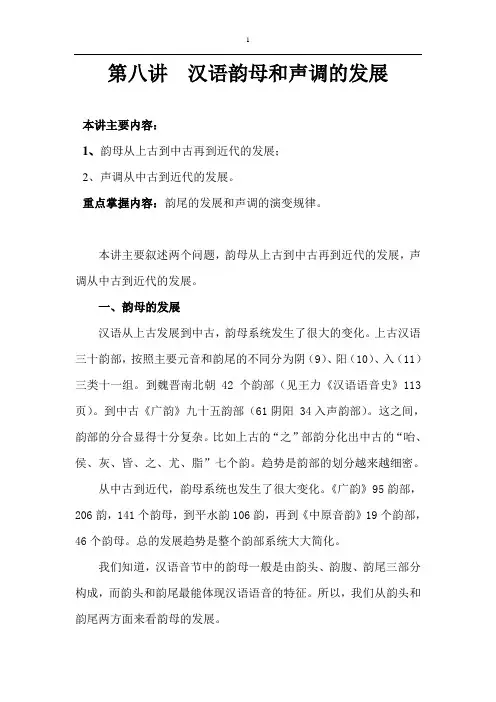
第八讲汉语韵母和声调的发展本讲主要内容:1、韵母从上古到中古再到近代的发展;2、声调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重点掌握内容:韵尾的发展和声调的演变规律。
本讲主要叙述两个问题,韵母从上古到中古再到近代的发展,声调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一、韵母的发展汉语从上古发展到中古,韵母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古汉语三十韵部,按照主要元音和韵尾的不同分为阴(9)、阳(10)、入(11)三类十一组。
到魏晋南北朝42个韵部(见王力《汉语语音史》113页)。
到中古《广韵》九十五韵部(61阴阳 34入声韵部)。
这之间,韵部的分合显得十分复杂。
比如上古的“之”部韵分化出中古的“咍、侯、灰、皆、之、尤、脂”七个韵。
趋势是韵部的划分越来越细密。
从中古到近代,韵母系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广韵》95韵部,206韵,141个韵母,到平水韵106韵,再到《中原音韵》19个韵部,46个韵母。
总的发展趋势是整个韵部系统大大简化。
我们知道,汉语音节中的韵母一般是由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构成,而韵头和韵尾最能体现汉语语音的特征。
所以,我们从韵头和韵尾两方面来看韵母的发展。
1、韵尾的发展韵尾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①、-p、-t、-k尾的消失;②、-m尾的消失。
[-p]、[-t]、[-k]是塞音,听起来很紧促,所以带这种韵尾的音节叫“促音尾”音节,也叫“塞音尾”音节,音韵学上称之为“入声韵”;[-m]、[-n]、[-g]是鼻音,用鼻音充当韵尾的音节叫“鼻音尾”音节,音韵学上称“阳声韵”。
戏曲界又把阳声韵中收[-m]尾的音节叫“闭口韵”。
塞音尾和鼻音尾因为都是唯闭音尾,听着不敞亮,所以合称“闭音节”。
用元音充当韵尾的音节叫“元音尾”音节,没有韵尾的音节叫“开音节”。
这两种音节在音韵学上合称“阴声韵”。
[-p]、[-t]、[-k]都是“唯闭音”,即只把双唇、舌尖、舌根急促地一闭就完了,并不让气流冲出来。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已经没有这类韵尾了。
但在现代粤方言广州话中,普通话里同音的“力、栗、力”三个字分别读作【lap】、【løt】、【lΙk】,还保留着韵尾[-p]、[-t]、[-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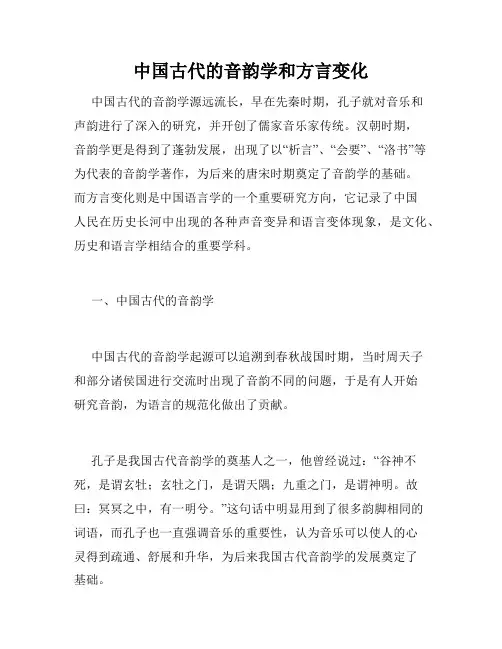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音韵学和方言变化中国古代的音韵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对音乐和声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开创了儒家音乐家传统。
汉朝时期,音韵学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出现了以“析言”、“会要”、“洛书”等为代表的音韵学著作,为后来的唐宋时期奠定了音韵学的基础。
而方言变化则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它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各种声音变异和语言变体现象,是文化、历史和语言学相结合的重要学科。
一、中国古代的音韵学中国古代的音韵学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周天子和部分诸侯国进行交流时出现了音韵不同的问题,于是有人开始研究音韵,为语言的规范化做出了贡献。
孔子是我国古代音韵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经说过:“谷神不死,是谓玄牡;玄牡之门,是谓天隅;九重之门,是谓神明。
故曰:冥冥之中,有一明兮。
”这句话中明显用到了很多韵脚相同的词语,而孔子也一直强调音乐的重要性,认为音乐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疏通、舒展和升华,为后来我国古代音韵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时期,音韵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音韵学著作,如《析言》、《会要》、《洛书》等,这些著作都对我国古代音韵学的体系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析言》是最为重要的一部音韵学著作,它主要收录了大量的古代方言发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系统化的分类整理和分析研究。
到了唐宋时期,音韵学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顶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对音韵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贡献,一直影响到了宋代。
宋代时期的音韵学家如沈括、蒲松龄、黄庭坚等人均有所建树,他们继承和创新了唐代音韵学的成果,推动了我国古代音韵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中国方言变化中国方言变化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各种声音变异和语言变体现象。
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的方言差异极大,因此对方言变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要了解中国方言变化,首先需要了解天京音和官府音。
天京音指的是北方方言,而官府音则指的是南方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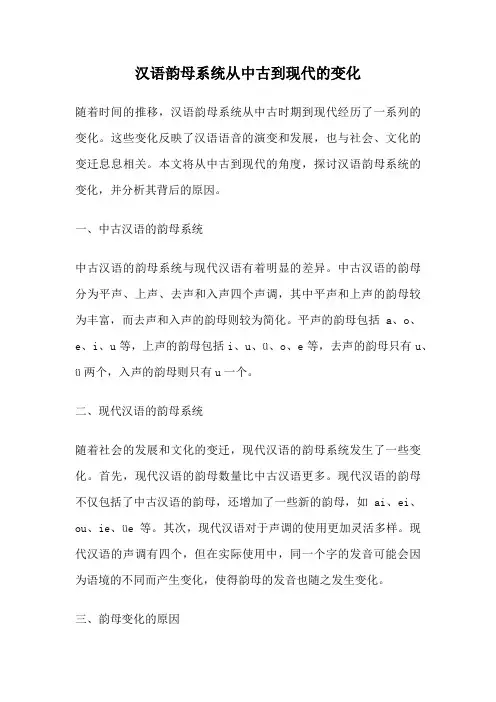
汉语韵母系统从中古到现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韵母系统从中古时期到现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些变化反映了汉语语音的演变和发展,也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息息相关。
本文将从中古到现代的角度,探讨汉语韵母系统的变化,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一、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与现代汉语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古汉语的韵母分为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四个声调,其中平声和上声的韵母较为丰富,而去声和入声的韵母则较为简化。
平声的韵母包括a、o、e、i、u等,上声的韵母包括i、u、ü、o、e等,去声的韵母只有u、ü两个,入声的韵母则只有u一个。
二、现代汉语的韵母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现代汉语的韵母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现代汉语的韵母数量比中古汉语更多。
现代汉语的韵母不仅包括了中古汉语的韵母,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韵母,如ai、ei、ou、ie、üe等。
其次,现代汉语对于声调的使用更加灵活多样。
现代汉语的声调有四个,但在实际使用中,同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使得韵母的发音也随之发生变化。
三、韵母变化的原因汉语韵母系统从中古到现代的变化,主要是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语音环境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人们的语音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导致了发音习惯的改变,进而影响了韵母的发音。
2.外来语的影响: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汉语中不断引入外来词汇。
为了适应这些外来词汇的发音,汉语中的韵母系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3.方言的影响:汉语是一个多方言的语言系统,不同地区的方言对于韵母的发音也存在差异。
这些方言的影响也促使了韵母系统的变化。
4.语言规范的调整:随着汉语规范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对于韵母的使用也有一定的规范要求。
这些规范要求也对韵母系统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韵母系统的变化是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语言适应社会变化的表现。
通过对汉语韵母系统从中古到现代的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汉语语音的演变和发展,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汉语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音韵学史
中国音韵学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
早在《诗经》和《论语》等古代文献中,就可以看到对音韵的研究。
在先秦时期,音韵学主要是以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韵书是一种对古代音韵进行整理和分类的著作。
最早的韵书是《尔雅》和《方言》。
《尔雅》是一部对古代汉语音韵进行解释和分类的辞书,而《方言》则是对古代汉语方言进行整理和比较的著作。
这些韵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音韵学的起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音韵学逐渐发展壮大。
在汉代,音韵学家陆终和许慎编写了《尔雅注》和《说文解字》,对古代音韵进行了更加详细和系统的研究。
在隋唐时期,音韵学家韩愈和刘知几等人对音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
到了宋代,中国音韵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宋代的音韵学家沈括编写了《唐韵正声谱》和《广韵正声谱》,对古代音韵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分类。
他提出了“四声八调”的理论,对后来的音韵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音韵学继续发展。
明代的音韵学家杨时和许慎等人对音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
清代的音韵学家郑方坤和李文藻等人则对音韵进行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他们编写了《中原音韵》和《切韵类编》等著作,对后来的音韵学
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音韵学继续发展并与西方音韵学进行了交流和对比。
20世纪以来,中国的音韵学研究逐渐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同时,中国的音韵学研究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和关注。
小论汉语音韵学的历史摘要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它始终有效地为人们服务。
但是,汉字一直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难写难读是它的特点之一。
为着识字,特别是为着当时文学创作的需要,于是人们编制了许多韵书。
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形成了一门学科,即汉语音韵学。
汉语音韵学的历史便是从这些韵书开始的。
关键词汉语音韵历史韵书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各个时期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它是中国一门传统的学问,是汉语语言学的一部分。
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者就开始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在这研究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音韵学这门科学。
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期这个时期从魏晋南北朝起到宋代为止。
.魏晋南北朝。
这时期虽是一个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时期,但写诗作文的风气很盛,随着汉末兴起的反切注音法的逐步流行,又加上印度佛教的传入为满足翻译佛经的需要,许多文章家自觉接受印度语音学的影响,音韵学知识得到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传统音韵学的草创期,主要有两项内容——辨出了韵母类别和四声区别、编纂了最早的一批韵书。
隋代陆法言《切韵》的出现标志着“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局面的结束。
《切韵》出现之后,增广《切韵》的韵书很多,影响大的有唐孙愐的《唐韵》,宋陈彭年、邱雍等受皇帝之命编修的《广韵》,其后还有《集韵》、《礼部韵略》、《五音集韵》(金)等等,这些韵书共同开创了“切韵系统”的中古音的研究新局面,其在汉语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可以上推古音,下推今音,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的语音系统,基本上可以从《切韵》音系系统上得到解释。
另外,也有颜之推等人在陆法言家讨论“古今是非,古今通塞”,颜著《家训》评论古韵书。
一方面引了最早讲叶音的话,一方面对他的任意性表示反对,作出解释。
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语音学。
第一时期可以叫“萌芽期”。
二、分类期这个时期从宋代从开始。
宋代吴棫采用叶音说,后人不从。
汉语韵母发展的总趋势汉语韵母是指汉语拼音中的元音音素,它们在语言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韵母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汉语阶段、中古汉语阶段和现代汉语阶段。
这三个阶段在韵母的数量、种类和规律上都有一定的变化。
古代汉语阶段的韵母数量相对较少,最早只有六个,分别是-a、-o、-e、-i、-u 和-ü。
随着语言的发展,古代汉语阶段的韵母数量逐渐增加,最终发展成32个。
这个阶段的韵母变化比较简单,多以音的入声和轻声为主,所以分析起来比较容易。
中古汉语阶段的韵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在这个阶段,韵母的数量增加到了48个。
这主要是由于古代汉语阶段声母的变化,导致韵母的分化和多样化。
比如,原本的-a韵分化出了-ia、-ua等变体,原本的-o韵分化为-uo韵等。
同时,这个阶段还发生了元音韵尾的清化,韵腹也发生了前移和后移的变化。
总体上,中古汉语阶段的韵母发展呈现多样化和分化的趋势。
现代汉语阶段的韵母发展是在中古汉语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这个阶段,韵母数量减少到了37个,但韵母的规律更加明显和稳定。
现代汉语阶段的韵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韵母数量减少,主要是由于韵尾的消失和合并。
比如,中古汉语阶段的许多韵尾发生了清化,或者在后来的语音演变过程中完全消失了。
这导致一些韵母之间的区分变得不再明显,最终合并成了新的韵母。
其次,韵母的分化和规律更加明显。
现代汉语的韵母变化多以韵头的不同而区分,这些韵头的变化包括声调、声母和声调方位等。
例如,-i韵在北方方言中分化为-i和-yi两个变体,其中-i韵是高调,而-yi韵是去声。
这种韵母的分化和规律的发展,表明了汉语韵母在现代汉语阶段的丰富和多样化。
最后,韵母的变化和演变更加复杂。
现代汉语阶段的韵母变化包括移位、合并和消失等。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鼻音韵母的变化。
现代汉语中的鼻音韵母包括-an、-ang、-en、-eng、-in、-ing、-ong、-uan、-un、-uo等。
汉语音韵学发展与变动研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汉语的学习和研究。
其中,汉语音韵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汉语音韵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汉语音韵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汉语声音的产生、变化以及发音技能的习得过程。
汉语音韵学的悠久历史汉语音韵学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音韵学家进行了汉语音韵的研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切韵》和《韵集》。
《切韵》是唐代孙思邈根据盛唐礼部的《大韵》修订,创作的一部汉语音韵的词典。
该词典用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要素,对唐代的音韵进行了系统的归类和整理。
《韵集》则是宋代的李昉在《切韵》的基础上,对唐代和五代十国时期的音韵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此外,北宋的黄庭坚也在他的书信中谈及音韵问题,表明了他对音韵学的关注。
元代辛弃疾也写有许多歌曲和诗歌,其中包含了许多对汉语音韵的表达和研究。
现代汉语音韵学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汉语的音韵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近代的汉语音韵学家开始以科学的方法,对汉语的音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扬州音。
扬州音是清代乾隆年间,来自江苏扬州的方言。
该方言中的音韵和北方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被称为“洪水猛兽”。
在20世纪初期,汉语音韵学开始走向了科学化的研究。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标志着汉语音韵学的一大发展,为后来对汉语音素的研究和汉语语音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的研究者通过大量地对不同方言的采集、整理和分析,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和音位分析理论。
其中,国内著名的音韵学家有钱君匋、陈斯威等。
同时,在国际上,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了国际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汉语音韵学的未来发展当前,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汉语声音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上、汉语发音技能的习得、语音变异和语音交际等方面。
另外,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声学、计算机语音处理、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领域,为发展语音技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的音韵变化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是汉语语音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古代汉语是指汉语在古代时期的语言形态,其音韵变化是指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
在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过程中,音韵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这对于了解和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可以分为多个阶段。
最早的阶段是古汉语时期,这一时期的发音还比较接近古汉语的来源,即汉字的形声结构和上古汉语的声母和韵母系统。
然而,受到历史和语言接触的影响,古汉语逐渐发生了一系列的音韵变化。
在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声母的变化。
在古汉语时期,声母系统相对简单,包括激短辅音、浊音和清音等。
而到了中古汉语时期,声母系统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辅音,并且有些辅音发生了合并或丢失的情况。
例如,古汉语中的"w"音在中古汉语中演变为"j"音,古汉语中的"kw"音在中古汉语中演变为"k"音。
除了声母的变化,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还涉及韵母的变化。
在古汉语时期,韵母系统比较丰富,包括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等。
然而,在中古汉语时期,韵母系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韵母,并且有些韵母发生了合并或丢失的情况。
例如,古汉语中的"ie"音在中古汉语中演变为"i"音,古汉语中的"uo"音在中古汉语中演变为"o"音。
此外,在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中还存在声调的变化。
在古汉语时期,声调系统比较简单,主要有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四个声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声调系统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声调合并、声调轻化等现象。
这些变化对于古代汉语的语音和声调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是汉语语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通过对古代汉语的发音演变进行系统研究,可以了解汉语的历史变迁和语音发展的规律,对于汉字的形态和发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音韵学史中国音韵学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它是一门研究语言声音和音节规律的学科。
下面我们来简要介绍中国音韵学史的发展。
古代的中国音韵学可以追溯到《尚书》和《雅》等古代文献。
在这些古代文献中,对于音的记载主要是象声和拟声的表示,对于语音的描述比较粗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对于声音和音节规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先秦时期的音韵学主要集中在韵书的编纂上。
《尔雅》是先秦时期最早的一部韵书,它收集了当时的许多韵母。
除了《尔雅》,先秦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韵书,虽然它们的内容已经不完整,但是它们对于后来的音韵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汉朝的兴起,学者们开始进行更加系统和科学的音韵学研究。
最重要的一位学者是张衡,他在《西京赋》中系统地研究了当时的声音和音节规律。
他把声音分为四个要素,即清音、浊音、开口、结口,并提出了很多与音韵相关的理论。
在唐宋时期,中国音韵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代的学者刘知几编纂了《韵略》,对当时的语音进行了更加详细和系统的描述。
他在书中提出了声、韵、调之分,并研究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变化规律。
宋代的学者李昉撰写了《集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韵书。
《集韵》收录了当时的许多音节,对于后来的音韵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宋代的学者们还对音韵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专门的音韵学理论。
明清时期,中国音韵学进一步发展。
明代的学者罗贯中研究了多个方言的音韵差异,并编纂了《代韵》,为后来的方言研究奠定了基础。
清代的学者孙星衍在《三合韵外编》中进一步完善了音韵学理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近代以来,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中国音韵学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20世纪,许多学者对音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他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语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工具。
总的来说,中国音韵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古代的简单描述到近代的科学研究的演变过程。
这门学科对于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方言的演变以及文化的传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音韵学发展历程中国音韵学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传统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汉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学科和基础学科。
回顾中国音韵学的发展历程,自东汉服虔、应劭为《汉书》作音注始,距今已有一千八九百年。
历代千百学者为之殚精竭虑,前赴后继,论著堪称汗牛充栋。
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古代曾受到梵语语音学的影响,近现代又接受了西学的精华。
在中国境内,除了丰硕的汉语音韵典籍外,还有大量域外对音音韵典籍,对中国音韵学的本体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繁荣。
可以说,中国音韵学研究史就是一部“一本”“多元”“争鸣”“创新”[1]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中国音韵学研究更是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在一代代音韵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在音韵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切韵学等韵学、方言语音史、音韵学与汉藏语等方面呈现出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局面。
70年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据若干目录及综述资料(详见文末的“参考文献目录”)共出版著作500余部,发表论文6 000余篇。
回望这70年所取得的成就,更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做总结、论得失、向未来、谋发展。
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划未来,就是为了更迅速、更持久地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的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4个时期:1. 1949-1966年——音韵学研究的发轫期;2. 1967-1976年——音韵学研究的停滞期;3.1977-1999年——音韵学研究的发展期;4. 2000-2019年——音韵学研究的辉煌期。
一、音韵学研究的发轫期(1949-1966)发轫期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初,音韵学家们都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教学与科研事业中,并建立自己完整的、系统的、统一的课程体系。
建国初期,高校经过院系调整,一些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高等院校陆续开设汉语史、音韵学等课程,需求量的增大,急需撰写、出版音韵学经典教材,以应音韵学教学之急。
方孝岳、罗常培、王力、魏建功、张世禄、殷焕先、黄典诚、周祖谟、俞敏(1)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编写教材,讲授音韵学课程。
简述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它始终有效地为人们服务。
但是,汉字一直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难写难读是它的特点之一。
自古以来,识字就是学童们在校学习的重要课程。
据《周礼》记载,那时的孩子“八岁入小学”,要学六门课,其中之一就是“六书”。
什么叫做“六书”?《周礼》没有作说明。
不管汉代的郑众、班固和许慎怎么解释,总该不是教几岁的孩子去造字,而应该是教他们识字。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到,当时的法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
今天通行的《新华字典》包括异体字在内才8500个字,一般的大学生都不能全部认识,可见汉代对青年们识字的要求很高。
而不论是周代的《史籀篇》也好,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也好,还是汉代的《训纂篇》、《凡将篇》、《元尚篇》、《急就篇》和《滂喜篇》,都是古代用来整理和规范汉字的识字课本。
识字既要辨别字形、字义,更要辨识字音。
语音是一发即逝的东西,加之古代书写工具落后,所以只能口耳相传。
要想传播得远一些、久一些,就要给汉字注音。
最早的汉字注音法是譬况法,由于声音是很难进行书面描述的,因此只好将发音时发音器官的动作和状态进行描写。
到了汉代,人们开始用同音字来注音,即所谓直音。
到了汉代末年,人们发明了反切注音法,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有了反切法,就可以为所有的汉字注音了。
反切法的产生,导致了韵书的产生。
从此,音韵学开始从小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
为了识字,特别是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需要,南北朝时,人们编制了许多韵书。
而随着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陆法言的《切韵》刊行以后,那几十种韵书都逐渐销声匿迹,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
唐代以后,历史上各个时期都编制了一些韵书。
这些韵书既可能是反映了某一时期通语的语音状态,也可能是反映了当时南北方言的差异。
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可以构筑成一部完整而生动的汉语语音发展史。
唐末至宋元时期的等韵学家们不满足于韵书那种只重在对声调和韵类的分析,为了更便利地拼读反切,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韵书所记录的语音系统,他们编制了等韵图。
他们以等韵学的观念分析汉语的声母、韵母、声调及其彼此的联系,是中国古代的语音学。
他们的研究比西文语音学的产生要早上将近一千年。
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清代无数朴学大师穷经皓首的研究,真可以说是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首先,汉字的传统注音法――反切经过明吕坤《交泰韵》和清初潘耒《类音》的改进,特别是通过李光地、王兰生《音韵阐微》的精心改良以后,反切上、下字相对固定,它们的声母、韵尾和声调也经过精心选择,拼读起来比以前便当得多了。
其次,宋元等韵图到了精于审音的江永等一批等韵学家的手中,研究得更加深入、系统和精密,等韵学成为朴学大师们辨析音理、分析汉语语音系统的主要工具,并促进了今音学和古音学的发展。
陈澧《切韵考》的问世,标志着《广韵》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古音系声类、韵类的研究已经渐趋成熟。
最值得一提的是古音学在清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上古韵部的研究基本定谳,在上古声母和声调的研究中也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
顾炎武是清代古音学的开创人,他“潜心声韵几五十年,作《音学五书》,而古音乃大明于天下”。
《音学五书》是研究古音的奠基之作,其中以《诗本音》、和《古音表》最为重要,《诗本音》是《古音表》的根据,《古音表》是《诗本音》的归纳。
顾炎武将上古韵划分为十类,并没有给韵部立专有名称只是用《广韵》平声五十五个韵目(庚尤不在内)分别给各类命名,十部之中,六、七、八、九等四个部为江永以后的古韵学家所接受,另外六个部比较粗疏。
江、段二人的分部“益密于顾氏,然皆自顾氏之十部导之,故通乎十部之说,则于求古人之音,思过半矣”江永是清代音韵学的者的直接导师。
他在音韵学方面著有《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和《音学辨微》, 对传统音韵学中的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 提出不少创见,获得许多成绩。
他分古韵舒声(平、上、去)十三部和入声八部, 把古韵研究推进一大步,他列了第一份“切字母位用字”即《广韵》反切上字表,在陈澄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指出“照穿床审四位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别”等等。
江永关于“等呼”的解释,既简明,又科学。
他说:“音呼有开口、合口,合口者吻聚,开口者吻不聚也。
”(《音学辨微》“七辨开口合口”)这从发音时唇吻聚合与否,即圆唇不圆唇来辨明开、合,抓住了关键,审音精到。
关于“四等”,江永说:“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
”以“洪细”(即发音时开口度的大小)来区别四等,这是我国音韵学史上首次对等韵学中的“等”这一核心概念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还常为讲传统等韵学的论著或音韵学教材所征引。
丁邦新先生亦据此认为江永是清代音韵学中审音派的始祖。
《四声切韵表》基本上是研究今韵学的,而其利用文字谐声考求通转现象,又在窥探古今音的演变规律。
其“数韵共一入”的学说就建立在阴、阳、入三种韵类脉络相通并可转化的基础之上。
江永利用《诗经》用韵、谐声和古读反复论证语音可以“互相转”。
这种所谓“互相转”就是阴声韵和阳声韵可以互相转化,入声韵也可以和阳声韵互相转化,这是汉语语音发展变化的一条基本规律,古今方音莫不如此。
戴震和他的学生孔广森进一步发展这种韵部互相转化的学说,概括为“阴阳对转”。
江永在其音韵学著述中特别注意利用方言以研究古音,他把《诗经》等先秦韵文中的特殊韵例看作是“方音偶借”,甚至认为“韵即其时之方音”,而且他还深刻认识到古音研究与辨析方音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审定正音(按,指古音)乃能辨别方音,别出方音更能审定正音。
诸部皆当如此。
”罗常培先生说:“自明迄清学者研究周秦古音有六大贡献,而段氏一人居其二。
”段玉裁在音韵学方面的成绩主要有:第一,把古韵分六类十七部。
段玉裁在顾、江的基础上,博稽文献,析其异同,进而将之脂支三部分立,并从真部分出文部,从幽部分出侯部,创为十七部,按音理使邻韵者以类相从,划归为六类。
从段玉裁创立十七部说开化寺,我们对上古韵母系统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后来诸家分部的学说,其实都是对段玉裁的补充。
第二,谐声声符相同者古韵必同部。
他说:“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
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
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
许书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
”“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
”段玉裁的这个论断为汉语古音的声韵研究开辟了通途,其后孔广森、严可均、朱骏声的撰著,都受到段氏这一学说的启迪。
第三,段玉裁认为音韵随时代迁移不可淆乱。
他开始给语音的历史发展作了分期工作,又明确提出了四声不同今韵说。
在音韵学领域,戴震对古音、今音、等韵诸方面均有精湛的研究,而对上古音的研究成绩最大。
《声类表》开创性的表现上古音类系统及其流变的等韵图表,《答段若膺论韵》阐述戴震的古韵观点和对段玉裁《六书音韵表》的评论,图表和书信合读,可以了解戴震的古音学说。
戴震在顾、江、段古韵分部的基础上,将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最大的特点是入声韵独立。
以之与阴声韵、阳声韵相配,并认为阴阳可对转,而入声是韵类通的枢纽。
戴震古韵分部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三个特点:第一,入声韵独立,阴阳入三分。
这在音韵学史上是开创性的突破,开后来所谓“阴阳对转”之先河。
近代黄侃的二十八部,王力的二十九部都是戴震古韵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霭(祭)部独立,是古韵系统更趋合理。
第三,韵部用影母字标目。
戴震首创以只表示韵母音值的影母字即零声母字命名。
古韵研究向来有考音和审音两种途径。
戴震师承江永,在考古的基础上尤其重视审音。
他在《答段若膺论韵》中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
”清代语言学家在声母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只有钱大昕一人,他在古声类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
钱大昕的语言学论述多散见于《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中,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完事讨论音韵的,其中以《古无轻唇音》和《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最为著名。
他集中解决了两大问题:一、古无轻唇音。
“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
”(《四声切韵表凡例》);二、“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
”钱大昕还提到“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就是说古代“章”、“昌”、“船”等生母的字也有不少归舌头音。
清代是音韵学大发展的时期,出现的语音学音韵学的著作也很多,但是清代音韵学研究进入全盛时期,无论从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然而,清代学者们的音韵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限:他们终生埋头于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中扒罗抉择,却只能停留在对古音声、韵的类属的归纳、分析之中,无法涉及古音的真正音值。
到了晚清时期,一些音韵学家也明显感觉到了汉字的这种局限和传统音韵研究的的不足,也想尽可能将古代汉字的读音标示出来。
例如戴震晚年所定的古音九类25部,所选的韵目字“阿乌垩膺噫亿翁讴屋央夭约……”等等,全部都是影母字。
影母字的特点就是主要元音前面没有声母,直接读出来的就是韵母。
――当然,它们毕竟还是汉字,还是不能摆脱汉字的限制。
到了章太炎手里,才第一个注意到古代的韵值,并开始用汉字去描写他的古韵23部的韵值(见《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
当然这种描写虽比前人更加细致,但由于语言含糊,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总而言之,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统音韵学已经发展到了它巅峰时代,并且也到了一个音韵研究方法论必须大变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