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型叙述声音完整版
- 格式:ppt
- 大小:151.00 KB
- 文档页数:9

33鲞第6朔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01.33 No.6 2014年12月J ou r n al o f Zh en gz ho u Institu te of Ae r o na u t ic a l Indus面M舳茹m ente Socia l S c i e n c e Edition) 2014.12曼斯菲德尔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李晶(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330103)摘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生命比较短暂,但是她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其短篇小说对整个英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被关誉为“英国契诃夫”、“英国短篇小说大师”。
苏珊·s·兰瑟的女性叙事学理论把女性作家的叙事声音划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等三种。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主要采用了苏珊·S·兰瑟前两种叙事声音。
因此,曼斯菲德尔短篇小说的女性主义叙述类型主要有“个人型”和“作者型”等两种。
文章对曼斯菲德尔短篇小说的叙事类型加以阐述,指出其“个人型”叙事模式,主要是“局外人”身份的自我“不发声”以及“作者型”叙事模式,主要是女性人物发出独立的“声音”。
关键词:曼斯菲德尔;短篇小说;女性主义叙事类型中图分类号:1561 文献标识码iA文章编号:1009—1750(2014)06—0026—04莉》、《夜深沉》等。
1917年至1922年是凯瑟琳·一、曼斯菲德尔及其短篇小说曼斯菲尔德的高峰期,优秀代表作有《序曲》、《毒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药》、《己故上校的女儿》、《巴克妈妈的一生》,等生命比较短暂,只有31岁(1888—1923),而且漂等。
总的来说,在其短暂的一生里,凯瑟琳·曼斯泊不定,出生于新西兰,拥有英国国籍,辗转于欧洲菲尔德一共创作88个短篇小说,被收录在《在德各国,生活较为坎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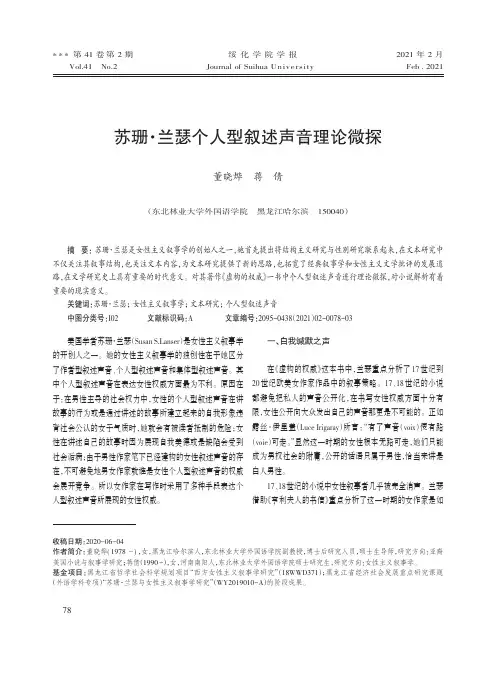
苏珊·兰瑟个人型叙述声音理论微探摘要:苏珊·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之一,她首先提出将结构主义研究与性别研究联系起来,在文本研究中不仅关注其叙事结构,也关注文本内容,为文本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经典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道路,在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对其著作《虚构的权威》一书中个人型叙述声音进行理论微探,对小说解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苏珊·兰瑟;女性主义叙事学;文本研究;个人型叙述声音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1)02-0078-03(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40)美国学者苏珊·兰瑟(Susan nser )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之一。
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独创性在于她区分了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
其中个人型叙述声音在表达女性权威方面最为不利。
原因在于: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权力中,女性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在讲故事的行为或是通过讲述的故事所建立起来的自我形象违背社会公认的女子气质时,她就会有被读者抵制的危险;女性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因为展现自我美德或是缺陷会受到社会诟病;由于男性作家笔下已经建构的女性叙述声音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男女作家就谁是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的权威会展开竞争。
所以女作家在写作时采用了多种手段表达个人型叙述声音所展现的女性权威。
一、自我缄默之声在《虚构的权威》这本书中,兰瑟重点分析了17世纪到20世纪欧美女作家作品中的叙事策略。
17、18世纪的小说都避免把私人的声音公开化,在书写女性权威方面十分有限,女性公开向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更是不可能的。
正如露丝·伊里盖(Luce Irigaray )所言:“有了声音(voix )便有路(voie )可走。
”显然这一时期的女性根本无路可走,她们只能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公开的话语只属于男性,恰当来讲是白人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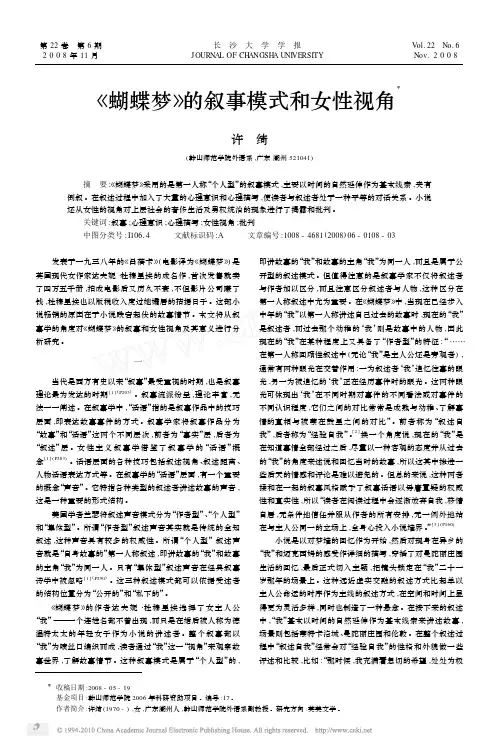
第22卷 第6期2008年11月长 沙 大 学 学 报J OURNA L OF CH ANGSH A UNI VERSITYVol.22 No.6Nov.2008《蝴蝶梦》的叙事模式和女性视角Ξ许 绮(韩山师范学院外语系,广东潮州521041)摘 要:《蝴蝶梦》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个人型”的叙事模式,主要以时间的自然延伸作为基本线索,夹有倒叙。
在叙述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心理意识和心理描写,使读者与叙述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小说还从女性的视角对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及男权统治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关键词:叙事;心理意识;心理描写;女性视角;批判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08)06-0108-03 发表于一九三八年的《吕蓓卡》(电影译为《蝴蝶梦》)是英国现代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成名作,首次发售就卖了四万五千册,拍成电影后又历久不衰,不但影片公司赚了钱,杜穆里埃也以版税收入度过她孀居的拮据日子。
这部小说畅销的原因在于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本文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蝴蝶梦》的叙事和女性视角及其意义进行分析研究。
一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1](P203)。
叙事流派纷呈,理论丰富,无法一一阐述。
在叙事学中,“话语”指的是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层面,即表达故事事件的方式。
叙事学家将叙事作品分为“故事”和“话语”这两个不同层次,前者为“事实”层,后者为“叙述”层。
女性主义叙事学借鉴了叙事学的“话语”概念[1](P283)。
话语层面的各种技巧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距离、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
在叙事学的“话语”层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声音”。
它特指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这是一种重要的形式结构。
美国学者兰瑟将叙述声音模式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
所谓“作者型”叙述声音其实就是传统的全知叙述,这种声音具有较多的权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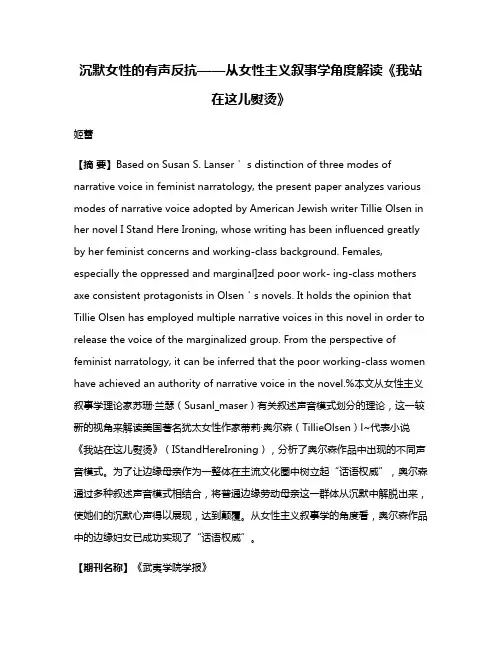
沉默女性的有声反抗——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我站在这儿熨烫》姬蕾【摘要】Based on Susan S. Lanser' s distinction of three modes of narrative voice in feminist narratology,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s various modes of narrative voice adopted by American Jewish writer Tillie Olsen in her novel I Stand Here Ironing, whose writing has been influenced greatly by her feminist concerns and working-class background. Females, especially the oppressed and marginal]zed poor work- ing-class mothers axe consistent protagonists in Olsen's novels. It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illie Olsen has employed multiple narrative voices in this novel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voice of the marginalized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poor working-class women have achieved an authority of narrative voice in the novel.%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家苏珊·兰瑟(Susanl_maser)有关叙述声音模式划分的理论,这一较新的视角来解读美国著名犹太女性作家蒂莉·奥尔森(TillieOlsen)l~代表小说《我站在这儿熨烫》(IStandHereIroning),分析了奥尔森作品中出现的不同声音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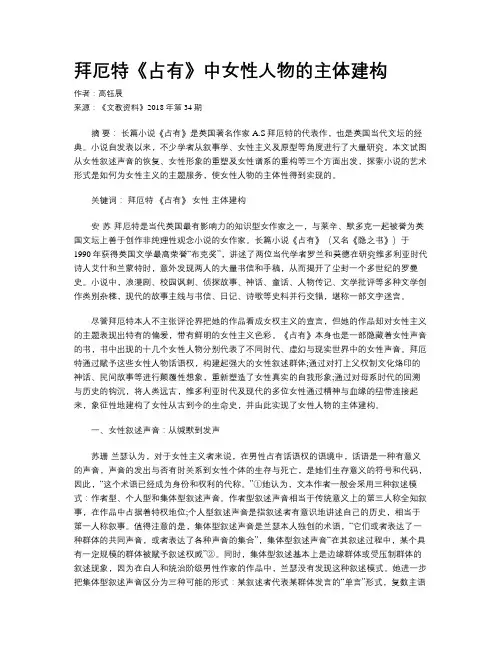
拜厄特《占有》中女性人物的主体建构作者:高钰晨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34期摘要:长篇小说《占有》是英国著名作家A.S拜厄特的代表作,也是英国当代文坛的经典。
小说自发表以来,不少学者从叙事学、女性主义及原型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
本文试图从女性叙述声音的恢复、女性形象的重塑及女性谱系的重构等三个方面出发,探索小说的艺术形式是如何为女性主义的主题服务,使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得到实现的。
关键词:拜厄特《占有》女性主体建构安·苏·拜厄特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型女作家之一,与莱辛、默多克一起被誉为英国文坛上善于创作非纯理性观念小说的女作家。
长篇小说《占有》(又名《隐之书》)于1990年获得英国文学最高荣誉“布克奖”,讲述了两位当代学者罗兰和莫德在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艾什和兰蒙特时,意外发现两人的大量书信和手稿,从而揭开了尘封一个多世纪的罗曼史。
小说中,浪漫剧、校园讽刺、侦探故事、神话、童话、人物传记、文学批评等多种文学创作类别杂糅,现代的故事主线与书信、日记、诗歌等史料并行交错,堪称一部文字迷宫。
尽管拜厄特本人不主张评论界把她的作品看成女权主义的宣言,但她的作品却对女性主义的主题表现出特有的偏爱,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占有》本身也是一部隐藏着女性声音的书,书中出现的十几个女性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时代、虚幻与现实世界中的女性声音。
拜厄特通过赋予这些女性人物话语权,构建起强大的女性叙述群体;通过对打上父权制文化烙印的神话、民间故事等进行颠覆性想象,重新塑造了女性真实的自我形象;通过对母系时代的回溯与历史的钩沉,将人类远古,维多利亚时代及现代的多位女性通过精神与血缘的纽带连接起来,象征性地建构了女性从古到今的生命史,并由此实现了女性人物的主体建构。
一、女性叙述声音:从缄默到发声苏珊·兰瑟认为,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在男性占有话语权的语境中,话语是一种有意义的声音,声音的发出与否有时关系到女性个体的生存与死亡,是她们生存意义的符号和代码,因此,“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利的代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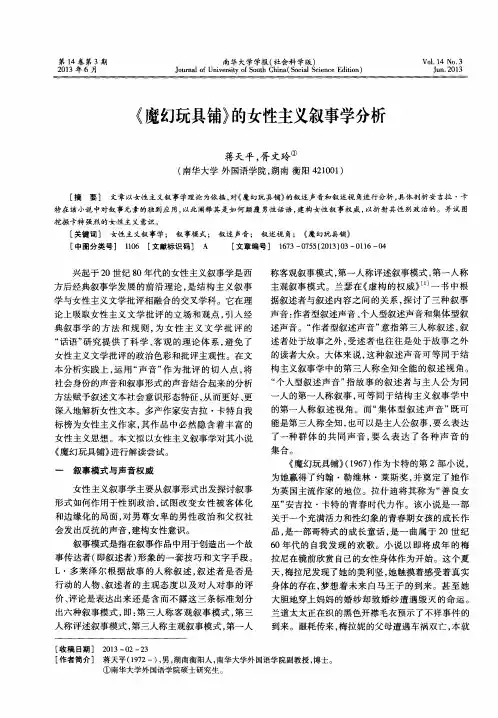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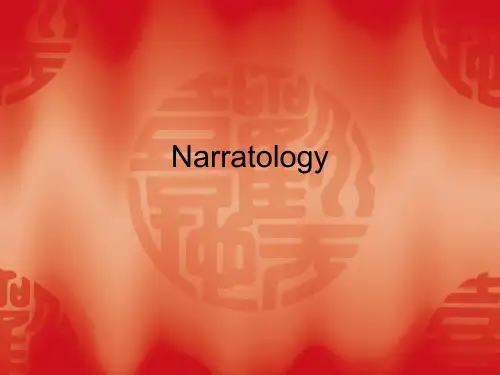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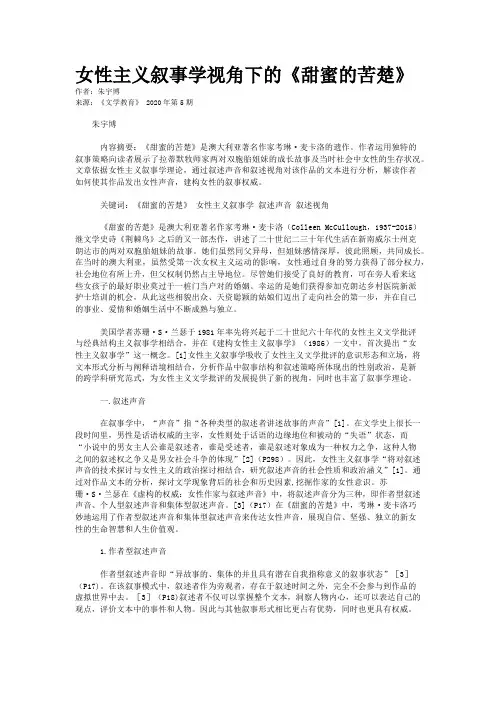
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的《甜蜜的苦楚》作者:朱宇博来源:《文学教育》 2020年第5期朱宇博内容摘要:《甜蜜的苦楚》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的遗作。
作者运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向读者展示了拉蒂默牧师家两对双胞胎姐妹的成长故事及当时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
文章依据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通过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对该作品的文本进行分析,解读作者如何使其作品发出女性声音,建构女性的叙事权威。
关键词:《甜蜜的苦楚》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声音叙述视角《甜蜜的苦楚》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1937-2015)继文学史诗《荆棘鸟》之后的又一部杰作,讲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新南威尔士州克朗达市的两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
她们虽然同父异母,但姐妹感情深厚,彼此照顾,共同成长。
在当时的澳大利亚,虽然受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部分权力,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但父权制仍然占主导地位。
尽管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在旁人看来这些女孩子的最好职业莫过于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
幸运的是她们获得参加克朗达乡村医院新派护士培训的机会,从此这些相貌出众、天资聪颖的姑娘们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并在自己的事业、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不断成熟与独立。
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于1981年率先将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并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1986)一文中,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
[1]女性主义叙事学吸收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和立场,将文本形式分析与阐释语境相结合,分析作品中叙事结构和叙述策略所体现出的性别政治,是新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丰富了叙事学理论。
一.叙述声音在叙事学中,“声音”指“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1]。
在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是话语权威的主宰,女性则处于话语的边缘地位和被动的“失语”状态,而“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谁是叙述者,谁是受述者,谁是叙述对象成为一种权力之争,这种人物之间的叙述权之争又是男女社会斗争的体现”[2](P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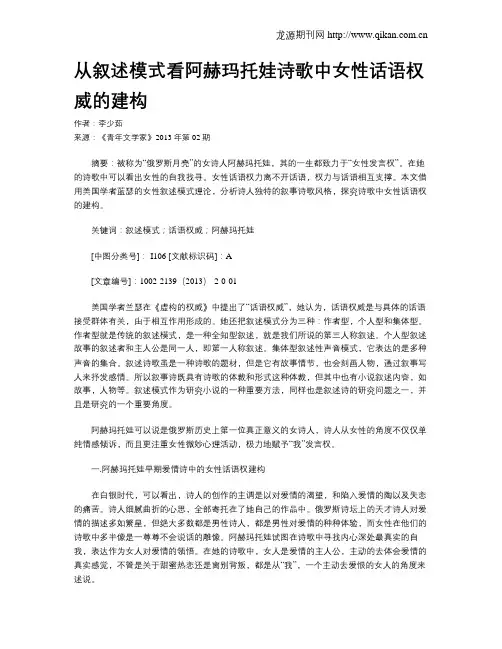
从叙述模式看阿赫玛托娃诗歌中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作者:李少茹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2期摘要:被称为“俄罗斯月亮”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其的一生都致力于“女性发言权”。
在她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自我找寻。
女性话语权力离不开话语,权力与话语相互支撑。
本文借用美国学者蓝瑟的女性叙述模式理论,分析诗人独特的叙事诗歌风格,探究诗歌中女性话语权的建构。
关键词:叙述模式;话语权威;阿赫玛托娃[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1美国学者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提出了“话语权威”,她认为,话语权威是与具体的话语接受群体有关,由于相互作用形成的。
她还把叙述模式分为三种: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
作者型就是传统的叙述模式,是一种全知型叙述,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人称叙述。
个人型叙述故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是同一人,即第一人称叙述。
集体型叙述性声音模式,它表达的是多种声音的集合。
叙述诗歌虽是一种诗歌的题材,但是它有故事情节,也会刻画人物,通过叙事写人来抒发感情。
所以叙事诗既具有诗歌的体裁和形式这种体裁,但其中也有小说叙述内容,如故事,人物等。
叙述模式作为研究小说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样也是叙述诗的研究问题之一,并且是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阿赫玛托娃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女诗人,诗人从女性的角度不仅仅单纯情感倾诉,而且更注重女性微妙心理活动,极力地赋予“我”发言权。
一.阿赫玛托娃早期爱情诗中的女性话语权建构在白银时代,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的主调是以对爱情的渴望,和陷入爱情的陶以及失恋的痛苦。
诗人细腻曲折的心思,全部寄托在了她自己的作品中。
俄罗斯诗坛上的天才诗人对爱情的描述多如繁星,但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诗人,都是男性对爱情的种种体验,而女性在他们的诗歌中多半像是一尊尊不会说话的雕像。
阿赫玛托娃试图在诗歌中寻找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表达作为女人对爱情的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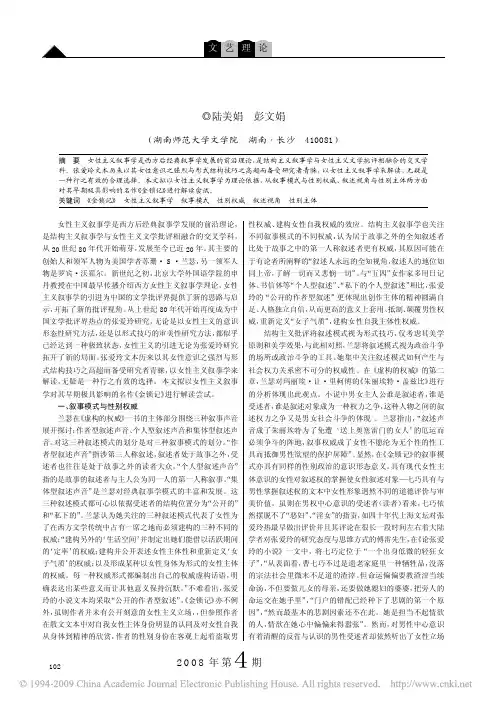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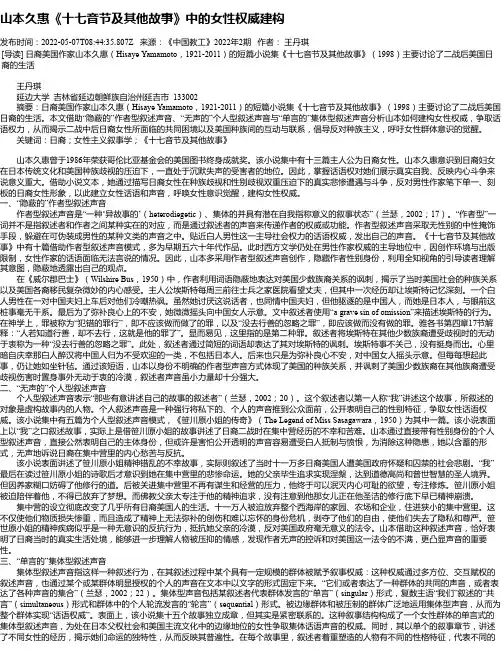
山本久惠《十七音节及其他故事》中的女性权威建构发布时间:2022-05-07T08:44:35.807Z 来源:《中国教工》2022年2期作者:王丹琪[导读] 日裔美国作家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1921-2011)的短篇小说集《十七音节及其他故事》(1998)主要讨论了二战后美国日裔的生活王丹琪延边大学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 133002摘要:日裔美国作家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1921-2011)的短篇小说集《十七音节及其他故事》(1998)主要讨论了二战后美国日裔的生活。
本文借助“隐蔽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无声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与“单言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分析山本如何建构女性权威,争取话语权力,从而揭示二战中后日裔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以及美国种族间的互动与联系,倡导反对种族主义,呼吁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日裔;女性主义叙事学;《十七音节及其他故事》山本久惠曾于1986年荣获哥伦比亚基金会的美国图书终身成就奖。
该小说集中有十三篇主人公为日裔女性。
山本久惠意识到日裔妇女在日本传统文化和美国种族歧视的压迫下,一直处于沉默失声的受害者的地位。
因此,掌握话语权对她们展示真实自我、反映内心斗争来说意义重大。
借助小说文本,她通过描写日裔女性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的真实悲惨遭遇与斗争,反对男性作家笔下单一、刻板的日裔女性形象,以此建立女性话语和声音,呼唤女性意识觉醒,建构女性权威。
一、“隐蔽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作者型叙述声音是“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兰瑟,2002;17)。
“作者型”一词并不是指叙述者和作者之间某种实在的对应,而是通过叙述者的声音来传递作者的权威或功能。
作者型叙述声音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
贴近白人男性这一主导社会权力的话语权威,发出自己的声音。
收稿日期:2020-11-10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性别化叙事□ 吕美琪 魏 文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该小说的一大特点是性别化叙事的运用。
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分析解读小说主人公悦子的第一人称回忆叙事。
叙事者悦子通过性别化的叙事声音对女性叙事权威进行建构,借用叙述视角转换再现包括自己在内的边缘女性群体的生存现状。
小说批判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也体现了同属边缘的少数族裔作家石黑一雄融入西方文坛中心的努力。
[关键词]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性别化叙事;叙事声音;叙事聚焦[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167(2021)11-0003-03作者简介:吕美琪,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魏文,文学博士,讲师。
研究方向:当代英国文学和文化研究。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作品在1982年一经出版,便在西方文坛引起巨大反响,正如石黑一雄本人所说:“通常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石沉大海,而我却赢得了许多关注,获得了很多鼓励,也接受了很多采访。
”(Rushdie ,1911:244)《远山淡影》讲述了身处英国的日裔遗孀悦子,在大女儿景子自杀后回顾日本生活点滴的故事。
主人公悦子有意虚构了佐知子和万里子这一对处在社会边缘地位的母女,来揭示日本女性在以男权为主导的日本社会所遭遇的重重压迫,以及悦子母女自身在母国和异乡所经历的身份困顿和压迫。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身份、跨文化以及不可靠叙事等方面来对《远山淡影》进行研究。
魏文(2015)从族裔身份出发,探讨了石黑一雄如何批判西方世界对少数族裔的偏见,从而颠覆西方对东方民族神话的臆想,实现后现代族裔身份的建构。
朱舒然(2014)从后殖民视角出发,探讨如何从文化杂合视角解构以悦子为代表的“他者”形象和二元对立问题。
刘玲(2015)从修辞叙事理论出发,从小说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以及审美判断三方面探讨悦子在回忆中逃避,在现实中忏悔、补救的心路历程。
2016.04(一)引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严歌苓只有8岁,在她之后的作品中也提及了这段特殊的历史对幼小的她造成的影响。
十年动乱对女性造成的政治强压和异化不可逆转,这也促使了严歌苓对于扭曲人性的丑恶现象有着更强烈的批判意识。
之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文工团演员使得严歌苓有机会到偏远地区为部队演出,这期间的所见所闻为严歌苓的创作积攒了许多灵感。
军旅生活也极大的影响了严歌苓的早期写作。
《雌性的草地》描写的就是军旅生活中的女性,以及她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畸形生存状态。
通过对这部作品中被异化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文革时期对人性的压制,对女性造成伤痛的多样性与深刻性。
作者独特的写作手法也表现出早期女性作者自我意识的苏醒,以及为女性权利的抗争。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由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合发展而成。
女性主义叙事学采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政治性批评的特点,为女性作家在文本建构中自我言说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借鉴了经典叙事学中的理论框架,使其对文本的分析更加客观。
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相关理论,从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两方面对《雌性的草地》进行解析尝试。
(二)运用作者型叙述声音描绘女性形象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对三种叙述声音进行了梳理:作者型叙述声音(传统全知叙述)、个人型叙述声音(故事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如叙述者为“我们”)。
“作者型叙述声音”指的是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处于故事之外的读者大众。
“个人型叙述声音”指的是故事的叙述者与主人公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事。
“集体型叙述声音”是兰瑟对经典叙事学模式的丰富和发展。
[1]这三种叙述模式都可根据受述者的结构位置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
所谓“公开的”指的是叙述者对处于故事之外的叙述对象(即广大读者)讲故事,“私下的”叙述指的则是对故事内的某个人物进行叙述。
《雌性的草地》描写到一群在草原上成立牧马班的女知青们,即使草原上荒无人烟、与世隔绝,她们仍因为老首长的一句“男娃女娃都一样,女娃也可以牧马”而聚集起来。
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叙事声音解读作者:刘琳李晓飞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09年第07期摘要: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学术发展的前沿理论。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品,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本分析方法。
本文根据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对叙事声音的划分,从“个人型”、“作者型”和“集体型”三种不同模式详细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事声音。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声音叙事声音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女性主义叙事学是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学术发展的前沿理论,在西方萌芽发展已有二十几年。
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军人物为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
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一书,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罗宾•沃霍尔,随着其著作《性别化的干预》的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声音”(voice)是女性主义批评中使用很多的词汇,它往往用来指传达出来由强烈意识形态意味的内容。
叙事学里的声音指的是文本形式,如区分叙事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及其各自的文本表现形式,并不关注这些声音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内涵。
而兰瑟则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将作为形式的叙事声音置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探讨女性叙事声音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学条件。
兰瑟创造性地将叙事声音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
“作者型”叙事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支撑意义的叙述状态。
集体型叙述声音完整版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声音无处不在,它是我们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之一。
而集体型叙述声音则是指多个人共同参与的声音表达形式。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集体型叙述声音的重要性以及其在不同场合中的运用。
一、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定义与特点集体型叙述声音是指多个人在一起发声表达或共同创造声音效果的声音形式。
它具有以下特点:1. 合声效果:多声部共同发声,形成和谐的声音效果。
2. 多样性:来自不同声部的人可以运用不同的音域、音量和音色,营造出丰富多样的声音层次。
3. 共振感:当多个人同时发声时,声音可以相互呼应、互相嵌套,产生共振效果,增强整体声音的饱满感。
4. 集体意识:参与者通过共同的声音表达,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形成共同的情感体验。
二、音乐演出中的集体型叙述声音音乐演出是集体型叙述声音最常见的运用场景之一。
合唱、管弦乐队和合奏等形式都能展现集体声音的魅力。
在合唱中,多个人的声音通过合理的编排和协调,形成一致的旋律和和声效果。
歌曲在合唱团的共同努力下,音符如同一片汪洋大海,唱出动人的旋律。
而在管弦乐队中,各乐器声部的协同演奏构成了宏伟壮丽的交响乐章。
乐手们通过和声、和弦以及和谐的演奏技巧,共同创造出整体声音的奇妙魔力。
无论是合唱、管弦乐队还是其他形式的音乐合奏,集体型叙述声音都能带给观众强烈的听觉享受,让他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感受到音符的力量。
三、戏剧表演中的集体型叙述声音除了音乐演出,戏剧表演也是集体型叙述声音的重要运用领域之一。
在戏剧中,演员们通过集体的声音表达,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表演效果。
合奏音乐、掌声、呐喊声等都是集体声音在戏剧演出中的应用方式。
当演员们齐声呐喊或通过合奏音乐的和声效果,他们可以将观众的情感推到高潮,给予观众强烈的心灵冲击。
此外,在舞台背景音效的运用上,通过多个声音来源的集体声音,可以营造出更加真实感的氛围,使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情节。
四、集体型叙述声音在社会活动中的运用除了音乐演出和戏剧表演,集体型叙述声音还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
/2012.2下半月xie zuo li lun yan jiu写作理论研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时序与叙事逻辑分析倪娟摘要:《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最耐人寻味的短篇小说之一。
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入手探讨小说叙述者的真实身份及时间错序问题,分析叙述中统一的内在逻辑,指出埃米莉人生的真正可悲之处。
关键词:真实面目;叙述声音;时序倒错;逻辑《一支给埃米莉的玫瑰》(下称《玫瑰》)(1930)是素有美国南方作家之称的福克纳的最著名、最耐人寻味的小说之一。
小说以“我们”作为叙述者,刻画了美国南方女子埃米莉历经时代变迁,孤独终老的故事。
小说问世八十年来,无数的评论者对它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可谓众说纷芸。
(笔者也于年初发表过一篇相关的评论)近年来评论家开始关注起作品的形式(刘立辉,王江2007),但绝大多数的评论仍止步于分析总结埃米莉悲剧。
本文拟再从叙事学角度入手,研究叙述者的真实身份,探讨作品中叙述顺序和事件顺序之间的倒错,挖掘作者在叙述者叙事过程中隐藏的内在统一线索,探寻埃米莉人生的真正可悲之处。
一、叙述者的真实面目苏珊·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把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叙述声音”。
按照兰瑟的方法,《玫瑰》中“我们”的叙述应归为共言形式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即“我们”指涉的是一个集体,是一群人。
那么“我们”是否如大多数评论者所认定的那样,代表了小说中那个美国南方城镇(杰斐逊)的全体居民?这样一个似乎昭然若揭的问题,却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叙述者的身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我们”到底指谁?故事一开始“我们”就进入回忆:“埃米莉·格里尔森小姐过世了,我们全镇的人都去送丧。
”既然是“我们全镇人”都参加了,镇民中当然也包括了叙述者。
然而,“我们”又回忆起“思想更为现代的新一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去找埃米莉收税的是“他们”;几十年过去了,撬开她四十年来从没人见到过的一个房间的也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