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常用药对赏析解析
- 格式:ppt
- 大小:7.28 MB
- 文档页数: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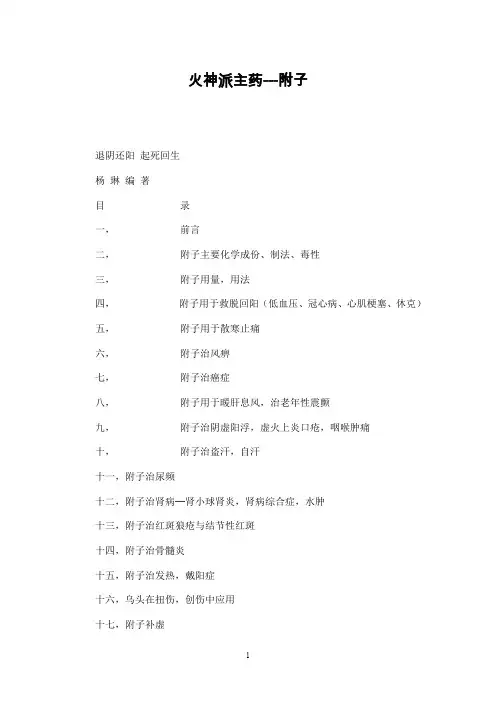
火神派主药---附子退阴还阳起死回生杨琳编著目录一,前言二,附子主要化学成份、制法、毒性三,附子用量,用法四,附子用于救脱回阳(低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休克)五,附子用于散寒止痛六,附子治风痹七,附子治癌症八,附子用于暖肝息风,治老年性震颤九,附子治阴虚阳浮,虚火上炎口疮,咽喉肿痛十,附子治盗汗,自汗十一,附子治尿频十二,附子治肾病─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症,水肿十三,附子治红斑狼疮与结节性红斑十四,附子治骨髓炎十五,附子治发热,戴阳症十六,乌头在扭伤,创伤中应用十七,附子补虚十八,附子治老年病,延年益寿十九,附子简易方一、前言附子为毛茛科乌头属植物乌头块根上的子根。
四川陕西栽培的乌头称天雄。
附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最重要的中药之一。
明医学家张景岳对附子有极精辟而详尽的论述:“…除表里沉寒,厥逆寒噤、温中强阴、暖五脏、回阳气、除呕哕、藿乱、反胃、噎膈、心腹绞痛、胀满、泻利、肢体拘挛、寒邪、湿气、胃寒、虫、寒痰、寒疝、风湿麻痹、阴疸、痈毒、久漏冷疮、格阳喉痹、阳虚、二便不通及妇人经寒不调、小儿慢惊等症。
大能引火归源,制伏虚热。
善助参芪建功,尤赞术地建效。
无论表症里症,但脉细无神,气虚无热者所当急用。
…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散失之阳,引补血药入血份,以药养不足之真阴。
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
引温暖药达下焦,以驱除在里之冷湿。
附子仍阴症要药,中寒夹阴,身虽大热而脉沉者必用之,或厥冷而脉沉细者尤须用之。
有退阴回阳之力,起死回生之功”。
因此把附子称为药中四维,治乱(人体功能紊乱)良将是名符其实的。
不独张景岳有此评论, 医圣张仲景《伤寒论》130方,用附子达21方。
近代名医赵锡武非常推崇《阴证略例》,认为王氏治疗阴证的特点是善用附子,重视温补脾肾。
我每提倡用真武汤不要怕附子用量大,取其鼓动心阳,抑阴邪上乘。
清同治年间,邛崃郑钦安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观其治病,恒以阴阳为纲,阴证则无论吐血、便血、尿血、喉蛾、失眠、牙痛、口臭、便秘,概投以附子、干姜之类效如桴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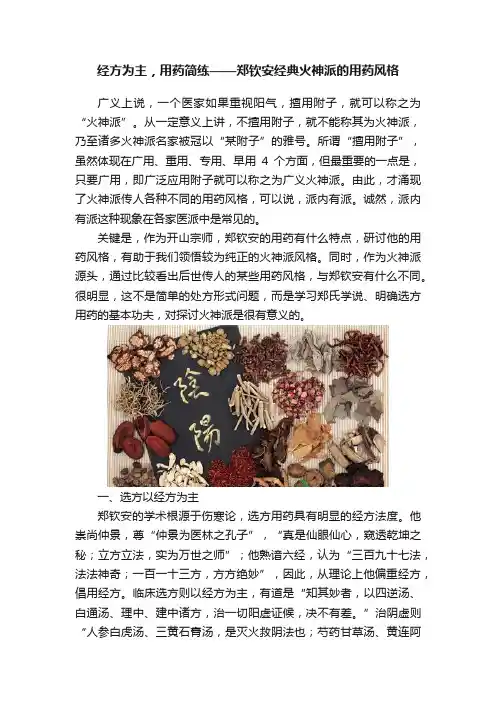
经方为主,用药简练——郑钦安经典火神派的用药风格广义上说,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擅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
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擅用附子,就不能称其为火神派,乃至诸多火神派名家被冠以“某附子”的雅号。
所谓“擅用附子”,虽然体现在广用、重用、专用、早用4个方面,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广用,即广泛应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广义火神派。
由此,才涌现了火神派传人各种不同的用药风格,可以说,派内有派。
诚然,派内有派这种现象在各家医派中是常见的。
关键是,作为开山宗师,郑钦安的用药有什么特点,研讨他的用药风格,有助于我们领悟较为纯正的火神派风格。
同时,作为火神派源头,通过比较看出后世传人的某些用药风格,与郑钦安有什么不同。
很明显,这不是简单的处方形式问题,而是学习郑氏学说、明确选方用药的基本功夫,对探讨火神派是很有意义的。
一、选方以经方为主郑钦安的学术根源于伤寒论,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
他崇尚仲景,尊“仲景为医林之孔子”,“真是仙眼仙心,窥透乾坤之秘;立方立法,实为万世之师”;他熟谙六经,认为“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神奇;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绝妙”,因此,从理论上他偏重经方,倡用经方。
临床选方则以经方为主,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证候,决不有差。
”治阴虚则“人参白虎汤、三黄石膏汤,是灭火救阴法也;芍药甘草汤、黄连阿胶汤,是润燥扶阴法也;四苓滑石阿胶汤、六味地黄汤,是利水育阴法也”。
看得出,大多数选用经方,这一点没有疑义。
郑钦安虽然有时亦称“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于经方,“所引时方,出不得已,非其本怀”(《医法圆通·沈序》)。
因为时方“大抵利于轻浅之疾,而病之深重者万难获效”,终究倡导的是经方。
二、用药精纯不杂《伤寒论》中的方剂用药是简练的,113方仅用药93味,平均药味为4.18味,由3~8味药组成的方剂最为常见,占82.3%。
其药味加减也是十分严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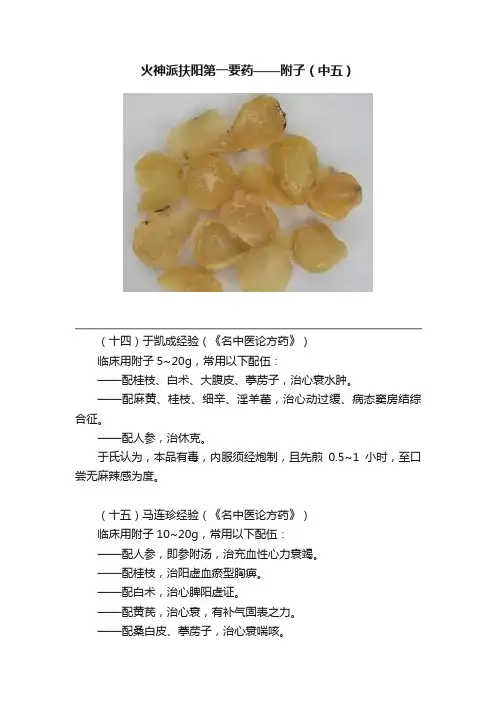
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中五)(十四)于凯成经验(《名中医论方药》)临床用附子5~20g,常用以下配伍:——配桂枝、白术、大腹皮、葶苈子,治心衰水肿。
——配麻黄、桂枝、细辛、淫羊藿,治心动过缓、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配人参,治休克。
于氏认为,本品有毒,内服须经炮制,且先煎0.5~1小时,至口尝无麻辣感为度。
(十五)马连珍经验(《名中医论方药》)临床用附子10~20g,常用以下配伍:——配人参,即参附汤,治充血性心力衰竭。
——配桂枝,治阳虚血瘀型胸痹。
——配白术,治心脾阳虚证。
——配黄芪,治心衰,有补气固表之力。
——配桑白皮、葶苈子,治心衰喘咳。
——配大黄,治心衰,可降气通大肠。
——配水蛭,治心脏病,可逐瘀止痛。
马氏认为,附子之功在于温五脏之阳,其性辛热燥烈。
一般用10g,先煎,根据病情可用至18~20g。
(十六)王乐善经验(《名中医论方药》)临床用附子3~10g,常用以下配伍:——配干姜、炙甘草,治四肢厥逆。
——配人参、白术、炮姜,治中寒呕痢腹痛。
——配甘草、白术、桂枝,治风湿痹证,关节疼痛。
(十七)石景亮经验(《名中医论方药》)临床用附子5~30g,常用以下配伍:——配大枣、沉香、炙甘草、太子参、麦冬、枸杞子,治病态窦房结综合征。
——配茯苓、刘寄奴、白术、白芍、淫羊藿、生姜、仙茅、陈皮、生黄芪、地龙、益母草、玉米须,治脾肾阳虚型肾病综合征。
——配红参、干姜、大枣,治阳虚大汗、休克虚脱。
石氏认为,附子用量30g以上者,需先煎2小时,以减轻其毒性。
(十八)朱良春经验(《名中医论方药》)临床用附子3~6~30g,常用以下配伍:——配人参、麦冬,治感染性休克、心源性休克。
——配党参、炮姜、白术,治脾阳虚之久泻。
——配桂枝、细辛,治风寒湿痹。
——配桃仁、红花、败酱草,治慢性肾炎。
——配黄芪、金刚骨,治慢性肾炎。
朱氏认为,大剂量使用附子,煎时宜加生姜三五片,或再加蜂蜜一匙,以防中毒,也可将附子先煎半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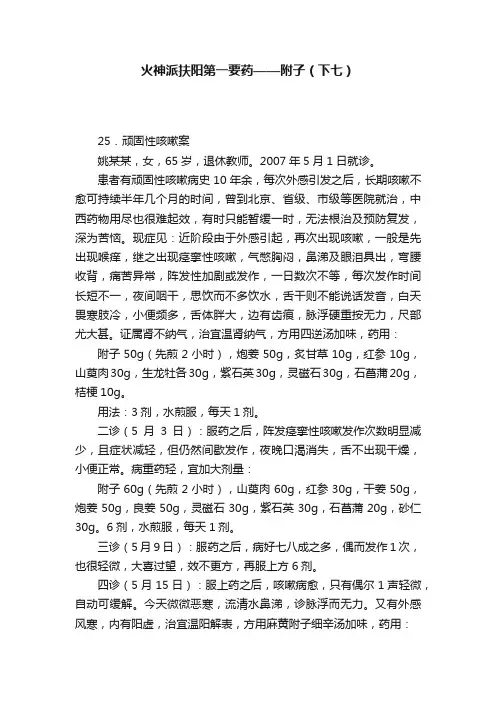
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下七)25.顽固性咳嗽案姚某某,女,65岁,退休教师。
2007年5月1日就诊。
患者有顽固性咳嗽病史10年余,每次外感引发之后,长期咳嗽不愈可持续半年几个月的时间,曾到北京、省级、市级等医院就治,中西药物用尽也很难起效,有时只能暂缓一时,无法根治及预防复发,深为苦恼。
现症见:近阶段由于外感引起,再次出现咳嗽,一般是先出现喉痒,继之出现痉挛性咳嗽,气憋胸闷,鼻涕及眼泪具出,弯腰收背,痛苦异常,阵发性加剧或发作,一日数次不等,每次发作时间长短不一,夜间咽干,思饮而不多饮水,舌干则不能说话发音,白天畏寒肢冷,小便频多,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脉浮硬重按无力,尺部尤大甚。
证属肾不纳气,治宜温肾纳气,方用四逆汤加味,药用:附子50g(先煎2小时),炮姜50g,炙甘草10g,红参10g,山萸肉30g,生龙牡各30g,紫石英30g,灵磁石30g,石菖蒲20g,桔梗10g。
用法:3剂,水煎服,每天1剂。
二诊(5月3日):服药之后,阵发痉挛性咳嗽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且症状减轻,但仍然间歇发作,夜晚口渴消失,舌不出现干燥,小便正常。
病重药轻,宜加大剂量:附子60g(先煎2小时),山萸肉60g,红参30g,干姜50g,炮姜50g,良姜50g,灵磁石30g,紫石英30g,石菖蒲20g,砂仁30g。
6剂,水煎服,每天1剂。
三诊(5月9日):服药之后,病好七八成之多,偶而发作1次,也很轻微,大喜过望,效不更方,再服上方6剂。
四诊(5月15日):服上药之后,咳嗽病愈,只有偶尔1声轻微,自动可缓解。
今天微微恶寒,流清水鼻涕,诊脉浮而无力。
又有外感风寒,内有阳虚,治宜温阳解表,方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药用:麻黄10g,附子60g(先煎2小时),细辛10g,干姜30g,炮姜30g,良姜30g,炙甘草10g,红参10g,半夏20g,桔梗10g。
5剂,水煎服,每天1剂。
复诊:服上方之后,外感解除,仍然恢复服用5月3日处方,并且要求附子加量至75g,每天1剂,越吃感觉精神越好,体力增强,咳嗽未再发作过,此张处方一至吃了约近2个月才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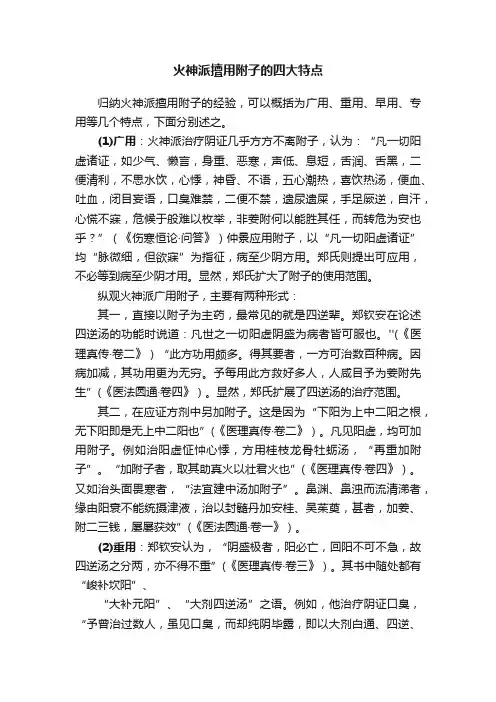
火神派擅用附子的四大特点归纳火神派擅用附子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1)广用:火神派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证,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于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也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凡一切阳虚诸证”均“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
郑氏则提出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才用。
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火神派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
郑钦安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
''(《医理真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
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
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
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
显然,郑氏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证方剂中另加附子。
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上中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
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
例如治阳虚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
“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
又如治头面畏寒者,“法宜建中汤加附子”。
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缘由阳衰不能统摄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茱萸,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2)重用: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
其书中随处都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
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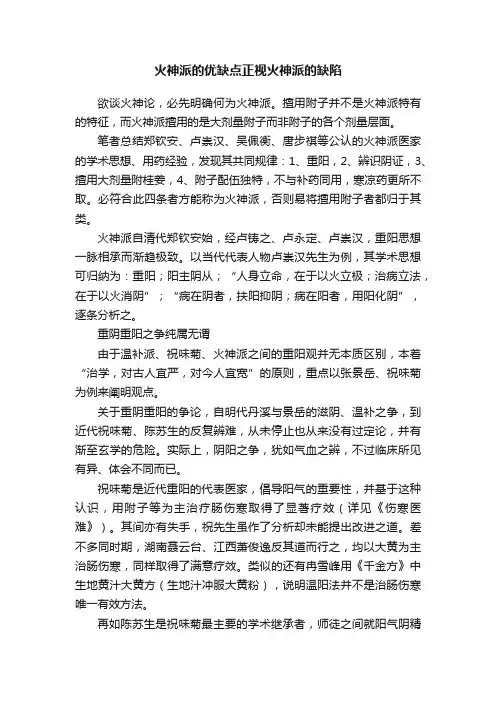
火神派的优缺点正视火神派的缺陷欲谈火神论,必先明确何为火神派。
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剂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个剂量层面。
笔者总结郑钦安、卢崇汉、吴佩衡、唐步祺等公认的火神派医家的学术思想、用药经验,发现其共同规律:1、重阳,2、辨识阴证,3、擅用大剂量附桂姜,4、附子配伍独特,不与补药同用,寒凉药更所不取。
必符合此四条者方能称为火神派,否则易将擅用附子者都归于其类。
火神派自清代郑钦安始,经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重阳思想一脉相承而渐趋极致。
以当代代表人物卢崇汉先生为例,其学术思想可归纳为:重阳;阳主阴从;“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逐条分析之。
重阴重阳之争纯属无谓由于温补派、祝味菊、火神派之间的重阳观并无本质区别,本着“治学,对古人宜严,对今人宜宽”的原则,重点以张景岳、祝味菊为例来阐明观点。
关于重阴重阳的争论,自明代丹溪与景岳的滋阴、温补之争,到近代祝味菊、陈苏生的反复辨难,从未停止也从来没有过定论,并有渐至玄学的危险。
实际上,阴阳之争,犹如气血之辨,不过临床所见有异、体会不同而已。
祝味菊是近代重阳的代表医家,倡导阳气的重要性,并基于这种认识,用附子等为主治疗肠伤寒取得了显著疗效(详见《伤寒医难》)。
其间亦有失手,祝先生虽作了分析却未能提出改进之道。
差不多同时期,湖南聂云台、江西萧俊逸反其道而行之,均以大黄为主治肠伤寒,同样取得了满意疗效。
类似的还有冉雪峰用《千金方》中生地黄汁大黄方(生地汁冲服大黄粉),说明温阳法并不是治肠伤寒唯一有效方法。
再如陈苏生是祝味菊最主要的学术继承者,师徒之间就阳气阴精孰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陈苏生最终还是未接受祝氏的重阳思想,在其晚年时指出:“重阴重阳只是一种宗派观念;始终是一场糊涂官司;擅用温补者自然强调阳重,擅用滋阴者自然强调阴重”(《陈苏生医集篡要》)。
在火神派的推广者张存悌总结的发扬火神派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由现代疾病的基本态势决定的,而未把重阳思想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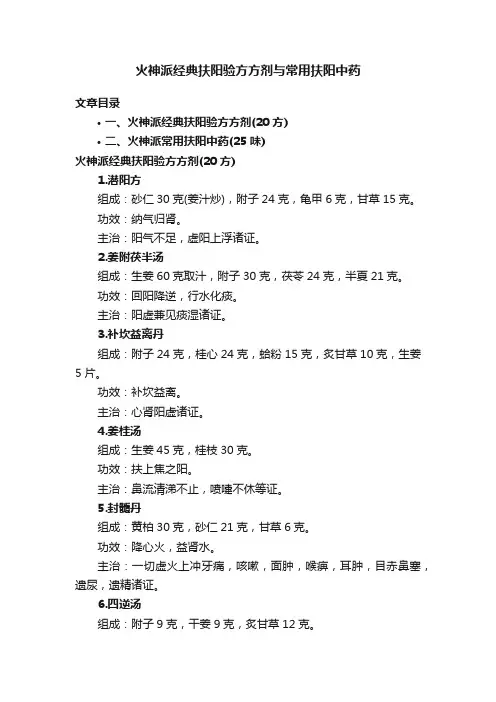
火神派经典扶阳验方方剂与常用扶阳中药文章目录•一、火神派经典扶阳验方方剂(20方)•二、火神派常用扶阳中药(25味)火神派经典扶阳验方方剂(20方)1.潜阳方组成:砂仁30克(姜汁炒),附子24克,龟甲6克,甘草15克。
功效:纳气归肾。
主治:阳气不足,虚阳上浮诸证。
2.姜附茯半汤组成:生姜60克取汁,附子30克,茯苓24克,半夏21克。
功效:回阳降逆,行水化痰。
主治:阳虚兼见痰湿诸证。
3.补坎益离丹组成:附子24克,桂心24克,蛤粉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5片。
功效:补坎益离。
主治:心肾阳虚诸证。
4.姜桂汤组成:生姜45克,桂枝30克。
功效:扶上焦之阳。
主治:鼻流清涕不止,喷嚏不休等证。
5.封髓丹组成:黄柏30克,砂仁21克,甘草6克。
功效:降心火,益肾水。
主治:一切虚火上冲牙痛,咳嗽,面肿,喉痹,耳肿,目赤鼻塞,遗尿,遗精诸证。
6.四逆汤组成:附子9克,干姜9克,炙甘草12克。
功效:回阳救逆。
主治:少阴痛,四肢厥冷,恶寒倦卧,吐利腹痛,下利清谷,神疲欲寐,口不渴,脉沉微细。
7.白通汤组成:葱白4根,干姜10克,附子15克。
功效:回阳救逆。
主治:少阳戴阳证,阴盛于下,虚阳上浮,手足厥冷,面色赤下利,脉微。
8.附子理中汤组成:附子10克,人参5克,干姜10克,炙甘草12克,白术10克。
功效:温阳祛寒,益气健脾。
主治:脾胃虚寒,心腹冷痛,口吐泻利,畏寒,肢冷等证。
9.大建中汤组成:花椒9克,生姜15克,人参6 g,饴糖30克。
功效:温中补虚,降逆止痛。
主治:脾胃虚寒,脘腹疼痛,呕吐,不能饮食等证。
10.金匮肾气丸组成:干地黄15克,山茱萸15克,山药15克,泽泻12克,茯苓12克,丹皮12克,桂枝10克,附子10克。
功效:温补肾阳。
主治:肾阳不足,腰酸脚软,小腹拘急,小便清长,舌质淡而胖,脉虚弱。
11.麻黄汤组成:麻黄9克,桂枝6克,杏仁9克,甘草3克。
功效:辛温解表,宣肺平喘。
主治:外感风寒表实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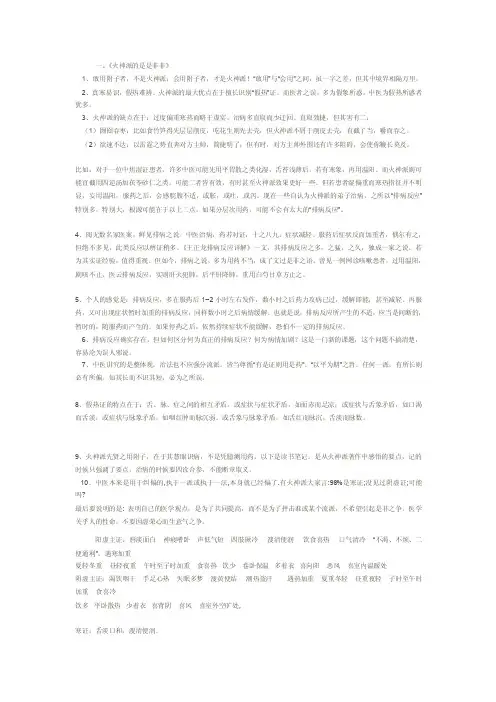
一、《火神派的是是非非》1、敢用附子者,不是火神派;会用附子者,才是火神派!“敢用”与“会用”之间,虽一字之差,但其中境界相隔万里。
2、真寒易识,假热难辨。
火神派的最大优点在于擅长识别“假热”证。
而医者之误,多为假象所惑。
中医为假热所惑者犹多。
3、火神派的缺点在于:过度偏重寒热而略于虚实。
治病多直取而少迂回。
直取效捷,但其害有二:(1)囫囵吞枣:比如食竹笋得先层层削皮,吃花生则先去壳,但火神派不屑于削皮去壳,直截了当,嚼而吞之。
(2)欲速不达:以雷霆之势直奔对方主帅,简捷明了;但有时,对方主帅外围还有许多阻碍,会使你鞭长莫及。
比如:对于一位中焦湿证患者,许多中医可能先用平胃散之类化湿,舌苔浅薄后,若有寒象,再用温阳。
而火神派则可能直截用四逆汤加茯苓砂仁之类。
可能二者皆有效,有时甚至火神派效果更好一些。
但若患者湿偏重而寒热指征并不明显,妄用温阳,服药之后,会感脘腹不适,或胀,或吐,或泻。
现在一些自认为火神派的弟子治病,之所以“排病反应”特别多,特别大,根源可能在于以上二点。
如果分层次用药,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排病反应”。
4、阅无数名家医案,鲜见排病之说。
中医治病,药若对证,十之八九,症状减轻。
服药后症状反而加重者,偶尔有之,但绝不多见,此类反应以痹证稍多。
《王正龙排病反应详解》一文,其排病反应之多,之猛,之久,独成一家之说。
若为其实证经验,值得重视。
但如今,排病之说,多为用药不当,成了文过是非之语。
曾见一例网诊咳嗽患者,过用温阳,剧咳不止,医云排病反应,实则肝火犯肺,后平肝降肺,重用白芍甘草方止之。
5、个人的感觉是:排病反应,多在服药后1--2小时左右发作,数小时之后药力攻病已过,缓解即能,甚至减轻。
再服药,又可出现症状暂时加重的排病反应,同样数小时之后病情缓解。
也就是说,排病反应所产生的不适,应当是间断的,暂时的,随服药而产生的。
如果停药之后,依然持续症状不能缓解,恐怕不一定的排病反应。
6、排病反应确实存在,但如何区分何为真正的排病反应?何为病情加剧?这是一门新的课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容易沦为误人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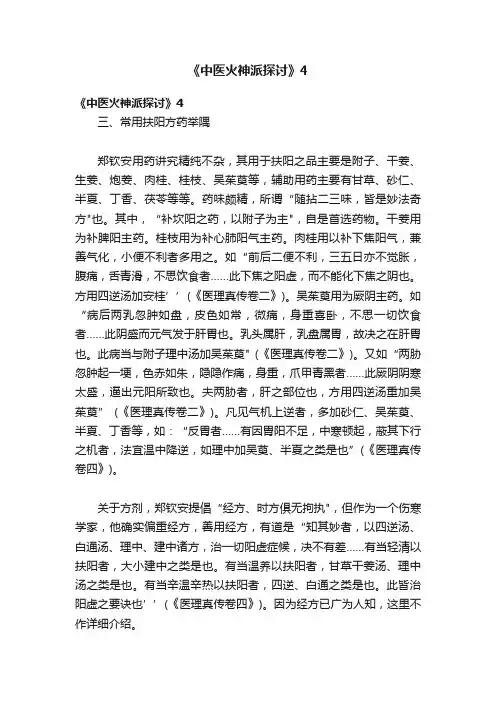
《中医火神派探讨》4《中医火神派探讨》4三、常用扶阳方药举隅郑钦安用药讲究精纯不杂,其用于扶阳之品主要是附子、干姜、生姜、炮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辅助用药主要有甘草、砂仁、半夏、丁香、茯苓等等。
药味颇精,所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也。
其中,“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自是首选药物。
干姜用为补脾阳主药。
桂枝用为补心肺阳气主药。
肉桂用以补下焦阳气,兼善气化,小便不利者多用之。
如“前后二便不利,三五日亦不觉胀,腹痛,舌青滑,不思饮食者……此下焦之阳虚,而不能化下焦之阴也。
方用四逆汤加安桂’’(《医理真传卷二》)。
吴茱萸用为厥阴主药。
如“病后两乳忽肿如盘,皮色如常,微痛,身重喜卧,不思一切饮食者……此阴盛而元气发于肝胃也。
乳头属肝,乳盘属胃,故决之在肝胃也。
此病当与附子理中汤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
又如“两胁忽肿起一埂,色赤如朱,隐隐作痛,身重,爪甲青黑者……此厥阴阴寒太盛,逼出元阳所致也。
夫两胁者,肝之部位也,方用四逆汤重加吴茱萸” (《医理真传卷二》)。
凡见气机上逆者,多加砂仁、吴茱萸、半夏、丁香等,如:“反胃者……有因胃阳不足,中寒顿起,蔽其下行之机者,法宜温中降逆,如理中加吴萸、半夏之类是也”(《医理真传卷四》)。
关于方剂,郑钦安提倡“经方、时方俱无拘执",但作为一个伤寒学家,他确实偏重经方,善用经方,有道是“知其妙者,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治一切阳虚症候,决不有差……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
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
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
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医理真传卷四》)。
因为经方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但四逆汤作为其最常用方,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故将郑氏对此方的论述予以简介。
他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所以大大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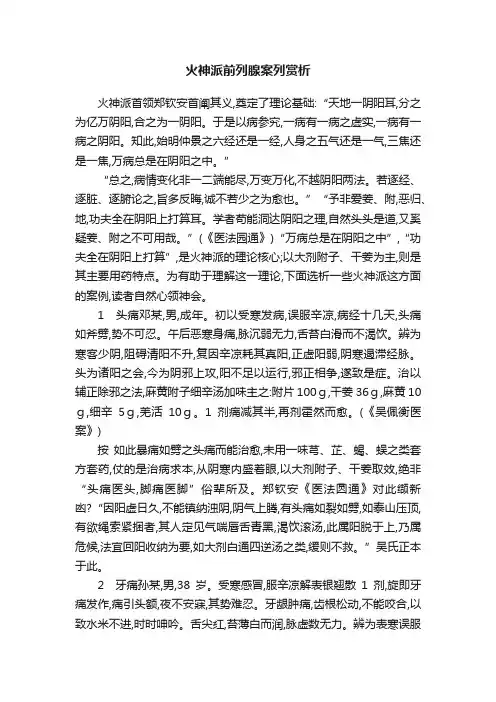
火神派前列腺案列赏析火神派首领郑钦安首阐其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
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
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
”“总之,病情变化非一二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
若逐经、逐脏、逐腑论之,旨多反晦,诚不若少之为愈也。
”“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
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
”(《医法园通》)“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以大剂附子、干姜为主,则是其主要用药特点。
为有助于理解这一理论,下面选析一些火神派这方面的案例,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1 头痛邓某,男,成年。
初以受寒发病,误服辛凉,病经十几天,头痛如斧劈,势不可忍。
午后恶寒身痛,脉沉弱无力,舌苔白滑而不渴饮。
辨为寒客少阴,阻碍清阳不升,复因辛凉耗其真阳,正虚阳弱,阴寒遏滞经脉。
头为诸阳之会,今为阴邪上攻,阳不足以运行,邪正相争,遂致是症。
治以辅正除邪之法,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主之:附片100g,干姜36g,麻黄10g,细辛5g,羌活10g。
1剂痛减其半,再剂霍然而愈。
(《吴佩衡医案》)按如此暴痛如劈之头痛而能治愈,未用一味芎、芷、蝎、蜈之类套方套药,仗的是治病求本,从阴寒内盛着眼,以大剂附子、干姜取效,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俗辈所及。
郑钦安《医法圆通》对此缬新凼?“因阳虚日久,不能镇纳浊阴,阴气上腾,有头痛如裂如劈,如泰山压顶,有欲绳索紧捆者,其人定见气喘唇舌青黑,渴饮滚汤,此属阳脱于上,乃属危候,法宜回阳收纳为要,如大剂白通四逆汤之类,缓则不救。
”吴氏正本于此。
2 牙痛孙某,男,38岁。
受寒感冒,服辛凉解表银翘散1剂,旋即牙痛发作,痛引头额,夜不安寐,其势难忍。
牙龈肿痛,齿根松动,不能咬合,以致水米不进,时时呻吟。
舌尖红,苔薄白而润,脉虚数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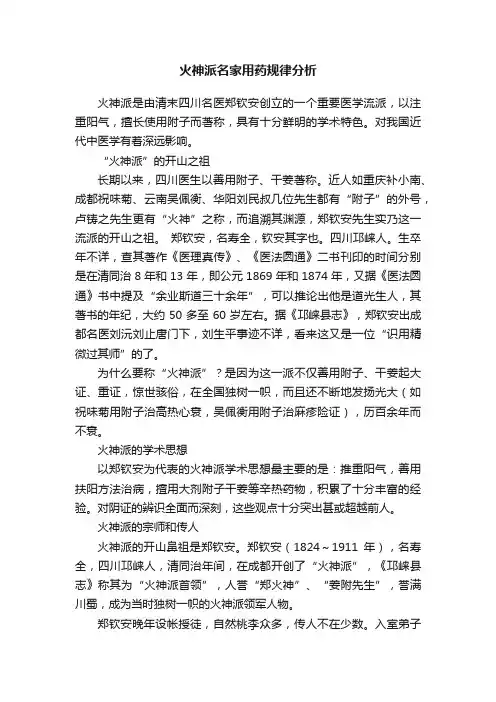
火神派名家用药规律分析火神派是由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创立的一个重要医学流派,以注重阳气,擅长使用附子而著称,具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
对我国近代中医学有着深远影响。
“火神派”的开山之祖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
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卢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钦安,名寿全,钦安其字也。
四川邛崃人。
生卒年不详,查其著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二书刊印的时间分别是在清同治8年和13年,即公元1869年和1874年,又据《医法圆通》书中提及“余业斯道三十余年”,可以推论出他是道光生人,其著书的年纪,大约50多至60岁左右。
据《邛崃县志》,郑钦安出成都名医刘沅刘止唐门下,刘生平事迹不详,看来这又是一位“识用精微过其师”的了。
为什么要称“火神派”?是因为这一派不仅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证、重证,惊世骇俗,在全国独树一帜,而且还不断地发扬光大(如祝味菊用附子治高热心衰,吴佩衡用附子治麻疹险证),历百余年而不衰。
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以郑钦安为代表的火神派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推重阳气,善用扶阳方法治病,擅用大剂附子干姜等辛热药物,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对阴证的辨识全面而深刻,这些观点十分突出甚或超越前人。
火神派的宗师和传人火神派的开山鼻祖是郑钦安。
郑钦安(1824~1911年),名寿全,四川邛崃人,清同治年间,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邛崃县志》称其为“火神派首领”,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成为当时独树一帜的火神派领军人物。
郑钦安晚年设帐授徒,自然桃李众多,传人不在少数。
入室弟子有卢铸之(1876~1963年)先生,光绪十六年从师于郑钦安,“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郑氏学术思想,时人尊为“卢火神”。
儿子卢永定、孙子卢崇汉亦以擅用大剂附子著称,为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可谓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上五)五、附子的合理应用(一)概论附子在临床中应用广泛,用之得当,效果卓著。
但也不可滥用附子,因附子毕竟是辛热有毒之品,用之当掌握其阳虚症的适应症,即辨证为前提的原则。
曾有人统计过某名医一段时间的处方,无一方不用附子,无一人不用附子,还有人撰文认为说什么方药里都可加附子,就像做菜放味精提鲜一样;还有的认为附子就像激素一样,什么病都可以用上一点儿。
这些观点都违背了辨证论治的精神,都是欠妥的。
特别是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加上某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火神派”的火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少数似懂非懂、浅尝辄止的医生,将“火神”的这把“火”与附子应用直接划上了等号,这种不分虚实寒热、阳虚、阴虚的做法,都严重地偏离了郑钦安的思想本意。
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在学好郑钦安医学三书的前提下,把握好阳虚、阴虚证的辨证原则,并且借鉴当代诸多火神派医家具体经验的同时,依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当热则热,当寒则寒,是在分辨阴阳辨证思想的指导下,“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郑钦安),善于抓住阳虚证本质的情况下,应用好扶阳学说理论,而后充分发挥附子的独特作用,而不能把“火神”之“火”看做为一种时尚流行。
有人认为,火神派源于四川一带,这与其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四川盆地属温润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春早、夏热、秋雨的特点,与中国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1月平均温度一般都高出3○C以上,最低温度一般高出10○C以上,造成盆地湿气重、雾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
成都一年中阴雨天多达250~300天,形成了阴雨多、阳光少的气候特点。
正是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形成了四川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川菜都以麻辣味为特点,全国闻名,而川人将附子当菜吃,也就意味着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受性,但是其他地区有多少人能耐受如此剂量的附子就很难说了。
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也并非完全正确。
原因是:郑钦安之亲传弟子卢铸之先生,在郑氏去世之后遵师命,曾3年多时间游遍中国的20多个省,去观察火神派理论是否能在全国合理应用,结果考察后认为,扶阳学说适用于全国各地区。
火神派扶阳临证备要,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介绍中药材硫磺中药硫磺是中药中使用了数千年的药材,常外用治疗疥癣,亦有很多口服的用途。
《中国药典》:硫黄【拼音名】Liú Huánɡ。
【英文名】 SULFUR【别名】硫磺、黄牙、天生黄【来源】本品为自然元素类矿物硫族自然硫,采挖后,加热熔化,除去杂质;或用含硫矿物经加工制得。
【性状】本品呈不规则块状。
黄色或略呈绿黄色。
表面不平坦,呈脂肪光泽,常有多数小孔。
用手握紧置于耳旁,可闻轻微的爆裂声。
体轻,质松,易碎,断面常呈针状结晶形。
有特异的臭气,味淡。
【鉴别】本品燃烧时易熔融,火焰为蓝色,并有二氧化硫的刺激性臭气。
【炮制】硫黄:除去杂质,敲成碎块。
制硫磺:取净硫黄块,与豆腐同煮,至豆腐显黑绿色时,取出,漂净,阴干。
每100kg硫黄,用豆腐200kg 。
【性味】酸,温;有毒。
【归经】归肾、大肠经。
【功能主治】外用解毒杀虫疗疮;内服补火助阳通便。
外治用于疥癣,秃疮,阴疽恶疮;内服用于阳痿足冷,虚喘冷哮,虚寒便秘。
【用法用量】外用适量,研末油调涂敷患处。
内服1.5~3g,炮制后入丸散服。
【注意】孕妇慎服。
【贮藏】置干燥处,防火。
【备注】(1)天生黄为天然升华硫磺。
呈不规则砂状结晶或颗粒状,大小不等,黄绿色,微有玻璃样光泽。
质较硫磺纯净,其性味、功能、主治与硫磺相似。
【摘录】《中国药典》如何评价火神派李可医案的真实性?我没有看过他的书。
但是我父亲是老中医,还有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是在我们当地非常非常有名望的老中医!对于我父亲的那位朋友,我是非常的敬佩他的!记得父亲以前给我推过他的书。
我父亲对他大加赞赏,记得理科好像和他的弟子写过一本关于癌症方面的书籍里面说了,治疗癌症和一切的妇科疾病都要从脾胃入手,真绝了。
火神派,我记得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曾经推过一个叫郑清安的人。
是四川籍的,非常的牛逼。
哦,对了,记得父亲也曾经说过,一定要注意人体的阴阳平衡,一切都得辩证的治疗,不能够一味的扶阳,反而有些人的身体会失衡。
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 (2011-12-19 16:30:37)转载▼标签:杂谈首先是火神派之体。
1)学中医,要从本质上去理解,抛开一切固有的执念,透过层层现象去把握本质,逐渐建立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逐渐的完善,逐渐逼近黄帝内外经,神农本草等四大的理论体系。
任何病症,任何病理,任何医理,任何药理都要把握其中核心本质,具体而抽象,要溯源而上,寻其源头一探究竟,由外而内,抽丝剥见,条分缕析,由表至里,由外而内,内到经络,而后脏腑,而后阴阳;在应用之时顺流而下,由内而外,由阴阳而脏腑,由脏腑而经络,由经络而皮毛肌肤,由抽象而具体。
这个和学任何高深的东西一样。
2)纯阴为鬼,纯阳为仙,阴阳各半而为人,阴阳平和谓之常。
正常人,阴阳平和,升降有序,经络畅通,一气运行无碍,自然无病。
阴阳失和,升降无序,经络不通是以致病。
诊断时,要回归本质,诊断出诊断出哪里过阴,哪里过阳,哪里阴阳虽和但俱虚;哪里升出了问题,哪里降出了问题;哪里经络不通了,哪里经络气血过虚了……………………3)治病时,从经络入手,导引行气(导引),移精易气(祝由),针灸。
祛经络之邪气,除经络之陈疴,使经络渐渐畅通,经络畅通,一气运行无碍,之后自然渐渐正气足,一方面气足自然慢慢的脏腑就强大了,另一方面,邪气去,正气足,自然神明现,之后自然神清气爽,三毒消灭。
4)或从药物入手,同时作用经络和脏腑,调整阴阳,梳理经络。
然药物皆借胃气鼓荡而各寻其经,格归其脏,胃为分金之炉,胃气绝而人必死。
故用药,首先要壮胃气,护胃气。
5)以上,后学小子以为是学医用药的根。
人之存活于世,一切活动都需要一股生生不已的少阳之气来驱动;而此少阳之气,实则由肾中真火催化而生。
打个生火做饭的比方。
拿火种点燃木柴,之后木柴着火,之后用此火做饭。
木柴燃烧的火,正如那驱动人活动生存的少阳之气,木柴则是精微,或饮**微,或先天真水,而点燃木柴的火,这一切的源头则是那肾中一点元阳真火。
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中一)一、张仲景应用乌附的经验(一)用法用量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应用附子非常广泛,《伤寒论》中应用有20方,《金匮要略》中(除去重复的)有13方,共计33方,加上方后加用附子者4方,经方中共有37方中应用附子。
张仲景所用之附子,有生用者,也有炮用者。
生附子多用于少阴病证中,共8方,其它则全用炮附子。
关于炮附子之制法,现代已经无法考证,但从一些专家研究者分析认为,可能是火制的一种,现代多不采用。
张仲景用附子有两个阶段。
小剂量为1~2枚,多用于治疗脉沉微、四肢逆冷等症;大剂量为3~5枚,多用于治疗关节疼痛或心腹大痛等症。
关于张仲景所用之附子相当于现代的多重?考证的结果,近些年来比较公认的张仲景时代的剂量,其一两相当现在的15g左右。
张仲景多是把附子炮,分8片。
已故名医何绍奇先生研究认为,一片附子相当于6~8g左右,如果按照所分为8片,少者也有50g左右,大者也有60g左右,也就是说,张仲景所用之附子的重量,一枚附子折算相当现在的50~60g左右。
如果用的是生附子话,生附子毒性很大,研究认为相当熟附子的5~10倍之多。
按照这样的情况分析,张仲景时代所用治少阴病的生附子,一枚相当现在的250~500g以上。
就是按照张仲景用一枚附子保守的计算50g,二枚也相当100g,三枚相当150g,四枚相当200g,五枚相当250g之多。
表明,张仲景时代用附子的剂量,已经相当很大了,不然的话,不可能写了一本著作《伤寒杂病论》成了经典与圣人。
这表明,火神派学术思想,并非是一种凭空异想天开,而是沿着张仲景的思路与方法,走了下来,并走到了现在。
在煎药方法上,张仲景并未指明先煎,均是与它药同煎。
但张仲景所同煎药物,多数是姜、甘草,特别是炙甘草的量,有时间用的量很大。
这充分地证明,附子与姜、草同煎,足以达到解毒并增效之双重目的,圣人肯定考虑了又考虑,思索了又思索。
而且现代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张仲景的这种附子与姜、草同煎的方法,不仅降解附子毒性疗效确切,而且尚有增效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
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上六)六、附子的中毒与救治(一)中毒原因“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金匮要略》)。
火神派医家推崇附子的效用,而附子的效用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并因此而造福病家、铸就擅用附子的医名。
但是因附子有大毒,用不好会中毒,甚至死亡。
因此,也多有“终身视附子为蛇蝎”而不敢用的医生。
明代的张志聪《本草崇原》中即记载了这样的医者,并记述了他们的劝告:“附子不可服,服之必发狂,而九窍流血;服之必发火,而痈毒顿生;服之必烂五脏,今年服之,明年毒发”。
这种看法,证明他们可能观察到因服附子不当而中毒者,而古往今来,发现附子服用不当而出现医疗事故者,也时有报道。
但仔细分析之,我们也不难发现,中药治病,在于以药物之偏性,来纠正人体的病证之偏。
如果医者在应用附子之时辨证有误,既使辨证无误而当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掌握好用的方法,就有可能发生中毒的反应。
显然,在这些某个环节中,减毒去毒的方法没有充分地掌握,这才是导致附子中毒发生的关键。
1.中毒分析总结各种中毒情况的发生,大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应用附子没有经过医生的安排,自己看书抄方,按书本办事,一些书上没有注明详细的服用方法。
(2)一些非正规大夫,我们所谓的“江湖游医”,才学识浅,为人看病,胡乱下药,由此而导致中毒。
(3)临床辨证功夫不过关,对三阴证的辨识不准确,治三阳病误用附子,而导致中毒。
(4)医生安排病人用药,比如先煎、舌尝无麻味等,而煎药者并非病人本人,由于误用而导致中毒。
(5)一些附子,在炮制等环节,没有严格把关,导致先煎也出现中毒。
(6)一些过敏或是高敏性体质的人,既是小剂量应用附子,也可能出现中毒现象。
因此,我们应用附子的每位医者,如果提高防范意识,了解附子的来源、炮制、配伍、剂量、煎煮、服法等各个环节,既胆大又心细,小心谨慎,防止附子的中毒意外反应完全是可能的。
鉴于此,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猛浪从事,而是以积极科学求实的态度,才能发挥好附子“百药之长”的最佳功效,而避免出现意外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