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大气边界层风洞流场特性的模拟
- 格式:pdf
- 大小:372.72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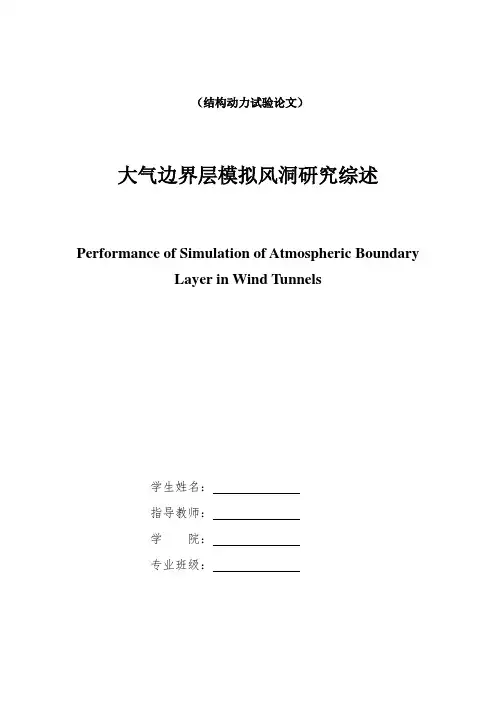
(结构动力试验论文)大气边界层模拟风洞研究综述Performance of Simulation of Atmospheric BoundaryLayer in Wind Tunnels学生姓名:指导教师:学院:专业班级:大气边界层模拟风洞研究综述姓名(大学学院)摘要:本文介绍了大气边界层风洞的发展过程和模拟方法。
大气边界层的模拟方法主要有主动模拟方法和被动模拟方法,前者包括多风扇风洞技术与振动尖塔技术,后者采用尖劈、粗糙元、挡板、格栅等装置进行模拟。
被动模拟技术较为经济、简便,所以得到了广泛采用。
关键词:风洞;大气边界层;主动模拟;被动模拟.Performance of Simulation of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in Wind TunnelsNAME(University)Abstract:In this paper , the simulation of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are introducte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methods of the technology. The methods of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simulation contain active simulation and passive simulation. The active simulation mainly include multiple fans wind tunnel technology and vibratile spire technology. The equipments of the passive simulation main include spire, roughness element, apron and gridiron. The passive simulation technology is simple and economical, so it has been widely used.Key words:wind tunnel;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 er; active simulation; passive simulation.一、引言1940年,美国塔科马悬索桥由于风致振动而破坏的风毁事故,首次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认识到了风的动力作用的巨大威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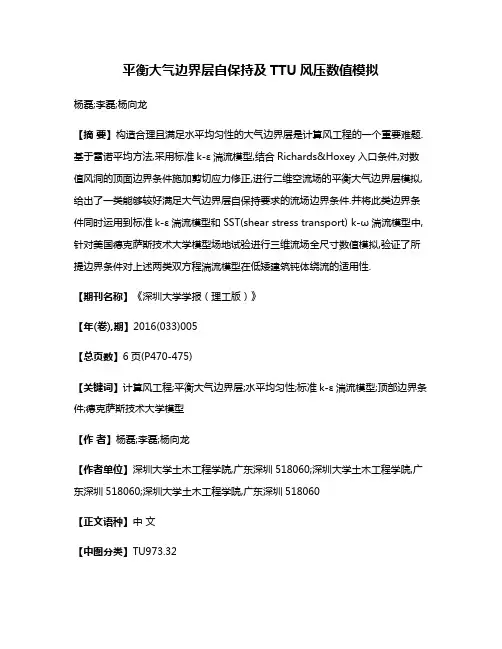
平衡大气边界层自保持及TTU风压数值模拟杨磊;李磊;杨向龙【摘要】构造合理且满足水平均匀性的大气边界层是计算风工程的一个重要难题.基于雷诺平均方法,采用标准k-ε湍流模型,结合Richards&Hoxey入口条件,对数值风洞的顶面边界条件施加剪切应力修正,进行二维空流场的平衡大气边界层模拟,给出了一类能够较好满足大气边界层自保持要求的流场边界条件.并将此类边界条件同时运用到标准k-ε湍流模型和SST(shear stress transport) k-ω湍流模型中,针对美国德克萨斯技术大学模型场地试验进行三维流场全尺寸数值模拟,验证了所提边界条件对上述两类双方程湍流模型在低矮建筑钝体绕流的适用性.【期刊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年(卷),期】2016(033)005【总页数】6页(P470-475)【关键词】计算风工程;平衡大气边界层;水平均匀性;标准k-ε湍流模型;顶部边界条件;德克萨斯技术大学模型【作者】杨磊;李磊;杨向龙【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东深圳518060;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东深圳518060;深圳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广东深圳51806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TU973.32计算风工程(computational wind engineering, CWE)是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方法研究不同类型建筑结构风荷载和风环境的学科.其中,准确模拟大气边界层内的湍流流动是利用数值方法研究结构风特性的重要前提.计算风工程应首先满足大气边界层(atmosphere boundary layer, ABL)的水平均匀性(horizontal homogeneity)要求.水平均匀性是指在没有障碍物的简单边界层流动下,数值风洞内风剖面的物理参数与测量地点无关,即计算域入口处定义的流动物理量(速度、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等),从入口到出口保持一致.满足水平均匀性要求的边界层称为平衡大气边界层.大气边界层的水平均匀性对CFD模拟结果的准确性有显著影响.在数值风洞内平衡大气边界层,影响自保持水平均匀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边界条件、湍流模型、壁面处理和网格划分等方面.Richards等[1-3]提出入流边界、湍流模型和地面粗糙度的综合作用会产生一个内边界层(internal boundary layer, IBL),使得风剖面在到达建筑物之前发生较大的改变;同时研究了来流边界条件的合理给定问题,给出了一组基于标准k-ε湍流模型的入口边界条件(Richards & Hoxey (RH)入口条件).Juretic'等[4]通过研究雷诺应力结合壁面函数的修正,给出了适用于标准k-ω湍流模型的来流边界条件.曾锴[5]基于shear stress transport (SST) k-ω湍流模型,考察了不同入口边界条件的设置对钝体绕流计算结构的影响,提出了入口湍流风剖面自保持的表达方法.杨伟等[6-8]从模型方程本身出发,基于风洞实验数据,推导出一类近似满足k-ε模型自保持边界要求的入口湍动能表达式,并定义了模型常数.顾明等[9]研究了壁面Y+值对平衡大气边界层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近壁面函数,通过近壁面网格来预测湍流的产生能提高模拟的准确性.孙玉航等[10]针对平衡大气边界层,基于标准k-ε湍流模型,通过推导耗散率表达式,并在输运方程中添加源项的方法,得到了一类较为适用的边界条件.对于计算域顶部,常用的边界条件有对称边界条件[11]、速度边界条件[12]、压力出口边界条件[13]和剪切应力边界条件[1,11].顶部边界条件对计算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剪切应力边界条件更符合物理实际,并且在计算域顶部施加剪切应力边界条件确实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然而,正如Hargreaves等[11]指出的,这种边界条件在通用的CFD模拟软件(如Fluent和CFX等)中难以实现,因此,被很多研究者忽略.Richards等[1]提出了通过在靠近顶部边界的一层网格中增加动量和湍流耗散率源项的方法来施加剪切应力的思想,但他们并没有给出相应的源项公式.目前已有的数值模拟研究中,尚未构造出全部主要特征量均能够很好满足水平均匀性的数值风洞.本研究基于标准k-ε湍流模型,采用RH入口条件,提出并验证了一种便于实现并能较好满足大气边界层自保持要求的顶部边界条件.采用此类边界条件对美国德克萨斯技术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 TTU)建筑周围风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将模拟结果与实测数据进行分析对比,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基于ANSYS—Fluent 15.0平台,利用标准k-ε湍流模型,研究顶部边界条件对平衡大气边界层自保持特性的影响.针对无建筑物扰动的空流场特征,采用二维数值模拟以突出重点和提高效率.计算区域尺寸为1 000 m×300 m,计算域内未放置任何障碍物.采用结构网格对计算域进行离散化处理,近地面沿高度方向最小网格大小为0.01 m,竖向增长因子为1.05,网格单元总数约为40 000个,如图1.计算域入口统一采用velocity-inlet边界条件,速度和湍动能以及湍流耗散率的数值利用RH入口条件确定.来流风速剖面u(z)采用对数率表达为湍动能k为湍流耗散率ε为其中,u*为摩擦速度,根据参考高度处的参考风速确定;κ为Von Karman常数,取κ= 0.41; z为离地面的高度; z0为粗糙度长度,取z0=0.01 m;Cμ为k-ε湍流模型常数,取0.09.计算域地面采用固壁边界条件,引入粗糙壁面修正.粗糙度常数Cs、粗糙度高度Ks以及粗糙度长度z0满足式(4),CsKs≈9.793z0其中, Cs=0.5, Ks=20, z0=0.2.出流面采用完全发展出流边界条件为其中, x表示顺流方向; u、 v和w分别为3个方向的速度分量.对于计算域顶部边界条件,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容易在通用CFD模拟软件中实现的施加剪切应力的方法.对紧靠顶部边界的两层网格,直接施加满足式(1)至式(3)的速度、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的条件.通过给定顶部边界附近的物理梯度的方法,达到施加剪切应力的目的.为比较分析顶部边界条件对大气边界层自保持特性的影响,采用4种不同顶部边界条件计算流域顶部,分别为对称边界条件、指定速度和湍动能的速度入口边界条件、静压边界条件以及在计算域顶部施加剪切应力边界条件.流动视为定常不可压缩流,采用速度-压力耦合方式(semi-implict method for pressure-linked equations consistent,SIMPLEC),对流项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进行离散化.当所有相关变量的迭代残差达到平稳且监测的某些典型物理量不再显著变化时,判定计算收敛.为比较各工况下平衡大气边界层效果,选取入流面、入流面下游300和600 m及出流面4个不同观测位置相应的速度、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等关键物理量进行比较.图2为4种不同计算工况下,4个不同观测位置平均速度随高度变化曲线.从图2可见,工况1和工况3的速度曲线在顶部出现了一定的分离,相比工况1的轻微分离,工况3的分离现象更加明显,表明在RH入口条件下,顶部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对速度剖面的水平均匀性有着不利的影响.而工况2和工况4的条件下,各观测位置的速度曲线都能很好的吻合,表现出很好的水平自保持效果.图3为4种不同计算工况下,4个不同观测位置湍动能随高度变化曲线.由图3可见,工况1至工况3的下游截面湍动能在壁面附近均大于入口处,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数值离散格式所引起的.随着高度的增加,湍动能逐渐减小,顶部位置的湍动能均小于入口处.特别是工况1和工况3,顶部位置的湍动能出现了明显的衰减,这表明顶部设置为对称边界条件和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对湍动能剖面的水平均匀性有不利影响,图3(d)所示工况4中,边界层湍动能剖面在大部分区域保持良好,特别是在顶部,基本与入口处完全吻合,而在近地面小范围区域存在一定的误差.这种误差可能与壁面粗糙度的设置有关.入口边界条件所设定的来流中包含的湍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面粗糙性质,而该性质与计算域地面的固壁边界条件所包含的粗糙性质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流场在向下游运动的过程中会反映出该差异性.相比工况1至工况3,工况4在顶部施加剪切应力边界条件后,不但能有效减小计算域顶部的湍动能差异,且能有效降低近地面小范围区域内的湍动能误差.综上分析表明,入口采用RH入口条件,顶部施加剪切应力边界条件,能够获得较好的平衡大气边界层,实现速度、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的自保持性.TTU实际尺寸场地试验由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风工程研究现场实验室于1991年完成[14-15].该实验室建造了一个永久的全尺寸金属建筑用以进行风压的测量.该试验建筑原始尺寸为13.7 m×9.2 m×3.9 m,建筑周围地势开阔平坦,建筑物表面光滑.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场实测数据,该试验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的评估数值模拟方法的基准试验,如图4.其中,1#~11#为测试点.文献[16-17]研究结果表明,SST k-ω湍流模型由于能够有效计算湍流切应力在逆压梯度边界层的输运,更适用于钝体分离流模拟.因此,本研究分别采用标准k-ε湍流模型和SST k-ω湍流模型,边界条件采用第2节工况4的设定,针对TTU试验的90°风攻角进行了三维全尺寸数值模拟,并将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计算域大小为200 m×100 m×50 m.建筑物放置在入口下游80 m处.设建筑物的长、宽、高分别为L、 B和H,模型距上游为9L,距下游为13L,计算域宽度为7.5B,在竖直方向上为12.5H,模型阻塞率为1.1%.计算域采用六面体网格进行划分,网格总数约150万个.图5为两种湍流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与TTU模型场地实测数据的对比.可见,在90°风攻角的典型计算工况下,采用标准k-ε和SST k-ω两种湍流模型得到的计算结果相差不大,与试验数据总体吻合,均落在TTU建筑现场实测数据的包络线范围内.在模型的迎风面,标准k-ε湍流模型略低于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而SST k-ω湍流模型略高,最大偏差为7.4%.对于4#测点之后的钝体绕流分离区,两种湍流模型得到的数值模拟结果均略低于TTU试验结果的平均值.最大偏差出现在4#测点,即建筑物迎风面与顶面相交的尖角分离处,此测点处标准k-ε和SST k-ω两种湍流模型的计算结果基本位于试验结果的下限,与试验平均值的误差分别为9.3%和7.9%.在数值模拟通常较为困难的背风面,计算结果整体与试验数据吻合良好.基于ANSYS—Fluent 15.0中的标准k-ε湍流模型,利用RH入口条件,通过本研究方法对顶面施加剪切应力边界条件,能够获得较好的平衡大气边界层,实现整个流域内速度、湍动能和湍流耗散率的自保持特性.在平衡大气边界层的条件下,采用标准k-ε湍流模型和SST k-ω湍流模型均能够较好地对TTU模型场地试验进行数值模拟,分辨钝体流动特征.[1] Richards P J, Norris S E. Appropriat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computational wind engineering models using the k-ε turbulence model[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1993,s46/s47(93): 145-153.[2] Richards P J, Younis B A. Comments on ‘Prediction of wind-generated pressure distribution around buildings’ by Mathews E H[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1990, 34(1): 107-110. [3] Richards P J, Quinn A D, Parker S. A 6 m cube in an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flow. Part 2, computational studies[J]. Journal of Wind and Structures, 2002, 5(2/3/4): 177-192.[4] Juretic' F, Kozmar H.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the neutrally stratified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flow using the standard k-ε turbulence model[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13, 115:112-120.[5] 曾锴. 计算风工程入口湍流条件改进与分离涡模拟[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7. Zeng Kai. The improvement of inlet turbulence boundary condition in CWE and detached eddy simulation[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7.(in Chinese)[6] 杨伟, 顾明, 陈素琴. 计算风工程中的k-ε模型的一类边界条件[J]. 空气动力学学报, 2005, 23(1): 97-102.Yang Wei, Gu Ming, Chen Suqin. A set of turbulenceboundary condition of k-ε model for CWE[J]. Acta Aerodynamica Sinica, 2005, 23(1): 97-102.(in Chinese)[7] Yang Wei, Quan Yong, Jin Xinyang, et al. Influences of equilibrium atmosphere boundary and turbulence parameter on wind loads of low-risebuildings[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08, 96(10/11): 2080-2092.[8] 杨伟, 金新阳, 顾明, 等. 风工程数值模拟中平衡大气边界层的研究与应用[J]. 土木工程学报, 2007, 40(2): 1-5.Yang Wei, Jin Xinyang, Gu Ming, et al. A study on the self-sustaining equilibrium atmosphere boundary layer in computational wind engineering and its application[J].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Journal,2007,40(2): 1-5.(in Chinese)[9] 顾明, 李孙伟, 周印. 平衡大气边界层的数值模拟和风洞实验[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37(3): 298-302.Gu Ming, Li Sunwei, Zhou Yin.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self-sustaining equilibrium atmosphere boundary layer[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09, 37(3): 298-302.(in Chinese)[10] 孙玉航, 王国砚, 王梦虹. 一类平衡大气边界层边界条件研究[J]. 力学季刊, 2015, 36(2): 328-335.Sun Yuhang, Wang Guoyan, Wang Menghong. A boundary condition of equilibrium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s[J]. Chinese Quarterly of Mechanics, 2015, 36(2): 328-335.(in Chinese)[11] Hargreaves D M, Wright N G. On the use of the k-ε model in commercial CFD software to model the neutral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07,95(5) : 355-369.[12] Blocken B, Stathopoulos T, Carmeliet J. CFD simulation of the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wall function problems[J]. AtmosphericEnvironment, 2007,41(2): 238-252.[13] Kose D A, Fauconnier D, Dick E. ILES of flow over low-rise buildings: Influence of inflow conditions on the quality of the mean pressure distribution prediction[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11,99(10): 1056-1068.[14] Levitan M L, Mehta K C, Vann W P. Field measurements of pressures on the texas tech building[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1991, 38(10/11): 227-234.[15] Levitan M L, Mehta K C. Texas tech field experiments for wind loads part 1: building and pressure measuring system[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1992, 43(1/2/3): 1565-1576. [16] Wilcox D C. Turbulence modeling for CFD[M]3rd ed. Los Angeles, USA: DCW Industries, Inc., 1994.[17] Taghinia J, Rahman M, Siikonen T. Simulation of indoor airflow with RAST and SST-SAS models: a comparative study[J]. Building Simulation, 2015, 8(3): 297-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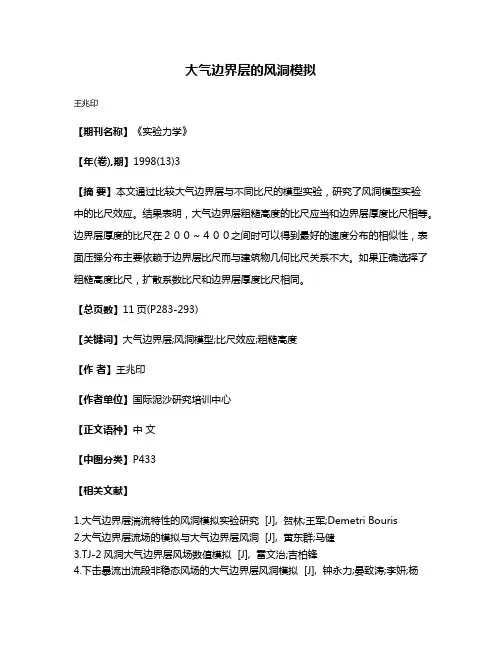
大气边界层的风洞模拟
王兆印
【期刊名称】《实验力学》
【年(卷),期】1998(13)3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大气边界层与不同比尺的模型实验,研究了风洞模型实验
中的比尺效应。
结果表明,大气边界层粗糙高度的比尺应当和边界层厚度比尺相等。
边界层厚度的比尺在200~400之间时可以得到最好的速度分布的相似性,表面压强分布主要依赖于边界层比尺而与建筑物几何比尺关系不大。
如果正确选择了粗糙高度比尺,扩散系数比尺和边界层厚度比尺相同。
【总页数】11页(P283-293)
【关键词】大气边界层;风洞模型;比尺效应;粗糙高度
【作者】王兆印
【作者单位】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P433
【相关文献】
1.大气边界层湍流特性的风洞模拟实验研究 [J], 贺林;王军;Demetri Bouris
2.大气边界层流场的模拟与大气边界层风洞 [J], 黄东群;马健
3.TJ-2风洞大气边界层风场数值模拟 [J], 雷文治;吉柏锋
4.下击暴流出流段非稳态风场的大气边界层风洞模拟 [J], 钟永力;晏致涛;李妍;杨
小刚;蒋森
5.海上采油平台锚泊状态和拖航状态海面上大气边界层模拟以及海面表层中海流模拟的风洞试验 [J], 施宗城;张大春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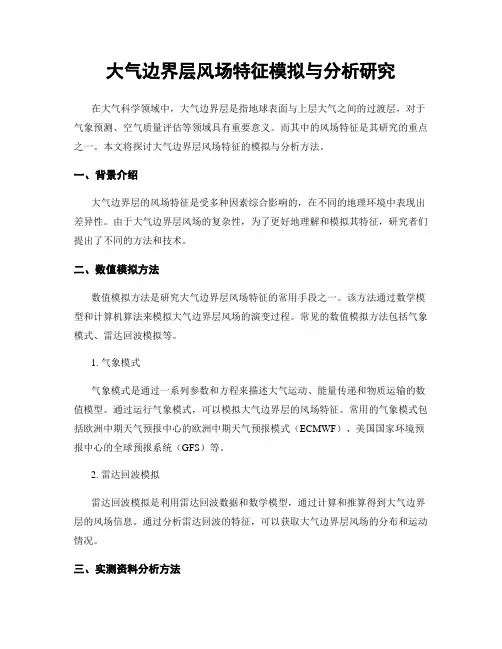
大气边界层风场特征模拟与分析研究在大气科学领域中,大气边界层是指地球表面与上层大气之间的过渡层,对于气象预测、空气质量评估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而其中的风场特征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
本文将探讨大气边界层风场特征的模拟与分析方法。
一、背景介绍大气边界层的风场特征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表现出差异性。
由于大气边界层风场的复杂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模拟其特征,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和技术。
二、数值模拟方法数值模拟方法是研究大气边界层风场特征的常用手段之一。
该方法通过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算法来模拟大气边界层风场的演变过程。
常见的数值模拟方法包括气象模式、雷达回波模拟等。
1. 气象模式气象模式是通过一系列参数和方程来描述大气运动、能量传递和物质运输的数值模型。
通过运行气象模式,可以模拟大气边界层的风场特征。
常用的气象模式包括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模式(ECMWF)、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的全球预报系统(GFS)等。
2. 雷达回波模拟雷达回波模拟是利用雷达回波数据和数学模型,通过计算和推算得到大气边界层的风场信息。
通过分析雷达回波的特征,可以获取大气边界层风场的分布和运动情况。
三、实测资料分析方法除了数值模拟方法外,实测资料的分析也是研究大气边界层风场特征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各种地面、航空、卫星观测站点所获取的实测数据,可以对大气边界层的风场特征进行分析。
1. 地面观测站点地面观测站点是通过建立气象观测站网络,采集并记录大气各种要素的实测资料。
通过对地面观测站点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到不同地理环境中大气边界层风场的特征。
2. 航空观测资料航空观测资料是通过飞机或无人机等航空平台所采集的数据。
通过对航空观测资料的分析,可以获取大气边界层风场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情况,进而揭示其垂直结构特征。
3. 卫星观测资料卫星观测资料是通过卫星对地球表面进行遥感探测所获取的数据。
卫星观测资料具有广覆盖区域、高时空分辨率的特点,通过对卫星观测资料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大气边界层风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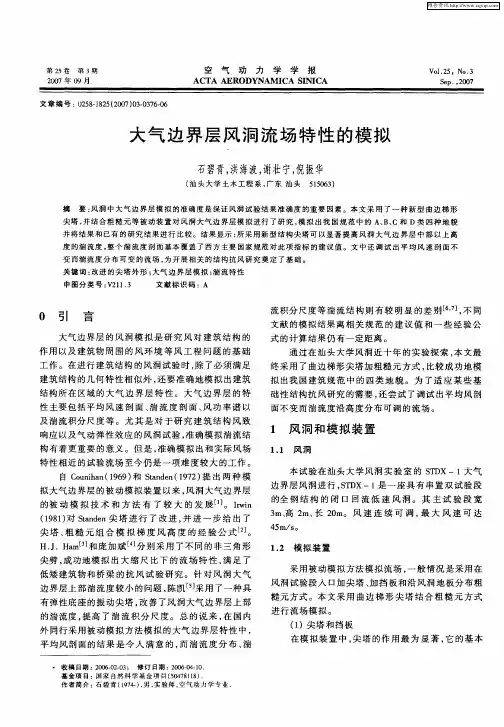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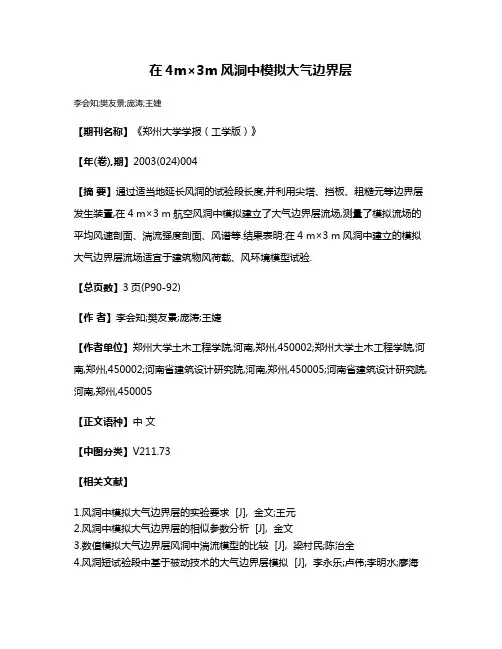
在4m×3m风洞中模拟大气边界层
李会知;樊友景;庞涛;王婕
【期刊名称】《郑州大学学报(工学版)》
【年(卷),期】2003(024)004
【摘要】通过适当地延长风洞的试验段长度,并利用尖塔、挡板、粗糙元等边界层发生装置,在4 m×3 m航空风洞中模拟建立了大气边界层流场,测量了模拟流场的平均风速剖面、湍流强度剖面、风谱等.结果表明:在4 m×3 m风洞中建立的模拟大气边界层流场适宜于建筑物风荷载、风环境模型试验.
【总页数】3页(P90-92)
【作者】李会知;樊友景;庞涛;王婕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河南,郑州,450002;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河南,郑州,450002;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5;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V211.73
【相关文献】
1.风洞中模拟大气边界层的实验要求 [J], 金文;王元
2.风洞中模拟大气边界层的相似参数分析 [J], 金文
3.数值模拟大气边界层风洞中湍流模型的比较 [J], 梁村民;陈治全
4.风洞短试验段中基于被动技术的大气边界层模拟 [J], 李永乐;卢伟;李明水;廖海
黎
5.在1.4米航空风洞中模拟大气边界层 [J], 李会知;刘忠玉;郑冰;吴义章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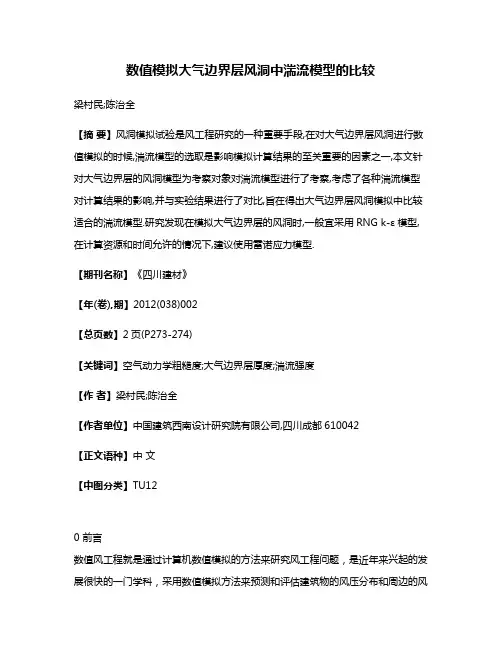
数值模拟大气边界层风洞中湍流模型的比较梁村民;陈治全【摘要】风洞模拟试验是风工程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对大气边界层风洞进行数值模拟的时候,湍流模型的选取是影响模拟计算结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针对大气边界层的风洞模型为考察对象对湍流模型进行了考察,考虑了各种湍流模型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并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旨在得出大气边界层风洞模拟中比较适合的湍流模型.研究发现在模拟大气边界层的风洞时,一般宜采用RNG k-ε模型,在计算资源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使用雷诺应力模型.【期刊名称】《四川建材》【年(卷),期】2012(038)002【总页数】2页(P273-274)【关键词】空气动力学粗糙度;大气边界层厚度;湍流强度【作者】梁村民;陈治全【作者单位】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成都61004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TU120 前言数值风工程就是通过计算机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风工程问题,是近年来兴起的发展很快的一门学科,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来预测和评估建筑物的风压分布和周边的风环境问题已越来越被学术界和工程界所接受。
风洞模拟试验是风工程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边界层风洞中正确复现大气边界层流动特性,是试验结果可信的必要条件,也是风工程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
本文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用数值模拟的方法(CFD)对风洞中的大气边界层进行了研究,模拟了在风洞中粗糙元和大气边界层之间的关系。
进行数值模拟时的主要手段是CFD技术,但在进行模拟时有诸多因素会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收敛性和精确性,如湍流模型、边界条件、网格划分等等。
其中湍流模型的合理选择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也引起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本文就是通过选取钝体绕流模拟过程中常见的湍流模型,包括RNG κ-ε模型、realizabl eκ-ε模型、SSTκ-ω模型、标准κ-ω模型、RSM模型,来研究风洞中第二试验段得到的风速廓线,通过与试验中得到的风速廓线的比较,选取合适的湍流模型对大气边界层风洞进行模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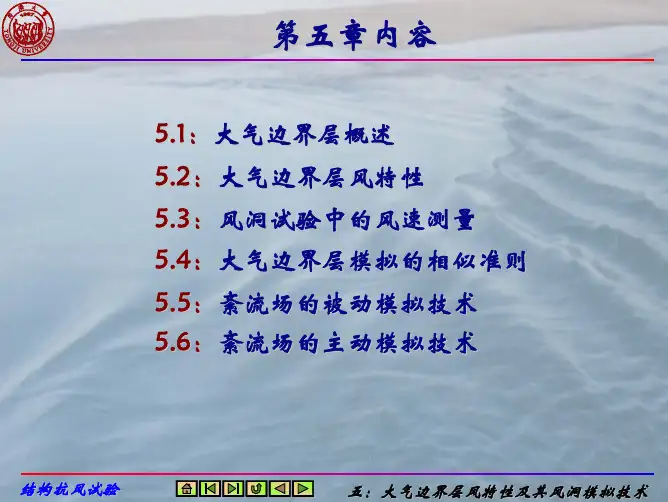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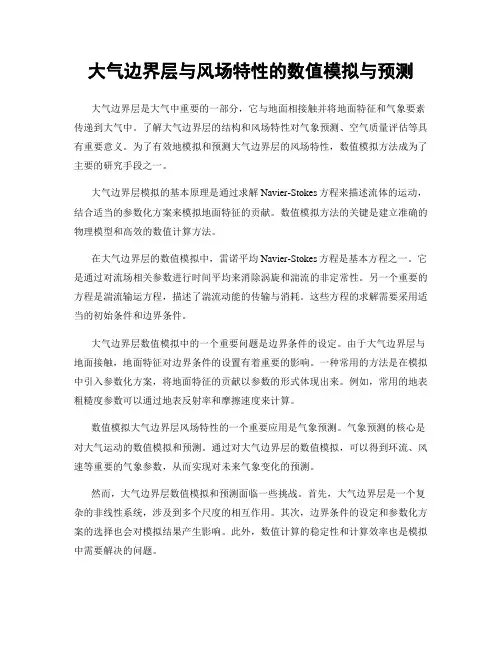
大气边界层与风场特性的数值模拟与预测大气边界层是大气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与地面相接触并将地面特征和气象要素传递到大气中。
了解大气边界层的结构和风场特性对气象预测、空气质量评估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有效地模拟和预测大气边界层的风场特性,数值模拟方法成为了主要的研究手段之一。
大气边界层模拟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求解Navier-Stokes方程来描述流体的运动,结合适当的参数化方案来模拟地面特征的贡献。
数值模拟方法的关键是建立准确的物理模型和高效的数值计算方法。
在大气边界层的数值模拟中,雷诺平均Navier-Stokes方程是基本方程之一。
它是通过对流场相关参数进行时间平均来消除涡旋和湍流的非定常性。
另一个重要的方程是湍流输运方程,描述了湍流动能的传输与消耗。
这些方程的求解需要采用适当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大气边界层数值模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边界条件的设定。
由于大气边界层与地面接触,地面特征对边界条件的设置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在模拟中引入参数化方案,将地面特征的贡献以参数的形式体现出来。
例如,常用的地表粗糙度参数可以通过地表反射率和摩擦速度来计算。
数值模拟大气边界层风场特性的一个重要应用是气象预测。
气象预测的核心是对大气运动的数值模拟和预测。
通过对大气边界层的数值模拟,可以得到环流、风速等重要的气象参数,从而实现对未来气象变化的预测。
然而,大气边界层数值模拟和预测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大气边界层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涉及到多个尺度的相互作用。
其次,边界条件的设定和参数化方案的选择也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
此外,数值计算的稳定性和计算效率也是模拟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数值模拟方法。
例如,引入多尺度模拟方法可以更好地捕捉到大气边界层的尺度特征。
同时,通过数据同化技术将实测数据与数值模拟结果相结合,可以提高模拟和预测的准确性。
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高性能计算平台也为大气边界层的数值模拟提供了更强的计算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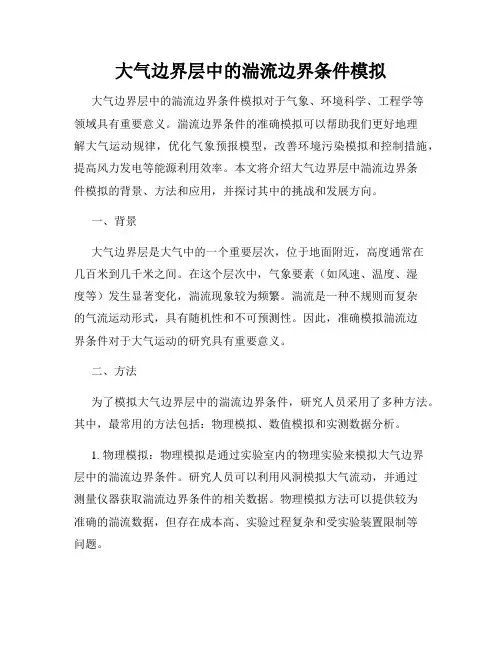
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边界条件模拟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边界条件模拟对于气象、环境科学、工程学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湍流边界条件的准确模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气运动规律,优化气象预报模型,改善环境污染模拟和控制措施,提高风力发电等能源利用效率。
本文将介绍大气边界层中湍流边界条件模拟的背景、方法和应用,并探讨其中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一、背景大气边界层是大气中的一个重要层次,位于地面附近,高度通常在几百米到几千米之间。
在这个层次中,气象要素(如风速、温度、湿度等)发生显著变化,湍流现象较为频繁。
湍流是一种不规则而复杂的气流运动形式,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因此,准确模拟湍流边界条件对于大气运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方法为了模拟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边界条件,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方法。
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包括:物理模拟、数值模拟和实测数据分析。
1. 物理模拟:物理模拟是通过实验室内的物理实验来模拟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边界条件。
研究人员可以利用风洞模拟大气流动,并通过测量仪器获取湍流边界条件的相关数据。
物理模拟方法可以提供较为准确的湍流数据,但存在成本高、实验过程复杂和受实验装置限制等问题。
2. 数值模拟:数值模拟是通过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湍流边界条件。
研究人员可以建立基于流体力学方程的数值模型,并使用数值计算方法求解得到湍流边界条件。
数值模拟方法可以有效地模拟湍流边界条件,但也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高精度的数值算法。
3. 实测数据分析:实测数据分析是通过现场观测获取大气边界层中湍流边界条件的相关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人员可以借助气象监测站、气球观测、卫星遥感等手段获取湍流边界条件的实测数据。
实测数据分析方法可以提供真实的湍流边界条件数据,但存在获取数据难、站点稀疏等问题。
三、应用湍流边界条件模拟在气象、环境科学、工程学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1. 气象预报模型:大气边界层中湍流边界条件的准确模拟可以帮助气象学家改善天气预报模型的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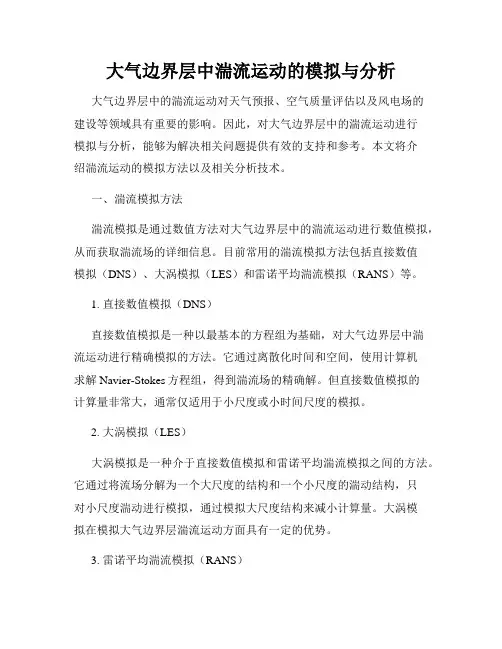
大气边界层中湍流运动的模拟与分析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运动对天气预报、空气质量评估以及风电场的建设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对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运动进行模拟与分析,能够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参考。
本文将介绍湍流运动的模拟方法以及相关分析技术。
一、湍流模拟方法湍流模拟是通过数值方法对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运动进行数值模拟,从而获取湍流场的详细信息。
目前常用的湍流模拟方法包括直接数值模拟(DNS)、大涡模拟(LES)和雷诺平均湍流模拟(RANS)等。
1. 直接数值模拟(DNS)直接数值模拟是一种以最基本的方程组为基础,对大气边界层中湍流运动进行精确模拟的方法。
它通过离散化时间和空间,使用计算机求解Navier-Stokes方程组,得到湍流场的精确解。
但直接数值模拟的计算量非常大,通常仅适用于小尺度或小时间尺度的模拟。
2. 大涡模拟(LES)大涡模拟是一种介于直接数值模拟和雷诺平均湍流模拟之间的方法。
它通过将流场分解为一个大尺度的结构和一个小尺度的湍动结构,只对小尺度湍动进行模拟,通过模拟大尺度结构来减小计算量。
大涡模拟在模拟大气边界层湍流运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3. 雷诺平均湍流模拟(RANS)雷诺平均湍流模拟是一种通过对时间和空间进行平均,将湍流场表示为平均量和脉动量的和的方法。
它通过求解雷诺平均Navier-Stokes方程和湍流能量方程,得到湍流场的平均解。
雷诺平均湍流模拟在计算上相对简单,适用于大尺度湍流的模拟。
二、湍流分析技术湍流模拟得到的湍流场数据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到有用的信息。
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湍流分析技术。
1. 自相关函数自相关函数是一种分析湍流场中各点相关性的方法。
它可以通过计算不同点之间的相关性来获取湍流运动的相关长度。
自相关函数可以用于描述湍流场的时空结构。
2. 能谱分析能谱分析是一种通过计算湍流场不同频率分量的能量来了解湍流场特性的方法。
它可以用于表征湍流场的能量分布情况和主导长度尺度。
大气边界层中的风场特性研究大气边界层是指地球表面与大气中上层之间存在明显温度、湿度、风速及其他气象元素变化的层次。
研究边界层中的风场特性对于理解大气运动、气象灾害的形成机制以及风能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大气边界层中风场的特性。
一、大气边界层简介大气边界层是地球表面到几千米以上高度的大气中相对较薄的一部分。
其上部是自由大气,下部是陆地或海洋。
大气边界层主要受到地表摩擦力和辐射作用的影响,形成了特殊的气象环境。
二、边界层中的风场特性1. 线性风场和湍流风场大气边界层中的风场可以分为线性风场和湍流风场。
线性风场是指在平稳的大气条件下,风速和风向呈直线分布。
湍流风场则是受到地表摩擦力和大气不稳定性的共同作用,风速和风向均存在相对明显的变化。
2. 影响风场的因素边界层中的风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表摩擦力、地形起伏、大气湍流、热力和动力过程等。
地表摩擦力是边界层风场变化的主要原因,地表粗糙度和风速之间的关系对边界层风场起到重要作用。
3. 风速和风向的时空变化在大气边界层中,风速和风向的时空变化较为显著。
在水平方向上,风速随着高度增加而逐渐增大,同时风向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在垂直方向上,风速和风向的变化较为复杂,通常表现为离地面越远,风速越大,风向的变化也越大。
4. 大气边界层中的风能利用由于大气边界层中风速和风向的变化特性,使得风能利用成为一种可行的可再生能源。
通过建立风电场,可以利用边界层中的风能进行发电,为人们提供清洁、可持续的能源。
三、风场特性研究的意义研究大气边界层中的风场特性对于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于气象灾害的研究和预测,了解边界层中的风场特性可以提前预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减轻灾害损失。
其次,风能利用是可再生能源的一种重要形式,研究风场特性可以帮助优化风电场的设计和机组布局,提高风能的利用效率。
此外,对于空气污染的传输和扩散研究也需要深入了解边界层风场的变化规律。
结论大气边界层中的风场特性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大气运动和气象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港口地貌大气边界层风洞试验模拟
白景峰;胡传新;洪宁宁
【期刊名称】《水道港口》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尖劈和粗糙元边界层模拟技术广泛地应用于风洞试验中的大气边界层模拟。
针对港口靠近海洋,附近建筑物较为稀疏的地貌特点,本文参考行业规范,选取符合港口地貌的A类和B类流场,较为全面的考虑了大气边界层流场特性,在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TKS-1边界层风洞对港口工程领域常用的几种流场成功进行了模拟。
【总页数】4页(P75-78)
【作者】白景峰;胡传新;洪宁宁
【作者单位】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水路交通环境保护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天津300456;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水路交通环境保护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天津300456;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水路交通环境保护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天津30045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U216.4
【相关文献】
1.建筑结构大气边界层风场风洞试验模拟 [J], 王洪兴;张彦军
2.风洞虚拟飞行试验模拟方法研究 [J], 李浩;赵忠良;范召林
3.飞机结冰风洞试验模拟研究 [J], 范洁川;于涛
4.飞机结冰风洞试验模拟研究 [J], 范洁川;于涛
5.细长体风洞试验模拟 [J], 孙鹏;母德伟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大气边界层湍流特性的风洞模拟实验研究边界层是近地面气体与地面之间的区域,通常定义为自由流的速度较小的区域,它包含了流体较强的水平和垂直的运动,这些运动包含大量的涡旋和湍流。
了解边界层内的湍流特性对于气象学、航空航天和建筑学等学科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风洞模拟实验可以提供一个便捷、可控、可重复的实验环境,用来研究边界层湍流特性。
本文将介绍一项大气边界层湍流特性的风洞模拟实验研究。
首先,将简要介绍实验的目的和重要性。
其次,将介绍实验的设计方案和程序。
接着,将介绍数据处理方法,分析实验结果。
最后,将讨论实验结果的意义和应用前景。
一、实验的目的和重要性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是一种强烈的流动行为,其动力学复杂而普遍存在。
湍流对空气质量、能源和温室效应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边界层湍流也是大型建筑和飞机等复杂工程设计的重要因素。
因此,了解边界层内的湍流特性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工程应用价值。
本实验的目的就是通过风洞模拟实验,对大气边界层中的湍流特性进行研究,为相关领域提供参考和指导。
二、实验的设计方案和程序1. 实验设计方案本实验选取直井状风洞为研究工具,它能够较好地模拟出大气边界层的流动情况。
在直径为1.5米,高为5.5米的风洞内,通过两个放置在风洞底部和顶部的网格板和两个旋转的切片风扇,模拟出边界层的结构和湍流特性。
在风洞内部安装压力传感器和热敏电阻器,用来测量边界层中的压力、温度和速度。
2. 实验程序a. 执行基准实验在进行边界层湍流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进行基准实验,用来检查风洞系统的运行状态和数据的获取准确性。
在基准实验中,我们分别分别测量风洞内的压力、温度和速度,并将数据与标准值进行对比。
b. 模拟大气边界层湍流实验在进行模拟大气边界层湍流实验时,我们将根据实际环境的特点来设置初始条件,比如制造不同形状和尺寸的障碍物,用来模拟大气中存在的复杂地形和建筑物。
然后通过调节风洞内的风速、风向和湍流程度,模拟出边界层中的湍流特性。
收稿日期:2019-02-15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478180;51778225),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51478180;51778225)作者简介:刘志文(1975—),男,山西阳高人,湖南大学副教授,工学博士†通讯联系人,E-mail :*****************.cn*第47卷第7期2020年7月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Vol.47,No.7Jul.2020DOI :10.16339/ki.hdxbzkb.2020.07.002文章编号:1674—2974(2020)07—0010—11基于边界层风洞的下击暴流稳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刘志文1,2†,陈以荣1,辛亚兵1,陈政清1,2(1.湖南大学风工程与桥梁工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长沙410082;2.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针对下击暴流稳态风场模拟问题,基于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首先分别采用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对下击暴流风场进行数值模拟,对下击暴流风场特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据下击暴流对桥梁结构作用主要受水平风速影响的特点,采用二维数值模拟方法对边界层风洞中设置倾斜平板模拟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场进行了研究.最后,设计并加工了边界层风洞下击暴流水平风速模拟试验装置,在边界层风洞中进行了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场模拟试验,并将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和已有文献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下击暴流风场的二维冲击射流模型模拟结果与三维冲击射流模型模拟结果吻合较好,即二维冲击射流模型是一种有效的下击暴流风场简化模拟方法;在边界层风洞中设置倾斜平板所模拟的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场数值模拟结果和风洞试验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与冲击射流模型数值模拟结果和现场实测结果均吻合较好,即在边界层风洞中设置倾斜平板可模拟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稳态风场特性.关键词: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场模拟;冲击射流模型;倾斜平板;数值模拟;风洞试验中图分类号:U441.2文献标志码:ANumerical Simulation on Steady Wind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Downburst Based on Atmosphere Boundary Layer Wind TunnelLIU Zhiwen 1,2†,CHEN Yirong 1,XIN Yabing 1,CHEN Zhengqing 1,2(1.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Win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China;2.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 :For the problems of downburst steady wind field simulation,based o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CFD)methods,firstly,2-dimensional (2-D)and 3-dimensional (3-D)impinging jet models were used to simulate thedownburst wind field,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wnburst wind field were studied.On this basis,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effect of downburst on bridge structure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horizontal wind speed,the horizontal wind field of downburst in Boundary Layer Wind Tunnel (BLWT)with inclined plate was studied by using 2-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Finally,the horizontal wind filed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device of the downburst in the BLWT wa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and the horizontal wind field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the downburst was carried out in the BLWT.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is刘志文等:基于边界层风洞的下击暴流稳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下击暴流是指雷暴云中局部性的强下沉气流冲击地面后,沿径向产生的直线型水平风速,最大风速可达240km/h(约为66.7m/s).根据下击暴流影响的范围分为微下击暴流(半径小于4km)和宏下击暴流(半径大于4km),下击暴流具有突发性,且风速变化剧烈.下击暴流会对输电线塔、建筑结构等产生破坏.已有统计表明83%的输电线塔系统破坏事故是由于下击暴流引起的.近年来研究表明,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结构风荷载控制值是由雷暴风确定[1-2]. Letchford和Lombardo建议在结构设计规范中考虑下击暴流作用[3].下击暴流风特性研究主要包括现场实测、试验模拟和数值模拟研究等.Fujita与Mccarthy等[4-5]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现场实测发现并定义了下击暴流,即强下沉气流引起的近地面强风,并总结了一系列下击暴流流场特点.由于下击暴流发生时间和发生地点随机性较强,生命周期短,覆盖范围小等特点,现场实测难度较大.Hjelmfelt[6]通过总结宏下击暴流实测数据,指出采用冲击射流装置可以实现在试验室中模拟下击暴流流场.Wood等[7]采用了连续稳态冲击射流模型,分别进行了数值模拟与试验模拟,得到了下击暴流作用下考虑地形影响的加速因子.Letchford等[8]从工程角度回顾了下击暴流研究,指出采用稳态冲击射流模型模拟下击暴流流场将丢失下击暴流流场环形涡与阵风峰面等动态特点.此外,Letchford等[9]对试验装置进行了改进,实现了喷嘴的移动,研究了喷嘴固定与喷嘴移动时下击暴流的流场特性,以及在两种流场中的立方体块表面压力分布情况.Mcconville 等[10]开发了一套试验装置,采用9组风扇来产生下沉气流,通过8组三角形襟翼实现了瞬态下击暴流的模拟.此外,西安大略大学开发的WindEEE风洞,是首座三维风洞实验室,可实现龙卷风、下击暴流等非良态风模拟[11].Butler和Kareem[12]利用旋转平板对稳态下击暴流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拟.Moustafa等设计了一套多道可独立运动并实现高速旋转的斜板组成的系统,可以在风洞中模拟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场,斜板运动方式采用CFD方法进行了优化,风洞试验结果表明模拟得到的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场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现场实测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13].旻国内学者段等[14]进行了带有可调节平板的稳态下击暴流风洞模拟,试验结果表明,该装置模拟的下击暴流水平风速分布与经验风剖面吻合较好. Oseguera和Bowles,Vicory以及Li等学者基于不可压欧拉方程并类比传统边界层经验模型,提出了下击暴流流场解析模型,但这些半经验公式并不能捕捉到下击暴流流场非稳态细节特征[15-17].CFD数值模拟由于可以获得高分辨率的流场信息、实现精准的结构荷载估算,广泛被各国学者用于下击暴流流场研究.Hjelemfelt等人基于微观物理全云模型,采用数值模拟对下击暴流进行了模拟;Anderson和Mason等人则采用冷源子云模型进行了模拟[18-20].这些学者考虑了气象方面的影响,对于面向工程的下击暴流数值模拟具有参考意义,但风工程研究侧重风对结构的荷载作用,此外简化模型也有利于工程应用.Selvam与Holmes采用了二维冲击射流模拟计算域并考虑了地形影响,研究了当下击暴流流场通过小山时,流场风速增加情况[21].汪之松等采用大涡数值模拟方法,考虑山脉地形影响建立了二维以及三维冲击射流模型,分析了山脉高度、间距等地貌因study and the results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e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2-D impinging jet model for the downburst wind field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at of the3-D impinging jet model,that is,the2-D impinging jet model is an effective simplified simulation method for the downburst wind field.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horizontal wind speed and wind field of the downburst simulated by setting up the inclined plate in the BLWT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wind tunnel test results,and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impinging jet model and the field measured results,that i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eady hori-zontal wind filed of downburst flow can be simulated by setting an inclined plate in BLWT.Key words:downburst;horizontal wind field simulation;impinging jet model;inclined plate;numerical simula-tion;wind tunnel test第7期11素对下击暴流风场的影响[22].Sengupta和Sarkar[23]采用了数值和试验方法,对下击暴流数值模拟的湍流模型、计算域和边界条件进行了深入研究.Kim与Hangan采用二维冲击射流模型计算域,并选用RSM (Reynolds stress model)湍流模型计算得到了下击暴流非定常流场,研究了下击暴流阵风峰面特点以及流场的雷诺数相关性问题[24].Mason等[25]则认为SST (Shear Stressed Transport)湍流模型在冲击射流的模拟中表现良好.Chay[26]等对多组不同直径和不同下沉气流速度的下击暴流风场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冲击射流数值模拟方法在模拟突发风场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下击暴流风场模拟方法[26].钟永力等[27]基于CFD方法,采用水平平板建立了二维平面壁面射流模型,并模拟了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数值模拟结果与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经验风剖面和已有的冲击射流模型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在研究下击暴流风场对桥梁结构作用方面,Hao 与Wu[28]利用滑移网格实现了冲击射流模型下三维移动下击暴流流场模拟,并基于有限元CSD方法对大跨度悬索桥进行了结构动力响应分析.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冲击射流模型的数值模拟和试验模拟是研究下击暴流风场的重要方法.然而,冲击射流模型通常由于喷嘴直径较小,形成的风场范围较小,导致结构试验模型较小,比较适合建筑结构下击暴流风效应研究.采用WindEEE专用风洞进行下击暴流风对结构作用效应研究则费用相对较大.考虑到下击暴流对桥梁结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水平风,下击暴流竖向风速对桥梁结构产生的竖向风荷载效应可以忽略,而由此导致的攻角效应则可通过改变桥梁主梁断面初始攻角来考虑.在传统大气边界层风洞中进行下击暴流风场水平风速模拟对桥梁结构下击暴流风效应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大气边界层风洞中模拟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特性,为桥梁结构下击暴流风效应试验研究奠定基础.首先采用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进行下击暴流风特性数值模拟研究,以进一步了解下击暴流风场特性;在此基础上,在边界层风洞中设置倾斜平板对下击暴流水平方向风场进行数值模拟和风洞试验研究.1下击暴流二维冲击射流模型模拟下击暴流冲击射流模型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模型.二维冲击射流模型数值模拟相比三维冲击射流模型数值模拟,网格数量可控,可计算得到更为详细的流场发展细节.本节采用二维冲击射流模型进行下击暴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1.1计算模型参考文献[24]确定二维冲击射流模型计算参数,即采用H/D jet=4(喷口直径D jet=600m,喷口距壁面距离H=2400m),计算域整体尺寸为10D jet×10D jet 进行数值模拟.为简化计算,选取对称一侧区域进行计算,计算域示意图如图1所示.分别采用剪应力输送湍流模型SST k-ω和雷诺应力湍流模型RSM进行计算,RSM模型计算时采用增强壁面处理[22].压力-速度耦合格式采用半隐式求解格式SIMPLEC (Semi Implicit Method for Pressure Linked Equation Consistent)算法求解.空间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此外,动量、湍动能、湍能耗散率和雷诺应力也采用二阶格式进行离散.计算域几何缩尺比为1∶2000,计算时间步长为0.001s[29].速度入口10D jetr0.5D jet压力出口对称轴边界无滑移壁面图1计算域示意图Fig.1Computational domain diagram网格全部采用结构化网格,采用ICEM CFD进行划分.考虑到冲击射流模型流体下冲于壁面处受阻后,流体流动情况复杂,因此在计算域底部处网格进行了加密处理.y+通常用来判断边界层是否满足计算要求,y+定义为:y+=Δy/υ·τw/ρ√(1)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12式中:Δy是网格中心至壁面的距离;υ是空气的动黏度系数;τw为壁面切应力;ρ是空气密度.为进行网格无关性检验,采用了3套网格进行计算,具体网格参数如表1所示,网格示意图如图2所示.计算域边界条件设置如下:速度入口边界(Ve-locity inlet),来流风速U jet=9.6m/s;计算域右侧、上侧为压力出口边界(Pressure outlet);对称轴处设置为对称边界(AXIS);入口上部壁面设置为滑移边界(Symmetry)[29].表12-D冲击射流模型网格参数Tab.12-D mesh parameters of impinging jet model 网格参数网格1网格2网格3首层网格高度/m5e-55e-5 2.5e-5流体下冲区竖向增长率 1.0296 1.0107 1.022径向增长率 1.014 1.0253 1.0075网格总数111763203353306963壁面y+值最大值0.8990.8990.445图2网格示意图Fig.2Mesh schematic diagram1.2计算结果1.2.1网格无关性检验网格无关性检验计算采用表1中三套网格,选用SST k-ω湍流模型进行.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图3(a)为径向距离r=1D jet位置处且计算时间t=0.3s 的水平风速竖向瞬时风剖面;图3(b)为径向距离r= 1D jet时,全部时程数据计算得到的水平风速竖向平均风剖面.由图3可知,3套网格计算结果差异较小,为节约计算资源,后续计算采用网格数量最少的网格1进行计算.1.2.2计算结果图4、图5所示分别为二维冲击射流模型模拟得到的不同时刻流场速度云图.由图4、图5可知两种模型计算得到的流场变化情况接近,初始时刻均产生了初始旋涡,随着时间推移开始冲击地面,产生沿水平方向的流动,同时产生了次生涡旋.1.00.80.60.40.2000.20.40.60.8 1.0 1.2网格1网格2网格3U rad/U jet(a)径向距离1D jet且t=0.3s结果00.20.40.60.8 1.0 1.21.00.80.60.40.2网格1网格2网格3U rad/U jet(b)径向距离1D jet平均值结果图图3网格无关性检查计算结果Fig.3Mesh independence check calculation results将计算周期内计算结果进行平均处理,得到两种湍流模型不同位置处水平风速竖向平均风剖面.选取距离径向位置r=1D jet以及r=1.5D jet处水平风速竖向平均风剖面,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两种湍流模型计算结果相近,SST k-ω湍流模型峰值速度要大于RSM湍流模型,其沿径向移动相比RSM湍流模型也更迅速(对比图4图5可知).图7为两种湍流模型峰值速度对应的风速时程曲线,由图7可知风速时程曲线0~0.5s时两种湍流模型计算结果保持一致,0.5s之后SST k-ω湍流模型结果波动较小,两者最终趋于稳定,其中速度最大时刻为t=0.3s 前后,由图4、图5可知,t=0.3s前后气流冲击地面,产生了分离和重新附着,Hangan等[24]认为:气流冲击地面过程中,产生了与主涡相反的次生涡,在两者展开并开始沿径向移动过程中对风场的径向速度起到了加速作用,本文计算结果也表明存在这种现象.刘志文等:基于边界层风洞的下击暴流稳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第7期130.50.40.30.20.1000.20.40.60.8 1.0RSM SST k-ωU rad/U jet(a)r=1D jet处的水平风速竖向平均风剖面00.20.40.60.8 1.00.50.40.30.20.1RSMSST k-ωU rad/U jet(b)r=1.5D jet处的水平风速竖向平均风剖面图6不同径向位置水平速度竖向平均风剖面图Fig.6Vertical mean wind profile of horizontalvelocity at different radial positionRSMSST k-ω1210864200.5 1.0 1.5 2.0 2.5时间/s图7距离壁面实际高度为10m处风速时程曲线Fig.7Time history curve of wind speed at10m fromthe actual height of the wall surface图8所示为径向位置r=1D jet时,二维数值模拟结果与NIMROD[30]和JASW[6]现场实测结果比较.为方便对比,将计算结果根据最大风速以及其对应高度进行归一处理.由图8可知,两种湍流模型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场实测结果吻合较好,且SST k-ω湍流模型计算结果要优于RSM湍流模型计算结果.(a)t=0.12s(b)t=0.28s(c)t=0.36s(d)t=0.68s(e)t=1s图4流场不同时刻速度云图(雷诺应力湍流模型RSM)Fig.4Velocity contour of flow field at different time(Reynolds Stress model turbulence model RSM)(a)t=0.12s(b)t=0.28s(c)t=0.36s(d)t=0.68s(e)t=1s图5流场不同时刻速度云图(剪应力输送湍流模型SST)Fig.5Velocity contour of flow field at different time(shear stress transportation turbulence model SST)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140.20.40.60.81.01.24.54.03.53.02.52.01.51.00.50JASW mean (Hjelmfelt ,1988)JASW maximum (Hjelmfelt ,1988)NIMROD (Fujita ,1981)Haojianming ,2018RSM (r =1D jet )SST k-ω(r =1D jet )U rad /U max图8r =1D jet 处平均风剖面对比图Fig.8Comparison of mean wind profiles at r =1D jet2下击暴流三维冲击射流模型模拟考虑到三维冲击射流模型可以从整体上模拟下击暴流风场特性,为了进一步比较二维冲击射流模型所模拟的下击暴流水平风速剖面特征,本节采用三维冲击射流模型进行下击暴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2.1计算模型二维冲击射流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计算域顶部区域流场扰动微小,为节约计算资源将计算域高度设定为8D jet ,其中速度入口距离地面4D jet ,保持与二维计算域一致.由于采用全尺寸计算域,原对称轴边界取消,其余边界条件与二维模拟一致.此外,三维数值模拟计算参数参照二维模拟进行设置.计算域轴对称切面图如图9所示,计算域直径为20D jet .20D jet压力出口压力出口速度入口无滑移壁面图9三维冲击射流模型计算域示意图Fig.93-dimensional impact jet model computationaldomain schematic diagram三维数值模拟同样采用剪应力运输SST k-ω湍流模型以及雷诺应力RSM 湍流模型进行计算.压力-速度耦合格式采用半隐式求解格式SIMPLEC 算法求解.空间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动量、湍动能、湍能耗散率和雷诺应力均采用二阶格式进行离散.计算域采用1∶2000几何缩尺,计算时间步长为0.001s.考虑首层网格厚度需满足无量纲距离要求,经试算后最终确定首层网格厚度为5×10-5m ,网格总数为3763323,网格核心区域径向增长率为1.039,竖向增长率为1.15,三维网格如图10所示,此外三维网格计算域壁面y +值均小于1.图10三维冲击射流模型网格示意图Fig.10Mesh for 3-dimensoinal impact jetmodel schematic diagram2.2计算结果图11所示为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采用不同湍流模型计算得到的径向位置分别为r =1D jet 、r =1.5D jet 处对应时均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图12所示分别为径向距离r =1D jet 时计算时间t =0.3s 、t =0.5s 时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采用不同湍流模型计算得到的瞬时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从图11、12中可以看出,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对应的不同湍流模型数值模拟结果总体吻合较好;随着高度增长,风速先增加后减小;相对而言,采用剪应力输送SST k-ω湍流模型分别进行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计算结果相对离差较小.0.20.40.60.81.01.21.00.80.60.40.20RSM_2DSST k-ω_2D RSM_3D SST k-ω_3DU rad /U jet(a )r =1D jet 处的水平风速竖向平均风剖面刘志文等:基于边界层风洞的下击暴流稳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第7期150.20.40.60.81.0 1.21.00.80.60.40.20RSM_2DSST k-ω_2D RSM_3D SST k-ω_3DU rad /U jet(b )r =1.5D jet 处的水平速度竖向平均风剖面图11不同径向位置平均风剖面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计算结果对比Fig.11Comparison of 2-dimensioanl and 3-dimensionalimpact jet models calculation results of average wind profiles with different radial positions0.20.40.60.81.0 1.21.00.80.60.40.20RSM_2DSST k-ω_2D RSM_3D SST k-ω_3DU rad /U jet(a )计算时间t =0.3s 的水平风速竖向瞬时风剖面00.20.40.60.81.01.21.00.80.60.40.20RSM_2DSST k-ω_2D RSM_3D SST k-ω_3DU rad /U jet(b )计算时间t =0.5s 的水平风速竖向瞬时风剖面图12r =1D jet 位置不同时刻风剖面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计算结果对比Fig.12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impinging Jet models of wind profileat different time when r =1D jet3边界层风洞下击暴流稳态风场数值模拟3.1计算模型为了在边界层风洞中模拟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为桥梁结构下击暴流风效应试验研究奠定基础.参考Butler 等[12]以及段旻[14]等研究成果,考虑在边界层风洞加入一块倾斜平板以实现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为此分别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和风洞试验方法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下击暴流冲击地面后形成的水平方向风速随竖向高度的变化情况,因此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形状以及最大风速位置是主要控制参数.参考湖南大学2号边界层风洞第二试验段几何尺寸确定计算域,倾斜平板中心距离速度入口4.61m ,可通过调节平板倾角α实现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分别在距离倾斜平板中心d =3.5m 、4m 、5m 、6m 处设置风速监控点,以分析不同位置处的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计算域如图13所示.计算域边界条件设置如下:计算域左侧为速度入口边界(Velocity inlet ),来流风速为10m/s ;计算域右侧为压力出口边界(Pressure outlet );计算域上、下侧以及下倾斜平板为无滑移壁面边界(Wall ).速度入口无滑移壁面无滑移壁面无滑移壁面压力出口5.017.012.0监控点0.51.01.06.394.61dα图13计算域示意图(单位:m )Fig.13Computational domain diagram (unit :m )采用分块结构化网格进行网格划分,为方便倾斜平板角度调整,以倾斜平板中心为圆心建立O 型网格,网格各方向增长率均小于1.2,网格总数为227484,网格示意图如图14所示.划分网格时,以计算域形心位置为坐标原点,倾斜平板壁面y +分布如图15所示.图14整体网格情况Fig.14Mesh schematic diagram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16-4.50-4.25-4.00-3.75-3.50-3.25y-plus543210坐标轴值/m图15倾斜平板处y +分布情况Fig.15y +distribution at inclined plate3.2计算结果综合考虑,分别采用大涡模拟(LES )和剪应力输送SST k-ω湍流模型进行边界层风洞下击暴流风场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数值模拟.时间、空间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速度-压力耦合采用SIMPLEC 算法求解,此外动量、湍动能、湍能耗散率和雷诺应力均采用二阶格式进行离散,计算时间步长为0.0005s.为便于比较,将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时均处理,并将结果按最大风速以及其对应高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图16所示分别为d =4m 、d =5m 及倾角分别为0.20.40.60.8 1.0 1.24.54.03.53.02.52.01.51.00.50JASW mean (Hjelmfelt ,1988)JASW maximum (Hjelmfelt ,1988)NIMROD (Fujita ,1981)Haojianming ,2018α=41°α=49°U rad /U max(a )LES 湍流模型d =4m 时的归一风剖面00.20.40.60.8 1.0 1.24.54.03.53.02.52.01.51.00.50JASW mean (Hjelmfelt ,1988)JASW maximum (Hjelmfelt ,1988)NIMROD (Fujita ,1981)Haojianming ,2018α=41°α=49°U rad /U max(b )LES 湍流模型d =5m 时归一风剖面0.20.40.60.8 1.04.03.53.02.52.01.51.00.50JASW mean (Hjelmfelt ,1988)JASW maximum (Hjelmfelt ,1988)NIMROD (Fujita ,1981)Haojianming ,2018α=41°α=49°U rad /U max(c )SST k-ω湍流模型d =4m 时归一风剖面00.20.40.60.8 1.04.03.53.02.52.01.51.00.50JASW mean (Hjelmfelt ,1988)JASW maximum (Hjelmfelt ,1988)NIMROD (Fujita ,1981)Haojianming ,2018α=41°α=49°U rad /U max(d )SST k-ω湍流模型d =5m 时归一风剖面图16数值模拟水平风速平均风剖面结果Fig.16Numerical results of horizontal mean wind profileα=41°、α=49°数值模拟结果.由图16可知,倾角α=41°~49°、d =4~5m 范围时,大涡模拟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总体吻合较好.总体而言,当倾斜平板倾角合适时可实现下击暴流稳态风场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Oseguera 和Bowles ,Vicory 以及Li 等[15-17]学者根据现场实测数据建立了下击暴流水平方向竖向风剖面解析模型.图17所示为本文数值模拟结果(SST k-ω湍流模型,α=41°,d =4m )与上述解析模型比较.由图17可知,实际下击暴流风场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最大风速位置距离地面为h =70~80m 左右,此外,Hjelmfelt [6]根据JAWS 实测数据总结了典型下击暴流风剖面,其中水平风速风剖面最大风速位置距离地面高度h =80m.综合考虑,本文后续计算取h =70m.根据实际下击暴流风场最大水平风速距离地面的位置h 和边界层风洞中模拟的最大水平风速距离风洞地面的位置h 0,可以得到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场几何缩尺比为:λL =h 0/h (2)刘志文等:基于边界层风洞的下击暴流稳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第7期17风速比的确定根据常规边界层风洞模型试验方法确定.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6543210 020406080100120102030U=21.03m/sh0=0.4m 风速/(m·s-1)风速/(m·s-1)图17下击暴流水平风速风剖面数值模拟结果与解析模型对比Fig.17Comparison between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and analytical model of horizontal wind profile of downburst由于倾斜平板角度α以及风速监测点距离倾斜平板中心d不同时,形成的竖向风剖面最大风速位置距离计算域下侧的h0不一样.将部分数值模拟结果的风场缩尺比计算结果列于表2中.由表2可知,倾角值α与监测点距离d越大,最大风速位置h0增大,风场几何缩尺比λL也随之增大.表2数值模拟下击暴流风场几何缩尺比计算Tab.2Calculation of geometric scale of downburstwind field in numerical simulation湍流模型α/(°)d/m最大风速位置h0/m风场几何缩尺比λLSST k-ω4140.41∶1754.50.31∶23350.31∶233 4540.41∶1754.50.41∶17550.41∶175LES 4140.31∶2334.50.51∶14050.41∶175 4540.81∶87.54.50.81∶87.550.81∶87.54边界层风洞下击暴流稳态风场试验模拟4.1试验装置根据边界层风洞倾斜平板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数值模拟结果,结合下击暴流稳态流场特点,设计了边界层风洞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试验装置,以实现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以及时变特性模拟.试验装置如图18所示,该装置主要组成部分为:支撑架、倾斜平板、竖向对称档板、伺服电机和控制系统.倾斜平板可实现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由控制系统控制的伺服电机可驱动两侧竖向对称挡风板快速转动,可实现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的时变特性模拟.为了测量不同高度处风速,研制了一套专用风速测量装置.通过伺服电机控制,眼镜蛇风速仪可沿竖向方便移动,实现风速的快速测量,眼镜蛇风速仪采样频率为321.5Hz.图19所示为置于风洞中的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装置照片.侧板架下压板驱动机构挡风门顶架底架图18下击暴流试验装置示意图Fig.18Schematic diagram of downburst experimentaldevice图19装置试验照片Fig.19Experimental photo of test device4.2试验结果试验时,通过不断调试倾斜平板的位置、倾角α以及风速测试位置距离平板中心d的位置获得最佳风剖面.图20给出了d=3m、倾角α分别为49°、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1860°和66°的试验结果.由图20可知,当测试断面距离为3m 时,倾角α为66°时风洞试验结果比倾角α为49°和60°更接近于现场实测结果,因此固定倾斜平板角度为66°,调节风速测量装置距倾斜平板的距离,以获得最佳距离d .0.20.40.60.8 1.0 1.24.03.53.02.52.01.51.00.50JASW mean (Hjelmfelt ,1988)JASW maximum (Hjelmfelt ,1988)NIMROD (Fujita ,1981)α=49°α=60°α=66°U rad /U max图20倾斜平板不同倾角在d =3m 时对应风剖面Fig.20Wind profiles corresponding to inclined platewith different inclination angles at d =3m图21分别显示了平板倾斜角度为66°时,不同监测位置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试验结果.从图21可以看出,当倾斜平板的角度为66°时,d =3.5m 和4.0m 风洞试验结果与现场实测结果吻合较好.综合图16和图21可知,下击暴流水平风速剖面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由于风洞试验中下击暴流模拟装置支架的干扰效应引起.0.20.40.60.8 1.0 1.24.03.53.02.52.01.51.00.50JASW mean (Hjelmfelt ,1988)JASW maximum (Hjelmfelt ,1988)NIMROD (Fujita ,1981)d =3m d =3.5m d =4mU rad /U max图21平板倾角为66°时不同测试断面距离对应风剖面Fig.21Wind profil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est section distances when inclination angle is 66°表3给出了不同倾角α及监测点距离d 处水平风速风剖面最大风速位置h 0和风场几何缩尺比λL .由表3可知,试验结果趋势与数值模拟结果总体一致,即当d 值不变时,随着倾角α的增大,风场几何缩尺比λL 增大.此外,由于本文仅采用一块倾斜平板进行试验模拟,由图21可知在风剖面最大风速位置以上试验结果与现场实测结果吻合效果不理想,考虑到本文试验装置模拟的最佳下击暴流风场几何缩尺比大约为λL =1∶200对应的最大水平风速距离风洞底部约为h 0=0.5m ,故当实际结构高度约为100m 以内时可采用本文方法进行相关试验研究.表3风洞试验模拟下击暴流风场几何缩尺比计算Tab.3Calculation of geometric scale of downburstwind field under wind tunnel test simulationα值/(°)d 值/m 最大风速位置h 0/m风场几何缩尺比λL4930.331∶2126030.381∶1846630.481∶14666 3.50.481∶1466640.481∶1465结论分别采用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对下击暴流风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对下击暴流风特性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了边界层风洞下击暴流水平风速数值模拟和风洞试验研究,实现了下击暴流水平风速模拟,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下击暴流风场二维、三维冲击射流模型数值模拟结果与现场实测结果吻合较好,且二维冲击射流模型数值模拟结果与三维冲击射流模型数值模拟结果吻合较好.2)边界层风洞中设置倾斜平板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挡板角度α、风速监测位置与倾斜平板中心距离d 合适时,形成的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与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实测值吻合较好,为试验模拟装置设计提供了依据.3)边界层风洞中设置倾斜平板风洞试验结果表明:下击暴流模拟试验装置在边界层风洞中可实现下击暴流水平风速竖向风剖面模拟,为桥梁结构下击暴流水平风速效应研究奠定了基础.参考文献[1]LOMBARDO F T.Improved extreme wind speed estimation for wind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Indus -trial Aerodynamics ,2012,108:278—284.[2]DE GAETANO P ,REPETTO M P ,Repetto T ,et al .Separation and刘志文等:基于边界层风洞的下击暴流稳态风场特性数值模拟第7期19。
第51卷第6期2020年6月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V ol.51No.6Jun.2020不同湍流边界层中高层建筑模型气动力特性李石清1,2,王汉封2,罗元隆3,罗振兵1(1.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73;2.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75;3.淡江大学工学院,中国台北,251301)摘要:在模型高宽比(H/d)为5,基于来流风速U∞与模型宽度d的雷诺数Red=6.0×104时,通过风洞试验研究2种湍流边界层中正方形截面高层建筑简化模型的气动力特性,并对模型表面脉动风压进行本征正交分解法(POD)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湍流边界层中模型时均阻力系数--Cd的最大值出现在自由端附近,脉动升力系数C'1的最大值出现在模型中间高度附近。
不同湍流边界层中模型侧面中间高度处平均风压系数--Cp与脉动风压系数C'p的分布差异较大;在湍流度较小的工况C中,脉动升力的周期性较强,两侧风压脉动由反对称状态主导;在湍流度较大的工况A中,模型侧面可能出现间歇性再附,两侧风压脉动转变为对称状态主导,脉动升力减小,且周期性减弱。
关键词:高层建筑;有限长方柱;湍流边界层;气动力特性;本征正交分解法(POD)中图分类号:TU9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7207(2020)06-1606-09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quare high-rise building models in different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sLI Shiqing1,2,WANG Hanfeng2,LO Yuanlung3,LUO Zhenbing1(1.College of Aerospac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410073,China;2.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410075,China;3.College of Engineering,Tamkang University,Taipei251301,China)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rodynamic forces on a simplified square high-rise building model immersed in two different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s were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through wind tunnel tests,and the 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POD)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fluctuation pressure on the model,when the model aspect ratio H/d was5,and the Reynolds number was6.0×104which was based on the oncoming flowvelocity U∞and the width 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Cdappears near the free end,while the maximumC'l appears near the middle-span of the model.The distribution of--C p and C'p on the two side faces of the model DOI:10.11817/j.issn.1672-7207.2020.06.015收稿日期:2019−06−22;修回日期:2019−09−23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472312)(Project(11472312)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通信作者:王汉封,博士,教授,从事实验流体力学与流动控制研究;E-mail:**************.cn第6期李石清,等:不同湍流边界层中高层建筑模型气动力特性exerts obvious difference near the middle-span region for the two tested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s.Particularly,for the one with lower turbulence intensity,the periodicity of lift is relatively stronger,and the pressure on side faces is dominated by anti-symmetrical mode.For the one with higher turbulence intensity,the predominant mode of pressure on side faces becomes symmetrical,resulting in smaller fluctuation lift with weakened periodicity.Key words:high-rise buildings;finite-length square cylinder;turbulent boundary layer;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POD)近年来,由于商业和居住的需要,高层建筑的数量急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