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介绍
- 格式:doc
- 大小:41.00 KB
- 文档页数: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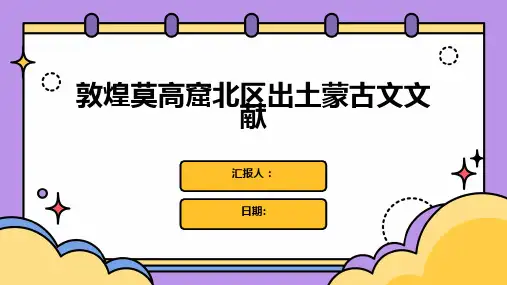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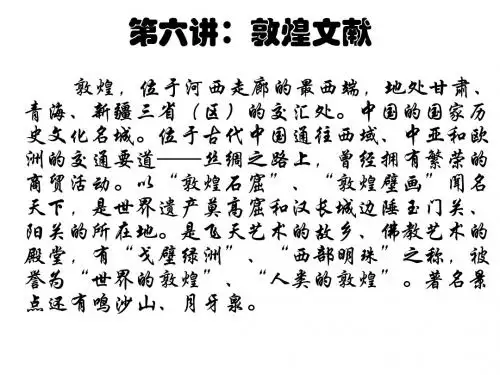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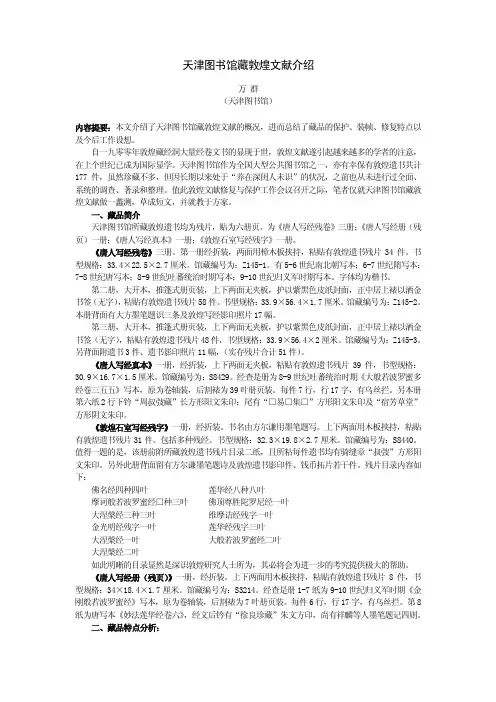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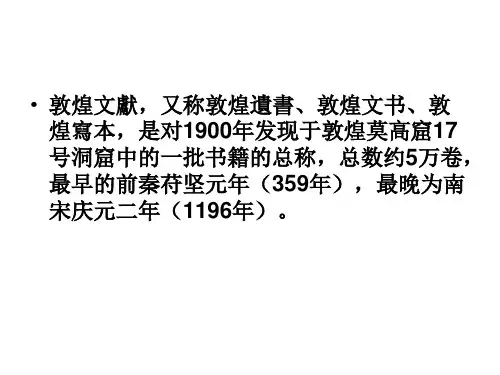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概述[马德]](https://uimg.taocdn.com/446d65583b3567ec102d8a29.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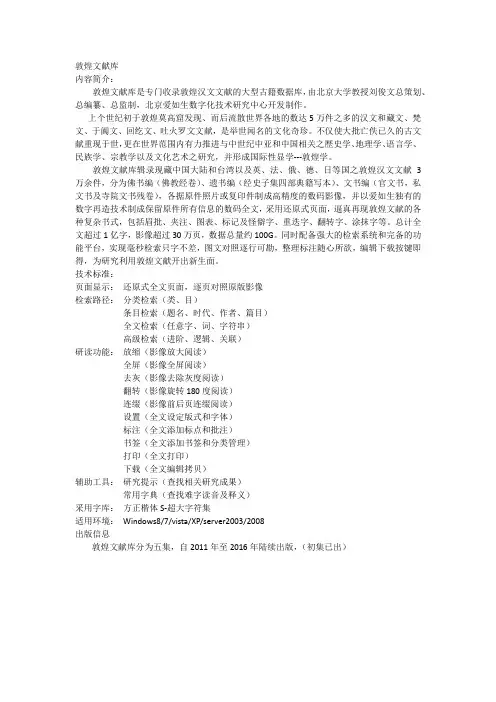
敦煌文献库内容简介:敦煌文献库是专门收录敦煌汉文文献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上个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发现、而后流散世界各地的数达5万件之多的汉文和藏文、梵文、于阗文、回纥文、吐火罗文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奇珍。
不仅使大批亡佚已久的古文献重现于世,更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进与中世纪中亚和中国相关之歴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化艺术之研究,并形成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库辑录现藏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之敦煌汉文文献3万余件,分为佛书编(佛教经卷)、遗书编(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写本)、文书编(官文书,私文书及寺院文书残卷),各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成保留原件所有信息的数码全文,采用还原式页面,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图表、标记及怪僻字、重迭字、翻转字、涂抹字等。
总计全文超过1亿字,影像超过30万页,数据总量约100G。
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整理标注随心所欲,编辑下载按键即得,为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开出新生面。
技术标准:页面显示:还原式全文页面,逐页对照原版影像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条目检索(题名、时代、作者、篇目)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高级检索(进阶、逻辑、关联)研读功能:放缩(影像放大阅读)全屏(影像全屏阅读)去灰(影像去除灰度阅读)翻转(影像旋转180度阅读)连缀(影像前后页连缀阅读)设置(全文设定版式和字体)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打印(全文打印)下载(全文编辑拷贝)辅助工具:研究提示(查找相关研究成果)常用字典(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采用字库:方正楷体S-超大字符集适用环境:Windows8/7/vista/XP/server2003/2008出版信息敦煌文献库分为五集,自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初集已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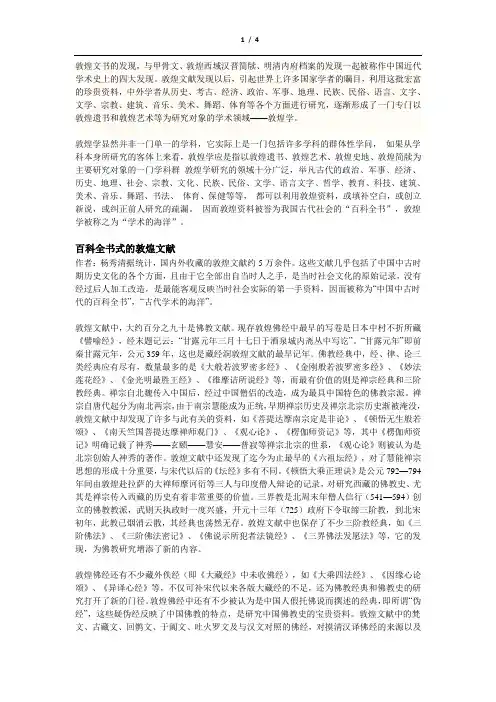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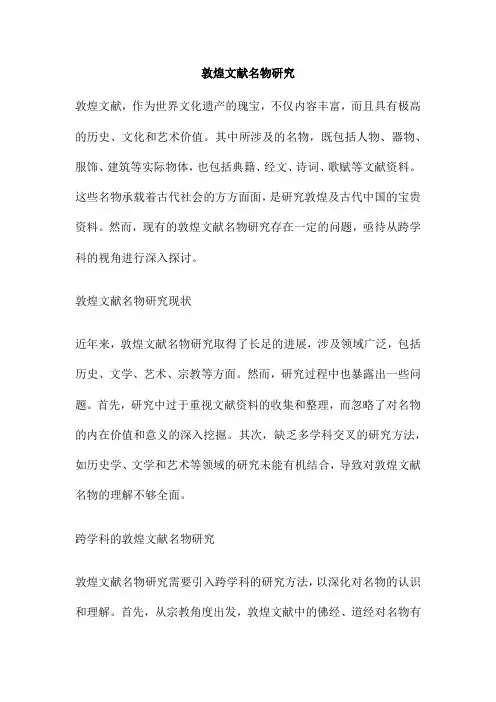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其中所涉及的名物,既包括人物、器物、服饰、建筑等实际物体,也包括典籍、经文、诗词、歌赋等文献资料。
这些名物承载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敦煌及古代中国的宝贵资料。
然而,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现状近年来,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
然而,研究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中过于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忽略了对名物的内在价值和意义的深入挖掘。
其次,缺乏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未能有机结合,导致对敦煌文献名物的理解不够全面。
跨学科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名物研究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深化对名物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从宗教角度出发,敦煌文献中的佛经、道经对名物有着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些经文,可以追溯名物的起源、演变和意义。
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宗教的名物,可以进一步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和交融。
其次,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名物的生动形象。
通过解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名物在古代社会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内涵。
同时,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可以揭示敦煌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最后,敦煌建筑史也是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的重要方向。
敦煌石窟、寺庙等建筑的真实写照,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名物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建筑的结构、风格、装饰等特点,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古代敦煌的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进而揭示其与中原及西域建筑的关联和差异。
结论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宗教、文学和历史等角度进行深入挖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未来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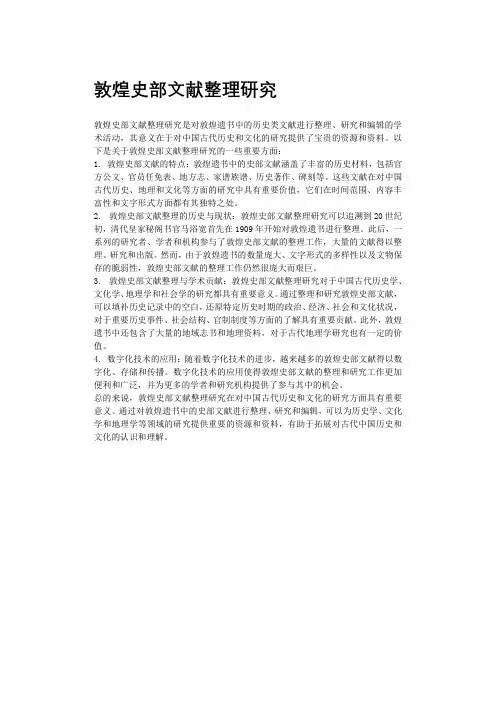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是对敦煌遗书中的历史类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和编辑的学术活动,其意义在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资料。
以下是关于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的一些重要方面:1. 敦煌史部文献的特点:敦煌遗书中的史部文献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包括官方公文、官员任免表、地方志、家谱族谱、历史著作、碑刻等。
这些文献在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它们在时间范围、内容丰富性和文字形式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2.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的历史与现状: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清代皇家秘阁书官马浴宽首先在1909年开始对敦煌遗书进行整理。
此后,一系列的研究者、学者和机构参与了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工作,大量的文献得以整理、研究和出版。
然而,由于敦煌遗书的数量庞大、文字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文物保存的脆弱性,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工作仍然很庞大而艰巨。
3.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与学术贡献: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整理和研究敦煌史部文献,可以填补历史记录中的空白,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社会结构、官制制度等方面的了解具有重要贡献。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地域志书和地理资料,对于古代地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4.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敦煌史部文献得以数字化、存储和传播。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敦煌史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更加便利和广泛,并为更多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参与其中的机会。
总的来说,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在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敦煌遗书中的史部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和编辑,可以为历史学、文化学和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源和资料,有助于拓展对古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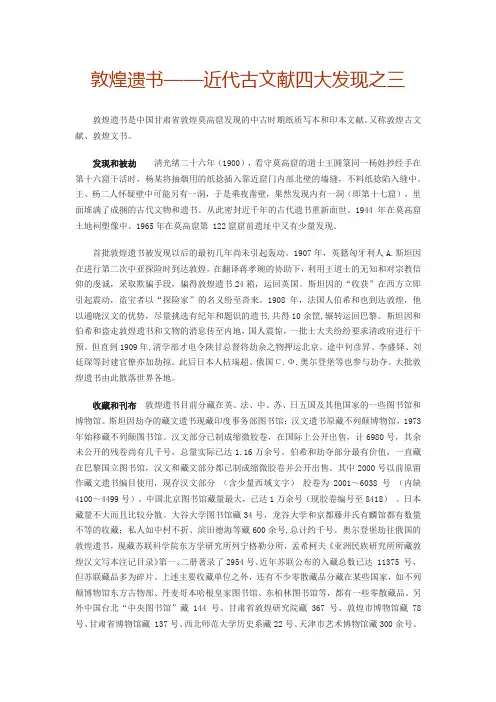
敦煌遗书——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三敦煌遗书是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
又称敦煌古文献、敦煌文书。
发现和被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
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
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
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
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骗手段,骗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
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到达敦煌,他以通晓汉文的优势,尽量挑选有纪年和题识的遗书,共得10余筐,辗转运回巴黎。
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消息传至内地,国人震惊,一批士大夫纷纷要求清政府进行干预。
但直到1909年,清学部才电令陕甘总督将劫余之物押运北京。
途中何彦昇、李盛铎、刘廷琛等封建官僚亦加劫掠。
此后日本人桔瑞超、俄国С.Ф.奥尔登堡等也参与劫夺。
大批敦煌遗书由此散落世界各地。
收藏和刊布敦煌遗书目前分藏在英、法、中、苏、日五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
斯坦因劫夺的藏文遗书现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汉文遗书原藏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始移藏不列颠图书馆。
汉文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在国际上公开出售,计6980号,其余未公开的残卷尚有几千号,总量实际已达1.16万余号。
伯希和劫夺部分最有价值,一直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和藏文部分都已制成缩微胶卷并公开出售。
其中2000号以前原留作藏文遗书编目使用,现存汉文部分(含少量西域文字)胶卷为 2001~6038号(内缺4100~449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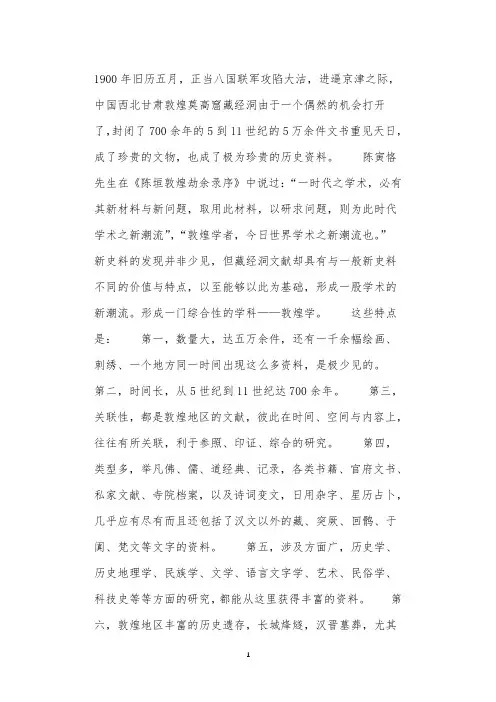
1900年旧历五月,正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进逼京津之际,中国西北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开了,封闭了700余年的5到l1世纪的5万余件文书重见天日,成了珍贵的文物,也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新史料的发现并非少见,但藏经洞文献却具有与一般新史料不同的价值与特点,以至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一股学术的新潮流。
形成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敦煌学。
这些特点是:第一,数量大,达五万余件,还有一千余幅绘画、刺绣、一个地方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资料,是极少见的。
第二,时间长,从5世纪到11世纪达700余年。
第三,关联性,都是敦煌地区的文献,彼此在时间、空间与内容上,往往有所关联,利于参照、印证、综合的研究。
第四,类型多,举凡佛、儒、道经典、记录,各类书籍、官府文书、私家文献、寺院档案,以及诗词变文,日用杂字、星历占卜,几乎应有尽有而且还包括了汉文以外的藏、突厥、回鹘、于阗、梵文等文字的资料。
第五,涉及方面广,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艺术、民俗学、科技史等等方面的研究,都能从这里获得丰富的资料。
第六,敦煌地区丰富的历史遗存,长城烽燧,汉晋墓葬,尤其是与敦煌文献同时期的以莫高窟为首的石窟群中保存完好的大量壁画与雕塑,都可以同藏经洞文献参照、结合,进行研究。
第七,敦煌的独特地位,它既是中原王朝的西陲,与周边的民族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是古代东西方交往要道丝绸之路上的要冲。
这些,在藏经洞文献中都有鲜明的反映。
因此,藏经洞文献既具有地方文献的意义,也具有全国性文献的意义,既具有汉族历史文化意义也具有周边民族历史文化的意义。
具有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关系的意义,还具有世界历史文化的意义、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
也是其他新发现的史料所少见的。
敦煌文献概述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
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
瓜沙二州离得不远。
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
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
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
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
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
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
行政单位叫归义军。
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
不光指莫高窟。
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
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
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
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
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
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
河对岸就是三危山。
(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
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
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
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
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
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
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
出了敦煌,分两路。
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
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
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
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
不让你往外运了。
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译注1. 引言1.1 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简介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是敦煌藏卷中的重要部分,包含着丰富的文献内容。
这一部分的文献涵盖了各个领域,包括宗教、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是研究敦煌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了解古代西域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是研究敦煌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文献,对于了解古代西域地区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这一部分文献的研究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西域地区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为我们深入探讨古代西域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2. 正文2.1 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内容概述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是敦煌文献中的重要部分,包括了大量珍贵的藏文文献。
这一部分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如佛教经典、历史记录、文学作品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在这部分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文化的独特风貌和历史背景。
佛教经典的出现反映了敦煌作为佛教发展中心的地位,历史记录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帮助我们了解敦煌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
文学作品也展现了敦煌人民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情趣。
这一部分内容丰富多样,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敦煌文化的精髓和特点。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揭示出敦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研究素材。
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内容的概述,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敦煌文化的一扇窗户,让我们对这个古老文明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2.2 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翻译注释敦煌藏文文献P.T.2第一部分翻译注释主要涉及对文献内容的解读和翻译工作。
该部分文献内容涵盖了各种主题,包括历史事件、宗教文化、文学作品等。
翻译注释的工作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献内容,解析其中的难点和疑惑。
在进行翻译注释时,需要准确理解原文意思,考虑古代文化和语境因素,同时结合现代语言表达方式,保持翻译准确和通顺。
敦煌文献的分布英国——藏卷最多最长者英国藏卷都是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得,凡是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文献皆归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保管;凡是于阗文、龟兹文、藏文、婆罗谜文文献皆归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管,绘画则由资助斯坦因探险的英国、印度分藏。
1973年,由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与英国博物馆分立,所以原在英国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的斯坦因敦煌收集品全部转移到新建的英国图书馆藏书库保管,现在编号S.00001-S.13624和P.01-20,“S.”是斯坦因(Stien)的缩写,所编皆为手写本,“P.”是印刷品(Printer)的缩写。
在13624号写本和20号印本中,S.00001-S.6980和P.01-19号是最早由英国学者翟林奈博士(Dr. Lionel Giles)编目的,并于1957年出版《英国博物馆藏敦煌出土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不久在日本学者努力下这部分内容全都摄成缩微胶卷公布于世,我国学者刘铭恕据以编成《斯坦因劫经录》,与王重民所编《伯希和劫经录》等合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于1962年5月出版。
其内容又印入了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大型图册中,黄永武还续编了S. 6981-S.7599号的卷子。
1991年,荣新江将S.6981-S.13624号中的非佛教文献编为《英国图书馆藏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一书并于1994年出版,其内容则全部印入《英藏敦煌文献》一书共15册中。
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共765卷,已由比利时藏学家瓦雷·普散编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卷目录》中,其后还附录日本学者从藏文、于阗文卷子背面著录的汉文内容的目录163号。
由于斯坦因最早进入藏经洞直接获得大批卷子,王道士又是把大捆的因而比较完整的卷子最先提出来,所以英藏卷子最多而又最长(俄藏号数虽多,但分量并不大)。
法国——藏卷最精最广者法国收藏的敦煌文献都是伯希和1908年所得收集品,全部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汉文写本3600馀号,回鹘文写本300馀号,粟特文写本78号,于阗文写本66号,藏文写本2216号,另有梵文写本若干卷和未编号藏文写本900馀号。
敦煌吐鲁番古籍中医药文献英译
敦煌吐鲁番是中国的两个重要古代城市,这两个地方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其中包括了一些关于中医药的文献。
以下是一些敦煌吐鲁番古籍中医药文献的英译:
1. 《黄帝内经》(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这是一部古代著名的中医药经典,它包含了关于中医诊断、治疗、养生等方面的内容。
2. 《伤寒杂病论》(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and Miscellaneous Illnesses)
这部文献详细描述了各种热性疾病的病因、病程、诊断和治疗方法,被视为中医药诊疗实践的重要参考。
3. 《千金方》(Thousand Ducat Formulas)
这本文献是一部中医药方剂集,收录了大量古代方剂的配方和应用指导。
4. 《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这是一本关于药物的规范及用途的文献,详细记录了中草药的性味、功效以及用法用量。
以上是一些敦煌吐鲁番古籍中医药文献的英译,它们对于研究中医药的历史和经典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因而它既是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地并已编目有序号的敦煌藏文文献达5000卷之多,仅次于敦煌汉文文献而位居其他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民族文献之首,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实乃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最为珍贵的古文献之一,对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在历史学方面的资料价值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建树卓著、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古代文明的黄金时期,为后人学者留下了丰厚的藏文古文献,除了佛教经典论著之外,大致可分为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书和敦煌文献四大类。
这些藏文古文献为研究藏族古代文明提供了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敦煌文献更引起国际藏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文古文献中不仅保持了原貌,而且内容丰富,正可谓包罗万象,它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法律、地理、文学、语言、民俗、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科技等。
首先它在历史学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因为以往研究吐蕃历史主要依据藏文伏藏文书,而伏藏文书大多又经过后人佛教徒的发掘润色或重新编辑,从而使资料的原始性或真实性大打折扣,并形成一种新的特色,正如陈庆英研究员指出:“藏族古典著作中,文史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
往往一部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
”这给历史学家描述吐蕃历史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对注重实证的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很不适应去辨别或引用此类史料。
自从1940年以法文出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后,才引起国际藏学界对吐蕃历史的极大关注。
当时藏学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藏族古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
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
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
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事务公文、法事记录以及施入疏、斋文、愿文、燃灯文、临圹文等,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兴盛起来。
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
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大多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
主要有老子《道德经》及该经的各种不同注本,如河上公注、想尔注、李荣注,以及该经的题解。
河上公注本为道徒所传颂,风行一时。
想尔注则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材料。
《太玄真一本际经》、《太平经》、《上清经》、《灵宝经》等道教经典,是研究道教理论的好材料。
《老子化胡经》是反映道教与佛教争夺地位的文献,元代以后,彻底亡佚,此经今仅存于敦煌文献中,十分珍贵。
而纸质优良、书法工整、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
除佛教、道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
摩尼教文献共有三件,即《摩尼光佛法仪略》、《证明过去教经》、《下部赞》,这仅有的三件文献,使人们对文献中屡有记载,但无法知其全貌的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得以明了。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唐贞观九年(635)传入我国。
景教在唐代流行情况,文献记载不详,直到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长安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才略知一二。
敦煌文献中有七种景教文献,它们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这些罕见的景教文献,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其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摩尼教、景教文献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本残卷外,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如孔衍《春秋后语》、邓粲《晋纪》、李荃《阃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论》等,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可订正史籍记载的讹误。
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如李泰的《括地志》、梁载言的《十道录》、贾耽的《贞元十道录》、韦澳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几种方志,更为史籍所不载,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沙州地志》等,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关于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在两《唐书》、《资汉通鉴》、以及新、旧《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非常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的了解。
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数十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公文书包括法制法制文书和“官文书”。
唐代法律由律、令、格、式四部分组成,传世文献中只有律保存下来,令、格、式则不为人们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虽然都有残缺,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
属于“官文书”的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公验、过所、度牒、告身、籍帐以及官府来文书等。
其中如“告身”是给予新任职事官、散官、勋官等的一种证书,的册授、制授、敕授、奏授、判补等多种形式。
“籍帐”则包括户籍、手实、差科簿、军政机关的会计簿等。
敦煌文献中的私文书,主要是指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社”的文书等。
契约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其中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贷契、雇佣契、买卖契、以及析产契等。
“社”文书中有社司转帖、社司牒状、社条、纳赠历、社斋文等。
此外,还有遗书、什物抄、放妻书、放良书、悼文、邈真赞、碑志、私家帐历等。
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
敦煌文献中属于子部的《书仪》,包括朋友书仪、吉凶书仪、状启书仪,不仅是当时的书信范本,也是研究礼学与风俗史的绝佳材料。
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读物和字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五代的教育情况,还为考订唐音,研究西北方言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丧葬、岁时、卜卦、看相、符咒、解梦、风水、驱傩及有关佛教风俗的资料,是研究敦煌民俗的极好材料。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类书,均为亡佚之书,对古籍整理及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
它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它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
其中《古文尚书》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论语郑氏注》,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郑玄注《毛诗故训传》,南朝徐邈《毛诗音》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敦煌本地诗人之作、释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
敦煌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主要有《唐人选唐诗》(拟)、《陈子昂集》、《高适集》、《李峤杂咏注》》、《白香山诗集》及一些残存诗篇,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
《秦妇吟》世无传本,直到藏经洞打开之后,才使这首诗完整地再现于世。
《秦妇咏》全诗句228句,1600余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篇叙事诗,它深刻反映了晚唐黄巢起义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善状况,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内容,而且有生动的艺术手法,也是研究晚唐农民战争的重要史料。
王梵志诗在唐代广为流传,但《全唐诗》里没有他的诗作,宋代以后几乎无人提及他,他的诗后来也绝迹了,直到敦煌文献的发现,王梵志诗才再度为世人所知。
王梵志诗的特点是用白话诗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它是唐代诗坛上的奇花异草,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探讨我国白话诗的发展,研究我国古典诗歌和白话诗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敦煌诗歌中保存的敦煌当地诗人之作有《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拟),《敦煌廿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多为反映敦煌社会现实,赞颂敦煌山水名胜和抒发个人情怀之作。
敦煌释氏佛徒之作主要是僧人所创作的僧诗,多为阐发佛教义理和劝善修道之作。
敦煌民间诗歌都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如《咏九九诗》、《咏二十四气诗》、家训诗、学郎诗等等,这些诗艺术成就虽不很高,却充满生活气息,是研究敦煌社会生活的活资料。
敦煌歌辞,过去一般称为曲子词,除少数文人作品外,大多数来自民间,作者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在这些歌辞中,值得一说的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这个集子编选了30首作品,从时间上看,明显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敦煌歌辞由于作者的广泛性,极大地影响了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使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
另外,一些民间小唱如《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等,也属于敦煌歌辞这一范畴。
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题体裁。
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变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佛教为题材的《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降摩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舜子变》、《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等,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