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_马伯里诉麦迪逊案_的启示
- 格式:pdf
- 大小:775.71 KB
- 文档页数:7

第1篇一、案件背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律案例,发生在1803年。
这一案件不仅确立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而且对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该案的基本背景:1801年,约翰·亚当斯总统在卸任前,任命了威廉·马伯里为美国马里兰州的治安法官。
然而,在亚当斯总统卸任后,新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及其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取消了马伯里的任命。
马伯里不服,认为其任命有效,并请求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
二、案件争议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宣布一个国会立法违宪,即是否拥有司法审查权。
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和宪法,但宪法并未明确赋予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
麦迪逊认为,最高法院无权干涉国会立法,否则将侵犯国会的立法权。
而马伯里则认为,其任命有效,最高法院应强制执行这一任命。
三、法院判决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
以下是判决的主要观点:1. 宪法至上:马歇尔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或立法行为都必须符合宪法。
如果一项法律与宪法相抵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该法律无效。
2. 司法审查权:马歇尔进一步指出,最高法院有权对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以确保其符合宪法。
这一权力是宪法赋予的最高法院的固有权力。
3. 马伯里任命无效:尽管马歇尔确认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但他也认为马伯里的任命无效。
原因在于,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1801年的司法条例)授权最高法院发布命令强制执行马伯里的任命,而这一法律与1789年的司法条例相冲突,后者规定最高法院只能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
四、案件影响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美国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确立司法审查权:该案确立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使最高法院成为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机构。
2. 平衡三权分立:司法审查权的确立有助于平衡三权分立,防止立法和行政机构滥用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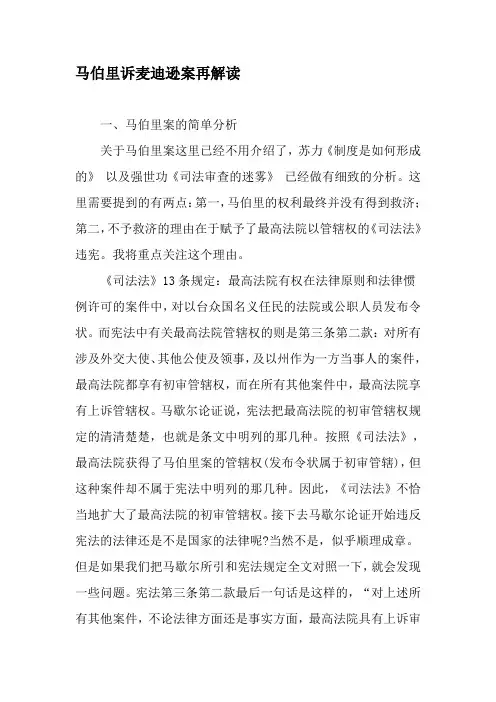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再解读一、马伯里案的简单分析关于马伯里案这里已经不用介绍了,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强世功《司法审查的迷雾》已经做有细致的分析。
这里需要提到的有两点:第一,马伯里的权利最终并没有得到救济;第二,不予救济的理由在于赋予了最高法院以管辖权的《司法法》违宪。
我将重点关注这个理由。
《司法法》13条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在法律原则和法律惯例许可的案件中,对以台众国名义任民的法院或公职人员发布令状。
而宪法中有关最高法院管辖权的则是第三条第二款:对所有涉及外交大使、其他公使及领事,及以州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最高法院都享有初审管辖权,而在所有其他案件中,最高法院享有上诉管辖权。
马歇尔论证说,宪法把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规定的清清楚楚,也就是条文中明列的那几种。
按照《司法法》,最高法院获得了马伯里案的管辖权(发布令状属于初审管辖),但这种案件却不属于宪法中明列的那几种。
因此,《司法法》不恰当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
接下去马歇尔论证开始违反宪法的法律还是不是国家的法律呢?当然不是,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如果我们把马歇尔所引和宪法规定全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宪法第三条第二款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对上述所有其他案件,不论法律方面还是事实方面,最高法院具有上诉审管辖权,但须依照国会所规定的例外和规章。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对某些案件的上诉管辖权可以被改变。
按照马歇尔的逻辑,最高法院享有的要么是初审管辖权,要么是上诉管辖权。
国会既然可以改变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结果无非是两种,一是变成初审管辖权,二是什么都没有。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国会的事情,而1789年的《司法法》正是国会立法。
也就是说,马歇尔在肯定联邦党人行为正当性的同时,又在极力回避与新政府的冲突,这一点在下面的案件中将看更清楚。
二、Stuart ird案――真相的展现实际上,在联邦党人的撤退战略中,不只是有一部《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还有一部《巡回法院法》,1801年2月13日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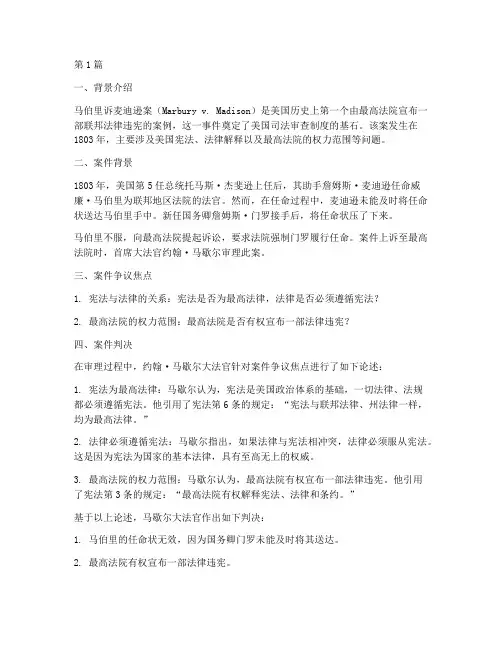
第1篇一、背景介绍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最高法院宣布一部联邦法律违宪的案例,这一事件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石。
该案发生在1803年,主要涉及美国宪法、法律解释以及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等问题。
二、案件背景1803年,美国第5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上任后,其助手詹姆斯·麦迪逊任命威廉·马伯里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
然而,在任命过程中,麦迪逊未能及时将任命状送达马伯里手中。
新任国务卿詹姆斯·门罗接手后,将任命状压了下来。
马伯里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强制门罗履行任命。
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时,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审理此案。
三、案件争议焦点1. 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宪法是否为最高法律,法律是否必须遵循宪法?2. 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宣布一部法律违宪?四、案件判决在审理过程中,约翰·马歇尔大法官针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如下论述:1. 宪法为最高法律:马歇尔认为,宪法是美国政治体系的基础,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遵循宪法。
他引用了宪法第6条的规定:“宪法与联邦法律、州法律一样,均为最高法律。
”2. 法律必须遵循宪法:马歇尔指出,如果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法律必须服从宪法。
这是因为宪法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3. 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马歇尔认为,最高法院有权宣布一部法律违宪。
他引用了宪法第3条的规定:“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法律和条约。
”基于以上论述,马歇尔大法官作出如下判决:1. 马伯里的任命状无效,因为国务卿门罗未能及时将其送达。
2. 最高法院有权宣布一部法律违宪。
五、案件影响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美国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该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石,使得最高法院有权宣布一部法律违宪。
2. 强调了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该案明确了宪法为最高法律,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遵循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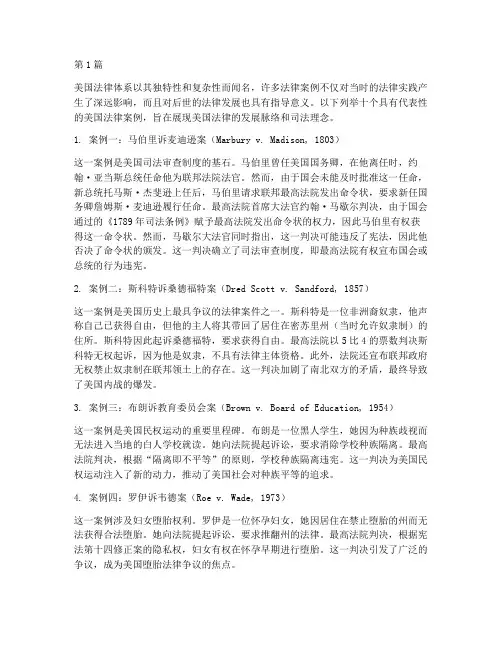
第1篇美国法律体系以其独特性和复杂性而闻名,许多法律案例不仅对当时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以下列举十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法律案例,旨在展现美国法律的发展脉络和司法理念。
1. 案例一: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 1803)这一案例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石。
马伯里曾任美国国务卿,在他离任时,约翰·亚当斯总统任命他为联邦法院法官。
然而,由于国会未能及时批准这一任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上任后,马伯里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发出命令状,要求新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履行任命。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决,由于国会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赋予最高法院发出命令状的权力,因此马伯里有权获得这一命令状。
然而,马歇尔大法官同时指出,这一判决可能违反了宪法,因此他否决了命令状的颁发。
这一判决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即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或总统的行为违宪。
2. 案例二:斯科特诉桑德福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 1857)这一案例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律案件之一。
斯科特是一位非洲裔奴隶,他声称自己已获得自由,但他的主人将其带回了居住在密苏里州(当时允许奴隶制)的住所。
斯科特因此起诉桑德福特,要求获得自由。
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判决斯科特无权起诉,因为他是奴隶,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
此外,法院还宣布联邦政府无权禁止奴隶制在联邦领土上的存在。
这一判决加剧了南北双方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的爆发。
3. 案例三: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这一案例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布朗是一位黑人学生,她因为种族歧视而无法进入当地的白人学校就读。
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消除学校种族隔离。
最高法院判决,根据“隔离即不平等”的原则,学校种族隔离违宪。
这一判决为美国民权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美国社会对种族平等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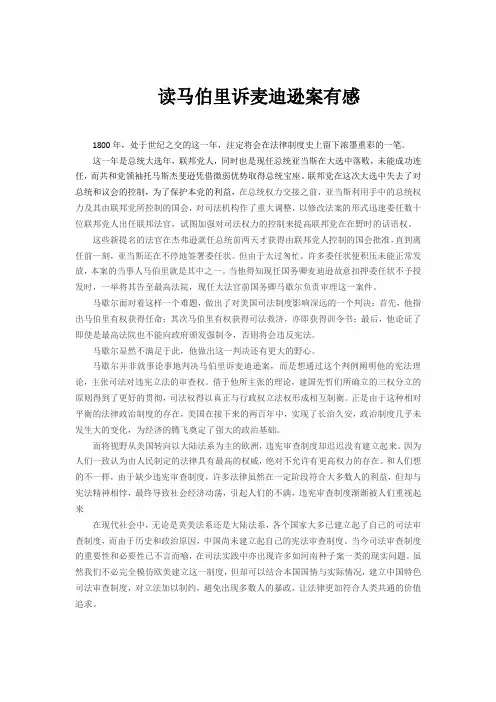
读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有感1800年,处于世纪之交的这一年,注定将会在法律制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是总统大选年,联邦党人,同时也是现任总统亚当斯在大选中落败,未能成功连任,而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凭借微弱优势取得总统宝座。
联邦党在这次大选中失去了对总统和议会的控制,为了保护本党的利益,在总统权力交接之前,亚当斯利用手中的总统权力及其由联邦党所控制的国会,对司法机构作了重大调整,以修改法案的形式迅速委任数十位联邦党人出任联邦法官,试图加强对司法权力的控制来提高联邦党在在野时的话语权。
这些新提名的法官在杰弗逊就任总统前两天才获得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批准,直到离任前一刻,亚当斯还在不停地签署委任状。
但由于太过匆忙,许多委任状便积压未能正常发放,本案的当事人马伯里就是其中之一。
当他得知现任国务卿麦迪逊故意扣押委任状不予授发时,一举将其告至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前国务卿马歇尔负责审理这一案件。
马歇尔面对着这样一个难题,做出了对美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一个判决:首先,他指出马伯里有权获得任命;其次马伯里有权获得司法救济,亦即获得训令书;最后,他论证了即使是最高法院也不能向政府颁发强制令,否则将会违反宪法。
马歇尔显然不满足于此,他做出这一判决还有更大的野心。
马歇尔并非就事论事地判决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是想通过这个判例阐明他的宪法理论,主张司法对违宪立法的审查权。
借于他所主张的理论,建国先哲们所确立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司法权得以真正与行政权立法权形成相互制衡。
正是由于这种相对平衡的法律政治制度的存在,美国在接下来的两百年中,实现了长治久安,政治制度几乎未发生大的变化,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而将视野从美国转向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欧洲,违宪审查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因为人们一致认为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绝对不允许有更高权力的存在。
和人们想的不一样,由于缺少违宪审查制度,许多法律虽然在一定阶段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却与宪法精神相悖,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动荡,引起人们的不满,违宪审查制度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大多已建立起了自己的司法审查制度,而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国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宪法审查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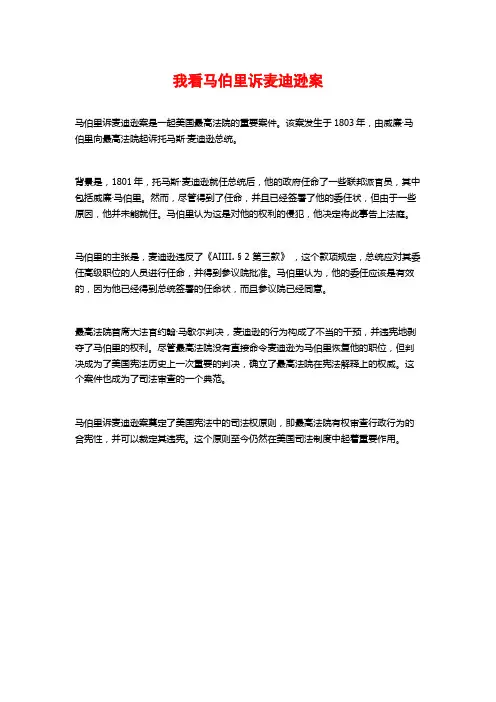
我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起美国最高法院的重要案件。
该案发生于1803年,由威廉·马伯里向最高法院起诉托马斯·麦迪逊总统。
背景是,1801年,托马斯·麦迪逊就任总统后,他的政府任命了一些联邦派官员,其中包括威廉·马伯里。
然而,尽管得到了任命,并且已经签署了他的委任状,但由于一些原因,他并未能就任。
马伯里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利的侵犯,他决定将此事告上法庭。
马伯里的主张是,麦迪逊违反了《AIIII. § 2 第三款》,这个款项规定,总统应对其委任高级职位的人员进行任命,并得到参议院批准。
马伯里认为,他的委任应该是有效的,因为他已经得到总统签署的任命状,而且参议院已经同意。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决,麦迪逊的行为构成了不当的干预,并违宪地剥夺了马伯里的权利。
尽管最高法院没有直接命令麦迪逊为马伯里恢复他的职位,但判决成为了美国宪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判决,确立了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上的权威。
这个案件也成为了司法审查的一个典范。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奠定了美国宪法中的司法权原则,即最高法院有权审查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并可以裁定其违宪。
这个原则至今仍然在美国司法制度中起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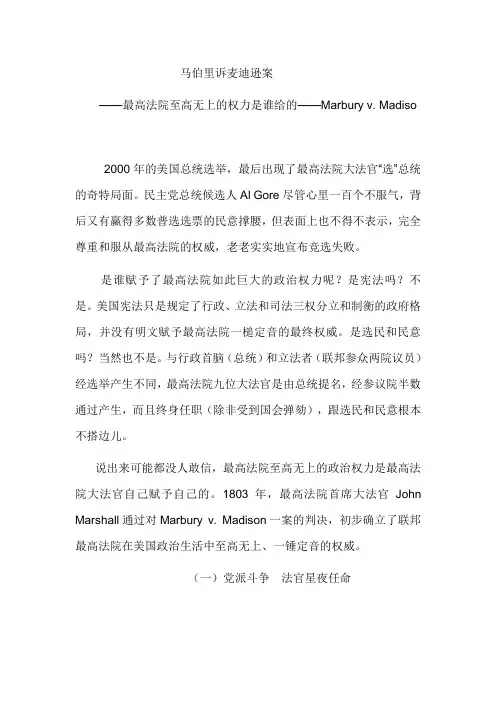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Marbury v. Madiso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最后出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选”总统的奇特局面。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Al Gore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服气,背后又有赢得多数普选选票的民意撑腰,但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完全尊重和服从最高法院的权威,老老实实地宣布竞选失败。
是谁赋予了最高法院如此巨大的政治权力呢?是宪法吗?不是。
美国宪法只是规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政府格局,并没有明文赋予最高法院一槌定音的最终权威。
是选民和民意吗?当然也不是。
与行政首脑(总统)和立法者(联邦参众两院议员)经选举产生不同,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半数通过产生,而且终身任职(除非受到国会弹劾),跟选民和民意根本不搭边儿。
说出来可能都没人敢信,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赋予自己的。
180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John Marshall通过对Marbury v. Madison一案的判决,初步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一锤定音的权威。
(一)党派斗争法官星夜任命William Marbury是美国首都Washington市Georgetown一位41岁的富商;James Madison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当时任美国政府国务卿。
富商William究竟有何政治背景?他为什么要起诉国务卿James呢?说起来,这桩影响极为深远的诉讼大案,与当时美国政坛中的党派斗争有直接关系。
经过六年的反英独立战争,美国终于在1783年赢得了独立。
美国人虽然赶走了殖民地的英国军队和总督,但却继承和发扬了英国法治传统的合理部分。
1787年9月,经联邦制宪会议制定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在美国Philadelphia诞生。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建立,却是在联邦宪法被各州批准之后(注一)。
1789年3月4日,联邦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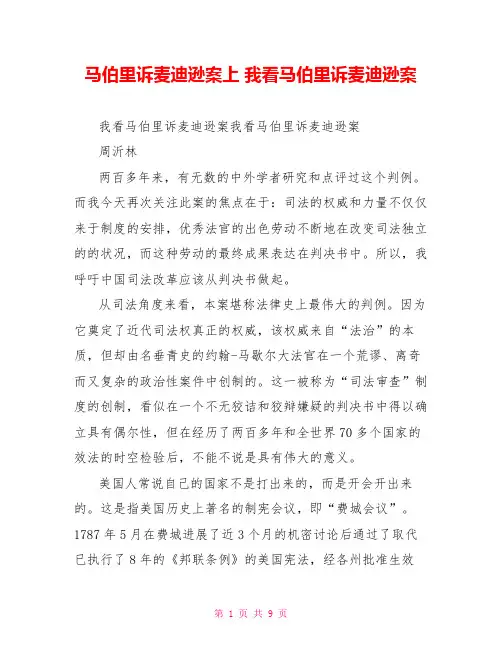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上我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我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我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周沂林两百多年来,有无数的中外学者研究和点评过这个判例。
而我今天再次关注此案的焦点在于:司法的权威和力量不仅仅来于制度的安排,优秀法官的出色劳动不断地在改变司法独立的的状况,而这种劳动的最终成果表达在判决书中。
所以,我呼吁中国司法改革应该从判决书做起。
从司法角度来看,本案堪称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判例。
因为它奠定了近代司法权真正的权威,该权威来自“法治”的本质,但却由名垂青史的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在一个荒谬、离奇而又复杂的政治性案件中创制的。
这一被称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创制,看似在一个不无狡诘和狡辩嫌疑的判决书中得以确立具有偶尔性,但在经历了两百多年和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效法的时空检验后,不能不说是具有伟大的意义。
美国人常说自己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而是开会开出来的。
这是指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即“费城会议”。
1787年5月在费城进展了近3个月的机密讨论后通过了取代已执行了8年的《邦联条例》的美国宪法,经各州批准生效后,美国才真正成为联邦制的统一国家。
从邦联到联邦,从制宪会议到批准宪法的全部过程中,充满了剧烈的辩论。
美国人自豪的地方在于:整个立国的过程是开会、辩论、智慧和“伟大的妥协”的精神,而不是诉诸武力。
这个立国和制宪传统贯彻至今、无处不有,乃至于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美国“简直是没有一个政治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的”(注1)。
本案被马歇尔大法官形容的“微妙”、“新奇”和“困难”,正是一个典型的党派政治斗争事件却必须由堂而惶之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的写照。
本案发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交替时,也是美国第二、三届总统交接时。
第二届总统是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
1800年大选,民主共和党的托马斯·杰斐逊击败亚当斯任第三届总统。
这期间两党斗争日趋剧烈。
最初的争论是围绕财政经济政策进展的。
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汉密尔顿在第一届华盛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他主张建立稳定的国家信贷、建立国家银行、征收进口税、集中权利于联邦政府,并要求从宽解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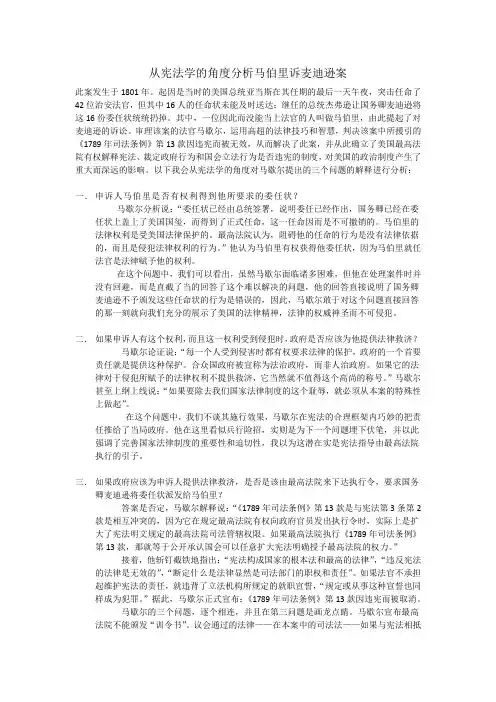
从宪法学的角度分析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此案发生于1801年。
起因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亚当斯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午夜,突击任命了42位治安法官,但其中16人的任命状未能及时送达;继任的总统杰弗逊让国务卿麦迪逊将这16份委任状统统扔掉。
其中,一位因此而没能当上法官的人叫做马伯里,由此提起了对麦迪逊的诉讼。
审理该案的法官马歇尔,运用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智慧,判决该案中所援引的《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因违宪而被无效,从而解决了此案,并从此确立了美国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裁定政府行为和国会立法行为是否违宪的制度,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下我会从宪法学的角度对马歇尔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解释进行分析:一.申诉人马伯里是否有权利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状?马歇尔分析说:“委任状已经由总统签署,说明委任已经作出,国务卿已经在委任状上盖上了美国国玺,而得到了正式任命,这一任命因而是不可撤销的。
马伯里的法律权利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
最高法院认为,阻碍他的任命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是侵犯法律权利的行为。
”他认为马伯里有权获得他委任状,因为马伯里就任法官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马歇尔面临诸多困难,但他在处理案件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直截了当的回答了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的回答直接说明了国务卿麦迪逊不予颁发这些任命状的行为是错误的,因此,马歇尔敢于对这个问题直接回答的那一刻就向我们充分的展示了美国的法律精神,法律的权威神圣而不可侵犯。
二.如果申诉人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受到侵犯时,政府是否应该为他提供法律救济?马歇尔论证说:“每一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提供这种保护。
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
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救济,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
”马歇尔甚至上纲上线说:“如果要除去我们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耻辱,就必须从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能产生的宪法学启示有哪些[本站推荐]](https://uimg.taocdn.com/f5ca6a5026284b73f242336c1eb91a37f0113241.webp)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能产生的宪法学启示有哪些[本站推荐]第一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能产生的宪法学启示有哪些[本站推荐]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能产生的宪法学启示有哪些?【高萌Goal的回答(43票)】: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并不是简简单单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而是自该案以后,美国彻底完善了三权分立制度中最后一项制度——司法权的归属。
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
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前,行政权归于美国总统、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立法权归于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司法权归于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院、联邦地方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州上诉法院、州基层法院。
但在当时,行政权和立法权相对比较强势,而各法院的司法权相对较弱,如:美国总统直接行使行政权,并且在立法方面通过否决国会的法案、向国会提交各种咨文以委托立法,在司法权可以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为终身制,且须获得参议院认可);美国国会直接行使立法权,并且在行政权方面可以弹劾总统,被否决的法案经国会2/3以上表决通过后可以推翻总动的否决令;在司法方面有权拒绝总统关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而对于美国法院来说,除直接行使司法权以外,仅剩下解释法律和联邦最高法院终身制两项权利,所以在当时三权分立中,美国法院的权限相对其他二者显得弱小许多。
但是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原国务卿、时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马歇尔确认联邦法院有权对于美国总统和政府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确立了违宪审查(又称司法审查)权利的最终归属,至此联邦最高法院除享有司法独立、解释法律、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终身制以外,还拥有对于美国总统、国会的违宪审查机制,当美国总统的行为或国会通过的法案被联邦法院认为违宪之时,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该行政命令或国会法案因违宪而无效,从而达到对于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制约,三权分立至此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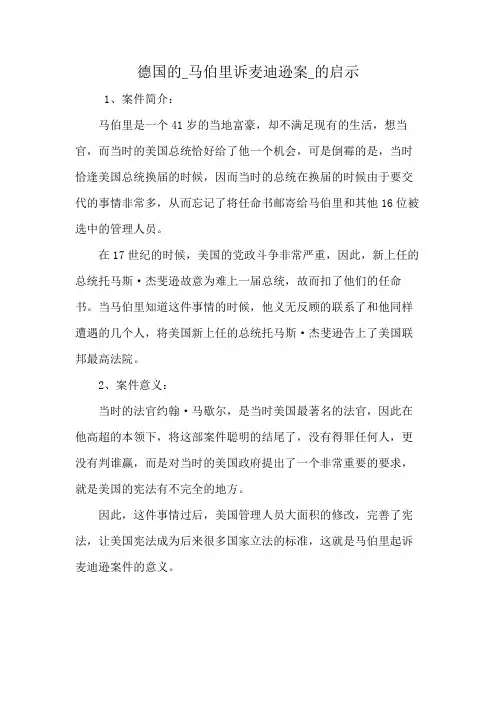
德国的_马伯里诉麦迪逊案_的启示
1、案件简介:
马伯里是一个41岁的当地富豪,却不满足现有的生活,想当官,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恰好给了他一个机会,可是倒霉的是,当时恰逢美国总统换届的时候,因而当时的总统在换届的时候由于要交代的事情非常多,从而忘记了将任命书邮寄给马伯里和其他16位被选中的管理人员。
在17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党政斗争非常严重,因此,新上任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故意为难上一届总统,故而扣了他们的任命书。
当马伯里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义无反顾的联系了和他同样遭遇的几个人,将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告上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2、案件意义:
当时的法官约翰·马歇尔,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法官,因此在他高超的本领下,将这部案件聪明的结尾了,没有得罪任何人,更没有判谁赢,而是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美国的宪法有不完全的地方。
因此,这件事情过后,美国管理人员大面积的修改,完善了宪法,让美国宪法成为后来很多国家立法的标准,这就是马伯里起诉麦迪逊案件的意义。
一、引言——缘何第一案我国法治实践中,曾经有很多的契机行使宪法审查权,但都与我们擦肩而过。
从几年前孙志刚案和齐玉苓案都可看出,我们对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是怎样的不敢面对又不能释怀。
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还可能对宪法审查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我们似乎还缺乏理论的积淀,仍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易发争议的要务。
近期,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审查的理论积累,考察各国宪法审查的实践和理论。
其中对美国和德国两个典型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审查原理情有独钟,特别是对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是津津乐道⑴。
对于宪政实践尚处于学步阶段的我国,“第一案”情结当然不可释怀,那么对于大陆法系典型的德国,其宪法审查之第一案似乎也不应绕开。
本文旨在对德国宪法审查第一案进行介绍与比较[1],并反观我国现实得出可供参考之经验。
二、棘手的遗案在德国,虽然宪法审查制度真正确立于基本法,但其雏形于帝国时期业已呈现。
帝国时期,帝国法院曾经根据联邦法和宪法优于州法的原则宣布州的立法违宪。
惟此时并未肯定宪法优于联邦议会通过的联邦法⑵,宪法与联邦法同为联邦议会所制定。
至魏玛宪法时期,情况有所转变,宪法已经赋予了法院的宪法审查权。
按照魏玛宪法,宪法院(Staatsgerichtshof)对州内部的宪法争议以及不同州或州和帝国之间的非民事的争议有管辖权,最高法院即帝国法院(Reichgericht)能够最终确定争议的州法律是否和联邦宪法相抵触。
然而宪法审查却没有真正得以实施,究其原因:(1)宪法的权利极度抽象,不具有确定的法律性,或许只能看作纲领性的原则。
(2)宪法规定议会通过法律可对宪法权利进行保留,此条款使得宪法权利的强制力大为削弱。
(3)同时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安全和秩序也可临时中止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再度受制于行政机关。
(4)未区分宪法修改与普通立法修改的程序。
议会可以通过立法修改宪145法,只要下议院的三分之二出席并且出席会议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即可通过宪法修正案。
第1篇一、引言法律是人类社会维护秩序、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工具。
在世界法律史上,涌现出了许多经典的案例,这些案例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以展现世界法律史的魅力。
二、经典案例解析1. 罗斯柴尔德诉沙普案(Roschier v. Sharp)案例背景:1784年,英国伦敦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商标侵权案。
原告罗斯柴尔德指控被告沙普侵犯了自己的商标权。
案例解析:这起案件是英国商标法历史上的第一起案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商标侵权的案例。
在判决中,法官托马斯·埃奇沃斯(Thomas Erskine)明确指出,商标是商人用来区分自己商品的一种标志,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这一判决确立了商标法的原则,对后世商标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案例背景: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司法审查权的案件。
案例解析:在这起案件中,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提出了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原则,即联邦法院有权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从而推翻这些法律。
这一原则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奠定了基础,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刑事上诉法院判决(Nuremberg Trials)案例背景:1945年至1946年,德国纳粹战犯在纽伦堡接受审判。
案例解析:纽伦堡审判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案件,它确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等概念。
刑事上诉法院的判决为战后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对国际法律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4. 艾尔斯诉汤普森案(Elsberg v. Department of Defense)案例背景:1971年,美国国防部雇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揭示了美国政府秘密参与越南战争的真相。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我国当代宪法司法化的启示
张理化
【期刊名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2012(030)001
【摘要】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马伯里决定导致了宪法的"司法化",使之成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
被部分学者誉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巨大争论。
本文从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分析适合我国当代宪政土壤的宪法司法化方案,从而期望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总页数】3页(P39-41)
【作者】张理化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1
【相关文献】
1.“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多重叙事与逻辑--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2.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启示
3.另一种视角下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4."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简评--兼议我国行政诉讼与"司法审查"
5.世界宪政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1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件,对本案的审理给法院确立了一项权利:法院有权决定议会通过的法案或总统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即司法审查原则。
个人认为本案是极为值得探讨与研究的案例,因为本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判例法的意义。
2 德莱德·斯科特案(1856年)德莱德·斯科特案结束了《密苏里妥协案》,该妥协案宣布位于北纬36度的路易斯安娜购买地区(包括现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佛蒙特州、缅因州、新泽西州和密歇根地区)的地域内,奴隶制为非法,它激化了南北两方的矛盾并促使了美国内战的发生。
与其说这是一件影响美国法学的案例,不如说它是一件推动了历史的案件。
3 雷诺德诉美利坚合众国(1879年)摩门教是犹他州的一个宗教团体,实行一夫多妻制。
在雷诺德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认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是合宪的,这与摩门教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不相矛盾,这是现存有关一夫多妻制的最重要案例。
4 布莱西诉弗古逊案(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公布布莱西诉弗古逊的判决后,“隔离而平等”成为国内法。
然而过了60多年,合法的隔离都未能完全消除。
这个案例对于美国的种族政策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法学界值得研究的案例,也是历史学上的大事。
5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确认实施种族隔离的学校是违宪的。
它推翻了“隔离而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自从布莱西诉弗古逊案(1896年)之后就成为国内法。
似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当一切矛盾都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个案件就成为了转折点。
对比1896年的案件,这是一个变革,推翻前例的变革。
6 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年)尼克松与美国政府的诉讼案发生之后,总统就不能利用行政特权——拒绝公开秘密信件的权利——而不将证据上交法庭。
水门事件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件。
7 贝克诉加利福尼亚大学案(1978年)最高法院认为,这是第一次颠倒的种族歧视案件。
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的个人见解事件概要:在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联邦党人遭到惨败,但即将卸任的联邦党人总统约翰•亚当斯利用仍然在职的机会任命了42名联邦党人担任哥伦比亚特区的治安法官。
不过时任亚当斯总统国务卿的约翰•马歇尔却没有把委任状全部发出。
当新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继任总统以后,他命令其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不向其中的17人颁发委任状,其中包括威廉•马伯里的委任状。
马伯里决定提起诉讼。
他所依据的理由是1789年《司法法》第13条的规定,即,“最高法院……有权在法律制度和习惯授予的权限的范围之内……向在合众国任职的人员……发布法院的命令状”(命令状是法院签发的一种要求具有法律责任的官员履行职责的命令)。
马伯里通过他的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最高法院向国务卿麦迪逊发布一道命令状,命令他发放委任状。
但最高法院的发言人约翰•马歇尔(当时已经成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则认为,1789年《司法法》第13条与联邦宪法第3条第1款相抵触,因为宪法本身把最高法院的初审权限制在“涉及到大使、公使、领事以及以州为当事人的案件”。
由于马伯里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类,最高法院不愿意受理此案,尽管《司法法》第13条与宪法相抵触。
判决内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主张:尽管马伯里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并应当得到法律救济,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一属于政治性的问题却没有管辖权,并且最高法院认为,马伯里所依据的1789年的《司法法》的有关规定违宪无效,不能适用于本案。
据此,最高法院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
个人见解:马伯里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如要真正拿到委任状,他必须从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
在时间与精力的不允许下,马伯里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妥协。
实际上委任状并未付诸实效,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纠纷没有达到白热化。
这场案件里,真正的赢家是马歇尔。
他作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站在全局的角度,超出了党派之争的范围,把司法的权力进行强化。
一、引言——缘何第一案我国法治实践中,曾经有很多的契机行使宪法审查权,但都与我们擦肩而过。
从几年前孙志刚案和齐玉苓案都可看出,我们对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是怎样的不敢面对又不能释怀。
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还可能对宪法审查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我们似乎还缺乏理论的积淀,仍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易发争议的要务。
近期,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审查的理论积累,考察各国宪法审查的实践和理论。
其中对美国和德国两个典型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审查原理情有独钟,特别是对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是津津乐道⑴。
对于宪政实践尚处于学步阶段的我国,“第一案”情结当然不可释怀,那么对于大陆法系典型的德国,其宪法审查之第一案似乎也不应绕开。
本文旨在对德国宪法审查第一案进行介绍与比较[1],并反观我国现实得出可供参考之经验。
二、棘手的遗案在德国,虽然宪法审查制度真正确立于基本法,但其雏形于帝国时期业已呈现。
帝国时期,帝国法院曾经根据联邦法和宪法优于州法的原则宣布州的立法违宪。
惟此时并未肯定宪法优于联邦议会通过的联邦法⑵,宪法与联邦法同为联邦议会所制定。
至魏玛宪法时期,情况有所转变,宪法已经赋予了法院的宪法审查权。
按照魏玛宪法,宪法院(Staatsgerichtshof)对州内部的宪法争议以及不同州或州和帝国之间的非民事的争议有管辖权,最高法院即帝国法院(Reichgericht)能够最终确定争议的州法律是否和联邦宪法相抵触。
然而宪法审查却没有真正得以实施,究其原因:(1)宪法的权利极度抽象,不具有确定的法律性,或许只能看作纲领性的原则。
(2)宪法规定议会通过法律可对宪法权利进行保留,此条款使得宪法权利的强制力大为削弱。
(3)同时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安全和秩序也可临时中止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再度受制于行政机关。
(4)未区分宪法修改与普通立法修改的程序。
议会可以通过立法修改宪145法,只要下议院的三分之二出席并且出席会议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即可通过宪法修正案。
(5)最后当时帝国内存在五个具有终审权的法院,在各自领域行使最终审判权,也使宪法审查权限分工不明。
以上诸多原因导致宪法审查在魏玛宪法时期夭折,从而导致法西斯统治下行政立法泛滥,人权惨遭践踏[2]。
这种状况在1949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联邦德国基本法在92条规定,最高司法权(包括宪法审查权)属于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联邦宪法法院权限范围在于以下几项,首先裁决联邦各个机关的争议(所谓的联邦宪法案件)和规范冲突案件(即联邦法和州法是否与基本法冲突以及州法是否与联邦法冲突)。
其次审查一项国际法是否能被联邦法承认;特定的政党是否因为侵犯了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而违宪;另外审查个人侵害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时其基本权是否应该受到限制,以及个人的基本权是否受到公共权力侵害等问题。
迥异于魏玛宪法,基本法设计了诸多具体落实宪法审查制度的条款。
(1)基本权条款不再是抽象的概括性的规定,代之以清晰的法律内容。
(2)纵使基本法也容许立法限制基本权,但是基本法19条明确宣称“在任何情况下,基本权的本质不可侵犯”。
(3)彻底埋葬了类似于魏玛宪法48条的宽泛的行政紧急权(Ausnahmerecht)。
基本法81条把紧急权限定在六个月内。
并不能修正、全部或局部废止或停止基本法。
(4)魏玛宪法中类似普通法的宪法修改程序发生重大嬗变,宪法修改必须分别经上议院票数的三分之二和下议院票数的三分之二方可通过。
同时规定修正案不能改变包含在基本权中的宪法基本原则。
(5)基本法规定惟有宪法法院有权宣布法律违宪,从而避免了魏玛时期宪法审查分工不明的缺陷。
凡此种种使德国阔别了魏玛宪法时代,铸就了强有力的宪法审查机制。
基本法确立宪法审查后不久,联邦宪法法院就做出了第一个违宪判决。
该案史称西南案,也被学者誉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2]。
在此,联邦宪法法院第一次判决联邦法律违宪,它指出宪法审查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也显示出联邦宪法法院对整个德国宪政制度的影响。
二战后,德国西南地区的两个州——巴登和符腾堡——被分割为三个州:符腾堡——巴登(包括巴登和符腾堡的北部),巴登(原巴登的南部)和符腾堡——霍亨左伦(包括符腾堡的剩余地区),成为联邦德国的独立的州。
这种安排是美国和法国针对占领地区设计的,但是不久人们就看出如此分割并不合适,1948年军事占领当局也建议各州的州长考虑按照传统边界进行必要的调整。
由于德国当时只有拜仁、汉堡和不来梅三个州沿用了原来的区域结构,所以德国人民也希望重新调整德国的各州区域,从而形成政治、经济和历史上联系更紧密的州。
这种要求最后体现在1949年基本法中,基本法规定了德国区域重新划分的原则。
基本法29条规定一般地区领土结构的调整原则,与该条不同的是,基本法118条对西南地区三个州的区域重组做出特殊的规定,即该地区的区域调整可以不依照本基本法第29条之规定,而依有关各州之协议进行⑶。
并且如果西南各州不能达成协议,应该由联邦通过立法予以调整,同时联邦立法必须规定先进行民意测验。
由于在重组过程中三个州确实没有达成协议,联邦政府就于1951年5月4日制定所谓的“第一区划调整法(Neugliederungsgesetz)”和“第二区划调整法”,同时按宪法要求规定了民意测验。
因为两州临近议会选举,第一部区划调整法规定延长巴登和符腾堡—霍亨左伦两州的州议会任期,直到西南地区区域重划完成并且州宪法被宣布无效时,但是不能超过1952年3月31日。
第二部区域调整法具体设计了公民投票的方式。
针对两部区域调整法,巴登州于1951年5月25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联邦通过的两项法律侵犯了巴登州公民的权利,该法律和基本法多个条款抵触因此不能生效⑷。
并要求确定两部法律从1951年5月4日起失效,同时请求法院颁发临时禁令,禁止两部法律的实施,直到法院做出判决。
其后1951年9月7日巴登又提出法院应该确认联邦无权通过第一区划调整法延长州议会的任期。
三、效法美国——融会贯通基本法确立宪法审查制度后,在制度设计上和具体裁判方法上,联邦宪法法院都毫不避讳地借鉴美国的经验。
特别是在该案中,联邦宪法法院第一次审查法律的合宪性,该制度在德国历史上尚属空白,法院大胆参照美国违宪审查的方法。
如德国学者麦伦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为美国法院的学生,效法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方法和风格[2]。
146(一)联邦宪法法院一如美国最高法院对违宪审查表现出积极的立场如同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一样,宪法法院并不拘泥于争讼双方的争议问题,而是全面解释了宪法上的原则,以展示宪法法院在宪法实施和保障中意欲扮演的积极角色。
这种积极的审查方式大多为其他普通法院审判所禁止,普通法院只能就当事人之间的争点做出判决,所谓“不告不理”。
在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案件核心在于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问题。
如果没有管辖权,法院就不需进入实体问题的讨论。
但马歇尔判决伊始即直奔宪法的实质问题,浓墨重彩地论述司法审查、宪法至上和普通法中司法独立第原则,而对程序问题却在结尾部分突然提出[3]。
凡此种种只为建立违宪审查辩护。
西南案中法院同样从每个可能的法律角度审查所有的条文的合宪性,包括那些没有被提起诉讼的问题⑸。
例如,本案中巴登州要求审查第二区域调整法的第10条规定的投票程序违反平等原则,而此条款正是根据基本法第118条第2款的授权制定的。
虽然宪法法院无需引征基本法第3条和第19条的平等条款同样能够作出判决,但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还是详细阐述了法律面前平等原则的内涵,力图一劳永逸地阐明宪法中平等原则的含义,然而在判决和文献中,平等原则的解释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
(二)在对宪法原则的解释上,德国法院也借鉴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意见针对巴登州提出的第二部区域调整法第10条规定之投票程序违反了法律面前平等原则的问题,法院采取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理论。
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各州不得否定任何人在其辖区内的平等保护“。
在立法上,惟有“合理”的差别待遇方能得以承认,并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实施三种不同强度的审查:严格审查、中度审查和合理审查。
类似地,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平等原则同样拘束立法机关,它禁止对实质上相同的事物差别对待,而不禁止对实质上不同的事物就其不同的程度给予不同待遇。
这种见解显然来源于美国的平等权判决。
宪法法院认为如果法律在给予同等对待或者差别对待时没有提出属于“事物本质”(Der Natur der Sache)的或逻辑上可以解释的理由,那么该法就违反了平等原则。
根据这项要求法院作出判决,西南地区的问题不同于联邦其他的州,它由占领军(Besatzungsmächte)划分,且一直被认为是临时的,人们确信这种现状将不会维持下去。
所以对西南地区采取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区划调整方法的基本法第118条第2款和第二部区域调整法第10条并不违反平等原则⑹。
同时法院也对民主和联邦原则进行解释。
按照民主原则(基本法第20,28条),州的合宪性秩序必须符合民主法治国的原则。
民主不只要求人民的代表统治政府,更重要的是选举权不能以宪法没有规定的方式随意剥夺或减少。
虽然议会的任期可以因为某些原因而延长,比如因为战争原因,但是联邦政府无权阻止某个州进行州宪法规定的选举,只有本州人民才可以决定延长议会任期。
本案中联邦通过立法延长州议会任期,推迟即将到期的选举,侵犯了该州人民的选举权,违反了民主原则。
另外联邦立法延长州议会的任期侵犯了联邦原则(基本法第20,28,30条)⑺。
第一,即使联邦法可以废除州,进而会缩短州的议会任期,但不能以此“延长”州议会的任期。
废除一个州一定会缩短州议会任期,而不可能延长州议会任期,州议会任期的延长必须由州自身的立法行为决定。
第二,联邦不能干涉州的内部事务,即使州同意接受联邦的安排也不可以干涉。
在联邦制下联邦不能经过州的同意获得立法权,在波恩基本法框架下州享有的统治权并非来自联邦,它是自始存在并被联邦承认的。
只要在基本法28条第1款的范围内⑻,州内部合宪性制度的安排都由该州决定,特别是有关州内部结构、功能和权限的安排就是州的自身事务,还包括公民行使表决权的期限,在什么前提下州议会必须停止工作等决定。
第三,基本法第70条第2款规定联邦享有专属立法和共同立法权⑼,但是只有在“单个州立法不能真正有效规制”时才需要联邦行使共同立法权。
本案中即使延长州议会的事项属于州和联邦的共同立法,也不存在“单个州立法不能真正有效规制”的情况⑽。
(三)西南案中宪法法院对宪法判决的效力认定也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法院规定判决和所依据的理由将拘束所有的宪法机关,立法机关不能再次讨论和通过同样内容的联邦法[4]。
麦伦(Arthur T. von Mehren)发现西南案判决的语言和推理显示法院有意识的证明自己的权威,并为以后的宪法审查的判决提供必备的要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