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指南专家共识解读
- 格式:pptx
- 大小:1.18 MB
- 文档页数: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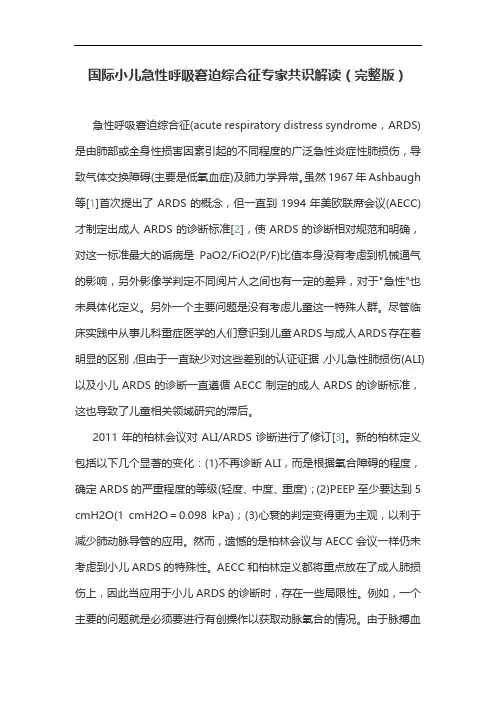
国际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专家共识解读(完整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由肺部或全身性损害因素引起的不同程度的广泛急性炎症性肺损伤,导致气体交换障碍(主要是低氧血症)及肺力学异常。
虽然1967年Ashbaugh 等[1]首次提出了ARDS的概念,但一直到1994年美欧联席会议(AECC)才制定出成人ARDS的诊断标准[2],使ARDS的诊断相对规范和明确,对这一标准最大的诟病是PaO2/FiO2(P/F)比值本身没有考虑到机械通气的影响,另外影像学判定不同阅片人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对于"急性"也未具体化定义。
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儿童这一特殊人群。
尽管临床实践中从事儿科重症医学的人们意识到儿童ARDS与成人ARDS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由于一直缺少对这些差别的认证证据,小儿急性肺损伤(ALI)以及小儿ARDS的诊断一直遵循AECC制定的成人ARDS的诊断标准,这也导致了儿童相关领域研究的滞后。
2011年的柏林会议对ALI/ARDS诊断进行了修订[3]。
新的柏林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显著的变化:(1)不再诊断ALI,而是根据氧合障碍的程度,确定ARDS的严重程度的等级(轻度、中度、重度);(2)PEEP至少要达到5 cmH2O(1 cmH2O=0.098 kPa);(3)心衰的判定变得更为主观,以利于减少肺动脉导管的应用。
然而,遗憾的是柏林会议与AECC会议一样仍未考虑到小儿ARDS的特殊性。
AECC和柏林定义都将重点放在了成人肺损伤上,因此当应用于小儿ARDS的诊断时,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必须要进行有创操作以获取动脉氧合的情况。
由于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仪的广泛使用,儿童动脉血气的测量越来越少,因此小儿ARDS的发生率可能会被低估。
第二个问题仍然是P/F比值问题,除了需要采集动脉血气测定氧分压以外,该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呼吸机参数的影响[4,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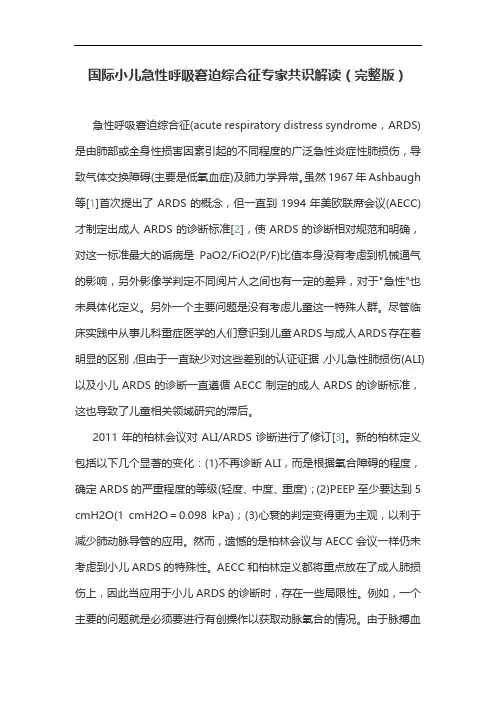
国际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专家共识解读(完整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由肺部或全身性损害因素引起的不同程度的广泛急性炎症性肺损伤,导致气体交换障碍(主要是低氧血症)及肺力学异常。
虽然1967年Ashbaugh 等[1]首次提出了ARDS的概念,但一直到1994年美欧联席会议(AECC)才制定出成人ARDS的诊断标准[2],使ARDS的诊断相对规范和明确,对这一标准最大的诟病是PaO2/FiO2(P/F)比值本身没有考虑到机械通气的影响,另外影像学判定不同阅片人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对于"急性"也未具体化定义。
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儿童这一特殊人群。
尽管临床实践中从事儿科重症医学的人们意识到儿童ARDS与成人ARDS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由于一直缺少对这些差别的认证证据,小儿急性肺损伤(ALI)以及小儿ARDS的诊断一直遵循AECC制定的成人ARDS的诊断标准,这也导致了儿童相关领域研究的滞后。
2011年的柏林会议对ALI/ARDS诊断进行了修订[3]。
新的柏林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显著的变化:(1)不再诊断ALI,而是根据氧合障碍的程度,确定ARDS的严重程度的等级(轻度、中度、重度);(2)PEEP至少要达到5 cmH2O(1 cmH2O=0.098 kPa);(3)心衰的判定变得更为主观,以利于减少肺动脉导管的应用。
然而,遗憾的是柏林会议与AECC会议一样仍未考虑到小儿ARDS的特殊性。
AECC和柏林定义都将重点放在了成人肺损伤上,因此当应用于小儿ARDS的诊断时,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必须要进行有创操作以获取动脉氧合的情况。
由于脉搏血氧饱和度监测仪的广泛使用,儿童动脉血气的测量越来越少,因此小儿ARDS的发生率可能会被低估。
第二个问题仍然是P/F比值问题,除了需要采集动脉血气测定氧分压以外,该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呼吸机参数的影响[4,5,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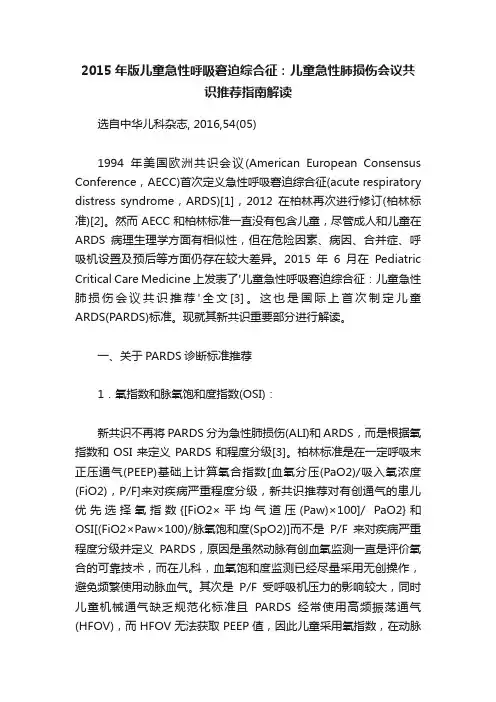
2015年版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儿童急性肺损伤会议共识推荐指南解读选自中华儿科杂志, 2016,54(05)1994年美国欧洲共识会议(American European Consensus Conference,AECC)首次定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1],2012在柏林再次进行修订(柏林标准)[2]。
然而AECC和柏林标准一直没有包含儿童,尽管成人和儿童在ARDS病理生理学方面有相似性,但在危险因素、病因、合并症、呼吸机设置及预后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
2015年6月在Pediatric Critical Care Medicine上发表了'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儿童急性肺损伤会议共识推荐'全文[3]。
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制定儿童ARDS(PARDS)标准。
现就其新共识重要部分进行解读。
一、关于PARDS诊断标准推荐1.氧指数和脉氧饱和度指数(OSI):新共识不再将PARDS分为急性肺损伤(ALI)和ARDS,而是根据氧指数和OSI来定义PARDS和程度分级[3]。
柏林标准是在一定呼吸末正压通气(PEEP)基础上计算氧合指数[血氧分压(PaO2)/吸入氧浓度(FiO2),P/F]来对疾病严重程度分级,新共识推荐对有创通气的患儿优先选择氧指数{[FiO2×平均气道压(Paw)×100]/ PaO2}和OSI[(FiO2×Paw×100)/脉氧饱和度(SpO2)]而不是P/F来对疾病严重程度分级并定义PARDS,原因是虽然动脉有创血氧监测一直是评价氧合的可靠技术,而在儿科,血氧饱和度监测已经尽量采用无创操作,避免频繁使用动脉血气。
其次是P/F受呼吸机压力的影响较大,同时儿童机械通气缺乏规范化标准且PARDS经常使用高频振荡通气(HFOV),而HFOV无法获取PEEP值,因此儿童采用氧指数,在动脉血气不可获取的情况下采用OSI评估儿童的氧合情况更加实际可行,当然P/F也被推荐用作PARDS的诊断标准,主要针对无创通气,如使用持续气道正压(CPAP),CPAP≥5 cm H2O(1 cmH2O=0.098 kPa)或双向气道正压(BiPAP)通气的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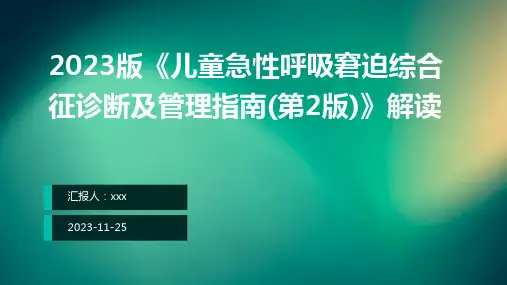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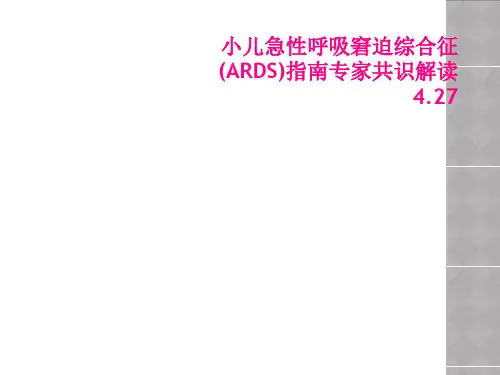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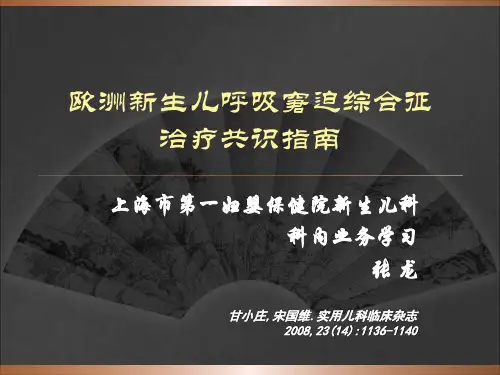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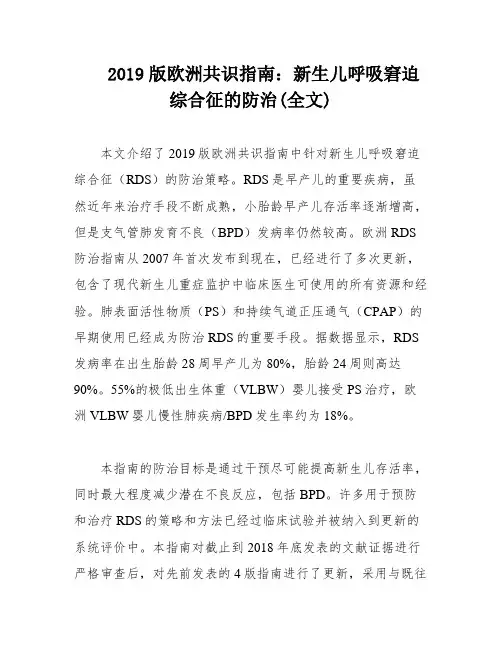
2019版欧洲共识指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防治(全文)本文介绍了2019版欧洲共识指南中针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DS)的防治策略。
RDS是早产儿的重要疾病,虽然近年来治疗手段不断成熟,小胎龄早产儿存活率逐渐增高,但是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发病率仍然较高。
欧洲RDS 防治指南从2007年首次发布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多次更新,包含了现代新生儿重症监护中临床医生可使用的所有资源和经验。
肺表面活性物质(PS)和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的早期使用已经成为防治RDS的重要手段。
据数据显示,RDS 发病率在出生胎龄28周早产儿为80%,胎龄24周则高达90%。
55%的极低出生体重(VLBW)婴儿接受PS治疗,欧洲VLBW婴儿慢性肺疾病/BPD发生率约为18%。
本指南的防治目标是通过干预尽可能提高新生儿存活率,同时最大程度减少潜在不良反应,包括BPD。
许多用于预防和治疗RDS的策略和方法已经过临床试验并被纳入到更新的系统评价中。
本指南对截止到2018年底发表的文献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后,对先前发表的4版指南进行了更新,采用与既往指南相似的格式总结防治策略,列出循证推荐,使用GRADE等级反映每个推荐意见的证据支持力度。
针对产前管理,本指南提出了多项建议。
妊娠<28~30周、存在早产风险的孕妇均应转诊到具有诊治RDS经验的围产中心。
理想情况下,对妊娠34周内存在早产风险的孕妇至少在分娩前24小时给予单疗程产前激素治疗。
妊娠<32周再次出现早产征象,且距第1个疗程产前激素治疗超过1~2周者,可重复给予1个疗程激素治疗。
妊娠<32周,紧急分娩前应给予硫酸镁(MgSO4)治疗。
先兆早产的孕妇,可进行宫颈长度测量和胎儿纤维连接蛋白含量测定,以避免不必要的使用保胎药和(或)产前使用激素。
对极早产孕妇应考虑短期使用保胎药治疗,以有时间完成1个疗程产前激素治疗和(或)将孕妇转运至围产中心。
在产房内稳定阶段,需要对新生儿进行评估,包括评估患儿病程早期呼吸做功和吸入氧浓度(FiO2),以判断是否需要给予PS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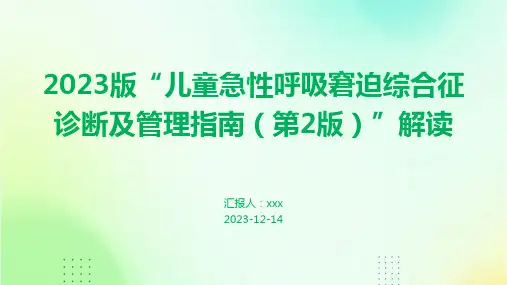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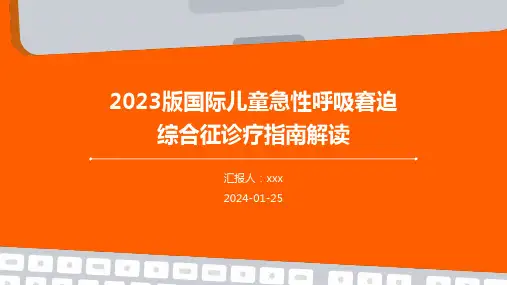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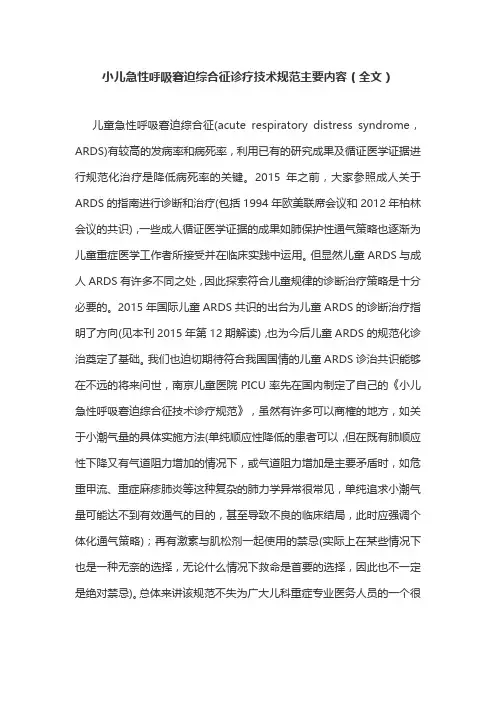
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疗技术规范主要内容(全文)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有较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循证医学证据进行规范化治疗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2015年之前,大家参照成人关于ARDS的指南进行诊断和治疗(包括1994年欧美联席会议和2012年柏林会议的共识),一些成人循证医学证据的成果如肺保护性通气策略也逐渐为儿童重症医学工作者所接受并在临床实践中运用。
但显然儿童ARDS与成人ARDS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探索符合儿童规律的诊断治疗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2015年国际儿童ARDS共识的出台为儿童ARDS的诊断治疗指明了方向(见本刊2015年第12期解读),也为今后儿童ARDS的规范化诊治奠定了基础。
我们也迫切期待符合我国国情的儿童ARDS诊治共识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问世,南京儿童医院PICU率先在国内制定了自己的《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技术诊疗规范》,虽然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如关于小潮气量的具体实施方法(单纯顺应性降低的患者可以,但在既有肺顺应性下降又有气道阻力增加的情况下,或气道阻力增加是主要矛盾时,如危重甲流、重症麻疹肺炎等这种复杂的肺力学异常很常见,单纯追求小潮气量可能达不到有效通气的目的,甚至导致不良的临床结局,此时应强调个体化通气策略);再有激素与肌松剂一起使用的禁忌(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论什么情况下救命是首要的选择,因此也不一定是绝对禁忌)。
总体来讲该规范不失为广大儿科重症专业医务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参考,也希望藉此开展关于儿童ARDS诊治的讨论,为今后制定相关共识打下基础。
1 定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由非心源性的各种肺内外致病因子所导致的急性进行性呼吸衰竭。
ARDS病理特征为肺泡毛细血管屏障广泛破坏、肺泡内蛋白渗出性肺水肿、肺不张、肺实变;临床以肺顺应性下降、呼吸窘迫、紫绀、顽固性低氧血症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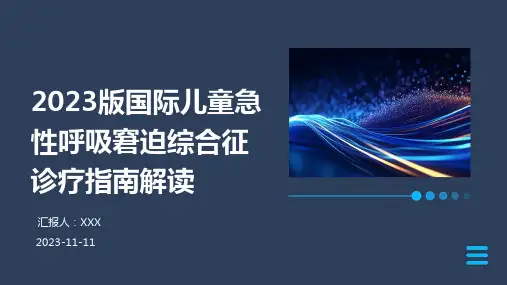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从共识到定义解读本文原载于《国际呼吸杂志》2012年第14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一具有复杂病理和发病机制的危重症临床综合征,病死率很高。
因此,为更好治疗、管理患者并改善疾病预后。
以及为临床研究人选此类患者提供具有可比性的统一标准,有必要制定有效且可靠的定义[1]。
从1967年Ashbaugh等I-幻首次报道ARDS以来,陆续有多种定义被提出,但是,得到广泛认同的是1994年美国一欧洲共识会(AECC)上提出的ARDS定义[3]。
此定义利于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的获取。
规范了临床研究患者人选的标准,并由此进行了多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ARDSnet),从而提高ARDS认识和治疗水平。
然而,在经过18年的实践研究后,发现了一些关于信度和效度的问题。
鉴于此,2011年欧洲急危重症医学学会组建专家小组制定了新版定义——柏林定义(该次行动经美国胸科学会及重症医学学会支持),重点关注其可行性、可靠性及有效性,并对其实用性进行了客观评价。
1AECC定义制定的局限性及柏林定义新进展1.1 AECC定义局限性及修正1994年AECC会议制定的ARDS定义存在的问题包括:急性肺损伤的时间标准存在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标准区别PaO2/Fi02对不同通气参数设置的敏感性;缺乏急性肺损伤与ARDS的鉴别标准;胸部影像学标准可靠性差;难以区分流体静力性肺水肿(表1)等。
新版定义——柏林定义指出了AECC定义的不足,并对其做出修正(表1)。
1.2 柏林定义——共识讨论与经验验证结合专家组在制定定义时,首次采用共识讨论与经验评价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关注定义的可行性、可靠性、实际有效性(如临床医师如何识别ARDS)及预测有效性[预测治疗反应和(或)预后的能力]。
经过初步的准备及面对面的共识讨论。
提出了定义草案,并经经验评价。
1.2.1 共识讨论后的定义草案 ARDS概念:ARDS是一种急性弥漫性炎症性肺损伤,导致肺血管通透性和肺重量增加,而肺含气组织减少。
2021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早期防治专家共识(全文)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的早期防治工作,在对我国不同胎龄早产儿RDS 发生率及高危因素进行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1-2]的基础上,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和《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经过充分讨论达成本共识,以供临床参考。
随着证据及经验的不断增加,此共识将适时予以更新修订。
一、产前糖皮质激素促胎肺成熟1.孕妇存在以下任一情况,且在7 d内有早产分娩可能,建议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在产前给予1个疗程的糖皮质激素以促胎肺成熟[1-7]:孕周<35周;妊娠期血糖控制未达到理想水平的糖尿病患者;孕35~36周+6择期剖宫产。
2.对已完成1个疗程糖皮质激素治疗7 d后的孕妇,如在孕34周前仍有发生早产的风险,可考虑再次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1个疗程[5-6]。
3.对于孕周<35周的孕妇,如无法完成1个疗程,应尽可能给予糖皮质激素≥1次[3,6]。
4.用法[3-6]:地塞米松5~6 mg/次,肌内注射,12 h重复1次,共4次,为1个疗程;倍他米松10~12 mg/次,肌内注射,24 h重复1次,共2次,为1个疗程。
5.注意[3,6]:不推荐常规使用2个及以上疗程的糖皮质激素;不推荐口服或静脉注射。
二、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nCPAP)1.根据临床情况,当早产儿存在以下指征时,应生后即刻给予nCPAP 治疗。
(1)出生胎龄≤30周,有较强自主呼吸[7-10]。
(2)出生胎龄>30周,有自主呼吸且具备下列其中2项以上者[9-13]:产前未进行糖皮质激素促胎肺成熟或剂量、疗程不足;出生体重<1 250 g;糖尿病患者孕期血糖未达到理想水平;择期或急诊剖宫产;多胎;男胎;母亲产前有发热、胎膜早破或白细胞计数>15×109/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