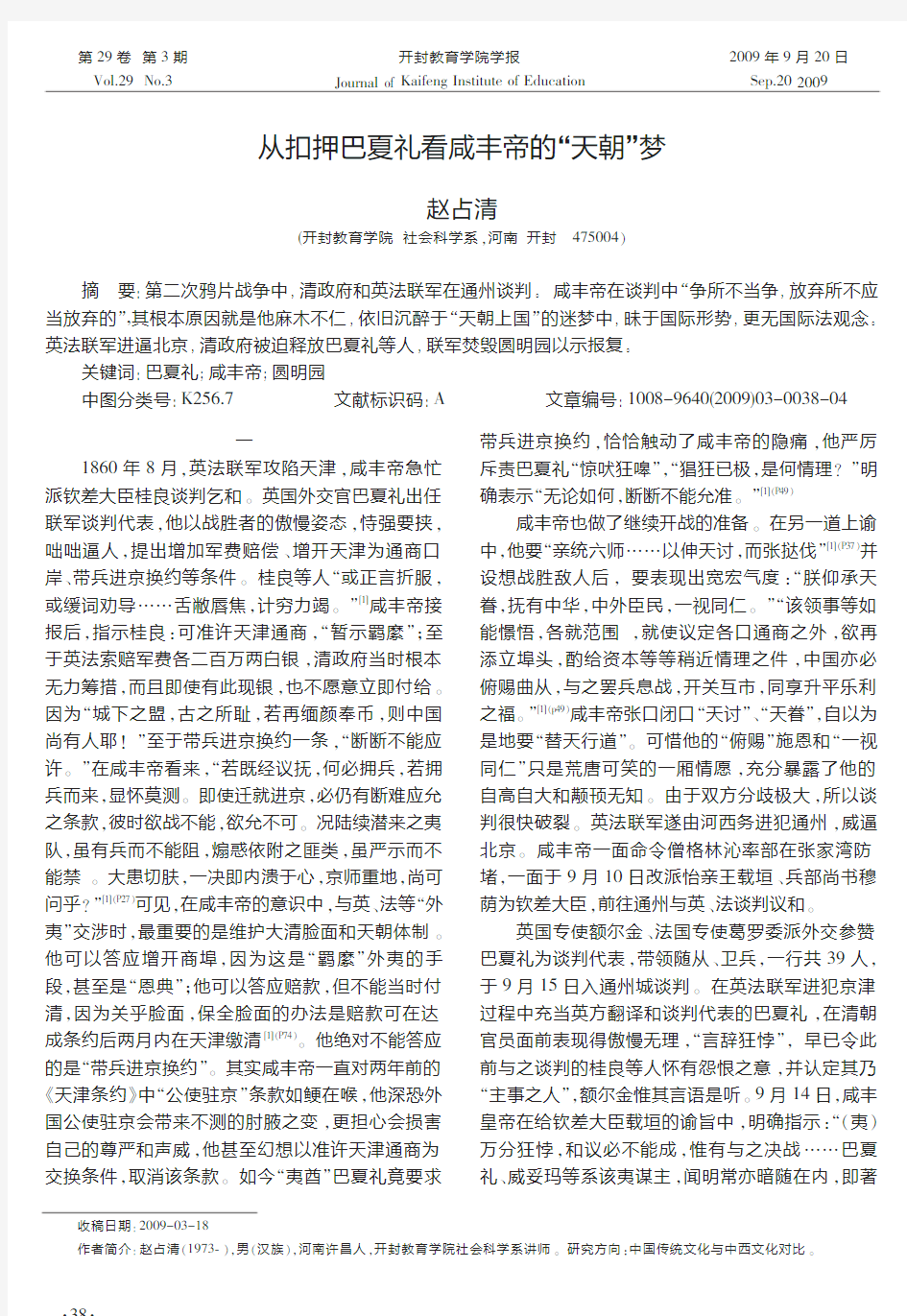

一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咸丰帝急忙
派钦差大臣桂良谈判乞和。英国外交官巴夏礼出任联军谈判代表,他以战胜者的傲慢姿态,恃强要挟,咄咄逼人,提出增加军费赔偿、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带兵进京换约等条件。桂良等人“或正言折服,或缓词劝导……舌敝唇焦,计穷力竭。”[1]咸丰帝接报后,指示桂良:可准许天津通商,“暂示羁縻”;至于英法索赔军费各二百万两白银,清政府当时根本无力筹措,而且即使有此现银,也不愿意立即付给。因为“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缅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至于带兵进京换约一条,“断断不能应许。”在咸丰帝看来,“若既经议抚,何必拥兵,若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即使迁就进京,必仍有断难应允之条款,彼时欲战不能,欲允不可。况陆续潜来之夷队,虽有兵而不能阻,煽惑依附之匪类,虽严示而不能禁。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京师重地,尚可问乎?”[1](P27)可见,在咸丰帝的意识中,与英、法等“外夷”交涉时,最重要的是维护大清脸面和天朝体制。他可以答应增开商埠,因为这是“羁縻”外夷的手段,甚至是“恩典”;他可以答应赔款,但不能当时付清,因为关乎脸面,保全脸面的办法是赔款可在达成条约后两月内在天津缴清[1](P74)。他绝对不能答应的是“带兵进京换约”。其实咸丰帝一直对两年前的《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条款如鲠在喉,他深恐外国公使驻京会带来不测的肘腋之变,更担心会损害自己的尊严和声威,他甚至幻想以准许天津通商为交换条件,取消该条款。如今“夷酋”巴夏礼竟要求
带兵进京换约,恰恰触动了咸丰帝的隐痛,他严厉斥责巴夏礼“惊吠狂嗥”,“猖狂已极,是何情理?”明确表示“无论如何,断断不能允准。”[1](P49)
咸丰帝也做了继续开战的准备。在另一道上谕中,他要“亲统六师……以伸天讨,而张挞伐”[1](P37)并设想战胜敌人后,要表现出宽宏气度:“朕仰承天眷,抚有中华,中外臣民,一视同仁。”“该领事等如能憬悟,各就范围,就使议定各口通商之外,欲再添立埠头,酌给资本等等稍近情理之件,中国亦必俯赐曲从,与之罢兵息战,开关互市,同享升平乐利之福。”[1](p49)咸丰帝张口闭口“天讨”、“天眷”,自以为是地要“替天行道”。可惜他的“俯赐”施恩和“一视同仁”只是荒唐可笑的一厢情愿,充分暴露了他的自高自大和颟顸无知。由于双方分歧极大,所以谈判很快破裂。英法联军遂由河西务进犯通州,威逼北京。咸丰帝一面命令僧格林沁率部在张家湾防堵,一面于9月10日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与英、法谈判议和。
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委派外交参赞巴夏礼为谈判代表,带领随从、卫兵,一行共39人,于9月15日入通州城谈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得傲慢无理,“言辞狂悖”,早已令此前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怀有怨恨之意,并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明确指示:“(夷)万分狂悖,和议必不能成,惟有与之决战……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
收稿日期:2009-03-18
作者简介:赵占清(1973-),男(汉族),河南许昌人,开封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中西文化对比。
从扣押巴夏礼看咸丰帝的“天朝”梦
赵占清
(开封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河南开封
475004)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和英法联军在通州谈判。咸丰帝在谈判中“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
当放弃的”,其根本原因就是他麻木不仁,依旧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昧于国际形势,更无国际法观念。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清政府被迫释放巴夏礼等人,联军焚毁圆明园以示报复。
关键词:巴夏礼;咸丰帝;圆明园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09)03-0038-04
第29卷第3期Vol.29No.3开封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09年9月20日Sep.202009
·38
·
将各该夷及随从人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1](P67)
由此可见,在通州谈判前,咸丰皇帝已有意相机扣押巴夏礼。他是以“擒贼先擒王”的传统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和议必不能成”,而且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可以杜其奸计,进一步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由于对战局实在没有把握,咸丰帝又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的回旋余地。很明显,虽然谈判前咸丰帝有羁禁“谋主”巴夏礼的意图,然而其态度尚模棱两可,并未下定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上谕中,咸丰皇帝还指示载垣,谈判时“恐该夷以宾礼自居,长其骄傲”,所以不必接见巴夏礼,只遣下属与之辩驳,“以崇天朝体制”。[1](P67)——
—敌兵压境,情势危急,咸丰皇帝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天朝体制”,这种虚文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根本行不通。
载垣等主持的通州谈判同样艰难。巴夏礼蛮横坚持天津谈判时的条件,依旧“狂悖无礼”。载垣等手中并无底牌,他们深知如果开战,依靠僧格林沁“实系毫无把握,并距京甚近,实有投鼠忌器之虑”[1](P71)最终不得不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并奏报咸丰帝。咸丰帝迫于严峻的形势,只得一一照准,甚至连此前“断断不能允准”的“带兵进京换约”也被批准了。真是步步退让,徒唤奈何!正当咸丰帝和载垣等人以为和议已经达成,所有问题已经解决时,又生枝节。9月17日,巴夏礼突然提出要求:他本人要向大清皇帝亲递和约并且不行跪拜大礼。载垣等认为以前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美、俄两国也无此先例,遂表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1](P79)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不必列入谈判内容,声称不许亲递国书,即是中国不愿和好。[1](P80)
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决,载垣等飞报咸丰帝。咸丰帝指示:“(亲递国书一事)国体所存,万难允许……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1](P86)同时谕令僧格林沁:“如果夷酋能遵天朝礼节,拜跪呈递国书,自属可行……诚恐夷情多生枝节,并无就抚之心,仍带夷兵过张家湾,著即行痛剿,不必再为顾惜抚局”[1](P87)但巴夏礼不仅拒绝跪拜,还要求僧格林沁撤军。面对巴夏礼的步步进逼,载垣等认为“该夷狂悖至此,抚局断无可议”[1](P80)遂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39人擒拿羁留。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在通州谈判过程中,咸丰帝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乾纲独断”。在前台与英法侵略者苦苦周旋的钦差大臣载垣、穆荫等事事都要请示汇报,处处秉承皇帝的谕旨行事,并无随机应变、灵活处置的权力。当然,作为“奴才”,他们也不会有这种意识和担当。面对强敌,咸丰帝步步退让,以求达成和议。当和议已成之际,咸丰帝却不惜决裂,下令扣押巴夏礼等谈判人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逆转呢?首要原因是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向咸丰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并且不愿遵从中国礼制行跪拜大礼。咸丰帝最看重的恰恰是“礼制”。在他眼中,赔款、通商都是小事,甚至是对外夷的恩典,最重大的事情是亲递国书时必须行“跪拜大礼”,事关“国体”,所以寸步不让,甚至不惜决裂。在咸丰帝做出重大让步,同意亲递国书的情况下,巴夏礼依然拒绝行跪拜大礼。如此“桀骜不驯”,咸丰帝终于“龙颜大怒”。另一原因是咸丰帝深谙“擒贼擒王”之道,他早已有意羁禁“谋主”,如今眼见巴夏礼如此“悖逆”,“丧心病狂”,最终下定扣押巴夏礼的决心。
二
扣押敌国的外交使节,竟然是为了维护“国体”。遗憾的是,咸丰和臣属维护的其实是一个梦,一个虚幻的、事实上早已破碎的“天朝上国”的迷梦。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是清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视其他国家为蛮夷,对外关系只讲“藩属朝贡”。“中国人相信:雄踞于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中国是君临一切的中心,中国的统治者的职责是把所有其他统治者当作他的臣属。远方的国家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关系,也被列为遥远的朝贡国,他们仍都被认为是藩。”[2]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深刻地左右着从皇帝到普通臣民的心理,影响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鸦片战争前,多个西方国家为与清王朝建立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向华遣使达25次之多。生活在封闭文明躯壳里的专制君主和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举国上下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不可能平等地对待域外的民族。统治者相信“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3]正因为如此,清朝皇帝对于来华的西方外交使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不管合理与否,一概严加排斥。不但如此,还满以为“天威能使万心降”,西方国家可以被感化,对天朝顶礼膜拜。1793年,清政府把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当做贡使团接待,要求英使对乾隆帝行跪叩大礼,双方因此发生激烈争执;二十多年后的1816年,这一幕再次上
·39·
演。清政府仍然把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当做贡使团接待,同样要求英使对嘉庆帝行跪叩大礼,遭到拒绝。嘉庆皇帝很扫兴,发出上谕:“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3]——
—充分暴露了蔑视西方、唯我独尊的大国心态和君临天下、颐指气使的帝王气概。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败迹象显露无遗,但巨大的历史惯性继续遮蔽着人们的视野。朝野上下,“开眼看世界”的人实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仍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咸丰皇帝也不例外。他在内忧外患中即位,很想有所作为,但并没有认真总结教训,仍然麻木不仁,妄自尊大。对于西方使节提出的“修约”要求,严排固拒。例如,在1858年广州陷落,部分地方大员如直隶总督谭廷襄等奏请清政府能否将英、法所请通商、保教等事“先行办理,以解危机”时,他严厉批评谭不识大体,指出“现在广东省城尚未交还,叶总督尚未送回,岂有不加罪反与加恩之礼?”[3]并坚持《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断难更改。如今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在谈判过程中一再退让,赔款、通商等条件一一应允,甚至接受了“亲递国书”的要求,最后却在外国公使是否行“跪拜大礼”的所谓“国体”问题上勃然大怒,下令扣押巴夏礼等谈判代表,以示“惩戒”——
—颟顸、骄纵、自大、无知……此种“帝王气概”令后人感慨万千: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近七十年了,清王朝从皇帝到大臣仍纠缠于“跪拜大礼”,死抱着陈腐的“国体”不知变通,没有对时代的变化做出一点积极的反应;鸦片战争结束已近二十年,但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满、汉大员们仍然没有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醒来。清政府在情势发生剧变时仍然顽固坚持贵华夏,贱夷狄,夷夏之大防不可僭越的传统观念,历史似乎停滞了!
三
扣押巴夏礼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P80)咸丰帝也相信“巴酋系该夷谋主,善于用兵,现在就获,夷心必乱,若更以民团截其后路,可望一鼓歼除。”[1](P89)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户部右侍郎袁希祖吹嘘“自古平夷之功,未有捷于此者也。”建议“皇上临御午门,献俘阙下,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奏请将巴夏礼“立正典刑,拔去祸根”。[4]一时间满朝高官弹冠相庆,似乎首逆既已就擒,全歼“丑夷”指日可待。
现实无情地证明了这是清政府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9月18日,联军发动猛烈进攻,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21日再败于八里桥。22日,咸丰皇帝仓皇出奔热河,并撤消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改授恭亲王奕讠斤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接办和局。
英法联军继续加紧进犯。奕讠斤拿不出任何退敌之策,只是认定“巴夏礼虽非渠魁,罪同首逆,又系该夷画策之人,幸已就获,岂可遽令生还?”[4](P217)企图以巴夏礼等为人质,要求英法先退兵,再画押(即订约),最后释放巴夏礼等。英法两国拒绝了奕讠斤的条件,并限期三日释还被押英法员弁,答应全部条件并盖印画押,否则就要攻破京师。双方照会往来,相持不下,奕讠斤并未按联军要求在三日之内释放巴夏礼,只是将其移至高庙,予以优待,并派人多次游说,劝说巴夏礼致信城外联军暂缓攻城,退兵议和。但联军依靠强大的军事后盾,态度强硬,坚决要求立即释放被扣人员。奕讠斤的“人质外交”毫无效果。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闯入圆明园,对这座清政府经营百余年,综合中外建筑艺术,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字画和奇珍异宝的皇家园林进行了持续两天的大肆劫掠,并对赃物公开拍卖。
奕讠斤见情势危急,仓皇出城避至长辛店,留直隶总督恒福在京与联军交涉。10月7日,威妥玛约见恒福,扬言除非立即放还巴夏礼等,否则即行攻城。此时的京城,危如累卵,人心大乱,难民逃兵充塞道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忧城破,求和之心急切;一方面对奕讠斤避居城外,不肯亲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满。于是,在10月8日与恒福公议将巴夏礼等八人先行释放,并由恒福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此时距巴夏礼被扣已有20余日。
巴夏礼等八人被释放后,英法联军照会奕讠斤,限13日交出安定门,否则立将京城攻开;又致函恒福,立将所拿获之英法诸人,尚未送还者即日送还。在侵略者炮口威胁下,13日午时留守官员打开安定门,联军顺利入城,控制了大清国的首都。
10月12日至16日,其他遭扣押的英法谈判人员陆续被送达联军大营。这些人受到了残酷折磨:二十六名英国人,死伤各半;十三名法国人,七死六伤。[5]《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4](P396)这种情形对联军刺激极大,英国专使额尔金做出强烈反应。他14日拟就的信函中,斥责清政府违背国际公法,要求赔偿英国抚恤银三十万两,法二十万两;并“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
·40·
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同时声称在圆明园内找到了被杀谈判人员的尸体和遗物,[4](P424)为了对清朝皇帝虐杀外交代表的这一野蛮行为实施报复,要将圆明园毁为平地,其理由如下: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严创中国政府,即就人道以言,亦不能厚非也。[4](P394)额尔金明确表示以上责罚未行之前,与清王朝决无和议可言。
法国反对焚毁圆明园及天津立碑纪念二事,希望早日达成和议。但英国人态度坚决,额尔金解释说毁坏圆明园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想取消毁坏圆明园这件事,若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呈现出来,作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4](P403)
10月16日,额尔金致函葛罗,坚持“毁坏圆明园一事,余决不能舍弃而不行也……于专制君主之暴行,不得不如此以惩之,使其觉悟责任之重大,行事必自食其报也。”[4](P452)10月18日,联军在驻地和圆明园等处公然贴出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既未参预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4](P400)
英军调集数千名士兵,在圆明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变成一片火海,黑烟笼罩,火光冲天,相距20多华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这座举世无双的宏伟秀丽的皇家园林,除少数建筑外,都化为灰烬。
四
清政府扣押作为英、法谈判代表的巴夏礼等人,是近代中外战争史和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事例。清政府是在将巴夏礼等人作为谈判代表接待、而不是两军对垒的状况下将其扣押,不能用“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解释。在当时明显的敌强我弱的局势下,这种做法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益处,只不过给侵略者提供了一个施展暴行的借口而已。
1840年,英国远征军的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原因,还不力图振作革新,这才是民族的致命伤。道光、咸丰年间的统治阶层并未汲取失败的教训,战前与战后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开眼看世界”的人士实属凤毛麟角,咸丰帝和他的那些重臣们,完全不懂国际形势,更无国际法观念,依旧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6]直到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圆明园燃起冲天大火后,少数满汉官员痛定思痛,才开始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上,我们追思它100多年前的劫难,固然要铭记英法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同时更要深刻反思清王朝茫然不察外情的积习之深、为害之大。“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7]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无情结论和深刻启迪。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2][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危兆盖.清季使节制度近代化开端述评[J].江汉论坛,1995,(11):35-40.
[4]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将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李楠)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