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反传统
- 格式:doc
- 大小:32.0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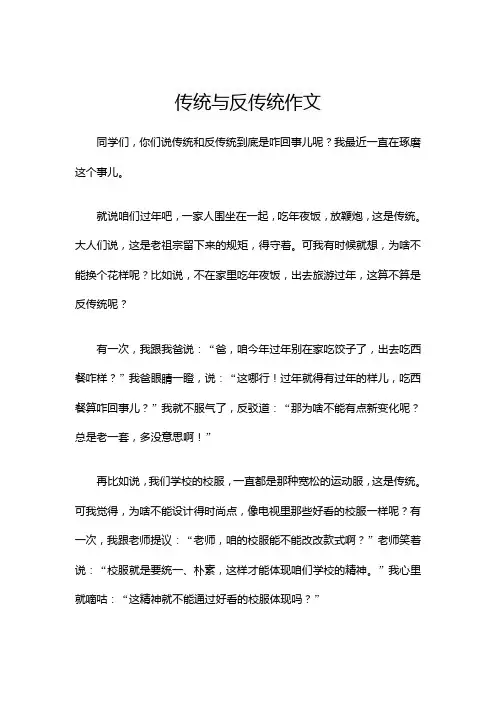
传统与反传统作文同学们,你们说传统和反传统到底是咋回事儿呢?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就说咱们过年吧,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放鞭炮,这是传统。
大人们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得守着。
可我有时候就想,为啥不能换个花样呢?比如说,不在家里吃年夜饭,出去旅游过年,这算不算是反传统呢?有一次,我跟我爸说:“爸,咱今年过年别在家吃饺子了,出去吃西餐咋样?”我爸眼睛一瞪,说:“这哪行!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样儿,吃西餐算咋回事儿?”我就不服气了,反驳道:“那为啥不能有点新变化呢?总是老一套,多没意思啊!”再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校服,一直都是那种宽松的运动服,这是传统。
可我觉得,为啥不能设计得时尚点,像电视里那些好看的校服一样呢?有一次,我跟老师提议:“老师,咱的校服能不能改改款式啊?”老师笑着说:“校服就是要统一、朴素,这样才能体现咱们学校的精神。
”我心里就嘀咕:“这精神就不能通过好看的校服体现吗?”还有啊,我们的课堂教学,一直都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我们在下面听,这也是传统。
可我听说有的学校,学生可以分组讨论,自己上台讲。
我就想,为啥咱们不能也这样呢?难道只有老师讲我们听才是对的吗?但是呢,反传统也不是啥都好。
比如说,尊老爱幼这可是传统美德,总不能反了吧?要是有人觉得老人啰嗦就不理他们,那能行吗?再比如诚实守信,这能反吗?要是大家都撒谎,那世界不就乱套啦?所以说啊,传统和反传统,就像两条路。
传统是我们熟悉的老路,走起来心里踏实;反传统呢,是一条新路,可能充满惊喜,也可能有坑洼。
我们不能一味地守着传统,不敢迈出一步;也不能啥传统都不管,瞎走乱闯。
那到底该咋办呢?我觉得啊,对于好的传统,咱们得珍惜,得传承;对于那些不太好的,或者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传统,咱们就可以勇敢地去改变,去创新。
就像一棵大树,根是传统,让我们稳稳地站立;枝叶是反传统,让我们向着阳光生长。
同学们,你们说我说得对不对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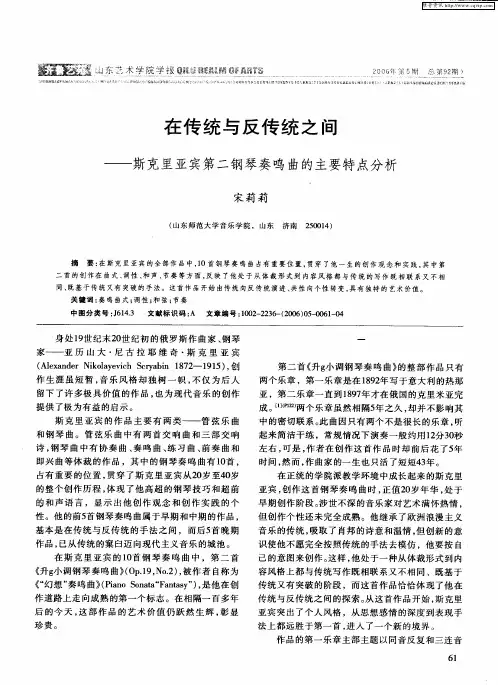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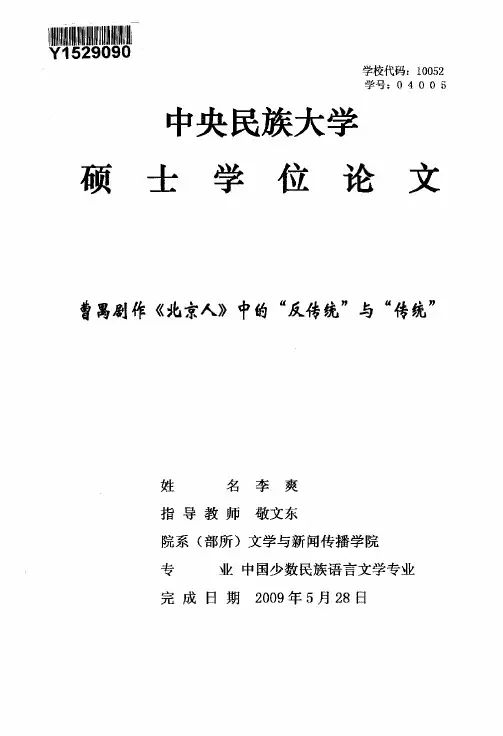
曹禺剧作《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作者:李爽
学位授予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1.孙兆恒.SUN Zhao-heng从《北京人》看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期刊论文]-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4)
2.刘静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以《北京人》为例[期刊论文]-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6(4)
3.李扬.LI Yang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期刊论文]-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
4.蔡年华.CAI Nian-hua走出"围城"——论曹禺戏剧中的"自由"思想[期刊论文]-新余高专学报2007,12(3)
5.赖琼玉.LAI Qiong-yu性格命运与文化悲剧--再读曹禺的《北京人》[期刊论文]-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22(1)
6.余竹平.YU Zhu-ping论曹禺的母性情怀[期刊论文]-许昌学院学报2008,27(6)
7.汪树东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期刊论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9(4)
8.孟显智生命的空壳地道的废物——谈《北京人》中的"中国多余人"[期刊论文]-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6(2)
9.曹树钧曹禺百年——江安之恋与《北京人》的诞生[期刊论文]-上海采风2010(7)
10.王凡文明批判视野下的理想探寻——曹禺前期戏剧中的原始追寻[期刊论文]-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0(10)
引用本文格式:李爽曹禺剧作《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学位论文]硕士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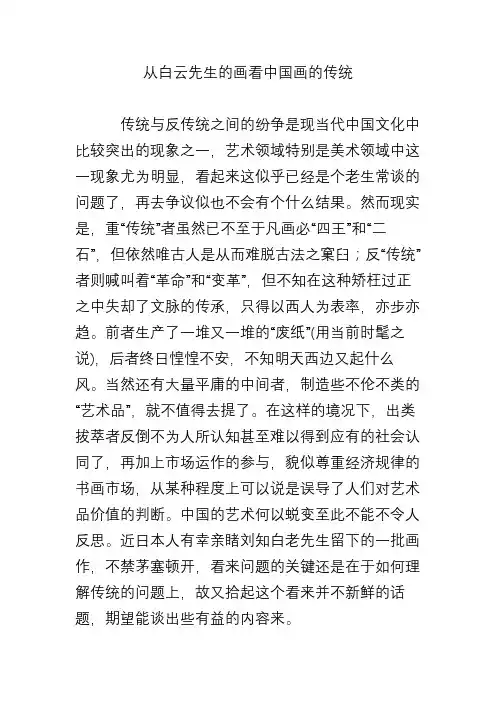
从白云先生的画看中国画的传统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纷争是现当代中国文化中比较突出的现象之一,艺术领域特别是美术领域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看起来这似乎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再去争议似也不会有个什么结果。
然而现实是,重“传统”者虽然已不至于凡画必“四王”和“二石”,但依然唯古人是从而难脱古法之窠臼;反“传统”者则喊叫着“革命”和“变革”,但不知在这种矫枉过正之中失却了文脉的传承,只得以西人为表率,亦步亦趋。
前者生产了一堆又一堆的“废纸”(用当前时髦之说),后者终日惶惶不安,不知明天西边又起什么风。
当然还有大量平庸的中间者,制造些不伦不类的“艺术品”,就不值得去提了。
在这样的境况下,出类拔萃者反倒不为人所认知甚至难以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同了,再加上市场运作的参与,貌似尊重经济规律的书画市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误导了人们对艺术品价值的判断。
中国的艺术何以蜕变至此不能不令人反思。
近日本人有幸亲睹刘知白老先生留下的一批画作,不禁茅塞顿开,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理解传统的问题上,故又拾起这个看来并不新鲜的话题,期望能谈出些有益的内容来。
由于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是由知白先生的泼墨山水画而引发的,也可以看作是对知白先生之艺术的一种品读和体悟吧,所以还得由知白先生的画说起。
隐逸于贵州数十年的刘知白先生过去并不为画坛所熟知,直至其仙逝的前几年(上世纪90年代末)被冯其庸先生慧眼所识并推介于大众后,才逐渐引起了中国画坛的关注,一时间评说者众,其中不乏国内知名的学者和美术批评家。
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给予画家的艺术成就以高度的评价,特别是对画家后期创作的泼墨山水画予以了颇具价值的剖析与释读。
所以,贵州画家刘知白的名字在现在的美术界已不陌生。
撰写本文的初衷并不是想锦上添花地凑个热闹,笔者以为出色的画家的价值并非靠几个评论家和几篇赞美文字就能够得以充分揭示的,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时间就是试金石;更不是依靠时下世俗中流行的充满商业气息的“包装”,那样只能让一些所谓的“名家”堕落成了“印钞机”,以及让那些做着增值之梦的“收藏者”懵懂解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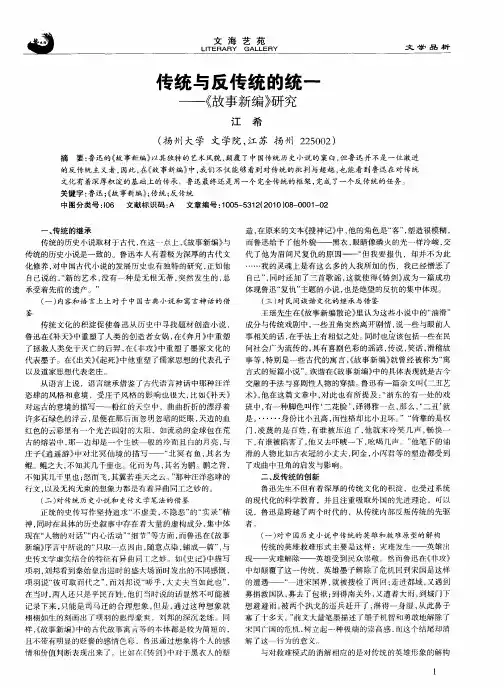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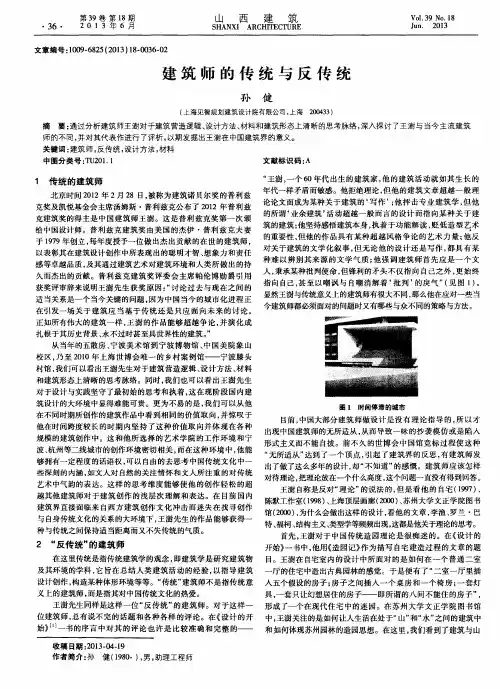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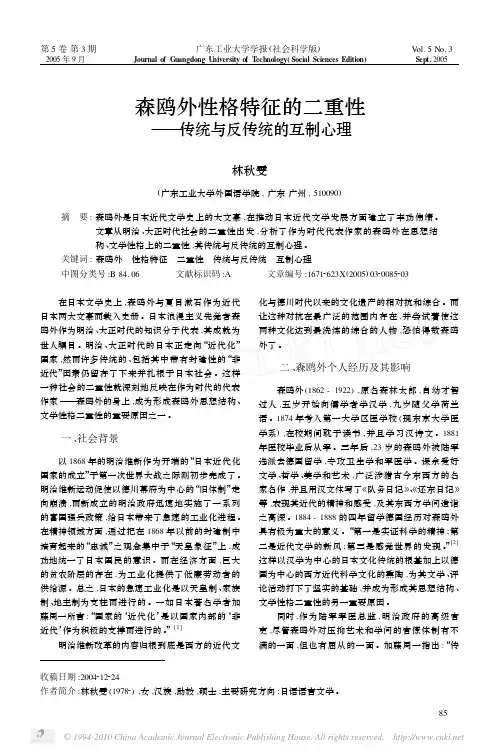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04212224作者简介:林秋雯(19782),女,汉族,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
森鸥外性格特征的二重性———传统与反传统的互制心理林秋雯(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090)摘 要:森鸥外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在推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
文章从明治、大正时代社会的二重性出发,分析了作为时代代表作家的森鸥外在思想结构、文学性格上的二重性,其传统与反传统的互制心理。
关键词:森鸥外 性格特征 二重性 传统与反传统 互制心理中图分类号:B 8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23X (2005)0320085203 在日本文学史上,森鸥外与夏目漱石作为近代日本两大文豪而载入史册。
日本浪漫主义先觉者森鸥外作为明治、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其成就为世人瞩目。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正走向“近代化”国家,然而许多传统的、包括其中带有封建性的“非近代”因素仍留存了下来并扎根于日本社会。
这样一种社会的二重性就深刻地反映在作为时代的代表作家———森鸥外的身上,成为形成森鸥外思想结构、文学性格二重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社会背景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作为开端的“日本近代化国家的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则初步完成了。
明治维新运动促使以德川幕府为中心的“旧体制”走向崩溃,而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迅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富国强兵政策,给日本带来了急速的工业化进程。
在精神领域方面,通过把在1868年以前的封建制中培育起来的“忠诚”之观念集中于“天皇象征”上,成功地统一了日本国民的意识。
而在经济方面,巨大的贫农阶层的存在,为工业化提供了低廉劳动者的供给源。
总之,日本的急速工业化是以天皇制、家族制、地主制为支柱而进行的。
一如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所言:“国家的‘近代化’是以国家内部的‘非近代’作为积极的支撑而进行的。
”[1]明治维新改革的内容归根到底是西方的近代文化与德川时代以来的文化遗产的相对抗和综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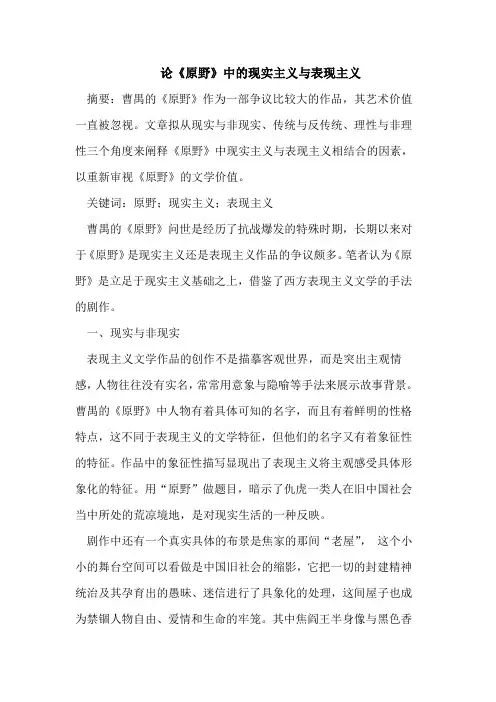
论《原野》中的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摘要:曹禺的《原野》作为一部争议比较大的作品,其艺术价值一直被忽视。
文章拟从现实与非现实、传统与反传统、理性与非理性三个角度来阐释《原野》中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相结合的因素,以重新审视《原野》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原野;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曹禺的《原野》问世是经历了抗战爆发的特殊时期,长期以来对于《原野》是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作品的争议颇多。
笔者认为《原野》是立足于现实主义基础之上,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文学的手法的剧作。
一、现实与非现实表现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不是描摹客观世界,而是突出主观情感,人物往往没有实名,常常用意象与隐喻等手法来展示故事背景。
曹禺的《原野》中人物有着具体可知的名字,而且有着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同于表现主义的文学特征,但他们的名字又有着象征性的特征。
作品中的象征性描写显现出了表现主义将主观感受具体形象化的特征。
用“原野”做题目,暗示了仇虎一类人在旧中国社会当中所处的荒凉境地,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
剧作中还有一个真实具体的布景是焦家的那间“老屋”,这个小小的舞台空间可以看做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它把一切的封建精神统治及其孕育出的愚昧、迷信进行了具象化的处理,这间屋子也成为禁锢人物自由、爱情和生命的牢笼。
其中焦阎王半身像与黑色香案中所供奉的狰狞可怖、三头六臂金眼的菩萨等摆设,都成为一种无形的封建权势代表。
仇虎与焦家的仇怨并不因为焦阎王的死而终结,而代之以心理上的冲突来支配戏剧动作。
焦阎王虽没有出场,但那阴森的照片却有着无形的力量,使得焦家人与仇虎在精神上仍旧承受着焦阎王遗留气息的冲击与影响。
《原野》一剧中的许多道具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火车”及“铁镣”。
在承载着人们痛苦、快乐和希望的“铁轨”上无边疾驰的“火车”,始终是仇虎与金子美好愿望的一种现实载体;而“铁镣”则是一种束缚物体,现实的铁镣可以束缚人的行动,可是心灵的铁镣却能禁锢人性。
剧本结尾处铁镣的再次出现,正是仇虎的灵魂再次被囚禁的真实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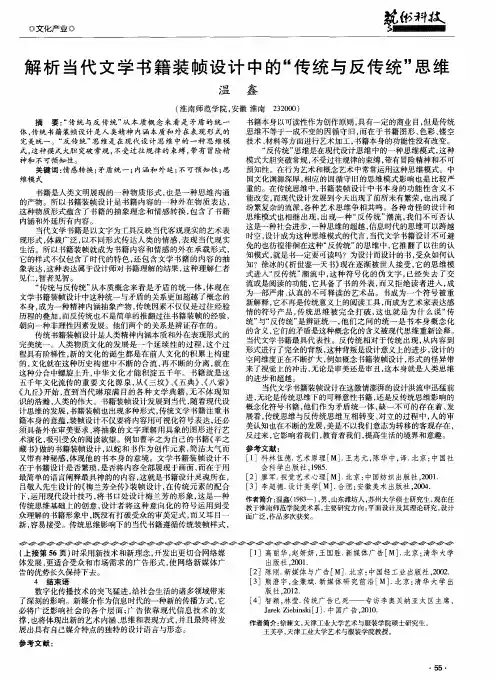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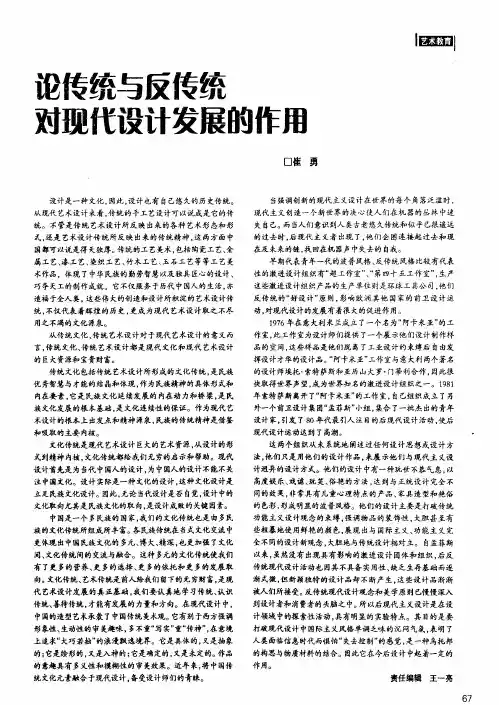
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作者:林贤治来源:《读书》2010年第09期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大会上做演讲,说到中国有两位“圣人”。
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但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圣人”就不再是圣人了。
几十年来,对鲁迅我们一直维持“三个家”的正面评价。
九十年代,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将各种恶谥加在鲁迅头上,大张挞伐,以至于把他的作品清扫出教科书之外。
几乎与此同时,“国学”大热,孔子再度成摩登圣人。
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不少地方举行祭孔的盛大礼仪,“孔子学院”多达四五百座,遍布世界各地。
古今两“圣人”在当代思想场域中的升沉变化,隐约透出某些历史的玄机。
但是孔子和鲁迅的阐释者,大抵埋首于个案研究,并不曾把他们的思想言论置于更廓大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比较,居间将玄机说破。
在比较思想史的意义上,王得后先生新近出版的《鲁迅与孔子》,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
王先生承了“五四”精神的余绪,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著作建立在“为人生”的基础上。
它既是学术性的,又是启蒙性的。
王先生认为,孔子和鲁迅都是为人生的,而且都是为了改良这人生,但接着指出:鲁迅与孔子的思想的全部差异,仅仅在于改良之道的不同。
按照鲁迅关于我们“当务之急”的意见,王先生把人生分解为“生存、温饱、发展”三个根本问题,其中又参考了孔子“三纲”中的男女、父子、君臣三项,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
作者从《论语》和《鲁迅全集》中找出相关的思想断片,《论语》还配了四家译文,以利于青年阅读;然后逐个梳理、阐述、比较、批判和总结。
问题意识在这里是支配性的。
由问题构成不同章节,每章结构大体相同,有如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加,从多个方面凸显作为中国新旧文化代表人物的分歧所在。
孔子和鲁迅处于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首尾两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转型时期。
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维护一种封闭的、僵死的专制等级制度,鲁迅却在极力促使据说是“天经地义”的既成的秩序趋于瓦解。
电影的叙事结构:传统与反传统在艺术创作中,所谓结构,指如何组织、安排作品中的内容、要素。
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不同构成要素。
比如说,音乐的构成要素是旋律、节奏、音色,绘画的构成要素是色彩、线条和明暗。
但是,在结构方面却有着相似或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音乐中的乐节、乐句、乐段、乐章就像文学中的词语、句子、段落、章回一样,在作曲家和作家的安排下展现各自的艺术魅力。
电影艺术的结构就是影片的叙事结构,它是影片生命的骨骼和主干,是确立一部影片的基本面貌和风格特征的最重要方面。
影片的叙事结构与剧本、导演风格和电影的主题密不可分。
不同的叙事方式有着各自的特点与功能。
一、传统的线性结构在电影艺术中最常见也最为传统的叙事手法就是线性叙事从故事的开始到故事的完结,始点和终点之间是保持直线的,这样的叙事就像音乐曲式结构中的单乐章,不仅结构单一明了,也有着起承转合的戏剧性。
线性结构还有个称呼叫做因果式或戏剧式线性结构。
电影的开始往往就是故事的起因,而观众探寻结果的好奇心理就成为剧情的推动力。
这种叙事中的因果关系可以设置很多要求:情节的完整、细节的可信、情感的真实等等。
在《看电影的艺术》中列举了好故事应具备的几点要素:好的故事要有完整的情节;好的故事是可信的;好的故事是有趣的;好的故事既简单又复杂;好的故事应有节制地处理感情戏。
采用线性叙事的电影必须是一个好故事,有趣的、值得回味的故事。
因为,只有好的故事才可以符合线性结构的叙事要求:以线性时间简单又复杂地展开故事,追求情节上环环相扣、符合逻辑完整可信的结局,强调感情,制造高潮,也不失控制。
这种叙事结构源于电影剧本的文学性、戏剧性。
此类型叙事结构有娓娓道来的情节铺垫,也有最后一分钟营救等高潮。
在电影艺术中,大部分影片都属于此类型的叙事方式。
影片《桃花灿烂》《理智与情感》都属于此类型的叙事结构。
在观影过程中,观看者不需要花费过多精力去猜测人物关系,事件的前因后果,也不会看到让人意外的结局,甚至观看者可以猜到故事发展的趋势。
Lu Xun's " Tradition" and " Anti-tradition"——Talking about It from "Youth Must Read Books"
作者: 冯跃华[1];陈瑾[2]
作者机构: [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2]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咸阳250022
出版物刊名: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35-341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4期
主题词: 鲁迅;"青年必读书";传统;启蒙
摘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语境中的鲁迅往往被视为"反传统"的代表.随着"后启蒙"时代的到来,鲁迅对"传统"的怀恋情愫开始被发掘,鲁迅的"传统"与"反传统"达成微妙的平衡.事实上,作为"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历史中间物",鲁迅在情感结构与文化心理上固然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但鲁迅的理性不允许鲁迅做出妥协.为此,鲁迅不惜在语言上进行极端言说,在逻辑上进行整体断裂,这恐怕是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认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缘由所在.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言论不仅是策略性的考量,同样源于鲁迅的生命体验、现实的力量驱使以及他对时代的体认.。
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文化”传统任何时代的思想构建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反思能力,以及在反思过程中挖掘思想、精神资源的深度。
对于思想史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我这里指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因为在七十年代以前,思想史上留下来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断层,只有七十年代末以后,政治局面的变化才使“思想”获得萌生与发展的机会一思想界面临着价值的危机与新生的契机。
价值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的急遽变化而产生的思想、精神资源的危机,而新生的契机则主要表现为,面对危机浮出水面并广受注意,如果能够营造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与一种保障自由权利的民主机制,这个时代有可能焕发出更强的思想活力。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
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
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
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
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
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
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
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
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
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
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
只要提起周星驰的电影,人们立刻会联想到一个关键词:无厘头。
现在一般都把“无厘头”理解为庸俗的搞笑,但其实它和单纯的恶搞还是有所区别的。
“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语,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语言和行为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无目的,粗俗随意,但并非没有道理。
由此可见,“无厘头”的语言或行为实质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是透过其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本质的一种手段。
而现在,人们往往只关注于它“无道”的表象而忽略了其“有道”的内涵。
这一点,尤其以不熟悉粤语文化的内地人最为明显。
纵观香港影史其实很早就有无厘头的传统,但直到周星驰的出现和风格的确立,“无厘头”才由一个雕虫小技演变成众人争相效仿的大智慧。
“无厘头”归结起来当属后现代文化的一脉,而且非常典型的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种种特征。
虽然当今对“后现代”的认识仍是比较模糊的,“即使在西方,‘后现代’一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概括的注解”。
但是“西方多位后现代理论家都直接对它做过说明、表述,国内也早有人总结过‘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如说后现代主要是无中心、无深度、零散化的,典型的表现为反历史主义、反形而上学”等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也将后现代定义为“叙述转向开放、嬉戏、中断、转换或模糊的种种更为多意的形式。
”其实这些表述归纳起来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个词——反传统。
而反传统恰恰是周星驰电影最大的特征。
反传统的外衣反传统的形式无外乎三种:夸张、讽刺和自嘲。
首先是夸张。
无厘头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是夸张。
这种夸张超越了电影本身所需要的夸张程度,使许多事情让观众一看就知道不可能,但仍然忍不住会为此而投入。
在《回魂夜》里,周星驰饰演的精神病患者可以用纸帽子带着大家飞翔,这是对传统理念的夸张;在《百变金刚》里,他一开始过的生活穷奢极欲,这是对生活方式的夸张;在《行运一条龙》里,阿水当众撕开了女同学的上衣,然后又痛不欲生,这是对情感欲望的夸张;在《喜剧之王》里,他面朝大海高呼“努力、奋斗”,这是对理想抱负的夸张。
不仅如此,周星驰在影片中的表演也一向是极尽夸张之能事,怪异的肢体语言和放肆的大笑成了他电影里的招牌动作。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观众明知情节虚假、缺乏可信度却仍然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呢?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些夸张所给人们带来的快感,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使平时生活中不能表现或不想表现因而有意或无意压抑着的情感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释放。
其次是讽刺。
社会的阴暗、污秽、人性的贪婪、自私,男人的好色,女人的善变,工作的无聊,挣钱的烦恼,这一切都可以成为讽刺的对象。
《月光宝盒》中至尊宝带领的一群手下在他跟蜘蛛精打斗时集体下跪求饶,这是对忠诚的讽刺;《大圣娶亲》中他勾引结拜大哥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这是对友谊的讽刺;《九品芝麻官》中,他在妓院里表演了一场“斗兽棋”式的明争暗斗,这是对权势的讽刺;《少林足球》中浆爆发表的宣言,“其实我浆爆又何尝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这是对被金钱腐蚀的梦想的讽刺;还有《喜剧之王》中那个被莫文蔚饰演的动作影后娟姐骂得狗血淋头的导演的设置,也是对香港电影圈充斥庸才的一种讽刺。
最后是自嘲。
自嘲是讽刺的升华。
它不仅是艺术的一个境界,也是思想的一个境界。
艺术家无疑都是自恋的,这种自恋是创作的动力同时也是阻力。
如果一个艺术家长期沉溺在自己过去的作品中,就很难开拓创新、更进一步。
所以《功夫》里,周星驰出场便踩破足球,以“还踢球?”作开场白,显然带有调侃前作《少林足球》和超越自己的野心。
纵观周星驰的所有影片,无一不带着浓厚的自嘲色彩,而其中又以《喜剧之王》为最甚。
那个整天说“我是一个演员”、到处主动教人演戏、追着阿姨问有没有角色的死跑龙套的,正是对他成名前生活的自我讽刺。
而在《大内密探零零发》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插入的一场电影颁奖典礼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剧中男主角在经过了一番努力的表演之后却没有得奖,由此引发出意味深长的对话。
零零发(周星驰饰):刚刚那场戏我从头带到尾,看上去是水准之作,有目共睹,你怎么会把奖给那个人(零零发的岳父)!佛印(罗家英饰):你也不错,但是流于表面,就像刚才你老婆听你心跳得那场戏,表情做作,略嫌浮夸。
零零发:那些是世俗人对我的看法,你该不会也不识货吧?零零发老婆(刘嘉玲饰):不对了,老公,我听你心跳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到我跟你有交流,只觉得你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入戏,你真的不是很会演戏呀。
零零发:你……佛印:听我说句公道话。
一句就好,你不懂演戏呀!这显然是周星驰发自内心的独白,努力却不被人认可,创新精神不被理解,佳作不少,票房也很高,但一直和影帝的桂冠无缘。
因而他在电影中安排这样的情节,带有浓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试想,除了周星驰,还有哪个电影人会在电影中突如其来安排这样的场景,并以自嘲的方式试图解释?这就验证了如下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企图抹去固有的身分,然后按照个人的取向,再任意为任何东西定位。
虽然周星驰在电影中并不是试图将自己的社会地位重新定位,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进行着自己的艺术的再定位过程。
反传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周星驰的电影中表现得十分显著,那就是反精英主义。
“现代主义美学是一种崇高的美学,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则是消解崇高的具有破坏性质的所谓‘后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桑才会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场‘摧毁运动’。
它倡导突出那些‘不可表现之物’,推崇多元化、零散化、非神话化,并与商品经济十分合拍,打上了大众消费的印记。
现代主义文化中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高雅’指向,后现代主义文化则注定是非精英的、通俗的,乃至流行的,因为也是‘媚俗’的。
”后现代的作品常常向高层次文化同低层次文化之间的界线发起挑战,这一特色在《食神》中有所体现。
这里要说的不是这部电影的故事内容,而是其中的一道菜式,那就是周星驰饰演的男主角斯蒂芬周在最后的厨艺大赛上最后完成的作品──黯然销魂饭。
而事实上,这是一碗叉烧饭。
当初男主角在庙街流落街头,正在饥饿至极的时候,女主角火鸡(莫文蔚饰)给他作了一碗叉烧饭,所以他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那样的街边小摊,是市井小民经常出没的场所;而厨艺大赛却是顶级菜肴云集,面对对手的极品用料做成的“佛跳墙”,男主角只是作了一碗看似极为普通,甚至随便在夜市就可以吃到的叉烧饭,却使评委感动的落泪。
如此把所谓的“低层次文化”和所谓的“高层次文化”融为一体、甚至是平民对贵族的胜利,与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精英主义是完全吻合的。
扭曲自己,夸张自己,讽刺自己,让观众笑起来,这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揭示和剖白。
把自嘲做得恰到好处,不给人以哗众取宠的感觉,那就更难了。
必须要有谦卑的外表、平凡的相貌、庸俗的举止、迟钝的谈吐,甚至看似愚蠢的行为。
这种看上去得愚蠢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影片所带给观众的快乐才是最大的智慧。
而对比一下“无厘头”的特征就可以发现,正是及时行乐、无深度表现、破坏秩序、离析正统的“无厘头精神”,恰到好处的诠释了后现代文化的内涵。
传统的精神内核伊哈布·哈桑认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是由铁障或长城分开的”。
他说:“在我看来,我们都同时可以是维多利亚人、现代人和后现代人。
”由此可见,传统和反传统之间其实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
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反传统”到了明天就必然成为明天所要反对的“传统”。
上升到哲学和美学层面来说,尽管理论家们“所描述的后现代景观望往往是感性的、非历史性的、无中心的、反形而上的(反传统表现),但他们自己的理论表述又恰恰仍是理性的、有历史性的、强调自我话语中心的和非常形而上的(传统内核)”。
这一点在周星驰的影片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
周星驰在影片中从来不曾掩饰自己对传统的欣赏与迷恋。
“那一天,我的意中人会驾着七彩霞云来接我……”红色天空,红色云朵,红色的心上人终于来了,《大话西游》最终的降落带着惊心动魄的意味:传统的爱情回归了。
虽然几经时光倒流、前世今生、百转千回,但最后周星驰饰演的至尊宝还是戴上了金箍完成了自度。
佛曰,我不度众生,是众生识心自度。
所以和牛魔王打斗时菩提老祖不讲义气的落荒而逃,看似是对神仙形象的完全颠覆,实际上却是佛理的最真实阐述。
不仅如此,周星驰电影的一大特色就是“小人物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小人物”刚刚出场的时候总是有着一些令人厌恶的性格。
比如《功夫》里一心想靠做坏事加入斧头帮的上海滩小混混,《情圣》里靠骗术混饭吃的流氓,《百变金刚》里胡作非为的富家子弟,《九品芝麻官》里贪赃枉法的小官……这一特色,跟以前香港流行的电影有所不同。
无论是李小龙、周润发还是成龙,他们扮演的都是一些英雄,这些角色满怀正义感,不畏艰难险阻,最终凭着一腔热血和过人的智慧及武功取得胜利。
如果说这样的英雄模式是传统的,那么,周星驰的小人物模式显然是反传统的了。
它甚至不同于传统的小人物成长模式,如《少林寺》一般,拜师学艺、历尽艰辛,最终惩奸除恶,得报大仇。
周星驰影片中的角色通常没有经历过量变的积累就直接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外在条件而发生了质变,甚至缺少铺垫。
如《功夫》里因被火云邪神打通了任督二脉便由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角色变为武林高手;《少林足球》里因为受辱而唤起失去武功的回归;《大话西游》里因为戴上金箍便由一个强盗成为身披金甲圣衣的齐天大圣;《百变金刚》里因为被黑帮炸死而变成了千变万化的机器人;《大内密探零零发》里因为被雷击中才使出绝招“天外飞仙”。
这些手段无疑是非常后现代的,这样的情节安排无疑是不合乎逻辑的。
但是周星驰的电影就是这样,观众不会觉得唐突,只会觉得感动。
为什么?仔细分析这些影片不难发现,透过反传统的表象,电影所要表现得主题仍然是非常传统的精神。
虽然这些小人物本身可能一无是处,但通过努力最终却奇迹般地作出壮举。
究其原因就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物自身善良的本性,或者说是内心中存留的一点未曾泯灭的良心。
《百变金刚》中当他和生父面对黑社会追杀,在两个只能活一个之时,他救出了生父,自己却被炸得粉身碎骨;《功夫》里,在神雕侠侣和火云邪神打得难解难分时,身为斧头帮的他却站到了正义一方反戈一击;《九品芝麻官》里他为了解救戚秦氏而被人诬陷冤枉……所以,虽然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都有一些令人厌恶的性格,但是总是能转变成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英雄被观众接受,从而赢得认同。
二是对理想的执着。
中国人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在香港这个过客社会更尤其如此。
激烈的竞争和无根感,使大多数港人都相信,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才能在香港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占有一席之地。
看看《喜剧之王》里那个坚持梦想、百折不挠的小龙套,《少林足球》里那个说“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的拾破烂的,甚至是《唐伯虎点秋香》里那个对梦中情人不懈追求的风流才子……观众怎能不为之感动?这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认同,还有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认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最重要、最核心的便是孔子“人皆可以为圣贤”的道德理想及其所开创的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