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红字_中的四种关系看霍桑的写作思想
- 格式:pdf
- 大小:449.25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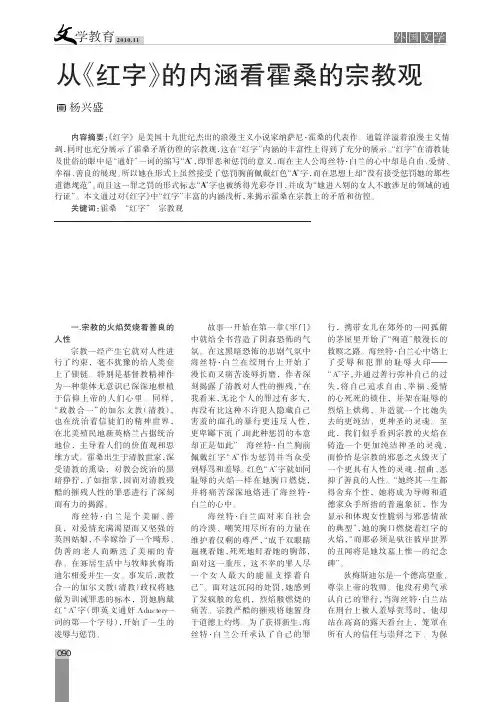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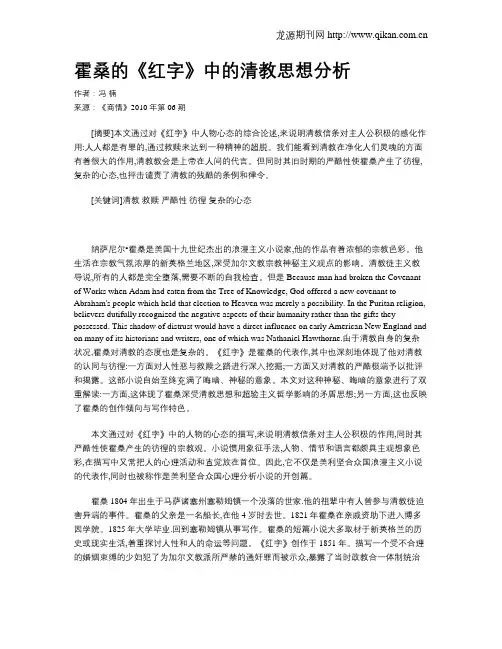
霍桑的《红字》中的清教思想分析作者:冯楠来源:《商情》2010年第06期[摘要]本文通过对《红字》中人物心态的综合论述,来说明清教信条对主人公积极的感化作用:人人都是有罪的,通过救赎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
我们能看到清教在净化人们灵魂的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清教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
但同时其旧时期的严酷性使霍桑产生了彷徨,复杂的心态,也抨击谴责了清教的残酷的条例和律令。
[关键词]清教救赎严酷性彷徨复杂的心态纳萨尼尔•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
他生活在宗教气氛浓厚的新英格兰地区,深受加尔文教宗教神秘主义观点的影响。
清教徒主义教导说,所有的人都是完全堕落,需要不断的自我检查。
但是Because man had broken the Covenant of Works when Adam had eaten from the Tree of Knowledge, God offered a new covenant to Abraham's people which held that election to Heaven was merely a possibility. In the Puritan religion, believers dutifully recognized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ir humanity rather than the gifts they possessed. This shadow of distrust would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early American New England and on many of its historians and writers, one of which was Nathaniel Hawthorne.由于清教自身的复杂状况,霍桑对清教的态度也是复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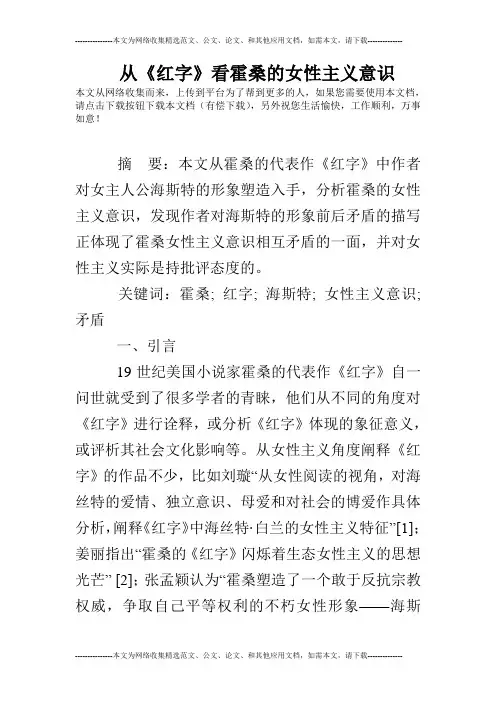
从《红字》看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摘要:本文从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中作者对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形象塑造入手,分析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发现作者对海斯特的形象前后矛盾的描写正体现了霍桑女性主义意识相互矛盾的一面,并对女性主义实际是持批评态度的。
关键词:霍桑; 红字; 海斯特; 女性主义意识; 矛盾一、引言19世纪美国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自一问世就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青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红字》进行诠释,或分析《红字》体现的象征意义,或评析其社会文化影响等。
从女性主义角度阐释《红字》的作品不少,比如刘璇“从女性阅读的视角,对海丝特的爱情、独立意识、母爱和对社会的博爱作具体分析,阐释《红字》中海丝特·白兰的女性主义特征”[1];姜丽指出“霍桑的《红字》闪烁着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光芒” [2];张孟颖认为“霍桑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宗教权威,争取自己平等权利的不朽女性形象——海斯特”[3] 笔者将试从另一个角度解析霍桑及其作品《红字》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意识。
二、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背景提到霍桑的女性主义意识,就不得不提霍桑的家庭背景,因为家庭背景对霍桑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霍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
他的家族曾是名门望族,几代祖先都是狂热的清教徒。
他的祖辈之中有人曾参与清教徒迫害异端的事件,为著名的1692年“塞勒姆驱巫案”的三名法官之一。
父亲是个船长,在霍桑四岁的时候死于海上,霍桑在母亲抚养下长大。
霍桑的母亲,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用丈夫留下的微薄的遗产以及兄弟姐妹的资助艰难地生活。
霍桑对母亲怀有极大的同情和感激,这也是为什么在《红字》中霍桑高度颂扬了母爱。
也正是母亲的处境引发了霍桑思考在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地位。
霍桑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清教主义传统对他影响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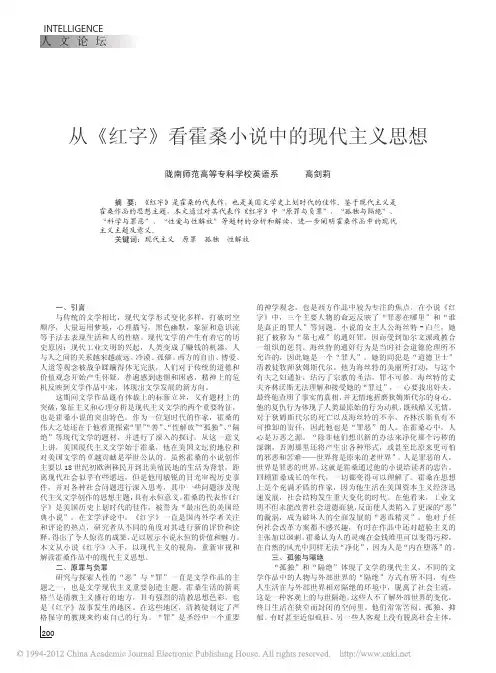
人 文 论 坛200INTELLIGENCE从《红字》看霍桑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思想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系 高剑莉摘 要:《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佳作。
鉴于现代主义是霍桑作品的思想主题,本文通过对其代表作《红字》中“原罪与负罪”、“孤独与隔绝”、“科学与罪恶”、“性爱与性解放”等题材的分析和解读,进一步阐明霍桑作品中的现代主义主题及意义。
关键词:现代主义 原罪 孤独 性解放一、引言与传统的文学相比,现代文学形式变化多样,打破时空顺序,大量运用梦境,心理描写,黑色幽默,象征和意识流等手法去表现生活和人的性格。
现代文学的产生有着它的历史原因: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人类变成了赚钱的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孤僻。
西方的自由、博爱、人道等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人们对于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开始产生怀疑,普遍感到迷惘和困惑,精神上的危机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体现出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这期间文学作品既有体裁上的标新立异,又有题材上的突破,象征主义和心理分析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也是霍桑小说的突出特色。
作为一位划时代的作家,霍桑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着重探索“罪”“善”、“性解放”“孤独”、“隔绝”等现代文学的题材,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始于霍桑,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和对美国文学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虽然霍桑的小说创作主要以18世纪初欧洲移民开到北美殖民地的生活为背景,距离现代社会似乎有些遥远,但是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历史事件,并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其中一些问题涉及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思想主题,具有永恒意义。
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佳作,被誉为“最出色的美国经典小说”。
在文学评论中,《红字》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评论的热点,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新的评价和诠释,得出了令人惊喜的成果,足以展示小说永恒的价值和魅力。
本文从小说《红字》入手,以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霍桑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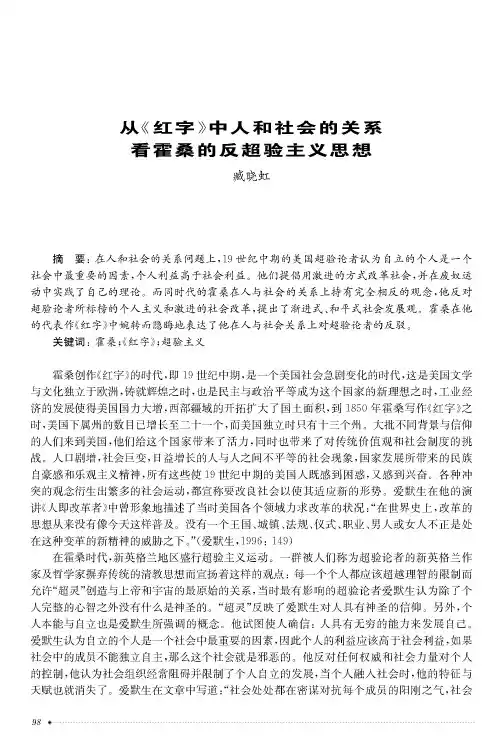
从《红字》中人和社会的关系看霍桑的反超验主义思想臧晓虹摘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19世纪中期的美国超验论者认为自立的个人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他们提倡用激进的方式改革社会,并在废奴运动中实践了自己的理论。
而同时代的霍桑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持有完全相反的观念,他反对超验论者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和激进的社会改革,提出了渐进式、和平式社会发展观。
霍桑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婉转而隐晦地表达了他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对超验论者的反驳&关键词:霍桑;《红字》;超验主义霍桑创作《红字》的时代,即19世纪中期,是一个美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这是美国文学与文化独立于欧洲,铸就辉煌之时,也是民主与政治平等成为这个国家的新理想之时,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国力大增,西部疆域的开拓扩大了国土面积,到1850年霍桑写作《红字》之时,美国下属州的数目已增长至二十一个,而美国独立时只有十三个州。
大批不同背景与信仰的人们来到美国,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挑战。
人口剧增,社会巨变,日益增长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乐观主义精神,所有这些使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既感到困惑,又感到兴奋。
各种冲突的观念衍生出繁多的社会运动,都宣称要改良社会以使其适应新的形势。
爱默生在他的演讲《人即改革者》中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美国各个领域力求改革的状况:“在世界史上,改革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
没有一个王国、城镇、法规、仪式、职业、男人或女人不正是处在这种变革的新精神的威胁之下。
”(爱默生,1996:149)在霍桑时代,新英格兰地区盛行超验主义运动。
一群被人们称为超验论者的新英格兰作家及哲学家摒弃传统的清教思想而宣扬着这样的观点:每一个个人都应该超越理智的限制而允许“超灵”创造与上帝和宇宙的最原始的关系,当时最有影响的超验论者爱默生认为除了个人完整的心智之外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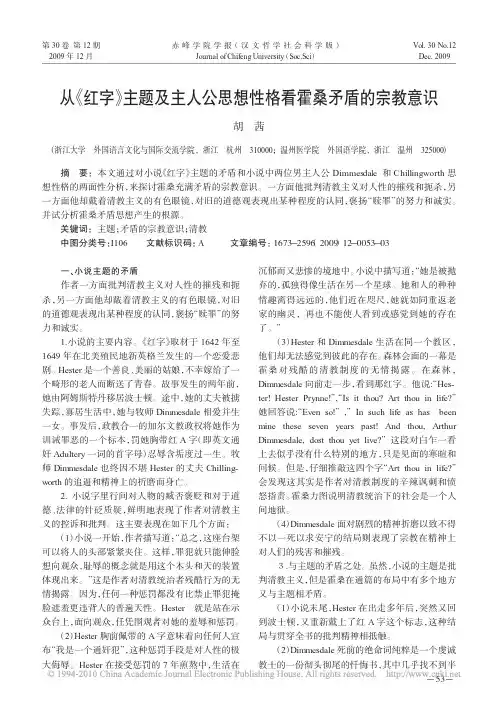
一、小说主题的矛盾作者一方面批判清教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和扼杀,另一方面他却戴着清教主义的有色眼镜,对旧的道德观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同,褒扬“赎罪”的努力和诚实。
1.小说的主要内容。
《红字》取材于1642年至1649年在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
Hester 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不幸嫁给了一个畸形的老人而断送了青春。
故事发生的两年前,她由阿姆斯特丹移居波士顿。
途中,她的丈夫被掳失踪,寡居生活中,她与牧师Dimmesdale 相爱并生一女。
事发后,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政权将她作为训诫罪恶的一个标本,罚她胸带红A 字(即英文通奸Adultery 一词的首字母)忍辱含垢度过一生。
牧师Dimmesdale 也终因不堪Hester 的丈夫Chilling-worth 的追逼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身亡。
2.小说字里行间对人物的臧否褒贬和对于道德、法律的针砭质疑,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清教主义的控诉和批判。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小说一开始,作者描写道:“总之,这座台架可以将人的头部紧紧夹住。
这样,罪犯就只能伸脸想向观众,耻辱的概念就是用这个木头和天的装置体现出来。
”这是作者对清教统治者残酷行为的无情揭露。
因为,任何一种惩罚都没有比禁止罪犯掩脸遮羞更违背人的普遍天性。
Hester就是站在示众台上,面向观众,任凭围观者对她的羞辱和惩罚。
(2)Hester 胸前佩带的A 字意味着向任何人宣布“我是一个通奸犯”,这种惩罚手段是对人性的极大侮辱。
Hester 在接受惩罚的7年煎熬中,生活在沉郁而又悲惨的境地中。
小说中描写道:“她是被抛弃的,孤独得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
她和人的种种情趣离得远远的,他们近在咫尺,她就如同重返老家的幽灵,再也不能使人看到或感觉到她的存在了。
”(3)Hester 和Dimmesdale 生活在同一个教区,他们却无法感觉到彼此的存在。
森林会面的一幕是霍桑对残酷的清教制度的无情揭露。
在森林,Dimmesdale 向前走一步,看到那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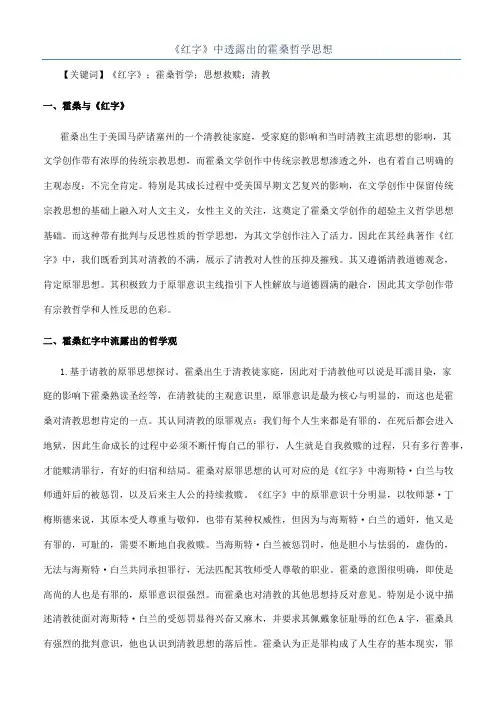
《红字》中透露出的霍桑哲学思想【关键词】《红字》;霍桑哲学;思想救赎;清教一、霍桑与《红字》霍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清教徒家庭,受家庭的影响和当时清教主流思想的影响,其文学创作带有浓厚的传统宗教思想,而霍桑文学创作中传统宗教思想渗透之外,也有着自己明确的主观态度:不完全肯定。
特别是其成长过程中受美国早期文艺复兴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保留传统宗教思想的基础上融入对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这奠定了霍桑文学创作的超验主义哲学思想基础。
而这种带有批判与反思性质的哲学思想,为其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
因此在其经典著作《红字》中,我们既看到其对清教的不满,展示了清教对人性的压抑及摧残。
其又遵循清教道德观念,肯定原罪思想。
其积极致力于原罪意识主线指引下人性解放与道德圆满的融合,因此其文学创作带有宗教哲学和人性反思的色彩。
二、霍桑红字中流露出的哲学观1.基于请教的原罪思想探讨。
霍桑出生于清教徒家庭,因此对于清教他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家庭的影响下霍桑熟读圣经等,在清教徒的主观意识里,原罪意识是最为核心与明显的,而这也是霍桑对清教思想肯定的一点。
其认同清教的原罪观点: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有罪的,在死后都会进入地狱,因此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忏悔自己的罪行,人生就是自我救赎的过程,只有多行善事,才能赎清罪行,有好的归宿和结局。
霍桑对原罪思想的认可对应的是《红字》中海斯特·白兰与牧师通奸后的被惩罚,以及后来主人公的持续救赎。
《红字》中的原罪意识十分明显,以牧师瑟·丁梅斯德来说,其原本受人尊重与敬仰,也带有某种权威性,但因为与海斯特·白兰的通奸,他又是有罪的,可耻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救赎。
当海斯特·白兰被惩罚时,他是胆小与怯弱的,虚伪的,无法与海斯特·白兰共同承担罪行,无法匹配其牧师受人尊敬的职业。
霍桑的意图很明确,即使是高尚的人也是有罪的,原罪意识很强烈。
而霍桑也对清教的其他思想持反对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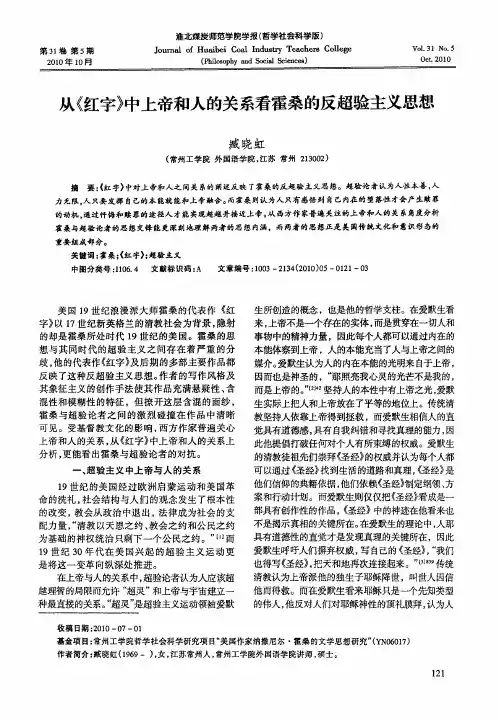

霍桑小说《红字》及其思想解读作者:王凡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0期霍桑小说《红字》及其思想解读王凡(安徽科技学院,安徽滁州233100)摘要:《红字》是19世纪美国小说作家霍桑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写了一位为了爱情宁愿牺牲自己,并勇于与传统腐朽的思想势力作斗争的女性,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自由与理性的尊崇,展现出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与愿望。
笔者从多个角度出发,深入地解读作者在《红字》中所寄托的思想情感。
关键词:霍桑;《红字》;女权;自然神论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45-02《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霍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上寄托着作者霍桑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
海丝特对爱情的忠贞,对男权主义的挑战,对女性自由、平等与尊严的争取,这些都表明了霍桑对女性的尊重,也渗透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理性的思考。
《红字》自然也就成了作者思想感情表达的一个渠道。
一、霍桑小说《红字》的创作背景经过17、18世纪的自然神论运动的洗礼,19世纪的美国掀起了一股宗教运动的狂潮,生活于19世纪的霍桑,受自然神论运动的影响,在《红字》的字里行间透漏出对理性与自由的渴望,当时美国最崇尚的哲学理论是“唯一神论”,但就其本质而言与自然神论差异并不大。
正是由于18世纪有很多文人墨客将这种自然神论思想融入其作品中,自然神论的思想才在美国得以传播,霍桑才有机会接受自然神论思想的洗礼。
自然神论所以对霍桑的影响如此至深,还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在霍桑4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在他9岁那年,他又患了足疾,寄住在舅舅家。
他喜欢一个人看书,精心研读了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那段历史,了解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时时洞察时事,分析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
他的心目中有两位对他至关重要的女性——母亲与妻子。
母亲对自由、平等以及尊严的理解,妻子对自己工作的无限支持,让霍桑对女性产生了不同一般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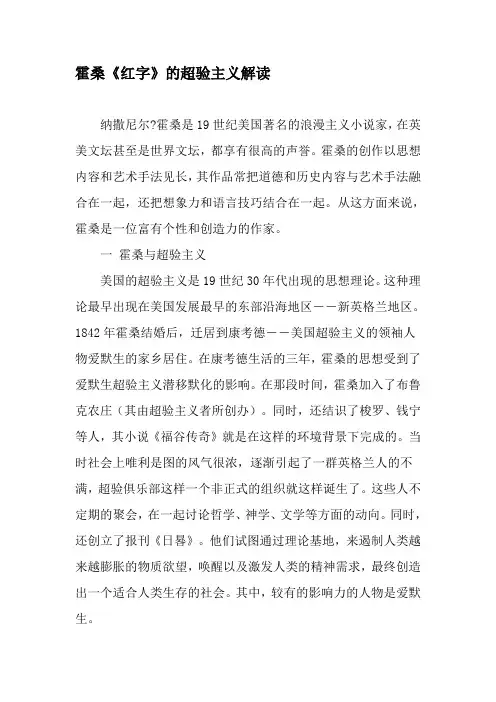
霍桑《红字》的超验主义解读纳撒尼尔?霍桑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在英美文坛甚至是世界文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霍桑的创作以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见长,其作品常把道德和历史内容与艺术手法融合在一起,还把想象力和语言技巧结合在一起。
从这方面来说,霍桑是一位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作家。
一霍桑与超验主义美国的超验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思想理论。
这种理论最早出现在美国发展最早的东部沿海地区――新英格兰地区。
1842年霍桑结婚后,迁居到康考德――美国超验主义的领袖人物爱默生的家乡居住。
在康考德生活的三年,霍桑的思想受到了爱默生超验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那段时间,霍桑加入了布鲁克农庄(其由超验主义者所创办)。
同时,还结识了梭罗、钱宁等人,其小说《福谷传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完成的。
当时社会上唯利是图的风气很浓,逐渐引起了一群英格兰人的不满,超验俱乐部这样一个非正式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这些人不定期的聚会,在一起讨论哲学、神学、文学等方面的动向。
同时,还创立了报刊《日晷》。
他们试图通过理论基地,来遏制人类越来越膨胀的物质欲望,唤醒以及激发人类的精神需求,最终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
其中,较有的影响力的人物是爱默生。
欧洲浪漫派和康德先验论的思想对爱默生的影响很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就吸收了其思想。
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以人本主义哲学为中心,提倡直接认识真理。
这就摈弃了加尔文等人的以神为中心的思想。
这在当时尤其是19世纪中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爱默生大力提倡人们要创造民主化文学。
这种言论对美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直接推动了一些文学家登上文坛,如诗人朗费罗,散文家梭罗,小说家麦尔维尔等,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美国文学的基础。
二《红字》与超验主义超验主义哲学给作家霍桑的影响很深,其小说《红字》自1850年问世以来,一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这部作品代表着霍桑的最高成就。
小说《红字》是一部主题多元的作品,不同的读者对这部作品有着不同的解读。
以上帝的名义―从《红字》看霍桑的宗教观【摘要】在霍桑的小说《红字》中,宗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本文从霍桑的宗教背景和《红字》对宗教的探讨入手,探讨了宗教对霍桑的影响、《红字》中的宗教符号、宗教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宗教与个体道德选择以及宗教对罪恶与赎罪的观念。
通过分析这些内容,可以看出霍桑对宗教的态度、宗教在《红字》中的作用以及宗教观的多元性。
霍桑巧妙地运用宗教元素,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内心的挣扎,让读者深思罪恶与赎罪的概念,并体会到宗教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整体而言,这篇文章将为读者带来对霍桑宗教观的深入理解和思考。
【关键词】霍桥宗教观, 红字, 宗教影响, 宗教符号, 社会秩序, 个体道德选择, 罪恶与赎罪, 宗教态度, 多元性。
1. 引言1.1 霍桑的宗教背景纳撒尼尔·霍桑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深受宗教的影响。
霍桑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其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牧师。
他在家庭和学校都接受了宗教的教育和影响,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霍桑的宗教背景让他对罪恶、赎罪、道德选择等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他对宗教的思考和探讨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尤其是在《红字》这部代表作中,宗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霍桑通过《红字》展现了对宗教的思考和反思,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关于宗教、道德、罪恶和赎罪的问题,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一部深具启发意义的文学作品。
霍桑的宗教背景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也为他的作品增添了宗教的深度和厚重感。
1.2 《红字》对宗教的探讨《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主人公海斯特·品钦的故事,探讨了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小说中,宗教被描绘为一种权威和规范,对品钦和其他人物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品钦因为与神秘的女子海斯特·品钦私通而被判刑,被迫背负着一枚红字“A”,这枚红字成为了他一生的标志,也是他与宗教的联系。
2009年5月社科纵横May,2009总第24卷第5期S OC I A L S C I E NCES RE V I E W VOL.24NO.5一位温和而坚定的卫道士———从《红字》解读霍桑的宗教情结鄢忠秀(五邑大学外语系 广东江门 529020)【内容摘要】《红字》层层深入地挖掘人性的罪恶,揭示出罪恶的普遍存在以及人类无法逃避的生存困境。
指出人们只有正视自身罪恶、真诚忏悔,才能获得最终救赎。
作品中看似矛盾晦涩的创作手法其实是霍桑呼吁倡导正统基督教人性观、道德观的一种折射,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正统基督教思想情怀及对宗教的感化力量所寄予的厚望。
【关键词】《红字》 罪恶 正视 真诚 救赎 正统基督教思想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9)05-0174-03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有着伟大的目的,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的匠心之作《红字》就是一部旗帜鲜明的道德小说。
长久以来,人们从象征手法、心理描写、红字意义嬗变、多元化主题、人名寓意、原型分析、甚至女权主义等角度来阐释《红字》,都无法解开大师那矛盾与暧昧的心态之谜。
若从其宗教情愫出发,或许能解读到大师在隐晦、多义的背后要传递的真正信息:罪恶的普遍存在、人类只有正视自身罪恶,真诚忏悔,才能达到灵魂与上帝冥合、万物平衡和谐相容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的伦理精神并行不悖地与作者敬重个体及心灵的浪漫主义情怀共同构筑着整部作品的道德维度[1],充分体现出作者倡导的道德准则是以基督教的人性观和道德观为核心的。
一、霍桑对人性之罪的探究霍桑毕生关注人性之罪,揭示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是其作品的突出特点[2](p199)。
《红字》完全遵循传统的宗教故事模式:犯罪———惩罚———赎罪———拯救。
作品首先体现了“开始即堕落”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督救命题。
根据《圣经》,世界之初便是堕落,人类始祖违抗旨令,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开始苦难的尘世生活。
从小说《红字》看霍桑的矛盾思想及宗教观作者:朴明珠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36期摘要:撒尼尔·霍桑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对人物心理做出了深入的挖掘和分析,从一个全知性的视角将社会与人类的黑暗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小说《红字》是霍桑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小说通过海斯特·白兰这一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女性主义视角将清教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将清教社会的传统、腐朽思想与人们的阴暗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霍桑在对海斯特这样一个对爱情与自由忠贞执着的女性形象进行赞颂的同时,也表现了他思想中的矛盾性。
关键词:霍桑;《红字》;矛盾思想;宗教观作者简介:朴明珠(1978-),女,吉林通化人,硕士,编辑,研究方向为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6-0-01撒尼尔·霍桑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其作品中的矛盾思想与象征手法让他的作品具有更大的解读与想象的空间,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至今仍然经久不衰。
小说《红字》是霍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作品通过霍桑丰富的想象力将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进行了解构,一部分人认为霍桑通过海斯特·白兰这样一个女性形象表达了他对于女性主义的支持与理解,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正是反映了霍桑对于当下女性的观照和理解,通过对海斯特这个人物形象的赞美表达了他对当时女性追求爱情与自由的支持与激励;但在评论界的另一方观点认为,霍桑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思想让他无法对海斯特白兰这样的前卫的女性形象进行赞美与歌颂,反而通过对于海斯特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从传统的清教主义思想角度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抨击与批判,表达了霍桑对于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的不满。
两种观点都是从各自的侧重点出发做出的分析和评论,下面本文从小说《红字》对于霍桑创作思想中的矛盾性与总教观做出研究和分析。
《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霍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上寄托着作者霍桑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
海丝特对爱情的忠贞,对男权主义的挑战,对女性自由、平等与尊严的争取,这些都表明了霍桑对女性的尊重,也渗透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理性的思考。
《红字》自然也就成了作者思想感情表达的一个渠道。
一、霍桑小说《红字》的创作背景经过17、18世纪的自然神论运动的洗礼,19世纪的美国掀起了一股宗教运动的狂潮,生活于19世纪的霍桑,受自然神论运动的影响,在《红字》的字里行间透漏出对理性与自由的渴望,当时美国最崇尚的哲学理论是“唯一神论”,但就其本质而言与自然神论差异并不大。
正是由于18世纪有很多文人墨客将这种自然神论思想融入其作品中,自然神论的思想才在美国得以传播,霍桑才有机会接受自然神论思想的洗礼。
自然神论所以对霍桑的影响如此至深,还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在霍桑4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在他9岁那年,他又患了足疾,寄住在舅舅家。
他喜欢一个人看书,精心研读了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那段历史,了解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时时洞察时事,分析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
他的心目中有两位对他至关重要的女性———母亲与妻子。
母亲对自由、平等以及尊严的理解,妻子对自己工作的无限支持,让霍桑对女性产生了不同一般的认识。
在《红字》中,海丝特勇敢追求爱情,誓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些都反映出作者霍桑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
但是对海丝特的爱人丁梅斯代尔内心的痛苦挣扎、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悲剧等则反映出作者对女性得到解放的怀疑,并由此产生的痛苦与煎熬。
二、《红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海丝特的圣母形象在小说中,新殖民地开拓者在建立属于自己的理想国后第一时间修建了监狱,这表明在文明社会中的美好往往伴随着被掩盖的邪恶。
监狱边的荒草也被同化成昏暗凄凉的色调,然而在这一片死寂的环境之下,还有一朵绚烂的花朵为人类道德带来希望。
在《红字》中,海丝特是以年轻妇人的形象出现的,作为婴儿的母亲,她的体态、身姿甚至一言一行都透露出她大方优雅的气质。
【教学研究】从《红字》中的四种关系看霍桑的写作思想臧晓虹Ξ(常州工学院教育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0)[摘 要]19世纪美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深受其清教徒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影响,他常以清教的善恶观来观察分析社会现象,但是他又厌恶清教的严酷性。
同时,19世纪各种新思潮的兴起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先验论,其精神是挑战清教主义的理论基础,霍桑既赞赏先验论本身所包含的激情及人文精神,又始终对其保持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
本文试从其代表作《红字》中人与上帝,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探索该作品的深刻内涵及霍桑的写作思想。
[关键词]《红字》;霍桑;清教主义;先验论[中图分类号] I10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49(2004)04—0068—04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是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常常以殖民时期为背景,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深层次的心理活动”以及“罪与罚的关系”。
在作品中辨析人与上帝、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美国作家探索的焦点,霍桑在其代表作《红字》中对以上关系作了精辟独到的阐述,从中我们也可以对霍桑深刻的写作思想有所了解。
一、人与上帝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国家,美国作家从未停止对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探索。
作为清教徒移民的后代,霍桑一直试图重新阐释及调整人与上帝的关系。
霍桑的清教徒祖先为了宗教自由来到新大陆,他们遭受了许多迫害,不顾艰难与挫折,下定决心用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宣扬清教教义。
在清教徒的眼里,上帝是威严的,任何对清教教义的违背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清教的讲道中充满对愤怒的上帝和可怕的地狱的描写,任何异教徒都会受到惩罚或处决。
霍桑在《红字》中表述了他对清教主义冷酷严厉性的反感和厌恶,在小说的一开始霍桑写到,“他们把宗教与法律几乎视为一体,而且这两者又完全浸润在他们的性格中,一个犯罪的人,站在绞刑台上,从这样的旁观者所能探求的同情,真是又贫乏又冷酷。
另一方面,在现今的时代中像那只会引起嬉笑嘲骂的一种刑罚,在当时也几乎会如死刑般罩上了叫人望而生畏的庄严。
”[1](p.153)清教徒们认为他们是“山巅之城”的居民,只有他们这些有着严厉教义的人们才会赢得上帝的垂青,至于像海丝特这样违背了清教教义的人,最后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霍桑与清教的观念很不相同,他对海丝特的描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青年夫人,身材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若是有一个罗马教徒的话,会从这个怀抱着孩子的美丽夫人身上,会从她那如画的服装和态度中,想起了圣母的形象。
”[1](p.158)霍桑把清教徒眼中的罪人比作圣母马利亚,可见霍桑对海丝特的同情与欣赏,但霍桑这样描述并不是原谅了海丝特的罪,而是谴责那些所谓虔诚的清教徒们的冷酷与无情,“他们会十分庄严地去观望她的死,不会抱怨一句判决太严格。
”[1](p.158)在霍桑的眼中,清教徒的上帝太严厉,他们没有释义出上帝充满怜悯与仁慈的一面来,上帝是令人敬畏的,但上帝也是仁慈的,对人所遭受的苦难充满怜悯宽容之心。
在霍桑的时代,清教徒们对上帝的理解与释义已经过时了,先验主义运动遍及全国,一群被人们称为先验论者的新英格兰作家及哲学家 Ξ[收稿日期]2004-10-27[作者简介]臧晓虹(1969- ),女,江苏省常州市人,讲师。
2004-12-15第6卷 第4期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SH AANXI RT VU JOURNA L Dec15,2004V ol 16 N o 14宣扬着这样的观点:每一个个人都应该超越理智的限制而允许情感,即“灵魂”创造与上帝和宇宙的最原始的关系。
在先验论者们看来,清教教义中关于上帝的绝对权威、人的堕落、宿命论及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拯救人类的理论不仅过时了,而且具有破坏性,他们认为每个人自身都拥有体验灵魂再生及得到拯救的能力。
先验论对清教主义的挑战及其本身所蕴含的激情和人文精神深深地吸引了霍桑,他把先验论当成是摆脱清教主义压迫的一个象征,然而随着受先验论影响组成的实验性公社纷纷解散、失败,霍桑也对先验论感到失望,先验论对上帝权威的彻底打破及对个人神性的极度强调在霍桑看来是利己主义者的观点,在霍桑的短篇小说《利己主义者》中,他称这些人“胸中隐藏着一条蛇,既是病态的幻想的牺牲品,又是不幸的身体的受害者。
”[2](p.912)在《红字》中,他也多次强调了一个人为他的骄傲和个人主义会付出巨大代价,海丝特既是反叛严酷的清教主义的象征,又是个人主义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身上带有先验论思想的特征。
她鄙视清教教义,犯下通奸罪行,尽管她被罚当众受辱,被迫戴上象征耻辱的标志,但她并不承认自己有罪,在内心,她认为她个人的神性比上帝的神性更重要,相信她的情感,即“灵魂”会超越理性,和她自己所释义的上帝融合。
海丝特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与上帝交流,这正是霍桑时代先验论者所大力提倡的精神生活方式。
海丝特心中的上帝和清教徒们所释义的上帝大不相同,那就是为什么尽管她受到清教徒严厉的惩罚,最后她仍会叫丁梅斯代尔和她一起私奔。
在故事的结尾,丁梅斯代尔的死和她惨淡爱情的悲剧结尾才使她意识到自己的罪,她重新回到了新英格兰,“这儿有她的罪,这儿有她的悲伤,这儿还有她的忏悔。
”起初,海丝特也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对严厉的清教教义的反叛,因此她是骄傲的,对别人的羞辱不屑一顾,书中结尾写到,“海丝特在早年曾经空想过,自己或许就是一个名定的女先知,可是不久就看明白,一个染上罪恶、为耻辱压倒、甚至负着一生忧患的女人,绝不可能有什么神圣和神秘的真理的使命来负托给她的。
”[1](p.317)对海丝特勇气的欣赏表明了霍桑对清教主义严酷性的反感,同时也说明他非常赞赏先验论对清教主义富有激情的挑战,而海丝特悲剧的命运又反映了霍桑对先验论极端个人主义的失望、对现实的幻灭及其对清教主义文化遗产的重新审视。
霍桑努力想重新调整人与上帝的关系,一种和清教主义及先验论所宣扬的不同的人神关系,不是清教主义所宣扬的神性至上,也不是先验论所强调的个人神性,霍桑所释义的上帝既对人威严又对人仁慈,既惩罚人的罪又怜悯人的苦难。
在小说《红字》中,霍桑暗示了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欢喜,与海丝特不同,她必须“崇高、纯洁、美丽;而且,她的智慧,不是得自阴暗的忧伤,而是来自欢喜的灵气;同时,她将用足以达到这样生活目的的、最真实的生活考验,显示出神圣的爱将会怎样地使我们幸福。
”[1](p.317)霍桑对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新的释义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红字》发表以后,许多人来找霍桑向他倾诉自己的秘密,好像霍桑不是位作家而是名牧师。
《红字》有一种强烈的宗教道德意识在里面,实际上,霍桑一直在作为一名道德家而写作,一直在努力重新调整人与上帝的关系。
二、人与社会《红字》的背景是殖民时期严酷教权统治下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社会,这是霍桑最喜爱的主题,清教社会中教会与政府之间没有区别,神权政治下,整个社会受到教会及镇议会的严厉控制,所有居民的思想及行为都受到相同宗教和社会准则的制约,教会联合执法机构主宰整个社会,正如霍桑在《红字》中所描述的,甚至海丝特和她孩子的待遇都奇怪地和立法者的立意及政府行为联系起来,关于一头猪的归属问题都会引起立法机构的激烈争论。
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会,任何违抗,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行为上的不规范都会受到教会及立法机构的惩罚。
新英格兰社会颁布了林林总总的处罚规则,由于新英格兰社会缺乏劳力,教会及立法机构不愿处决潜在的劳动力或把他们投入监狱,更常见的处罚是当众羞辱-鞭笞、烙印及强迫佩带耻辱标志。
霍桑在《红字》中描述海丝特佩带象征通奸的“A”字并非是作者的杜撰,历史文件中的确有这种惩罚的记载。
新英格兰社会就是这样根据清教教义制定了自己的法律规则。
尽管霍桑是清教徒移民的后代,但他并非是清教主义的卫道士,这一点从他对海丝特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可以看出来,海丝特背叛了她所不爱的丈夫而有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这种行为严重地违背了清教教义,在清教徒眼里,海丝特是背负着耻辱罪行的女人,她被赶出了清教徒社会,孤独地住在镇郊的一所破茅舍里,而霍桑却在书中对海丝特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他对海丝特及其女儿珠儿的欣赏也是显而易见的,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海丝特的心理变化和人们对海丝特态度的变化,最后,海丝特胸前的红字不再是耻辱的象征而成了德行的标志。
霍桑同情海丝特是因为海丝特不仅是她自己激情的受害者,也是严酷的神权政治社会的牺牲品。
霍桑对清教社会的种种弊端极为不满,而海丝特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是他对清教社会的反叛。
但是,霍桑对清教社会的情感是复杂的,不仅有反感,也有留恋。
霍桑时代的美国是一个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运动的时代,各种冲突的观点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运动,人们都想通过改革使社会适应新的情况。
1841年,在霍桑的家乡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社会模式叫布莱克农场,所有农场居民平等地分担劳动分享成果,他们试图创建一个接近自然、自食其力、相互友爱的社会。
布莱克农场是人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象征,也是霍桑理想的社会模式。
从1841年的4月到11月霍桑一直住在布莱克农场,起初,他对农场的新生活充满欣喜之情,然而,随着农场里各种矛盾逐渐突现出来,其中主要是个人自由的理想与集体社会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霍桑越来越无法接受农场的生活,亦无法认同农场成员的盲目乐观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再加上农场上的劳作没有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什么好处,在那儿住了7个月后他便离开了,布莱克农场也在几年后被解散了。
霍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布莱克农场的失败对霍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霍桑对现实的幻想完全破灭并且使他重新审视他的清教徒祖先传给他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为什么新英格兰和清教徒社会总是他最喜爱的主题。
事实上,霍桑既不能接受清教社会的冷酷严厉,也不能认同布莱克农场那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更无法接受他那个时代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同他笔下的主人公海丝特独自住在林边的小木屋里一样,霍桑一生也大都过着独处及沉思冥想的生活,对现实社会幻想的破灭使他只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未来,在小说的结尾霍桑写到:“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时期,到了世界成熟的时候,到了天国降临的时期,必将呈现出一种新的真理。
”[1](p.137)三、人与自然在《红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很独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和先验论者歌颂自然,主张人回归自然的理念不同,清教徒对自然的态度是敌对的,自然常常代表着清教社会的对立面。
小说中,自然是由森林代表的。
首先,森林是诱惑的象征。
由于海丝特已经被清教社会驱逐出去,森林就是她经常去的地方,虽然森林有时给她带来少许慰藉,但更多地使她想起自己已被人们从社会中驱逐出去,使她感悟到自己精神上的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