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物哀精神的传承与演化
- 格式:docx
- 大小:18.87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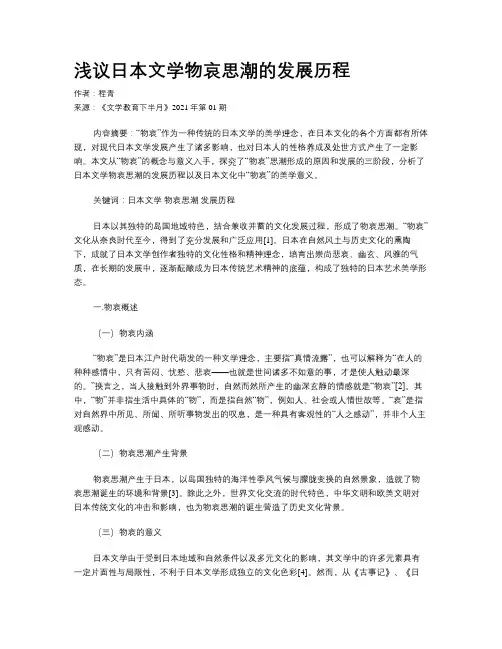
浅议日本文学物哀思潮的发展历程作者:程青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21年第01期内容摘要:“物哀”作为一种传统的日本文学的美学理念,在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对现代日本文学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也对日本人的性格养成及处世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从“物哀”的概念与意义入手,探究了“物哀”思潮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三阶段,分析了日本文学物哀思潮的发展历程以及日本文化中“物哀”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日本文学物哀思潮发展历程日本以其独特的岛国地域特色,结合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过程,形成了物哀思潮。
“物哀”文化从奈良时代至今,得到了充分发展和广泛应用[1]。
日本在自然风土与历史文化的熏陶下,成就了日本文学创作者独特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理念,培育出崇尚悲哀、幽玄、风雅的气质,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酝酿成为日本传统艺术精神的底蕴,构成了独特的日本艺术美学形态。
一.物哀概述(一)物哀内涵“物哀”是日本江户时代萌发的一种文学理念,主要指“真情流露”,也可以解释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世间诸多不如意的事,才是使人触动最深的。
”换言之,当人接触到外界事物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幽深玄静的情感就是“物哀”[2]。
其中,“物”并非指生活中具体的“物”,而是指自然“物”,例如人、社会或人情世故等。
“哀”是指对自然界中所见、所闻、所听事物发出的叹息,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人之感动”,并非个人主观感动。
(二)物哀思潮产生背景物哀思潮产生于日本,以岛国独特的海洋性季风气候与朦胧变换的自然景象,造就了物哀思潮诞生的环境和背景[3]。
除此之外,世界文化交流的时代特色,中华文明和欧美文明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也为物哀思潮的诞生营造了历史文化背景。
(三)物哀的意义日本文学由于受到日本地域和自然条件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其文学中的许多元素具有一定片面性与局限性,不利于日本文学形成独立的文化色彩[4]。
然而,从《古事记》、《日本书纪》时代开始,日本文学开始出现了“哀”这一美学理念,尽管经历了时代变换,“哀”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日本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之中,其内容和概念也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得到了丰富,最终形成了“物哀”这样一种特殊的日本艺术美的形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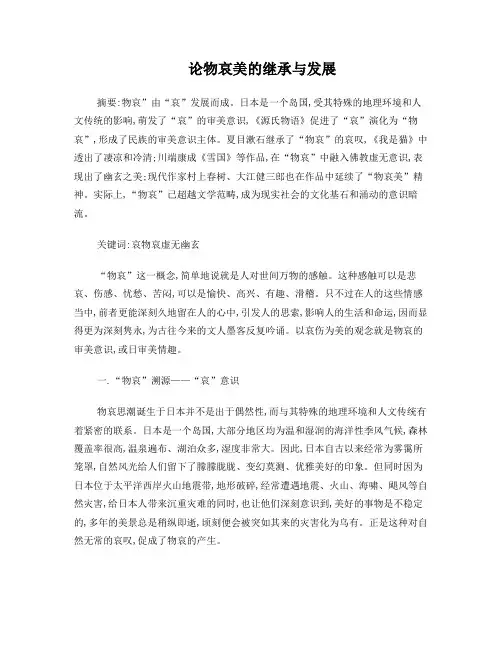
论物哀美的继承与发展摘要:物哀”由“哀”发展而成。
日本是一个岛国,受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影响,萌发了“哀”的审美意识,《源氏物语》促进了“哀”演化为“物哀”,形成了民族的审美意识主体。
夏目漱石继承了“物哀”的哀叹,《我是猫》中透出了凄凉和冷清;川端康成《雪国》等作品,在“物哀”中融入佛教虚无意识,表现出了幽玄之美;现代作家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也在作品中延续了“物哀美”精神。
实际上,“物哀”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石和涌动的意识暗流。
关键词:哀物哀虚无幽玄“物哀”这一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人对世间万物的感触。
这种感触可以是悲哀、伤感、忧愁、苦闷,可以是愉快、高兴、有趣、滑稽。
只不过在人的这些情感当中,前者更能深刻久地留在人的心中,引发人的思索,影响人的生活和命运,因而显得更为深刻隽永,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反复吟诵。
以哀伤为美的观念就是物哀的审美意识,或日审美情趣。
一.“物哀”溯源——“哀”意识物哀思潮诞生于日本并不是出于偶然性,而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日本是一个岛国,大部分地区均为温和湿润的海洋性季风气候,森林覆盖率很高,温泉遍布、湖泊众多,湿度非常大。
因此,日本自古以来经常为雾霭所笼罩,自然风光给人们留下了朦朦胧胧、变幻莫测、优雅美好的印象。
但同时因为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火山地震带,地形破碎,经常遭遇地震、火山、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给日本人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让他们深刻意识到,美好的事物是不稳定的,多年的美景总是稍纵即逝,顷刻便会被突如其来的灾害化为乌有。
正是这种对自然无常的哀叹,促成了物哀的产生。
物哀成了日本大和民族文学的代表性特色,也是其他民族不曾具有的。
早在奈良时代、平安初期,“哀”意识开始形成。
到了《万叶集》中后期,万叶歌从客观叙述发展到主观抒情的阶段,开始抒发个人感情的感伤性“,哀”渐次过渡到个人的感动,成为一种单纯的怜爱的咏叹。
这一演化,意味着古代审美意识逐渐走向个人的、自我的感情的“真实”咏叹,形成“哀”的审美理念的雏形,也由此开辟了日本固有的“哀”的审美范畴。

我理解的日本“物哀”--------我眼中的的日本文化物哀是日本平安时代的王朝文学上重要的文学审美理念之一。
在文学上,主要是通过写一些景物,例如萧条的冬景、残破的一处小山丘等等,来表达和宣泄人物内心深处的哀伤和幽情、感慨以及对世界黑暗的无奈。
在日本,“物哀”之说,一般人认为应该是来源于日本传统的。
日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形成的一大佐证,东瀛列岛有着优美宜人的自然风土,但是由于生存资源的相对匮乏和天灾的频仍,令日本人形成了崇尚哀伤的气质。
“物哀传统说”要从本居宣长在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的注释《源氏物语玉小栉》说起。
但我们可以反观本居宣长所生活的时代,似乎所谓“物哀传统说”还是值得考证的,本居宣长所处的历史背景,是17~19 世纪日本学界风行的“古道学”思潮,它是日本在隋唐时期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德川氏锁国政策施行后日本民族精神重建的反映。
复古学思潮的发端与文艺复兴类似,均为对本民族经典古籍的总结与再阐释,但民族主义的复古学者们在整理古籍时因时生义地添加了自己的思想。
本居宣长的老师贺茂真渊,确立了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一直为后世的复古追随者们效法。
所以,“物哀”是日本大和民族自古所有的一种美学理念或是民族性情,还是那些民族主义者的复古思潮在其所在时代因时生义所“创造”的,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思索的。
今日关于“物哀”产生于何时似乎不怎么重要,因为不管是复古主义者根据日本民族经典古籍所“创造”还是日本文化从生就有的,但其都离不开日本文化这个载体。
关于“物哀”的概念,中日学者都有许多见解,就“物哀”的最先提出者本居宣长来说,其在《紫文要领》中是这样阐述“物哀”的:世上万事万物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身体力行地体验,把这万事万物都放到心中来品味,内心里把这些事物的情致一一辨清,这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就是懂得物之哀。
进一步说,所谓辨清,就是懂得事物的情致。
辨清了,依着它的情致感触到的东西,就是物之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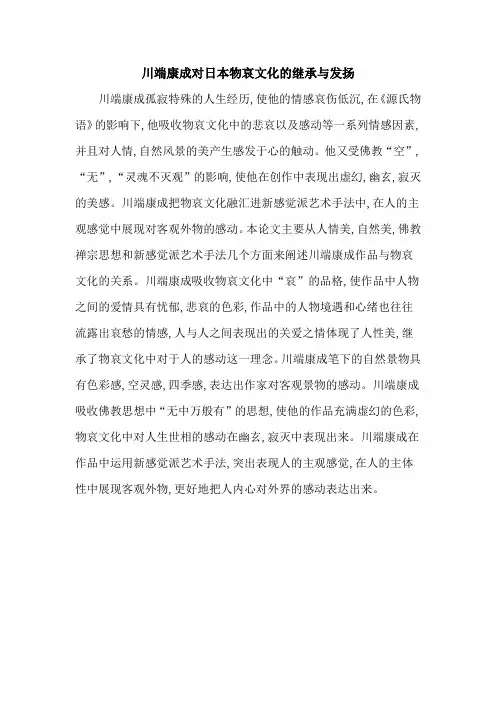
川端康成对日本物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川端康成孤寂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的情感哀伤低沉,在《源氏物语》的影响下,他吸收物哀文化中的悲哀以及感动等一系列情感因素,并且对人情,自然风景的美产生感发于心的触动。
他又受佛教“空”,“无”,“灵魂不灭观”的影响,使他在创作中表现出虚幻,幽玄,寂灭的美感。
川端康成把物哀文化融汇进新感觉派艺术手法中,在人的主观感觉中展现对客观外物的感动。
本论文主要从人情美,自然美,佛教禅宗思想和新感觉派艺术手法几个方面来阐述川端康成作品与物哀文化的关系。
川端康成吸收物哀文化中“哀”的品格,使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爱情具有忧郁,悲哀的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境遇和心绪也往往流露出哀愁的情感,人与人之间表现出的关爱之情体现了人性美,继承了物哀文化中对于人的感动这一理念。
川端康成笔下的自然景物具有色彩感,空灵感,四季感,表达出作家对客观景物的感动。
川端康成吸收佛教思想中“无中万般有”的思想,使他的作品充满虚幻的色彩,物哀文化中对人生世相的感动在幽玄,寂灭中表现出来。
川端康成在作品中运用新感觉派艺术手法,突出表现人的主观感觉,在人的主体性中展现客观外物,更好地把人内心对外界的感动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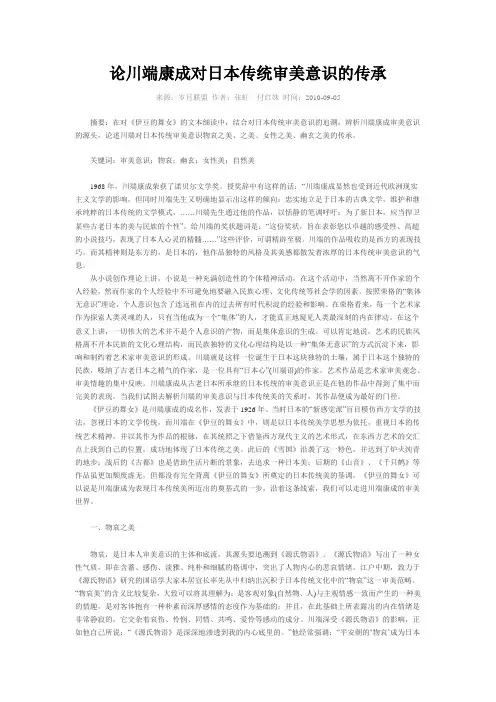
论川端康成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传承来源:岁月联盟作者:张虹付红妹时间:2010-09-05摘要:在对《伊豆的舞女》的文本细读中,结合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追溯,辨析川端康成审美意识的源头,论述川端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物哀之美、之美、女性之美、幽玄之美的传承。
关键词:审美意识;物哀;幽玄;女性美;自然美1968年,川端康成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授奖辞中有这样的话:“川端康成显然也受到近代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同时川端先生又明确地显示出这样的倾向: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和继承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川端先生通过他的作品,以恬静的笔调呼吁:为了新日本,应当捍卫某些古老日本的美与民族的个性”。
给川端的奖状题词是:“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这些评价,可谓精辟至极。
川端的作品吸收的是西方的表现技巧,而其精神则是东方的,是日本的,他作品独特的风格及其美感都散发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气息。
从小说创作理论上讲,小说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个体精神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当然离不开作家的个人经验,然而作家的个人经验中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社会学的因素。
按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个人意识包含了连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时代积淀的经验和影响。
在荣格看来,每一个艺术家作为探索人类灵魂的人,只有当他成为一个“集体”的人,才能真正地窥见人类最深刻的内在律动。
在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伟大的艺术并不是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意识的生成。
可以肯定地说,艺术的民族风格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而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沉淀下来,影响和制约着艺术家审美意识的形成。
川端就是这样一位诞生于日本这块独特的土壤,属于日本这个独特的民族,吸纳了古老日本之精气的作家,是一位具有“日本心”(川端语)的作家。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审美观念、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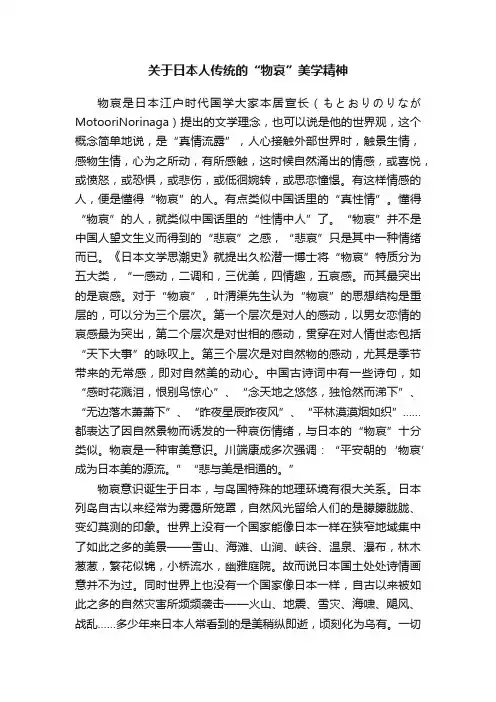
关于日本人传统的“物哀”美学精神物哀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もとおりのりながMotooriNorinaga)提出的文学理念,也可以说是他的世界观,这个概念简单地说,是“真情流露”,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生情,感物生情,心为之所动,有所感触,这时候自然涌出的情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恐惧,或悲伤,或低徊婉转,或思恋憧憬。
有这样情感的人,便是懂得“物哀”的人。
有点类似中国话里的“真性情”。
懂得“物哀”的人,就类似中国话里的“性情中人”了。
“物哀”并不是中国人望文生义而得到的“悲哀”之感,“悲哀”只是其中一种情绪而已。
《日本文学思潮史》就提出久松潜一博士将“物哀”特质分为五大类,“一感动,二调和,三优美,四情趣,五哀感。
而其最突出的是哀感。
对于“物哀”,叶渭渠先生认为“物哀”的思想结构是重层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
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
中国古诗词中有一些诗句,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无边落木萧萧下”、“昨夜星辰昨夜风”、“平林漠漠烟如织”……都表达了因自然景物而诱发的一种哀伤情绪,与日本的“物哀”十分类似。
物哀是一种审美意识。
川端康成多次强调:“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
”“悲与美是相通的。
”物哀意识诞生于日本,与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日本列岛自古以来经常为雾霭所笼罩,自然风光留给人们的是朦朦胧胧、变幻莫测的印象。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一样在狭窄地域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美景——雪山、海滩、山涧、峡谷、温泉、瀑布,林木葱葱,繁花似锦,小桥流水,幽雅庭院。
故而说日本国土处处诗情画意并不为过。
同时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自古以来被如此之多的自然灾害所频频袭击——火山、地震、雪灾、海啸、飓风、战乱……多少年来日本人常看到的是美稍纵即逝,顷刻化为乌有。

浅议日本文学物哀思潮的发展历程CATALOGUE目录•引言•“物哀”的起源及早期发展•“物哀”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的体现•“物哀”在当代日本文学中的表现及影响•“物哀”思潮对日本文学的深远意义•结论CATALOGUE 引言研究背景和意义背景物哀思潮是日本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流派,起源于平安时代,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物哀一词,最早出现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是日本文学中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
通过对物哀思潮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追求和思想文化。
意义物哀思潮作为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日本文化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物哀思潮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可以揭示日本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思想内涵,为中日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研究目的和方法目的方法CATALOGUE“物哀”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平安时代《源氏物语》起源镰仓时代物哀思潮在镰仓时代逐渐发展,与武士文化和佛教思想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
室町时代物哀思潮在室町时代进一步发展,与禅宗思想相互融合,强调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悟,以及对悲剧美的欣赏。
早期发展CATALOGUE“物哀”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的体现多样化表达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体现现代日本文学中“物哀”的多样性“物哀”与日本自然景观的融合自然景观的“物哀”自然景观与“物哀”的融合“物哀”与人物命运在许多现代日本文学作品中,“物哀”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人物的命运往往成为“物哀”情感表达的载体。
要点一要点二“物哀”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作家常常通过“物哀”的情感表达来反映人物的命运,如《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对逝去爱人的怀念和追忆,就是一种“物哀”的情感体现。
“物哀”与人物命运的交织CATALOGUE“物哀”在当代日本文学中的表现及影响从传统到现代多元化的表现与西方文化的交融030201当代日本文学中“物哀”的演变情感表达的深化物哀思潮激发了日本作家的创新精神,尝试运用新的创作手法表现主题,如象征、隐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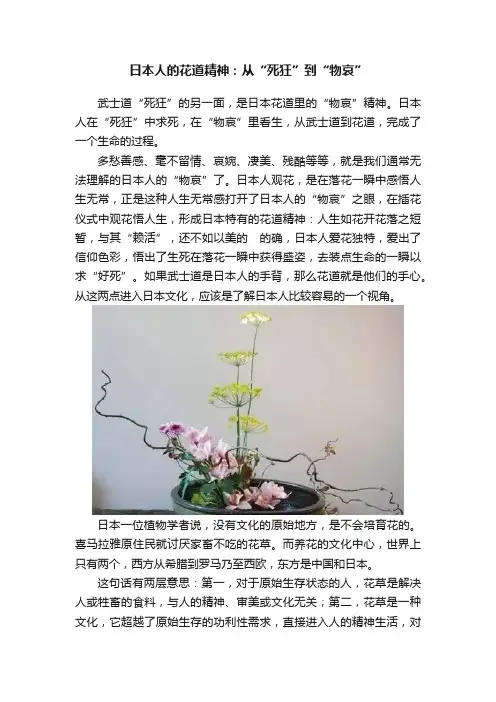
日本人的花道精神:从“死狂”到“物哀”武士道“死狂”的另一面,是日本花道里的“物哀”精神。
日本人在“死狂”中求死,在“物哀”里看生,从武士道到花道,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多愁善感、毫不留情、哀婉、凄美、残酷等等,就是我们通常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物哀”了。
日本人观花,是在落花一瞬中感悟人生无常,正是这种人生无常感打开了日本人的“物哀”之眼,在插花仪式中观花悟人生,形成日本特有的花道精神:人生如花开花落之短暂,与其“赖活”,还不如以美的的确,日本人爱花独特,爱出了信仰色彩,悟出了生死在落花一瞬中获得盛姿,去装点生命的一瞬以求“好死”。
如果武士道是日本人的手背,那么花道就是他们的手心。
从这两点进入日本文化,应该是了解日本人比较容易的一个视角。
日本一位植物学者说,没有文化的原始地方,是不会培育花的。
喜马拉雅原住民就讨厌家畜不吃的花草。
而养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两个,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乃至西欧,东方是中国和日本。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对于原始生存状态的人,花草是解决人或牲畜的食料,与人的精神、审美或文化无关;第二,花草是一种文化,它超越了原始生存的功利性需求,直接进入人的精神生活,对花的态度,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格调。
的美学意义,这印证了知堂老人所说的: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美。
永恒的“物哀”对于日本人来说,“物哀”不仅是情和意的状态,还是知的态度。
知、情、意是合一的,可文化的选择,却往往突出其中一字。
例如,古希腊文化是爱知的,情、意二字,亦趋于知,连艺术都知性化了,哲学就更是爱知的学问了。
而日本文化是主情的,表现为一种“物哀”的美学样式。
“物哀”在这里并非消极的心态,也没有颓废意识,而是关于人对花所产生的生命感发,赋予了美学意义上的道德指向,所谓“仁民爱物”和佛教慈悲心,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
在日本人看来,瞬间是一种时间的残缺美,在这瞬间的残美中截取人生的意义,以获得对终极死亡的自由,才是一场永恒的“物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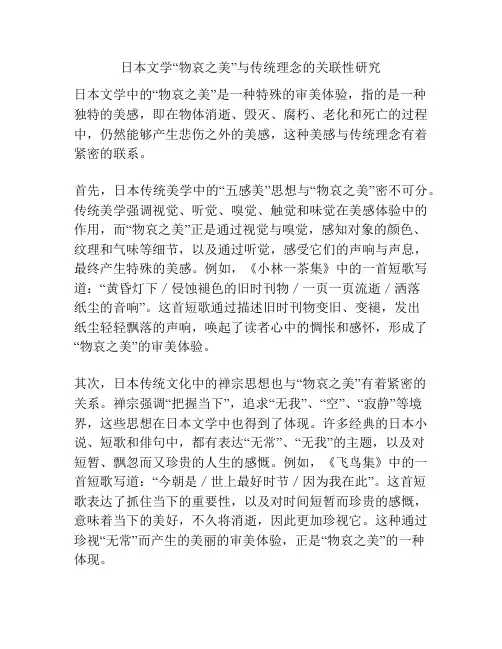
日本文学“物哀之美”与传统理念的关联性研究日本文学中的“物哀之美”是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美感,即在物体消逝、毁灭、腐朽、老化和死亡的过程中,仍然能够产生悲伤之外的美感,这种美感与传统理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日本传统美学中的“五感美”思想与“物哀之美”密不可分。
传统美学强调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在美感体验中的作用,而“物哀之美”正是通过视觉与嗅觉,感知对象的颜色、纹理和气味等细节,以及通过听觉,感受它们的声响与声息,最终产生特殊的美感。
例如,《小林一茶集》中的一首短歌写道:“黄昏灯下/侵蚀褪色的旧时刊物/一页一页流逝/洒落纸尘的音响”。
这首短歌通过描述旧时刊物变旧、变褪,发出纸尘轻轻飘落的声响,唤起了读者心中的惆怅和感怀,形成了“物哀之美”的审美体验。
其次,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禅宗思想也与“物哀之美”有着紧密的关系。
禅宗强调“把握当下”,追求“无我”、“空”、“寂静”等境界,这些思想在日本文学中也得到了体现。
许多经典的日本小说、短歌和俳句中,都有表达“无常”、“无我”的主题,以及对短暂、飘忽而又珍贵的人生的感慨。
例如,《飞鸟集》中的一首短歌写道:“今朝是/世上最好时节/因为我在此”。
这首短歌表达了抓住当下的重要性,以及对时间短暂而珍贵的感慨,意味着当下的美好,不久将消逝,因此更加珍视它。
这种通过珍视“无常”而产生的美丽的审美体验,正是“物哀之美”的一种体现。
此外,日本文学中的“侘寂”美学也是“物哀之美”的表现。
侘寂美学强调自然的不完美、独特和独特之美,以及生命的脆弱和有限性,这种思想在日本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例如,《枕草子》中写道:“秋之夕,或らへば、天の涯まで、あらしふく、/ときもあり、けさもあら、ゆめのかよひ路”。
“秋之夕”是一句特别的季节性词汇,黄昏时的感受和境界被表现出来了,黄昏时,人们不禁会想象到秋天的到来,在黄昏的时刻,这种想象尤其的强烈;而“天の涯まで”表现出人类永远无法到达那片天空的边缘,即使多么美丽和令人向往的东西也是如此,这种茫然不知道日积月累会不会真正实现的、遥远却又真实存在的感觉,可以称作“物哀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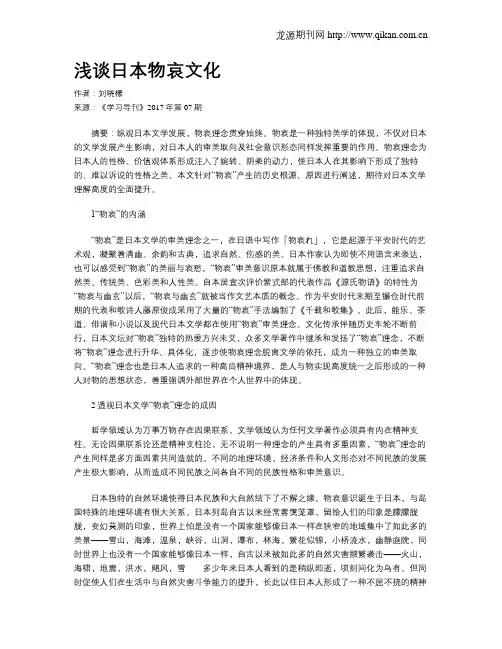
浅谈日本物哀文化作者:刘晓檬来源:《学习导刊》2017年第07期摘要:纵观日本文学发展,物哀理念贯穿始终。
物哀是一种独特美学的体现,不仅对日本的文学发展产生影响,对日本人的审美取向及社会意识形态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
物哀理念为日本人的性格、价值观体系形成注入了婉转、阴柔的动力,使日本人在其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难以诉说的性格之美。
本文针对“物哀”产生的历史根源、原因进行阐述,期待对日本文学理解高度的全面提升。
1“物哀”的内涵“物哀”是日本文学的审美理念之一,在日语中写作「物哀れ」,它是起源于平安时代的艺术观,凝聚着清幽、余韵和古典,追求自然、伤感的美。
日本作家认为即使不用语言来表达,也可以感受到“物哀”的美丽与哀愁。
“物哀”审美意识原本就属于佛教和道教思想,注重追求自然美、传统美、色彩美和人性美。
自本居宣次评价紫式部的代表作品《源氏物语》的特性为“物哀与幽玄”以后,“物哀与幽玄”就被当作文艺本质的概念。
作为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前期的代表和歌诗人藤原俊成采用了大量的“物哀”手法编制了《千载和歌集》。
此后,能乐、茶道、俳谐和小说以及现代日本文学都在使用“物哀”审美理念。
文化传承伴随历史车轮不断前行,日本文坛对“物哀”独特的热爱方兴未艾,众多文学著作中继承和发扬了“物哀”理念,不断将“物哀”理念进行升华、具体化,逐步使物哀理念脱离文学的依托,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取向。
“物哀”理念也是日本人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境界,是人与物实现高度统一之后形成的一种人对物的思想状态,着重强调外部世界在个人世界中的体现。
2 透视日本文学“物哀”理念的成因哲学领域认为万事万物存在因果联系。
文学领域认为任何文学著作必须具有内在精神支柱。
无论因果联系论还是精神支柱论,无不说明一种理念的产生具有多重因素,“物哀”理念的产生同样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
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人文形态对不同民族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从而造成不同民族之间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审美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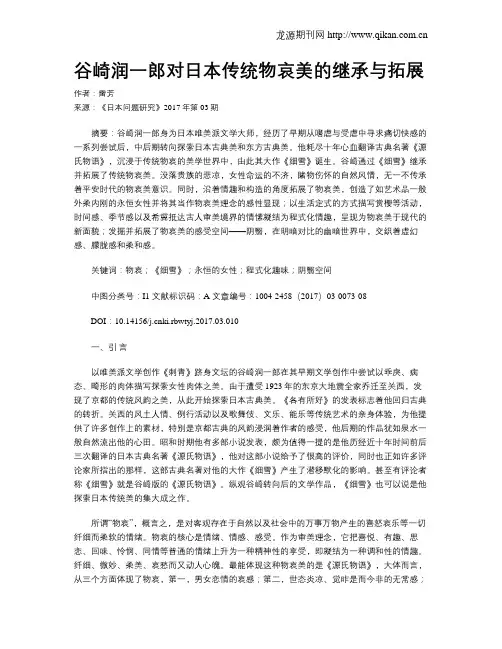
谷崎润一郎对日本传统物哀美的继承与拓展作者:雷芳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03期摘要:谷崎润一郎身为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经历了早期从嗜虐与受虐中寻求痛切快感的一系列尝试后,中后期转向探索日本古典美和东方古典美。
他耗尽十年心血翻译古典名著《源氏物语》,沉浸于传统物哀的美学世界中,由此其大作《细雪》诞生。
谷崎通过《细雪》继承并拓展了传统物哀美。
没落贵族的悲凉,女性命运的不济,睹物伤怀的自然风情,无一不传承着平安时代的物哀美意识。
同时,沿着情趣和构造的角度拓展了物哀美,创造了如艺术品一般外柔内刚的永恒女性并将其当作物哀美理念的感性显现;以生活定式的方式描写赏樱等活动,时间感、季节感以及希冀抵达古人审美境界的情愫凝结为程式化情趣,呈现为物哀美于现代的新面貌;发掘并拓展了物哀美的感受空间——阴翳,在明暗对比的幽暗世界中,交织着虚幻感、朦胧感和柔和感。
关键词:物哀;《细雪》;永恒的女性;程式化趣味;阴翳空间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3-0073-08DOI:10.14156/ki.rbwtyj.2017.03.010一、引言以唯美派文学创作《刺青》跻身文坛的谷崎润一郎在其早期文学创作中尝试以乖戾、病态、畸形的肉体描写探索女性肉体之美。
由于遭受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全家乔迁至关西,发现了京都的传统风韵之美,从此开始探索日本古典美。
《各有所好》的发表标志着他回归古典的转折。
关西的风土人情、例行活动以及歌舞伎、文乐、能乐等传统艺术的亲身体验,为他提供了许多创作上的素材,特别是京都古典的风韵浸润着作者的感受,他后期的作品犹如泉水一般自然流出他的心田。
昭和时期他有多部小说发表,颇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历经近十年时间前后三次翻译的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他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古典名著对他的大作《细雪》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试论川端康成文学作品之“物哀”美传承摘要:“物哀”作为日本文学的审美理念,表达的是一种物与心交融后的感动。
川端康成在他的作品中孜孜不倦地传承和发扬“物哀”美,使自己崇尚的日本传统之美在淡淡的哀愁中不断升华。
本文在探究“物哀”内涵的基础上,解读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对“物哀”美的传承。
关键词:川端康成“物哀”同情传承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一生写了100余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那些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女性的悲惨遭遇,刻画她们对生活、爱情和艺术追求的作品,如《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等。
在这些作品中,川端用大量的笔墨表现出了对以薰子、驹子、千重子等渺小人物的特有悲哀与同情,同时又以咏叹的方式表露出了对渺小人物的赞赏、同情、怜悯和哀伤的真实情感。
作品中主人公的悲哀感与作家自身的同情哀感相融合,再加上借用自然美的作用,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得到塑造。
在这些作品中,他致力于追求美,创造出有所感觉的美,并由此继承和发扬富有日本传统美学特色的“物哀”美。
本文拟在探究“物哀”内涵的基础上,解读川端康成文学作品中日本式“物哀”美的传承与发展。
一何谓“物哀”1 “物哀”之起源“物哀”作为日本文学审美理念,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记》及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之后的世界首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
据《源氏物语论》的作者藤井贞和统计,在“《源氏物语》中用了一千多次‘哀’和‘物哀’”。
据此,体现“物心合一”审美情趣的日本文学传统审美理念——“物哀”基本形成。
在此之后,日本江户时代的国学大家本居宣长(1730-1801)就《源氏物语》加以研究、整理,对“物哀”做出了如是概述:其一,“凡‘哀’者,本来是耳闻、目睹、感触到外在事务时,内心有所触动而发出的叹息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啊’‘哦’之类。
”其二,“‘哀’不单指悲哀,高兴、有趣、快乐、可笑,但有‘啊’‘哦’之叹,都是‘哀’。
日本物哀论文开题报告日本物哀论文开题报告背景介绍:物哀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源自于日本文化中对于物品的情感化表达。
它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对物品的功利性看待,而是将物品赋予了情感和灵魂。
日本人对于物品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使得物哀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
本论文将探讨日本物哀的起源、表达方式以及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一部分:物哀的起源1.1 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物品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这种观念使得日本人对于物品的态度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更加注重物品的精神内涵和情感价值。
1.2 宗教信仰的影响日本的宗教信仰,如神道教和佛教,也对物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神道教中的神灵崇拜和佛教中的生死观念,使得人们对物品的珍视和怀念更加深刻。
第二部分:物哀的表达方式2.1 文学作品中的物哀日本文学中经常出现对于物品的描写和赋予情感的表达。
例如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通过猫的视角来描绘人类社会中的种种荒谬和无奈,表达了对于物品的无尽思考和感慨。
2.2 电影艺术中的物哀日本电影中常常以物品为媒介,表达对于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思考。
例如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通过一台摄像机的视角,揭示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和无助。
2.3 设计与建筑中的物哀日本的设计和建筑注重细节和内涵,通过对于物品的精心设计和呈现,表达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物品的敬重。
例如日本的茶道和花道,将物品与人的情感融为一体。
第三部分:物哀对现代社会的影响3.1 消费主义与物哀在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人们对于物品的追求往往只停留在功利性层面。
然而,物哀的概念提醒人们重新审视物品的价值,从而减少浪费和过度消费。
3.2 环境保护与物哀物哀的概念使得人们对于环境保护产生更深刻的思考。
通过对于物品的珍视和保护,人们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资源,减少浪费和污染。
3.3 心灵抚慰与物哀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常常感到压力和焦虑。
物哀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心灵抚慰的方式,通过对于物品的陪伴和体验,人们可以平复内心的不安和疲惫。
川端康成作品中的“物哀”精神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恒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京师迁至京都,上一为平安朝。
自此,日本文学进入了一个足以彪炳千秋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治安定,商贾兴盛,人民乐业,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为历代所无。
朝野上下均重文事,所以文学极为发达。
以《源氏物语》与《古今和歌集》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在这个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相继诞生了。
伴随着这些文学作品一起诞生的,是萦绕在日本传统文化灵魂深处的“物哀”精神。
所谓“物哀”,是日本文学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主体的哀感往往投射在客体的呈现之上,于是人和景物的宿命也就透过这种既纤细又颓废的描述层层交叠,紧密相系。
物哀是日本传统美学的源流,而物哀精神本身,又源自大和民族与生俱来的敏锐的“季节感”与纤细的洞察力。
雪,月,花,是日本文学历代以来咏叹不衰的主题。
见花而感聚散,窥月而叹无常。
如《古今和歌集》中在原平业的和歌:“月非昔日的月,春非昔日的春,唯有我是昔日的我”又如《万叶集》山部赤人歌:“想送给朋友看的梅花,积了白雪,花也难以分辨了”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正是由于日本文学传统追求这种心物融合,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故而描景绘物,无不带着一缕柔和而纤巧的主观感情色调。
日本人擅长寻觅美感,哪怕是转瞬既逝的美,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到,进而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被无限的放大然而,不妨引用对日本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
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
”美的事物难以长久,这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世间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种生死一瞬的飘忽的生命感悟,折射到精神世界中,变成为一种永恒的,深刻的悲哀感。
日本文学的始祖《古事记》中记载,女神伊邪那美命被火灼伤,临终遗言:“以花祭我。
”后世的武士道兴起之时,大和民族对花的崇拜之情亦同时兴起。
日本传统物哀精神的传承与演化——评漆原友纪《虫师》在众多优秀的日本动漫中,漆原友纪的《虫师》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
与主流日本动漫主题相比,这部以描写世间纷繁芜杂的“虫”以及与从事与之相关的协调工作的“虫师”主题的动漫显然有别于动辄打打杀杀的少年漫画和情爱跌宕的少女漫画;事实上,《虫师》更加接近日本本土的精神文化特色。
既不依靠惊心动魄的武打情节,也不依靠缠绵悱恻的恋爱故事,更不依靠无厘头搞笑来吸引观众,《虫师》以宁静淡远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以一个个由“虫”引起的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为故事依托,向观众展开一个哀而不伤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正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精神的体现。
自这个方面而言,《虫师》当为日本动漫中最得传统精神传承的作品。
第一次看动漫《虫师》的人都会为那其中茫茫群山的苍翠欲滴而震撼。
——生活在喧嚣繁杂的城市中,我们俨然忘记了大自然的颜色,而当最纯正自然的颜色出现在我们眼里的时候,给我们的触动是最深的,——所谓返朴归真,最平凡最自然的恰恰是最能打动人的。
——《虫师》就在这一片最自然质朴的绿色中向我们展开了它的故事,而它淡然如水娓娓道来的背景基调也就此奠定。
在我们熟知的世界里,住着一群与常见动植物孑然不同的生物。
远古以来,人们敬畏地称它们为『虫』。
当虫的世界和人的世界重合并发生矛盾时,虫师银古便会出现。
这里提到的虫显然不是看上去肉呼呼扭动的小东西,而是一种最接近生命本源,类似灵体的生物。
它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这种方式却可能有驳于人类的常识,甚至危害人类的生存。
于是就出现了『虫师』这种职业,他们云游四方,对虫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进行研究,并接受人们的委托,解决可能是由虫引起的怪异事件。
银古,正是他们的一员。
作为虫师的银古出入穷乡僻壤去追寻虫的足迹。
虫可能潜伏在人的身体中,潜伏在沼泽地中,潜伏在整个山岭中;带来疾病、瘟疫等可怕的灾难。
银古穿越草木的意识,找到结症,予以化解。
他一路走来,与少年天才画师、写虫之卷的女孩,保佑一方平安的大师等惺惺相惜,又黯然别离。
在这里,共存与牺牲,始终是最伤感的话题。
以此为背景,一个个与虫有关的故事娓娓展开在我们面前。
历史上的日本文化一直以清淡、寡欲、自哀为基调。
这与日本的地理环境有着潜在的关系。
一方面日本土地贫瘠,多台风地震,这在日本民族深层的心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哀感,从而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创作中表现出人在面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时的脆弱;另一方面日本虽山峦颇多,但怪山峻岑却少,小溪众多,长江大河却无,日本的国花樱花——那即开即败、随风凋零的羸弱风貌也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真实写照。
这些地理上的因素便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日本人的心理定势,使日本人特别地注重自我心理的平衡和更加纯粹的精神渴求。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由民族潜在心理生发开来,影响主体对外在客体的审美感知的情结,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其专有的名词,即物哀。
文化学术界对于“物哀”一词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有的人认为:“物”就是自然风景,自然风物;“哀”则指由自然景物诱发,或因长期审美积淀而凝结在自然景物中的人的情思。
也有人认为:物哀是一种审美意识。
川端康成多次强调:“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
”“悲与美是相通的。
” 还有人认为:物哀是一种生死观。
其主体追求“瞬间美”,不惜在美的瞬间“求得永恒的静寂”。
川端康成既认为“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也“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
……认为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
叶渭渠更指出:“日本人的美意识中存在着一种‘瞬间美’的理念,即赞美‘美之短暂’。
古代日本人更以樱花自比,将那‘瞬间美’的观念转变为视自杀为人生之极点的行为。
他们的殉死,其意义也在于追求瞬间的生命的闪光,企图在死灭中求得永恒的静寂”。
不管是上述怎样的说法,一种无可言说的至纯至美的悲泣感是物哀公认的表现之一。
《虫师》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风貌,在苍翠欲滴的茫茫群山之中,在虫师银古恬淡的行游之中,生命无常、万事万物轮回的故事徐徐展开……不论是人,还是虫,都有其宿命的归属去向。
首先从虫师银古的出身谈起。
少年银古,流落世间,被女虫师奴伊所收留,从目击银虫的那一瞬间起,他们的最终命运,将是栖息在永暗最底部……《眇之鱼》揭开的不仅是银古左眼的秘密,还预言了他必然的归宿。
主人公银古的出身不明寓示着世间生命的辗转无常颠沛流离,而他遭遇银虫之后作为虫师又注定栖息在永暗最底部的命运则寓示着世间一切生命都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最终化归尘土,——不论是自诩高贵的人,还是以原生态存在的虫。
这样的人物设定符合《虫师》的物哀精神氛围。
但是与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氛围表现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各传统艺术形式往往将这种生老病死的命运的不可抗拒性视作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对世间生命瞬息万变表现出纤细敏感的哀感。
叶渭渠指出:“日本国民性的特点……更爱残月、更爱初绽的蓓蕾和散落的花瓣儿,因为他们认为残月、花蕾、花落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会增加美感。
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但是在《虫师》中,主人公银古不停地游历中面对世间万物生命的瞬息消长,也坦然面对自己早已了然的归宿,心若止水地继续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行游工作——这是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中所没有的超脱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虫师》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化精神中对万事万物不定、光阴瞬息变幻的认识,但同时也弱化了传统文化精神对这种认识的哀感,突出了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安天命态度。
其次,从《虫师》的故事叙述方法来看:整部作品由一个个互不相干的故事组成,主要讲述平常人的生活,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姐妹之情等等,其实在这些故事模型中,大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比如《晓之蛇》,如果抽取掉其中关于虫的情节,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常见的妻子携幼寻夫而夫喜新厌旧另觅新欢的故事原型;比如《旅之沼》抽取掉关于虫的情节,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迷信的年代为平息河神而送女子献祭的愚昧故事;还有《迷茧探虚》,其实是一个姐妹情深、妹妹坚持不懈寻找姐姐的故事;而《雨临虹起》抽取掉关于虫的情节之后它讲述的是一个儿子承父之志的故事……诸如此类,虽然故事总由虫引起,总是表现平常人生活与虫的冲突或和谐,但虫师虫师,说的似乎是各种各样虫的故事,表现的其实是还是人最真挚朴实的情感。
因此,从整体看,《虫师》借写虫表现了对世间芸芸众生的描绘;从细节看貌似谈虫事,实则借虫事表现了普通人的生活以及情感——这种情感往往是静静的,不张扬,比如《天边之丝》,地主的儿子与女佣的爱情刚开始不被父亲接受,但最终在儿子的努力下留住了自己爱人作为人的信念,——这样一个故事隐含在女佣被一种叫作“天边草”的虫掳食的故事之下,当姑娘没有得到爱人的信任和安慰时,成为虫的意念占据了心灵,这使她逐渐身体轻浮随时可能离开地面飞走甚至隐形;而当地主的儿子在银古的点拨下着手做一些真正安抚爱人心灵的事情,比如正式成婚、离家与看不见的爱人一起生活……这一切使得逐渐虫化了的姑娘又渐渐萌生了作为人和爱人共处的愿望,于是虫的影响渐渐消退,姑娘重新回到了爱人的身边——这其实是借虫给人施加的影响来表现人世间普普通通的爱情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始终是以一种安静的态度来面对她身边发生的一切,哪怕是爱人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的时候,她也只是默默面对自己的哀伤。
可以说,这也是《虫师》所有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共有的特点:长相普通,出身平凡,性格温驯,默默无闻——这是典型的传统日本女性形象。
这样的形象风格也是物哀精神形成的缘由之一。
南开大学东方审美文化研究中心在2006年所发表的《“物哀”与日本民族的植物美学观》一文中指出:“在日本原始社会的母系家族制度时期,女性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化被公认为有女性痕迹。
感伤自然、愍物宗情的物之哀审美意识,大概从这一时期到平安时代就已经形成并成为整个日本历史的一个审美传统。
”因此,不仅是《天边之丝》中的女主人公,还有诸如《旅之泽》中被村民用以献祭河神但被虫所救的姑娘等等,她们哪怕面对死亡的恐惧也很少流露出情绪的波动。
这样的“不提哀感,却字里行间透出悲哀与静穆”正是物哀的精髓所在。
通观《虫师》全篇,无一不流露出这样的格调。
在《虫师》这部作品当中,虫师银古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正是他不断行走在一个个故事之中,因为天生招虫的体质,无法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呆下去,注定了一生漂泊,这样的宿命又增加了《虫师》通篇洋溢的哀感,增加了一种不安定性和稍纵即逝带来的茫然,在他不断的行走中,我们感到仿佛如流水般带走了世间人事的悲喜,而反过来正因为这种不断行走带来的不安定感增强了人世间悲哀的茫然——哀感未尽,已忘缘由,“书中人已然忘,看书人依旧伤。
”这样的茫然更增强了在淡淡中余韵袅袅的哀感。
虫师银古作为一个目睹一切的中间人,串连起一个个虫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故事,并将一个个故事中虫与人的矛盾一一化解。
“你没有过错,虫也没有过错,你们都只是在完成各自的人生而已……”这是剧中银古的话。
的确,虫师的存在意义就是调解虫与人之间因生存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
在这里,虚幻的虫实际上是在寓指大自然。
漆原友纪借银古之口以及借虫事表达了她自己的观点,即人与自然应当是互相依存的和谐关系,既不应当为人过分追求利益而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也不应当损害人的基本生存利益。
这也可以看作日本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今的发展和变化。
原先面对自然界灾害束手无策的日本民族其民族心理也相应地呈现为哀伤无奈的格调,而现今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类在防范和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技术已经突飞猛进,与过去那种小国寡民的心态已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昔日惜花哀月、追悼人生无常、年华易逝的被动心理已经被自信与尊重所取代。
这也是漆原友纪能够产生这样观点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虫师》在继承传统的物哀精神的同时也融合进现代日本民族的心理观念。
春花秋月,韶华易逝,沧海桑田,浮生沧桑……这些原本化作紫式部笔下源氏公子贯彻终身恬淡如水却又刻骨铭心的哀伤的情景状物,在现代日本背景下漆原友纪的动漫《虫师》中已经可以找到较为通脱豁达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