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体用说
- 格式:docx
- 大小:23.62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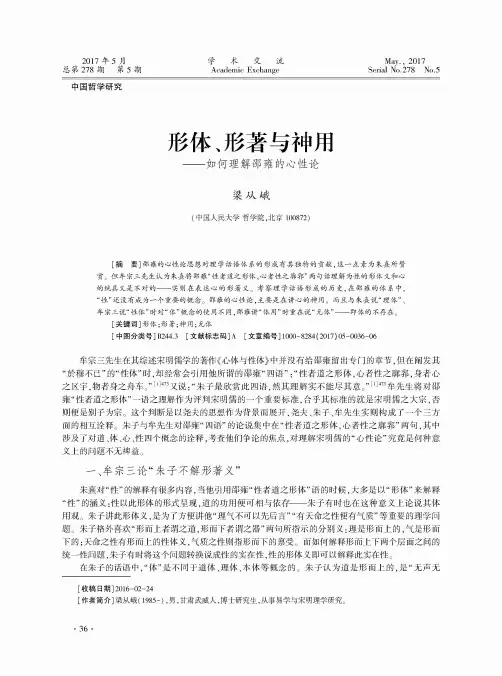
2017年5月学术交流 May., 2017总第 278 期 第 5 期 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278 No.5中国哲学研究形体、形著与神用—如何理解邵雍的心性论梁从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摘要]邵雍的心性论思想对理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贡献,这一点素为朱熹所赞 赏。
但牟宗三先生认为朱熹将邵雍“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廓郛”两句话理解为性的形体义和心的统具义是不对的——实则在表达心的形著义。
考察理学话语形成的历史,在邵雍的体系中,“性”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
邵雍的心性论,主要是在讲心的神用。
而且与朱熹说“理体'牟宗三说“性体”时对“体”概念的使用不同,邵雍讲“体用”时重在说“无体”—即体的不存在。
[关键词]形体;形著;神用;无体[中图分类号]B244.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 05-0036-06牟宗三先生在其综述宋明儒学的著作《心体与性体》中并没有给邵雍留出专门的章节,但在阐发其 “於穆不已”的“性体”时,却经常会引用他所谓的邵雍“四语”:“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廓郛,身者心 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车。
,’⑴473又说:“朱子最欣赏此四语,然其理解实不能尽其意。
,’⑴473牟先生将对邵 雍“性者道之形体”一语之理解作为评判宋明儒的一个重要标准,合乎其标准的就是宋明儒之大宗,否 则便是别子为宗。
这个判断是以尧夫的思想作为背景而展开,尧夫、朱子、牟先生实则构成了一个三方 面的相互诠释。
朱子与牟先生对邵雍“四语”的论说集中在“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廓郛”两句,其中 涉及了对道、体、心、性四个概念的诠释,考查他们争论的焦点,对理解宋明儒的“心性论”究竟是何种意 义上的问题不无裨益。
一、牟宗三论“朱子不解形著义”朱熹对“性”的解释有很多内容,当他引用邵雍“性者道之形体”语的时候,大多是以“形体”来解释 “性”的涵义:性以此形体的形式呈现,道的功用便可相与依存一朱子有时也在这种意义上论说其体 用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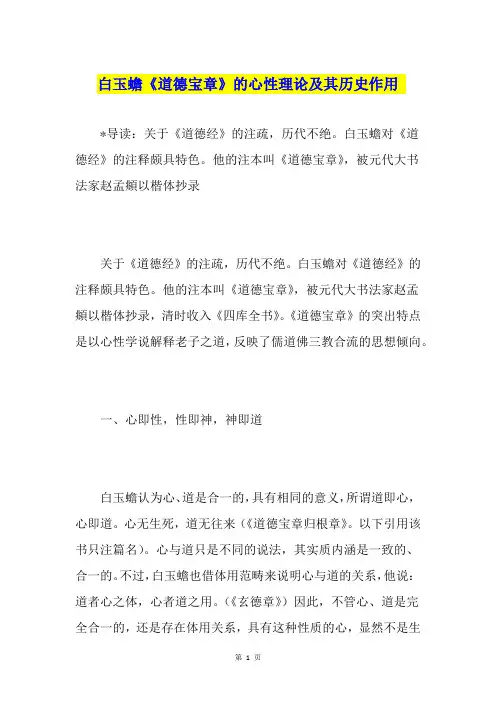
白玉蟾《道德宝章》的心性理论及其历史作用*导读:关于《道德经》的注疏,历代不绝。
白玉蟾对《道德经》的注释颇具特色。
他的注本叫《道德宝章》,被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以楷体抄录关于《道德经》的注疏,历代不绝。
白玉蟾对《道德经》的注释颇具特色。
他的注本叫《道德宝章》,被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以楷体抄录,清时收入《四库全书》。
《道德宝章》的突出特点是以心性学说解释老子之道,反映了儒道佛三教合流的思想倾向。
一、心即性,性即神,神即道白玉蟾认为心、道是合一的,具有相同的意义,所谓道即心,心即道。
心无生死,道无往来(《道德宝章归根章》。
以下引用该书只注篇名)。
心与道只是不同的说法,其实质内涵是一致的、合一的。
不过,白玉蟾也借体用范畴来说明心与道的关系,他说: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
(《玄德章》)因此,不管心、道是完全合一的,还是存在体用关系,具有这种性质的心,显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人心(心脏),也不是心理意义上的思维意识,而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心。
这种心被称作本心、真心、道心。
故而与道合一。
在阐明即心即道,即道即心(心、道合一)的基础上,白玉蟾又提出了心即性,性即神,神即道(《益谦章》)以及即心是道,神亦道,性亦道(《谦德章》)的命题。
这都说明心、性、神、道在世界的本原、本体的意义上是同一的。
既然心、道合一,所以凡道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亦为心所具有。
首先,从本原意义上说,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世界万有都由道所产生。
在《道德宝章》中,心亦具备这种属性,所谓心者,大道之源(《谦德章》),及心者,造化之源(《为道章》)。
这表明心是宇宙万物的根源。
其次,从道、心与万物的关系角度讲,道创造了宇宙万物,并支配着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所以,道寓存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之中,但又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事物。
道的运行表现出循环往复的特性(所谓反者道之动),这使得宇宙万物都融入大化流行之中。
白玉蟾把这些特性概括为何物不在此道之中,此道常在万物之内(《任为章》)、道为万化之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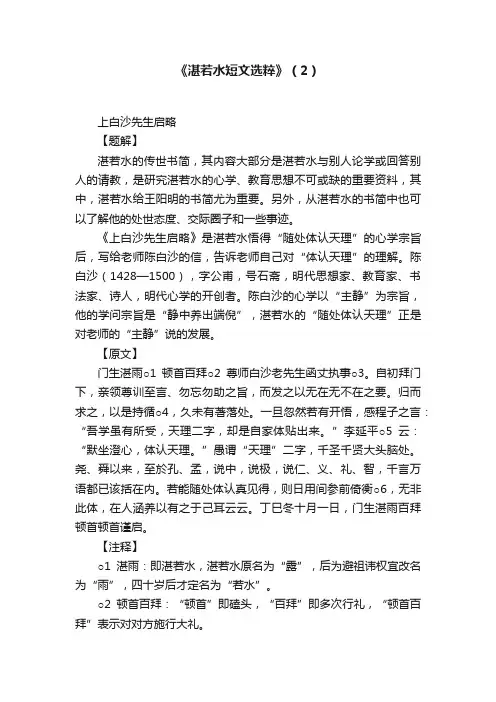
《湛若水短文选粹》(2)上白沙先生启略【题解】湛若水的传世书简,其内容大部分是湛若水与别人论学或回答别人的请教,是研究湛若水的心学、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中,湛若水给王阳明的书简尤为重要。
另外,从湛若水的书简中也可以了解他的处世态度、交际圈子和一些事迹。
《上白沙先生启略》是湛若水悟得“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宗旨后,写给老师陈白沙的信,告诉老师自己对“体认天理”的理解。
陈白沙(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心学的开创者。
陈白沙的心学以“主静”为宗旨,他的学问宗旨是“静中养出端倪”,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正是对老师的“主静”说的发展。
【原文】门生湛雨○1顿首百拜○2尊师白沙老先生函丈执事○3。
自初拜门下,亲领尊训至言、勿忘勿助之旨,而发之以无在无不在之要。
归而求之,以是持循○4,久未有著落处。
一旦忽然若有开悟,感程子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李延平○5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愚谓“天理”二字,千圣千贤大头脑处。
尧、舜以来,至於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该括在内。
若能随处体认真见得,则日用间参前倚衡○6,无非此体,在人涵养以有之于己耳云云。
丁巳冬十月一日,门生湛雨百拜顿首顿首谨启。
【注释】○1湛雨:即湛若水,湛若水原名为“露”,后为避祖讳权宜改名为“雨”,四十岁后才定名为“若水”。
○2顿首百拜:“顿首”即磕头,“百拜”即多次行礼,“顿首百拜”表示对对方施行大礼。
○3函丈执事:“函丈”原意是老师讲席与学生坐席之间要留出一丈的空地,后作为对老师的尊称;“执事”是对对方的敬称。
○4持循:遵照。
○5李延平:即李侗(1093一1163),字愿中,南宋学者,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属今福建南平)人,程颐的二传弟子,朱熹曾曾从游其门。
○6参前倚衡:意指言行要讲究忠信笃敬,站着就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四字展现于眼前,乘车就好象看见这几个字在车辕的横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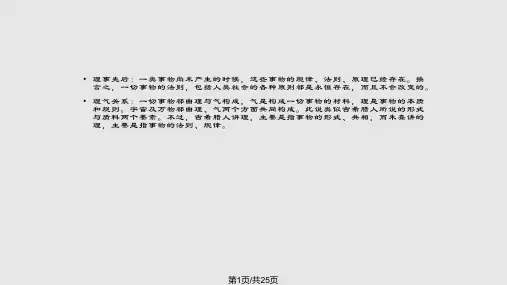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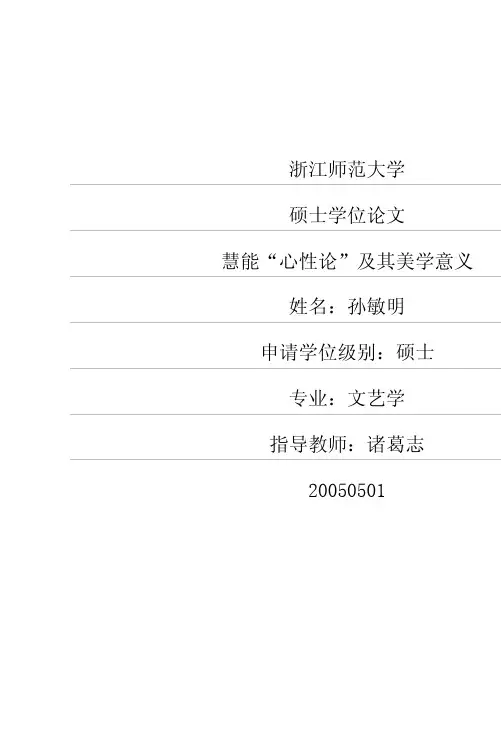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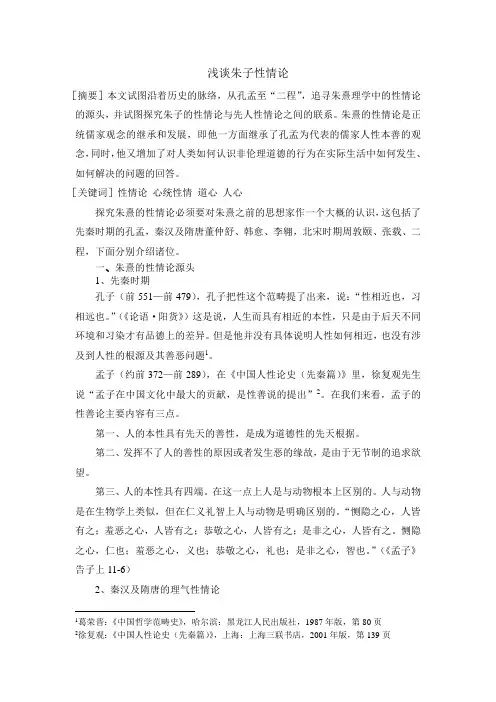
浅谈朱子性情论[摘要]本文试图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孔孟至“二程”,追寻朱熹理学中的性情论的源头,并试图探究朱子的性情论与先人性情论之间的联系。
朱熹的性情论是正统儒家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即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观念,同时,他又增加了对人类如何认识非伦理道德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发生、如何解决的问题的回答。
[关键词]性情论心统性情道心人心探究朱熹的性情论必须要对朱熹之前的思想家作一个大概的认识,这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孔孟,秦汉及隋唐董仲舒、韩愈、李翱,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下面分别介绍诸位。
一、朱熹的性情论源头1、先秦时期孔子(前551—前479),孔子把性这个范畴提了出来,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这是说,人生而具有相近的本性,只是由于后天不同环境和习染才有品德上的差异。
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说明人性如何相近,也没有涉及到人性的根源及其善恶问题1。
孟子(约前372—前289),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里,徐复观先生说“孟子在中国文化中最大的贡献,是性善说的提出”2。
在我们来看,孟子的性善论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是成为道德性的先天根据。
第二、发挥不了人的善性的原因或者发生恶的缘故,是由于无节制的追求欲望。
第三、人的本性具有四端。
在这一点上人是与动物根本上区别的。
人与动物是在生物学上类似,但在仁义礼智上人与动物是明确区别的。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告子上11-6)2、秦汉及隋唐的理气性情论1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9页汉代的董仲舒(公元前约179—约104),他吸收阴阳观念而把性情看成犹天之阴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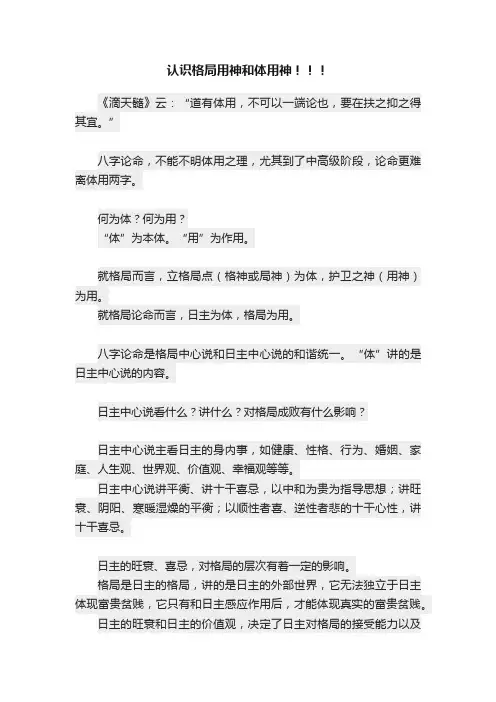
认识格局用神和体用神《滴天髓》云:“道有体用,不可以一端论也,要在扶之抑之得其宜。
”八字论命,不能不明体用之理,尤其到了中高级阶段,论命更难离体用两字。
何为体?何为用?“体”为本体。
“用”为作用。
就格局而言,立格局点(格神或局神)为体,护卫之神(用神)为用。
就格局论命而言,日主为体,格局为用。
八字论命是格局中心说和日主中心说的和谐统一。
“体”讲的是日主中心说的内容。
日主中心说看什么?讲什么?对格局成败有什么影响?日主中心说主看日主的身内事,如健康、性格、行为、婚姻、家庭、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幸福观等等。
日主中心说讲平衡、讲十干喜忌,以中和为贵为指导思想;讲旺衰、阴阳、寒暖湿燥的平衡;以顺性者喜、逆性者悲的十干心性,讲十干喜忌。
日主的旺衰、喜忌,对格局的层次有着一定的影响。
格局是日主的格局,讲的是日主的外部世界,它无法独立于日主体现富贵贫贱,它只有和日主感应作用后,才能体现真实的富贵贫贱。
日主的旺衰和日主的价值观,决定了日主对格局的接受能力以及日主对富贵贫贱的态度。
因此,格局论命离不开日主的旺衰、喜忌。
这篇文章为日主中心说的初级文章,为了便于学习,避免各种平衡理论的混淆,这里主要论述日主中心说中的旺衰平衡法,其它部分的内容要到全面深入论命时才能用得上,以后有机会再详论。
接下去我要讲的以日主为中心的旺衰平衡法,就是我们以前所学的身旺身弱的内容。
身旺身弱旺衰平衡法,我想学习命理两年以上的朋友,都已经掌握的够好了,无须我来重复。
越是简单的文章越难写。
旺衰平衡法差不多每本书中都有论及,大同小异,已经没什么看头了。
我是最不喜欢炒冷饭的人,这篇文章就写点其他老师们没谈到的内容,算是对旺衰平衡法的补充吧。
判断日主及各五行十神旺衰的主要依据为:月令、通根、透干、组合。
现在评定旺衰的方法已越来越灵活,不会拘泥于有些古书所言的:得时俱为旺论,失时便作衰看。
月令在判断旺衰中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通根透干、组合同样重要,因此就有了:得时不旺、失时不弱的经验之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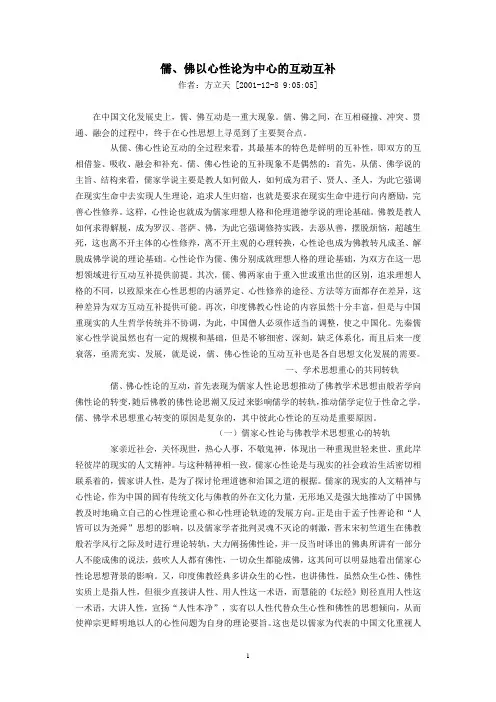
儒、佛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互动互补作者:方立天 [2001-12-8 9:05:05]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佛互动是一重大现象。
儒、佛之间,在互相碰撞、冲突、贯通、融会的过程中,终于在心性思想上寻觅到了主要契合点。
从儒、佛心性论互动的全过程来看,其最基本的特色是鲜明的互补性,即双方的互相借鉴、吸收、融会和补充。
儒、佛心性论的互补现象不是偶然的:首先,从儒、佛学说的主旨、结构来看,儒家学说主要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君子、贤人、圣人,为此它强调在现实生命中去实现人生理论,追求人生归宿,也就是要求在现实生命中进行向内磨励,完善心性修养。
这样,心性论也就成为儒家理想人格和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
佛教是教人如何求得解脱,成为罗汉、菩萨、佛,为此它强调修持实践,去恶从善,摆脱烦恼,超越生死,这也离不开主体的心性修养,离不开主观的心理转换,心性论也成为佛教转凡成圣、解脱成佛学说的理论基础。
心性论作为儒、佛分别成就理想人格的理论基础,为双方在这一思想领域进行互动互补提供前提。
其次,儒、佛两家由于重入世或重出世的区别,追求理想人格的不同,以致原来在心性思想的内涵界定、心性修养的途径、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为双方互动互补提供可能。
再次,印度佛教心性论的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是与中国重现实的人生哲学传统并不协调,为此,中国僧人必须作适当的调整,使之中国化。
先秦儒家心性学说虽然也有一定的规模和基础,但是不够细密、深刻,缺乏体系化,而且后来一度衰落,亟需充实、发展,就是说,儒、佛心性论的互动互补也是各自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
一、学术思想重心的共同转轨儒、佛心性论的互动,首先表现为儒家人性论思想推动了佛教学术思想由般若学向佛性论的转变,随后佛教的佛性论思潮又反过来影响儒学的转轨,推动儒学定位于性命之学。
儒、佛学术思想重心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彼此心性论的互动是重要原因。
(一)儒家心性论与佛教学术思想重心的转轨家亲近社会,关怀现世,热心人事,不敬鬼神,体现出一种重现世轻来世、重此岸轻彼岸的现实的人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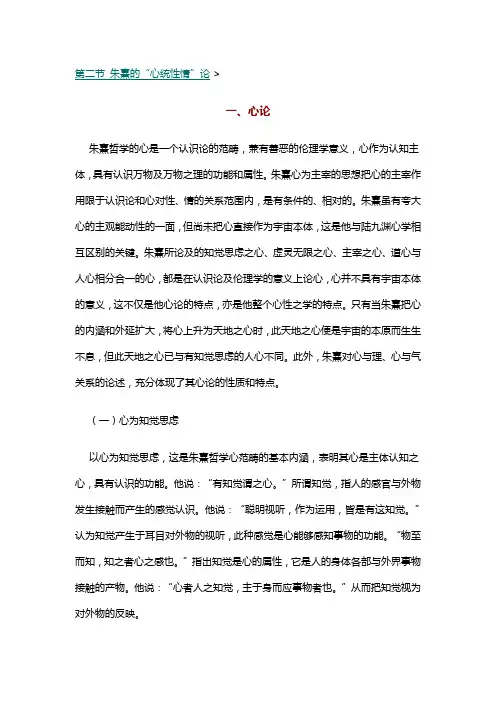
第二节朱熹的“心统性情”论 >一、心论朱熹哲学的心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兼有善恶的伦理学意义,心作为认知主体,具有认识万物及万物之理的功能和属性。
朱熹心为主宰的思想把心的主宰作用限于认识论和心对性、情的关系范围内,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朱熹虽有夸大心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但尚未把心直接作为宇宙本体,这是他与陆九渊心学相互区别的关键。
朱熹所论及的知觉思虑之心、虚灵无限之心、主宰之心、道心与人心相分合一的心,都是在认识论及伦理学的意义上论心,心并不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这不仅是他心论的特点,亦是他整个心性之学的特点。
只有当朱熹把心的内涵和外延扩大,将心上升为天地之心时,此天地之心便是宇宙的本原而生生不息,但此天地之心已与有知觉思虑的人心不同。
此外,朱熹对心与理、心与气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其心论的性质和特点。
(一)心为知觉思虑以心为知觉思虑,这是朱熹哲学心范畴的基本内涵,表明其心是主体认知之心,具有认识的功能。
他说:“有知觉谓之心。
”所谓知觉,指人的感官与外物发生接触而产生的感觉认识。
他说:“聪明视听,作为运用,皆是有这知觉。
”认为知觉产生于耳目对外物的视听,此种感觉是心能够感知事物的功能。
“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
”指出知觉是心的属性,它是人的身体各部与外界事物接触的产物。
他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
”从而把知觉视为对外物的反映。
朱熹对知觉又细加区分,指出:“知是知此一事,觉是忽然自理会得。
”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觉则是自心中有所觉悟。
“认为知是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此一事物的了解;觉是在知的基础上,心中有所觉悟,对事物进一步理会,并形成一定的见解。
可见知、觉虽同是人的感官与外物接触产生的认识,但二者有层次的深浅。
此外,朱熹所说的知、有广、狭两种意义。
狭义的知如上所述,是指对一事一物的了解;广义的知,是指人的整个认识能力。
他说:“知者,吾自有此知。
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要当极其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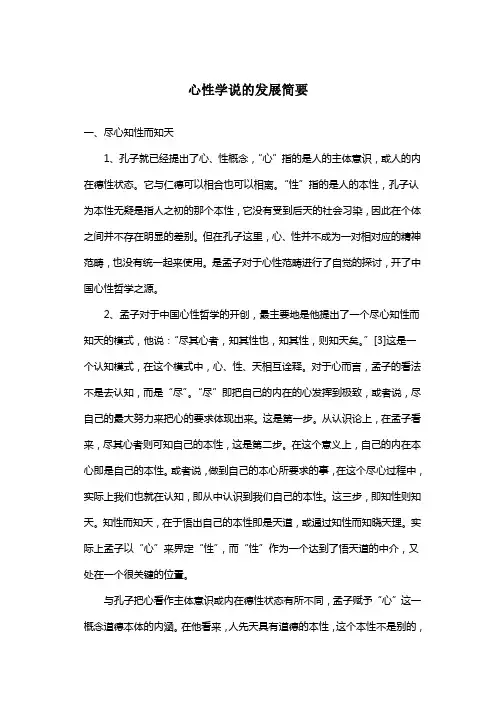
心性学说的发展简要一、尽心知性而知天1、孔子就已经提出了心、性概念,“心”指的是人的主体意识,或人的内在德性状态。
它与仁德可以相合也可以相离。
“性”指的是人的本性,孔子认为本性无疑是指人之初的那个本性,它没有受到后天的社会习染,因此在个体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但在孔子这里,心、性并不成为一对相对应的精神范畴,也没有统一起来使用。
是孟子对于心性范畴进行了自觉的探讨,开了中国心性哲学之源。
2、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最主要地是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3]这是一个认知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心、性、天相互诠释。
对于心而言,孟子的看法不是去认知,而是“尽”。
“尽”即把自己的内在的心发挥到极致,或者说,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把心的要求体现出来。
这是第一步。
从认识论上,在孟子看来,尽其心者则可知自己的本性,这是第二步。
在这个意义上,自己的内在本心即是自己的本性。
或者说,做到自己的本心所要求的事,在这个尽心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也就在认知,即从中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性。
这三步,即知性则知天。
知性而知天,在于悟出自己的本性即是天道,或通过知性而知晓天理。
实际上孟子以“心”来界定“性”,而“性”作为一个达到了悟天道的中介,又处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与孔子把心看作主体意识或内在德性状态有所不同,孟子赋予“心”这一概念道德本体的内涵。
在他看来,人先天具有道德的本性,这个本性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他认为,这四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因此又称为“本心”。
在孟子的思想中,“心”的概念还有主体意识的内涵。
孟子认为,心具有思维功能,只有在思的活动中,人们才能认识到什么,而如果放弃思考,在思想上则不会有什么收获。
但我们不要认为,孟子这里的“思”,并非完全是在我们现代的认识论意义上讲的,思也是一种对本心的自觉。
孟子的四心说实际上并非强调它的本源性,而是强调后天自觉的重要性。
理学渊薮的形成:宋代江西理学的昌明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宋一代,以学派林立、学术多元、思想自由、成果丰硕而堪称造极。
便利的交通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学习风气,使宋代江西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聚徒讲学的理想场所。
前有欧阳修、李觏与“三先生”共启理学先声,继有周敦颐莅赣为理学开山奠基,至朱熹、陆九渊等一代理学宗师崛起,理学终于在江西系统集成、发扬光大。
江西也因理学家活动时间早、学派多、人数众、地位高、贡献大、影响远而成为宋代理学渊薮。
放[中国学术思想史,有宋一代以学派林立、学术多元、思想自由、成果丰硕而堪称造极。
深入研究宋代理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尤为引人注目:一大批本土理学家的涌现和外埠理学家的进入,使得江西成为真儒过化之地、诸子向往之所,是全国的学术中心,有理学渊薮之美誉。
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略申管见。
一、北宋江西理学思潮的涌动宋代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逐渐融合而创生的和合理论。
宋代学者大体上把隋唐以来整饬师道衰微之功归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视其为理学先驱。
其实北宋时期理学的先驱除“三先生”之外,还应加上欧阳修和李觏,理学的开创者则是周敦颐。
(一)欧李并“三先生”同启理学先声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谥文忠公,江西庐陵人。
“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王安石及苏洵父子皆出其门下。
苏轼称其“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1](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P10381)。
欧阳修大力提倡风教,重视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尝言:“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2](卷二十五《胡先生瑗墓表》)对办学有功的胡瑗等人倍加赞赏,大力举荐。
欧阳修对五代以来“锼刻骈偶、羜羠弗振”[1](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P10375)的学风深恶痛绝,致力于倡导新的学术风气。
陈傅良在总结北宋学术嬗变时指出:“盖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始与其徒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恥无以自见也,欧阳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3](卷三十九《温州淹补学田记》,P501)欧阳修还以对佛学的独到批判,开启了庐陵学派,有“佛入中国千余年,只韩(愈)、欧(阳修)二公立得定耳”[4](卷四《庐陵学案》,P181)之说。
『宋明理学』弁言☆一.儒家、儒学、儒教大体上,“儒家”的用法可强调其与道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分别;“儒学”的用法强调其作为学术体系的意义;“儒教”的用法往往注重其作为教化体系的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习惯使用的“儒家”、“儒学”,一般都指“儒家思想”而言,换言之,“儒学”、“儒家”是指称孔子所开创的思想传统。
☆二. 儒学与理学1.儒学儒学首先是哲学思想,是对宇宙、道德、知识的知性探究(intellectual inquiry),也是对人心、人生、人性的内在体验,又是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与实践,也是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主张和探索。
2.理学儒学的这种特点,不仅体现于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王阳明、王船山这些著名思想家,也体现于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众多思想家。
只要翻阅《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从其中充满着宋明理学有关道体、性体、心体、有无、动静的详尽讨论中,就可了解,中国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宋明理学的思想家对宇宙、人心、体验、实践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化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辨析分疏。
因此,不可否认,理学既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体验,当然也是通向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三.宋明理学的文化背景在文化上,中唐出现了三大动向:宗教的,新禅宗的盛行宗教改革;文学的,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古文复兴;思想的,新儒家的兴起儒学重构。
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平民性、合理性。
引言☆一.宋明理学的正名1.“存天理,去人欲”整个康德伦理学的基调就是用理性克抑感性。
从孔子的“克己”,孟子的“取义”到来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与康德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宋明儒者所说的“存天理、去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用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
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关于《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
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中国佛学;和谐;心性和谐;修行观;心性论;境界论[中图分类号]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7-0031-04学术界关于佛教和谐思想的一般性探索较多,往往将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和谐思想作笼统的阐述,而就中国佛学和谐思想则没有专门论述。
和谐本身存在不同的层次,主要包括人自身的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层面。
和谐精神是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维度,东方古代文化均倾向于将和谐视作世界万物存在的本然状态,作为人自身生命、人格修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存在状态,作为自身文化的根本价值追求。
中国佛学作为东方古代思想的一部分,同样体现出鲜明的和谐精神。
中国佛学和谐思想是在印度佛学和谐思想基础上,吸收融合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谐思想形成的。
中国佛学和谐思想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以心性和谐思想为核心,是从心性和谐出发,关注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本文主要论述中国佛学的心性和谐思想。
中国佛学继承了印度佛教以心的解脱和心性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和思想特征,心性和谐思想在中国佛学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南北朝时期的涅??佛性论诸家异说多从心神、心识角度诠释佛性,以及隋唐佛学重心向心性论的偏移,均体现了中国佛学对心性问题的关注。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在印度佛学心灵净化、心性本净观念基础上,吸收融合了老庄玄学心性自然观念、体用一致思想,以及传统儒家的性善理论,具有融合中印佛学心性思想的特征。
明心见性1心性概述所谓心者,并不是我们胸膛里的肉团心,而是我们对境生起来的念头和思想,佛经称为六尘缘影,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落谢的影子,简称曰集起为心。
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没有心——思想和念头,而是由于有色等境在,才从各别的境缘上领受它的形象,产生认识,分别它的同异,安立名字,发生爱嗔、取舍、造作,才生出种种心念。
这心是和环境集合起来而生出的,不是片面单独起的,所以称为集起为心,也就是现代学说所谓“思想是客观环境的反映”。
要详细谈它的形象和内容,法相宗《成唯识论》说得很清楚,它可以分为八大心王和五十一心所。
这里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不详细说它了,请读者自己去研读《成唯识论》吧。
心既如斯,性又是何物呢?性是生起心的根本,是心的本源。
现代学说认为,它是生起心的能量。
没有它,对境生不起心来。
我们之所以能对境生心,全是它的作用。
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眼不能见,但它能起种种作用,故确实是有。
古人比为色里胶青,水中盐味,虽不可目睹,但事实上确实在起作用,在佛经上它有很多异名,如一真法界、真如、如来藏、佛性、真心、大圆胜慧等等。
只因众生迷而不觉,不知有此妙体,无始以来,只与生灭和合,变为妄心。
故心性原是一物,如水之与波,不是两回事。
现在世界得以飞跃前进,全靠自动化,而自动化又靠热能,无有热能,即无动力;无有动力,一切都是静止的、死的。
同样,我人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等,也靠体内的动力,而这动力就是性的作用。
所以性虽不能眼见,但确实在起一切作用,犹如电虽不能目见,而一切照明、发动等等都是它在起作用。
佛经内称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
但宗下常两者混用,称心为性,称性为心,我们只要洞悉它们的底蕴,搞清它们的分野,也就不至为之混淆惑乱了。
性和心不可强分为二,也不可视之为一。
犹如镜是性,镜与外境相对而现影,这个影就是心。
影非无,但不可着实,因为外境若没了,影也就没了,这个影是虚幻的。
幻影之心,时而明、时而暗、时而迷、时而解,所以叫做无明。
⼼性释义(⼆)⼼性释义(⼆) 欲见乎性,须先明⼼。
性为⼼之体,⼼乃性之⽤,体⽤⾮⼆,皆名⾔⽿。
性⽆形段,常恒不变,不⽣不灭,⾮可眼见,故名实相。
⼼为幻有,缘境⽽起,似有⽣灭,⽽实⽆⽣,故名幻⼼。
⼼发于性,灭还于性,动不见其来,息不知其去,⽆所从来,亦⽆所去。
⾔明⼼者,明此幻象似有去来,尚可以理解,明其为幻也。
⾔见性者,意见其实相决有,但可⾃觉,⽆法以⽰⼈⽿。
实相者,⾮有相之相也,⼼息则见,如波⽌⽽湛寂之⽔⾃显,能见性者,即同诸佛。
以常见此性体,⽽不为外境所惑,内见所囿,超然离⼀切诸相矣。
⼼⽆所著,则此法性周遍法界,⽆所不包,故名性海。
此⼈之同具,⽆别圣凡,以迷悟之分,遂若为⼆,悟则处处之见性,虽纷乱之际,亦⾃了然。
⼼即于境,⽆惑乱颠倒诸苦,⼤机⼤⽤,发乎⾄性,遂能⽆⼀事⽽不可应,⽆⼀处⽽不是道,⽆⼀物⽽可迷,⽆⼀境⽽不空,为超然⼤⾃在者矣。
⼼者,主于中⽽包罗万有者也。
⼼者⼟也,藏于⾝⽽可化⽣万法,故名法性⾝。
众⽣⼼⼼不断,有如⽆尽之锁链,若⼼⼼⼼⼼⼼联系⽽下。
是以妄念不断,幻成⽣死,⽽有六道。
然此⼼字,明表上⽆可加,见闻了了,廓然⽆有,是⼼之正者,乃名真⼼。
宗门⼼性不分者,即指此寂然之⼼为性,不可分也。
若稍加⼀“⼃”,则变为必矣。
⼼取于相,即成为想,⼼上加刃,即成为忍,⼼为形奴⽽为怒,⼼与⼼如⽽为恕,⼼⼼相互成为恒,⼼恋往昔成为惜,尽于⼰之为忠,闭于门之为闷,上下不安之为忐忑,千变万化,皆⼼上所加,⾮⼼之正也,乃妄也,幻影也。
⽽世⼈独指此幻妄者,名之⽈我⼼,《圆觉经》所谓六尘缘影为⾃⼼相,此⽣死颠倒之本也,亦即恒沙世界⽆尽众⽣若⼲⼈事起灭变化之所建⽴也。
即佛菩萨之度⽣弘化,亦如空华之乱起灭⽿,岂有实体,然不可⾔断灭也。
⼼上虽起万千变态,⽽⼼之本位勿移也,善⽆所加,恶⽆所损,此不可移者,亦假名⽈菩提⽽已。
菩提⽆相,⽽真实不虚,乃名实相,此不⽣不灭之性也。
今见⽆所加之⼼,为荡然⽆著之⼼,此⽆⼼⼼也,⽆⼼可⼼,⽽不动之性见矣。
《双旗镇刀客》中的禅宗美学作者:李洪武来源:《电影评介》2009年第01期[摘要]《双旗镇刀客》中的主人公孩哥,在一刀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但在决战时却突然战胜了强大的一刀仙。
影片出现这样的结局,观众不仅不觉突兀,反而得到了—种极大的艺术享受,这不仅归因于影片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人物刀法境界的刻画,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凭空臆造,而是建立在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有着丰富的禅宗文化内涵。
[关键词]《双旗镇刀客》禅宗心性真空妙有《双旗镇刀客》充满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尤其在人物刀法境界的刻画方面独具特色。
在一刀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哥,在决战时却突然战胜了强大的一刀仙。
这不仅归因于电影诸多艺术手法的运用,且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影片加入了丰富的禅宗文化内涵。
孩哥自从杀了一刀仙的弟弟以后,与一刀仙的矛盾就此开始。
孩哥的命运,一下子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关心。
影片中的孩哥,在一刀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
尤其是在电影最后。
孩哥的弱势被渲染到了顶点。
广袤的原野上。
一刀仙一行七骑。
迅捷有力的马蹄,践起股股沙土。
带着浓烈的杀气,向双旗镇滚滚而来。
孩哥孤身坐在旗杆下,面前的饭菜原封未动,蓬乱的头发,干裂的嘴唇,迷离的眼神,孩哥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
瘸子替孩哥承担责任,被一刀仙杀死:铁匠替孩哥说情,惨死在一刀仙刀下:钉马掌的老人装疯嘲弄一刀仙,也成了一刀仙的刀下之鬼。
一刀仙越过一具具尸体,带着满身的血腥气,一步步逼近了孩哥。
孩哥踉踉跄跄从地上爬起来,紧张得大口喘着粗气,看着一步步逼近的一刀仙。
但,随着孩哥钢刀出鞘的铿然之声,双方钢刀撞击的声音响过之后。
一直处于弱势的孩哥,杀死了强大的一刀仙!影片出现这样的结局。
观众不仅不觉突兀,反而从中得到了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这是因为,影片这种对孩哥刀法境界的表现方法,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凭空臆造,而是建立在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有着丰富的禅宗文化内涵。
禅宗认为,人的心性,始终处于“空”的状态,这样才能更好的“用”,即心性之体是空。
心性体用说
心性体用说探讨的主要是在以性为体,把道德理性视为本体的前提下,如何看待主体之心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如果说,心性一元说和心性二元说讲的是心性的联系与区别的话,那么,心性体用说则讲的是本体与本体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控制和把握人的道德本性及人的情感的问题。
这涉及到伦理学和修养论,亦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理论构成。
(一)性体心用说
性体心用说在宋明时期经历了一个提出、批判、再次提出,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在宋代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即提出和被否定的阶段。
至明代则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后一个阶段,即重新提出,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阶段。
性体心用说在张地匠思想里有所萌发,而始由程颐提出,经胡宏完善并确立。
胡宏的思想曾影响到张栻和朱熹,朱张早期均持性体心用之说。
后来朱张通过‚中和之辩‛,并对胡宏著作《知言》展开讨论,而放弃了前说,转而对性体心用说持批评态度。
这个过程对于理学心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主体思维的能动作用,并完善了理学的道德修养论。
之后,明代气学家罗钦因、吴廷翰在气本论的前提下重新提出了性体心用说,以强调心性有别。
1程颐在与弟子吕大临的辩论中提出了‚凡言心者,皆者已发而言‛的观点,以心为已发之用,以性为未发之体。
性体心用说初见端倪。
不过程颐后来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
胡宏在程颐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的思想,指出:
‚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
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
‛认为性为本体,性动为心,心是性本体的表现和作用。
朱熹和张栻早期都曾接受过胡宏的这一思想。
朱熹说:
‚《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
‛这说明朱熹曾赞同性为未发之体,心
为已发之用的观点。
张栻早期也持胡宏性体心用之师说,并使朱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这一观点。
后来朱熹悟前说之非,对性体心用说提出批评。
‚熹按:
心性体用之云,恐自上蔡谢子失之。
此云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语尤未安。
‛张栻此时也指出:
‚心性分体用,诚为有病。
‛朱张明确否定性体心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心统性情‛及‚心主性情‛说。
性体心用说在南宋被否定,在元代仍有影响。
许衡提出以仁为体,以知觉为用。
他说:
‚若夫知觉则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
‛其以仁为体,即是以性为体;以知觉为用,即是以心为用。
这是对胡宏思想的继承。
至明代,性体心用说被重新提起并有了发展。
罗钦顺、吴廷翰为了批佛和批陆王心学,强调心性二分,都持性体心用说。
与程颐、胡宏不同的是,罗钦顺、吴廷翰在气本论的前提下讲性体心用,体2
用关系限于性心的范围,整个宇宙则以气为本。
罗钦顺提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的命题,在心本于气和性为阴阳之理思想的基础上论性体心用。
他说:
‚盖天性之真,乃其本体;明觉自然,乃其妙用。
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
有体必有用,而用不可以为体也。
‛明觉之心为用,有性必有心,但心之用不可为性之体。
既把性作为心之用产生的原因,又强调性没有灵明知觉的属性,把心性区别开来。
xx指出:
‚性即是气‛,‚性为阴阳之气之所成‛,而‚性者,心之所以生也,知觉运动,心之灵明,其实性所出也。
‛也就是说,从本原上讲,气为本,性是气凝聚而形成的条理;从心的产生上讲,则心出于性。
由于‚性即是气‛,所以心出于性即心出于气,性心均以气为本。
恢复并发展了张载把道德理性客体化的思想,这也是对朱熹等否定性体心用说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
从而在气本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性体心用说。
(二)性体情用与心统性情说
性体情用与心统性情说有密切的联系。
‚心统性情‛说始由张载提出,至朱熹集大成。
理学把代表儒家伦理本质的人性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便在本体的作用为何物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见解。
胡宏以心为性的作用,其心性论没有‚情‛的位臵。
朱熹对此提出批评:
‚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
‛把胡宏的性体心用说改造为性体情用说。
朱熹又吸取张载的3‚心统性情‛说,并把胡宏的心以成性说改造为‚心统情性‛说。
朱熹在同张栻的讨论中指出:
心‚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
欲作而统性情也,如何?‛张栻则突出心的主宰性,指出:
‚统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张栻在理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的命题,强调主体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情感的把握与控制。
这一思想对朱熹影响很大,‚熹谓:
所改主字极有功。
‛并把心对性情的主宰纳入自己的‚心统性情‛说的体系之中。
朱熹分别吸取了张载的‚心统性情‛的命题和程颐‚心兼体用‛的思想,以‚性体情用‛说为基础,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
又吸取其他有关理论,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心统性情‛思想。
张载虽然最早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但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
程颐虽然提出了心兼体用的思想,这是他在修正自己的心为已发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他说:
‚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
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但程颐心兼体用的思想没有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
朱熹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又赋予张载的命题以具体的内涵,指出:
‚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
故程子曰:
‘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
‛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心贯通两端,管摄性情。
4这便是朱熹的新见。
性体情用与心统性情的结合,既标志着朱熹自己的‚心统性情‛说的确立,又丰富了自张载以来理学‚心统性情‛理论的内涵。
‚心统性情‛说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理论,也是朱熹心性学说的纲领,对后世影响甚大。
在这个理论体系里,朱熹十分重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把心从‚性体心用‛说中提出来,单独与性情对说,突出了人心对性、情的主宰。
通过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来强调平时(未发时)的道德培养与遇事(已发之际)按道德原则办事的一致性,把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情欲纳入心的统御和把握之下,提倡和肯定道德自觉,控制与节制情欲,这体现了理学重道德原则,轻物质欲望和利益的特征。
朱熹以静动、体用、未发已发论性情,又以心兼性情,心主宰性情,详尽地论述了各个范畴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理论的系统性、精致性和完善性达到了宋代理学心性论及道德修养论的高峰,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朱熹理学自身的特点,而与同时代陆九渊专论心,少论性,不讲心有体用,体现其简易工夫的心性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需要指出,在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里,心兼体用,以性为心之体,以情为心之用,这并不意味着心就是体,心性完全等同。
也不能把心是体说成心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由心派生。
如前所述,朱熹在批佛的过程中,明确反对心为宇宙本体、心生天地的思想,其心、性也是有区别的。
此外,受张栻‚心主性情‛思想的影响,朱熹持心主宰性情的观点。
5但朱熹的心为主宰,只涉及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问题,而不涉及本体论。
这与张栻的心不仅主宰性情,而且主宰万物思想明显不同,也与陆九渊的心本论有严格的区别。
这从朱熹本人对张栻、陆九渊心学的批评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明代吴廷翰从‚心生于性‛的思想出发,对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提出了批评。
他说‚张子有‘心统性情’之说,朱子以为性情之上,皆着得心字,所以言心统性情。
此犹未究心性之生与其本也。
天下无性外之物,心之在人,亦是一物,而不在性之外,性岂心之所能统乎?‛吴廷翰认为,‚心统性情‛说没有弄清心性之间
的关系,以及二者以何为本,因而有失。
他提出,心作为一物,不能超越性外,所以不可讲以心统性。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