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世界”:沈从文笔下的一个现代神话
- 格式:docx
- 大小:19.69 KB
- 文档页数: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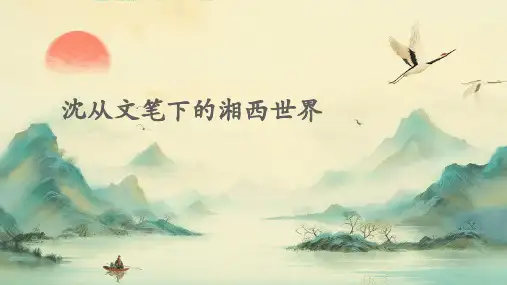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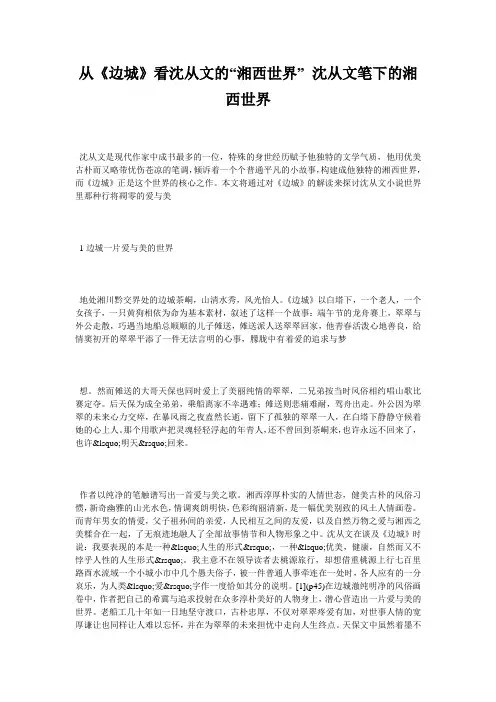
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沈从文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特殊的身世经历赋予他独特的文学气质,他用优美古朴而又略带忧伤苍凉的笔调,倾诉着一个个普通平凡的小故事,构建成他独特的湘西世界,而《边城》正是这个世界的核心之作。
本文将通过对《边城》的解读来探讨沈从文小说世界里那种行将凋零的爱与美1边城一片爱与美的世界地处湘川黔交界处的边城茶峒,山清水秀,风光怡人。
《边城》以白塔下,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相依为命为基本素材,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端午节的龙舟赛上,翠翠与外公走散,巧遇当地船总顺顺的儿子傩送,傩送派人送翠翠回家,他青春活泼心地善良,给情窦初开的翠翠平添了一件无法言明的心事,朦胧中有着爱的追求与梦想。
然而傩送的大哥天保也同时爱上了美丽纯情的翠翠,二兄弟按当时风俗相约唱山歌比赛定夺。
后天保为成全弟弟,乘船离家不幸遇难;傩送则悲痛难耐,驾舟出走。
外公因为翠翠的未来心力交瘁,在暴风雨之夜盍然长逝,留下了孤独的翠翠一人,在白塔下静静守候着她的心上人。
那个用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作者以纯净的笔触谱写出一首爱与美之歌。
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绚丽清新,是一幅优美别致的风土人情画卷。
而青年男女的情爱,父子祖孙间的亲爱,人民相互之间的友爱,以及自然万物之爱与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无痕迹地融人了全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中。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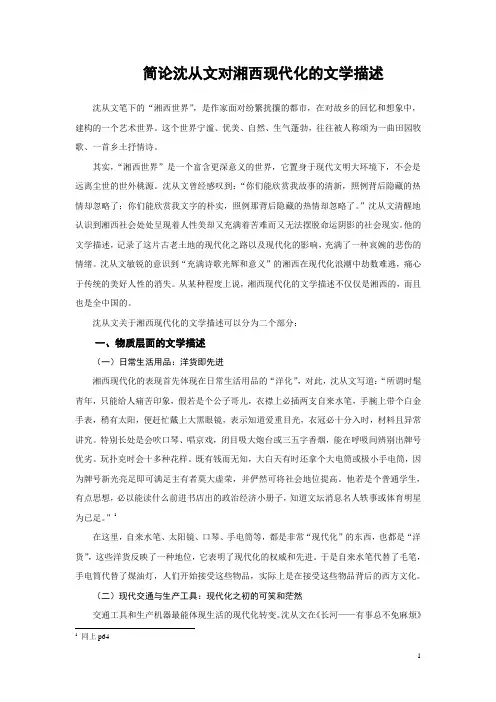
简论沈从文对湘西现代化的文学描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作家面对纷繁扰攘的都市,在对故乡的回忆和想象中,建构的一个艺术世界。
这个世界宁谧、优美、自然、生气蓬勃,往往被人称颂为一曲田园牧歌、一首乡土抒情诗。
其实,“湘西世界”是一个富含更深意义的世界,它置身于现代文明大环境下,不会是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
沈从文曾经感叹到:“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
”沈从文清醒地认识到湘西社会处处呈现着人性美却又充满着苦难而又无法摆脱命运阴影的社会现实。
他的文学描述,记录了这片古老土地的现代化之路以及现代化的影响,充满了一种哀婉的悲伤的情绪。
沈从文敏锐的意识到“充满诗歌光辉和意义”的湘西在现代化浪潮中劫数难逃,痛心于传统的美好人性的消失。
从某种程度上说,湘西现代化的文学描述不仅仅是湘西的,而且也是全中国的。
沈从文关于湘西现代化的文学描述可以分为二个部分:一、物质层面的文学描述(一)日常生活用品:洋货即先进湘西现代化的表现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用品的“洋化”,对此,沈从文写道:“所谓时髦青年,只能给人痛苦印象,假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
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
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
既有钱而无知,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
他若是个普通学生,有点思想,必以能读什么前进书店出的政治经济小册子,知道文坛消息名人轶事或体育明星为已足。
”1在这里,自来水笔、太阳镜、口琴、手电筒等,都是非常“现代化”的东西,也都是“洋货”,这些洋货反映了一种地位,它表明了现代化的权威和先进。
于是自来水笔代替了毛笔,手电筒代替了煤油灯,人们开始接受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接受这些物品背后的西方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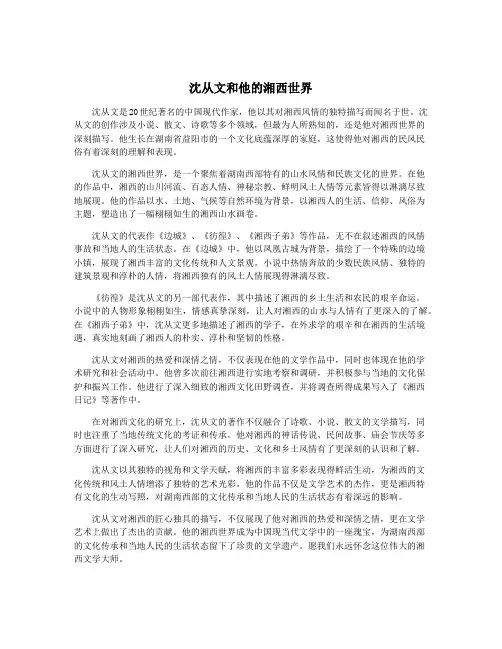
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世界沈从文是20世纪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以其对湘西风情的独特描写而闻名于世。
沈从文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多个领域,但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他对湘西世界的深刻描写。
他生长在湖南省益阳市的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这使得他对湘西的民风民俗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表现。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个聚焦着湖南西部特有的山水风情和民族文化的世界。
在他的作品中,湘西的山川河流、百态人情、神秘宗教、鲜明风土人情等元素皆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他的作品以水、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为背景,以湘西人的生活、信仰、风俗为主题,塑造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湘西山水画卷。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彷徨》、《湘西子弟》等作品,无不在叙述湘西的风情事故和当地人的生活状态。
在《边城》中,他以凤凰古城为背景,描绘了一个特殊的边境小镇,展现了湘西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文景观。
小说中热情奔放的少数民族风情、独特的建筑景观和淳朴的人情,将湘西独有的风土人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彷徨》是沈从文的另一部代表作,其中描述了湘西的乡土生活和农民的艰辛命运。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情感真挚深刻,让人对湘西的山水与人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湘西子弟》中,沈从文更多地描述了湘西的学子,在外求学的艰辛和在湘西的生活境遇,真实地刻画了湘西人的朴实、淳朴和坚韧的性格。
沈从文对湘西的热爱和深情之情,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中。
他曾多次前往湘西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保护和振兴工作。
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湘西文化田野调查,并将调查所得成果写入了《湘西日记》等著作中。
在对湘西文化的研究上,沈从文的著作不仅融合了诗歌、小说、散文的文学描写,同时也注重了当地传统文化的考证和传承。
他对湘西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庙会节庆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让人们对湘西的历史、文化和乡土风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文学天赋,将湘西的丰富多彩表现得鲜活生动,为湘西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增添了独特的艺术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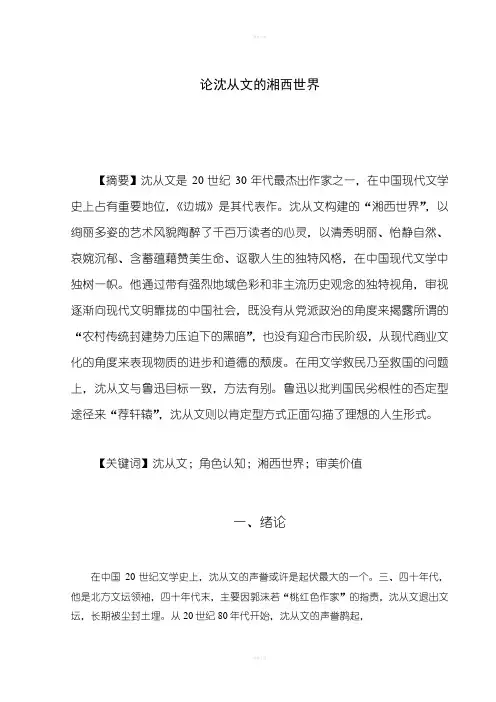
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摘要】沈从文是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作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边城》是其代表作。
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以绚丽多姿的艺术风貌陶醉了千百万读者的心灵,以清秀明丽、怡静自然、哀婉沉郁、含蓄蕴藉赞美生命、讴歌人生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他通过带有强烈地域色彩和非主流历史观念的独特视角,审视逐渐向现代文明靠拢的中国社会,既没有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揭露所谓的“农村传统封建势力压迫下的黑暗”,也没有迎合市民阶级,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废。
在用文学救民乃至救国的问题上,沈从文与鲁迅目标一致,方法有别。
鲁迅以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否定型途径来“荐轩辕”,沈从文则以肯定型方式正面勾描了理想的人生形式。
【关键词】沈从文;角色认知;湘西世界;审美价值一、绪论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
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四十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责,沈从文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
在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些作家或被读者遗忘,或被史家遗弃,而沈从文却跻身于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
目睹这种变化,不禁令人感慨唏嘘。
早在30年带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到:“……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
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之上。
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我没有方法拒绝。
”果然,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沈从文的作品再现了我国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生面影和生活方式,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及文体形式等诸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领域。
本文通过对作家的文学观、人生经历及其乡土小说的艺术风格的分析,来领略作家笔下的“湘西世界”,让我们共同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无疑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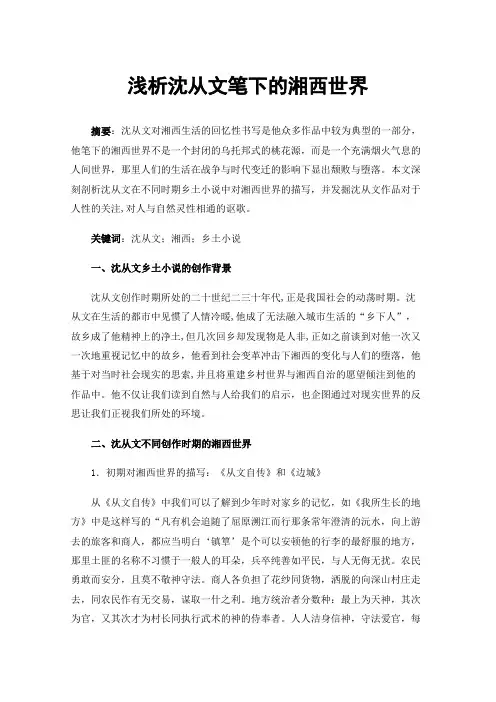
浅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摘要:沈从文对湘西生活的回忆性书写是他众多作品中较为典型的一部分,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人间世界,那里人们的生活在战争与时代变迁的影响下显出颓败与堕落。
本文深刻剖析沈从文在不同时期乡土小说中对湘西世界的描写,并发掘沈从文作品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人与自然灵性相通的讴歌。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一、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背景沈从文创作时期所处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我国社会的动荡时期。
沈从文在生活的都市中见惯了人情冷暖,他成了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乡下人”,故乡成了他精神上的净土,但几次回乡却发现物是人非,正如之前谈到对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视记忆中的故乡,他看到社会变革冲击下湘西的变化与人们的堕落,他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并且将重建乡村世界与湘西自治的愿望倾注到他的作品中。
他不仅让我们读到自然与人给我们的启示,也企图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让我们正视我们所处的环境。
二、沈从文不同创作时期的湘西世界1.初期对湘西世界的描写:《从文自传》和《边城》从《从文自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少年时对家乡的记忆,如《我所生长的地方》中是这样写的“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的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
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
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村庄走去,同农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一什之利。
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武术的神的侍奉者。
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皆有兵役……”(沈从文,1992)我们可以看到,湘西普通人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人们守法敬神,遵从古礼,甚至连兵卒都“纯善”如民。
不难看出沈从文记忆中的家乡人事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是一种和谐尽然有序的状态。
同样沈从文的《边城》留给大家的印象相似,可却又有本质的不同,即沈从文笔下的茶峒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现实世界,一条河打通了它与外界的联系,人们去附近的城镇赶集,庆祝节日,村民们同样按照古老的遗风生活,可这里不只有美好,仍然有苦难,这里的湘西世界似乎更加有魅力,因为这个地方是存在的,并不是桃花源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现代文学】沈从文小说里的湘西世界是啥样的?一、原始健全的人性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飞扬着灵气的圣地,持存着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真诚、朴实、自然、强悍的人生形式。
虚伪、懦弱绝对不属于这个世界,人们要笑就笑,要哭就哭。
这里的人生不是由理性支配的有社会实践意义的生命活动,而是作为肉体的、有感性、有欲望、有自然生命力的人的个体存在方式与状态,就像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一样,在原始、野性中充满了生命的顽强活力,寄寓了沈从文对健康、善良、美丽的人性美的深情赞颂。
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人是沈从文小说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
前者如《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后者如《边城》中的老水手等。
在湘西山明水秀中,受着自然的养育,远离尘嚣。
女孩子浪漫如花,清纯如水,他们的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的纤尘,诚实无邪,聪明伶俐,是人类天性的真正代表;老爷爷忠厚善良,慈爱可亲,生活的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
在这个世界里,不论是家境殷实的富人,还是精明的商人,都未受到商业文化的渲染,均待人以诚;不论是农人还是水手,都仁厚朴实;即便是娼妓,也依然保留着淳朴、善良的人性之光。
作家对这些人物饱含感情,在回避现实生活中民生与社会窘境的同时,寄寓了作者对健康、善良、淳厚的人性美的深情赞颂。
二、秀丽清新的自然风光自小生活在湘西的青山绿水中,沈从文对这一片美丽的景色有着深深的眷恋。
在小说中,他以饱满的情感,描绘了湘西绮丽动人的风光,这是一种虽被外来文明侵蚀但仍保存着古老原始状态的自然,镌刻着宁静、质朴与美丽,弥漫着古朴、幽静和祥和的情调,令人心动、痴迷。
这里有青山绿水,有弯弯的山路,有往来的船只,有吊脚楼支撑的小镇,还有色彩鲜艳的桃花杏花,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这样秀美淳朴的大自然陶冶着湘西人民,是他们完美人性的外在表现。
草木、小虫、飞鸟都被赋予了原始的生命力和深深的爱与美的情意,充满了山乡远古的生态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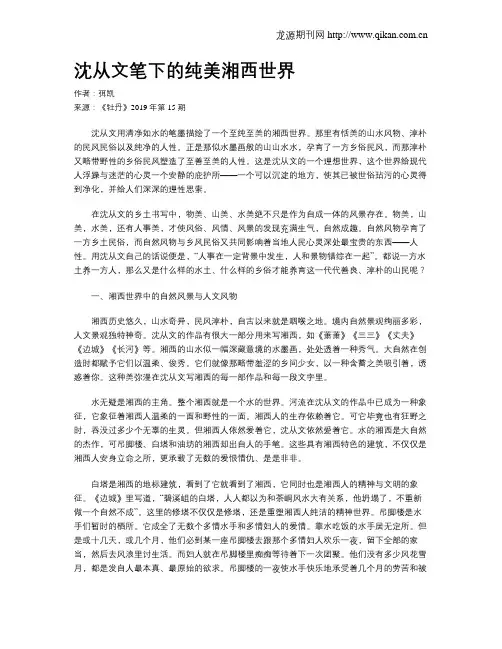
沈从文笔下的纯美湘西世界作者:弭凯来源:《牡丹》2019年第15期沈从文用清净如水的笔墨描绘了一个至纯至美的湘西世界。
那里有恬美的山水风物、淳朴的民风民俗以及纯净的人性。
正是那似水墨画般的山山水水,孕育了一方乡俗民风,而那淳朴又略带野性的乡俗民风塑造了至善至美的人性。
这是沈从文的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给现代人浮躁与迷茫的心灵一个安静的庇护所——一个可以沉淀的地方,使其已被世俗玷污的心灵得到净化,并给人们深深的理性思索。
在沈从文的乡土书写中,物美、山美、水美绝不只是作为自成一体的风景存在。
物美,山美,水美,还有人事美,才使风俗、风情、风景的发现充满生气,自然成趣。
自然风物孕育了一方乡土民俗,而自然风物与乡风民俗又共同影响着当地人民心灵深处最宝贵的东西——人性。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便是,“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人和景物错综在一起”。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水土、什么样的乡俗才能养育这一代代善良、淳朴的山民呢?一、湘西世界中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物湘西历史悠久,山水奇异,民风淳朴,自古以来就是咽喉之地。
境内自然景观绚丽多彩,人文景观独特神奇。
沈从文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用来写湘西,如《萧萧》《三三》《丈夫》《边城》《长河》等。
湘西的山水似一幅深藏意境的水墨画,处处透着一种秀气。
大自然在创造时都赋予它们以温柔、俊秀。
它们就像那略带羞涩的乡间少女,以一种含蓄之美吸引着,诱惑着你。
这种美弥漫在沈从文写湘西的每一部作品和每一段文字里。
水无疑是湘西的主角。
整个湘西就是一个水的世界。
河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已成为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湘西人温柔的一面和野性的一面。
湘西人的生存依赖着它。
可它毕竟也有狂野之时,吞没过多少个无辜的生灵。
但湘西人依然爱着它,沈从文依然愛着它。
水的湘西是大自然的杰作,可吊脚楼、白塔和油坊的湘西却出自人的手笔。
这些具有湘西特色的建筑,不仅仅是湘西人安身立命之所,更承载了无数的爱恨情仇、是是非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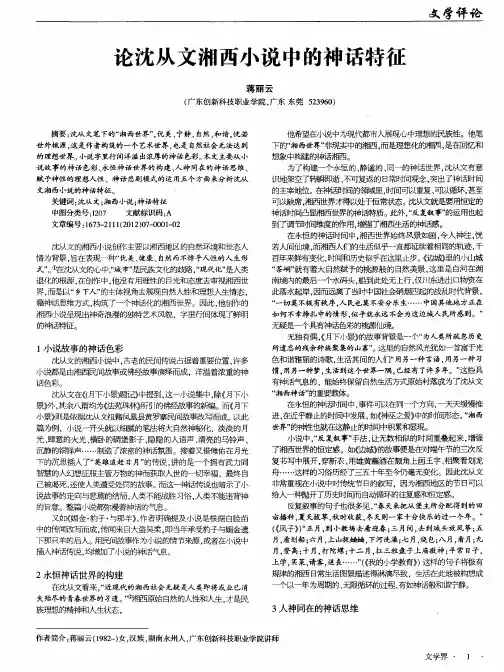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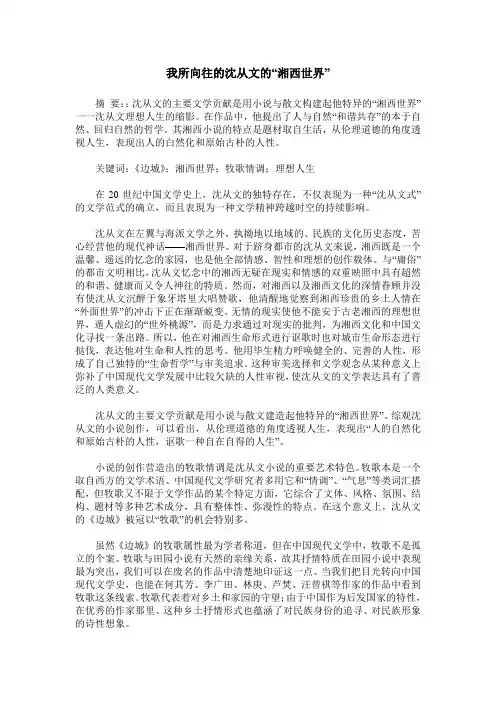
我所向往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摘要::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构建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一一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
在作品中,他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其湘西小说的特点是题材取自生活,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表现出人的白然化和原始古朴的人性。
关键词:《边城》;湘西世界;牧歌情调;理想人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的独特存在,不仅表现为一种“沈从文式”的文学范式的确立,而且表現为一种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持续影响。
沈从文在左翼与海派文学之外,执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他的现代神话——湘西世界。
对于跻身都市的沈从文来说,湘西既是一个温馨、遥远的忆念的家园,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创作载体。
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从文忆念中的湘西无疑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具有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
然而,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眷顾并没有使沈从文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
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人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
所以,他在对湘西生命形式进行讴歌时也对城市生命形态进行挞伐,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
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的、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与审美追求。
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使沈从文的文学表达具有了普泛的人类意义。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表现出“人的自然化和原始古朴的人性,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
小说的创作营造出的牧歌情调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
牧歌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类词汇搭配,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它综合了文体、风格、氛围、结构、题材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整体性、弥漫性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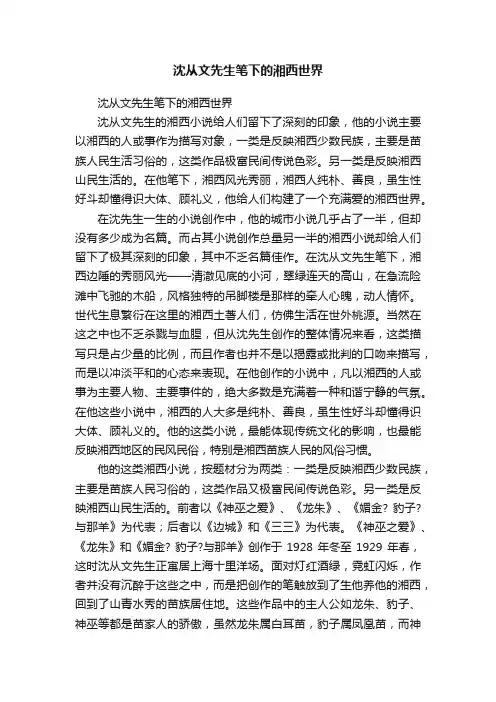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先生的湘西小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小说主要以湘西的人或事作为描写对象,一类是反映湘西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人民生活习俗的,这类作品极富民间传说色彩。
另一类是反映湘西山民生活的。
在他笔下,湘西风光秀丽,湘西人纯朴、善良,虽生性好斗却懂得识大体、顾礼义,他给人们构建了一个充满爱的湘西世界。
在沈先生一生的小说创作中,他的城市小说几乎占了一半,但却没有多少成为名篇。
而占其小说创作总量另一半的湘西小说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其中不乏名篇佳作。
在沈从文先生笔下,湘西边陲的秀丽风光——清澈见底的小河,翠绿连天的高山,在急流险滩中飞驰的木船,风格独特的吊脚楼是那样的牵人心魄,动人情怀。
世代生息繁衍在这里的湘西土著人们,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
当然在这之中也不乏杀戮与血腥,但从沈先生创作的整体情况来看,这类描写只是占少量的比例,而且作者也并不是以揭露或批判的口吻来描写,而是以冲淡平和的心态来表现。
在他创作的小说中,凡以湘西的人或事为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的,绝大多数是充满着一种和谐宁静的气氛。
在他这些小说中,湘西的人大多是纯朴、善良,虽生性好斗却懂得识大体、顾礼义的。
他的这类小说,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最能反映湘西地区的民风民俗,特别是湘西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他的这类湘西小说,按题材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湘西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人民习俗的,这类作品又极富民间传说色彩。
另一类是反映湘西山民生活的。
前者以《神巫之爱》、《龙朱》、《媚金? 豹子?与那羊》为代表;后者以《边城》和《三三》为代表。
《神巫之爱》、《龙朱》和《媚金? 豹子?与那羊》创作于1928 年冬至1929 年春,这时沈从文先生正寓居上海十里洋场。
面对灯红酒绿,霓虹闪烁,作者并没有沉醉于这些之中,而是把创作的笔触放到了生他养他的湘西,回到了山青水秀的苗族居住地。
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如龙朱、豹子、神巫等都是苗家人的骄傲,虽然龙朱属白耳苗,豹子属凤凰苗,而神巫属白脸苗,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皆是人中之龙。
浅谈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世界”作者:李丹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6期摘要:中国现代文坛上,勤奋多产的沈从文以小说和散文见长。
“犹如一幅幅湘西风俗画”,是沈从文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他的笔下,湘西是那样的宁静祥和,湘西人民是那样的淳朴善良,让人暂时摆脱了世俗的喧嚣烦扰。
一幅幅多彩多姿的湘西水墨画,连起来则是一长轴完整而绚丽的画卷。
就像沈从文自己说的那样:“一切皆那么和谐,那么愁人。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世外桃源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7-0018-01沈从文来自风光秀美如画的湘西,湘西的山山水水孕育了他的才情,民风淳朴的凤凰小镇赋予了他多情的个性。
他对自己的故乡有着不可言说的热爱,他所有的眷恋和乡愁都像涓涓细流,流淌在字里行间。
丰富浓重的本土性和民族色彩,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挥洒得淋漓尽致。
他描写了苗寨秀美怡人的景色:峰峦叠嶂、碧波绿水;生活在苗乡的人们:水手、士兵、土妓、苗妇;湘西独特的风物:码头、船只、吊脚楼;当地的民风民俗:漂滩、呼号、放蛊、赛龙舟。
多彩多姿的民族风情,连同那如雨似雾的轻烟细雨,如我这般没有到过湘西的人,读了都好似身临那片多情的土地,心中生起无限的向往。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质朴自然的桃源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和美好,没有战乱,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点的吵嚷声音都听不到。
而身处动荡年代的沈从文,也用他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而又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美、充满爱的天堂。
《市集》中,普通的乡下赶集场景在他的笔下也变得那样生动、有趣。
雨丝织成的帘幕下,“归去的人们,也间或有骑着家中打筛的雌马,马项颈下挂着一串小铜铃叮叮当当跑着的,但这是少数;大多数还是赖着两只脚在泥浆里翻来翻去。
他们总是笑嘻嘻的担着箩筐或背一个大竹背笼……有的却是口袋满装着钱心中满装着欢喜,——这之间各样人都有。
”这是一副多么美丽生动的乡村水墨画。
以《边城》为例,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摘要:在沈从文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作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边城》在人物的塑造及审美艺术特色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沈从文所营造的自然与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的意境,他用深沉厚重的文字,传达出了一份可贵的对于整个民族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通过对翠翠、爷爷、天保两兄弟的健康、美好人性的描写来表达湘西世界的人性美,又对湘西百姓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来表达湘西世界的人情美,及其与人合一的自然之景的描绘了一片自然美。
下面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他作品中的“湘西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T正文:一、湘西世界的概述本文以《边城》为主体的“湘西世界”几个层面上的接受变迁,分析其成因和蕴涵.沈从文在1926年至1928年的早期创作中,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是其稚嫩的习作阶段。
30、40年代是其创作成熟丰收的阶段,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等。
其中《柏子》(1928)是他成名的第一篇小说。
这些湘西题材的小说中,人物遍及社会多个层面,有船夫、水手、妓女、军人、老板、杂役等等。
他对小说独特的设计与追求,他的对湘西边地这个“蛮荒世界”的展示,当时就影响了很多读者,作者本人也成为进京文学青年拜访的首选。
其中的优秀之作,还被国外的译者翻译介绍。
鲁迅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称其为最好的中国小说家之一。
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里,统治一切的是自然,不是道德也不是法律。
湘西人民所具有的“神性”响彻着嘹亮的呼声,这个世界人性的完美(包括商人、吊脚楼的妓女及泊船的水手)、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和至死不喻、生命的健康和自由,纯纯跃然于纸上。
而这些精彩感人的人性描写,有很多是通过性爱这一内容来呈现的。
这类以《边城》为代表。
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题目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神巫形象专业汉语言文学班级 09级2班学号 0901020131姓名王金露指导教师伍宝娟老师成绩论文工作时间:2012 年 3 月至2012 年 5 月浅析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神巫形象学生:王金露指导老师:伍宝娟摘要:沈从文的创作是与楚巫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作家,他在他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中创作的大量风格各异的“巫”的形象,并再现了各种巫术场面,他的小说创作中与“巫”有关的作品有十几篇,虽然数量不多,却形成了他湘西小说世界中独特巫楚文化氛围和原始野性的宗教信仰,沈从文通过其作品来表现“巫”形象和巫术活动,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湘西文化长期以来失去话语权,被肆意丑化的现象进行的反拨,同时发展了“巫”的文化意蕴,赋予巫师以雄强健康的人生形象,体现了他重构健康人性的文学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神巫形象;野性;雄强Analyses wizard of Shen congwen 'novel about west HunanUndergraduate:Wang jinluSupervisor:Wu baojuanAbstract:Shen Congwen's writing and Chu witch culture are closely tied to a writer, in his description of Xiangxi world in the cre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different styles of the "witch" image, and reproduces a variety of witchcraft scene, his novel creation and the "witch" related works are more than a dozen, although the amount is not much, but he formed the Xiangxi in the world's unique culture atmosphere and Wu Chu wild's religious beliefs, Shen Congwen through his works to express the "witch" image and witchcraft activities, is in fact a certain degree of Xiangxi culture has long lose the right to speak, is deliberately defacing phenomenon in the backwash,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witch"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gives the sorcerer to male strong healthy life image, he embodie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health human ideal of literature.Key words:Shen Congwen;The image of wizard;Wild ;Strong目录中文摘要 (1)英文摘要 (2)目录 (3)前言 (4)一、楚巫文化 (4)二、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神巫形象的三种类型 (5)(一)异化的神巫形象 (6)(二)写实化的神巫形象 (6)(三)诗化的神巫形象 (6)三、巫师行巫场面 (7)(一)场面血腥 (7)(二)巫师衣饰华美,载歌载舞 (8)四、张扬跋拓之美 (9)结语 (10)参考文献 (11)致谢 (12)前言巫最早出现在文学题材,是在屈原的《九歌》这部作品中。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
他以湘西为背景,通过独特的语言和描述方式,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让无数读者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湘西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这里的人们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
他通过对湘西风土人情的描绘,表现出一种对乡土文化的深深眷恋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笔下的“边城”。
《边城》是一部描绘湘西小镇生活的小说,它以翠翠、傩送和天保三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湘西社会的风俗人情与人的善良、正直。
沈从文用他独特的语言和描述方式,将湘西的风景、人物和人情味儿融为一体,让人仿佛置身于这个远离尘嚣的世界。
除了《边城》,沈从文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小说作品,如《长河》、《萧萧》、《菜园》等,这些作品同样展现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和沈从文对乡土文化的深刻理解。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感受到淳朴的民风、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人性的美好。
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对乡土文化的眷恋,更体现了对现代社会的思考和批判。
湘西的美丽风光和朴实人民,成为了沈从文笔下永恒的主题,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总结起来,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个融汇了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理想世界,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世界呈现给了读者。
这个世界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它代表了沈从文对乡土文化的深刻眷恋和对现代社会的思考与批判。
在这个世界里,读者可以体会到不同于城市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人性的美好,从而感受到沈从文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与艺术魅力。
沈从文,这位湘西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人文思考,创造了一个鲜活而独特的湘西世界。
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文化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沈从文文学作品在文化传承、思想深度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独特性。
浅析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世界”论文沈从文作为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初颇具影响力的乡土作家,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是他生命的起点。
下面是店铺带来的关于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世界”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世界”论文篇1:《浅析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世界”》【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湘西世界”【论文摘要】在对沈从文进行深入的阐释与研究中,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重心。
与整个沈从文研究的发展相应,人们对“湘西”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也呈现出一个不断深入与丰富,多元与复杂的状态。
沈从文研究从其创作伊始到21世纪的今天,可谓几经曲折变化。
时至今日,沈从文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日渐成为了一门显学。
沈从文研究呈现出日渐完备成熟,多元丰富,不断推进的良性状态……而在对沈从文进行深入的阐释与研究中,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重心。
具体而言,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认识呈现出几种这样的态势。
建国前,人们多注重肯定其湘西世界所特有的朴质自然、和谐优美的人生情趣与牧歌风味。
同时,也注意到湘西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建国后到新时期,其湘西世界与沈从文整个创作一块归于另类而湮没无闻。
新时期以来,随着沈从文热的悄然而起,人们对“湘西”的认识与理解、阐释与发掘则呈现出多元丰富,不断深入的状态。
首先,是沈从文创作中“湘西”与都市相对而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发现。
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作为国内第一部对沈从文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就将湘西作为与“沉落的都市”而对立存在的“生命多方的乡村世界”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沈从文创作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特点做了整体性的把握,并充分认识到了“湘西”世界构成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他认为,那里不仅“跃动着的原始生命活力”,而且呈现了“与世沉浮的乡村灵魂”;不仅悲悯着“巨压下的性格变异”的苦难,而且也在积极地“向生命的神性凝目”。
同时,凌宇还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与生存视阈中,对湘西世界中所独有的苗族文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发掘与精辟的分析。
“湘西世界”:沈从文笔下的一个现
代神话
【内容提要】
沈从文采取反复叙事的方法,构筑了神话
化的“湘西世界”。
实际上,“湘西世界”是针对现代人审美精神的丧失,人生的散文化,而籍神话的形式,为现代人找寻生存依据的一个审美世界。
沈从文在这个审美的“湘西世界”中,旨在用无功利的“爱”来表达神话世界的纯度,向现代人敞明生存的意义。
【关键词】神话;审美;现代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作者面对纷繁
扰攘的都市,在对故乡的回忆和想象中,建构的一个艺术世界。
这个“湘西世界”宁谧、优美、自然、生气蓬勃,往往被人称颂为一曲田园牧歌、一首乡土抒情诗。
其实,“湘西世界”是一个富含更深厚意义的世界,是沈从文在神之解体的时代为生存失去依持
的现代人找寻的一个现代神话。
一
神我们是看不见的,然而,我们处处都看见神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先、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明智的人的心中,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作品的深处见出它。
[1]我们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见到的“神“,首先显现在《龙朱》、《凤子》、《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一系列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的古老传说的作品中。
在这些小说里,有关湘西的巫术宗教、人物传奇、奇风异俗,无不深深的烙着神话的印迹,赋予了“湘西世界”神话特质,使人感受到湘西民族的高贵神性。
上述奇幻的故事,让我们在显在的层面上见到了“湘西世界”的神性,而在“湘西世界”的深处,还藏匿着一种隐在的神话因子,那就是时间。
时间是神话世界的真正核心。
卡西尔指出:从基本意义上来讲,神话一词体现的不是空间观而是纯粹的时间观。
它表示借以看待世界整体的一个独特的时间“侧面”。
神是由时间构成的,只有借助于时间,神才从无数非人格的自然力量中被选择出来,成为独立
的存在而凌驾于那些力量之上。
同样,时间在沈从文建构的湘西神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所尊奉的神性在时间的延展形成的历史中显现出来。
“湘西世界”是一个静谧、和缓、永恒的世界。
它的时间是近乎停滞的,“湘西世界”的神性也就在这静止的时间中积累和显现。
无时间性的意识正是神话时间的特质,神话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神圣的、神话的时间内,与日常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日常所生活的时间具有不断流逝、刹那生灭、去不复返的特性。
而神话所展现的时间却是循环的、可重复地被实现的。
“湘西世界”就处于这种永恒的神话时间中。
在构成“湘西世界”世界的小说中,时间推进极其缓慢。
沈从文采取反复叙事的手法,让无数相似的事件重叠起来,使“湘西”生活处于恒常状态,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进行下去,仿佛从来没有变化,把“湘西”留在永恒的和毫无疑问的神性中。
如《边城》,整个故事
就是在对端午节的三次反复叙写中展开,每个端午节都是小城四面八方的人齐聚酉水
河边,敲锣打鼓赛龙舟,赛后捉鸭子,每年如此,似乎几百千年来从未变过。
另外,边城男女在有月亮的中秋晚上整夜唱歌,在新年里舞狮子龙灯。
“这些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
”不仅边城的节日给人一种抛开了历史时间而自动循环运转和存在的恒定感,其日常生活似乎也处于一种无限循环之中。
“冬天的白日里……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如一座一座宝塔。
间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做事。
一切总永远那么寂静,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
”无数个冬天已经过去了,可边城中的男女仿佛仍然在那个地方,做着同样的事。
整个“湘西世界”近乎处于静止的时间中,映照着一层高贵、光辉、朴素的氛围。
透过这样的叙述,读者被牵引到一种新的时间里,如同临现在神话中,世俗的、历史的时间暂时地、象征地被废除、隐
没和超越,取而代之的则是神圣的、神话的时光。
这样,作者与读者都借着故事的叙述而被卷入了另一种光阴。
在那个境界里,世俗的、历史的时刻已被隐没和克服了,他们已浸润在一种超越延展性的、永恒的、可一再临现的时间之中。
正是由于突出了时光的主宰地位,时间才在沈从文的湘西作品中显现出结构贯穿的力量,神话的血脉由此在“湘西世界”流淌。
二
神话是人类最初感觉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是人类为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寻得的一种意义,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神话就象用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一样,它总带有娇爱、稚气、散漫的特点,丝毫不带有功利的目的。
因此,神话的世界是一个超功利的、审美的、诗意的世界。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长,随着自然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泛化,人通过神话的感觉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消失了。
正如诺瓦利斯在《断片》中所言,这个世界的意义早已丧失,上帝的精神得以理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人陷入一种空虚之中,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