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文学构思和学术问题
- 格式:doc
- 大小:44.00 KB
- 文档页数: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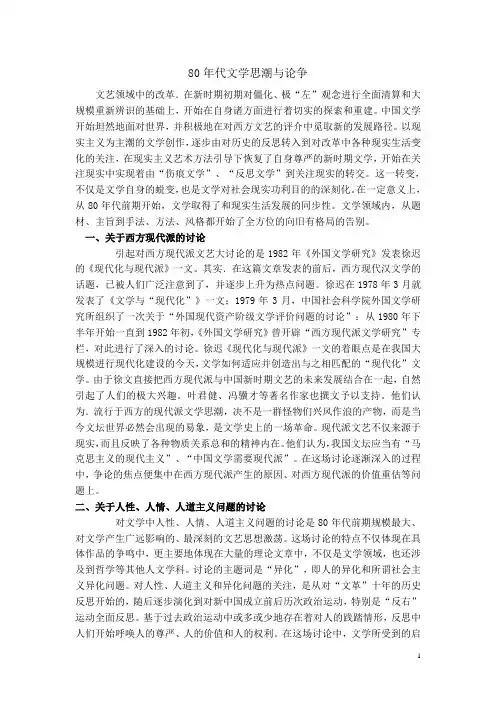
80年代文学思潮与论争文艺领域中的改革.在新时期初期对僵化、极“左”观念进行全面清算和大规模重新辨识的基础上,开始在自身诸方面进行着切实的探索和重建。
中国文学开始坦然地面对世界,并积极地在对西方文艺的评介中觅取新的发展路径。
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创作,逐步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入到对改革中各种现实生活变化的关注,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引导下恢复了自身尊严的新时期文学,开始在关注现实中实现着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关注现实的转交。
这一转变,不仅是文学自身的蜕变,也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功利目的的深刻化。
在一定意义上,从80年代前期开始,文学取得了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
文学领域内,从题材、主旨到手法、方法、风格都开始了全方位的向旧有格局的告别。
一、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讨论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的是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西方现代汉文学的话题,已被人们广泛注意到了,并逐步上升为热点问题。
徐迟在1978年3月就发表了《文学与“现代化”》一文;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关于“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初,《外国文学研究》曾开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专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的着眼点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
由于徐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叶君健、冯骥才等著名作家也撰文予以支持。
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决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文坛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易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现代派文艺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反映了各种物质关系总和的精神内在。
他们认为,我国文坛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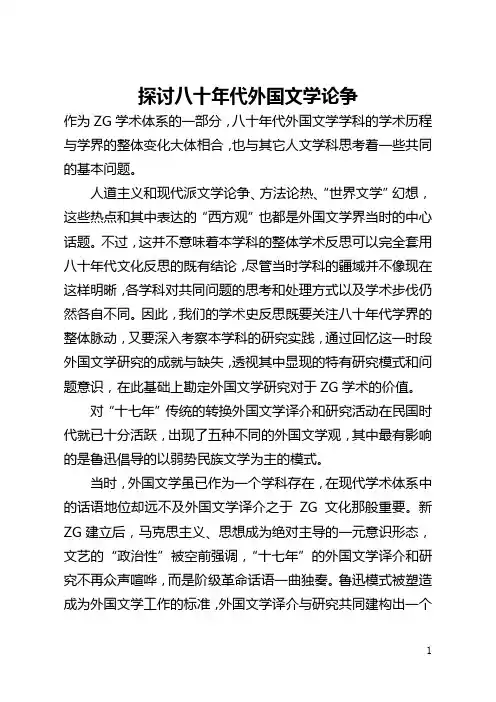
探讨八十年代外国文学论争作为ZG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外国文学学科的学术历程与学界的整体变化大体相合,也与其它人文学科思考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
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文学论争、方法论热、“世界文学”幻想,这些热点和其中表达的“西方观”也都是外国文学界当时的中心话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学科的整体学术反思可以完全套用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既有结论,尽管当时学科的疆域并不像现在这样明晰,各学科对共同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以及学术步伐仍然各自不同。
因此,我们的学术史反思既要关注八十年代学界的整体脉动,又要深入考察本学科的研究实践,通过回忆这一时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透视其中显现的特有研究模式和问题意识,在此基础上勘定外国文学研究对于ZG学术的价值。
对“十七年”传统的转换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活动在民国时代就已十分活跃,出现了五种不同的外国文学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鲁迅倡导的以弱势民族文学为主的模式。
当时,外国文学虽已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话语地位却远不及外国文学译介之于ZG文化那般重要。
新ZG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绝对主导的一元意识形态,文艺的“政治性”被空前强调,“十七年”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不再众声喧哗,而是阶级革命话语一曲独奏。
鲁迅模式被塑造成为外国文学工作的标准,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共同建构出一个颇具ZG特色的外国文学版图,那就是:苏俄文学最受重视、地位最高,亚非拉文学得到空前强调;欧洲古典文学则是批判与汲取相结合;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为糟粕,基本消逝。
此时的学术研究遵循着固定的模式:首先对作家及作品人物进行阶级定性,然后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展开详细分析,再加一点艺术上的评价,最后得出总体结论。
在具体分析中,对归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给予无保留的赞美,那些表现出阶级局限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被一分为二地看待,阶级立场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作品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应该说,以阶级革命话语为基础构建的这一外国文学秩序,是冷战形势下ZG对西方中心话语的有意识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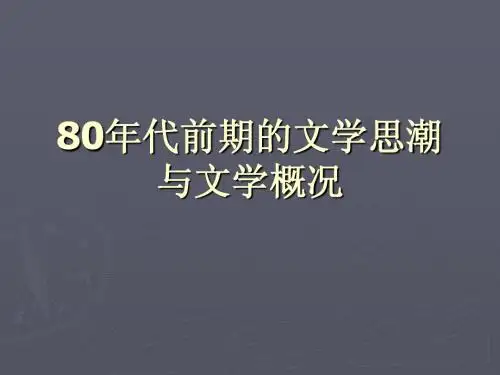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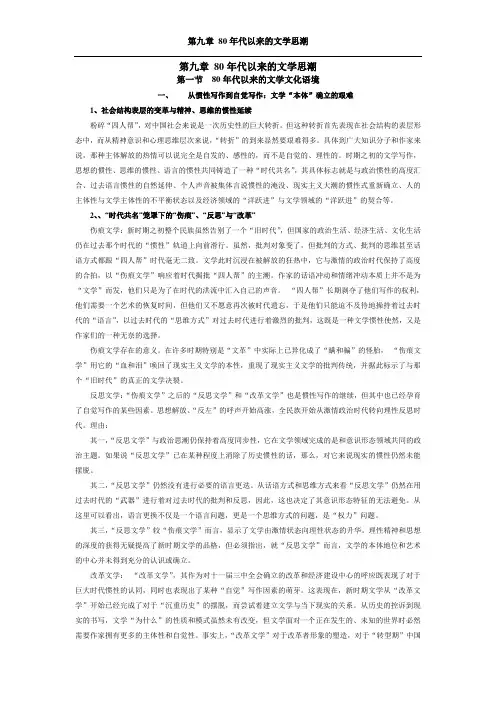
第九章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第一节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文化语境一、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1、社会结构表层的变革与精神、思维的惯性延续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
但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
具体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那种主体解放的热情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觉的、理性的。
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经济领域的“洋跃进”与文学领域的“洋跃进”的契合等。
2、、“时代共名”笼罩下的“伤痕”、“反思”与“改革”伤痕文学:新时期之初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
虽然,批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话语方式都跟“四人帮”时代毫无二致。
文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伤痕文学”响应着时代揭批“四人帮”的主潮。
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
“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伤痕文学存在的意义。
在许多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已异化成了“瞒和骗”的怪胎,“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的文学决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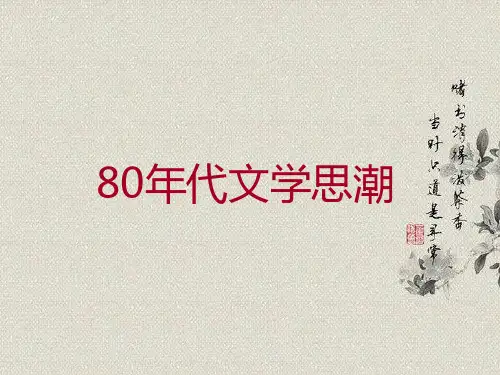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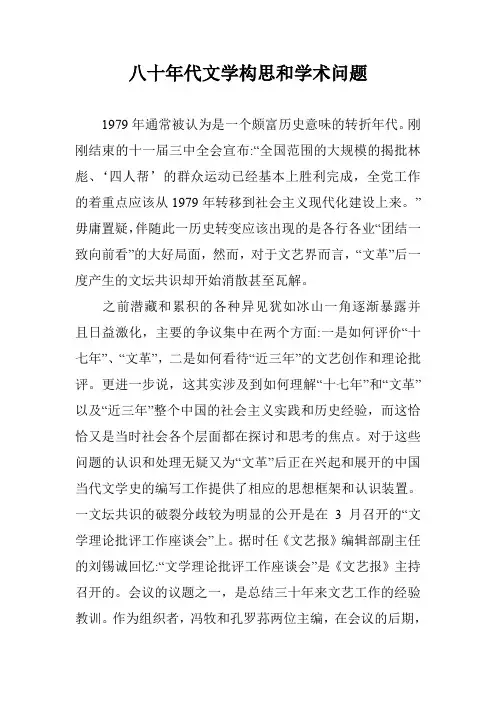
八十年代文学构思和学术问题1979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颇富历史意味的转折年代。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毋庸置疑,伴随此一历史转变应该出现的是各行各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好局面,然而,对于文艺界而言,“文革”后一度产生的文坛共识却开始消散甚至瓦解。
之前潜藏和累积的各种异见犹如冰山一角逐渐暴露并且日益激化,主要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评价“十七年”、“文革”,二是如何看待“近三年”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涉及到如何理解“十七年”和“文革”以及“近三年”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历史经验,而这恰恰又是当时社会各个层面都在探讨和思考的焦点。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无疑又为“文革”后正在兴起和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相应的思想框架和认识装置。
一文坛共识的破裂分歧较为明显的公开是在3月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
据时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刘锡诚回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是《文艺报》主持召开的。
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
作为组织者,冯牧和孔罗荪两位主编,在会议的后期,邀请“文革”前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文革”后仍在文艺界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的陈荒煤、林默涵、周扬三位老领导到会讲话。
他们每人讲了半天。
21日是陈荒煤讲,22日是林默涵讲,23日是周扬讲。
他们讲话之后,代表们进行座谈会讨论。
陈荒煤和周扬的讲话,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争论。
在23日上午的讨论中,代表们对林默涵同志的讲话,主要是对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林默涵同志观点的批评与商讨。
……默涵的讲话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总结三十年的经验问题。
有争议的就是这一部分。
他的讲话说:“(在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中)我们肯定有‘左’的错误,但是这里面也有复杂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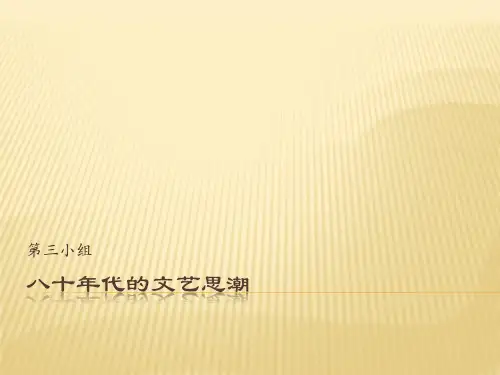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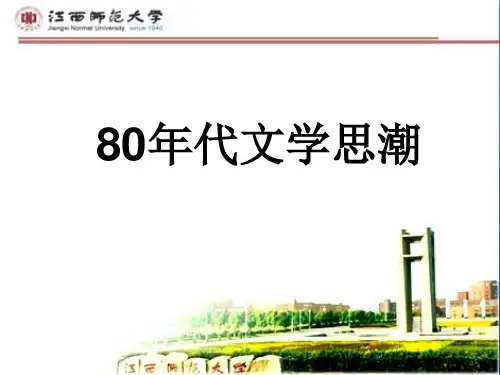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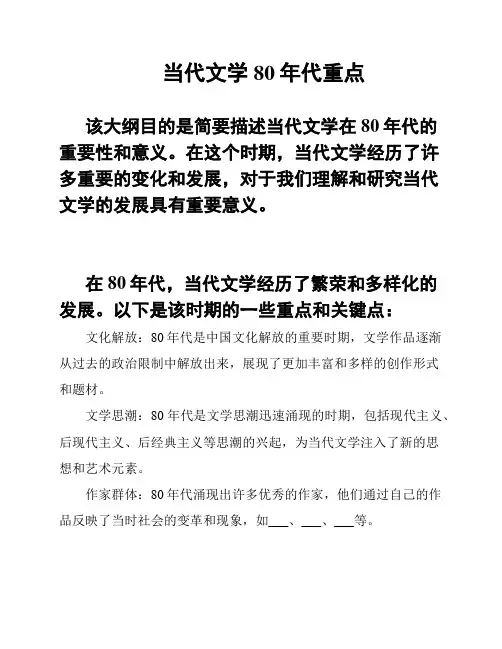
当代文学80年代重点该大纲目的是简要描述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重要性和意义。
在这个时期,当代文学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80年代,当代文学经历了繁荣和多样化的发展。
以下是该时期的一些重点和关键点:文化解放:80年代是中国文化解放的重要时期,文学作品逐渐从过去的政治限制中解放出来,展现了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创作形式和题材。
文学思潮:80年代是文学思潮迅速涌现的时期,包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经典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艺术元素。
作家群体:80年代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现象,如___、___、___等。
重要作品:80年代涌现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如___的《活着》、___的《撒哈拉的故事》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也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批评与评论:80年代也是文学批评和评论蓬勃发展的时期,大量关于当代文学作品的批评和评论问世,为我们理解和解读这些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理论支持。
在总体上看,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它标志着___转向了人文关怀和艺术追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在8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主要流派和代表作家。
以下是其中一些流派和作家,以及他们在当代文学中的影响。
现代主义文学作家:___主要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影响:___以其生动而深刻的描写方式,以及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成为80年代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代表。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___主要作品:《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影响:___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入探讨人类存在的多个层面,引领了80年代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潮流。
现实主义文学作家:___主要作品:《洗澡》、《家》影响:___以其真实而细腻的描写方式,以及对人性和生活细节的关注,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对80年代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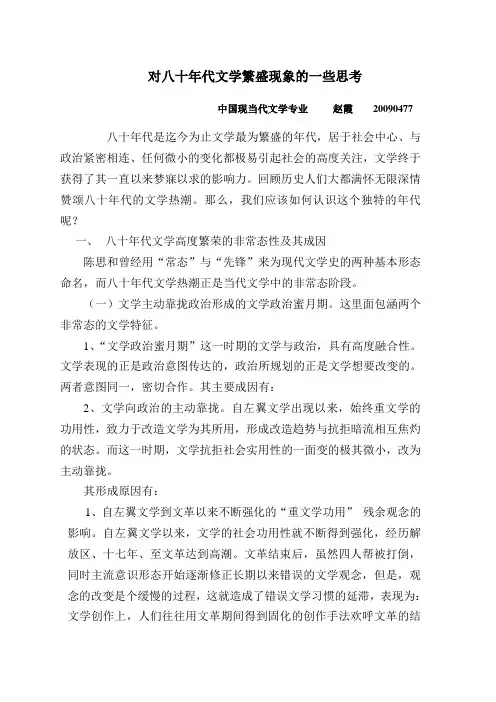
对八十年代文学繁盛现象的一些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赵霞20090477八十年代是迄今为止文学最为繁盛的年代,居于社会中心、与政治紧密相连、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极易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文学终于获得了其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影响力。
回顾历史人们大都满怀无限深情赞颂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独特的年代呢?一、八十年代文学高度繁荣的非常态性及其成因陈思和曾经用“常态”与“先锋”来为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命名,而八十年代文学热潮正是当代文学中的非常态阶段。
(一)文学主动靠拢政治形成的文学政治蜜月期。
这里面包涵两个非常态的文学特征。
1、“文学政治蜜月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政治,具有高度融合性。
文学表现的正是政治意图传达的,政治所规划的正是文学想要改变的。
两者意图同一,密切合作。
其主要成因有:2、文学向政治的主动靠拢。
自左翼文学出现以来,始终重文学的功用性,致力于改造文学为其所用,形成改造趋势与抗拒暗流相互焦灼的状态。
而这一时期,文学抗拒社会实用性的一面变的极其微小,改为主动靠拢。
其形成原因有:1、自左翼文学到文革以来不断强化的“重文学功用”残余观念的影响。
自左翼文学以来,文学的社会功用性就不断得到强化,经历解放区、十七年、至文革达到高潮。
文革结束后,虽然四人帮被打倒,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逐渐修正长期以来错误的文学观念,但是,观念的改变是个缓慢的过程,这就造成了错误文学习惯的延滞,表现为:文学创作上,人们往往用文革期间得到固化的创作手法欢呼文革的结束;文学观念上,则紧贴社会改革的风吹草动加以表现,形成文学创作上强烈的时效性特点。
2、对压抑的反拨。
十七年以来,基于政治对文学创作的不断强制诱导,文学中个体性、抒情性的创作迅速消失。
尤其是十年文革,文学致力于图解国家意识形态要求、阶级论、高大全的理想人物等,将集体无条件的置于个人之上,使所有关心个人表现个人的意图都成为罪恶。
直到文革结束后,长期的压抑引爆了个体表现与倾诉的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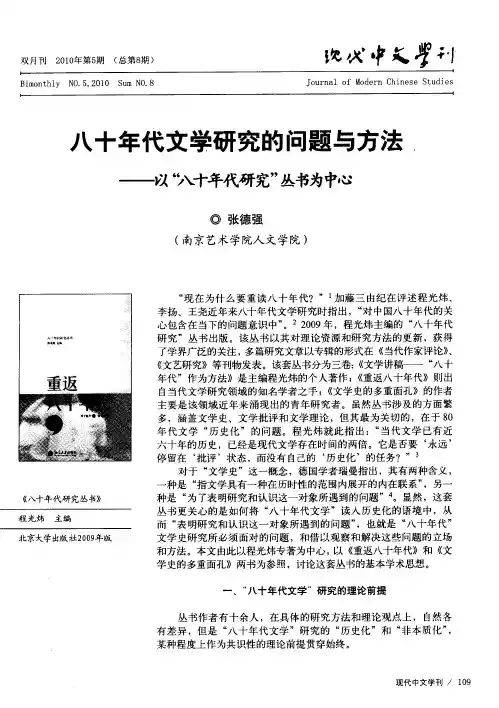
□第三編1978年—1989年第十章八十年代文學思潮一理论思潮的阵歇性波动80年代的文学思潮大致以1985年为界,前期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后期逐渐走向反文化性的文化热。
(一)“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1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辨识和争鸣。
1980年“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明确提出,对新时期文艺复苏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现实主义的争论:围绕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诸方面问题而展开,并通过对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而逐步深入。
(二)80年代前期文学思潮特征1文学取得了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潮。
2文学领域内,从题材、主旨到手法、方法、风格都开始了全方位的向旧有格局的告别。
3自觉地、大规模地把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现代文学、思潮作为革新文艺的主要参照。
4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此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
(三)8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思潮特征:1着眼于新格局的建立。
文学要求回到自身的呼声日渐普遍和高涨,文学在表现时代时如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独特性是作家们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表现在创作与文艺理论观念上。
2文学的本体性备受关注。
“表现生活”已完全代替了“反映生活”,艺术观念发生整体位移,文学创作的“现代性”特征愈加鲜明,文学从观念到创作开始了全方位突破。
影响较大的争鸣:1方法年是指1985年和1986年,又被称为“观念年”。
这两年间,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问题成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
从1984年开始,经过1985年一年的发展,流行于当代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被大规模介绍进来,同时被批评家迅速运用到对新时期文学乃至过去文学的研究实践中。
有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文化分析等,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谓“三论”的引入和运用最为普遍,代表性论文有林兴宅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等。
20世纪80年代文学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普遍的认知是线性而模块化的,即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新历史等文学潮流的更替,构成了线索清晰、逻辑井然的存在。
它仿佛在昭示后人:80年代的文学创作就是按顺序在这些板块之下进行思想演绎与形式探索的。
这种“常识”的获得,一方面来自文学史的强大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其实来自后者)。
所谓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是指批评家倾向于将一时的文学创作纳入某种特定的文学潮流中,致力于用某种“共名”[1]的话题或理论来阐释作品和创作现象。
这种批评使纷繁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某一话语的支持与开发,在凝结成“共同体”的同时,也迅速成为文坛热点,从而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双双拥有了令人迷恋的前沿品格或革新光晕。
文学批评的“潮流化”不仅为80年代文坛建构了一条发展主线,而且也构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一股强大驱力。
与此同时,这种“潮流化”的文学批评也历史性地留下了某些问题。
《回忆与反思:19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摘要:80年代给了我青春,80年代使我重新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我在80年代那样令人怀念的环境中做我的学问,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80年代做的,所以你们会感谢80年代,黄子平、王晓明、张志忠都会感谢80年代,黄子平:为什么问谢老师怕不怕,因为我们当时跟着谢老师读硕士的时候,谢老师一下子开给我们200本必读书目,全部是诗集,里面就包括这些泰斗的诗集,所以我们就很诧异谢冕黄子平王晓明张志忠黄子平:各位晚上好!今天由我来主持,我是主动申请兼座谈的主持的。
我是谢老师四十多年的弟子兼张志忠的师兄,和王晓明也是将近40年的老朋友,因此这个战略地位是最适合我的。
这题目是我和晓明一起讨论出来的。
今晚的分工是这样的,谢老师、我和晓明负责回忆的部分,反思就由张志忠来负责。
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呢?于我来讲,我特别看重情感上的联系,当初我和晓明在沟通这个题目的时候,晓明突然想起来在80年代,我们有过一次的答问。
当时林斤澜先生在当《北京文学》主编的三年里,他着力主办文学批评的专栏,想要建立青年批评家的队伍,由我和一些青年批评家笔谈,我记得只做了三到四个,里面就有王晓明、陈平原等人。
后来我问了晓明,问他有没有保存相关的资料,晓明便拍了照片给我,居然是他的自选集全选,题目是“答黄子平问”。
我读完之后,感触颇深,当年的我们能够谈如此有深度的问题,内容是关于作者已死、作家的心理分析等等。
它让我在情感上产生了某种回应,一种怀旧之感。
有一段时间,怀旧似乎成了不好的词语,“一谈到80年代就在怀旧”,但我始终觉得不太公道,活到这把年纪还不让怀旧。
怀旧当然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上的反应。
为什么光回忆不反思呢?反思是理性的运作,而我现在相当重视情绪上的回应。
趁着今天当业余金牌主持人的机会,想问谢老师当年我不敢问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说起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谈到谢老师的名字一定会和三个崛起联系在一起,三个崛起和朦胧诗有关系,而且三篇文章发表的方式都很不一样,谢老师是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
八十年代文学构思和学术问题1979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颇富历史意味的转折年代。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毋庸置疑,伴随此一历史转变应该出现的是各行各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好局面,然而,对于文艺界而言,“文革”后一度产生的文坛共识却开始消散甚至瓦解。
之前潜藏和累积的各种异见犹如冰山一角逐渐暴露并且日益激化,主要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评价“十七年”、“文革”,二是如何看待“近三年”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涉及到如何理解“十七年”和“文革”以及“近三年”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历史经验,而这恰恰又是当时社会各个层面都在探讨和思考的焦点。
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无疑又为“文革”后正在兴起和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相应的思想框架和认识装置。
一文坛共识的破裂分歧较为明显的公开是在3月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
据时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刘锡诚回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是《文艺报》主持召开的。
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
作为组织者,冯牧和孔罗荪两位主编,在会议的后期,邀请“文革”前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文革”后仍在文艺界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的陈荒煤、林默涵、周扬三位老领导到会讲话。
他们每人讲了半天。
21日是陈荒煤讲,22日是林默涵讲,23日是周扬讲。
他们讲话之后,代表们进行座谈会讨论。
陈荒煤和周扬的讲话,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争论。
在23日上午的讨论中,代表们对林默涵同志的讲话,主要是对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林默涵同志观点的批评与商讨。
……默涵的讲话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总结三十年的经验问题。
有争议的就是这一部分。
他的讲话说:“(在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中)我们肯定有‘左’的错误,但是这里面也有复杂的情况。
我们一方面犯‘左’的错误,一方面又感到有‘左’的问题,多次提出克服‘左’的错误。
”“认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是从十七年的‘左倾’文艺路线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我感到现在还很难论定,因为这和政治路线是分不开的。
”①林默涵对历史的把握之所以遭到质疑必须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去理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的路线已经“明确抛弃‘左’倾主义及其变种”,②由于“重新解释党的历史和学说是导向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论题”,③因而,“十七年”和“文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已经基本被定位为一个“左”的问题,相应地,文艺领域亦呈现出同样的状况。
林默涵模糊的表态给代表们造成的印象却是“十七年文艺工作的错误主要是右”,同时,代表们还尖锐地指出:“否认或者回避我们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左’的缺点、错误和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是不可能很好总结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
”④林默涵与代表们的冲突可以简单归结为如何解释“十七年”文艺的性质,即“十七年”文艺究竟是“左”还是“右”的问题。
而此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于“十七年”文艺的主要焦点集中于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文艺黑线”论的讨论上。
1966年转发全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
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
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的‘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由于《纪要》是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的,事实上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随着‘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台,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遭到错误批判就是被打入冷宫,广大文艺工作者也由此遭到打击迫害,本应百花齐放的文艺界一片凋零”,①因此,“文革”结束之后,文艺界重建合法性的首要突破口就是必须展开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到了这场批判之中。
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坚决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
参加座谈会的首都文艺界人士有:茅盾、刘白羽、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等。
到会人员中,除了李春光是当年的造反派外,其他人,全部是“文革”前文艺界的老同志和名流。
到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和政治镣铐。
它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主导地位,篡改文艺路线斗争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摧残“文化大革命”前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重要理论支柱。
只有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肃清它的流毒,才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②《人民日报》的这次举措迅速促成了整个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批判的积极推进。
同年12月,《人民文学》发起了“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关于‘十七年’文艺的评价,是与会人士发言中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③就此问题发言的包括李曙光、冯牧、李準、吴组缃、韦君宜、秦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尚未恢复职务的周扬和林默涵等“十七年”文艺的主要领导也在会上发表了相关讲话。
其中,周扬的看法是:建国以后,毛主席对文艺非常重视,亲自领导了、过问了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
毛主席对“十七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
周(恩来)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大的关怀。
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十七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江青夸耀的八个样板戏,也是属于“十七年”的,怎么能否定呢?“四人帮”和胡风、右派、苏修等敌人是一致的,否定“十七年”。
他们把“十七年”说成“黑线专政”,目的是反对毛主席、周总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他们的靶子。
“十七年”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有刘少奇路线的干扰破坏,也有我们路线性的错误。
错误由我主要负责,他们打击我是为了反(周)总理。
三年困难时期,我授意写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说文艺服务的对象除工农兵外,还有知识分子,这就错了。
第一次文代会上,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得很高,第二次文代会就不那么高了。
第三次文代会由于反修,又提得高些。
说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我们头脑中扎根不深,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结合得不够好。
其次,在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上,在对待遗产的问题上,也有错误。
毛主席作了两个批示之后,我们真心诚意想解决这些问题,谁不想把工作做好?我们进行了整风,“四人帮”却说是“假整风”。
你可以说整风还不彻底,为什么要说成是假的呢?1956年底到1966年初,我向中央写了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问题,送到政治局通过,准备公开发表,但被“四人帮”压下了。
他们总不会准人家革命,不许检讨,而是要打倒!④如果将周扬此番言论与林默涵在此前后的观点相对照,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对“四人帮”的定性、“十七年”文艺的主要问题还是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二人的结论都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也代表了当时文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①一切都在谨慎的措辞中将反思局限于揭批“四人帮”、否定“文革”的范围之内,这无疑是受制于”凡是派”当权的政治状况。
然而,随着“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②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出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稿,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等人修订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路线,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随着讨论的不断推进,文艺界在维持着表面共识的局面下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分化。
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继续深入到了“文艺黑线”论。
为配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1月20日至25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召开了编委联席会议。
会议主持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提出:“在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必须把构成这个谬论的前提———‘文艺黑线’论彻底批倒,连根拔除,不能有任何迟疑”,③赢得了与会者的共鸣与响应。
从发言记录来看,批判“文艺黑线”本身并没有引来异议,但是稍加留意即可看出在这次会议中林默涵的发言就已经与其它与会者的发言产生了裂隙,关键词落在“文艺黑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八论”上,林默涵认为:“四人帮”用来指责我们的“黑八论”,是他们“文艺黑线”的重要内容。
所谓“黑八论”,是“四人帮”拼凑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们批判过的,而且是把内容加以歪曲了。
“写真实”论。
写真实,我们是没有意见的。
我们所批评的,是认为只有写黑暗面才是真实。
这一点,请看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第三部分。
可是“四人帮”和我们不同,他们是一概不要真实。
“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秦兆阳),我写了文章。
我不同意说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
现实主义是不变的。
“四人帮”发展到不要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深化”论是冯雪峰提出的。
与胡风的理论有共同性。
现实主义要深化,就只有写黑暗面。
二次作协理事扩大会的报告,就没有让雪峰做,而是茅盾做的。
“中间人物”论,是中宣部文艺处批评的。
认为只有写中间人物才有教育意义。
我们认为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还是应该提倡写英雄人物。
我们并不是不要写中间人物,但说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写中间人物,是不对的。
我觉得批评还是对的。
但“四人帮”接过去,根本不能写中间人物。
“反火药味论”,也是我们批评过的。
只是内部讲的。
当时讲的是出口的影片,不要净搞那些战争片。
“真人真事”论,搞得荒唐不堪。
这是起码的常识。
我们认为,真人真事不是不能写,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很多好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写得就很好。
这要看作者掌握的材料。
“四人帮”批“真人真事”论,把大量的群众创作给毁了。
工农兵作者还不能脱出真人真事,不许写真人真事,就是不要群众创作。
“无差别境界”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哲学方面的问题。
《文艺报》也批评过。
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
④陈荒煤、韦君宜、冯牧都迅速地对林默涵的解释作出了回应,陈荒煤是从《文艺报》的功能谈起的:“《文艺报》过去针对文艺界,发表过不少文章和意见,部分是错误的,大部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