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 弗利德曼与《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
- 格式:pdf
- 大小:207.71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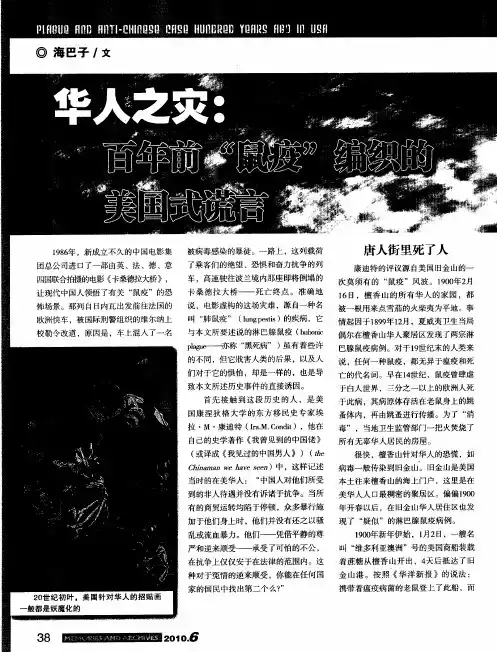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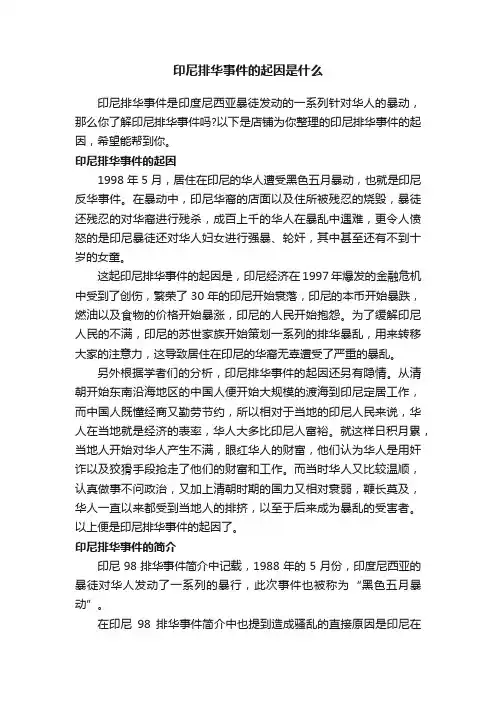
印尼排华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印尼排华事件是印度尼西亚暴徒发动的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那么你了解印尼排华事件吗?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印尼排华事件的起因,希望能帮到你。
印尼排华事件的起因1998年5月,居住在印尼的华人遭受黑色五月暴动,也就是印尼反华事件。
在暴动中,印尼华裔的店面以及住所被残忍的烧毁,暴徒还残忍的对华裔进行残杀,成百上千的华人在暴乱中遇难,更令人愤怒的是印尼暴徒还对华人妇女进行强暴、轮奸,其中甚至还有不到十岁的女童。
这起印尼排华事件的起因是,印尼经济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创伤,繁荣了30年的印尼开始衰落,印尼的本币开始暴跌,燃油以及食物的价格开始暴涨,印尼的人民开始抱怨。
为了缓解印尼人民的不满,印尼的苏世家族开始策划一系列的排华暴乱,用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这导致居住在印尼的华裔无辜遭受了严重的暴乱。
另外根据学者们的分析,印尼排华事件的起因还另有隐情。
从清朝开始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国人便开始大规模的渡海到印尼定居工作,而中国人既懂经商又勤劳节约,所以相对于当地的印尼人民来说,华人在当地就是经济的表率,华人大多比印尼人富裕。
就这样日积月累,当地人开始对华人产生不满,眼红华人的财富,他们认为华人是用奸诈以及狡猾手段抢走了他们的财富和工作。
而当时华人又比较温顺,认真做事不问政治,又加上清朝时期的国力又相对衰弱,鞭长莫及,华人一直以来都受到当地人的排挤,以至于后来成为暴乱的受害者。
以上便是印尼排华事件的起因了。
印尼排华事件的简介印尼98排华事件简介中记载,1988年的5月份,印度尼西亚的暴徒对华人发动了一系列的暴行,此次事件也被称为“黑色五月暴动”。
在印尼98排华事件简介中也提到造成骚乱的直接原因是印尼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们持续了30年的经济繁荣分崩离析,暴跌的本币以及暴涨的物价使得印尼人民埋怨不断。
为了能够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印尼政府的一些内部人员策划了一系列杀害学生以及华人的阴谋,意在挑拨种族矛盾,6名印尼大学生在游行示威活动中遭到枪杀,正式拉开了排华暴乱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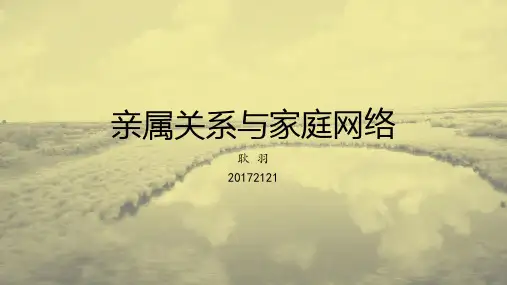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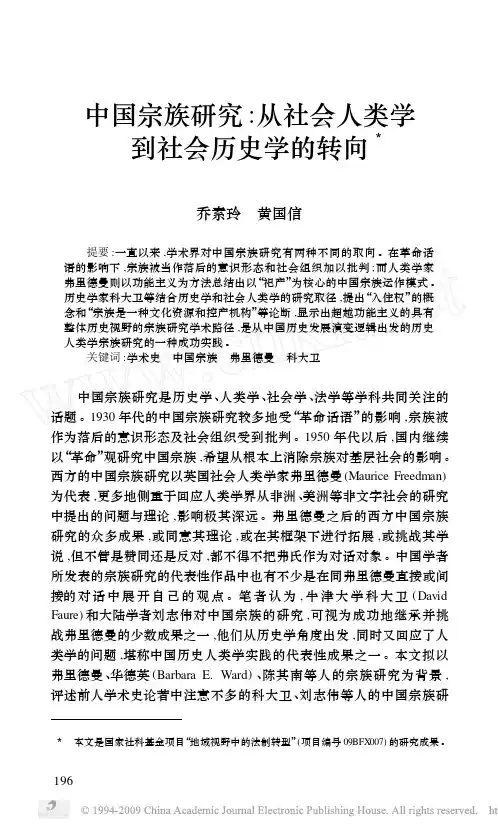
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3乔素玲 黄国信提要: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
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宗族被当作落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加以批判;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则以功能主义为方法总结出以“祀产”为核心的中国宗族运作模式。
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提出“入住权”的概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
关键词:学术史 中国宗族 弗里德曼 科大卫 中国宗族研究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
1930年代的中国宗族研究较多地受“革命话语”的影响,宗族被作为落后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受到批判。
1950年代以后,国内继续以“革命”观研究中国宗族,希望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对基层社会的影响。
西方的中国宗族研究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代表,更多地侧重于回应人类学界从非洲、美洲等非文字社会的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与理论,影响极其深远。
弗里德曼之后的西方中国宗族研究的众多成果,或同意其理论,或在其框架下进行拓展,或挑战其学说,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得不把弗氏作为对话对象。
中国学者所发表的宗族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在同弗里德曼直接或间接的对话中展开自己的观点。
笔者认为,牛津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和大陆学者刘志伟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可视为成功地继承并挑战弗里德曼的少数成果之一,他们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同时又回应了人类学的问题,堪称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本文拟以弗里德曼、华德英(Barbara E.Ward)、陈其南等人的宗族研究为背景,评述前人学术史论著中注意不多的科大卫、刘志伟等人的中国宗族研3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视野中的法制转型”(项目编号09BFX007)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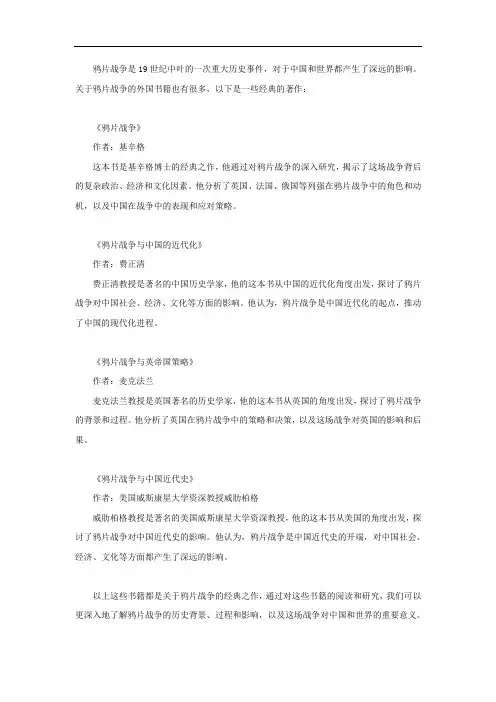
鸦片战争是19世纪中叶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鸦片战争的外国书籍也有很多,以下是一些经典的著作:
《鸦片战争》
作者:基辛格
这本书是基辛格博士的经典之作,他通过对鸦片战争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这场战争背后的复杂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他分析了英国、法国、俄国等列强在鸦片战争中的角色和动机,以及中国在战争中的表现和应对策略。
《鸦片战争与中国的近代化》
作者:费正清
费正清教授是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从中国的近代化角度出发,探讨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他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与英帝国策略》
作者:麦克法兰
麦克法兰教授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从英国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鸦片战争的背景和过程。
他分析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策略和决策,以及这场战争对英国的影响和后果。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
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威肋柏格
威肋柏格教授是著名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他的这本书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他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这些书籍都是关于鸦片战争的经典之作,通过对这些书籍的阅读和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过程和影响,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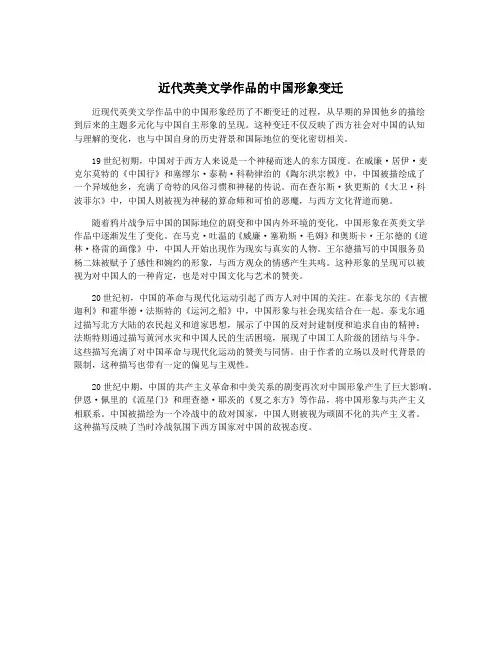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近现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不断变迁的过程,从早期的异国他乡的描绘到后来的主题多元化与中国自主形象的呈现。
这种变迁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的变化,也与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19世纪初期,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神秘而迷人的东方国度。
在威廉·居伊·麦克尔莫特的《中国行》和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的《陶尔洪宗教》中,中国被描绘成了一个异域他乡,充满了奇特的风俗习惯和神秘的传说。
而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中国人则被视为神秘的算命师和可怕的恶魔,与西方文化背道而驰。
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剧变和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马克·吐温的《威廉·塞勒斯·毛姆》和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中国人开始出现作为现实与真实的人物。
王尔德描写的中国服务员杨二妹被赋予了感性和婉约的形象,与西方观众的情感产生共鸣。
这种形象的呈现可以被视为对中国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赞美。
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运动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
在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霍华德·法斯特的《运河之船》中,中国形象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
泰戈尔通过描写北方大陆的农民起义和道家思想,展示了中国的反对封建制度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法斯特则通过描写黄河水灾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困境,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斗争。
这些描写充满了对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运动的赞美与同情。
由于作者的立场以及时代背景的限制,这种描写也带有一定的偏见与主观性。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中美关系的剧变再次对中国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
伊恩·佩里的《流星门》和理查德·耶茨的《夏之东方》等作品,将中国形象与共产主义相联系。

社会学研究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师云蕊莫里斯·弗里德曼是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他的研究主题涉及婚姻、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等诸多领域,其中,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卓越分析使他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声名鹊起,在贯通人类学和汉学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更是令人肃然起敬(Firth,1991:1-2)。
①弗里德曼为中国学界所熟知也是通过其宗族研究。
弗里德曼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Freedman,1958)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Freedman,1966),此外,1971年为纪念露西·美尔(Lucy Mair)所撰写的《从中国宗族看古老异域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n Old State: A View from the Chinese Lineage)(转引自Freedman,1979a),可看作他在学术生涯晚期对中国宗族研究的简要总结。
鉴于中国社会及中国宗族的复杂性,弗里德曼宗族理论的解释力及研究方法一度引发了极大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著作的不断回顾。
总体而言,围绕《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所做的探讨居多,《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则较少受到重视。
《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被弗里德曼本人定位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续篇,结合两本著作,他的宗族范畴才会显现出清晰的纹理。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著作本身对“地方性知识”描述所引发的争议外,更在于它开启了一个“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新时代”。
弗里德曼从未在福建和广东进行过实地调查,他书中的民族志描述多整理、归纳自二手资料及短暂的新界之行,“摇椅上的人类学”在弗里德曼的奥德赛之旅中不可或缺,这种特殊的研究经历使他意识到历史材料对文明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他发现,达不到对社会整① 有关弗里德曼学术生涯及成就的详细介绍,可参见Baker & Feuchtwang, 1991; Firth, 1991;Skinner, 1979, 1991.社会学研究体的把握就无法实现完整宗族模型的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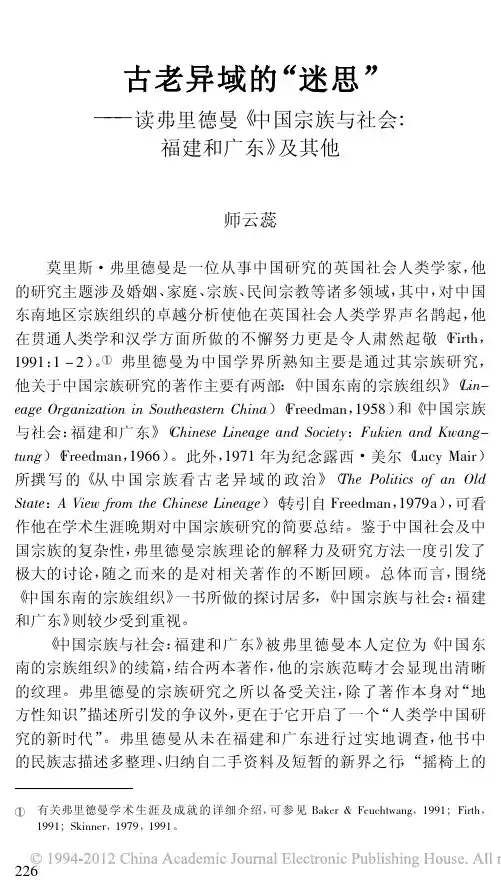
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师云蕊莫里斯·弗里德曼是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他的研究主题涉及婚姻、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等诸多领域,其中,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卓越分析使他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声名鹊起,他在贯通人类学和汉学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更是令人肃然起敬(Firth,1991:1-2)。
①弗里德曼为中国学界所熟知主要是通过其宗族研究,他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Freedman,1958)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Freedman,1966)。
此外,1971年为纪念露西·美尔(Lucy Mair)所撰写的《从中国宗族看古老异域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n Old State:A View from the Chinese Lineage)(转引自Freedman,1979a),可看作他在学术生涯晚期对中国宗族研究的简要总结。
鉴于中国社会及中国宗族的复杂性,弗里德曼宗族理论的解释力及研究方法一度引发了极大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是对相关著作的不断回顾。
总体而言,围绕《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所做的探讨居多,《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则较少受到重视。
《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被弗里德曼本人定位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续篇,结合两本著作,他的宗族范畴才会显现出清晰的纹理。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著作本身对“地方性知识”描述所引发的争议外,更在于它开启了一个“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新时代”。
弗里德曼从未在福建和广东进行过实地调查,他书中的民族志描述多整理、归纳自二手资料及短暂的新界之行,“摇椅上的①有关弗里德曼学术生涯及成就的详细介绍,可参见Baker&Feuchtwang,1991;Firth,1991;Skinner,1979,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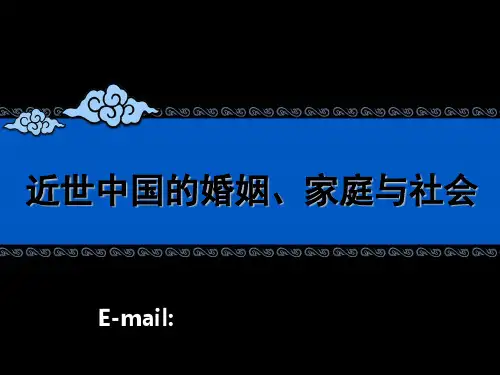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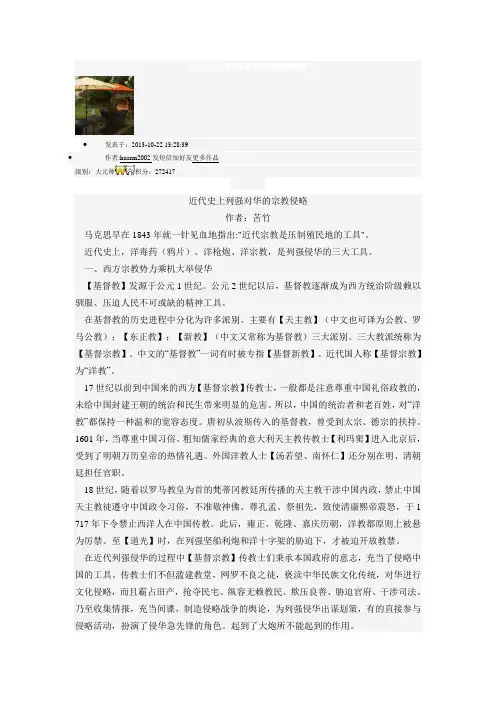
近代史上列强对华的宗教侵略•发表于:2013-10-22 13:28:39•作者:huarm2002发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级别:大元帅积分:272417近代史上列强对华的宗教侵略作者:苦竹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近代史上,洋毒药(鸦片)、洋枪炮、洋宗教,是列强侵华的三大工具。
一、西方宗教势力乘机大举侵华【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
公元2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统治阶级赖以驯服、压迫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工具。
在基督教的历史进程中分化为许多派别。
主要有【天主教】(中文也可译为公教、罗马公教);【东正教】;【新教】(中文又常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
三大教派统称为【基督宗教】。
中文的“基督教”一词有时被专指【基督新教】。
近代国人称【基督宗教】为“洋教”。
17世纪以前到中国来的西方【基督宗教】传教士,一般都是注意尊重中国礼俗政教的,未给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和民生带来明显的危害。
所以,中国的统治者和老百姓,对“洋教”都保持一种温和的宽容态度。
唐初从波斯传入的基督教,曾受到太宗、德宗的扶持。
1601年,当尊重中国习俗、粗知儒家经典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后,受到了明朝万历皇帝的热情礼遇。
外国洋教人士【汤若望、南怀仁】还分别在明、清朝廷担任官职。
18世纪,随着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所传播的天主教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不准敬神佛、尊孔孟、祭祖先,致使清康熙帝震怒,于1 717年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
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历朝,洋教都原则上被悬为厉禁。
至【道光】时,在列强坚船利炮和洋十字架的胁迫下,才被迫开放教禁。
在近代列强侵华的过程中【基督宗教】传教士们秉承本国政府的意志,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
传教士们不但滥建教堂,网罗不良之徒,亵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华进行文化侵略,而且霸占田产,抢夺民宅、纵容无赖教民、欺压良善、胁迫官府、干涉司法。
2023-2024学年岳麓版高中历史单元测试学校 __________ 班级 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 考号 __________注意事项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一、选择题(本大题共计17小题每题3分共计51分)1.1918年夏季孙中山通过美洲华侨向到列宁和苏俄政府发去电报对列宁和苏俄政府表示祝贺 1923年8月又派出“孙逸仙博士访苏代表团”赴苏考察这表明()A. 中苏两国已结成联盟B. 孙中山“以俄为师” 走苏俄道路C. 孙中山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D. 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答案】C【解析】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在会议上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阐释为新三民主义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根据材料时间和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1918至1923年已产生联俄的倾向说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故故C正确中苏两国结成联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排除A孙中山进行的革命一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排除B新三民主义在1924年提出排除D2.中山公园即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公园如表为《民国时期(1925﹣1949年)全国中山公园分布及数量一览表》(单位个)分析下表得出的结论正确的是()①覆盖全国多数省份②南方地区明显多于北方地区③国人对于孙中山的纪念普及面广泛④政府强力筹建的结果A. ①②③B. ①②④C. ①③④D. ②③④【解析】通过材料可以看出中山公园的命名覆盖了全国多数省份①正确通过中山公园的分布可以看出南方的中山公园明显多于北方②正确通过全国各地对中山公园的命名可以看出国人对孙中山的纪念普及面广③正确中山公园的命名是自发行为不是政府筹建的结果排除④3.“改造中国、拯救人民之路到底在何方?”1923年前后在孙中山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时你应该这样地回答他()A. 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联合中共反帝反封建B. 继续承认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利益以寻求其更大更广泛的支持C. 采取更灵活的革命策略争取更多的军阀倒向革命者建立和巩固政权D. 暂时放弃政治革命先发展资本主义壮大资产阶级力量【答案】A【解析】4.1651年为了与荷兰争夺海上霸权克伦威尔颁布了()A. 《大宪章》B. 《航海条例》C. 《权利法案》D. 《独立宣言》【答案】B【解析】1651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排斥荷兰的中转贸易《大宪章》颁布于1215年《权利法案》颁布于1689年《独立宣言》颁布于1776年5.克伦威尔在其施政纲领中说“护国主为终身职务与国会共同掌握立法权与国务会议共同行使行政权……议会的议案必须经过护国主的批准才能生效”这表明克伦威尔()A. 蜕变为封建专制君主B. 主张分散国家权力C. 严格遵守共和国原则D. 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答案】D【解析】从材料中的“护国主……与国会共同掌握立法权与国务会议共同行使行政权”“议会的议案必须经过护国主的批准才能生效”等信息可以看出护国主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这表明克伦威尔已经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故D正确克伦威尔虽然建立的是个人独裁统治但仍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不是封建专制君主故排除A从材料中可以看出护国主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而不是分散国家权力故排除B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克伦威尔实行个人独裁共和国的原则已被破坏故排除C故选D6.20世纪初期亚洲掀起的民族民主运动除中国的辛亥革命外还有()A. 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B. 埃及的华夫脱运动C.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D. 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解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其中有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埃及的华夫脱运动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属于非洲的民族民主运动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则属于美洲故选A项排除BCD.7.英国革命中出现了克伦威尔任护国主的军事独裁统治法国大革命出现了拿破仑称帝这主要是由于()A. 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B. 资产阶级民主发展不充分C. 稳定资本主义统治的需要D. 防止封建王朝复辟的需要【答案】C【解析】依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出现都是为了维护革命成果稳定了资本主义统治故C项正确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体现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故A项正确B项不是主要原因应排除D项明显不符合史实应排除故选C8.孙中山非常推崇洪秀全但他决不满足于做“洪秀全第二” 孙中山相对于洪秀全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A. 顺应近代化的潮流B. 提出反清的方略大计C. 反对满洲贵族统治D. 构建未来社会的蓝图【答案】A【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属于典型的农民战争尽管后段提出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资政新篇》但仍不能改变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运动的本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旨政治方面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同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据此可知A正确BC是二人的共同点故排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太平天国“太平盛世”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故排除D9.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所写的《英语民族的历史》一书中有关克伦威尔时代的章节写于1938~1939年间书中把克伦威尔“或多或少地当成了20世纪的独裁者” 不过丘吉尔后来在书中告诫人们“克伦威尔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的独裁者不是一种类型” 对上述历史叙述的解读中不准确的是()A. 克伦威尔的护国主统治是丘吉尔立论的重要依据B. 历史叙述者所处的时代会影响叙述者的历史评价C. 对历史人物的定性评价应根据现实需要不断更新D. 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把他放到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中【答案】C【解析】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把他放到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中而不是根据现实需要不断更新故C错误符合题意故选C10.17世纪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建立护国主政体 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将邦联制改造成联邦制 19世纪初拿破仑建立法兰西帝国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A. 新旧交替时代“君权神授”观念影响深远B. 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曲折艰难C. 高效的军事体制有利于维护新生政权的统治D. 确立制度与稳定秩序是巩固革命成果的必需【答案】D【解析】依据已学史实可知材料中英国的克伦威尔建立护国主政体美国独立战争后将邦联制改造成联邦制体现了重视制度的建设而法兰西帝国则突出中央集权制国家稳定统治秩序因此D项正确符合题意“君权神授”、“军事体制”题干中没有反映排除AC“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曲折艰难”的表述不符合美国排除B故选D11.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作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杰出代表有着诸多相同之处三人的共同之处有①具有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②建立过民主共和政治体制③制定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④对外实行贸易保护的政策A. ①②B. ②④C. ①③D. ③④【答案】C【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三者都具有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都制定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故①③正确选C 只有华盛顿建立起了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都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治故②不是三者共同点拿破仑推行关税保护与“大陆经济封锁”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故④不是三者共同点排除所有带②④的选项即ABD错误12.据台湾《联合报》(2004年11月13日)报道有83%的台湾民众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这主要基于孙中山()A. 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B. 为维护民主共和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C.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D. 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答案】A【解析】依据题干“中华民国的国父” 结合所学可知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因此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故A项正确BCD三项均不符合题意应排除故选A动,按时间排列正确的是①马斯顿草原大战,赢得“铁骑军”称号②解放“小议会”,被拥立为终身护国主③组建“新模范军”,发动纳西比战役④发布《航海条例》,排斥荷兰中转贸易A. ①③④②B. ③①②④C. ①③②④D. ④①③②【答案】A【解析】根据所学①是1644年②是在1653年③是1645年6月④是1651年故①③④○A正确排除BCD.14.克伦威尔组建的骑兵军获“铁骑军”称号是在()A. 马斯顿荒原战役后B. 纳西比战役后C. 第二次内战后D. “新模范军”组建时【答案】A【解析】结合所学知识克伦威尔组建的骑兵军获“铁骑军”称号是在马斯顿荒原战役后故A正确BCD均不符合题意排除故选A15.《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有这样一段内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下列哪个人物的思想和斗争实践与上述材料内容相符合()A. 甘地B. 孙中山C. 凯末尔D. 华盛顿【答案】A【解析】材料反映的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是甘地的思想故A正确BCD均不符合题意排除16.到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不少人开始回顾起“为他们海外扩展开辟道路”的克伦威尔这主要是由于他()①颁布了《航海条例》②与葡萄牙等国签订商约③抵制法国的“大陆封锁令”④远征爱尔兰和苏格兰A. ③④B. ①③C. ②④D. ①②【解析】依据所学知识可知颁布《航海条例》、与葡萄牙等国签订商约均与海外扩展直接相关故①②正确③④均不符合题意排除17.恩格斯说“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而集权不无道理正在于此每个国家必要力求实现集权每个国家从专制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止都是集权的”下列史实中不能佐证这一观点的是()A. 克伦威尔就任终身护国公B. 华盛顿力辞连任第三届总统C. 拿破仑建立法兰西帝国D. 苏维埃政府将全部企业收归国有【答案】B【解析】材料“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每个国家必要力求实现集权…只要存在着国家每个国家就会有自己的中央”可以得出观点是集权是国家的本质无论何种政体都须集权克伦威尔就任终身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能佐证排除A拿破仑建立法兰西帝国建立独裁统治能佐证排除C苏维埃政府将全部企业收归国有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能佐证排除D华盛顿力辞连任第三届总统是尊重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不能佐证故B合题意二、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计3小题每题15分共计45分)18.(1)依据材料一概括甘地的主张18.(2)据材料一、二指出甘地思想主张与经济主张的矛盾之处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从思想、经济角度指出其矛盾产生的原因18.(3)据材料三指出尼赫鲁的观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理由【答案】(1)主张有文化自由传播民族文化本位思想反对任何形式歧视(如种族、宗教歧视)【解析】(1)根据材料信息“我要各方面的文化都尽其所能地在我屋里传播” “它完全有地方容纳上帝所创造的最微小的东西” 反映了平等的自由的文化传播态度反对不平等的文化宗教现象【答案】(2)矛盾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平等反对歧视在经济上抵制外国货物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原因思想上受到印度教、基督教仁爱、博爱思想的影响倡导平等经济上印度遭到英国经济侵略反对工业文明【解析】(2)第一小问矛盾材料一中思想上主张平等自由反对歧视但在材料二中称西方工业文明却是“魔鬼和怪物” 说明在思想上和经济主张上的矛盾之处第二小问其产生的原因主要从甘地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当时印度殖民地灾难下争取独立的民族愿望出发进行分析【答案】(3)观点甘地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的不足对其评价不公正理由过分强调印度遭受西方殖民侵略以及西方文明的道德沦丧忽视了工业文明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和方向【解析】(3)根据材料“对西方文明作了极其不公正的评价将它不足之处过于夸大了”进行归纳说明对西文明认识上存在不足阐明对工业文明客观的评价态度19.(1)材料一的规定中如何能体现《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19.(2)《资政新篇》的提出有何意义?其未能实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简要说明理由19.(4)指出材料二中“用‘最新的火轮车’”的含义列举孙中山为此作出的努力19.(5)材料三中图一、图二所示历史事件选择的革命道路有何不同?谈谈你对中俄两国选择不同革命道路的认识【答案】(1)体现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解析】(1)材料反映的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他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从理论上要求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农民的要求【答案】(2)意义这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一个改革方案未能实行的主要原因缺乏实行的社会基础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解析】(2)《资政新篇》的提出是先进中国人最早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和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最终没有实施【答案】(3)观点不对理由《天朝田亩制度》是建立在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而《资政新篇》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两者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解析】(3)《资政新篇》不是对《天朝田亩制度》的继承《天朝田亩制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资政新编》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答案】(4)含义实行民主共和努力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进行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解析】(4)材料中孙中山把中国革命比作修建铁路和制造火车最新的火轮车应该是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为此他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维护共和的斗争【答案】(5)不同俄国城市武装起义(或以城市为中心)中国工农武装割据(或农村包围城市)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解析】(5)图片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图片图片二反映的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一个是以城市为中心一个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国情相结合20.(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人历史活动的相似之处20.(2)根据材料二华盛顿政府推行了什么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及其体现的外交原则在一战前后有何变化?【答案】(1)相似之处领导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进行对外扩张与征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视法律和文化教育实行宗教宽容.【解析】(1)根据表格列举的二者的活动事迹可以看出二者都领导和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进行对外扩张与征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视法律和文化教育实行宗教宽容.【答案】(2)政策孤立主义政策.变化一战前及战争初期严守中立 1917年放弃中立政策参加一战战后孤立主义盛行拒绝加入国联.【解析】(2)根据题干材料“禁止美国公民在公海从事任何敌对行动”可以看出美国推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一战前及战争初期严守中立 1917年放弃中立政策参加一战战后孤立主义盛行拒绝加入国联.。
各国著名汉学家见国图网“汉学家资源库”姓名中文译名国籍生卒年月研究领域 Ferdinand 南怀仁,字比利时1623-1688 西学东渐(天文历法、敦伯,又字铸炮等) Verbiest 勋卿Philippe 柏应理比利时 1623-1693 中国经典思想译介 CoupletMichel Boym 卜弥格波兰 1612—1659 中国动植物学、医药学、地图学等 Herbert Franke 福赫伯德国 1914, 中国古代史,重点是宋元史和蒙古史,兼及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和边疆民族史 Johann Adam S汤若望,字德国 1592-1666 西学东渐——天文历chall von Bell 道未算Otto Franke 奥托?福兰德国 1863-1946 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出阁版了巨著《中国通史》。
Richard Wilhel卫礼贤德国 1873—1930 翻译中国古典经籍;研m 究中国传统文化 Wilhelm Grube 顾路柏(又德国 1855-1908 中国文化与文学译顾威廉)Wolfgang Baue鲍吾刚德国 1930.2.23,1中国哲学史、思想史 r 997.1.14 Wolfgang Frank傅吾康德国 1912—明清史;中国近代史;e 近代东南亚华人碑刻史籍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阿列克俄国 1716-1786 汉语ьевичЛеонтие谢?列昂季в 耶维奇?列昂季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瓦西里?巴俄国 1818.2-1900.佛教,中国历史、地理、вич Васильев 甫洛维4 语言、文学奇?瓦西里耶夫(王西里,魏西里夫)Илларион Кал伊拉里俄国 1707-1761 汉语иновичРазсох昂?卡利诺ин (Россохин,维奇?罗索Рассохин) 欣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康斯坦俄国 1821-1883 收藏,天文、气象,农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丁?安德列业、手工业чков 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孙琪庭,孔气,孔琪)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尼基塔?雅俄国 1777.8-1853.汉语、中国边疆民族史вич Бичурин(П科夫列维5 地、中国传统文化ичуринский) 奇?比丘林(法号雅金夫,亚金甫)ПавелИванови巴维尔?伊俄国 1765-1845 满学,汉语чКаменский 万诺维奇?卡缅斯基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巴维尔?斯俄国 1842.8-1913.汉语、中国政治вич Попов(Ма捷巴诺维12о Линь) 奇?波波夫(柏百福,茂陵)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彼得?伊万俄国 1817.9-1878.宗教、汉语、中国边疆Кафароф 诺维奇?卡12 史地法罗夫(法号鲍乃迪,巴拉第)Сергей Михай谢尔盖?米俄国 1851.10-189汉语,中国古代史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哈伊洛维3.7вский 奇?格奥尔基耶夫斯基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鲍利斯?李俄罗斯 1932.9- 中国文学Рифтин 沃维奇?里弗京(李福清)Владимир Сте弗拉基米俄罗斯 1931.5- 俄罗斯汉学史,俄中关панович Мясн尔?斯捷潘系史иков 诺维奇?米亚斯尼科夫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弗拉季斯拉俄罗斯 1927- 中国文学о ович Сороки夫?费德罗н 维奇?索罗金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列夫?尼古俄罗斯 1926.2-2005.中国古典文学,敦煌写ч Меньшиков 拉耶维10 本奇?缅希科夫(孟列夫)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列奥纳俄罗斯 1928.12- 中国古代政治史,儒学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德?谢尔盖в 耶维奇?贝列罗莫夫(嵇辽拉)Михаил Леонт米哈伊俄罗斯 1934.4- 中国哲学、中国政治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尔?列昂季ко 耶维奇?季塔连科Николай Троф尼古拉?特俄罗斯 1912.10-200中国文学имович Федор拉菲莫维0.10енко 奇?费德林Рудольф Всево鲁道夫?弗俄罗斯 1910.3-1998.中国历史лодович Вятки谢沃洛多维9н 奇?维亚特金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谢尔盖?列俄罗斯 1918.9- 中国近代现代史、俄中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奥尼多维关系、苏中关系、日本ий 奇?齐赫文近现代史斯基(齐赫文)Donald Holzma侯思孟法国 1926- 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n 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思想等许多方面,文学方面尤其以中国魏晋南北朝诗与乐府最为突出,同时对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英国文学对中国人民的刻画随着英国文学的发展和影响,中国在英国文学中的刻画也越来越多,在不同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对中国人民的刻画。
英国文学中对中国人民的种族歧视是普遍存在的,英国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和主题都反映出这一点。
例如,John Chinese小说《中国家庭》描绘了一个家庭控制力量强大的父亲与被动接受、不被尊重的孩子之间的关系。
而威廉迪曼斯的小说《乡村教师》则是关于一个文化尊重度很低的乡村家庭的描述。
还有许多关于对中国人民的歧视的文学作品,他们描绘了中国人民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之中面临的无端困境。
另外,英国文学中也体现出很强的调侃和讽刺的态度,对于中国人民的刻画也不例外。
例如,在Bram Stoker的小说《吸血鬼》中,主人公德西利(Dracula)被描绘成一个“中国人”,他屡次侮辱中国人,表露出英国对中国深层的不满。
此外,还有大量的与中国相关的题材,如中国政治事件,中国历史、文化等也都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无疑,在英国文学中,中国人民的刻画越来越全面。
有些作品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更加健康、宽容的,更加积极主动地生活在一个更多元素及多方位文化的国家里,而有些作品则偏向于相对歧视的描述。
但无论如何,在英国文学中,中国人民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体,受到英国文学家们的关注。
此外,英国文学中关于中国人民刻画的作品也有助于英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
它们对英国人民的把握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价值作用,英国文学家们在调查中国及其文化的同时,也为中英相互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英国文学对中国人民的刻画越来越深入,说明英国文学家们在考察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在了解中国,因此,只有通过深入的文学研究,积极投入英国文学中的对中国的刻画,才能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进而促进中英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进步。
《来自华南的明信片》诞生记——“华南明信片”如何飞上
《纽约时报》
展江
【期刊名称】《对外传播》
【年(卷),期】2008(000)010
【摘要】《纽约时报》2008年8月31日刊登了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来自华南的明信片》,有人戏言,这是在给广东免费做广告。
这段中国对外传播的佳话源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一本闻名全球的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隐曼的“神交”,早在他任重庆市委领导期间就十分赞同《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表述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观念,并号召当地官员阅读此书,他还邀请弗里德曼到重庆做客,
【总页数】2页(P53-54)
【作者】展江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系主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721.2
【相关文献】
1.手绘明信片中的晚清社会读《远去的大清帝国——解读清代手绘明信片》 [J], 邓北野
2.新中国第一套市内互寄免资明信片诞生记 [J], 冯永祥
3.“奥运版彩信明信片”限量发行活动正式启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市邮政公司全力推出“彩信明信片”新业务 [J],
4.浅析"互联网+"思维下的明信片新形态——电子明信片 [J], 马尚
5.来自华南的明信片 [J],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莫里斯·弗利德曼与《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钱 杭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by Maurice Freedman THE ATHLONE PRE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58一有关莫里斯·弗利德曼的生平、履历、业绩和他的学问背景,笔者已在《莫里斯·弗利德曼与〈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史林》1999年第3期)一文中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出版于1958年的《东南部中国的中国组织》(以下简称《东南》)一书,是莫里斯·弗利德曼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以一种整体构想的形式来重新理解旧中国社会的初次尝试;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与社会》(以下简称《中国宗族》),则是遵循着《东南》一书所提出的框架,在实践中对新出现的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两书在结构上密切关连,相辅相成。
如果勉为区分的话,《东南》一书通过系统整理作者所定义的“中国学的人类学”(Sinological Anthropology)的学术史,率先在以中国宗族为对象的研究中推出了“世系群”(lineage)分析模型的构想,奠定了以社会人类学为理论指针的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基础;而《中国宗族》一书则是通过分析1958年以来新收集的实例,实践并完善了这一分析模型。
笔者是先读1966年的《中国宗族》,再读1958年的《东南》;读毕发现,这个阅读顺序完全应该倒过来。
这不仅因为两书的写作顺序本来如此,后书构成了前书的基础,而且因为《东南》一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已被《中国宗族》所忽略,或曰超越。
而恰恰是这些问题,可以带给研究者许多新的启发。
本文就是对这些“新启发”的断想。
二宗族与“世系群”(lineage)从一开始,弗利德曼就用“世系群”一词来对译中国的“宗族”;但同时,弗利德曼又从来没有认为世系群就是宗族。
这似乎不符合逻辑。
然而这正是弗利德曼在理论上的精确和高明之处。
他知道,世系群是一个来源于非洲研究的社会人类学的分析概念,它主要是指这样一种亲族集团:以共同的祖先为中介,成员之间能够明确寻找到单系的系谱关系———父系或母系。
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实行外婚制的,拥有共同财产和独自的运营组织的团体。
其内部也根据同样的原理形成分支。
现代社会人类学著作对单系集团又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即分为能具体、清晰地寻找到系谱关系的世系群(实体性组织),和在这之上的、系谱关系模糊的、互相的联结仅仅依靠关于祖先的神话性传承的clan(虚拟性组织)。
总之,世系群是单系亲族组织,但这单系组织的性质却并不确定,可以是父系,也可以是母系;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虚拟;而中国的宗族毫无疑问肯定是父系实体性组织,这就使宗族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才能被称为世系群之一种。
弗利德曼在需要精确的时候,比如在第四章《男系单位的层次》(The Hierarchy of Agnatic Units)中,对“宗族”直接使用汉语拼音tsung-tsu,就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深沉。
弗利德曼对这两个术语的处理方式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已故社会人类学家王崧兴认为,“宗族”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个民俗语汇,而“世系群”则是来自英语的人类学术语,将两者直接对应显然不妥,原因是:由于民俗语汇没有如专门用语那样的严格定义,因此容易引起各种问题。
以lineage为例。
中文译文为“世系群”,但也常用民俗语汇译为“宗族”。
然而中国社会中的“宗族”未必与人类学术语lineage的定义完全一致,把宗族作为专门用语显然会发生很多困惑。
(王崧兴:《关于人类学语汇的对译问题》,《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末成道男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
附录五《人类学语汇英、中、日文对照表》序。
)王崧兴发生“困惑”感觉是对的,但“困惑”之发生并非因为宗族这一“民俗语汇”没有“严格定义”;恰恰相反,宗族自古有严格定义,详见《尔雅·释亲》“宗族”章、班固《白虎通德论》卷八“宗族”章。
宗族与世系群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原则。
两者的联接必须依靠理论说明作为中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不知是不是有意地想避开这类“困惑”,有些学者尝试着走了一步偏棋。
如日本学者田中真砂子在研究“单系世系群”时,就曾经把lineage改译为“系族”。
原文是:基于与一个始祖或一组始祖(一般情况下采取“始祖—配偶”联接的形式)之间共同的系谱关系而形成的、被人们自觉认识到的亲族集团,称为继嗣集团(descent group)。
在社会人类学著作中,虽然分别将其中可以明确寻找到与特定始祖关系的集团,称为“系族”(lineage),而将无法加以确定的集团,称为“氏族”(clan),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将两者清晰地区分常常难以做到。
在同时存在氏族和系族的社会中,系族往往是氏族的一个分支;但是还有仅存在氏族的社会和仅存在系族的社会,甚至还有两者都不存在的社会。
《事典·家族》,比较家族史学会编,弘文堂,1996年1月。
又参见日文版D.米切尔《新社会学辞典》,页68,lineage条。
下田直春监译,新泉社,1987年。
这一译法至今尚未在国际人类学界获得认真回应。
笔者以为,既然lineage 是对实行单系世系原则的亲族组织的一种描述方法,那么将此术语所泛指的亲族团体称之为“系族”,也未尝不可,至少可以避免弗利德曼以来人们已经感觉到的问题,不与作为中国“民俗语汇”的“宗族”的原意相混淆。
当然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宗族与世系群在对译上出现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只有Chinese lineage(即“中国世系群”)一词,直译为“宗族”才较为恰当。
80年代以后,国际人类学界对世系群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和批评。
有些批评相当著名,常常被人们引用。
如J.Goody在其编著的《东洋的、古代的、原始的:欧亚大陆前近代社会中各种婚姻和家族制度》(The Oriental, the Ancient and the Primitive: Systems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of Eurrasia, 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一书中警告说,lineag概念具有狭窄僵硬的普遍弊病;被它所忽略的重要问题中,有亲族、婚姻和人口学动态之间的关系,对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联也没有加以彻底的探索。
此外,对居于世系群之下的层次,如以“家”为中心的生产和再生产集团、财产和习惯、家户、家族、农商工经营联合体、居住集团等等问题注意不够,对地域和地区的偏差也有忽略的倾向。
Goody指出,一般来说,莫里斯·弗利德曼的分析模型没有表现出他具有很深的文化偏见,但由于他对东南亚华侨中亲族关系的强大程度,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因此就偏向于从世系群的观点来解释一切。
这一批评似乎有些不着边际。
“世系群”是社会人类学众多分析概念中的一个,其有用性的基础,建立在它所严格划定的学术范围上。
若要超出它的规定,研究“它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尽管研究就是了,与它的“狭窄僵硬”何干?弗利德曼对世系群理论的把握无疑是有缺陷的,但缺陷不是他涉及的研究领域不够宽,而恰恰是他没有更为集中地研究世系群最本质的“世系”问题,反而过多地关心世系群外在的功能问题。
从类似的批评看来,弗利德曼的许多批评者本身也未必对世系群与宗族的区别有比弗利德曼更清醒的认识。
在弗利德曼之后,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各类世系集团作出不同的区分,即⑴注重共有族产的广东“股份公司”(corporation)型世系群;⑵其族产仅限于仪礼目的的长江流域的中等规模集团;⑶华北地区程度较低的公司型继嗣集团,等等。
弗利德曼的好友 A.Wolf则将世系群组织区分出三种类型,⑴拥有族产的corporation型世系群;⑵只具备祠堂、祖坟的世系群;⑶虽然编纂了族谱,但没有显示出公司类型的世系群。
(A.P.Wolf, The Origins and Explanation of Variation in the Chinese Kinship System. MS. 1985)诸如此类的细致划分,当然有实证的支持,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来,也不过是世系群功能主义研究策略的进一步发挥;既没有弥补弗利德曼的缺陷,也没有把宗族与世系群的关系整理得更加清楚一些。
三族谱是宗族的“宪章”(charters)这是弗利德曼在第一章《福建、广东地区的村落及世系群》(Village andLineage in Fukien and Kwangtung)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原文是:族谱对世系群的发展和结构具有影响,并成为世系群的宪章。
(Genealogi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lineages for which they constituted the charters.) 这种“宪章”性质,主要表现在族谱与宗族之间的具体关系上。
弗利德曼在第八章《世系群内部的权力分配》(The Differen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Lineage)中,分析了以下三个层次。
一,族谱明确了世系群成员的范围。
每隔一至二代,就将积累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的材料加入已有的内容之中。
当然,这里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宗族规定,在把出生情况加入新修订的族谱时,需要征收一定数量的费用,这就使得世系群成员资料的完整性受到外在的经济条件的制约。
二,族谱记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族的现实要求。
弗利德曼以中国学者胡先晋研究江西谭姓宗族的成果说明,由于宗族内各分支的不均衡发展,导致出现人数和财力方面实力不等的分支;一旦发生这种结果,宗族管理者就会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在世系群内部进行重新编组。
比如由于谭姓宗族在成员数量和财富方面出现了不均衡的发展,于是,就先将一个超过所有分支规模的最大分支(房)分解成五份,随后再将其余各房合并为两个部分。
通过引进防止一房独大、一房垄断的新制度,使全族各分支的力量获得了新的均衡。
谭姓宗族的族谱忠实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使之成为一个体现了宗族规范的范例,供谭姓后人参照。
在《中国宗族》一书的第四章《世系群间的关系》(Relations brtween Lineages)中,弗利德曼重申了这个观点:“大规模的族谱是作为潜在的世系集团的一部宪章,因此它向我们揭示了这一集团结构上的重要关系。
”三,族谱本身也有一套独立的规则,有时表现得相当程式化,弗利德曼将这一特征称为“编纂族谱的方式缺乏可塑性”。
这就使得族谱往往滞后于宗族内部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