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共61页
- 格式:ppt
- 大小:8.07 MB
- 文档页数: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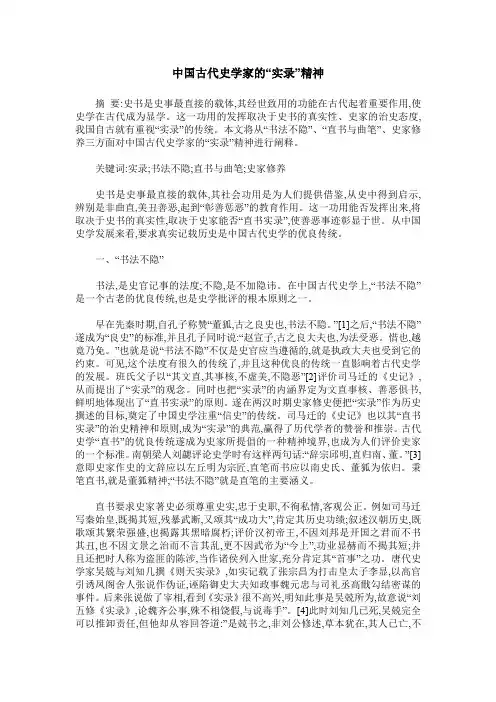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摘要: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在古代起着重要作用,使史学在古代成为显学。
这一功用的发挥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史家的治史态度,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实录”的传统。
本文将从“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进行阐释。
关键词:实录;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社会功用是为人们提供借鉴,从史中得到启示,辨别是非曲直,美丑善恶,起到“彰善惩恶”的教育作用。
这一功用能否发挥出来,将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取决于史家能否“直书实录”,使善恶事迹彰显于世。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要求真实记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书法不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是不加隐讳。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不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自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1]之后,“书法不隐”遂成为“良史”的标准,并且孔子同时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竟乃免。
”也就是说“书法不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
可见,这个法度有很久的传统了,并且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
班氏父子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从而提出了“实录”的观念。
同时也把“实录”的内涵界定为文直事核、善恶俱书,鲜明地体现出了“直书实录”的原则。
遂在两汉时期史家修史便把“实录”作为历史撰述的目标,奠定了中国史学注重“信史”的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也以其“直书实录”的治史精神和原则,成为“实录”的典范,赢得了历代学者的赞誉和推崇。
古代史学“直书”的优良传统遂成为史家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成为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
南朝梁人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3]意即史家作史的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应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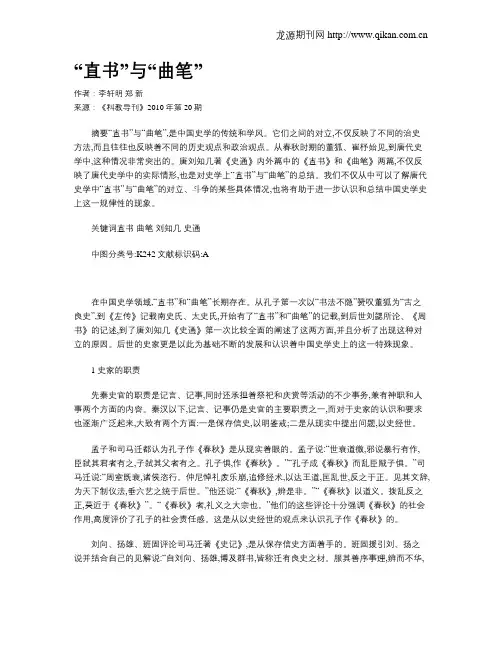
“直书”与“曲笔”作者:李轩明郑新来源:《科教导刊》2010年第20期摘要“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学风。
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
从春秋时期的董狐、崔杼始见,到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非常突出的。
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篇中的《直书》和《曲笔》两篇,不仅反映了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形,也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
我们不仅从中可以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关键词直书曲笔刘知几史通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在中国史学领域,“直书”和“曲笔”长期存在。
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后世刘勰所论、《周书》的记述,到了唐刘知几《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
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1 史家的职责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
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对于史家的认识和要求也逐渐广泛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
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
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
”他还说:“《春秋》,辨是非。
”“《春秋》以道义。
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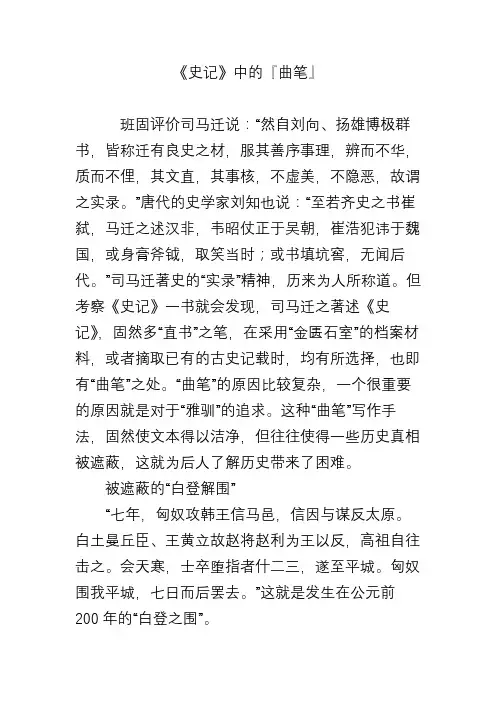
《史记》中的『曲笔』班固评价司马迁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唐代的史学家刘知也说:“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司马迁著史的“实录”精神,历来为人所称道。
但考察《史记》一书就会发现,司马迁之著述《史记》,固然多“直书”之笔,在采用“金匮石室”的档案材料,或者摘取已有的古史记载时,均有所选择,也即有“曲笔”之处。
“曲笔”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雅驯”的追求。
这种“曲笔”写作手法,固然使文本得以洁净,但往往使得一些历史真相被遮蔽,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带来了困难。
被遮蔽的“白登解围”“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
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
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
”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
这年冬天,刘邦率领的32万汉军被匈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一连七天七夜,这是汉代外交史上的一次巨大挫折,世称“平城之辱”。
关于这次解围,《史记》中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为: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
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
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
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司马迁认为“其计秘,世莫得闻”,所以说不清。
另一种解释为: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
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
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
”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
在这里,司马迁给出的解释是“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这就和历史上的“鸡鸣狗盗”有异曲同工之妙:“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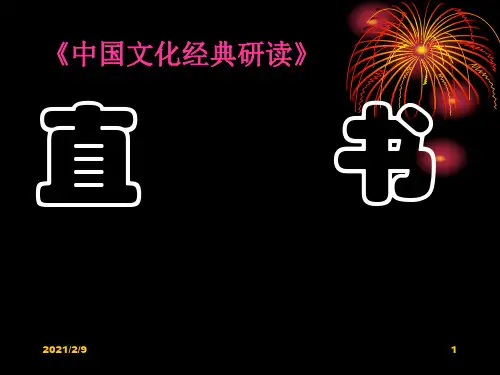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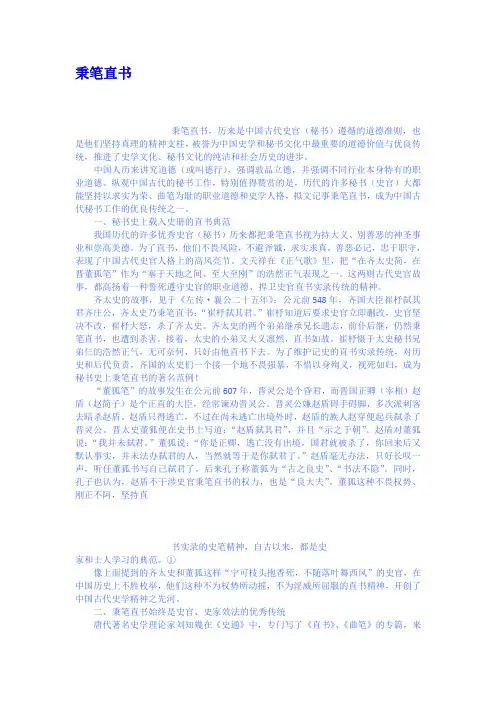
秉笔直书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
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一、秘书史上载入史册的直书典范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
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
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
”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
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
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
崔杼慑于太史秘书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
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著名范例!“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
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
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
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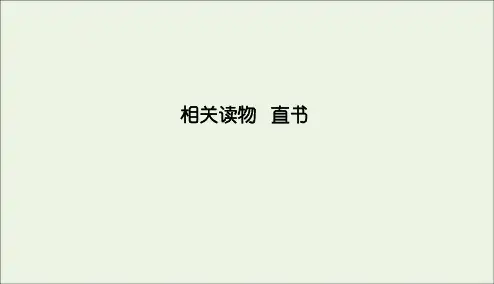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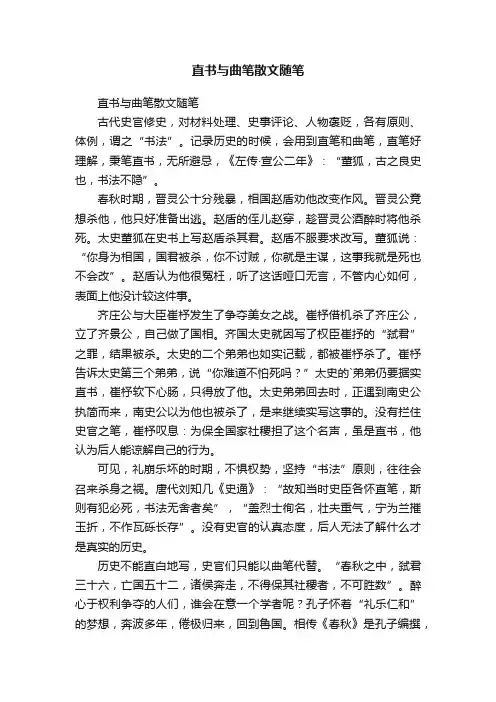
直书与曲笔散文随笔直书与曲笔散文随笔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原则、体例,谓之“书法”。
记录历史的时候,会用到直笔和曲笔,直笔好理解,秉笔直书,无所避忌,《左传·宣公二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劝他改变作风。
晋灵公竟想杀他,他只好准备出逃。
赵盾的侄儿赵穿,趁晋灵公酒醉时将他杀死。
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杀其君。
赵盾不服要求改写。
董狐说:“你身为相国,国君被杀,你不讨贼,你就是主谋,这事我就是死也不会改”。
赵盾认为他很冤枉,听了这话哑口无言,不管内心如何,表面上他没计较这件事。
齐庄公与大臣崔杼发生了争夺美女之战。
崔杼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
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被杀。
太史的二个弟弟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说“你难道不怕死吗?”太史的`弟弟仍要据实直书,崔杼软下心肠,只得放了他。
太史弟弟回去时,正遇到南史公执简而来,南史公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没有拦住史官之笔,崔杼叹息:为保全国家社稷担了这个名声,虽是直书,他认为后人能谅解自己的行为。
可见,礼崩乐坏的时期,不惧权势,坚持“书法”原则,往往会召来杀身之祸。
唐代刘知几《史通》:“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没有史官的认真态度,后人无法了解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
历史不能直白地写,史官们只能以曲笔代替。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醉心于权利争夺的人们,谁会在意一个学者呢?孔子怀着“礼乐仁和”的梦想,奔波多年,倦极归来,回到鲁国。
相传《春秋》是孔子编撰,春秋笔法,也称春秋书法,是他的首创,现多称文章用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委婉的表达倾向,也指一字置褒贬,简练而含蓄地点评人事,亦称“微言大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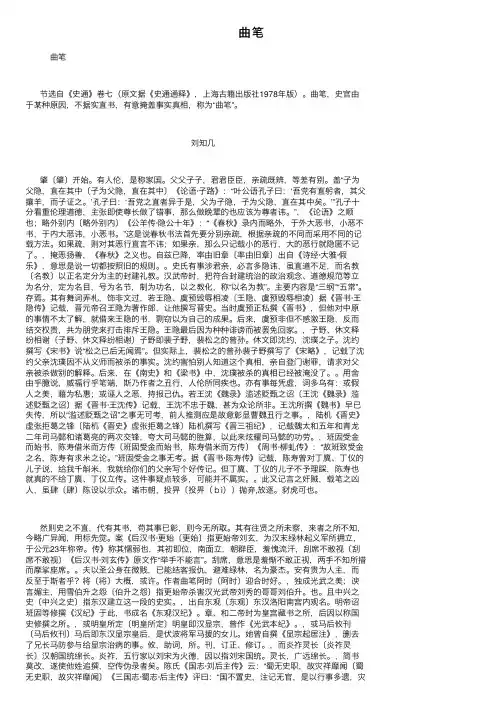
曲笔 曲笔节选⾃《史通》卷七(原⽂据《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曲笔,史官由于某种原因,不据实直书,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称为“曲笔”。
刘知⼏肇〔肇〕开始。
有⼈伦,是称家国。
⽗⽗⼦⼦,君君⾂⾂,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为⽗隐,直在其中〔⼦为⽗隐,直在其中〕《论语·⼦路》:“叶公语孔⼦⽈:‘吾党有直躬者,其⽗攘⽺,⽽⼦证之。
’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为⼦隐,⼦为⽗隐,直在其中矣。
’”孔⼦⼗分看重伦理道德,主张即使尊长做了错事,那么做晚辈的也应该为尊者讳。
”,《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略外别内〕《公⽺传·隐公⼗年》:“《春秋》录内⽽略外,于外⼤恶书,⼩恶不书,于内⼤恶讳,⼩恶书。
”这是说春秋书法⾸先要分别亲疏,根据亲疏的不同⽽采⽤不同的记载⽅法。
如果疏,则对其恶⾏直⾔不讳;如果亲,那么只记载⼩的恶⾏,⼤的恶⾏就隐匿不记了。
,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兹已降,率由旧章〔率由旧章〕出⾃《诗经·⼤雅·假乐》,意思是说⼀切都按照旧的规则。
史⽒有事涉君亲,必⾔多隐讳,虽直道不⾜,⽽名教〔名教〕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为名分,定为名⽬,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教化,称“以名为教”。
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
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王隐、虞预毁辱相凌〕据《晋书·王隐传》记载,晋元帝召王隐为著作郎,让他撰写晋史。
当时虞预正私撰《晋书》,但他对中原的事情不太了解,就借来王隐的书,剽窃以为⾃⼰的成果。
后来,虞预⾮但不感激王隐,反⽽结交权贵,共为朋党来打击排斥王隐。
王隐最后因为种种诽谤⽽被罢免回家。
,⼦野、休⽂释纷相谢〔⼦野、休⽂释纷相谢〕⼦野即裴⼦野,裴松之的曾孙。
休⽂即沈约,沈璞之⼦。
沈约撰写《宋书》说“松之已后⽆闻焉”。
但实际上,裴松之的曾孙裴⼦野撰写了《宋略》,记载了沈约⽗亲沈璞因不从义师⽽被杀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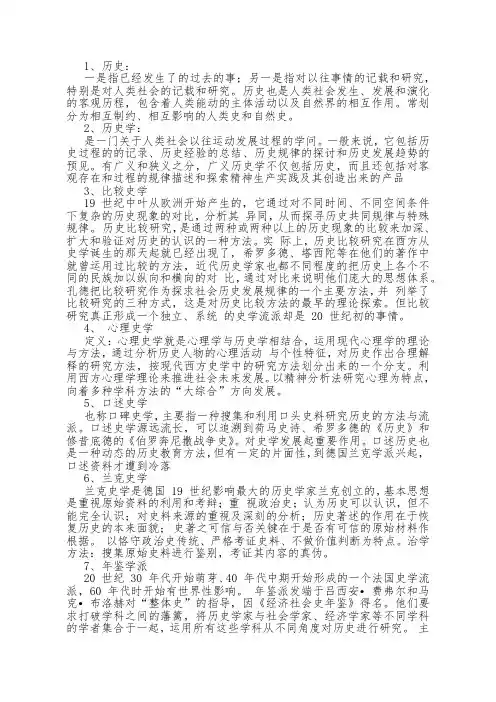
1、历史:一是指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另一是指对以往事情的记载和研究,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的记载和研究。
历史也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客观历程,包含着人类能动的主体活动以及自然界的相互作用。
常划分为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人类史和自然史。
2、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一般来说,它包括历史过程的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不仅包括历史,而且还包括对客观存在和过程的规律描述和探索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3、比较史学19 世纪中叶从欧洲开始产生的,它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对比,分析其异同,从而探寻历史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
历史比较研究,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历史比较研究在酉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近代历史学家也都不同程度的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
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
但比较研究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 20 世纪初的事情。
4、心理史学定义:心理史学就是心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与个性特征,对历史作出合理解释的研究方法,按现代西方史学中的研究方法划分出来的一个分支。
利用西方心理学理论来推进社会未来发展。
以精神分析法研究心理为特点,向着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方向发展。
5、口述史学也称口碑史学,主要指一种搜集和利用口头史料研究历史的方法与流派。
口述史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对史学发展起重要作用。
口述历史也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教育方法,但有一定的片面性,到德国兰克学派兴起,口述资料才遭到冷落6、兰克史学兰克史学是德国 19 世纪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兰克创立的,基本思想是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辩;重视政治史;认为历史可以认识,但不能完全认识;对史料来源的重视及深刻的分析;历史著述的作用在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史著之可信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材料作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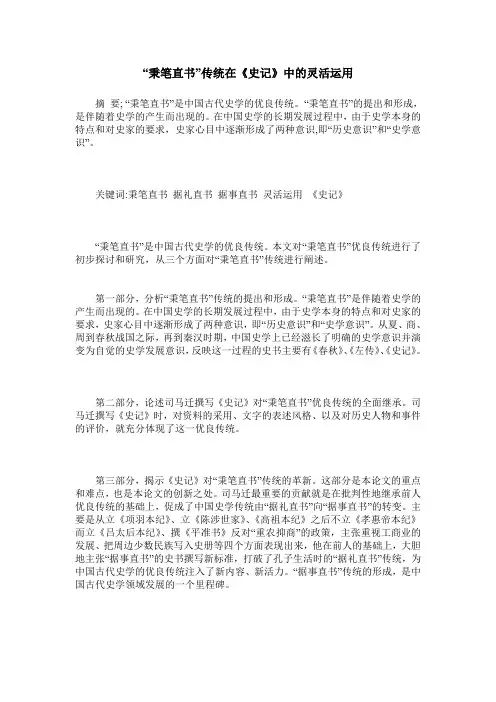
“秉笔直书”传统在《史记》中的灵活运用摘要;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秉笔直书”的提出和形成,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出现的。
在中国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求,史家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
关键词:秉笔直书据礼直书据事直书灵活运用《史记》“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本文对“秉笔直书”优良传统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从三个方面对“秉笔直书”传统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分析“秉笔直书”传统的提出和形成。
“秉笔直书”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出现的。
在中国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史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史家的要求,史家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识,即“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之际,再到秦汉时期,中国史学上已经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反映这一过程的史书主要有《春秋》、《左传》、《史记》。
第二部分,论述司马迁撰写《史记》对“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全面继承。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对资料的采用、文字的表述风格、以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就充分体现了这一优良传统。
第三部分,揭示《史记》对“秉笔直书”传统的革新。
这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司马迁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促成了中国史学传统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转变。
主要是从立《项羽本纪》、立《陈涉世家》、《高祖本纪》之后不立《孝惠帝本纪》而立《吕太后本纪》、撰《平准书》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把周边少数民族写入史册等四个方面表现出来,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地主张“据事直书”的史书撰写新标准,打破了孔子生活时的“据礼直书”传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注入了新内容、新活力。
“据事直书”传统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章“秉笔直书”的提出“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他的提出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教学参考0831 1347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一)直书与曲笔:一体两翼的关系及其在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从远古的口述史学、古代的叙事史学,到近代的分析史学,再到现代的系统史学的演进过程。
古代史学是一种叙事史学,对于理论的分析和综合并不擅长,其最基本工作便是“修史”,表现为历史记述的连贯性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
从黄帝到宣统的历史,均记录在册,历代相续,源流清晰;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典章制度体到纪事本末体,均为叙事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叙事史学既以记述为其特征,那么时代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记事的真实性;同时,古代史学的主题取向于政治,造成记事的求真性与政治的实用性的相遇、相克和相成,使“直书—曲笔”问题显露出来,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史学的核心和时代的焦点。
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
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指出:“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
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柳宗元对直书的解释是史官“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
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
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
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妍媸必露”,“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了唐朝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个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所谓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
而曲笔,则是指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
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从二者的含义可以看出,直书就是要史家秉笔直书,遵从客观事实,“仗气直书,不畏强御”,从而给后人一个真正的历史记载。
对于曲笔,或是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是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是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
然后,史书不实,史德不存,徒留下千古遗憾。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直书和曲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存在。
无论是直书其事,还是采用曲笔手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渊源。
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下的史学,既有秉笔直书的记载,又有曲笔回护的内容。
关于直书的记载,其一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日:“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乎!越竟乃免。
”其二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以说于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
直笔与曲笔作者简介:赵京战,笔名苇可,河北安平县赵院村人,1947年出生,1966年入伍。
空军功勋飞行员。
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副师职,大校军衔。
中华诗词学会原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原副主编,执笔编写《中华新韵(十四韵)》。
主要著作:《飞行员论文选》、《苇可诗选》、《苇航集》、《中华新韵(十四韵)》(执笔)、《诗词韵律合编》、《网上诗话》、《新韵三百首》、《“诗词韵库”检索与输入软件(光盘)》(合著)、《居庸诗钞》。
直笔与曲笔赵京战为诗如为文,有时要用直笔,有时要用曲笔。
直笔开门见山,通达晓畅。
状物不蔓不枝;抒情不弯不绕,如快人快语,直达胸臆,读后有淋漓尽致的畅快。
曲笔曲径通幽,委婉曲折。
状物侧面下笔,偏处着色;抒情千回百转,如一波三折,回环激荡,读后余音袅袅,绕梁三日。
有时曲直交错,虚实相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拘于一法也。
杜甫《石壕吏》的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便是曲笔的典范。
“逾墙走”的老翁回来了没有?“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老妇是否被抓走了?作者不作直接回答,而是用“独与老翁别”曲笔作答。
试想,如果直接回答,一是没有必要,二是趣味大减。
不直接说破,把回忆和推理留给读者,把巨大的心灵创伤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把卷沉思,痛楚叠加不已,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李清照《如梦令》“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试想,“卷帘人”是现场亲眼所见,这还能看错吗?一夜的风雨,就“绿肥红瘦”了?变化有那么快那么大吗?那不是真的“绿肥红瘦”,二是诗人的心情使然。
作者用“应是”一词,那就是说应该是这样,不一定真的是这样。
作者的感情心绪,渲染渗透于海棠花树,产生了“绿肥红瘦”的曲笔,成就了这一千古名句。
瓦桥关故址位于今河北省雄县城西南,地当冀中大湖白洋淀之北,拒马河之南,与益津关和淤口关,合称“三关”(即杨六郎所镇守之三关)。
三关早已不存,无遗迹可考,去瓦桥关凭吊怀古,怎么下笔呢?我们看杨逸明《瓦桥关》是如何用曲笔妙手回春的:“一行人立雨潺潺。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了唐朝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个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所谓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
而曲笔,则是指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
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从二者的含义可以看出,直书就是要史家秉笔直书,遵从客观事实,“仗气直书,不畏强御”,从而给后人一个真正的历史记载。
对于曲笔,或是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是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是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
然后,史书不实,史德不存,徒留下千古遗憾。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直书和曲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存在。
无论是直书其事,还是采用曲笔手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渊源。
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下的史学,既有秉笔直书的记载,又有曲笔回护的内容。
关于直书的记载,其一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日:“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乎!越竟乃免。
”其二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以说于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