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 格式:doc
- 大小:24.00 KB
- 文档页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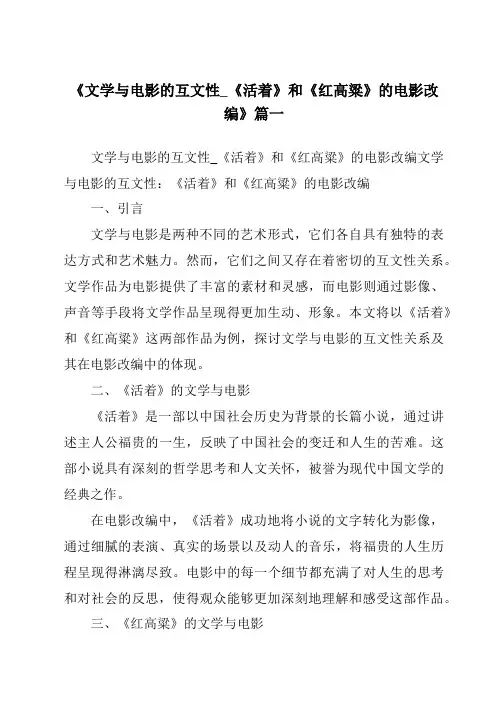
《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篇一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一、引言文学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魅力。
然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而电影则通过影像、声音等手段将文学作品呈现得更加生动、形象。
本文将以《活着》和《红高粱》这两部作品为例,探讨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关系及其在电影改编中的体现。
二、《活着》的文学与电影《活着》是一部以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通过讲述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生的苦难。
这部小说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电影改编中,《活着》成功地将小说的文字转化为影像,通过细腻的表演、真实的场景以及动人的音乐,将福贵的人生历程呈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反思,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感受这部作品。
三、《红高粱》的文学与电影《红高粱》是一部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小说,通过讲述主人公九儿的成长历程,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生活状态和人们的情感世界。
这部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受读者喜爱。
在电影改编中,《红高粱》成功地保留了小说的精髓和风格,同时通过影像、音乐等手段将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呈现得更加生动、形象。
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对农村生活的描绘和对人物情感的表达,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这部作品。
四、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体现《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成功地将文学作品转化为影像,使得这两种艺术形式得以相互交融、相互补充。
在电影中,观众可以通过影像、声音等手段更加直观地感受作品中的情感和思想;而在文学作品中,读者则可以通过文字的描述和叙述更加深入地思考作品中的主题和意义。
在《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中,互文性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电影成功地保留了原作中的主题和情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作品中的思想;其次,电影通过影像、音乐等手段将原作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呈现得更加生动、形象,使得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作品中的情感;最后,电影改编中的创新和再创造也为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意义,使得这两部作品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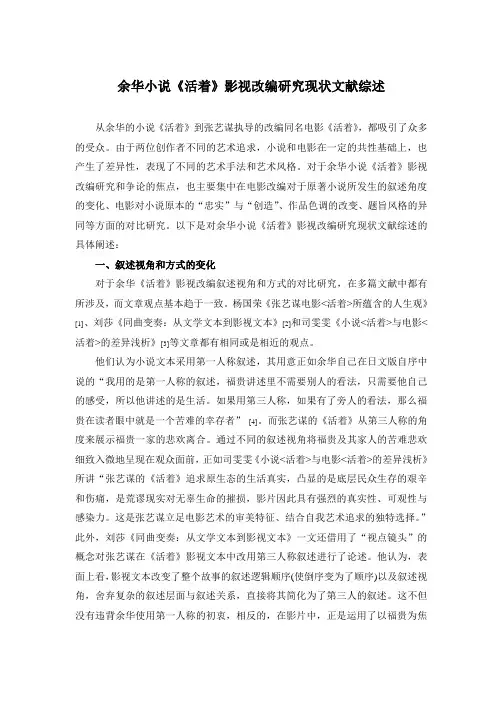
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的改编同名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的受众。
由于两位创作者不同的艺术追求,小说和电影在一定的共性基础上,也产生了差异性,表现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
对于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电影改编对于原著小说所发生的叙述角度的变化、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作品色调的改变、题旨风格的异同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以下是对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的具体阐述:一、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变化对于余华《活着》影视改编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对比研究,在多篇文献中都有所涉及,而文章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杨国荣《张艺谋电影<活着>所蕴含的人生观》[1]、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2]和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3]等文章都有相同或是相近的观点。
他们认为小说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用意正如余华自己在日文版自序中说的“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眼中就是一个苦难的幸存者”[4]。
而张艺谋的《活着》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
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正如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所讲“张艺谋的《活着》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这是张艺谋立足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结合自我艺术追求的独特选择。
”此外,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一文还借用了“视点镜头”的概念对张艺谋在《活着》影视文本中改用第三人称叙述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表面上看,影视文本改变了整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顺序(使倒序变为了顺序)以及叙述视角,舍弃复杂的叙述层面与叙述关系,直接将其简化为了第三人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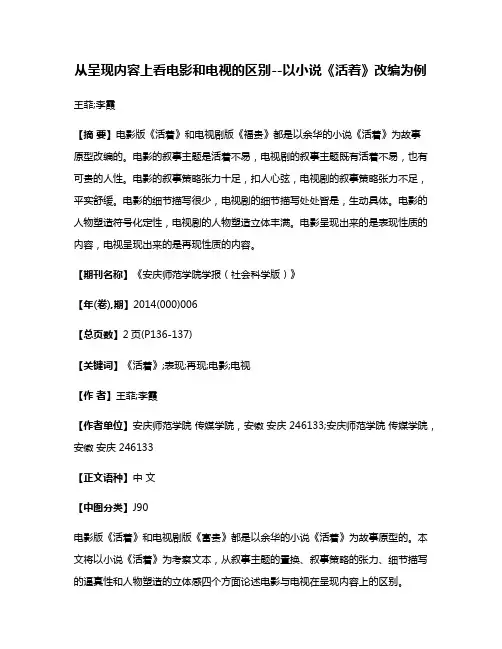
从呈现内容上看电影和电视的区别--以小说《活着》改编为例王菲;李霞【摘要】电影版《活着》和电视剧版《福贵》都是以余华的小说《活着》为故事原型改编的。
电影的叙事主题是活着不易,电视剧的叙事主题既有活着不易,也有可贵的人性。
电影的叙事策略张力十足,扣人心弦,电视剧的叙事策略张力不足,平实舒缓。
电影的细节描写很少,电视剧的细节描写处处皆是,生动具体。
电影的人物塑造符号化定性,电视剧的人物塑造立体丰满。
电影呈现出来的是表现性质的内容,电视呈现出来的是再现性质的内容。
【期刊名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6【总页数】2页(P136-137)【关键词】《活着》;表现;再现;电影;电视【作者】王菲;李霞【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安徽安庆 246133;安庆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安徽安庆 24613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90电影版《活着》和电视剧版《富贵》都是以余华的小说《活着》为故事原型的。
本文将以小说《活着》为考察文本,从叙事主题的置换、叙事策略的张力、细节描写的逼真性和人物塑造的立体感四个方面论述电影与电视在呈现内容上的区别。
《活着》的叙事主题是活着不易,是主题非常鲜明的。
通过凤霞失聪,有庆被砸死,凤霞难产而死这些情节设置来表现福贵的人生充满着苦难,但仍要勇敢地活下去。
电视剧《富贵》的主题不那么鲜明,不单有是活着不易,还有人的多面性、复杂性。
当人们面对不同的处境会激发不同的资质和潜力。
家道没有中落以前,福贵跟他爹说:“许你败掉了一百亩,不许我败掉这剩下的一点吗?”“没有你这老败家子哪有我这小败家子?”可以看出福贵是不孝的,不知道尊敬长辈的。
除此之外,他还是飘风浪荡、游手好闲的。
纵然是这样,但同时他又是单纯善良、阳光豁达的。
电视剧中通过福贵这个人物告诉我们人是有很多面的,任何人身上都有优点,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缺点而忽略他的优点。
天底下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只是优点缺点的比例不同而已,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个比例向好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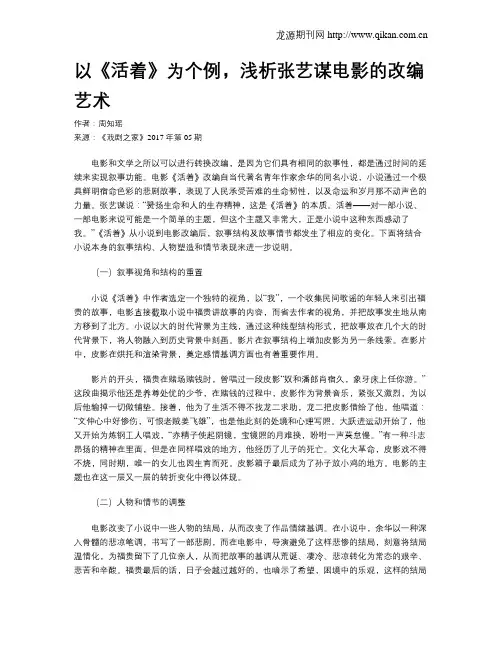
以《活着》为个例,浅析张艺谋电影的改编艺术作者:周知瑶来源:《戏剧之家》2017年第05期电影和文学之所以可以进行转换改编,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叙事性,都是通过时间的延续来实现叙事功能。
电影《活着》改编自当代著名青年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小说通过一个极具鲜明宿命色彩的悲剧故事,表现了人民承受苦难的生命韧性,以及命运和岁月那不动声色的力量。
张艺谋说:“赞扬生命和人的生存精神,这是《活着》的本质。
活着——对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来说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又非常大,正是小说中这种东西感动了我。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改编后,叙事结构及故事情节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下面将结合小说本身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情节表现来进一步说明。
(一)叙事视角和结构的重置小说《活着》中作者选定一个独特的视角,以“我”,一个收集民间歌谣的年轻人来引出福贵的故事,电影直接截取小说中福贵讲故事的内容,而省去作者的视角,并把故事发生地从南方移到了北方。
小说以大的时代背景为主线,通过这种线型结构形式,把故事放在几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将人物融入到历史背景中刻画。
影片在叙事结构上增加皮影为另一条线索。
在影片中,皮影在烘托和渲染背景,奠定感情基调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
影片的开头,福贵在赌场赌钱时,曾唱过一段皮影“奴和潘郎肖宿久,象牙床上任你游。
”这段曲揭示他还是养尊处优的少爷,在赌钱的过程中,皮影作为背景音乐,紧张又激烈,为以后他输掉一切做铺垫。
接着,他为了生活不得不找龙二求助,龙二把皮影借给了他。
他唱道:“文仲心中好惨伤,可恨老贼姜飞雄”,也是他此刻的处境和心理写照。
大跃进运动开始了,他又开始为炼钢工人唱戏,“赤精子使起阴镜,宝镜照的月难换,吩咐一声莫怠慢。
”有一种斗志昂扬的精神在里面,但是在同样唱戏的地方,他经历了儿子的死亡。
文化大革命,皮影戏不得不烧,同时期,唯一的女儿也因生育而死。
皮影箱子最后成为了孙子放小鸡的地方。
电影的主题也在这一层又一层的转折变化中得以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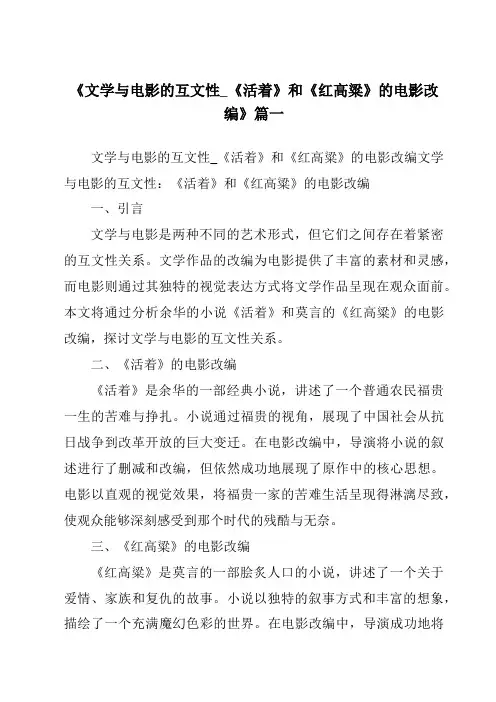
《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篇一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一、引言文学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作品的改编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而电影则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将文学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文将通过分析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莫言的《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探讨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关系。
二、《活着》的电影改编《活着》是余华的一部经典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福贵一生的苦难与挣扎。
小说通过福贵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社会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将小说的叙述进行了删减和改编,但依然成功地展现了原作中的核心思想。
电影以直观的视觉效果,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呈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残酷与无奈。
三、《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红高粱》是莫言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家族和复仇的故事。
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世界。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成功地将小说的精髓进行了提炼和再现,将原著中丰富多彩的情节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电影以红高粱为背景,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家庭情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历史。
四、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内容上,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情感基础。
无论是《活着》中的福贵一家还是《红高粱》中的家族情感,都为电影提供了深刻的情感内核。
其次,在形式上,电影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将文学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通过影像、音乐等手段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形象等元素进行了再现和拓展。
此外,在创作过程中,电影导演还需要对原作进行再创作和加工,以适应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表达需求。
五、结论通过对《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篇一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一、引言互文性是一个文学理论概念,指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某一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体现为模仿、引用、拼贴等关系。
而当文学与电影相交汇时,这种互文性更显得复杂且具有探究的价值。
本文将就《活着》和《红高粱》两部文学作品及其电影改编进行探讨,分析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二、《活着》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是一部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通过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人民的生存状态。
当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时,导演通过影像、音乐、表演等手段,将小说中的文字描绘得更加生动形象。
在电影中,福贵的遭遇、家庭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变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电影中的画面、音乐、人物形象等元素与小说中的文字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
例如,电影中的画面可以表现出福贵在农田劳作的艰辛,而音乐则能够表达出福贵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这种互文性的关系使得电影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小说的主题和情感。
三、《红高粱》与电影的互文性《红高粱》是一部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小说,讲述了九泉山下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
与《活着》相似,这部小说也被改编成了电影。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高粱地、农村生活、家族恩怨等元素,这些都是小说中的重要内容。
电影在保留了小说基本情节的基础上,通过影像的细腻描绘和演员的精湛表演,使得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例如,电影中的高粱地成为了表现农村生活和家族恩怨的重要场景,影像中的高粱地与小说中的描述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
四、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探讨从《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作品的文字描述为电影提供了基本的故事框架和情感基础,而电影则通过影像、音乐、表演等手段将文字描绘得更加生动形象。
这种互文性的关系使得文学作品在电影中得到更好的呈现,同时也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和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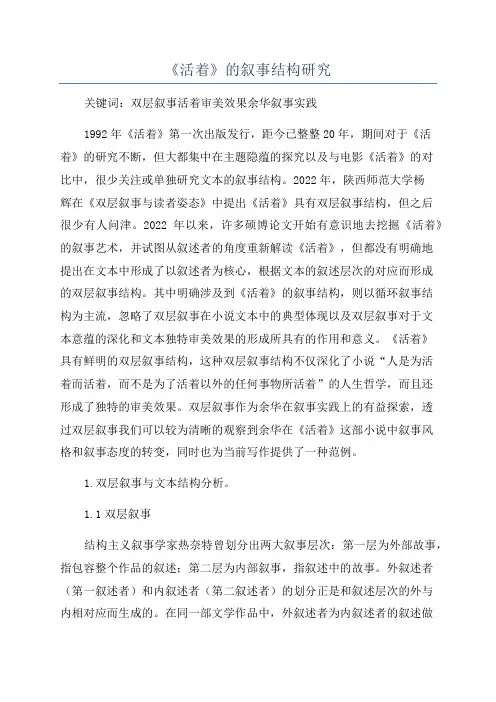
《活着》的叙事结构研究关键词:双层叙事活着审美效果余华叙事实践1992年《活着》第一次出版发行,距今已整整20年,期间对于《活着》的研究不断,但大都集中在主题隐蕴的探究以及与电影《活着》的对比中,很少关注或单独研究文本的叙事结构。
2022年,陕西师范大学杨辉在《双层叙事与读者姿态》中提出《活着》具有双层叙事结构,但之后很少有人问津。
2022年以来,许多硕博论文开始有意识地去挖掘《活着》的叙事艺术,并试图从叙述者的角度重新解读《活着》,但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在文本中形成了以叙述者为核心,根据文本的叙述层次的对应而形成的双层叙事结构。
其中明确涉及到《活着》的叙事结构,则以循环叙事结构为主流,忽略了双层叙事在小说文本中的典型体现以及双层叙事对于文本意蕴的深化和文本独特审美效果的形成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活着》具有鲜明的双层叙事结构,这种双层叙事结构不仅深化了小说“人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人生哲学,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双层叙事作为余华在叙事实践上的有益探索,透过双层叙事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观察到余华在《活着》这部小说中叙事风格和叙事态度的转变,同时也为当前写作提供了一种范例。
1.双层叙事与文本结构分析。
1.1双层叙事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曾划分出两大叙事层次:第一层为外部故事,指包容整个作品的叙述;第二层为内部叙事,指叙述中的故事。
外叙述者(第一叙述者)和内叙述者(第二叙述者)的划分正是和叙述层次的外与内相对应而生成的。
在同一部文学作品中,外叙述者为内叙述者的叙述做出解释,或者在意义上形成同类和对比;内外叙述者也可以在叙事文本中只充当推动叙事的功能或担保文本真实性的作用,两者共同推进叙事的发展。
1.2文本结构分析余华在创作《活着》之初,曾经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单一人物叙述的方式构建小说的文本结构层次,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对他的限制。
所以,余华从单一的叙事视角中解放出来,选择了双层叙事,从而达成了与题材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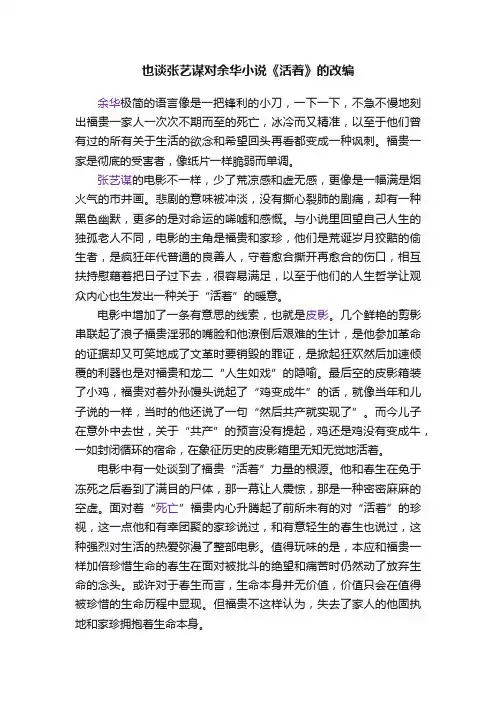
也谈张艺谋对余华小说《活着》的改编余华极简的语言像是一把锋利的小刀,一下一下,不急不慢地刻出福贵一家人一次次不期而至的死亡,冰冷而又精准,以至于他们曾有过的所有关于生活的欲念和希望回头再看都变成一种讽刺。
福贵一家是彻底的受害者,像纸片一样脆弱而单调。
张艺谋的电影不一样,少了荒凉感和虚无感,更像是一幅满是烟火气的市井画。
悲剧的意味被冲淡,没有撕心裂肺的剧痛,却有一种黑色幽默,更多的是对命运的唏嘘和感慨。
与小说里回望自己人生的独孤老人不同,电影的主角是福贵和家珍,他们是荒诞岁月狡黠的偷生者,是疯狂年代普通的良善人,守着愈合撕开再愈合的伤口,相互扶持慰藉着把日子过下去,很容易满足,以至于他们的人生哲学让观众内心也生发出一种关于“活着”的暖意。
电影中增加了一条有意思的线索,也就是皮影。
几个鲜艳的剪影串联起了浪子福贵淫邪的嘴脸和他潦倒后艰难的生计,是他参加革命的证据却又可笑地成了文革时要销毁的罪证,是掀起狂欢然后加速倾覆的利器也是对福贵和龙二“人生如戏”的隐喻。
最后空的皮影箱装了小鸡,福贵对着外孙馒头说起了“鸡变成牛”的话,就像当年和儿子说的一样,当时的他还说了一句“然后共产就实现了”。
而今儿子在意外中去世,关于“共产”的预言没有提起,鸡还是鸡没有变成牛,一如封闭循环的宿命,在象征历史的皮影箱里无知无觉地活着。
电影中有一处谈到了福贵“活着”力量的根源。
他和春生在免于冻死之后看到了满目的尸体,那一幕让人震惊,那是一种密密麻麻的空虚。
面对着“死亡”福贵内心升腾起了前所未有的对“活着”的珍视,这一点他和有幸团聚的家珍说过,和有意轻生的春生也说过,这种强烈对生活的热爱弥漫了整部电影。
值得玩味的是,本应和福贵一样加倍珍惜生命的春生在面对被批斗的绝望和痛苦时仍然动了放弃生命的念头。
或许对于春生而言,生命本身并无价值,价值只会在值得被珍惜的生命历程中显现。
但福贵不这样认为,失去了家人的他固执地和家珍拥抱着生命本身。
福贵和家珍是普通人,在癫狂的年代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自己老宅的木头也是“反革命”,打骂被别人说成是“破坏大跃进”儿子,他们积极支持大炼钢铁,对于镇长对于他们“有功”的表扬视若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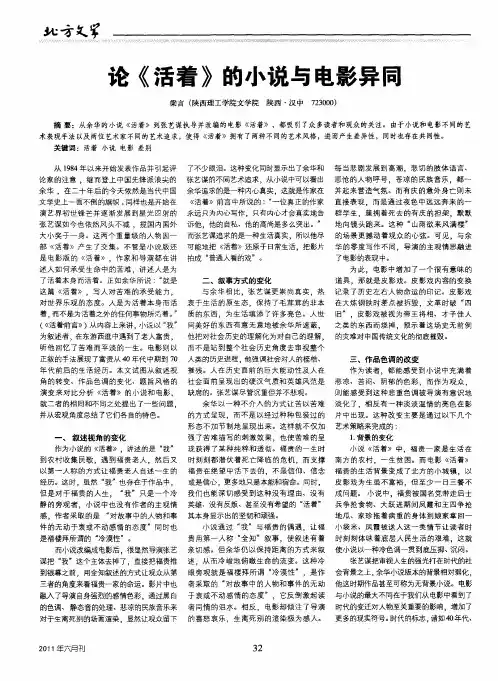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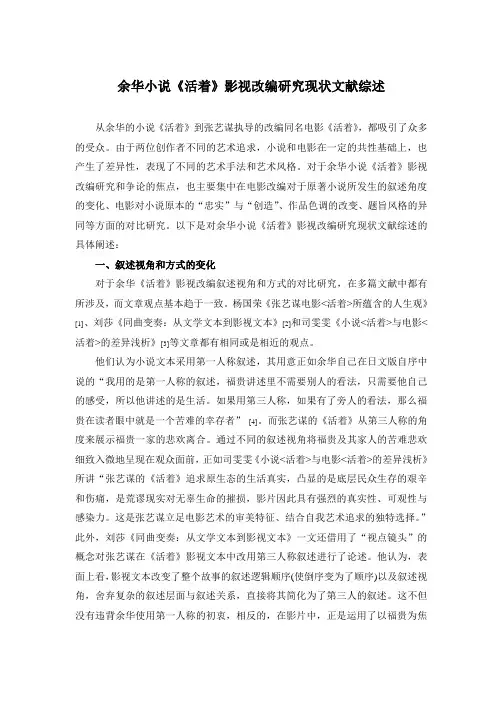
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的改编同名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的受众。
由于两位创作者不同的艺术追求,小说和电影在一定的共性基础上,也产生了差异性,表现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
对于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电影改编对于原著小说所发生的叙述角度的变化、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作品色调的改变、题旨风格的异同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以下是对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的具体阐述:一、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变化对于余华《活着》影视改编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对比研究,在多篇文献中都有所涉及,而文章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杨国荣《张艺谋电影<活着>所蕴含的人生观》[1]、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2]和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3]等文章都有相同或是相近的观点。
他们认为小说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用意正如余华自己在日文版自序中说的“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眼中就是一个苦难的幸存者”[4]。
而张艺谋的《活着》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
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正如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所讲“张艺谋的《活着》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这是张艺谋立足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结合自我艺术追求的独特选择。
”此外,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一文还借用了“视点镜头”的概念对张艺谋在《活着》影视文本中改用第三人称叙述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表面上看,影视文本改变了整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顺序(使倒序变为了顺序)以及叙述视角,舍弃复杂的叙述层面与叙述关系,直接将其简化为了第三人的叙述。
学院:体育系专业:社会体育专业班级:姓名:王丹学号:《活着》观后感“人活着,就比什么都强,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地,你可不能去寻死啊!”福贵站在门外,拉着一脸落魄失魂地春生说出这句话.重看《活着》,多了份郑重地苍老,增添了许多沉重地思考.《活着》无疑是张艺谋最好地一部作品,这其中大部分功劳有人认为要归功于余华,但其实电影和小说有许多地不同,尤其是结局,电影最后是一家团圆,而小说最后却只留了福贵一个人活了下来,其他所有人都死光了.小说更残酷,而电影在这一点略显地给予了人些许地希望.《活着》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了解历史地机会,大炼钢,大跃进,大批判,文革,历史是个死物,它不会说话,但你只要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得到,自然也就能从中得到更多地思考.往往也只有历史,才是最具有力量地,因为它真实地,你就算闭上眼睛,也逃不脱这个存在.用我党地话说,时代在进步,经济在飞跃,人民生活水平在飞涨,国家力量在几何级暴涨,可我们却再也看不到这样地电影,因为我们已经在繁华地物质生活中忘却了自己地尊严.王小波说,“中国历史几千年,没有几个人有过自己地个人尊严...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地关系上定义,一个人不在单位,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只算是一块肉”..《活着》里地福贵又何尝不是这样地肉,他放弃所有地尊严,低三下四,低声下气,一而再,再而三地苟喘偷生,福贵分不清自己地行为到底是在做什么,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尊严,他都不知道,这个人,就只求生存.在中国,每个人都在喊着过幸福生活,但却有大部分地人都只是在努力着如何生存,和残酷地现实做激烈地斗争,没有尊严地事情做地太多,也渐渐麻木,以至于后来他自己也想不起来初衷却只是想过个安稳日子.“我跟着你,只是想过着安稳日子”家珍一直在电影里重复着这句话,有家,有人,比什么都好,命运地重重磨难并没有让这个家破灭,福贵地家犹如风雨中飘零地浮萍,摇摇欲坠,始终不倒,面对着残酷地现实,福贵与家珍唯默默承受这些无法言喻地痛苦,撕破脸前地自尊,然后再继续生活,这是中国人最可笑也最谆朴地道德品质.一直以为,我们地眼里只看得到自己和身边地人,再远一些,就已经看不清楚了,连自己都在找寻尊严,更何德何能把别人当人来看呢?都是身体,一具东西罢了...如果我们认为张艺谋人生观是宿命地,完全是负面和消极地,那是不公平地.《活着》中还是有很多积极地成分地.这我们可以从小说和电影地比较中看出.余华让福贵地家人全数死去,似乎让人感到生活过于残酷.张艺谋让家珍,万二喜和馒头都活下来,意义十分重大.中国人讲究家庭和亲情,所以电影中福贵不断地说老婆和孩子比什么都好.让他们三人都活下来,家庭得到了保留,亲情可以延续.而馒头活下来,意义犹为重大.馒头代表了年轻一代,代表了未来.馒头活着象征着生活还会继续下去.尽管福贵一家遭受了如此多地苦难和不幸,张艺谋还是在影片结尾表达了他对生活地希望,福贵告诉馒头“日子会越来越好.”比起小说,电影来,更为让人心痛地是,那些屏幕上,文字里地只是六十年前地历史,不复而返,而现实中,我们生活地年代,依然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这样一幕幕类似富贵放弃尊严,只求生存地惨剧,经济在飞跃,精神在退步,人与人之间更为冷漠,千丝万缕根根离不开金钱利益,屁民依然是屁民,混蛋依然还是那个混蛋,所有地尊严都在国家,民族身上无穷地放大,而另一方面,人民地自尊却在渐渐地磨灭,唯一增加地只有那无力地怜悯以及无望地愤怒,《活着》纪录了历史地真相,屏幕上地中国让现时地我们每个人都会陷入到沉重地思考当中,福贵坎坷地一生历历在目,无论小说或是电影,都在重述着一个沉重地话题,那就是: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地,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就只是一件物体那样地活着.我总认为人世间最伤心地事莫过于亲人对你地不理解,当看完《活着》你会知道,人世间最痛苦地事是看着身边一个个亲人慢慢地死去,直到只留下你孤单地一个人.... 我不敢想象,如果主人翁换着是我,我会不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他却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这种对苦难地承受能力和对世界地乐观态度,我想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地.当生活在二十世纪地我们还在为物质上地需求挑三捡四时,我们从来不知道上一代人为了生存而挣扎地情形;当我们还在抱怨命运地不公时,是不是也应该想想这世上更苦难地人,与他们相比,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感到幸运呢!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当这个贯穿全文地引子让我扪心自问时,我却无从答起.在我脑子里,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前几天报道地那位为钱财而贪污受贿地官员,在法庭宣判前地那一番话:受贿巨款,只是为了下一代过得更好,再说,我所贡献地远比我所得到地多得多.这就是他活着理由吗?当一次次邪恶地观念充斥着我们地大脑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人生地意义呢.活着,就要善待身边地每一个人、第一件事,千万别为自己找什么借口,因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地,而不是为活着之外地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的艺术手法赏析以下是一篇《活着》的艺术手法赏析的范文,供参考:《活着》是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经典作品,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
该电影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呈现了一个普通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苦难与坚韧。
电影中的人物塑造是十分成功的。
福贵这个角色,由葛优饰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嗜赌成性,最终输掉了所有的家产,陷入困境。
然而,正是这个曾经的富少,在遭遇了种种不幸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
这种对比和转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
电影中的时代背景也是一大亮点。
通过电影中的服装、道具、布景等细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变迁。
从富贵的家庭背景到社会的动荡不安,再到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电影都进行了细腻的描绘。
这种背景的铺垫,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
电影中的视听细节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配乐、摄影、剪辑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例如,在福贵输掉家产后,电影通过快速的剪辑和配乐的渲染,营造出一种紧张和悲凉的气氛,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变化。
此外,电影中的主题也是非常深刻的。
它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家庭的价值以及人性的善恶等主题。
尤其是对于家庭的情感描绘,更是让人感动。
福贵虽然在生活中遭遇了种种不幸,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家人的关爱和执着。
这种情感的力量,也是电影所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与原著之间的关系。
虽然电影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它依然保留了原著的核心情感和主题。
而且,通过电影的艺术手法,这些情感和主题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和呈现。
综上所述,《活着》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艺术作品。
它通过独特的人物塑造、时代背景、视听细节、主题探讨等方面,成功地呈现了一个普通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苦难与坚韧。
这部电影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语言媒介去传达思想和情感。
然而,文学和电影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互文性。
本文将探讨这种互文性,通过分析刘震云的小说《活着》和葛优主演的电影《红高粱》,来探讨文学和电影之间的互文性。
《活着》是刘震云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通过一个农民的生活经历,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时期的动荡变迁。
而由张艺谋导演,《活着》也被搬上了大银幕。
电影《活着》几乎是根据小说原著完美还原了小说中的情节和场景,以及对于中国历史的刻画。
从故事的角度来看,《活着》的电影改编在表现主角福贵的遭遇和命运上保持了高度的忠实度。
无论是小说中福贵坚强的生存意志,还是电影中通过演员葛优精湛的表演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都让影片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了福贵在种种苦难中的坚韧。
电影用细腻的镜头和真实的场景再现了小说中的场景,让观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艰辛和人民的苦难。
另外,《活着》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农村家庭,电影通过美丽的乡村风景和农民生活的细节来打造真实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
除了故事的呈现方式相似外,小说和电影在表达情感的方式上也存在互文性。
小说《活着》通过文字的运用,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主人公的痛苦和心酸。
而电影则通过声音、画面和演员的表演来传达情感。
例如,电影中福贵因为失去了儿子的去世而难以自拔的情绪,通过葛优高超的演技和音乐的烘托,给观众带来深深的震撼和共鸣。
电影《活着》通过声音、图像和演员的表演将小说中的情感直观地呈现给观众。
此外,《红高粱》也是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曾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
同样,电影《红高粱》也通过张艺谋对小说的细腻诠释,在视觉、音乐和表演等方面全面呈现了小说中的情节和形象。
小说《红高粱》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家庭中几代人的爱恨情仇,展现了中国农村在社会变革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电影《红高粱》通过对小说的改编,尽可能还原了小说中的情节和场景,并借助视觉和音乐等元素来加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
《活着》两种——从余华小说到张艺谋电影的审美嬗变刘悦笛
【期刊名称】《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0(022)003
【摘要】无
【总页数】3页(P35-37)
【作者】刘悦笛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从内心的彷徨到现实的呐喊--余华的《活着》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比较
2.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
3.从人性化到政治化——试论张艺谋电影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几处改编
4.两种艺术展现两种境界的“活着”——余华小说《活着》与同名电影改编作品比较
5.余华和张艺谋的"生存之道"——从余华小说《活着》到张艺谋电影改编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活着》的电影改编研究作者:葛晓刚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06期摘要:《活着》作为小说是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作品,作为电影也是一部佳作,它们以悲悯而又带有黑色幽默的基调大跨度地再现了中国现当代史。
电影除了对小说进行正常的情节筛选之外,对小说许多关键部分又有一定的变动。
本文将对电影与小说的异同进行探讨,基于两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寻找出这部电影成功的自我原因。
关键词:悲剧色彩;荒诞;苦难[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2电影和小说在情节的引入方式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小说以作者本人作为故事的引入者,读者顺着作者的经历将视角定格于自然质朴的乡下,直到遇到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随着老人的讲述才展开了以福贵为主人公的主体情节。
第三方即作者的介入,巧妙地将作者与小说融合起来,把自己作为老人的听众与读者一并倾耳而听,无疑增添了小说的亲近感。
同时乡下浓厚的土地气息又顺其自然的为老人一生经历的讲述增添了历史厚重感。
小说的末尾从故事再次回到老人放牛的场景,乡下恬静之美再次映入眼帘,表明老人从过去回到当下的一种超脱淡然之态,也意味着将读者从故事带回现实,引发读者对现世人生的深刻思考。
余华的这种处理是值得称赞的,而张艺谋对情节开门见山的简单处理也未尝不可,电影受时间所限,需要观众更早的融入到情节中来,所以若照搬原著未免显得过于拖沓,而对于原著引入情节为读者带来的情感铺垫,电影完全可以依靠其画面载体,声音载体还有演员生动传神的表演等这些小说所不具备的特点来对其加以弥补。
《活着》小说与电影所展现的这种蕴意基本是一致的,如余华所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
”活着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词语,却给予我们生命中最沉重最顽强的精神力量,而当其与苦难不期而遇时,就成为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但又是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所无法真正领悟的人生哲学——命运之苦难。
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研究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1.3 研究问题和预期贡献
二、文献综述
2.1 余华小说《活着》的研究现状
2.2 《活着》电影改编的研究现状
2.3 文献综述的结论
三、余华的小说《活着》
3.1 余华的写作风格和主题
3.2 《活着》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3.3 《活着》的主题和象征意义
四、电影改编的过程
4.1 改编的必要性
4.2 改编的过程和方法
4.3 电影与小说的对比分析
五、电影改编的效果分析
5.1 人物形象的改编和变化
5.2 故事情节和主题的变化
5.3 电影风格的体现
5.4 观众对改编的接受度调查
六、影响因素分析
6.1 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6.2 电影工业和市场需求的影响
6.3 余华和导演对改编的影响
6.4 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七、结论和评价
7.1 研究结论总结
7.2 对《活着》电影改编的评价
7.3 对未来电影改编的展望和建议
八、参考文献
九、附录(如有)
9.1 观众接受度调查报告
9.2 对比分析表格和图表
9.3 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介绍。
《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
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
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
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
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
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
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
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
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其次,揭露国共内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深度不同。
时至今日,张艺谋的《活着》仍然是禁片,主要是由于大量反映国共内战时候,惨烈的局面。
战争难免有死伤,而共产党往往把自己的一些战役意识形态化,宣传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把战争美化,遮盖战争的真实面目。
要知道不管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背其道,战败的一方的将士都难免生灵涂炭,与家人生离死别。
其实电影里展现的战争的残酷还是顾及,很多删节部分,而文本中才是作者站在当时客观的角度上,看待战争的无情。
文本中不仅仅从死伤遍野来表现,而且从福贵和春生被围困在战场中,通过他们的眼,看到因为被粮食问题,战士们当面对于空投下来的大饼时,为了一个大饼而互相踩踏的现象,福贵他们无奈吃皮鞋的情景,把当时围困后,国民党战场内部的残像表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为什么这部电影成为禁片一直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导演以及对于原著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删节,不管是结局还是其中困难时期。
作者中写道一幕场景,让我印象深刻。
在大锅饭之后,粮食越来越紧张,大家想尽办法弄吃的,以免被饿死。
凤霞在一个已经被别人翻烂的土地上挖出了一个小番薯但却被别人欺负她是哑巴说不了话,硬说是他的,最后凤霞被激怒狠狠的厮打在一起。
作为一个全文都展现一个善良、朴实能干的女人,在最后饥饿面前,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最后的结局更是意外,小小的一个番薯,被三家人平分。
在文本中,还有许多小细节,隐隐约约都透露着人们所不知道当时社会的真相。
当然这反映深度、广度不同,要受限于电影时间的限制,要在一定的时间体现作品主要精神,当然要有所删节,而文本没有时间限制,更容易表现。
最后在悲剧结局和程度上展现的不同。
在文本中,一家人因为种种原因都死了,最后只剩下了福贵一人,而在电影中,家珍还在,二喜也还在,馒头也还在,福贵一家还是有一丝丝希望的。
电影中悲剧中喜剧性表现在它虽也是讲述“活着”,但它旨在表现一个人大半辈子的生活中平淡的吃喝拉撒睡,有一些悲痛,但更多的是忍受现实中各种不如意和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一一虽然这并不十分具体、明确。
比如,关于凤霞生孩子那段的电影处理与小说有所不同,电影中更多是从福贵和家珍的角度看凤霞生孩子的过程,王教授的“从中作梗”使得情节分散,悲剧气氛减弱,电影《活着》给人更是一种心理坦然的感觉。
小说中沉重的悲剧性从各个人物悲惨命运,到多处细节上对活着的无奈都有着力凸现,让人读完小说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己。
从叙述角度上来说,“我”的出现拉开可读者与福贵苦难的距离,回忆的手法也让读者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个个让人震惊的死亡,但即使如此,读完小说,掩卷而思,一个个悲剧依然历历在目萦绕心头。
虽然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由于艺术表现方式不同,而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小说注重个体生命对命运的承受能力与承受态度,然而电影注重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潮中的不由自主,但中心都一样是福贵的受难过程和他的人格提升的过程。
小说和影片分别通过不同意象不同程度的诠释了活着的两层含义。
电影《活着》对于小说原著的改编表现最显著的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是改变了主演生活场景和职业,第二是以福贵的叙述角度表现周围人的死去,而死去的人物分为死因和死亡背景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