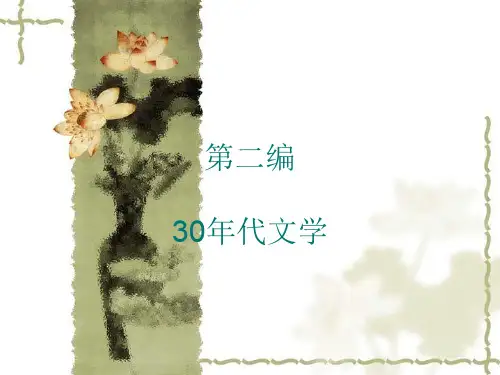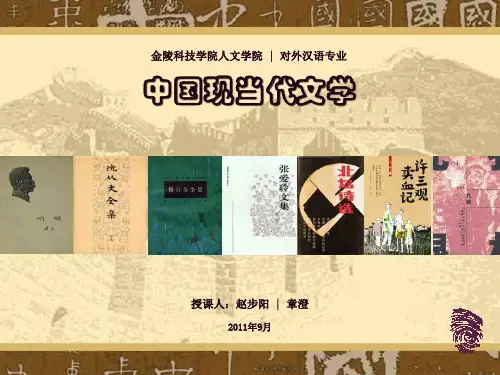专题五 三十年代小说的三大流派(课堂PPT)
- 格式:ppt
- 大小:37.50 KB
- 文档页数: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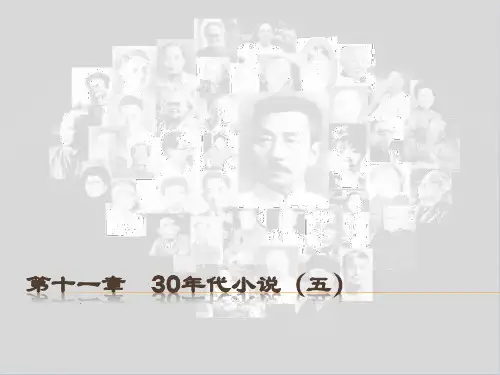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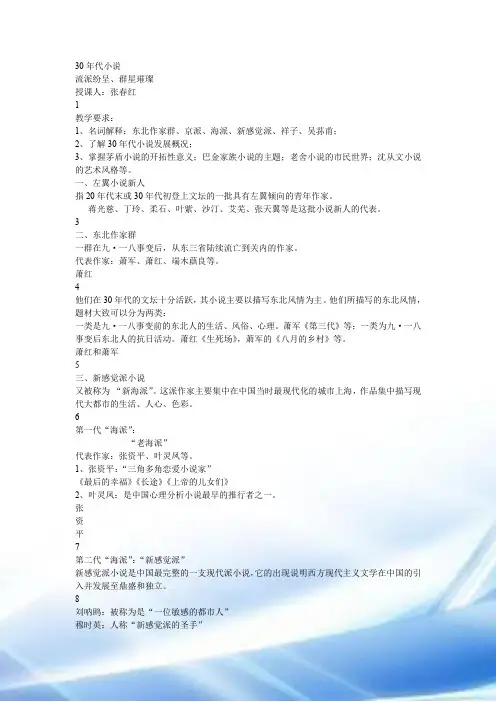
30年代小说流派纷呈、群星璀璨授课人:张春红1教学要求:1、名词解释:东北作家群、京派、海派、新感觉派、祥子、吴荪甫;2、了解30年代小说发展概况;3、掌握茅盾小说的开拓性意义;巴金家族小说的主题;老舍小说的市民世界;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风格等。
一、左翼小说新人指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一批具有左翼倾向的青年作家。
蒋光慈、丁玲、柔石、叶紫、沙汀、艾芜、张天翼等是这批小说新人的代表。
3二、东北作家群一群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三省陆续流亡到关内的作家。
代表作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
萧红4他们在30年代的文坛十分活跃,其小说主要以描写东北风情为主。
他们所描写的东北风情,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人的生活、风俗、心理。
萧军《第三代》等;一类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的抗日活动。
萧红《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
萧红和萧军5三、新感觉派小说又被称为“新海派”。
这派作家主要集中在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作品集中描写现代大都市的生活、人心、色彩。
6第一代“海派”:“老海派”代表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
1、张资平:“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2、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
张资平7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出现说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并发展至鼎盛和独立。
8刘呐鸥:被称为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穆时英:人称“新感觉派的圣手”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小说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借鉴日本“新感觉派“的小说方法,揭示中国大都市上海的畸形生活和生活在上海的市民的畸形心态。
川端康成102、描写“性”的苦闷3、描写人的潜意识11四、京派和海派的论争: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沈从文等海派:杜衡等杜衡译作121、京派30年代形成的一个作家群,也称“北方作家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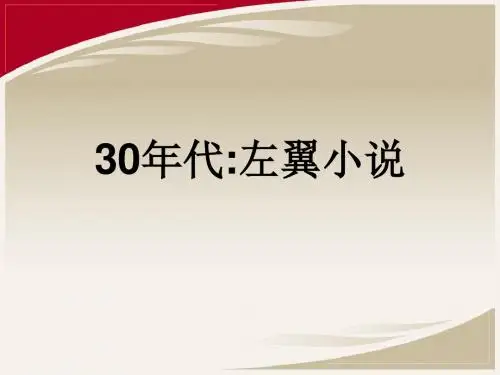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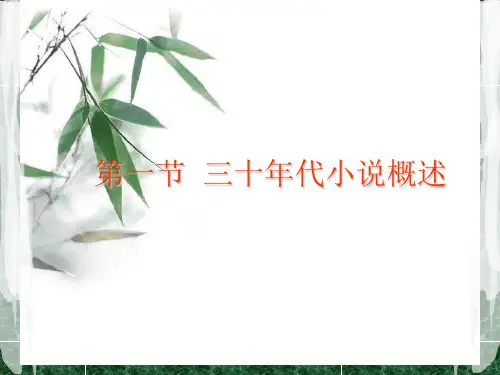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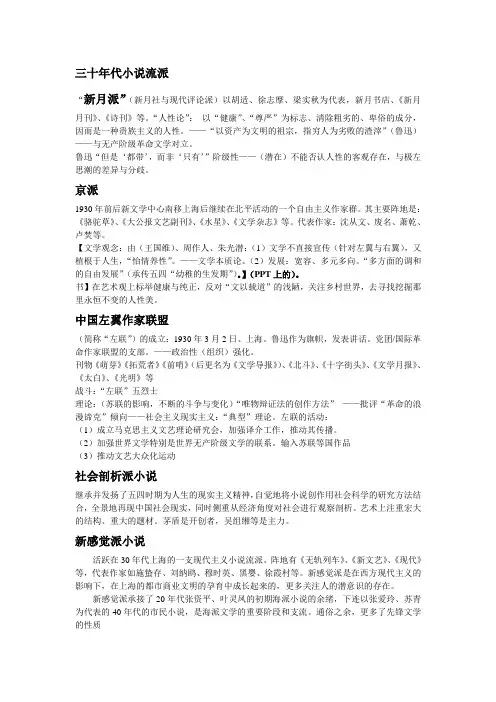
三十年代小说流派“新月派”(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新月书店、《新月月刊》、《诗刊》等。
“人性论”:以“健康”、“尊严”为标志、清除粗劣的、卑俗的成分,因而是一种贵族主义的人性。
——“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鲁迅)——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立。
鲁迅“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阶级性——(潜在)不能否认人性的客观存在,与极左思潮的差异与分歧。
京派1930年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在北平活动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
其主要阵地是:《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等。
代表作家:沈从文、废名、萧乾、卢焚等。
【文学观念:由(王国维)、周作人、朱光潜:(1)文学不直接宣传(针对左翼与右翼),又植根于人生,“怡情养性”。
——文学本质论。
(2)发展:宽容、多元多向。
“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承传五四“幼稚的生发期”)。
】(PPT上的)。
书】在艺术观上标举健康与纯正,反对“文以载道”的浅陋,关注乡村世界,去寻找挖掘那里永恒不变的人性美。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立:1930年3月2日、上海。
鲁迅作为旗帜,发表讲话。
党团/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支部。
——政治性(组织)强化。
刊物《萌芽》《拓荒者》《前哨》(后更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太白》、《光明》等战斗:“左联”五烈士理论:(苏联的影响,不断的斗争与变化)“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批评“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理论。
左联的活动:(1)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译介工作,推动其传播。
(2)加强世界文学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联系。
输入苏联等国作品(3)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社会剖析派小说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时期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将小说创作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全景地再现中国社会现实,同时侧重从经济角度对社会进行观察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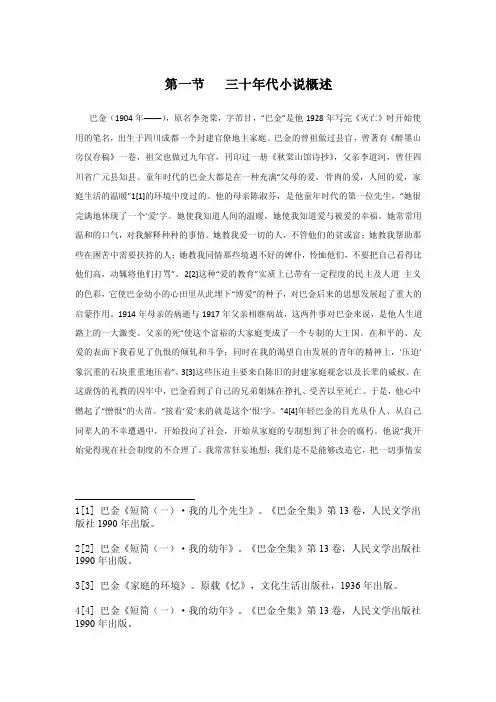
第一节三十年代小说概述巴金(1904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1928年写完《灭亡》时开始使用的笔名,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
巴金的曾祖做过县官,曾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一卷,祖父也做过九年官,刊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抄》,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省广元县知县。
童年时代的巴金大都是在一种充满“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1[1]的环境中度过的。
他的母亲陈淑芬,是他童年时代的第一位先生,“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
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
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的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
2[2]这种“爱的教育”实质上已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及人道主义的色彩,它使巴金幼小的心田里从此埋下“博爱”的种子,对巴金后来的思想发展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
1914年母亲的病逝与1917年父亲相继病故,这两件事对巴金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激变。
父亲的死“使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
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象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3[3]这些压迫主要来自陈旧的封建家庭观念以及长辈的威权。
在这虚伪的礼教的囚牢中,巴金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在挣扎、受苦以至死亡。
于是,他心中燃起了“憎恨”的火苗。
“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4[4]年轻巴金的目光从仆人、从自己同辈人的不幸遭遇中,开始投向了社会,开始从家庭的专制想到了社会的腐朽。
他说“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
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1[1]巴金《短简(一)·我的几个先生》。
《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2]巴金《短简(一)·我的幼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