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孙伟铭案”的法律分析与思考
- 格式:pdf
- 大小:1.43 MB
- 文档页数: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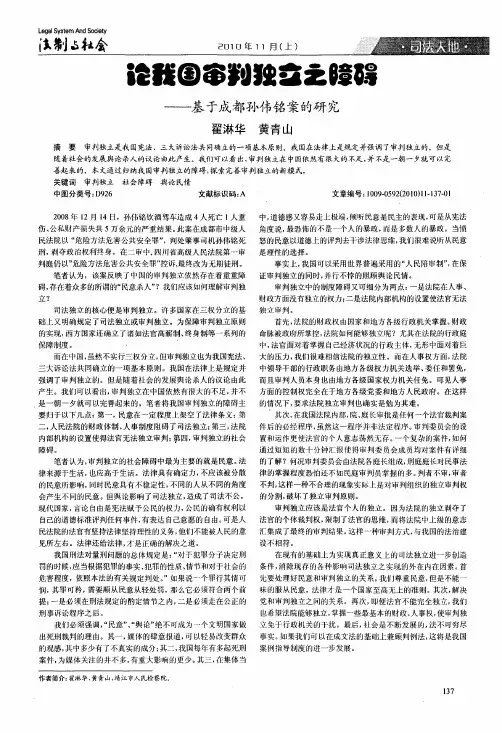
Legal Sys t em A n d So c i et yf叁整!圭塾垒三!!!竺!!望堕i耋i|_篮翟豳蟹圈论嚣@鸯翔跑§乏障碍——基于成都孙伟铭案的研究翟淋华黄青山摘要审判独立是我国宪法、三大诉讼法共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在法律上是规定并强调了审判独立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舆论杀人的议论由此产生。
我们可以看出,审判独立在中国依然有很大的不足,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善起来的。
本文通过归纳我国审判独立的障碍,探索完善审判独立的新模式。
关键词审判独立社会障碍舆论民情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137-0l2008年12月14日,孙伟铭饮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结果。
此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肇事司机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二审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控诉,最终改为无期徒刑。
笔者认为,该案反映了中国的审判独立依然存在着重重障碍,存在着众多的所谓的“民意杀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审判独立?司法独立的核心便是审判独立。
许多国家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明确规定了司法独立或审判独立。
为保障审判独立原则的实现,西方国家还确立了诸如法官高薪制、终身制等一系列的保障制度。
而在中国,虽然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审判独立也为我国宪法、三大诉讼法共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在法律上是规定并强调了审判独立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舆论杀人的议论由此产生。
我们可以看出,审判独立在中国依然有很大的不足,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善起来的。
笔者将我国审判独立的障碍主要归于以下几点:第一,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法律条文;第二,人民法院的财政体制、人事制度J j且碍了司法独立;第三,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使得法官无法独立审判:第四,审判独立的社会障碍。
笔者认为,审判独立的社会障碍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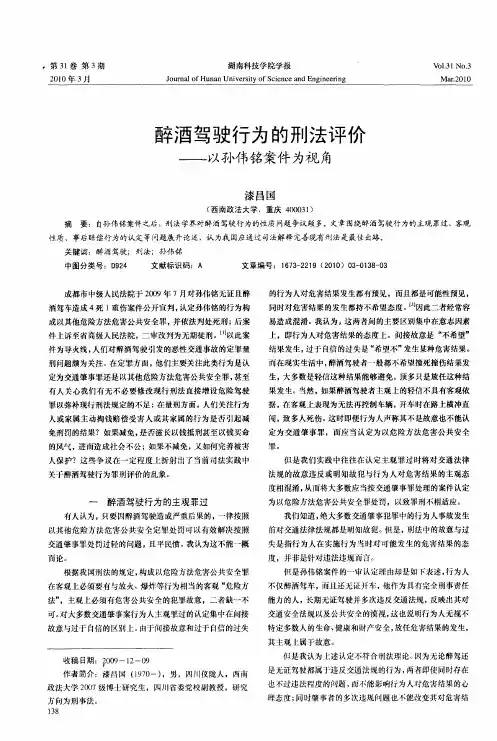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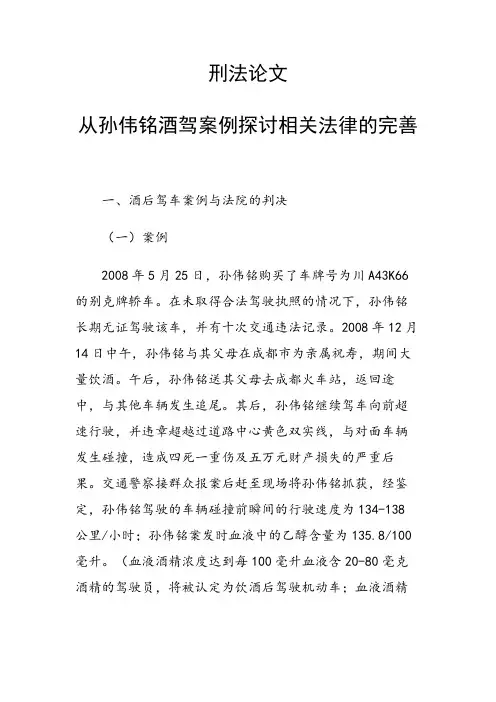
刑法论文从孙伟铭酒驾案例探讨相关法律的完善一、酒后驾车案例与法院的判决(一)案例2008年5月25日,孙伟铭购买了车牌号为川A43K66的别克牌轿车。
在未取得合法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十次交通违法记录。
2008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与其父母在成都市为亲属祝寿,期间大量饮酒。
午后,孙伟铭送其父母去成都火车站,返回途中,与其他车辆发生追尾。
其后,孙伟铭继续驾车向前超速行驶,并违章超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与对面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四死一重伤及五万元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
交通警察接群众报案后赶至现场将孙伟铭抓获,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车辆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公里/小时;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100毫升。
(血液酒精浓度达到每100毫升血液含20-80毫克酒精的驾驶员,将被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浓度达到每100毫升血液含80毫克酒精以上的驾驶员,将被认定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二)法院判决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事实及证据证明的情况看,上诉人孙伟铭购置汽车后,未经正规驾驶培训长期无证驾驶车辆,并多次违章。
众所周知,汽车作为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其使社会受益的同时,由于其高速行驶的特性又易给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国家历来对车辆上路行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孙伟铭作为受过一定教育、具有安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明知国家的规定,仍漠视社会公众和重大财产安全,藐视法律、法规,长期持续违章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的公共道路,威胁公众安全。
尤其是在本次醉酒驾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后,孙伟铭不计后果,放任严重后果的发生,以超过限速二倍以上的速度驾车在车辆、人流密集的道路上穿行逃逸,以致又违章跨越道路黄色双实线,冲撞多辆车辆,造成四死一伤、公私财产损失数万元的严重后果。
事实表明,孙伟铭对其本次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完全能够预见,其虽不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但其完全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间无任何避免的措施,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规定,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处孙伟铭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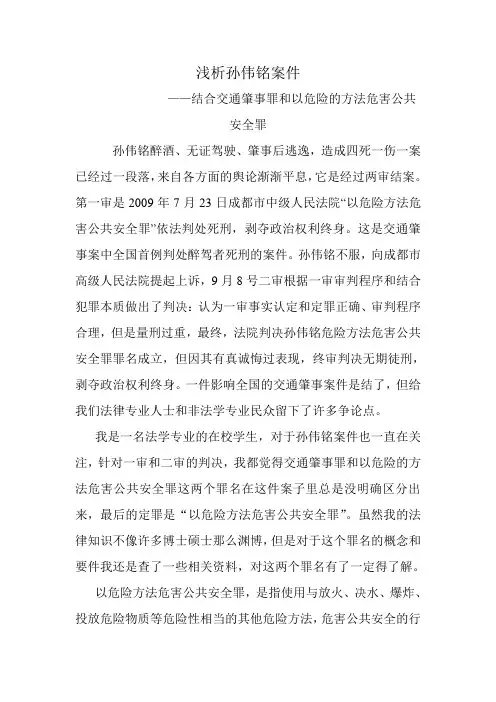
浅析孙伟铭案件——结合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孙伟铭醉酒、无证驾驶、肇事后逃逸,造成四死一伤一案已经过一段落,来自各方面的舆论渐渐平息,它是经过两审结案。
第一审是2009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是交通肇事案中全国首例判处醉驾者死刑的案件。
孙伟铭不服,向成都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9月8号二审根据一审审判程序和结合犯罪本质做出了判决:认为一审事实认定和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理,但是量刑过重,最终,法院判决孙伟铭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因其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件影响全国的交通肇事案件是结了,但给我们法律专业人士和非法学专业民众留下了许多争论点。
我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对于孙伟铭案件也一直在关注,针对一审和二审的判决,我都觉得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个罪名在这件案子里总是没明确区分出来,最后的定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虽然我的法律知识不像许多博士硕士那么渊博,但是对于这个罪名的概念和要件我还是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对这两个罪名有了一定得了解。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所谓“其他危险方法”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为下行相当的危害方法,如私设电网、使用放射性物质、投放危险物质、驾车冲撞人群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只要足以危害公共的,既可以构成本罪。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为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可以是间接故意。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本罪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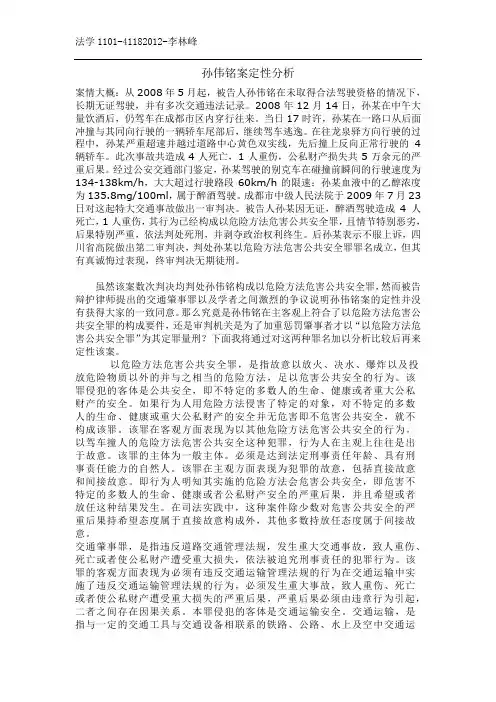
孙伟铭案定性分析案情大概:从2008年5月起,被告人孙伟铭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
2008年12月14日,孙某在中午大量饮酒后,仍驾车在成都市区内穿行往来。
当日17时许,孙某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尾部后,继续驾车逃逸。
在往龙泉驿方向行驶的过程中,孙某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
此次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经过公安交通部门鉴定,孙某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大大超过行驶路段60km/h的限速;孙某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3日对这起特大交通事故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孙某因无证,醉酒驾驶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后孙某表示不服上诉,四川省高院做出第二审判决,判处孙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其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决无期徒刑。
虽然该案数次判决均判处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被告辩护律师提出的交通肇事罪以及学者之间激烈的争议说明孙伟铭案的定性并没有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
那么究竟是孙伟铭在主客观上符合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还是审判机关是为了加重惩罚肇事者才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其定罪量刑?下面我将通过对这两种罪名加以分析比较后再来定性该案。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如果行为人用危险方法侵害了特定的对象,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并无危害即不危害公共安全,就不构成该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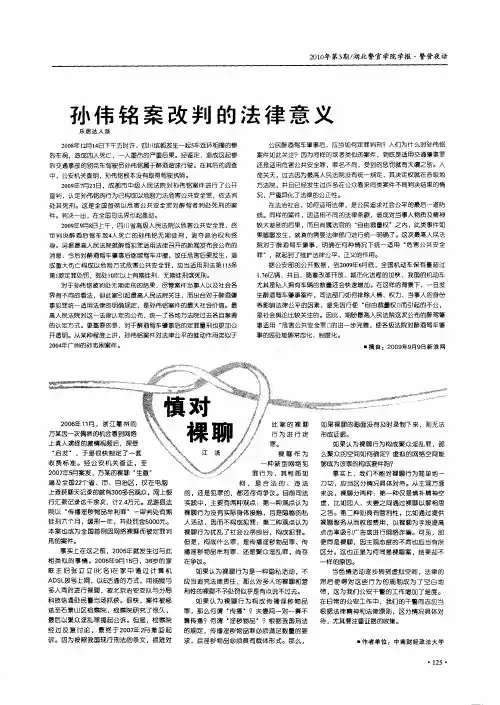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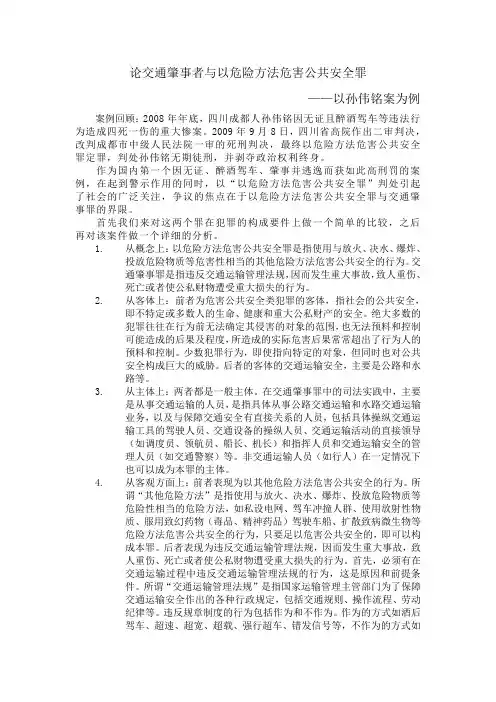
论交通肇事者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孙伟铭案为例案例回顾:2008年年底,四川成都人孙伟铭因无证且醉酒驾车等违法行为造成四死一伤的重大惨案。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死刑判决,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作为国内第一个因无证、醉酒驾车、肇事并逃逸而获如此高刑罚的案例,在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争议的焦点在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界限。
首先我们来对这两个罪在犯罪的构成要件上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之后再对该案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1.从概念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害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2.从客体上:前者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客体,指社会的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绝大多数的犯罪往往在行为前无法确定其侵害的对象的范围,也无法预料和控制可能造成的后果及程度,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常常超出了行为人的预料和控制。
少数犯罪行为,即使指向特定的对象,但同时也对公共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
后者的客体的交通运输安全,主要是公路和水路等。
3.从主体上:两者都是一般主体。
在交通肇事罪中的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是指具体从事公路交通运输和水路交通运输业务,以及与保障交通安全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包括具体操纵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领导(如调度员、领航员、船长、机长)和指挥人员和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如交通警察)等。
非交通运输人员(如行人)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4.从客观方面上:前者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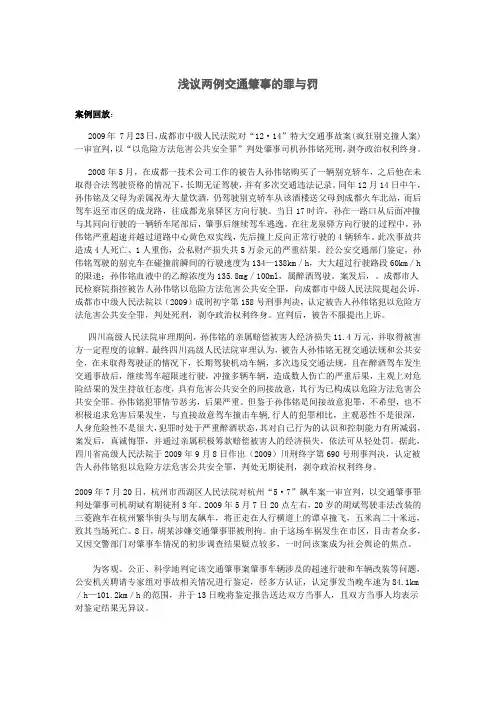
浅议两例交通肇事的罪与罚案例回放:2009年 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2·14”特大交通事故案(疯狂别克撞人案)一审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肇事司机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8年5月,在成都一技术公司工作的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之后他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
同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及父母为亲属祝寿大量饮酒,仍驾驶别克轿车从该酒楼送父母到成都火车北站,而后驾车返至市区的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
当日17时许,孙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尾部后,肇事后继续驾车逃逸。
在往龙泉驿方向行驶的过程中,孙伟铭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
此次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结果。
经公安交通部门鉴定,孙伟铭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大大超过行驶路段60km/h 的限速;孙伟铭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属醉酒驾驶。
案发后,。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9)成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
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孙伟铭的亲属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1.4万元,并取得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谅解。
最终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伟铭无视交通法规和公共安全,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驾驶机动车辆,多次违反交通法规,且在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冲撞多辆车辆,造成数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对危险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孙伟铭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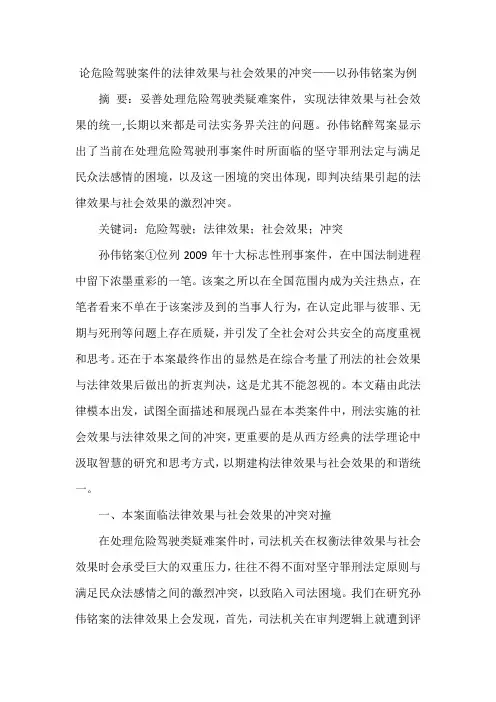
论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以孙伟铭案为例摘要:妥善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长期以来都是司法实务界关注的问题。
孙伟铭醉驾案显示出了当前在处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坚守罪刑法定与满足民众法感情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的突出体现,即判决结果引起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激烈冲突。
关键词:危险驾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冲突孙伟铭案①位列2009年十大标志性刑事案件,在中国法制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案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关注热点,在笔者看来不单在于该案涉及到的当事人行为,在认定此罪与彼罪、无期与死刑等问题上存在质疑,并引发了全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思考。
还在于本案最终作出的显然是在综合考量了刑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后做出的折衷判决,这是尤其不能忽视的。
本文藉由此法律模本出发,试图全面描述和展现凸显在本类案件中,刑法实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从西方经典的法学理论中汲取智慧的研究和思考方式,以期建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一、本案面临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对撞在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时,司法机关在权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时会承受巨大的双重压力,往往不得不面对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与满足民众法感情之间的激烈冲突,以致陷入司法困境。
我们在研究孙伟铭案的法律效果上会发现,首先,司法机关在审判逻辑上就遭到评论人士质疑:“如果按此逻辑,一个人如果长期无证驾驶,一旦出现危害后果,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次,该案的矛盾之处可借由一位最高院的法官②的观点给予概括:“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刑罚轻重之悬殊,客观上埋下了一个司法危险,即以后果选择罪名,从而导致轻罪重罪化。
”③显然,当这种客观上的司法危险与主观上的附和舆论相结合时,司法危险很容易演化为个案不公。
与本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生于前的杭州胡斌飙车案④,法院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刑法案例孙伟铭被控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上诉一案,将于2009-09-07上午8时30分在四川省高院第三审判法庭进行公开宣判。
从2008年5月起,被告人孙伟铭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
去年12月14日,孙伟铭在中午大量饮酒后,仍驾车在成都市区内穿行往来。
17时许,孙伟铭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尾部后,继续驾车逃逸。
在往龙泉驿方向行驶的过程中,孙伟铭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
此次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结果。
经公安交通部门鉴定,孙伟铭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大大超过行驶路段60km/h的限速;孙伟铭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属醉酒驾驶。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3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被告人孙伟铭当庭提出不服判决要上诉。
此次四川省高院的宣判,依照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将是终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此前,在该案民事赔偿部分处理中,受害人三家共向孙伟铭的父亲孙林(癌症患者)提出180万元的赔偿要求,在几次谈判以后降到了100万,以换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只要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受害人,能够取得受害人谅解,法院在量刑时可以考虑)。
孙家现在每月的收入就是孙林夫妇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
孙林表示,愿意在维持基本生计情况下,把每月的工资全部给受害者家属。
这里,我想说一说“我国的刑法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
刑法第二条明确地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近日,公众瞩目的孙伟铭交通肇事案尘埃落定:成都青年孙伟铭交通肇事后,架车逃逸,途中又撞死4人,造成严重后果,引起了社会的愤怒。
成都市中院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提起上诉,孙家人以百万巨款换得了受害人家属的一纸谅解协议。
凭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改判孙无期徒刑。
首先,孙伟铭的行为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所谓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此罪有两个构成要件,即主观上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客观了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使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危害或足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二者缺一不可。
孙伟铭的行为确实不齿,令人震怒。
其肆意无证驾驶,酒后架驶,在肇事后,又肆意逃逸,在逃逸途中,又撞死4人,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客观上,也确实危害了公共安全。
但仅凭此就认定其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似有不妥。
如前文所说,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两个构成要件,即主观上要求存在犯罪故意,即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存在犯罪行为。
孙伟铭的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孙是否存在犯罪故意,尚无法认定。
众所周知,犯罪行为存在故意和过失之说。
所谓故意犯罪是指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而积极追求或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
过失犯罪则是指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导致发生严重后果。
从本案来讲,孙伟铭与他人无怨无仇,不存在故意撞死他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动机,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讲,并非想要撞死多人,危害公共安全,制造出一件惊天动地的血案。
孙的行为只是在交通肇事逃逸后又肇事的一种行为。
其目的是为了逃避打击,避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存在撞死他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缺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所以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
还有人称孙伟铭在肇事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而依然驾车逃逸,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
孙伟铭案二审未宣判孙伟铭如今颇有名,因为他在四川成都酒后驾车撞死4人、撞伤1人,被成都市中院一审判决死刑,成为敲响许多人抵御美酒诱惑的警钟。
今天他在二审时听到一线生机。
在四川省高院举行的二审当中,公诉人员向法官表示,孙伟铭酒后肇事行为属于间接故意,事发后大呼快救伤员,以及积极赔偿受害者,鉴于这三点因素,不宜将他判处死刑。
受害者的家属们对此感到失望。
由于孙伟铭的酒后驾车,张志宇失去了父母,他表示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是判孙伟铭死刑,不希望二审改变一审的判决。
四川大学法学教授周伟指出,从全球趋势来看,死刑应当尽量避免。
一2008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在成都市万年场的一家酒楼参加亲戚80大寿的宴会,席间饮用了大量白酒。
下午4点多,他驾驶“别克”轿车送走父母后,由成都市区方向沿成龙路往龙泉驿区方向行驶。
17时许,孙伟铭驾车行驶至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从后面撞上了正常行驶的一辆“比亚迪”轿车尾部,事故发生后,孙伟铭不仅未立即停车查看,而是迅速倒车,从被撞的“比亚迪”车右侧超出,高速驾车往龙泉驿区方向行驶。
孙伟铭在驾车至成龙路卓锦城路段时,高速向右侧绕行后又向左侧迅速绕回,越过中心双实线,与相对方向正常行驶的一辆“长安奔奔”轿车猛烈相撞,造成“长安奔奔”车上的5名驾乘人员中1人受伤、4人死亡(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两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孙伟铭所驾车又与一辆“奥拓”车相撞,再与“奥拓”车后的一辆“蒙迪欧”轿车发生擦挂,接着与一辆“QQ”车相撞,直至自己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孙伟铭的“疯狂之旅”才停了下来。
事后经司法鉴定,孙伟铭所驾驶的别克轿车在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事故路段限速60km/h)。
事故发生后,伤员及孙伟铭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交警部门随救护车到医院,发现孙伟铭有饮酒嫌疑,当即提取孙伟铭血液进行乙醇检验,检验结果为:其血液中乙醇浓度为135.8mg /100mL,属于醉酒驾车。
第1篇一、案件背景孙伟铭案件是指2009年12月14日,四川成都发生的一起严重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当事人孙伟铭酒后驾驶一辆红色轿车,在成都市区内高速行驶,撞击多名行人,造成4人死亡、16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事发后,孙伟铭逃离现场,后被警方抓获。
此案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关于酒驾、交通肇事逃逸等法律问题的讨论。
二、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1. 酒驾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孙伟铭在案发时酒后驾驶,属于醉酒驾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孙伟铭在案发后逃离现场,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且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对机动车进行有效管理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本案中,孙伟铭所驾驶的车辆属于其所有,其在酒后驾驶过程中,未对车辆进行有效管理,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4. 保险公司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二条,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在本案中,孙伟铭的车辆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案件判决1. 孙伟铭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2. 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 孙伟铭所驾驶的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因未对车辆进行有效管理,被判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案件启示1. 酒驾、交通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刑法作业题目:关于孙伟铭案的案件分析班级:法学1501姓名:***学号: **********关于孙伟铭案的案件分析再仔细查阅了有关孙伟铭案的相关案件事实、审判过程和结果、有关各方的回应之后,产生了以下感想:孙伟铭案争论的焦点在于其所犯罪行应该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又或者可以说是其犯下这些罪行的主观心态应该认定为“过失”还是“故意”。
“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过失行为,后者则是故意行为。
而在刑法中区别故意和过失,有着特殊意义。
在刑法上,许多犯罪构成要件要求是故意,才构成犯罪,比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等,并且量刑也很重。
而过失犯罪的量刑往往较轻。
与此同时,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过失”和“故意”这两种主观心态又分别有不同的分类,“过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行的过失”,“故意”则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在本案中难以界定的则是其行为时的心态究竟是该定性为“过于自行的过失”还是“间接故意”。
而对于这两种心态的认定我认为恰恰是交通类刑事案件中最难界定的。
“过于自信的过失”又叫“有认识的过失”。
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特征表现为认识特征和行为特征,认识特征表现为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同时又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意志特征表现为行为人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即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的意志的。
行为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认识,采取一定的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
而“间接故意”则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所谓放任,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虽没有积极地追求,但也没有有效地阻止,既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反对,而是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任凭它发生与否,对结果的发生在行为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但在心理上是肯定的,不与其意志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