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 格式:doc
- 大小:34.0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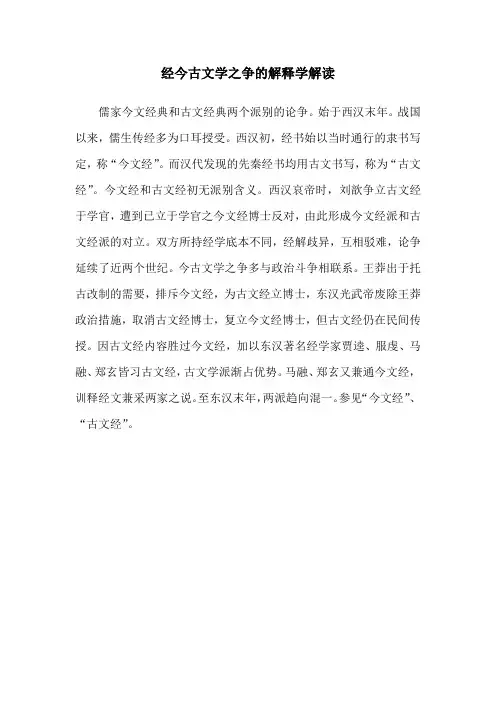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儒家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两个派别的论争。
始于西汉末年。
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多为口耳授受。
西汉初,经书始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经”。
而汉代发现的先秦经书均用古文书写,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初无派别含义。
西汉哀帝时,刘歆争立古文经于学官,遭到已立于学官之今文经博士反对,由此形成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的对立。
双方所持经学底本不同,经解歧异,互相驳难,论争延续了近两个世纪。
今古文学之争多与政治斗争相联系。
王莽出于托古改制的需要,排斥今文经,为古文经立博士,东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政治措施,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但古文经仍在民间传授。
因古文经内容胜过今文经,加以东汉著名经学家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皆习古文经,古文学派渐占优势。
马融、郑玄又兼通今文经,训释经文兼采两家之说。
至东汉末年,两派趋向混一。
参见“今文经”、“古文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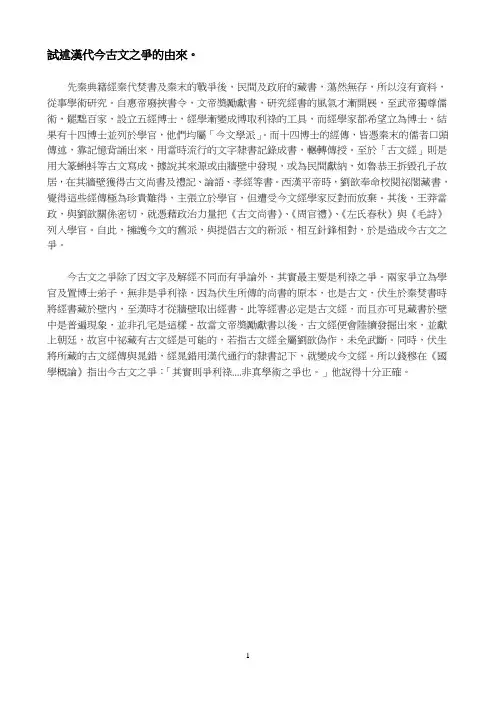
試述漢代今古文之爭的由來。
先秦典籍經秦代焚書及秦末的戰爭後,民間及政府的藏書,蕩然無存,所以沒有資料,從事學術研究。
自惠帝廢挾書令,文帝獎勵獻書,研究經書的風氣才漸開展,至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漸變成博取利祿的工具,而經學家都希望立為博士,結果有十四博士並列於學官,他們均屬「今文學派」。
而十四博士的經傳,皆憑秦末的儒者口頭傳述,靠記憶背誦出來,用當時流行的文字隸書記錄成書,輾轉傳授。
至於「古文經」則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寫成,據說其來源或由牆壁中發現,或為民間獻納,如魯恭王拆毀孔子故居,在其牆壁獲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書。
西漢平帝時,劉歆奉命校閱祕閣藏書,覺得這些經傳極為珍貴難得,主張立於學官,但遭受今文經學家反對而放棄。
其後,王莽當政,與劉歆關係密切,就憑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書》、《周官禮》、《左氏春秋》與《毛詩》列入學官。
自此,擁護今文的舊派,與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針鋒相對,於是造成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除了因文字及解經不同而有爭論外,其實最主要是利祿之爭。
兩家爭立為學官及置博士弟子,無非是爭利祿,因為伏生所傳的尚書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於秦焚書時將經書藏於壁內,至漢時才從牆壁取出經書。
此等經書必定是古文經,而且亦可見藏書於壁中是普遍現象,並非孔宅是這樣。
故當文帝獎勵獻書以後,古文經便會陸續發掘出來,並獻上朝廷,故宮中祕藏有古文經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經全屬劉歆偽作,未免武斷。
同時,伏生將所藏的古文經傳與晁錯,經晁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記下,就變成今文經。
所以錢穆在《國學概論》指出今古文之爭:「其實則爭利祿....非真學術之爭也。
」他說得十分正確。
試述今文經與古文經之主要分別。
今古文經的分別,不僅在於書寫文字的不同,還有多方面之不同。
現分述兩家之主要分別如下:從經傳版本來比較。
今文家的經典底本,除了公羊、穀梁外,大體是古文所寫;但自改成隸書後,一切經典以當時流行的隸書寫本為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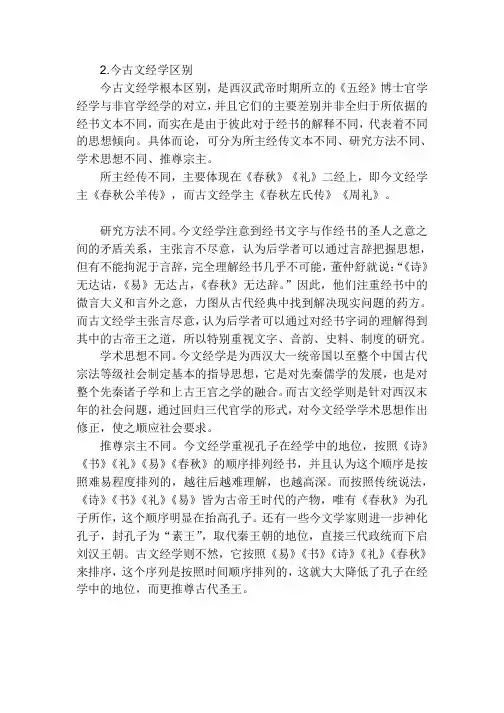
2.今古文经学区别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
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
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
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
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
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
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
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
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争论。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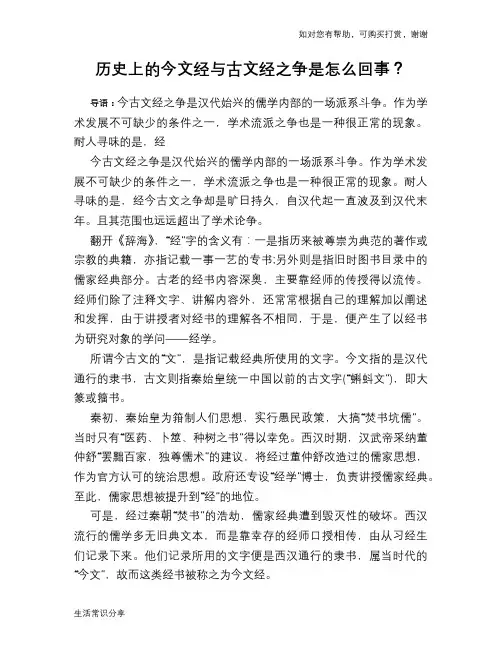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历史上的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是怎么回事?导语: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
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
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
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
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
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生活常识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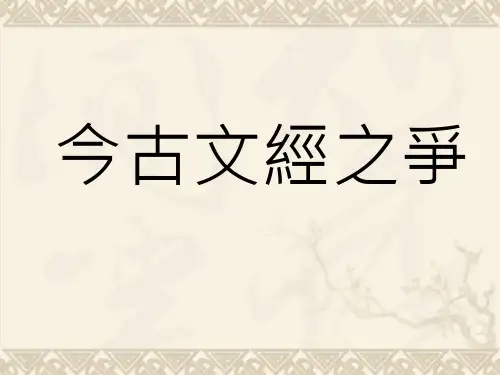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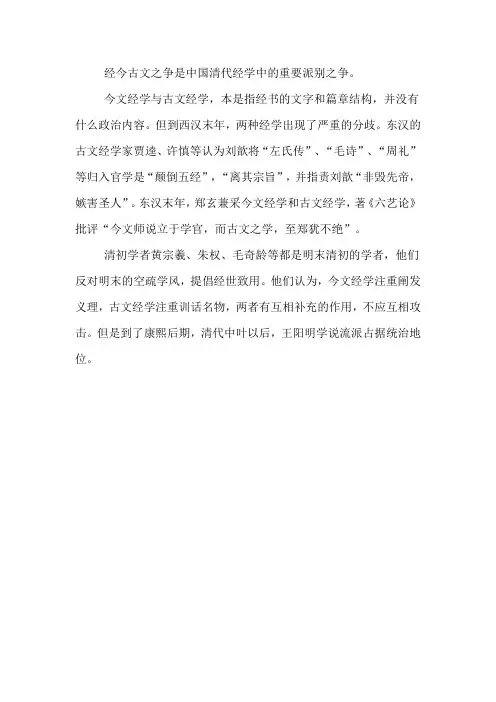
经今古文之争是中国清代经学中的重要派别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本是指经书的文字和篇章结构,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
但到西汉末年,两种经学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许慎等认为刘歆将“左氏传”、“毛诗”、“周礼”等归入官学是“颠倒五经”,“离其宗旨”,并指责刘歆“非毁先帝,嫉害圣人”。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著《六艺论》批评“今文师说立于学官,而古文之学,至郑犹不绝”。
清初学者黄宗羲、朱权、毛奇龄等都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他们反对明末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
他们认为,今文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古文经学注重训话名物,两者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应互相攻击。
但是到了康熙后期,清代中叶以后,王阳明学说流派占据统治地位。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内容摘要: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
经今古文之争,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但最终在一批批经学大师的努力下,双方开始趋向融合。
这不仅仅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贯穿着之后近两千年的学术史之中。
关键词:今古文含义斗争原因过程影响以“经”专指儒家经典,是在汉武帝之时。
汉初,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博士”,这时候的经已经初步具备了法定经典之意。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经下设置一名或几名法定博士,各自以家法传授给弟子,研究儒家经典,贯通古今。
为了激励士人专心儒学,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
这一制度的推行,使得天下学士靡然风从,鹜求补列博士弟子、受业习经。
因此,传经、注经和解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便是两汉至明清被神学化了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之后,经学被推尊为了统一天下的思想的官方哲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学术的总源。
但是,由于经学内部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延续千年的经今文和经古文之争。
西汉初年,重修文治,开始对古籍进行发掘与整理。
然而秦朝时期的焚书使得前秦的古书典籍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已无旧本,有的仅是战国秦代以来的老儒家们凭借记忆背诵,口耳相授,由弟子们以当时所使用的文字——隶书抄写并整理而成,这部分儒家经典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派为什么由互相间对于经书、经学的说法发生了那么多的不同?第一个原因在于无意间的立异。
各家的老师在讲解经书时难免有不一样的各家之言,或是在听、记时也难免弄错的。
接着就一代代的往下传,错误也就随着一代代的传授下去。
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这就是无意之间形成的分歧所发生的变异。
第二个原因是故意的分歧。
因为要争着当“博士”,就故意立异。
于是对于经书越讲越错,而经书本身也就越来变化越多,甚至于故意将经文写错。
这就是汉朝经书的变异情况。
由于今文学派既读不通书又权势过大,以致经学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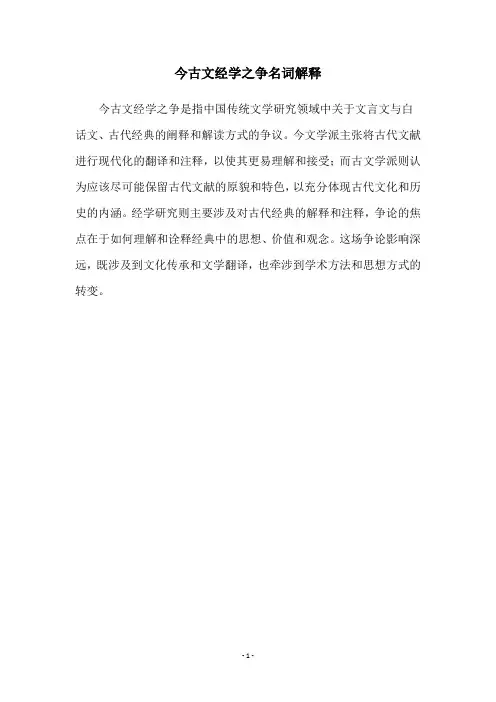
今古文经学之争名词解释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指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古代经典的阐释和解读方式的争议。
今文学派主张将古代文献进行现代化的翻译和注释,以使其更易理解和接受;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应该尽可能保留古代文献的原貌和特色,以充分体现古代文化和历史的内涵。
经学研究则主要涉及对古代经典的解释和注释,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和诠释经典中的思想、价值和观念。
这场争论影响深远,既涉及到文化传承和文学翻译,也牵涉到学术方法和思想方式的转变。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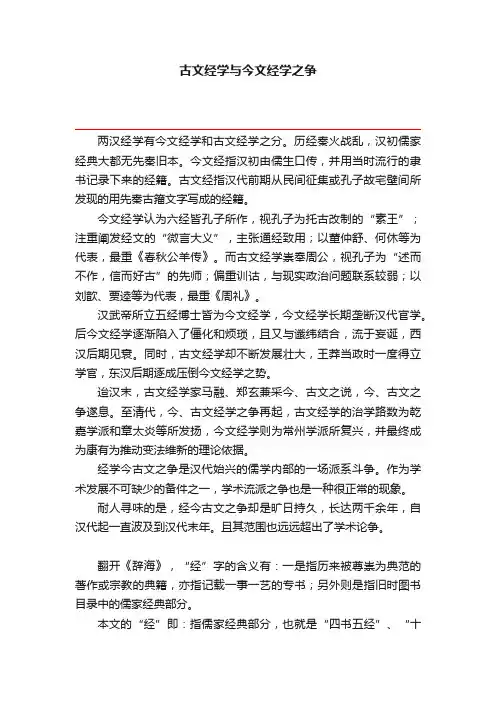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
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
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
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
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
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经学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长达两千余年,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
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
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
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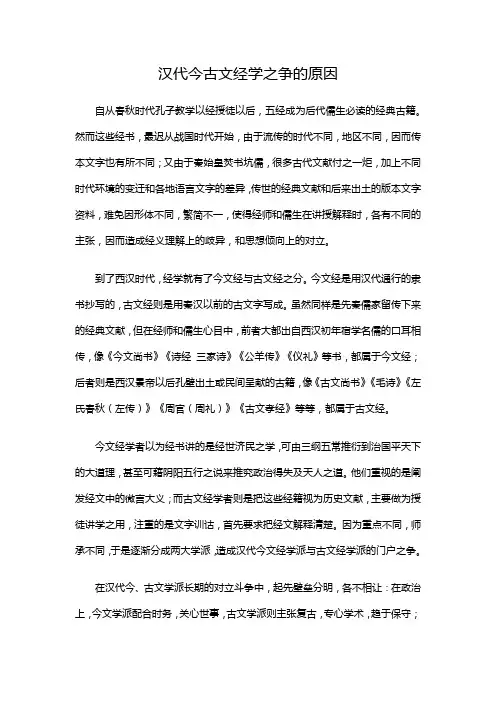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原因自从春秋时代孔子教学以经授徒以后,五经成为后代儒生必读的经典古籍。
然而这些经书,最迟从战国时代开始,由于流传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因而传本文字也有所不同;又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代文献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各地语言文字的差异,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后来出土的版本文字资料,难免因形体不同,繁简不一,使得经师和儒生在讲授解释时,各有不同的主张,因而造成经义理解上的歧异,和思想倾向上的对立。
到了西汉时代,经学就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
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
虽然同样是先秦儒家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在经师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像《今文尚书》《诗经三家诗》《公羊传》《仪礼》等书,都属于今文经;后者则是西汉景帝以后孔壁出土或民间呈献的古籍,像《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左传)》《周官(周礼)》《古文孝经》等等,都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学者以为经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学,可由三纲五常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
他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者则是把这些经籍视为历史文献,主要做为授徒讲学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训诂,首先要求把经文解释清楚。
因为重点不同,师承不同,于是逐渐分成两大学派,造成汉代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门户之争。
在汉代今、古文学派长期的对立斗争中,起先壁垒分明,各不相让:在政治上,今文学派配合时务,关心世事,古文学派则主张复古,专心学术,趋于保守;在思想上,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古文学派则讲究典章制度,论政亦悉依古圣先王;在学术上,今文学派喜就经文以阐发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多按字面以训解经文本义。
演变到后来,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家有家法,师有师法,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矣。
起码在西汉末年已是如此。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今文经学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学派的学者受到重用,有的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多止流行于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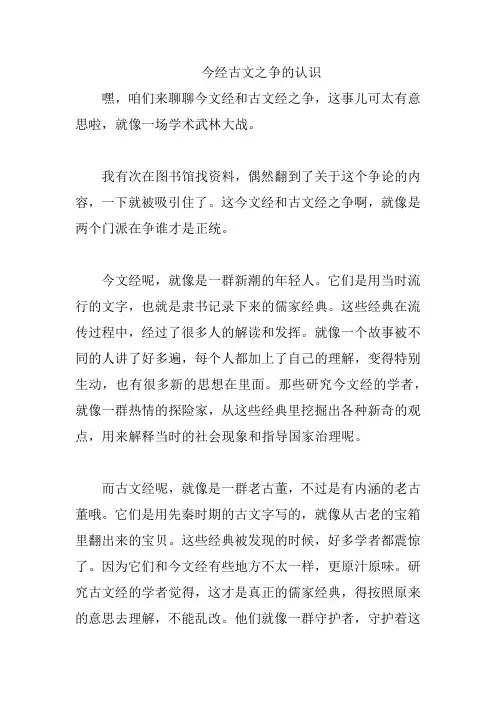
今经古文之争的认识嘿,咱们来聊聊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这事儿可太有意思啦,就像一场学术武林大战。
我有次在图书馆找资料,偶然翻到了关于这个争论的内容,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这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啊,就像是两个门派在争谁才是正统。
今文经呢,就像是一群新潮的年轻人。
它们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也就是隶书记录下来的儒家经典。
这些经典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很多人的解读和发挥。
就像一个故事被不同的人讲了好多遍,每个人都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变得特别生动,也有很多新的思想在里面。
那些研究今文经的学者,就像一群热情的探险家,从这些经典里挖掘出各种新奇的观点,用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指导国家治理呢。
而古文经呢,就像是一群老古董,不过是有内涵的老古董哦。
它们是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写的,就像从古老的宝箱里翻出来的宝贝。
这些经典被发现的时候,好多学者都震惊了。
因为它们和今文经有些地方不太一样,更原汁原味。
研究古文经的学者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得按照原来的意思去理解,不能乱改。
他们就像一群守护者,守护着这些古老经典的本来面貌。
我就想象啊,当时两派的学者见面争论,那场面肯定热闹。
就像两拨人在吵架,一方说:“我们的解读才是对的,符合时代需要!”另一方就喊:“你们那是乱改,得尊重经典原来的样子!”他们为了一个字、一句话的解释都能争得面红耳赤。
比如说,对某个经典里的一个词,今文经派觉得是这个意思,能和当下的政治联系起来,古文经派就说:“你们错啦,根据古文字的理解,它应该是另一个意思。
”这场争论虽然吵吵闹闹,但其实对文化发展有很大好处。
它让儒家经典被从不同角度研究,让各种思想碰撞出火花。
就像不同口味的调料混在一起,调出了更丰富的味道。
我们现在再看这场争论,就像看一场精彩的学术辩论赛,从中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这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真是学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啊!。
如何看待今古文经之争?郑玄两汉之际,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两种。
一方面,今文经着重閛发经文的微言大义,大讲“天人感应”和灾异之说,势必导致迷信附会之风滋生。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用谶语解释经典的纬书,如《春秋纬》、《礼纬》、《白虎通义》等。
另一方面,从民间发掘出不少用先秦古文写的古文经典,如《周礼》、《毛诗》、《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等。
西汉末年经学大师刘歆率一批儒生对古文经进行了一次大整理,还奏请设立古文博士,遭到了今文经学家的反对,于是,出现了今古文经之争。
王莽执政时,任用刘歆为国师,设立古文博士,古文经学发展起来,与今文经学相抗衡。
今古文经学除了在文字、训诂方面有别,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说。
两汉之际的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都是支持或倾向于古文经学派的,东汉时马融、许慎也是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
两派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其实质是官方经学与非官方经学之间的对立。
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两派趋于合流,今古文之争逐渐平息。
郑玄兼通古今文,他剔除谶纬学的糟粕,糅和各家学说,不拘泥于各家的“师法”、“家法”,重新注释诸经。
曹魏王肃注经也是兼通今古文不拘师法家法的。
今古文经学虽有争论,有师法、家法之别,但从几个主要思想家来说,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王充、王符、郑玄等,他们对于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则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在“天人关系”上有种种不同甚至于对立,但在王道政治和道德伦理学说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
尤其是王充和董仲舒两个人,在天道观和天人关系上,王充固然颇多批评董仲舒之言,但在王道政治理论和道德思想方面,不仅肯定而且赞美董仲舒,认为董仲舒是继承并发扬孔子学说和事业的。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论衡.超奇篇》)在人性论方面,王充的《论衡.本性篇》载:“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
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1、概念不同今文学派就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构成的学派,它的发生须要追溯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
今文经,则所指汉初由老儒诵读,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表述,由弟子用当时的楷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
与“今文经学”相对。
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
2、构成方式相同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
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公开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辨认出的用先秦和古籀文字译成的经籍。
3、对孔子态度不同今文经学指出六经皆孔子所并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著重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轻《春秋公羊传》。
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4、经典顺序相同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将五经顺序定为《诗》、《书》、《礼》、《易》、《春秋》,由浅入深;古文经学视孔子为史学家,将五经顺序定为《易》、《书》、《诗》、《礼》、《春秋》,按时间顺序排列。
钱穆先生认为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利益之争,当是定论之言。
5、兴盛衰败相同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
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
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故去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过今文经学之势。
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
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今古文经学之争2.今古文经学区别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
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
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
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
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
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
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
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
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争论。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
儒学史话:今文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
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
“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
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
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
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
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
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
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
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
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
趋近混于一同。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
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
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
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
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能延续数千年之久?导语:一提到汉代映入大家脑海的不是文景之治国家富强的局面,就是汉武帝马踏匈奴辉煌的盛世场景。
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汉朝在文化领域出现的一场著名争论——经今古文之争。
这场争论虽然不像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平定匈奴那样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它却在悄无声息之中改变着整个历史的格局。
这场争论从汉高祖时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时期,持续长达两千多年。
即使到了现代,我们的思想仍然悄无声息的受着今古文之争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来从头到尾讲述一下今古文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古文经书一、秦始皇焚书坑儒——经今古文之争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大一统局面,实行了焚书坑儒政策。
规定凡是六国史书和诸子百家,除了博士官能够收藏之外,其他人一律焚毁,不得私藏。
并且坑杀了一些方士儒生。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也就成为今古文经之争的罪魁祸首。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下令焚烧儒家作品之后,很多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就此失传。
因此在秦代没有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
在汉初流传的儒家经典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保存下来:•途径一(今文经的来源):饱学儒家经典的老儒通过背诵记忆的方式,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这也就是今文经产生的主要途径。
因为秦朝存在时间并不长,只有30多年的时间。
因此它的短命而亡为今文经能够保存下来提供了可能性。
•途径二(古文经的来源):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前,一些儒生把儒家经典埋藏起来,在秦朝灭亡之后,这些儒家经典又得以重见天日。
话说,他们埋藏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有把书藏在墙缝里的,也有把书藏在地底下的。
总之,都是藏在一些犄角旮旯,很难让人发现的地方。
一、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
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
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
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权而亡。
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
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
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
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号其书日《新语》。
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
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
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
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
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
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
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
《易》四:施、孟、梁邱、京氏。
《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
《诗》三:鲁、齐、韩氏。
《礼》二:大、小戴氏。
《春秋公羊》二:严、颜氏。
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
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
宣帝时增倍之。
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
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
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
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
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
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
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
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
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
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
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职尊。
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二、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
《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
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江公呐于口。
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
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
其后浸微。
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
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
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
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
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
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
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
后有过,左迁平陵令。
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
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
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
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
江博士复死。
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官。
使卒授十人。
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
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
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
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
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
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
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
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
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
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
诸儒执经问难于前。
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
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
《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
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
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
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
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三、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
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
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
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
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
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
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
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
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
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
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
”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
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章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
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
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
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摧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
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
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
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
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
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卒,年七十二。
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
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
郑众亦为左氏作注。
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
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
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
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
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
《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
”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
”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
桓帝时为南郡太守。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
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
教养诸生,常有千数。
……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
居字器服,多存侈饰。
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
”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
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
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
《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
“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
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
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
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
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
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
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
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
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在外游学十余年。
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
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
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
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
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