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流
- 格式:doc
- 大小:2.51 KB
- 文档页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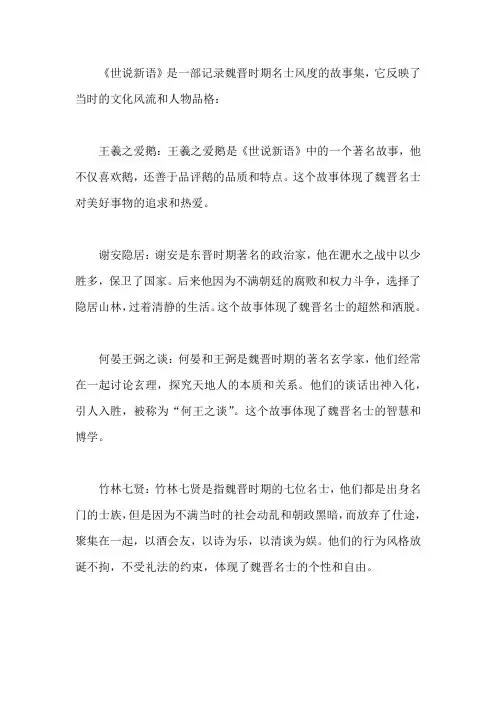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名士风度的故事集,它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风流和人物品格:
王羲之爱鹅:王羲之爱鹅是《世说新语》中的一个著名故事,他不仅喜欢鹅,还善于品评鹅的品质和特点。
这个故事体现了魏晋名士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热爱。
谢安隐居:谢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保卫了国家。
后来他因为不满朝廷的腐败和权力斗争,选择了隐居山林,过着清静的生活。
这个故事体现了魏晋名士的超然和洒脱。
何晏王弼之谈:何晏和王弼是魏晋时期的著名玄学家,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玄理,探究天地人的本质和关系。
他们的谈话出神入化,引人入胜,被称为“何王之谈”。
这个故事体现了魏晋名士的智慧和博学。
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都是出身名门的士族,但是因为不满当时的社会动乱和朝政黑暗,而放弃了仕途,聚集在一起,以酒会友,以诗为乐,以清谈为娱。
他们的行为风格放诞不拘,不受礼法的约束,体现了魏晋名士的个性和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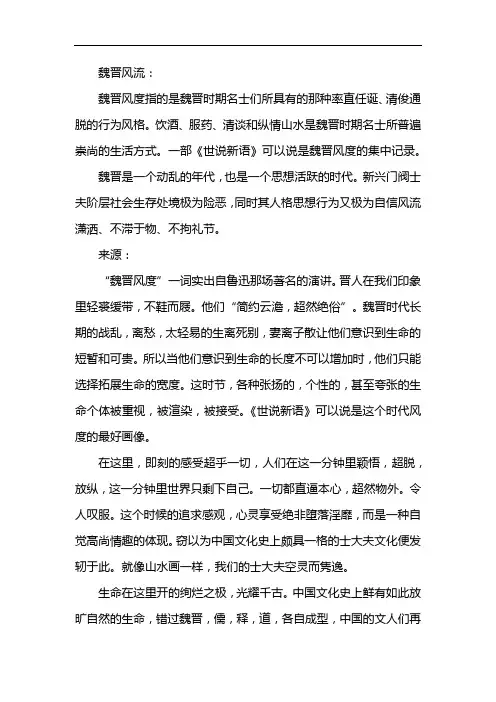
魏晋风流: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来源:“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
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
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
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
令人叹服。
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
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
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
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
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
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
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那为一杯酒放弃身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
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
这就是魏晋风度。
美学命题:王弼:得意忘象“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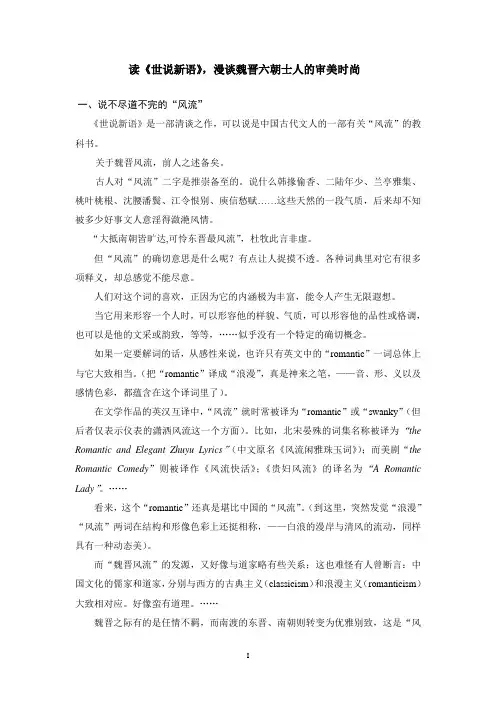
读《世说新语》,漫谈魏晋六朝士人的审美时尚一、说不尽道不完的“风流”《世说新语》是一部清谈之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部有关“风流”的教科书。
关于魏晋风流,前人之述备矣。
古人对“风流”二字是推崇备至的。
说什么韩掾偷香、二陆年少、兰亭雅集、桃叶桃根、沈腰潘鬓、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这些天然的一段气质,后来却不知被多少好事文人意淫得潋滟风情。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杜牧此言非虚。
但“风流”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各种词典里对它有很多项释义,却总感觉不能尽意。
人们对这个词的喜欢,正因为它的内涵极为丰富,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当它用来形容一个人时,可以形容他的样貌、气质,可以形容他的品性或格调,也可以是他的文采或韵致,等等,……似乎没有一个特定的确切概念。
如果一定要解词的话,从感性来说,也许只有英文中的“romantic”一词总体上与它大致相当。
(把“romantic”译成“浪漫”,真是神来之笔,——音、形、义以及感情色彩,都蕴含在这个译词里了)。
在文学作品的英汉互译中,“风流”就时常被译为“romantic”或“swanky”(但后者仅表示仪表的潇洒风流这一个方面)。
比如,北宋晏殊的词集名称被译为“the Romantic and Elegant Zhuyu Lyrics”(中文原名《风流闲雅珠玉词》);而美剧“the Romantic Comedy”则被译作《风流快活》;《贵妇风流》的译名为“A Romantic Lady”。
……看来,这个“romantic”还真是堪比中国的“风流”。
(到这里,突然发觉“浪漫”“风流”两词在结构和形像色彩上还挺相称,——白浪的漫岸与清风的流动,同样具有一种动态美)。
而“魏晋风流”的发源,又好像与道家略有些关系;这也难怪有人曾断言:中国文化的儒家和道家,分别与西方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大致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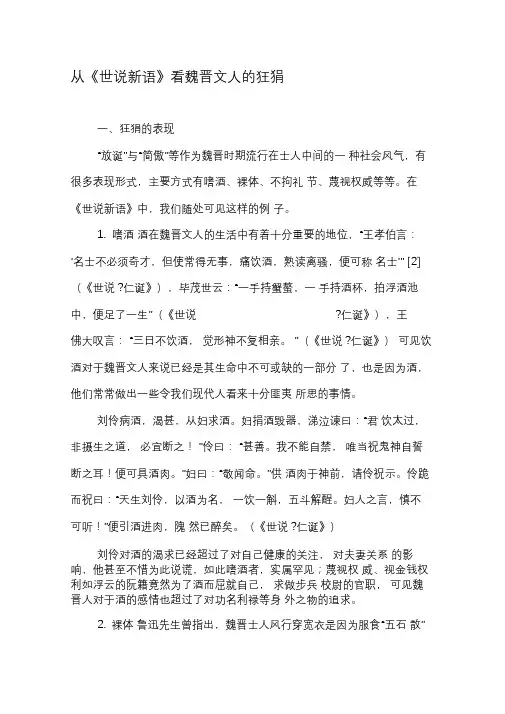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一、狂狷的表现“放诞”与“简傲”等作为魏晋时期流行在士人中间的一种社会风气,有很多表现形式,主要方式有嗜酒、裸体、不拘礼节、蔑视权威等等。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1.嗜酒酒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2](《世说?仁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仁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世说?仁诞》)可见饮酒对于魏晋文人来说已经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也是因为酒,他们常常做出一些令我们现代人看来十分匪夷所思的事情。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
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
”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
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仁诞》)刘伶对酒的渴求已经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他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如此嗜酒者,实属罕见;蔑视权威、视金钱权利如浮云的阮籍竟然为了酒而屈就自己,求做步兵校尉的官职,可见魏晋人对于酒的感情也超过了对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追求。
2.裸体鲁迅先生曾指出,魏晋士人风行穿宽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
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
” [3] 或许魏晋文人中间有裸体的风潮也是因为他们服药的缘故,毕竟穿的衣服再宽松舒适也难免会磨破皮肤,倒不如干脆不穿更为自在。
不管原因为何,裸体都实在是魏晋文人放达狂狷的一种表现。
在这些用裸体表现狂放的士人中间,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伶了: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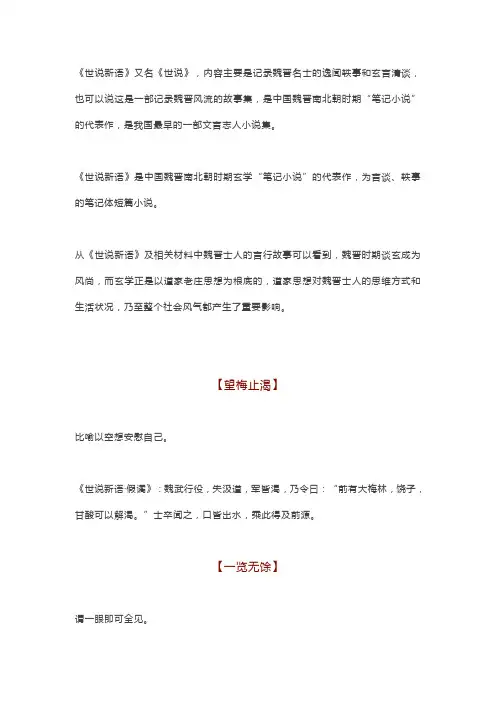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望梅止渴】比喻以空想安慰自己。
《世说新语·假谲》: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
”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一览无馀】谓一眼即可全见。
《世说新语·排调》: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
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穅粃在前。
”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
”【肃然起敬】肃穆地产生敬佩的态度或心情。
《世说新语·规箴》: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
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
”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
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华亭鹤唳】为感慨生平,悔入仕途之典。
《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蒹葭玉树】蒹葭,指毛曾;玉树,指夏侯玄,谓两个品貌极不相称的人在一起。
后以“蒹葭玉树”表示地位低的人仰攀、依附地位高贵的人。
亦常用作谦辞。
【身无长物】形容极其贫穷。
《世说新语·德行》:(王恭)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道边苦李】喻庸才,无用之才。
《世说新语·雅量》: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兒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兒竞走取之,唯戎不动。
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
”取之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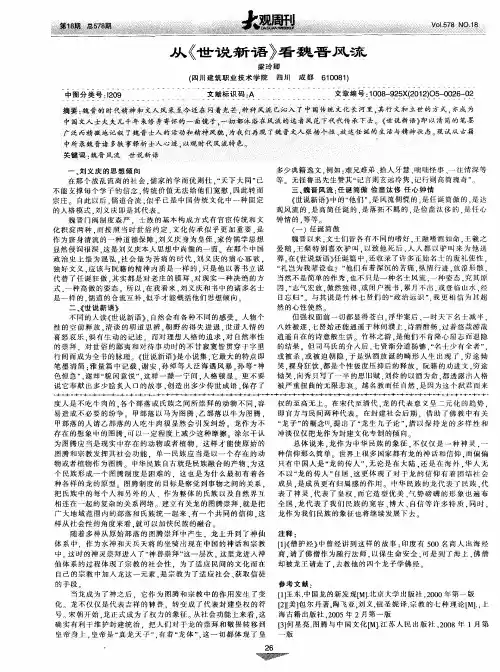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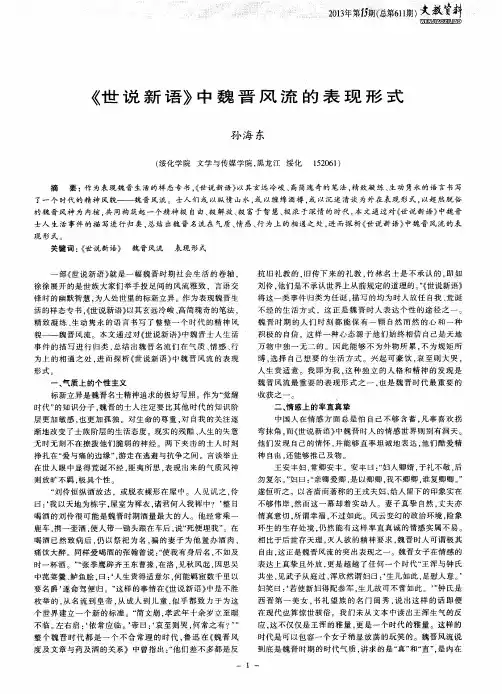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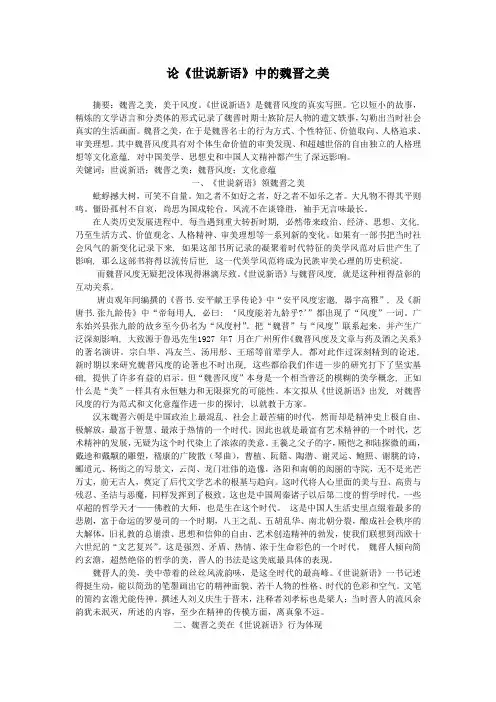
论《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之美摘要:魏晋之美,美于风度。
《世说新语》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
它以短小的故事,精炼的文学语言和分类体的形式记录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遣文轶事,勾勒出当时社会真实的生活画面。
魏晋之美,在于是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个性特征、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理想。
其中魏晋风度具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审美发现、和超越世俗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等文化意蕴, 对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人文精神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之美;魏晋风度;文化意蕴一、《世说新语》领魏晋之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 每当遇到重大转折时期, 必然带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乃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审美理想等一系列新的变化。
如果有一部书把当时社会风气的新变化记录下来, 如果这部书所记录的凝聚着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范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那么这部书将得以流传后世, 这一代美学风范将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
而魏晋风度无疑把没体现得淋漓尽致。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就是这种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
唐贞观年间编撰的《晋书.安平献王孚传论》中“安平风度宏邈, 器宇高雅”, 及《新唐书.张九龄传》中“帝每用人, 必曰: ‘风度能若九龄乎?’”都出现了“风度”一词。
广东始兴县张九龄的故乡至今仍名为“风度村”。
把“魏晋”与“风度”联系起来、并产生广泛深刻影响, 大致源于鲁迅先生1927 年7 月在广州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
宗白华、冯友兰、汤用彤、王瑶等前辈学人, 都对此作过深刻精到的论述, 新时期以来研究魏晋风度的论著也不时出现, 这些都给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但“魏晋风度”本身是一个相当普泛的模糊的美学概念, 正如什么是“美”一样具有永恒魅力和无限探究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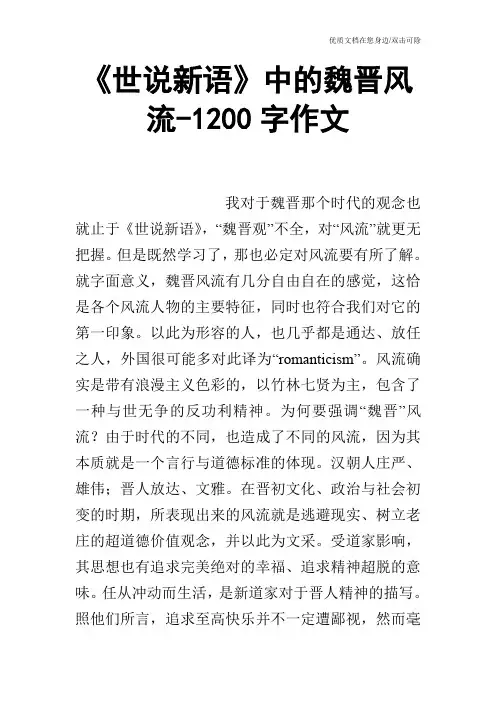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流-1200字作文我对于魏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就止于《世说新语》,“魏晋观”不全,对“风流”就更无把握。
但是既然学习了,那也必定对风流要有所了解。
就字面意义,魏晋风流有几分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恰是各个风流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符合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以此为形容的人,也几乎都是通达、放任之人,外国很可能多对此译为“romanticism”。
风流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竹林七贤为主,包含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反功利精神。
为何要强调“魏晋”风流?由于时代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风流,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言行与道德标准的体现。
汉朝人庄严、雄伟;晋人放达、文雅。
在晋初文化、政治与社会初变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风流就是逃避现实、树立老庄的超道德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文采。
受道家影响,其思想也有追求完美绝对的幸福、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
任从冲动而生活,是新道家对于晋人精神的描写。
照他们所言,追求至高快乐并不一定遭鄙视,然而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风流,也不是完全的风流。
刘伶有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他固然去寻快乐,但对超乎形象有所体会,意蕴深长,此等超越感也是魏晋风流内在的性质。
《世说新语》中有关支公与鹤、阮咸与猪的两篇,从中看出,支道林对鹤的同情和阮咸对猪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他们物我无别的感觉。
这种感觉须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将他的感情投射到描绘的对象上面,并通过某种媒介表现出来。
“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支道林本人也许就不愿做别人的玩物,因此将其感情放在鹤上。
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名风流艺术家。
按照晋代名士的看法,风流源于自然,嵇康有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这时候儒家衰微,只有乐广等人坚持地说“名教中自有乐地”。
嵇康不遵从礼仪风俗,任社会变动,取天下常而无事,这些新道家都一致同意,但还有主情派与主理派的区别。
向秀、王戎等都强调遵从理性,而嵇康、阮咸等则任从冲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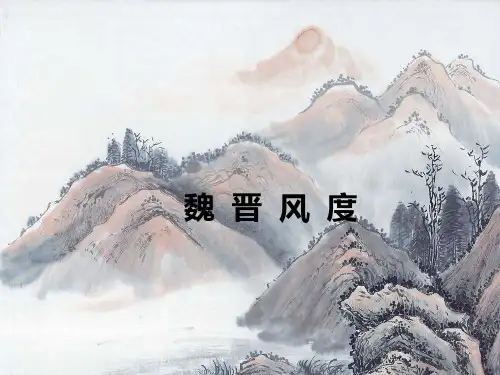
主要内涵为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定义:魏晋人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乱世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是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否定,认为名教是执和障,主张破执除障,保持本来面目。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潇洒风流、通脱自然的精神风貌与思想风格,所以又被称为“魏晋风流”。
何晏、王弼以及“竹林七贤”等人是这批士人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崇尚老庄、蔑视礼教,放达不羁、遗落世事。
魏晋风度形成于魏晋时期,不仅在六朝时期有延续与发展,就是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扩展资料:魏晋风度的主要行为表现是饮酒服药、扪虱清谈等,往往慷慨洒脱,随性而为,放达不羁,但这些行为只是魏晋风度的外在表象,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底蕴,也就是隐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内在精神。
魏晋风度是名士们追求的精神自由同黑暗的社会现实碰撞出的矛盾体,是他们外表的飘逸、豁达、欢乐、奔放与心底的沉重、执着、痛苦、压抑对立冲突的产物,而他们那些放达不羁的行为恰恰说明了他们从未实现绝对的精神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
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士谢安的趣闻轶事
导语:《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刘义庆组织人编著的笔记小说,主要记录了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的上流人士们的生活,有言行举止,有趣闻轶事。
书中所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刘义庆组织人编著的笔记小说,主要记录了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的上流人士们的生活,有言行举止,有趣闻轶事。
书中所写对象以魏晋的风流名士为主,而其中又以谢安为最。
有人粗略作了一个统计,《世说新语》全书共有1100多条事迹,其中涉及谢安的就有114条。
所以可以说,谢安是《世说新语》中出场次数最多的人物,因此他也是书中描写刻画最多最形象的人物。
而且谢安的事迹在该书中,只有一条出现在“政事”这一篇,最多的两条却是“商誉”和“品藻”。
由此可见,谢安在魏晋南北朝是多么的著名,是万千知识分子的偶像,不过他受追捧的原因并非他在政治与军事等的成就,而是他的性格、道德和精神,这大概就是魏晋风流。
比如,书中常常夸赞谢安非凡的气度。
在雅量篇第28条中说,谢安在东山时,有次与好友出去泛舟游玩,突然波涛汹涌,旁人见了面色惊慌坐立不安,而谢安镇定自若,还跟他们说:“这么惊慌还怎么回去?”这一则故事不仅体现出谢安处事不惊的态度,也表明他乐观豁达的性格。
再比如,书中也多次提及谢安在家的教育方法。
在德行篇第36条里说,谢安妇人教育孩子,有次问谢安为何不见他教导,谢安回答:“我一直在用自己教育他们。
”可见谢安比起读书写字上的教导更重视言传身教。
谢安赴宴
“谢安赴宴”出自《世说新语》中的雅量篇第29条,讲述的是桓温三生活常识分享。
51.魏晋风流: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电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
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而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
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52.建安风骨:这是对汉末魏初时期的优秀诗歌创作特色所作出的概括。
建安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主要成就在诗歌。
建安诗人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
后人把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其内涵主要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
“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浮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53.三曹: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涛文俱佳,风格清峻通脱。
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
结合世说新语谈谈你对魏晋风度的理解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出色的人物和文化,这些人物和文化构成了魏晋时期的风度。
世说新语是魏晋时期的一部流传广泛的笔记小说,它记录了魏晋时期的风土人情和人物风采,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范。
在世说新语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文化和风度。
一、文化的多元化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化多元化、交融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形态。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不同流派的文化,如儒、道、法、南北宗、墨驴、释等流派。
这些文化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有千秋。
魏晋时期文化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让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二、人物成就的凸显魏晋时期有很多杰出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世说新语中都有相应的记载。
这些人物的成就凸显了魏晋时期的人物风度。
其中包括了孙权、曹操、刘备等历史上的名人,还有一些隐逸的风流人物。
这些人物的才华、胆略、美德等方面的表现,让人们钦佩不已,形成了魏晋时期人物性格的风格特点,也是其人物风度的体现。
三、贵族风度的转变在魏晋时期,贵族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先前重视礼教的贵族文化渐渐走向没落,而新贵族阶层的文化显现出来。
随着政治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新贵族阶层开始反叛官方的礼教,它们开始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表达。
这种铺天盖地的自由和个性表达在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得到,让人们惊叹新贵族阶层的开放思想,也是其人物风度的体现。
四、儒家风度的保持魏晋时期是儒家文化的鼎盛时期,儒家文化始终有其较高的地位和影响。
在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出,在魏晋时期,尽管道教、佛教等异质文化也有所发展,但儒家文化仍然占据了当时文化的主流地位,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儒家思想和观念在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中依然是深入人心的,这是其文化品质的保持和人物风度的体现。
总之,魏晋时期的风度是多样化的。
尽管社会在变革,但是,无论是在文化形态、人物成就、贵族风貌还是儒家文化等方面,都有其较高的品质,这也是魏晋时期特有的风度。
我对于魏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就止于《世说新语》,“魏晋观”不全,对“风流”就更无把握。
但是既然学习了,那也必定对风流要有所了解。
就字面意义,魏晋风流有几分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恰是各个风流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符合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以此为形容的人,也几乎都是通达、放任之人,外国很可能多对此译为“romanticism”。
风流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竹林七贤为主,包含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反功利精神。
为何要强调“魏晋”风流?由于时代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风流,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言行与道德标准的体现。
汉朝人庄严、雄伟;晋人放达、文雅。
在晋初文化、政治与社会初变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风流就是逃避现实、树立老庄的超道德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文采。
受道家影响,其思想也有追求完美绝对的幸福、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
任从冲动而生活,是新道家对于晋人精神的描写。
照他们所言,追求至高快乐并不一定遭鄙视,然而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风流,也不是完全的风流。
刘伶有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他固然去寻快乐,但对超乎形象有所体会,意蕴深长,此等超越感也是魏晋风流内在的性质。
《世说新语》中有关支公与鹤、阮咸与猪的两篇,从中看出,支道林对鹤的同情和阮咸对猪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他们物我无别的感觉。
这种感觉须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将他的感情投射到描绘的对象上面,并通过某种媒介表现出来。
“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支道林本人也许就不愿做别人的玩物,因此将其感情放在鹤上。
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名风流艺术家。
按照晋代名士的看法,风流源于自然,嵇康有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这时候儒家衰微,只有乐广等人坚持地说“名教中自有乐地”。
嵇康不遵从礼仪风俗,任社会变动,取天下常而无事,这些新道家都一致同意,但还有主情派与主理派的区别。
向秀、王戎等都强调遵从理性,而嵇康、阮咸等则任从冲动生活。
魏晋风流还有一种外在表现,就是清谈。
清谈的艺术,在于用最精准之词,最精确之语,言最精粹之思。
清谈盛极一时,属于当时的高智商人物娱乐活动,常手持麈尾而指画。
在此之前,各界人士纷纷臧否品评人物与时事,称为“清议”。
政府开始树威信,也就由清议转化为不着边际的清谈,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与老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相合。
对此,王羲之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之所宜。
”清谈误国?大体是这样,但个别不一定,比如“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阮籍确是很有政治才能,大刀阔斧修订地方管理办法,而且这些方案都行得通。
可是他不抱有政治理想,另一次当官,也只是为了喝酒。
隐士大概都是这样,不当不知道,一当吓一跳;反倒是那些登上仕途好久的人,几乎都为好名利者。
老子的“无为而治”——可以无为,但还是要治啊!就这样任由自己的发散性思维与别人雄辩,废了整个社会体系,这应该是魏晋风流中,最使我反感的一个因素了。
透过《世说新语》总结这段时期,就是士庶之别、酒药之醉、清谈之风组成的时代。
“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此书还大有可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