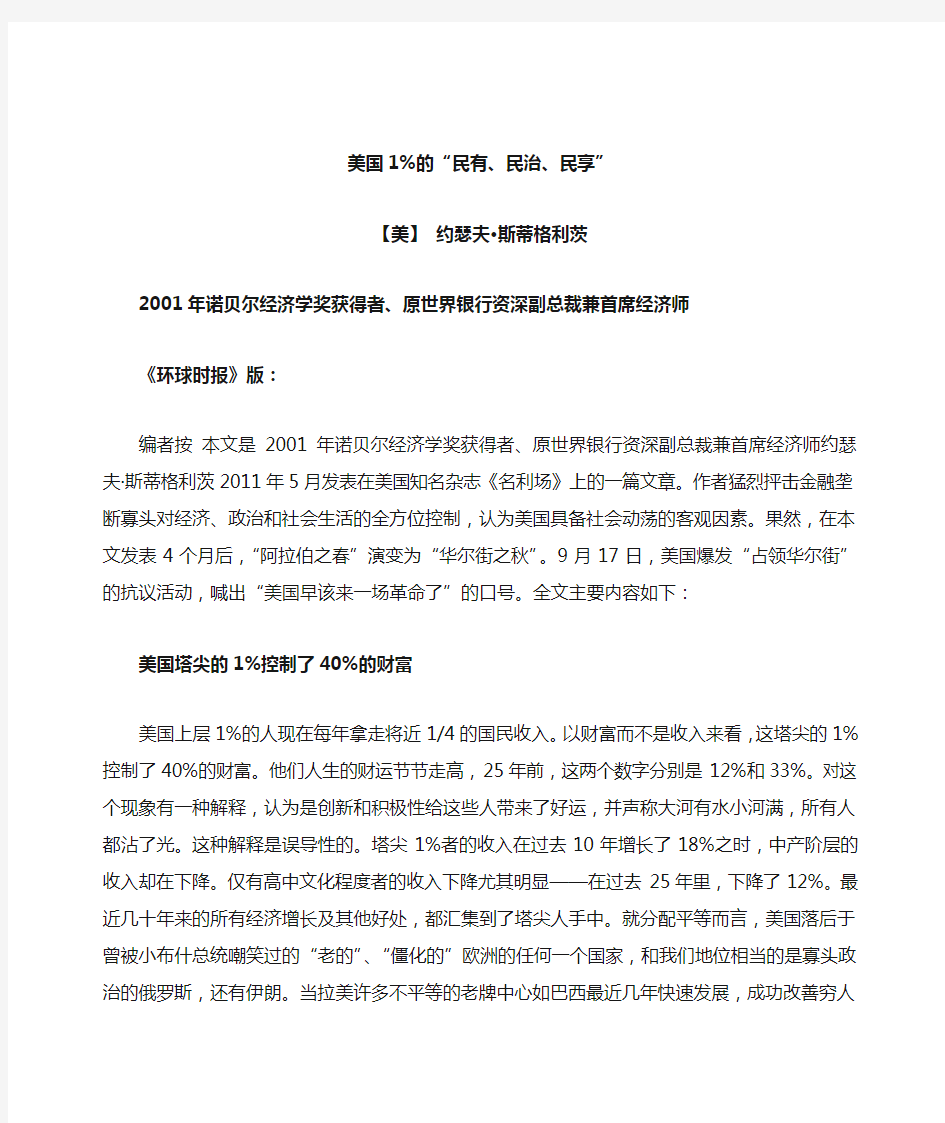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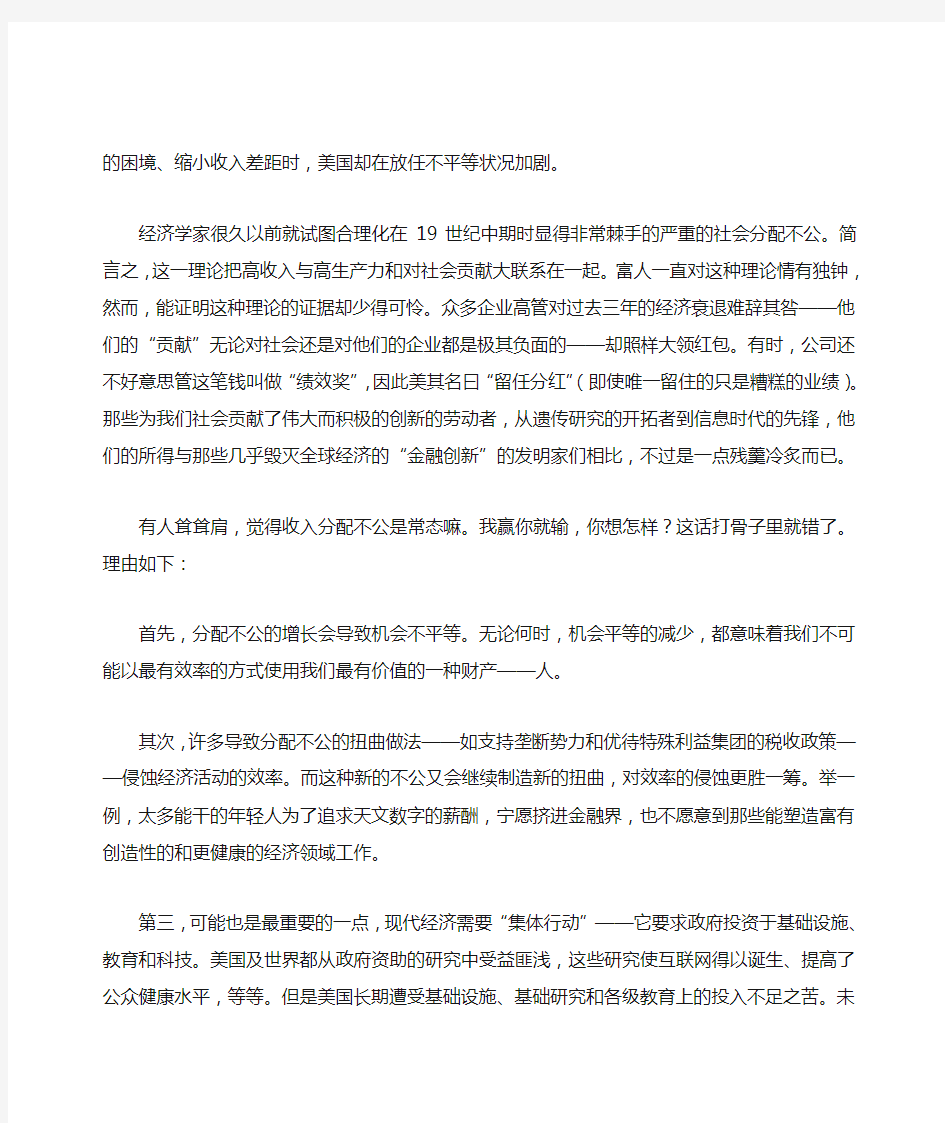
美国1%的“民有、民治、民享”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
《环球时报》版:
编者按本文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名利场》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认为美国具备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果然,在本文发表4个月后,“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华尔街之秋”。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喊出“美国早该来一场革命了”的口号。全文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
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
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手中。就分配平等而言,美国落后于曾被小布什总统嘲笑过的“老的”、“僵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地位相当的是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改善穷人的困境、缩小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加剧。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合理化在19世纪中期时显得非常棘手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简言之,这一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做“绩效奖”,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业绩)。那些为我们社会贡献了伟大而积极的创新的劳动者,从遗传研究的开拓者到信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所得与那些几乎毁灭全球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发明家们相比,不过是一点残羹冷炙而已。
有人耸耸肩,觉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态嘛。我赢你就输,你想怎样?这话打骨子里就错了。理由如下:
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长会导致机会不平等。无论何时,机会平等的减少,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种财产——人。
其次,许多导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垄断势力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政策——侵蚀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这种新的不公又会继续制造新的扭曲,对效率的侵蚀更胜一筹。举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天文数字的薪酬,宁愿挤进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创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经济领域工作。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它要求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美国及世界都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这些研究使互联网得以诞生、提高了公众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国长期遭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各级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来这些领域的经费还将遭进一步削减。
这并不令人惊讶。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严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钱。富人无须在公园、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方面依赖政府,他们完全可以用钱为自己买到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人民。富人还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会动用权力调节平衡:取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投资于公共利益。塔尖的1%也抱怨我们现有的美国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缩手缩脚,内讧不断,除了减税什么也办不成,其实他们拥护它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美国社会不公会愈演愈烈
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释美国的社会不公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规律肯定有一定影响:节约人力的技术减少了对
许多“有益无害的”中间阶层的需求,也减少了蓝领岗位。全球化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使昂贵的美国低技能工人与便宜的国外低技能工人竞争。社会变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以工会衰落为例,它曾代表1/3的美国工人,而现在只有大约12%是其成员。
但是,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下调资本收益税率相当于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搭乘免费顺风车。
从上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纪末的比尔〃盖茨,垄断和准垄断企业一直是经济权力的一个来源。对反垄断法的马虎执行,对于1%的塔尖者来说不啻为意外之福。今日不平等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金融行业对金融系统的操纵,这一操纵由金融行业花钱改变规则得以实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当其他手段都失效时,政府会贷给金融机构几乎无息的贷款,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则视而不见。
当你审视这个国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存贷款丑闻中——这桩丑闻的涉案金额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真是
少见多怪微不足道——银行家查尔斯〃基廷被一位国会议员讯问,他花在数位当选要员身上的150万美元是否能买到权势时,查尔斯回道:“我肯定希望如此。”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经费上限,赋予企业买通政府的权利。现在代理人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大体而言,美国历任贸易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也来自这一人群。当制药公司获得万亿美元的大礼时——通过立法禁止作为最大药品采购方的政府讨价还价——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除非给富人大幅减税的条款已经到位,否则一份税收法案就不会在国会出现。鉴于塔尖儿的能量,这才是应该预料到的体制运作方式。
不平等扭曲了美国社会
美国的不平等以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社会。比如,大肆宣扬的生活方式效应。先富带动后富的“滴漏型经济”可能是一个妄想,但行为作派的向下“滴漏”却已经实现了。
社会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对外政策。塔尖1%者很少有服过兵役的——事实是“全志愿兵”军队的工资吸引不了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也就那么多。此外,最富有的阶层在战时也不会为高额税收头痛:多发国债不就行了。对外政策,从定义来看,是实现国家利益与国家资源之间的平衡。可当家的 1%者不知
柴米贵,什么均衡、约束,全扔到窗外去了。没有什么险是我们不能冒的,企业和承包商等着发财。
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似乎也是为富人受益而量身定做的:以鼓励国家间商业竞争为名压低企业税率、弱化公众健康和环保要求、侵蚀过去视为“核心”的包括集体协商权在内的劳工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塔尖1%者认为他们无须关注这些,他们为我们社会带来的最严重代价或许莫过于:对我们身份认同感的侵蚀,其中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都是如此重要。美国长期以来都以“人人皆有可能”的公平社会而自豪,不过统计数字可不这么认为:贫穷的美国公民,甚至中间阶层的公民,能挤进美国上流社会的机率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低很多。他们手里抓的可不是什么好牌。正是人们对一个没有出路的不公制度的意识酿成了中东乱象:食品价格上涨和青年长期失业率高企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就有1个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无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样的数字)——所有这些就足以证明,有什么堵塞了那种吹嘘的能从塔尖1%者手中“滴漏”给所有人的好处。从而疏离感的产生就可想而知了——20-30岁人群在最近一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指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中东民众上街,抗议他们所在不公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
况。当我们注目这些街头民众的力量时,一个问题浮上脑海:什么时候美国也会这样?我们国家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和某个遥远的动荡之地差不多了。
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描述过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独有的主要优势——“适度的利己主义”。“适度”两个字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狭隘的利己主义:我要我想要的东西,马上!“适度的”利己主义则不同,它意味着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实上是实现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一观点有什么高尚或者多理想主义,事实正相反,他认为这是美式实用主义的标志。狡猾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替别人着想不仅有益灵魂,对钱袋也有好处。
塔尖1%者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看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即意识到他们命运和其余99%的人生活得怎样息息相关。这就是历史上塔尖儿们最终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为时已晚。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权把巨大的财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样一种不平等最终也会让富人后悔。▲(【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宋
丽丹译,
网站翻译版:
1%民有,1%民治,1%民享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1%民有,1%民治,1%民享
美国民众看到了很多对专制政权的抗议,在这些国家里,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里。然而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1%国民却占了国民收入的近1/4—这种不平等甚至使富人们觉得遗憾。
By Joseph E.Stiglitz
May 2011
富裕者和愤怒者1%的富人也许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命运与其他99%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密切相关。不用掩饰,这些显然已经发生了。现在,每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占有1/4的国民总收入,
更甚的是,1%的人们拥有40%的财富。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相应的数据在25年前是:12%的人占有33%的
财富。也许有人会赞美富人们获取财富的独创精神和自我驱动力,并认为这种上升趋势会使其他人的财富水涨船高------这种想法是被误导的。虽然1%富人的收入在过去十年里上升了18%,但中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而那些仅有高中文凭的人,他们的收入仅在过去的25年里就锐减了12%,最近10年或更远一段时期内,所有的增长都集中到了最上层的人们那里。在收入公平方面,美国落后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而布什总统层嘲笑欧洲老而僵化。在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比如巴西,过去有很多不平等,但现在一直在努力改善穷人的困境,减少收入差距,这些做法已相当成功,而美国却放任不平等加剧。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们试图为19世纪中叶看似很严重的不平等辩解,但那正是目前美国状况的一个缩影。他们辩解的依据是边界生产力理论,简而言之,这个理论将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的贡献联系起来,这个理论很得富人们欢心。然而其证据是无力的:这些“得力”的公司高管们,引起了3年来的大衰退,他们对社会,对所在的公司的贡献是极负面的,但他们继续领着高额奖金。有时候,公司不好意思称这些奖金为绩效奖,不得不改称为挽留金
----尽管挽留的只是糟糕的业绩。与这些发明金融产品,导致全球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人们相比,那些为社会贡献出积极的革新的人们仅仅获得了一点残羹剩炙,他们有的是遗传理解的拓荒者,有的是信息时代的急先锋。
有人看见了这种不平等,但却满不在乎:一个得到,另一个总要失去,要怎么样呢?他们争辩的问题不是怎么分蛋糕,而是蛋糕有多大。这种争论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个经济体,比如美国,人们一年比一年差,其未来不可能会好。有几个原因如下:
首先,越来越多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少的机会,当我们破坏了机会平等,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没有按最有效的方式使用最优资产——我们的人才。
其次,很多畸变导致了不平等,比如垄断势力,特殊利益的税收优惠,这些损害了经济效率。新的不平等继续产生新的畸变,加深损害效率。仅举一例,,因为天文数字般奖金的诱惑,大部分优秀的青年投身金融界,而非提升经济效率和经济健康度的领域。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协同作业,需要政府对基础建设,教育及技术进行投资。美国及全世界都曾从政府资助研究中受益,这些研究产生了互联网,公
共健康发展等。但是美国已因为基础建设,基础研究,各级教育投资不足,长期大受其害,而在这些领域,更大的削减又将到来。
当社会分配变得不平衡时,其结果已可想而知了。社会财富越两极分化,就越不情愿花钱在大众需求上。富人不依赖政府的公园,教育,人身安全保障等,他们自己买得到这些。与此同时,他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不再移情于普通人,他们也担心一个强力政府,因为强力政府会强制调整社会平衡,用富人的财富投资在公共利益上。高高在上的1%富人也会批评美国政府,但实际上,他们正喜欢如此:因为阻碍重重,不会再分配,因为两极分化,除了降低税率,什么也不能做。
经济学家们不知怎么才能圆满地解释美国正加剧的不平等。正常的供需变化是一个因素:节约劳力的技术应用减少了中产的蓝领工作,全球化提供了世界范围的市场,促使美国昂贵的非技术工人与海外便宜的非技术工人竞争。社会变革是另一个因素,比如,工会的衰落,这个曾代表1/3美国工人权益的组织,现在只代表着12%美国工人。
但是,之所以我们有这么多不平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最富有的人想要这样。税收政策即是明证。不断降低的资本利得税率,是富人大部分收入的途径-------已经让最富有的美国人近乎不劳而获。垄断及准垄断总是经济权力的来源,从上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世纪末的比尔盖茨,莫不如是。反垄断法执行无力,尤其在共和党执政期间。今天大多不平等应归因于对金融体系的操纵,规则本身能被操纵——规则已然被金融业自己拿来买卖——这是他们最好的投资之一。政府以近乎零利率借钱给金融业,当一切都完蛋时,又以优惠的条件慷慨的提供救援。而监管者对这些不透明做法和利益冲突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你看到庞大的财富被1%人控制,不由得觉得美国想要这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但是现在我们的不平等已达到世界水平。并且我们的未来也要建立在这个不平等之上,其过程不断自我强化:金钱带来权力,权力又产生更多的财富。1980年代储贷公司丑闻时——其规模,按今天的标准,几乎是小儿科——银行家Charles Keating被问及他散发到几个关键选举官员的150万美元能否产生影响时,他回答道“我当然希望能够”。最高法院最近在公民联合案的裁决中,已经去除了竞选费用的限制,“赋予”了公司购买
政府的权利。个人和政客成为完美的盟友,实际上,所有的参议员,大部分众议员,一产生就是是“1%俱乐部”的会员,他们被来自富人的钱供养着,并且知道如果他们为富人服务的好,离职后将会得到奖赏。大体来说,关于贸易,经济方面的关键行政政策制定者也来自“1%俱乐部”。当制药公司收到万亿美元的“礼物”时,法律则禁止政府(药物最大的买家)高价交易,这样就避免了怀疑。除非为富人实施减税,税单不会出现在国会,这样就不会使人惊讶。就是按照你希望的方式运行着,但被富人赋予了“特殊力量”。
不平等在我们可想象的各个方面扭曲我们的社会。首先,对生活方式的影响,1%之外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多地超过了他们的平均水平,滴入式经济学(中国说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也许是个妄想,但“滴入式”行为却是真实存在着。不平等大大地扭曲了外交政策,高高在上的富人们很少在军队服役。现实是兵役制的军队对人民没有吸引力,迄今只有爱国主义在发挥作用。另外,当国家进入战争,需要提高税率,对最富有阶层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借入的钱(和平时期,低税率)总是要还的。外交政策,按照定义本来是是平衡国家利益和
国家资源的,在上层富人的支配下,他们自己不须付出代价,将平衡和克制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则无限度的冒险,公司和承包商只为了收钱。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同样是为“济富”设计的:鼓励国家间贸易竞争,于是降低公司税收,削弱健康和环境保护,损害原本视为核心的劳工权利,比如集体谈判权利。想象一下,如果全球化规则是为国家间劳动者竞争而设计,那会是什么状况?政府会争相为普通工薪阶层提供经济保障,低税率,良好教育,整洁的环境——所有工人们关心而富人不在乎的事情。
或者,更精确的说,在所有富人施加与这个社会的影响中,最严重的是对我们身份认同得侵蚀,这些认同感中,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社区观念都很重要,很久以来,美国以一个平等社会而骄傲,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出人头地。但是统计数据显示:穷人甚至使中产阶层,出人头地的机会要小于很多欧洲国家。没有机会,不公正的体制,导致了中东的冲突:食品价格上涨,年轻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轻易成为了导火索。在美国,失业率在20%上下(有些地区或某些人口组别中。失业率要翻番),1/6美国人渴望一个全职工作而不可得,1/7的人口需要食品救济(同样数量的人遭受食品安全问题)——所有的这些,
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所吹嘘的富人向其他人的“下滴”通道已经被堵塞了。所有的这些,不出所料的正产生异化效果——这些人在20岁时,选举投票率在21%,和失业率不相上下。
最近几周,我看到在很多专制国家,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抗议活动。在埃及,突尼斯,政府已被推翻。利比亚,也门,巴林也爆发了抗议。该地区的其他统治家族也万分紧张——我们会是下一个吗?他们有理由担心,在这些社会里,小于1%的富人控制了大部分财富,财富就是权力的决定因素,根深蒂固的腐化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改善民众生活的政策实施受阻。
当我们关注着街头民众时,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些什么时候会发生在美国?在一些方面,我们的国家已经很像这些遥远的,动乱的地方。
托克维尔曾按照他的观察描述美国精神——----他称之为“正确理解的利己主义”。关键是最后两字(properlyunderstood)。每个人都具备狭义的利己主义思想:我马上想得到对我有好处的东西!“正确理解的利己主义”则不同,它需要注意其他人的利益,换言之,普
遍的福利——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终极幸福的前提。托克维尔没说这个观点有很多高尚和理想化色彩,实际上,他说的正好相反,那就是美国实用主义。精明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寻找另一个家伙不仅仅是心灵愉快,而且要对生意有益。
最富有的1%人有最好的房子,教育,医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金钱也无能为力:他们的命运与其他人的生活状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观历史,当这些富人们最终领悟到这个真理时,已经太迟了。
网站英文版:
Americans have been watching protests against oppressive regimes that concentrate massive wealth in the hands of an elite few. Yet in our own democracy, 1 percent of the people take nearly a quarter of the nation’s income—an inequality even the wealthy will come to regret.
By Joseph E. Stiglitz?
Illustration by Stephen Doyle
May 2011
THE FAT AND THE FURIOUS The top 1 percent may have the best houses, educations, and lifestyles, says the author, but “their fate is bound up with how the other 99 percent live.”
I t’s no use pretending that what has obviously happened has not in fact happened. The upper 1 percent of America ns are now taking in nearly a quarter of the nation’s income every year. In terms of wealth rather than income, the top 1 percent control 40 percent. Their lot in life has improved considerably. Twenty-five years ago,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s were 12 percent and 33 percent. One response might be to celebrate the ingenuity and drive that brought good fortune to these people, and to contend that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That response would be misguided. While the top 1 percent have seen their incomes rise 18 perc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ose in the middle have actually seen their incomes fall. For men with only high-school degrees, the decline has been precipitous—12 percent in the last quarter-century alone. All the growth in recent decades—and more—has gone to those at the top. In terms of income equality, America lags behind any country in the old, ossified Europe tha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used to deride. Among our closest counterparts are Russia with its oligarchs and Iran. While many of the old centers of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such as Brazil, have been striving in recent years, rather successfully, to improve the plight of the poor and reduce gaps in income, America has allowed inequality to grow.
Economists long ago tried to justify the vast inequalities that seemed so troubling in the mid-19th century—inequalities that are but a pale shadow of what we are seeing in America today. The justification they came up with was called “marginal-productivity theory.” In a nutshell, this theory associated higher incomes with higher productivity and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It is a theory that has always been cherished by the rich. Evidence for its validity, however, remains thin. The corporate executives who helped bring on the recession of the past three years—whose contribution to our society, and to their own companies, has been massively negative—went on to receive large bonuses. In some cases, companies were so embarrassed about calling such rewards “performance bonuses” that they felt compelled to change the name to “retention bonuses” (even if the only thing being retained was bad performance).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great positive innovations to our society, from the pioneers of genetic understanding to the pioneer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have received a pittance compared with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that brought our global economy to the brink of ruin.
S ome people look at income inequality and shrug their shoulders. So what if this person gains and that person loses? What matters, they argue, is not how the pie is divided but the size of the pie. That argument is fundamentally wrong. An economy in which most citizens are doing worse
year after year—an economy like America’s—is not likely to do well over the long haul.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First, growing inequality is the flip side of something else: shrinking opportunity. Whenever we diminish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t means that we are not using some of our most valuable assets—our people—in the most productive way possible. Second, many of the distortions that lead to inequality—such 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monopoly power and preferential tax treatment for special interests—und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conomy. This new inequality goes on to create new distortions, undermining efficiency even further. To give just one example, far too many of our most talented young people, seeing the astronomical rewards, have gone into finance rather than into fields that would lead to a more productive and healthy economy.
Third,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 a modern economy requires “collective action”—it needs government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have benefited greatly from government-sponsored research that led to the Internet, to advances in public health, and so on. But America has long suffered from an under-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look at the condition of our highways and bridges, our railroads and airports), in basic research, and in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Further cutbacks in these areas lie ahead.
None of this should come as a surprise—it is simply what happens when a society’s wealth distribution becomes lopsided. The more divided a society becomes in terms of wealth, the more reluctant the wealthy become to spend money on common needs. The rich don’t need to rely on government for parks or education or medical care or personal security—they can buy all these things for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they become more distant from ordinary people, losing whatever empathy they may once have had. They also worry about strong government—one that could use its powers to adjust the balance, take some of their wealth, and invest it for the common good. The top 1 percent may complain about the kind of government we have in America, but in truth they like it just fine: too gridlocked to re-distribute, too divided to do anything but lower taxes.
E conomists are not sure how to fully explain the grow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The ordinary dynamics of supply and demand have certainly played a role: laborsaving technologies have reduced the demand for many “good” middle-class, blue-collar jobs. Globalization has created a worldwide marketplace, pitting expensive unskilled workers in America against cheap unskilled workers overseas. Social changes have also played a role—for instance, the decline of unions, which once represented a third of American workers and now represent about 12 percent.
But one big part of the reason we have so much inequality is that the top 1 percent want it that way.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involves tax policy. Lowering tax rates on capital gains, which is how the rich receive a large portion of their income, has given the wealthiest Americans close to a free ride. Monopolies and near monopolies have always been a source of economic power—from John D. Rockefell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to Bill Gates at the end. Lax enforcement of
anti-trust laws, especially during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has been a godsend to the top 1 percent. Much of today’s inequality is due to manip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enabled by changes in the rules that have been bought and paid for by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tself—one of its best investments ever. The government lent money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t close to 0 percent interest and provided generous bailouts on favorable terms when all else failed. Regulators turned a blind eye to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
When yo u look at the sheer volume of wealth controlled by the top 1 percent in this country, it’s tempting to see our growing inequality as a quintessentially American achievement—we started way behind the pack, but now we’re doing inequality on a world-class lev el. And it looks as if we’ll be building on this achievement for years to come, because what made it possible is
self-reinforcing. Wealth begets power, which begets more wealth. During the savings-and-loan scandal of the 1980s—a scandal whose dimensions, b y today’s standards, seem almost quaint—the banker Charles Keating was asked by a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whether the $1.5 million he had spread among a few key elected officials could actually buy influence. “I certainly hope so,” he replied. The Supreme Court, in its recent Citizens United case, has enshrined the right of corporations to buy government, by removing limitations on campaign spending.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 are today in perfect alignment. Virtually all U.S. senators, and most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House, are members of the top 1 percent when they arrive, are kept in office by money from the top 1 percent, and know that if they serve the top 1 percent well they will be rewarded by the top 1 percent when they leave office. By and large, the key executive-branch policymakers on trade and economic policy also come from the top 1 percent. Whe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receive a trillion-dollar gift—through legislation prohibiting the government, the largest buyer of drugs, from bargaining over price—it should not come as cause for wonder. It should not make jaws drop that a tax bill cannot emerge from Congress unless big tax cuts are put in place for the wealthy. Given the power of the top 1 percent, this is the way you would expect the system to work.
America’s inequality distorts our society in every conceivable way. There is, for one thing, a
well-documented lifestyle effect—people outside the top 1 percent increasingly live beyond their means. Trickle-down economics may be a chimera, but trickle-down behaviorism is very real.
Inequality massively distorts our foreign policy. The top 1 percent rarely serve in the military—the reality is that the “all-volunteer” army does not pay enough to attract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and patriotism goes only so far. Plus, the wealthiest class feels no pinch from higher taxes when the nation goes to war: borrowed money will pay for all that. Foreign policy, by definition, is about the balancing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resources. With the top 1 percent in charge, and paying no price, the notion of balance and restraint goes out the window.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adventures we can undertake; corporations and contractors stand only to gain. The rul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re likewise designed to benefit the rich: they encourage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for business, which drives down taxes on corporations, weaken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and undermines what used to be viewed as the “core” labor rights, which include the right to collective bargaining. Imagine what the world might look like if the rules were designed instead to encourage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for workers. Governments would compete in providing economic security, low taxes on ordinary wage earners, good education, and a clean environment—things workers care about. But the top 1 percent don’t need to care.
O r, more accurately, they think they don’t. Of all the costs imposed on our society by the top 1 percent, perhaps the greatest is this: the erosion of our sense of identity, in which fair pla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are so important. America has long prided itself on being a fair society, where everyone has an equal chance of getting ahead, but the statistics suggest otherwise: the chances of a poor citizen, or even a middle-class citizen, making it to the top in America are smaller than in many countries of Europe. The cards are stacked against them. It is this sense of an unjust system without opportunity that has given rise to the conflagr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rising food prices and growing and persistent youth unemployment simply served as kindling. With youth unemployment in America at around 20 percent (and in some locations, and among some socio-demographic groups, at twice that); with one out of six Americans desiring a full-time job not able to get one; with one out of seven Americans on food stamps (and about the same number suffering from “food insecurity”)—given all this,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somet hing has blocked the vaunted “trickling down” from the top 1 percent to everyone else. All of this is having the predictable effect of creating alienation—voter turnout among those in their 20s in the last election stood at 21 percent, comparable to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 recent weeks we have watched people taking to the streets by the millions to protes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oppressive societies they inhabit. Governments have been toppled in Egypt and Tunisia. Protests have erupted in Libya, Yemen, and Bahrain. The ruling familie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look on nervously from their air-conditioned penthouses—will they
第9篇宏观经济学的其他专题 第37章通货膨胀与失业 一、概念题 1.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答:菲利普斯曲线指表示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一曲线是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提出来的。这条曲线表示,当失业率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低;反之,当失业率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高。因此,如图37-1所示,横轴代表失业率(U),纵轴代表货币工资增长率(W),菲利普斯曲线(PC)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根据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货币工资增长率决定了价格增长率,所以,菲利普斯曲线也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即当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低,当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高。 图37-1菲利普斯曲线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把菲利普斯曲线作为调节经济的依据,即当失业率高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承受一定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当通货膨胀率高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借助提高失业率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论述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进一步解释不同条件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以理性预期为依据解释了菲利普斯曲线。他们既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货币主义的说法。他们认为,由于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总是一致的,不会出现短期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大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情况,所以,无论在短期或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都不存在稳定的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只能是一条垂直线。 2.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答:自然失业率又称“有保证的失业率”、“正常失业率”、“充分就业失业率”等,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起作用时,总供给和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失业率。所谓没有货币因素干扰,指的是失业率的高低与通货膨胀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 自然失业率取决于经济中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因素,取决于劳动市场的组织状况、人口组成、失业者寻找工作的愿望、现有工作的类型、经济结构的变动、新加入劳动者队伍的人数等众多因素。 自然失业率是充分就业时仍然保持的失业水平。任何把失业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企图都将造成加速的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发展的一种观点,他将长期的均衡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它可以和任何通货膨胀水平相对应,且不受其影响。
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特色是民本主义,其含义可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概括。"作之君",君王须负责民众的生育长养;"作之师",君王须负起民众的教化之责。倘若君王没能很好地"养民"以致民众不得不"自养",那么这个君王就不合格。仅仅做到"养民"而没有"教民",也还是不够的,"不教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如果君王很好地做到了"养民"和"教民",那么他就是一个"仁君",君民之间就达致理想的和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亦天下,忧亦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后世范仲淹将孟子的这种思想还推进了一步,提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民众这一面来说,"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视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荀子·富国》)自汉武帝时期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民本主义就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原则,以致两千多年后,中国的统治者依旧念兹在兹:"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子。""朕……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惮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雍正:《大义觉迷录》)民本主义的内容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所有的人分为两个群体:君和以君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治人者"),民众("治于人者");二、道德诉求是这两个群体作为政治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三、两个群体的道德诉求有所不同:"治人者"要求"爱民"("仁"),"治于人者"要求"忠君"("忠");四、道德诉求既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对方,成为带有普遍性色彩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本主义以其田园诗般的温情撩人遐想,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自古自视为"天下"的封闭圈子里,更成为人们千古不易之理想。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却与之完全相背,不仅"圣君贤相旷百世不一遇",(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中国社会历数千年,也"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严复:"《法意》按语")一旦与完全异质的西方文明碰撞,立即一败涂地。很多人在探讨个中原由,但他们的思路仍然局限在民本主义的圈子中: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说:"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聩,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不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乎,孰使之然哉!(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 [!--empirenews.page--] 在这段话中,民本主义依旧是衡量、检讨政治得失的标准,依据这样的标准,之所以有如此不幸的现实,根源在于"君"不尽责,"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没有做一个"仁君"。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聋聩",听从孔孟之言,真正成为一个爱民如子的"仁君",就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而是相反。这正是中国人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的一贯思维,究其实,还是缘于人们没有摆脱民本主义的窠臼。理性如梁漱溟者,也作如是观,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之不免于专制,并非其本意,而"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按照他的说法,这样的现实只是因为理想没有落实的缘故,倘若理想得到落实,就不会是这样的现实了。他与郑观应并无实质区别,民本主义仍然是其思维的主导。又过了许多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样式更为丰富、结果更为惨烈的"试错",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现实,原因正在于我们有那样温情脉脉的民本主义理想。我们姑且同意统治者并无建立极权专制的本意吧,但民本主义必定要导致极
第31章 总需求与通货膨胀 31.1 复习笔记 1.实际利率与资本市场 (1)实际利率与总支出 实际利率是影响总支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封闭经济中,较高的实际利率通过两条基本渠道来降低总支出:①较高的利率降低了投资的盈利性,导致厂商缩减投资项目。②消费者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较高的利率使家庭减少对新住宅和耐用消费品(例如汽车)的购买。 (2)实际利率与资本市场均衡 图31-1 实际利率与资本市场均衡 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实际利率调整将平衡储蓄和投资。当经济不处于充分就业时,储蓄和投资仍然必须平衡以保证资本市场的均衡。储蓄和投资既依赖于实际利率,也依赖于产出水平。图31-1显示了两个不同的产出水平上资本市场的均衡。当经济在充分就业水平时,储蓄和投资曲线由f S 和f I 给出。当收入从f Y 下降到1Y 时,将使储蓄曲线f S 从左移到1S 。
如果投资曲线保持不变,资本市场的均衡将出现在较高的实际利率1r 和较低的实际收入水平 上。然而,当企业在每一实际利率值缩减投资支出时,产出的下降可能使投资曲线向左移动。如果新的投资曲线是1I ,利率就是2r 。 2.总需求—通货膨胀曲线(ADI 曲线) (1)美联储的政策规则 美联储对经济的系统反应被称为货币政策规则,政策规则是美联储变动利率以对经济状况作出反应的说明。美联储所采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政策规则是:当通货膨胀上升时,美联储提高利率;当通货膨胀下降时,美联储降低利率。 (2)总需求—通货膨胀曲线(ADI 曲线) ①含义 通货膨胀与支出的反向关系被称为总需求—通货膨胀曲线(或ADI 曲线)。它显示了在每一通货膨胀水平,由收入—支出分析所决定的均衡产出水平。 ②原理 在简单政策规则下,如图31-2所示,当通货膨胀上升时,实际利率上升,总支出和产出下降;当通货膨胀下降时,实际利率下降,总支出和产出上升。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与产出的运动方向相反,它们有着反向的关系。 图31-2 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影响 ③均衡产出与ADI 曲线 对于每一通货膨胀率,ADI 曲线显示了经济的均衡产出水平。如图31-3所示,如果通货膨胀率为0 ,与均衡一致的产出水平为0Y ,在0Y ,总支出等于产出。在较高的通货膨胀
看了很多bbs上的讨论,发现大家都不说阿罗-德布鲁,而是在重复阿马蒂亚.森论证过的工作。但其实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有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之间也有不同的分工。我冒不讳,斗胆说几句。 sologram的三人经济学包括哈福德周其仁和薛兆丰,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位忠诚的FTchinese 读者?呵呵,至少加上张五常和科斯吧,没有这两位使用经济解释的路子,大概也就没有哈福德、周其仁和薛兆丰什么事情了。而对这一路的经济解释来说,逻辑上推到底,的确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对这一路有兴趣的可以偶尔去看看铅笔经济研究社https://www.doczj.com/doc/8a17218132.html,/,如果我们可以分一类的话,应该可以分到媒体经济学家这一类。 另外阿罗-德布鲁的分支与真实世界的关联甚小,可以被认为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他们不关心时事,但对经济学的理论本身有很强的感觉。钻研基本假设或者经济研究的新方法是他们的长处。这一类现在还要包括一些实验经济学家,例如神经元经济学https://www.doczj.com/doc/8a17218132.html,/subject/2063520/ 再有是政府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一些公共政策的效应问题,林毅夫,李玲等都是这一路,还包括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一路与媒体经济学家有重叠之处,例如周其仁曾经就数网竞争问题发表看法,直接参与了电信分拆的决策等。而最近沸沸扬扬的医疗体制改革,更是吸引了诸多政府经济学家的眼球。 以上三类,职业无贵贱,理论有高下。学院经济学家为另外两类经济学家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以哈福德为例,他自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我评论过他的书:https://www.doczj.com/doc/8a17218132.html,/review/1084979/他的每一个文章都来自其他人的paper作为观点支撑。 (注:还有人指出企业经济学家也应该算一类,比如投行经济学家,说实话,我觉得投行经济学家之类的那纯粹是乱说了,我之所以分类中没有这一类,是因为我认为投行向来只有经济师而没有经济学家:)) 除了这三种按照职业来分之外,还有种分类是按照研究领域来分,除了微观宏观的基础理论之外,我觉得至少有那么几类: 1,计量和数理,我觉得一般bbs上很少讨论这一块,因为写字不方便。 2,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包括经济学与伦理学,最著名的是森的那个小册子《伦理学与经济学》,以及最近的《理性与自由》。 3,经济学与心理学,以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等人的工作为基础。建立在普通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等属于这一分支。 4,经济学与生物学,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为代表,后面跟了一串研究演化的经济学者。这一路有不少做计算机模拟的学者,已经出了些很厉害的研究成果。 5,经济学与生理学,这是以上面所谓的神经元经济学为代表,其中也得益于3-4的发展,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或者说,理性决策的脑神经元表现,主要利用Fmri等技术手段来进行。 6,经济学与政治学,这一路其实是最古老的经济学传统,叫做政治经济学,新的发展是在布坎南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宪政经济学的研究,包括投票,社会选择等。
2019届湖北省武汉市毕业班2月调研文综历史试卷 【含答案及解析】 姓名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 一、选择题 1. 秦在统一前,巨贾吕不韦曾位至相国;统一后,“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发“贾人略取陆梁地(泛指桂林、象郡、南海等岭南边远蛮荒地区)”。这一现象说明秦朝 A.小农经济形成 B.工商食官出现 C.中央集权加强 D.江南得到开发 2.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窦太后好读老子书,辕固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说,这怎么能比得上你们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随后惩罚辕固“入圈刺豕(猪)”。汉景帝派人往猪圈里递进一把刀让辕固得以杀猪自存。“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这反映了汉景帝时期 A.采用儒家思想治国 B.放弃休养生息政策 C.维持无为而治思想 D.存在无为、有为之争 3. 宋朝许多蜚声中外的文学家往往是朝廷命官,如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等。这在他朝,对于整日被冗杂的政事缠身的政府官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与宋代实行官、职、 差遣分离政策,“吏强官弱”“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等有关。上述现象 A.体现了宋代重文轻武治国传统 B.反映了宋代官僚制度发生变化 C.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 D.说明了理学深刻影响宋代科举 4. 1842-1880年,中国进口以鸦片、棉布为主,出口以丝、茶为主;1881-1910年,棉布在进口贸易中的重要性超过鸦片,丝、茶出口的重要性下降。影响晚清贸易结构变化的 主要因素是 A.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 B.西方国家侵华方式的变化 C.西方社会工业革命的发展 D.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剧变
三、斯蒂格利茨和信息经济学 柯荣住 一、斯蒂格利茨的保险市场模型 (一)以自行车险为例: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完全信息下,投保人的信息为保险公司所知道,此时不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1.道德风险: 由于其行为无法被保险公司所观察到,投保人看管自行车的努力可能会因为投保而发生改变,从而可能使自行车被盗概率上升,保险公司就可能会亏损。结果是没有公司愿意提供自行车保险,即前面所说的“无交易”:社会中有帕累托有效的一些交易可能不会发生。 2.逆向选择: 每个投保人可能知道自己自行车失窃的概率,而保险公司不一定知道这种信息。那些觉得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的概率比较大的人会更有积极性投保,这样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也会变高,会更加容易亏损。同样最终这个保险市场也会不存在。 3.改进方法 A. 提高保费 斯蒂格利茨(1976):提高保费不能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消失。 提高保费时,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可能就会选择不保险,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丢车概率比较小的人,因为丢车概率越小,他所能接受的保费就越低。这时保险市场同样难以存在。 B. 分离均衡 斯蒂格利茨证明:在竞争市场上,不存在混同均衡,只存在分离均衡。这是因为保险市场存在竞争。比如保险公司A提供一种合同使这两类人都选择投保,那么总会有另外一个保险公司设计一个合同,把低丢车概率的人吸引过去。 混同均衡:使丢车概率高的人和丢车概率低的人都愿意接受的合同; 分离均衡:保单会使不同的人做不同的选择。 (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和斯宾塞的不同之处 1.斯宾塞模型
拥有信息的人如何传递信息,不拥有信息优势的人只能消极地等待拥有信息优势的人传递出他的信号。 2.斯蒂格利茨模型 不拥有信息的人可以主动设计一个菜单,来甄别不同人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必然存在均衡。 二、斯蒂格利茨的信贷市场配给模型(1981,1983) 古典经济学认为:既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能够决定利率的话,利率币供需平衡时的利率要低是偶然的短期的现象,长期来看供求平衡。 斯蒂格利茨认为:借贷市场上供求不相等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瓦尔拉斯均衡是不存在的,而实际的利率比瓦尔拉斯的均衡利率要低。 一个人借钱投资,如果投资风险很低,回报率不高,那么他会不愿意借比较高利率的钱;而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率的投资,会越有可能申请比较高利率的贷款。这时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来弥补自己的亏损,就会把那部分有稳定回报率的那部分投资者拒之门外。 银行不得不采用信贷配给,即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得到满足。这样银行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而不是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增加收入。 斯蒂格利茨除了在这两方面做出了贡献之外,还在发展经济学上,国际贸易上,关于金融市场有效假说上,都有大量的文献。 三、斯宾塞、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的理论贡献的运用 (一)契约经济学 契约经济学的运用非常广泛,如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 (二)组织设计 1.组织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设计官僚选拔机制的时候,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衷。比如老师让没做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 2.在中央集权制下,数目化管理不可实施。 人事任免权在上级官僚手中,而只要上机官僚对下级官僚的政绩是不完全信息的话,必然出现数字造假。
论经济学和相邻学科 科斯的著作《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有一篇文章谈及经济学相之于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点与研究经济学的优势。名为“经济学和相邻学科”。本文即论述科斯对于该文章的写作思路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科斯既然提及了“相邻学科”这一概念,他文章开头便陈述了“学科的边界”这一概念。是什么决定了学科之间的边界?他自己的观点是学科的边界是由竞争决定的。他认为每个领域的学者都有扩大自己研究领域并将另外领域的学者逐出的欲望。所以在两方的竞争中,学科的边界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之后解释经济学家把他们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科,及所谈论的相邻学科。 之后科斯便诠释为什么经济学家能够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所有的社会 学科,而这就是他本文所重点论述的内容。之后的论述以“提出解释——驳论——再提出解释——驳论”的方式进行分析。第一种解释是经济学家已经解决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为找到新的课题而进入其他领域。科斯提出任意经济领域不可能找不出可供研究的未解答的问题,于是解释不能接受。第二种解释是现代经济学家的兴趣更为广泛,从而扩大了研究领域。然而通过观察发现,经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的研究范围相之于现代经济学家更为广泛,现代反而更专,更精于数学演算,从而驳斥。第三种解释是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学分析方法可以构成经济学家涉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手段。经济学家的决定性优势在于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或方法是把人当作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然而一旦人们认识到这种经济学智慧,其他领域的从业者也会获得这种方法,而使经济学家失去其优势。最后,科斯提出他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的优势在于:一.经济学家把经济体系作为一个统一的、相互依赖的系统来研究,因此相对于那些不太把体系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学者相比,经济学家更可能揭示社会体系中的基本相互关系;二.经济学研究很难忽略那些在所有社会体系中都发挥重要作用的明显因素。而经济学家进入其他领域的动机在于研究其他社会科学的同时可以促进其对经济体系的研究。 在本文中科斯还穿插提到了如何定义经济学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学产生的原因是存在“学科黏合力”。即是说共同的分析技巧、共同的理论或方法以及共同的研究对象将研究不同领域的人分到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说是研究对象——即
一关于儒家的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1]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民主(democracy),就其基本的或主要的涵意而言,是指一种与君主制、贵族制相区别的由人民治理(th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政治体制(或管理形式)。我认为,儒家的民本(regarding the people as foundation)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其二,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二者合一的典型表达是皇帝起居室里的一幅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与民主是相对立的;但从价值观上说,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这一种子的萌芽表现在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的政治思想中。人权(human rights)是近代以来不断发展进化着的观念。“第一代人权”[2]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等人提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英国权利法案》(1689)、《美国独立宣言》(1776)和《法国人权宣言》(1789)是反映第一代人权思想的代表作。第一代人权主要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发表意见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生命安全和财产的权利等等。显然,第一代人权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人权观念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严复所谓“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人权又需要从民主制度得到承认和保障。就此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是否包含人权的观念,似乎不宜作出笼统的判断。民本在政治体制上与民主相对立,儒家思想中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设定,因此似可说,民本思想中没有第一代人权的观念;但就民本的价值观而言,其中也包含着第一代人权的某些因素。儒家的民本思想源于中国上古时期(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政治观。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中写道:在记载夏、商、周三代史迹的《尚书》中,政治上的最高权威是“王”,而思想观念上的最高崇拜者则是具有人格和道德意志的“天”(神)。天神所具有道德,也就是“保民”、“裕民”的道德;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也就是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民之上是王,而王是天所选择的能够秉承天的道德意志而“敬德”“保民”的统治者。天所选择的王称为“天子”,因天子能够像父母般地爱护、保护人民,所以他才能成为王。……如果王违背了天的道德意志,肆虐于人民,那么天“惟德是辅”,“改厥元子”,选择另外一个诸侯,讨伐暴君,取代他为王。我曾设了一个比喻,即:“在夏、商、周三代也潜含着三权分立的观念。因为天的意志代表民的意志,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尚书·皋陶谟》说:“天工,人其代之”,意谓统治者是代表天命而行事。就统治者必须“敬德”“保民”、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而言,我们也可说是“民工,天其代之”,亦即人民把监督、节制君王的权利委托给“天”了。在此结构中,人民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利,其意志的实现要靠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信仰或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道德自觉。[!--empirenews.page--]儒家的政治设计一直未脱夏、商、周三代的原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天神的观念受到怀疑甚至否定,统治者的私有观念也愈发膨胀,在此形势下,儒家更主要以“仁”的思想启发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寄希望于“仁者得天下”,“君仁莫不仁”,“天下定于一”。面对现实中的君主的非道德,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也主张“社稷之臣”对君主要实行“谏、争、辅、拂”(《荀子·臣道》)。孟、荀都肯定了“汤武革命”之说。但在孟子的思想中,这种“革命”的权利还是源于“天”对桀、纣的“所废”和圣王之受命(“天与之”,参见《孟子·万章上》),就一般情况而言,只有“贵戚之卿”才能“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对于“异姓之卿”,只能“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1993年出土的郭店
第三部分章节题库 第5篇宏观经济学引言 第21章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前景 一、名词解释 1.宏观经济学 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现代的经济分析方法。它以国民经济总体作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生活中有关总量的决定与变动,解释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波动、国际收支与汇率的决定与变动等经济中的宏观整体问题,所以又称之为总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中心和基础是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总需求理论、总供给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内容。 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宏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是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奠定基础,二战后逐步走向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60年代后的“滞胀”问题使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并形成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对立争论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又使国家干预思想占据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当代发展最为迅猛,应用最为广泛,因而也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学科。
2.滞胀与通货紧缩 答:(1)滞胀指经济处于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情况下的状态。滞胀最初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济状态超出了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普斯曲线所能解释的范围。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是并存的,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替的关系。滞胀现象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不呈交替关系,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不能调整滞胀状态。 (2)通货紧缩指在经济均衡的状况下,由于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货币供给锐减或银行信贷收缩等原因造成投资需求突然下降或泡沫破灭,居民财富萎缩造成消费需求突然剧减等原因使总需求下降,从而出现供给大于需求,于是物价水平显著、持续地下降。 二、判断题 1.作为基本分析工具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正如在微观经济学中一样,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处于核心地位。() 【答案】√ 【解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 2.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包含政策变量,如政府防务采购。() 【答案】√ 【解析】政策性变量,如军事支出,是已知变量,因此根据定义,它在模型中没有行为方程。同样地,考虑经济条件对军事经济的影响,这个考虑要求将军事支出的行为“模型化”,
2019届贵州省遵义市高三第一次模拟文综历史试卷 【含答案及解析】 姓名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 一、选择题 1. 在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位于亚欧大陆另一侧的欧洲西部 则普遍流行民主制度或带有民主色彩的君主制度等。其根本原因在于() A.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传统不同 B.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心理素质不同 C.中国与西方的经济结构与形式的差异 D.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 2. 春秋时期,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并订立盟约:“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 树子指古代诸侯立为世子的嫡子 ) 。这说明齐桓公 (________ ) A.挟天子以令诸侯______________ B.想要维护宗法制 C.主张废除分封制___________ D.极力推崇法家思想 3. 元代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乾隆时期 , 大部分土司被废,改为流官统治。土司制度的这一变化发展轨迹反映了() A.中央集权的强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 B.西南军务的强化 C.君主专制主义的强化_________________ D.民族融合的强化 4. 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 ( 约当今三分之一亩 ) 在平常年景, 可以产粟一石半,……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战国时期农 业的发展 (________ ) A.阻碍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____________________ B.抑制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C.导致畜力与铁制农具的使用____________________ D.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
国外经济学家言论集锦 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什么高度的持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须善于运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断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须保持着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地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认为的力量更大,事实上,世界是由少数思想统治的。掌权的疯子,道听途说,从若干年前的拙劣的学者那里获取疯狂之念。我确信,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比起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被大大地夸大了。思想的作用确实不是能立即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因为在经济和政治哲学领域,并没有多少人在25岁或30岁还会受新理论的影响,所以,公务员、政治家、甚至鼓动者所运用的思想,一般不是最新的。但或迟或早,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经济学是一门按照模式进行思维的科学,而模式本身又夹杂着艺术,这种艺术就是能选出适合当前世界的模型。……出色的经济学家十分稀少,因为要运用“有准备的观察”才能捕捉到好的模型,尽管这种天赋并不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能,但却显得十分难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成为本质上的不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什么。在他使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出得到最大的价值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对不是他个人所追求的东西。 亚当·斯密
1%的“民有、民治、民享” 编者按本文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名利场》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认为美国具备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果然,在本文发表4个月后,“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华尔街之秋”。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喊出“美国早该来一场革命了”的口号。作者于10月4日来到纽约示威者聚集地声援抗议。现将全文主要内容刊登如下: 美国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 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手中。就分配平等而言,美国落后于曾被小布什总统嘲笑过的“老的”、“僵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地位相当的是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改善穷人的困境、缩小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加剧。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合理化在19世纪中期时显得非常棘手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简言之,这一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
经济学家为什么长寿? ——浅谈经济学与人生法则 摘要:经济学家是一个长寿的群体,不是他们具有超人的体质,也不是有过人的智慧,是他们参悟了财富人生的诸多烦恼。那么经济学中蕴含哪些人生法则呢?在这个物欲横流时代,人的烦恼大都是为物所扰,了解经济学家们的人生,领悟经济学中的法则,也许对我们的人生有不少启示。 关键字:经济学,长寿,人生法则 Abstract:Economists all have a long life. The reason is not that they have strong bodies or exceptional wisdom but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wealth in life full of troubles. So what laws of life does the economics contain? Toda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stuck in seeking frame and wealth. The life of the economists and the laws of economics may give you much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economics, longevity, laws of life 正文: 有幸聆听了经济管理学院周勤教授的精彩演讲“经济学与人生法则”。周勤教授就经济学家长寿这一现象进行了探究,论述了经济学中蕴含的人生法则,聆听完毕,自觉收获良多。 从周教授统计的数据来看,69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平均寿命高达85.7岁(其中数人仍在世,按现今年龄计算),过百岁者也有几人,可见经济学家确实是一个高寿的群体。实际上,经济学家也是人生质量高的一个群体,那么他们高寿或者说人生质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经济学与人生法则这一话题。 首先,得说说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独立学科,包含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众多专业方向,并应用于各垂直领域,指导人类财富积累与创造。可以说,经济学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而又复杂高深的学科,这是由经济本身复杂多变的特性所决定的,故即使是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未必能精准地把握住经济的走向。但是经济学家往往都是出色的投资家,
第一单元测试卷 一、选择题: 1. 一位亲眼见过俄国炮兵的外国军官感叹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炮兵能达到俄国炮兵的水平。”那么彼得一世采取了哪些措施实现了强兵( D ) A.设立参政院 B.鼓励兴办手工工场 C.提倡学习西方的礼节与生活方式 D .创建常备军 2、巴西是名列全球第五的世界大国。历史上巴西曾沦为下列哪个国家的殖民地 ( D ) A.英国 B.法国 C.西班牙 D.葡萄牙 3、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主要打击的殖民国家是( B ) A.英国和法国 B.西班牙和葡萄牙 C.英国和美国 D.法国和葡萄 牙 4、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不断扩张的时期。下列各项没有反映这一历史特征的是( C ) A.日本明治维新 B.俄国农奴制改革 C.法国大革命 D.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 5、1819年,玻利瓦尔曾说:“西班牙王室对美洲大陆敲骨吸髓的掠夺性已成为过去……我们的政体应该成为一种建立在民权基础上,使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共和政体,尊重公民自由,废除奴隶制度,取消等级特权。”这表明对拉美独立运动影响最深远的是 ( C ) A. 文艺复兴 B.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C. 美国独立战争 D. 美国南 北战争 6、列宁说:“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列宁评价的是( B ) A.资本主义制度 B.农奴制改革 C.社会主义制度 D.殖产兴业 7、4.亚历山大二世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这说明沙皇推行1861年改革的直接原因是( C ) A. 解放农奴 B. 顺应资本主义发展潮流 C. 避免革命,挽救统治危机 D. 加强沙皇专制 8、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0000人……”材料显示这次改革( C ) A.使俄国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B.使俄国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C.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D.推翻了俄国沙皇专制统治
斯蒂格利茨 一、背景 从历史角度看,里程碑式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几十年内长盛不衰的情况并不鲜见。 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之来,西方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三部公认的里程碑之作。 第一部是1848年首版问世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多次重版,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中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 第二部是1890年首版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该书一直被奉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 直到1948年才出现第三部“集大成”之作,即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于2009年12月13日去世)的《经济学》。 斯蒂格利茨在在其著作中说道:100年前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时代的经济学,50年前是苏缪尔森经济学时代的经济学,他们都不是当代的经济学。 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8)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二、人物介绍 生平(1943年2月9日——) 斯蒂格利茨博士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24岁时,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的学生,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9年,36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自2000年至今,斯蒂格利茨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3年,也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成了学生会主席。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很大影响。 附:履历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 1964年,获阿墨斯特学院学士学位。 1967年,在他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搏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
经济学家需要具备的能力 转载中信出版社吴敬琏主编《比较》第一辑 如何培养最好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具有哪些标准和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在应用经济学或在经济学上作出贡献?这些问题似乎近来常常被提及。我以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三方面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 一是观察能力。很自然地,这是指经济学家要有能力在现实中观察出重大问题,规律性与决定性的问题。这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也包括历史问题。人们是否能够发现和解释历史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是否有能力解释现在。如果没能力解释历史,往往也没能力解释现在。现实问题总是非常复杂的。从学术上来说,如何找出现实或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提出一个解释,这是很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学者与非学者是如何区分的?什么是经济学者心里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想区别他们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们心里有没有一个理论的基准(benchmark)。好的经济学家要能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发现问题,寻找到疑问。也就是说有洞察力。好的社会科学家一定要有能力找到问题。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相当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所谓的问题,即是疑问。他所产生的疑问、看到的现象,有没有什么规律,能不能解释。如果没有什么规律,那就谈不上是经济学问题;如果这个规律能够被已有的道理所解释,也谈不上是问题。观察到现象,且能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这非常取决于学者心里存在的理论基准。一个学者能抓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基本上决定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重要的经济学家抓到的是重要的问题。有理论素养的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脑子里面有没有这个基准。 经济学教育中大量的内容是机械的,问题在于,怎么培养人的观察能力。这是教育中的重要问题。观察能力中,有一部分是可以培养的,有一部分是不能培养的。从经济学教育的角度,我们现在只讨论可以培养的部分。要培养出观察能力,核心的东西是脑子里要有对经济学中基准的透彻理解。当一个好的学者对经济学理论中提供的基准吃透了,这个基准就能帮助他判断什么地方是有疑问的,什么地方并不是疑问。为了讲得更通俗,可以比喻为结晶。基准就相当于一种结晶的基本结构。它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理想的、简化的结构。有这样一个结晶在脑子里,在观察现实的时候,就能依据它来判断什么问题是原有的基准解释得了的,什么是解释不了的。解释不了的问题,就可能成为是好的问题。这就是好的经济学家所要做的事情。 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人们很熟悉的科斯定理,这是科斯暑期在美国打工时发现的。他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不能解释。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念本科的时候,学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形成了他头脑中的基准。经济学告诉他,市场在理想竞争状态下是最有效率的。在理想竞争状态下,企业应该是无限小的,经济行为是由市场价格来协调的。可是,科斯观察到,在通用汽车公司,大量的交易不在市场上完成的,不靠市场价格机制来协调和运转,而是在企业内部协调的,是上下级调动的关系。什么是企业的边界?是什么决定了什么应当在市场上交易,什么不能在市场上?当时学到的经济学不可能给他好的结论。科斯虽然只是本科生,但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结晶,这就是相当于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里的厂商理论的基准。没有这个基准,就没有后来的发展。头脑里没有好的基准,就很难发现问题。头脑里有好的基准对观察能力很重要。 一个好的基准一定是抽象的、简单的。所以,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限制和经济学的指导能力时,绝不应该只由于某个理论有“不符合实际”的什么假设,就断言它是不真实的,不适用的。实际上,往往正因为好的理论做了好的重要的假设,才给了我们重要的分析力量。 二是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是理论的——其中包括数学类型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