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德国判例中的适用
- 格式:doc
- 大小:37.50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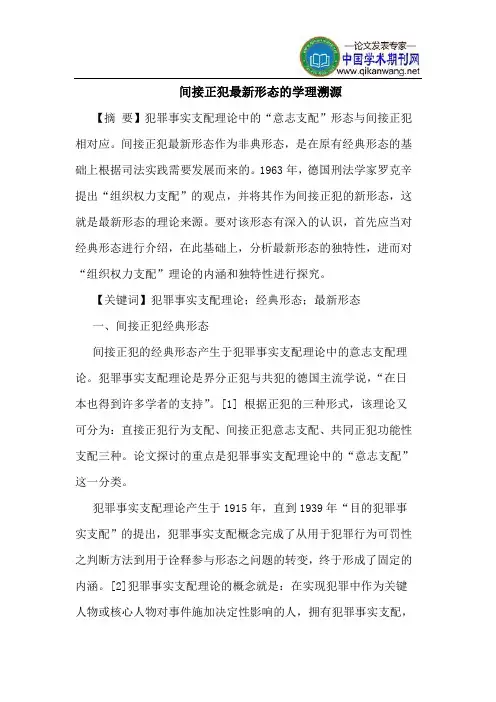
间接正犯最新形态的学理溯源【摘要】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中的“意志支配”形态与间接正犯相对应。
间接正犯最新形态作为非典形态,是在原有经典形态的基础上根据司法实践需要发展而来的。
1963年,德国刑法学家罗克辛提出“组织权力支配”的观点,并将其作为间接正犯的新形态,这就是最新形态的理论来源。
要对该形态有深入的认识,首先应当对经典形态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最新形态的独特性,进而对“组织权力支配”理论的内涵和独特性进行探究。
【关键词】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经典形态;最新形态一、间接正犯经典形态间接正犯的经典形态产生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中的意志支配理论。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是界分正犯与共犯的德国主流学说,“在日本也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1] 根据正犯的三种形式,该理论又可分为:直接正犯行为支配、间接正犯意志支配、共同正犯功能性支配三种。
论文探讨的重点是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中的“意志支配”这一分类。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产生于1915年,直到1939年“目的犯罪事实支配”的提出,犯罪事实支配概念完成了从用于犯罪行为可罚性之判断方法到用于诠释参与形态之问题的转变,终于形成了固定的内涵。
[2]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的概念就是:在实现犯罪中作为关键人物或核心人物对事件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人,拥有犯罪事实支配,并且是正犯。
它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标准,必须借助不同的事实形态加以具体化。
[3]正犯是犯罪中的核心人物,根据行为人是否对犯罪事实具有支配行为的标准,又可分为:“支配犯”、“亲手犯”和“义务犯”。
在这三种形式中,“支配犯”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后两种形式只是附带的被提及。
对于“支配犯”这种形式,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也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正如前所述,将其分为“行为支配、意志支配和功能支配”。
每一种形态都具有独特的判断标准。
通过他人实现犯罪构成要件,被称为间接正犯,这一类正犯是“意志支配”的体现。
如参与者具有纵向的前后关系存在时,对于幕后者的参与形态,必须透过意思支配基准来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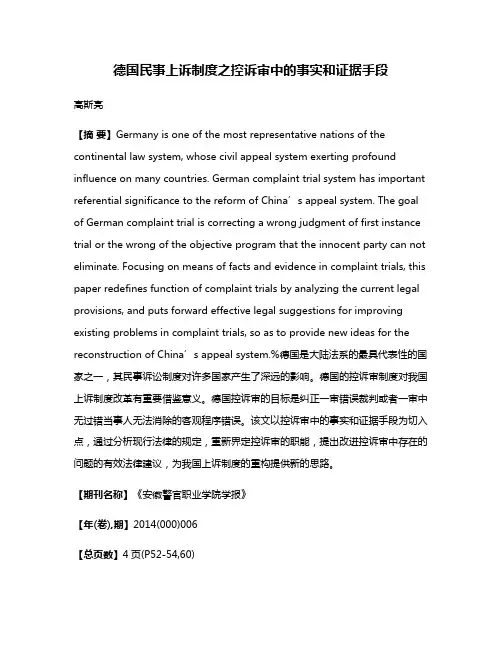
德国民事上诉制度之控诉审中的事实和证据手段高斯亮【摘要】Germany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nations of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whose civil appeal system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on many countries. German complaint trial system has importan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form of China’s appeal system. The goal of German complaint trial is correcting a wrong judgment of first instance trial or the wrong of the objective program that the innocent party can not eliminate. Focusing on means of facts and evidence in complaint trials, this paper redefines function of complaint trial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legal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existing problems in complaint trials, 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appeal system.%德国是大陆法系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其民事诉讼制度对许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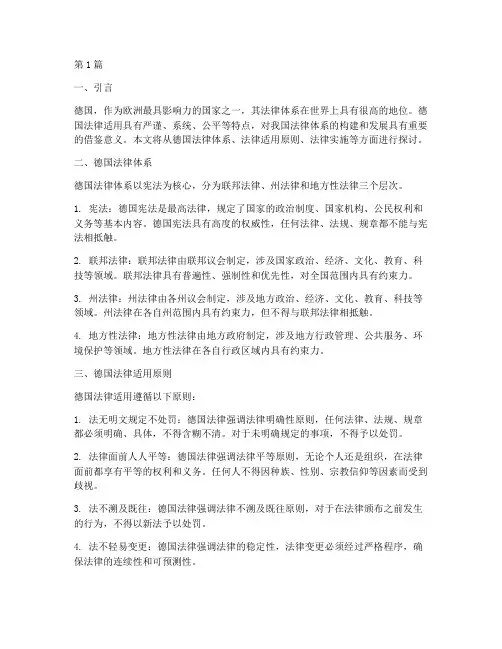
第1篇一、引言德国,作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其法律体系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德国法律适用具有严谨、系统、公平等特点,对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将从德国法律体系、法律适用原则、法律实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德国法律体系德国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分为联邦法律、州法律和地方性法律三个层次。
1. 宪法:德国宪法是最高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机构、公民权利和义务等基本内容。
德国宪法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任何法律、法规、规章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2. 联邦法律:联邦法律由联邦议会制定,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
联邦法律具有普遍性、强制性和优先性,对全国范围内具有约束力。
3. 州法律:州法律由各州议会制定,涉及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
州法律在各自州范围内具有约束力,但不得与联邦法律相抵触。
4. 地方性法律:地方性法律由地方政府制定,涉及地方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
地方性法律在各自行政区域内具有约束力。
三、德国法律适用原则德国法律适用遵循以下原则:1.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德国法律强调法律明确性原则,任何法律、法规、规章都必须明确、具体,不得含糊不清。
对于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不得予以处罚。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德国法律强调法律平等原则,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因素而受到歧视。
3. 法不溯及既往:德国法律强调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对于在法律颁布之前发生的行为,不得以新法予以处罚。
4. 法不轻易变更:德国法律强调法律的稳定性,法律变更必须经过严格程序,确保法律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
四、德国法律实施德国法律实施具有以下特点:1. 强调法律监督:德国建立了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包括宪法法院、行政法院、普通法院等。
法律监督机构对法律实施进行监督,确保法律得到正确执行。
2. 注重法律宣传教育: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法律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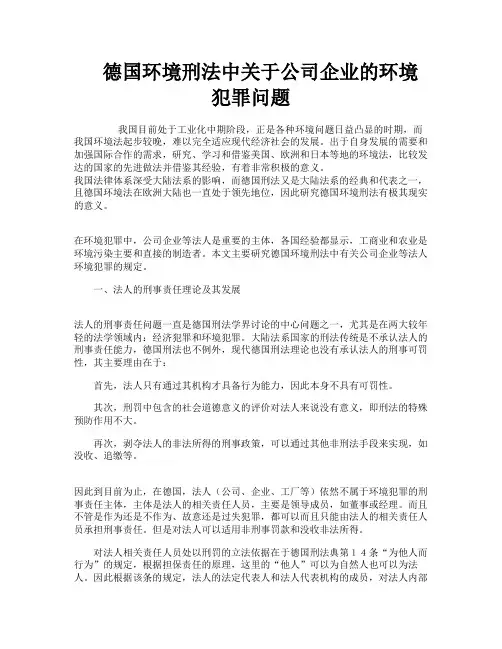
德国环境刑法中关于公司企业的环境犯罪问题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各种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期,而我国环境法起步较晚,难以完全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
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加强国际合作的需求,研究、学习和借鉴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的环境法,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先进做法并借鉴其经验,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国法律体系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而德国刑法又是大陆法系的经典和代表之一,且德国环境法在欧洲大陆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研究德国环境刑法有极其现实的意义。
在环境犯罪中,公司企业等法人是重要的主体,各国经验都显示,工商业和农业是环境污染主要和直接的制造者。
本文主要研究德国环境刑法中有关公司企业等法人环境犯罪的规定。
一、法人的刑事责任理论及其发展法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一直是德国刑法学界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在两大较年轻的法学领域内:经济犯罪和环境犯罪。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传统是不承认法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德国刑法也不例外,现代德国刑法理论也没有承认法人的刑事可罚性,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法人只有通过其机构才具备行为能力,因此本身不具有可罚性。
其次,刑罚中包含的社会道德意义的评价对法人来说没有意义,即刑法的特殊预防作用不大。
再次,剥夺法人的非法所得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其他非刑法手段来实现,如没收、追缴等。
因此到目前为止,在德国,法人(公司、企业、工厂等)依然不属于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主体,主体是法人的相关责任人员,主要是领导成员,如董事或经理。
而且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故意还是过失犯罪,都可以而且只能由法人的相关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对法人可以适用非刑事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
对法人相关责任人员处以刑罚的立法依据在于德国刑法典第14条“为他人而行为”的规定,根据担保责任的原理,这里的“他人”可以为自然人也可以为法人。
因此根据该条的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机构的成员,对法人内部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无限的担保责任;而其他法人成员,只有在受委托从事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时,才能对其下属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
![[德]金德豪伊泽尔:适应与自主之间的德国刑法教义学](https://uimg.taocdn.com/74a831bc69dc5022aaea005b.webp)

德、日刑法理论中的间接正犯摘要:间接正犯是指利用他人来实现犯罪目的的情形,是德日刑法体系中共同犯罪理论的特殊问题,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本文主要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标准及间接正犯与自手犯的关系四个方面介绍了德、日刑法中关于间接正犯的理论。
关键词:间接正犯正犯性利用人被利用人一、间接正犯的概说所谓间接正犯,是指利用他人来实现犯罪目的的情形。
从学说史上来说,间接正犯是德日刑法学者为了弥补共犯理论的不足而提出来的概念。
根据德、日刑法学最初共犯理论的通说极端从属性说,教唆犯、帮助犯的成立,要以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行为为前提。
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许多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犯罪目的的情形。
此时,被利用人的行为因不具备有责性,根据极端从属性说,利用人不成立共犯,而利用人又并未直接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不成立正犯。
但是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刑法学界便提出了间接正犯这一概念。
所以间接正犯最初仅是一个替补性概念。
而现在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正犯与共犯的关系,应是先有正犯概念,再有共犯概念,而不是因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共犯,而考虑将他视为正犯,且其成立教唆犯也并非取决于被利用人有无责任。
因此,把间接正犯看做一个替补性概念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所以学者们多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质,即间接正犯作为一种正犯的表现形式,在认定时考虑其的正犯性特征。
[1]间接正犯这一概念在理论界产生虽早,但是在刑事立法上,却仅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对间接正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大多国家的现行刑法都没有对间接正犯做出明文规定,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间接正犯无存在之必要。
尽管如此,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间接正犯仍是一个通用的理论,在共同犯罪理论中立有一席之地。
二、间接正犯的正犯性间接正犯并未直接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仅是利用他人的行为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那利用人为什么成立正犯呢?这便是间接正犯的正犯性所要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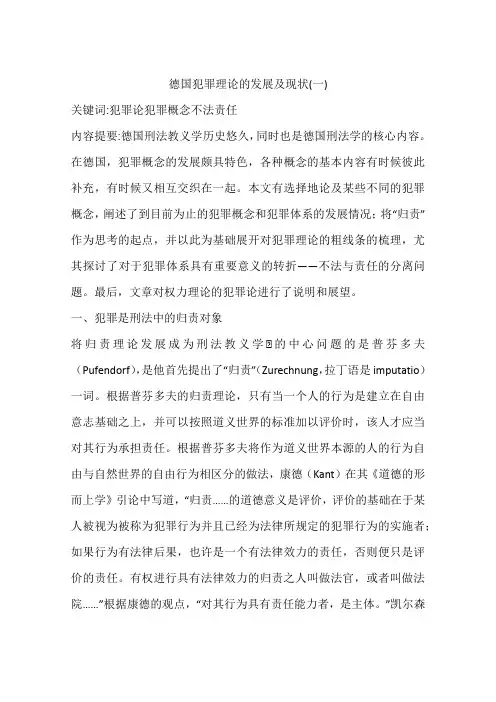
德国犯罪理论的发展及现状(一)关键词:犯罪论犯罪概念不法责任内容提要:德国刑法教义学历史悠久,同时也是德国刑法学的核心内容。
在德国,犯罪概念的发展颇具特色,各种概念的基本内容有时候彼此补充,有时候又相互交织在一起。
本文有选择地论及某些不同的犯罪概念,阐述了到目前为止的犯罪概念和犯罪体系的发展情况;将“归责”作为思考的起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犯罪理论的粗线条的梳理,尤其探讨了对于犯罪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不法与责任的分离问题。
最后,文章对权力理论的犯罪论进行了说明和展望。
一、犯罪是刑法中的归责对象将归责理论发展成为刑法教义学⑴的中心问题的是普芬多夫(Pufendorf),是他首先提出了“归责”(Zurechnung,拉丁语是imputatio)一词。
根据普芬多夫的归责理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是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之上,并可以按照道义世界的标准加以评价时,该人才应当对其行为承担责任。
根据普芬多夫将作为道义世界本源的人的行为自由与自然世界的自由行为相区分的做法,康德(Kant)在其《道德的形而上学》引论中写道,“归责……的道德意义是评价,评价的基础在于某人被视为被称为犯罪行为并且已经为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如果行为有法律后果,也许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责任,否则便只是评价的责任。
有权进行具有法律效力的归责之人叫做法官,或者叫做法院……”根据康德的观点,“对其行为具有责任能力者,是主体。
”凯尔森(Kelsen)对责任的描述略有不同:责任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要素的连结。
”费希特(Fichte)则同时论述归责与罪过:“除了对于制定法而言以外,罪过和归责没有任何意义。
强制社会利用人为的外力,以便阻止他的对大众的安全不利的动机之人,便是有罪过并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之人。
”由于归责的复杂性,因此,归责概念的背后有完全不同的意思。
例如,有时候“归责”只是部分地与行为有关,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放弃责任归属。
有人则从个性结构中寻找归责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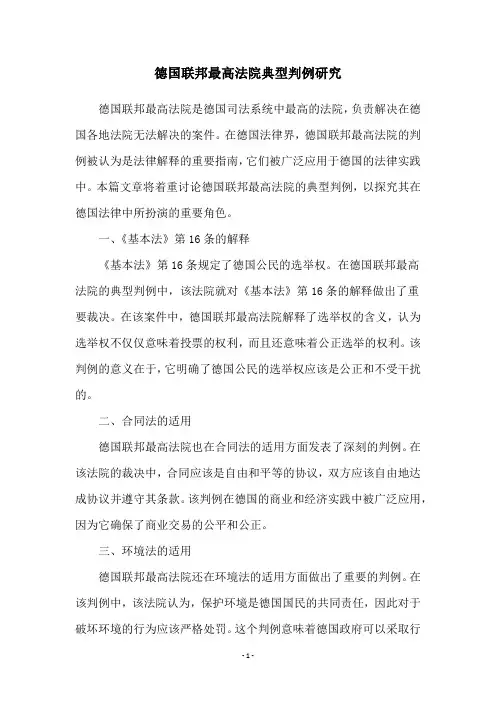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德国司法系统中最高的法院,负责解决在德国各地法院无法解决的案件。
在德国法律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被认为是法律解释的重要指南,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德国的法律实践中。
本篇文章将着重讨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典型判例,以探究其在德国法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基本法》第16条的解释
《基本法》第16条规定了德国公民的选举权。
在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的典型判例中,该法院就对《基本法》第16条的解释做出了重
要裁决。
在该案件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了选举权的含义,认为选举权不仅仅意味着投票的权利,而且还意味着公正选举的权利。
该判例的意义在于,它明确了德国公民的选举权应该是公正和不受干扰的。
二、合同法的适用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在合同法的适用方面发表了深刻的判例。
在该法院的裁决中,合同应该是自由和平等的协议,双方应该自由地达成协议并遵守其条款。
该判例在德国的商业和经济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因为它确保了商业交易的公平和公正。
三、环境法的适用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还在环境法的适用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判例。
在该判例中,该法院认为,保护环境是德国国民的共同责任,因此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应该严格处罚。
这个判例意味着德国政府可以采取行
动,以确保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性。
总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典型判例对于德国法律的发展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些判例不仅明确了德国法律的规定,而且还为德国社会提供了法律领域的指导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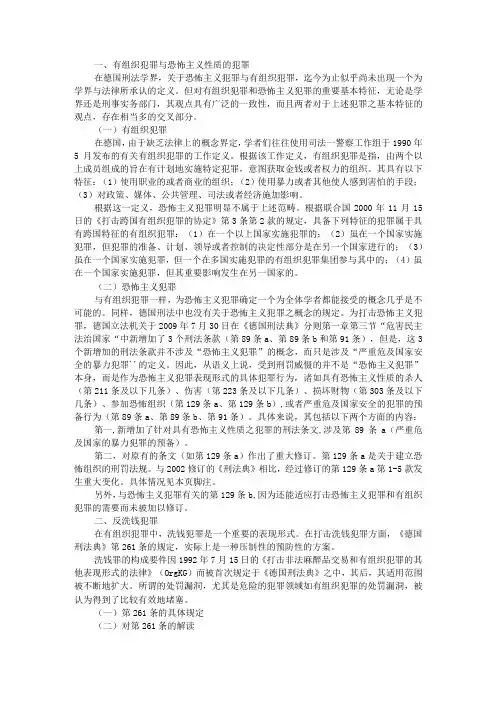
一、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在德国刑法学界,关于恐怖主义犯罪与有组织犯罪,迄今为止似乎尚未出现一个为学界与法律所承认的定义。
但对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基本特征,无论是学界还是刑事实务部门,其观点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而且两者对于上述犯罪之基本特征的观点,存在相当多的交叉部分。
(一)有组织犯罪在德国,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概念界定,学者们往往使用司法一警察工作组于1990年5月发布的有关有组织犯罪的工作定义。
根据该工作定义,有组织犯罪是指,由两个以上成员组成的旨在有计划地实施特定犯罪,意图获取金钱或者权力的组织。
其具有以下特征:(1)使用职业的或者商业的组织;(2)使用暴力或者其他使人感到害怕的手段;(3)对政策、媒体、公共管理、司法或者经济施加影响。
根据这一定义,恐怖主义犯罪明显不属于上述范畴。
根据联合国2000年11月15日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协定》第3条第2款的规定,具备下列特征的犯罪属于具有跨国特征的有组织犯罪:(1)在一个以上国家实施犯罪的;(2)虽在一个国家实施犯罪,但犯罪的准备、计划、领导或者控制的决定性部分是在另一个国家进行的;(3)虽在一个国家实施犯罪,但一个在多国实施犯罪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参与其中的;(4)虽在一个国家实施犯罪,但其重要影响发生在另一国家的。
(二)恐怖主义犯罪与有组织犯罪一样,为恐怖主义犯罪确定一个为全体学者都能接受的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德国刑法中也没有关于恐怖主义犯罪之概念的规定。
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德国立法机关于2009年7月30日在《德国刑法典》分则第一章第三节“危害民主法治国家“中新增加了3个刑法条款(第89条a、第89条b和第91条),但是,这3个新增加的刑法条款并不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而只是涉及“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定义。
因此,从语义上说,受到刑罚威慑的并不是“恐怖主义犯罪”本身,而是作为恐怖主义犯罪表现形式的具体犯罪行为,诸如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杀人(第211条及以下几条)、伤害(第223条及以下几条)、损坏财物(第303条及以下几条)、参加恐怖组织(第129条a、第129条b),或者严重危及国家安全的犯罪的预备行为(第89条a、第89条b、第91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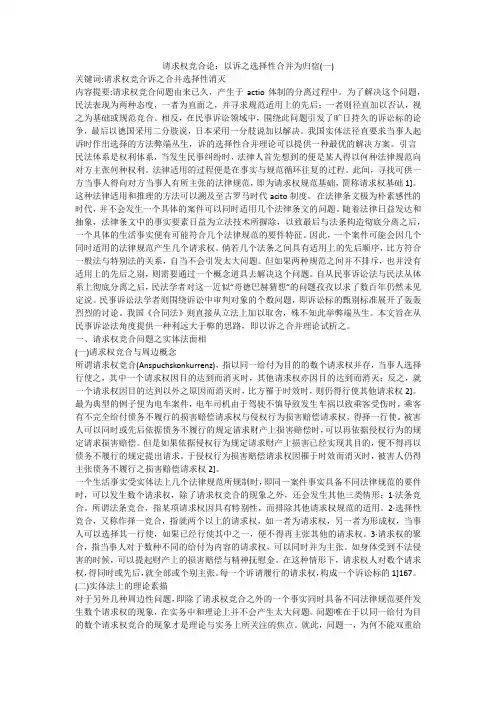
请求权竞合论:以诉之选择性合并为归宿(一)关键词:请求权竞合诉之合并选择性消灭内容提要:请求权竞合问题由来已久,产生于actio体制的分离过程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法表现为两种态度,一者为直面之,并寻求规范适用上的先后;一者则径直加以否认,视之为基础或规范竞合。
相反,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围绕此问题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诉讼标的论争,最后以德国采用二分肢说,日本采用一分肢说加以解决。
我国实体法径直要求当事人起诉时作出选择的方法弊端丛生,诉的选择性合并理论可以提供一种最优的解决方案。
引言民法体系是权利体系,当发生民事纠纷时,法律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某人得以何种法律规范向对方主张何种权利。
法律适用的过程便是在事实与规范循环往复的过程。
此间,寻找可供一方当事人得向对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1]。
这种法律适用和推理的方法可以溯及至古罗马时代acito制度。
在法律条文极为朴素感性的时代,并不会发生一个具体的案件可以同时适用几个法律条文的问题。
随着法律日益发达和抽象,法律条文中的事实要素日益为立法技术所摒除,以致最后与法条构造彻底分离之后,一个具体的生活事实便有可能符合几个法律规范的要件特征。
因此,一个案件可能会因几个同时适用的法律规范产生几个请求权。
倘若几个法条之间具有适用上的先后顺序,比方符合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自当不会引发太大问题。
但如果两种规范之间并不排斥,也并没有适用上的先后之别,则需要通过一个概念道具去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民事诉讼法与民法从体系上彻底分离之后,民法学者对这一近似“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孜孜以求了数百年仍然未见定说。
民事诉讼法学者则围绕诉讼中审判对象的个数问题,即诉讼标的甄别标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
我国《合同法》则直接从立法上加以取舍,殊不知此举弊端丛生。
本文旨在从民事诉讼法角度提供一种利远大于弊的思路,即以诉之合并理论试析之。
一、请求权竞合问题之实体法面相(一)请求权竞合与周边概念所谓请求权竞合(Anspuchskonkurrenz),指以同一给付为目的的数个请求权并存,当事人选择行使之,其中一个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时,其他请求权亦因目的达到而消灭;反之,就一个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以外之原因而消灭时,比方罹于时效时,则仍得行使其他请求权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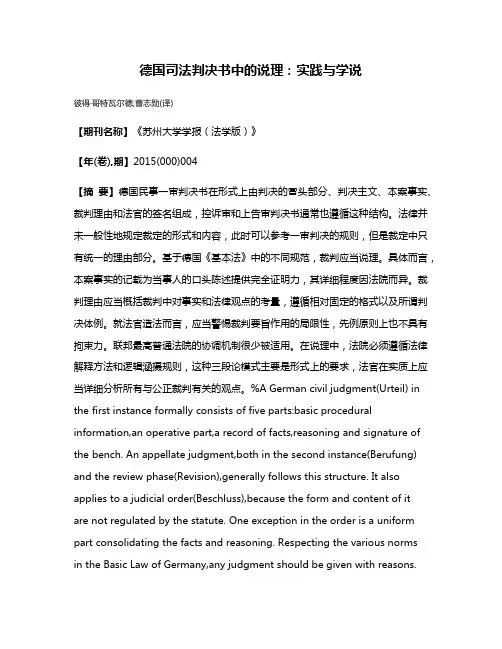
德国司法判决书中的说理:实践与学说彼得·哥特瓦尔德;曹志勋(译)【期刊名称】《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年(卷),期】2015(000)004【摘要】德国民事一审判决书在形式上由判决的冒头部分、判决主文、本案事实、裁判理由和法官的签名组成,控诉审和上告审判决书通常也遵循这种结构。
法律并未一般性地规定裁定的形式和内容,此时可以参考一审判决的规则,但是裁定中只有统一的理由部分。
基于德国《基本法》中的不同规范,裁判应当说理。
具体而言,本案事实的记载为当事人的口头陈述提供完全证明力,其详细程度因法院而异。
裁判理由应当概括裁判中对事实和法律观点的考量,遵循相对固定的格式以及所谓判决体例。
就法官造法而言,应当警惕裁判要旨作用的局限性,先例原则上也不具有拘束力。
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的协调机制很少被适用。
在说理中,法院必须遵循法律解释方法和逻辑涵摄规则,这种三段论模式主要是形式上的要求,法官在实质上应当详细分析所有与公正裁判有关的观点。
%A German civil judgment(Urteil) in the first instance formally consists of five parts:basic procedural information,an operative part,a record of facts,reasoning and signature of the bench. An appellate judgment,both in the second instance(Berufung) and the review phase(Revision),generally follows this structure. It also applies to a judicial order(Beschluss),becaus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itare not regulated by the statute. One exception in the order is a uniform part consolidating the facts and reasoning. Respecting the various normsin the Basic Law of Germany,any judgment should be given with reasons.Specifically,the factual record in the judgment should provide the oral statements of the parties’ with full probative force,while the requirement of its detail depends on the practice of the court in charge. The reasoning part is supposed to summarize the judicial consideration both on the factual and legal issues. Its internal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fixed and called Urteil-style. The function to further develop the law is for the German courts very important. However,the limitation of summarizedprinciples(Leitsätze) in the judgment should be attached attention to and existing precedents have normally no binding effect.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side the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BGH) has been rarely used. During the reasoning process,a court should follow method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rules of logical subsumption. This mode of syllogism is mainly a formal requirement. At the same time,the bench is obliged to carefully analyze all viewpoints which relate to the demand for fair trial.【总页数】10页(P83-92)【作者】彼得·哥特瓦尔德;曹志勋(译)【作者单位】德国雷根斯堡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3【相关文献】1.德国司法判决书中的说理:实践与学说简 [J], 彼得·哥特瓦尔德;曹志勋;2.基于教材解读的小学数学说理课堂的实践与研究 [J], 彭丽敏3.知”书”达”理”——基于教材解读的小学数学说理课堂的实践与探究 [J], 陈玲4.指向远算能力的小学数学说理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J], 刘红花5.基于深度学习的小学高段数学说理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J], 严青青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一、简答题1.大陆法系国家将不作为犯罪区分为真正(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真正(不纯正)不作为犯。
真正的不作为犯与不真正的不作为犯的特征是:真正的不作为犯刑法明文将不作为规定为构成要件要素,常采用“没有、不、拒绝”之类的表述,而不真正的不作为犯刑法没有明文将不作为规定为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了通常由作为实施的构成要件。
2.英美法系中的严格责任是在风险社会的概念下,凡是参与风险行为的人,即使没有故意与过失,也要承担责任。
但是,从道德上说,惩罚一些意外造成社会危害而不是基于自己意志造成了社会危害的人是不正当的,因为这种做法只是将行为人当作了工具,而没有尊重认为人的人格,国民也没有自由可言,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也遭到了反对。
“现代很多刑法学者都不很看好摒弃犯罪心理要件的主张”。
3.间接正犯是指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来实施犯罪,自己不参与实行行为(即犯罪事实支配)。
可以将间接正犯分为:①被利用者欠缺构成要件的特定要素的间接正犯,例如:利用他人反射举动或者梦游中的动作来实施犯罪的;②被利用者具有违法阻却事由的间接正犯,例如:利用他人正当防卫行为实施的犯罪、利用被害人自我侵害行为实施的犯罪;③利用被利用者欠缺责任的行为利用无责任能力者的行为、利用欠缺目的和故意的行为、利用他人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行为。
4.行为无价值是对于与结果切断的行为本身的样态所作的否定评价。
其是相对于结果无价值而言的,行为无价值的“行为”是指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内容,“无价值”是指行为违反社会伦理秩序或者行为缺乏社会相当性,行为违反法律规范。
故行为无价值认为故意与过失是主观违法性的要素。
一元的行为无价值认为行为的目的、故意、过失决定了行为的违法性,法益侵害以及危险对违法性没有实质意义。
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存在有的以行为无价值为基础有的则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的不同主张。
5.被害人承诺是指在被害人请求或者许可行为人侵害其法益,表明被害人放弃了该法益,放弃了对该法益的保护。
德国刑法理论中原因自由行为之处罚根据德国刑法理论中原因自由行为之处罚根据一、处罚原因自由行为的疑虑所谓原因自由行为,指在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一时陷入丧失或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
在原因自由行为的界定上,依其事实基础,可将其划分为两个行为阶段:出现时间在前者为原因行为,在后者为结果行为。
原因行为是行为人在其具备完全责任时,因故意或过失自陷精神障碍之行为,而由于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在此时是饱满的状态,并未受到消减,因而称其原因是自由的。
然而行为人在此精神障碍状态下,所实施的满足构成要件之行为,由于其此时是处于心神丧失或精神耗弱之中,因此可认为结果行为在实行时是不自由的。
此类行为,虽然在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时刻,行为人并不具备自由决定的责任能力,但就先前的原因行为而言,却是基于具有自由决定的状态,因而称为原因自由行为。
国家刑罚权的发动需以罪责之存在为前提,即无罪责无刑罚,作为现代刑法的出发点,统称为罪责原则或责任原则。
而刑法要求的罪责是行为罪责,因此在企图发动刑罚权时应当考虑特定行为之罪责。
再者,何种行为属于刑法关心的犯罪行为,对这些行为应该施加何种法律效果,皆应该由立法者加以确立,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表现,配合上“无罪责就无刑罚”的思考,构筑成刑法规范的可罚性界限。
罪责原则的基础思想,是建立在人有自由意思之前提。
也就是说,罪责是以行为人的判断能力为基础的,即其在自由状态下,正确判断并辨别合法与不法的能力,此为行为人之自由意思,在此自由意思的基础上,才会生出罪责非难的基础。
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负担罪责的能力,包括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
有无责任能力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并且是以行为时作为判断时点。
责任能力是成立罪责评价时不可或缺的要件,行为人若没有责任能力,则无法成立犯罪,也就不可能对其施以刑罚制裁,此为行为与罪责同时存在原则的必然要求。
基本概念和术语之概述一、德国刑法的思想体系德国刑法是以教义为主导的,与采用案例分析为方法的的英美刑法或普通法系的刑法体系有所不同。
然而事实是近几十年来,英美法系中议会立法取得了长足发展,英美法系在传统上是依赖于法官在个案中的判断而得以不断发展。
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的适用要经过外行以及陪审员、法官的使用,十分强调法律与法官所称谓的“常识”之间的紧密联系。
下面讲了一个故意醉酒对被告人犯罪意图的影响,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不同的法系对相同观点接受的不同路径;一些杰出的的学者是根据逻辑来支撑其论点。
不管是特别意图还是一般意图,仍然是意图。
如果承认通过喝酒或嗑药而使自己意识不清,进而可以否定特定犯罪故意的存在,例如杀人和盗窃。
那么如何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其不能否定一般故意的存在,如殴打和非法伤人的故意。
答案是不能论证的。
而这种观点亦为普通法系中的英格兰所接受,它不是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依据常识和经验。
在19世纪当法院要放宽醉酒对刑事责任能力影响,甚至建议由于醉酒导致精神病而免除罪责时除非能够证明具有特定目的,这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引用的。
程序规则重要性的类似争论在国际层面上被澳大利亚法官戴维·亨特提出,戴维·亨特法官曾是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普通法的首席法官,是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针对被控犯下战争罪的前塞尔维亚总统米鲁蒂诺维奇和其他人时提出的。
当时他说的是检方的控告,他不再依据控告而作出司法判决:程序与证据规则的设立是庭审的仆人的而不是庭审的主人。
在德国法律制度下,没有事物可以背离真想更远,即是说离真相更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国法律中广泛运用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
忽视的事实是德国刑法的发展受到对法律原则的司法推理影响,特别是宪法法院或联邦最高法院的层面的司法推理。
学术著作对德国刑法学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基于德国一种法律评论的文化氛围。
数百年来,德国学者和法律实务者生产出了大量而复杂的,在不同法领域的法律评论。
从“德国诉意大利”案看国家主权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学号:***************学院:国际法学院专业:法学指导老师:***联系方式:188****5334从“德国诉意大利”案看国家主权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摘要:国家主权豁免与强行法的冲突一直以来为国际法学界所关注,2012年9月,国际法院对“德国诉意大利”一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德国于二战期间入侵意大利,并对意大利公民所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役的行为虽然触犯国际强行法,但因享有国家豁免权而最终不承担相应责任。
单从两个规则的法律位阶来看,二者之间似乎不应出现冲突,但是实践中无论是欧洲人权法院、还是国际法院所做出判决都最终认为违反强行法的行为不影响国家享有的主权豁免权。
此次国际法院也再次以其判例认定了“违反强行法不能作为国家主权豁免例外”的规则。
伴随着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国际法学界对于强行法的研究开始侧重于侵害基本人权的国际犯罪领域。
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呼吁建立新的习惯法规则,强调遵循国际法的规则体系。
为此,本文欲从“德国诉意大利”一案,探讨国家主权豁免和强行法的关系。
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国家主权豁免的基本概念和本案相关案情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介绍强行法的法律地位和近年的发展;第三部分通过对本案中国际法院的判决进行分析,探讨国家主权豁免对强行法的挑战。
Abstract:It has been a concern among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about the confliction of Sovereign immunity with jus cogens. In September 2012,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entered a final judgment on the case, " Germany v. Italy". The court held that although Germany’s actions as invading Italy during World War II, putting Italiancitizens imprison and forcing people working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t did not need to assum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since Germany enjoyed State immunity.It seems there should not b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party according to the legal hierarchy of the two rules, but in practice, whether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r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verdict, in their final acts, that violating jus cogens does not affect the countries’ privilege of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And in this cas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nce again cognizance the rule that a viola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not the exception of jus cogens in its preceden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law scholars began to study jus cogens focused on areas of international crime against basic human right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begun to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rules of customary law and abiding by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an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law of sovereign immunity and jus cogens in the light of "Germany v. Italy" case.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introduce to the basic concept of national sovereign immunity and the relevant facts in this case; the second part mainly discusses the legal status of jus cogens an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third part will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of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and jus cogens from analyzing the preced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关键词:国家主权豁免强行法德国诉意大利费里尼诉德国Key words: State sovereign immunity jus cogens Germany v. Italy Fellini v. Germany目录摘要 (2)绪论 (5)正文 (6)一、国家主权豁免的概念 (6)(一)国家主权豁免的定义和性质 (6)(二)从“绝对主权豁免”到“相对主权豁免” (7)(三)“费里尼诉德国”案中,意大利宪法法院认定德国不享有主权豁免 (8)二、国际强行法的法律地位.................................. 错误!未定义书签。
德国的犯罪理论体系一、引言德国和日本的犯罪理论体系都是以构成要件为中心构建的构成要件理论体系。
这是德、日犯罪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无论在德国或者在日本,都可以把构成要件理论体系等同于犯罪理论体系,它们的含义是完全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构成要件概念的沿革一、Constare de delicto的概念二、Corpus delicti的概念作为程序意义的证明犯罪行为的全部客观事实就是所谓的Corpus delicti的最初含义。
它只是诉讼法上的概念,其意义主要是用于证明客观犯罪事实的存在,强调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证据法则得来的确证,就不得进行特殊纠问。
三、费尔巴哈、斯蒂贝尔的Tatbestand概念最早将Corpus delicti译成德语Tatbestand(构成要件)的,是克莱因(Klein)。
泷川幸辰教授说:“首先把构成要件当作刑法上的概念来使用的,是克拉因1796年的著作”费尔巴哈(Feuerbach 1775-1833)首先明确地把构成要件作为刑法上的概念来使用。
费尔巴哈是心理强制说的创始人。
斯蒂贝尔教授(Stüebel)说:“构成要件就是那些应当判处法律所规定的刑罚的一切情况的总和”。
在这里,构成要件这个概念,也是指犯罪成立条件的总体。
还有贝尔纳(Berner)、弗兰克(Frank)、弗罗伊登塔尔(Freudenthal)等人。
但在整个19世纪,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却非常缓慢,关于构成要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成要件的概念;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的区别;主观的构成要件与客观的构成件的区别等问题上。
四、贝林的Tatbestand概念20世纪初,贝林认为,所谓构成要件,就是指刑法分则(罪状中)所具体描述的各种犯罪类型要件,是“特别构成要件”。
他指出,“构成要件,从狭义上说,就是表明犯罪类型轮廓的全部要素(特别构成要件)。
”在贝林那里,构成要件不是犯罪成立的诸要件的总体(或者说总和),而只是刑法分则(罪状中)所具体描述的各种犯罪类型的要件。
浅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德国判例中的适用 摘要: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最初进入德国判例时,主要是用来限制极端的主观理论,没有独立的地位。之后至今,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也即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支配和主观利益理论,成为区分共同正犯与共犯的主流理论。但由于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分明确贯彻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而且支撑判例中主观理论的法政策背景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有望在德国未来的司法判例中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主观理论/德国判例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Tatherrschaftlehre)又被翻译为行为支配理论、行为控制理论、犯罪支配理论,是德国刑法理论界区分正犯与共犯①的绝对主导性理论,在我国大陆得到了著名刑法学者张明楷等之赞同,在我国台湾得到了林山田、蔡墩铭、韩忠谟等之认可。由于“德国刑法是一种有体系的刑法,主要以判例为根据,也就是根据过去已经作出判决的真正案件来与其他法律制度加以区别。……德国刑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通过立法和学术,而且是通过司法判决来向前推动的;《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一套多达50卷的汇编,是每个刑法工作者,同时也是学生们经常使用的。”(p3)可见,德国虽然是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但是判例在德国也颇为发达,并且对法律制度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考察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判例中的适用情况,以期全面掌握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的概貌。笔者以为,综观德国刑法判例,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德国判例中的适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限制极端主观理论;第二阶段,综合考量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和主观利益理论;第三阶段,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有望成为司法实务界的主导观点,而这一阶段还只能说是一种趋势,是笔者在分析相关判例及刑事政策背景后得出的结论。 一、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极端主观理论的限制 在正犯与狭义共犯的区分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最初从纯粹的主观理论出发,继帝国法院“澡盆案”之后通过运用空洞的意志公式或者采纳利益说来确定正犯,但同时从1950年开始犯罪事实支配概念越来越多地涌入司法判例,并且与各种不同的意义相关联。 援引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的首创判例当属第三裁判委员会1950年11月21日的判决。(p90)这一判决涉及的问题是,亲手实现所有构成要件要素的人是否可能是帮助犯。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行为人的意志完全从属于他人,听任该他人具有完全的犯罪事实支配,那么即使他通过自己的行为完全实现了所有构成要件要素,仍然可能成立帮助犯。很明显,在此犯罪事实支配概念只应从主观上理解为有利于故意理论所确立的从属标准的复苏,在此犯罪事实支配概念被用来为主观意图进行辩解。这一结论,即某人虽然负有罪责地亲手实现了所有构成要件但仍然可能缺少正犯的品质,通常几乎被所有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的追随者明确反对,稍后甚至同样被援引它的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反对。 1952年2月12日(p91)第一裁判委员会的著名判决首次从根本上运用客观的犯罪事实支配思想修正主观上的苛求。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没有阻止丈夫自杀的妻子,能否由于不作为的杀人而受到刑罚处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故意理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他人意志决定的服从,在义务的事实支配面前,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在此正犯意志的缺乏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妻子的帮助义务意味着客观上妻子对丈夫自杀后果的犯罪事实支配,妻子应以正犯的身份承担责任。 从上述判例可知,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进入司法判例以来,其主要用来限制极端的主观理论,也就是用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改造极端的主观理论。而且就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的运用来看,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有时立足于主观理解犯罪事实支配,有时却立足客观理解犯罪事实支配;有时同一法院对相似的案件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有时不同法院对性质相同的案件采取迥然不同的立场。但是判例不能因为其立场的摇摆不定受到责难,因为这恰好反映了学科上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混乱状况。从19年Welzel确立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以来直至1963年Roxin提出其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之前,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明显带有主、客观区分理论的痕迹,他们无非是在主、客观理论上做文章,并时而遵循主观理论,时而遵循客观理论,或者将主观理论和客观理论综合起来,有的甚至只是做了术语上的改变,实质上是新瓶装旧酒,并没有超出主、客观理论的窠臼。由于在这一阶段犯罪事实支配思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用于确定正犯还不清楚,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最新判决②又认为正犯同样可能没有犯罪事实支配;即便在运用犯罪事实支配概念的判决中,也不能清楚获悉就内容而言他利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完成,因此这阶段很难确定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对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明确鲜明的立场,也不可能展现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判例中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路径。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司法判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仅仅作为论证主观理论的一个附属理论而已。因此虽然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已经涌入了司法实践领域,但是司法实践领域区分正犯与共犯的主导观点仍然是主观理论。
二、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与主观理论的综合考量 1963年Roxin多元正犯下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为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赢得了主导性的地位。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公布了某种程度上有效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判决。从这些判决中可以发现,联邦最高法院正逐渐防止仅依正犯意志加以区分的纯粹主观理论,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发展而来的标准正逐渐渗入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p642-643)在这些判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判例,其依据价值的总体考察进行判断,据此犯罪利益,犯罪参与的着手,犯罪事实支配或者成立犯罪事实支配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意思被视为区分正犯与共犯的重要依据。这即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张明楷教授一改以往将主观理论视为德国审判实践通说的认识,(p291)现在认为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是德国判例的立场。(p303)由于“犯罪事实支配的意思”和“犯罪参与的着手”原本只是犯罪事实支配的前提条件,由此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主观理论和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的综合,“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成为当今德国司法判决的两个核心标准。在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集于一身时,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没有适用上的阻碍,但是当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分离时,法院又将如何协调或取舍呢?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到底孰轻孰重呢? 在第二刑事裁判委员会1987年2月6日作出的一起抢劫案判决(p601)中,被告人A和W计划在法兰克福的社会车站抢劫并预计至少可以
分赃3万马克,W利用武器抢钱而A一同前往以确保W的安全,但是在离车站入口处几米A丧失了勇气,于是W单独实施了犯罪,犯罪得逞之后A又与W结伴而行共同乘坐市区有轨电车。联邦最高法院虽然也以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为基础,仔细斟酌各个要素,但是认为A在实行阶段没有予以犯罪加担,没有共同支配实行行为,因此仅仅将其视为帮助犯。可见联邦最高法院仅仅依靠是否共同支配实行行为来区分共同正犯与帮助犯,犯罪事实支配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 在第一刑事裁判委员会1984年11月6日有关抢劫的判决(p594)中,尽管被告人在实行阶段的犯罪加担非常重要,尽管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否认被告人对实行行为的共同支配,但是仍然判处其为纯粹的帮助犯,因为其是基于其同伙的持续的欲望而表示愿意共同抢劫,自己对犯罪结果没有重大利益。在此“犯罪利益”标准明显优于犯罪事实支配标准。 从上述判例可知,在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分离时,规范的综合理论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时而犯罪事实支配起决定性作用,时而犯罪利益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没有确定统领性的原则,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极大,或多或少由法官决定是偏向犯罪利益标准还是犯罪事实支配标准,因而造成这一理论适用上的混乱。在偏向犯罪事实支配标准的判例中,通常将犯罪事实支配限制在实行阶段。在偏向犯罪利益标准的判例中,法院要么在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中择优选择犯罪利益,要么将并不存在犯罪事实支配的情况认定为具有犯罪事实支配,往往不是犯罪事实支配的实质内涵决定犯罪事实支配的存否,而是根据犯罪利益的需要决定犯罪事实支配的存否。可见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虽然综合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区分正犯与共犯,但是当两者不能协调一致时,有时法院为了既偏向犯罪利益又贯彻综合的判断理论不得不在形式上靠近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而在实质上远离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其实偏向犯罪利益标准还是偏向犯罪事实支配标准并不成问题,最关键的是这往往取决于法官不可审查的裁量决定,不是由法律决定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而是由法官的不可审查的裁量决定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因此这一理论的最大缺陷始终在于,犯罪利益和犯罪事实支配分离时,哪个要素应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不清楚。 三、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有望占据主导地位 从前述分析中似乎可以认为,德国司法实务界从主观区分理论转向了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由限制主观理论的工具变成了与主观理论的综合考虑,并在有些判例中置于主观理论之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趋势显然提升了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司法实务界的地位,确立了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司法判例中的独立“人格”。但是与此同时在相当多判例中仍然以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为幌子,践行主观区分理论。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是否能超越主观理论,超越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成为司法实务界的主导性立场呢?笔者以为这完全有可能,除了学理上的支持,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窥见这一趋势。 (一)司法判例层面。 虽然有人认为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是当前德国判例的立场,也确实有不少判例采取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但是仔细斟酌采取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的案例实际上主要关系到共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因此认为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在共同正犯的确定中属于支配性观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其是否为当今司法实务界区分正犯与共犯的主流观点仍然值得商榷,这有待考察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领域的区分状况。 1.在直接正犯方面可以确定,在这期间联邦最高法院毫无例外地承认,亲手实现构成要件的是正犯,而且同样毫无例外地以实行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支配为成立正犯的基础。继1962年Staschynskij判决采纳主观共犯论之后,第三裁判委员会于1986年的一起偷税案(p600)首次再度致力于“亲手实现构成要件是否必然成立正犯”这一问题的探讨。案件中,被告人从外在形式上颇似主,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