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代表作中主人公分析
- 格式:pdf
- 大小:133.9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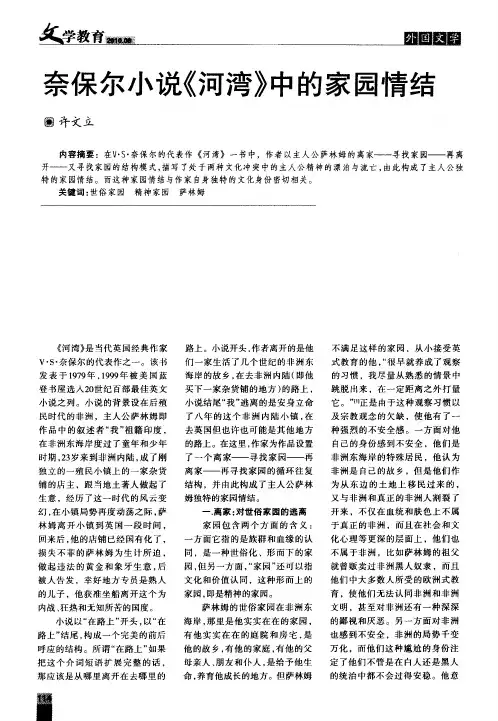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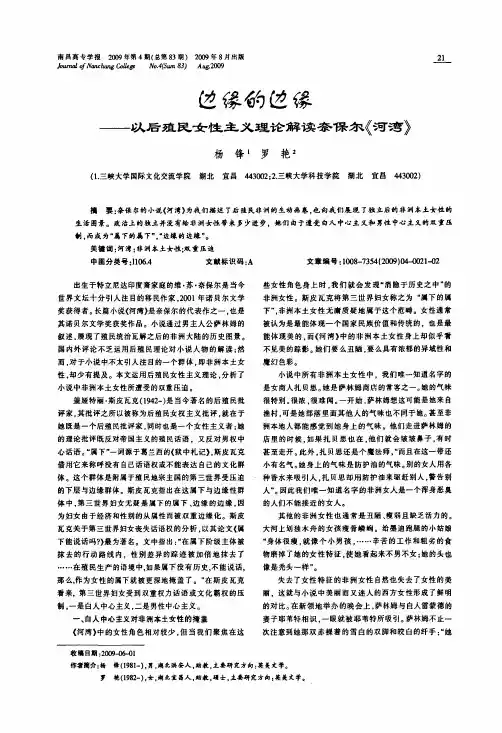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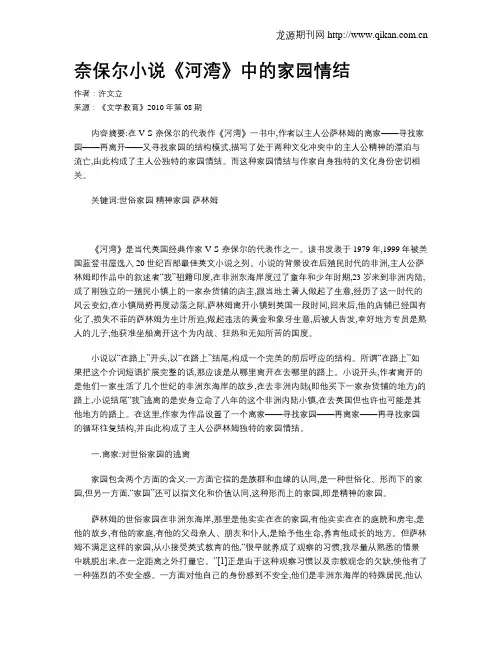
奈保尔小说《河湾》中的家园情结作者:许文立来源:《文学教育》2010年第08期内容摘要:在V·S·奈保尔的代表作《河湾》一书中,作者以主人公萨林姆的离家——寻找家园——再离开——又寻找家园的结构模式,描写了处于两种文化冲突中的主人公精神的漂泊与流亡,由此构成了主人公独特的家园情结。
而这种家园情结与作家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
关键词:世俗家园精神家园萨林姆《河湾》是当代英国经典作家V·S·奈保尔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发表于1979年,1999年被美国蓝登书屋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列。
小说的背景设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主人公萨林姆即作品中的叙述者“我”祖籍印度,在非洲东海岸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23岁来到非洲内陆,成了刚独立的一殖民小镇上的一家杂货铺的店主,跟当地土著人做起了生意,经历了这一时代的风云变幻,在小镇局势再度动荡之际,萨林姆离开小镇到英国一段时间,回来后,他的店铺已经国有化了,损失不菲的萨林姆为生计所迫,做起违法的黄金和象牙生意,后被人告发,幸好地方专员是熟人的儿子,他获准坐船离开这个为内战、狂热和无知所苦的国度。
小说以“在路上”开头,以“在路上”结尾,构成一个完美的前后呼应的结构。
所谓“在路上”如果把这个介词短语扩展完整的话,那应该是从哪里离开在去哪里的路上。
小说开头,作者离开的是他们一家生活了几个世纪的非洲东海岸的故乡,在去非洲内陆(即他买下一家杂货铺的地方)的路上,小说结尾“我”逃离的是安身立命了八年的这个非洲内陆小镇,在去英国但也许也可能是其他地方的路上。
在这里,作家为作品设置了一个离家——寻找家园——再离家——再寻找家园的循环往复结构,并由此构成了主人公萨林姆独特的家园情结。
一.离家:对世俗家园的逃离家园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族群和血缘的认同,是一种世俗化、形而下的家园,但另一方面,“家园”还可以指文化和价值认同,这种形而上的家园,即是精神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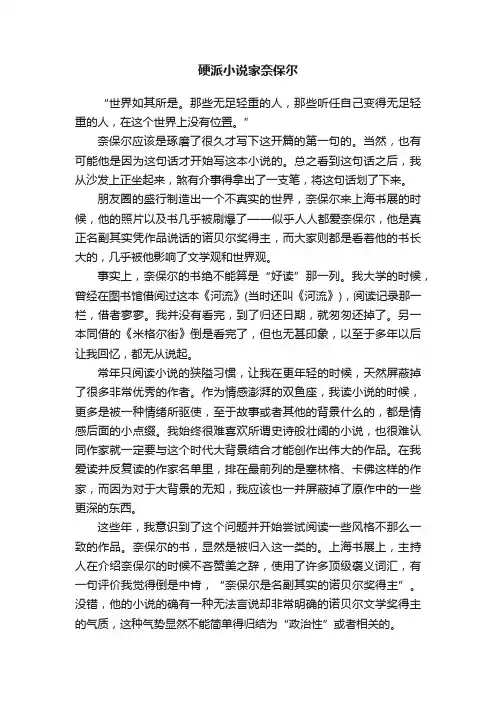
硬派小说家奈保尔“世界如其所是。
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奈保尔应该是琢磨了很久才写下这开篇的第一句的。
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因为这句话才开始写这本小说的。
总之看到这句话之后,我从沙发上正坐起来,煞有介事得拿出了一支笔,将这句话划了下来。
朋友圈的盛行制造出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奈保尔来上海书展的时候,他的照片以及书几乎被刷爆了——似乎人人都爱奈保尔,他是真正名副其实凭作品说话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大家则都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几乎被他影响了文学观和世界观。
事实上,奈保尔的书绝不能算是“好读”那一列。
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在图书馆借阅过这本《河流》(当时还叫《河流》),阅读记录那一栏,借者寥寥。
我并没有看完,到了归还日期,就匆匆还掉了。
另一本同借的《米格尔街》倒是看完了,但也无甚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让我回忆,都无从说起。
常年只阅读小说的狭隘习惯,让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天然屏蔽掉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者。
作为情感澎湃的双鱼座,我读小说的时候,更多是被一种情绪所驱使,至于故事或者其他的背景什么的,都是情感后面的小点缀。
我始终很难喜欢所谓史诗般壮阔的小说,也很难认同作家就一定要与这个时代大背景结合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在我爱读并反复读的作家名单里,排在最前列的是塞林格、卡佛这样的作家,而因为对于大背景的无知,我应该也一并屏蔽掉了原作中的一些更深的东西。
这些年,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尝试阅读一些风格不那么一致的作品。
奈保尔的书,显然是被归入这一类的。
上海书展上,主持人在介绍奈保尔的时候不吝赞美之辞,使用了许多顶级褒义词汇,有一句评价我觉得倒是中肯,“奈保尔是名副其实的诺贝尔奖得主”。
没错,他的小说的确有一种无法言说却非常明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气质,这种气势显然不能简单得归结为“政治性”或者相关的。
《大河湾》其实是在奈保尔写完了《米格尔街》,写完了《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写完了《模仿者》、《游击队员》等一系列涉及到移民者身份认同的小说后的一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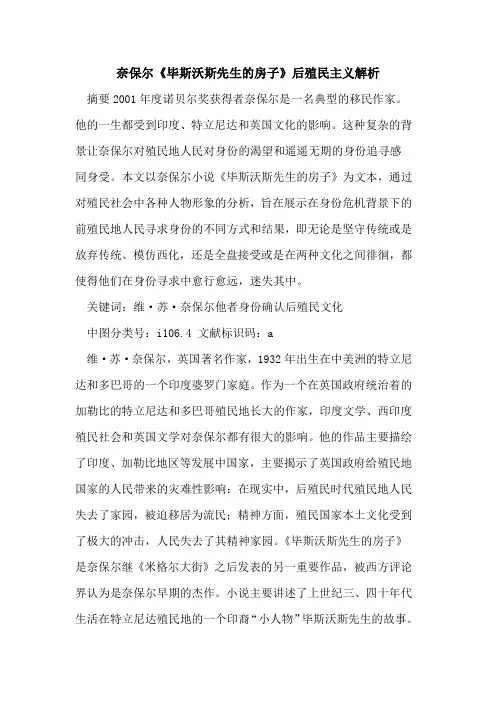
奈保尔《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后殖民主义解析摘要2001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奈保尔是一名典型的移民作家。
他的一生都受到印度、特立尼达和英国文化的影响。
这种复杂的背景让奈保尔对殖民地人民对身份的渴望和遥遥无期的身份追寻感同身受。
本文以奈保尔小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为文本,通过对殖民社会中各种人物形象的分析,旨在展示在身份危机背景下的前殖民地人民寻求身份的不同方式和结果,即无论是坚守传统或是放弃传统、模仿西化,还是全盘接受或是在两种文化之间徘徊,都使得他们在身份寻求中愈行愈远,迷失其中。
关键词:维·苏·奈保尔他者身份确认后殖民文化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维·苏·奈保尔,英国著名作家,1932年出生在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
作为一个在英国政府统治着的加勒比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殖民地长大的作家,印度文学、西印度殖民社会和英国文学对奈保尔都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主要描绘了印度、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揭示了英国政府给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在现实中,后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失去了家园,被迫移居为流民;精神方面,殖民国家本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民失去了其精神家园。
《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继《米格尔大街》之后发表的另一重要作品,被西方评论界认为是奈保尔早期的杰作。
小说主要讲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特立尼达殖民地的一个印裔“小人物”毕斯沃斯先生的故事。
毕斯沃斯先生为了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奋斗了一生。
他的人生经历象征着广大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普遍困境,同时也可以被视作是对泛人类的无根漂泊和寻求归属感的人群的写照。
一殖民文化中的他者后殖民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他者”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
然而,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复杂的,仍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但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东方”,即被殖民的一方,是“在西方人对熟悉的事物的藐视和对新奇事物的狂喜或恐惧之间摇曳不定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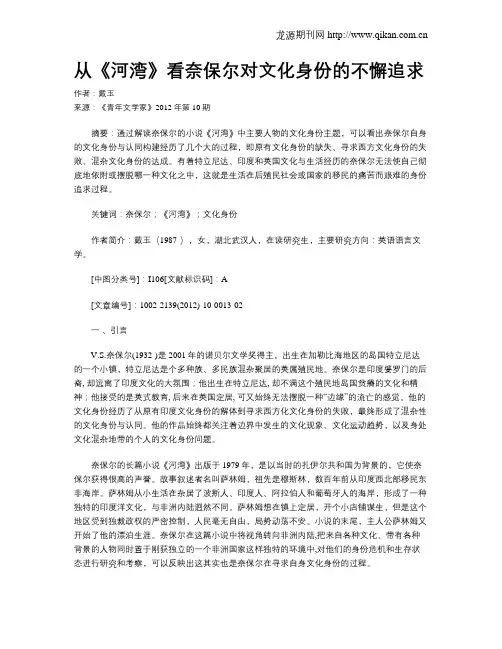
从《河湾》看奈保尔对文化身份的不懈追求作者:戴玉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0期摘要:通过解读奈保尔的小说《河湾》中主要人物的文化身份主题,可以看出奈保尔自身的文化身份与认同构建经历了几个大的过程,即原有文化身份的缺失、寻求西方文化身份的失败、混杂文化身份的达成。
有着特立尼达﹑印度和英国文化与生活经历的奈保尔无法使自己彻底地依附或摆脱哪一种文化之中,这就是生活在后殖民社会或国家的移民的痛苦而艰难的身份追求过程。
关键词:奈保尔;《河湾》;文化身份作者简介:戴玉(1987-),女,湖北武汉人,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0-0013-02一、引言V.S.奈保尔(1932-)是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特立尼达的一个小镇,特立尼达是个多种族、多民族混杂聚居的英属殖民地。
奈保尔是印度婆罗门的后裔, 却远离了印度文化的大氛围;他出生在特立尼达, 却不满这个殖民地岛国贫瘠的文化和精神;他接受的是英式教育, 后来在英国定居, 可又始终无法摆脱一种“边缘”的流亡的感觉。
他的文化身份经历了从原有印度文化身份的解体到寻求西方化文化身份的失败,最终形成了混杂性的文化身份与认同。
他的作品始终都关注着边界中发生的文化现象、文化运动趋势,以及身处文化混杂地带的个人的文化身份问题。
奈保尔的长篇小说《河湾》出版于1979年,是以当时的扎伊尔共和国为背景的,它使奈保尔获得很高的声誉。
故事叙述者名叫萨林姆,祖先是穆斯林,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东非海岸。
萨林姆从小生活在杂居了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的海岸,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印度洋文化,与非洲内陆迥然不同。
萨林姆想在镇上定居,开个小店铺谋生,但是这个地区受到独裁政权的严密控制,人民毫无自由,局势动荡不安。
小说的末尾,主人公萨林姆又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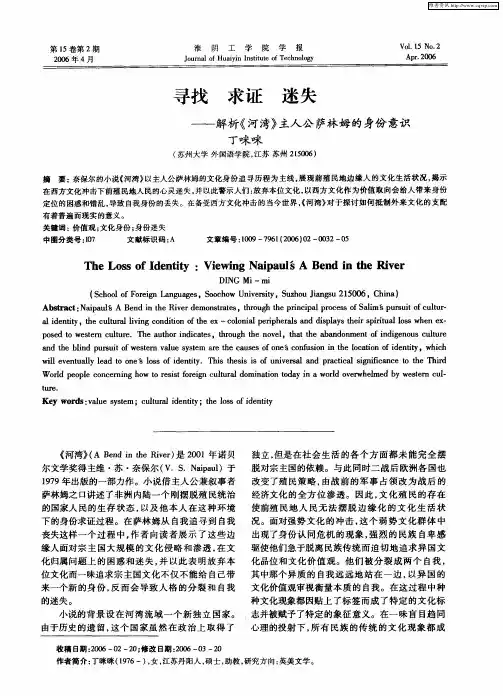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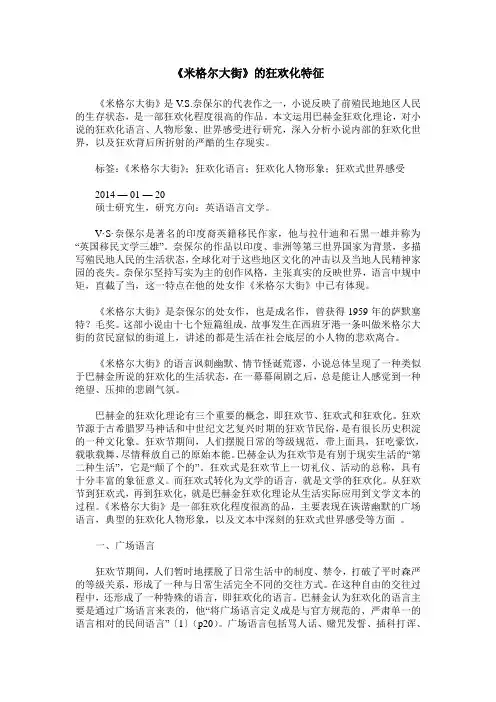
《米格尔大街》的狂欢化特征《米格尔大街》是V.S.奈保尔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反映了前殖民地地区人民的生存状态,是一部狂欢化程度很高的作品。
本文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小说的狂欢化语言、人物形象、世界感受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小说内部的狂欢化世界,以及狂欢背后所折射的严酷的生存现实。
标签:《米格尔大街》;狂欢化语言;狂欢化人物形象;狂欢式世界感受2014 — 01 — 20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V·S·奈保尔是著名的印度裔英籍移民作家,他与拉什迪和石黑一雄并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
奈保尔的作品以印度、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为背景,多描写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全球化对于这些地区文化的冲击以及当地人民精神家园的丧失。
奈保尔坚持写实为主的创作风格,主张真实的反映世界,语言中规中矩,直截了当,这一特点在他的处女作《米格尔大街》中已有体现。
《米格尔大街》是奈保尔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曾获得1959年的萨默塞特?毛奖。
这部小说由十七个短篇组成,故事发生在西班牙港一条叫做米格尔大街的贫民窟似的街道上,讲述的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米格尔大街》的语言讽刺幽默、情节怪诞荒谬,小说总体呈现了一种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生活状态,在一幕幕闹剧之后,总是能让人感觉到一种绝望、压抑的悲剧气氛。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三个重要的概念,即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
狂欢节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民俗,是有很长历史积淀的一种文化象。
狂欢节期间,人们摆脱日常的等级规范,带上面具,狂吃豪饮,载歌载舞,尽情释放自己的原始本能。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第二种生活”,它是“颠了个的”。
狂欢式是狂欢节上一切礼仪、活动的总称,具有十分丰富的象征意义。
而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就是文学的狂欢化。
从狂欢节到狂欢式,再到狂欢化,就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从生活实际应用到文学文本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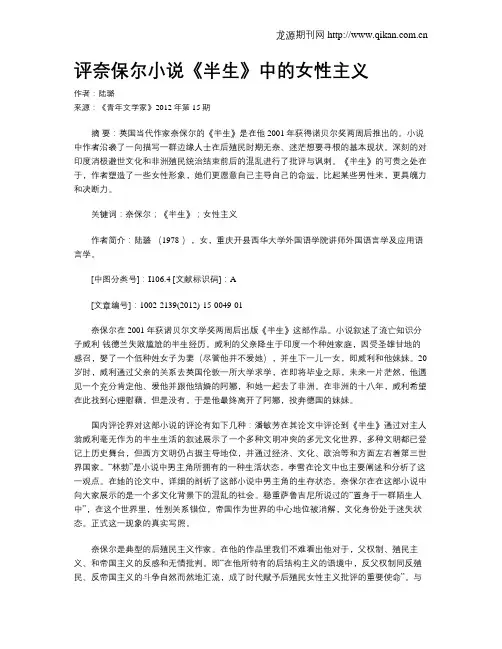
评奈保尔小说《半生》中的女性主义作者:陆璐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5期摘要:英国当代作家奈保尔的《半生》是在他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两周后推出的。
小说中作者沿袭了一向描写一群边缘人士在后殖民时期无奈、迷茫想要寻根的基本现状。
深刻的对印度消极避世文化和非洲殖民统治结束前后的混乱进行了批评与讽刺。
《半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塑造了一些女性形象,她们更愿意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比起某些男性来,更具魄力和决断力。
关键词:奈保尔;《半生》;女性主义作者简介:陆璐(1978-),女,重庆开县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5-0049-01奈保尔在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两周后出版《半生》这部作品。
小说叙述了流亡知识分子威利·钱德兰失败尴尬的半生经历。
威利的父亲降生于印度一个种姓家庭,因受圣雄甘地的感召,娶了一个低种姓女子为妻(尽管他并不爱她),并生下一儿一女,即威利和他妹妹。
20岁时,威利通过父亲的关系去英国伦敦一所大学求学,在即将毕业之际,未来一片茫然,他遇见一个充分肯定他、爱他并跟他结婚的阿娜,和她一起去了非洲。
在非洲的十八年,威利希望在此找到心理慰藉,但是没有。
于是他最终离开了阿娜,投奔德国的妹妹。
国内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有如下几种:潘敏芳在其论文中评论到《半生》通过对主人翁威利毫无作为的半生生活的叙述展示了一个多种文明冲突的多元文化世界,多种文明都已登记上历史舞台,但西方文明仍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等和方面左右着第三世界国家。
“林勃”是小说中男主角所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李雪在论文中也主要阐述和分析了这一观点。
在她的论文中,详细的剖析了这部小说中男主角的生存状态。
奈保尔在在这部小说中向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多文化背景下的混乱的社会。
稳重萨鲁吉尼所说过的“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在这个世界里,性别关系错位,帝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地位被消解,文化身份处于迷失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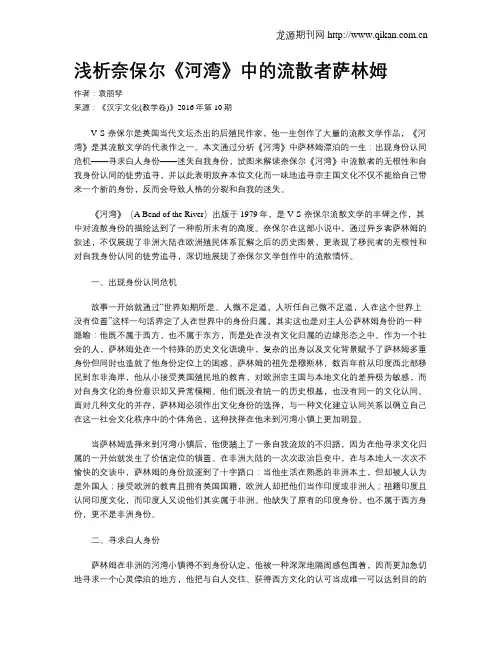
浅析奈保尔《河湾》中的流散者萨林姆作者:袁丽琴来源:《汉字文化(教学卷)》2016年第10期V·S·奈保尔是英国当代文坛杰出的后殖民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流散文学作品,《河湾》是其流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河湾》中萨林姆漂泊的一生: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寻求白人身份——迷失自我身份,试图来解读奈保尔《河湾》中流散者的无根性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徒劳追寻,并以此表明放弃本位文化而一味地追寻宗主国文化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一个新的身份,反而会导致人格的分裂和自我的迷失。
《河湾》(A Bend of the River)出版于1979年,是V·S·奈保尔流散文学的丰碑之作,其中对流散身份的描绘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奈保尔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异乡客萨林姆的叙述,不仅展现了非洲大陆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的历史图景,更表现了移民者的无根性和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徒劳追寻,深切地展现了奈保尔文学创作中的流散情怀。
一、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故事一开始就通过“世界如期所是。
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这样一句话界定了人在世界中的身份归属,其实这也是对主人公萨林姆身份的一种隐喻:他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而是处在没有文化归属的边缘形态之中。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萨林姆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复杂的出身以及文化背景赋予了萨林姆多重身份但同时也造就了他身份定位上的困惑。
萨林姆的祖先是穆斯林,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到东非海岸,他从小接受英国殖民地的教育,对欧洲宗主国与本地文化的差异极为敏感,而对自身文化的身份意识却又异常模糊。
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历史根基,也没有同一的文化认同。
面对几种文化的并存,萨林姆必须作出文化身份的选择,与一种文化建立认同关系以确立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这种抉择在他来到河湾小镇上更加明显。
当萨林姆选择来到河湾小镇后,他便踏上了一条自我流放的不归路,因为在他寻求文化归属的一开始就发生了价值定位的错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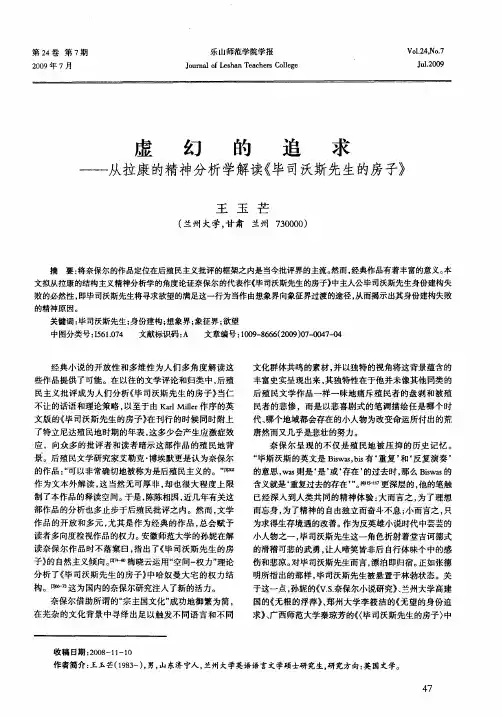
奈保尔《抵达之谜》的生态意识张弛【摘要】In the worldwide ecological crisis, a lot of critics and writers try to fight against the negative human interference on the nature through eco-criticism so that they can restore the polluted environment as far as possible, which is similar to Naipaul’s long term journey to search and identify his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close analysis of three aspects in The Enigma of Arrival including Naipaul’s simple life, his view of ecological holism in the unbalanced environment, and his equal treatment to the animals, we try to investigate Naipaul’s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aesthetics of the suzerain.%在当今全球范围下的生态危机中,批评家和作家们试图以生态批评为媒介,抨击人类以往施加在生态系统上的桎梏,尽可能还原出一个绿色、原始的地球。
作为后殖民作家群体代表人物的奈保尔在追寻文化身份的旅途中肩负着还原自我、定位自我的相同使命,他犀利地刻画了殖民地居民在殖民者撤离之后寻找、还原自我的心灵旅程。
《抵达之谜》中奈保尔展现出的安宁静雅的简单生活观、失衡环境中的生态整体观和敬重动物的万物平等观三方面,体现出作家所表现出的生态意识和对宗主国自然风貌的生态审美。
《米格尔街》:世事如斯展开全文序:局外人2001年,奈保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里这样形容他的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
”正如这句话所言,洞察是奈保尔的特长。
在他的作品序列中,不论是以非洲为创作背景的《自由国度》和《大河湾》,还是“印度三部曲”《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中,奈保尔都扮演着冷漠到几近刻薄的观察者角色。
但在《米格尔街》这本书里,奈保尔显得温情了很多。
在这本书中,奈保尔以少年的视角,甚至参与者的身份,观察着住在米格尔街上17个人。
尽管依旧保持审视和批判,但悲悯的角度、惆怅的情绪,柔化了奈保尔的尖锐。
即使这样,《米格尔街》的最后一个故事也是以“我”离开米格尔街作为结局。
和世界保持距离,才能不为世俗左右,奈保尔选择让自己变成一个局外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而且我很喜欢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
”米格尔街上的微缩世界“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肯定只会说:‘贫民窟’,因为他看不见别的。
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
”米格尔街的人都从事一些奇奇怪怪的工作。
鲍嘉假装要开裁缝店谋生,而在我印象里,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
波普自称是木匠,他在做一件没有名字的东西。
疯子曼曼想当政客,每逢选举必参加,每次得到的选票总是正好三张。
诗人B·华兹华斯要创作一首世界上最伟大的诗,迄今为止,写了五年。
摩根想做花炮师,但在特立尼达很少有人使用摩根的花炮。
叔叔巴库堪称机械天才,常常把发动机拆得一塌糊涂。
米格尔街的人活得很自在。
鲍嘉是我见过最百无聊赖的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纸牌游戏。
波普像个哲学家,谈的都是关于生死、工作之类的严肃话题。
曼曼从不干活,可他从来没闲着,为了写好一个字,会花上一整天的功夫。
B·华兹华斯的诗一个月写一行,预计再花二十二年可以完成。
摩根是我们的小丑,他整天都在琢磨一些新招,希望博我们一笑。
(英)奈保尔《米格尔大街》第一篇《博加特》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朝对面喊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博加特在床上翻个身,用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咕哝着:“有什么新鲜事吗,海特?”人们叫他“博加特”是有什么原因的,可我总觉得这是海特送给他的雅号。
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上映的那一年,博加特的名字风靡了整个西班牙港,硬汉子博加特的形象,成为成千上万年轻人崇拜的偶像。
在他被称作“博加特”之前,人们叫他“扑克算命先生”,因为他一天到晚总是在玩这种把戏,尽管他一点也不喜欢玩扑克。
无论什么时间你到“博加特”那间小屋子里去,总会看到他坐在床上,面前的小桌子上排列着七行扑克牌。
“有什么新鲜事吗,伙计?”他只轻轻地问这么一句,便一声不吭地呆上十几分钟。
使你感到几乎无法和“博加特”搭上话。
他看上去是那么愚昧和傲慢;一双睡意蒙胧的眼睛,脸庞臃肿,头发漆黑,肌肉丰满的胳膊,但他倒也算不上古怪滑稽。
不管干什么事,他老是像睡不醒似的,无精打采,就连舔拇指分发扑克牌时也是那么一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样子。
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乏味的。
他装出一副靠做裁缝维持生计的样子,甚至还出钱让我给他写了一副招牌。
缝纫,裁剪制作成衣技术高超,款式新颖,价钱公道他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的、白的、褐色的粉饼。
我简直想像不出他到底能干些什么,我也从不曾记得他做成过一件衣服。
在这一点上,他倒有点像隔壁的波普,那个从没做出过一件家具,却整天在画呀、凿呀、鼓捣那被他称作榫眼的木匠。
每当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干什么呀?”他总是回答道:“嘿,孩子,问得好,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来的事。
”就连这类事情,博加特也从没干过。
那时我还是个毛孩子,从没想过“博加特”是怎么搞来的钱,我觉得凡是大人总会有钱的。
波普有个干杂活的老婆,后来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
我简直想不出“博加特”会有母亲或是父亲,电从没见一个女人到他小房子里去。
那间被他称为是下人住的厢房,却设有一个侍候正房里主人的下人住过,说是下人住的厢房,也只不过从建筑的角度这么叫而已。
论《米格尔街》中的边缘人物惠慧摘要:《米格尔街》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移民作家维·苏·奈保尔的早期代表作品。
小说以生活在其中的小主人公“我”的童年经历为线索,叙述了米格尔街上那些精神恍惚、行为怪异的人物,他们身在特立尼达,因为被殖民太久而没有传承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而殖民他们的国家也并没有给他们文化上的认同感,导致他们对自身充满疑惑,不断去效仿他人,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面对他们人生中呈现的那种充满着激情与悲伤的狂欢化状态,人们不得不去思考殖民地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不得不去探究边缘人物内心的空缺感。
研究《米格尔街》中的边缘人物,不仅是对殖民地人民精神家园的一种关怀,也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意义的一种探索。
关键词:殖民地;边缘化;《米格尔街》;悲剧性本文主要论述《米格尔街》中的边缘人物,以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为背景,分析居住在殖民地地区一系列边缘人物的生活状态。
这部小说里曾写道:“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时,只能说一句:‘贫民窟!”但是居住在那里的人却把这条街看成一个世界。
我们不难看出生活在米格尔街上的人过着一种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生活,而那种被边缘化的生活和人物正是本文研究的主体。
本文将从殖民地文化、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划分、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论等多个理论出发,结合作品以及相关文献探究那些根植于边缘人物身上琐屑的理想、欲望以及人生追求,并通过对《米格尔街》中边缘人物的悲剧根源进行反思,谈谈人生之中不可规避的挫折以及理想的价值。
一、奈保尔的人生经历及其对《米格尔街》的影响维·苏·奈保尔于1932年8月17日出生在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奈保尔在他的影响下自小就喜爱文学,长大以后成了一名专职作家。
有人评论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极为少见的,一直而且仅仅依靠写作而生的作家中的一个”。
奈保尔中学毕业后获得了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奖学金,大学毕业后不久就以童年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米格尔街》,这部小说让他一举成名。
解析小说《毕斯瓦司先生的房子》中后现代女性主义色彩摘要:小说《毕斯瓦司先生的房子》中在性别差异中的平等,女性同盟话语权的建构以及两性关系的和谐方面体现出后现代女性主义色彩,在后现代语境下分析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有利于给读者提供评析小说的另一个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差异权利话语《毕斯瓦司先生的房子》是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的成名作,主人公毕斯瓦斯先生是以奈保尔的父亲为部分原形记录了毕斯瓦斯一生对于房子的渴望和追求。
研究者大多以毕斯沃斯先生对自己房子的不懈追求为出发点,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评论其个人对身份、地位和尊严的要求的内涵,但却忽略了作品中的众多女性形象。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二十世纪 80、90年它从女性立场经验出发,以女性独特的思维表述方式将后现代思想导向对男权制文化的批判,通过构建一套关注个体差异、强调多元的女性话语体系来颠覆男权秩序”。
[1]71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包括以下观点:“否定所有宏大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挑战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论,反对性别两分和性别不平衡;反对传统男性话语霸权模式,主张构建女性话语;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模式,提倡多元论和相对论。
由此可见,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了女性内部、两性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差异的不同意义,并试图通过构建一套关注个体差异、注重多元的女性话语体系来颠覆男权体制,关注女性受压迫的复杂性并对其成因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从而实现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
小说《毕斯瓦司先生的房子》中所包含的两性观正是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阐释。
一、性别差异中的平等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贬斥女性不擅长于任何理性的认识,这是父权制社会的专制与阴谋”。
[2]119如果不动摇父权制的这个基础,任何女性主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小说对于人物的刻画试图提倡弱化两性差异,消除性别对立的特点,重视两种性别内部的差别。
小说中莎玛的形象“大约中等个头,苗条而结实,有着精致的五官”。
第11卷第3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1,No.3
2009年5月JournalofLiaoningTechnic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May2009
永远的他者———奈保尔代表作中主人公分析
徐 键(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外语系,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通过对奈保尔不同时期的三部代表作中主人公的分析,揭示出移民及其后裔在后殖民主义阶段面临的身份困惑、文化错位和权利失衡。透过奈保尔文学经验总结出正如奈保尔代表着全球化时代英语离散文学的世界性一样,后殖民主义时代文化他者的出路是世界身份。关键词:奈保尔;文化身份;他者;世界身份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1X(2009)03-0310-02
PermanentDrifters———analysisoftheheroesinNaipaul’snovels
XUJian(DepartmentofForeignLanguages,LiaoningTechnicalUniversity,Fuxin123000,China)Abstract:TheheroesinNaipaul’snovelsrevealtheidentity-puzzle,culturaldislocationandpowerim2balanceencounteredbyimmigrantsandtheiroffspringinpost-colonialperiod.AsNaipaulstandsfortheunityofEnglishliteraturediversityintheglobalizingtime,theseculturaldriftersinthepost-coloni2alperiodhavenochoicebuttoresorttotheirglobalidentity.Keywords:V.S.Naipaul;culturalidentity;drifters;globalidentity
收稿日期:2008-10-15
作者简介:徐 键(1978-),女,辽宁阜新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0 引 言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文学三杰”之一的V.S.奈保尔是来自加勒比海特立尼达的印度裔英国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是定位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的历史背景之下,充满了对后殖民政治文化的反思,引起了不同文化的对位性阅读:后殖民理论家批判他是“白人文化的新鼓吹者”;欧美批评界却称赞他是“早期移民作家中有自觉意识的一位”,“促进我们注意到那一段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本文通过分析奈保尔三部代表作中的主人公,揭示出移民及其后裔在后殖民主义阶段面临的身份困惑,文化错位和权利失衡。1 游荡在宗主国的他者———桑陀西奈保尔1971年创作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主人公桑陀西是一个于20世纪70年代非法移民到华盛顿的印度人。桑陀西的身上有着他者闲逛、旁观的特征。当他跟随主人来到华盛顿时,把行李放在房间就立刻去街上游荡,甚至在工作的间隙也要上街去逛逛。桑陀西对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华盛顿心存敬畏。是殖民者向被殖民者灌输西方文明先进性的结果。桑陀西对华盛顿最初的印象是:有很多“绿化带和宽敞的马路,众多急驰而过的摩托车持续发出嘶嘶声,和孟买城里的交通噪音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华盛顿城里那些高大的建筑、宽阔的公园和数量众多的商业区”。这些都彰显着华盛顿的现代化和生活的快节奏,但桑陀西却觉得自己“永远地被禁锢了”,“像个囚犯”。桑陀西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白人殖民者为了驯服被殖民者,对他们进行思想控制,就刻意贬低殖民地的民族文化,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推崇西方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当桑陀西这样的被殖民者来到华盛顿这样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城市,他就感到拘束、胆怯,并对殖民者文化产生敬畏感[1]。当被殖民者像桑陀西一样来到宗主国,他们也不能摆脱被殖民者的身份、和殖民者一样平起平坐,享受人类的文明成果。桑陀西刚到华盛顿,就感到格格不入:在现代化的公寓里迷路,不会乘电梯,不会说英语,吃一块蛋糕、看一场电影就用完一个月的工资。如果说这些生活上的笨拙带给桑陀西的还只是不熟悉新环境的不安全感的话,那么对他最大的冲击则是来自对自己他者身份的认识。桑陀西发现华盛顿街道上的行人(包括和他一样的印度人)都一身正装,好像永远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反观自己,身穿皱巴巴的印度长衫,用一根细麻绳拴着宽松的短裤裤腰,光着脚板,连一间小小的咖啡馆都拒绝接待他,这才让桑陀西意识到自己的他者身份。即使桑陀西穿上昂贵的西装和皮鞋,却“在镜子里再也看不到自己的脸”(意即失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那是因为,他仍然是一个模仿人,仍然摆脱不了他者的身份标签,同时还因为与母国文化的割离而失却了自己的文化归属感。2 三重他者———萨林姆奈保尔1979年的代表作《河湾》以印度后裔萨林姆在非洲内陆小镇河湾的经历为叙事主线,展现了前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却内乱不断的困境。然而,作品的关注点并不局限于后殖民时代的政治问题,而是延伸到前殖民地人们文化心理与身份意识的嬗变。如果说独立后的非洲本地人经过政治身份的更替置换,通过重构民族文化可以恢复文化自我意识,那么对萨林姆等移民后裔来说,殖民地的独立则意味着他们要直面痛苦而无奈的身份放逐之旅。萨林姆的祖先是穆斯林,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移民到东非海岸,“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形成一种印度洋文化,与非洲内地迥然有别”。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萨林姆文化身份的意识异常模糊。生活在非洲东海岸已有几个世纪,萨林姆却与真正的非洲文化隔离;有时他坚信自己是属于印度的穆斯林后裔,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看着自己的婶婶擦拭作为穆斯林神器的铜瓶,他又感到“这个女人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碎”,而“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有时他崇拜欧洲文化并认为“如果没有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却又感到“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有时他认同“我们阿拉伯人是当年的冒险家和作家”,时而坚持“‘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是我们波斯人”,却又憎恨阿拉伯人与当地黑人女子混血失去穆斯林的民族血缘和文化谱系,转而认定“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起来,我们又感觉自己是非洲人”。萨林姆生活在非洲,熟悉非洲本土,但非洲人认为他是外国人;接受欧洲的教育,拥有宗主国的合法身份,欧洲人却把他当作印度人或非洲人;他祖籍印度,认同印度文化,然而印度人又说他属于非洲。文化的错位使得萨林姆对欧洲、印度与非洲文化间的差异极为敏感,但身份的错位却让他在文化夹缝中处于三重的他者地位,“时刻感到自己处于不安与警觉之中,随时可能被排斥,而无意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导致大祸临头”。出于对文化归属的身份焦虑,萨林姆在非洲内乱前离开了生养他的东海岸,迫切地踏上了前往内陆小镇河湾的自我放逐之行。在河湾小镇,他既惧怕“大人物”、“偶像”和总统这些内心矛盾的本土民族主义者,有羡慕在新领地的文理学院中像雷蒙德、因达尔这类靠“非洲题材发学术财”的寄生虫,却更加担忧仆人穆迪恢复的非洲本土意识与费尔迪南的新非洲人身份。实际上,让萨林姆恐惧的是自己在非洲文化中作为他者的危险境地,而让他无比羡慕的是其他人在民族文化中所自然拥有的身份意识与权利。3 漂泊半生的他者———威利奈保尔在2001年获诺贝尔奖两周后出版了小说《半生》。《半生》记录了主人公威利・钱德兰漂泊、寻找但没有成就的尴尬半辈子。作者沿袭了一贯的反映后殖民时期边缘人寻根、焦虑但无所适从的主题,对印度的消极避世文化和非洲殖民统治结束前后的混乱进行了讽刺与批评。小说标题《半生》的字面意思是指主人公威利41岁的半辈子生活。从出身上看,威利是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与最低种姓首陀罗结合的后代,是混血的“杂种”。血混在了一起,但并没有“溶合在一起”。从一生下来,威利所生活的世界就不是完整的,撕裂的,既不高等也不低等,卡在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是奈保尔所说的“林勃”(limbo)状态[2]。伴随着父亲的冷漠和残酷成长的威利长大后一心想离开印度、离开父亲。50年代初抵达伦敦的威利,面对陌生与冷漠的种族歧视的环境无所适从,他“修改了自己的出身”才慢慢适应。他靠拙劣的模仿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又靠朋友的影响得以发表,但小说给他带来了爱情和婚姻。威利跟随妻子阿娜来到位于非洲莫桑比克的庄园,给妻子的家族当监工。非洲生活对威利来说不适应的首先是语言,他得学习葡萄牙语,逐渐地忘记了印度语,忘记了英语,忘记了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更不用说成为真正的作家了。有了庄园,并不意味着有了心灵扎根的土壤。在殖民地,他们来往的大都是像阿娜一样既不属于葡萄牙又不属于非洲的混血儿,种姓的等级在非洲表现为种族的分野。威利在非洲18年弹指一挥间,非洲的殖民统治已是日薄西山,革命和游击运动风起云涌,殖民者纷纷鸟散。威利也厌倦了“阿娜的英国男人”的角色,决心离开阿娜“我已经41岁了。我厌倦了过你的生活。”阿娜说:“是你要到非洲来的呀。”威利告诉她:“……当年我向你要求来非洲时,我很害怕。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已过去了,我却一事无成……现在即使我们去葡萄牙,那也还是你的生活。我已经躲藏得太久了。”威利又一次离开了,但似乎总逃不脱父亲的宿命———遁入被别人安排和控制的角色,无奈于社会的分野。正如布鲁斯・金所总结的:“在奈保尔对后殖民和帝国主义社会的关注背后更重要的主题是对普世人生的思考。当人们或民族为了空间、舒适、性和安全感去竞争时,总是会产生不公平的社会等级,总是会有统治和特权,也总是有人会需要被保护。那些缺少途径、意志力和精力去提升自己并保护自己的人会成为他人的牺牲者,或者他们不停地离开,不停地迁移去寻求生存和更好的生活。在新的土地上,人们需要他人作保护者和向导。《半生》表明生命是一系列的离散,不断的移植,似乎安稳的状态实际上正经历着一系列的改变”[3]。4 结 语奈保尔的作品从时代背景和创作时间来看应归为后殖民主义时代,但他追求的是一种格格不入的身份书写,一种身份错位的自我表述,他的作品无不透露出他本人对移民及其后裔的身份焦虑,而通过一位位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的放逐历程,作者的身份困惑在多元化的文学世界里也得到暂时的舒缓。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二元的颠覆、殖民主客体的消亡促进了基于文化身份的新型叙事的发展,文化身份的他者成了新的被压迫者[4]。可贵的是,在最近的作品《半生》中,奈保尔给了非洲同情和尊敬,并试着去理解他祖先的国度印度,
对第二世界人民少了尖锐的批评,多了宽容和理解,对人生也有了更广泛的认同。从桑陀西、萨林姆、威利这三个越来越丰满和复杂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想塑造的混合身份———不是消极、避世、认命的印度身份,不是狂热的加勒比海身份,不是自命不凡的欧洲身份,不是任性的非洲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