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游记叙事结构
- 格式:pdf
- 大小:102.13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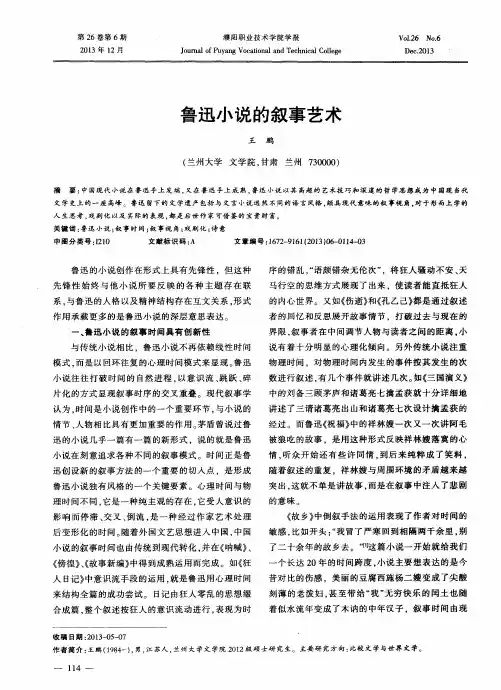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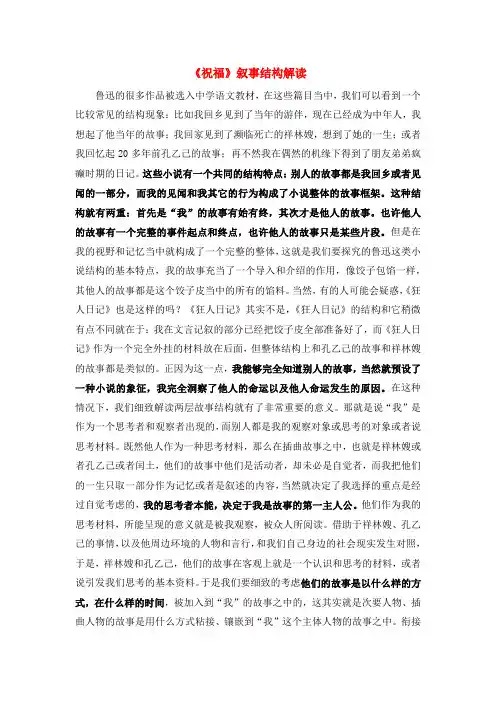
《祝福》叙事结构解读鲁迅的很多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在这些篇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常见的结构现象:比如我回乡见到了当年的游伴,现在已经成为中年人,我想起了他当年的故事;我回家见到了濒临死亡的祥林嫂,想到了她的一生;或者我回忆起20多年前孔乙己的故事;再不然我在偶然的机缘下得到了朋友弟弟疯癫时期的日记。
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点:别人的故事都是我回乡或者见闻的一部分,而我的见闻和我其它的行为构成了小说整体的故事框架。
这种结构就有两重:首先是“我”的故事有始有终,其次才是他人的故事。
也许他人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事件起点和终点,也许他人的故事只是某些片段。
但是在我的视野和记忆当中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这就是我们要探究的鲁迅这类小说结构的基本特点,我的故事充当了一个导入和介绍的作用,像饺子包馅一样,其他人的故事都是这个饺子皮当中的所有的馅料。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疑惑,《狂人日记》也是这样的吗?《狂人日记》其实不是,《狂人日记》的结构和它稍微有点不同就在于:我在文言记叙的部分已经把饺子皮全部准备好了,而《狂人日记》作为一个完全外挂的材料放在后面,但整体结构上和孔乙己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都是类似的。
正因为这一点,我能够完全知道别人的故事,当然就预设了一种小说的象征,我完全洞察了他人的命运以及他人命运发生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细致解读两层故事结构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说“我”是作为一个思考者和观察者出现的,而别人都是我的观察对象或思考的对象或者说思考材料。
既然他人作为一种思考材料,那么在插曲故事之中,也就是祥林嫂或者孔乙己或者闰土,他们的故事中他们是活动者,却未必是自觉者,而我把他们的一生只取一部分作为记忆或者是叙述的内容,当然就决定了我选择的重点是经过自觉考虑的,我的思考者本能,决定于我是故事的第一主人公。
他们作为我的思考材料,所能呈现的意义就是被我观察,被众人所阅读。
借助于祥林嫂、孔乙己的事情,以及他周边环境的人物和言行,和我们自己身边的社会现实发生对照,于是,祥林嫂和孔乙己,他们的故事在客观上就是一个认识和思考的材料,或者说引发我们思考的基本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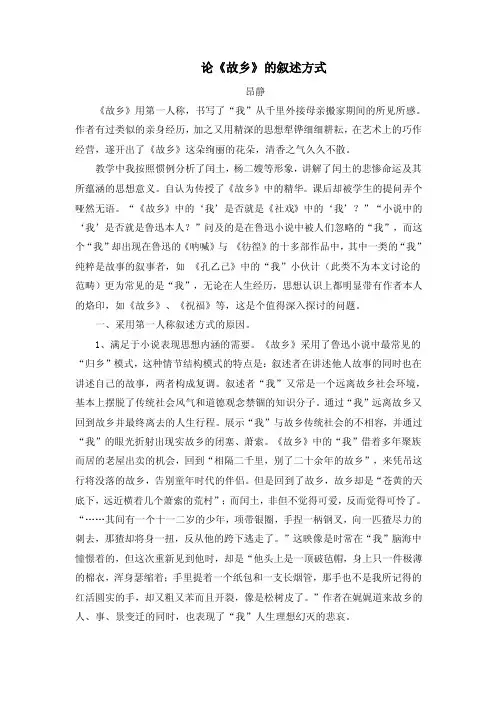
论《故乡》的叙述方式昂静《故乡》用第一人称,书写了“我”从千里外接母亲搬家期间的所见所感。
作者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加之又用精深的思想犁铧细细耕耘,在艺术上的巧作经营,遂开出了《故乡》这朵绚丽的花朵,清香之气久久不散。
教学中我按照惯例分析了闰土,杨二嫂等形象,讲解了闰土的悲惨命运及其所蕴涵的思想意义。
自认为传授了《故乡》中的精华。
课后却被学生的提问弄个哑然无语。
“《故乡》中的‘我’是否就是《社戏》中的‘我’?”“小说中的‘我’是否就是鲁迅本人?”问及的是在鲁迅小说中被人们忽略的“我”,而这个“我”却出现在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的十多部作品中,其中一类的“我”纯粹是故事的叙事者,如《孔乙己》中的“我”小伙计(此类不为本文讨论的范畴)更为常见的是“我”,无论在人生经历,思想认识上都明显带有作者本人的烙印,如《故乡》、《祝福》等,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原因。
1、满足于小说表现思想内涵的需要。
《故乡》采用了鲁迅小说中最常见的“归乡”模式,这种情节结构模式的特点是:叙述者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构成复调。
叙述者“我”又常是一个远离故乡社会环境,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
通过“我”远离故乡又回到故乡并最终离去的人生行程。
展示“我”与故乡传统社会的不相容,并通过“我”的眼光折射出现实故乡的闭塞、萧索。
《故乡》中的“我”借着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出卖的机会,回到“相隔二千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来凭吊这行将没落的故乡,告别童年时代的伴侣。
但是回到了故乡,故乡却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而闰土,非但不觉得可爱,反而觉得可怜了。
“……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跨下逃走了。
”这映像是时常在“我”脑海中憧憬着的,但这次重新见到他时,却是“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苯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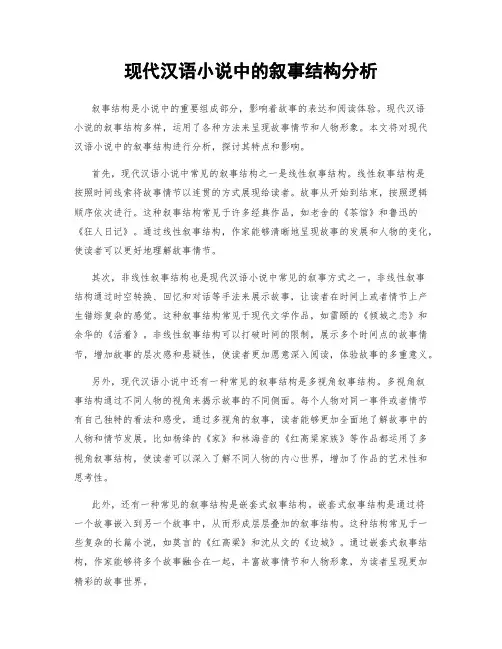
现代汉语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分析叙事结构是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故事的表达和阅读体验。
现代汉语小说的叙事结构多样,运用了各种方法来呈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本文将对现代汉语小说中的叙事结构进行分析,探讨其特点和影响。
首先,现代汉语小说中常见的叙事结构之一是线性叙事结构。
线性叙事结构是按照时间线索将故事情节以连贯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故事从开始到结束,按照逻辑顺序依次进行。
这种叙事结构常见于许多经典作品,如老舍的《茶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
通过线性叙事结构,作家能够清晰地呈现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变化,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
其次,非线性叙事结构也是现代汉语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方式之一。
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时空转换、回忆和对话等手法来展示故事,让读者在时间上或者情节上产生错综复杂的感觉。
这种叙事结构常见于现代文学作品,如雷颐的《倾城之恋》和余华的《活着》。
非线性叙事结构可以打破时间的限制,展示多个时间点的故事情节,增加故事的层次感和悬疑性,使读者更加愿意深入阅读,体验故事的多重意义。
另外,现代汉语小说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叙事结构是多视角叙事结构。
多视角叙事结构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揭示故事的不同侧面。
每个人物对同一事件或者情节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感受,通过多视角的叙事,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发展。
比如杨绛的《家》和林海音的《红高粱家族》等作品都运用了多视角叙事结构,使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考性。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叙事结构是嵌套式叙事结构。
嵌套式叙事结构是通过将一个故事嵌入到另一个故事中,从而形成层层叠加的叙事结构。
这种结构常见于一些复杂的长篇小说,如莫言的《红高梁》和沈从文的《边城》。
通过嵌套式叙事结构,作家能够将多个故事融合在一起,丰富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为读者呈现更加精彩的故事世界。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多种多样,包括线性叙事结构、非线性叙事结构、多视角叙事结构和嵌套式叙事结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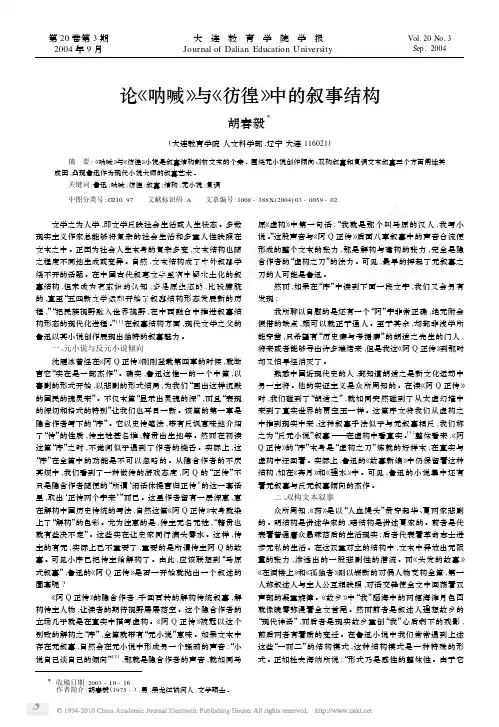
论《呐喊》与《彷徨》中的叙事结构胡春毅Ξ(大连教育学院人文科学部,辽宁大连116021)摘 要:《呐喊》与《彷徨》小说是叙事结构剖析文本的个案。
围绕元小说创作倾向、双构叙事和复调文本叙事三个方面阐述其成因,凸现鲁迅作为现代小说大师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鲁迅;呐喊;彷徨;叙事;结构;元小说;复调中图分类号:G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88X(2004)03-0059-02 文学之为人学,即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或人生状态。
多数现实主义作家总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多重人性映照在文本之中。
正因为社会人生本身的复杂多变,文本结构也随之程度不同地生成或变异。
自然,文本结构成了中外叙事学绕不开的话题。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里有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结构,但未成为有意识的认知,多是原生态的,比较朦胧的,直至“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了叙事结构形态发展新的历程,”“把民族视野融入世界视野,在中西融合中推进叙事结构形态的现代化进程。
”[1]在叙事结构方面,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以其小说创作展现出独特的叙事魅力。
一、元小说与反元小说倾向沈雁冰曾经在《阿Q正传》刚刚登载第四章的时候,就断言它“实在是一部杰作”。
确实,鲁迅这惟一的一个中篇,以喜剧的形式开始,以悲剧的形式结局,为我们“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不仅本篇“显示出灵魂的深”,而且“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让我们也耳目一新。
该篇的第一章是隐含作者写下的“序”。
它以史传笔法,带有反讽意味地介绍了“传”的性质,传主姓甚名谁,籍贯出生地等。
然而在初读这篇“序”之时,不觉间似乎遇到了作者的饶舌。
实际上,这“序”在全篇中的功能是不可以忽略的。
从隐含作者的不厌其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做传的游戏态度,阿Q的“正传”不只是隐含作者随便的“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的这一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而已。
这里作者留有一层深意,意在解构中国历史传统的写法,自然这篇《阿Q正传》本身就染上了“解构”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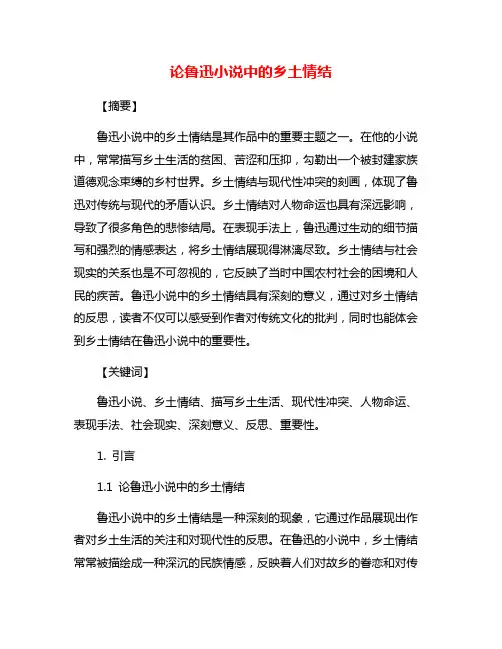
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摘要】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是其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描写乡土生活的贫困、苦涩和压抑,勾勒出一个被封建家族道德观念束缚的乡村世界。
乡土情结与现代性冲突的刻画,体现了鲁迅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认识。
乡土情结对人物命运也具有深远影响,导致了很多角色的悲惨结局。
在表现手法上,鲁迅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强烈的情感表达,将乡土情结展现得淋漓尽致。
乡土情结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困境和人民的疾苦。
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对乡土情结的反思,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同时也能体会到乡土情结在鲁迅小说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鲁迅小说、乡土情结、描写乡土生活、现代性冲突、人物命运、表现手法、社会现实、深刻意义、反思、重要性。
1. 引言1.1 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是一种深刻的现象,它通过作品展现出作者对乡土生活的关注和对现代性的反思。
在鲁迅的小说中,乡土情结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人们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珍视。
乡土情结在鲁迅的作品中常常与现代性进行对比,揭示出现代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和颠覆。
乡土情结还对人物命运产生重要影响,塑造了许多鲁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使他们面对现实的残酷与困惑。
鲁迅在小说中运用多种手法表现乡土情结,通过对环境、风俗和人物的描写,深刻展现了乡土情结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方式。
乡土情结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它既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探讨。
通过对鲁迅小说中乡土情结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背后的种种含义,以及作者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思考。
2. 正文2.1 鲁迅小说中对乡土生活的描写鲁迅小说中对乡土生活的描写是其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他通过对乡土生活的细致描写,展现了乡村的贫困、落后、饥饿、疾病等残酷的一面。
在《呐喊》中,鲁迅描绘了农民靠卖儿女度日、女人被卖掉变卖的悲惨命运;在《阿Q正传》中,鲁迅通过对阿Q在乡村生活中的种种屈辱和挫折的描写,反映了乡村社会的黑暗和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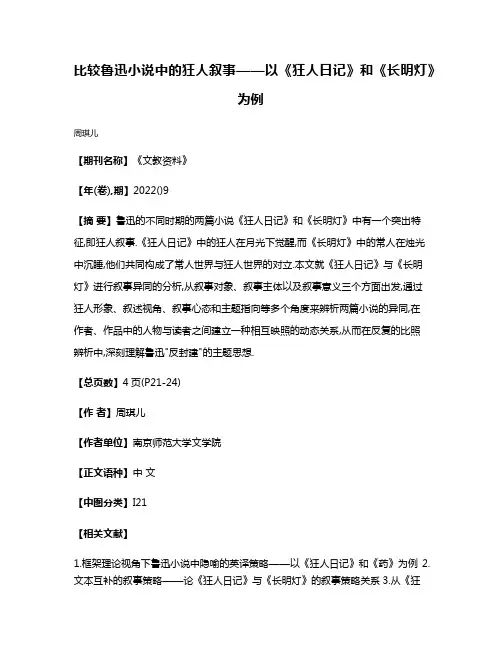
比较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叙事——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
为例
周琪儿
【期刊名称】《文教资料》
【年(卷),期】2022()9
【摘要】鲁迅的不同时期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中有一个突出特征,即狂人叙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月光下觉醒,而《长明灯》中的常人在烛光
中沉睡,他们共同构成了常人世界与狂人世界的对立.本文就《狂人日记》与《长明灯》进行叙事异同的分析,从叙事对象、叙事主体以及叙事意义三个方面出发,通过
狂人形象、叙述视角、叙事心态和主题指向等多个角度来辨析两篇小说的异同,在
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映照的动态关系,从而在反复的比照
辨析中,深刻理解鲁迅"反封建"的主题思想.
【总页数】4页(P21-24)
【作者】周琪儿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1
【相关文献】
1.框架理论视角下鲁迅小说中隐喻的英译策略——以《狂人日记》和《药》为例
2.文本互补的叙事策略——论《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叙事策略关系
3.从《狂
人日记》到《长明灯》看鲁迅革命思想的发展4.借鉴基础上的独创——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5.认知隐喻视角下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r——以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药》为例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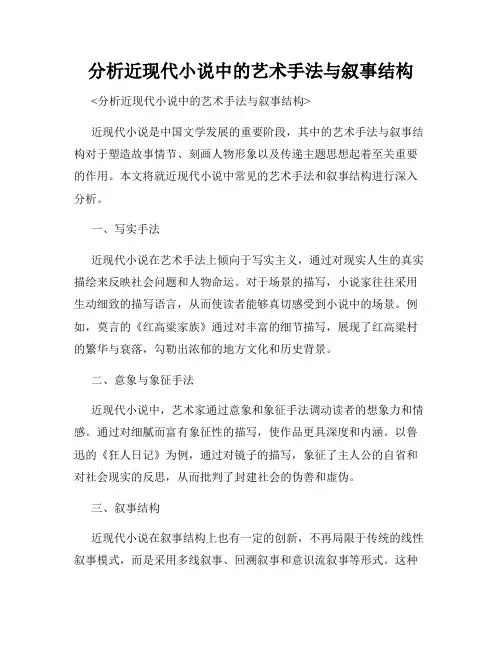
分析近现代小说中的艺术手法与叙事结构<分析近现代小说中的艺术手法与叙事结构>近现代小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的艺术手法与叙事结构对于塑造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以及传递主题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就近现代小说中常见的艺术手法和叙事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一、写实手法近现代小说在艺术手法上倾向于写实主义,通过对现实人生的真实描绘来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物命运。
对于场景的描写,小说家往往采用生动细致的描写语言,从而使读者能够真切感受到小说中的场景。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通过对丰富的细节描写,展现了红高粱村的繁华与衰落,勾勒出浓郁的地方文化和历史背景。
二、意象与象征手法近现代小说中,艺术家通过意象和象征手法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情感。
通过对细腻而富有象征性的描写,使作品更具深度和内涵。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通过对镜子的描写,象征了主人公的自省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从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伪善和虚伪。
三、叙事结构近现代小说在叙事结构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采用多线叙事、回溯叙事和意识流叙事等形式。
这种叙事结构的运用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性,还能够更好地展示故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例如,钱钟书的《围城》就将不同人物的视角融入其中,通过多线叙事的方式呈现出了一个特殊而独立的社会群体。
四、人物刻画近现代小说对人物的刻画也是其独特之处,小说家常常通过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言行举止的描写来展示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
同时,近现代小说也注重对社会人物的描摹,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刻画,揭示出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和社会问题的存在。
例如,韩寒的《三重门》通过对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物性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刻画,揭示出当代中国青年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综上所述,近现代小说中的艺术手法与叙事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写实手法、意象与象征手法、叙事结构以及人物刻画,小说家们得以更加生动地塑造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并通过作品传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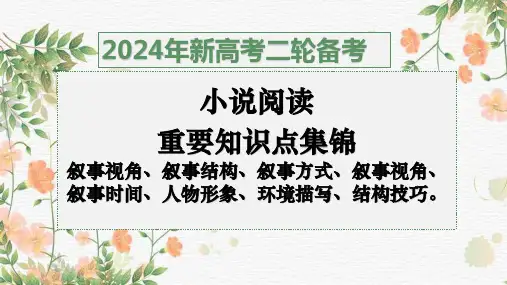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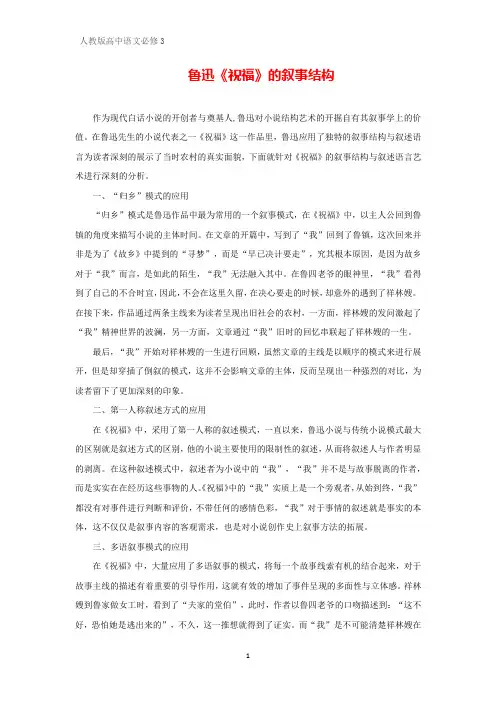
鲁迅《祝福》的叙事结构作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创者与奠基人,鲁迅对小说结构艺术的开掘自有其叙事学上的价值。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之一《祝福》这一作品里,鲁迅应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为读者深刻的展示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下面就针对《祝福》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的分析。
一、“归乡”模式的应用“归乡”模式是鲁迅作品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叙事模式,在《祝福》中,以主人公回到鲁镇的角度来描写小说的主体时间。
在文章的开篇中,写到了“我”回到了鲁镇,这次回来并非是为了《故乡》中提到的“寻梦”,而是“早已决计要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故乡对于“我”而言,是如此的陌生,“我”无法融入其中。
在鲁四老爷的眼神里,“我”看得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因此,不会在这里久留,在决心要走的时候,却意外的遇到了祥林嫂。
在接下来,作品通过两条主线来为读者呈现出旧社会的农村,一方面,祥林嫂的发问激起了“我”精神世界的波澜,另一方面,文章通过“我”旧时的回忆串联起了祥林嫂的一生。
最后,“我”开始对祥林嫂的一生进行回顾,虽然文章的主线是以顺序的模式来进行展开,但是却穿插了倒叙的模式,这并不会影响文章的主体,反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为读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应用在《祝福》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一直以来,鲁迅小说与传统小说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叙述方式的区别,他的小说主要使用的限制性的叙述,从而将叙述人与作者明显的剥离。
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为小说中的“我”,“我”并不是与故事脱离的作者,而是实实在在经历这些事物的人。
《祝福》中的“我”实质上是一个旁观者,从始到终,“我”都没有对事件进行判断和评价,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我”对于事情的叙述就是事实的本体,这不仅仅是叙事内容的客观需求,也是对小说创作史上叙事方法的拓展。
三、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在《祝福》中,大量应用了多语叙事的模式,将每一个故事线索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故事主线的描述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就有效的增加了事件呈现的多面性与立体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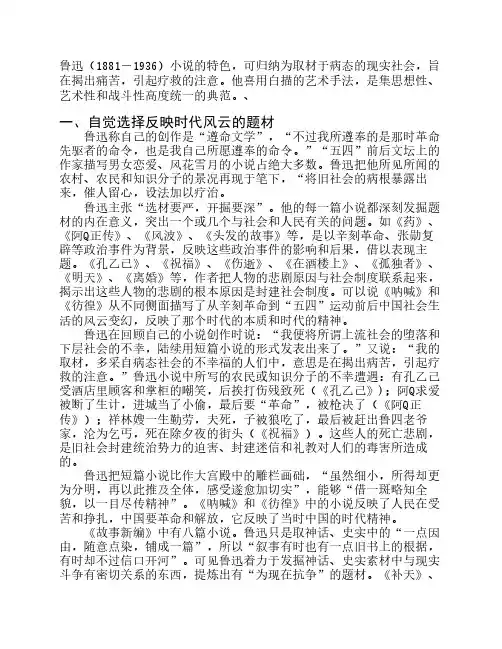
鲁迅(1881-1936)小说的特色,可归纳为取材于病态的现实社会,旨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他喜用白描的艺术手法,是集思想性、艺术性和战斗性高度统一的典范。
、一、自觉选择反映时代风云的题材 鲁迅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遵奉的命令。
”“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的小说占绝大多数。
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鲁迅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
如《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是以辛刻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反映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借以表现主题。
《孔乙已》、《祝福》、《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明天》、《离婚》等,作者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
可以说《呐喊》和《彷徨》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刻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又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福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小说中所写的农民或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有孔乙己受酒店里顾客和掌柜的嘲笑,后挨打伤残致死(《孔乙己》);阿Q求爱被断了生计,进城当了小偷,最后要“革命”,被枪决了(《阿Q正传》);祥林嫂一生勤劳,夫死,子被狼吃了,最后被赶出鲁四老爷家,沦为乞丐,死在除夕夜的街头(《祝福》)。
这些人的死亡悲剧,是旧社会封建统治势力的迫害、封建迷信和礼教对人们的毒害所造成的。
鲁迅把短篇小说比作大宫殿中的雕栏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能够“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
【课外阅读】鲁迅小说的叙事时间模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就颇具慧眼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那么,鲁迅小说的新形式表现在那里?本文依据叙事学的叙事时态,来探讨鲁迅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之处。
一尽管现代小说有了与传统小说的种种变化,但根本一点是不能变的,即作为小说总得有故事,故事是小说的核心因素。
就此来讲,小说也可称为讲故事的艺术。
小说的故事是作者从生活捕捉的,或是心里有的。
从文学创作来讲,故事是小说的创作素材,有的理论家又叫故事为“底本”。
素材-底本不动,照录故事原样,是不能成为小说的。
要想成为小说,就要在“怎么讲”故事上下功夫。
“怎么讲”即是对素材的加工。
小说是人类叙事艺术之一。
因此这种对素材的加工,也就被称为叙事艺术。
对小说素材的加工包括:对素材的删节、调位、重组,形成结构;叙事角度的选择;作者介入态度的确定;叙述时间的变形;叙述语言方式确立等。
这其中叙述时间的变形是对小说素材加工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区别的重要方面。
伊丽莎白·鲍温说得好,“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
”可见,时间也是作家小说叙事艺术风格的重要标志。
怎样认识小说中的叙事时间?时间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物理时间,一种是心理时间。
物理时间是指自然存在的时间。
它是不受人的意识影响的客观存在,永向一个方向流逝,不停止,不重复,不逆流。
心理时间是人的心理感觉的时间。
它是人的一种主观存在,可以随意将自然时间延长、紧缩、停滞、省略,以至交叉、倒流。
物理时间是纯客观的,心理时间是纯主观的。
小说的叙事时间既不是纯客观的又不是纯主观的,而是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
这种两重性要求叙事时间是在自然规律所规定的不可违背的客观性前提下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和把握。
论鲁迅《祝福》的叙事话语一、引言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短篇小说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和情节。
《祝福》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位勇敢坚强的女性白桦林的故事。
在该小说中,鲁迅运用了许多叙事话语,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氛围,本文将对《祝福》的叙事话语进行探讨。
二、叙事的主题《祝福》的主题是人性的关怀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小说着重描写了白桦林这个女性角色的艰辛历程,她在各种困境下都保持着一份坚韧不拔和乐观的态度,最终获得了真正的祝福。
鲁迅在小说中通过叙事话语来表现出这种主题,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叙事的角度在小说中,鲁迅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即改用“我”来叙述故事。
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者更加亲近故事的主人公,更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她的坚韧不拔和执着精神。
例如,在小说开头,鲁迅写道:“我记得,那是大约廿年前的事;我还小,不过却已经记得很清楚了。
……”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鲁迅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温暖而亲切的环境中。
四、叙事的结构小说的叙事结构相对简单,主要分为三部分:开头、中间和结尾。
在开头部分,鲁迅通过回忆的方式介绍了白桦林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她。
中间部分是白桦林奋斗的过程,她在经历了各种挫折和困难后,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结尾部分,鲁迅通过白桦林的一番话道出了小说的主旨:“等到了最坏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还有一点力量……”这种叙事结构简洁明了,概括性强,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整个故事。
五、叙事的语言鲁迅在《祝福》中的叙事语言简洁明了,富有情感。
例如,在描写白桦林和她的父亲的感情时,鲁迅写道:“她的父亲虽说年迈,却像个慈爱的孩子一样依偎在她的怀里。
”这句话情感真挚,极具感染力,让人感觉到一种亲情的温暖。
此外,鲁迅在小说中还使用了许多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让整个叙事更加生动有趣。
六、叙事的语调《祝福》的叙事语调温和、朴素,既不浮夸,也不过于冷静。
《狂人日记》的时间叙事结构探析摘要:《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以内容的独特和表现的深切独具异彩。
文章从《狂人日记》的时间叙事结构出发,深入剖析狂人的情感变化、形象衍变以及与常人引发的冲突和吃人意义等方面,力图从时间境遇的角度为我们描述、展示、再现“狂者”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狂人日记》时间叙事结构狂人形象吃人主题一、导言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时间文学”发展时期。
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鲁迅《狂人日记》,这是时间文学的典型代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
所谓“人的时间文学”,从广义上讲,是指某个时期的文学文本以“人”为描写对象,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将人上升到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审美层次的文学创作方法;同时将个体的时间置于客观环境、主观感情的表达之中,对事件的构合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统一于文本之中,实现了时间是构合文学文本的关键要素。
从狭义上讲,指的是五四时期,尤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充分发挥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让时间成为一种关系文本叙事结构的关键要素,表达作家情感的重要方法和实现个体思想延伸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说,经由作家感知和体验过的时间成为整合的和归属的而非梳理的和破碎的质素,它的最终确立固然离不开作为文本的物质技术条件。
但更深层意义上来说是作家痛苦的体验所致并加以艺术塑造和话语定格,是作为思想家而非社会普通成员的介入和发声。
这种文本的“时间”真正的顺序不是机械式的物理时间顺序,而是主体心灵的独特感悟和当下思考。
现实时间重在展示,客观冷静,为宇宙的原生状态;艺术时间(心理时间)重在展开,抑扬顿挫,为生命的情势征候。
在这类文本中,时间呈现出两种表征系统:其一,它基本上构成了隐藏于人物本身的恐惧、焦虑、绝望;其二,它成为了映射人物生命本体、生命意义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