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夫之的情景说
- 格式:doc
- 大小:36.0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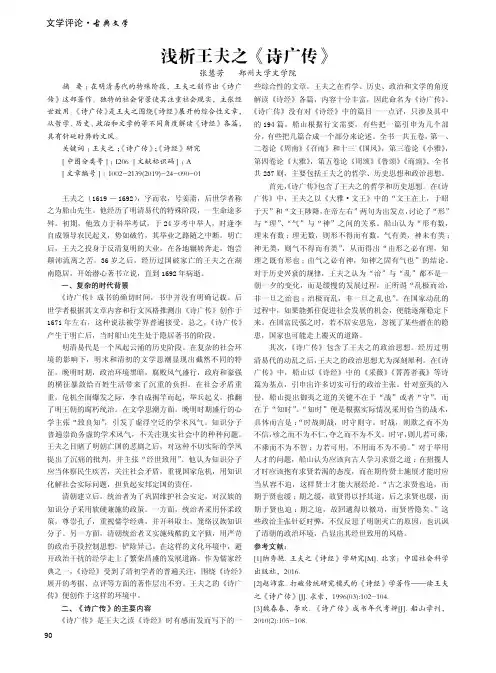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浅析王夫之《诗广传》张慧芳 郑州大学文学院摘 要:在明清易代的特殊阶段,王夫之创作出《诗广传》这部著作。
独特的社会背景使其注重社会现实,主张经世致用。
《诗广传》是王夫之围绕《诗经》展开的综合性文章,从哲学、历史、政治和文学的等不同角度解读《诗经》各篇,具有针砭时弊的文风。
关键词:王夫之;《诗广传》;《诗经》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90-01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后世学者称之为船山先生。
他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特殊阶段,一生命途多舛。
初期,他致力于科举考试,于24岁考中举人,时逢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势如破竹,其举业之路随之中断。
明亡后,王夫之投身于反清复明的大业,在各地辗转奔走,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36岁之后,经历过国破家亡的王夫之在湖南隐居,开始潜心著书立说,直到1692年病逝。
一、复杂的时代背景《诗广传》成书的确切时间,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
后世学者根据其文章内容和行文风格推测出《诗广传》创作于1671年左右,这种说法被学界普遍接受。
总之,《诗广传》产生于明亡后,当时船山先生处于隐居著书的阶段。
明清易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阶段。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明末和清初的文学思潮显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晚明时期,政治环境黑暗,腐败风气盛行,政府和豪强的横征暴敛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全面爆发之际,李自成揭竿而起,举兵起义,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
在文学思潮方面,晚明时期盛行的心学主张“致良知”,引发了虚浮空泛的学术风气。
知识分子普遍崇尚务虚的学术风气,不关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
王夫之目睹了明朝亡国的悲剧之后,对这种不切实际的学风提出了沉痛的批判,并主张“经世致用”。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体察民生疾苦,关注社会矛盾,重视国家危机,用知识化解社会实际问题,担负起安邦定国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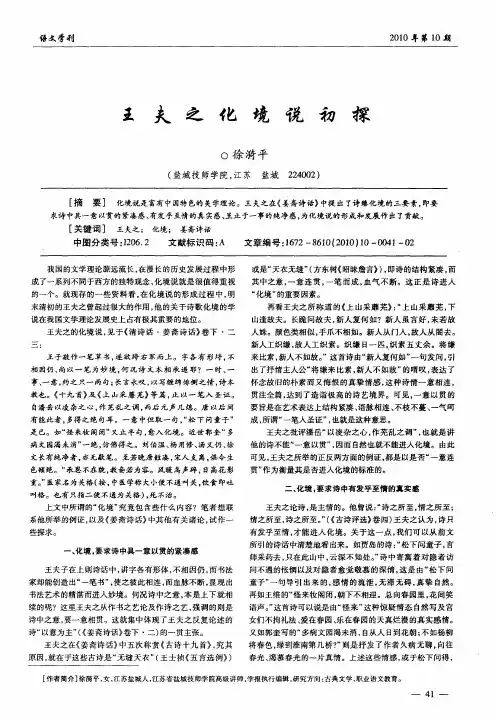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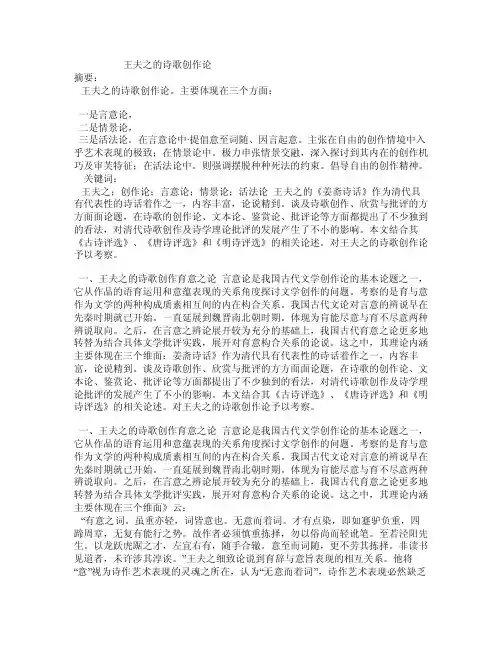
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摘要: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言意论,二是情景论,三是活法论。
在言意论中·提倡意至词随、因言起意。
主张在自由的创作情境中入乎艺术表现的极致;在情景论中。
极力申张情景交融,深入探讨到其内在的创作机巧及审芙特征;在活法论中。
则强调摆脱种种死法的约束。
倡导自由的创作精神。
关键词:王夫之;创作论;言意论;情景论;活法论王夫之的《姜斋诗话》作为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话着作之一,内容丰富,论说精到。
谈及诗歌创作、欣赏与批评的方方面面论题,在诗歌的创作论、文本论、鉴赏论、批评论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看法,对清代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本文结合其《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的相关论述。
对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予以考察。
一、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育意之论言意论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基本论题之一,它从作品的语育运用和意蕴表现的关系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
考察的是育与意作为文学的两种构成质素相互间的内在构合关系。
我国古代文论对言意的辨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
一直延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体现为肓能尽意与育不尽意两种辨说取向。
之后,在言意之辨论展开较为充分的基础上,我国古代育意之论更多地转替为结合具体文学批评实践,展开对育意构合关系的论说。
这之中,其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姜斋诗话》作为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话着作之一,内容丰富,论说精到。
谈及诗歌创作、欣赏与批评的方方面面论题,在诗歌的创作论、文本论、鉴赏论、批评论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看法,对清代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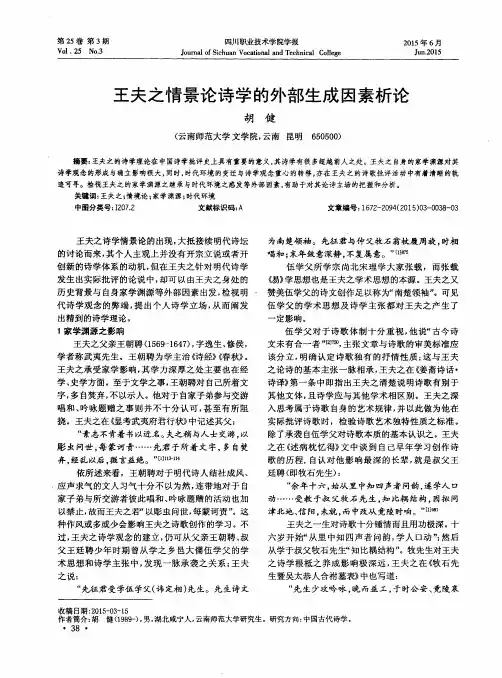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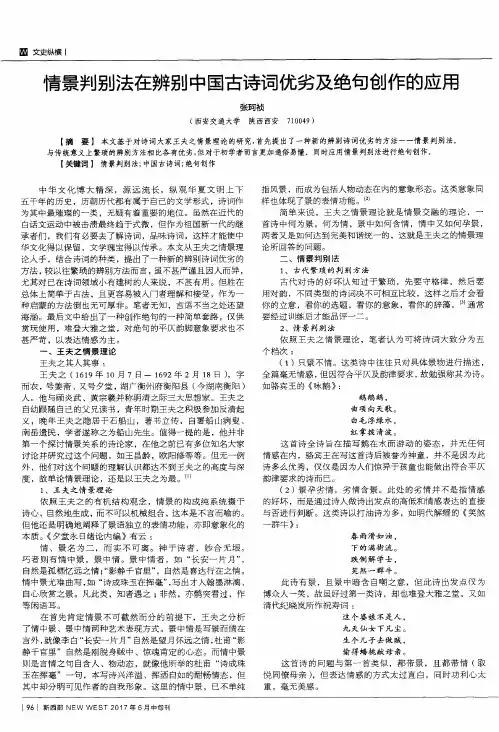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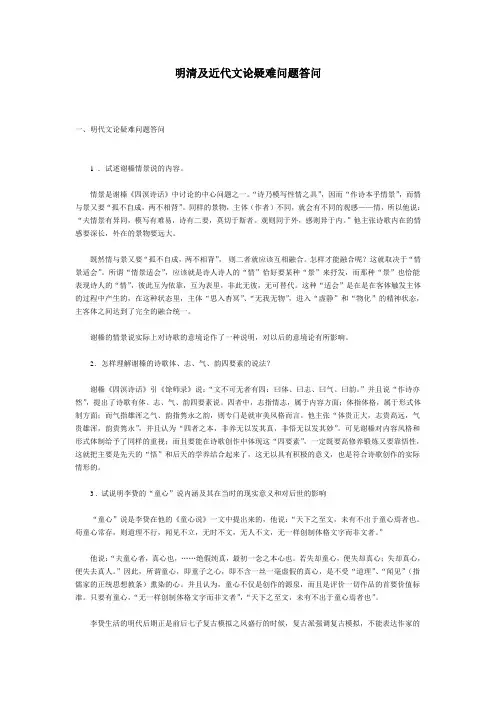
明清及近代文论疑难问题答问一、明代文论疑难问题答问1 .试述谢榛情景说的内容。
情景是谢榛《四溟诗话》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诗乃模写性情之具”,因而“作诗本乎情景”,而情与景又要“孤不自成,两不相背”。
同样的景物,主体(作者)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观感——情,所以他说:“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
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
”他主张诗歌内在的情感要深长,外在的景物要远大。
既然情与景又要“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则二者就应该互相融合。
怎样才能融合呢?这就取决于“情景适会”。
所谓“情景适会”,应该就是诗人诗人的“情”恰好要某种“景”来抒发,而那种“景”也恰能表现诗人的“情”,彼此互为依靠,互为表里,非此无彼,无可替代。
这种“适会”是在是在客体触发主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种状态里,主体“思入杳冥”、“无我无物”,进入“虚静”和“物化”的精神状态,主客体之间达到了完全的融合统一。
谢榛的情景说实际上对诗歌的意境论作了一种说明,对以后的意境论有所影响。
2.怎样理解谢榛的诗歌体、志、气、韵四要素的说法?谢榛《四溟诗话》引《馀师录》说:“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并且说“作诗亦然”,提出了诗歌有体、志、气、韵四要素说。
四者中,志指情志,属于内容方面;体指体格,属于形式体制方面;而气指雄浑之气、韵指隽永之韵,则专门是就审美风格而言。
他主张“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并且认为“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发其妙”。
可见谢榛对内容风格和形式体制给予了同样的重视;而且要能在诗歌创作中体现这“四要素”,一定既要高修养锻炼又要靠悟性,这就把主要是先天的“悟”和后天的学养结合起来了,这无以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是符合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形的。
3 . 试说明李贽的“童心”说内涵及其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童心”说是李贽在他的《童心说》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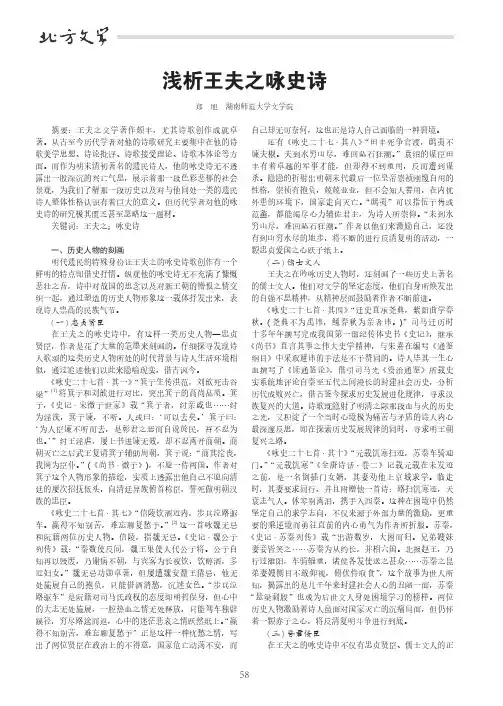
58浅析王夫之咏史诗郑 旭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王夫之文学著作颇丰,尤其诗歌创作成就卓著。
从古至今历代学者对他的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诗歌美学思想、诗论批评、诗歌接受理论、诗歌本体论等方面。
而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他的咏史诗无不透露出一股深沉的兴亡气息,展示着那一段色彩悲郁的社会景观,为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以及对与他同处一类的遗民诗人整体性格认识有着巨大的意义。
但历代学者对他的咏史诗的研究极其匮乏甚至忽略这一题材。
关键词:王夫之;咏史诗一、历史人物的刻画明代遗民的特殊身份让王夫之的咏史诗歌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借史抒情。
纵观他的咏史诗无不充满了慷慨悲壮之音,诗中对故国的思念以及对新王朝的憎恨之情交织一起,通过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一载体抒发出来,表现诗人祟高的民族气节。
(一)忠贞贤臣在王夫之的咏史诗中,有这样一类历史人物—忠贞贤臣,作者是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刻画的。
仔细探寻发现诗人歌颂的这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与诗人生活环境相似,通过追述他们以此来隐喻现实,借古讽今。
《咏史二十七首·其一》“箕子生传洪范,刘歆死击谷梁”[1]将箕子和刘歆进行对比,突出箕子的高尚品质。
箕子,《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者,纣亲戚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
人或曰:‘可以去矣。
’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
’”纣王淫虐,屡上书进谏无效,却不忍离开商朝。
商朝灭亡之后武王复请箕子辅助周朝,箕子说:“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
”(《尚书·微子》),不愿一侍两国。
作者对箕子这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实质上透露出他自己不愿向清廷的屡次招抚低头,向清廷异族俯首称臣,誓死做明朝汉族的忠臣。
《咏史二十七首·其七》“信陵饮酒近内,步兵泣路驱车。
赢得不知别苦,难忘聊复愁予。
”[2]这一首咏魏无忌和阮籍两位历史人物。
信陵,指魏无忌。
《史记·魏公子列传》载:“秦数使反间,魏王果使人代公子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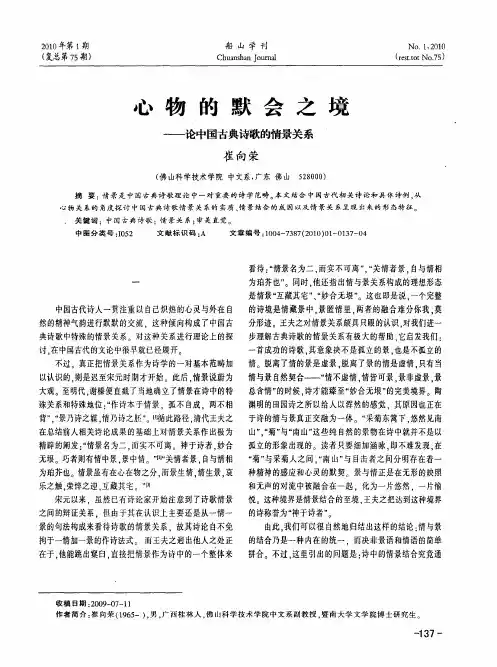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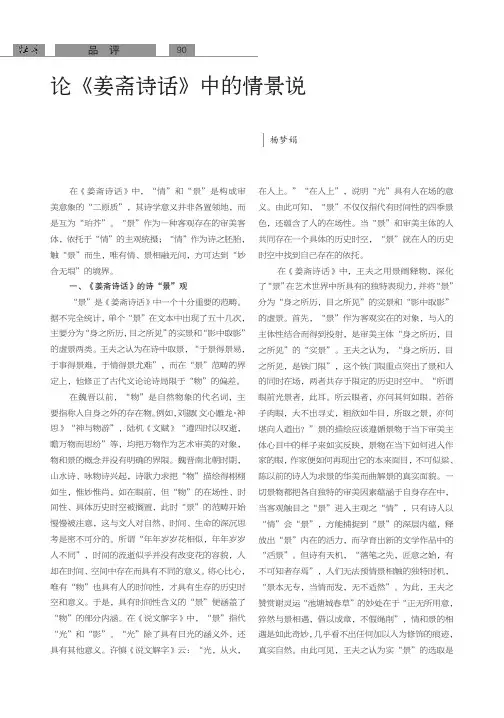
论《姜斋诗话》中的情景说杨梦娟在《姜斋诗话》中,“情”和“景”是构成审美意象的“二原质”,其诗学意义并非各置领地,而是互为“珀芥”。
“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审美客体,依托于“情”的主观统摄;“情”作为诗之胚胎,触“景”而生,唯有情、景相融无间,方可达到“妙合无垠”的境界。
一、《姜斋诗话》的诗“景”观“景”是《姜斋诗话》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
据不完全统计,单个“景”在文本中出现了五十几次,主要分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实景和“影中取影”的虚景两类。
王夫之认为在诗中取景,“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而在“景”范畴的界定上,他修正了古代文论论诗局限于“物”的偏差。
在魏晋以前,“物”是自然物象的代名词,主要指称人自身之外的存在物。
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神与物游”,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等,均把万物作为艺术审美的对象,物和景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咏物诗兴起,诗歌力求把“物”描绘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如在眼前,但“物”的在场性、时间性、具体历史时空被搁置,此时“景”的范畴开始慢慢被注意,这与文人对自然、时间、生命的深沉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时间的流逝似乎并没有改变花的容貌,人却在时间、空间中存在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将心比心,唯有“物”也具有人的时间性,才具有生存的历史时空和意义。
于是,具有时间性含义的“景”便涵盖了“物”的部分内涵。
在《说文解字》中,“景”指代“光”和“影”。
“光”除了具有日光的涵义外,还具有其他意义。
许慎《说文解字》云:“光,从火,在人上。
”“在人上”,说明“光”具有人在场的意义。
由此可知,“景”不仅仅指代有时间性的四季景色,还蕴含了人的在场性。
当“景”和审美主体的人共同存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景”就在人的历史时空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依托。
在《姜斋诗话》中,王夫之用景阐释物,深化了“景”在艺术世界中所具有的独特表现力,并将“景”分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实景和“影中取影”的虚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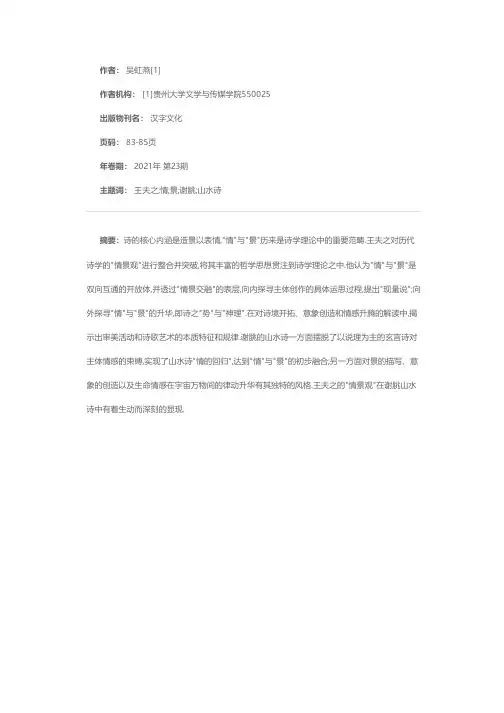
作者: 吴虹燕[1]
作者机构: [1]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550025
出版物刊名: 汉字文化
页码: 83-85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23期
主题词: 王夫之;情;景;谢脁;山水诗
摘要:诗的核心内涵是造景以表情,"情"与"景"历来是诗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王夫之对历代诗学的"情景观"进行整合并突破,将其丰富的哲学思想贯注到诗学理论之中.他认为"情"与"景"是双向互通的开放体,并透过"情景交融"的表层,向内探寻主体创作的具体运思过程,提出"现量说";向外探寻"情"与"景"的升华,即诗之"势"与"神理".在对诗境开拓、意象创造和情感升腾的解读中,揭示出审美活动和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谢脁的山水诗一方面摆脱了以说理为主的玄言诗对主体情感的束缚,实现了山水诗"情的回归",达到"情"与"景"的初步融合;另一方面对景的描写、意象的创造以及生命情感在宇宙万物间的律动升华有其独特的风格.王夫之的"情景观"在谢脁山水诗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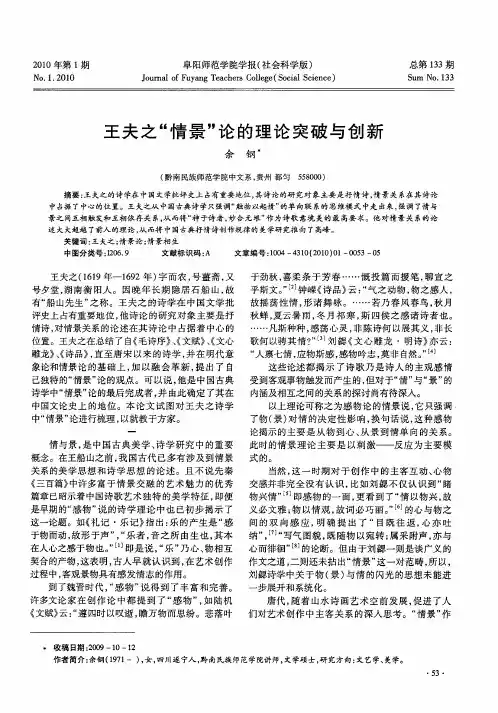
文艺理论60中国古典诗学的构成要素诸多,而情与景无疑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在中国诗歌发展早期,情与景即是诗歌的重要元素,且对诗歌的发生与演变有重要的影响。
而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及美学的集大成式的人物,王夫之的情景说在中国古典诗学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其情景说既继承了前人学说的优秀传统,又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将中国诗学中的情景学说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峰,同时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探讨中国古典诗学的发生时,情景的发生机制以及关系无疑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探讨的重要概念。
作为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范畴,情景学说源远流长,且愈来愈为诗家所重视。
在中国早期诗学理论中,就有丰富的关于情景理论的记载,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
《诗经》是散发出独特艺术魅力的成熟作品,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美学特征。
正如《小雅•采薇》之中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于景中生情,情中见景。
情景的交融恰到妙处,作者的心情恰如此景,合而为一,进入了独特的审美境界。
不过《诗经》并非理论专著,没有对情景学说做系统的评价。
情景学说作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其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生成、演变直至走向成熟的过程。
大体来说,情景说萌芽于先秦时期,至六朝已逐渐完善,唐宋之时达到高峰,而明清则进入成熟期,对前代多有总结,并出现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趋势。
关于情景说,学者多认为最初是情以物而兴起,是由于“感物”而引起的,这一点在陆机、刘勰、钟嶸等人的著作多有论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
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在此,著作是从创作发生上的角度来论述情的,诗人之情因物而生。
并且情与物的契合是一致的。
在陆机的诗缘情学说之后,刘勰、钟嶸等人进一步提出了“情以物迁”的学说。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①黄秀洁:《王夫之诗论中情与景》,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二辑),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印,1982年,第245页。
②萧驰:《船山天人之学在诗学中的展开———兼论情景交融与儒家生命智慧》,《圣道与诗心》,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22页。
③王诗评:《从王船山“乾坤并建”论其“情景交融”之诗学基础》,《中国学术年刊》第三十三期(春季号),2011年3月。
④李瑞卿:《王夫之诗学的〈易〉学观照》,《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3~320页。
就王夫之诗学与《易》学的关系,学界已经有所论述。
黄秀洁认识到王夫之没有把情与景看成绝然对立的东西,并援据《周易外传》认为,“这种立场植根于他的宇宙观”①。
萧驰的论述在黄氏的基础上有所加进:“船山诗学中的情/景范畴是由《易》学中乾/坤、阴/阳对应的符号范畴中展开。
”②之后,王诗评认为:“‘乾坤并建’是王船山‘情景交融’的理论基础”③;李瑞卿认为:王夫之“将阴阳错综引入到情景关系中,以自然化生的模式来观照诗的发生”④。
以上诸家,黄秀洁具开创之功,萧驰的论述最具理论深度。
但不无遗憾的是,就这一论题,却见不到论者对其语源出处的追索,而其正好源自《易》学史上的经典著述。
理解古人的学说不明出处,极易导致论述上的偏差,思理的阐发只有落在原始文献之上才深切著明。
所以,以《易》学为参照研究王夫之情景诗论,仍有可以开拓的理论空间。
一相为珀芥《周易》阴阳交感相应的思想,在王夫之对诗歌情景关系的认识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诗译》云: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
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
情景虽有在心在物陈勇内容提要:王夫之治学以《易》为宗,其情景诗论有着深厚的《易》学内蕴。
他有关“景自与情相为珀芥”的说法,即依据阴阳交感相应的思想,认为情与景的感应是同步的、无涯际的,“珀芥”之喻强调情景之间的异类相感,实际上肯定了取景的客观化。
王夫之中国古典美学在明末清初进⼊了⾃⼰的总结时期。
作为这⼀时期的标志,是王夫之和叶燮的美学体系。
王夫之,《姜斋诗话》、《古诗/唐诗/明诗评选》三本。
王夫之建⽴了⼀个以诗歌的审美意象为中⼼的美学体系。
情景说。
对诗歌意象的基本结构进⾏了分析。
诗的本体乃是审美意象。
现量说。
对审美观照、审美感兴的基本性质作了深刻的分析。
在情景说和现量说的基础上对诗歌意象的整体性、真实性、多义性、独创性等特点作了深⼊的分析。
情景说王廷相指出,诗歌之所以动⼈,就在于意象。
审美意象乃是诗的本体。
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王廷相的这⼀说法。
对“情直致⽽难动物”的发展:王夫之明确区分了“诗”和“志”、“意”。
⼀⾸诗好不好,不在于“意”如何,⽽在于审美意象如何。
诗⼈把⾃⼰有限的、确定的“意”强加于读者,是不可能使⼈感动的。
对“⾔征实⽽寡余味”对发展:王夫之明确区分了“诗”和“史”。
诗虽然可以叙事,但并不等于写史,是要创造意象。
写诗虽然也要剪裁,却是从实落笔。
⼆者有本质的不同,所以王夫之对与杜甫的⼀些诗“于史有余,于诗不⾜”。
(唉其实就是站在⾃⼰⾓度上的理解啦。
王夫之认为的诗已经是⼀个⾼度凝结的艺术了,诗的本体就是审美意象了。
但是王所处的时代和杜所处的时代是截然不同的。
在唐代,诗是⼀种主要的⽂体,不仅是艺术,更多的是为政治所⽤,批判社会、表达⾃⼰的政见、警戒统治者等等,不是为了美⽽作的诗。
)王廷相提出“⾔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难动物”的命题,归结到⼀点,就是诗的本体是“意象”。
但是他对诗歌“意象”的基本结构并没有进⾏分析。
王夫之则总结了宋、元、明 美学家的成果,对诗歌“意象”的基本结构作了具体的分析,这就是他有名的情景说。
诗不同于志、不同于史,诗是审美意象,那意象是什么?意象就是情与景的内在统⼀。
情景的统⼀乃是诗歌意象的基本结构。
诗歌的审美意象不是孤⽴的景、也不是孤⽴的情,景离开了情就成了虚景,情离开了景就是虚情,情景必须是内在的统⼀,⽽不是⼀联景、⼀联情这样外在的拼合。
浅析王夫之的情景说
摘要:王夫之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情景说”源远流长,在前人的
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情景说”理论。其对“情”与“景”的论述尤为全面,许多方面在
继承前人的同时又突破了前人的局限。他从中国古典诗学之强调“触物以起请”的单向联系的模
式中走出来,强调了情与景之间相互触发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作
为诗歌意境美的最高要求。本文通过探究王夫之诗学理论、分析诗歌创作中的情景关系、
(兴及
情景之间的关系及其现量说在情景关系中的体现,从更深层次来挖掘情景说的内在意蕴。)
结合
具体的诗歌作品,浅析王夫之提出的对于情景的艺术处理方式——“情中景,景中情”。以及他
所推崇的独特至高的艺术境界——情景秒和无垠。
关键词: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薑斋,又号夕堂,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长居石船
山,故有船山先生之称。他是一位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创造性贡献的文
学理论家。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情景说,这套情景说关系的论述在其诗论
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在我国文论史上,关于情与景的探讨源远流长,有关情景的论说十分的丰富。到了晚清,王国
维将情景论升华并提出了境界说,明末清初的诗歌理论家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前人
情境论的思想精华,总结了自两汉的《毛诗序》、魏晋南北朝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
龙》、以及钟嵘的《诗品》,直至唐宋以来的诗学,并在明代象征论和情境论的基础上加以融会革
新,提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情境论观点——强调创作中情景之间的关系,批评那种以“一
情一景为格律”的诗法规范的和情景分离的创作倾向,反复申明“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
情与景相互依存,水乳交融而不露痕迹。其情境论是支撑王国维“境界说”走向集大成的巨人,
他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明清之际的一位承上启下的、十分重要
的诗歌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一、简要回顾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情景说。
情景说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王夫之之前,我国就已有许许多多
的有关情景关系的美学思想和诗学思想的论述。且不说在先前《三百篇》中,许多富有情景交融
的艺术魅力的优秀篇章昭示着中国诗歌艺术特征的美学特征。即便是早期的“感物”说的诗学理
论中已初步揭示了这一课题。到了魏晋时代,“感物说”得到了丰富和完善。许多文论家在创作
中都提到了“感物”,如陆机的《文赋》中有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慨投篇
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1】(《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通过陆机在这里的论
述,我们可以得出“诗歌乃是诗人的主观情感受到客观事物触发而产生的”。但对于情与景的内
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唐代,随着山水诗画艺术空前的发展,促进
了人们对艺术创作中主客关系的深入思考,“情景”作为诗的美学范畴被正是提了出来。宋代的
山水画诗意更趋成熟,已有人初步的揭示了情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即情中有景,静中
有情。元代的情景论有所发展,但还不成熟。一方面指出情与景之间应相互渗透——“景在情中,
情在景中”。另一方面又坚持从律诗的句法安排角度来探讨情与景结合的具体模式,推崇一句情
一句景的组合模式。可见元代的情景论大有发展,但是他最终还是未能摆脱诗的句法结构的束缚。
在明代,情景论已经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局面,谢榛抓住了情景交融乃是诗生成之根本,从宋人言
情景不离章法句法的狭隘圈子跳了出来,深化了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
的诗论家,摆脱不了从诗法给格律角度来论情景,且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混乱。
二,情景交融
从情景说的发展史来看,情与景的论述一直都在进步,但是一直到明代都还未成熟,都还摆
脱不了从诗法格律的角度来论情景。直到到了王夫之手上,情景论才真正的上升到诗歌美学的高
度,并成为一种系统的诗学创作理论。王夫之认为在诗歌的情景关系中,情景两者不可分开而说,
情是景,景是情,互不相干,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作为诗人应该将情与景融合为一。即“妙
和无垠”,“互藏其宅”,这样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心与物融,情与景合。王夫之所谓“景”有
两种含义:一是指外界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比如“景生情”;另一是指存在于诗歌作品中的“景”
或“景语”。有人把王夫之所说的诗歌作品中的“景”单纯地理解为自然景色的描写,这显然是
片面的。王夫之所说的“景”是个广义的,而自然景物的描写仅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当然,除
了自然景物外,一切社会人事、性情器物的具体描写,在王夫之那里都称作“景”。所以它是“景象”、
“图景”的意思,指诗歌的形象意义的具体描写。情与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名为二而实不
可离”,二者“互藏其宅”互相转换呈现“景生情,情生景”和“情中景”、“景中情”的现象。故有“景者
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其实,从王夫之的论述和诗例来看,所谓的“景中情”,就是以抒情为主,
描写所构成的形象为抒情服务,情感色彩比较明显强烈。
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其艺术特征与写作技巧都离不开“情”与“景”的描写。王夫之在他的《姜
斎诗话》中也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他自己的诗论主张——情景说。他反复指出:“情”与“景”是
审美意象不可分离的因素,他在《姜斋诗话》中云:“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
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情和景的关系:第一,在王夫之看来,最好的是情
景“妙合无垠”,结合的天衣无缝,无法划分;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中蕴涵有情,如(李
白《子夜吴哥》)“长安一片月”,自然(在长安月夜之景中)有一种(女子)独自栖息,思
念远征夫君的情怀。(杜甫《喜达行在所》)“影静千宫里”,自然有(诗人长期流离后)终于
到达天子所在之地的欢喜之情。;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让读者看到诗中带有感情
的形象特别难以曲折地表达,如(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成珠玉在挥毫”,写
出了诗人才子纵情挥毫,驰骋笔墨的自我欣赏的欣喜之景。总之,写景定为生情,写情必寓
于景。景不能脱离情,情也不能脱离景。景脱离了情,景就成了虚景,就不能构成审美意象。
情脱离了景,情就成了虚情,也不能构成审美意象。这就是他所说的“情、景名为二,而实
不可离”。
王夫之诗论的对象主要是抒情诗,他强调诗歌的抒情性,这是他论诗的出发点。他主要从时
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表达抒情诗歌的艺术特质,提出了“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观点。即在时间上,
诗歌所表现的应是诗人“一时”的感情活动;在空间上,诗歌所表现的应是诗人驻足于某一定点
所观周遭的事。从本质上来说,即景与情之间必须有思想,从而达到情景交融。比如:“池塘生
春草”、“蝴蝶飞南国”,从中可以看到情景交融的最佳境界。在中国众多优秀的古典诗歌中,情
和景是密不可分的,情缘景生,景中含情而情景交融已然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审美境界创造的普遍
形式。情的抒发要借助于景,景的呈现隐含着情。理解情景交融,其实乃是主观与客观,抽象与
具体,情感与形象的统一。我国古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则突出体现了这种主客体情景互生的关
系。又如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一首歌咏景观的诗。其中一句:“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从中可以看到诗人从一开始就置于江潮连海、月共潮生、水绕芳甸的自然花
林的良辰美景之中。但是诗人并未沉浸于此美景中无法自拔,而遐思冥想地运用跳跃型思路回归
于人生。后句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诗
人从景观欣赏跳跃到人生体验感悟上,月的永存,人生的短暂,使得人生的意义变的更加非凡。
接下来的诗句:“白云一片去悠悠,清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诗人
又从白云飘忽、扁舟逐波得眼前景物转而跳跃到人生相思、相念与离愁别恨的意味之中,用“昨
夜闲潭梦花落,可怜春半不还家”之类精妙细微的情景来表达寄寓男女恨别的凄苦寂寞。诗人面
对自然景观,将情景交融合二为一,这种触景生情,情景交融较之前人的理论往前推进了一步。
参考文献:
【1】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
][3]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4][5]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郭邵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