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刺客聂隐娘》对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营造
- 格式:docx
- 大小:12.61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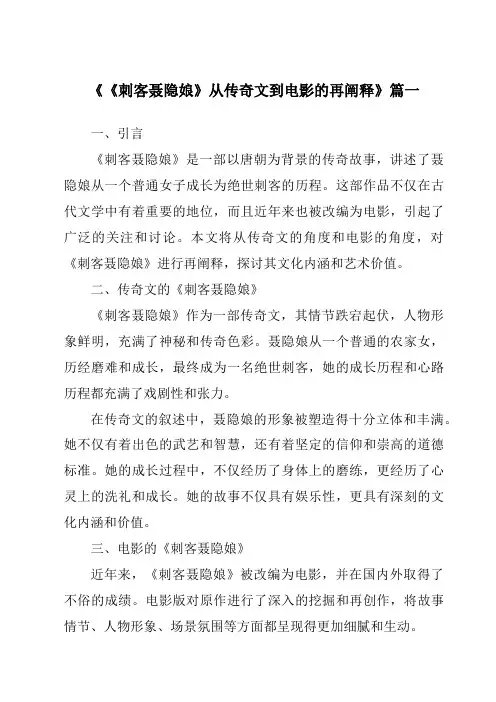
《《刺客聂隐娘》从传奇文到电影的再阐释》篇一一、引言《刺客聂隐娘》是一部以唐朝为背景的传奇故事,讲述了聂隐娘从一个普通女子成长为绝世刺客的历程。
这部作品不仅在古代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近年来也被改编为电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将从传奇文的角度和电影的角度,对《刺客聂隐娘》进行再阐释,探讨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二、传奇文的《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作为一部传奇文,其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色彩。
聂隐娘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历经磨难和成长,最终成为一名绝世刺客,她的成长历程和心路历程都充满了戏剧性和张力。
在传奇文的叙述中,聂隐娘的形象被塑造得十分立体和丰满。
她不仅有着出色的武艺和智慧,还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道德标准。
她的成长过程中,不仅经历了身体上的磨练,更经历了心灵上的洗礼和成长。
她的故事不仅具有娱乐性,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三、电影的《刺客聂隐娘》近年来,《刺客聂隐娘》被改编为电影,并在国内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电影版对原作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再创作,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场景氛围等方面都呈现得更加细腻和生动。
在电影中,导演通过精湛的镜头语言和画面表现,将唐朝的繁华和荒凉、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电影还通过对聂隐娘的成长历程和心路历程的深入挖掘,将她的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和丰满。
电影版不仅保留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更通过现代的电影语言将其呈现得更加生动和有力。
四、再阐释从传奇文到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再阐释具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这种再阐释不仅是对原作的一种传承和发展,更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通过对聂隐娘的形象和故事进行深入挖掘和再创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
其次,《刺客聂隐娘》的再阐释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在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难,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和鼓舞自己。
聂隐娘的形象和故事,正是一种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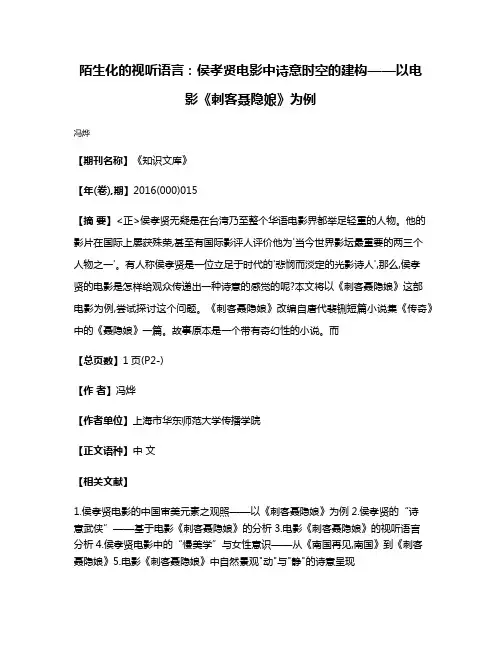
陌生化的视听语言:侯孝贤电影中诗意时空的建构——以电
影《刺客聂隐娘》为例
冯烨
【期刊名称】《知识文库》
【年(卷),期】2016(000)015
【摘要】<正>侯孝贤无疑是在台湾乃至整个华语电影界都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影片在国际上屡获殊荣,甚至有国际影评人评价他为'当今世界影坛最重要的两三个人物之一'。
有人称侯孝贤是一位立足于时代的'悲悯而淡定的光影诗人',那么,侯孝
贤的电影是怎样给观众传递出一种诗意的感觉的呢?本文将以《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为例,尝试探讨这个问题。
《刺客聂隐娘》改编自唐代裴铏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的《聂隐娘》一篇。
故事原本是一个带有奇幻性的小说。
而
【总页数】1页(P2-)
【作者】冯烨
【作者单位】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侯孝贤电影的中国审美元素之观照——以《刺客聂隐娘》为例
2.侯孝贤的“诗
意武侠”——基于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分析3.电影《刺客聂隐娘》的视听语言
分析4.侯孝贤电影中的“慢美学”与女性意识——从《南国再见,南国》到《刺客聂隐娘》5.电影《刺客聂隐娘》中自然景观"动"与"静"的诗意呈现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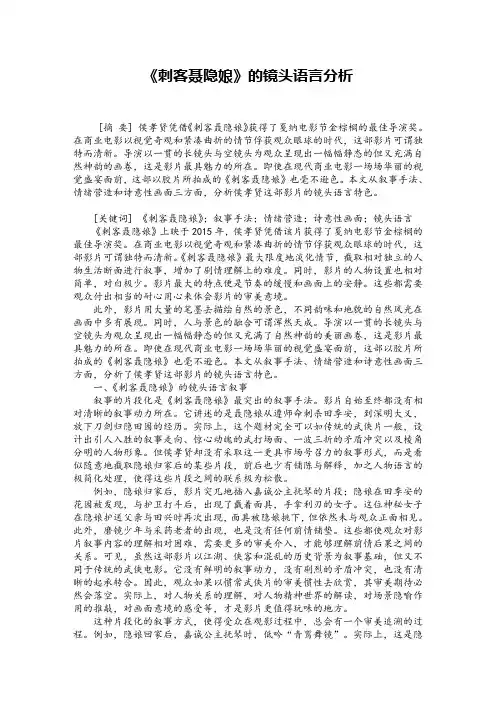
《刺客聂隐娘》的镜头语言分析[摘要] 侯孝贤凭借《刺客聂隐娘》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的最佳导演奖。
在商业电影以视觉奇观和紧凑曲折的情节俘获观众眼球的时代,这部影片可谓独特而清新。
导演以一贯的长镜头与空镜头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幅静态的但又充满自然神韵的画卷,这是影片最具魅力的所在。
即使在现代商业电影一场场华丽的视觉盛宴面前,这部以胶片所拍成的《刺客聂隐娘》也毫不逊色。
本文从叙事手法、情绪营造和诗意性画面三方面,分析侯孝贤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特色。
[关键词] 《刺客聂隐娘》;叙事手法;情绪营造;诗意性画面;镜头语言《刺客聂隐娘》上映于2015年,侯孝贤凭借该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的最佳导演奖。
在商业电影以视觉奇观和紧凑曲折的情节俘获观众眼球的时代,这部影片可谓独特而清新。
《刺客聂隐娘》最大限度地淡化情节,截取相对独立的人物生活断面进行叙事,增加了剧情理解上的难度。
同时,影片的人物设置也相对简单,对白极少。
影片最大的特点便是节奏的缓慢和画面上的安静。
这些都需要观众付出相当的耐心用心来体会影片的审美意境。
此外,影片用大量的笔墨去描绘自然的景色,不同韵味和地貌的自然风光在画面中多有展现。
同时,人与景色的融合可谓浑然天成。
导演以一贯的长镜头与空镜头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幅静态的但又充满了自然神韵的美丽画卷,这是影片最具魅力的所在。
即使在现代商业电影一场场华丽的视觉盛宴面前,这部以胶片所拍成的《刺客聂隐娘》也毫不逊色。
本文从叙事手法、情绪营造和诗意性画面三方面,分析了侯孝贤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特色。
一、《刺客聂隐娘》的镜头语言叙事叙事的片段化是《刺客聂隐娘》最突出的叙事手法。
影片自始至终都没有相对清晰的叙事动力所在。
它讲述的是聂隐娘从遵师命刺杀田季安,到深明大义,放下刀剑归隐田园的经历。
实际上,这个题材完全可以如传统的武侠片一般,设计出引人入胜的叙事走向、惊心动魄的武打场面、一波三折的矛盾冲突以及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
但侯孝贤却没有采取这一更具市场号召力的叙事形式,而是看似随意地截取隐娘归家后的某些片段,前后也少有铺陈与解释,加之人物语言的极简化处理,使得这些片段之间的联系极为松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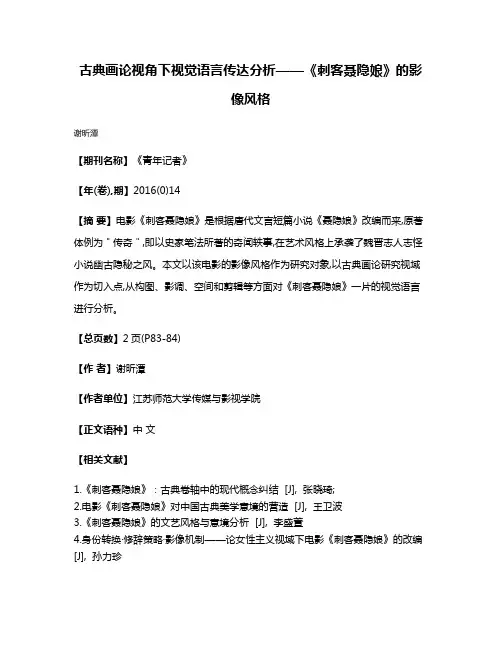
古典画论视角下视觉语言传达分析——《刺客聂隐娘》的影
像风格
谢昕潭
【期刊名称】《青年记者》
【年(卷),期】2016(0)14
【摘要】电影《刺客聂隐娘》是根据唐代文言短篇小说《聂隐娘》改编而来,原著体例为"传奇",即以史家笔法所著的奇闻轶事,在艺术风格上承袭了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幽古隐秘之风。
本文以该电影的影像风格作为研究对象,以古典画论研究视域作为切入点,从构图、影调、空间和剪辑等方面对《刺客聂隐娘》一片的视觉语言进行分析。
【总页数】2页(P83-84)
【作者】谢昕潭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刺客聂隐娘》:古典卷轴中的现代概念纠结 [J], 张晓琦;
2.电影《刺客聂隐娘》对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营造 [J], 王卫波
3.《刺客聂隐娘》的文艺风格与意境分析 [J], 李盛萱
4.身份转换·修辞策略·影像机制——论女性主义视域下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改编[J], 孙力珍
5.孤独的坚守:侯孝贤的电影美学风格——试析武侠电影《刺客聂隐娘》 [J], 牛肇鑫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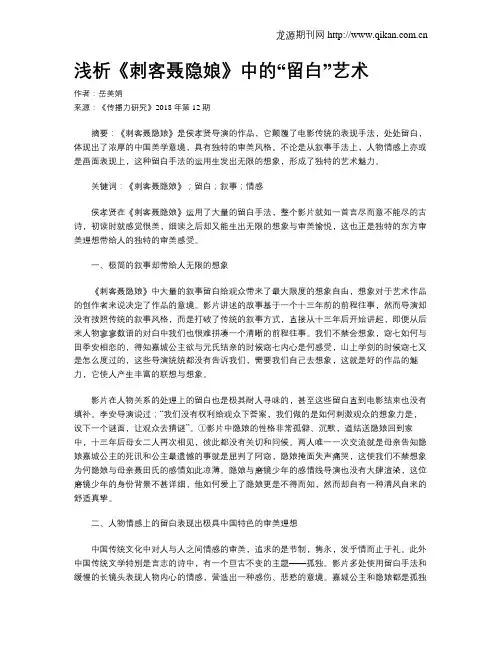
浅析《刺客聂隐娘》中的“留白”艺术作者:岳美娟来源:《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12期摘要:《刺客聂隐娘》是侯孝贤导演的作品,它颠覆了电影传统的表现手法,处处留白,体现出了浓厚的中国美学意境,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
不论是从叙事手法上,人物情感上亦或是画面表现上,这种留白手法的运用生发出无限的想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刺客聂隐娘》;留白;叙事;情感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运用了大量的留白手法,整个影片就如一首言尽而意不能尽的古诗,初读时就感觉很美,细读之后却又能生出无限的想象与审美愉悦,这也正是独特的东方审美理想带给人的独特的审美感受。
一、极简的叙事却带给人无限的想象《刺客聂隐娘》中大量的叙事留白给观众带来了最大限度的想象自由,想象对于艺术作品的创作者来说决定了作品的意境。
影片讲述的故事基于一个十三年前的前程往事,然而导演却没有按照传统的叙事风格,而是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直接从十三年后开始讲起,即便从后来人物寥寥数语的对白中我们也很难拼凑一个清晰的前程往事。
我们不禁会想象,窈七如何与田季安相恋的,得知嘉城公主欲与元氏结亲的时候窈七内心是何感受,山上学剑的时候窈七又是怎么度过的,这些导演统统都没有告诉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去想象,这就是好的作品的魅力,它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与想象。
影片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的留白也是极其耐人寻味的,甚至这些留白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有填补。
李安导演说过;“我们没有权利给观众下答案,我们做的是如何刺激观众的想象力是,设下一个谜面,让观众去猜谜”。
①影片中隐娘的性格非常孤僻、沉默,道姑送隐娘回到家中,十三年后母女二人再次相见,彼此都没有关切和问候。
两人唯一一次交流就是母亲告知隐娘嘉城公主的死讯和公主最遗憾的事就是屈判了阿窈,隐娘掩面失声痛哭,这使我们不禁想象为何隐娘与母亲聂田氏的感情如此凉薄。
隐娘与磨镜少年的感情线导演也没有大肆渲染,这位磨镜少年的身份背景不甚详细,他如何爱上了隐娘更是不得而知,然而却自有一种清风自来的舒适真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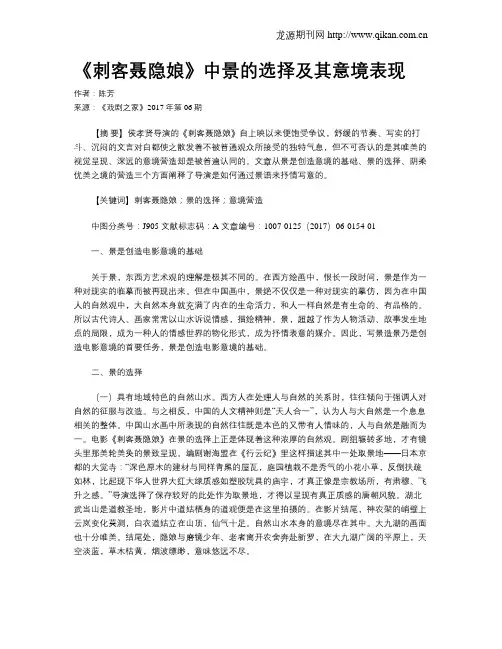
《刺客聂隐娘》中景的选择及其意境表现作者:陈芳来源:《戏剧之家》2017年第06期【摘要】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自上映以来便饱受争议,舒缓的节奏、写实的打斗、沉闷的文言对白都使之散发着不被普通观众所接受的独特气息,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唯美的视觉呈现、深远的意境营造却是被普遍认同的。
文章从景是创造意境的基础、景的选择、阴柔优美之境的营造三个方面阐释了导演是如何通过景语来抒情写意的。
【关键词】刺客聂隐娘;景的选择;意境营造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154-01一、景是创造电影意境的基础关于景,东西方艺术观的理解是极其不同的。
在西方绘画中,很长一段时间,景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的临摹而被再现出来。
但在中国画中,景绝不仅仅是一种对现实的摹仿,因为在中国人的自然观中,大自然本身就充满了内在的生命活力,和人一样自然是有生命的、有品格的。
所以古代诗人、画家常常以山水诉说情感,描绘精神。
景,超越了作为人物活动、故事发生地点的局限,成为一种人的情感世界的物化形式,成为抒情表意的媒介。
因此,写景造景乃是创造电影意境的首要任务,景是创造电影意境的基础。
二、景的选择(一)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山水。
西方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倾向于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
与之相反,中国的人文精神则是“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大自然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
中国山水画中所表现的自然往往既是本色的又带有人情味的,人与自然是融而为一。
电影《刺客聂隐娘》在景的选择上正是体现着这种浓厚的自然观。
剧组辗转多地,才有镜头里那美轮美奂的景致呈现。
编剧谢海盟在《行云纪》里这样描述其中一处取景地——日本京都的大觉寺:“深色原木的建材与同样青黑的屋瓦,庭园植栽不是秀气的小花小草,反倒扶疏如林,比起现下华人世界大红大绿质感如塑胶玩具的庙宇,才真正像是宗教场所,有肃穆、飞升之感。
”导演选择了保存较好的此处作为取景地,才得以呈现有真正质感的唐朝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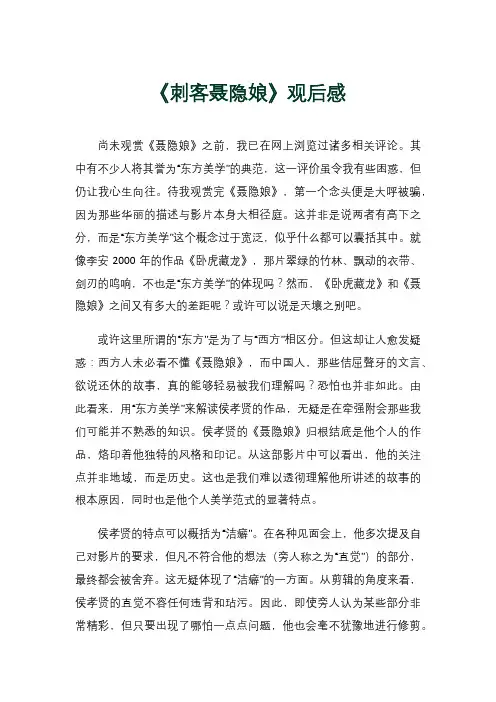
《刺客聂隐娘》观后感尚未观赏《聂隐娘》之前,我已在网上浏览过诸多相关评论。
其中有不少人将其誉为“东方美学”的典范,这一评价虽令我有些困惑,但仍让我心生向往。
待我观赏完《聂隐娘》,第一个念头便是大呼被骗,因为那些华丽的描述与影片本身大相径庭。
这并非是说两者有高下之分,而是“东方美学”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似乎什么都可以囊括其中。
就像李安 2000 年的作品《卧虎藏龙》,那片翠绿的竹林、飘动的衣带、剑刃的鸣响,不也是“东方美学”的体现吗?然而,《卧虎藏龙》和《聂隐娘》之间又有多大的差距呢?或许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吧。
或许这里所谓的“东方”是为了与“西方”相区分。
但这却让人愈发疑惑:西方人未必看不懂《聂隐娘》,而中国人,那些佶屈聱牙的文言、欲说还休的故事,真的能够轻易被我们理解吗?恐怕也并非如此。
由此看来,用“东方美学”来解读侯孝贤的作品,无疑是在牵强附会那些我们可能并不熟悉的知识。
侯孝贤的《聂隐娘》归根结底是他个人的作品,烙印着他独特的风格和印记。
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出,他的关注点并非地域,而是历史。
这也是我们难以透彻理解他所讲述的故事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他个人美学范式的显著特点。
侯孝贤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洁癖”。
在各种见面会上,他多次提及自己对影片的要求,但凡不符合他的想法(旁人称之为“直觉”)的部分,最终都会被舍弃。
这无疑体现了“洁癖”的一方面。
从剪辑的角度来看,侯孝贤的直觉不容任何违背和玷污。
因此,即使旁人认为某些部分非常精彩,但只要出现了哪怕一点点问题,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修剪。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洁癖”导致了《聂隐娘》的“难懂”。
结果就是,整部影片的剧情只剩下了骨架,那些蒙太奇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枝节、能让结构主义者玩出花样的细碎段落,都已被剪辑得无影无踪。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见,侯孝贤也在“洁癖”的影响下,在“极简”的对立面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视觉奇观。
那些未经后期处理的山涧瀑流、缭绕云雾、自然景观,以及那些经过无数次构思和雕琢才形成的深焦与长镜、庄严和摇曳,都将《聂隐娘》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和巅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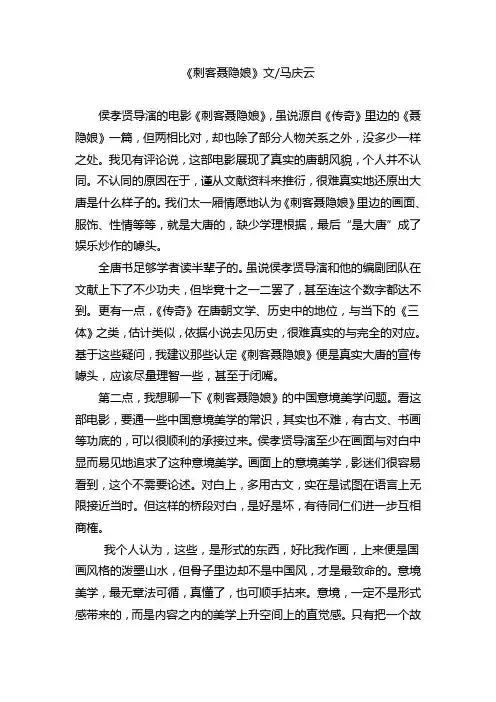
《刺客聂隐娘》文/马庆云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刺客聂隐娘》,虽说源自《传奇》里边的《聂隐娘》一篇,但两相比对,却也除了部分人物关系之外,没多少一样之处。
我见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展现了真实的唐朝风貌,个人并不认同。
不认同的原因在于,谨从文献资料来推衍,很难真实地还原出大唐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太一厢情愿地认为《刺客聂隐娘》里边的画面、服饰、性情等等,就是大唐的,缺少学理根据,最后“是大唐”成了娱乐炒作的噱头。
全唐书足够学者读半辈子的。
虽说侯孝贤导演和他的编剧团队在文献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毕竟十之一二罢了,甚至连这个数字都达不到。
更有一点,《传奇》在唐朝文学、历史中的地位,与当下的《三体》之类,估计类似,依据小说去见历史,很难真实的与完全的对应。
基于这些疑问,我建议那些认定《刺客聂隐娘》便是真实大唐的宣传噱头,应该尽量理智一些,甚至于闭嘴。
第二点,我想聊一下《刺客聂隐娘》的中国意境美学问题。
看这部电影,要通一些中国意境美学的常识,其实也不难,有古文、书画等功底的,可以很顺利的承接过来。
侯孝贤导演至少在画面与对白中显而易见地追求了这种意境美学。
画面上的意境美学,影迷们很容易看到,这个不需要论述。
对白上,多用古文,实在是试图在语言上无限接近当时。
但这样的桥段对白,是好是坏,有待同仁们进一步互相商榷。
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形式的东西,好比我作画,上来便是国画风格的泼墨山水,但骨子里边却不是中国风,才是最致命的。
意境美学,最无章法可循,真懂了,也可顺手拈来。
意境,一定不是形式感带来的,而是内容之内的美学上升空间上的直觉感。
只有把一个故事讲圆润了,才能形成美感。
我不知道,磕磕巴巴地讲故事,如何形成美感。
侯孝贤的桎梏,就是用镜头的方式试图讲这个中国传统意境上的故事,他没有先人经验,不像唐诗宋词那样,大伙都可以顺手做一小段,毕竟可学古人。
镜头美学,很可能从根本上就限制住了这种所谓的中国传统叙事。
侯孝贤导演又太过于追求大量画面的所谓中国画风格,因此丧失了讲故事的正确节奏,如一个口吃患者在吟诵唐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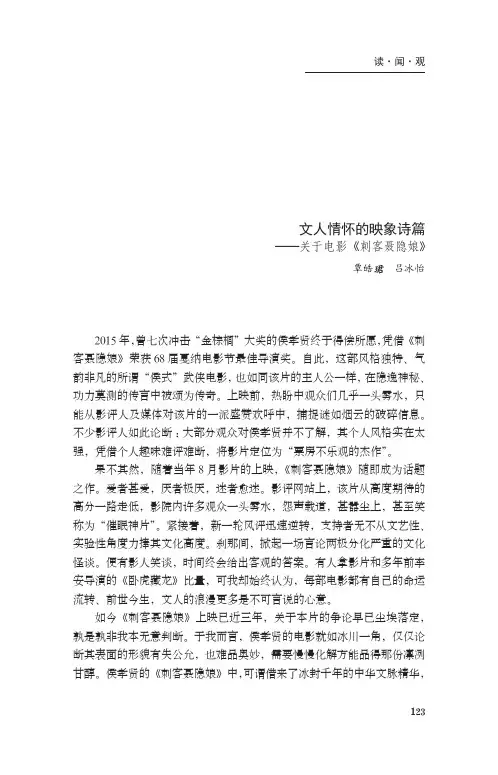
文人情怀的映象诗篇——关于电影《刺客聂隐娘》覃皓 吕冰怡2015年,曾七次冲击“金棕榈”大奖的侯孝贤终于得偿所愿,凭借《刺客聂隐娘》荣获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自此,这部风格独特、气韵非凡的所谓“侯式”武侠电影,也如同该片的主人公一样,在隐逸神秘、功力莫测的传言中被颂为传奇。
上映前,热盼中观众们几乎一头雾水,只能从影评人及媒体对该片的一派盛赞欢呼中,捕捉谜如烟云的破碎信息。
不少影评人如此论断:大部分观众对侯孝贤并不了解,其个人风格实在太强,凭借个人趣味难评难断,将影片定位为“票房不乐观的杰作”。
果不其然,随着当年8月影片的上映,《刺客聂隐娘》随即成为话题之作。
爱者甚爱,厌者极厌,迷者愈迷。
影评网站上,该片从高度期待的高分一路走低,影院内许多观众一头雾水,怨声载道,甚嚣尘上,甚至笑称为“催眠神片”。
紧接着,新一轮风评迅速逆转,支持者无不从文艺性、实验性角度力捧其文化高度。
刹那间,掀起一场言论两极分化严重的文化怪谈。
便有影人笑谈,时间终会给出客观的答案。
有人拿影片和多年前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比量,可我却始终认为,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流转、前世今生,文人的浪漫更多是不可言说的心意。
如今《刺客聂隐娘》上映已近三年,关于本片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孰是孰非我本无意判断。
于我而言,侯孝贤的电影就如冰川一角,仅仅论断其表面的形貌有失公允,也难品奥妙,需要慢慢化解方能品得那份凛冽甘醇。
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中,可谓借来了冰封千年的中华文脉精华,123献祭了他近乎半生的才华与时间。
文人初心,文脉渊源拍摄一部关于“刺客聂隐娘”的电影,是年近古稀的侯孝贤自学生时代开始便置于心头的夙愿,其文脉渊源亦堪称传奇中的传奇。
原本的唐传奇小说《聂隐娘》初始文本仅仅1700字,以诡异的文风、离奇的故事、玄妙的意境与生动的人物而被称为唐传奇中武侠小说代表之作。
侯孝贤从小痴迷武侠,无论是金庸小说还是功夫电影都广泛“研习”,唐人小说中的武侠传奇更是令他感到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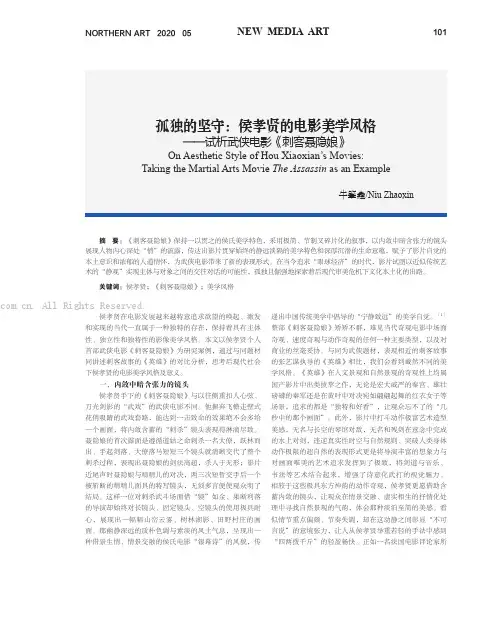
101NEW MEDIA ARTNORTHERN ART 2020 05摘 要:《刺客聂隐娘》保持一以贯之的侯氏美学特色,采用极简、节制又碎片化的叙事,以内敛中暗含张力的镜头展现人物内心深处“情”的流露,传达出影片贯穿始终的静远淡隔的美学特色和深厚沉潜的生命意蕴,赋予了影片自觉的本土意识和浓郁的人道情怀,为武侠电影带来了新的表现形式。
在当今追求“眼球经济”的时代,影片试图以近似传统艺术的“静观”实现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交往对话的可能性,孤独且倔强地探索着后现代审美危机下文化本土化的出路。
关键词:侯孝贤;《刺客聂隐娘》;美学风格侯孝贤在电影发展越来越特意追求欲望的唤起、激发和实现的当代一直属于一种独特的存在,保持着具有主体性、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影像美学风格。
本文以侯孝贤个人首部武侠电影《刺客聂隐娘》为研究案例,通过与同题材同讲述刺客故事的《英雄》的对比分析,思考后现代社会下侯孝贤的电影美学风格及意义。
一、内敛中暗含张力的镜头侯孝贤手下的《刺客聂隐娘》与以往侧重扣人心弦、刀光剑影的“武戏”的武侠电影不同。
他摒弃飞檐走壁式花俏吸睛的武戏套路,能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绝不会多给一个画面,将内敛含蓄的“刺杀”镜头表现得淋漓尽致。
聂隐娘的首次露面是遵循道姑之命刺杀一名大僚,跃林而出、手起剑落、大僚落马短短三个镜头就清晰交代了整个刺杀过程,表现出聂隐娘的剑法高超,杀人于无形;影片近尾声时聂隐娘与精精儿的对决,两三次短暂交手后一个被斩断的精精儿面具的特写镜头,无须多言便使观众明了结局。
这样一位对刺杀武斗场面惜“镜”如金、果断利落的导演却始终对长镜头、固定镜头、空镜头的使用极具耐心,展现出一幅幅山峦云雾、树林湖影、田野村庄的画面。
那幽静深远的质朴色调与素淡的风土气息,呈现出一种借景生情、情景交融的侯氏电影“银幕诗”的风貌,传递出中国传统美学中倡导的“宁静致远”的美学自觉。
[1]整部《刺客聂隐娘》矫矫不群,难见当代奇观电影中场面奇观、速度奇观与动作奇观的任何一种主要类型,以及对商业的丝毫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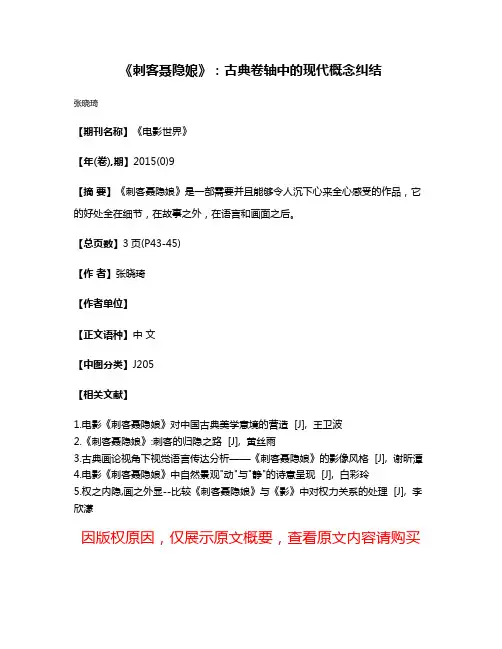
《刺客聂隐娘》:古典卷轴中的现代概念纠结
张晓琦
【期刊名称】《电影世界》
【年(卷),期】2015(0)9
【摘要】《刺客聂隐娘》是一部需要并且能够令人沉下心来全心感受的作品,它的好处全在细节,在故事之外,在语言和画面之后。
【总页数】3页(P43-45)
【作者】张晓琦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205
【相关文献】
1.电影《刺客聂隐娘》对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营造 [J], 王卫波
2.《刺客聂隐娘》:刺客的归隐之路 [J], 黄丝雨
3.古典画论视角下视觉语言传达分析——《刺客聂隐娘》的影像风格 [J], 谢昕潭
4.电影《刺客聂隐娘》中自然景观"动"与"静"的诗意呈现 [J], 白彩玲
5.权之内隐,画之外显--比较《刺客聂隐娘》与《影》中对权力关系的处理 [J], 李欣濛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刺客聂隐娘》观后感中秋时节,我有幸在奈良唐招提寺赶上了一场中秋赏月活动。
当夜幕完全降临,我们在寺外排起长队,终于得以入内。
在这个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竟还有如此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然而,正是在这片黝黯之中,我见到了东山魁夷的屏风《云影》与《涛声》,那一刻,我才真正领略到唐人在散文中所描绘的那些溢美之词并非夸张。
而在二十一世纪的影院中观赏到《刺客聂隐娘》,则更让我有了类似的感受。
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无疑是近年来我在电影院中所看到的最令人满足的作品之一,我坚信它必将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一名影迷,能赶上这样一部被铭记的影片的放映,此生已无憾事。
侯孝贤成功地将武侠片从一种打斗的类型中解脱出来,不再局限于江湖恩怨和人生哲理的探讨。
他将焦点投向了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这种功力非深厚者难以企及。
看过《聂隐娘》后,李安的《卧虎藏龙》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在我眼中都显得“商业”了许多。
相较于《聂隐娘》,《卧虎藏龙》和《一代宗师》仍将武侠片视为一种类型片来拍摄。
类型片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有精彩的打斗场面,同时也要有深入的人生思考。
然而,侯孝贤并非如此,他的选择让许多怀揣着看武侠大片或探讨江湖人生心态的观众感到失望,甚至望而却步。
在《聂隐娘》中,打斗场面寥寥无几,每场平均只有三四个回合,简洁而克制,绝无炫耀技巧之嫌。
侯孝贤的果断取舍,为《刺客聂隐娘》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没有了取悦观众的大段打斗,整部影片显得更加悠远宁静,甚至可以说决绝。
它安静得让人能够听见晚唐夏夜里蛐蛐和金铃子的鸣叫声,清晰地感受到风进出幔子留下的痕迹。
当镜头静止,人物渐行渐远,我们仿佛看到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唐朝气韵。
或者说,这不仅仅是唐朝的气韵,更是从《诗经》到《汉乐府》,从甲骨文到草书所蕴含的“中国”或“东方”的气韵。
这种气质在中国电影中已经久违多年。
这种气韵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画面直觉,无论是中国画、唐诗宋词,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刺客聂隐娘观后感及人物分析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是由叶伟民执导,赵雅芝、黄秋生等主演的一部古装武侠片。
该片改编自金庸先生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聂隐娘这位宗师级刺客的故事。
在我观看完《刺客聂隐娘》后,我对影片整体呈现出的氛围、人物刻画以及剧情发展等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影片以古代背景为舞台,营造出了一种古朴、浑厚的氛围。
整个电影以寒冷、阴郁的色调为主,这种氛围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其中,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同时,电影中大量运用了古代建筑与景观的场景,如古城墙、庙宇、庭院等,这些场景不仅增添了古代风情,还为观众呈现出了一种古代江湖武林的氛围。
其次,影片刻画了一个个极具个性的人物角色。
其中,聂隐娘作为影片的主要角色,拥有超凡的刺杀技巧和冷酷的外表。
她聪明、机智,同时又充满了冷静和果断,这些特质使她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角色。
影片中刻画了聂隐娘的内心世界,通过她的动作、表情和台词等细节来展现她的情感和内心矛盾。
除聂隐娘外,影片还塑造了许多其他鲜明的角色,如高度忠诚的忍者、心机深沉的反派角色以及善良正直的戏子等,这些角色丰富了整个故事的层次和张力。
再者,故事情节的剧情发展令人过目不忘。
电影以刺杀任务为线索展开,紧凑的节奏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使得观众一直保持着紧张的观影体验。
影片通过多次的刺杀任务和追逐战斗,展现了聂隐娘惊险刺激的生活,同时也暴露了她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剧情的高潮部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逐渐揭开了聂隐娘背后隐秘的身世之谜,这种反转和发展让人意想不到,给予观众强烈的观看冲击力。
最后,《刺客聂隐娘》在深入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也对于人性与命运等主题做出了深刻的探讨。
聂隐娘作为一个职业刺客,常常面对道德与情感的冲突。
她在刺杀任务中展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对正义的追求和对亲情的执着。
她的内心矛盾和自我挣扎让人动容,引发了观众对于道德、正义与命运等深刻的思考。
总体而言,《刺客聂隐娘》在电影制作、人物刻画和剧情发展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高水平的表现。
电影《刺客聂隐娘》对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重要范畴,更是诗歌、绘画、书法、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
在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中,意境营造被视为构成艺术美的必要因素,更是衡量评判艺术作品品格高低的标准和关键。
电影作为舶来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更注重大众娱乐、消费等社会功能。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电影艺术家也把意境范畴纳入电影审美的视野,对电影进行本民族艺术经验的借鉴和化用,在丰富电影美学形态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电影的艺术品格。
作为东方电影的制作者,台湾导演侯孝贤对华语电影的民族化、本土化有着自觉的追求,其以多年的探索和坚持,拍摄了一系列具有独特人文关怀和鲜明写意倾向的影片,堪称为“诗意电影”的典范。
2015 年,侯孝贤拍摄的影片《刺客聂隐娘》,更是延续他鲜明的“诗意” 电影风格,不仅在思想内涵上表现了侯孝贤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且在电影语法和表现手法上,摒弃电影惯有的戏剧化叙事手法,形成淡化情节、注重氛围营造的诗意叙事,以长镜头、空镜头等拍摄手法呈现电影画面的诗意情景,以细腻的声音设计烘托意境营造,这些共同构成了影片表意空间的存在。
侯孝贤以意境营造作为其电影艺术探索的重要内容,不仅提升了本部影片的美学品格,更为中国电影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形成本民族的电影美学风格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对意境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中国古典美学“意境”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其概念和内涵也众说纷纭,然而,无论就其历史形成,还是就其本身的丰富内涵来看,“意境”的含义都不单指对外在物象的单纯描摹或单层面的自然再现,而是具有无限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的创构。
?W界认为,意境的哲学根源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内心世界的外化。
因此,艺术作品中意境的营造其实就是创作主体吸纳自然人生万象而在内心咀嚼、体味后所营造的,含意于“言”内,流“余味”于象外,能唤起接受主体对自然人生的无尽情思和体验的审美空间。
所以,意境的本质和精神,就在于这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的创构和拓展。
侯孝贤深受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其对“意境”理论的本质和精髓深有体会,其电影作品即是通过电影这样一种现代艺术形式营构了各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构成了独特的“东方情调”和“东方美学”风格。
作为侯孝贤的首部武侠电影作品,《刺客聂隐娘》更是延续了其“诗意电影”的美学风格,营造了独特审美意味的表意空间。
这个表意空间是一个综合性的意义层构,既包含创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和意志情趣,也包含经过摄影、剪辑、造型所呈现的电影画面和场景,更包含受众自己的想象和感受。
下面即从创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电影视听元素两方面细致剖析该部影片意境表意空间的营造。
意境表意空间的营造(一)创作者生命体验的投射:意境表意空间之一中国古典美学认为“意境”所呈现出的世界不同于外界物理存在的感性世界,而是带有情感性质的感性世界,这种以情感性质的形式所揭示的世界的意义就是意境的意蕴所在。
所以,中国古典美学总是用情景交融来说明意境的特质。
清代学者王夫之确定“情”与“景”为意境的一对基本范畴:“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
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
[1] 在这之后,朱光潜认为意境是“情” (情趣)与“景” (意象)的契合,宗白华也认为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
可见,情景交融作为意境的特质已经成为共识,电影意境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一特质,创作者的主体情思与电影画面的相融合,才能产生具有生命力的意境。
从这个角度而言,电影意境的生成需要创作者主体情思、生命体验的投射与灌注。
好的电影导演在这方面总是有着自觉地、有意识地追求。
侯孝贤即是这样一位导演。
侯孝贤曾讲:“我儿时爱吃芒果,有次踏树采摘芒果,站在树上突然静默下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树在轻抚树杈,俯瞰树下熙攘的人群,时间在那个时刻停了下来,看见了自己身处的时间与空间。
” [2] 由此可以断定,侯孝贤通过这种独特视角和镜头语言所呈现的电影世界,必定带着他自己的某种情感性质的投射,包含着他对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最原初的经验世界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又包含着一种抽离世外、俯瞰世间芸芸众生的悲悯之情。
这构成了其电影意境表意空间的第一层存在,影片《刺客聂隐娘》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侯孝贤借用一个武侠躯壳表达的,其实却是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
影片改编自唐传奇,借用历史中的某个封闭空间或者既定故事,演绎的却是侯孝贤对人性命运的感悟与思考。
影片中的聂隐娘,已不是唐传奇中的那个神秘侠客,而是经历着从刺客到女人的回归,从一个工具(刺客身份)到感受内心(受情感影响而放弃刺杀)再到回归生活(与磨镜少年离去)的转变,体现的正是侯孝贤对人的孤独状态、自我选择等生命境遇的体悟和思考。
总之,这种创作者本人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的投射和灌注,成为了该部影片“意境”表意空间存在的重要因素。
(二)视听语言的运用:意境表意空间之二电影的本质是视听艺术,不同视听语言的运用决定了电影不同的审美风格。
侯孝贤在电影视听语言的运用上,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他坚持以华夏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进行影像表达,追求具有东方文化格调和美学意蕴的电影风格。
侯孝贤曾经表示:“我感觉冲突没有什么好描写的,啪啪两下就没了,对我来讲是一种韵味……我感觉我们是华人、东方人看事情的角度,而且是我们的习惯,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是非常正直的民族,谁愿意听难听话呢?谁愿意直截了当地直接批判呢?没有,我们没有这种,很少……就像张爱玲所说,我们一落地其实就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所以你总是要绕一个弯,讲话就是要绕弯子,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直接。
这其实,就是因为有所谓的形式。
”[3] 正是这种含蓄婉转的东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造就了侯孝贤的影视表达视角与方式:他摒弃电影惯有的戏剧化叙事手法,以淡化情节、注重氛围营造的诗意叙事形成独特的影像叙事语法,以长镜头、空镜头等拍摄手法呈现电影画面的诗意情景,以细腻的声音设计烘托意境营造,从而构成其电影意境表意空间的又一层存在。
《刺客聂隐娘》的视听语言运用及表达完美地体现了这点。
1. 电影画面:意境营造的主体首先来看《刺客聂隐娘》的视觉元素――电影画面的意境营造。
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也是电影意境营造的主体。
观众对一部影片风格与审美的感受首先来自于一幅幅的电影画面。
为了营造这些画面的意境,首先在影像叙事手法上,侯孝贤摒弃惯有的戏剧化叙事手法,采用诗意叙事手法,最大限度地淡化情节,简化人物台词,用更多的镜头呈现人物情绪和心绪的画面。
如影片开头聂隐娘归家的片段场景,无论是侍女服侍聂隐娘沐浴更衣,还是聂隐娘拜见祖母及母亲亦或是影片突兀插入嘉城公主抚琴片段,表面看来似乎都游离于刺杀这一叙事主线,况且这些画面场景也缺乏强烈的视觉冲击,对于深受好莱坞大片和惯常武侠片影响的观众来讲,这样的画面不免枯燥乏味。
然而,影片却对其进行了较多篇幅和更多细节上的展示,正是因为这些画面和场景更能表现主人公聂隐娘初回日常生活中的不适、孤独等情感心绪,对影片主题“一个人没有同类”也起到了深化的作用。
所以,《刺客聂隐娘》虽是以传统侠客、刺杀为题材,但却不同于一般武侠题材电影的叙述套路,一般武侠题材电影所要极力展现的扣人心弦的叙事走向、惊心动魄的武打场面以及一波三折的矛盾冲突(戏剧化叙事)正是《聂隐娘》要规避和舍弃的。
其次,在具体的拍摄手法上,以长镜头、空镜头等拍摄手法呈现电影画面的诗意情景,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外景设计上。
其外景设计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为观众呈现出一幅幅充满着自然神韵的山水画卷,风起鸟落,雾霭山河,寒鸦涟漪,倒影幻化,烟云流荡,岚气清新,在这样元气淋漓的自然景象之中,不仅能感受到导演本人对中国古典美学生命意?R 的传承,更能感受到一种深邃的人生感、宇宙感乃至历史感,这正可谓艺术意境。
在影片中,这样的外景拍摄,侯孝贤更多以长镜头、空镜头呈现。
如影片结尾,聂隐娘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一起归隐江湖的情景,影片并没有简单地一闪而过,而是以时长足足一分半的长镜头予以呈现和展示。
摄影机明显采用的是固定机位,镜头凝滞不动,只有镜头中的人物与景物在不断变化。
聂隐娘等一行人逐渐从中景变为远景,人物背影越来越小,直至与远方黑色的树影逐渐融为一体,消失在天际之处。
而前景处,枯黄的野草仍在风中微微摇曳,翠绿的青山在远处静默伫立,湛蓝辽远的天空与之相互交映。
这种以固定的视角与静态的机位反衬人物的活动,营造出大自然的伟岸永恒与人类活动渺小短暂的强烈反差。
更深层次的意味则在于聂隐娘所生活的现实的、当下的、欲望的世界,包含着太多的矫饰、虚伪,太多的与人的真性相违背的东西,而只有在无限永恒的自然世界中,才能还原人质朴、原初的精神,彰显人的生命真性。
所以,聂隐娘最终违背师命,放下刺杀,远离纷争,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一起,隐匿江湖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真性也是影片合乎逻辑的展演。
2. 声音设计:意境营造的烘托除了画面元素,声音元素也是电影意境营造的有力手段。
影片《刺客聂隐娘》中的声音设计,对整部影片含蓄蕴藉的意境生成起到了很好的烘托和渲染作用。
首先影片采用的背景音乐很好地表现了人物复杂细腻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这比让人物直接情感爆发更具张力和韵味。
影片中人物情感的处理方式极其克制和内敛,无论是聂隐娘面对阔别多年的父母,还是在暗处窥视情人田季安,人物情绪很少外露,甚至连面部表情的变化都极其有限。
然而,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剧烈的内心冲突就隐藏在克制、隐忍的外表之下,背景音乐的使用使这种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复杂情感得以发掘,并产生无尽的审美韵味。
如嘉城公主抚琴片段,在萧瑟凄凉的琴声中嘉诚公主讲述了“青鸾舞镜,悲鸣而绝”的凄美故事,故事讲完琴声结束,背景音乐响起了幽怨缠绵的洞箫声。
那轻柔、涓细、如泣如诉的萧声,不仅传达出嘉诚公主难以言说的孤独幽怨心境,也暗示聂隐娘拥有同样难以言表的复杂心境。
另外,当聂隐娘放下玉佩引诱田季安出来时,响起的是紧张略带悬疑感的背景音乐,很好地表达出聂隐娘在刺杀对象与青梅竹马的昔日情人之间如何抉择、取舍的复杂矛盾心理。
当聂隐娘躲在帷幕后倾听田季安向胡姬讲述年少往事时,配的又是哀婉舒缓的音乐。
此时,躲在暗处的聂隐娘看似无声的存在,但哀婉惆怅的音乐旋律分明就是聂隐娘的心声流露。
一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全都在这哀婉的配乐声中了。
影片结尾处,采用了非洲打击乐“ RohaS,音乐旋律混杂了悲伤、喜悦以及更多的激荡之情。
不仅表达出聂隐娘经过重重挣扎后摆脱俗世束缚归隐江湖、走向自由境界的大悲大喜之情,更让观影者也产生一种追随聂隐娘而去,去过潇洒自由生活的审美快感。
由此可见,尽管影片人物本身并没有直接进行内心独白和情感展现,但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承担了人物内心感受表达的功能,而且更能产生体味不尽的审美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