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
- 格式:doc
- 大小:39.50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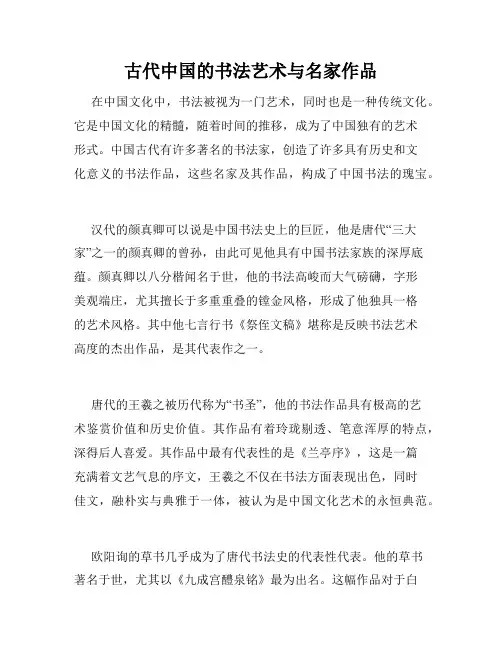
古代中国的书法艺术与名家作品在中国文化中,书法被视为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种传统文化。
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
中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创造了许多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书法作品,这些名家及其作品,构成了中国书法的瑰宝。
汉代的颜真卿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巨匠,他是唐代“三大家”之一的颜真卿的曾孙,由此可见他具有中国书法家族的深厚底蕴。
颜真卿以八分楷闻名于世,他的书法高峻而大气磅礴,字形美观端庄,尤其擅长于多重重叠的镗金风格,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其中他七言行书《祭侄文稿》堪称是反映书法艺术高度的杰出作品,是其代表作之一。
唐代的王羲之被历代称为“书圣”,他的书法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和历史价值。
其作品有着玲珑剔透、笔意浑厚的特点,深得后人喜爱。
其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兰亭序》,这是一篇充满着文艺气息的序文,王羲之不仅在书法方面表现出色,同时佳文,融朴实与典雅于一体,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永恒典范。
欧阳询的草书几乎成为了唐代书法史的代表性代表。
他的草书著名于世,尤其以《九成宫醴泉铭》最为出名。
这幅作品对于白话文的运用,尤其对于隶书与草书两种书体的结合是开创性的。
这幅作品在书法界一度被誉为“天下第一草书”。
beyond the abilities of any other calligrapher before or since and created the “Eight Immortals” styl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诸樊秦的春秋时期的楚国小官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中国书法史的佼佼者,他的字正如其人,深入骨髓,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诸樊秦的颜体草书,素有“能书能画,自成一家”的赞誉,代表作品有《Muxi Tie》和《Luoshenfu》,在中国书法史上高居一席之地。
另外,王献之、褚遂良、张旭等中国古代书法家也是不可逾越的巨匠,他们用自己的独特创意和风格创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都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中国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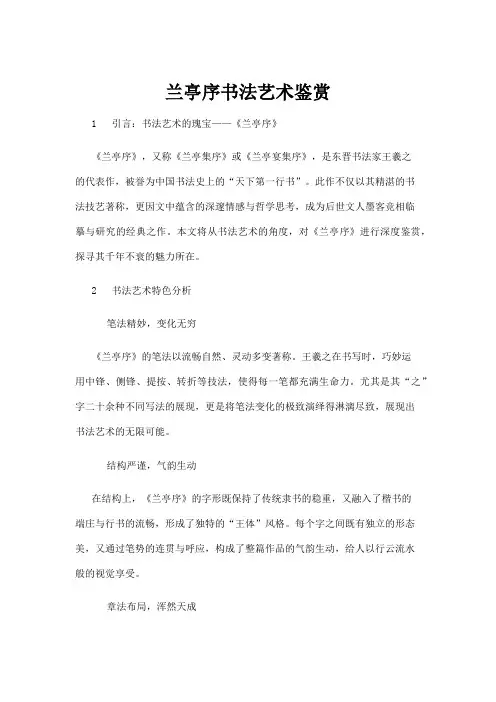
兰亭序书法艺术鉴赏1️⃣ 引言:书法艺术的瑰宝——《兰亭序》《兰亭序》,又称《兰亭集序》或《兰亭宴集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天下第一行书”。
此作不仅以其精湛的书法技艺著称,更因文中蕴含的深邃情感与哲学思考,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竞相临摹与研究的经典之作。
本文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兰亭序》进行深度鉴赏,探寻其千年不衰的魅力所在。
2️⃣ 书法艺术特色分析笔法精妙,变化无穷《兰亭序》的笔法以流畅自然、灵动多变著称。
王羲之在书写时,巧妙运用中锋、侧锋、提按、转折等技法,使得每一笔都充满生命力。
尤其是其“之”字二十余种不同写法的展现,更是将笔法变化的极致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书法艺术的无限可能。
结构严谨,气韵生动在结构上,《兰亭序》的字形既保持了传统隶书的稳重,又融入了楷书的端庄与行书的流畅,形成了独特的“王体”风格。
每个字之间既有独立的形态美,又通过笔势的连贯与呼应,构成了整篇作品的气韵生动,给人以行云流水般的视觉享受。
章法布局,浑然天成《兰亭序》的章法布局极为讲究,全文28行,324字,字字独立而又相互关联,行距疏密有致,字距恰到好处,形成了一种既和谐统一又富有节奏感的视觉效果。
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王羲之高超的书法技艺,更展现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3️⃣ 情感与哲学思想的融合《兰亭序》不仅是一篇书法作品,更是一篇情感丰富、思想深邃的散文。
文中描述了王羲之与友人于兰亭集会,饮酒赋诗,畅谈人生哲理的情景。
在王羲之的笔下,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也有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感慨。
这种情感与哲学思想的融合,使得《兰亭序》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富有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自然之美与人生哲理的交融王羲之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情的文字,将自然之美与人生哲理巧妙融合,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他感叹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但又能在瞬息万变中寻找到永恒的美与真理。
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自然的精神风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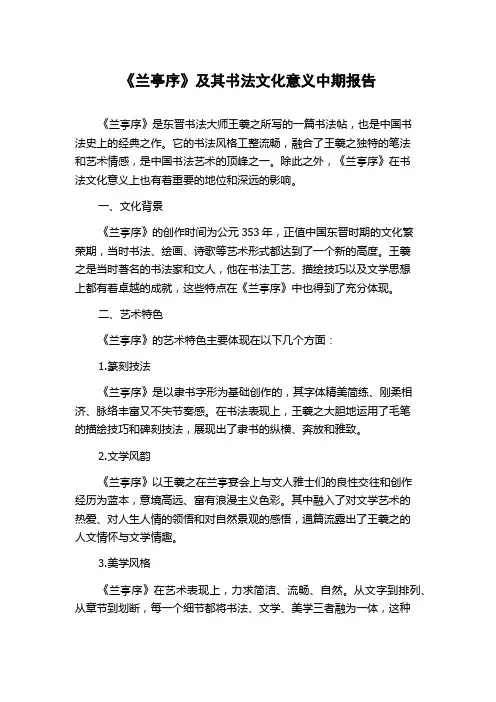
《兰亭序》及其书法文化意义中期报告《兰亭序》是东晋书法大师王羲之所写的一篇书法帖,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它的书法风格工整流畅,融合了王羲之独特的笔法和艺术情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顶峰之一。
除此之外,《兰亭序》在书法文化意义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一、文化背景《兰亭序》的创作时间为公元353年,正值中国东晋时期的文化繁荣期,当时书法、绘画、诗歌等艺术形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羲之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和文人,他在书法工艺、描绘技巧以及文学思想上都有着卓越的成就,这些特点在《兰亭序》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艺术特色《兰亭序》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篆刻技法《兰亭序》是以隶书字形为基础创作的,其字体精美简练、刚柔相济、脉络丰富又不失节奏感。
在书法表现上,王羲之大胆地运用了毛笔的描绘技巧和碑刻技法,展现出了隶书的纵横、奔放和雅致。
2.文学风韵《兰亭序》以王羲之在兰亭宴会上与文人雅士们的良性交往和创作经历为蓝本,意境高远、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其中融入了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对人生人情的领悟和对自然景观的感悟,通篇流露出了王羲之的人文情怀与文学情趣。
3.美学风格《兰亭序》在艺术表现上,力求简洁、流畅、自然。
从文字到排列、从章节到划断,每一个细节都将书法、文学、美学三者融为一体,这种雅致的联通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使《兰亭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璀璨夺目的瑰宝。
三、文化意义《兰亭序》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顶峰之作,它在书法文化意义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兰亭序》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技法对后来的书法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后来书法艺术的典范和标志。
同时,《兰亭序》的人文思想、文学情趣、美学风格也为后来的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
它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念,对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形成和流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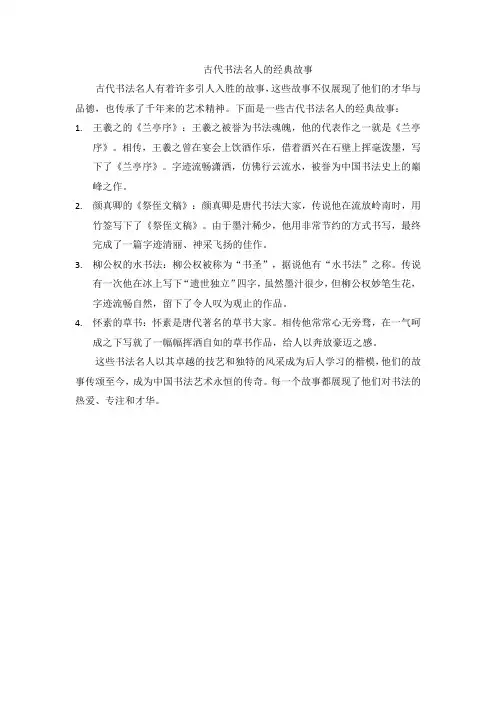
古代书法名人的经典故事
古代书法名人有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才华与品德,也传承了千年来的艺术精神。
下面是一些古代书法名人的经典故事:1.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羲之被誉为书法魂魄,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兰亭
序》。
相传,王羲之曾在宴会上饮酒作乐,借着酒兴在石壁上挥毫泼墨,写下了《兰亭序》。
字迹流畅潇洒,仿佛行云流水,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之作。
2.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大家,传说他在流放岭南时,用
竹签写下了《祭侄文稿》。
由于墨汁稀少,他用非常节约的方式书写,最终完成了一篇字迹清丽、神采飞扬的佳作。
3.柳公权的水书法:柳公权被称为“书圣”,据说他有“水书法”之称。
传说
有一次他在冰上写下“遗世独立”四字,虽然墨汁很少,但柳公权妙笔生花,字迹流畅自然,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
4.怀素的草书:怀素是唐代著名的草书大家。
相传他常常心无旁骛,在一气呵
成之下写就了一幅幅挥洒自如的草书作品,给人以奔放豪迈之感。
这些书法名人以其卓越的技艺和独特的风采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故事传颂至今,成为中国书法艺术永恒的传奇。
每一个故事都展现了他们对书法的热爱、专注和才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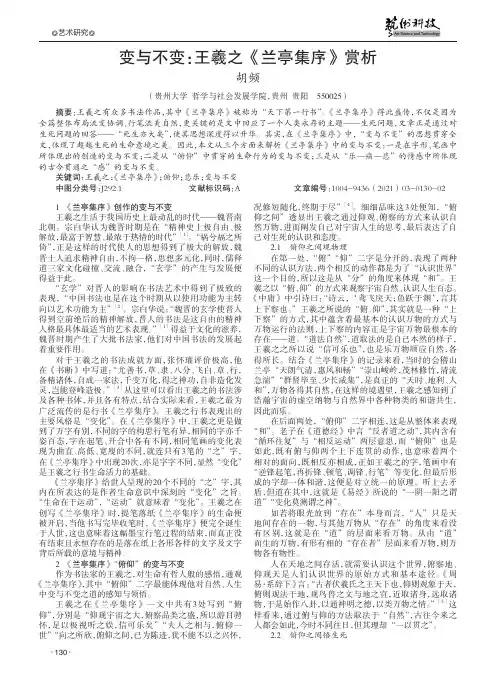
艺术研究变与不变:王羲之《兰亭集序》赏析胡频(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摘要:王羲之有众多书法作品,其中《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得此盛传,不仅是因为全篇整体布局流变协调、行笔流美自然,更关键的是文中回应了一个人类永存的主题——生死问题,文章正是通过对生死问题的回答——“死生亦大矣”,使其思想深度得以升华。
其实,在《兰亭集序》中,“变与不变”的思想贯穿全文,体现了超越生死的生命意境之美。
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解析《兰亭集序》中的变与不变:一是在字形、笔画中所体现出的创造的变与不变;二是从“俯仰”中贯穿的生命行为的变与不变;三是从“乐—痛—悲”的情感中所体现的古今贯通之“感”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王羲之;《兰亭集序》;俯仰;悲乐;变与不变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3-0130-021 《兰亭集序》创作的变与不变王羲之生活于我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魏晋南北朝。
宗白华认为魏晋时期是在“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1]。
“祸兮福之所倚”,正是这样的时代使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魏晋士人追求精神自由,不拘一格,思想多元化,同时,儒释道三家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便得益于此。
“玄学”对晋人的影响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极致的表现,“中国书法也是在这个时期从以使用功能为主转向以艺术功能为主”[2]。
宗白华说:“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
”[1]得益于文化的滋养,魏晋时期产生了大批书法家,他们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方面,张怀瓘评价极高,他在《书断》中写道:“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3]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羲之的书法涉及各种书体,并且各有特点,结合实际来看,王羲之最为广泛流传的是行书《兰亭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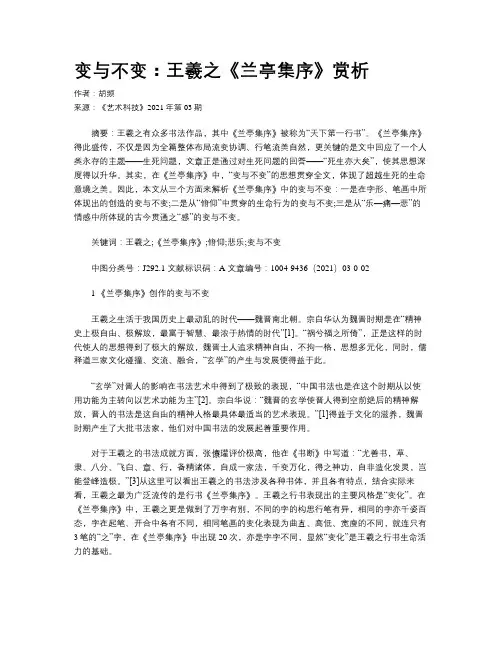
变与不变:王羲之《兰亭集序》赏析作者:胡频来源:《艺术科技》2021年第03期摘要:王羲之有众多书法作品,其中《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得此盛传,不仅是因为全篇整体布局流变协调、行笔流美自然,更关键的是文中回应了一个人类永存的主题——生死问题,文章正是通过对生死问题的回答——“死生亦大矣”,使其思想深度得以升华。
其实,在《兰亭集序》中,“变与不变”的思想贯穿全文,体现了超越生死的生命意境之美。
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解析《兰亭集序》中的变与不变:一是在字形、笔画中所体现出的创造的变与不变;二是从“俯仰”中贯穿的生命行为的变与不变;三是从“乐—痛—悲”的情感中所体现的古今贯通之“感”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王羲之;《兰亭集序》;俯仰;悲乐;变与不变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3-0-021 《兰亭集序》创作的变与不变王羲之生活于我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魏晋南北朝。
宗白华认为魏晋时期是在“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1]。
“祸兮福之所倚”,正是这样的时代使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魏晋士人追求精神自由,不拘一格,思想多元化,同时,儒释道三家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便得益于此。
“玄学”对晋人的影响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极致的表现,“中国书法也是在这个时期从以使用功能为主转向以艺术功能为主”[2]。
宗白华说:“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
”[1]得益于文化的滋养,魏晋时期产生了大批书法家,他们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方面,张懷瓘评价极高,他在《书断》中写道:“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3]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羲之的书法涉及各种书体,并且各有特点,结合实际来看,王羲之最为广泛流传的是行书《兰亭集序》。
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来源空间转载)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及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月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习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趋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出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得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成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家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携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重,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传承之绪。
王羲之书法的“变体”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四、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至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印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然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了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留传很少,以后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汇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难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书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串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书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阴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它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孙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合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全面表现。 以行书为代表的中和文化精神。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中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头,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间”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创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书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子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常,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和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书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到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的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可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二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可以发现: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理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