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新思考
- 格式:doc
- 大小:39.00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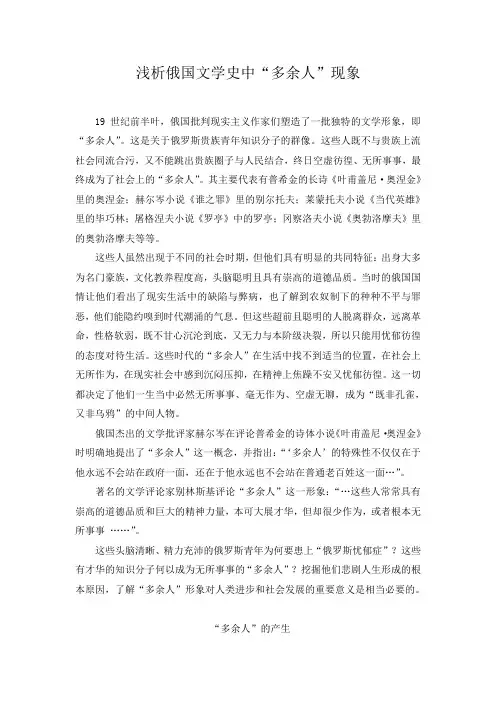
浅析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现象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
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期,但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
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
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
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这一形象:“…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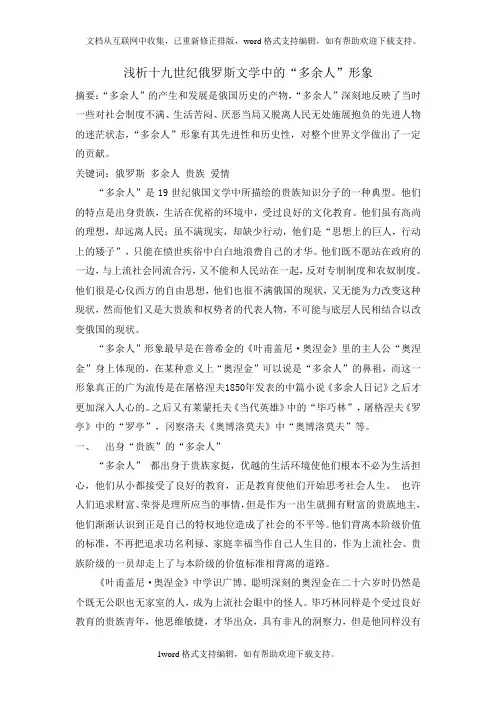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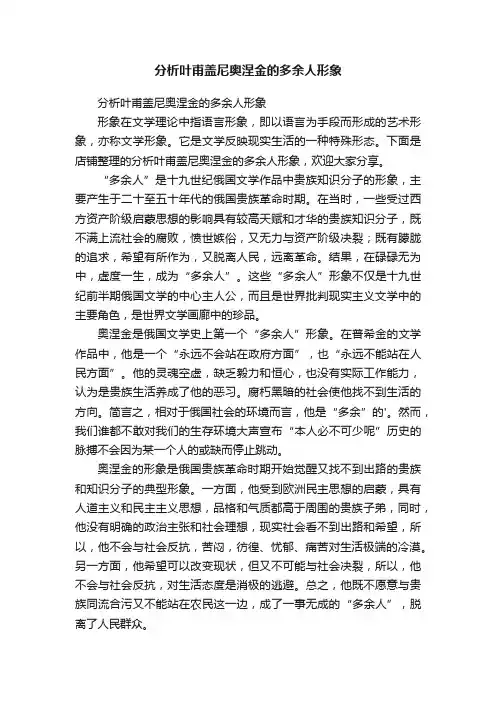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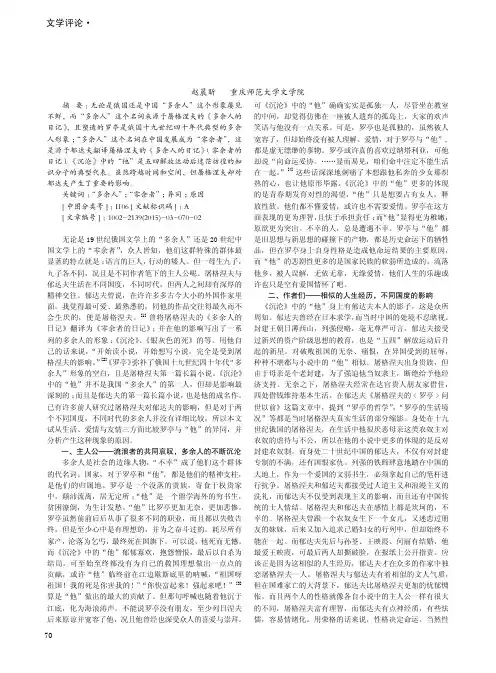

从普希金“多余人”形象分析俄国文学的民族性(一)摘要]《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之作,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研究可发现,多余人是当时社会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探索作品主人公奥涅金作为多余人存在的深层内涵,可以揭示出作者由自己的文化积淀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关键词]多余人;民族性;历史文化;宗教《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之作,是公认的俄罗斯文学的典范,小说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杜勃罗留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
”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的多余人的典型,诸如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他们身上无一不或多或少地有着奥涅金的影子。
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果,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它鲜明地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一、民族性特征的表现1.多余人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19世纪20年代正是俄罗斯解放运动第一代战士——贵族革命家成长的时期,同时也是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酝酿、爆发和失败的时期。
当时俄罗斯经历了1812年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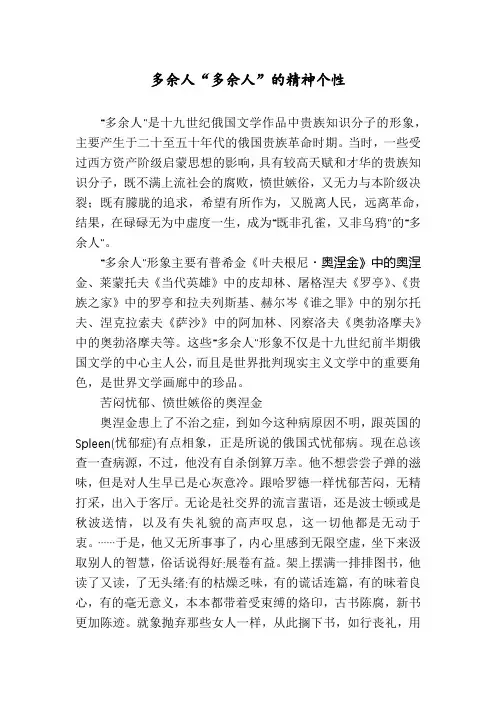
多余人“多余人”的精神个性“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主要有普希金《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中的罗亭和拉夫列斯基、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涅克拉索夫《萨沙》中的阿加林、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苦闷忧郁、愤世嫉俗的奥涅金奥涅金患上了不治之症,到如今这种病原因不明,跟英国的Spleen(忧郁症)有点相象,正是所说的俄国式忧郁病。
现在总该查一查病源,不过,他没有自杀倒算万幸。
他不想尝尝子弹的滋味,但是对人生早已是心灰意冷。
跟哈罗德一样忧郁苦闷,无精打采,出入于客厅。
无论是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还是波士顿或是秋波送情,以及有失礼貌的高声叹息,这一切他都是无动于衷。
……于是,他又无所事事了,内心里感到无限空虚,坐下来汲取别人的智慧,俗话说得好:展卷有益。
架上摆满一排排图书,他读了又读,了无头绪:有的枯燥乏味,有的谎话连篇,有的昧着良心,有的毫无意义,本本都带着受束缚的烙印,古书陈腐,新书更加陈迹。
就象抛弃那些女人一样,从此搁下书,如行丧礼,用黑色塔夫绸蒙上书架,连同上面那些尘封的书籍。
我跟他一样,远离闹市,抛开社交界的缛礼繁文,彼此情投意合,结为至交,我喜欢他的性格超群:常常于无意中陷入幻想,头脑冷静,智慧过人,连他的怪癖也不可模仿。
……我们倾吐积愫,置腹推心,谈得投机,津津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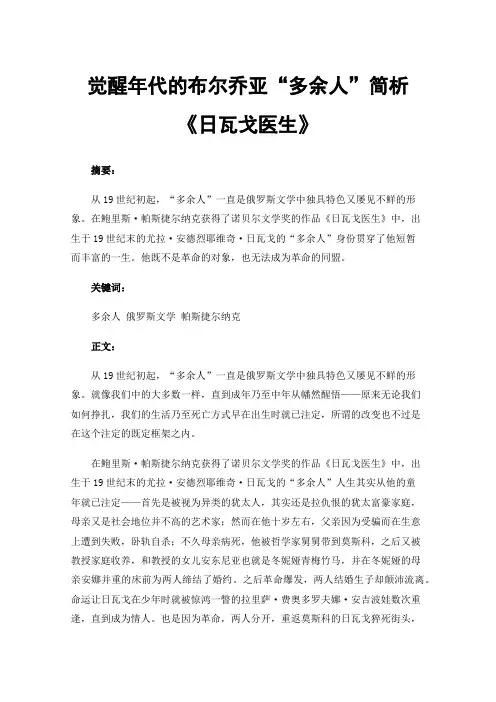
觉醒年代的布尔乔亚“多余人”简析《日瓦戈医生》摘要:从19世纪初起,“多余人”一直是俄罗斯文学中独具特色又屡见不鲜的形象。
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中,出生于19世纪末的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的“多余人”身份贯穿了他短暂而丰富的一生。
他既不是革命的对象,也无法成为革命的同盟。
关键词:多余人俄罗斯文学帕斯捷尔纳克正文:从19世纪初起,“多余人”一直是俄罗斯文学中独具特色又屡见不鲜的形象。
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直到成年乃至中年从幡然醒悟——原来无论我们如何挣扎,我们的生活乃至死亡方式早在出生时就已注定,所谓的改变也不过是在这个注定的既定框架之内。
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中,出生于19世纪末的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的“多余人”人生其实从他的童年就已注定——首先是被视为异类的犹太人,其实还是拉仇恨的犹太富豪家庭,母亲又是社会地位并不高的艺术家;然而在他十岁左右,父亲因为受骗而在生意上遭到失败,卧轨自杀;不久母亲病死,他被哲学家舅舅带到莫斯科,之后又被教授家庭收养,和教授的女儿安东尼亚也就是冬妮娅青梅竹马,并在冬妮娅的母亲安娜并重的床前为两人缔结了婚约。
之后革命爆发,两人结婚生子却颠沛流离。
命运让日瓦戈在少年时就被惊鸿一瞥的拉里萨·费奥多罗夫娜·安吉波娃数次重逢,直到成为情人。
也是因为革命,两人分开,重返莫斯科的日瓦戈猝死街头,拉里萨冒着生命危险回来为他治丧,在将他的遗稿整理出版后果不其然被抓到集中营,之后不知所踪。
和那个时代许多出生贵族或富豪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样,日瓦戈不仅是“多余人”,而且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本性善良,同情贫苦大众,然而无论怎么同情,却始终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而怜悯着大众。
说到底,他们不从群众中来,更无法到群众中去;既不是革命的对象,也无法成为革命的同盟——从始至终,他都是多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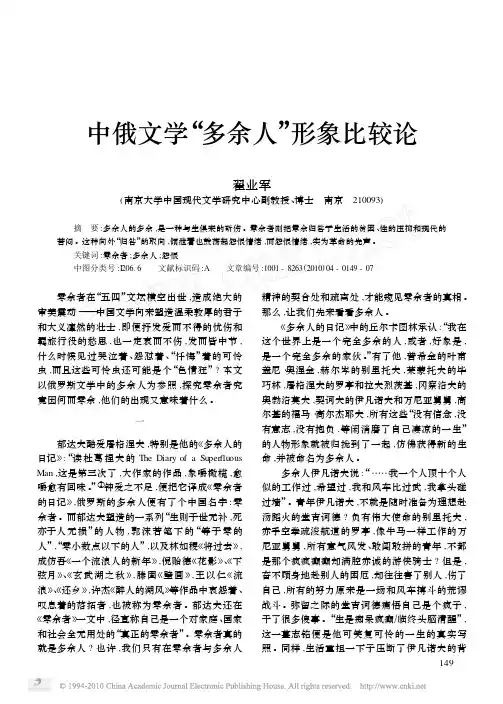
中俄文学“多余人”形象比较论翟业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0093)摘 要:多余人的多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斫伤。
零余者则把零余归咎于生活的贫困、性的压抑和现代的苦闷。
这种向外“归咎”的取向,倾泄着也鼓荡起怨恨情绪,而怨恨情绪,实为革命的先声。
关键词:零余者;多余人;怨恨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4-0149-07 零余者在“五四”文坛横空出世,造成绝大的审美震动———中国文学向来塑造温柔敦厚的君子和大义凛然的壮士,即便抒发爱而不得的忧伤和羁旅行役的愁思,也一定哀而不伤,发而皆中节,什么时候见过哭泣着、怨怼着、“忏悔”着的可怜虫,而且这些可怜虫还可能是个“色情狂”?本文以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为参照,探究零余者究竟因何而零余,他们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一郁达夫酷爱屠格涅夫,特别是他的《多余人的日记》:“读杜葛捏夫的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这是第三次了,大作家的作品,象嚼橄榄,愈嚼愈有回味。
”①钟爱之不足,便把它译成《零余者的日记》,俄罗斯的多余人便有了个中国名字:零余者。
而郁达夫塑造的一系列“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人物,郭沫若笔下的“等于零的人”,“零小数点以下的人”,以及林如稷《将过去》,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倪贻德《花影》、《下弦月》、《玄武湖之秋》,滕固《壁画》,王以仁《流浪》、《还乡》,许杰《醉人的湖风》等作品中哀怨着、叹息着的落拓者,也被称为零余者。
郁达夫还在《零余者》一文中,径直称自己是一个对家庭、国家和社会全无用处的“真正的零余者”。
零余者真的就是多余人?也许,我们只有在零余者与多余人精神的契合处和疏离处,才能窥见零余者的真相。
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多余人。
《多余人的日记》中的丘尔卡图林承认:“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完全多余的人,或者,好象是,是一个完全多余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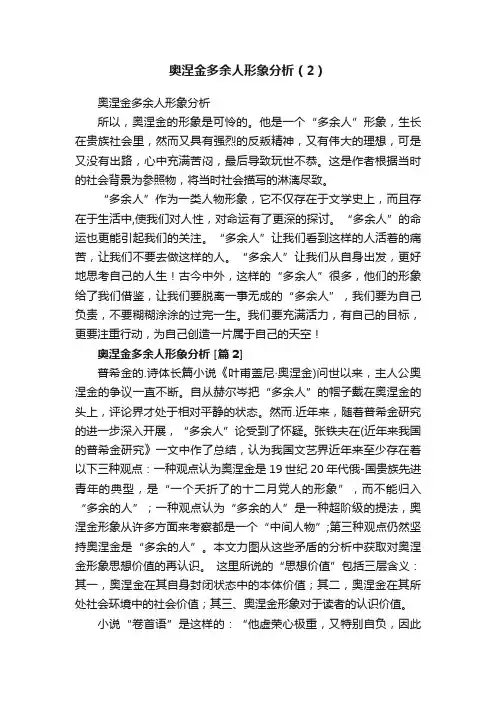
奥涅金多余人形象分析(2)奥涅金多余人形象分析所以,奥涅金的形象是可怜的。
他是一个“多余人”形象,生长在贵族社会里,然而又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又有伟大的理想,可是又没有出路,心中充满苦闷,最后导致玩世不恭。
这是作者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为参照物,将当时社会描写的淋漓尽致。
“多余人”作为一类人物形象,它不仅存在于文学史上,而且存在于生活中,使我们对人性,对命运有了更深的探讨。
“多余人”的命运也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
“多余人”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活着的痛苦,让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人。
“多余人”让我们从自身出发,更好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古今中外,这样的“多余人”很多,他们的形象给了我们借鉴,让我们要脱离一事无成的“多余人”,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不要糊糊涂涂的过完一生。
我们要充满活力,有自己的目标,更要注重行动,为自己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奥涅金多余人形象分析 [篇2]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问世以来,主人公奥涅金的争议一直不断。
自从赫尔岑把“多余人”的帽子戴在奥涅金的头上,评论界才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
然而.近年来,随着普希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多余人”论受到了怀疑。
张铁夫在(近年来我国的普希金研究》一文中作了总结,认为我国文艺界近年来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先进青年的典型,是“一个夭折了的十二月党人的形象”,而不能归入“多余的人”;一种观点认为“多余的人”是一种超阶级的提法,奥涅金形象从许多方面来考察都是一个“中间人物”;第三种观点仍然坚持奥涅金是“多余的人”。
本文力图从这些矛盾的分析中获取对奥涅金形象思想价值的再认识。
这里所说的“思想价值”包括三层含义:其一,奥涅金在其自身封闭状态中的本体价值;其二,奥涅金在其所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价值;其三、奥涅金形象对于读者的认识价值。
小说“卷首语”是这样的:“他虚荣心极重,又特别自负,因此无论在谈到自己的好的或坏的行为时都抱着同样冷漠的态度—这也许是他自以为比别人优越所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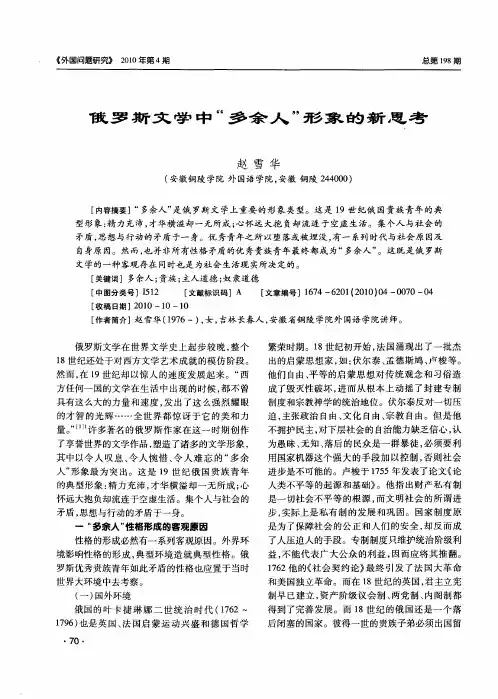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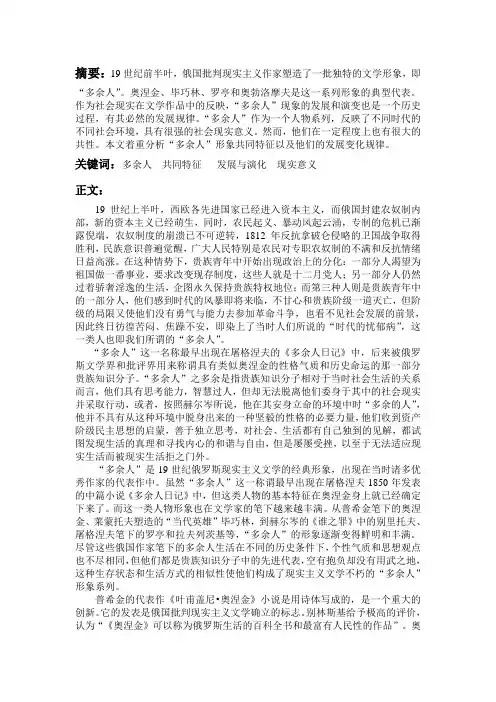
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
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正文: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
“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某些贵族知识分子,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不能有所作为。
“多余人”具有复杂的性格,有独立的人格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但往往也具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他们试图改变俄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奥涅金,别尔托夫,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并且阐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如赫而岑所说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奥涅金是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
他有过热情和梦想,可是他既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又找不到出路,因此热情消失了,梦想破灭了,只能整天无所事事,通过舞会,剧院,醇酒和美女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毕巧林是俄国文学史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
毕巧林富有教养,精力充沛而又智慧过人。
庸俗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抑郁苦闷,失去了爱情和友谊后,他在通往波斯的旅途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毕巧林的“恶习”和他的悲剧人生经历引起读者的批判谴责,叹息和同情。
别里托夫和罗亭是第二代“多余人”的代表。
《谁之罪》以三个青年的消沉苦闷告终。
贫寒的大学生克鲁采费斯基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恋爱结婚,离开将军的庄园,过着独立平庸的小康生活,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他们的家庭,和柳邦卡相爱,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而远走国外。
别里托夫对社会不满,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脱离实际,一事无成。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纵谈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杨婉莹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多余人”这一崭新的名词,无疑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新发现”,因为有了它,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孤单、平凡。
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可谓是“多余人”的鼻祖,在他的笔下,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多余人。
”当然,深入了解“多余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俄罗斯19世纪文学史和漫长悠久的具有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
关键词:多余人;主要典型;现实意义作者简介:杨婉莹(1993-),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136-01一、“多余人”的诞生在19世纪、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史从未出现过“多余人”——这一文学现象,而它的诞生也推动了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
最初“多余人”的形象源自于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著名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而这部长篇诗体小说也是作者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之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从小就生活在富庶的家庭环境里,自幼便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拥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于人民;他们对当时的现实社会都有极大的不满,但缺乏行动。
因此有这样一句话是对他们的最好概括——那便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所以,这样一群多余人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他们异于常人的才华和禀赋。
二、“多余人”形象的主要典型最早是在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普希金是“多余人”的鼻祖,但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却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在普希金之后,先后有四位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多余人”的形象。
奥涅金“多余人”人格形象分析刘雨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09501262内容提要:以叶普盖尼·奥涅金为代表,“多余人”之所以被称为“多余人”,是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自认为是“多余”的。
受特定社会环境影响,其人格中,本我和超我强烈冲突,自我渐渐迷失了,只能被动选择各种各样的逃避行为。
关键词:奥涅金多余人精神分析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多余人”。
这一形象不仅多次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如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里的别里托夫;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里的奥勃洛莫夫等,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亦有一定影响。
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笔下《后来的事》主人公长井代助、鲁迅《伤逝》的主人公涓生,甚至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多余人”的影子。
作为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诸多人物形象中总结出“多余人”的共同的特征: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诞生于现实主义文学,必然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多余人”生存状况的真实记录。
“多余人”大多是悲剧的,可是“多余人”的悲剧是如何诞生的?贵族知识分子们的“多余人”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依德提出的人格结构分析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将人格的结构概括为三个方面: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id)是在潜意识型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人最为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如饥饿、生气、性欲等;本我为与生俱来的,亦为人格结构的基础。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中文题目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方鸿渐和毕巧林形象比较分析俄语题目Лишнийчеловек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сравнениеианализПечоринаифаннонЦзянь学院外国语学院专业俄语语言文学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设计)承诺书本人重承诺:所呈交的学士学位毕业论文(设计),是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实验、设计、调研等工作基础上取得的成果。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容外,本论文(设计)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作品成果。
对本人实验或设计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注明。
本人完全意识到本承诺书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士学位论文(设计)作者签名:年月日目录绪论 (2)Введен .............................................. . (3)一、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4)(一)方鸿渐 (4)(二)毕巧林 (5)二、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相似性 (5)(一)时代背景的相似性 (5)(二)出身和所受教育的相似性 (6)(三)个人性格的相似性 (7)(四)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8)三、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差异性 (10)(一)时代背景的差异性 (10)(二)对待爱情的态度的差异性 (11)(三)对待现实的态度的差异性 (12)(四)阶级属性的差异 (13)(五)民族特性的差异 (14)(六)艺术特色的差异 (15)四、结语............................................................16.. 致 (18)参考文献 (19)绪论多余人形象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种典型形象,描述的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出身高贵,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胸怀理想,但由于阶级局限性,又不能跳出自己生活的圈子,他们看到了社会的弊病,但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的统治下又无能为力,他们虽有改革的抱负,但又缺少实践的勇气与智慧,他们只能随波逐流,在彷徨和苦闷中沦落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
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新思考赵雪华(安徽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铜陵244000)[内容摘要]“多余人”是俄罗斯文学上重要的形象类型。
这是19世纪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却一无所成;心怀远大抱负却流连于空虚生活。
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于一身。
优秀青年之所以堕落或被埋没,有一系列时代与社会原因及自身原因。
然而,也并非所有性格矛盾的优秀贵族青年最终都成为“多余人”。
这既是俄罗斯文学的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为社会生活现实所决定的。
[关键词]多余人;贵族;主人道德;奴隶道德[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0)04-0070-04[作者简介]赵雪华(1976-),女,吉林长春人,安徽省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起步较晚,整个18世纪还处于对西方文学艺术成就的模仿阶段。
然而,在19世纪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西方任何一国的文学在生活中出现的时候,都不曾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和速度,发出了这么强烈耀眼的才智的光辉……全世界都惊讶于它的美和力量。
”[1]1许多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塑造了诸多的文学形象,其中以令人叹息、令人惋惜、令人难忘的“多余人”形象最为突出。
这是19世纪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却一无所成;心怀远大抱负却流连于空虚生活。
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于一身。
一、“多余人”性格形成的客观原因性格的形成必然有一系列客观原因。
外界环境影响性格的形成,典型环境造就典型性格。
俄罗斯优秀贵族青年如此矛盾的性格也应置于当时世界大环境中去考察。
(一)国外环境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代(1762~1796)也是英国、法国启蒙运动兴盛和德国哲学繁荣时期。
18世纪初开始,法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
他们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对传统观念和习俗造成了毁灭性破坏,进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
伏尔泰反对一切压迫,主张政治自由、文化自由、宗教自由。
但是他不拥护民主,对下层社会的自治能力缺乏信心,认为愚昧、无知、落后的民众是一群暴徒,必须要利用国家机器这个强大的手段加以控制,否则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
卢梭于1755年发表了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他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文明社会的所谓进步,实际上是私有制的发展和巩固。
国家制度原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正和人们的安全,却反而成了人压迫人的手段。
专制制度只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不能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应将其推翻。
1762他的《社会契约论》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
而在18世纪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早已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两党制、内阁制都得到了完善发展。
而18世纪的俄国还是一个落后闭塞的国家。
彼得一世的贵族子弟必须出国留学的政策使一些贵族青年有机会走出闭塞的俄国,接触西欧的启蒙思想。
在国外的先进贵族青年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后,开始剖析自我,思考社会的发展。
(二)国内环境海外留学的先进贵族青年的思想明显带有反封建反专制色彩,这是令当时国内的贵族大为惊讶的,惊呼他们是“疯子”。
他们的主张和想法不可能得到周围人的支持和理解。
所有的思想也无法付诸实施,即便有些人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难免落败的结果。
他们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们所崇尚的启蒙思想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英法的启蒙思想家们往往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身上,而且又不完全否定宗教和上帝;他们的自由平等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所理解和要求的自由平等,因而他们所倡导的“华美的口号”在农奴制的俄国最终都得变成一纸空文[2]。
第二,当时的俄国封建专制制度不可能让他们有所作为。
如果有人胆敢提出异端思想便被迫害和镇压:剥夺贵族封号、囚禁、流放、甚至处决。
单个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又能有何作为。
第三,他们的思想不但不被上层社会所理解,也不被社会下层所理解。
彼得一世的教育改革使社会分裂,一边是受全方位高等教育的贵族,另一边是近乎文盲的广大农奴群众。
十二月党人为了解放受压迫的广大民众在参政院广场起义,而愚昧无知的民众还以为他们在军事演习。
真枪实弹的射击和流血牺牲也未能唤醒他们。
贵族优秀人士灿灿生辉的进步思想与当时黑暗的俄国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
理想无法化为现实,现实也不可能变成“理想国”。
二、“多余人”性格形成的主观原因性格的形成不仅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各阶层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也决定着性格的形成。
“多余人”们都是贵族中的优秀代表:高贵富有、才华横溢、博闻强识、思维敏捷、谈吐非凡、精力充沛、善良敏感。
时刻思考着如何为祖国、为民众贡献自己的力量。
希望富国强民,又无从着手;有所行动,又以失败告终。
身为统治阶级,又憎恨统治阶级的压迫行径。
深深地同情劳苦大众,又不愿低下他的高贵的头颅,与劳苦大众结成同盟。
游移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无法确定自己的社会归属,而成为“多余人”。
社会精英如何成为“多余人”?这些优秀贵族青年为何过着优裕的生活,而脑子里却盘算着要跟统治阶级对抗,乃至在参政院广场武装起义?首先我们要追溯贵族的起源。
贵族是俄国古老的社会阶层,起源于12世纪[3]41-47。
原是大公们的亲兵和侍卫,后因作战有功,得到世袭领地等封赏,养尊处优。
由于世袭制,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政府和军队中占据要职。
1722年彼得一世颁布“职官秩序表”(Табельорангах),将文武官员分为14个等级,其特点是破除门阀,不以门第取仕,而凭才能和论功选官,从而把公职人员与贵族合为一体[3]47-48。
主要思想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
所有人论功分级,不分出身。
这个制度提升了平民地位的同时也降低了贵族的社会地位。
贵族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成为为国家和沙皇服役的社会阶层。
当时社会执行的是沙皇专制制度。
沙皇令贵族锦衣玉食,贵族也可能因为触怒沙皇,被剥夺贵族封号,流放乃至处决。
贵族阶级既是统治阶级的支柱,又是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贵族社会属性的分裂造成了其心理分裂。
一方面,痛恨沙皇一人掌握生杀大权;一方面又依赖沙皇,希望在仕途能飞黄腾达,被加官晋爵。
贵族社会越是发展,这种自我毁灭性的内心矛盾就越是加剧。
矛盾激化到顶点就是进步贵族青年与沙皇政府由相安无事发展到针锋相对。
其次,“多余人”脱离了社会上层,在社会下层也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贵族有贵族自己的道德标准,使他们不能与广大民众融为一体。
贵族相信在人们之间存在长长的等级阶梯和差别。
贵族处在贵族阶层就要做贵族的事,民众处在民众的阶层就要做民众的事。
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沙皇和贵族是社会上层,广大民众属于社会下层。
社会上层是知识和财富的所有者,理应统治愚昧无知、一无所有的社会下层。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W 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阐释“什么是贵族”时,把道德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4]187。
高傲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特征,是主人道德规范。
而奴隶道德规范指顺从、俯首帖耳、不由自主、身不由己。
与高傲相对的是卑贱。
目光游移、沿街乞讨、逢迎攀附都是卑贱之举,贵族自觉与之划清界限[4]188。
贵族对这些软弱,附和他人之徒嗤之以鼻,他们崇尚力量,即权威。
有权威才会有尊严。
严格遵守主人道德的贵族被视为典范、榜样、优秀者。
他们的眼睛不会向上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在社会上层。
当他们向下看时,分两种情况:一是教训下层民众,二是同情下层民众,这种同情也不过是他们旺盛的精力宣泄的一种方式。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中的贵族聂赫留朵夫放弃贵族荣誉与财产,追随玛丝洛娃来到流放地。
他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拯救玛丝洛娃;另一个是拯救他自己。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都是把自己同玛丝洛娃区别并对立起来。
封号、金钱、地位无非是外在的东西,改变不了人的本质,贵族终究是贵族,一无所有也是贵族。
旺盛的精力应该有个方向,他把目标锁定在玛丝洛娃身上。
这是一种同情之举,而不是融合。
第三,不仅仅是贵族,人类本身也具有一些人类特质,这也决定了性格的形成。
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认为:两个互不相干却又密切相连的事物——思想和行动——统一于人的生命冲动,它们都是人的生命冲动的一种表达。
人的生命冲动就是人的实质,即自我维护和自我保护[5]32。
人的所有原始的本能都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当人类发展到理性阶段,人经过理性思考所追求的其实和人的原始本能盲目追求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追求自我维护和自我保护。
所以,经过理性思考后的自我牺牲也是不可能的。
人自然地会尽量维护和加强任何提高生命力的东西,破坏和减弱任何降低生命力的东西。
与之相应地就是赠所爱之人以欢乐,赠所恨之人以痛苦[5]34。
所以,利他主义行为实质上来自于利己主义动机。
虽然这种观点令人悲伤,却是人的本质。
聂赫留朵夫四方奔走,尽可能在衣食住多方面给狱中的玛丝洛娃各种关照。
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是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而是出于为自己赎罪的动机。
他深感社会下层被欺凌被压迫,自己在玛丝洛娃面前是有罪的。
赎罪之后呢?他就又可以是心安理得的贵族了。
他依然是贵族,她依然是底层一员,什么也没改变。
所以人类的这种源于利己主义的利他主义思想也很难使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融为一体。
三、对“多余人”的重新分类“多余人”的形成固然有其多方面原因,是19世纪一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形象。
但我们纵观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人”画廊,会发现也并不是所有内心矛盾、性格分裂的优秀贵族青年最终都成了“多余人”。
贵族青年奥涅金(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1823-1831)从小跟从法国家庭教师学习,受的是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典型的贵族教育。
既无“艰苦劳作”的习惯,又不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也不想通过进入军界光宗耀祖[1]124。
世袭制让他从出生便拥有了一切。
彼得堡的舞会、沙龙、剧院不足以吸纳他那旺盛的精力。
决斗,追求有夫之妇……这些都是他的所作所为。
他还到乡下做些“减少地租”等所谓的善事。
他读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这是一本关于政权和人民的关系的书,想过社会政治问题,也想过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也思考过自己的未来生活。
他“冷漠而懒散”的心灵在觉醒之后发生的新变化并未导致他性格的根本改变。
他对上流社会憎恨也好,厌恶也好,但并没有脱离和抛弃。
他从彼得堡来到乡下,也从没想过要过社会底层的生活。
他归顺了空虚无聊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也接纳了他。
最后在小说结尾处奥涅金还是在彼得堡将军家的舞会现身了。
因此,奥涅金还不足以是“多余人”,顶多是“多余人”的前身。
1840年,莱蒙托夫发表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