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加注版)
- 格式:doc
- 大小:85.00 KB
- 文档页数: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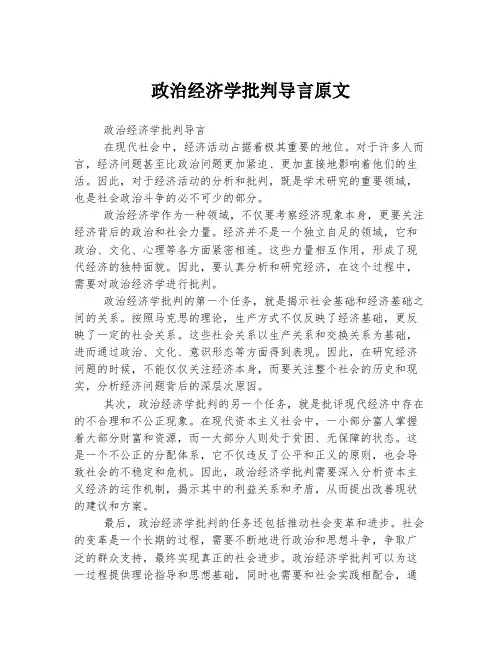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原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于许多人而言,经济问题甚至比政治问题更加紧迫、更加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对于经济活动的分析和批判,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领域,不仅要考察经济现象本身,更要关注经济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它和政治、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紧密相连。
这些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了现代经济的独特面貌。
因此,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揭示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方式不仅反映了经济基础,更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以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基础,进而通过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得到表现。
因此,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经济本身,而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分析经济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批评现代经济中存在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现象。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小部分富人掌握着大部分财富和资源,而一大部分人则处于贫困、无保障的状态。
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分配体系,它不仅违反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危机。
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机制,揭示其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从而提出改善现状的建议和方案。
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还包括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社会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进行政治和思想斗争,争取广泛的群众支持,最终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
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基础,同时也需要和社会实践相配合,通过各种途径提高群众的认识和觉悟,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平等、更加和谐的社会。
总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现代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的过程,它关注经济本身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分析经济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批评现有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现象,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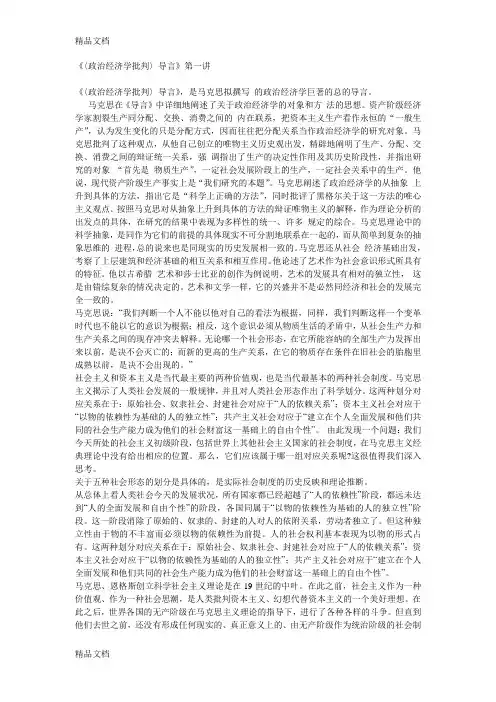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一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总的导言。
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永恒的“一般生产”,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因而往往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从他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精辟地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指出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并指出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产。
他说,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马克思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同时批评了黑格尔关于这一方法的唯心主义观点。
按照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的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
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抽象,是同作为它们的前提的具体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从简单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总的说来也是同现实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
马克思还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考察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他论述了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所具有的特征。
他以古希腊艺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例说明,艺术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
艺术和文学一样,它的兴盛并不是必然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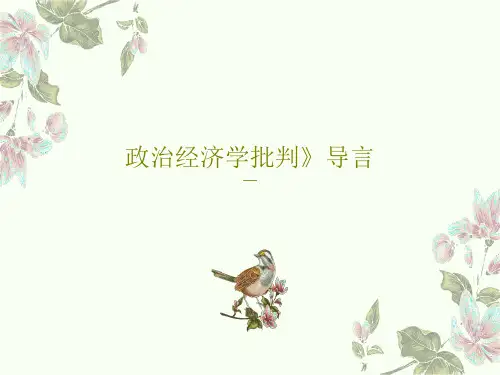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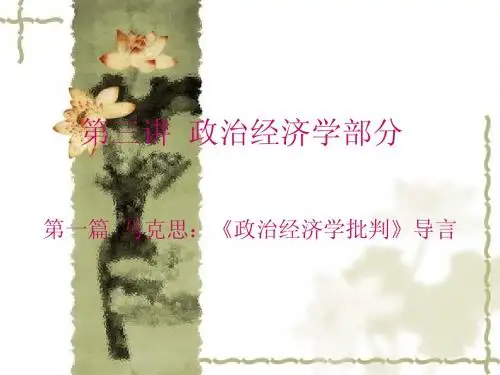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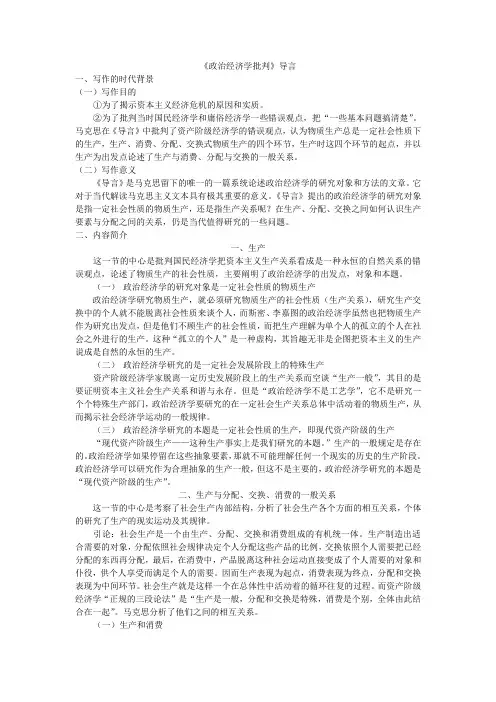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写作的时代背景(一)写作目的①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实质。
②为了批判当时国民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一些错误观点,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马克思在《导言》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观点,认为物质生产总是一定社会性质下的生产,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式物质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时这四个环节的起点,并以生产为出发点论述了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的一般关系。
(二)写作意义《导言》是马克思留下的唯一的一篇系统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文章。
它对于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导言》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指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还是指生产关系呢?在生产、分配、交换之间如何认识生产要素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仍是当代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
二、内容简介一、生产这一节的中心是批判国民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的错误观点,论述了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主要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对象和本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政治经济学研究物质生产,就必须研究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生产关系),研究生产交换中的个人就不能脱离社会性质来谈个人,而斯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出发点,但是他们不顾生产的社会性质,而把生产理解为单个人的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的生产。
这种“孤立的个人”是一种虚构,其旨趣无非是企图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说成是自然的永恒的生产。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生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脱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而空谈“生产一般”,其目的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谐与永存。
但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它不是研究一个个特殊生产部门,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总体中活动着的物质生产,从而揭示社会经济学运动的一般规律。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题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即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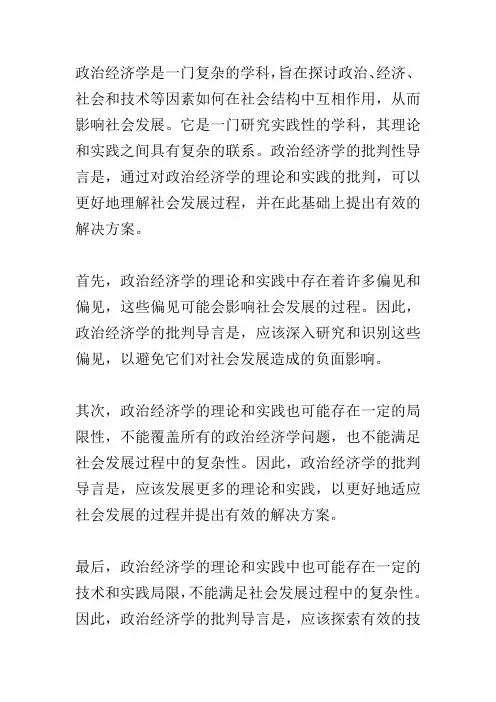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旨在探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因素如何在社会结构中互相作用,从而影响社会发展。
它是一门研究实践性的学科,其理论和实践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导言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首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偏见和偏见,这些偏见可能会影响社会发展的过程。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导言是,应该深入研究和识别这些偏见,以避免它们对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覆盖所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也不能满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导言是,应该发展更多的理论和实践,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最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技术和实践局限,不能满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导言是,应该探索有效的技
术和实践,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总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导言是,应该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入研究和识别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偏见、局限性和技术局限,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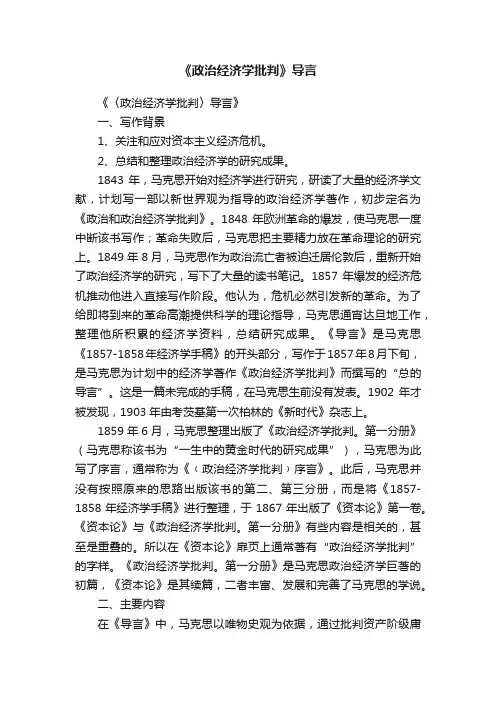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写作背景1、关注和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2、总结和整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1843年,马克思开始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计划写一部以新世界观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初步定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一度中断该书写作;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理论的研究上。
1849年8月,马克思作为政治流亡者被迫迁居伦敦后,重新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185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推动他进入直接写作阶段。
他认为,危机必然引发新的革命。
为了给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通宵达旦地工作,整理他所积累的经济学资料,总结研究成果。
《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写作于1857年8月下旬,是马克思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撰写的“总的导言”。
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
1902年才被发现,1903年由考茨基第一次柏林的《新时代》杂志上。
1859年6月,马克思整理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马克思称该书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为此写了序言,通常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此后,马克思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思路出版该书的第二、第三分册,而是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整理,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有些内容是相关的,甚至是重叠的。
所以在《资本论》扉页上通常著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字样。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初篇,《资本论》是其续篇,二者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的学说。
二、主要内容在《导言》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依据,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各种谬论和错误观点,精辟地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以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伟大变革。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1857年8月)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1生产(a)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鲁宾逊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
这倒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
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他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
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做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愈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愈不独立,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
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来看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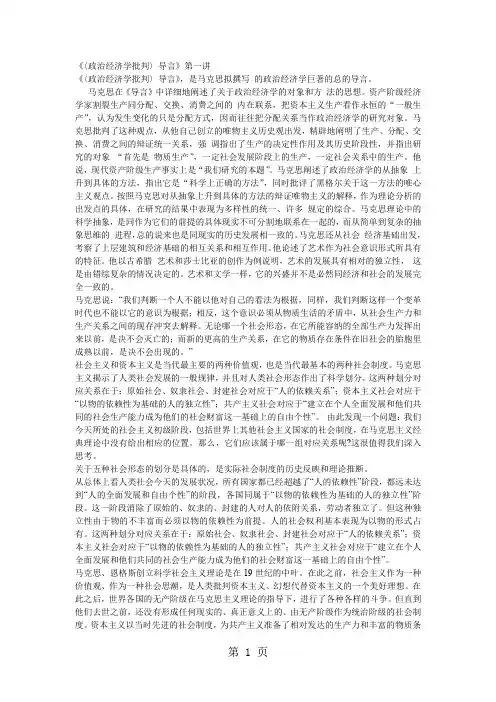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一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总的导言。
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永恒的“一般生产”,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因而往往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从他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精辟地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指出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并指出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产。
他说,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马克思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同时批评了黑格尔关于这一方法的唯心主义观点。
按照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的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
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抽象,是同作为它们的前提的具体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从简单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总的说来也是同现实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
马克思还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考察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他论述了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所具有的特征。
他以古希腊艺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例说明,艺术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
艺术和文学一样,它的兴盛并不是必然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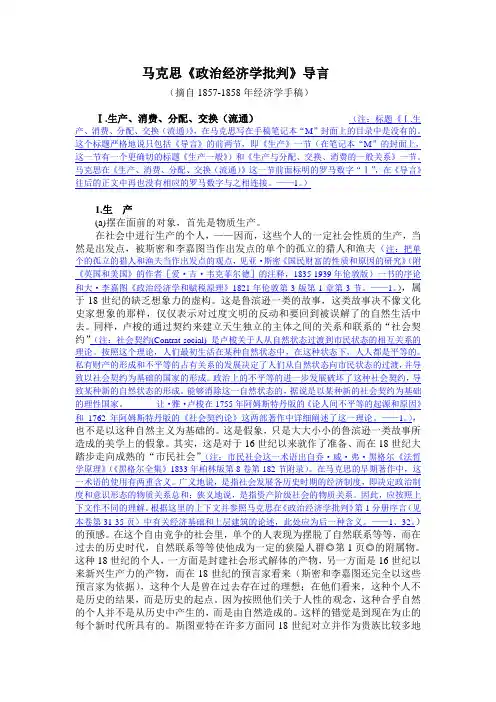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注:标题《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手稿笔记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
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笔记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确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
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Ⅰ”,在《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与之相连接。
——1。
)1.生产(a)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注: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注释,1835-19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
——1。
),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注: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 是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
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
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
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让·雅·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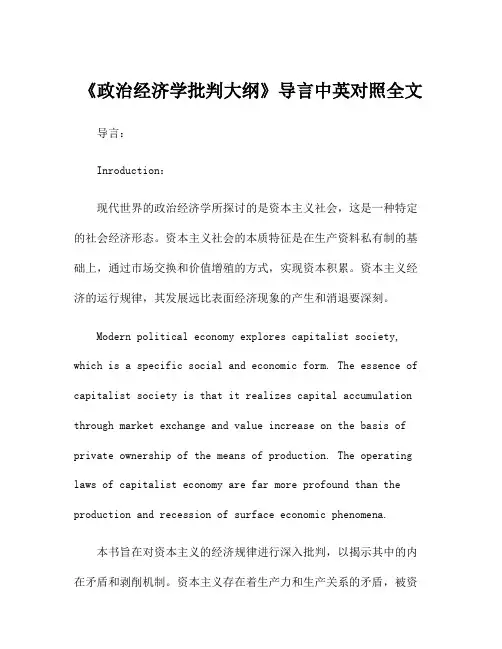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英对照全文导言:Inroduction: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交换和价值增殖的方式,实现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其发展远比表面经济现象的产生和消退要深刻。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explores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is a specific social and economic form.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that it realizes capital accumulation through market exchange and value increase on the basis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operating laws of capitalist economy are far more profound than the production and recession of surface economic phenomena.本书旨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进行深入批判,以揭示其中的内在矛盾和剥削机制。
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劳动者既是资本的创造者,又是被剥削压迫的阶级。
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必然导致着阶级斗争的激化。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o critically analyze the economic laws of capitalism in order to reveal it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nd exploitation mechanisms. Capitalism ha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workers surrounded by capitalism are both the creators of capital and the exploited and oppressed clas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of capitalism inevitably lead to intensified class struggle.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将政治经济学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加以研究。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写作背景1、关注和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2、总结和整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1843年,马克思开始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计划写一部以新世界观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初步定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一度中断该书写作;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理论的研究上。
1849年8月,马克思作为政治流亡者被迫迁居伦敦后,重新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185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推动他进入直接写作阶段。
他认为,危机必然引发新的革命。
为了给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通宵达旦地工作,整理他所积累的经济学资料,总结研究成果。
《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写作于1857年8月下旬,是马克思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撰写的“总的导言”。
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
1902年才被发现,1903年由考茨基第一次柏林的《新时代》杂志上。
1859年6月,马克思整理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马克思称该书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为此写了序言,通常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此后,马克思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思路出版该书的第二、第三分册,而是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行整理,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有些内容是相关的,甚至是重叠的。
所以在《资本论》扉页上通常著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字样。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初篇,《资本论》是其续篇,二者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的学说。
二、主要内容在《导言》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依据,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各种谬论和错误观点,精辟地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以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注:标题《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手稿笔记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
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笔记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确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
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Ⅰ”,在《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与之相连接。
——1。
)1.生产(a)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注: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注释,1835-19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
——1。
),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注: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 是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
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
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
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让·雅·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
——1。
),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
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
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出自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节附录)。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两重含义。
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
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
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并参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见本卷第31-35页)中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此处应为后一种含义。
——1、32。
)的预感。
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第1页◎的附属物。
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
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
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注:氏族的原文是“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现在通用的“氏族”(Gens)和“部落”(Stamm)两个概念。
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
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作为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的意义。
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于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
恩格斯在184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本选集第4卷第1-189页)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
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第(50a)注。
——2。
)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注:政治动物(Ζουπολιτιχóυ),从更广泛意义来说是“社会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1篇开头给人下的定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第(13)注中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
——2。
),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方面无须多说。
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
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第2页◎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注:关于蒲鲁东所说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参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137页)作的评论。
——3。
)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
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
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
[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
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
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
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
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
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
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第3页◎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
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
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
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
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
生产一般。
特殊生产部门。
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注: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1篇《生产》第1章,就加上了《生产的要素》这一标题。
——4。
)),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
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
可是,我们将会知道,这些要素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
(注: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篇第8章和第11章结束语。
——4。
)要把这些在亚·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
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
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
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
这又是同义反◎第4页◎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