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
- 格式:docx
- 大小:27.30 KB
- 文档页数:3

2012年第7期山东社会科学No.7总第203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20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学术主持人:孙伟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孙伟平周广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具体路径,成为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层面上都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化”的可能性;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完全可能的。
这既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合法性;可能性;必要性[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7-0005-06“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既是一个政治理念,又是一个哲学命题;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学术运动。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具体路径,成为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可能”“中国化”?“如何可能”“中国化”?“中国化”“何以必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些问题一直都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这里我们不妨结合相关学者的意见作些讨论,以消解和祛除“中国化”的合法性危机,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cy)一词通常是在法学或法哲学领域中使用的,意指某一存在物或某一活动是否为法律所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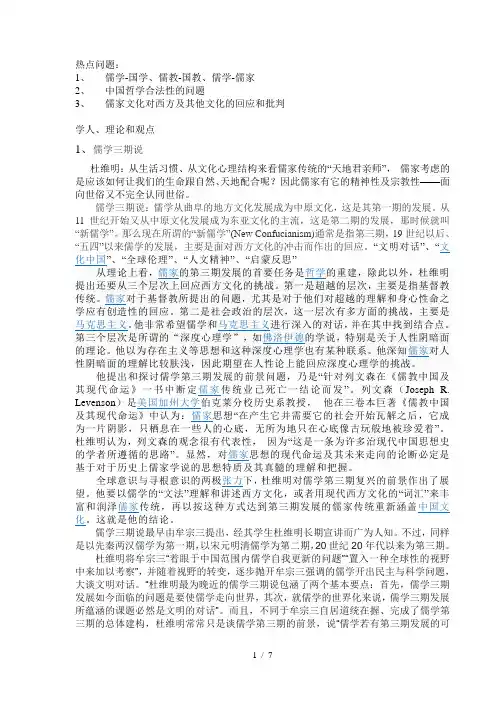
热点问题:1、儒学-国学、儒教-国教、儒学-儒家2、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3、儒家文化对西方及其他文化的回应和批判学人、理论和观点1、儒学三期说杜维明:从生活习惯、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看儒家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儒家考虑的是应该如何让我们的生命跟自然、天地配合呢?因此儒家有它的精神性及宗教性——面向世俗又不完全认同世俗。
儒学三期说:儒学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发展成为中原文化,这是其第一期的发展。
从11世纪开始又从中原文化发展成为东亚文化的主流,这是第二期的发展,那时候就叫“新儒学”。
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通常是指第三期,19世纪以后、“五四”以来儒学的发展,主要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作出的回应。
“文明对话”、“文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家传统业已死亡一结论而发”。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他在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
杜维明认为,列文森的观念很有代表性,因为“这是一条为许多治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遵循的思路”。
显然,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走向的论断必定是基于对于历史上儒家学说的思想特质及其真髓的理解和把握。
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两极张力下,杜维明对儒学第三期复兴的前景作出了展望。
他要以儒学的“文法”理解和讲述西方文化,或者用现代西方文化的“词汇”来丰富和润泽儒家传统,再以按这种方式达到第三期发展的儒家传统重新涵盖中国文化。
这就是他的结论。
儒学三期说最早由牟宗三提出,经其学生杜维明长期宣讲而广为人知。
不过,同样是以先秦两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20世纪20年代以来为第三期。
杜维明将牟宗三“着眼于中国范围内儒学自我更新的问题”“置入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中来加以考察”,并随着视野的转变,逐步抛开牟宗三强调的儒学开出民主与科学问题,大谈文明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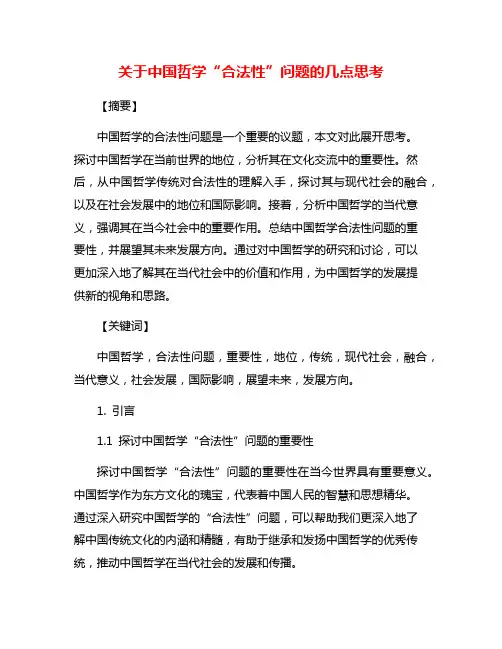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摘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本文对此展开思考。
探讨中国哲学在当前世界的地位,分析其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然后,从中国哲学传统对合法性的理解入手,探讨其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
接着,分析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强调其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总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讨论,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重要性,地位,传统,现代社会,融合,当代意义,社会发展,国际影响,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1. 引言1.1 探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探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作为东方文化的瑰宝,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思想精华。
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有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推动中国哲学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传播。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审视中国哲学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探寻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所蕴含的“合法性”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和价值体系,更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智慧。
通过研究和探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有助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多元发展和共同繁荣。
1.2 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其强调的和谐、平衡、中庸的思想,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哲学的理念和智慧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由于其深刻的内涵和普世价值,中国哲学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方法选择转向问题意识(一)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在学科创建之初就被尖锐地提出来的问题,近年来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
概括起来,讨论的关键有二点:其一,能否以“哲学”来命名中国古代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反思的那部分内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的那部分知识体系。
正如金岳霖先生提出所指出的,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实在是独具只眼。
其二,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着哲学,那么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梳理中国哲学是否“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从而使中国哲学失去了丰富的色彩。
本文试图以这两个问题为基点,说明这种合法性的危机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以及应对这种危机的可能的出路。
一、西方文化强势下的“地方性知识”的难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教育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其最基本的功能和目标指向并不是知识传播而是一种道德的教化,在科举作为制度化儒家的核心设置之后,书院和私塾几乎就成为科举的预备机构。
而中国的知识分类系统也是自成体系。
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独特的知识分类和教育体制被认为是阻碍人才出现的根本性原因,在遭受了甲午战争特别是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为标志的“庚子事变”的屈辱之后,开始了以全面学习西方为特征的“新政”。
在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最先,或者被当时认为是最迫切的改革措施便是废除科举,设学堂,培养新式人才,以期能“保国、保种、保教”,这样便开始了向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全面模仿。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就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八科,虽然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经学科依然存在,但这最多可以被看作是“中体西用”的一种体现。
因为这样一来经学已经被看作是众多学科之一,就被“去魅”,失去了神秘色彩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即便如此,针对当时新政改革中出台的由张之洞审定的《奏定学校章程》中规定“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而代之以经学科的折衷性方案,遭到了王国维等人的尖锐批评,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提出的反对理由就是与西方的大学体制不合。

作者: 任文启[1,2]
作者机构: [1]甘肃政法学院,兰州730070;[2]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出版物刊名: 经济研究导刊
页码: 234-235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4期
主题词: 金岳霖问题;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话语系统
摘要:金岳霖问题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探讨的一个起点,然而金岳霖问题其实是一个悖论,是基于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关系就会出现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这一悖论是西学东渐以来,西方话语相对于中国话语的强势所造成的,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一悖论的可能出路是:建构中国哲学独立自洽的话语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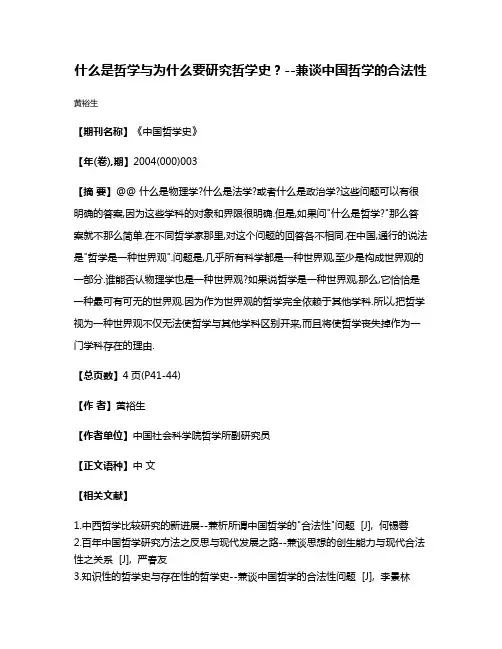
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黄裕生
【期刊名称】《中国哲学史》
【年(卷),期】2004(000)003
【摘要】@@ 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法学?或者什么是政治学?这些问题可以有很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些学科的对象和界限很明确.但是,如果问"什么是哲学?"那么答案就不那么简单.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是,几乎所有科学都是一种世界观,至少是构成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能否认物理学也是一种世界观?如果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那么,它恰恰是一种最可有可无的世界观.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完全依赖于其他学科.所以,把哲学视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无法使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而且将使哲学丧失掉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
【总页数】4页(P41-44)
【作者】黄裕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兼析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J], 何锡蓉
2.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J], 严春友
3.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J], 李景林
4.“兼总百家,必归于儒”——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J], 覃江华
5.从突破“两军对阵”到关注“合法性”——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之趋向 [J], 陈卫平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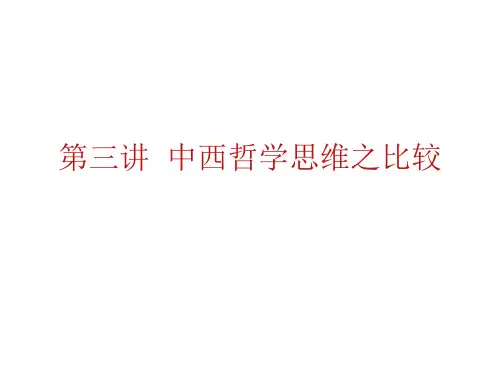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摘要】中国哲学学科存在合法性危机,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和支持。
传统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受到西方哲学的批评。
中国哲学在学科地位和认可度上面临挑战,教育现状也需要改善。
未来,中国哲学学科需要进行前景分析,提升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为了探索中国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应当积极支持和关注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以维护其合法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传统、影响、西方哲学、批评、学科地位、认可度、教育、前景分析、关注、支持、学术地位、影响力、当代社会、意义、作用。
1. 引言1.1 中国哲学学科的悠久历史中国哲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可追溯至古代华夏文明的初期,中国哲学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传承至今。
最早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易经》、《老子》、《庄子》等经典著作,这些作品深刻探讨了人生、世界和道德等诸多问题,对中国哲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学科体系,涵盖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多种学派和流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
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
中国哲学的悠久历史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思辨能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对中国哲学学科的悠久历史的研究和传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特点,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哲学学科的悠久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1.2 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现状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现状可以说是在不断变化中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哲学在国际上也逐渐受到关注。
在国内,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境。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应用型学科的需求逐渐增加,中国哲学这一传统学科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不如西方哲学那么重要,导致其在学术界和教育领域的地位相对较低。
中国哲学论⽂题⽬ 写毕业论⽂就少不了要确定题⽬,那哲学的论⽂题⽬有多少呢?下⾯是店铺带来的关于中国哲学论⽂题⽬的内容,欢迎阅读! 中国哲学论⽂题⽬: 1.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2.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研究 3.中国哲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可选⼀对范畴来分析) 4.儒道墨法价值观之⽐较 5.《坛经》的⼼性论 6.王阳明贺麟知⾏学说⽐较研究 7.中国的“语⾔”哲学 ——(1)以《论语》为例(2)以《道德经》为例(3)以“⾔意之辨”为例 8.《孟⼦》理想⼈格的哲学分析 9.朱熹的分殊思想研究 10.儒家思想(或道家、墨家)的现代价值: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视⾓ 11.中国传统哲学的特⾊ 12.中国传统⼈⽂精神 13.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14.儒家的和合思想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15.儒学与全球伦理 1.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2.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研究 3.中国哲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可选⼀对范畴来分析) 4.儒道墨法价值观之⽐较 5.《坛经》的⼼性论 6.王阳明贺麟知⾏学说⽐较研究 7.中国的“语⾔”哲学 ——(1)以《论语》为例(2)以《道德经》为例(3)以“⾔意之辨”为例 8.《孟⼦》理想⼈格的哲学分析 9.朱熹的分殊思想研究 10.儒家思想(或道家、墨家)的现代价值: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视⾓ 11.中国传统哲学的特⾊ 12.中国传统⼈⽂精神 13.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14.儒家的和合思想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15.儒学与全球伦理 16.⽼⼦的辩证法思想研究 17.庄⼦的⾃由观 18.孟⼦、荀⼦⼈性论思想⽐较研究 19.先秦⾄两汉的真理观 20.魏晋⾔意之辨的哲学价值 21.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研究 22.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从本体到⼯夫:王阳明的知⾏合⼀思想研究) 23.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再评价 24.章太炎(炳麟)的“俱分进化论” 25.孙中⼭“知难⾏易”说的现代价值 26.冯友兰的⼈⽣境界说 27.《国语》中的“和”思想研究 28.《论语》“仁”的多元阐释 29.“蝴蝶梦”与庄⼦哲学的意境 30.《庄⼦》中⼈物形象的哲学隐喻 31.孟⼦与告⼦⼈性善恶论争的伦理意蕴 32.《论语》的“⾔”“语”伦理思想研究 33.⽼庄的本体思想⽐较研究 34.《盛世危⾔》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建构 35.《墨⼦》的伦理思想研究 36.中国“孝”⽂化传统的现代转换 37.中国⽂化传统中的“⼈” 38.中国传统“天⼈合⼀”说与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39.郭店楚简的思想价值(也可选取其中的⼀篇进⾏研究) 40.论《易传》的辩证法思想 41.论禅宗的“顿悟成佛”论 42.论牟宗三“智的直觉”的观念 43.中国传统哲学与21世纪中国哲学 44.和谐:《洪范》的政治哲学 45.《国语》的和同哲学 46.价值论视野下孟⼦和告⼦⼈性论的分歧 47.苏格拉底和孔⼦的朋友哲学 48.“欲”与“仁”:《论语》关于“欲”的哲思 49.韩⾮⼦《五蠹》的哲学价值 50.⾃然境界论——以冯友兰为核⼼ 51.道德境界论——以冯友兰为核⼼ 52.功利境界论——以冯友兰为核⼼ 53.宗教境界论——以冯友兰为核⼼ 54.冯友兰和唐君毅⼈⽣境界论⽐较 55.梁漱溟的科学观 56.梁漱溟的⾃由观 57.梁漱溟的国家观 58.什么是科学——胡适的科学观。
[收稿日期] 2003203202[作者简介] 张立文(1935—),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摘 要] 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肯定不能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直面中国哲学“话题本身”;自我定义,自立标准;采取“六经注我”、“以中解中”的和合诠释方法,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摆脱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的惟一选择是中国哲学的自我创新,对先前和当前的“问题”、“话题”做出新的义理性的化解。
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哲学自由,没有哲学自由,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创新,和合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现代理论形态。
[关键词] 中国哲学;话题本身;讲自己;创新[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420(2003)022******* 晚清以来,中国在西学及武力的入侵下,无论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还是在文化、道德、观念层面,沉沦于整体的危机之中,这些危机有的一直延续下来,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们不得不回应一些不清不楚和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前者的问题本文不做探讨,后者的问题本文仅涉及学术、思想、观念层面。
一、危机与合法性问题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向西方追求真理,在人们的心目中,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和中国。
这种判断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一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但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
日本学者西周最早将西方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这与中国古代使用的“哲”字有关系。
据学者考证,西周在1875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用“哲学”翻译philosophy,而“在津田进藤于1861年出版的《新理论》的附录中,西周翻译‘哲学’一词用的字是‘希贤学’或‘希哲学’,意思是追求贤人之学,或追求哲人之学”。
由此看来,“哲学”译名的成立,先已经过类似佛教东传时那样的“连类”或“格义”的工夫,其中浸润了东方学人对于“哲学”的特殊理解。
philosophy 在西方为“爱智之学”,中国的“哲”字即是“智”或“大智”之义(《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希贤”出自周敦颐《通书》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将西方的“爱智”翻译为中文的“希哲”,从词组结构上说,比一个“哲”字更为合适。
关键是中国古代没有“爱智”或“希哲”后面的那个“学”(学科),而且中国古人对“智”或“哲”的追求亦与西方人有差异。
这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人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所遇到的困难。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学科,也就没有哲学的“形式上的系统”,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绪论”中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此所谓“找出”,也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这里首先是要立“中国哲学”之名,但金岳麟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这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2014.09.05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李存山一、早期的“国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国学”与“中国哲学”都是中西文化交汇而产生的概念,它们差不多同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文著述中。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首先关涉中国传统学术中是否有“哲学”,而其更深层的意涵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梁启超在1902年有倡办《国学报》的设想,同年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前六章,其中已使用了“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先秦之哲学”等表述[1]。
在1904年续作的此书第八章“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
吾不此之惧也。
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
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传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2]梁启超所说的“外学”主要是指严复等人译介的西学,而“国学”即指中国传统的学术。
中国古代有“国学”之名,是指由国家在京师设立的学校。
此处“国学”是相对于地方的“乡学”而言。
在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乃有“中学”与“西学”之名。
“国学”即相对于“西学”而言,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有“经、史、子、集”和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划分。
其中“义理之学”与“哲学”的涵义相近,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我们现在所用的“哲学”一词是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
西周最初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3]。
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
”[4]由此可见,“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philosophy”的原义是“爱智之学”,西周把“philosophy”译为“希哲学”或“哲学”,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有密切的关系。
“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
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据此,孔子的学说可以称为“哲人之学”。
严复在1898年作的《保教余义》中说“大《易》则有费拉索非之学”[5]。
他当时没有用“哲学”之名,而王国维在1903年作的《哲学辨惑》中说:“夫哲学者,尤中国所谓理学云尔。
……‘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
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
”[6] 他明确提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先秦与宋代是“中国哲学最盛之时”,如周敦颐的“太极”之说、张载的“正蒙”之论等等“皆深入哲学之问题”。
1906年,章太炎发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其中也提到“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7]。
章太炎在1922年作了关于国学的十场演讲,其中第六、七场是讲“哲学的派别”,他说:“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在《汉书·艺文志》所列的“九流”中,“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二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8]。
除先秦诸子外,章太炎对两汉至清代的哲学也有所论述。
从早期国学研究的脉络看,虽然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哲学”之名,或者说没有“哲学”这样一个近现代意义的“学科”,但一般都不否认国学中含有哲学的思想。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出自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或特殊性,也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或如何认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有讨论。
他说:“中国之哲学,多属于人事上,国家上,而于天地万物原理之学,穷究之者盖少焉。
”[9]后来梁启超在1927年作的《儒家哲学》讲演中又说:“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
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
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
”而中国哲学主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
……直译的philosophy,其函义实不适于中国。
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
”从另一个意义上,梁启超又说:“自儒家言之,必(仁智勇)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
这样看来,西方所谓爱智,不过儒家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
所以儒家哲学的范围,比西方哲学的范围,阔大得多。
”[10]梁启超实际上指出了中西哲学各有所长。
王国维在1904、1905年作的《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和《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提到:“盖吾中国之哲学,皆有实际的性质……皆以实用为宗旨。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斯可异已!”“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伦理哲学耳。
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
”[11]王国维所说的“纯粹之哲学”,就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那种“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2]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
这种思想传统的引进,对于在中国文化中确立知识或学术的相对独立价值,推动中国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但是,如果以这种“纯粹之哲学”为哲学的惟一标准,那么中国哲学就会发生“合法性”的危机。
如王国维在1906年作的《文学小言》中所说:“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
”[13]不过,中国哲学是求真与善的统一,并非“不顾真理之如何”。
因此,王国维又为中国哲学辩护,说《易传·系辞》等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又说“形而上学”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所必需:“《易》不言太极,则无以明其生生之旨;《周子》不言无极,则无以固其主静之说;伊川、晦庵若不言理与气,则其存养省察之说为无根柢。
故欲离其形而上学而研究其道德哲学,全不可能之事也。
”[14]王国维最终不否认国学中有哲学思想。
二、“中国哲学史”之名称的“困难”及其解决“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近现代意义的“学科”,是在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哲学门”而建立的。
当时,哲学门之下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类,起初因为没有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所以1914年正式招生时有所谓“中国哲学门”之称。
此后便有陈黻宸、马叙伦等讲授“中国哲学史”,又有谢无量在1916年出版《中国哲学史》。
而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最具有意义的是,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并在1934年出齐此书的上下两册。
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说,此书的“特长”主要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
而“扼要的手段”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
所谓“系统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15]。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的“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这里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参照)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他又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16]。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之初,胡适和冯友兰都是为了强调“中国哲学史”之名的现代意义,而侧重于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即普遍性。
于是,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就不免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金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的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可以理解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the philosophical history in China),就是“发现于中国”的“普遍哲学”的史。
金先生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17]。
金先生又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18]。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金先生的“审查报告”对于张岱年先生在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有重要影响。
金先生对冯著提出的问题,正是张著在“序论”中首先要解决的。
于是,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先讲“哲学的定义”,也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的先讲“哲学之内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首先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也就是首先要解决“哲学”的普遍性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
张先生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19]。
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
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
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
《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
张先生肯定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的观点。
《中国哲学大纲》所注重的方法之一就是“察其条理系统”,张先生指出:“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
”[20]在这里,对中国哲学“系统”的考察已经不是片面地讲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而是强调“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