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汉文学批评
- 格式:ppt
- 大小:67.00 KB
- 文档页数: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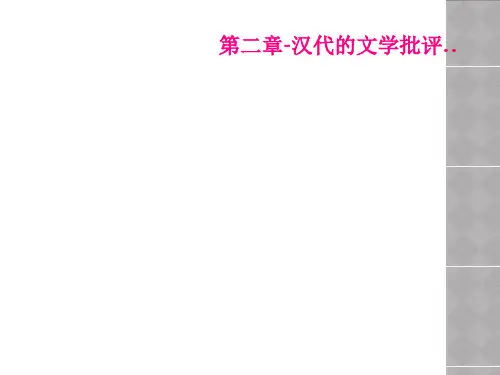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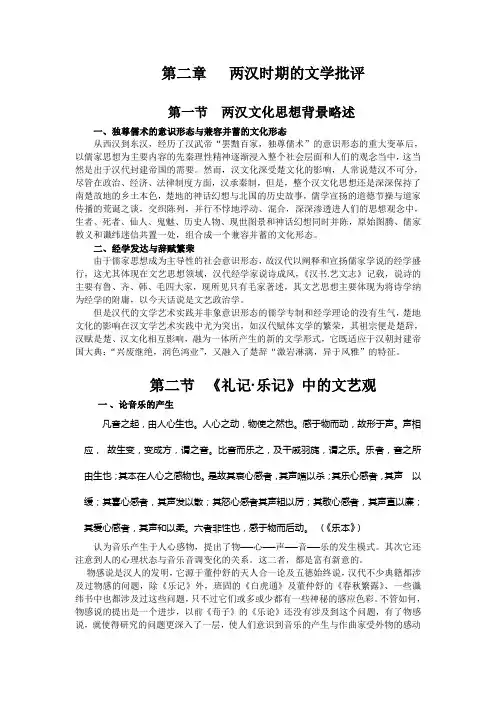
第二章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一节两汉文化思想背景略述一、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与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逐渐浸入整个社会层面和人们的观念当中,这当然是出于汉代封建帝国的需要。
然而,汉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人常说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是,整个汉文化思想还是深深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诞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谶纬迷信共置一处,组合成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
二、经学发达与辞赋繁荣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故汉代以阐释和宣扬儒家学说的经学盛行,这尤其体现在文艺思想领域,汉代经学家说诗成风,《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诗的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大家,现所见只有毛家著述,其文艺思想主要体现为将诗学纳为经学的附庸,以今天话说是文艺政治学。
但是汉代的文学艺术实践并非象意识形态的儒学专制和经学理论的没有生气,楚地文化的影响在汉文学艺术实践中尤为突出,如汉代赋体文学的繁荣,其祖宗便是楚辞,汉赋是楚、汉文化相互影响,融为一体所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它既适应于汉朝封建帝国大典:“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又融入了楚辞“激岩淋漓,异于风雅”的特征。
第二节《礼记·乐记》中的文艺观一、论音乐的产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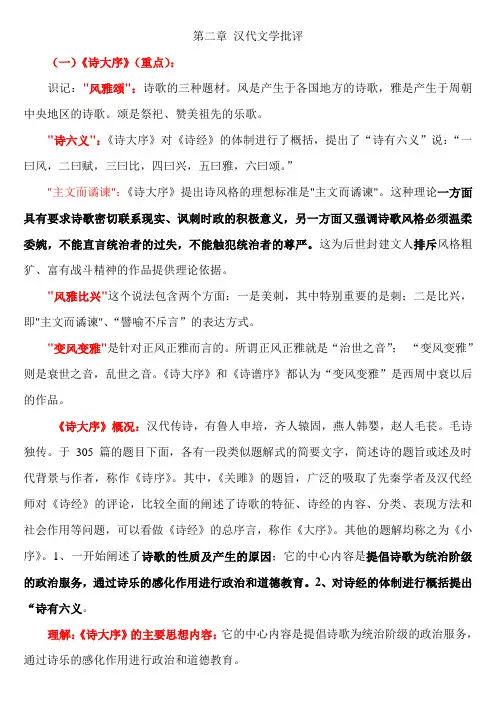
第二章汉代文学批评(一)《诗大序》(重点):识记:"风雅颂":诗歌的三种题材。
风是产生于各国地方的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诗歌。
颂是祭祀、赞美祖先的乐歌。
"诗六义":《诗大序》对《诗经》的体制进行了概括,提出了“诗有六义”说:“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主文而谲谏":《诗大序》提出诗风格的理想标准是"主文而谲谏"。
这种理论一方面具有要求诗歌密切联系现实、讽刺时政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风格必须温柔委婉,不能直言统治者的过失,不能触犯统治者的尊严。
这为后世封建文人排斥风格粗犷、富有战斗精神的作品提供理论依据。
"风雅比兴"这个说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美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刺;二是比兴,即"主文而谲谏"、“譬喻不斥言”的表达方式。
"变风变雅"是针对正风正雅而言的。
所谓正风正雅就是“治世之音”;“变风变雅”则是衰世之音,乱世之音。
《诗大序》和《诗谱序》都认为“变风变雅”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
《诗大序》概况:汉代传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赵人毛苌。
毛诗独传。
于305篇的题目下面,各有一段类似题解式的简要文字,简述诗的题旨或述及时代背景与作者,称作《诗序》。
其中,《关雎》的题旨,广泛的吸取了先秦学者及汉代经师对《诗经》的评论,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诗歌的特征、诗经的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可以看做《诗经》的总序言,称作《大序》。
其他的题解均称之为《小序》。
1、一开始阐述了诗歌的性质及产生的原因;它的中心内容是提倡诗歌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通过诗乐的感化作用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
2、对诗经的体制进行概括提出“诗有六义。
理解:《诗大序》的主要思想内容:它的中心内容是提倡诗歌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通过诗乐的感化作用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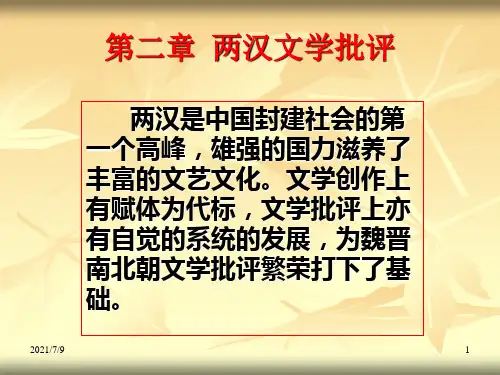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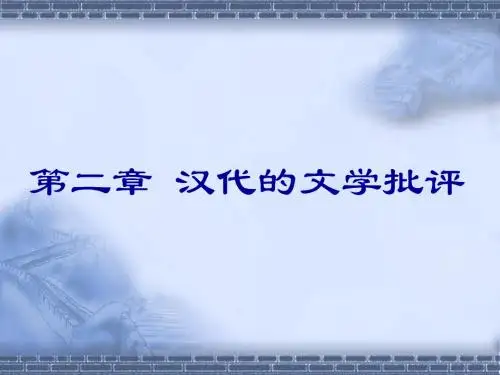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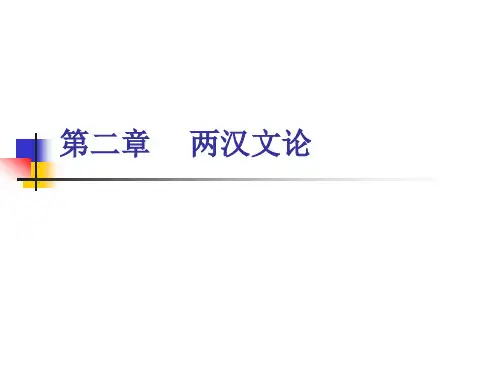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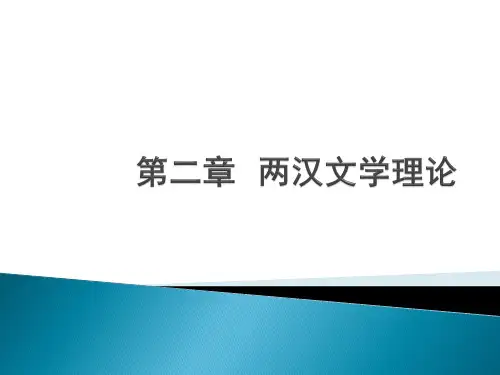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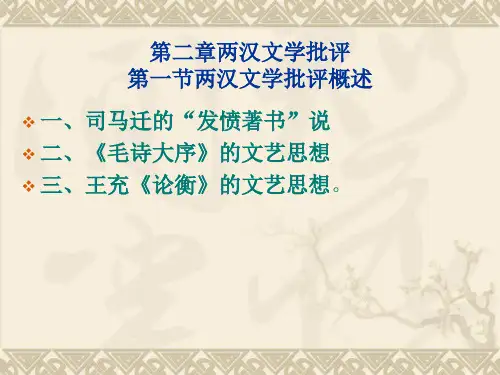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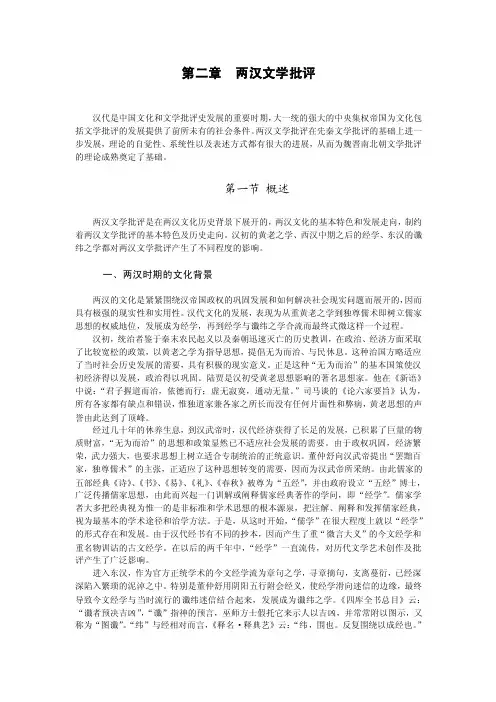
第二章两汉文学批评汉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大一统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为文化包括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
两汉文学批评在先秦文学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性以及表述方式都有很大的进展,从而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理论成熟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概述两汉文学批评是在两汉文化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两汉文化的基本特色和发展走向,制约着两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色及历史走向。
汉初的黄老之学、西汉中期之后的经学、东汉的谶纬之学都对两汉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两汉时期的文化背景两汉的文化是紧紧围绕汉帝国政权的巩固发展和如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实用性。
汉代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从重黄老之学到独尊儒术即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发展成为经学,再到经学与谶纬之学合流而最终式微这样一个过程。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末农民起义以及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提倡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这种治国方略适应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正是这种“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发展,政治得以巩固。
陆贾是汉初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著名思想家。
他在《新语》中说:“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所有各家都有缺点和错误,惟独道家兼各家之所长而没有任何片面性和弊病,黄老思想的声誉由此达到了顶峰。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代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政策显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政权巩固,经济繁荣,武力强大,也要求思想上树立适合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
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适应了这种思想转变的需要,因而为汉武帝所采纳。
由此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被尊为“五经”,并由政府设立“五经”博士,广泛传播儒家思想,由此而兴起一门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的学问,即“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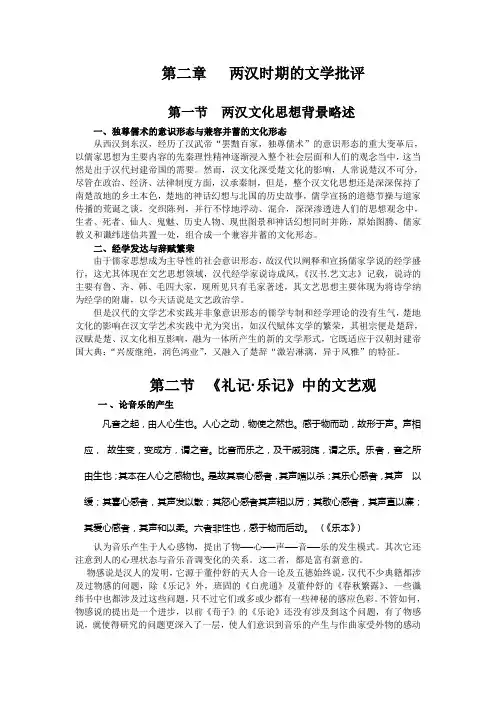
第二章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第一节两汉文化思想背景略述一、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与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后,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逐渐浸入整个社会层面和人们的观念当中,这当然是出于汉代封建帝国的需要。
然而,汉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人常说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方面,汉承秦制,但是,整个汉文化思想还是深深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诞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谶纬迷信共置一处,组合成一个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
二、经学发达与辞赋繁荣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故汉代以阐释和宣扬儒家学说的经学盛行,这尤其体现在文艺思想领域,汉代经学家说诗成风,《汉书.艺文志》记载,说诗的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大家,现所见只有毛家著述,其文艺思想主要体现为将诗学纳为经学的附庸,以今天话说是文艺政治学。
但是汉代的文学艺术实践并非象意识形态的儒学专制和经学理论的没有生气,楚地文化的影响在汉文学艺术实践中尤为突出,如汉代赋体文学的繁荣,其祖宗便是楚辞,汉赋是楚、汉文化相互影响,融为一体所产生的新的文学形式,它既适应于汉朝封建帝国大典:“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又融入了楚辞“激岩淋漓,异于风雅”的特征。
第二节《礼记·乐记》中的文艺观一、论音乐的产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第二章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两汉时期两汉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特点: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侧重探讨文学的外部规律汉代儒家思想在先秦基础上有了新发展,形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的文艺思想也发展成为封建正统的文艺思想,其基本纲领就是“文学-人心-治道”的“诗教”公式,注重阐述文艺和现实、文艺和时代的关系,明确提出美刺讽谏说。
在文学创作思想和文学批评上进一步形成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
道家文艺思想的潜流一直存在。
第一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重要建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二是在《史记》中专门为文学家设传,并对作家们的生平事迹及作品展开评论,推动了古代作家论和作品评论的发展。
一、“发愤著书”说(一)“发愤著书”说的理论背景▪《诗经》:《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小雅.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孔子:“诗可以怨”▪屈原《惜诵》:“发愤以抒情”▪《淮南子》:“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之后,很多理论家和艺术家都对此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说,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欧阳修、李贽、金圣叹、张竹坡、蒲松龄、廖燕等。
▪“发愤著书”说自司马迁提出后,贯穿古代文论史始终。
(二)“发愤著书”的理论意义及价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这种面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激情和“直谏”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