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
- 格式:ppt
- 大小:158.50 KB
- 文档页数: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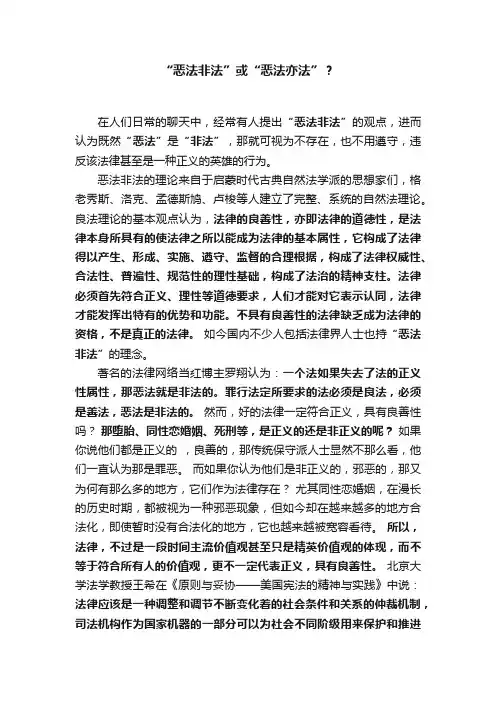
“恶法非法”或“恶法亦法”?在人们日常的聊天中,经常有人提出“恶法非法”的观点,进而认为既然“恶法”是“非法”,那就可视为不存在,也不用遵守,违反该法律甚至是一种正义的英雄的行为。
恶法非法的理论来自于启蒙时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建立了完整、系统的自然法理论。
良法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法律的良善性,亦即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使法律之所以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属性,它构成了法律得以产生、形成、实施、遵守、监督的合理根据,构成了法律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规范性的理性基础,构成了法治的精神支柱。
法律必须首先符合正义、理性等道德要求,人们才能对它表示认同,法律才能发挥出特有的优势和功能。
不具有良善性的法律缺乏成为法律的资格,不是真正的法律。
如今国内不少人包括法律界人士也持“恶法非法”的理念。
著名的法律网络当红博主罗翔认为:一个法如果失去了法的正义性属性,那恶法就是非法的。
罪行法定所要求的法必须是良法,必须是善法,恶法是非法的。
然而,好的法律一定符合正义,具有良善性吗?那堕胎、同性恋婚姻、死刑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呢?如果你说他们都是正义的,良善的,那传统保守派人士显然不那么看,他们一直认为那是罪恶。
而如果你认为他们是非正义的,邪恶的,那又为何有那么多的地方,它们作为法律存在?尤其同性恋婚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被视为一种邪恶现象,但如今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合法化,即使暂时没有合法化的地方,它也越来越被宽容看待。
所以,法律,不过是一段时间主流价值观甚至只是精英价值观的体现,而不等于符合所有人的价值观,更不一定代表正义,具有良善性。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希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中说:法律应该是一种调整和调节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条件和关系的仲裁机制,司法机构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可以为社会不同阶级用来保护和推进自己的利益。
美国著名法学家,曾任美国法律与社会学会会长,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碰撞——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一书中说:法律、判决、规则和规章从何而来?实际上,它们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力量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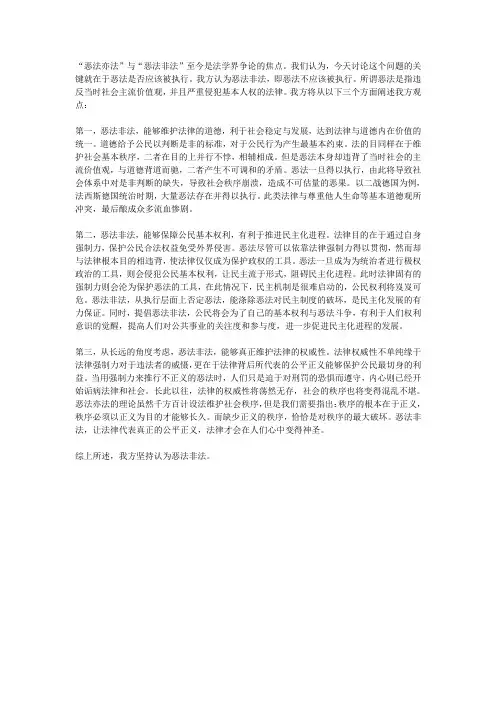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至今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
我们认为,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恶法是否应该被执行。
我方认为恶法非法,即恶法不应该被执行。
所谓恶法是指违反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且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律。
我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我方观点:第一,恶法非法,能够维护法律的道德,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达到法律与道德内在价值的统一。
道德给予公民以判断是非的标准,对于公民行为产生最基本约束。
法的目同样在于维护社会基本秩序,二者在目的上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但是恶法本身却违背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道德背道而驰,二者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恶法一旦得以执行,由此将导致社会体系中对是非判断的缺失,导致社会秩序崩溃,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
以二战德国为例,法西斯德国统治时期,大量恶法存在并得以执行。
此类法律与尊重他人生命等基本道德观所冲突,最后酿成众多流血惨剧。
第二,恶法非法,能够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有利于推进民主化进程。
法律目的在于通过自身强制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免受外界侵害。
恶法尽管可以依靠法律强制力得以贯彻,然而却与法律根本目的相违背,使法律仅仅成为保护政权的工具。
恶法一旦成为为统治者进行极权政治的工具,则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让民主流于形式,阻碍民主化进程。
此时法律固有的强制力则会沦为保护恶法的工具,在此情况下,民主机制是很难启动的,公民权利将岌岌可危。
恶法非法,从执行层面上否定恶法,能涤除恶法对民主制度的破坏,是民主化发展的有力保证。
同时,提倡恶法非法,公民将会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与恶法斗争,有利于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提高人们对公共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进一步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第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恶法非法,能够真正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法律权威性不单纯缘于法律强制力对于违法者的威慑,更在于法律背后所代表的公平正义能够保护公民最切身的利益。
当用强制力来推行不正义的恶法时,人们只是迫于对刑罚的恐惧而遵守,内心则已经开始诟病法律和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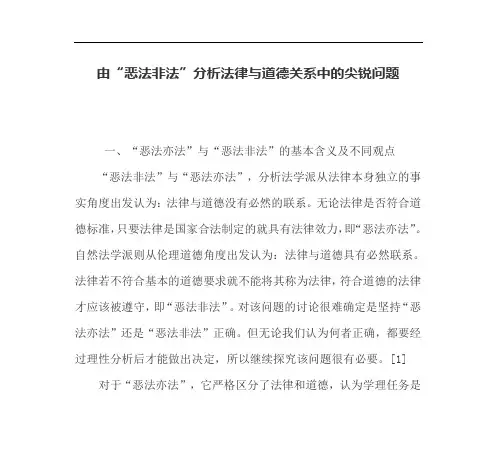
由“恶法非法”分析法律与道德关系中的尖锐问题一、“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基本含义及不同观点“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分析法学派从法律本身独立的事实角度出发认为: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
无论法律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只要法律是国家合法制定的就具有法律效力,即“恶法亦法”。
自然法学派则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认为: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
法律若不符合基本的道德要求就不能将其称为法律,符合道德的法律才应该被遵守,即“恶法非法”。
对该问题的讨论很难确定是坚持“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正确。
但无论我们认为何者正确,都要经过理性分析后才能做出决定,所以继续探究该问题很有必要。
[1] 对于“恶法亦法”,它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学理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其道德上的善与恶。
[2]它坚持一项法律只要主体适格、程序正当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但这样的观点片面强调了维护法律权威而无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这必然会导致人民与法律的对立。
现在若坚持“恶法亦法”,不仅会在立法层次上也会在国家政治法律领域中出现“有权就有法”的不利后果。
执法者和司法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执行和运用法律,所以即使是完全按照立法原意,没有掺杂任何私心来运行法律,也不能避免将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上升为法律。
这样在执法与司法层面也会出现“谁有权谁就是法”的现象,从而导致法律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那法律实施的效果可想而知。
“恶法非法”则认为法律若是违背了社会道德,就是非理性的,它们不具备道德上的效力就更不具备法律上的效力,不能称之为法律。
该论断捍卫了立法权属于人民,这样可以使国家的立法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以保证法律是符合道德的法律,以实现真正的法治。
法律只有在做到合情合理的基础上,才可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
如何保证我们的法不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我们必须以普通民众都能理解的常识、常情、常理作为指导我们制定、适用、执行法律的基础、灵魂、限度和根本标准。
[3]所以我们不可能强迫不懂法的部分群众去靠拢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应该做到让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向人民共同认可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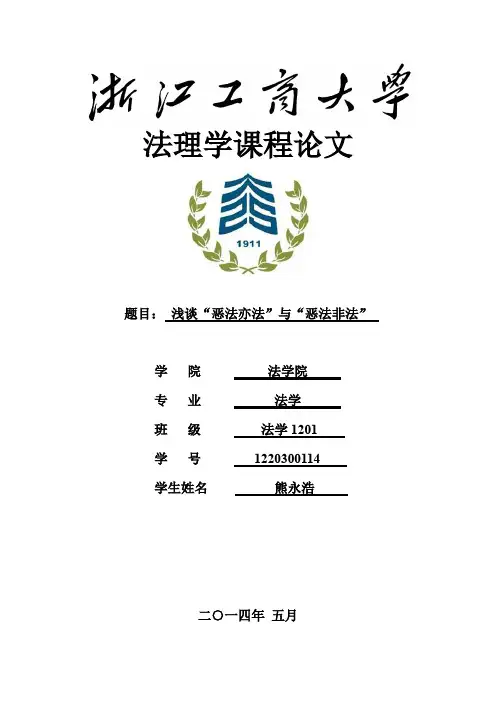
法理学课程论文题目:浅谈“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学院法学院专业法学班级法学1201学号1220300114学生姓名熊永浩二○一四年五月浅谈“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摘要:本文从“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两种法律思想入手,从而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再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述“良法”的真正含义,最后得出将正义性与强制性有机统一的法律才是现实意义中的“良法”的结论。
关键词:恶法非法恶法亦法道德与法律正义性与强制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至今争论不休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上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对立的观点。
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有着必然联系,法律应当是合乎道德的“良法”,不合道德的“恶法”不应叫做法律,即“恶法非法”。
而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法律就是国家制定的实在法,不道德的法律只要合法制定的程序与规则就具有法律效力,即“恶法亦法”。
由于该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在法理思想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争议,因而我国法学界的主流一般不再关注这些纯粹的法律理论问题,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法律现象的社会学解释上。
虽然如此,但问题依旧存在,并且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无法回避。
无论我们选择“恶法非法”论还是“恶法亦法”的观点,都要经过理性分析后才能作出决定,这是我国建立“法治国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要求。
由于道德与法律不但都是关于人们的社会行为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而且都是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规范。
因此,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两种观点的联系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一、两种观点在法律与道德问题上的表现“恶法亦法”是在分析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的效力不在于它是否符合道德而在于它是否是适格的主体以恰当的方式颁布。
只要是适格的主体以恰当的方式颁布的法律,即使它再不符合道德,它再不被人们所接受,它仍是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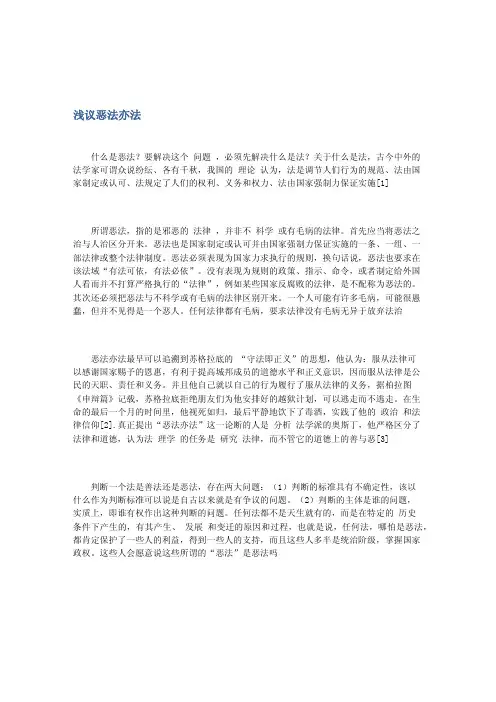
浅议恶法亦法什么是恶法?要解决这个 问题 ,必须先解决什么是法?关于什么是法,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我国的 理论 认为,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法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义务和权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1]所谓恶法,指的是邪恶的 法律 ,并非不 科学 或有毛病的法律。
首先应当将恶法之治与人治区分开来。
恶法也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条、一组、一部法律或整个法律制度。
恶法必须表现为国家力求执行的规则,换句话说,恶法也要求在该法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没有表现为规则的政策、指示、命令,或者制定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严格执行的“法律”,例如某些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是不配称为恶法的。
其次还必须把恶法与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区别开来。
一个人可能有许多毛病,可能很愚蠢,但并不见得是一个恶人。
任何法律都有毛病,要求法律没有毛病无异于放弃法治恶法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 “守法即正义”的思想,他认为:服从法律可以感谢国家赐予的恩惠,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平和正义意识,因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和义务。
并且他自己就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朋友们为他安排好的越狱计划,可以逃走而不逃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视死如归,最后平静地饮下了毒酒,实践了他的 政治 和法律信仰[2].真正提出“恶法亦法”这一论断的人是 分析 法学派的奥斯丁,他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法 理学 的任务是 研究 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与恶[3]判断一个法是善法还是恶法,存在两大问题:(1)判断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该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有争议的问题。
(2)判断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实质上,即谁有权作出这种判断的问题。
任何法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 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其产生、 发展 和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也就是说,任何法,哪怕是恶法,都肯定保护了一些人的利益,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且这些人多半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浅,议,恶,其他论文文档]浅议恶法亦法(1)论文](https://uimg.taocdn.com/4880fdb7a417866fb94a8e75.webp)
浅议恶法亦法(1)论文恶法亦法“的形式逻辑结构是”坏人也是人“,然而这不过是对论题望文生义的理解,没有多大意义。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的真正意义在于:执法者是否应当执行恶法,守法者是否应当遵守恶法?什么是恶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什么是法?关于什么是法,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我国的理论认为,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法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义务和权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所谓恶法,指的是邪恶的法律,并非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
首先应当将恶法之治与人治区分开来。
恶法也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条、一组、一部法律或整个法律制度。
恶法必须表现为国家力求执行的规则,换句话说,恶法也要求在该法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没有表现为规则的政策、指示、命令,或者制定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严格执行的“法律”,例如某些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是不配称为恶法的。
其次还必须把恶法与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区别开来。
一个人可能有许多毛病,可能很愚蠢,但并不见得是一个恶人。
任何法律都有毛病,要求法律没有毛病无异于放弃法治。
恶法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守法即正义”的思想,他认为:服从法律可以感谢国家赐予的恩惠,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平和正义意识,因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和义务。
并且他自己就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朋友们为他安排好的越狱计划,可以逃走而不逃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视死如归,最后平静地饮下了毒酒,实践了他的政治和法律信仰.真正提出“恶法亦法”这一论断的人是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他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与恶 .判断一个法是善法还是恶法,存在两大问题:(1)判断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该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有争议的问题。
判断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实质上,即谁有权作出这种判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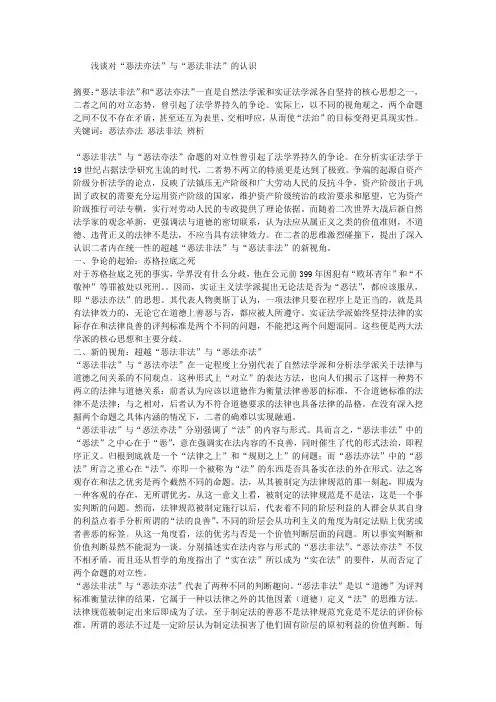
浅谈对“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认识摘要:“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一直是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各自坚持的核心思想之一,二者之间的对立态势,曾引起了法学界持久的争论。
实际上,以不同的视角观之,两个命题之间不仅不存在矛盾,甚至还互为表里、交相呼应,从而使“法治”的目标变得更具现实性。
关键词:恶法亦法恶法非法辨析“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命题的对立性曾引起了法学界持久的争论。
在分析实证法学于19世纪占据法学研究主流的时代,二者势不两立的特质更是达到了极致。
争端的起源自资产阶级分析法学的论点,反映了法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出于巩固了政权的需要充分运用资产阶级的国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它为资产阶级推行司法专横,实行对劳动人民的专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然法学家的观念革新,更强调法与道德的密切联系,认为法应从属正义之类的价值准则,不道德、违背正义的法律不是法,不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在二者的思维激烈碰撞下,提出了深入认识二者内在统一性的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非法”的新视角。
一、争论的起始: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事实,学界没有什么分歧,他在公元前399年因犯有“败坏青年”和“不敬神”等罪被处以死刑。
因而,实证主义法学派提出无论法是否为“恶法”,都应该服从,即“恶法亦法”的思想。
其代表人物奥斯丁认为,一项法律只要在程序上是正当的,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无论它在道德上善恶与否,都应被人所遵守。
实证法学派始终坚持法律的实际存在和法律良善的评判标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这两个问题混同。
这些便是两大法学派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分歧。
二、新的视角: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关于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不同观点。
这种形式上“对立”的表达方法,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种势不两立的法律与道德关系:前者认为应该以道德作为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不合道德标准的法律不是法律;与之相对,后者认为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也具备法律的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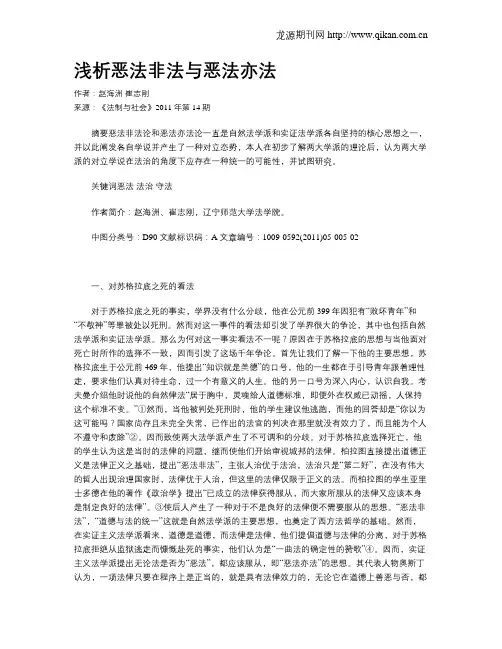
浅析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作者:赵海洲崔志刚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4期摘要恶法非法论和恶法亦法论一直是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各自坚持的核心思想之一,并以此阐发各自学说并产生了一种对立态势,本人在初步了解两大学派的理论后,认为两大学派的对立学说在法治的角度下应存在一种统一的可能性,并试图研究。
关键词恶法法治守法作者简介:赵海洲、崔志刚,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005-02一、对苏格拉底之死的看法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事实,学界没有什么分歧,他在公元前399年因犯有“败坏青年”和“不敬神”等罪被处以死刑。
然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却引发了学界很大的争论,其中也包括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
那么为何对这一事实看法不一呢?原因在于苏格拉底的思想与当他面对死亡时所作的选择不一致,因而引发了这场千年争论。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他的主要思想,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他提出“知识就是美德”的口号,他的一生都在于引导青年跟着理性走,要求他们认真对待生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他的另一口号为深入内心,认识自我。
考夫曼介绍他时说他的自然律法“居于胸中,灵魂给人道德标准,即便外在权威已动摇,人保持这个标准不变。
”①然而,当他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学生建议他逃跑,而他的回答却是“你以为这可能吗?国家尚存且未完全失常,已作出的法官的判决在那里就没有效力了,而且能为个人不遵守和废除”②。
因而致使两大法学派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对于苏格拉底选择死亡,他的学生认为这是当时的法律的问题,继而使他们开始审视城邦的法律。
柏拉图直接提出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之基础,提出“恶法非法”,主张人治优于法治,法治只是“第二好”,在没有伟大的哲人出现治理国家时,法律优于人治,但这里的法律仅限于正义的法。
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提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理论分歧与契合-法理学论文-法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理论分歧在法学世界里,有三大传统学术流派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就是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
良好的法律是人们美好的追求,然而关于恶法是否也是法律却是法学家们一直争论的主题,由此形成了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两派对立的观点。
自然法学派是西方法律思想古老的学派,它源远流长,时至今日依然是主流学派之一。
所谓自然法,即道德法、正义法。
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
自然法被理解为人类共同生活所遵循的法则,人们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一切成文法的基础。
在西方资产阶级时期,自然法的思想被当作的口号,写进了法国的《宣言》和美国的《宪法》。
然而,自然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是人们对真理追求的美好愿望,但现实法却并不一定总是符合自然法的要求。
到19世纪,自然法学一度衰落。
就在此时,以实证哲学方法为基础,分析法学在具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诞生。
分析法学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边沁、奥斯丁等。
大哲学家休谟曾提出一个命题:应该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在法学语境中,这一命题可以表述为:应该区别实际存在的法和应当存在的法。
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去除应当存在的法,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命题。
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道德上的法律仍然是法律,即恶法亦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恶法亦法被法西斯分子利用,导致了巨大的灾难。
特别是纽伦堡审判后,自然法学派重新获得生机并逐渐占据上风,而分析学派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些学者纷纷转向新自然法学派或者其理论向自然法学派靠拢。
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富勒、罗尔斯等。
富勒认为法律必须以基本道德为基础,法律必须具有内在正义性,不符合基本道德的法律不应该成为法律或者不应该继续成为法律。
而新分析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凯尔森、英国的哈特等。

第16卷第4期2017年8月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AIBEI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Vol. 16 No. 4Aug. 20 7“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王天煜(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黴淮北235000)摘要:恶法亦法”强调法的形式,恶法非法”重视法的内在价值,这两种观点共同催生了现代法治。
当下中国仍处 社会主义法治的初级阶段,强调“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两种观点的结合,有助于法治的完善。
立法层面上,法律 的制定要具备前瞻性,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要体现自然法的价值追求;司法层面上,要注重探求情、理、法在司法裁 判中的兼容;守法层面上,要强调对法律的绝对服从。
关键词:恶法亦法;恶法非法;立法;司法;守法中图分类号:D920. 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275(2017)04-0081-03“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是西方新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争端的一个焦点,两种观点的产生有着各自的历史背景、时代意义和一定的局限性,而当下法学界对此争端早有定论,更不用提经济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等学派的出现,使得这一矛盾的基础—应然法和实然法之争显得无足轻重了。
然而,通过对这一争端产生和发展的重新审视,对 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大有助益。
一、“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明确这一争端,首先需要认知两点内容:其一,“恶法”存在的前提是承认有“良法”和“恶法”的区 分,用以区分二者的标尺可以笼统地归结为抽象的道德。
通常情况下,“恶法”大多在法律原则上为“良”,即法律在创制时体现出的法律制定者的意志和价值追求、对社会秩序保护的预期往往是“良”的,然而通过法律规则形成法律条文时,可能出现表述不周或在法律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为恶”的现象。
其二,关于法之“善恶”的讨论范畴为何。
根 据严存生教授的观点,法可分为必然法、应然法、实 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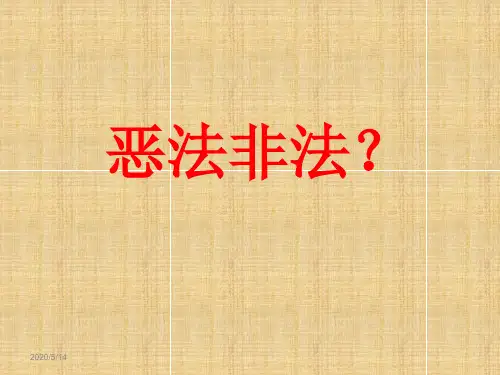
关于“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思考关于“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的思考“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是我们在讨论法律问题时常常提出的说法,但是这两种说法往往被误用,想在实践中对这两种说法有更好的认识与理解,我们需要从一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解与思考。
一、思想源流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法治的双重含义始,即“良法”必须符合实质和形式的双重标准,制定自然公正的法律一直都是大多数思想家的理想。
特别是经自然法学派的鼓吹,“邪恶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这样的法律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恶法非法”论独领风骚近两个世纪。
但是,18 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自此,资产阶级在国内才算真正站稳脚跟,西方社会步入真正的现代社会。
与此同时,近代的古典自然法学开始衰落,分析法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恶法亦法”论自然也就成了当时法理学的主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自然法学开始了真正的复兴。
这同法西斯暴行及其与实证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审理法西斯战犯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难题密切相关。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哈特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提出,说明了“恶法非法”论与“恶法亦法”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并在当代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二、现实认知“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问题争论的实质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争论。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在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包容、无涉、交叉。
自然法学主张包容说,认为二者有着必然联系,法律应当合乎道德,不合道德的法律不应叫做法律,即“恶法非法”。
实证主义法学主张无涉说,认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法律就是国家制定的实在法,不道德的法律只要合法制定就是法律,即“恶法亦法”。
但实际的情形是,道德和法律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规范体系,二者的规定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地方。
例如,偷盗、抢劫、杀人等犯罪行为是道德和法律共同反对的,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要罚款比人们的道德谴责严厉得多,通奸为许多国家道德所反对而法律却不禁止,帮助弱势群体是道德义务但不是法律义务,等等。
浅议恶法亦法恶法亦法“的形式逻辑结构是”坏人也是人“,然而这不过是对论题望文生义的理解,没有多大意义。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的真正意义在于:执法者是否应当执行恶法,守法者是否应当遵守恶法?什么是恶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什么是法?关于什么是法,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我国的理论认为,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法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义务和权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所谓恶法,指的是邪恶的法律,并非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
首先应当将恶法之治与人治区分开来。
恶法也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条、一组、一部法律或整个法律制度。
恶法必须表现为国家力求执行的规则,换句话说,恶法也要求在该法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没有表现为规则的政策、指示、命令,或者制定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严格执行的“法律”,例如某些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是不配称为恶法的。
其次还必须把恶法与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区别开来。
一个人可能有许多毛病,可能很愚蠢,但并不见得是一个恶人。
任何法律都有毛病,要求法律没有毛病无异于放弃法治。
恶法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守法即正义”的思想,他认为:服从法律可以感谢国家赐予的恩惠,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平和正义意识,因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和义务。
并且他自己就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朋友们为他安排好的越狱计划,可以逃走而不逃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视死如归,最后平静地饮下了毒酒,实践了他的政治和法律信仰.真正提出“恶法亦法”这一论断的人是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他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与恶 .判断一个法是善法还是恶法,存在两大问题:(1)判断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该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有争议的问题。
(2)判断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实质上,即谁有权作出这种判断的问题。
关于“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讨论之比较(一)两篇文章之简述:(1)第一篇是《试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以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为视角》,作者是李姗芙,该篇文章通过对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对此问题的阐述进行探讨,浅析这一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尚未盖棺定论的争端的深远影响以及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首先文章从苏格拉底之死,后世的法学家们开始对于“法律”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思考。
以自然法学派为代表的“恶法非法”与实证法学派的“恶法亦法”逐渐活跃在历史舞台。
接下来又讨论“恶法非法”的历史渊源,价值,“恶法亦法”的历史渊源,价值。
最后通过再讨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间的博弈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要想实现法的价值追求,就要将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与法的形式的“合法性”有机结合,所谓良善的法律,它不应该只是单单符合道德,符合自然法的规范的,法律的主体是否适格、形式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当也是法律是否为良法的重要评判标准。
(2)第二篇是《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本体分析》,作者是李寿初。
作者认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各有其片面性。
但其实,道德与法律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所以作者放弃大众的论述方式,从道德与法律的角度展开讨论。
在结构上,他比较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共性,区别以及关系,得出结论:通过对规范属性的分析发现,二者都是关于社会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道德是表现为道德形式的道德价值,法律是表现为法律形式的道德价值。
道德和法律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拥有国家权力属性而道德则没有。
人们在接受法律规范的同时也要接受道德的调整。
由于二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既有共同的规则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于共同的规则,人们在遵守一方时也就遵守了另一方。
对于不一致的规则,如果遵守法律就违背了道德,而遵守道德就违背了法律,从而产生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
在传统人治国家,由于统治者具有至高地位,该问题的处理最终取决于统治者的决断。
浅谈“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摘要]文章从“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两种法律思想入手,从而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再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述“良法”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恶法亦法;恶法非法;法律与道德“恶法亦法”是在分析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的效力不在于它是否符合道德而在于它是否是适格的主体以恰当的方式颁布。
只要是适格的主体以恰当的方式颁布的法律,即使它再不符合道德,它再不被人们所接受,它仍是法律。
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奥斯丁在论证“恶法亦法”这一命题时,列出了以下几点理由:(1)道德上邪恶的法律,尽管人们的憎恶和反对,也不会失去作为“主权者的命令”的性质,同样具有强制力。
(2)自然法学提出的评价法律的良恶的自然法标准,并不具有其绝对的客观真理性,因为理性法或上帝之法,并不是明确的,而是一些人的价值主张,在革命时期,这种理论的目的在于论证某种革命主张的正当性;而在和平时期,这种理论主张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3)与理性法相冲突的人法不可能具有义务性或拘束力,不能被认为是法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与分析法学派的“恶法亦法”截然相反的是自然法学派的“恶法非法”理论。
自然法学派认为,在人定法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法律即自然法。
自然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它体现着正义与公平,自然法是基于人性的道德法,是对上帝永恒法的参与。
自然法强调的是法律与道德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
新自然法学的代表富勒将法律分为内在的道德和外在的道德。
法律所应当遵循的内在道德准则是程序自然法,它应当遵循的外在道德准则是实体自然法。
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法律不仅体现了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即他称之为法律的外在道德,而法律制度作为整体必须满足程序上的八项要求,即法律的内在道德。
他首先探讨了道德的本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
试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作者:李姗芙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09期摘要关于“恶法”是否为“法”的争论已在法学界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围绕这一争论焦点许多法学流派应运而生。
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学派的理论体系已经隐没在时光长河中,但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关于此问题的探讨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成为主流法律思想,至今依然具有极高的法学研究价值。
本文拟通过对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对此问题的阐述进行探讨,浅析这一场尚未盖棺定论的争端的深远影响以及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关键词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道德秩序作者简介:李姗芙,中南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19.03.237一、“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争的开端——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3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腐蚀和误导许多青年人”。
在执行死刑前,他的朋友假借狱中探望的名义,悄悄告诉苏格拉底他可以帮助他从监狱里轻易逃走,苏格拉底没有必要去遵循这样一部荒诞的,充满恶意的法律。
但是苏格拉底却严词拒绝道:人难道没有遵守任何一部法律的义务?国家还没有完全失去常态,已经做出的判决就已经被宣告无效,可以被个人无视和废除?最终,这位伟大的哲人从容赴死,用生命诠释了“守法即正义”的命题。
在苏格拉底的眼中,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比法律的公正性更为重要,宁可牺牲公民因判决不公而不服从判决的权利也不能破坏这个社会的“方圆”。
一个人若是不服从法律的判决就相当于亲手撕毁了这个人与这个国家订立的契约,毁约也是不道德的表现。
面对苏格拉底从容作出的选择,后世的法学家们开始对于“法律”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思考。
浅析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摘要: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争论由来已久,其反映了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对立。
自然法学大多主张“恶法非法”或者“良法之治”,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主张“恶法亦法”,强调法律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本文旨在剖析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异同,揭示“恶法亦法”理论对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性关键词:自然法;法律实证主义;恶法亦法;恶法非法;法治一.由“苏格拉底之死”所看到的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的古希腊雅典,一个民主制度发达的城邦。
苏格拉底擅长辩论,经常将人辩的哑口无言,让人下不了台面,而且喜欢对世风说三道四。
借着假装无知的方式,苏格拉底强迫他所遇见的人们运用本身的常识。
这种装傻、装呆的方式,我们成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即使在市区广场的中心,他也照做不误。
于是,对某些人而言,与苏格拉底谈话无异于当众出丑并成为众人的笑柄[1]。
苏格拉底曾说;“雅典就像一匹驽马,而我就是一只不断叮它,让它具有活力的牛蝇。
但牛蝇终究是不受欢迎的。
终于,在公元前399年,三个曾被苏格拉底数落过的雅典人控告他犯下两条罪状:渎神和腐化误导青年。
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对一切不信现存宗教者和与神事不同见解者治罪惩罚。
”尽管苏格拉底能言善辩,坚持不认为自己有罪,雅典的民众最终以281票对220票判他死罪无赦。
临刑前,他的老朋友借探望之际告诉苏格拉底,朋友们决定帮他越狱。
克力同想尽办法说服苏格拉底,雅典的法律是多么的不公正,遵守这种法律简直就是愚蠢,但是终归无效[2]。
苏格拉底反问克力同:“越狱就是公正的吗?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是正当了?”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这位临终的圣贤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好,惟有神知道。
”苏格拉底给出了两条不越狱的理由:一,如果人人都以法律判决不公正为理由而逃避裁判,那么国家社会岂能有个规矩方圆?法律判决的公正固然重要,但秩序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