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
- 格式:doc
- 大小:27.00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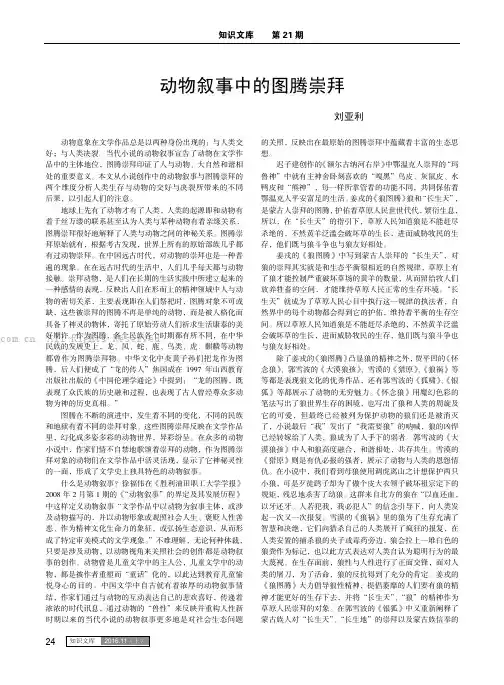
动物叙事中的图腾崇拜刘亚利动物意象在文学作品总是以两种身份出现的:与人类交好;与人类决裂。
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宣告了动物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图腾崇拜印证了人与动物、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
本文从小说创作中的动物叙事与图腾崇拜的两个维度分析人类生存与动物的交好与决裂所带来的不同后果,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地球上先有了动物才有了人类,人类的起源即和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人类与某种动物有着亲缘关系,图腾崇拜很好地解释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神秘关系。
图腾崇拜原始就有,根据考古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原始部族几乎都有过动物崇拜。
在中国远古时代,对动物的崇拜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在远古时代的生活中,人们几乎每天都与动物接触。
崇拜动物,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感情的表现,反映出人们在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中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即在人们祭祀时,图腾对象不可或缺,这些被崇拜的图腾不再是单纯的动物,而是被人格化而具备了神灵的物体,寄托了原始劳动人们祈求生活康泰的美好期许。
作为图腾,各个民族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龙、凤、蛇、鹿、鸟类、虎、麒麟等动物都曾作为图腾崇拜物。
中华文化中炎黄子孙们把龙作为图腾,后人们便成了“龙的传人”焦国成在1997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伦理学通论》中提到:“龙的图腾,既表现了众氏族的历史融和过程,也表现了古人曾经尊众多动物为神的历史真相。
”图腾在不断的演进中,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民族和地狱有着不同的崇拜对象。
这些图腾崇拜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幻化成多姿多彩的动物世界,异彩纷呈。
在众多的动物小说中,作家们情不自禁地歌颂着崇拜的动物,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动物们在文学作品中活灵活现,显示了它神秘灵性的一面,形成了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动物叙事。
什么是动物叙事?徐福伟在《胜利油田职工大学学报》2008年2月第1期的《“动物叙事”的界定及其发展历程》中这样定义动物叙事“文学作品中以动物为叙事主体,或涉及动物描写的,并以动物形象或观照社会人生、褒贬人性善恶、作为精神文化生命力的象征,或弘扬生态意识,从而形成了特定审美模式的文学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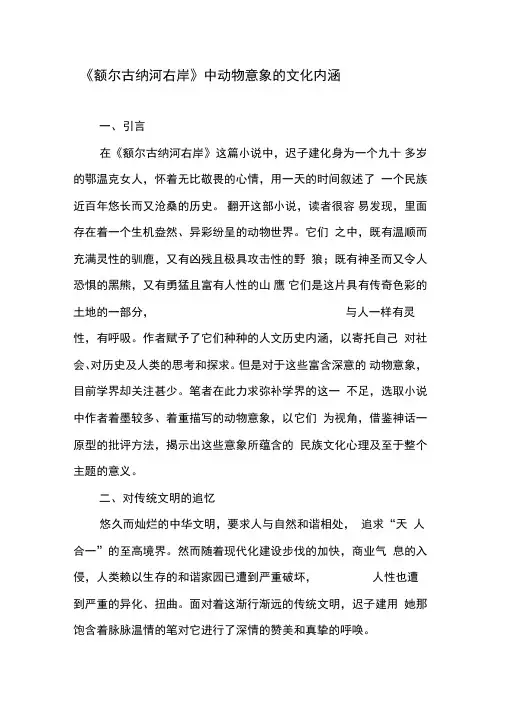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一、引言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篇小说中,迟子建化身为一个九十多岁的鄂温克女人,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用一天的时间叙述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悠长而又沧桑的历史。
翻开这部小说,读者很容易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个生机盎然、异彩纷呈的动物世界。
它们之中,既有温顺而充满灵性的驯鹿,又有凶残且极具攻击性的野狼;既有神圣而又令人恐惧的黑熊,又有勇猛且富有人性的山鹰它们是这片具有传奇色彩的土地的一部分,与人一样有灵性,有呼吸。
作者赋予了它们种种的人文历史内涵,以寄托自己对社会、对历史及人类的思考和探求。
但是对于这些富含深意的动物意象,目前学界却关注甚少。
笔者在此力求弥补学界的这一不足,选取小说中作者着墨较多、着重描写的动物意象,以它们为视角,借鉴神话一原型的批评方法,揭示出这些意象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及至于整个主题的意义。
二、对传统文明的追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然而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商业气息的入侵,人类赖以生存的和谐家园已遭到严重破坏,人性也遭到严重的异化、扭曲。
面对着这渐行渐远的传统文明,迟子建用她那饱含着脉脉温情的笔对它进行了深情的赞美和真挚的呼唤。
这种呼唤,不仅是通过人表现出来,在动物身上,也可见一斑(一)对自然的崇拜与信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着力表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自然万物的平等相处,自然在她笔下既是人物灵魂栖居的自然,又是被赋予人格情态的自然。
如果说把动物作为自然的代表,那么这种情感在它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驯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驯鹿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人们专门放养的一种动物,作者在书中对它作了专门介绍。
它“有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①喜食苔藓,善于在深山密林、沼泽或者是深雪中行走,被人们誉为“林海之舟”。
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把驯鹿当做自己的祖先、守护神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它在小说中一出场便被染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尼都萨满和我父亲一点儿也不像亲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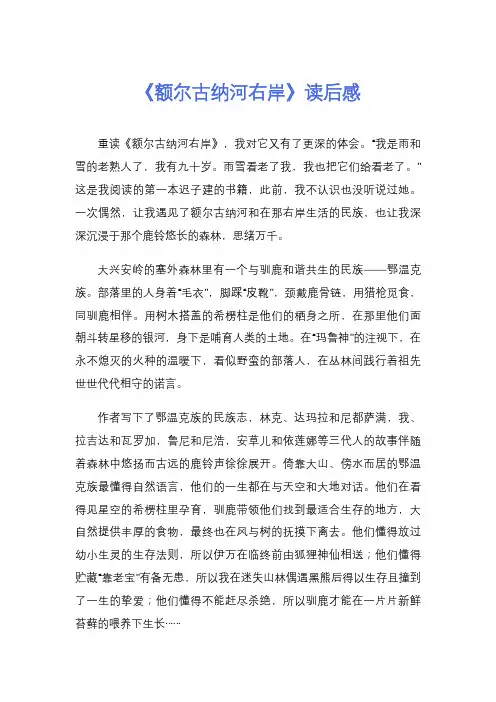
《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重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对它又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
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这是我阅读的第一本迟子建的书籍,此前,我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她。
一次偶然,让我遇见了额尔古纳河和在那右岸生活的民族,也让我深深沉浸于那个鹿铃悠长的森林,思绪万千。
大兴安岭的塞外森林里有一个与驯鹿和谐共生的民族——鄂温克族。
部落里的人身着“毛衣”,脚踩“皮靴”,颈戴鹿骨链,用猎枪觅食,同驯鹿相伴。
用树木搭盖的希楞柱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面朝斗转星移的银河,身下是哺育人类的土地。
在“玛鲁神”的注视下,在永不熄灭的火种的温暖下,看似野蛮的部落人,在丛林间践行着祖先世世代代相守的诺言。
作者写下了鄂温克族的民族志,林克、达玛拉和尼都萨满,我、拉吉达和瓦罗加,鲁尼和尼浩,安草儿和依莲娜等三代人的故事伴随着森林中悠扬而古远的鹿铃声徐徐展开。
倚靠大山、傍水而居的鄂温克族最懂得自然语言,他们的一生都在与天空和大地对话。
他们在看得见星空的希楞柱里孕育,驯鹿带领他们找到最适合生存的地方,大自然提供丰厚的食物,最终也在风与树的抚摸下离去。
他们懂得放过幼小生灵的生存法则,所以伊万在临终前由狐狸神仙相送;他们懂得贮藏“靠老宝”有备无患,所以我在迷失山林偶遇黑熊后得以生存且撞到了一生的挚爱;他们懂得不能赶尽杀绝,所以驯鹿才能在一片片新鲜苔藓的喂养下生长……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是许多与自然相伴的少数民族的缩影,风、雨、雪、水……一切都是自然的化身,他们保护自然也敬畏自然。
被自然养育的人们,朴实而纯洁。
书中最触动人的是妮浩萨满,她从尼都萨满手中接过“玛鲁神”、神鼓、披风等神物后,幻化为部族的守护神,一心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人。
冰天雪地里,神赋予了妮浩使命,身怀六甲的她在雪地里轻盈起舞,犹如人间守护神。
但被选为萨满是有代价的,她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别人的孩子,每当自己的的孩子出事时,她都心疼却又义无反顾地用别人的孩子来拯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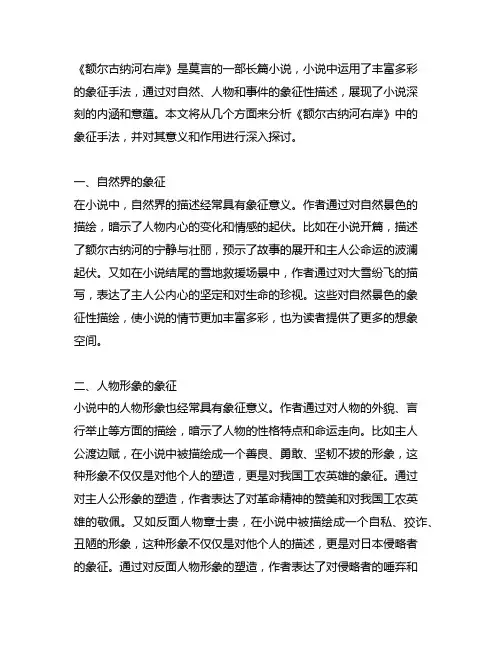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运用了丰富多彩的象征手法,通过对自然、人物和事件的象征性描述,展现了小说深刻的内涵和意蕴。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象征手法,并对其意义和作用进行深入探讨。
一、自然界的象征在小说中,自然界的描述经常具有象征意义。
作者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暗示了人物内心的变化和情感的起伏。
比如在小说开篇,描述了额尔古纳河的宁静与壮丽,预示了故事的展开和主人公命运的波澜起伏。
又如在小说结尾的雪地救援场景中,作者通过对大雪纷飞的描写,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坚定和对生命的珍视。
这些对自然景色的象征性描绘,使小说的情节更加丰富多彩,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二、人物形象的象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经常具有象征意义。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外貌、言行举止等方面的描绘,暗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走向。
比如主人公渡边赋,在小说中被描绘成一个善良、勇敢、坚韧不拔的形象,这种形象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塑造,更是对我国工农英雄的象征。
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作者表达了对革命精神的赞美和对我国工农英雄的敬佩。
又如反面人物章士贵,在小说中被描绘成一个自私、狡诈、丑陋的形象,这种形象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描述,更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象征。
通过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表达了对侵略者的唾弃和对正义的追求。
三、事件情节的象征小说中的事件情节也经常具有象征意义。
作者通过对事件的发展和情节的渲染,传递了许多深刻的哲理和人生感悟。
比如在小说中主人公渡边赋的种种遭遇,都可以被解读为对生命的考验和对信念的坚守。
又如小说中的许多战争场景,都可以被解读为对战争的悲哀和对和平的追求。
这些事件的象征意义,为小说的情节增添了更多的内涵和意蕴。
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象征手法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融合了丰富多彩的象征元素,通过对自然、人物和事件的象征性描绘,展现了丰富的内涵和意蕴。
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艺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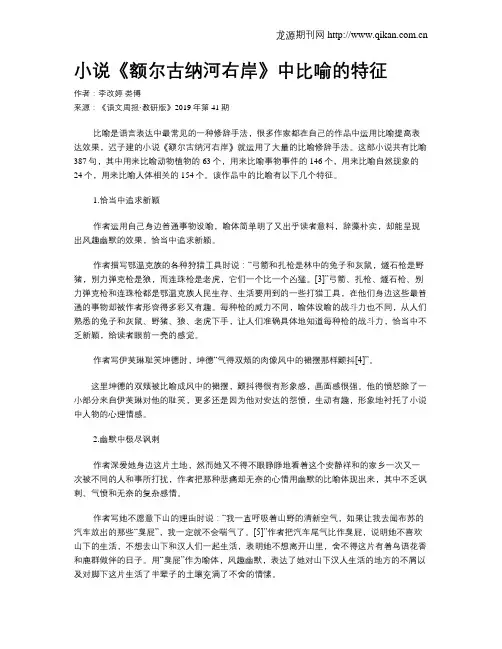
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比喻的特征作者:李改婷娄博来源:《语文周报·教研版》2019年第41期比喻是语言表达中最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比喻提高表达效果,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就运用了大量的比喻修辞手法。
这部小说共有比喻387句,其中用来比喻动物植物的63个,用来比喻事物事件的146个,用来比喻自然现象的24个,用来比喻人体相关的154个。
该作品中的比喻有以下几个特征。
1.恰当中追求新颖作者运用自己身边普通事物设喻,喻体简单明了又出乎读者意料,辞藻朴实,却能呈现出风趣幽默的效果,恰当中追求新颖。
作者描写鄂温克族的各种狩猎工具时说:“弓箭和扎枪是林中的兔子和灰鼠,燧石枪是野猪,别力弹克枪是狼,而连珠枪是老虎,它们一个比一个凶猛。
[3]”弓箭、扎枪、燧石枪、别力弹克枪和连珠枪都是鄂温克族人民生存、生活要用到的一些打猎工具,在他们身边这些最普通的事物却被作者形容得多彩又有趣。
每种枪的威力不同,喻体设喻的战斗力也不同,从人们熟悉的兔子和灰鼠、野猪、狼、老虎下手,让人们准确具体地知道每种枪的战斗力,恰当中不乏新颖,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
作者写伊芙琳耻笑坤德时,坤德“气得双颊的肉像风中的裙摆那样颤抖[4]”。
这里坤德的双颊被比喻成风中的裙摆,颤抖得很有形象感,画面感很强。
他的愤怒除了一小部分来自伊芙琳对他的耻笑,更多还是因为他对安达的怨愤,生动有趣,形象地衬托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情感。
2.幽默中极尽讽刺作者深爱她身边这片土地,然而她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安静祥和的家乡一次又一次被不同的人和事所打扰,作者把那种悲痛却无奈的心情用幽默的比喻体现出来,其中不乏讽刺、气愤和无奈的复杂感情。
作者写她不愿意下山的理由时说:“我一直呼吸着山野的清新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
[5]”作者把汽车尾气比作臭屁,说明她不喜欢山下的生活,不想去山下和汉人们一起生活,表明她不想离开山里,舍不得这片有着鸟语花香和鹿群做伴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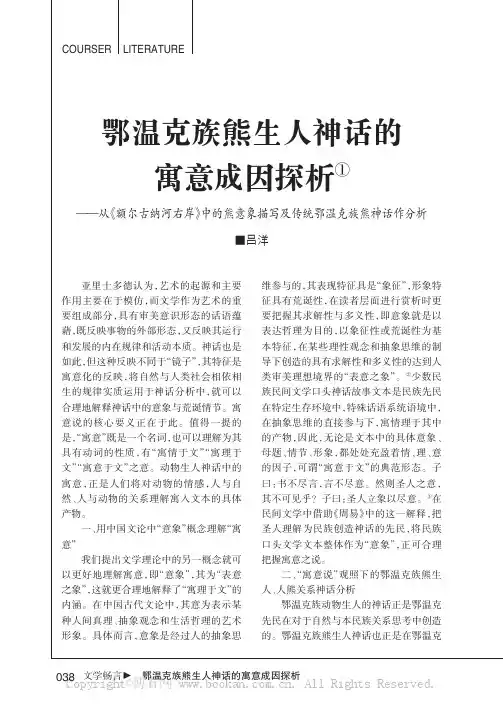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起源和主要作用主要在于模仿,而文学作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话语蕴藉,既反映事物的外部形态,又反映其运行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活动本质。
神话也是如此,但这种反映不同于“镜子”,其特征是寓意化的反映,将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依相生的规律实质运用于神话分析中,就可以合理地解释神话中的意象与荒诞情节。
寓意说的核心要义正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寓意”既是一个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其具有动词的性质,有“寓情于文”“寓理于文”“寓意于文”之意。
动物生人神话中的寓意,正是人们将对动物的情感,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理解寓入文本的具体产物。
一、用中国文论中“意象”概念理解“寓意”我们提出文学理论中的另一概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寓意,即“意象”,其为“表意之象”,这就更合理地解释了“寓理于文”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其意为表示某种人间真理、抽象观念和生活哲理的艺术形象。
具体而言,意象是经过人的抽象思维参与的,其表现特征具是“象征”,形象特征具有荒诞性,在读者层面进行赏析时更要把握其求解性与多义性,即意象就是以表达哲理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基本特征,在某些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制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
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口头神话故事文本是民族先民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特殊话语系统语境中,在抽象思维的直接参与下,寓情理于其中的产物,因此,无论是文本中的具体意象、母题、情节、形象,都处处充盈着情、理、意的因子,可谓“寓意于文”的典范形态。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③在民间文学中借助《周易》中的这一解释,把圣人理解为民族创造神话的先民,将民族口头文学文本整体作为“意象”,正可合理把握寓意之说。
二、“寓意说”观照下的鄂温克族熊生人、人熊关系神话分析鄂温克族动物生人的神话正是鄂温克先民在对于自然与本民族关系思考中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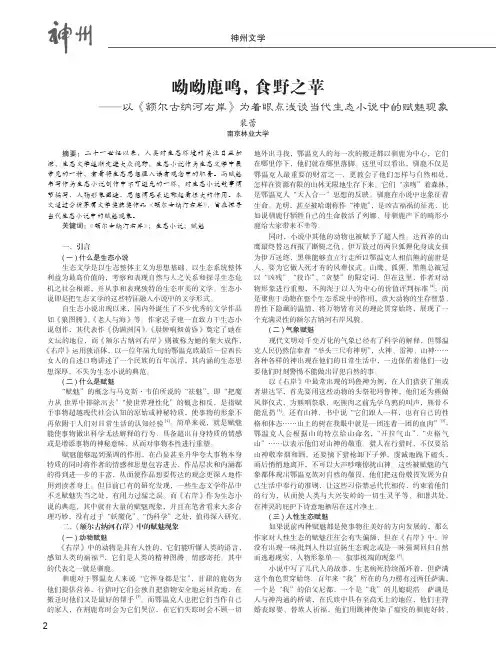
2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着眼点浅谈当代生态小说中的赋魅现象裴蕾南京林业大学摘要: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日益加深,生态文学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生态小说作为生态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有着将生态思想植入读者观念中的职责。
而赋魅书写作为生态小说创作中不可避免的一环,对生态小说故事情节描写、人物形象塑造、思想情感表达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旨在探寻当代生态小说中的赋魅现象。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小说;赋魅一、引言(一)什么是生态小说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
生态小说即是把生态文学的这些特征融入小说中的文学形式。
自生态小说出现以来,国内外诞生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狼图腾》、《老人与海》等。
作家迟子建一直致力于生态小说创作,其代表作《伪满洲国》、《晨钟响彻黄昏》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则被称为她的集大成作,《右岸》运用独语体,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沉浮,其内涵的生态思想深厚,不失为生态小说的典范。
(二)什么是赋魅“赋魅”的概念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即“把魔力从 世界中排除出去”“使世界理性化”的概念相反,是指赋予事物超越现代社会认知的原始或神秘特质,使事物的形象不再依附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认知经验[1]。
简单来说,就是赋魅能使事物做出科学无法解释的行为、具备超出自身特质的情感或是增添事物的神秘意味,从而对事物本性进行重塑。
赋魅能够起到强调的作用,在凸显甚至升华夸大事物本身特质的同时将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包容进去,作品层次和内涵都的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从而使作品想要传达的观念更深入地作用到读者身上。
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发现,一些生态文学作品中不乏赋魅失当之处,有用力过猛之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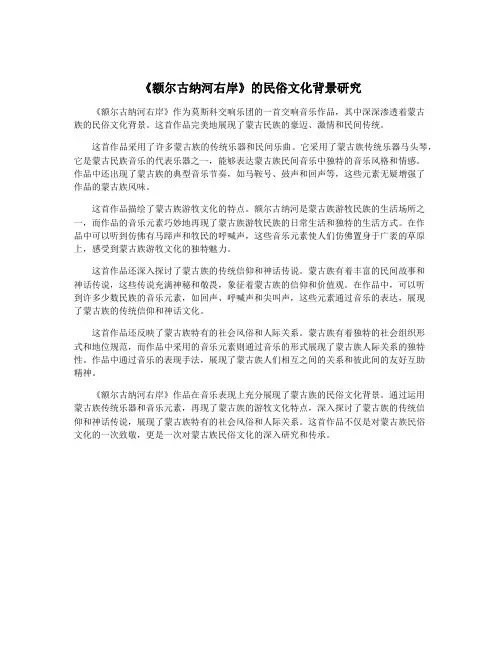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俗文化背景研究《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莫斯科交响乐团的一首交响音乐作品,其中深深渗透着蒙古族的民俗文化背景。
这首作品完美地展现了蒙古民族的豪迈、激情和民间传统。
这首作品采用了许多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和民间乐曲。
它采用了蒙古族传统乐器马头琴,它是蒙古民族音乐的代表乐器之一,能够表达蒙古族民间音乐中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
作品中还出现了蒙古族的典型音乐节奏,如马鞍号、鼓声和回声等,这些元素无疑增强了作品的蒙古族风味。
这首作品描绘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点。
额尔古纳河是蒙古族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所之一,而作品的音乐元素巧妙地再现了蒙古族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作品中可以听到仿佛有马蹄声和牧民的呼喊声,这些音乐元素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广袤的草原上,感受到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首作品还深入探讨了蒙古族的传统信仰和神话传说。
蒙古族有着丰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些传说充满神秘和敬畏,象征着蒙古族的信仰和价值观。
在作品中,可以听到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如回声、呼喊声和尖叫声,这些元素通过音乐的表达,展现了蒙古族的传统信仰和神话文化。
这首作品还反映了蒙古族特有的社会风俗和人际关系。
蒙古族有着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地位规范,而作品中采用的音乐元素则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了蒙古族人际关系的独特性。
作品中通过音乐的表现手法,展现了蒙古族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彼此间的友好互助精神。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品在音乐表现上充分展现了蒙古族的民俗文化背景。
通过运用蒙古族传统乐器和音乐元素,再现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特点,深入探讨了蒙古族的传统信仰和神话传说,展现了蒙古族特有的社会风俗和人际关系。
这首作品不仅是对蒙古族民俗文化的一次致敬,更是一次对蒙古族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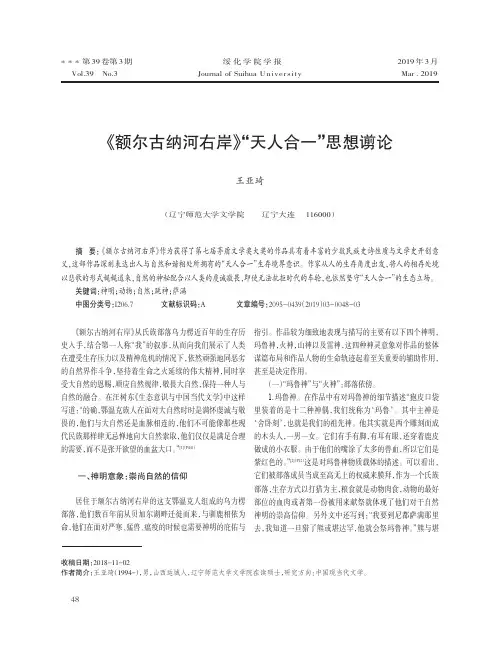
《额尔古纳河右岸》“天人合一”思想谫论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大奖的作品具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史诗性质与文学史开创意义,这部作品深刻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拥有的“天人合一”生存境界意识。
作家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将人的相存处境以悲歌的形式娓娓道来,自然的神秘配合以人类的虔诚敬畏,即使无法抗拒时代的车轮,也依然坚守“天人合一”的生态立场。
关键词:神明;动物;自然;跳神;萨满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9(2019)03-0048-03(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00)王亚琦∗∗∗第39卷第3期绥化学院学报2019年3月Vol.39No.3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Mar .2019收稿日期:2018-11-02作者简介:王亚琦(1994-),男,山西运城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额尔古纳河右岸》从氏族部落乌力楞近百年的生存历史入手,结合第一人称“我”的叙事,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遭受生存压力以及精神危机的情况下,依然顽强地同恶劣的自然界作斗争,坚持着生命之火延续的伟大精神,同时享受大自然的恩赐,顺应自然规律,敬畏大自然,保持一种人与自然的融合。
在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写道:“的确,鄂温克族人在面对大自然时时是满怀虔诚与敬畏的,他们与大自然还是血脉相连的,他们不可能像那些现代民族那样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索取,他们仅仅是满足合理的需要,而不是张开欲望的血盆大口。
”[1](P441)一、神明意象:崇尚自然的信仰居住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这支鄂温克人组成的乌力楞部落,他们数百年前从贝加尔湖畔迁徙而来,与驯鹿相依为命,他们在面对严寒、猛兽、瘟疫的时候也需要神明的庇佑与指引。
作品较为细致地表现与描写的主要有以下四个神明,玛鲁神,火神,山神以及雷神,这四种神灵意象对作品的整体谋篇布局和作品人物的生命轨迹起着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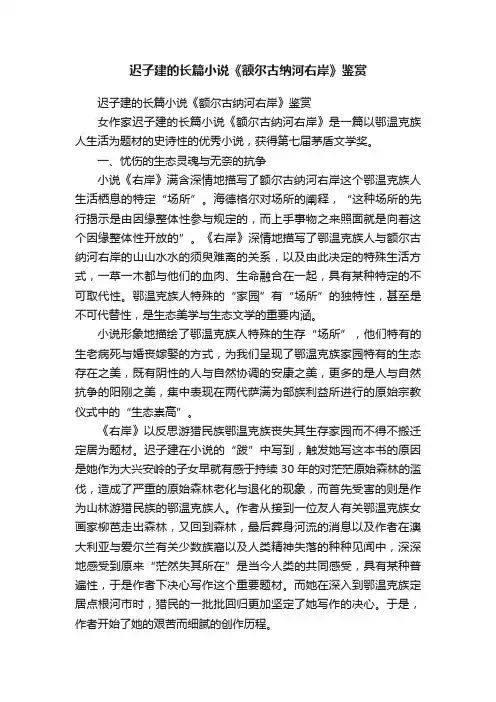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鉴赏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鉴赏女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篇以鄂温克族人生活为题材的史诗性的优秀小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一、忧伤的生态灵魂与无奈的抗争小说《右岸》满含深情地描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个鄂温克族人生活栖息的特定“场所”。
海德格尔对场所的阐释,“这种场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缘整体性参与规定的,而上手事物之来照面就是向着这个因缘整体性开放的”。
《右岸》深情地描写了鄂温克族人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山水水的须臾难离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特殊生活方式,一草一木都与他们的血肉、生命融合在一起,具有某种特定的不可取代性。
鄂温克族人特殊的“家园”有“场所”的独特性,甚至是不可代替性,是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重要内涵。
小说形象地描绘了鄂温克族人特殊的生存“场所”,他们特有的生老病死与婚丧嫁娶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鄂温克族家园特有的生态存在之美,既有阴性的人与自然协调的安康之美,更多的是人与自然抗争的阳刚之美,集中表现在两代萨满为部族利益所进行的原始宗教仪式中的“生态崇高”。
《右岸》以反思游猎民族鄂温克族丧失其生存家园而不得不搬迁定居为题材。
迟子建在小说的“跋”中写到,触发她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她作为大兴安岭的子女早就有感于持续30年的对茫茫原始森林的滥伐,造成了严重的原始森林老化与退化的现象,而首先受害的则是作为山林游猎民族的鄂温克族人。
作者从接到一位友人有关鄂温克族女画家柳芭走出森林,又回到森林,最后葬身河流的消息以及作者在澳大利亚与爱尔兰有关少数族裔以及人类精神失落的种种见闻中,深深地感受到原来“茫然失其所在”是当今人类的共同感受,具有某种普遍性,于是作者下决心写作这个重要题材。
而她在深入到鄂温克族定居点根河市时,猎民的一批批回归更加坚定了她写作的决心。
于是,作者开始了她的艰苦而细腻的创作历程。
作者采取史诗式的笔法,以一个90多岁的鄂温克族老奶奶、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口吻,讲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百年来波浪起伏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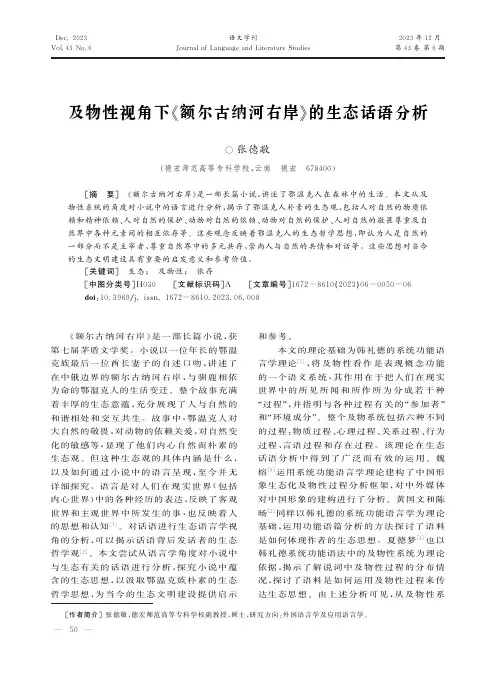
D e c .2023V o l .43N o .6语文学刊J o u r n a l o fL a n g u a ge a n dL i t e r a t u r eS t u d i e s 2023年12月第43卷第6期[作者简介]张德敬,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㊂及物性视角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话语分析ʻ张德敬(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德宏 678400)[摘 要]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鄂温克人在森林中的生活㊂本文从及物性系统的角度对小说中的语言进行分析,揭示了鄂温克人朴素的生态观,包括人对自然的物质依赖和精神依赖㊁人对自然的保护㊁动物对自然的依赖㊁动物对自然的保护㊁人对自然的敬畏尊重及自然界中各种元素间的相互依存等㊂这些观念反映着鄂温克人的生态哲学思想,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㊁尊重自然界中的多元共存㊁崇尚人与自然的共情和对话等㊂这些思想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㊂[关键词] 生态; 及物性; 依存[中图分类号]H 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23)06-0050-06 d o i :10.3969/j .i s s n .1672-8610.2023.06.008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㊂小说以一位年长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妻子的自述口吻,讲述了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变迁㊂整个故事充满着丰厚的生态意蕴,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交互共生㊂故事中,鄂温克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动物的依赖关爱,对自然变化的敏感等,显现了他们内心自然而朴素的生态观㊂但这种生态观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小说中的语言呈现,至今并无详细探究㊂语言是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反映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也反映着人的思想和认知[1]㊂对话语进行生态语言学视角的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背后发话者的生态哲学观[2]㊂本文尝试从语言学角度对小说中与生态有关的话语进行分析,探究小说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以汲取鄂温克族朴素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和参考㊂本文的理论基础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1],将及物性看作是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和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 过程 ,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 参加者 和 环境成分 ㊂整个及物系统包括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㊁心理过程㊁关系过程㊁行为过程㊁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㊂该理论在生态话语分析中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运用㊂魏榕[3]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建构了中国形象生态化及物性过程分析框架,对中外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进行了分析㊂黄国文和陈旸[2]同样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运用功能语篇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语料是如何体现作者的生态思想㊂夏德梦[4]也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系统为理论依据,揭示了解说词中及物性过程的分布情况,探讨了语料是如何运用及物性过程来传达生态思想㊂由上述分析可见,从及物性系统的角度来分析语料中蕴含的生态思想是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方法,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㊂本研究也将采用该分析方法,对‘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生态话语进行分析,探究鄂温克人的生态思想㊂一㊁理论介绍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m a t e r i a l p r o c e s s)㊁心理过程(m e n t a l p r o c e s s)㊁关系过程(r e l a t i o n a l p r o c e s s)㊁行为过程(b e h a v i o r a l p r o c e s s)㊁言语过程(v e r b a l p r o c e s s)和存在过程(e x i s t e n t i a l p r o c e s s)[1]㊂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情的过程,一般包含动作者和动作的目标,如在M y b r o t h e r b u i l t a l l t h e s eh o u s e s一句中,m y b r o t h e r为动作者,h o u s e s为目标,这一过程体现了动作者对客观世界的改造㊂心理过程是表示 感觉 反应 和 认知 等心理活动的过程㊂心理过程一般有两个参加者,包括心理活动的主体即 感觉者 和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如在H e l i k e s t h e m i l k 一句中,h e为心理活动的主体,具体的感觉或反应是l i k e,被感知的客体是m i l k㊂关系过程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分为归属和识别两大类,如在M a r y i s a t e a c h e r 一句中,t e a c h e r表示一种属性,M a r y则是属性的载体,整个句子是对载体属性㊁性质或价值的定性㊂行为过程指诸如呼吸㊁叹息㊁苦笑等生理活动过程,描述的是行为者的某个生理过程,如在S h ec r i e ds a d l y一句中,c r y为行为过程,s h e则是行为过程的参与者㊂言语过程是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通常包括言语者㊁受话者和言语内容,如在I s a i d t h a t y o u s h o u l dk e e p q u i e t一句中,言语者为 I ,受话者为 y o u ,言语内容为 y o u s h o u l dk e e pq u i e t ㊂存在过程表示的是有某物存在的过程,如T h e r e i s a b o o k o n t h e t a b l e一句中,b o o k 为存在物,o n t h e t a b l e则为存在的环境㊂二㊁‘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话语分析在精读小说的基础上,笔者对文中的生态话语进行提取,以及物性系统作为理论基础,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典型语句进行及物性标注,分析语料中的语言特征,揭示其中传达的生态观点㊂(一)人对自然的物质依赖对自然的物质依赖指的是鄂温克人从自然中获取基本生存资料,这种依赖主要通过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体现㊂物质过程体现的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关系过程体现的是自然资源对人的生存价值,如:(1)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2)黄昏时,我们在额尔古纳河上燃起篝火,吃烤鱼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3)我和列娜从小就跟着母亲学活计,熟皮子,熏肉干,做桦皮篓和桦皮船,缝狍皮靴子和手套 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4)鹿奶是清晨时流入我们身体的最甘甜的清泉㊂(关系过程:载体+属性+过程)第1㊁2和3句均为动作过程,展现了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依赖㊂ 坐 吃 做 缝 描述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四个动作的目标 狍皮褥子 烤鱼 熟皮子,熏肉干 桦皮篓和桦皮船 狍皮靴子和手套 说明自然资源是人类的食物来源和生活用品来源,强调了鄂温克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㊂第4句体现的是一种关系过程,强调了鹿奶对人的重要性,其中的 最甘甜 体现了这种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及鄂温克人对这种资源的珍惜㊂前三句展现了人利用自然求生存的过程,第四句描述的是一种客观关系,即动物资源对人的滋养,这种评价性陈述是对鹿奶价值的肯定,展现了人对鹿奶的依赖㊂在小说中,鄂温克人对自然的物质依赖主要通过上述两个角度呈现,即人对自然合理而充分的利用,以及人对自然资源价值的高度肯定和珍惜㊂鄂温克人内心的这种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引导他们合理㊁充分㊁平衡地利用自然资源㊂(二)人对自然的生活依赖对自然的生活依赖指的是鄂温克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的工具性依赖,如将驯鹿作为日常的搬运工具,以及将驯鹿㊁风㊁水等作为交流伙伴等,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对话㊂如:(5)行猎时,它们是猎人的好帮手,只要你把打到的猎物放到它身上,它就会独自把它们安全地运到营地㊂(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6)搬迁时,它们不仅负载着我们那些吃的和用的东西,妇女㊁孩子和年老体弱的人还要骑乘它,而它却不需要人过多的照应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心理过程:体验者+过程+现象)(7)我们用木棒敲击大树,游走在附近的驯鹿知道有人要役使它们,不一会儿就有六七头返回营地㊂我们选择了四头健壮的,分别骑了上去㊂(心理过程:体验者+过程+现象;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8)在我看来,风能听出我的病,流水能听出我的病,月光也能听出我的病㊂(心理过程:体验者+过程+现象)鄂温克人对自然的生活依赖主要通过物质过程㊁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体现㊂物质过程体现了鄂温克人在日常生活中对驯鹿的驱使,具体的发生场景包括打猎和搬家等,如第5句的 只要你把打到的猎物放到它身上,它就会独自把它们安全地运到营地 和第6句的 搬迁时,它们不仅负载着我们那些吃的和用的东西,妇女㊁孩子和年老体弱的人还要骑乘它 ,都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和场景展现了鄂温克人在日常生活中对驯鹿的依赖㊂第5句中的 行猎时,它们是猎人的好帮手 通过关系过程界定了驯鹿和猎人之间的关系,突显了驯鹿对猎人的价值㊂第7句中的 我们用木棒敲击大树,游走在附近的驯鹿知道有人要役使它们,不一会儿就有六七头返回营地 ,这一心理过程将驯鹿视为心理活动的主体,即感觉者,能够感觉并理解 木棒敲击大树 这一人类行为,反映了人与驯鹿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强调了驯鹿和人之间的依赖驱使是建立在和谐理解的关系之上㊂此外,第8句中的 风 流水 月光 等自然元素也被赋予了人的特性,具有了 听 的能力,能对人表现出深切的关照,能 听出我的病 ,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联系㊂(三)人对自然的精神依赖鄂温克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超出了物质和生活的层面㊂他们赋予了大自然灵性,在情感和精神层面与自然发生了联系,如:(9)柳沙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玛克辛姆呢,他一看到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㊂(行为过程:行为者+过程)(10)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㊂(心理过程:体验者+过程;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11)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㊂(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心理过程:体验者+过程)第9句是行为过程,表现的是与人的生理有关的活动㊂行为者为人,行为过程为 哭 ,所发生的环境条件为 月圆的日子 和 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 ,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情感㊂第10句前半句表示意愿,后半句表示关系过程,强调了我和星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㊂第11句也是关系过程,呈现了我和大山之间的关系,强调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以及基于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意愿,即我要在山里,死后也要回归大山,反映了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依赖和共存㊂(四)人类对自然的保护鄂温克人对自然的保护主要通过物质过程和言说过程体现㊂物质过程体现的是鄂温克人自身的所作所为对自然的关切保护,以及鄂温克人对破坏森林行为的反抗;言语过程呈现的是鄂温克人与生活在森林之外的人之间的对话,通过这种形式强调了鄂温克人的生态观,如:(12)一个地方的灰鼠打稀少了,我们就要搬到下一个地方,所以这时每隔三四天就要换一个地方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13)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㊂(言语过程:言说者+言说内容+受话者)(14)刘博文说,马粪包看到空着进山的运材车时还没什么,一旦看到满载原木的长条卡车轰隆隆驶过,他的情绪就会激动 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举起猎枪,对着运材车的轮胎就是一顿扫射㊂(行为过程:行为者+过程;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第12句为动作过程,表现了鄂温克人在打猎的同时对动物的保护,展现了较强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㊂第13句和14句通过言语过程展现了鄂温克人和森林之外的 他 具有不同的生态意识㊂鄂温克人将自己和驯鹿定位为 我们 ,用 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 描绘了 我们 与森林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㊂第14句中用 看到 这一心理过程,凸现了心理活动的主体在看到森林遭到破坏之后的生理反应,即 情绪就会激动 ,以及随之带来的行为反应,即 举起猎枪和对着运材车的轮胎一顿扫射 ,这种感觉和反应体现了鄂温克人对森林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破坏森林行为的反抗㊂(五)动物对自然的依赖和保护动物对自然的依赖和保护是动物所展现出来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是通过鄂温克人的视角观察并表达出来的,属于鄂温克人生态思想的一部分㊂如:(15)它们总是自己寻找食物,森林就是它们的粮仓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16)它们渴了夏季喝河水,冬季则吃雪㊂(行为过程:行为者+过程)(17)它们吃东西很爱惜,它们从草地走过,是一边行走一边轻轻地啃着青草的,所以那草地总是毫发未损的样子,该绿还是绿的㊂它们吃桦树和柳树的叶子,也是啃几口就离开,那树依然枝叶茂盛㊂(行为过程:行为者+过程;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第15句通过关系过程表明了森林对动物的价值和意义,突显了动物对森林的依赖㊂第16句为行为过程,反映了动物对自然的依赖㊂第17句通过行为过程描绘了动物吃草的方式,即 轻轻地啃着青草 ,表现了对自然的爱护和珍惜,又通过关系过程呈现了动物爱护自然所带来的 依然枝叶茂盛 的结果㊂(六)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鄂温克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来自于对自然强大力量的敬畏和对自然变化的敏感㊂他们长期生活在山林里,非常熟悉那里的自然,熟悉之后就会建立一种互相的信赖和敬畏㊂如:(18)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㊂(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19)北部森林的秋天,就像一个脸皮薄的人,只要秋风多说了它几句,它就会沉下脸,抬腿就走㊂(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行为过程:行为者+过程)(20)妮浩说有一次她捉来一只黄蝴蝶,说是要把它放进自己的肚子里,让它在里面飞,跟自己玩耍㊂(言语过程:言说者+言说内容+受话者)(21)猎人行猎时,看见刻有白那查山神的树,不但要给它敬奉烟和酒,还要摘枪卸弹,跪下磕头,祈求山神保佑㊂(行为过程:行为者+过程;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22)坤德对我说,走夜路不能大声说话,会惊着山神的㊂(言语过程:言说者+言说内容+受话者)鄂温克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是通过将自然拟人化和神化来体现的㊂拟人的过程也是赋予自然以人的动作和情感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鄂温克人将自然界中的各种元素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实体,它们有感情,有思想,可交流㊂上例中的 红着脸 黄着脸 脸皮薄 沉下脸 抬腿就走 跟自己玩耍 都体现了鄂温克人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将自然界中的元素视为有情感和可交流的实体㊂(七)自然界中各种元素间的相互依存在鄂温克人看来,除了人和其它动物之外,自然界中的其它元素之间也存在着动态或静态的依存和转化㊂如:(23)落在沟谷里的叶子会化作泥,落在林地的叶子会成为蚂蚁的伞,而落在流水中的叶子就成了游鱼,顺水而去了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24)山能生水,水能养山㊂山水相连,天地永存㊂(物质过程:动作者+过程+承受者;关系过程:载体+过程+属性)第23和24句通过物质过程呈现了自然界各种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又通过关系过程从静态的角度呈现了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展现了 天人合一 的思想,把 天㊁地㊁人 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了人类㊁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关系㊂三㊁‘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思想分析(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从上述分析可知,鄂温克人从未表现出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意图和想法,而是在顺应自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寻求生存㊂ 走夜路不能大声说话,会惊着山神的 林克是被雷神取走的 北部森林的秋天,就像一个脸皮薄的人,只要秋风多说了它几句,它就会沉下脸,抬腿就走 等话语表明,在鄂温克人的意识中,人不是世界的主宰,不是世界的中心㊂这种以生物为中心的平等思想认为,所有生物和实体都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和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都有自己的情感和认知㊂鄂温克人通过使用不同的及物性过程将非人类生命体拟人化,以承认人类㊁非人类生命体以及非生命体在自然界中的平等地位㊂(二)多种元素的和谐共生多元 是 和 具备真正内涵与意义的前提㊂多元和谐反映的是一种共生的状态,这种状态蕴含在 交互共生 的过程之中[5]㊂在小说的具体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层面的和谐共生㊂首先是人类和动物资源之间的交互共生㊂人类依赖动物获取食物及日常其它所需,同时,动物也依赖人的相对保护获得可持续生存,如猎人打猎时从不多打,够吃不贪㊂其次是动物资源和森林资源的交互共生㊂森林是动物的粮仓,为动物的生存提供栖息地,同时,动物也会保护森林资源,如 它们从草地走过,是一边行走一边轻轻地啃着青草的,所以那草地总是毫发未损的样子,该绿还是绿的 ㊂此外,人类和森林资源之间也是相互依赖,交互共生㊂森林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条件㊁燃料㊁制作日常用具的材料和食物来源等㊂同时,人类也极力保护着森林,具体体现在 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 一旦看到满载原木的长条卡车轰隆隆驶过,他的情绪就会激动 等描述之中㊂最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则体现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如 达西眼睛不好,所以肝脏基本都会分配给他 ㊂总之,人类依靠动物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动物也要依靠人类的保护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动物依靠森林资源获得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依靠动物的保护;人类从森林中获取栖息地和生活资料,森林资源的存在和可持续发展也依赖人类的保护和适度利用;人与人之间也同样需要相互依赖,共同克服困难㊂(三)人与自然的共情和对话多种元素的共生体现的是物质层面的相互依赖,而多种元素之间的共情则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理解和尊重㊂共情指在理性基础上认识到他者的独立性与独特性,通过批判性视角审视自身与他者的客观处境及联系,虽然这种审视的出发点是情感,但是最终被延伸至与情感有关的几乎所有现实情境的各个角落[6]㊂在小说中,自然世界被赋予了人性的特征,它们的存在有意识,有意志,有权威和有力量,是可以对话和交流的对象㊂对话的目的是为了尊重他者的主体性,只有对话,自我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才能发生紧密联系,同时与他人思想融合,充分保留他人思想的独立性㊂所有的对话的主体都是地位平等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存在㊂对话就是为了消除独语霸权,所有主体都能发出声音,而且每个主体都有独立的不可取代的价值[7]㊂鄂温克人将自然界中的各种元素都进行了拟人化,将它们视作与人类平等的主体,具有人的情感和意识,并在此基础上与自然进行对话,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平等㊁共情和对话㊂四、结语本文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长篇小说为语料来源,以及物性理论为基础,探究了小说中传达的生态观点及背后的生态思想㊂整部小说富有浓厚的生态意蕴,呈现了人类㊁动物㊁森林及其它自然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交互共存,体现了鄂温克人尊重自然㊁与自然对话㊁与自然共情的生态思想㊂这种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㊂任何一种观念和思想的形成都有深刻复杂的过程㊂鄂温克人对自然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㊁文化㊁历史等因素,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话题㊂ʌ参考文献ɔ[1]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2]黄国文,陈旸.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J].外国语文,2017(2).[3]魏榕.中外媒体中国形象的生态话语对比研究[J].现代外语,2022(3).[4]夏德梦.及物性系统视角下‘完美星球“解说词的生态话语分析[J].文化综合,2022(31).[5]何伟,魏榕.多元和谐,交互共生 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之生态哲学观建构[J].外语学刊,2018(6). [6]李克,朱宏宇.共情修辞视域下的国家外部认同建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2).[7]张素玫.巴赫金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A nE c o l i n g u i s t i c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R i g h tB a n ko f A r g u nR i v e rZ h a n g D e j i n g(D e h o n g N o r m a l C o l l e g e,D e h o n g,Y u n n a n,678400)A b s t r a c t:T h eR i g h tB a n ko f A r g u nR i v e r i san o v e l a b o u tE w e n k i s l i f e i nf o r e s t s.B y m e a n so f t r a n s i t i v i t y a n a l y s i so fv e r b s,t h e p r e s e n t t h e s i sa t t e m p t s t or e v e a l t h eo r i g i n a l e c o l o g i c a lb e l i e f sh e l db y E w e n k i,i n c l u d i n g t h e i n t e r d e p e n d e n c eb e t w e e nh u m a nb e i n g s,a n i m a l s,f o r e s t r e s o u r c e s a n d s oo n.S u c h b e l i e f s a r eb e l i e v e d t o a r i s e f r o mt h e i r e c o l o g i c a l p h i l o s o p h y,s u c ha sh u m a nb e i n g s a r e j u s t a p a r t o f t h e n a t u r e,a l l e l e m e n t s i nn a t u r e s h o u l d r e s p e c t e a c ho t h e r a n d a l l e l e m e n t s s h o u l d c o-e x i s t b a s e do n e m p a-t h y.K e y w o r d s:e c o l o g y;t r a n s i t i v i t y;i n t e r-d e p e n d e n c e。
《额尔古纳河右岸》阅读感想每个人的童年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幻想: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中。
在那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轻柔地洒在脸上,唤醒的不仅是双眼,还有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母亲忙碌的身影在厨房中若隐若现,弟弟妹妹们还在甜甜的梦乡中沉睡着,窗外的鸟儿欢快地唱着歌,一切都显得那么温馨和美好。
在这个童话世界里,父亲早已和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一同出门打猎,而女性成员则在营地中照料驯鹿,为它们锯下鹿茸。
驯鹿是这个部族最亲近的朋友,它们白天会自己外出寻找山林间的苔藓作为食物,晚上又会乖乖地回到营地。
它们不仅是部族迁徙渔猎的运输工具,也是衣食的重要来源。
在这里,人们信奉着玛鲁神,将猎杀的动物首先供奉给玛鲁神,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然后自己才可以开始享用。
萨满则是部族中人与神之间的使者,他们拥有着神奇的魔法,可以通过祭祀和祷告来治病救人,但同时也需要以损失自己至亲的方式,以命换命。
部族之间相互通婚,男女之间的爱情简单而热烈,朴素而长久。
当有男女步入婚姻的殿堂时,他们会在河边架起篝火,所有人围绕在篝火旁,一起跳舞、唱歌,分享着喜悦。
皎洁的月光洒在额尔古纳河上,泛起点点白鳞,鱼儿在水中跳跃,微风拂过脸庞,就像爱人的手一样轻柔。
而驯鹿则带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来到河边饮水,小驯鹿在母驯鹿的腿边蹭来蹭去,母驯鹿温柔地舔着小驯鹿的脸颊,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美好的画面啊。
然而,当我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时,却常常感到一阵深深的遗憾。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去体验那个充满神秘和浪漫的童话世界。
但这本书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能够透过文字,窥视到那个曾经存在过的世界。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民族的百年历史。
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九十多岁的鄂温克女人,她用自己的口吻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民族的兴衰与变迁。
在她的叙述中,我们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遥远的过去,见证了这个民族的兴衰与变迁。
部族的迁徙、与其他部族的战争、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消亡,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生命的无常。
透过民俗事象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地域情结【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充满地域情结的文学作品,通过民俗事象展现了特定地区的文化特色。
本文从民俗事象在小说中的表现、民俗文化对地域情结的影响、地域情结在小说中的体现等方面展开讨论。
民俗事象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它深化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并赋予作品独特的地域色彩。
通过分析小说中的民俗事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域情结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小说通过民俗事象展现地域特色的方式。
通过对民俗事象的审视,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额尔古纳河右岸》所蕴含的深厚地域情结,从而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这部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地域文化。
【关键词】文学作品、地域文化、民俗事象、《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域情结、民俗文化、影响、体现、深化、理解、价值、意义、重要性、地域特色1. 引言1.1 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域文化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元素,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地域情感。
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借助地域文化的元素来构建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从而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地域情感。
地域文化不仅是作家灵感的源泉,也是作品中展现不同地域特色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
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描写和表现,文学作品能够传递出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感悟和理解,引发读者对地域的共鸣和思考。
地域文化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地域文化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而文学作品又通过对地域文化的再现和诠释,为地域文化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生命力。
2. 正文2.1 民俗事象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表现民俗事象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表现包括对当地传统节日、习俗和风土人情的描写。
小说中通过描绘当地村民在传统节日中的活动、服饰、食物等细节,展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独特的民俗风情。
农历新年、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被生动地描绘出来,让读者感受到小说背景地区浓厚的节日氛围。
小说中还通过描写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饮食习惯、传统手工艺、信仰和习俗等方面,展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独特的文化特色。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文素材《额尔古纳河右岸作文素材》素材一《驯鹿的故事》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驯鹿可是个神奇的存在。
那些驯鹿啊,就像是这片土地上自由的精灵。
我有一次亲眼看到一位鄂温克族的老人和他的驯鹿。
那老人年过半百,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可眼睛里透着精明与和蔼。
他的驯鹿特别漂亮,鹿角就像书上描写的珊瑚一样,枝枝叉叉的,还泛着一种暖棕色的光泽。
那驯鹿啊,一点也不怕人。
我走近的时候,它正慢悠悠地嚼着苔藓,厚厚的苔藓被它嚼得嘎吱嘎吱响。
我好奇地伸手想摸一下它的毛,可又有点害怕。
老人看出来了,笑着说,“莫怕,这驯鹿温顺着嘞。
”我鼓起勇气轻轻碰到它的背,那毛既厚又软,挨着皮肤的地方还特别暖和。
你要是在旁边看啊,会觉得驯鹿和老人就像一对相识很久的老友,驯鹿依赖老人的照顾,老人也把驯鹿当作生活的伙伴,这画面就像一幅古老而又质朴的画。
素材二《鄂温克族的传统住居》鄂温克族的传统住居绝对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一大特色。
那就是“撮罗子”。
有一回我跟着一个鄂温克族小伙子去看他家的撮罗子。
刚走到那里,感觉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小窝棚。
它是用木杆搭成的,外面围着桦树皮或者兽皮,看起来简单又结实。
撮罗子里住着一代又一代的鄂温克族人。
小伙子指着周围,告诉我这里面不同的角落放置着不同的东西。
进门的左边是堆放杂物的地方,什么打猎用的工具啦,缝制衣服的针线什么的都在那边。
中间有个小火炉,这个火炉可关键了,既用来做饭又可以取暖。
到了冬天,外面大雪纷飞,一家人围着火炉,吃着烤肉,听着外面风声呼啸,那感觉既惊险又温馨。
我在撮罗子里待着的时候,阳光透过顶部的小孔洒下一些斑驳的影子,就像时光在那里停滞了,静谧又美好。
素材三《额尔古纳河的黄昏》额尔古纳河的黄昏那简直是美如画卷。
我有一次就在河边待到黄昏时分。
太阳渐渐西斜,整个河流像被镀上了一层金箔。
河面上波光粼粼的,犹如无数细碎的金子在跳舞。
两岸的草地也变得金黄一片,风微微吹过,草就像起伏的海浪。
我看到一只小狐狸从河边的草丛里探出脑袋,它可能也在欣赏这黄昏美景。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俗文化背景研究《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由蒋子龙执导,姜文、姜宇星、尤勇等演员主演的电影,该电影讲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牧民们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守护。
影片中融入了大量的民俗文化元素,展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独特风情和传统习俗。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探究《额尔古纳河右岸》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额尔古纳河右岸位于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是蒙古族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民俗文化受到蒙古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蒙古族是一个勇敢、豪迈的民族,他们崇尚自由和独立,喜欢游牧生活,对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人们以牧民为主,他们过着简单而朴实的生活,依靠牛羊为生,以草原为家,对祖先的传统和信仰有着深厚的敬畏之情。
影片中展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俗文化,我们可以看到牧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和传统。
在片中出现了蒙古族传统的射箭比赛,射箭是蒙古族的传统运动项目,被誉为“蒙古三绝”之一,展现了蒙古族人的勇敢和豪迈;还有片中展现了蒙古族人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和歌曲,这些舞蹈和歌曲反映了蒙古族人的生活情感和生活态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还有许多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和仪式。
片中展现了牧民们的婚礼仪式,这是蒙古族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代表了生活的新开始和家族传承的延续。
而影片中还展现了牧民们的祭祀活动,祭祀在蒙古族文化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人们通过祭祀仪式来祈求风调雨顺、牛羊平安和家庭幸福。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和传统外,《额尔古纳河右岸》还展现了蒙古族人对自然的崇敬和对祖先的敬畏。
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牧民们对自然界的景色和动植物的敬畏之情,他们把蒙古族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影片的结尾,也展现了祖先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这体现了蒙古族人对祖先先辈的敬仰和传统文化的重视。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展现蒙古族人的民俗文化,成功地捕捉到了蒙古族生活的细节和特色,展现了蒙古族人对自然的崇敬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额而古纳河的右岸读后感《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述鄂温克族人生活的小说,作者迟子建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深入探索了这一古老民族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首先,这部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鄂温克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描述。
作者通过描述他们的狩猎、饲养驯鹿、制作毛皮等生活细节,以及祭祀、婚嫁等文化习俗,使我对这个民族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些描述不仅展现了鄂温克族的生活方式,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其中,主人公的坚强和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虽然在生活中遭遇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信仰。
这种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此外,小说中的自然描写也非常出色。
作者通过对额尔古纳河两岸的风景、气候等自然景观的描述,营造出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世界。
这些描写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也让我对自然有了更加深刻的敬畏之情。
最后,这部小说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通过描写鄂温克族人的日常生活,作者展现了生活中的美好和艰辛,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同时,我也认识到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挫折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态度,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信仰,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实现自己的价值。
总之,《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小说。
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和文化,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一古老民族的内心世界。
同时,它也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我相信这部小说将会成为我内心深处永远珍藏的一份宝贵财富。
DOI:10.19392/j.cnki.1671 7341.202008207透过民俗事象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地域情结姚冬青 姜 波齐齐哈尔大学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摘 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以家乡黑土地为创作对象进行写作的作品。
在作品里她写了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活的人们所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民俗事象。
黑土地的地域特色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通过这些民俗事象得到体现,而这也是迟子建所要表达内容的关注点之一。
本文通过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民俗事象尤其是萨满跳神,来探索其中所蕴含的地域情结,以及地域对人的影响和带给人们的思考。
关键词:民俗事象;《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域情结 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
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搬迁、游猎。
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尽管人口式微,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备尝艰辛。
他们的生存环境几经变化,日寇侵略、“文革”、还有现代文明的到来,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依然保有大爱,但又有着大痛。
他们在命运面前殊死抗争,却又无奈地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
然而,这个过程中鄂温克这个具有独特民风却又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却从头到尾一以贯之,不管是爱恨情仇,还是生死传奇。
[1]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关于鄂温克族生活环境作了介绍,展示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有当地延续下来的传统习俗。
在这些习俗里有关于驯鹿的,有关于凿冰捕鱼的,有训鹰的,还有关于萨满跳神的,等等。
在迟子建的笔下把这些民俗事象描写得很细致,从这具体过程中却透露出对于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对于家乡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一种关爱与忧虑,对于自然人性流露出的赞美,同时也透露着对于生存状态的一种焦虑与思考。
一、民俗事象的展现在自己生存环境中形成的世俗民情等地区性的文化生存形态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们不知不觉接受并实践,久而久之形成传统,它们同样影响着生存于其间的人们的思维。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的代表作,它所包含的动物意象富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其中驯鹿、马、鹰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动物意象,它们体现了迟子建对传统文明的追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这一主要文化内涵。
笔者将结合意象批评及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探讨这些意象是如何体现迟子建的创作思想的。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动物意象一、引言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篇小说中,迟子建化身为一个九十多岁的鄂温克女人,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用一天的时间叙述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悠长而又沧桑的历史。
翻开这部小说,读者很容易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个生机盎然、异彩纷呈的动物世界。
它们之中,既有温顺而充满灵性的驯鹿,又有凶残且极具攻击性的野狼;既有神圣而又令人恐惧的黑熊,又有勇猛且富有人性的山鹰……它们是这片具有传奇色彩的土地的一部分,与人一样有灵性,有呼吸。
作者赋予了它们种种的人文历史内涵,以寄托自己对社会、对历史及人类的思考和探求。
但是对于这些富含深意的动物意象,目前学界却关注甚少。
笔者在此力求弥补学界的这一不足,选取小说中作者着墨较多、着重描写的动物意象,以它们为视角,借鉴神话—原型的批评方法,揭示出这些意象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及至于整个主题的意义。
二、对传统文明的追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然而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商业气息的入侵,人类赖以生存的和谐家园已遭到严重破坏,人性也遭到严重的异化、扭曲。
面对着这渐行渐远的传统文明,迟子建用她那饱含着脉脉温情的笔对它进行了深情的赞美和真挚的呼唤。
这种呼唤,不仅是通过人表现出来,在动物身上,也可见一斑。
(一)对自然的崇拜与信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着力表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自然万物的平等相处,自然在她笔下既是人物灵魂栖居的自然,又是被赋予人格情态的自然。
如果说把动物作为自然的代表,那么这种情感在它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驯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驯鹿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人们专门放养的一种动物,作者在书中对它作了专门介绍。
它“有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①喜食苔藓,善于在深山密林、沼泽或者是深雪中行走,被人们誉为“林海之舟”。
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把驯鹿当做自己的祖先、守护神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它在小说中一出场便被染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尼都萨满和我父亲一点儿也不像亲兄弟。
他们很少在一起说话,狩猎时也从不结伴而行……父亲爱说话,而尼都萨满哪怕是召集乌力楞的人商议事情,说出的话也不过是只言片语。
据说只有我出生那天,尼都萨满因为前一天梦见了一只白色的小鹿来到我们的营地,对我的降生就表现出无比的欣喜,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
这段话中的尼都萨满仅仅因为在“我”出生的前一天梦见了一头鹿,原本和父亲很少来往的他竟然主动来到营地为“我”庆生,很少说话的他竟然“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这足以证明驯鹿作为一种吉祥物在鄂温克人们心中的分量。
不仅如此,驯鹿还是十分有灵性的动物,它和人一样有情感,明事理。
如书中提到的一只母鹿,在知道自己的小鹿仔代替生病的列娜死去后,“它一直低头望着曾拴着鹿仔的树根,眼睛里充满了哀伤。
从那以后,原本奶汁最旺盛的它奶水就枯竭了”。
①一次部落搬迁时,“它自动走到列娜身边,温顺地俯下身。
列娜什么也没想,顺手就把鞍桥搭在了它身上,骑上去”。
①后来列娜骑在这匹驯鹿身上时因瞌睡而掉到了地上,冻死了。
在列娜追随那只小驯鹿去了那个世界时,母驯鹿又重新有了丰富的奶汁。
这样的驯鹿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代人死,也可以取走人的性命。
鄂温克人对身上所存在的这种非凡的神力是深信不疑的。
他们最尊敬的祖先神——玛鲁王是骑在驯鹿身上的;萨满为了使法器有鹿的灵魂力量,常以鹿血荣法器之魂;婴儿患重病请萨满时,必备黑白驯鹿各一只,杀之,以供萨满到天界接回乌麦时骑用……和驯鹿一样,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在鄂温克人的眼中都具有灵魂,具有神力,所以他们敬畏自然中的任何生灵。
这是这种原始的图腾信仰,使得鄂温克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是十分关注和爱护的,所以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总是那么诗情画意,宛若世外桃源。
对于这渐行渐远的和谐文化,迟子建用她手中的笔一一将之拾起,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无限向往。
(二)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前面所说的对自然的关爱之情,使得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大自然、大森林不仅是鄂温克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主要载体,而且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与自然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也正是前面所说的对自然的崇敬之情,使得鄂温克人相信,大自然、大森林的动物与植物充满了灵性与神性,它们和人类共同谱写着一曲歌颂和谐生命的赞歌。
作为这曲赞歌中一个动人的音符,动物们也向人们传达着来自这个和谐世界的声音。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动物是具有人性的,他们能听懂人类的语言,感知人类的祸福。
小说中驯鹿仿佛不是一只动物,而是一个有思想、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
它会根据现场判断事情的经过和性质,它会对如何处理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它会为身边人的离去表达自己的哀思。
对这样有人性的驯鹿,人们也是平等对待,驯鹿和人之间建立了浓厚的情谊。
小说中在描写驯鹿所遭遇的一场瘟疫时,把这种情谊展现得特别真挚、感人:尼都萨满的脸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塌陷了。
他黯然无神地穿戴上神衣、神帽、神裙和神裤,为挽救驯鹿而开始了跳神……他足足跳了七八个小时,双脚已经把希楞柱的一块地踏出了一个大坑,他就栽倒在那个坑里。
他倒在坑里后毫无声息,不过没有多久,一阵“呜哇呜哇”的哭声响了起来。
从尼都萨满的哭声里,我们明白驯鹿在劫难逃了。
那场瘟疫持续了近两个月……达西一看到我们在埋葬驯鹿,就“呜噜噜”地叫,叫得泪水横流。
没人理会他的泪水,因为人人的心底都淤积着泪水。
这段文字描写的场面是十分感人的。
在驯鹿遭受瘟疫面临死亡时,人们表现的是那样的难过与痛苦。
尼都萨满仿佛被击垮一般,“在这场瘟疫中彻底苍老了”,“原本就不爱讲话的他,更加沉默了”。
①而平常看似铁心肠的达西在面对死去的驯鹿时,也是那样的悲痛,总是不自主地号啕大哭。
试想鄂温克人若不是把驯鹿当做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不是把驯鹿当做自己的亲人对待,情又何以至此?对人与驯鹿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情谊,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一个动物通人性,把动物当人对待的民族,如何能不与自然和谐相处?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迟子建在对传统文明中的人性之美、自然之美尽情赞美时,对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则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她往往调动一切因素来揭露现实的罪恶。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从“马”这一动物意象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迟子建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的驳斥与质疑。
在大兴安岭一带生活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是不使用马的。
小说中鄂温克人所拥有的第一匹马是坤得从俄罗斯人手中换来的。
第二次拥有的马是从日本人手中得来的。
日本上尉吉田骑着战马来到了他们的部落,他不相信尼都萨满具有神力,于是就和尼都萨满打赌。
如果尼都萨满跳神让吉田的伤口愈合,吉田就得把他的战马当牺牲品,让它死去。
结果尼都萨满跳完神,吉田的伤口已经愈合,而他的战马也悄然死去。
吉田大为震惊,走时留下了另外的两匹战马。
达西很喜欢这两匹马,而依芙琳却说:“既然来到我们乌力楞的第一匹马没有给我们带来幸运,这两匹日本人留下的马只会带来灾祸。
”①果然,依芙琳的话应验了。
这匹马导致了拉吉达的死亡。
后来,这匹马也给拉吉达的弟弟拉吉米带来了灾难,致使他终身残疾。
正因为马给他们带来如此深的伤害,所以后来一个马贩子“带来了四匹马,想要跟我们换两只驯鹿。
我们没有跟他做这笔交易。
我们不需要马,马给我们带来了痛苦的回忆”。
①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马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相传为文化肇始的河图洛书,是由白马驮经驮来外来文化之滋润;《吕氏春秋》中有“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之句;曹操亦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叹。
但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却把它视为一种不祥之物,无疑是有意为之,富含深意。
作为外来物的马,就像是入侵的现代文明一样,带给鄂温克人的不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而是对他们原有文明的一种破坏,是一种灾难。
因此从“马”这个意象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驳斥。
四、结语在中国众多的作家中,迟子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游离于任何文学流派、文学群体之外,她总是用她那只笔执著地书写着那个生存在边缘地带的古老民族的传奇历史,吟唱着他们的传奇人生,呼唤着“天人合一”的和谐世界的到来。
而《额尔古纳河右岸》所描写的动物,无论是与人们生死相存的驯鹿、给人们带来灾难的马匹,还是勇猛顽强、知恩图报的山鹰,我们亦能从其身上体会到迟子建的创作理念。
注释①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17,17,30,46,204.参考文献[1]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2] 迟子建.我伴我走[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3] 孟慧英.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0.[4]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 周景雷.挽歌从历史密林中升起——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j].当代作家评论,2006(04).[6] 单艳红.迟子建作品动物意象浅析[j].当代文坛,2004(01).(作者单位:深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