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
- 格式:ppt
- 大小:39.0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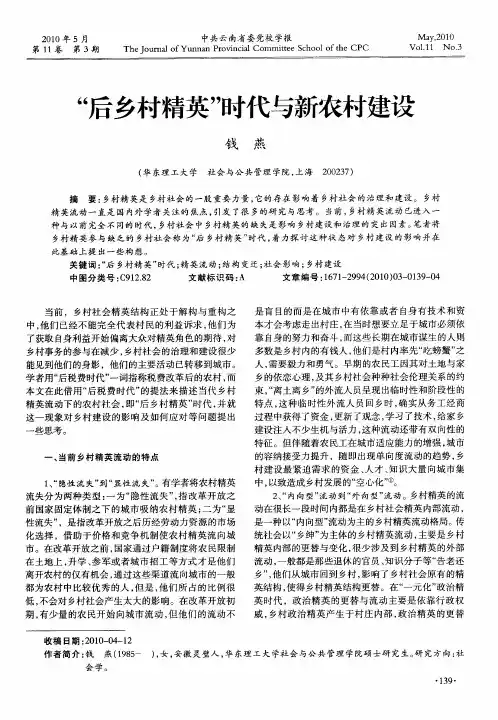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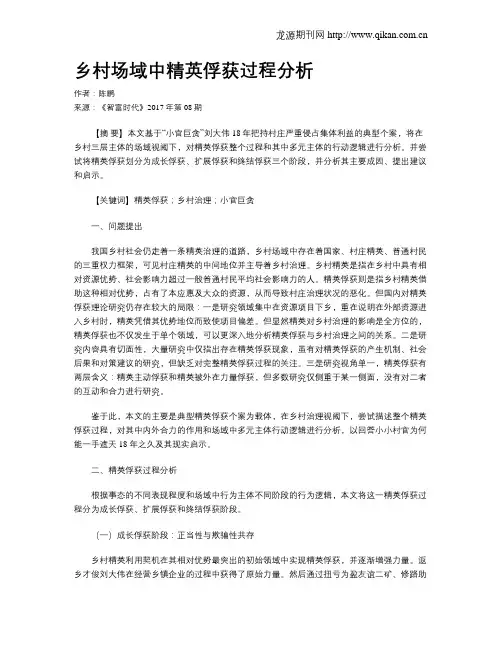
乡村场域中精英俘获过程分析作者:陈鹏来源:《智富时代》2017年第08期【摘要】本文基于“小官巨贪”刘大伟18年把持村庄严重侵占集体利益的典型个案,将在乡村三层主体的场域视阈下,对精英俘获整个过程和其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
并尝试将精英俘获划分为成长俘获、扩展俘获和终结俘获三个阶段,并分析其主要成因、提出建议和启示。
【关键词】精英俘获;乡村治理;小官巨贪一、问题提出我国乡村社会仍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乡村场域中存在着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三重权力框架,可见村庄精英的中间地位并主导着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指在乡村中具有相对资源优势、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普通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人。
精英俘获则是指乡村精英借助这种相对优势,占有了本应惠及大众的资源,从而导致村庄治理状况的恶化。
但国内对精英俘获理论研究仍存在较大的局限:一是研究领域集中在资源项目下乡,重在说明在外部资源进入乡村时,精英凭借其优势地位而致使项目偏差。
但显然精英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精英俘获也不仅发生于单个领域,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精英俘获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
二是研究内容具有切面性,大量研究中仅指出存在精英俘获现象,虽有对精英俘获的产生机制、社会后果和对策建议的研究,但缺乏对完整精英俘获过程的关注。
三是研究视角单一,精英俘获有两层含义:精英主动俘获和精英被外在力量俘获,但多数研究仅侧重于某一侧面,没有对二者的互动和合力进行研究。
鉴于此,本文的主要是典型精英俘获个案为载体,在乡村治理视阈下,尝试描述整个精英俘获过程,对其中内外合力的作用和场域中多元主体行动逻辑进行分析,以回答小小村官为何能一手遮天18年之久及其现实启示。
二、精英俘获过程分析根据事态的不同表现程度和场域中行为主体不同阶段的行为逻辑,本文将这一精英俘获过程分为成长俘获、扩展俘获和终结俘获阶段。
(一)成长俘获阶段:正当性与欺骗性共存乡村精英利用契机在其相对优势最突出的初始领域中实现精英俘获,并逐渐增强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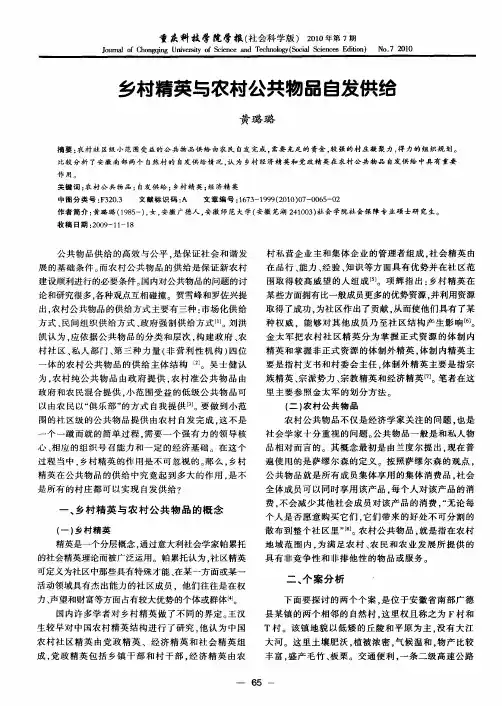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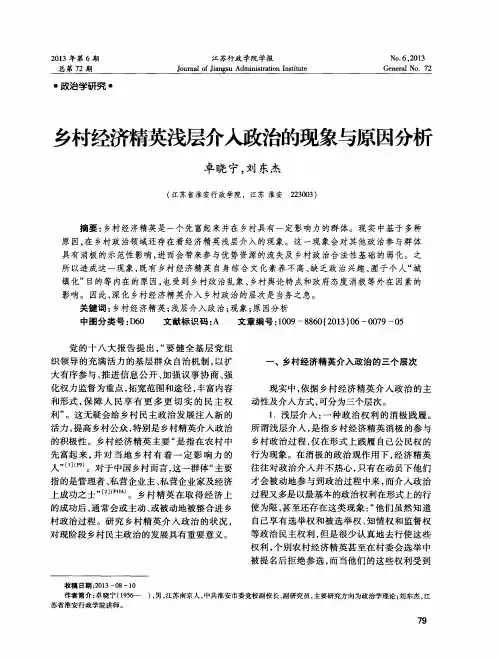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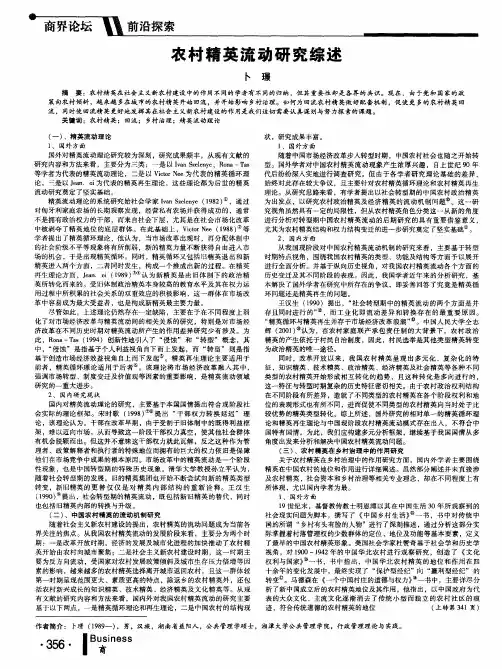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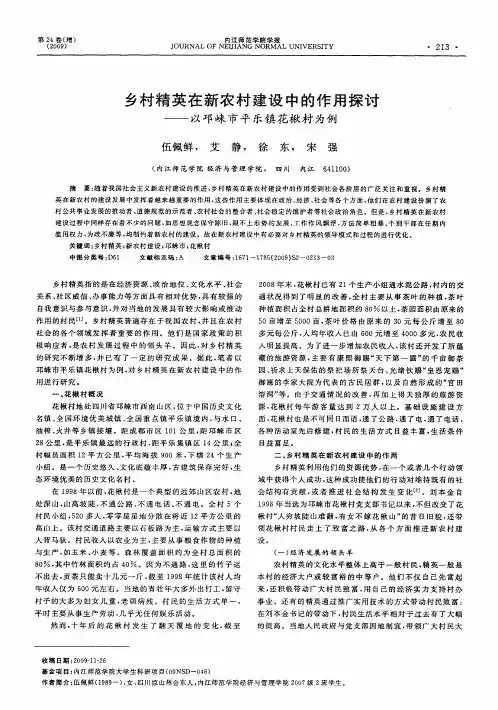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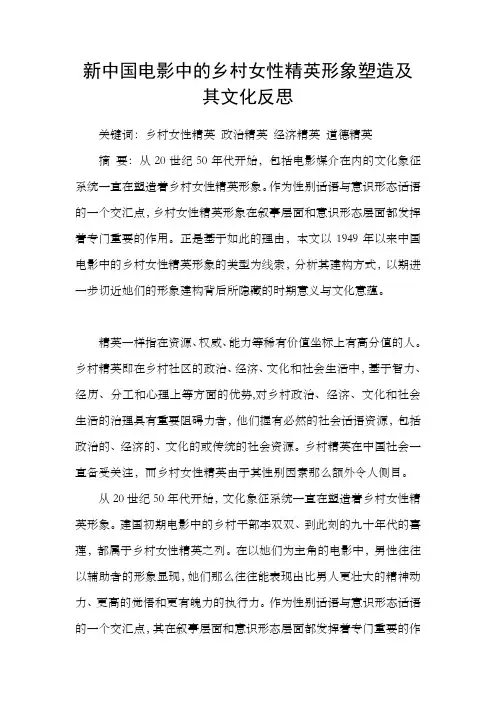
新中国电影中的乡村女性精英形象塑造及其文化反思关键词:乡村女性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道德精英摘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包括电影媒介在内的文化象征系统一直在塑造着乡村女性精英形象。
作为性别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交汇点,乡村女性精英形象在叙事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都发挥着专门重要的作用。
正是基于如此的理由,本文以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的乡村女性精英形象的类型为线索,分析其建构方式,以期进一步切近她们的形象建构背后所隐藏的时期意义与文化意蕴。
精英一样指在资源、权威、能力等稀有价值坐标上有高分值的人。
乡村精英即在乡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基于智力、经历、分工和心理上等方面的优势,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治理具有重要阻碍力者,他们握有必然的社会话语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传统的社会资源。
乡村精英在中国社会一直备受关注,而乡村女性精英由于其性别因素那么额外令人侧目。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化象征系统一直在塑造着乡村女性精英形象。
建国初期电影中的乡村干部李双双、到此刻的九十年代的喜莲,都属于乡村女性精英之列。
在以她们为主角的电影中,男性往往以辅助者的形象显现,她们那么往往能表现出比男人更壮大的精神动力、更高的觉悟和更有魄力的执行力。
作为性别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交汇点,其在叙事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都发挥着专门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过该类人物在中国电影史上特殊的文化意蕴以历时态呈现的方式,并疏理其形象在中国电影中的嬗变进程。
由于叙事重点和说明框架的需要,该论文着重分析了新时期以前的女强者形象,而对新时期以来和乡村女性精英的整体概貌关注那么留给读者意犹未尽之感①。
正是基于如此的理由,本文以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的乡村女性精英形象的类型为线索,分析其建构方式,以期进一步切近她们的形象建构背后所隐藏的时期意义与文化意蕴。
依照精英阻碍力的要紧来源来对中国电影中的乡村女性精英进行分类,本文将其要紧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道德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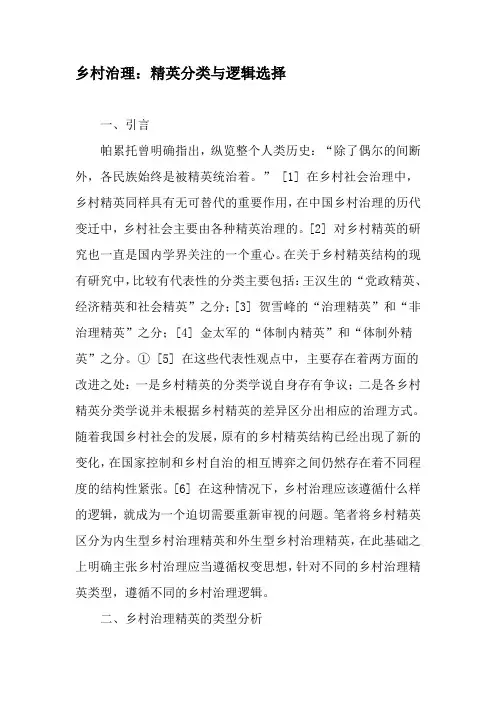
乡村治理:精英分类与逻辑选择一、引言帕累托曾明确指出,纵览整个人类历史:“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
” [1] 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精英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代变迁中,乡村社会主要由各种精英治理的。
[2] 对乡村精英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心。
在关于乡村精英结构的现有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类主要包括:王汉生的“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之分;[3] 贺雪峰的“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之分;[4] 金太军的“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之分。
① [5] 在这些代表性观点中,主要存在着两方面的改进之处:一是乡村精英的分类学说自身存有争议;二是各乡村精英分类学说并未根据乡村精英的差异区分出相应的治理方式。
随着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乡村精英结构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国家控制和乡村自治的相互博弈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结构性紧张。
[6]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治理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
笔者将乡村精英区分为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在此基础之上明确主张乡村治理应当遵循权变思想,针对不同的乡村治理精英类型,遵循不同的乡村治理逻辑。
二、乡村治理精英的类型分析帕累托认为:“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
”[1] 在笔者的叙述语境中,对于乡村精英的探讨主要局限于自身承担一定正式职务的各类乡村治理精英,并不包括未承担正式职务的其他各类乡村精英,故笔者将这种精英称之为乡村治理精英。
和贺雪峰的治理精英概念相比,这里的乡村治理精英,不但包括了村干部群体,还包含了基层政府选派的各类驻村干部,其中也包括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等。
并依据乡村治理精英的产生方式,将其进一步分为: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
(一)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所谓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主要是指由乡村共同体内成员通过自主选择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共同体领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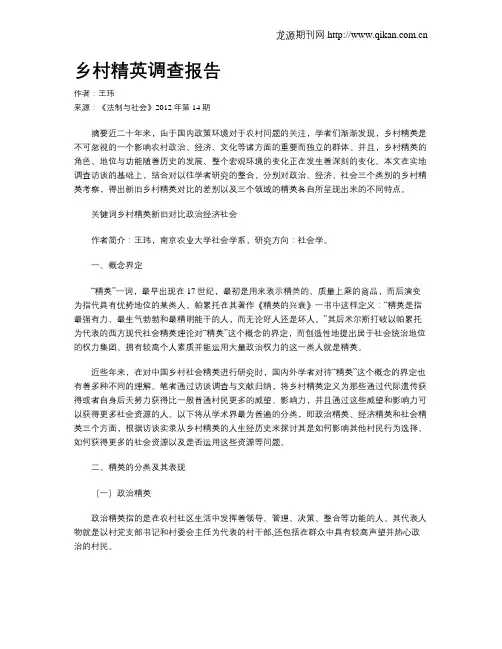
乡村精英调查报告作者:王玮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4期摘要近二十年来,由于国内政策环境对于农村问题的关注,学者们渐渐发现,乡村精英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影响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重要而独立的群体。
并且,乡村精英的角色、地位与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本文在实地调查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对以往学者研究的整合,分别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类别的乡村精英考察,得出新旧乡村精英对比的差别以及三个领域的精英各自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关键词乡村精英新旧对比政治经济社会作者简介:王玮,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社会学。
一、概念界定“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最初是用来表示精美的、质量上乘的商品,而后演变为指代具有优势地位的某类人。
帕累托在其著作《精英的兴衰》一书中这样定义:“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
”其后米尔斯打破以帕累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社会精英理论对“精英”这个概念的界定,而创造性地提出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拥有较高个人素质并能运用大量政治权力的这一类人就是精英。
近些年来,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精英进行研究时,国内外学者对待“精英”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
笔者通过访谈调查与文献归纳,将乡村精英定义为那些通过代际遗传获得或者自身后天努力获得比一般普通村民更多的威望、影响力,并且通过这些威望和影响力可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人。
以下将从学术界最为普遍的分类,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三个方面,根据访谈实录从乡村精英的人生经历史来探讨其是如何影响其他村民行为选择、如何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及是否运用这些资源等问题。
二、精英的分类及其表现(一)政治精英政治精英指的是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等功能的人。
其代表人物就是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干部,还包括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声望并热心政治的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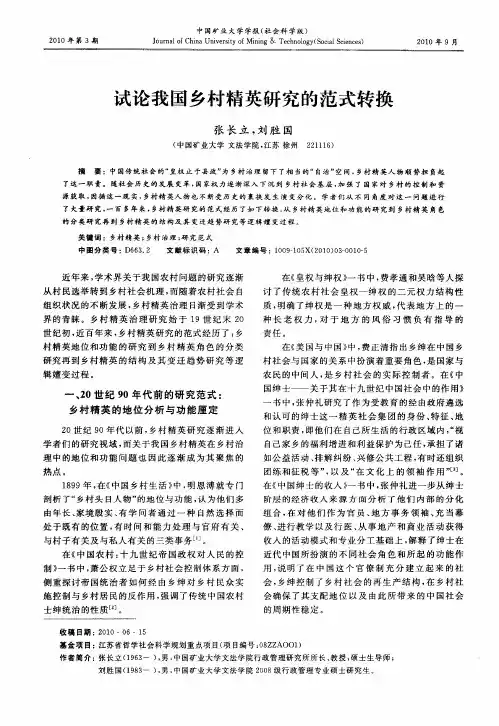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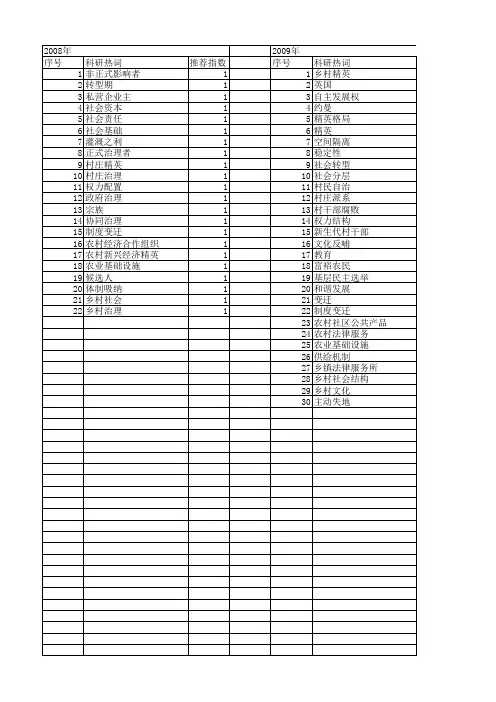
中国新农村选举政治中的精英分化与制度回归根据当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理论的研究,乡村精英可以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
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掌握正式权力资源的精英,而体制外精英则掌握传统资源等其他资源。
金太军等人的研究表明,体制内精英处于干部系统和民众系统的边际地位,处于乡镇干部、民众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的结合点和触发点上,并在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夹缝中工作。
①由于其“双重角色”的无法调适,使其往往徘徊于“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的角色冲突的阴影当中。
②在体制内精英中,处于中枢地位的是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这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形成了广受关注的“两委”关系。
而体制外精英则主要包括宗族精英、宗教精英、宗派势力、经济乡绅等。
③在传统乡村社会.这些精英构成了乡村自治的主体力量。
在人民公社时期,伴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高度统合,这些精英被纳入新的公社体制中。
因此,在这段时期除了体制内精英外,基本不存在体制外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行政控制的弱化以及农村社会的分化和重组,村庄精英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并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格局。
一、乡村精英的流失目前,中国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开局阶段,精英对于乡村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希望。
所以,新农村建设对于“乡村精英”的需求是迫切的。
乡村精英即在乡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基于智力、经历、分工和心理等方面的优势,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他们握有一定的社会话语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传统的社会资源。
④他们在乡村社区中具有非正式的权威,起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对乡村社会中意见的表达、政策的执行、政策的评估以及各种信息的反馈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乡村社区中的“守门员”角色。
后发国家持续不断的现代化,使农村不得不依赖于城市,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这种体制导致农村人力资源不断地流失,众多农民子女把脱离“农门”当作毕生的追求。
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乡村精英对政策资源的俘获现象,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
乡村精英通过与体制精英联盟,误传政策信息,抬高政资源使用门槛,将扶贫资源和贫困户资质转化为可运作资本等路径,俘获精准扶贫政策资源。
对乡村精英的政策资源俘获,不能片面否定,要意识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需要乡村精英的参与。
要从反思贫困现象和贫困问题着手,优化扶贫政策设计和工作措施,以压缩乡村精英俘获政策资源空间。
完善对乡村精英激励与约束机制,使乡村精英既能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又不敢侵占政策资源。
强化贫困群体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使其更积极主动对接、使用扶贫资源,并监督乡村精英行为。
借助大数据等新工具,优化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机制,提高乡村精英俘获政策资源的成本和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辉煌成就。
但是截止2017年底,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046万人。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级政府推出了许多措施。
但是,这些政策资源在与农村发展项目结合,向基层落实的过程中,却无法避免被乡村精英———在本土生长起来且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社会精英———俘获。
这一现象在精准扶贫开展之前就受到了关注。
如温铁军(2009)对新农村建设中被乡村精英获益多。
刑成举和李小云(2013)等,也关注到农村精英在扶贫资金和项目利益上的精英俘获,导致扶贫项目目标偏离。
针对精准扶贫开展后出现的精英俘获现象,刘升(2015)关注到农村精英通过掌控扶贫资源使用权,将扶贫资源作为资本进行经营进而获利。
朱战辉(2017)通过研究揭示了乡村精英通过组织动员,整合农村贫困户群体以规模化方式承接扶贫资源,但事实上通过扶贫资源巩固自身优势,进而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
文字下乡后,乡村精英的流逝读后感自从有了农村电影队之后,就发现村里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电影在农村还是个奢侈品,除了红白喜事之外,平时很难有机会看到电影,而那些看电影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自从农村电影队成立以后,看电影的机会明显多了起来。
再加上今年放映数字电影,可选择的机会更多了。
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农民看电影的机会更多了。
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近年来农村电影下乡的情况时,却不由地为乡村精英的流逝而叹息。
前些日子又看了一本有关文字下乡的书《文字下乡后,乡村精英的流逝》。
书中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方式对当下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进行了调研,分析其变化趋势和原因,并提出建议。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对诸如春节晚会、奥运会等文化活动的评价,认为春节晚会仅是“娱乐至死”,且受到权力话语的干预,缺乏文化良知;“文字下乡”则流于形式,变成政治手段下乡,文化“风水轮流转”,使大批农村青年的梦想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的观点值得深思。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也曾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下乡”运动。
回忆往事,颇有感慨。
其间有不少事迹堪称楷模,诸如:“村村通”工程,其中涌现出的优秀文艺创作者李春雨,贾万超夫妇等;社会调查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的调查员袁莉莉,杜国旺等;网络文学创作中的优秀作家姚雪垠,王蒙等;文化普及教育中的优秀宣讲团演说家刘燕杰,高玉峰等;以及奥运文化活动中的先进代表李瑞芳、王爱华、薛立新等,他们无不闪耀着时代的光芒,展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的活力来自这些充满朝气的青年群体。
现在,当你走在喧嚣的街道上,商店里挂着巨幅的广告牌上“超级女声”“好男儿”的标志刺激着你的眼球,商业化色彩日益浓厚的电视节目不断推陈出新,村口路边大量设立的LED电子显示屏广告吸引着你的注意力。
在这种环境中,在一种非正常的氛围中,你渐渐会感到自己已不知不觉地被异化了,丢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