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语文小小说两篇3
- 格式:pdf
- 大小:1.28 MB
- 文档页数: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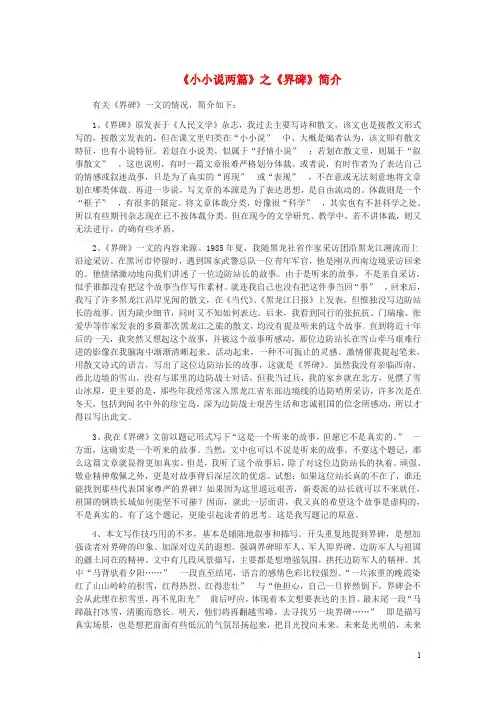
《小小说两篇》之《界碑》简介有关《界碑》一文的情况,简介如下:1、《界碑》原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我过去主要写诗和散文,该文也是按散文形式写的,按散文发表的,但在课文里归类在“小小说”中,大概是编者认为,该文即有散文特征,也有小说特征。
若划在小说类,似属于“抒情小说”;若划在散文里,则属于“叙事散文”。
这也说明,有时一篇文章很难严格划分体裁。
或者说,有时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或叙述故事,只是为了真实的“再现”或“表现”,不在意或无法刻意地将文章划在哪类体裁。
再进一步说,写文章的本源是为了表达思想,是自由流动的。
体裁则是一个“框子”,有很多的限定。
将文章体裁分类,好像很“科学”,其实也有不甚科学之处。
所以有些期刊杂志现在已不按体裁分类。
但在现今的文学研究、教学中,若不讲体裁,则又无法进行,的确有些矛盾。
2、《界碑》一文的内容来源。
1985年夏,我随黑龙社省作家采访团沿黑龙江溯流而上沿途采访。
在黑河市停留时,遇到国家武警总队一位青年军官,他是刚从西南边境采访回来的。
他情绪激动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位边防站长的故事。
由于是听来的故事,不是亲自采访,似乎谁都没有把这个故事当作写作素材。
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
回来后,我写了许多黑龙江沿岸见闻的散文,在《当代》、《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但惟独没写边防站长的故事。
因为缺少细节,同时又不知如何表达。
后来,我看到同行的张抗抗、门瑞瑜、张爱华等作家发表的多篇那次黑龙江之旅的散文,均没有提及听来的这个故事。
直到将近十年后的一天,我突然又想起这个故事,并被这个故事所感动,那位边防站长在雪山牵马艰难行进的影像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活动起来,一种不可扼止的灵感、激情催我提起笔来,用散文诗式的语言,写出了这位边防站长的故事,这就是《界碑》。
虽然我没有亲临西南、西北边境的雪山,没有与那里的边防战士对话,但我当过兵,我的家乡就在北方,见惯了雪山冰原,更主要的是,那些年我经常深入黑龙江省东部边境线的边防哨所采访,许多次是在冬天,包括到闻名中外的珍宝岛,深为边防战士艰苦生活和忠诚祖国的信念所感动,所以才得以写出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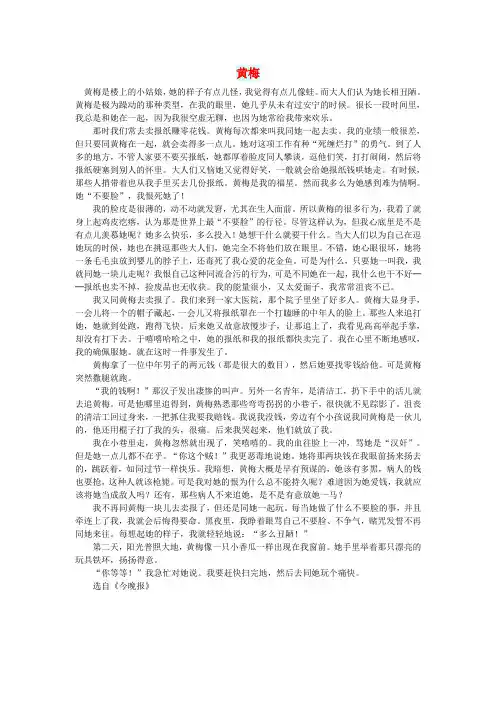
黄梅黄梅是楼上的小姑娘,她的样子有点儿怪,我觉得有点儿像蛙。
而大人们认为她长相丑陋。
黄梅是极为躁动的那种类型,在我的眼里,她几乎从未有过安宁的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和她在一起,因为我很空虚无聊,也因为她常给我带来欢乐。
那时我们常去卖报纸赚零花钱。
黄梅每次都来叫我同她一起去卖。
我的业绩一般很差,但只要同黄梅在一起,就会卖得多一点儿。
她对这项工作有种“死缠烂打”的勇气。
到了人多的地方,不管人家要不要买报纸,她都厚着脸皮同人攀谈,逗他们笑,打打闹闹,然后将报纸硬塞到别人的怀里。
大人们又恼她又觉得好笑,一般就会给她报纸钱哄她走。
有时候,那些人捎带着也从我手里买去几份报纸。
黄梅是我的福星。
然而我多么为她感到难为情啊。
她“不要脸”,我恨死她了!我的脸皮是很薄的,动不动就发窘,尤其在生人面前。
所以黄梅的很多行为,我看了就身上起鸡皮疙瘩,认为那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行径。
尽管这样认为,但我心底里是不是有点儿羡慕她呢?她多么快乐,多么投入!她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
当大人们以为自己在逗她玩的时候,她也在挑逗那些大人们,她完全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不错,她心眼很坏,她将一条毛毛虫放到婴儿的脖子上,还毒死了我心爱的花金鱼。
可是为什么,只要她一叫我,我就同她一块儿走呢?我恨自己这种同流合污的行为,可是不同她在一起,我什么也干不好──报纸也卖不掉,捡废品也无收获。
我的能量很小,又太爱面子,我常常沮丧不已。
我又同黄梅去卖报了。
我们来到一家大医院,那个院子里坐了好多人。
黄梅大显身手,一会儿将一个的帽子藏起,一会儿又将报纸罩在一个打瞌睡的中年人的脸上。
那些人来追打她,她就到处跑,跑得飞快。
后来她又故意放慢步子,让那追上了,我看见高高举起手掌,却没有打下去。
于嘻嘻哈哈之中,她的报纸和我的报纸都快卖完了。
我在心里不断地感叹,我的确佩服她。
就在这时一件事发生了。
黄梅拿了一位中年男子的两元钱(那是很大的数目),然后她要找零钱给他。
可是黄梅突然撒腿就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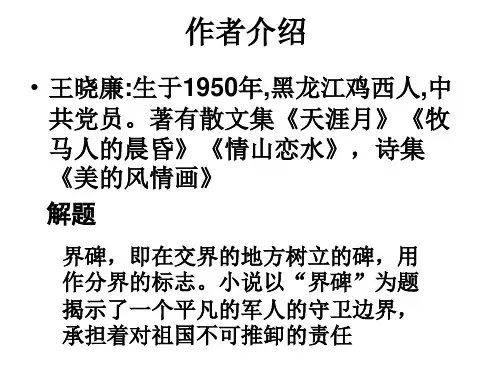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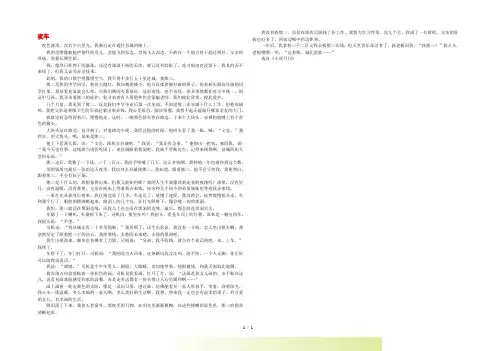
夜车夜色漆黑,没有半点星光,我独自走在通往县城的路上。
我的思绪像被枪声惊吓的鸟儿,忽地飞到东边,忽地飞去西边,不敢在一个地方停下超过两秒。
父亲的肝病,需要长期住院。
钱,像烈日炙烤下的露珠,还没有濡湿干枯的禾苗,就已没有踪影了,连点痕迹也没留下。
我真的弄不来钱了,但我又必须弄出钱来。
此刻,我的口袋空得像团空气,我不得不步行五十里进城,找熊三。
熊三是我的中学同学,他高大健壮,我却瘦弱矮小,他可以揉着被打破的鼻子,抡着砖头跟高年级的同学打架,我却看见血就会头晕。
可我们俩的关系很好,这很奇怪,也不奇怪。
很多事情都在对立中统一,辩证中互补。
我寻求着熊三的庇护,他寻求着有人帮他抄作业蒙骗老师。
我们彼此欣赏,彼此爱护。
几个月前,我见到了熊三,这是我们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见面。
不知道熊三在县城干什么工作,但他很阔绰。
我把父亲送到镇卫生院后就赶紧出来弄钱,我心里很急,脚步很慢,我想不起还能敲开哪家亲友的大门。
我就这样急得冒着汗,缓慢地走。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下来个大块头,赤裸的胳膊上有个青色的狼头。
大块头站在路边,扯开裤子,对着路沟小便。
我经过他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喊:“文亮。
”我停步,望大块头,哦,原来是熊三。
他上下看我几眼,说:“文亮,跟我去县城吧。
”我说:“我还有急事。
”他掏出一把钱,塞给我,说:“我今天也有事,这钱就当请你吃饭了,来县城跟着我混吧,我缺个管账先生。
记得来找我啊,县城西街天堂俱乐部。
”熊三走后,我数了一下钱,三千二百元。
我的手哆嗦了几下,这么多钱啊,我种地一年也难挣到这个数。
等到钱用完最后一张的这天夜里,我动身去县城找熊三。
我知道,跟着熊三,他不会亏待我,我更明白,跟着熊三,不会有好下场。
熊三是干什么的,我想象得出来。
但我又能如何呢?我的人生不就像此刻走着的夜路吗?漆黑,没有星月,没有温暖,没有希望,父亲在病床上等着我弄来钱,母亲和几个幼小的弟弟妹妹也等着我弄来钱。
一束灯光从我身后射来,我往路边靠了几步。




荒劫这里是一片大洼,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几十里路不见人烟。
宁静的月夜里,远处突然传来了马蹄声。
一匹快马疾驰而来,马上坐着一个黑塔般的汉子。
马行到坡中,那儿正好有片稀疏的小树林。
大汉勒马减速,警惕地望了望四周,正要加鞭飞奔,不料被三条突然蹿出的黑影拦住了去路。
三条黑影一胖一瘦一高。
高黑影举着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大声对马上的汉子说:“朋友,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弟兄只要钱财,放下钱财,走人!”马上汉子望了望三条黑影,拱手道:“好汉,很对不起,我没带什么钱!”“少废话!”高个子厉声说,“没钱就把命留下来!”马上汉子迟疑片刻,最后笑道:“钱再好,也没命金贵!今日碰上几位,算我倒霉!喏,全给你们!”说着,汉子用匕首割开面前布袋口上的绳索,一下抖落开来,银元哗啦啦如滚石流砂,瞬间泻了一地。
地上一片银白。
三条黑影一拥而上,正抢夺间,突然,枪声响,高个子和瘦黑影应声倒地,只剩下一个胖子,吓傻了。
马上汉子挥舞着双枪,命令胖黑影说:“快把枪放下!”胖子这时方想起怀中还有枪,急忙掏出扔了,跪在地上只顾磕头,恳求饶命。
马上汉子撂下那条空布袋,命令道:“快把大洋给我装起来!”胖子不敢怠慢,急忙朝布袋里装银元,满了,系好,递了上去。
马上汉子重新放好布袋,问胖子说:“半个月前,你们是不是劫过一个商人?”“我们每天晚上都劫道,记不起了!”胖子哆哆嗦嗦地说。
“告诉你,就是他们的家人雇我来复仇的!到阴间你们可别忌恨我!”言毕,汉子挥手一枪,那胖子顿时如水桶被打烂般射出血来,很快就“瘪”了下去。
马上汉子“哈哈”大笑,勒马赶路。
这时候,那个倒地多时的瘦黑影蠕动了一下,然后麻利地坐起,对着马上开了一枪。
马上汉子像头熊一样从马上栽了下来。
瘦黑影爬过去,很艰难地上了马,回头看了看地上的三具尸首,又挨个儿给他们补了一枪,确认他们全都死了,才勒马朝黑暗中跑去……半年以后,陈州南关的尚武街中心,新开张了一家药铺。
老板很瘦,一脸地谦和与恭顺,只是拐着一条腿。
藏刀向叫驴好赌,手头一旦有几文钱,必做的事情便是进赌场。
别瞅他是一个赌徒,但有桃花运,娶的那媳妇很有几分姿色。
人家要个头有个头,要身段有身段儿,模样儿没得说。
疤眼儿会贩牲口,什么牛驴马骡他全贩,手头很宽裕。
疤眼子和向叫驴的女人一块长大的,很喜欢她。
请媒人提过亲,但人家没搭理他。
她最终成了向叫驴的女人。
虽然成了向叫驴的女人,但疤眼子仍不死心,发誓一定要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人。
疤眼子后来也学会了进赌场,赌的对象总喜欢选择向叫驴,但赌时,十有八九是输给向叫驴。
疤眼子也真是个怪物,输也愿意跟向叫驴赌。
因为疤眼子每赌必输,所以向叫驴也偏爱与疤眼子赌。
其实,向叫驴经女人苦口婆心地劝说,在赌徒的路上基本已经悬崖勒马,但有疤眼子这个输家垫底,就再起了赌心。
快过年的时候,疤眼子又输给了向叫驴。
向叫驴得意扬扬,而疤眼子因为输了钱,心情自然不佳,就邀此处有名的“赌王”莫二进了酒店,一是让酒洗滤一下他的不快,再是向他心目中的“赌王”取经,看能否赌艺有所进展,不至于输得太惨。
酒桌上,疤眼子与赌王很投缘,无话不谈,酒喝得也很顺畅,酒酣耳热之时,疤眼子无意中流露出向叫驴目中无人自称赌王的意思。
赌王阴森森狞笑着:“噢,我倒要见识一下!”向叫驴赌瘾愈来愈大,不想,那次与赌王再赌时,竟突然输得一塌糊涂。
末了,只好把自己的女人押给了莫二。
赌王只喜欢钱,并不喜欢女人,尤其是已嫁的女人。
赌王不喜欢,疤眼子喜欢,花了些钱,从赌王那里买了过来。
疤眼子买了女人,但买不了人家的心,女人根本不喜欢他。
疤眼子就挑拨离间女人,说:“向叫驴有什么好,就知道赌,根本就不喜欢你,你才是我最喜欢的人。
”女人说:“你咋知道他不喜欢我?”疤眼子说:“真是个痴心女人,这真叫人家把你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呢!他喜欢你,怎么还把你在赌桌上押给了别人?”女人张了张很好看的嘴巴,无语。
可一会儿又道:“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嫌弃他。
我就是这样贱!”这真是饽饽用尿泡着吃,好的就是这一口。
他真觉得这女人不可思议,就无计可施地说:“这样吧,我已经花钱把你从别人手里买了过来,钱已经花了,加上我也非常喜欢你,要是我不喜欢你,早就娶房媳妇过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