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康德哲学汉译评论
- 格式:doc
- 大小:58.00 KB
- 文档页数:8

3. Social ContractKant provides two distinct discussions of social contract. One concerns property and will be treated in more detail in section 5 below. The second discussion of social contract comes in the essa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an a priori restriction on the legitimate policies the sovereign may pursue. The sovereign must recognize the “original contract” as an idea of reason that forces the sovereign to “give his law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ould have arisen from the united will of a whole people and to regard each subject, insofar as he wants to be a citizen, as if he has joined in voting for such a will” (8:297). This original contract, Kant stresses, is only an idea of reason and not a historical event. Any rights and duties stemming from an original contract do so not because of any particular historical provenance, but because of the rightful relations embodied in the original contract. No empirical act, as a historical act would be, could be the foundation of any rightful duties or rights. The idea of an original contract limits the sovereign as legislator. No law may be promulgated that “a whole people could not possibly give its consent to” (8:297). The consent at issue, however, is also not an empirical consent based upon any actual act. The set of actual particular desires of citizens is not the basis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y could possibly consent to a law. Rather, the kind of possibility at issue is one of rational possible unanimity based upon fair distributions of burdens and rights in abstraction from empirical facts or desires. Kant's two examples both exemplify this consideration of possible rational unanimity. His first example is a law that would provide hereditary privileges to members of a certain class of subjects. This law would be unjust because it would be irrational for those who would not be membersof this class to agree to accept fewer privileges than members of the class. One might say that no possible empirical information could cause all individuals to agree to this law. Kant's second example concerns a war tax. If the tax is administered fairly, it would not be unjust. Kant adds that even if the actual citizens opposed the war, the war tax would be just becaus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war is being waged for legitimate reasons that the state but not the citizens know about. Here possible empirical information might cause all citizens to approve the law. In both these examples, the conception of “possible consent” abstracts from actual desires individual citizens have. The possible consent is not based upon a hypothetical vote given actual preferences but is based on a rational conception of agreement given any possible empirical information.Kant's view is similar to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of Hobbes in a few important respects. The social contract is not a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does not involve a historical act. In fact it can be dangerous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to even search history for such empirical justification of state power (6:318). The current state must be understood, regardless of its origin, to embody the social contact. The social contract is a rational justification for state power, not a result of actual deal-making among individuals or between them and a government. Another link to Hobbes is that the social contract is not voluntary. Individuals may be forced into the civil conditionagainst their consent (6:256). Social contract is not based on any actual consent such as a voluntary choice to form a civil society along with others. Since the social contract reflects reason, each human being as a rational being already contains the basis for rational agreement to the state. Are individuals then coerced to recognize their subjection to state power against their will? Since Kant defines “will” as “practical reason itself” (Groundwork, 4:412), the answer for him is “no.” If one defines “will” as arbitrary choice, then the answer is “yes.” This is the same dichotomy that arises with regard to Kant's theory of punishment (section 7).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Kant and Hobbes is that Hobbes bases his argument on the individual benefit for each party to the contract, whereas Kant bases his argument on Right itself, understood as freedom for all persons in general, not just for the individual benefit that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obtain in their own particular freedom. To this extent Kant is influenced more by Rousseau's idea of the General Will.10. Social Philosophy“Social philosophy,” can be taken to mean the relationship o f persons to institutions, and to each other via these institutions, that are not part of the state. Family is a clear example of a social institution that transcends the individual but has at least some elements that are not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Other examples would be economic institutions such as businesses and markets, religious institutions, social clubs and private associations created to advance interests or for mere enjoyment, educational and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social systems and classifications such as race and gender, and endemic social problems like poverty. It is worth noting a few particulars, if only as examples of the range of this topic. Kant advocated the duty of citizens to support those in society who could not support themselves, and even gave the state the power to arrange for this help (6:326). He offered a b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race in several essays and also, certainly into his “Critical” period, held that other races were inferior to Europeans. He supported a reform movement i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presented by Rousseau in “Emile”. I will not provide detailed treatement of Kant's views on these particular matters (some of which are scant) but only focus on the nature of social philosophy for Kant.Kant had no comprehensive social philosophy. One might be tempted to claim that, in line with natural law theorists, Kant discusses natural rights related to some social institutions. One might read the first half of the “Doctrine of Right” as a socialphi losophy, since this half on “Private Right” discusse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relative to one another, in contrast to the second half on “Public Right” that discusses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relative to the state. Kant even offers an explanation of this difference by claiming that the opposite of state of nature is not a social but the civil condition, that is, a state (6:306). The state of nature can include voluntary societies (Kant mentions domestic relations in general) where there is no a priori obligation for individuals to enter them. This claim of Kant's, however, is subject to some doubt, since he explicitly links all forms of property to the obligation to enter the civil condition (see section 5 above), and his discuss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mes in the form of property relations akin to contract relations. It is thus not obvious how there can be any social institutions that can exist outside the civil condi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ocial institutions presuppose property relations.Another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social philosophy in Kant is to view it in terms of moral philosophy properly speaking, that is, the obligations human beings have to act under the proper maxims, as discussed in the “Doctrine of Virtue” (see section 1 above). In t he “Doctrine of Virtue” Kant talks about the obligation to develop friendships and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intercourse (6:469–74). In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Kan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thical commonwealth” in which hu man beings strengthen one another's moral resolve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moral community of a church. He also holds tha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subject of his book On Pedagogy, should be designed toprov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 human beings, who lack a natural disposition for the moral good. In these cases Kant's social philosophy is treated as an arm of his theory of virtue, not as a freestanding topic in its own right.A third approach to social philosophy comes through Kant's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Kant had envisioned anthropology as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ethics, akin to empirical psychology as a application of pure metaphysical principles of nature. Knowledge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ing as well as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s, races, nationalities, etc, can aid in determining one's precise duties toward particular individuals. Further, this knowledge can aid moral agents in their own task of motivating themselves to morality. These promises of anthropology in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re unfulfilled, however, in the details of Kant's text. He does little critical assessment of social prejudices or practices to screen out stereotypes detrimental to moral development. His own personal views, considered sexist and racist universally today and even outof step with some of his more progressive colleagues, pervade his direct discussionsof these social institutions.10.社会哲学“社会哲学”,可以用来表示人对机构的关系,彼此通过这些机构,不属于国家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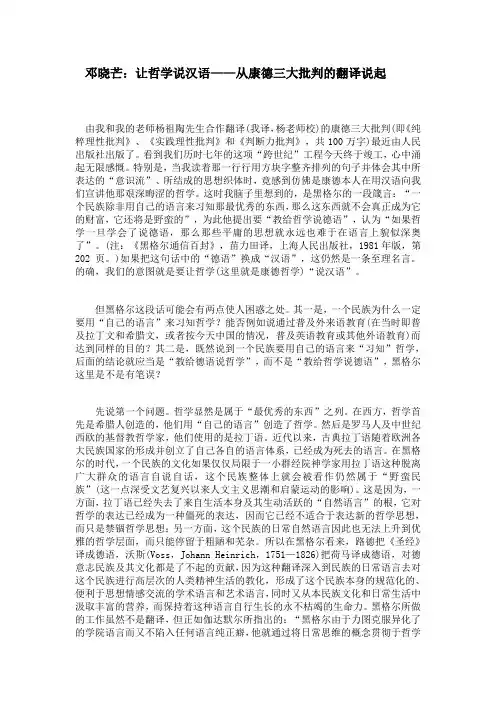
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由我和我的老师杨祖陶先生合作翻译(我译,杨老师校)的康德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共100万字)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看到我们历时七年的这项“跨世纪”工程今天终于竣工,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特别是,当我读着那一行行用方块字整齐排列的句子并体会其中所表达的“意识流”、所结成的思想织体时,竟感到仿佛是康德本人在用汉语向我们宣讲他那艰深晦涩的哲学。
这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黑格尔的一段箴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
(注:《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德语”换成“汉语”,这仍然是一条至理名言。
的确,我们的意图就是要让哲学(这里就是康德哲学)“说汉语”。
但黑格尔这段话可能会有两点使人困惑之处。
其一是,一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能否例如说通过普及外来语教育(在当时即普及拉丁文和希腊文,或者按今天中国的情况,普及英语教育或其他外语教育)而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二是,既然说到一个民族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后面的结论就应当是“教给德语说哲学”,而不是“教给哲学说德语”,黑格尔这里是不是有笔误?先说第一个问题。
哲学显然是属于“最优秀的东西”之列。
在西方,哲学首先是希腊人创造的,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哲学。
然后是罗马人及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哲学家,他们使用的是拉丁语。
近代以来,古典拉丁语随着欧洲各大民族国家的形成并创立了自己各自的语言体系,已经成为死去的语言。
在黑格尔的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一小群经院神学家用拉丁语这种脱离广大群众的语言自说自话,这个民族整体上就会被看作仍然属于“野蛮民族”(这一点深受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的影响)。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翻译理念] 康德哲学的主要观点](https://uimg.taocdn.com/e9d5ca2ac8d376eeafaa31b2.webp)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翻译理念] 康德哲学的主要观点》杨祖陶和邓晓芒两位先生编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恰逢其时,我对康德哲学兴味正浓。
在把杨、邓两位先生所编译的《精粹》后半部即《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精粹读完后,颇有所思,乃是关于翻译的,兹记于后。
按此书后记,精粹全部译文均由邓晓芒先生据德文本译出,又由杨祖陶先生逐一校订之。
我以为,精粹本所体现出的翻译理念,对于我们应当如何恰当地引译西方哲学原典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颇具特色而又富启发性的回答。
可概括为两点。
特色之一,译者试图实现译文�汉语�与原文�德文�在句法结构上的对应。
译文应当忠实地表达原文的义理,这乃是译界的公论,舍此恐怕也谈不上什么翻译了。
所谓“信”、“达”也。
译界的另一似乎已成为“公论”的要求,便是“雅”。
就是说,在翻译中,考虑到译文�汉语�与原文�如德文�之间的语法不同,翻译应当灵活而忌死板。
西方哲学文献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构造很复杂却又不失逻辑的简明与严格的、有时候长达一整段话的长句,而汉语又被认为是“不适合于”构造长句的,所以,在把长句式的西文译成汉语时,尤其需要通过一些翻译技巧,将其拆成几个句子,以使其合乎汉语的“习惯”。
这一观念在精粹本中可说是受到挑战。
比照一下同样是据德文原本所译出的《判断力批判》的宗白华译本和精粹本,不同之处是显著的:同样一段话,宗译本有时需两三句才译出,而精粹本却能做到只用一句译出。
这说明了什么?这并非一个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因为精粹本已经做出了回答:汉语同样可以做到与西文对应的既不失逻辑的清晰又体现句式的庞杂繁冗的表达。
这也不是一个在语言上的翻译能力高低的问题:老一辈学者们治学的严谨和西语功底的深厚,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两种译本间的差别,乃是各自所持翻译理念不同的表现,而两者翻译理念的不同,在我看来,其实是对于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之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我们可以问,那使人们感到艰涩沉重�甚至矫揉造作�的,也因而译家们想要“雅”起来的东西是什么?仅仅只是西语的长句式吗?的确,西语是能构造长句式的,但问题在于:它也不只是长句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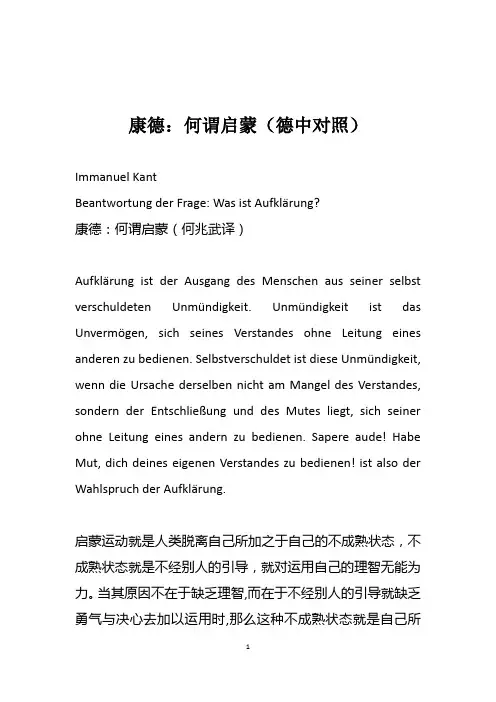
康德:何谓启蒙(德中对照)Immanuel Kant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康德:何谓启蒙(何兆武译)Aufklärung ist 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 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Unmündigkeit ist das Unvermögen, sich seines Verstandes ohne Leitung eines anderen zu bedienen. Selbstverschuldet ist diese Unmündigkeit, wenn die Ursache derselben nicht am Mangel des Verstandes, sondern der Entschließung und des Mutes liegt, sich seiner ohne Leitung eines andern zu bedienen. Sapere aude! Habe Mut, dich deines eigenen Verstandes zu bedienen! ist also der Wahlspruch der Aufklärung.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Faulheit und Feigheit sind die Ursachen, warum ein so großer Teil der Menschen, nachdem sie die Natur längst von fremder Leitung frei gesprochen (naturaliter maiorennes), dennoch gerne zeitlebens unmündig bleiben; und warum es anderen so leicht wird, sich zu deren Vormündern aufzuwerfen. Es ist so bequem, unmündig zu sein. Habe ich ein Buch, das für mich Verstand hat, einen Seelsorger, der für mich Gewissen hat, einen Arzt, der für mich die Diät beurteilt, u.s.w.: so brauche ich mich ja nicht selbst zu bemühen. Ich habe nicht nötig zu denken, wenn ich nur bezahlen kann; andere werden das verdrießliche Geschäft schon für mich übernehmen. Daß der bei weitem größte Teil der Menschen (darunter das ganze schöne Geschlecht) den Schritt zur Mündigkeit, außer dem daß er beschwerlich ist, auch für sehr gefährlich halte: dafür sorgen schon jene Vormünder, die die Oberaufsicht über sie gütigst auf sich genommen haben. Nachdem sie ihr Hausvieh zuerst dumm gemacht haben, und sorgfältig verhüteten, daß diese ruhigen Geschöpfe ja keinen Schritt außer dem Gängelwagen, darin sie sie einsperreten, wagen durften: so zeigen sie ihnen nachherdie Gefahr, die ihnen drohet, wenn sie es versuchen, allein zu gehen. Nun ist diese Gefahr zwar eben so groß nicht, denn sie würden durch einigemal Fallen wohl endlich gehen lernen; allein ein Beispiel von der Art macht doch schüchtern, und schreckt gemeiniglich von allen ferneren Versuchen ab.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己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naturaliter maiorennes)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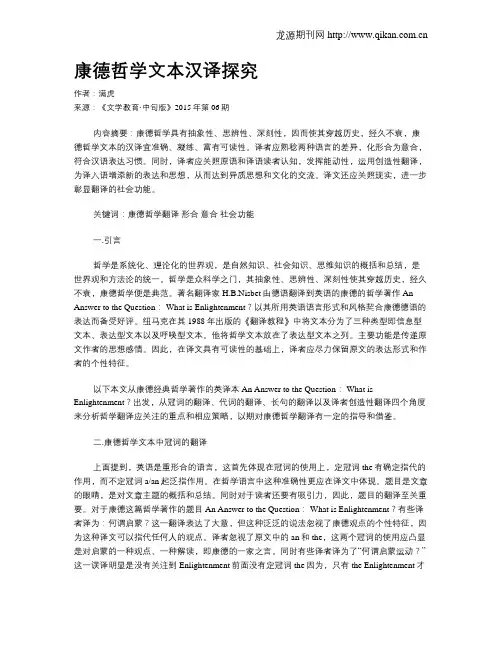
康德哲学文本汉译探究作者:满虎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5年第06期内容摘要:康德哲学具有抽象性、思辨性、深刻性,因而使其穿越历史,经久不衰,康德哲学文本的汉译宜准确、凝练、富有可读性。
译者应熟稔两种语言的差异,化形合为意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同时,译者应关照原语和译语读者认知,发挥能动性,运用创造性翻译,为译入语增添新的表达和思想,从而达到异质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译文还应关照现实,进一步彰显翻译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康德哲学翻译形合意合社会功能一.引言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哲学是众科学之门,其抽象性、思辨性、深刻性使其穿越历史,经久不衰,康德哲学便是典范。
著名翻译家H.B.Nisbet由德语翻译到英语的康德的哲学著作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以其所用英语语言形式和风格契合康德德语的表达而备受好评。
纽马克在其1988年出版的《翻译教程》中将文本分为了三种类型即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以及呼唤型文本。
他将哲学文本放在了表达型文本之列。
主要功能是传递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
因此,在译文具有可读性的基础上,译者应尽力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和作者的个性特征。
以下本文从康德经典哲学著作的英译本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出发,从冠词的翻译、代词的翻译、长句的翻译以及译者创造性翻译四个角度来分析哲学翻译应关注的重点和相应策略,以期对康德哲学翻译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二.康德哲学文本中冠词的翻译上面提到,英语是重形合的语言,这首先体现在冠词的使用上,定冠词the有确定指代的作用,而不定冠词a/an起泛指作用。
在哲学语言中这种准确性更应在译文中体现。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是对文章主题的概括和总结。
同时对于读者还要有吸引力,因此,题目的翻译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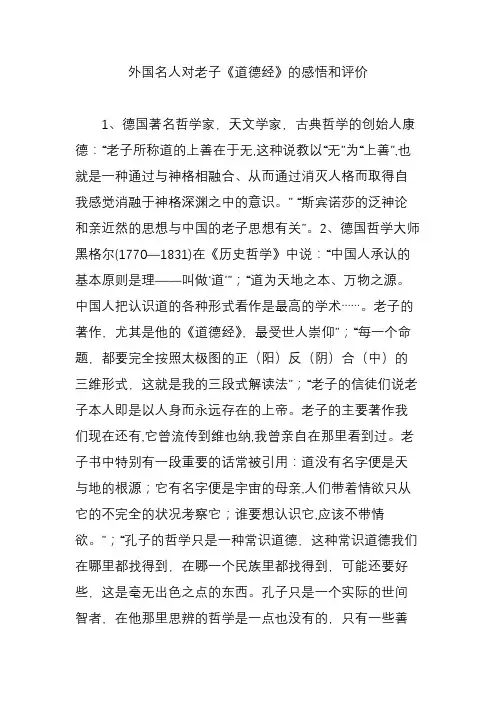
外国名人对老子《道德经》的感悟和评价1、德国著名哲学家,天文学家,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老子所称道的上善在于无,这种说教以“无”为“上善”,也就是一种通过与神格相融合、从而通过消灭人格而取得自我感觉消融于神格深渊之中的意识。
”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
2、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
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
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每一个命题,都要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这就是我的三段式解读法”;“老子的信徒们说老子本人即是以人身而永远存在的上帝。
老子的主要著作我们现在还有,它曾流传到维也纳,我曾亲自在那里看到过。
老子书中特别有一段重要的话常被引用:道没有名字便是天与地的根源;它有名字便是宇宙的母亲,人们带着情欲只从它的不完全的状况考察它;谁要想认识它,应该不带情欲。
”;“孔子的哲学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 “孔子哲学毫无出色之点,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中国哲学》3、德国哲学家谢林(1775-1854)在《神话哲学:中国哲学》中指出:“道不是人们以前翻译的理,道是门”。
老子哲学是“真正思辨的”,他“完全地和普遍地深入到了存在的最深层”。
4、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曾评论《老子》一书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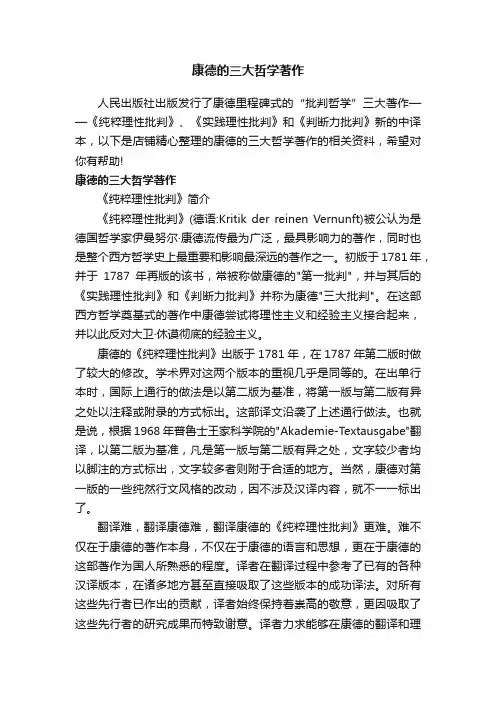
康德的三大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康德里程碑式的“批判哲学”三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新的中译本,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康德的三大哲学著作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康德的三大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简介《纯粹理性批判》(德语: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被公认为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流传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
初版于1781年,并于1787年再版的该书,常被称做康德的"第一批判",并与其后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并称为康德"三大批判"。
在这部西方哲学奠基式的著作中康德尝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接合起来,并以此反对大卫·休谟彻底的经验主义。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于1781年,在1787年第二版时做了较大的修改。
学术界对这两个版本的重视几乎是同等的。
在出单行本时,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以第二版为基准,将第一版与第二版有异之处以注释或附录的方式标出。
这部译文沿袭了上述通行做法。
也就是说,根据1968年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Akademie-Textausgabe"翻译,以第二版为基准,凡是第一版与第二版有异之处,文字较少者均以脚注的方式标出,文字较多者则附于合适的地方。
当然,康德对第一版的一些纯然行文风格的改动,因不涉及汉译内容,就不一一标出了。
翻译难,翻译康德难,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难。
难不仅在于康德的著作本身,不仅在于康德的语言和思想,更在于康德的这部著作为国人所熟悉的程度。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各种汉译版本,在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这些版本的成功译法。
对所有这些先行者已作出的贡献,译者始终保持着崇高的敬意,更因吸取了这些先行者的研究成果而特致谢意。
译者力求能够在康德的翻译和理解方面有所创新,对一些术语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自知学养有限,"众口难调",谨欢迎学界和读者提出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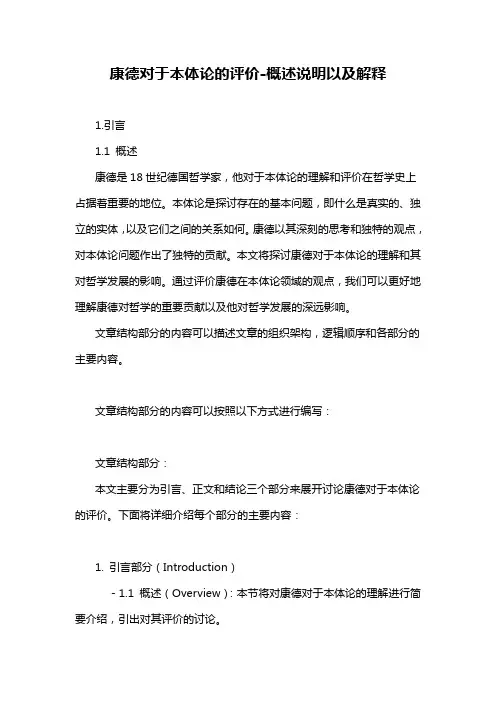
康德对于本体论的评价-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康德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他对于本体论的理解和评价在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本体论是探讨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真实的、独立的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康德以其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观点,对本体论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本文将探讨康德对于本体论的理解和其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通过评价康德在本体论领域的观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康德对哲学的重要贡献以及他对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描述文章的组织架构,逻辑顺序和各部分的主要内容。
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编写:文章结构部分:本文主要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来展开讨论康德对于本体论的评价。
下面将详细介绍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1. 引言部分(Introduction)- 1.1 概述(Overview):本节将对康德对于本体论的理解进行简要介绍,引出对其评价的讨论。
- 1.2 文章结构(Structure of the Article):本节将对整篇文章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进行说明,概括介绍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 1.3 目的(Purpose):本节将明确说明本文撰写的目的,即对康德对本体论的评价进行客观分析和总结。
2. 正文部分(Main Body)- 2.1 康德对本体论的理解(Kant's Understanding of Ontology):本节将详细探讨康德对本体论的理解,包括他对存在、实在性和物体性等概念的看法,以及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本体论问题的阐述和分析。
- 2.2 康德对本体论的贡献(Kant's Contribution to Ontology):本节将重点讨论康德对本体论领域的贡献,分析他的思想对该领域的影响和启示。
具体包括他引入的"转向主体"的观念、对哲学先验知识的贡献以及对本体论研究方法的改进等方面。
3. 结论部分(Conclusion)- 3.1 康德对本体论的评价(Evaluation of Kant's Ontology):本节将对康德的本体论观点进行评价和分析,探讨其优点、局限和争议点。

康德的法哲学思想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3-1804年)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人类思想天空中的一颗巨星。
在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其哲学被称为“批判哲学”。
在法律思想方面,主要代表作有《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和《永久和平论》。
康德的法哲学思想是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充满了哲学和伦理学的名词术语和阐述,在理解上有些艰涩难懂。
一、人的本性与道德律康德认为,人是二重的存在物,既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人的行为具有合规律性和合目的的双重特点。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其行为要服从自然的普遍规律和目的。
“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向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的目标即使是为他们所认识,也对他们会是无足轻重的。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同样的,历史也是如此,历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过程。
历史中的多种多样的国家、民族、不同的政治派别等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它们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战争)都是历史进步所采取的手段,只是相对于人了历史的最后目的才有意义。
这样,人类的历史过程就是和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是二重性的存在物,即人既是“自然人”,有自然界其他事物特别是生物同样的本能;又是“道德人”,能辨别善恶和分别是非;既能从善,也能作恶。
因而人必须服从两种规律,即自然律和道德律。
人既要服从自然法则,还要服从理性法则。
这两种规律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自然律对人来说是外在的,是他律;而道德是人的实践理性给人立的法,是自律。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考,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是以“自由”概念为出发点的,他将之成为他社会理论的“拱心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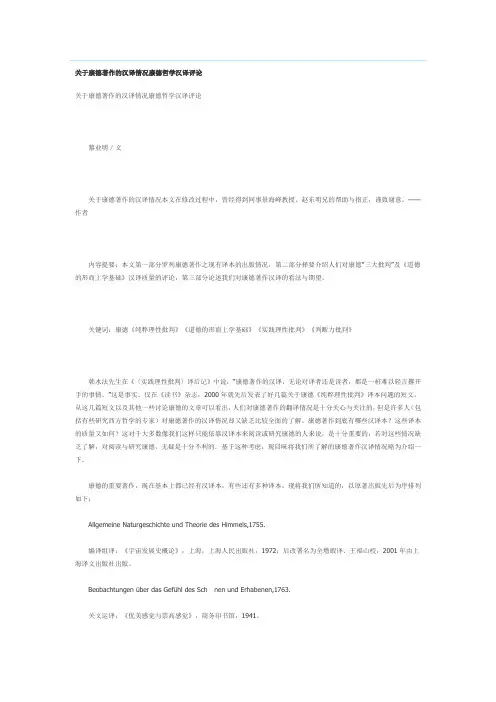
关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康德哲学汉译评论关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康德哲学汉译评论黎业明/文关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曾经得到同事景海峰教授、赵东明兄的帮助与指正,谨致谢意。
——作者内容提要:本文第一部分罗列康德著作之现有译本的出版情况,第二部分择要介绍人们对康德“三大批判”及《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汉译质量的评论,第三部分论述我们对康德著作汉译的看法与期望。
关键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韩水法先生在《〈实践理性批判〉译后记》中说:“康德著作的汉译,无论对译者还是读者,都是一桩难以轻言撂开手的事情。
”这是事实。
仅在《读书》杂志,2000年就先后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本问题的短文。
从这几篇短文以及其他一些讨论康德的文章可以看出,人们对康德著作的翻译情况是十分关心与关注的,但是许多人(包括有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对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却又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
康德著作到底有哪些汉译本?这些译本的质量又如何?这对于大多数像我们这样只能依靠汉译本来阅读或研究康德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若对这些情况缺乏了解,对阅读与研究康德,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基于这种考虑,现冒昧将我们所了解的康德著作汉译情况略为介绍一下。
康德的重要著作,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有汉译本,有些还有多种译本。
现将我们所知道的,以原著出版先后为序排列如下: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1755.编译组译:《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后改署名为全增嘏译、王福山校,200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 nen und Erhabenen,1763.关文运译:《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商务印书馆,1941。
曹俊峰译:《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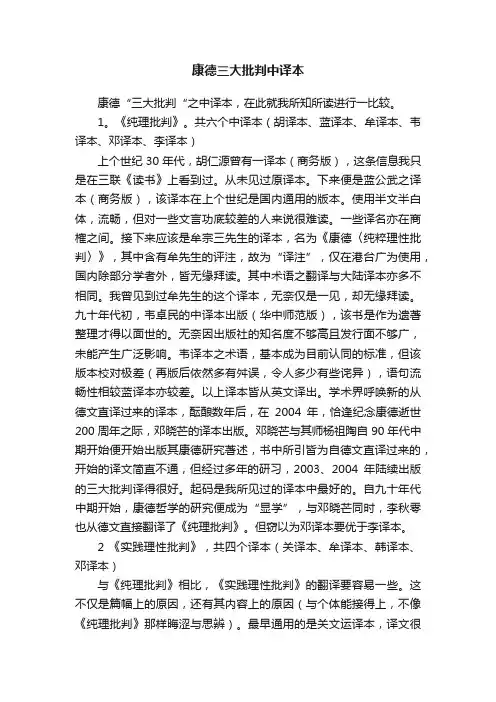
康德三大批判中译本康德“三大批判“之中译本,在此就我所知所读进行一比较。
1。
《纯理批判》。
共六个中译本(胡译本、蓝译本、牟译本、韦译本、邓译本、李译本)上个世纪30年代,胡仁源曾有一译本(商务版),这条信息我只是在三联《读书》上看到过。
从未见过原译本。
下来便是蓝公武之译本(商务版),该译本在上个世纪是国内通用的版本。
使用半文半白体,流畅,但对一些文言功底较差的人来说很难读。
一些译名亦在商榷之间。
接下来应该是牟宗三先生的译本,名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其中含有牟先生的评注,故为“译注”,仅在港台广为使用,国内除部分学者外,皆无缘拜读。
其中术语之翻译与大陆译本亦多不相同。
我曾见到过牟先生的这个译本,无奈仅是一见,却无缘拜读。
九十年代初,韦卓民的中译本出版(华中师范版),该书是作为遗著整理才得以面世的。
无奈因出版社的知名度不够高且发行面不够广,未能产生广泛影响。
韦译本之术语,基本成为目前认同的标准,但该版本校对极差(再版后依然多有舛误,令人多少有些诧异),语句流畅性相较蓝译本亦较差。
以上译本皆从英文译出。
学术界呼唤新的从德文直译过来的译本,酝酿数年后,在2004年,恰逢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之际,邓晓芒的译本出版。
邓晓芒与其师杨祖陶自90年代中期开始便开始出版其康德研究著述,书中所引皆为自德文直译过来的,开始的译文简直不通,但经过多年的研习,2003、2004年陆续出版的三大批判译得很好。
起码是我所见过的译本中最好的。
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康德哲学的研究便成为“显学”,与邓晓芒同时,李秋零也从德文直接翻译了《纯理批判》。
但窃以为邓译本要优于李译本。
2 《实践理性批判》,共四个译本(关译本、牟译本、韩译本、邓译本)与《纯理批判》相比,《实践理性批判》的翻译要容易一些。
这不仅是篇幅上的原因,还有其内容上的原因(与个体能接得上,不像《纯理批判》那样晦涩与思辨)。
最早通用的是关文运译本,译文很不错。
牟宗三先生的译本名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我甚至连见之缘分都没有,甚憾!以上皆是据英译本译出。
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中文译本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日益重要地位,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需求也日益增加。
哲学范畴学是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研究的是各种普遍概念和原则,对于推动我国哲学界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就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探讨,旨在探究其对于我国哲学学术界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一、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重要性1. 哲学范畴学的理论价值哲学范畴学是研究概念、范畴和普遍规律的哲学学科,其理论研究对于深化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改善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在具有自身理论深度的也融合了不同文化和思想背景,对于我国学术界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2. 推动哲学学术界的国际化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引进和翻译有助于推动我国哲学学术界的国际化进程,丰富了我国哲学界对于国际学术动态的了解,并促进了我国哲学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二、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中文译本现状1. 已经译本的著作目前,一些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在我国出版。
例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已经有了杰出的中文译本,并在我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 尚未译本的著作然而,仍然有许多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尚未被翻译成中文。
例如西方现象学、分析哲学等重要范畴学著作在我国学术界尚未广泛传播和研究,这些著作的中文译本对于我国哲学学术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中文翻译与传播1. 翻译水平和质量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中文译本需要具备翻译水平和质量达到国际标准,才能确保传达原著的思想和理论内涵。
翻译者需要具备扎实的哲学功底和出色的语言功底,同时确保在传达原著内涵的适当考虑到我国读者的接受和理解。
2. 传播渠道和方式国外哲学范畴学著作的中文译本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
除了传统的出版物渠道外,还可以利用网络、学术讲座等多种方式进行推广,以确保广大读者能够接触到这些重要的著作。
邓晓芒: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序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出版于1788年。
全书除序言和导言外,为纯粹实践理性的'要素论'和'方法论'两部分,外加一个'结论'。
'要素论'里面又分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和'辩证论'。
这一套结构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大体结构完全相同,但在划分的细节上却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完全相反。
这是由于两个批判的任务、对象和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所决定的。
康德在'序言'中一开始就指出,本书的任务并不是批判'纯粹实理性',而是立足于无人可以怀疑的'纯粹实践理性'去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即不是像《纯粹理性批判》那样考察人的各种知识'如何可能'的先天条件,而是从人的纯粹理性现实具有的实践能力出发并以之作标准,批判和评价一般的(不纯粹的)理性在实践活动中的种种表现,从中确认纯粹理性的先天普遍规律,这就是道德律。
道德律使人认识到人在实践中事实上是自由的,并反过来确定了人的自由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这样一来,自由就由于存在着道德律这一事实而不再仅仅《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设想的那种可能的'先验自由',而成为了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实践的自由'即'自由意志'了。
自由概念就此成为了两大批判体系结合的关键('拱顶石')。
之所以有如此区别,是由于这里所谓的'实在性'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实在性具有不同的含义,不是知识的实在性,而是实践的实在性,它不给我们带来任何有关对象的知识,但却有可能基于自在之物而现实地对现象世界发生作用,因而是同一个理性在不同的方面即实践方面(而非认识方面)的运用。
但这种实践的运用本身也有它的理论上的要求,即为了保证纯粹道德律的完全实现和至善的完成而必须假定(悬设)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存有,这些假定也由于自由概念的实在性而带上了实践意义上的实在性,即能够现实地对人的行动起作用。
康德的思想及评价汪光宇09724126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
思想主张:人非工具,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康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不可知论者,他调和了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矛盾,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不可知的物自体,人类的理性无法认识,人又先天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分别对应数学的代数和几何,人的认识能力由于物自体作用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知觉,然后知性运用范畴去整理这些杂乱的材料,使之成为具有必然性的科学知识。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不被动消极的面对世界,而是运用知性为自然界立法,这也可以看出康德极大的调动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面对怀疑主义者休谟对自然科学的摧毁他拯救了自然科学,也打破了大陆独断论的机械论。
但是人类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当人类的理性企图去认识物自体是就会导致幻想和二律背反。
他在这里限制了人类的理性,为宗教留下了地盘!康德思想的简单评价一、何谓“启蒙”,何谓“成熟”?“自由”乃是“自己”。
一切出于“自己”,又回归于“自己”。
“启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
所谓“外在”,乃是“它者”,包括了“人-他人”和“事-客观世界”对“自己”的支配;“摆脱”一切羁绊,也是“自由”的基本意义。
所以康德谈论“启蒙”,强调的是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种职能,来认知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导。
“启蒙”精神是“摆脱-不需要”“他者”指导的独立自主精神。
这样,康德就把自己的“启蒙”观念和传统的“启蒙”口号——“敢于认知”联系起来。
《判断力批判》中文译本考-2019年文档《判断力批判》中文译本考A study on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Critique of judgmentXiong Cheng(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Sichuan Nanchong,637000): Critique of Judgment written by Kant, one of the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founder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Many Chinese studied this book,but nobody discussed about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systematically. There are three main separate Chinese translation booklets in China. In addition,some anthology of Kant also included Critique of Judgment. The present article mainly investigates five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Critique of Judgment.Keywords: Critique of Judgment; Kant;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一、康德及《判断力批判》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为其哲学代表作。
中国翻译康德作品的译者,较早有胡仁源、张铭鼎、蓝公武、牟宗三、韦卓民、宗白华等,近些年又有邓晓芒、李明辉、韩水法、曹峻峰等。
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我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觉得康德的哲学,不是为他那代人而写的,而是为我们这一代人而写的。
并且觉得,他是为我们这一代——中马列唯物辩证法毒素很深的中國人而专门作解答的哲学家。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对馬克思这个唯物论哲学是多么坚信不疑呀。
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章也说过,一般来说,人类的知识,是经验后得出来的,没有经验,就谈不上什么知识。
而经验的来源是什么?不就是客体给予我们主体的东西吗?没有客体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无知识可谈。
这也是唯物论者坚定物质意识的论调。
可是,康德把话语一转,他说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验后的知识,他要说的知识,是验前的知识。
康德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两分法思维模式。
康德称他的哲学为哥白尼式的反转(革命)。
很多人简单地将康德归为唯心主义者,说康德不就是说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生会思维的脑袋而已。
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哲学,就会发现,康德已了解到人认识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这就奠定了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
在康德的先验论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要么怀疑我们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要么独断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
康德给我们的认识论来个突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洞见。
我们拿当今常用的电脑来说康德这个认识论,你就觉得康德是多么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就如打开的一台电脑,我们的知识,都是由客体输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
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争论不休了:是物质(康德称为“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争论就如同“输入的东西决定电脑呢还是电脑决定输入的东西”?这时,康德的先验论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
在现象还没有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脑袋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之前,我们要研究电脑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会认为,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反应,也就想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
康德的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没有知识里面看到有知识。
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黎业明人们对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是十分关心的。
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翻译尤为关心。
2000年的《读书》杂志就发表了好几篇谈论《纯粹理性批判》汉译的短文。
从这几篇短文以及其他一些讨论康德的文章可以看出,许多人(包括有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对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现冒昧将我们所了解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情况略为介绍。
据我们所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现有四种汉译本:(1)胡仁源先生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2)蓝公武先生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1960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牟宗三先生译本,题为《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分为上、下两册,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4)韦卓民先生译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0年校订版。
对于这些译本的质量,人们时有评论,现摘要介绍如下:在现有四种汉译中,以胡仁源先生的译本为最早。
韦卓民先生说:“胡氏中译本,读来确甚晦涩,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从德文原本译出,而对于康德的哲学术语似乎没有深加留意,且对于康德的整个体系又好像未深入研究,况且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习惯。
”(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
顺便说一句,王若水先生认为胡译本并非从德文原本译出,而是根据F.Max Müller1896年的英译本转译。
见王若水撰:《再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读书》,2000年第6期。
)王太庆先生也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他读胡译本的感受。
他说:“在翠湖中间的那所省立图书馆里,我一连几天借阅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可是尽管已经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做基础,我还是一点没有看懂。
不懂的情况和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旧译本差不多,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
后来看了Kemp Smith的英译本和Barni的法译本,才发现康德的写法尽管有些晦涩,却并不是那样绝对不能懂的。
关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康德哲学汉译评论关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康德哲学汉译评论黎业明/文关于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曾经得到同事景海峰教授、赵东明兄的帮助与指正,谨致谢意。
——作者内容提要:本文第一部分罗列康德著作之现有译本的出版情况,第二部分择要介绍人们对康德“三大批判”及《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汉译质量的评论,第三部分论述我们对康德著作汉译的看法与期望。
关键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韩水法先生在《〈实践理性批判〉译后记》中说:“康德著作的汉译,无论对译者还是读者,都是一桩难以轻言撂开手的事情。
”这是事实。
仅在《读书》杂志,2000年就先后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本问题的短文。
从这几篇短文以及其他一些讨论康德的文章可以看出,人们对康德著作的翻译情况是十分关心与关注的,但是许多人(包括有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对康德著作的汉译情况却又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
康德著作到底有哪些汉译本?这些译本的质量又如何?这对于大多数像我们这样只能依靠汉译本来阅读或研究康德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若对这些情况缺乏了解,对阅读与研究康德,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基于这种考虑,现冒昧将我们所了解的康德著作汉译情况略为介绍一下。
康德的重要著作,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有汉译本,有些还有多种译本。
现将我们所知道的,以原著出版先后为序排列如下: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1755.编译组译:《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后改署名为全增嘏译、王福山校,200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 nen und Erhabenen,1763.关文运译:《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商务印书馆,1941。
曹俊峰译:《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何兆武译:《论优美感与崇高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Tr ume eines Geistersehers,erl utert durch Tr ume der Metaphysik,1766.李明辉译:《通灵者之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1787.胡仁源译:《纯粹理性批判》,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列入“万有文库”丛书。
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57;商务印书馆,1960。
牟宗三译注:《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上、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83。
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初版;2000校订版。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1783.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1785.唐钺译:《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修订本。
谢扶雅译:《道德形上学根本原理》,收入《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60初版;1986第三版。
列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丛书。
牟宗三译:《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收入《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2。
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002重排新版。
李明辉译:《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刘汉译:《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收入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1786.邓晓芒译:《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北京,三联书店,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修订新版。
韦卓民译:《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张铭鼎译:《实践理性批判》,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关文运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谢扶雅译:《实践理性批判》,收入《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60初版;1986第三版。
列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丛书。
牟宗三译注:《实践理性底批判》,收入《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2。
龙斌、秦洪良、刘克苏译:《实践理性批判》,收入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1997。
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001年第3次印本略有订正。
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下卷,韦卓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其中,宗译上卷又收入《宗白华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牟宗三译注:《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92、1993。
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1793.李秋零译:《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Metaphysik der Sitten,1797.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此为《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前半部分之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又收入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199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增订新版。
Immanuel Kants Logik,ein Handbuch zu Vorlesungen,1800.许景行译:《逻辑学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此外,还有周暹与德国人尉礼贤合译《人心能力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瞿菊农译《康德论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韦卓民译《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约翰·华特生编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何兆武编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收康德1784—1793年论文八篇。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收康德1749—1802年书信100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后略加删订、增加20多幅图片并改题为《彼岸星空:康德书信选》,由北京的经济日报出版社于2001年印行);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等等。
由上可见,现在已有将近20种康德著作有汉译,译本总数将近40个。
其中,以译本论,译本最多的是《纯粹理性批判》,有四个,《实践理性批判》与《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各有六个;以译者论,翻译康德著作种数与字数最多的当属牟宗三先生、邓晓芒先生与韦卓民先生。
(据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卓民学术论著选》附录“韦卓民著述目录”,除已出版的几种以外,韦先生在1964、1965年还译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卷与《一切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尚未出版,译稿存放于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
)要对康德著作之所有译本的评论都加以罗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康德著作中最重要、阅读人数最多、引述最多的是《纯粹理性批判》、《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
这也是汉译本最多、汉译质量争议性最大的几种。
现将与这几种著作的译本有关的评论择要抄录如下:《纯粹理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现有的四种译本中,以胡仁源先生的译本为最早。
韦卓民先生说:“胡氏中译本,读来确甚晦涩,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从德文原本译出,而对于康德的哲学术语似乎没有深加留意,且对于康德的整个体系又好像未深入研究,况且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习惯。
”韦卓民:《〈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第4页;2000年校订版,第8页。
顺便说一句,王若水先生认为胡译本并不是从德文原本译出,他通过对照发现,胡译“实际上是从F.Max Müller 1896年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不过它略去了英译者的序言”。
(王若水:《再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读书》,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6期,第27页。
)王太庆先生也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他读胡译本的感受。
他说:“在翠湖中间的那所省立图书馆里,我一连几天借阅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可是尽管已经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做基础,我还是一点没有看懂。
不懂的情况和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旧译本差不多,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
后来看了Kemp Smith的英译本和Barni的法译本,才发现康德的写法尽管有些晦涩,却并不是那样绝对不能懂的。
我怀疑汉译本的译者没有弄懂康德的意思,只是机械地照搬词句,所以不能表现论证过程。
这说明不懂哲学和哲学史是无法传达哲学思想的,要想多了解一点康德靠读旧翻译还是不行。
”王太庆:《读懂康德》,《读书》,1999年第10期,第74页。
依韦先生与王先生的说法,胡先生并不懂康德哲学。
不懂康德哲学,却去翻译康德著作中最难懂的《纯粹理性批判》,其译本质量如何,可想而知。
蓝公武先生的译本,据《译者后记》所说,是1933年开始翻译的,1935年秋天全部译完,但迟至1957年才出版发行。
这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汉译本。
韦卓民先生说:“蓝公武先生的中译本,据该译本的《译后记》所说,也是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译出的,但是我们与原英译本详细对照,许多地方像是不忠于英译原文,甚至误解英译的词句。
原英译本的脚注不少是精辟之处,而蓝译不予译出,也似乎是不应该的。
”韦卓民:《〈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1991年初版,第4页;2000年校订版,第8页。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蓝译本是流传最广、也是我们阅读与研究康德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译本。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著作等身。
他早年即对康德有兴趣,希望把康德的思想融会到儒学当中来,晚年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把康德的四部重要著作全部译为汉语。
蔡仁厚先生说:“以一人之力,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先生乃二百年来世界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