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避讳字说(一)
- 格式:docx
- 大小:23.07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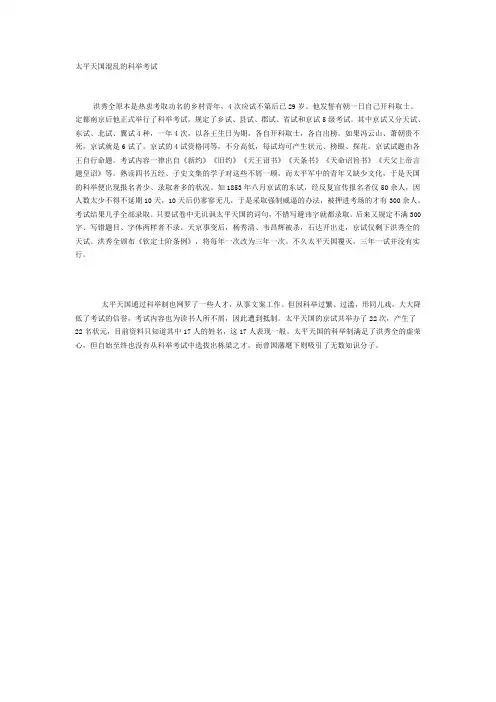
太平天国混乱的科举考试洪秀全原本是热衷考取功名的乡村青年,4次应试不第后已29岁。
他发誓有朝一日自己开科取士。
定都南京后他正式举行了科举考试,规定了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京试5级考试。
其中京试又分天试、东试、北试、翼试4种,一年4次,以各王生日为期,各自开科取士,各自出榜。
如果冯云山、萧朝贵不死,京试就是6试了。
京试的4试资格同等,不分高低,每试均可产生状元、榜眼、探花。
京试试题由各王自行命题,考试内容一律出自《新约》《旧约》《天王诏书》《天条书》《天命诏旨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等。
熟读四书五经、子史文集的学子对这些不屑一顾,而太平军中的青年又缺少文化,于是天国的科举便出现报名者少、录取者多的状况。
如1853年八月京试的东试,经反复宣传报名者仅50余人,因人数太少不得不延期10天,10天后仍寥寥无几,于是采取强制威逼的办法,被押进考场的才有300余人。
考试结果几乎全部录取。
只要试卷中无讥讽太平天国的词句,不错写避讳字就都录取。
后来又规定不满300字、写错题目、字体两样者不录。
天京事变后,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京试仅剩下洪秀全的天试。
洪秀全颁布《钦定士阶条例》,将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
不久太平天国覆灭,三年一试并没有实行。
太平天国通过科举制也网罗了一些人才,从事文案工作。
但因科举过繁、过滥,形同儿戏,大大降低了考试的信誉,考试内容也为读书人所不屑,因此遭到抵制。
太平天国的京试共举办了22次,产生了22名状元,目前资料只知道其中17人的姓名,这17人表现一般。
太平天国的科举制满足了洪秀全的虚荣心,但自始至终也没有从科举考试中选拔出栋梁之才,而曾国藩麾下则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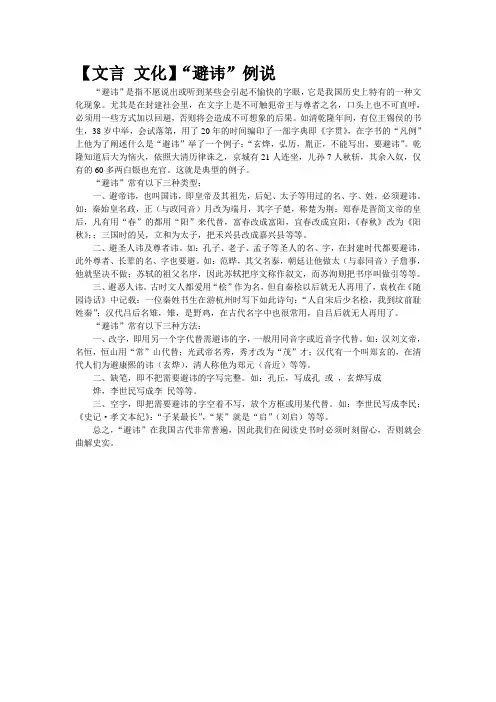
【文言文化】“避讳”例说“避讳”是指不愿说出或听到某些会引起不愉快的字眼,它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里,在文字上是不可触犯帝王与尊者之名,口头上也不可直呼,必须用一些方式加以回避,否则将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如清乾隆年间,有位王锡侯的书生,38岁中举,会试落第,用了20年的时间编印了一部字典即《字贯》,在字书的“凡例”上他为了阐述什么是“避讳”举了一个例子:“玄烨,弘历,胤正,不能写出,要避讳”。
乾隆知道后大为恼火,依照大清历律诛之,京城有21人连坐,儿孙7人秋斩,其余入奴,仅有的60多两白银也充官。
这就是典型的例子。
“避讳”常有以下三种类型:一、避帝讳,也叫国讳,即皇帝及其祖先,后妃、太子等用过的名、字、姓,必须避讳。
如:秦始皇名政,正(与政同音)月改为端月,其字子楚,称楚为荆;郑春是晋简文帝的皇后,凡有用“春”的都用“阳”来代替,富春改成富阳,宜春改成宜阳,《春秋》改为《阳秋》;;三国时的吴,立和为太子,把禾兴县改成嘉兴县等等。
二、避圣人讳及尊者讳。
如:孔子、老子、孟子等圣人的名、字,在封建时代都要避讳,此外尊者、长辈的名、字也要避。
如:范晔,其父名泰,朝廷让他做太(与泰同音)子詹事,他就坚决不做;苏轼的祖父名序,因此苏轼把序文称作叙文,而苏洵则把书序叫做引等等。
三、避恶人讳。
古时文人都爱用“桧”作为名,但自秦桧以后就无人再用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载:一位秦姓书生在游杭州时写下如此诗句:“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耻姓秦”;汉代吕后名雉,雉,是野鸡,在古代名字中也很常用,自吕后就无人再用了。
“避讳”常有以下三种方法:一、改字,即用另一个字代替需避讳的字,一般用同音字或近音字代替。
如:汉刘文帝,名恒,恒山用“常”山代替;光武帝名秀,秀才改为“茂”才;汉代有一个叫郑玄的,在清代人们为避康熙的讳(玄烨),清人称他为郑元(音近)等等。
二、缺笔,即不把需要避讳的字写完整。
如:孔丘,写成孔或,玄烨写成烨,李世民写成李民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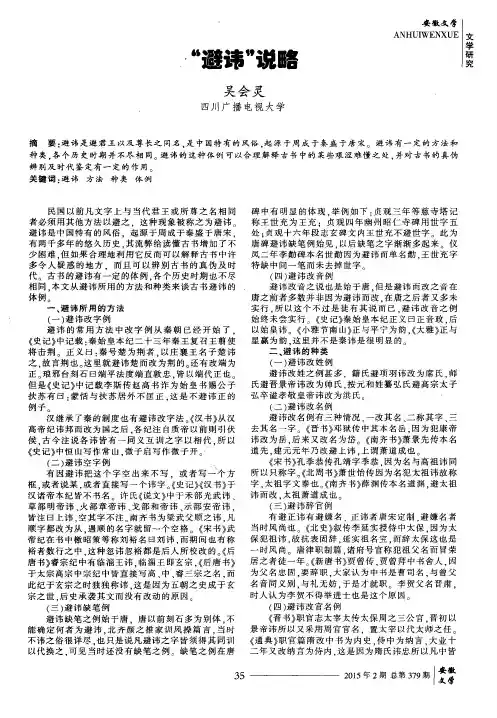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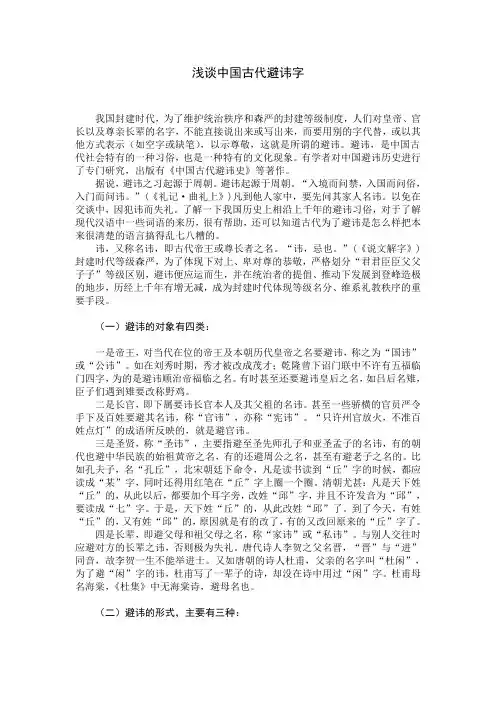
浅谈中国古代避讳字我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对皇帝、官长以及尊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而要用别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笔),以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避讳。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有学者对中国避讳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避讳史》等著作。
据说,避讳之习起源于周朝。
避讳起源于周朝。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礼记·曲礼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问其家人名讳。
以免在交谈中,因犯讳而失礼。
了解一下我国历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讳习俗,对于了解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来历,很有帮助,还可以知道古代为了避讳是怎么样把本来很清楚的语言搞得乱七八糟的。
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
“讳,忌也。
”(《说文解字》)封建时代等级森严,为了体现下对上、卑对尊的恭敬,严格划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区别,避讳便应运而生,并在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经上千年有增无减,成为封建时代体现等级名分、维系礼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一)避讳的对象有四类:一是帝王,对当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要避讳,称之为“国讳”或“公讳”。
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
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二是长官,即下属要讳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
甚至一些骄横的官员严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讳,称“官讳”,亦称“宪讳”。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讳。
三是圣贤,称“圣讳”,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
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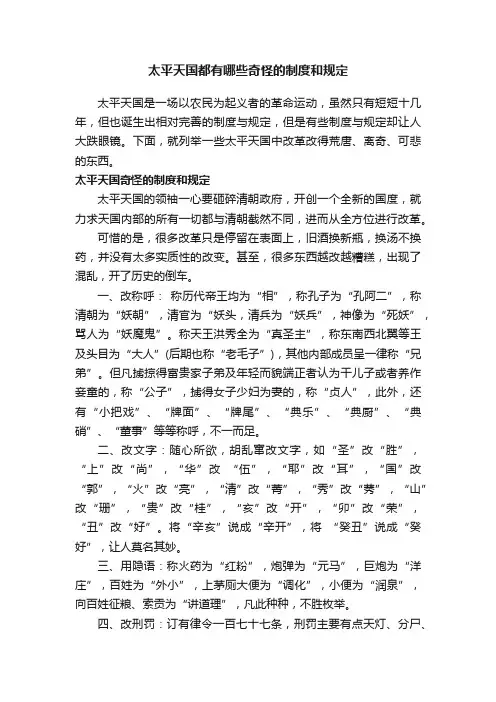
太平天国都有哪些奇怪的制度和规定太平天国是一场以农民为起义者的革命运动,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年,但也诞生出相对完善的制度与规定,但是有些制度与规定却让人大跌眼镜。
下面,就列举一些太平天国中改革改得荒唐、离奇、可悲的东西。
太平天国奇怪的制度和规定太平天国的领袖一心要砸碎清朝政府,开创一个全新的国度,就力求天国内部的所有一切都与清朝截然不同,进而从全方位进行改革。
可惜的是,很多改革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旧酒换新瓶,换汤不换药,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改变。
甚至,很多东西越改越糟糕,出现了混乱,开了历史的倒车。
一、改称呼:称历代帝王均为“相”,称孔子为“孔阿二”,称清朝为“妖朝”,清官为“妖头,清兵为“妖兵”,神像为“死妖”,骂人为“妖魔鬼”。
称天王洪秀全为“真圣主”,称东南西北翼等王及头目为“大人”(后期也称“老毛子”),其他内部成员呈一律称“兄弟”。
但凡掳掠得富贵家子弟及年轻而貌端正者认为干儿子或者养作妾童的,称“公子”,掳得女子少妇为妻的,称“贞人”,此外,还有“小把戏”、“牌面”、“牌尾”、“典乐”、“典厨”、“典硝”、“董事”等等称呼,不一而足。
二、改文字:随心所欲,胡乱窜改文字,如“圣”改“胜”,“上”改“尚”,“华”改“伍”,“耶”改“耳”,“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秀”改“莠”,“山”改“珊”,“贵”改“桂”,“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
将“辛亥”说成“辛开”,将“癸丑”说成“癸好”,让人莫名其妙。
三、用隐语:称火药为“红粉”,炮弹为“元马”,巨炮为“洋庄”,百姓为“外小”,上茅厕大便为“调化”,小便为“润泉”,向百姓征粮、索贡为“讲道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四、改刑罚:订有律令一百七十七条,刑罚主要有点天灯、分尸、剥皮、铁杵、顶车,反弓、跪火、杖肋、鞭背、木架等等。
其中的点天灯,也叫倒点人油蜡,把犯人扒光衣服,用麻布包裹,再放进油缸里浸泡,入夜后,将他头下脚上拴在一根挺高的木杆上,从脚上点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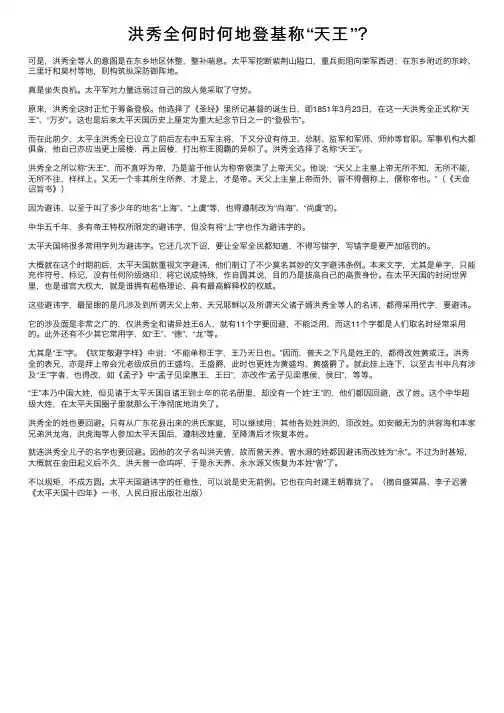
洪秀全何时何地登基称“天王”?可是,洪秀全等⼈的意图是在东乡地区休整,整补喘息。
太平军挖断紫荆⼭隘⼝,重兵扼阻向荣军西进;在东乡附近的东岭、三⾥圩和莫村等地,则构筑纵深防御阵地。
真是坐失良机。
太平军对⼒量远弱过⾃⼰的敌⼈竟采取了守势。
原来,洪秀全这时正忙于筹备登极。
他选择了《圣经》⾥所记基督的诞⽣⽇,即1851年3⽉23⽇,在这⼀天洪秀全正式称“天王”、“万岁”。
这也是后来太平天国历史上厘定为重⼤纪念节⽇之⼀的“登极节”。
⽽在此前⼣,太平主洪秀全已设⽴了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下⼜分设有侍卫、总制、监军和军师、师帅等官职。
军事机构⼤都俱备,他⾃⼰亦应当更上层楼、再上层楼,打出称王图霸的异帜了。
洪秀全选择了名称“天王”。
洪秀全之所以称“天王”,⽽不直呼为帝,乃是鉴于他认为称帝亵渎了上帝天⽗。
他说:“天⽗上主皇上帝⽆所不知,⽆所不能,⽆所不往,样样上。
⼜⽆⼀个⾮其所⽣所养,才是上,才是帝。
天⽗上主皇上帝⽽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
”(《天命诏旨书》)因为避讳,以⾄于叫了多少年的地名“上海”、“上虞”等,也得遵制改为“尚海”、“尚虞”的。
中华五千年,多有帝王特权所限定的避讳字,但没有将“上”字也作为避讳字的。
太平天国将很多常⽤字列为避讳字。
它还⼏次下诏,要让全军全民都知道,不得写错字,写错字是要严加惩罚的。
⼤概就在这个时期前后,太平天国就重视⽂字避讳,他们制订了不少莫名其妙的⽂字避讳条例。
本来⽂字,尤其是单字,只能充作符号、标记,没有任何阶级烙印;将它说成特殊,作⾃圆其说,⽬的乃是拔⾼⾃⼰的⾼贵⾝份。
在太平天国的封闭世界⾥,也是谁官⼤权⼤,就是谁拥有超格理论、具有最⾼解释权的权威。
这些避讳字,最显眼的是凡涉及到所谓天⽗上帝、天兄耶稣以及所谓天⽗诸⼦婿洪秀全等⼈的名讳,都得采⽤代字,要避讳。
它的涉及⾯是⾮常之⼴的,仅洪秀全和诸异姓王6⼈,就有11个字要回避,不能泛⽤,⽽这11个字都是⼈们取名时经常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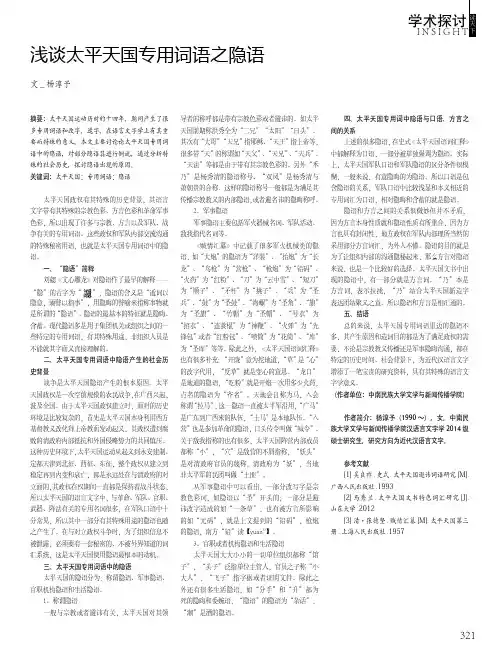

李秀成自述时逢甲子六月,国破①被拏,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承<丞>②大人量广,日食资云。
又蒙老中堂③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遂(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
自我主应立开塞〈基〉之情节,衣〈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
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
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其父□名不知。
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後母所生。
④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
长、次兄往家种田。
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
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 年)之病,死去七日还魂。
自还魂之後,俱讲天话,凡问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芾,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
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後,具〈俱〉不敢拜别神。
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寻〈浔〉州桂平武宣象洲〈州〉腾〈藤〉县陆川博白,具〈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
是以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
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章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①六人深知。
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後分别再清。
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住山名叫做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
自拜上帝之後,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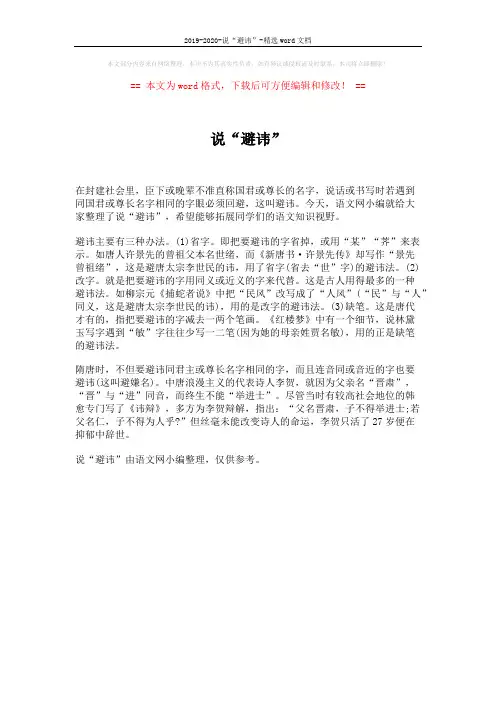
2019-2020-说“避讳”-精选word文档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说“避讳”在封建社会里,臣下或晚辈不准直称国君或尊长的名字,说话或书写时若遇到同国君或尊长名字相同的字眼必须回避,这叫避讳。
今天,语文网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说“避讳”,希望能够拓展同学们的语文知识视野。
避讳主要有三种办法。
(1)省字。
即把要避讳的字省掉,或用“某”“荠”来表示。
如唐人许景先的曾祖父本名世绪,而《新唐书·许景先传》却写作“景先曾祖绪”,这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用了省字(省去“世”字)的避讳法。
(2)改字。
就是把要避讳的字用同义或近义的字来代替。
这是古人用得最多的一种避讳法。
如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把“民风”改写成了“人风”(“民”与“人”同义,这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用的是改字的避讳法。
(3)缺笔。
这是唐代才有的,指把要避讳的字减去一两个笔画。
《红楼梦》中有一个细节,说林黛玉写字遇到“敏”字往往少写一二笔(因为她的母亲姓贾名敏),用的正是缺笔的避讳法。
隋唐时,不但要避讳同君主或尊长名字相同的字,而且连音同或音近的字也要避讳(这叫避嫌名)。
中唐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李贺,就因为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而终生不能“举进士”。
尽管当时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韩愈专门写了《讳辩》,多方为李贺辩解,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但丝毫未能改变诗人的命运,李贺只活了27岁便在抑郁中辞世。
说“避讳”由语文网小编整理,仅供参考。
中国古代的名讳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常呼备字。
马超跟刘备混熟了,不叫“⽼⼤”直接叫⽞德,关⽻就⽣⽓要杀马超……中国古代避讳⼀般只避名,不避字。
关⽻吃醋 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常呼备字。
关⽻怒“请杀之”。
马超跟刘备混熟了,不叫“⽼⼤”直接叫⽞德,关⽻就⽣⽓要杀马超……中国古代避讳⼀般只避名,不避字。
“冠⽽字之,敬其名也。
”这段话很有趣,关⽻莫⾮吃醋了? 洪秀全的名字洪秀全⾃⼰记载,上帝让他改名时嘱咐“下凡这⼏年”有时要叫“洪秀”,有时候叫“洪全”;后来当了天王给⾃⼰起了个⼩名叫“洪⽇”。
连起来读:洪秀全⽇。
太平天国的避讳乱七⼋糟,上下级的避讳看官⼤⼩,但杨秀清就不避洪秀全的“秀”;李寿成偏偏把名字改成李秀成(⼀说洪赐的),以为王和王之间姓名冲突没事,可靖王李开芳避翼王⽯达开改成李来芳……避讳改名不计其数。
现在没有皇帝了,倒是普通百姓还有信风⽔的,亲戚之间讲避讳常有改名的。
州官放“⽕” 北宋有个太守叫⽥登,为避讳不许州内说与“登”同⾳字。
元宵节惯例要放灯三天。
写告⽰的只能把“灯”字改成“⽕”,于是“本州照例放⽕三⽇”。
“只许州官放⽕,不许百姓点灯”就这么来的。
谭谈混⽤ 唐武宗叫李炎。
凡是遇到两个“⽕”相重的字都要避讳,⽤其他字代替,⼤都⽤“谭”。
这个说法其实牵强,谭、谈这俩字三国时代就混⽤。
武宗原名李瀍,临死前10⼏天才改名李炎,根本推⼴不了也影响不到。
孙休造字 古代避讳太严重以⾄于字不够⽤,皇上也不想给⼤伙添⿇烦,就造字,武则天那个“曌”现在还能⽤,三国时吴的孙休给⼉⼦造了⼋个字,现在全打不出来:太⼦(⾬单)次⼦(雷⼤)次⼦(⾖巨)……全是上下写,看完这⼋个分裂字,谁眼睛都得散光。
王羲之不避“之” 斐松之、刘牢之、寇谦之、司马孚之、司马亮之、司马景之、司马昙之……王羲之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孙⼦桢之、静之。
上述⼈为什么不避家讳?这⾥藏着个⼤秘密,与西汉张良有关的秘密。
王羲之⼀辈⼈名有“之”字的12个,⼦侄辈有“之”22个,孙辈12个,曾孙13个,⽞孙9个,五世孙4个……陈寅恪说这些⼈所以不避讳是因为都是天师道成员,这个“之”是暗号、徽章。
清朝的避讳字表包括:
1.天命(1616-1626):努尔哈赤,原名“奴儿哈赤”,避讳“奴儿”。
2.天聪(1627-1636):皇太极,原名“皇太极”,避讳“皇”字。
3.崇德(1636-1643):皇太极,避讳“皇”字。
4.顺治(1644-1661):福临,避讳“福”字。
5.康熙(1662-1722):玄烨,避讳“玄”字,同时将“烨”字的末笔去掉。
6.雍正(1723-1735):胤禛,避讳“胤”字,同时将“禛”字的末笔去掉。
7.乾隆(1736-1796):弘历,避讳“弘”字,同时将“历”字的末笔去掉。
此外,清朝还有一些其他的避讳规定,例如在书写皇帝的名讳时要用缺笔或改字的方式来避讳,或者在说话时也要避免说出皇帝的名讳。
这些规定都旨在表达对皇帝的尊重和敬畏,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和权威。
太平天国诸王名录及其官职太平天国前期仅置王、侯二爵,在王、侯之下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官职,又有尚书、承宣、仆射、引赞、通赞、指使、侍臣、侍卫、参护、尉、伺、典官、掌书、掌门、大旗手、经历、通传、书理、疏附等属官杂职。
王爵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爵位。
洪秀全从拜上帝教义出发,认为只有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帝,人间之主称王足矣,故金田起义时自称天王,托言受天真命,由皇上帝所封。
1851年12月17日在永安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受东王节制。
另对前期功臣封侯爵,秦日纲为顶天侯;胡以晃为护天侯(初为护国侯);陈承容为佐天侯(初为兴国侯);黄玉昆为卫天侯(初为卫国侯);卢贤拔为镇国侯;林启荣为贞天侯;李俊昌为补天侯;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朱锡琨为剿胡侯;黄益芸为灭胡侯。
1854年5月,升封秦日纲为燕王,6月升封胡以晃为豫王,二人旋被革爵。
前期王爵,除韦昌辉因天京事变被处死削爵外,余皆世袭。
天京事变后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以挟制石达开。
石达开回天京辅政,曾被晋封义王未受。
旋又削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而以被削之王的爵号加上原有的侯爵设立六等爵位,按高低次序依次为:义、安、福、燕、豫、侯。
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封为干王,随后陆续增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并大封洪氏亲属诸王。
至1861年《朝天朝主图》颁布时,连爵同王的驸马、西王父在内共二十八个王。
后越封越多,且有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小王” 之封。
至天京失陷前,封王达二千七百多人。
滥封王爵破坏了论功行赏的原则,造成朝政紊乱。
因封王过多,爵号不够用,以致后来六等爵无字号可用,遂用数字代替,如第三百六十八天安廖深。
后期除增设列王、小王外,还增设掌率、统管、尽管、天将、朝将、主将、佐将、神使、神将之官职,地位在六等爵之上,另有正副总提等官职。
太平天国疯狂的避讳癖民间故事明末陕西农民起义,最初的起义首领几乎都用的是假名,究其原因,是这些人虽然造反,但他们的妻儿老小却还在老家当百姓,所以他们隐姓埋名,为的是不连累家人。
然而,当太平军举家随营时,他们却不屑前辈们那种躲躲闪闪的窝囊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改名,恰恰相反,太平天国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普通兵,改名蔚然成风。
改名蔚然成风洪秀全自己的名字,按他儿子的话,是“天安的”。
他本来谱名仁坤,小字火秀,开始传教之初,就假托天父旨意,改名洪秀全,这是因为上帝叫“爷火华”,自己名字当然不能有火。
不但如此,秀全这两个字可以很方便地拆开来做文章。
后来金田起义,有人便开始大玩拆字游戏,编造什么“三星高照日出天”,什么“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合在一起就是洪秀全要当帝王。
这招显然十分好使,直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编造着新字谜。
不过洪秀全可不是只有一个名字,他自己记载,上帝让他改名时嘱咐,他“下凡这几年”,有时候要叫洪秀,有时候叫洪全,这大约是为了保密和逃避清方追查;后来当了天王,他给自己起了个小名叫“洪日”,这自然是因为他自称太阳之故。
洪秀全的重臣、大将中,改名字的也很多。
比如北王韦昌辉和弟弟韦志俊,原本叫韦正、韦俊;大将李来芳,本名叫李开芳;名医李俊良,原本叫李俊昌;英王陈玉成,原本叫陈丕成;答天豫薛之元,原本叫薛小。
其中有些人甚至改了不止一次姓名。
如忠王李秀成,本名李以文,改名寿成,又改名秀成;赞王蒙得恩,本名上升,改名得天,又改名得恩;奏王赖世就,本名赖九,改名赖世国,又改名赖世就。
避讳爱好几近疯狂封建时代,各朝都有“避讳”。
帝王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于其他场合,如果是双名,一般规定不能连用。
所以,太平天国对避讳的爱好,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洪秀全父子和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名字要避讳,一些不好的字眼,如丑、亥(和“害”同音)等要避讳,甚至有些常用字,如师(只许用于军师、先师、后师等)、龙(只许说“宝贝龙”而不许用于取名)等也不能用,“王”、“主”等看上去比较“威风”的字同样不允许用。
太平天国避讳字说(一)一避讳是我国特有的风俗,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礼制。
在西方,基督教徒的小孩受洗取名,不但不回避、而且有意识地与敬爱的尊亲、长辈同名。
斯拉夫人的名(教名)和姓(家族名)之间,还得加上父名。
以帝王、英雄、闻人、学者、发明家、创始者的姓名来命名事物,作为纪念,加以褒扬,千人写,万人叫,更是视为尊荣。
而在我国,则君主、圣贤、尊长、父祖的名讳,口头上不能叫,文字上不准写,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回避,这就叫做避讳。
避讳原先出于子孙对父祖的尊敬,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等级从属关系的制度。
避讳制度始于周、秦,盛于唐、宋,下迄清末。
它维护宗法制度和三纲五常,禁止犯上作乱,是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
民国以来,实行共和,避讳作为一种制度是被废除了。
然其遗风,恐怕还不能说是完全泯灭了吧。
避讳淆乱文书而产生讹异,更改史实而造成误解,流弊甚多。
但在另一方面,则又可以利用避讳来校勘古籍,鉴定文物,考订史实,解释疑滞。
清代学者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与《二十二史考异》、赵翼《陔余丛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对历代避讳有所著录,并借以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研究避讳并应用到校勘学和考据学的,叫做避讳学。
避讳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
近代历史学家陈垣撰著的《史讳举例》,凡八卷八十二例,集避讳学之大成。
正如陈氏在自序中所说,“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陈垣:《史讳举例》,1933年刊。
本文引: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励耘书屋丛刻》本,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
惟该书于太平天国讳例独付阙如。
《史讳举例》是避讳学的总结,但不是避讳学的终结,后学者可以而且应该在前辈学者已经达到的科学高峰上继续攀登。
用太平天国讳例来补其未备,并在避讳学的研究方面有所前进,也是符合陈氏自序期待“纠谬拾遗”的初意的。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又是盛行的习俗。
探讨这种礼俗,是太平天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初期规定比较粗疏。
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宗法式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
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杨秀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等级森严不可逾越,避讳制度渐趋严密。
1856年天京事变导致人心涣散,洪秀全为了维系人心,借助神灵加强皇权,强化了避讳这种手段,至1862年颁布了《钦定敬避字样》,作为全国遵行的法规。
太平天国避讳方法之多样,种类之繁伙,字数之众多,范围之广泛,规定之烦琐,执行之严格,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是太平天国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日益封建化的趋向(参祁龙威、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考释》,见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1980年)。
)。
因此,探讨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有助于深入太平天国史研究,总结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肃清封建主义残余,也不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避讳学在太平天国文物鉴定、史料辨伪、史事考证、词语诠释、版本校勘与文献整理等方面的实际应用十分广泛。
太平天国避讳学,是太平天国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半个世纪来,罗尔纲老前辈为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与利用开辟了途径,做出了典范,启迪了后学,继而有所发明。
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拙撰《略论太平天国避讳的研究与利用》,收入《太平天国学刊》第五辑。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掌握避讳这一项工具,对读懂读通太平天国文献是必不可少的。
王庆成同志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天情道理书》早于“戊午遵改”本的修改本:将“北王”改为“背土”,不提行;把顶撞杨秀清而被处死的“参护李风先”,改为“背土参护李凤先”。
他并提出解释:“‘土’或意味‘王’字斩首,‘背’或意味着反叛。
但被处死之参护也加上‘背土’,则以‘土’释为‘王’斩首,似不可通。
太平天国有‘脚底生泥’之语,意为‘入地狱’,‘背土’或者也是此意。
”(王庆成:《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王文称,柯文南发现《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内容与己未遵改本相同。
)这个发现对版本校勘和史事考证均有重要意义,但这两种解释似乎都还没有说到点子上。
如果我们利用避讳学这把钥匙来启其奥秘,就可以豁然开朗了。
太平天国文书、印书中,往往因嫌恶某些罪犯或有严重过错的人而避改其姓名,这在避讳学上叫做恶意避讳,而加笔、减笔则是常用的方法。
1856年天京事变中北王韦昌辉被诛削爵,1857年刊印的《天父诗》,把“不信山中清贵正”改为“不信山中清贵止”,就是恶意避讳减笔之例。
大约就在这一年,《天情道理书》的修改本,避“北王”恶讳,“北”字加笔作“背”,“王”字减笔作“土”。
这是否纯属猜测呢?否。
《旧遗诏圣书·创世传》第四十九章第二十节:“亚沙将出产膏粮,又产王之甘物。
”钦定本避“王”字讳减笔作“土”,可为旁证。
《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
”“北”即“背”的古字,《国语》韦昭注已有明言。
这里的“背”字既是“北”字避讳加笔,又取其“背反”的贬义,与“脚底生泥”未必有关。
至于把“参护李凤先”改“背土参护李凤先”,王庆成同志没有说明其行款格式如何。
我们校以影印伦敦藏《天情道理书》“已未遵改”本,发现“参护李凤先”不应抬行而抬行,其抬头反比不抬头的低一格,而较“东殿”低两格。
据“北王”讳改“背土”之例可以推知,“背土参护李凤先”,初刻本当作“北殿参护李凤先”,“北殿”抬头与“东殿”同。
1858年间遵照洪秀全旨意修改印书,既要继续贬斥韦昌辉,又要改得通顺合理。
前引《天父诗》1857年本“不信山中清贵止”,1858年天王《赐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诏》所引又改“止”为“出”。
《天情道理书》原当与东、西、南、翼诸王抬头相同的“北王”,1857年本铲改为“背土”,不抬头;1858年(王庆成:《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王文称,柯文南发现《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内容与己未遵改本相同。
)和1859年修订本又将“背土”改为“昌辉”,不称王号,不避讳,但恢复抬头与东王等并列。
原当与“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并列的“北殿参护李凤先”,1857年本铲改为“背土参护李凤先”,“背土”二字不抬头,“参护”之上空两格;1858年和1859年的修改本,则又去“背土”二字,“参护”之上仍有两个空格,这是避“北殿”恶讳空字之例。
《太平天国》丛刊本照原格式排印,可资校勘;而《太平天国印书》横排本,则连排去空格,就无从寻觅“北殿”二字的踪迹了。
二太平天国避讳字,应该如何分类?总数有多少?各家记载颇有出入。
1856年前成书的清人著作,如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分为五类:1.天父名、各“伪”王及“伪”王子孙名讳改诸字,2.皇上帝、天王、圣神讳改诸字,3.年月日、地支所改诸字,4.“贼”中忌讳及毫无情理所改诸字,5.妄造诸字;剔去非避讳字,计有避讳字三十八个。
汪士铎《乙丙日记》据他在天京的见闻所记太平天国避讳字,附有代用字者四十四个,但言“不准用”者十四个,合为五十八个。
太平天国于1862年颁行的《钦定敬避字样》,明确规定的避讳字五十七个,禁用的字十二个,共计六十九个。
前辈学者和时贤的太史专着,则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把太平天国避讳字分为代用字和改字,共五十四个。
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把太平天国“代改字”分做“改写字”和“改称字”,略去非避讳字,计有六十个。
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分为造字与改字。
太平天国造字、改字不全是由于避讳,而以避讳为主。
其区别,“汉字本无,太平天国新造,谓之造字,汉字本有,太平天国改用之字,谓之改字。
”所谓有无,以是否见于《康熙字典》为准。
除去非避讳字,剔去重复,著录太平天国避讳字实有六十四个。
笔者综合上举各家及其他零星记载,考诸现存可以看到的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则查有实据的太平天国避讳字就上百个;见于时人记载,尚待查找例证的还有几十个,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为什么诸家所记太平天国避讳字的数目各不相同,以至相差如此悬殊?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是发展变化的,前后期避讳字数不同。
尽管有的改字如“岁(年)”、“期(月)”、“旦(日)”不久就改还本字,但总的来说是愈演愈烈,越来越多。
商衍鎏氏以为“前期所改的字数较多”,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根据的。
其次,视野有广狭,所据材料有多寡。
《天父圣旨》、《天父圣旨》的发现与公布,《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武略书》等的校勘与整理,都是近年的事情,而若干太平天国后期刊行的印书中,避讳的实例特多。
后学者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理应有所前进。
第三,对于太平天国避讳的范围和特色,区别是否避讳字的标准,太平天国避讳字的分类,等等,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
太平天国避讳字,有避尊讳的,也有避恶讳的;有《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了的,也有《钦定敬避字样》所不载的;有全国通行的,也有局限一地的;有始终敬避的,也有行于一时的;人们有恪遵的,也有不遵的;文书、印书有遵改的,也有改而不尽的。
情况参差,不可一概而论。
即就《钦定敬避字样》而言,也不能说都研究透彻、理解准确了。
有的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造字与改字,统计为四十五字,除去重复,不过四十一个避讳字(史式:《太平天国造字与改字表》,《太平天国词语汇释》附录。
),就是把一些“不得僭”、“不得渎”、“不准称”、“不准用”的避讳字忽略过去了。